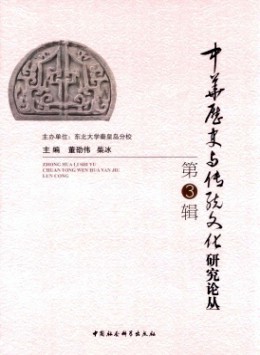金院曲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性

本文作者:牛贵琥 单位:山西大学 国学院
元代以降,一方面是俗文学戏曲的完备和盛行,成为文学史上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形式。另一方面传统的雅文学诗文也在产生着变化。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元代的戏曲不会是突然产生的。那么元代戏曲和金院本的关系是什么,金院本的特点又如何呢?关于金元的雅文学,人们关注的是元代诗歌继承金代诗人“以唐人为旨归”的传统,宗唐得古成为潮流和风气,左右文坛的也是金代宗唐宗宋的两大派别,并以王若虚、元好问宗宋文的传统为主要倾向。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传统文学和俗文学不可能是互不相关的封闭的系统,特别是元代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这关系到对金代和元代文学的正确理解和评价,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金院本之特征
关于金院本的特征,人们已经从多方面进行过探讨。如:我们可以从山西晋城县莒山乡司徒村二仙庙有施门刻石及队戏图和巾舞图石刻;侯马董明墓、稷山马村、化峪、苗圃以及襄汾南董等金墓的戏曲砖雕;高平市寺庄乡王报村二郎庙金代之戏楼;阳城润城镇屯城村东岳庙正殿须弥座台基束腰处泰和八年的两幅戏曲故事石刻等文物,来为金代戏曲提供佐证。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戏曲文本,我们从这些实物资料中很难对金代的戏曲得出清晰的认识。我们也可以从音乐的角度来考查金代音乐对元代的影响。《金史•乐志》云:“及乎大定、明昌之际,日修月葺,粲然大备。”“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元史•礼乐志》云“: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王世贞《艺苑卮言》云:“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徐渭《南词叙录》更是说:“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狼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然而音乐毕竟不能代表文学。同理,元好问《闻歌怀京师旧游》写他曾在金之都城与人一起听人唱散曲,《杜生绝艺》写杜生弹奏散曲。元杨朝英所编《太平乐府》收有元好问的五首歌曲,《遗山乐府》也有四首曲子,但其《骤雨打新荷》是曲还是词一直受到后人的质疑。事实上包括他在内的金末文士都有以词例曲的现象。金元的戏曲是一个发展中的集合体,不可分割,元杂剧也不可能是突然成熟的产物。陶宗仪就在《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中说:“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然而,陶宗仪以元人厘而二之的标准列出六百九十种院本的名目,后人也就依照这种标准去探讨金院本的特征,于是金院本也就成为以科白滑稽为主的类似于小品的短小戏剧。徐充《暖姝由笔》便说“:扮演戏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由于金院本没有剧本留下来,也缺乏关于它的体制的文献记载,人们从元杂剧中保留的院本或从明人所写的拟院本探讨金院本的面貌,更加深化了这种认识。比如刘唐卿《降桑椹》第二折两个太医的打诨情节,研究者认为就是院本《双斗医》;明朱有燉《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第二折中的戏中戏《献香添寿》院本以打诨为主;李开先《园林午梦》院本也属只演片刻的短剧。由此推论,元杂剧改变了金院本以打诨为主的特点,摆脱滑稽戏面目,完成戏剧史上的革新,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应该说这种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由元代已经改变了的标准来判断金院本的面貌是不可取的。
第一,山西马村金墓1、4、5号墓戏曲砖雕中有乐队伴奏,其中5号墓还雕有乐床,说明并非如徐充所言“跳而不唱”。
第二,从院本中的一些名目如《赤壁鏖兵》《杜甫游春》《张生煮海》《蝴蝶梦》等等来看,似乎剧情十分复杂并非滑稽短剧。杜善夫《庄家不识勾栏》:“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么末敷演刘耍和。”《调风月》也是元杂剧中的剧本。还有《错立身》南戏“:末白:‘你会做甚院本?’生唱《圣药王》:‘更做四不知双斗医,更做风流娘子两相宜,黄鲁直打到底,马明王村里会佳期,更做搬运太湖石。’”而《正音谱》“古今无名氏杂剧”则也有:策立阴皇后、双斗医、明皇村里会佳期、黄鲁直打到底、风流浪子两相宜、搬运太湖石。证明正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中所说,金院本和杂剧本是一个性质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包含着元杂剧的性质在内,并不是如元代院本一样纯为滑稽之短剧。事实上,古人在谈到金元戏曲时往往金元连称。如李梦阳《诗集自序》中讲民间之乐“是金元之乐也。”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云词“然俱以金元为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何也?词肇于金而盛于元。”这里的词是指曲。尤侗《西堂杂俎》中的《名胜选胜序》云李笠翁“尤擅金元词曲。”王士祯《池北偶谈》也云“:袁崇冕,字西野,工金元词曲……又有张国寿者善金元词曲。”
第三,金代的诸宫调也和戏曲关系密切。《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云:“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陶宗仪将传奇、杂剧、诸宫调《董西厢》在一起论,就证明在他的心目中,这三者是一类型的东西。《董西厢》开篇列举当时的诸宫调“: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这些故事也大多为元杂剧所采用。事实上,固然诸宫调说唱艺术的叙述体和戏曲的代言体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看诸宫调《董西厢》,其中的大多数唱词除了不多的叙述情节的段落外,都是代张生、莺莺、红娘等人抒发内心感情或描绘所见所想。而元杂剧也带有明显的叙述因素,其中的人物可以自报家门,可以追述情由、倾诉经过、说明现状。焦循在《剧说》卷一中记《董西厢》的演出体制就有戏曲的雏形。“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畤者,始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则纯以事实谱词曲间,然犹无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实作《西厢》㑳弹词,则有白有曲,专以一人㑳弹并念唱之。嗣后金作清乐,仿辽时大乐之制,有所谓连厢词者,则带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词,而复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儿者并杂色人等入勾栏扮演,随唱词作举止。如‘参了菩萨’,则末泥祗揖;‘只将花笑撚’,则旦儿撚花类。北人至今谓之连厢,曰打连厢、唱连厢,又曰连厢搬演。大抵连四厢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犹舞者不唱,唱者不舞,与古人舞法无以异也。”他还由此领悟到“:少时观《西厢记》,见一剧末必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于扮演人下场后复唱且复念正名四句。此是谁唱谁念?至末剧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齐下场后,复有《随煞》一曲、正名四句、总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连厢词例,则司唱者在坐间,不在场上,故虽变杂剧,犹存坐间代唱之意。”卷二又引《笔谈》云:“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遽歌之,谓之磨唱。卢氏盛歌舞,然一件后无继者。赵长向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马上戳本此。”由此可见,诸宫调有着多种表演方式,如果是一个人演则是讲唱,如果是两个人以上就接近戏剧了,其和元杂剧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应该说,金代的戏剧已经很发达了。如果说麻九畴《俳优》“:施能卖晋移君贰,旃觧讥秦救陛郎。多少谏臣翻获罪,却教若辈管兴亡”中的俳优还不好说就是戏剧演员,那么杨维桢《宫词十二首》:“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中的关卿,不管是不是关汉卿,则是金代有戏剧作家的证明。
二、金元之曲与传统文学之关系
人们一般都习惯于将金元的曲归入和诗文传统文学相对立的俗文学,并且也习惯于接受由一代又一代之文学而来的“诗衰而词作,词衰而曲作”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有其误区。这在于:
第一,金元的曲固然是从音乐上受到女真、蒙古的影响,但从曲词的本质上讲,和传统的诗词是相一致的,属于格律诗的范畴,甚至比诗词的格律还要严格,并不同于纯粹的通俗的歌曲,如汉代的《戚夫人歌》、明代以降的《山歌》《挂枝儿》那样。黄周星《制曲枝语》就云:“诗降而词,词降而曲。名为愈趋愈下,实则愈趋愈雅。何也?诗律宽而词律严,若曲又倍严矣。按格填词,通身束缚。盖无一字不由凑泊,无一语不由扭揑而成者。故愚谓曲之难有三:叶律一也,合调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尝为之语曰:三仄更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诗与词曾有是乎?”从这个意义上讲,曲的本质是雅的。事实上《董西厢》就雅得很,文士气十足。涵虚子《正音谱》说得好“: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谓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倡优岂能扮乎?”
第二,不仅仅是散曲和套曲,就是金元时期的诸宫调、杂剧,也是以曲词为主体,和诗词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如姚华在《曲海一勺•明诗第三》中讲诸宫调和词之关系:“此类歌辞,既别于词,泛滥其名,总谓之曲,是即今语所谓时调。其所流传,则弦索《西厢》,至今存焉。观董氏之所为,虽与词颇有出入,亦未尝无词格存乎其中。(自注:《沁园春》《水龙吟》其一二只得例也。)信其滋生,必出于词。奚以明之?夫弦索《西厢》,旧谓传奇之祖,(自注:《少室山房笔丛》)不入杂剧、院本,然与诸杂剧、院本,皆不外以所演之事,系所歌之曲。杂剧词始北宋初叶,今虽无传,第以旧目考之,则以调名者,词曲参半。曲之题名,大率为弦索《西厢》及元曲之题名诸本所祖述。”李渔《闲情偶寄》又言曲词乃是北曲杂剧之主体。《密针线》:“然传奇一事也,其中义理,分为三项: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元人所长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与关目,皆其所短。吾于元人,但守其词中绳墨而已矣。”《宾白》中又说:“北曲之介白者,每折不过数言。即抹去宾白而止阅填词,亦皆一气呵成,无有断续,似并此数言亦可略而不备者。由是观之,则初时止有填词,其介白之文,未必不系后来添设。在元人,则以当时所重不在于此,是以轻之。”[2]11,40
第三,相对于诗,曲和词的关系更为密切。王骥德《曲律》云:“北则于金而小令如《醉落魄》《点绛唇》之类,长调如《满江红》《沁园春》之类,皆仍其词而易其声。于元而小令如《青玉案》《捣练子》类,长调如《瑞鹤仙》《贺新郎》《满庭芳》《念奴娇》类,或稍易字句,或止用其名而尽变其调。”这是从调名上来谈其既承继又变化。何良俊《曲论》云:“夫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流别。……苟诗家独取李、杜,则沈、宋、王、孟、韦、柳、元后,将尽废之耶?”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既有曲时,曲可悟词。苟曲可悟词理未明,词亦恐难独善矣。”姚华《曲海一勺•述旨》:“金元起于北方,音律异声,词弗能叶,新声以创,而曲遂作。寻其渊源,一本诸词。远祖南唐,近宗北宋。诸家小令,痕迹分明,不独大曲为散套、杂剧、传奇之滥觞而已也。是以词曲界划,虽极谨严,然多蒙旧语,曲亦名词,或曰乐府,少示区别,则曰词余、曰今乐府。”他们都明确讲出曲是词所发展而来。金末蒙古时期的元好问、商衟、商挺、杨果等人都有以作词的法子写曲的情况,更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金元戏曲实际上包含了传统文学的所有质素。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刘师培《论文杂记》所论更为详细:“予按《诗》三百篇,如《六月》《采芑》《大名》《笃公刘》《江汉》诸作,皆为叙事之诗。而汉人乐府之诗,如《孔雀东南飞》数篇,咸杂叙闾里之事。叙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乐府者,又乐教之支派也。是为《春秋》家与乐教合一之始。(自注:唐杜甫之诗,亦称诗史。)此即金元曲剧之滥觞也。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乐府之诗,或由一解至数解,即套曲之始也。乐府之句,或由三字至七字,即长短句之始也。且乐府之中,如《孔雀东南飞》诸篇,非惟叙众人之事,亦且叙众人之言,此又曲剧之描摹口吻之权与也。特曲剧之用,声容相兼,声出于《雅》,雅训为正,乃声音之失其正者也。容出于颂,颂容互训,乃用佾舞以节八音者也。(自注:《左传》隐五年)曲剧之兴,实兼二体。”
总之,曲(包括戏曲)和诗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是各有各自的特色。正如在诗之后有了词,词虽然增加了诗之所无的新质素,但词并不能代替诗。词之后有了曲,曲也有着词之所无的新质素,但曲同样无法代替词。直到今天,诗、词、曲三者还是并行而不悖,都是传统文学的组成部分,保持着各自的特色。这就证明,曲的兴起并不是和传统文学相对立,更不可能是取而代之。重要的是关注其相对于诗词增加了些什么,并把这些放到文学发展的大环境中去考查。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曲的兴起,实际上体现了这个时期文学的总趋向,而金代文学的价值则在于为元代文学作了厚实的铺垫,研究金代文学就成为正确理解和评判元代文学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 上一篇:传统文化中审丑的表达方式范文
- 下一篇:女性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重要性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