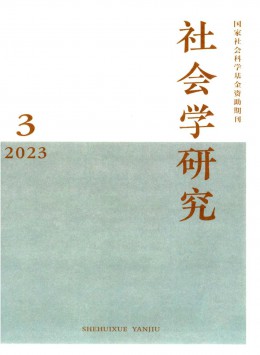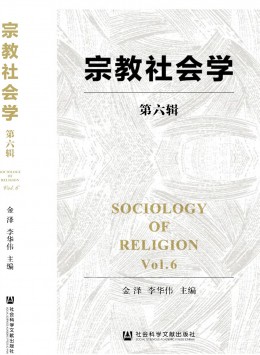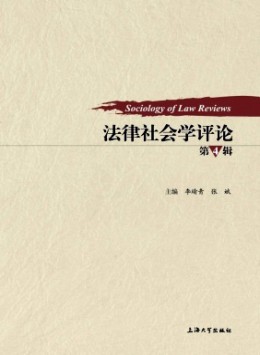从社会学视觉读情绪

一、情绪与理性:消解二元对立
情绪与理性的关系是近年来情绪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论题。社会学者的分析表明,人们对情绪和理性之间关系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演化过程,其中共包括三种形式:情绪干扰理性;情绪为理性服务;情绪与理性相互交织。[7]11-12第一种形式认为情绪是“行动机械中的沙砾”,损害了我们的理性决策,因此需要被消除或严密地加以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哲学和心理学研究之中。第二种形式认为只要让情绪处于理性的引导之下,它就能促进或者润滑(lubricate)由认知代表的理性,从而为我们的思维活动提供帮助———这是20世纪80年代情绪研究兴起以来认知心理学者通常所持的观点。他们发现,情绪对认知有着多种作用,如发起和结束信息处理;导致信息的选择性处理;影响记忆、决策与问题解决的组织和执行等。于是,这些学者认识到缺乏情感、意动的认知研究的局限,开始尝试将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这种受到情绪、动机影响的认知活动通常被称为“热认知”。随着认知心理学者对情绪之作用的接受,情绪与理性的关系也显得密切起来。近年来兴起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便是平息情绪与理性之争的一种心理学尝试。其倡导者认为,“边缘系统和新皮质、杏仁核与前额叶都是相辅相成的,彼此合作无间时,情绪与智力自是相得益彰”。[8]45简言之,它是指与我们处理情绪信息有关的一组能力,包括我们感受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产生适当的情绪体验的能力;理解自我及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自我情绪的能力。不可否认,情绪智力这一概念有助于弥合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分离,但这种弥合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正如这一术语所显示的那样,它将情绪视为智力的一种形式,从而将其纳入理性的统辖范围之中。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一概念背后所隐藏的假设与“情绪为理性服务”并无二致。上述两种形式的共同特征是把情绪与理性或认知分离开来,赋予理性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把情绪作为理性的对手或仆人。然而,情绪与理性不是相互对立的,也不仅仅是后者为前者服务,二者的关系远比这两种形式所假定的要紧密得多。
在整合情绪与理性关系这一点上,社会学者走得更远。这种努力是从解构情绪与理性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关系方面入手的。社会学者指出,情绪与理性之间等级性二元对立在西方的哲学和文化史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对清晰观念和理性判断的强调,以及亚理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女性的心灵更少理性而更多激情的观点。在近代,笛卡儿(Descartes,R.)的身心二元论和康德(Kant,I.)关于观念和感觉的区分进一步加剧了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分离。尽管哲学史中也有另类的声音,如怀疑论者休谟认为“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激情(passion)的奴隶”,然而这种声音毕竟太过微弱。事实上恰恰相反,“主人与奴隶”是西方思想史中形容理性与情绪之间关系的最悠久的隐喻。在这种二分法中,理性被认为是客观的、普适的、分析的、冷静的和男性的,情绪则是主观的、个人的、综合的、温暖的和女性的。[9]3-8这一分析说明,情绪与理性之间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关系并非我们想象得那样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和文化建构。为满足人们对客观、普适和确定性的向往,情绪被描述为理性的对立面,并且在与理性的争斗中扮演了牺牲品的角色。
要整合情绪与理性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在承认情绪之特性的基础上恢复情绪与理性的平等地位。在这种关于情绪与理性之关系的新观点中,二者是相互交织、互相渗透、彼此融合的。没有所谓的纯粹的、情绪中立的认知,思维和决策总是充满着情绪;也没有所谓毫无理性、完全失控的情绪,情绪本身便体现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判断。情绪与理性彼此均非对方的主宰,而是共同熔铸在人类意识这个统一的模具之中。人类意识是思维和感受、理性和情绪之间天衣无缝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并不只是社会学者天马行空的设想,它还得到了脑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研究证据的支持。对脑、情绪、理智(reason)等神经机制的研究表明,[10]250情绪并非理智堡垒的入侵者,而是与理智一起构成了这个堡垒的结构并推动着它的操作———笛卡儿在对待身与心、情绪与理性关系的问题上恰恰犯了一个错误。
二、情绪与自我:迈向情绪理解
自我(self)与身份(identity)是紧密相联的一对概念,对身份的社会学探讨大抵始于对自我的研究。尽管二者是都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但前者往往指向单个的个体自身,旨在强调个体与他人的差异;后者在表达这种涵义的同时,还把个体和周围具有相同属性的他者联系起来,从而包含了一个描述群体共享特征的集体维度。例如,利科(Ricoeur,P.)把身份分为“作为自我(selfhood)的身份”和“作为共性(sameness)的身份”,吉登斯(Giddens,A.)认为身份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其中“作为自我的身份”和“自我认同”均对应于身份中描述的个体差异的维度———自我。在社会学者看来,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反身性(reflexivity)”———个体反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在自我形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我的本质属性就是个体反身思考、把自己作为其注意和思维之客体的能力,这是社会学者在自我问题上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例如,库利(Cooley,C.H.)用“观镜”隐喻作为自我感受的来源,提出了“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的观点。
米德(Mead,G.H.)延续了这种传统,并且突出了社会互动的作用,认为自我的形成是在“角色扮演(role taking)”中完成的,即个体从心理上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并且把自己作为一个客体反观自身。正是在这种反观自身的过程中,个体发展出对自我的意识。正是这种反身性把情绪和自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Rosenberg指出,反身性在人类情绪中发挥着基本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情绪过程中:(1)情绪识别: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一种诠释过程;(2)情绪呈现(display):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对表情和行为的自我调节;(3)情绪体验: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内部唤醒状态的形成。[11]可以说,反身性对情绪过程的任何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反观自身中,个体认识、体验和呈现着自身的情绪和感受,形成关于他人或周围环境的意义,从而实现了对自我的认同,而情绪则时刻在传递着关于自我的生物和社会信息。就象我们的感官能够对物理现象做出反应一样,情绪让我们对周围的社会现象保持敏感,让我们知道在自我的边界上发生了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Denzin认为,“情绪的栖息之处是自我。情绪是自我感受。情绪当下地体现在、坐落在、产生于人们指向自我或他人指向自我的情绪的、认知的社会行动之中的自我感受”。49在澄清了情绪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情绪为何能够在具有不同自我的个体之间相互交流?换言之,我们为何能够理解他人的情绪?社会学者认为,理解是个体之间交流信息、达成共识从而维持社会互动的基本途径。正如自我在人际互动中得以塑造一样,人际互动还要求我们理解情绪传递的社会信息。这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如何理解他人的情绪体验和表达;二是这种理解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个体。这个互动过程需要情绪理解(emotionalunderstanding),即“个体进入他人经验领域,使自己体验到与他人相同或相似经验的主体间过程。从个体自身的立场出发对他人情绪经验的主观诠释是情绪理解的核心”。[1]137情绪主体间性(emotional intersubjectivity),即在情绪体验的共享领域中对集体自我(selves)的认识和感受,为情绪理解提供了基础。借助反身性和主体间性,社会学不仅指出了情绪对自我认同的重要意义,并且把这一貌似极端个人化的现象和他人联系起来,从而阐明了情绪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的社会学原理。
情绪理解的独特之处还和它的发生机制有关。Denzin进一步区分了理解的两个理想型:认知理解和情绪理解。[1]142-143他指出,尽管认知理解与情绪理解在现实中是相互交织的,但前者是逐步进行的(polythetically),个体逐个语词、逐个动作地仔细分析他人的言行,试图找出其精确的顺序及其背后隐藏的动机。逻辑推理是这种理解的核心要素。与之相对,情绪诠释则是瞬间完成的(monothetically),个体迅速将他人放入自己的经验框架,从而近乎直觉地诠释和理解他人赋予情绪的意义。共享体验是这种理解的核心要素。若个体的情绪储备库中拥有与他人相似的经验,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情绪理解就更容易达成。
三、情绪与权力:揭示社会控制
情绪论述也是权力论述。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情绪与理性之间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在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度中得到了延续和强化。科层制把理性从血缘、家世等武断的独裁权威下解放出来,将其定位于命令、规则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尽管这种科层制看似中立,但它们事实上支持了男性特征,并且沿着原有的性别路线再造了权力关系的父权形式。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权力已经从上述宏观层面渗透到情绪的每一个细微角落,“权力关系决定在诉说自我和情绪时哪些能够、不能或者必须说,哪些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哪些是个体能够说的权力关系决定着人们对情绪的感受和言说,反过来,情绪也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以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图1呈现了羞耻、骄傲、内疚、狂妄等发挥社会控制功能的情绪的产生机制。简言之,个体会根据对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既定的组织或社会法则的评价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当个体发现自己某种特定的行为不符合社会法则时,个体会感到内疚,反之则感到骄傲;当个体发现自己所有的行为皆不符合社会法则时,个体会感到羞耻,反之则产生狂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机制就处在情绪之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情绪既可以导致顺从和维护社会秩序,又具有颠覆现存权力结构的潜力。例如,如果我们不能感受到爱、内疚和羞耻,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会崩溃,但是过多的内疚、羞耻又可以导致人们对既有法则的怀疑、嘲讽甚至愤怒,从而引发个体或集体的自我解放行动。在这一点上,Hochschild对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和情绪法则(emotional rules)的研究最为全面地揭示了情绪与权力、社会控制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她指出,随着服务行业在当代社会的普及,雇员不仅要做传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还要做大量的情绪劳动。所谓情绪劳动是指个体管理自身的感受以产生为公众可见的情绪表达,这意味着个体需要诱导或抑制自身的感受,以维持适合他人心理状态的外部表情。[14]7情绪劳动也经常被称为情绪工作、情绪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一样,情绪劳动可以出售以获得薪水,因此具有交换价值;情绪工作、情绪管理则是指个体所做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相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情绪不再是私人的拥有物,而是进入公共领域,接受盈利目的和商业逻辑的支配。
雇员从事劳动的工作具有三个特征:(1)它们要求雇员和他人进行面对面、声音对声音的接触;(2)它们要求雇员使他人产生某种情绪状态,如感谢或恐惧等;(3)它们允许雇主通过培训和监督对雇员的情绪活动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14]147因此,情绪劳动者通常是服务行业中的雇员,如空乘人员,然而许多专业人士,如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医生、律师等也是情绪劳动者。在这些行业中,尽管其从业人员并没有直接的情绪监督者,但对他们的控制来自隐性的专业标准和顾客期望。与情绪劳动相对应,情绪法则是指文化、社会或组织情境中界定或重构情绪的准则和规范体系。[14]56它通常是隐性的,反映了文化脉络和意识形态中处理情绪的那个侧面,告诉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表达是否适合特定情境———上述专业标准和顾客期望就是情绪法则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情绪劳动反映了个体或社会组织在按照情绪法则的要求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常常表现为情绪劳动的主体所采用的应对策略。在个体层面上,我们会采用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扮演(deep acting)顺应情绪法则的要求:前者是指我们改变自己的外在表现,有意表现出适宜的情绪,这往往导致情绪的表达与感受之间出现失调;后者是指我们改变情绪体验的那些决定因素而使我们产生相应的体验,如想象、自我劝服、内化情境的情绪法则等。显然,从这些术语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情绪劳动与戈夫曼(Goffman,E.)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theory)之间的联系:在情绪由私人领域走到公共领域之后,人们就必须借助各种道具、台词和表演策略,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呈现那些处在社会前台的情绪活动,从而尽量使他人相信自己能够胜任社会所期望的角色。组织同样会成为情绪劳动或情绪管理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机制取代了个体进行扮演。组织的本质就是秩序和控制,否则组织就无以形成和维持。组织既要使个体产生那些符合组织利益的“积极情绪”,又要抑制那些有可能危及组织结构的“消极情绪”,为此,组织一方面会采用激励(物质或精神奖励)、动员(远景规划或集体动员)等策略调动其成员的某些情绪;另一方面,组织也会采用抑制(限制不良情绪的升级)、隔离(分离那些干扰组织正常活动的情绪)等手段调节那些不为组织认可的情绪。
四、结语
勿庸讳言,情绪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都处于边缘位置,这种现象在西方尤甚。人们通常把情绪放在理性的对立面上。只有当情绪作为理性的仆从、为理性服务的时候,它的地位和价值才会得到承认。作为这种等级性的二元对立的结果,以追求理性、纯粹知识为己任的学术研究从启蒙运动以来就把情绪排除在对真理、理智和知识的追求之外。再考虑到情绪现象极不稳定、难以捉摸,这更加使得研究者很少涉足这一问题。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在专业场景中,情绪被视为一种女性化的、非专业的表现。专业人士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工作不受情绪的干扰。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情绪也扮演着被压迫者的角色,因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科层体制对情绪持有一种异常谨慎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可能危及现有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黑色”情绪。然而,情绪在今天正在逐步———同时也是艰难地———摆脱它的边缘位置,走入社会组织、政治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的聚光灯下。这首先要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剧变。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服务行业、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工作。这不仅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其深远影响还弥漫在包括个体情绪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导致情绪逐渐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使个体情绪负载的社会信息也日益明确地彰显出来。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今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被称为“后情绪(post-emotional)社会”的发展时期,其中虚伪的、理性化的、大规模生产的情绪登上了世界舞台。人们理智地选择和表现出愤慨、友好或其它预先设计好的情绪,从而创造出人造的、迪斯尼式的(Disneyesque)真实。[15]26无论“后情绪社会”是否是一个描述当今时代的恰当术语,我们能确定的一点是,当情绪成为社会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主要议题时,学术研究就不能再对情绪问题无动于衷。于是,情绪在近年来得到了研究者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综上所述,社会学关于情绪的解读把我们对情绪的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这种解读使我们发现,情绪不仅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它还扮演着十分积极的社会角色,与许多社会和文化建构具有密切联系,如理性、自我与身份、权力和地位、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等。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情绪的性质呢?本文的分析表明,情绪不仅是生理的、心理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道德的和价值负载的。在对待像情绪这样的复杂现象时,我们必须在个体心理和社会建构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一点上,Hochschild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我把情绪界定为我们通常同时体验到的四种因素的意识:(1)对情境的评估;(2)身体感觉的变化;(3)表情姿态的自由或抑制地呈现;(4)应用于前三种因素之集合的文化标签。这就是情绪的定义”。[16]118-119这意味着,情绪既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一方面,它有着具体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受到本能、驱力以及神经生理机制的推动和调节;另一方面,它又受到社会文化脉络的深刻影响,反映着特定历史脉络的文化观念、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简言之,情绪虽然的确是由社会建构的,但是这种建构具有大量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并且这个基础也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之内。”
作者:尹弘飚 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 上一篇:剖析戏剧小品的用语特征范文
- 下一篇:探究戏剧对儿童创造力的影响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