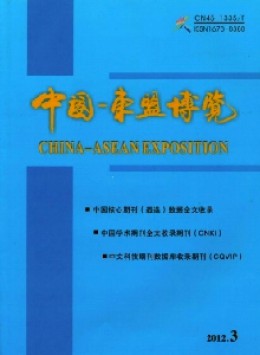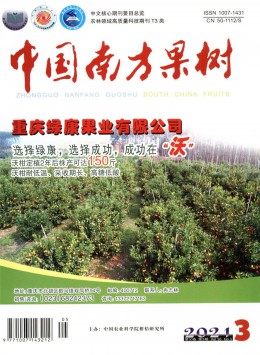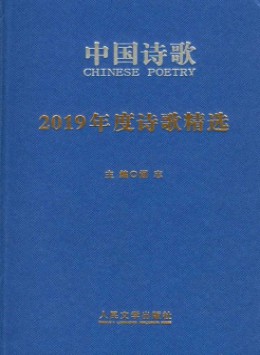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著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时,“对于中国的出版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他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西方出版社会从我们的书目中选中哪本’,而是‘我们有哪些他们需要的产品或者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任何一次成功的合作都需要长期的沟通。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上更是如此”。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作家关愚谦说:“一个国家只要国强民富,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兴趣。目前,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我完全有信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高潮必将到来”。而法国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说,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了。这两句话都没错,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前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传播与影响还很有限,需要加大力度。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扩容”的角度上讲的。后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它一直在场,只是在域外的数量少了些。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观念”和“写作水准”上来讲的。因此,我们需要把两者统筹起来予以综合考虑,把量与质,把“走出去”与“中国学”,把观念与事实结合起来考虑。(本文作者:杨四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上一篇: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范文
- 下一篇:铁人精神对油田企业的作用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