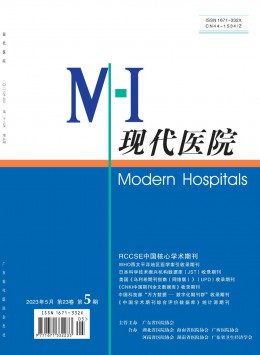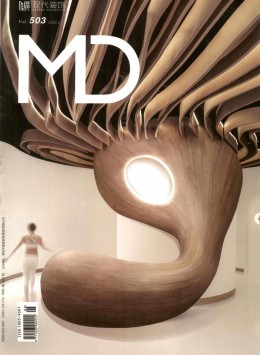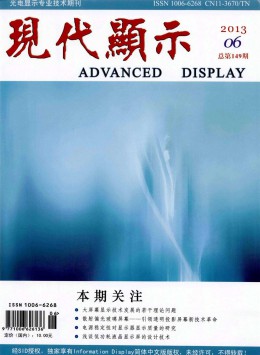现代文学作品跨文化阅读障碍思考

[摘要]文章在对外国学生的文章、论文、课堂讨论等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的基础上,研究总结了外国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跨文化阅读的主要障碍,包括语言上的局限语码特征、文学能力的欠缺和跨文化阅读策略上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阅读;障碍
中国现代文学课是国内院校普遍开设的对外国学生的文化选修或必修课程,课程的核心是来自异文化的外国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和具体作品的跨文化阅读。这样一种跨文化阅读实际上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意义。微观层面是指对具体的文学文本的阅读;宏观层面指对30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包含1917到1949年间中国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的阅读。这两个层面的阅读实际上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般而言,对具体作品的阅读理解是文学课教学的基础和重点,我们认为对外国学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也不能例外。脱离开对具体作品的阅读理解,中国文学课的教学就是空中楼阁,而且对外国学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中产生的、以形象的方式表现社会历史文化的一系列话语和篇章,对作品的解读无法脱离开对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跨文化阅读本质上也是一种在一定社会语境中的交际过程,对现代文学的跨文化阅读是来自异文化的读者和中国现代作者、作品的交流过程,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理解过程,围绕具体作家作品的广义的历史文化是这一交际过程的语境。这种阅读是从一个跨文化的角度发现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双向的、对话式的理解阐释过程,一种理想的跨文化阅读甚至能帮助我们看到从单一文化内部难以发现的文本的意义。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和阅读中遇到障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中高级、在一般性阅读和交际中已经相当自如的学生在开始文学课学习和作品阅读时也感到非常困难。一些学生在阅读时往往无法顺利理解词汇、句子、篇章直到作品的主题和作家的意图,对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的理解也零散、杂乱,甚至相互矛盾。同时,在阅读顺利的学生和阅读困难的学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2009至2014年共159名学习过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认为该课程“难”或“很难”的学生约占79%,同时也有约12%的学生表示“不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很多学生并不具备很好的跨文化阅读能力,而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阅读能力,对学生跨文化阅读障碍的分析研究就成为一种必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为找到学生学习的障碍和难点,从2009年开始,我们对学生的文章、论文、课中的讨论等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并做了6批次问卷、访谈调查,分析研究其跨文化阅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综合各方面材料,我们认为外国学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跨文化阅读存在语言、文学、文化3方面的障碍。
一、语言障碍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外语阅读障碍,而是由于学生汉语能力特征和作品语言特征冲突而产生的语言障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学生普遍认为阅读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作品的语言太难。例如有很多“特别”、“不常用”的词汇,有一些的“复杂”、“没见过”的句子。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和外国学生的语言学习特点有关,也和文学作品的语言特点有关,即外国学生的语言和文学作品的语言之间存在着需要跨越的障碍。借用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rnstein)的一个概念,我们认为这里存在为局限语码(restrict-edcodes)和复杂语码(elaboratedcodes)的冲突。伯恩斯坦认为语码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具体的选择原则,能调节他对一种特定语言所代表的全部可能性进行的选择。这些选择起初诱发一个人在准备讲话和听别人说话时所用的计划步骤,然后逐渐强化它们,最后把它们固定下来。伯恩斯坦区分了两种调节言语计划功能的语码体系,即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他强调从表象上看,如果一个人倾向运用复杂语码来组织他的典型言语,那么其句法选择很难预测,因为他是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以精确、详细地把个人意图、独特经验明确地用词语表达出来,并力图使自己的言语富有个性以区别于他人。但是在局限语码里,正确预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为词汇和句法结构都局限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①大部分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和交际过程是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环境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语言群体,外国学生的语言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他们倾向某种“标准化”的语言,希望形式———语义———功能之间具有一种简洁、清晰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语言知识的掌握逐步发展语言能力。而在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对外国学生汉语教学广泛采用的是“结构———功能”综合教学法。
在教材设计和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词汇和句法结构是经过选择的、限定的,其功能和语义也是根据等级严格限定的。学生通过相对机械的学习———操练———反复的程序掌握结构和功能。言语信号的编辑过程被大大简化了,而且一般都是一个模拟的过程,并不具备真正传达个人意图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语言课程中所学习的词汇和句法是经过选择、限定的,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模仿用重复率较高的词汇和粗略句法而不是精确地表达个人意图。而在交际过程中,又会发生吉尔斯(H.Giles)提出的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accommodationtheory)中的“靠拢”(convergence)现象。即在与外语学习者的交际过程中,操母语的人出于使交际能够顺利有效地进行或者支持鼓励帮助对方学习外语等等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言语方式去适应对方的语言水平,包括放慢速度,发音更清楚,改变用词和语法结构,更多地采用非语言信号如表情、体态、手势等等帮助交际。这种特殊的言语交际策略实际上就是主动限制自己选择词汇、句法的范围以及传达信息、表达意图的自由,部分放弃表达的精确性。在此环境下,外语学习者更注重某些“基本的”词汇,和“标准的”语法结构,而常常忽略语言的复杂性和表达的精确性。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语言关系和语言学习环境会引导学习者对接触到的语言要素进行心理标注,标明那些“标准的”、重复率较高的词汇和句法是应该并且是可以学到的,而一些主要用于清楚、精确地表达个人意图的“不常用”的形式则是可以忽略的,从而逐步形成局限语码倾向。但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作家们一般来说总是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选择词汇和句法,尽可能精确、详细地阐述个人意图,并力图使自己的话语富有个性以区别于他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作家们总是倾向于运用另一个层次的语码,即复杂语码。虽然两种语码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的差别,而是语言使用上的差别,是对待语言及其用法的内在态度的区别,但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语码的差异,足以造成学生的阅读障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很多学生都觉得鲁迅的语言很“别扭”,有太多的“然而”、“却”、“便”、“也就”这类副词和特别的短语,很不容易真正理解。鲁迅的语言自然不是一种“标准”、易于模仿和重复的语言。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思想者、一个探索者,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话语环境,他写作的目的在于发现、揭示传统文化的弊病,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表现自己内心复杂剧烈的矛盾冲突,例如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的徘徊挣扎。例如《孔乙己》里最后一句话“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很多学生就觉得费解,不理解为什么“大约”和“的确”两个矛盾的词要用在一个句子里,常常提出孔乙己到底死了还是没死的疑问。同时由于鲁迅并不希望读者只是一个听众、一个看客,而是设想读者与叙事者或是作者一同思考。所以鲁迅在写作中更多地倾向于利用语言的认识功能,在很多时候作品中的叙事者又是自己的受话人,在很多时候他在与自己对话,做灵魂的交战。这样的对话在《祝福》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也较容易解释鲁迅作品在话语上的一些特征,例如语调一般较为平稳,节律上又多曲折,即使在叙述时也喜欢用“然而”、“却”、“便”、“也就”这类副词等等现象,因为这些正是思考过程的一种外在表达。外国学生在原有的语言基础和习惯下要阅读这样的语言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因此,在他们不能通过大量阅读来习惯鲁迅特有的语码特征的情况下,指导外国学生阅读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阅读前简要分析说明鲁迅的话语特点,在阅读中通过实例反复提示学生,帮助学生进入阅读、对话情境理解作品语言,并逐渐培养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语码转换意识,在阅读其他作品时也有意识地关注作者的语言风格,以减少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语言障碍。
二、文学障碍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能较深入地进入作品,理解作品的意义、风格和时代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些学生在了解了《孔乙己》的时代背景和主要情节后仍然表示:“我现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但是不能了解孔乙己为什么要那样生活。”一些学生在课后讨论中坚持认为《阿Q正传》主要是批评那个时代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们缺乏的是一种文学能力,一种在理解文学规则的基础上与中国现代文学作者、作品对话交流的能力。缺乏这种文学能力就会如卡勒(1975)所说:“一个人如果完全不懂文学或不了解阅读文学作品的规则……那么当他面对一首诗时一定会无可措手……他或许根本不能从文学的角度理解这首诗,因为他缺乏读诗时所必备的文学能力。他还没有内化文学的语法,而这种内化才能帮助他将语言组合成为文学的结构和意义。”①我们知道尽管文学作品是结合了作者的经验、情感、想象力和创作灵感等等的一种个人性的创作,但并非是纯个人性的自由创作,而是由语言、情节、人物、符号、风格等元素按照一定的文学规则组成的,这是它可以被接受和阐释并呈现意义的前提。如同我们理解、掌握了语法规则,熟悉了形式和语义、功能的对应关系之后才能顺利进行言语交际一样,一个读者只有理解、掌握了文学话语的语法规则,具备了“文学能力”,阅读才成为可能。所以卡勒所说的“文学能力”实际上是指读者运用“文学规则”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也就是读者以一种可以接受的、符合文学规则的方式去阅读和阐释文本的能力,而这种作者创作、读者解读具体作品依赖的文学规则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规则外,还包括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时代的文学潮流。因此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要想能够找到适当的阅读规则来“读懂”作品,发现作品的意义,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他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阅读经验和能力,同时对中国文学的传统以及现代文学的潮流有所了解。
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在学习中国文学课程之前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过中国文学作品的学生人数占到了48%,但认为自己对作品留下较深影响或能够准确说出作品名字的学生仅占约9%。在对作品本身极度缺乏接触、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理解和熟悉文学规则并形成所谓的文学阅读能力是不现实的。而这种能力的缺失必然形成外国学生阅读时的障碍,阅读作品时只是把作品作为一篇记叙、说明文字看待,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故事情节、人物结局等等,而忽略了其他文学表现手段。这常常会导致学生了解了故事的过程经过,而误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不少学生在阅读沈从文的《萧萧》的时候常常只注意到那种特殊的婚姻及人物结局,而把对恬淡自然的农村生活场景、淳朴美好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忽略不看,觉得“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禾花风翛翛吹到脸上”这样的句子“难以理解”、“没什么意思”等等。结果最终很多学生在读完作品后留下的最深印象只是中国有小丈夫和童养媳的奇异风俗。这种文学阅读能力的缺失导致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作品,很难真正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不少学生因而产生对文学作品阅读和文学课的倦怠情绪,进一步形成情绪上的障碍。
三、文化障碍
外国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在文化方面构成主要障碍的并不是文化差异本身,因为理解阐释文化差异就是跨文化阅读的主要目的。真正的障碍是学生的某些跨文化阅读策略,包括定型观念(stereotype)、由于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而产生的同质化的假设倾向和在读解作品策略上的简单化判断的倾向,这些策略阻碍了学生跨越文化差异解读作品。对于Lippmann在1922年提出的定型观念,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概念在认知心理学上的意义,即认为虽然定型观念这种对某一群体或社会类型所共有的特征的认识,常常带有类型化或简单化的倾向,但在人类认知行为上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它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基础,“这样一个基础不单对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是必不可少的屏障,而且是对行动的鼓励。”①认知心理学也在阅读感知方面提出了这样的假设:阅读过程是读者在自我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定型观念和文本所表达的现象和内容交织在一起产生意义的过程。接受未知的新信息的阅读行为必然会激活读者所固有的定型观念,作为对新信息进行分类、简化、加工的一个基础,但另一方面,新信息也会反过来对固有的定型观念产生修正和调适作用。从这一角度说,定型观念对阅读的影响是必然的,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其定型观念的影响,但是如果在跨文化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定型观念过分强化、固化,拒绝新信息的修正与扩展,定型观念的消极阻碍作用就会暴露无遗。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化的观念去理解作品,把作品作为对这种观念的印证和注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例如一些学生在读了许地山的《春桃》后不能从作者塑造人格理想的角度去理解,而出于对现代中国妇女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固有印象,认为这样的故事在那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而“是可笑的”。与定型观念不同的是另一种阅读障碍是学生在读解作品策略上的简单化判断的倾向,这种阅读不是从学生自己固有的观念出发,而是将某种具体的解读角度和背景知识过度泛化,把众多作品纳入到单一的阐释模板中。在实际的现代文学课教学和一些现代文学教材中,对时代历史背景的介绍被作为帮助学生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手段,但在教学中我们发现,部分由于前述语言和文学方面两个因素对学生阅读造成的障碍,学生常常不对作品做深入细致的解读,而是试图带着某种对时代历史的印象去笼统地理解作品的整体意义,在缺乏对作品话语进行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就成了本末倒置,其结果常常是用某种观念去误读作品,把作品曲解成某种时代特征、历史状况的注脚。例如很多学生对中国现代历史印象最为深刻的两点是新旧传统的冲突和抗日战争,所以常常从这两个背景出发理解所有作品。例如不少学生在回答关于“骆驼祥子”的悲剧原因时都把这两点作为主要的原因,这显然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误读。另一个阅读策略上的问题是由于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而产生的同质化假设倾向。从文化的普遍性意义上讲,任何文化之间都存在某些共同点,这些文化间的重叠之处正是与异文化交流的出发点和基础,我们从这里出发,参照这种共同性,从而发现文化间的差异性。但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同质化假设倾向,这种现象也同时存在于跨文化阅读中: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忽略文化差异,从母语文化的观念出发理解作品。
这种倾向在有些时候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作品,例如韩国有所谓“日据时期”,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感触有助于他们理解与中国抗战有关的作品,所以很多韩国学生都觉得艾青的诗《我爱这土地》很容易理解并产生共鸣。但这种倾向的泛化则常常产生阅读上的障碍,例如韩国学生就很不理解闻一多《口供》中的“我爱的是……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因为“‘鸦’在韩国老人说是凶鸟,它代表了死人或坏的事情,蝙蝠也是让人害怕讨厌的鸟。”所以他们无法理解诗人为什么会爱这样的东西,最终全诗的整体意义也变得无法解读。发现文本的意义或者说阅读理解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外国学生具有跨文化阅读能力。在佛马克等人看来,跨文化阅读阐释能力是人的一种基本潜能:“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恰恰就在于他们具有判断力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摆脱由其阶段、种族、性别、文化或语言所决定的成规性角色的能力。”①只有具有这种能力,人才能从不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中获得新的文化因素,丰富和扩张自己的文化视域,但这种能力在个人身上是需要在跨越障碍、读解作品、发现意义的过程中发掘培养的,像中国文学这一类课程的最终目标还是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理解几部文学作品。
作者:李炜东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 上一篇:建筑工程测量项目化教学探究与实践范文
- 下一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