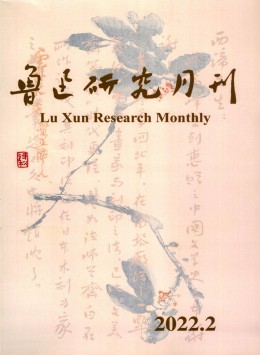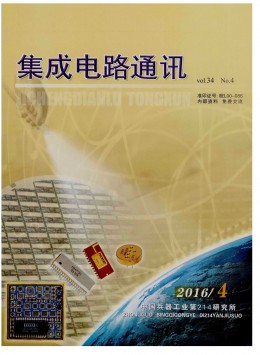鲁迅的作品故乡精选(九篇)

第1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归纳总结,要远比我们现在某些“理论家们”更为深刻。因为从创作《狂人日记》开始,鲁迅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性,就不是什么他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叛”,而是对“狂人”荒谬行为的强烈质疑。这篇小说的艺术构思,仔细分析一下颇耐人寻味:“狂人”在“月光”的感召之下,突然因“觉醒”而变得“发狂”,并对“狼子村”的“吃人”历史,展开了随心所欲的全而攻击。学界历来都对“狂人”的这一壮举,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去给予肯定,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我”既是叙事者,同时也是主人公;两者合二而一的双重身份,更能体现出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志。作为叙事者与主人公的“狂人”,刚一“觉醒”便迷失了自我身份—他用“吃人”去概括“狼子村”的文化历史,一下子就使自己变成了全体村民的对立而,“狂人”终于从那些冷漠与敌视的“眼光”中,发现了自己四而树敌的严酷现实,这令其感到由衷的恐惧与害怕。曾有学者认为,“狂人”之所以会受到“狼子村”村民的强烈拒斥,是因为“狂人”是先觉者而村民们都是“庸人”,他们之间所反映的是“自觉的‘人’与非自觉的‘奴隶’的深刻矛盾”。可是作品文本却并不支持这种说法。《狂人日记》的叙事结构,就是让“狂人”从反叛到饭依,而叙事者与主人公“狂人”,也一直在不停地追问“我”是“谁”。当他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我妹子的几片肉”时,终于“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如果说“狂人”的第一次“觉醒”,使他完全忘却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狂人”的第二次“觉醒”,则暗示着叙事者与主人公回答了“我”是“谁”的精神困扰—“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不是“英雄”的鲁迅与同样不是“英雄”的“狂人”,他们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就是“狼子村”文化的象征符号,是“狼子村”历史过程中的“中间物”,鲁迅最终让“狂人”病愈且“赴某地候补”,其“结局”放在“篇首”就很能说明问题。笔者非常不赞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鲁迅是在以“狂人”的自我否定去否定传统,去充分“肯定‘中间物’的先觉意义。”恰好相反,笔者认为鲁迅是在用他自己的经验理性,去讽喻《新青年》阵营那种狂热反传统的激进行为。因为鲁迅本人要比言说鲁迅者头脑清醒得多,倘若“自我”与“传统”都被否定了,那么中华民族还会存在吗?诚如鲁迅警告许广平时所说的那样,“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人一发狂—自己吃亏,”容易丧失理智。而丧失理智之“狂”,则属于非理性之“狂”,这与鲁迅所主张的“韧战”思想,明显又是相违背的。
如果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让“狂人”从反叛走向了饭依,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故乡》里那个叙事主人公“我”,又因自己与传统的无法割舍性,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过的精神痛苦。小说《故乡》在叙事开端,便推出这样一幅凄凉景象:“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于是,研究者便断言,鲁迅是从批判理性的切入角度,去审视故乡“人”与“物”的落后状态,进而去表达他思想启蒙的现代意识。这种观点貌似合理,其实却多少有点牵强附会。《故乡》明确地传达着作者“怀旧”与“失望”这两种情绪—线环旧”是他文化寻根的本质所在,他忘不了少年闰土捉罐子时的聪明伶俐,也忘不了杨二嫂少女时代的端庄秀丽,这些记忆令鲁迅与故乡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不可磨灭的情感联系。“失望”则是鲁迅思想的真实表达,与外而五彩缤纷的世界相比较,故乡仿佛处于一种比步不前的停滞状态,这是作为现代人的“我”所难以接受的现实,所以“我”才会发现自己与故乡之间,“己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从表而观之,“怀旧”与“失望”的矛盾冲突,加速着鲁迅对于思想启蒙的深度思考,但是细读文本,有两个重要情节显然是被研究者人为地忽略了。
首先,鲁迅曾在作品故事的叙事当中,特别交代过此行故乡的真实原委,是“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己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搬到我谋食的异地去。”毋庸置疑,“熟识的老屋”与“熟识的故乡”,都充满着极其浓厚的留恋色彩,而“异地”一词更是一种强化了的乡愁情绪。这一切都在说明,鲁迅此次回乡,心态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被迫出卖祖屋而隔断其与故乡的文化情缘,鲁迅的内心是不满与愤慨的。比如当挚友许寿裳问他是否有回乡定居之意时,鲁迅的回答是“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挚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并非是鲁迅自己的本意,而是被族人“所迫”的结果。故鲁迅对于故乡的失望感,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由“爱”而“恨”的抵触情绪。
其次,是鲁迅对于中年闰土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感到非常的失望,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鲁迅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鲁迅自己却并这么认为。在作品的结尾处,鲁迅写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鲁迅这段话是大有深意的,“切近”暗示着他对闰土务实性人生观的充分肯定,而“茫远”则暗示着他对自己务虚性人生观的强烈质疑。因为经验理性使鲁迅明白,“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那都是“聪明人”自欺欺人的障眼法;但归根结底,“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毫无疑问,鲁迅赞赏闰土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实际上就是在赞赏那些淳朴故乡人的生存智慧,他们不会说“正人君子”那种“热昏似的妙语”,而是默默地咀嚼着“生的乐趣”与“生的苦趣”。如今他却要永久性地告别故乡去“异地”谋食了,这种灵魂漂泊意识才是导致鲁迅痛苦思索的精神动因。
第2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关键词:《朝花夕拾》;乡土世界;江南风情;影响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010-01
一、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乡土世界滋养了鲁迅的精神世界
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的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的积累,以及对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的感受能力,具体说来就是作家的乡土情结。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品中所洋溢而出的江南风情和深厚的越文化风物,以及随着年华的逝去,烙印在作品文字中的时代的痕迹。
在鲁迅的作品中,乡土风情主要起到的是烘托氛围和情调的作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者有序的描写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色。春天,从的菜洼写到桑葚;夏天的鸣蝉长吟到叫天子在草间直窜;秋天,泥墙根带一部分的描写;草园的冬天又是怎样的呢?“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于是到雪地里捕鸟,那快乐、那情趣,自在其中了。四季的不同景色给我们呈现了充满乡土风味的江南风情。油蛉、蟋蟀、蜈蚣、斑蝥,还有何首乌,等等,这些看似毫无趣味的小东西,在作者的眼里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石井栏之所以“光滑”,是因为井经过了常年累月的使用;之所以知道它“光滑”,是因为童年的鲁迅多次好奇地摸过它。说黄蜂“肥胖”,不仅是它的体态较别的昆虫肥大,而且体现了儿童特别的感觉。叫天子忽然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也不单写出这种鸟儿的机灵轻捷,还表现出儿童的羡意。在鲁迅的笔下,我们总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绍兴一带那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以及城镇乡村的乡土气息。
二、人文精神的亲切土壤――乡土世界的历史沉淀
外在的环境对于作品的理解本身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真正处于核心位置的,我们认为始终是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的山川灵秀之气丛聚于人,逐渐成为这一地域的人群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性格。《朝花夕拾》中的很多文字,都十分的温暖人心,好像一股温和的暖流缓缓地流过,河底蓄满的是鲁迅浓浓的故乡情、亲情、友情。
《朝花夕拾》写了鲁迅童年时的求学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与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及师长的怀念之情,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其中《狗.猫.鼠》即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而引发的嘲讽。嘲讽他们散布的“留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的弱者、“到处嗥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达了对弱小者的同情以及对施暴施虐者的憎恨。《朝花夕拾》里的一些作品,表面上是回忆性文章,但它们不单单是对往事的单调记录,而是用娴熟的文学手法交织成的优美散文珍品。尤以作者善于描摹人物的神情心态,把人物描写得活灵活现,《朝花夕拾》就像是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年时代与人类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在《藤野先生》中,“藤野先生是大约三十年前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教授,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我想他现在已经有七十岁了”,对于鲁迅来说,藤野先生是他心中的一股暖流,就算世事浮沉,也不将不会忘记老师的面容,对于已经是不惑之年的鲁迅来说,这确实是一份值得回忆的温暖。
三、文学作品对地域文化的反作用
散文《朝花夕拾》中浓郁的思乡笔调,《故乡》、《社戏》中快乐回想的童年往事,他深情描绘的故乡的桥、乌篷船、集镇、村庄、农舍、酒店……鲁迅记忆深处的民间故事、迎神赛会、社戏、目莲戏、无常等,构成了鲁迅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些鲁迅文字体现的山川风物、民俗文化,构成了绍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鲁迅的笔触,这些事物也就拥有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感染力。鲁迅,作为一种精神,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符号,在绍兴不断传承延续。
《朝花夕拾》为读者刻画出形形的人物很具典型性代表性,它饱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内容表现了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江浙文化的自然风采和人文景观也在这些作品中得以充分彰显,同时对于江浙文化的无限影响也体现在了方方面面。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回顾往事解剖人性的目的,是为了战胜光明,所以他在平静、朴素的叙述中饱含爱憎深情。在行云流水般的笔触下,留有深长的令人深思的韵味。其隽永的艺术魅力,让我们体悟到江浙文化中独特的地理、文化气息。战斗的思想内容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也使得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参考文献:
[1]鲁迅《朝花夕拾》后记[M].1926.
[2]夏中华.中国现代散文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建国后部分)[M].锦州师范学院,1983.
[3]鲁迅.故事新编(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第3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关键词:迟子建;鲁迅;乡土小说;浪漫叙事;生态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I21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6.0031
鲁迅对中国乡土文学发展有突出的贡献,其乡土小说充分代表了他的小说成就的基本地位。正如丁帆所说,“鲁迅小说的重要贡献多由乡土小说所体现”[1]41,而“作为一个乡土小说的伟大实践者,鲁迅为乡土小说提供的典范性作品不仅是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和叙事视角所形成的多元创作方法的生成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所形成的‘乡土’审美形态几乎成为以后乡土小说创作稳态的结构模式”[1]40。同时,鲁迅的乡土小说也为中国当代乡土叙事的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众所周知,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创作的乡土小说,站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探索并谋求改造国民性格,有强烈的写实风格,也不乏浪漫抒彩,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代作家迟子建就深受鲁迅的影响。
迟子建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与体会时谈到,她曾担任过三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师,阅读了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郁达夫等作家的许多作品,认为他们的“很多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散发着经典的光泽”,而他们成就的取得,“除了这些作家身处一个思想变革的时代、深切关注民族的命运之外,还与他们深厚的学养和开阔的眼界有关”,因此,处在成长期的“我们可以更刻苦一些,为自己补充营养上的不足”,努力“吸收和借鉴”他们作品中的“有益的东西” [2]。而迟子建吸收和借鉴鲁迅作品的突出之处在于,自觉继承鲁迅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借鉴鲁迅乡土小说的浪漫抒情风格,培育了她自己的生态主义温情叙事风格。在谈到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调子时,迟子建说,这调子就是小说开头的那句话,即“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有一种“冷冷的暖”[3]。这种兼容冷峻与温情的格调,在她参观、体验鲁迅故居时的情感与精神世界里鲜明流淌,见证了她对鲁迅的无比敬重,见证了她对鲁迅乡土世界的精神传承与开掘。在她的散文《鲁镇的黑夜与白天》中,迟子建写道:“绍兴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鲁镇。”而在鲁镇的子夜时分,“我与几位朋友寻找到了一处大排档”,然后,“我们要了炸臭豆腐干、咸蛋黄炒南瓜丝、爆炒黄泥螺、辣椒鳝丝、盐水煮茴香豆等菜叫了一壶酒。酒不用说了,一定是孔乙己和阿Q都喝过的黄酒。这酒被温过,未放城市里时尚喝法中所加的话梅、姜丝、冰糖等调味品,因而纯正敦厚。”此时此刻,“我心目中的鲁镇的影子就一闪闪地呈现了,我嗅到了一种古中国生活的气息。我仿佛看到了孔乙己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情形,他用尖细的手指在柜台上排出一文一文的铜钱;我还看到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讲述两朵剪绒花故事时怅惘的神情。我甚至想,如果不远处的护城河下停泊着一条船,我们登得船上,在夜色中划浆而行,一定能够看到真正的社戏,能喝到戏台下卖的豆浆,当然,如果碰到一个老旦坐在椅子上咿咿呀呀地唱个不休,我也一样会烦得撑船就走。如果偷不成别人家的豆子在船上煮着吃,就偷一缕月光来当发带,让它束着我随风飘荡的长发。”[4]6-7正是鲁镇唤起的有关鲁迅的回忆、思索与体验,让迟子建意识到:“鲁迅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4]9可以说,迟子建乡土小说的生态叙事精神就是对鲁迅浪漫主义乡土叙事风格的继承和开掘。
一、迟子建对鲁迅乡土叙事精神宗旨的继承与开掘
迟子建眼中的鲁迅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这种浪漫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鲁迅乡土叙事宗旨所蕴藏的浪漫情怀。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创者,鲁迅与中国农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和精神牵连,对乡土世界充满了热情与期待。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一员,鲁迅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胸怀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和现性精神,借以观察和反思传统乡土文明,期望用文学来改造愚弱的国民。鲁迅笔下的传统农民,由于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状况,遭到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同时,由于乡土世界带给他的眷恋与乡愁,使得其文字浸润了对传统农民的深切悲悯与同情。他用自己的笔,书写了乡土世界,流露了诗意的苦涩、愁绪、不安、挣扎,透出对乡土世界的理想或幻想。鲁迅开创了乡土叙事艺术的新气象,展现了乡土小说创作的卓著成绩,但在精神内质上,怀抱着深切的现实主义关怀,袒露出浪漫主义情愫。
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目的,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表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这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文学来改良愚弱国民,体现了革命的、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出自“未庄”、“鲁镇”的乡民,如“未庄”的阿Q及其身上体现出来的封建文化,鲁迅进行了猛烈批判,对造成闰土、祥林嫂等乡土人物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鲁迅用其犀利的目光与笔触展开了剖析,对这类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国民劣根性与奴性进行了抨击与嘲讽。同时,在《祝福》、《社戏》、《故乡》等小说中,鲁迅对乡土生活也有诗意的、温情的细致描绘,表达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
在迟子建文学创作之初,即20世纪80年代,她还没有明确自己的文学宗旨,几乎是凭着自己的直觉或本能,去书写她所熟悉的生活与自然世界,最终成长为当代中国乡土浪漫派的代表。迟子建的创作经历与成就日益丰厚起来,但是,她并没有抛开自然与大地。她秉承鲁迅的乡土文学精神,坚持根植于乡土与自然世界进行书写,对乡土乡民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她并没有回避现实的苦难与人间的恶,坚持在小说中营造诗意、温情,以此来抗拒人性的恶。她站在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立场,将乡土叙事精神的表达,从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主题意识,转换、拓展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关切。由此,她对乡土世界的描述,传达了对现代文明病的批判,体现了对社会生活中的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忧患意识。
迟子建从大自然的变化中敏感地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期的时候, 秋霜不期而至, 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就憔悴了, 这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憾。”[6]她也深知人生有太多的悲凉苦难、善恶纷争,她从乡民身上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善良、隐忍。因此,她并不回避人生的苦难,处处透出对人类的悲悯,并由人及物,对世上所有生灵都体现出深深的爱怜。迟子建认为:“一个好作家对有灵性的万事万物有一种关爱怜悯之情。”[7]在迟子建的创作生涯中,我国文学思潮历经数次变革,迟子建自己的创作技巧和风格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但在作品中营造温情、给生活更多温暖和爱,一直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宗旨。迟子建就是要在小说中留住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生命旅程中那些温暖美好的温馨画面。
在谈到文学的功能时,迟子建毫不隐讳地说:“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8]这既是她的人生观、世界观使然,也是鲁迅的影响使然。鲁迅对人生的悲凉感受比谁都深切,对国民性的剖析比谁都锋利,但他常常在小说的结尾用曲笔来表达美好的期望,因为鲁迅自己也不愿将自己感受到的悲凉寂寞传染给那些还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也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迟子建对于文学疗治心灵的看法与鲁迅是相通的,她相信温情的力量同时就是批判的力量。迟子建的这种文学精神气质得到了文学理论界的理解,如金理说:“迟子建笔下的善意和希望,并不意味着温情主义者的浅薄与局限,它恰恰显现了作家的责任感与写作良知。”[9]
在20至21世纪之交,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显现,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失之殆尽。迟子建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对大自然索取得太多,环境破坏、资源缺失、人类多样化生存消失的危机步步逼近。在执着于人性温暖的同时,她将“关爱怜悯”之情,施于“有灵性的万事万物”,形成了生态责任感和生态叙事伦理,在小说写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在《原始风景》中,那种用瓢舀鱼、用麻绳捕鱼的动人故事只能成为历史,成为后辈者的童话了。在《白银那》中,白银那的渔民经常提着空网,站在萧瑟的江岸上摇头叹息,而一场回光返照的鱼汛,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更多的自然之思、人性之思。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她叙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于其中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部落,道出了人类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尴尬、悲哀与无奈,表达出浓烈的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文明批判精神,传达了和谐的生态理想追求。
二、迟子建对鲁迅乡土叙事美学形态的继承与开掘
关于鲁迅乡土叙事美学形态的特点,根据丁帆的评价,他“首先强调的是那种‘隐现着乡愁’,但又充满着‘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的‘乡土文学’”[1]14,而“‘地域色彩’与‘异域情调’交融一体的‘风土人情’可以展开为差异与魅力共存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1]21。鲁迅的乡土叙事最初突出的是“地方特色”、“风俗画面”,后来正式确立了“乡土文学”概念。这表明,乡土叙事美学形态的基本特点源自乡土风景、风俗、人情的描写。这是乡土文学既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也适宜现实人性的揭露与批判的文本基础。
在鲁迅的《故乡》中,既有“海边的沙地”与“月夜下的少年”交相辉映,也有“荒村”、“冷风”、“枯草”、“断茎”等荒凉风景的呈现。在《社戏》中,既有“豆麦的花香”、“水草”、“连山的两岸”、“渔火”、“航船”、“松柏林”等儿时记忆中的清新风景,也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角下的“戏园”、“红的绿的”、“满是许多头”、“专等看客的车辆”等都市风景。在《祝福》中,既有了无生气的阴暗天色,也有狂乱飞舞的雪花中点上香烛恭请福神、燃放鞭炮的祝福年俗。浙东水乡的风景、民俗、人情历历展现,但同时,这些风景、民俗更具象征意味,借以展现作者的情感,推进主题的展开。
与鲁迅类似,迟子建也成了地域乡土的代言人,即北国的森林黑土的代言人。她的创作极具个性化的地域乡土特色,显示出强烈的北国气息。迟子建对故土与大自然的钟情几乎是很少有人能比的,她是如此执着地抒写那片土地上的生灵万物。她说:“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对我而言,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和生活。”[10]从最初的《北极村童话》到最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北国那茫茫的雪原、铺天盖地的冰冻、流淌不息的江河、无边的松林、神奇的白夜、令人震颤的鱼汛、嫩绿的青葱、散发着香气的土豆花、醉人的冬柿、会流泪的鱼、连绵不绝的秋雨、春日泥泞不堪的街道以及飘渺的雾蔼构成北国独特的地域风景画。而与此相关的风俗民情更是令人应接不暇:《原始风景》中高大气派的木刻楞房、《腊月宰猪》中对过年前男女忙忙碌碌准备过年的场景的描绘以及对齐二嫂葬礼的铺陈、《清水洗尘》中有过春节前的洗尘风俗、《秧歌》中有正月十五看秧歌、看冰灯等娱乐活动的习俗、《逝川》中捕泪鱼的传说和放生的习俗。《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住在自己用木棍兽皮搭建的希愣柱里,随驯鹿觅食而迁徙,他们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萨满是沟通天和地的通灵人,会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赋予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氏族,让整个氏族人口兴旺、驯鹿成群,狩猎年年丰收。萨满通过跳神和唱神歌等仪式来拯救族民和其他生灵。他们还祭奠“白那查”山神,他们猎获了熊或林中最大的动物堪达罕时,就要先祭祀他们的祖先神玛鲁神,祭祀完了之后才分享猎物。他们还为熊做风葬仪式,为熊唱祭歌。他们还常常在跳一种叫做“翰日切”的舞时,发出像天鹅飞过湖面一样的“给咕给咕”的声音。
鲁迅主要是站在启蒙立场对乡下人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精神状态进行批判,因此,鲁迅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仪式往往用于表现乡下人愚昧落后的劣根性,有时也用于表现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如《祝福》中,“祝福”年俗对人的歧视与戕害,贫穷的闰土除了要些实用的物件之外,还不忘要了烛台。而《社戏》中的习俗与风景更多表现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回忆与期待,也与现实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但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民俗风情的描绘通常用于表达对美好人性的礼赞、对古朴民风的留恋和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如捕泪鱼并放生的仪式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以及人对自然的敬畏,《额尔古纳河右岸》有大量的习俗禁忌与祭奠仪式的描绘,作者借此表明人类与其他生灵是相互依存的,这些生灵并不是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猎取的对象,我们应摒弃那种仅仅以自然为资源的思想,既然它们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需,人类应对此感恩并心存敬畏,同时也对文明进程中人性的贪婪、人与自然的疏离进行揭露,让人们切身体验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困境。
另外要注意,鲁迅及其所代表的“五四”小说家,他们“对风土人情的重视,不再只是为了增加小说的真实感,而是承认其具备美感价值。”[11]而地域化的乡风民俗所享有的独立叙事美学价值,被迟子建注入了自觉的生态审美精神。在迟子建的笔下,大自然不只是背景,亲人、故土、动物、植物以及民俗风情都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它们悉数走上前台,甚至成为叙事的主角。迟子建对乡风民俗几近写实的实录,使几近消失的东北民俗仪式得以精彩呈现,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又具备了民俗学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在迟子建的乡土小说中,民俗仪式成了返归自然、寻找精神家园、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
三、迟子建对鲁迅乡土叙事艺术策略的继承与开掘
鲁迅开创了多种现代乡土叙事艺术手法,而迟子建的乡土小说对此多有继承和开掘。
首先,迟子建继承了鲁迅在乡土小说中熟练应用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
在小说创作中,以“我”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和描绘人物,能够更好地表达故事和人物的深层思想意蕴。“我”既是叙述者,讲述着他人的故事,也是故事中的人物,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鲁迅的《社戏》主要讲述“我”在成人后和儿童时代看戏的故事。《祝福》既讲述了祥林嫂的故事,也讲述了自己回乡的故事。在《故乡》中,“我”带着儿时的美好回忆,回到了久别的故乡,由此叙述了回乡行程及“所见”、“所闻”。而其中的“所见”、“所闻”主要讲述儿时曾经的玩伴闰土、曾经的豆腐西施的故事,以及乡邻们的故事。在整个行程中的所忆与所感,经由自己的故事来叙述,借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而所忆与所感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叙事方式打破了旧的叙事传统,增强了主体情感,形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直接对话关系,也使小说具有一定的诗化色彩,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迟子建大量应用了这种第一人称的乡土叙事方式。比如她的小说《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朋友们来看雪吧》、《额尔古纳河右岸》完全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白银那》中有一条叙事线索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都产生了特殊的叙事效果。迟子建发挥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便于抒情的优势,既用强烈的主体情感冲淡小说的故事性,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力,也保障作者的主观意识在小说中显现,便于表达作者的自省意识与强烈的责任感。
其次,迟子建开掘了鲁迅乡土小说所开创的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体现了儿童化的思维与叙事方式。儿童的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相对单纯、原始、直接。鲁迅在回乡的记忆中通过儿童视角回忆曾经的故乡生活,如《故乡》中的“我”对少年闰土海边自由浪漫生活的美好回忆与想象,《社戏》中儿时好友的情谊,对“百草园”的留恋。这些表现出对封建文化和教育的反叛,对自由、自然、平等、互助的文化生活方式的留恋和向往,对造成乡民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因由予以揭露。同时,通过儿童视角的过滤,使传统文化习俗中的美好一面得以呈现,具备特定的审美价值。
迟子建的乡土叙事也巧妙地利用了儿童思维的特点。在《原始风景》与《北极村童话》中,回忆童年生活与自然风光,就以儿童视角观照人生与自然万物。《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上部“清晨”部分选取儿童视角以及儿童语言进行言说,使得生命万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显得和谐而诗意,使自然呈现出成人眼中难以显露的灵性与情感。由于儿童视角对人与物不做严格区分,将人与物当作平等的统一世界来对待,这使得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的过程中,丝毫不觉得有做作之嫌和审美疲劳之感,只感受到一个充满生气、和谐圆融的世界。这与当下人类现实的生存状态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得人类童年时代那种对美和纯真的感悟和追求的意义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这正是迟子建所追求的叙事效果。而迟子建对儿童视角和童年生活的热爱和迷恋,传达了现代人面对社会发展进程中违背人性与自然规律的现象所持有的担心和焦虑,传达了现代人对人类童年记忆的眷恋和回归自然的渴望。这实际上也是作家本人对现实的一种微弱却极富韧性的抗争。
再次,迟子建开掘了鲁迅的“曲笔”手法,形成了乡土叙事的“回归结构”。
在小说创作中使用曲笔,并不是鲁迅开创的。但是,鲁迅专门谈到了曲笔问题,也在自己的小说包括乡土小说以及散文中常常用到,有他自己的独特意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12]所谓“曲笔”,除了受当时的政治压迫而不能明说的不得已之外,还有文学创作本身所需要的含蓄委婉,便于留出“亮色”,为置身于悲剧性生存处境中的人们带来希望,激发人们变革现实、创造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是鲁迅改良人生、反对封建、变革现实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体现。
迟子建也常常在她的乡土小说中营造温情,表达对人性美的追求与礼赞。这种温情叙事方式有其特殊之处,她的许多作品会在结尾处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类似古代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但内涵更丰富、更复杂,可称之为“回归式结构”[13]。在《逝川》中,年老独身未嫁的吉喜因为帮人接生,错过了一年一度的捕泪鱼的时间,当吉喜回到岸边取木盆时,发现木盆中的清水里游着十几条美丽的蓝色泪鱼。在《亲亲土豆》的结尾,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死相隔,在妻子以土豆为丈夫培坟后离开时,从坟顶上坠下了一个又圆又胖的土豆。在《白银那》中,自私有报复心的马家夫妇,在卡佳上山取冰被熊伤害致死后,良心发现,给每家送盐。这一类结尾或是让人在苦难中看到希望,或是于丑恶中发现人性的美好,或是于无望中给人些许慰藉。总之,这类结尾凸显了作者的道德倾向,表现出一种美好的期望,也透出作者对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关心和同情,对文学作为安慰人们心灵的方式这一信念的坚守。迟子建相信,作家越是胸怀开阔,就越具有涵盖苦难的力量。如果作家能够执着地传达这种信念,那么读者也会从中获得驱除苦难、超越苦难的信心和勇气,让苦难变得渺小。毕竟,文学对人性的挖掘和拷问,最终是要引人向善、使人温暖。有时,正是因更加洞悉人间的苦难与残缺,才更想通过想象力在艺术世界中创造一个朴素、温馨的世界,这样才不让人们在苦难中绝望和沉沦。
总之,迟子建自觉坚持以乡土叙事作为安慰心灵的方式,继承了鲁迅关注现实、同情乡土的人道主义立场,将乡土叙事宗旨从“为人生”即人与社会相和谐的主题拓展到“为人类”即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传承并创新了鲁迅乡土叙事美学形态,借鉴并拓宽了鲁迅乡土小说的叙事艺术策略,借以生动地描绘东北地域特色的风景、民俗、人情,礼赞美善人性,既给人以独到的审美享受,也激发人们关注人类所生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表达了重建自我意识、返归精神家园的美好期待,彰显了当代乡土小说的生态叙事精神。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迟子建.生活照亮艺术[N].光明日报,2012-05-24(007).
[3]迟子建,孙小宁.我要冷冷的暖[N].北京晚报,2008-11-17(38).
[4]迟子建.迟子建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5]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6]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J].小说评论,2002(2):35-37.
[7]迟子建,闫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J].小说评论,2002(2):28-31.
[8]王薇薇,迟子建.为生命的感受去写作[J].作品,2007(8):49-52.
[9]金理.温情主义者的文学信仰[J].小说评论,2007(6):17-22.
[10]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06(2):34-35.
[1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2.
[12]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1-442.
[13]管怀国.从“回归式结构”看迟子建的温情主义世界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1):114-118.
From Romanticism to Ecologism: Narrative Comparison
between Lu Xun's and Chi Zijian's Local Novels
LI Hui-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Xiangyang441053, Hubei,China)
第4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父母关爱备至
1929年9月27日,周海婴生于上海,海婴出生时属难产,鲁迅在医院里焦急万分,想方设法抢救许广平母子。海婴降生后,鲁迅给儿子取名“海婴”,就含有“上海出生的婴儿”的意思。后来鲁迅曾对海婴说:“你长大后如果对这个名字不满意,自己可以重新取过。”可见鲁迅对儿子的宽厚。
周海婴儿时他家住在上海大陆新村,楼下的房间用装有玻璃的门隔开。有一天,一位邻居小朋友来他家玩,不慎把海婴关在里间。由于门太紧,海婴一时打不开,他心里非常焦急,拼命想把门打开,他一掌用力推过去,一块门玻璃就被他打破了,手也被碎玻璃划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海婴一时慌了,在楼下放声大哭,正在楼上书房中写作的鲁迅听见哭声,三步并作两步奔下楼梯,马上用云南白药和纱布将海婴手上的伤口包扎起来,并安慰海婴说:“孩子别慌、别慌,过几天就好啦。”紧接着鲁迅又和蔼地将吓得呆在一旁的那位小朋友送走了,事后鲁迅也没有责骂海婴,而是请师傅将门玻璃重新装好。这件小事给周海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周海婴与邻居的小朋友关系一直都很友好。周海婴的夫人马新云当年就住在他家对面,所以他俩长大后还结为夫妻。
鲁迅平时忙于写作,经常接待来访的进步学生和作家,但他每天总要抱一抱海婴,有时还要与许广平抱着海婴去照相馆照相。照片取来后,还要写上日期,然后珍藏在影集里。在与友人的书信里,鲁迅曾多次提到海婴,可见鲁迅对海婴非常喜欢。
鲁迅对儿子的爱护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字所能概括的。他有一句名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话凝聚了鲁迅先生的一腔父爱,也包含了鲁迅对孩子的人格尊重。
鲁迅和许广平都爱好文学,为什么周海婴没有从事文学创作呢?原来他上大学时,最初在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就读了两年,后来又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他为什么没有向父母学写作呢?一方面是周海婴对理化科目,特别是无线电非常喜欢;另一方面跟父母对他的家教有很大关系。还在海婴年幼时,鲁迅就教育儿子“不要去当空头文学家”,这也成了鲁迅对海婴的遗嘱。鲁迅去世时,海婴才7岁,此后母亲经常与海婴在一起回忆鲁迅,可以说鲁迅的许多情况是母亲讲故事一样讲给海婴听的,他从母亲那儿进一步了解到父亲鲁迅。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二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后于1968年因病不幸去世。许广平生前也经常告诫海婴:“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去沾鲁迅的光,而应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足。”
生在鲁迅光环下的周海婴一直牢记着父母的教诲,从不沾父母亲的光,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社会上立足。1956年他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正赶上我国搞核武器研制,他便被分配到北大核物理系,从事筹建实验室工作。1960年以后,他又到国家广电局技术部搞无线电规划工作,曾担任过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一直干到1994年离休。他是中国鲁迅研究室和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顾问。经有关部门特批,他的家中至今还装有一个无线电台,平时可经常摆弄一番。
周海婴曾当选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第八届至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建议,特别是针对《著作权法》和反盗版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明确意见,在履行全国人大代表义务和参政议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鲁迅的儿子,他在业余时间和离休后,为研究鲁迅的人生和文学作品、传播鲁迅爱国主义精神,宣传鲁迅的创作思想、维护鲁迅的尊严等方面,默默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主编出版了《鲁迅回忆录》,并积极推动《鲁迅大全集》的出版工作。他还兼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和绍兴、上海、北京、厦门鲁迅纪念馆或鲁迅博物馆名誉馆长、顾问。
一生爱好摄影
周海婴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摄影,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退休后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拍摄了许多反映时代变化的风土人情照片。
周海婴在回忆自己的第一架照相机时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只有一架照相机。他虽然用过不少机型,但手里总是只有正在使用的一架。对于儿子痴迷于摄影,母亲许广平非常支持。周海婴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都是许广平帮儿子细心粘贴的,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许广平还为海婴的初学摄影簿亲笔题字:“雪痕鸿爪”、“大地蹄痕”。1948年,许广平还将买防寒衣服的钱省下来,给海婴买了台照相机和20个胶卷。这架相机,周海婴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还存放在家中。
一生热爱摄影的周海婴,共拍摄了2万多张的照片。2008年9月27日金秋时节,他在北京举办《镜匣人间――周海婴80摄影展》。2009年10月到11月,他又举办了《朝影夕拾・周海婴1943一1950摄影展》。人们在这两次展览上,看到了1948年郭沫若、侯外庐、宦乡等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到沈阳后又留下迎接“新政协”的历史瞬间。周海婴1956年10月拍摄的《鲁迅墓迁墓》和《文学家巴金》等老一辈著名文学家系列摄影作品,《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的召开(沈阳铁路宾馆)》、《黄炎培在火车上致词(火车上)》等历史题材摄影作品被摄影界称为见证那段历史的“孤本”。
周海婴撰写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还收录了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该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热爱故乡浙江
受父亲的影响,周海婴对故乡浙江特别是绍兴经常念念不忘。早在1936年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后于1948年秋随母亲许广平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再到解放区,最终定居在北京,但他始终忘不了故乡绍兴。海婴儿时常听父亲在家中说绍兴话,他后来也学会讲一口地道的绍兴话,这跟父亲不无关系。海婴还喜欢吃绍兴菜,那是鲁迅先生逝世后,海婴的叔叔周建人先生为了照顾许广平和周海婴母子,专门搬到海婴家楼下住。有一段时间,海婴由师母王蕴如女士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并经常做绍兴菜给他吃。尤其是霉毛豆、霉千张,这些菜虽闻起来臭,吃起来却很香,又开胃口,海婴十分爱吃,于是绍兴菜也吃就习惯了。1948年春天,他第一次随母亲和周建人叔叔回绍兴时,就买了老酒、茴香豆、鹅肉吃,还乘乌篷船到大禹陵、东湖游览了一天。
周海婴1997年10月回到绍兴,被鲁迅中学聘请为名誉校长。在故乡住了好几天时间,也到大禹陵、东湖等景区重游过。在游柯岩风景区的“名士苑”时,他看到一块石碑上写有自己的名字,谦虚地说:“我不是名士,我是绍兴人。”说罢倚在刻有“我是绍兴人”的大字石碑上,特意请人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绍兴人的周海婴,一直关心故乡的变化,并为绍兴鲁迅纪念馆提供了很多鲁迅的物品,提出过许多宝贵建议。
正因为海婴热爱父母和故乡,所以他对鲁迅中学的校领导和笔者说:“我对鲁迅中学这尊鲁迅雕塑非常满意,因为这是鲁迅当教师时的形象。我父亲非常热爱学生,热爱青年,对朋友和同学、同事和蔼可亲。母亲和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脾气,但有段时间为了政治的需要,有些人把鲁迅说成‘老生气、老发脾气、老骂人的人’,这是错误的,其实骨头硬的人并不一定老骂人。‘横眉冷对千夫指’,这句话表现了鲁迅对敌人的憎恨;‘俯首甘为孺子牛’,则是植根于鲁迅对人民的热爱。”周海婴还向鲁迅中学捐献了一些鲁迅的书,他对该校的师生们说:“我父亲是个很普通的老师,很普通的文化人,是人民大众的一员。其实,他最初并没有想当什么‘家’,他只是时刻想着中国的命运,想着中国的未来,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才成为今天人们心目中爱戴的鲁迅。学习鲁迅,不要单纯地学习鲁迅的一两篇著作,要了解他是怎样成长,了解他怎样和社会、历史结合,了解他怎样为人类发展进步、为国家命运着想、奋斗……”
近年来,周海婴更是经常回到故乡,开展或参加各种活动,与故乡的联系越来越密切。2004年4月28日,他出席了绍兴县鲁镇主题公园的开园仪式,被聘为鲁镇名誉镇长,并为鲁镇开园开启钥匙;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绍兴举行,海婴出席了典礼并与父亲笔下闰土的原型章运水的孙子章贵相见。2008年,鲁迅先生逝世72周年纪念日,55件鲁迅的墨宝真迹亮相于绍兴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中国兰亭书法节上。这个展览能成功举办,周海婴付出了许多努力,有些国宝级展品是他出面向国家文物局借展的。同年10月,海婴将他的摄影作品带到绍兴鲁迅纪念馆,并举行了《许广平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展》。其中有《母亲许广平在外滩》《周家“老台门”》等系列作品,受到了乡亲们的欢迎。那次回故乡,乡亲们为庆贺海婴八十寿诞,还在海港大酒店为他举行了寿宴。席间他激动地说:“谢谢父老乡亲。在我父亲去世72年的今天,大家团聚在这里,为我的生日祝福,这么浓浓的乡情,让我感动不已。”
此外,早在1909年6月,鲁迅结束了留学日本7年的生活回到祖国,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现为杭州高级中学)任教。2009年是鲁迅在杭高任教满100周年,杭高特地把周海婴请到杭州,为400多名学生做了场讲座。因鲁迅在杭高任教的这段历史,北京、上海、绍兴等地的鲁迅纪念馆都没有史料,因此海婴特别感兴趣,一到杭高就忙着寻找父亲的踪迹。在杭高鲁迅纪念室内,海婴手拿放大镜,仔细地鉴赏父亲鲁迅留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学生毕业证书上的印章。在杭高校史陈列馆,看到鲁迅的一件手稿藏品,他立刻举起相机拍摄了下来。
Lu Xun’s Son Passes away at 81
By Xu Zhongyou
Zhou Haiying, the son of the famous 20th century Chinese writer Lu Xun (1881-1936), died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7, 2010 at the age of 81 in Beijing. His death received extensive coverage in news media across the country largely because he was the son of Lu Xun. He is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son of all the sons of well known writers in China.
Zhou Haiying was born on September 27, 1929 in Shanghai. After learning that Xu Guangping was having a difficult labor, Lu Xun instructed the doctor to save his wife first if any emergency should happen. The mother and the baby boy both were safe. Lu Xun named his son Haiying, meaning a baby born in Shanghai. Lu Xun advised his son later that he could change the name if he grew up disliking it.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son liked the name or not, but it was his name for all of 81 years in his life.
Though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were writers, Zhou Haiying did not pursue literary fame at all. He studied sociology for two years in Beijing-based Fu Jen University before he turned to study radio at the Physics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He chose such a future for two reasons: he did have a passion for science and radio in particular and he followed his parents’ advice. When he was a baby, his father advised him never to become a man of letters who could do nothing but play with empty words. This advice also appeared in Lu Xun’s famous will.
When Lu Xun died in 1936, Zhou Haiying was seven years old. What he knew about his father came largely from his mother, who passed away in 1968 after serving many prestigious positions. Xu Guangping repeatedly cautioned her son against making use of the glory of Lu Xun at any time. Instead, she advised, he should establish himself on his own in society.
He minded the parental advice to the letter. In 1956 he graduated from the Physics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As China was going all out to produce its own nuclear weapons at that time, the young scientist was assigned to the nuclear physics department of the Beijing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put in charge of setting up a lab. In 1960 he was appointed to a position at the Broadcasting Administration, the predecessor of the present-day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He worked there until retirement in 1994. He was an expert in radio communication. With special approval, he had a radio transmitter at home.
Zhou Haiying is also known for his hobby: photography. He started learning to take photos when he was just a boy. A friend of his mother’s lent him a camera. His mother encouraged him. In 1948, she bought him a camera and 20 film roles. The camera was in use until the 1980s. In his lifetime, Zhou Haiying took more than 20,000 photos. Many historical moments he captured on his camera are the only existing visual records of some historical events and some historical people.
In September 2008, he staged a solo show of his photographic works in celebrat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in advance. A year later he staged another show of the photos he took from 1943 to 1950.
He was the author of the book “Lu Xun and Me in 70 Years”. The memoir, published by Wenhui Press, includes many of his photographs.
Zhou Haiying had a passion for his hometown Shaoxing in Zhejiang, a coastal province in eastern China. His mother and he continued to live in Shanghai for about ten plus years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in 1936. In the autumn of 1948, the two moved via Hong Kong to the liberated area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s and they settled down in Beijing. He heard his father speaking the Shaoxing Dialect at home for seven years. He learned to speak the dialect perfectly. After his father died, his Uncle Zhou Jianren and Aunt Wang Yunru moved in to take care of the mother and the son. The dishes prepared by his aunt customized the boy’s stomach to the taste of Shaoxing. In the spring of 1948, the 19-year-old Zhou Haiying visited Shaoxing for the first time. He tried Shaoxing rice wine, beans flavored with aniseed, and goose meat. He also took a black-awning boat ride to visit the Mausoleum of Yu the Great and the East Lake.
第5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关键词】《祝福》;叙事结构;叙述语言艺术
叙事结构是一部小说布局的纲领,叙事结构的形式对于小说情节的思想主题与展开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之一,在这一作品里,鲁迅应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为读者深刻的展示了当时农村的真实面貌,下面就针对《祝福》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的分析。
一、“归乡”模式的应用
“归乡”模式是鲁迅作品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叙事模式,在《祝福》中,以主人公回到鲁镇的角度来描写小说的主体时间。在文章的开篇中,写到了“我”回到了鲁镇,这次回来并非是为了《故乡》中提到的“寻梦”,而是“早已决计要走”,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故乡对于“我”而言,是如此的陌生,“我”无法融入其中。在鲁四老爷的眼神里,“我”看得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因此,不会在这里久留,在决心要走的时候,却意外的遇到了祥林嫂。在接下来,作品通过两条主线来为读者呈现出旧社会的农村,一方面,祥林嫂的发问激起了“我”精神世界的波澜,另一方面,文章通过“我”旧时的回忆串联起了祥林嫂的一生。
最后,“我”开始对祥林嫂的一生进行回顾,虽然文章的主线是以顺序的模式来进行展开,但是却穿插了倒叙的模式,这并不会影响文章的主体,反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为读者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应用
在《祝福》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一直以来,鲁迅小说与传统小说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叙述方式的区别,他的小说主要使用的限制性的叙述,从而将叙述人与作者明显的剥离。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为小说中的“我”,“我”并不是与故事脱离的作者,而是实实在在经历这些事物的人。《祝福》中的“我”实质上是一个旁观者,从始到终,“我”都没有对事件进行判断和评价,不带任何的感彩,“我”对于事情的叙述就是事实的本体,这不仅仅是叙事内容的客观需求,也是对小说创作史上叙事方法的拓展。
三、多语叙事模式的应用
在《祝福》中,大量应用了多语叙事的模式,将每一个故事线索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故事主线的描述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就有效的增加了事件呈现的多面性与立体感。祥林嫂到鲁家做女工时,看到了“夫家的堂伯”,此时,作者以鲁四老爷的口吻描述到:“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不久,这一推想就得到了证实。而“我”是不可能清楚祥林嫂在做女工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正好就借鲁家人的口中表达了出来。此外,作者也安排了卫家山卫老婆子这一人物,她成为了联系祥林嫂与鲁家的一个纽带,合理的展示出了祥林嫂的人生经历,这就对祥林嫂未来的人生悲剧奠定了基础。此外,鲁镇的人、四婶、柳妈也或多或少的参与到了事件的叙述过程中,这都是通过与“我”独立的语言来描述出来的,让作品可以表现出一种多角度的叙事模式。从这一层面而言,《祝福》中通过主体事件与多语叙事模式的应用将事件的原始形态生动客观的展示出来。
在故事中,“我”的存在与多语叙事模式属于一个两面性问题,“我”通过不同角度的补充让故事更加的真实、完整,多语叙事模式则可以对事件中的不同声音进行有机结合,让事件的内部逻辑关系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可以看出,“我”并非一个全能的存在,也需要通过不同的语言来了解事件,此外,“我”不可能详细了解事件的细节,文章使用了虚拟视角的叙述模式有效丰富了主体事件,这不仅没有让叙事风格变得累赘,反而让叙事模式变得更加生动、真实。
四、叙事结构的变化
在很多小说之中,情节模式都十分的有限,只在少数的篇章中应用了插叙与倒叙的模式,在鲁迅的小说在这一方面就有了很大的突破,他的小说主要以叙述人语言来表达情节,叙述人语言对于鲁迅小说叙事结构转换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叙述的不单单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状态的变化,在这种状态变化过程中,作者为读者呈现出了下层劳动者精神上的变化动态,虽然没有外部斗争,但是却有冷血的内部斗争,这是人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悲剧。
这种审美思维是与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思维相统一的,叙述人并不会着力表现事件的变化,着重表达的是状态的变化,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艺术是与小说主旨相符的,这也是鲁迅小说之所以成为名作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凯.谈鲁迅小说《祝福》非个人化视角的出色运用[J].语文学刊,2007(16)
第6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论文摘要: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兴起的一个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大约形成于二十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作家有普迅、许杰、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等。乡土文学作家与其描写对象之间有丰富的精神联系与复杂的情感矛盾,既包含理性的批判又有情感的怀恋,大多是批判与怀恋交织。其中乡土写实的一脉,到三十年展成左冀文学一派,代表作家有张天翼、茅质、吴组湘、沙汀、艾芜等。而另一批作家却表现了一种复杂心态,即将对农村落后文化的批判和乡村纯朴民情的礼赞交织在一起,代表作家有废名、沈从文、芦焚等,到三十年展为“京派文学”。
“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兴起的一个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大约形成于二十年代中期,成员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也包括语丝社、未名社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主要代表有许杰、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鲁彦、赛先艾等。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分析赛先艾、许钦文、鲁彦、台静农等作家的作品时,就用了“乡土文学”一词。这个术语后来就被用来概括这一小说流派的创作特色:“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过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们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由此可见,鲁迅所定义的“乡土文学”,主要是从三方面来谈,其一,作者的身份特征是离开乡土、侨寓都市的知识分子;其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乡土的回忆性叙述;其三,作品的情感基调是隐现着乡愁。
其实,就乡土小说来说,首开风气之先的作家正是鲁迅本人。他“于乡土文学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抱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他的《故乡》、《孔乙己》、《风波》等都出现得很早,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所以成为20年代、以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中国农民深深的“爱”上。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情感的文字表现。
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是乡土文学的常见内容。鲁迅 乡土小说的环境大都以海边水乡为背景,在《社戏》里描绘了飞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胧下起伏的连山,两岸碧绿的豆麦夹杂着河底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二‘…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那种近乎“仙境”般的表现真是令人陶醉,引人遐想,把读者领到江南水乡月夜的境地。在《故乡》里把少年闰土融进浙东海滨绚丽的画面里,奇幻美妙,新鲜动人,写出了诗一般的环境,童心和稚气,温暖与慰藉。此外,鲁迅重视人情的描写。在《社戏》中描写了农村农民和小朋友的好客,双喜、阿发等小朋友的热情天真,六一公公的憨厚纯朴,揭示了他们的心灵之美,农村的古朴之风,农民的憨厚之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等级观念日益的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情也随之变化。闰土对“我’,竟然喊起“老爷”来,杨二嫂也变得刻薄刁滑起来。人与人之间变得隔阂,人情变得淡薄,既揭示中国农民整体生活的现状,也反映了当地的民情时尚。
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农民的作家。鲁迅与农民存在着深刻的血缘联系,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经历已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形成他强烈的“乡土情结”,使他把最真挚、最深厚、最热烈的情感倾注到农民身上,写出了农民在重重压迫下喘息的苦难。鲁迅“像一个成年,的儿子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一样,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地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的农民”,“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人感到他对农民群众,具有鲁迅那样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的感情。TR叹故乡》中老实忠厚的闰土,年复一年地在土地的死亡战线上挣扎着,被压榨得说不出话来,变成了木然毫无表情的“石像”。鲁迅了解农民,他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上的困苦,更写出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并揭示了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同时鲁迅还在积极探索着农民摆脱困境的道路。
在鲁迅开创了乡土小说范型之后,一批学步鲁迅青年作家也注目乡土,登上文坛,构成了二十年代中期颇为可观的乡土小说家群体。他们的作品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他们的作品有的描绘现代工业文明对封建宗法制农村的冲击,揭露军阀肆虐、社会动乱给农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如许杰《赌徒吉顺》、鲁彦的《黄金》;有的展示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造成的种种人生悲剧,如台静农《烛焰》;还有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的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如许杰《惨雾》、彭家煌《活鬼》。
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呈现出乡土文学作家与描写对象(故乡生活)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时间距离,作家叙述的都是记忆中的、发生在以前的故事;二是空间距离,作家已经远离故事发生的地点(故乡),大都侨居北京;三是文化距离,乡土文学作家从乡镇走到都市,进人另外一种文化环境,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浸染,于是能够用新的眼光、新的价值尺度去审视、衡量故乡的生活。这三种距离的统一决定着乡土文学作家与描写对象之间丰富的精神联系与情感联系—理性的批判、情感的怀恋、或者批判与怀恋的交织。
理性的批判是乡土小说最为突出的立意。其中最为直接表现的是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这种创作主旨,在许钦文、赛先艾、彭家煌、台静农等人的作品创作中也显现出来。
作为觉醒的现代知识者,乡土文学作家们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生活过的乡村时,种种落后、愚昧、闭塞的景象,带给他们总是焦灼、忧思、激愤,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文化批判。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对乡村文化及其鄙习陋俗的批判。乡土小说以大量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诸如“水葬”、“冥婚”、“械斗”、“典妻”、“偷汉”等等乡土风俗,表现了现代乡土中国的农民们落后愚昧的生存方式。赛先艾的《水葬》展现了贵州乡俗的残忍和蒙昧。骆毛偷窃被抓,村人决定处以“水葬”。而执刑者、被执刑者和围观者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家认为“犯罪用不着裁决,私下就可以处置”。千百年来停滞的小农生活方式陶铸了这种原始野蛮的乡俗,和这种文化下人们的麻木。其二,是对乡民生存方式和蒙昧文化心理的反思。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菊英在死去十几年后,母亲为其准备嫁妆、选定鬼婿、挑选良辰吉日、举行婚礼等等,一切如活人出嫁一样。而婚礼双方、围观者却都认为这很合情理。这种村民的集体意识是中国封建闭塞文化的真实写照,而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乡民,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是愚昧、麻木的。许钦文的《鼻涕阿二》中,体面人家的二女儿菊花小时候被叫做鼻涕阿二,受尽凌辱打骂,乡村维新时因进夜校被传为“和木匠阿龙自由恋爱”,被迫嫁给寿头阿三,丈夫死后又被卖给钱师爷为妾,得宠后却又残酷地虐待奴摔,“这是一个自由在冷淡、轻视、侮辱、虐待的空气中长大的可怜人,然而她却并不知道自己可怜,并且自己地位稍优时还将她所受的一切,施之于别人。最终她于钱师爷死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乡村妇女的一幕幕悲剧(延伸至整个乡民群体),正缘于鲁迅所指出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
此外,除对乡村中国病苦的揭示之外,乡土小说作家更将文化审视的眼光进人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以此寻找病苦的根源。王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中写了“一个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一个在城里读了多年书的大学生子平因为接受的新思想的熏陶,变得不合乡村的古老规范而最终被逼上绝路。通过子平的悲剧,我们看到了杀死他的乡村文化的这种凝固、保守的“东方不动性”品格。这种乡村文化具有极强的内聚力,任何异质文化都将在其中失色变质。而在这种不动性品格之下,国人的落后、保守、麻木也是必然的。“落后的国民性”成为乡土文学作家思考的重点,对国民性的拯救成为重要的文化启蒙主题。
总之,上述小说执著于现时的乡土生存方式,没有关于乡土过去的梦,也没有关于乡土将来的梦,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中写实的一脉。这乡土写实的一脉,到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如张天翼、茅盾、吴组湘、丁玲、沙汀、艾芜等人那里,已经从一般的乡村苦难的书写演变成了对乡土的社会阶级分析与政治批判,从而构成了左翼文学一派。
但对于乡土小说的多数作家来说,对古老乡村文化的批判和对喧嚣繁华都市的拒斥是同时存在的。他们在小说中同样表现了强烈的乡情乡愁。王鲁彦在《童年的悲哀》中说到:“啊,我愿意回到我可爱的童年时代,回到我那梦幻的浮云的时代!神啊,给我伟大的力,不能让我回到那时代去,至少也让我的回忆拍着翅膀飞到那最凄凉的一隅去,暂时让悲哀的梦来充实我吧!我愿意这样,因为即使童年的悲哀也比青年的欢乐来的梦幻,来的甜蜜啊!”许钦文也痛悼失掉了“父亲的花园”。
作为与乡土中国的“离”而“不弃”的现代知识者,他们在与传统决裂时,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依依乡情与锐利理性时时在冲突碰撞,从而表现出一种文化选择上的仿徨。在诸多的乡土小说中,对农村落后文化的批判和对乡村纯朴民情的礼赞又总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二三十年代另一批作家,如废名、沈从文、芦焚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废名在《竹林的故事》中透露出一种“隐逸之气”,到了《桥》等作品中,其笔下的乡土,回荡的已经是一曲纯粹的田园牧歌了。在《河上柳》中对“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是远古乡村生活的的一往情深的描摹。“竹林”的恬静,“河上柳”的古朴,“桃园”的静谧,,·…修竹绿水,小桥古塔,迷人的自然风光,“三姑娘”的清纯,“李妈”的慈爱,“聋子长工”的勤敏……这些都描写了朴实木呐、宽厚仁爱的美好乡村韧性,一幅宁静和谐的乡村乐景。
沈从文更是极大地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田园视角,强化了乡土小说的牧歌情调。如《神巫之爱》、《龙朱》等展示的前现代文明的乡村图景,洋溢着充满野性生命的自然之美。《边城》中,就连吊脚楼上的妓女性情“也。永远那么浑厚”。在他的几乎所有的描写乡村的作品中,未被文明污染了的村庄、古朴和谐的民风、纯净自然的人性成为永恒的主题。
然而诸如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对于古朴民风的留恋和歌颂,潜在的心理是现代知识者对现实的乡土中国和都市生存环境双重的失望,以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飘浮感,从而造成了乡土和都市之间,乡土作家们两难的文化选择。
废名在对传统的乡村文化的批判和选择中,选择了乡情,最终试图通过宗教式的自我修复,寻找精神的寄寓之所。通过刻意表现远离尘嚣的静谧谐和的乡村风光,和与之相协调的古朴淳厚的人际关系,建立起与被现代商业文明污染了的半殖民地都市文化的对立物,表现出强烈的“逃逸”气息。
沈从文则是出于沉重的乡土悲悯感和忧患,进行了所谓的“经典重造”,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依托,建立一个“供奉着人性”的“希腊神庙”。对于城市中的污浊和畸形,他都将之作为梦中湘西的对立存在,进行辛辣的揭露和讽刺,如《八骏图》、《城市一妇人》等等。他也对乡土现代变异显示出了深深的忧患。会明(《会明》)、老兵汉灯》)身上那副古道热肠,却与现代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被看作是难以理喻的“呆子”。他们身上的那点“乡下人”的乡村古风正日渐消失。在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冲击下,《丈夫》中的乡下妇人身上出现的变化,也预告着古老乡村精神的崩溃和解体。但沈从文坚信人类纯真的情感和完整的人格只有到古朴的田园中去寻找。
第7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抛锚式教学(anchored instruction)模式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所谓抛锚式教学,是要求教学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学生间的互动、交流,凭借学生的主动学习、生成学习,亲身体验从识别目标、提出目标到达到目标的全过程。这类真实事例或问题就作为“锚”,而建立和确定这些事件或问题就可形象地比喻为“抛锚”。一旦这类事件或问题被确定了,整个学习内容和学习进程也就像轮船被锚固定一样而被确定了。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品数量也渐为古今中外名家之首。但由于鲁迅的作品既富于思想深度,又比较重视行文的技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们普遍认为鲁迅的文章往往比较难教,学生则觉得较难理解。在教学中,我发现抛锚式教学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其主要的方法,就是从组织“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入手来展开教学,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并在此过程中寻求对作品的理解。
抛锚式教学的过程结构可用以下简式表示:
创设情境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评价
一、创设情境
所谓创设情境,就是使学生的学习能在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或相类似的情境中发生。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想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即达到对该知识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联系的深刻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让学习者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通过获取直接经验来学习,而不是仅仅聆听教师关于这种经验的介绍和讲解。抛锚式教学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创设一个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问题的情景,也就是设计一个宏观情境下的“锚”。
二、确定问题
在上述情境下,选择出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性事件或问题作为学习的中心内容,让学生面临一个需要立即去解决的现实问题。选出的事件或问题就是“锚”,这一环节的作用就是“抛锚”。
例如《记念刘和珍君》一课,根据“抛锚”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先让学生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刘和珍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纪念她?请在文中找出刘和珍不平凡的事迹来。
2.这篇文章浓缩了作者的真切的感情。你能了解这种情感是怎样的吗? 请在文中找出作者所寄予的深厚感情。
这两个问题相当于为学生设计相应的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的问题——一个“真实宏观情境”的“锚”。而这些问题都是学生比较容易感兴趣的,并且也能从课文中寻找答案。有了这些设计,学生理解课文就容易多了。事件清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基调就一目了然,而文章的教学难点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三、自主学习
在抛锚式教学中,不是由教师直接告诉学生应当如何去解决面临的问题,而是由教师向学生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鼓励学生围绕“锚”自己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收集信息、确定完成任务的子目标、利用并评价有关信息与材料、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等。教师则应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提供一定的“脚手架”,以使学生的理解进一步深入。
例如,《祝福》运用了鲁迅小说最常用的“归乡”模式,这种情节结构模式的特点是: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构成一个复调。作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在这里,恰当的视角是作者展开故事与读者理解作品的关键。在《祝福》中,作者为什么选择“我”这一个远离故乡的知识分子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冲茶的短工或是柳妈呢?在学习中,可让学生围绕着这个“锚”去收集材料,从而获得对作品的理解。
四、协作学习
讨论、交流,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补充、修正、加深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理解,这是协作学习的要旨。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应该鼓励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特别是后者)的讨论或对话,从多个角度寻求解决“锚”中问题的可能办法,提高学生的合作、交流的能力。例如,《故乡》一文中写了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理想中的。小说突出描绘的是现实的故乡。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 它与回忆中的和理想中的故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它是由哪些不同的人及其精神关系构成的呢? 怎样概括自己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呢? “故乡”与鲁迅心目中的“祖国”有何关系呢?这些问题,就需要通过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才能达到对作品的充分的理解。
五、效果评价
抛锚式教学要求学生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学习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即由该过程可以直接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对这种教学效果的评价往往不需要进行独立于教学过程的专门检测,只需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观察并记录学生的表现即可。抛锚式教学不仅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解决“锚”中的问题,而且要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自主地完成学习目标,自主地解决复杂背景中的真实问题,以及与他人合作、交流、相互评价和自我反思的能力。
与大多数思想内容丰富的作品一样,鲁迅作品的阅读与理解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鲁迅作品教学的根本任务是要引导学生自己去阅读鲁迅的原作,与鲁迅直接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教师的讲解只是一座桥梁,目的是使学生认真地读鲁迅作品,懂得多方面、多角度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从而得到感悟与体会,形成自己的看法与评价。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抛锚式教学,正是为学生提供了这种学习的途径和空间。
【参考文献】
第8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关键词: 乡土小说 写作视角 鲁迅 沈从文
乡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母题。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最早始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以法国卢梭、英国哈代等为代表。这些来自乡土的作家感受到乡土变迁的危机,开始用他们的笔描写美好自然的乡土生活,寻找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形成世界性的乡土文学创作。时隔百余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由于西方经济的涌入,城乡地域差别的扩大。另一方面,不少乡村知识青年在都市中受挫,理想一点点被摧毁,心理上产生了无法摆脱的焦虑感,“为了消解或缓和这种焦虑感,由乡村迁移到都市的现代知识分子大都自豪地树起乡下人的盾牌来抵御都市社会的冷漠。他们蜗居于都市却对都市充满着厌倦乃至敌意,他们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却不由自主地用记忆中的故乡作精神的慰安”。[1]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乡土题材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那些来自乡村、寓居于大都市的游子,在目击了现代文明与宗法制农村的差异后,带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2]乡土小说迅速崛起。
一
在乡土小说创作中,鲁迅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带动了“乡土文学”流派的创作,从而直接影响到整个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发展。思乡念土之情作为人类最久远、最刻骨铭心的感情,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现象中的一种本能和感情。作家们的思乡念土之情是对“精神家园”的呼唤,是他们灵魂的最终归宿。故土是他们情感的依托,心理的支点,更是他们躲避风浪的港湾。对创作者而言,每一次对故土的回忆都会使其得到一种心灵的慰籍和巨大的精神补偿。因此,乡土成为古往今来文化中的一个主题原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乡土文学有着它存在的空间和意义。
鲁迅是乡土小说创作的领军人和推动者。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主将,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他从一开始便高扬“人的文学”的大旗,努力寻求人的合理、健康的生存形式。在他看来,对于下层受压迫民众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改变他们长期以来被封建传统观念所禁锢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他期望用文学来解构传统文化,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唤醒民众,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
《故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乡土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在小说中对人物的追忆和事件的叙述远远多于对乡间景物的描写。“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个鲜活的世界,有五彩的鸟雀,五色的贝壳,碧绿的西瓜……最重要的是有个“十一二岁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极富活力的少年:闰土。然而境转时迁,二十年后的闰土已为人父,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眼睛肿得通红,头戴一顶破毡帽,身上穿件极薄的棉衣,粗笨而开裂的手上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不仅如此,昔日的亲近已然不在,而是木讷而拘谨地喊“我”作“老爷”。在闰土叫出“老爷”的刹那,“我”对故乡唯一残存的美好理想也彻底破灭了。小说通过对二十年前后闰土形象的对比描写,揭示了凋零、凋敝,残缺的乡土上未开化民众的麻木、愚昧和守旧。《风波》以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为背景,围绕鲁镇船夫七斤因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怕被坐了龙庭的皇帝杀头而引起的一场虚惊,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心的戕害,展示了处于封建统治和控制之下农民的愚昧落后和冷漠保守。《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是旧中国千百万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她最大的不幸不是其曲折悲惨的人生经历,主要在于其精神上如何受到压制遭受毒害,是灵魂的愚昧与不幸。
鲁迅的乡土小说始终关注着充满蛮风陋俗的乡土,且表现的多是故乡的阴郁与破败、传统文化造成乡民的愚钝与麻木,他总是以启蒙的目光解剖着生活在古老乡土上愚昧不幸的民众的精神病苦,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这正映衬了他所说的:“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
鲁迅的乡土小说以乡土为切入点,以启蒙为视角,以批判封建和蒙昧为最终指向,意在通过描写乡土民众的愚昧落后,用现代民主思想来开化民众,达到疗救民众的目的。他从文学启蒙与“思想革命”的视野出发,极其深刻地从文化意义上挖掘乡土中国的痼疾,对国民性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这种启蒙式的批判归根结底受“五四”启蒙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鲁迅的影响下,一些乡土小说创作者从闭塞的乡镇走入都市,汲取着城市化文化的营养,审视批判着宗法制农村的呆板和因循守旧。他们师承鲁迅的写作视角,作品中回荡着批判的感情旋律,批判着农民的愚昧落后,震惊于农民对革命的隔膜,愤慨于农民对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盲目认同,力求能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二
三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与前期乡土小说不同的是,创作者的写作视角发生了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在思想上的启蒙遭到了挫败,一部分知识分子倍感悲观,于是这些人便把书写和描绘遁世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和途径,以此排解和消除现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困扰。他们开始把批判的目光转移到对地域风俗、人文环境的关注和描写上,意在回归自然,赞颂人性美,寻觅理想和精神的家园,代表作家是沈从文。与鲁迅浓烈地渲染乡间的苦难来批判乡土、批判蒙昧不同,沈从文对乡土进行的是田园式的抒写,他善于描绘民风民俗,歌颂自然美、人性美,把自然作为精神归宿,寻求心灵的放松地。
翻开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着湘西浓郁的边地风情和朴素自然的民间生活。他以“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审视着湘西,排拒城市“文明”侵扰,营造着自己的“理想国”,构筑着自己的“希腊小庙”。[4]沈从文一生都以“乡下人”自居,他在《自我评述》中曾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的感情同他们不可分。”他为读者展现的湘西世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乡下人”的世界。与鲁迅笔下反映农村农民落后和愚昧的乡土小说不同,沈从文显现出与其他启蒙文学不同的异质特色。在他的笔下,村民是那么朴实、热情、充满生命活力,乡土无不散发着自然美和人性美的光辉。
在《三三》、《柏子》、《萧萧》中,沈从文抒写着湘西土地上的山水草木、风俗民情、行船水手、动人山歌等等,对这些自然生命状态的描绘真切的表达了他回归自然的思想。《边城》达到了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完美统一。作品中有对“茶峒”山城的风景描写:“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5]。也有对边城风情的描述:冬天城里各家门前晾衣服,檐下挂红薯,口袋装栗子,男人劈柴,妇人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淳朴和谐的乡土上孕育着健康充满生机的生命,翠翠便是典型的代表。她有黑黑的皮肤,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和如山头黄麂般乖巧的性格。她的恬静、温柔、纯净、善良、淳朴与对爱情的执着,集中地表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具有原始形态的自然人性美。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在他亲身感受着中国都市半殖民地过程中道德的堕落和文明的丧失后,转而向幼时的故乡寻求补救的精神力量。在对地域景观、民族风情的描写背后,还蕴含着他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注和忧患意识,因此他的田园式牧歌显得不再那样淡远和闲适,在淡淡的愁绪和感伤的背后隐匿着深深的焦虑和思考。从这个层面上看,沈从文对湘西自然与风俗人情的描写已超越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狭小视野和一般的温情感伤情调而具有了文化的标张与价值忧患的自觉。[6]
鲁迅和沈从文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透视乡土中国,解读乡土文化,构筑乡土母题文学。无论是对乡间荒凉凋蔽、乡村民众麻木冷漠的批判式叙写,还是对乡土淳朴地域风俗的田园式歌颂,都因糅进了对人类发展的文明历史、对民族文化的演进进程的深刻思考与理解,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7]对这两种写作视角的审视与解读,有助于我们透视乡土小说创作的动力和方向,从整体上把握乡土文学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谭桂林.鲁迅乡土创作的主题学阐释[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A].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林乐齐选编.沈从文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第9篇:鲁迅的作品故乡范文
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鲁迅也有微笑时》。
“鲁迅的骨头很‘硬’;鲁迅的头发很‘酷’;鲁迅的身材很‘修长’”——每每读完有关鲁迅的文字,眼前便会出现这样一个图像:两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透那沉沉的黑夜;一头不屈的硬发,根根显示着与恶势力的不调和;一张消瘦的脸庞,露出刚毅与坚强。这形象与那不朽的文字一起,随岁月的增长由模糊到清晰,终于画出我的,相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在众多作家中,鲁迅是突出的一个。他敢骂,骂苟延残喘、阴险狡诈的“落水狗”,骂奴颜婢膝的伪君子;他敢论,论国民众生的劣根本性;他敢抨击,抨击狂人眼中“吃人”的世界,抨击把孔乙己推上绝路的封建礼教;他敢呐喊,为艰辛而麻木地生活着的闰土,为受封建四大权力压迫的祥林嫂——无疑,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战士。
可能,人们看惯了《呐喊》、《野草》,看惯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但他并非只有一副面孔。在《朝花夕拾》里,关于他幼年时的快乐时光也有所记录。其实,《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无不写出了鲁迅对故乡及幼年时代的怀念。《朝花夕拾》这部集子,最初拟定题目为《旧事重提》,无论是《朝花夕拾》还是《旧事重提》都写出了作者在经历家业衰败、多年沉浮后,对幼年时美好回忆。在这些作品里,虽然或多或少也离不开抨击旧社会恶势力,但读起来感觉已不是那么慷慨激昂,而是一种很平静很优美的感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六一公公的罗汉豆......人们说一个人的文章可以反映他的性格、心情等等,而记忆又是最让人着迷的东西,我想,鲁迅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脸上一定荡漾着微笑,而不会是一张“酷到家的冷脸”了吧。
原来鲁迅也有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就比如当他想起了故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