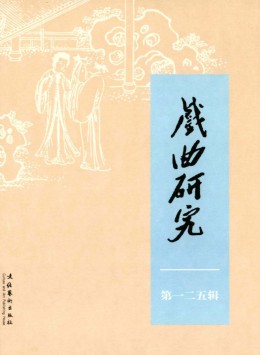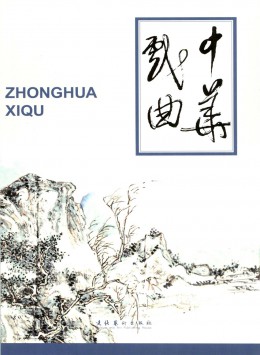论戏曲的性别话语

两性话语的纯净化
对于新中国的戏曲定位,田汉将之概括为“人民新戏曲”。人民,这一政治意识鲜明的词汇成为戏曲的风向标,意味着以往在民间恣意沉浮的戏曲将要接受来自意识形态的种种审查与规驯,性别话语便是当中的一例。传统戏曲因见弃于文人和朝堂,在民间沉浮中难免藏污纳诟,戏曲文本与舞台表演中调笑、淫乐的成分并非个例,甚至流传极广的名剧也不乏“粉戏”。“戏改”既以建构人民新戏曲为宗旨,对旧戏的情色表现必然加以清洗,将其改造为契合于社会主义新文艺的符号,其策略则是去芜存菁、纯净化的两性话语。“戏改”的剧目审定按照有益、无害、有害三种标准进行,按其性质则归为三类:准演及暂准演、修改后可演、禁演。实际上真正准演的剧目极少,即使是流传极广、当时几乎是样板性剧目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经过了大范围的修改,而修改的原则,即“真实的描绘,合理的净化,与适当的创造,使含糊的明确起来,歪曲的拨正过来,不完整的完整起来”①。其中合理的净化便主要指向了性别话语。堪称伶界魁首的梅兰芳在此方面亦做出了表率。《贵妃醉酒》是梅派看家戏之一,梅兰芳对该戏已有几十年的演出实践,期间不断修缮,在“戏改”中他更是着力加工,特别是杨玉环醉酒后涉嫌思春猥亵的言词与身段、表情都被删除。当杨玉环吟唱“这才是酒入愁肠人易醉,平白诓架为何情!啊,为何情!”时,一个荡妇淫娃借酒发疯的场面(原唱词为:“这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啊,人自迷!”)被改造为深锁皇宫、精神压抑的女性的内心独白,杨玉环也不再是以色事君王的尤物,而是回归其女性真属性。当然,这样的改动也顺便传达了对封建帝王的控诉。
在男权主导的世界中,女性一直是被窥视的,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对象,《游龙戏凤》等剧更是在剧名中明目张胆地将女性置于被调笑、被“戏弄”的地位,“戏改”所谓合理的纯净化,恰是扭转这种倾斜的两性关系,将女性置于平等的、人的地位。《蓝桥会》是黄梅戏传统小戏之一,描写嫁了小丈夫的蓝玉莲在井畔汲水,偶遇书生魏魁元讨水喝,二人攀谈、互表身世而终至定情,约于八月十五蓝桥下相会,对天盟誓后分别。原本中魏魁元“家中妻子有一个”,却又见到蓝玉莲的美貌便“跪讨姻缘”,还用扇子挑开蓝玉莲的裤脚偷看其三寸金莲,一副浪荡子弟的嘴脸;而蓝玉莲本已有丈夫,却又和陌生男子在公众场合打情骂俏,接受魏魁元的挑逗,显然是一个自轻自贱、甘愿被男子欲望所俘获的轻浮女子。严凤英的演出本则将蓝玉莲的唱词改为“玉莲今年二十多,惟有那小丈夫未满十三”,魏魁元的唱词则改成“盼着早娶妻一个,要和大姐一样贤”,二人一个未娶,一个是饱受婚姻不幸的等郎媳,由此调情升华为真正的爱情,反抗封建道德、追求个人幸福的新戏曲格调得以显现。在传统戏曲倾斜的两性话语中,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则是被动承受者,因而想要纯净两性话语,男性形象的净化至关重要。京剧《坐楼杀惜》(又名《乌龙院》)是一出唱念和表演得到完美结合的生旦“对子戏”,但也夹杂着诸多庸俗的台词,诚如周信芳所言:“从前被人叫好的地方,有不少正是此刻需要商榷之处,比如原来的宋江对阎婆惜所表示的那种愚蠢的样子,这不仅将宋江形容成一个嫖客,而且是上海话所谓的瘟生了。”①由嫖客到及时雨、由争风吃醋杀人到维护大义而不得已的自卫,宋江形象中猥亵成分的有效去除不仅净化了性别话语,更为整部戏的人物塑造、主题意义的传达奠定了基础。越剧《西厢记》中的张生、《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等观众所熟知的人物也都经过了类似的提纯,其舞台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为他们进入人民新文艺扫除了障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戏改”纯净化两性话语的努力并不仅体现于剧目修改,舞台呈现方式亦是其关注的重点,“五五指示”便明确强调:除“革除有重要毒害的思想内容”外,“并应在表演方法上”,删除各种野蛮的、猥亵的成分。被打上野蛮、猥亵嫌疑的表演方法,首当其冲的便是跷功。作为旦角的基本功,跷功在晚清至民国年间极为兴盛,乾隆年间秦腔花旦魏长生便以此大大出名者,此后魏长生的弟子、门徒及一批效仿者竞相研习,跷功逐渐流传开来。梅兰芳、荀慧生等诸多名角都练过跷功,练踩跷对于训练旦角演员的腰腿功夫大有益处,梅兰芳在花甲之年还能演出《醉酒》、《穆柯寨》、《虹霓关》一类做功繁复的戏,不能不归于当年跷功的严格训练。但跷功自民国年间便不断遭遇到非议,禁止跷功的声音不绝于耳。对于跷功,梅兰芳曾表态说:“对于跷功存废,曾经引起各种不同的看法、激烈的辩论。这一个问题,像这样多方面的辩论、研究,将来是可得到一个适当结论的。”②联想到梅兰芳的移步不换形主张、透视他对戏曲艺术表现形式的维护,对于跷功梅兰芳未必会持完全废除观点。然而,1949年后,跷功终于被明令禁止、绝迹于舞台,擅演跷功的艺人小翠花还饱受牵连。审视跷的舞台功能,大致有技术与象征两个层面,技术层面如使角色的身材更显修长、使演员的动作更加自如、在武打中的保护作用等,但跷的象征功能才是真正将其置于风口浪尖的关键所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缠足的象征,跷“显示女性是男性的性目标”,在一些传统剧目中,跷被用来表现男女之间的调情,是“粉戏”惯用的道具,如小翠花的《战宛城》、《翠屏山》中与和尚私通的潘功云、《挑帘裁衣》中与西门庆私通的潘金莲、《三雅园》中与人私通谋杀亲夫的黑老虎之妻等,跷甚至被视为“祸起纤足”的导淫之具”。③因涉淫而被禁,跷功的遭遇印证了“戏改”对性别话语纯净化的迫切愿望,至于其艺术功能只能在“人民新戏曲”这一洪流中被湮没了。由于女性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戏改”对两性话语的纯净化为女性在戏曲中的常态存在提供了更多可能,由此引发女性话语的张扬。
女性话语的张扬与蜕变
在传统戏曲中,女性或者如杨玉环、潘金莲等人,以色事他人,沦为男性淫乐的对象;或者如窦娥、祝英台等人,成为各种暴力的牺牲品;自然,也不乏王宝钏等女性,似乎守得云开日出、盼来大团圆结局,却不过是为封建伦理添加一个注脚而已。从新戏曲的视角审视这些女性,她们无疑都是被遮蔽的异化性存在,亟等“人民”话语的启蒙与拯救。对弱势女性的救赎,是十七年非常普通的模式,喜儿、二妹子(电影《柳堡的故事》)、吴琼花(电影《红色娘子军》)已经成为经典的“被拯救者”形象。然而“戏改”面对的拯救对象与小说、电影不同,那些生活于封建历史中的女性们不可能沐浴到革命的春风,故而她们也无法成为戏曲舞台上的“红色”形象。但历经两性话语的纯净化,摆脱了“粉戏”泥淖的女性们却可以反抗、斗争、个人意志等为屏障获得更为广泛的生存空间,并进一步为戏曲“新”女性的产生铺设道路。对于“戏改”,田汉率先垂范,而他的戏曲文本多数带有鲜明的女性话语特色,如京剧《白蛇传》,便开篇明义要渲染一种“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不可征服的意志”。④由田汉改编的另一剧作《情探》亦可清楚地显示这一诉求。《情探》原名《王魁负桂英》(也叫《焚香记》),是京剧、川剧等诸多剧种的保留剧目。1950年田汉曾经著有京剧本《情探》,或许顾忌于当时的政治氛围,他放弃了敫桂英鬼魂活捉王魁的结局,而是让义士刘耿光救下自尽的敫桂英,并将王魁绳之以国法。这一版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之后,田汉、安娥夫妇合力将其改编为越剧版,3最初仍然没有鬼魂形象,敫桂英却死于王魁的剑下。直到1956年,田汉重新执笔该戏,恢复了敫桂英鬼魂活捉王魁的结局,并浓墨重彩地设置了“行路”这折戏,将敫桂英的善良和痴情渲染到极至后才愤然活捉王魁。对比这三种版本,义士相助、绳之以国法传达的是强大的男权话语和国家意志,女性只是哀怨无助的被拯救者;被王魁刺死则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女性话语更加无从展现。而1956年的越剧版中虽然几经渲染敫桂英对王魁的幻想、委曲求全,但最终以激烈的爆发收场,前面抑之越甚,后面的爆发越强烈,最终完成了女性自我的张扬。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黄梅戏《天仙配》中的七仙女。
黄梅戏原本只是流传于安徽安庆一带的地方小戏,建国后却凭借一部《天仙配》誉满全国,甚至传遍了东南亚。《天仙配》来源于著名的青阳腔《槐荫记》,主人公董永是《二十四孝》中的一位孝子,其孝行感天动地,玉帝命七女下凡与他相守百日作为褒奖,所以该戏又名《百日缘》,其中“路遇”、“织绢”、“分别”等精彩片段都早已存在,但仅仅是这些还不足以成为经典。1952年,在安徽省和安庆市两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调遣下,编剧、音乐、演员等开始了全面的改编工作,改编中情节有三处重大的改动:将七女奉玉帝之命下凡匹配百日姻缘改为厌倦天宫的禁锢生活,羡慕人间欢乐多,且同情爱怜董永,私自下凡;将董永由书生改为农民,创造了符合“人民”要求的劳动者形象;将善人傅员外改为为富不仁的地主。由此,七仙女背叛了她所属的统治者阶层,与董永一道成为被压迫的“人民”的代言人,二者同玉帝、地主构成了誓不两立的敌对阵营。七仙女由被动的、工具性存在,转变成自主的行为主体,这一形象的变异,同样折射出“戏改”氛围中女性话语的彰显。从某种程度上说七仙女、白素贞、敫桂英等女性是幸运的,其形象的产生出自艺术家的主动选择,是他们基于政治与艺术双重标准的创造,这种创造既满足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需求,又兼顾了艺术规律,其社会效应也算尽如人意。当时曾一度出现过“翻开报纸不用看,梁祝姻缘白蛇传”的状况,尽管是对剧目贫乏现象的讥讽,却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祝英台、白娘子故事的风行,这些形象的广泛传播,恰是其女性话语成功的一个佐证。但随着政治话语越来越强烈的介入,戏曲创作中的禁锢日益严酷,戏曲中女性话语的张扬便不再是艺术家的主动选择,而更多地体现为政治上的“避难”,包含着太多的无奈。1959年3月,中国京剧院召开院务会议,商议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目,梅兰芳的献礼剧目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此之前,剧院已由文学组组长范钧宏和吕瑞明写成《龙女牧羊》,准备提供给梅兰芳演出。但梅兰芳则提出因自己年龄、体态等原因,他选中的是豫剧本《穆桂英挂帅》,希望将此戏移植为京剧。梅兰芳决定移植该剧目的原因还包括:“因这个人物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自己产生了共鸣,况自己早年常演穆桂英青年时代的戏,对这个人物熟悉、有感情”,他还一再表示说“:挂帅、出征能发挥京剧特点……”①显然,梅兰芳在提出自己意思之前已经深思熟虑过该戏,表面看来他的理由都是基于艺术效果的考虑,但纵览这一时期的其他戏剧剧目,便可窥知其中端倪。
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戏曲舞台扎堆出现了杨家将题材,如1953年的豫剧《穆桂英挂帅》、1959年的扬剧《百岁挂帅》(1960年范钧宏、吕瑞明将它改编为京剧《杨门女将》)和京剧《佘赛花》以及1961年的《雏凤凌空》等。以穆桂英、佘太君、杨排风等巾帼女性传达爱国、民族大义等政治内涵,以女性话语作为规避政治的暗礁,不能不说是艺术家的良苦用心。纵观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修改老戏使之适应时代并尽可能地创排新戏是当时“戏改”工作的主要环节,而适应新时代、创排新戏,这对于高度程式化的京剧(包括程式化相对明显的其他剧种)来说绝非易事,当戏曲固有的程式同新时生冲突时,必须舍弃戏曲的本性而确保思想内容的正确性、进步性,特别是当梅兰芳的“移步不换形”主张遭到批评后,戏曲界人士更加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也越发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女性话语在此时便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庇护所。早在50年代初《婚姻法》颁布实施时,便陆续出现了沪剧《罗汉钱》、评剧《小女婿》和《刘巧儿》等新剧目,其中《罗汉钱》和《小女婿》曾在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中获得剧本奖。这些剧目,包括上述样板式的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天仙配》等都是借助婚姻这一平台来彰显女性话语,并最终实现向“人民戏曲”的靠拢。只是到了50年代末期,时代氛围已经不再青睐于悲凄、哀切,而是雄壮、阳刚,女性话语的展示重心便由她们所遭受的压迫转向其“铿锵玫瑰”特质,杨门女将恰是一个极好的载体。再联想到那一时期影响较大的几部女性题材剧目,如《花木兰》、《秦香莲》(不是哭哭啼啼的弃妇,而是大义凛然与皇家对抗)、《谢瑶环》等,可知其时戏曲中的女性都负担着沉甸甸政治使命、传达着所谓的“刚烈”之气,而其自身的本性却被日渐放逐。始于彰显,终于放逐,这是戏曲的女性话语所遭遇的悖论,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男性话语的强势凸显。
男性话语的凸显
所谓男性话语是指那种体现男性自我中心的“霸权”话语,它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强调一种唯男性独尊的强权意识,置女性于”他者“的地位,对其进行客体化的审视,维护自身的绝对权力。“戏改”以“人民新戏曲”为标尺改革旧戏,但“人民”中的男女却并不拥有同等的展现机会,女性生存空间被男性话语强行侵占、挤压,成为畸形的存在,被誉为一出戏求活了一个剧种的《十五贯》便是典型的一例。昆曲《十五贯》,原由浙江国风昆苏剧团改编自清代朱素臣的《双熊梦》,1953年后便经常上演;1955年冬,由黄源、郑伯永、周传瑛、陈静、王传淞、朱国梁等人组成了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对该剧再次进行改编,这一改编本1956年进京演出后大为轰动,影响迅速遍及全国。1956年的演出本在情节上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通常所谓的由双线结构变成了单线,原本熊友兰、熊友蕙兄弟与苏戌娟、侯三姑四个人都因十五贯铜钱而构成连环冤狱,1956年本删去熊友蕙和侯三姑,只保留熊友兰和苏戌娟这一桩冤案;同时,1956年本恢复了朱素臣原著中过于执审案的场次,将昆苏剧团最初版本中以暗场处理的过于执审案过程重新转为明场。此外,最后的结局也有所不同,最初版本中过于执心怀愧疚,力图促成两对青年男女的姻缘却遭到拒绝,最后通过况钟的计谋,得以实现大团圆。情节变动后,《十五贯》的风格及其关注焦点都发生了变化:最初版不脱传统昆曲的传奇本色,两对男女、两个冤案,历经劫难后却能以婚姻的方式获得抚慰,人性、人情内涵得以展现;1956年的定型版则完全将重心置于况钟的审案、翻案,全力打造这一青天形象,熊友兰、苏戌娟只是帮助这一形象诞生的工具,而在这一过程中,苏戌娟尤其被扭曲、被异化。
苏戌娟在戏中以孤女形象出现,缺少基本的安全保障:母亲亡故,继父尤葫芦贫困而嗜酒,尤葫芦醉酒后戏言要卖她为奴,虽然戏言却也表明尤葫芦拥有这种权利,而苏戌娟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尤葫芦对于她来说其实是一种男性话语的压迫。深夜逃走后,苏戌娟连续遭到熊友兰和乡邻的质疑:单身女子行色匆匆,熊友兰怀疑她不是良家妇女,追踪而至的乡邻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她勾结奸夫、谋害父亲。至公堂之上,过于执则认为“她艳若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非常明确地将其置于“祸水”的地位。所有种种,都是立足于男性的权威立场对苏戌娟进行的无妄判断。最后真相大白,况钟将二人当场释放,并赠与苏戌娟10两银子助她去投亲,似乎显现出些许的人性关怀,其实也只是况钟“民为贵、君为轻”理论的实践,其施舍行为只是为其清官形象再添加上仁慈、爱护百姓这样一个光明的尾巴,同初版本中缔结良缘的意义完全不同:缔结姻缘是对遭受冤屈者的补偿,体现了错误办案的过于执的自省;而现在通行的版本中苏戌娟终究未能摆脱“祸水”这一嫌疑。可以说自始至终,苏戌娟都被笼罩于强势的男性话语中,关于她的一切都经男性视角折射过,是变形的。但剧作却为男性话语的粗暴设置了看似合理的解释,即苏戌娟是有过失的:连夜离家却没有关门,给凶手入室行凶提供了契机;与熊友兰一路同行,将原本好意帮她的正人君子拖入杀人、盗财、通奸的滔天大罪中……或者也可以说,况钟这一清官形象、《十五贯》非凡的主题意蕴,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苏戌娟的“祸水化”为代价产生的。苏戌娟的境遇在“戏改”氛围中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思维,即突出正面男性形象所代表的政治主题意蕴,其他形象都被不同程度地加以工具化,尤其是女性。越剧《胭脂》的改编思路与《十五贯》几乎同出一辙。
早在1955年下半年肃反工作结束后,就亲自选定了《聊斋志异》中的《胭脂》等几篇文章让大家学习;1960年,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再次提出要大家读读《胭脂》等文章。此后,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的组织下,开始了越剧《胭脂》的改编工作。在《聊斋志异》中,少女胭脂偶遇书生鄂秋隼,便心生情愫,邻家寡妇王氏戏言愿为之牵线。王氏将此事告知自己的情人宿介,宿介便冒名去会胭脂,得到胭脂的一只绣鞋作为信物。宿介在路上丢失绣鞋,被恶人毛大捡到。毛大垂涎胭脂,深夜持鞋冒名而来,却误入胭脂父亲房间,慌乱中将其杀死。县令重刑逼供,鄂秋隼屈打成招,济南府吴南岱复审时,发现有冤,释放了鄂秋隼,却又错误地将宿介定为凶手;最后学使施愚山出面,此案才最终水落石出。而施愚山怜惜胭脂与鄂秋隼,为二人作主,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小说的重点是冤案平反的曲折过程,其主旨在于告诫为官者要体恤百姓、不可妄动刑罚,赞誉公正廉明、洞察秋毫又怜才爱民的清官。乾隆年间剧作家沈起凤曾创作过传奇《文星榜》,部分情节与《胭脂》十分类似,其重心则是讲述才子历经坎坷最终得到圆满结局的故事。越剧《胭脂》恢复了小说的清官主题,对胭脂却并不像原著那般眷顾,甚至强化了她的祸水性。
《胭脂》同样是由女性过失引发的冤案故事,较之苏戌娟,其过失更为严重:良家女子思春,与男子私下约会,害得父亲送命;不明就里,置鄂秋隼于凶手地位。当知县张宏见到死者卞三手中的绣鞋时,断定“其中定有奸情”,一旦得知绣鞋属于胭脂,便已将她视为“淫妇”。当胭脂含羞不肯说出绣鞋赠给何人时,张宏呵斥她“见了本官,竟敢闭口不言”,而胭脂一旦开口说出不合自己主观臆断的言论时,张宏更直叱她“不是好东西”……在张宏充满男性霸权的话语透视中,胭脂不折不扣是一个祸水式存在。这一判定持续至终,吴南岱、施愚山都只是关注案子的审理,并不关心胭脂本人的境遇。在原著中,鄂秋隼“为人谨讷”、“羞涩如童子”,他“上堂不能置词,惟有战栗”、不敢张口和胭脂对质,致使县令深信他便是凶手。在越剧版中,鄂秋隼显然强势了许多,他申辩自己同胭脂无冤无仇,要她不可冤枉好人。鄂秋隼的控诉无疑增加了胭脂的“罪”感。实际上,胭脂先后成为了宿介、毛大的欲望对象,成为知县张宏偏见、臆断的牺牲品,但是所有这些都被所谓的清官、法理、道义等宏大主题所淹没,胭脂只有步苏戌娟后尘,成为男性话语的祭品。
在评论《秦香莲》的改编时,张炼红说:“单就《秦香莲》本身而言,不论是从哪个结果看,直接受害的都将是作为妻子的两个女性。‘铡美’貌似伸张了正义,但这对秦香莲的‘苦命’没有真正的改善”,而“另一个受害者显然是皇姑,而对于她的委屈人们却视而不见”①。其实被损害、被视而不见的何止秦香莲与皇姑两个,苏戌娟、胭脂等等,无论卑贱的黎民,还是贵为皇室,在道义、正义、社稷、法理等面具遮掩的男性强权话语下,都一样的无助。(本文作者:张艳梅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 上一篇:中国画对戏曲形象的运用范文
- 下一篇:戏曲艺术电视传播路径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