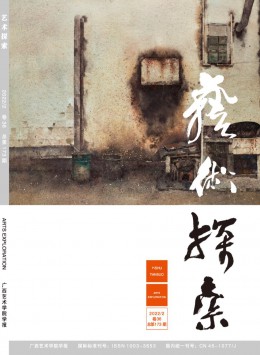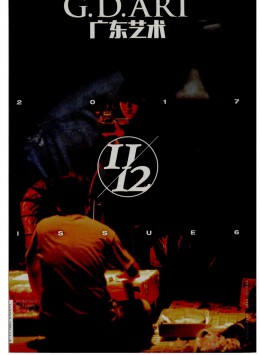艺术精神对京派小说的作用

本文作者:文学武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传统文论对于空灵和虚静有很多形象的描述,如“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贵在虚静”(刘勰),“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司空图)等。只有具备了空灵的品格,才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在艺术的天地中自由飞翔。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持很深感情的京派作家多表达了对这种美学境界的追求、向往。朱光潜认为第一流的小说家并不仅仅擅长讲故事,他们更靠故事以外诗的元素,原因就在于诗给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沈从文认为中国宋元以来绘画最高的成就并不体现在“似真”、“逼真”的层面上,而是在“设计”,因此短篇小说向过去的传统学习“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①。凌叔华称自己的一部分小说是“写意画”。沈从文、废名、师陀、萧乾、凌叔华、汪曾祺等人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把追求艺术的空灵、诗情作为自觉的选择,作品达致含蓄、温婉的境界。
首先,京派小说的空灵表现为对抒情氛围的创造。作者有时把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美学理念熔铸在作品中,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作品中的情绪氛围融合为一,泯灭了主我和客我的界限,从而构设了一幅和谐、完整的图画,这在京派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沈从文的《边城》充满了浓重的牧歌情调,作家关注的中心始终不是对现实的描摹,而是情绪和氛围。作家的自我或隐藏在“人”与“物”的背后,或消融在“人”、“物”之中,在情景交融中烘托出作家的情绪。汪曾祺的不少小说也都在叙事中增强了主观的自我情绪,像《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等被公认为空灵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
其次,京派小说的空灵还表现在对大量自然景物的描写上。描写风景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悠久传统,这些优秀作品对京派作家是很有启发的。比如京派不少作家都很推崇陶渊明,究其原因,除了他们把陶渊明的作品当作“静穆”境界的典范外,陶诗出色的景物描写和由此带来的空灵的艺术风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废名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山水等自然景物的钟情。如《桥》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故事情节几乎被完全淡化,人物典型的塑造也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与此相反,自然景物的描写却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此有人把它当作山水小品来看也不无道理。沈从文的作品同样如此,“沈从文不是一个雕塑家,他是一个画家。一个风景画的大师。他画的不是油画,是中国的彩墨画,笔致疏朗,着色明丽”②。汪曾祺曾说沈从文最为钦佩郦道元的《水经注》。显然,在郦道元笔下,山水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无生命的景物,而是溶入了作者的生命情感。沈从文的不少小说都以很大的篇幅描写湘西的山水风情,山、水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沈从文曾说过:“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③正是因为用了很多的笔墨来写水,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具有一种灵动的生命。
最后,京派小说的空灵表现在它的含蓄、蕴藉上。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在于它是对现实、现象的超越,德国哲学家谢林所说的“美是在有限中看出无限”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梁宗岱在论及象征主义时曾经非常精当地概括出它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他认为象征主义揭示了艺术的无限性:“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底惝恍迷离,融成一片;含蓄是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④其实这一点和中国的道家美学思想倒有不谋而合的地方,“道家美学,还讲求语言的空白(写下的是‘实’,未写的是‘虚’),空白(虚,无言)是具体(实,有言)不可或缺的合作者。语言全面的活动,应该像中国画中的虚实,让读者同时接受‘言’(写下的句子)所指向的‘无言’(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使负面的空间(在画中是空白,在诗中是弦外的颤动)成为更重要、更积极、我们应作美感凝注的东西”⑤。我们看到,京派小说家大都不热衷当时从西方引进的小说理论,无论是在描写人物还是环境上,常常用写意的笔法,注重留取空白,尽可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产生出无言之美。比如汪曾祺的名作《受戒》很多地方使用了这种手段,其它如废名的《菱荡》、《河上柳》、《桃园》,沈从文的《边城》,凌叔华的《花之寺》等也都如此。凌叔华在《小哥儿俩》的自序中明确地说自己的一部分小说是“写意画”,不求形似,注重神韵。这表明了他们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承继。
与空灵一样,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对京派作家的创作同样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他们矢志追寻的目标。意境是中国独有的审美范畴,它源自老庄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尽管人们对意境的定义和特征颇有争议,但它最核心部分,即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以实境表现虚境,最终达到浑然一体,表现出宇宙内在的生命这一点上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什么是意境?唐代大画家张璪论画有两句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和心源的凝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结晶体,鸢飞鱼跃,剔透玲珑,这就是‘意境’,一切艺术的中心之中心。”①宗白华先生言简意赅的概括和归纳,对于人们理解这个核心审美范畴有很好的启发。在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话语长驱直入的时代,还是有不少现代作家始终把中国传统的意境作为审美批评的重要标准。周作人说:“废名君用了他简炼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②朱光潜评论废名的《桥》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③沈从文的《边城》是作家中国艺术精神最完美的体现,这部作品刚发表,就有人评论说它“能融化唐诗意境而取得可喜的成功”④。这样的艺术追求在20世纪初中国文坛全面移植西方文学理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这也使得京派小说的艺术价值比起看重艺术价值论、忽略审美情趣的左翼小说,以及简单模仿外国文学追求花样翻新的海派小说来要厚重得多。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只有有机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意蕴丰赡的境界。对于作家而言,一般都是通过客观景物的寻求来寄托、象征作家的情感,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讲得就是这个意思。京派小说家虽然借鉴了外国文学大量描写风景的手法,但同时他们认识到纯粹的自然景物描写并不必然构成一个丰盈的艺术生命,它必须与作家的情感相融合才能达致艺术的境界。
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擅长在直观的自然景物描写中传达出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营造出静穆悠远的画境之美: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上(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拣野鸭蛋),把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大淖记事》看了这段文字,大家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也会很自然地想到秦观《鹊桥仙》中的美妙境界。而对于废名来说,其作品很大程度上致力于表现的是“禅境”。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理想的境界如宗炳所说的那样转向了“澄怀观道”,要在拈花微笑中领悟深层的禅境。“由于禅宗强调感性即超越,瞬刻可永恒,因之更着重就在这个动的普通现象中去领悟、去达到那永恒不动的静的本体,从而飞跃地进入佛我同一、物己双忘、宇宙与心灵融合一体的那异常奇妙、美丽、愉快、神秘的精神境界”⑤。废名对禅学有很深的研究,他的长篇小说《桥》与其说是在演绎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毋宁说是一部禅趣盎然的小说更准确,他写史家庄的清幽:史家庄是一个“青庄”。三面都是坝,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树则沿坝有,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这里的环境优雅宁静,远离俗世的尘嚣,大自然处处充满生机,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禅宗淡远的心境和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也使人在悠闲、超脱的心境中体味到生命的华严境界。
卡西尔说:“艺术王国是一个纯粹形式的王国”,而“这些形式不是抽象的,而是诉诸感觉的”①。如果说意境是情与景、意与象、隐与秀的交融而构成的完整统一的世界,那么意象就是构成意境的具体、细小、形象的单位。意象虽然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但这种形式实际上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为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审美意蕴,一个意象就是一部历史,它以最简洁凝练的方式表现了人类的艺术史和心灵史。“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②。虽然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主要运用在诗词等文学领域,但它对于小说这种文体依然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意象在小说中的使用同样可以化实景为虚静,创形象为象征,表达出含蓄幽深的意境。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菊花”、“白塔”、“虎耳草”、“磨坊”、“渡船”、“月光”、“烟雨”等意象,在废名的小说中则经常出现“竹林”、“桃园”、“桥”、“灯”、“青草”等意象。不少学者都曾注意到沈从文《边城》中的意象呈现的复杂性和象征色彩。废名《竹林的故事》中反复出现的“竹林”显然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竹”的隐含意义,象征了女性的青春活力、纯洁和遗世独立。由此可见,作家们选择了一种意象,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言说历史的叙述方式和审美方式,使人们透过表层去领悟其深层、博大、精微的另一个世界。
不仅如此,京派小说的语言描写也深得中国传统文学的神韵。语言是一切文学形式的基石,海德格尔说:“在词和语言中,万物才首先进入存在并是起来。”③中国传统文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东方民族特征的语言方式,比如重诗性传达、简洁自然、讲究声韵、追求含蓄,尤其是赋予语言以多重的含义和联想功能,通过有限的形式到达无限的广阔世界。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形式在外来文学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语言上的变化,但实际上并没有中断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学语言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对京派小说家而言颇具吸引力,废名文章中表达了他的神往之情:“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到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④。正因为如此,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提及废名小说的价值就在于文字之美,而这种文字恰来自于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汪曾祺也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当代价值,并把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有学者甚至认为:“就讲究语言这一点说,京派在中国现代各小说流派中,也许是努力最多的。”⑤
京派小说语言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简约、自然,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禅宗的精神是契合的。“道家重天机而推出忘我忘言,尽量不断消除演绎性、分析性、说明性的语言及程序……而语言像一指,指向具体万物无言独化的自然世界,像‘道’字一样,说出来便应忘记,得意忘言,得鱼忘筌”⑥。而禅宗作为佛教的中国化,更是摒弃了佛教繁琐的教义和推理过程,代之以形象直觉的方式来表达和传递某些不可意会的东西。随着庄禅哲学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日益扩大,它也越来越渗透到一切艺术的领域,带来了中国文学艺术形态的重大变化,其中一点就是讲究语言的自然、简洁。京派小说家一般对冗长欧化的句式都比较反感,他们尽可能追求语言的精炼含蓄,把语言的张力发挥到极致。废名的一些文字学习唐人的绝句,用最简洁的语言表现出诗的意境。因此废名的小说不仅篇幅短,人物的对话、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非常凝练的,富有暗示性、象征性,而且擅长表现婉约深层的意境,充满了对宇宙、青春、生命的感叹,这一点恰与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不谋而合。废名的《桥》虽名之曰长篇,实际上是由一个个散文片段构成,主人公小林和琴子的对话简单到了极点,却处处含着禅机,耐人寻味。沈从文的语言也向来为人们所称道,汪曾祺说沈从文的作品受到《史记》、《世说新语》、《水经注》等的影响,因而大都朴实流畅。沈从文写景如此,写人也同样如此,往往用简略的笔墨便勾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种传统的白描手法在《边城》、《三三》、《丈夫》等篇目中都有成功的运用。
与前面两位比较起来,汪曾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甚至更自觉,更有认同感,他尤其推崇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对归有光《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篇目中平淡、自然、简洁的文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汪曾祺对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①汪曾祺在自己的作品中比较完美地展现了文字符号的魅力,精炼的语言中闪烁的是诗人的智慧。
由于京派作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其在语言的选择上也更倾向接受中国古典文学雅致、诗性的一面,这一点无论是和当时的左翼文学还是海派文学比较都有很大的不同。左翼文学由于过分看重文学的政治功能,把文学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宣传工具,在语言的使用上比较随意、缺少精雕细刻,因而大都比较粗糙、直白,缺少韵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文字乃至文学的美感。海派小说过于追逐语言的新奇,抛弃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长处,颇有食洋不化的味道。而京派小说在这一点上就显示了它的特长。“文学不简单是对语言的运用,而是对语言的一种艺术认识(如同语言学对它的科学认识一样),是语言形象,是语言在艺术中的自我意识”②。京派小说家在语言的运用上非常讲究,他们完全把语言当作艺术生命的精髓来看待,因此从古典文学借鉴了丰赡而富有诗性的表达方式。像林徽因的小说《钟绿》整部作品始终飘荡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其语言的表达也充满了东方的诗性。
京派小说还注重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诗句、典故、对仗、双声、叠韵等形式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他们在作品中恰当地穿插了一些古典诗句,废名的《桥》在这方面比较突出,对名句的直接引用比比皆是。如“青青河畔草”,“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池塘生春草”。不仅如此,他的一些描写还化用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如一些描写丝丝细雨的句子让人很容易想起李璟、杜牧等人的诗词。沈从文、汪曾祺和凌叔华等人则通过较多地插入旧体语言的形式,如典故、对仗、古语等,突破了早期白话文单一、单薄的审美格局。沈从文说自己的部分文字“文白杂糅”。汪曾祺则推崇韩愈的“气盛言宜”和桐城派的散文。他们重视字句的声音、节奏,这些都丰富了现代白话文的形式。
总之,京派小说与中国艺术精神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不仅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反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列文森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他的观点在冯至的言论中得到了反映。冯至后来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拿我在20年代接触的一些青年说,往往是先接受外国的影响,然后又回到文学的传统上来。”③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诠释和重构,京派小说才能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显得卓尔不群,为中国文学弹奏了一曲不绝如缕的悠悠神韵。
- 上一篇:散文对意象的多元经营研讨范文
- 下一篇:京派作家的启蒙现代性解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