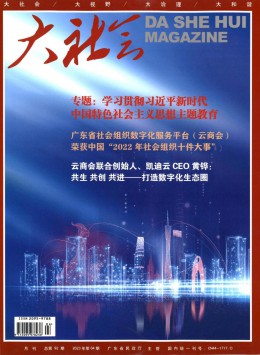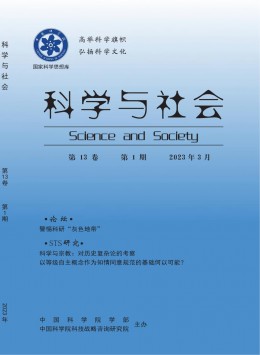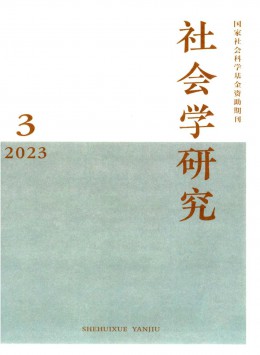社会分层卫生公平性研究

社会学大师涂尔干更倾向以职业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分层,强调由于社会分工不同而引起的社会差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专著《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以职业地位为标准的划分模式,其主要观点是阶级虽然可以根据经济资源和利益来定义,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决定这些的首要因素是其职业地位[6]。此外,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家很多,新韦伯主义者戈德索普(Gold-thorpe)与埃里克森(Erikson)合作,提出了包含36种职业分类的戈德索普量表(EGP)。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划分也主要以职业分层为标准[7]。另一学者李路路则以权力和工作自主性为核心,将职业区分为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体力劳动者阶层、自雇佣者阶层和未就业或无业人士6类[8]。布迪厄(Bourdieu)和迪玛吉欧(DiMaggio)则对文化资源的分层进行过专门研究和讨论[9]。在社会分层中最早重视社会关系资源的是沃纳(Warner)等人,他们的著作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对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等,同样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指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然而,从实践层面上,中国自古讲人情关系,这一研究也最为发达,代表观点有林南等人[6]。以沃纳和帕森斯(Parsons)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沃纳学派主张以社会声望资源来区分社会分层,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的声望地位往往和经济地位不一致,而社会声望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如特莱曼(Teriman)整合了60个国家85套职业声望数据,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声望量表”,具有国际代表性[10]。但有研究显示,我国的职业声望地位和国际上较为公认的职业声望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异[11]。另外,政治资源、民权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分配也是划分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之一。
卫生公平性的内涵
近年来,卫生公平性的研究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提高卫生公平性是卫生改革的重要目标。但对于卫生公平性的定义和内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卫生公平性是指人们应该以需求为导向获得相应的卫生服务,而不是取决于社会地位和收入等因素。在国内,不少学者也对卫生公平性的内涵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徐凌中等认为卫生公平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健康状况的公平性,指不同收入、种族、性别的人群应该具有同样的健康水平;二是卫生服务提供的公平性,指相同卫生服务需求的人应该得到相同的卫生服务,需求越多理应获得更多的卫生服务;三是卫生筹资的公平性,指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应对卫生服务提供同等的支付,而支付能力高的人应该多支付。一个公平的卫生系统应当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下,根据人们的支付能力进行卫生筹资,按照人们的需要提供卫生服务,同时应达到理想的满意度[12]。李顺平等对此内涵进行的一定的补充,增加了卫生资源在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的公平性,并对影响卫生公平性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综述[13]。梁维萍等则阐述了健康与卫生保健公平性概念的理解及各种测量方法[14]。翟铁民等通过对教育公平和卫生公平的内涵、研究数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政策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剖析了彼此的异同及优缺点并剖析了彼此的异同及优缺点[15],为卫生公平性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还有学者对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卫生筹资公平性以及健康不公平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6-18]。
不同社会分层的卫生公平性差异
社会分层与卫生公平性的研究,从已有的文献评阅来看,多数研究者把焦点放在对健康状况的公平性的研究。不同优势的社会群体之间具有系统性差异的健康水平,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等群体比其他社会群体遭遇更多的健康风险和疾病。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流行病学专家马木特(MichaelMarmot)花费了30年的时间开展了两个关于英国公务员健康的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处于办公室最底层的男性,死亡风险是顶层行政官员的4倍,个人的社会地位每上升一个台阶都曾经有一个相应的健康方面的改善[19]。埃尔斯塔德(Elstad)等在1985年和1995年对挪威9189名年龄在25~49岁的成年男性进行了2次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职业阶层越高,其自我健康评价也越高,在1985年,高级白领阶层、中间职业阶层、体力劳动阶层和无业阶层自我健康状况评价较差的比例分别是8.1%、9.9%、12.9%和36.2%,到了1995年时,4个阶层自我健康状况评价较差的比例分别是11.4%、17.1%、20.4%和55.9%,研究证实了不同阶层等级之间存在明显的健康梯度,这一梯度还在不断加大[20]。美国学者斯密斯(GeogeDavey-Smith)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和死亡率存在着剃度变化的关系,对于年收入7500美元的个人,其死亡率与年收入32500美元者相比,几乎高出两倍[21]。劳瑞(Lowry)等运用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的健康不公平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的健康状况同他们的收入水平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另外,他们还发现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的健康不公平呈扩大的趋势,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有累积效应[22]。周菲等采用浙江省城市农民工数据,检验了城市农民工自评健康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其中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其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选取职业来代表社会经济地位。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城市农民工的自评健康与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23]。陈定湾等曾利用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浙江省数据,分别利用Logistic回归和劳伦斯曲线等方法分析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公平性,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社会阶层越高,健康状况也越好[24]。对不同社会分层人群,在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差异也有报道,西班牙学者CarmeBorrell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实施了一项调查研究,共涉及超过14岁以上人口12245人。该研究证实,在被调查人群中,大约有1/4的人拥有私人医疗保险,但这一比例在不同社会阶层人群中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和第二阶层人群可以达到50%,但第四和第五阶层大约只有16%。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在两周就诊率和过去一年的住院率等卫生服务利用方面没有明显区别。但在等候时间上,有购买私人保险的平均为18.8分钟,而同样都是参加NHS的人群,第四和第五阶层的等候时间也要长于第一和第二阶层,分别为35.5分钟和28.4分钟[25]。希腊学者YannisTountas在一项涉及1005个样本的调查研究中显示,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利用,社会阶层较高的人群和那些拥有私人保险的人群要高于其他人群,在一般人口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住院服务的利用没有明显区别[26]。
社会分层影响健康公平性的主要通道和机制
对于社会分层所造成的健康不平等的机制和通道,学术界仍有不少争议,也有不少实证研究。但总结起来,主要包含三种观点:一是健康选择论,这种观点认为健康状况较好的人能够有较好的条件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反,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由于身体原因,收入和教育会受影响而向下流动,从而导致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之间健康梯度的扩大。埃尔斯塔德(El-stad)和劳瑞(Lowry)的研究均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差异在逐步增加[20,22]。二是社会因果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地位较高,因此具有较好的职业环境、生活环境以及更高的医疗水平,以及较少的压力,从而具有更好的健康状况。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滋曼(Hertzman)认为,在早期童年,社会经济状况对人生的成长、教育、就业、收入和健康都有深远的影响[27]。马木特的研究提供了工作场所对健康影响的一些线索和证据[19]。另外,社会地位的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马木特研究显示即使是在中等和上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层面,仍然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康差异。英国公务员均具有良好的职业和生活环境,但处于最低职位的公务员死亡率风险是平均值的2倍,而高级官员的死亡率风险仅为平均值的60%,因此他认为可以用对健康有害的压力来解释,因为收入和地位的差异在细分阶层内依旧会通过社会攀比给人以压力并损害健康[28]。关于影响健康公平性的机制研究目前大多以欧美国家经验数据为主,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在国内,王甫勤曾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机制,并从侧面比较了健康选择论和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9]。三是健康行为的解释,研究显示,尽管卫生保健服务的差异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而存在,但在死亡率和发病率方面,卫生保健服务的差异在社会经济地位梯度中只占较少一部分,如只有10%的早产儿死亡可以归咎于不适当的保健,50%则归咎于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因此,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分层影响健康的一个主要通道就不足为奇了。吸烟、酗酒、不良饮食和长期不运动的生活方式对社会经济地位显示出与健康结果相同的梯度关系[30]。陈定湾等人对分析了不同社会阶层人群中三种常见健康行为的差异,显示了社会阶层越高,其健康行为的采纳情况也越好[31]。除此之外,社会分层对健康的影响无处不在,很多联系还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存在许多通道,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作者:陈定湾、王妮妮、刘盼盼、尹口 单位: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上一篇:小议比较视野中的艺术设计教育范文
- 下一篇:小议儿童牙科行为管理问题的成因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