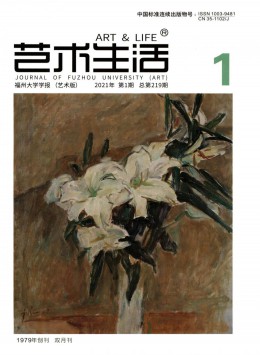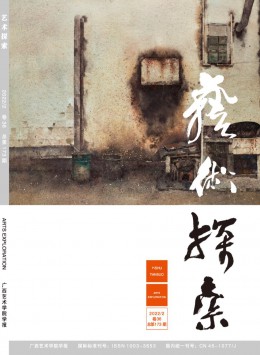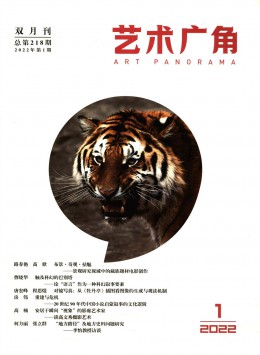艺术论文全文(5篇)

第1篇:艺术论文范文
我国的民间艺术是观念艺术,因此,色彩更是观念上的。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使得民间艺术中色彩表现出了很强的审美特征和感情特征,这从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习俗的影响。所谓观念,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被淳朴的理解为吸福纳祥,消灾辟邪等传统的世俗目的。从而形成了民间艺术中火红喜庆的特色。很多的词语如万紫千红表现着喜庆吉祥的含义,还有很多描述色彩的词语,一般来说都是图个吉利,很多的描述色彩的词汇已经成为观念上的造型语言,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其在陶瓷艺术品的设计中也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可以通过陶瓷设计将本民族的观念和信仰加之其中,体现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大大超出单纯色彩所能传达的信息,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色达意”的效果。
二、民族艺术在陶瓷艺术品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对陶瓷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很大影响和促进作用。比如:剪纸、漆器工艺、编制、绣花、彩绘等等都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化遗留下来的瑰宝,我们必须加以传承和发展。民间艺术中有非常多的图案,每种纹样,每一幅画都不是单单存在着的,其能够流传至今,不仅仅是因为其美丽的色彩图案,而是蕴含在其中很厚的文化气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中,其不断被传承和发展,一路上记录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坎坷经历,与外部民族交流的成果。就像一本历史剧值得人们细细品味,其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和文化内涵还需要广大的科学工作者挖掘。在陶瓷艺术品的创作过程中,设计人员通常将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图案植入其中加以利用,以提高其文化内涵和艺术韵味,通过刻、划、剔、釉色等传统工艺程序,让陶瓷艺术品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艺术感召力。这种将民族美术语言与价值实践统一起来的活动是一种装饰艺术,是民族艺术图案的传承和创造应用,充分体现了本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精神。所谓剪纸艺术,其包含的领域非常广泛,有着很多的表现手法,比如:阳剪法、阴剪法、剪影法等,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一些美妙的神话传说。剪纸艺术中多样的题材包罗万象,其中很多不单单是对生活现象的再现和描绘,而是具有很多特定的含义,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将剪纸艺术运用到陶瓷设计中,最早是出现在晚唐时期。通过两次釉色而烧制成的陶瓷制品,呈现出有层次感的花纹,具有剪纸的效果,其画面有层次感,视觉效果很好。现代艺术家们通过一些新的方法将剪纸和陶瓷结合到一起,然后融入现代时尚元素,创造出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巧妙结合了时代特色和传统文化,为民间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很好的思维途径。民间艺术是生活的语言更是艺术的语言,人们可以将感情寄托其中,将生活中感情物化。成为劳动者和造物者通透的桥梁和纽带,把人类的创造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民间艺术是一种和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创造方式,可以丰富和充实我们的社会生活。民族艺术的创作和思维方式、语言风格、情感表达方式也独具特色。一般来说陶瓷艺术和民间艺术史同根的,在原始社会中陶片上的各种图案、符号,具有标记某种意义的作用。由于民间艺术所涉及的范畴十分广泛,其可以为陶瓷艺术品的设计提供极其丰富的养分和经验借鉴。
三、吉祥图案的寓意
所谓吉祥,意为美好的预兆,吉就是福善的事情,祥就是嘉庆的象征。吉祥的图案可以使用花鸟、走兽、人物以及一些吉祥的文字。这些文字可以是吉语、谚语甚至是一些神话故事为题材,在使用过程中可以通过比拟、象征、双关、隐喻等修辞手法,形成“一语一图”的民族艺术美的表现形式。不仅可以通过这些展现人们的幸福快乐,还可以寄托愁思,表达对长寿的向往,以及各种吉祥喜庆的理想。可以这样说,吉祥在我国是一个几千年亘古不变的主题,同时在陶瓷艺术的设计中吉祥必须体现出来,很多艺术家通过谐音、比拟、寓意等表现手法,来展示现代陶瓷艺术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现代活力特征。所谓象征,就是根据事物的具体形态、色彩、习性等,使用其相似或者相近的含义。比如:鸳鸯象征着爱情,牡丹象征着富贵,竹子象征着君子,莲花象征着高洁等等。谐音原本是文学中的语言表达形式,民间通过谐音的方式表达吉祥,比如:在结婚的时候,会有枣,寓意为“早生贵子”,人们在吃饭的时候通常会有鱼,其寓意为“年年有余”,年糕的糕与“高”谐音,有步步高升的寓意。
第2篇:艺术论文范文
釉是七十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瓷器装饰材料和技法。亦称高温快烧颜料。颜料的熔剂成分不含铅或少含铅,按釉上彩方法施于器物釉面,通过1100~1260℃的高温快烧(一般在最高温阶段不超过半小时),釉面软化熔融,使颜料渗入釉内,冷却后釉面封闭。尽管《中国古陶瓷图典》没有把“釉”同“釉上彩”、“釉下彩”、“釉上、釉下双层彩”并列成类,但实际上已经承认“釉”的存在事实,并且使用了“釉”这个概念。书中关于褐彩、褐绿彩和白釉绿彩的条目中,分别介绍了唐代四川邛崃窑和湖南长沙窑的“釉中褐彩”、“釉中褐绿彩”、和“釉中绿彩”等特色品种。这就说明“釉”这类彩瓷早在唐代已经创烧成功,成为正式的产品。如今在市场上,釉工艺已被用来绘制大路货商品,“釉”的大字广告招牌随处可见,货架上排满釉产品。据说釉之所以时兴有两个原因:一是迎合人们认为釉上彩料会产生污染,而釉不会污染的心理。二是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坯胎釉上绘彩后再薄薄喷上一层面釉,然后一次烧成。之所以绘彩后喷层薄釉,一是怕彩料不能完全沉入釉中,二是使器物表面更加光平。巧合的是,这种釉又回到了康熙名品“豇豆红”的制作方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回转”。
二、釉上彩形式
1、粉彩是釉上彩
最具代表性的陶瓷绘画,粉彩又叫“软彩”。粉彩瓷的彩绘方法一般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干净毛笔轻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依次洗开,让画面有层次变化和光影变化,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明的浅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寡来获得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给人粉润柔和之感。
2、新彩是釉上彩
第3篇:艺术论文范文
纵观当下世界戏剧舞台,对外国戏剧莎士比亚戏剧持续、广泛的演出、研究是确立其无与伦比经典地位的重要原因。当代莎学研究证明,对莎剧的阐释早已不是英美莎学研究的专利,对莎氏戏剧的跨文化阐释,也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现象,并且已经成为激发莎学研究持久活力的最主要动力。诚如耶鲁大学戏剧系大卫•钱伯斯教授(DavidChambers)所指出的:“莎士比亚的未来在于非英语区的世界文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种‘异国的莎士比亚’实验所提供的启示要大过一般的英语莎剧演出。”因为时代在发展变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艺术语言和审美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举办为标志,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改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犹可宝贵的是,相对于当下莎剧改编中的穿越、互文、拼贴、挪移、颠覆、解构试验,以《温》剧为代表的回到话剧“从生活出发的舞台现实主义”和莎剧审美艺术本体的改编,显得更为稀少也更弥足珍贵,甚至在导表演上也更显难度和功力。莎剧改编不易,要达到很高的审美艺术成就,获得当代观众的心灵震撼更是难上加难。惟其如此,《温》剧才成为中国莎剧改编中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温》剧改编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以作为世界经典的莎剧审美魅力为号召,在遵循原作乐观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生活原则方面,力求在不改变原作轻松愉悦喜剧效果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式的幽默,通过笑声反映人性中的弱点与道德缺失,甚至在基本沿用原作台词的基础上,既比较忠实地按照原作中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在明快乐观和开怀畅笑中展现了“轻松活泼的生活情趣和严肃的生活准则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而中文剧名中的“风流”,其实就是“快乐”的误植。在舞台叙事上,该剧既符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话剧舞台上主流话剧的呈现模式,又在写实的主流话剧之外掺入了对斯坦尼体系的辩证认识,尝试用“多种手法反映生活真实”,以此对现实人生、扭曲人性作戏谑式的嘲笑与批判。诚如方平先生所言:“在莎士比亚的全集中,《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占有一个特殊地位。它是最散文化、最富于现实主义风格的一个戏剧……只有在这个莎剧里,当时很富于生命活力的英国社会的市民阶层和他们的妻女,作为主要人物登上了舞台,向观众展现了他们活跃的精神面貌,和他们家庭的内部情景。”显然,《温》剧主要以“生活于角色”的写实叙事把握、突出原作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但同时也不过分拘泥于舞台叙事的写实风格,试图突破在舞台上创造幻觉的写实手法的束缚,以“非幻觉主义艺术”的写意手法,特别是“舞台假定性”和“陌生化”的叙事增强该剧的表现力,这也是该剧舞台叙事的主要特点。但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话剧的大趋势之中观察,《温》剧仍与其前后产生的“写意话剧”或以更加纯粹的陌生化舞台叙事引起轰动的戏剧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二、两大戏剧体系之间的叙事
结束,新时期伊始,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话剧走在了前列,对外国戏剧包括莎剧的改编也是这一行列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我们看到,尽管《温》剧的排演仍然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来处理诸如剧本主题、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但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戏剧本质的反思和对形式多样化的探索相呼应,此时《温》剧的改编也在试图突破以再现美学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和单纯写实的斯氏戏剧的束缚,尝试运用更为丰富、更加多样的舞台叙事手段,在幻觉的真实情景之外,给“欣赏者提供想象驰骋余地的‘意中之境’”,瑏瑠“拿笑声做武器,对于各种各样阻挠社会向前发展的封建保守势力,给予无情的讽刺”,而这本身就是对以及所谓批判“大、洋、古”戏剧,视爱情、性为洪水猛兽等极左思想的一种反拨。但是,由于当时现实主义的戏剧表演方式仍然是舞台叙事的主流,所以《温》的叙事也依然是建立在符合文艺复兴时代感、异域特征、莎剧意味,具有英国小城镇特点的背景之下,甚至人物的化妆也要具有异域特征,以此与本土的中国戏剧相区别,即更多的强调叙事中的所谓现实主义的“莎味”。而这种舞台呈现方式正是那一时期中国舞台改编外国戏剧的主流叙事模式。但是,随着戏剧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有些戏剧开始强调演员的表演“既是角色又不化身为角色的陌生化效果”。尽管这一时期莎剧的改编,显然还没有也难以适应这一变化,但与斯氏写实戏剧不同的舞台叙事手法毕竟已经成为该剧导表演一种自觉追求。因此,《温》剧的舞台叙事和呈现方式既成为衔接,以斯坦尼戏剧理论指导莎剧改编,也掺入了“陌生化”的话剧莎剧表现方式,成为既连接过去也面向未来,改编严谨,体现原作主要思想,也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莎剧。《温》剧改编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始终以原作的讽刺精神为依托,以写实手法体现其喜剧精神的实质,既不盲从也不固执地以斯坦尼戏剧理论体系作为改编的唯一指导思想,也根据改编者对该剧深入的理解,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表现形式,因此,这一时期以《温》剧为代表的这类莎剧改编,可以视为从斯氏戏剧理论体系向多元化改编方向发展的过渡时期的一类中国话剧莎剧。现实主义的文学强调时代背景,《温》剧亦突出时代特征,塑造了一个以福斯塔夫为代表的从破落贵族封建骑士堕落为游民的泼皮无赖形象,并且给予了富于“生活气息和现实性”讥讽。《温》剧以已经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福斯塔夫等人所处社会环境为背景,其审美价值在于完成了福斯塔夫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准确塑造。改编紧扣福斯塔夫愚蠢追求肉欲“可爱的堕落”和自作聪明的“放荡”,⑥并时时与人文主义的爱情观进行了比对。因为对于封建包办婚姻和以金钱财产缔结的婚姻来说,正如剧中所说,“爱情这回事,自有上天来作主;买田,要金钱;娶老婆,要靠命数。”而这个所谓命数正是指当事人具有自主追求婚姻爱情的权利。为此,《温》剧的舞台呈现既在观众面前徐徐展现出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下层社会的风情画,又通过流畅的舞台叙事使观众领略到画中人的幽默、诙谐与乐观精神。该剧的导演和演员从人物的性格出发,在准确渲染《温》剧欢乐主题的前提下,把重点始终“植根于深厚的内心体验和生活,以强烈的形体表达和情感释放,着力于舞台人物的塑造”。原作由于具有闹剧的因素,在排演中很容易做过火的闹剧演绎,但是,导表演并“没有依据剧本中的闹剧因素去过火地处理,而是十分注意地体味莎翁笔下的英国式的幽默”。扮演福斯塔夫的张家声致力于“真实地刻画出一个虽已七十高龄,却因种种强烈欲望而骚动不安的,自以为聪明可又处处被捉弄的形象。”《温》剧的幽默通过张家声扮演的福斯塔夫以“松弛、自然、夸张、含蓄的表演,张弛有致地描绘了有着各种色彩的爵爷”。瑏瑡导表演所欲建构的是围绕着福斯塔夫这个人物形象周围的各色人物,所展现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对经典的重新建构中,《温》剧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舞台叙事手法,“尽量做到生活化”,瑏瑢以及表演上有意穿帮的陌生化表演方式,在幽默、讽刺中张扬人文主义的爱情婚姻观,并且通过斯坦尼与布莱希特戏剧审美思想的交织与交汇运用,实现了生活与艺术在舞台表演上的双重审美叠加。
三、镜像:双重身份的跨体系建构
19~20世纪的莎剧演出经历了从富丽堂皇的布景到布景越来越少的过程。世界范围内的莎剧改编已经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各种形式的莎剧演出层出不穷,中国的莎剧改编也不例外。尽管多元化莎剧改编有其存在的理由,也确实给人们欣赏、阐释莎剧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但是,严格按照原作思想改编的莎剧具有恒定的审美价值,由于较为接近原著,故也受到观众的喜爱,并在莎氏戏剧传播中占有重要位置。莎氏通过其剧作显示出“戏剧艺术是最贴近人生现实的”艺术,现实主义的改编,要求导表演在反映原作主题思想的基础上,准确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塑造人物形象,而舞台叙事、环境、服装也仍然要求获得逼真的舞台艺术效果。为此,《温》剧的改编不做拼贴与戏仿阐释,也不对原作的主题、人物给予所谓的现代演绎,而是在不偏离原作主题、内容的基础上,遵循现实主义美学所倡导的“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原则,强调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温》剧调侃、幽默、好玩的氛围中,在轻松与愉悦中,通过挖苦福斯塔夫这一类人,达到批判的目的。更由于该剧现实主义与陌生化表现手法相交织的叙事艺术,使原作的喜剧精神与幽默叙事成为贯穿整个舞台审美过程的主旋律。这就是说,《温》剧是以展现“真实作者”的喜剧精神为目标,叙事始终遵循“舞台上的真实,是演员所真心相信的东西,是自身以内的真实,这样才能成为艺术”④的现实主义表现风格。而作为“扮演者”的演员也必须在“角色”和“叙事者”的双重身份之间形成有机互动,进入“角色的一切情感、感觉、念头都应该成为演员本人的活生生的、跳动着的情感、感觉和念头”。作为“角色”体现者———扮演福斯塔夫的张家声塑造的福斯塔夫强调的是“用动作来帮助言语和思想”,所以“角色”始终是内在的角色与外在的叙述者的统一体和矛盾体,“角色”在斯氏现实主义演剧体系与布莱希特陌生化表现手法之间来回穿梭,人物在“现实主义”与“间离”的舞台叙事中,有规律、有分寸地不断“再现莎剧真善美面貌和神韵”,并得到真实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呈现以及莎学专家与观众的认同。“莎士比亚的剧本是用来演出的,而且始终听命于剧场演出的实际需要。”演员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是“从内心去体验并终而去表现的那个人的生活状况”。张家声按照人物的思想、行动、行为逻辑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当福斯塔夫写好了勾引福德大娘和培琪大娘的情书,命令跟包送出时,先是自以为得计的笑,继而暴怒,在怒火中烧中显现出某种优越感,转而又在歇斯底里中咒骂,然后从牙缝里蹦出一连串骂人的语言。人物塑造的层次性是在“更朴素的表演”基础上谐谑这个丑恶、有些做法又傻得可爱的形象,从而有层次、多侧面、层层递进地创造出“人物”狡黠的复杂性格。在舞台叙事中,人物个性是否鲜明取决于“角色”外叙述者演技高低和内叙述者表演的逼真与否。而叙事就是要在“舞台上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的精神生活,并通过富于艺术性的舞台形式反映这种生活。”瑏瑡我们看到,《温》剧的导演和演员是深谙斯氏这一思想的,叙事既实现了借助莎剧的经典性超越时间、空间的阻隔,以真实、自然、准确的表演,细致传神地开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以松弛、夸张、形象的戏拟,张弛有致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福斯塔夫的形象是一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缺乏善良和仁慈的负面人物的镜像,但却又是无伤大雅的好玩人物,这也许就是作品所要表现的莎氏喜剧精神的实质。
四、原著精神的体现与民族化
西方学者曾将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改编归纳为经典、本土、后现代三种形式,所谓“经典的莎士比亚”,就是原作被精确翻译,演出完全是西式的。《温》剧的创排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突破话剧理论界以北京人艺独特演剧风格为标志的现实主义原则的话剧形式,所以表现为,对莎剧的诠释更加自信、更为自如,也更有底气。诚如童道明先生所言,《温》剧是“莎剧演出民族化”③的大胆实践。但是《温》剧的民族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化,即《温》剧的民族化有别于着中国戏曲服装,运用戏曲程式,操戏曲声腔的戏曲莎剧。较少有学者注意到,《温》剧的民族化并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一种内在表演形式的创新,是化莎氏喜剧精神,又能得到中国观众理解、联想和会心一笑的民族化。统观该剧的演出,我们可以看到,《温剧》的改编,既致力于营造原作欢乐、轻松的人文主义乐观精神,演出中也对内容、情节不作大的变动;对白既包含了原作中的幽默、调侃,又不完全拘泥于原作所提供的意蕴;叙事既与原作中人物对白、语境相适应,又在化用原作的过程中,增加了中国元素和中国色彩。例如,《温》剧开始和结尾都将原作第四幕第二场培琪大娘的“不要看我们一味胡闹,这蠢猪是他自取其辱,我们要让天下人知道,风流娘们不一定轻浮。”化为:“我们这就要让大家瞧个明白,娘儿们爱闹着玩,可照样清白。莫怪我们爱玩、爱乐,太胡来,俗话说得好,蠢猪只配吃泔水。”如此解释,既在戏剧的开场点明了喜剧的主要内容,又在结尾再一次营造了喜剧气氛,引发观众意犹未尽中的回味,同时也造成了首尾呼应,强化喜剧精神的舞台效果。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人物,主要依靠语言和形体,这就要求在形体表现上既要表现人物形象特征,又要通过动作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舞台表现的形式美。在《温》剧中张家声根据人物特点和不同语境突出福斯塔夫这个人物语言的粗俗、幽默和“滑稽幻象”,并力求真实地在福斯塔夫外形之外,刻画出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因为“戏剧的本质不在于创造一个酷似现实的舞台时空,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舞台假定性的魅力,”即在舞台叙事中“以夸张的形式引入讽刺喜剧所具有的真实感,”⑧例如在第一幕第一场中,当夏禄要跟福斯塔夫算账时,原作中福斯塔夫说:“可是没有吻过你家看门人女儿的脸吧?”在《温》剧中则改为:“可是我没有搂着你家女人亲嘴吧?”瑏瑠显然,这一改动更加凸显出福斯塔夫沦入社会底层,毫不避讳的放荡与幽默,在调侃中使矛盾的指向更为明确,因为吻看门人的女儿与搂着你家女人亲嘴的行为显然是不等值的。《温》剧的民族化还表现为利用人物对某些词语的误读或采用中国语境特有的口语,以加强喜剧效果。同样是在第一幕第一场“傻得可爱”瑏瑡的斯兰德说:“喝酒喝得叮当大醉”,操一口河南话的牧师,纠正他应该是“酩酊大醉”;剧中巴道夫等人一连说了两个“你可真咯啊”,瑏瑢在全剧中“咯”这个北京土语共出现了6次以上,以拉近当代观众与《温》剧之间的距离;当斯兰德表示要向安妮•培琪小姐求婚,把“牢不可破”,说成了是:“这是我牢不可靠的决心”;瑏瑣这种张冠李戴、弄巧成拙,恰恰弄拧的人物语言,凸显出斯兰德矫揉造作、装模做样的性格特征,而福斯塔夫此时则揶揄地嘲笑:“胡说、瞎说、乱说,一派醉说……哈、哈、哈。”再如在第一幕第三场福斯塔夫说:“我快要穷得鞋子都没有后跟啦。”《温》剧紧接是“逼得我要去打野食”,②在这里“野食”也具有特定的含义,能为中国观众所理解。所谓对人性的刻画,包括对人身上缺点、丑陋面的形象反映,是通过舞台叙事,真实、朴素地展现了人生之过程、人生之态度、人生之位置,个体之性格与他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温》剧既通过写实的叙事方式塑造人物的性格特征,以“戏剧接近实际生活”的艺术理念建构舞台叙事,又采用陌生化、大写意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舞台叙事创造出使中国观众感到愉悦、认可、开心的舞台语汇。显然,编导在《温》剧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之间寻找一系列映射的支点,将原作中的喜剧精神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求新、求变、创新、开放、放松的心态呈现于舞台之上,在亦美亦丑、亦庄亦谐、亦张亦驰、亦实亦虚、亦真亦假、亦俗亦雅、亦莎亦中的表演中,创造出一部既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风格,也融会了布莱希特陌生化戏剧特点,且又具有中国风格的莎剧。莎剧被搬上西方现代剧场或中国舞台,没有不经过改编的,只不过考虑的焦点常常是采用何种改编形式,改编保留多少莎剧内容、精神而已。即使被认为是严肃、严谨的演出,也会根据现代导演、演员对莎剧的理解,以及现代观众的观剧习惯给予或多或少的改动,《温》剧的改编岂能例外。在现代戏剧舞台上,“导演是演出形式的创造者”。《温》剧的改编遵循在信息的传送与接受之中,尽力扩展舞台空间和时间的表现范围,舞台设计力求简约、洗练,实景与象征性舞台布景相结合,无论是培琪家门前,还是嘉德饭店、温莎街道、福德家中和温莎公园,都利用旋转舞台创造出演员行动的支点。也就是说《温》剧既借助于建构人物活动的真实氛围,也力求通过舞台假定性存在,在“一种现实的力量”秩序之外,营造出莎士比亚喜剧所需要的美学效果。我们看到,《温》剧中的男女艳闻也成为推进情节发展的动力。在伊丽莎白时代,“花心男子的艳闻是一定会被邻居七嘴八舌地传颂”的。莎剧中有许多乐天而充满感情的妻子类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风格较为浓郁的话剧莎剧,《温》剧通过角色创造人物艳闻、笑料的戏谐性,即“运用台词为行动手段来创造人物的行动”,例如第二幕第一场福斯塔夫给培琪大娘的信:“我就是那忠诚的骑士供归你差遣……我要高高举起宝剑,为了你把天下打遍……”原作中福斯塔夫说:“我不过略有几分才干而已,怎么会有魔力呢?”在《温》剧舞台上变为:“我哪有什么勾引女人的绝招啊?”在《温》剧中这类接地气的言语可以说时时在撩动着观众幽默的心弦,刺激、愉悦着观众的神经。例如“胖得有线条”“揍我个底掉是什么意思?”“不准武斗”“小公鸡、小跟包”“土豹子”“肉山”“活王八”“别价”“三从四德”等等,甚至在击剑的决斗中,决定胜负的不是人物手中的剑,而是一本当做了武器敲到头上的《圣经》;在第四幕第二场,当福斯塔夫第二次来到福德家中,熊抱福德大娘时,培琪大娘在里面弄出声响,福斯塔夫懊恼地嚷道:“这才他妈是时候啊”;瑏瑡而当福德要翻动筐子时,福德大娘有意举起了女人的乳罩在人们眼前挥动。显然,《温》剧的舞台叙事不是机械和僵硬地忠实于原作,而是在强调忠实于人物性格和规定情景的前提下,挖掘、创造出符合人物心理特征和性格逻辑的舞台形象,动作成为叙事的重要手段,为人物的行动和表现人物多侧面性格服务,同时也通过滑稽的造型和具有强烈暗示色彩的冲突、行动和语言,赋予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性格特征。再如《温》剧第二幕第二场中福德化名为“白罗克”要福斯塔夫把福德家的女人弄上手,“假如我能够抓住她一个把柄,知道她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就可以放大胆子,去实现我的愿望了。”呈现出来……滑稽是人物性格的自然流露。”此处,雷恪生扮演的福德在和张家声扮演的福斯塔夫的对手戏中,有意使人物的动作多次“穿帮”(粘在脸上的胡子几次险些掉下来,又不故意扶正),“白罗克”为了掩饰自己被福斯塔夫骂为“王八”的尴尬,故意装蚊子叫,二人对话中,福斯塔夫看着假扮为“白罗克”的福德说:“我眼里有这个混蛋家伙吗?”②陌生化叙事增添了喜剧效果,表现出福德心虚、好吃醋的性格,此时演员与角色之间的间离,有助于把握事物的本质真实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使观众看到,福德与福斯塔夫其实是一路的好色货色。此时,现实生活与剧中人物感情的南辕北辙,形成了戏剧对世界的间离反映。这种通过“穿帮”造成的间离幽默效果,在《温》剧的叙事中得到了多次运用,按照布莱希特的想法“演员在舞台上不可完全转变为表演的人物……他尽量真实地传达出他的言辞,按照自己对人的理解,表演他的举止行为,但是,他绝对不试图使自己(并且借此也使别人)幻想由此而完全转变了另外一个人。”“穿帮”既使演员同角色保持了距离,又在距离感中使观众获得了观察人物内心世界的愉悦。戏剧的言说(表达)方式是“代言体”,在代言中,雷恪生和张家声的表演都“批判地注意着他的人物的种种表演,批判地注意与他相反的人物和戏里所有别的人物的表演,”从而以轻松自如的表演,表现出对人物的深刻理解。《温》剧避免容易造成幻觉的“生活本真美”的叙事,也不取中国戏曲写意性的隐喻叙事,而是根据作品中提供的人物活动环境,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使舞台上的每一因素尽可能参与“多重叙事”带来的“莎味”。《温》剧致力于以细腻的表演,对人物精神、心理的准确把握,穿插陌生化表演方法,共同为全剧的诙谐、幽默、乐观的叙事效果服务,创造出一幅英国文艺复兴时代色彩斑斓的风俗长卷。而当“演员运用动作进行行动了以后……内心生活”得到了明确诠释之时,可恨、可爱而又可笑的福斯塔夫等一干人也就跨越时代、民族、语言和文化来到了中国观众中间。《温》剧有意识地运用“间离效果”,人物扮演者以游戏性的间离和戏谑性引观众开心,又在“间离”的叙事中,使“人物”成为精神层面漫画化的夸张与世俗社会的特定“符号”,在莎氏喜剧乐观精神的引导下,《温》剧探寻了三教九流本我中“贪婪”“下流”“泼皮”“虚伪”“好色”的行为,以接民族地气的叙事方式打通了莎氏喜剧与中国当代观众之间的时空、文化隔阂。
五、结语
第4篇:艺术论文范文
(一)老杨公
“老杨公”能历时几百年而流传至今,是跟它的地域性特色和原生态特色分不开的。早在2008年,老杨公就被评为北海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仅是因为了老杨公的故事反映了人们互敬互爱,教育婆媳和睦相处、夫妻合好,赞颂勤劳勇敢、驱恶行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既了保留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和乡土文化意识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老杨公”采用广西合浦地方方言演唱,主要由民族乐器+打击乐锣鼓+独唱、对唱、三人联唱+舞蹈+顺口溜+讲故事等多种艺术形式构成,表演形态富有原生性,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老杨公》的音乐是以廉州方言发音音调为基础的,富于原生性的民间音乐结构。它的歌曲种类是山歌类歌种。音乐曲调是民族调性sol1adoremi的微调式。从音乐结构来看,“老杨公”以“西海歌”的音乐旋律为核心,配以其它音乐曲牌如“东海歌”“西海歌”、“撑船调”、“棹船调”、“西江月”、“犯仙调”等,通过重复、变化、交替发展等方法,构成具有浓郁而鲜明的沿海地方特色、曲牌丰富多彩、风格统一的联曲,“老杨公”的音乐虽然曲牌种类繁多,但一般都是二乐句和四乐句的乐段结构;在四乐句的乐段结构中,第三句往往是第一句的变化扩展,第四句往往是第二句的变化重复。第一句一般结束在调式音阶的第三级或第四级上,形成半终止,两句乐句一起一伏,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曲调优美,亲切流畅。“老杨公”的表演有别于北部湾地区其它民歌的艺术表演,它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歌舞表演形式,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边唱边跳的民间歌舞艺术。它能深深扎根在民众之中,代代相传,深受广大群众喜欢,是与其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事一物,并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较高的艺术性和广泛的影响力分不开的。《老杨公》全场表演只需两个演员,分别表演“老杨公”和“仙姑”,台下锣鼓手4~5人以及一名掌板者(兼送白、送歌)来配合台上的表演。“老杨公”和“仙姑”要唱、跳、演样样具备,因此舞蹈动作编配不能太复杂,但是,人物扮相和表演特征却十分重要。换句话说,老杨公和仙姑的形象能否独具一格,从人物扮相和表演特征来看,它必须更加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老杨公”的歌词采用廉州地方方言来演唱,有着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不仅具有原生性发音特点,而且思想内涵丰富。它的歌词词牌如同它的曲牌一样,种类繁多,有“大唐歌”、“东海歌”、“西海歌”、“西江月”、“犯仙调”等。这些词牌往往运用“比兴”、“双关”、“歇后语”、“谐音”、“比拟”、“析字”、“叠字”等不同的修辞手法,特点鲜明涵丰富,富于哲理,艺术性高,富有魅力。其中的“大唐歌”是北海民歌当中流传最早的一种词牌,它强调双关,重在抒情,意义深远,属于赋体歌讲究第二第四句压脚韵。
(二)耍花楼
“耍花楼”也是北海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类,是合浦县有名的民间歌舞之一,用合浦本地话廉州方言演唱,主要流传于廉州、党江、西场、沙岗、石湾、写家等讲廉州话的乡镇,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不但舞蹈动作多彩,歌调也较多且感人。“耍花楼”主要是一男一女两人身穿传统服装,在舞台上交叉穿插表演,对歌对舞,动作潇洒大方而又优美热烈,舞步多姿多彩。歌舞时男持一把花伞和一把纸折扇,女持一方绢帕和一把纸折扇,边唱边舞,常用的曲牌有:“花楼调”、“游山打猎”、“开经调”、“叹世调”、“插花调”、“采茶调”、“挂金索”、“二环调”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花楼调”和“游山打猎”。这种曲调唱词情调优美,富有浪漫想象的神话色彩。由于这种歌舞极其引人入胜,又被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解放后,合浦人民对“耍花楼”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改革后的“耍花楼”它已去除了那些迷信成分,多是表现劳动生活的谐趣性,也逐渐成为庆丰收、迎新春的喜庆歌舞。广西北海的“耍花楼”很像东北的二人转,其舞步轻捷、活泼、轻松、幽默,如“跑马步”、“捣碓脚”、“走车盘”、“耍伞花”、“耍巾花”等,音乐节奏明快,动作舞蹈性强,旋律高亢热烈、语言亦庄亦谐,深受老百姓喜爱,也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三)咸水歌
北海“咸水歌”几百年来都是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至今的,它精简短小,但又富有内涵,以极具地方特色的音乐风格被疍民所喜爱。作为一种民间歌曲,它不仅体现了该群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风俗的特殊性,还在本质上反映出疍民独特的水乡情怀。其演唱形式与我国其他民族民间歌曲有着相同之处,但又因风俗、语言、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疍家独特的演唱特点。咸水歌是疍家人广为传唱的口头文化,在日常生活劳作,特别是在谈婚论嫁、丧葬等过程中,触景生情,随编随唱,以歌谣形式描绘不同的情感,所以说咸水歌的歌唱内容十分丰富。北海“咸水歌”曲调繁多,歌词内容涵盖疍家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叹家姐》、《咸水歌调》、《姑里妹》、《十二月送人歌》、《伴郎》、《伴嫁》、《叹古人》、《叹字眼》等。而《叹家姐》、《咸水歌调》是最具典型性的传统的北海外沙“咸水歌”,它们的曲调亲切自然,热情悠扬,委婉感人,甜美流畅。歌曲常常都是上下两句的一段体,每句字数不尽相同,句末一般要求押韵,但也有少数不押韵的,每句曲调多是因字取腔,但衬字的音调及句末收音都必须是相同的,并且不管唱多少段,其反反复复的基本结构是不变的。“咸水歌”有独唱、男女对唱、三人联唱、小组唱等演唱形式,格调清新,韵律天然,唱、叹流畅,感情浓郁、亲切。工作和休闲时叹唱儿句,焕发精神。北海“咸水歌”,因传唱地域而得名。这种富含海之韵味的歌谣,随着疍民迁徙漂移,在北海的文化土壤落地生根,既保持原生地同名歌种的血缘关系,又吸收了迁入地土著渔民歌种的养分而不断发展成熟,至今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是北部湾沿海一带以船为家的疍民世代传承的一个歌种。
二、传承思考
由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厚,文化生活日加丰富多彩,加上疍民的上岸、时代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会唱、会演、喜欢听、听得懂的人越来越少,使得这些传统民间艺术面临传人和听众双双流失的危险,甚至面临失传。因此,我们探讨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的审美属性,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最终还是要让研究成果发挥作用而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此外就是试图籍此引起人们对它的密切关注以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当务之急的就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把保护传承落到实处:一是要全面发掘、搜集、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文字、影像等资料。二是要积极改革、创新,创造一个全新生存环境,赋予它在信息时代新的意义。三是要大力普及、提高,努力提升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实现经常性,稳定性,持久性。四是要加大教育力度,努力把这些传统民间艺术引进校园,开展传承教育。
三、结语
第5篇:艺术论文范文
儿童时期通过学习器乐演奏来培养音乐的情感表现,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器乐是没有语言的歌唱艺术音乐,演奏者只能通过演奏来调动音乐语言各元素,以表现那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这就是我们常把在音乐中所表达的情感称为乐感。事实说明只有乐感好的儿童,在将来学习声乐的过程中与人类语言相融合,才能唱出最完美的歌声而成为歌唱家。可见对乐感的培养,最好也是在童年通过学习乐器的方式为好,当然儿童通过唱歌(并非声乐训练)对乐感的培养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与通过器乐演奏的方式培养乐感相比还是有所不及的。卡拉斯童年学习钢琴,这对她后来成为声乐大师的作用不可低估。她深有体会地把器乐与声乐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她认为,“我们必须做一位器乐演奏者做的每一件事,还需加上更多的事。”①其意为学习声乐应向学习器乐那样处理音乐语言中的每一因素,还要加上对歌词的理解、处理和情感表现等。钢琴(或其它乐器)的学习过程是以声音的表现来完成的,是一种逐渐加深加宽的实践体验。这种实践促进了创造性思维和表现意识的养成,极大地丰富了艺术感受力和艺术表达力。尼古拉•列西奥在评价卡拉斯时说:“她有三百种声音。她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用一种特有的声音,在特殊的速度中不断地变化音色,传达作曲家的乐段。”能达到这种超凡的境界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她童年学习钢琴的经历。
2.良好音乐欣赏习惯的重要性
卡拉斯厚重的歌唱艺术音乐修养,得益于她非常丰富的音乐欣赏(主要是歌剧欣赏)的积累。从4岁开始,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在收音机旁收听歌剧院的实况演播。父母也为满足她将来实现当歌唱家的意愿,给她购置了唱机和大量唱片,卡拉斯从进音乐学院大门到她几十年演艺生涯里,购买唱片已成为一种习惯,据报道,她是“唱片店的常客,买回大量唱片后便连续几小时地聆听”。她把音乐欣赏当作音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收集的唱片数量之多,与同一时代的歌唱家相比首屈一指。由于她聆听了大量的歌剧唱段从而熟悉了各名家的演唱,才使她能取众家之长,在积累演唱经验,提高审美视角,形成独特风格,丰富情感表现,在音乐记忆和想象能力等修养方面得以全面的提高。因此,卡拉斯在排演每部歌剧时,她所具有的音乐修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调动起来,经过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情感表现,展现出自己独有的大师风范。这也从反面说明不具备全面修养是那些歌唱家很难成为歌唱大师的重要原因之一。卡拉斯大量欣赏歌剧作品,这不仅使她在音乐修养方面得以很大提高,同时也使她所排演的每一部新歌剧,都以排演过程顺利、周期短和演出效果极佳而称著。其原因是她所排练的每一部新歌剧都是她早已听过,并已熟知这部歌剧的剧情和唱段,她没有因边排练边熟悉剧情而浪费时间,如在1949年1月卡拉斯在她即将排练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之时,突然接到指挥家赛拉宾的邀请,要她接替突然患病的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卡西奥所扮演的角色,并要求在一周内排练好贝利尼的歌剧《清教徒》。本来卡拉斯从未排演过这部歌剧,但凭借她曾多次欣赏过并熟悉这部歌剧的情节和唱段。结果按期顺利地完成了这部歌剧的排练,演出大获成功,受到歌剧导演的赞佩,对她的评价是:“只有熟悉歌剧的人才懂得这部歌剧的价值”。卡拉斯真正的舞台生涯只有l5年,排演歌剧却有1OO多部,更加证实她所排演的每部歌剧排练时间短而顺利,并以演绎水平高超而备受赞誉。这不能不说与她通过音乐欣赏积淀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有关。由此可见,音乐欣赏与积累是歌唱家成功道路上的重要阶石。
3.音乐表演中表情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