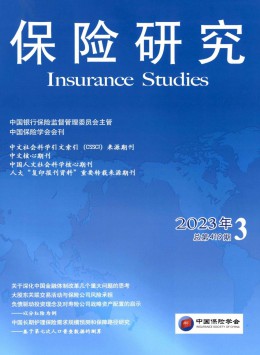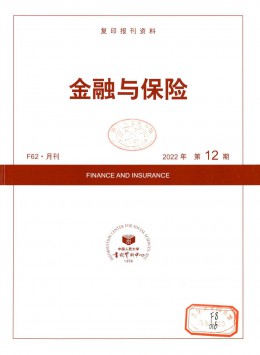论保险如实告知制度重构的必要性

在理论界,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应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存在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主流观点。肯定论认为被保险人作为被保险合同保障的主体,对于保险标的物的风险状况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只有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扩展至被保险人,才能符合如实告知义务的创设目的,也才能更加顺应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已不完全局限于同一主体的现实潮流。而否定论则认为,当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时,被保险人是无法承担如实告知义务的。
本文认为,无论是财产保险抑或是人身保险,只有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物的风险状况才是最为熟悉的。因此,从如实告知义务创设的目的以及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角度出发,应将被保险人纳入如实告知义务承担主体的范畴。承担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在具体义务的履行上可以采取主动告知和询问告知两种方式。法国以及比利时等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即是主动告知模式。包括我国、德国以及奥地利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采取的则是询问告知模式。相较于询问告知而言,主动告知对于义务主体的要求较高,尤其是对于那些对到处充斥着专业术语的保险合同不甚了解的人而言更显苛刻。但是询问告知也并非完美无瑕。询问告知下保险人的疏忽可能会给投保人以可乘之机。然而,无论是主动告知也好,询问告知也罢,对于义务人而言,告知的内容仅以能够影响到费率标准或者保险人是否承保之重要事实为必要。而何为重要事实?英国保险学者克拉克认为,凡是能够影响到保险人觉得是否与要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以及影响到费率水平的事实都属于重要事实。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影响谨慎的保险人在确定收取保险费的数额和决定是否承保的每一项资料就认为是重要事实。”[1]我国《保险法》亦是将重要事实限定在足以影响费率标准以及保险人是否承保的事项范围内。当然,为保证如实告知义务的有效规制,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该义务时,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是,当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保险人才发现有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时,保险人是否可以一概地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仍存有争议。以德国、日本、美国的堪萨斯州、密苏里州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认为,只有当不如实告知的内容和风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时,保险人才可据此行使解除权,并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但是,美国的大部分州却认为,无论是否存在上述因果关系,只要有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保险人即可以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我国和美国大部分州的立法观点一致。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4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第5款:“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笔者认为,不考虑因果关系有一定的道理,也更可行。这看似严苛,但却可以打消投保人的任何侥幸心理,更好地消除道德风险。
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博弈策略
如实告知义务无论是对于投保人还是保险人而言都可谓关乎重大。于投保人而言,直接影响其是否能够获得保险合同的保障以及保险成本与保险收益的对比是否理想;于保险人而言则会影响经营效益。因此,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投保人和保险人基于如实告知义务,展开了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双方可供选择的策略如下:
(一)保险人的策略选择
1.严格核保。保险人通过严格核保,可以较大程度地规避道德风险,避免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不如实告知行为对保险保障基金以及保险人经营绩效的侵蚀。但是,当保险人选择实施严格核保策略时,将会为此支付高额的核保成本。该成本支出的结果可能是拒绝承保,成本支出无积极的经营效果产生;可能是加收保费以抵偿成本支出;亦可以是在合同成立后的法定期间内行使合同解除权,以支付解除权行使成本为对价进行保险费的留存或返还。相比较而言,“严格核保+行使法定合同解除权”的策略更为理想,乃因为在行使法定解除权之前,保险人尚可将扣除责任准备金后的保险费余额部分用于保险投资。
2.怠于严格核保。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保险人实难做到核保的准确无误。这就难免会使得极具道德风险的投保人心存侥幸。但保险人有时却会恶意利用投保人的此种侥幸心理,通过怠于严格核保的方式得利。在保险人怠于严格核保时,保险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支出进行风险核查,并将所收保费提取了责任准备金之后的余额部分用于股票、债券等项目赚取投资收益,再待收益实现之后的法定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有效期间内,以支付少量解除权行使成本的方式解除保险合同。如此一来,保险人既实现了投资收益,又避免了保险责任的承担,而且所支付之两项成本的总和亦与严格核保时无明显不同。该策略使得保险人在怠于严格核保之假象的掩饰下,以法定合同解除权为倚仗,给投保人设置了一个“保险人陷阱”,该陷阱的成功设置,使得投保人产生了保险人严格核保意图将不得以实现的幻觉,进而铤而走险地选择以为不如实告知的策略来加以应对。
(二)投保人的策略选择
可供投保人选择的策略包括为如实告知和为不如实告知两种。究竟采取何种策略,取决于投保人自身道德水准的高低以及对于保险人应对行为的预期。然因本文并不意欲对投保人的道德问题加以研究,因此仅从投保人对保险人应对行为预期的角度来探讨投保人的策略选择问题。
1.为如实告知。当投保人预期保险人将会严格核保时,为避免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产生的不利后果,投保人将会选择为如实告知的策略。该策略的实施意味着投保人可以以支付少量保险费的方式,换取来自保险人的保险保障。投保人所缴纳保险费的具体数额以保险人风险核查的结果为准,但亦会因保险人是否严格核保而有所不同。
2.为不如实告知。投保人是保险标的之风险因素的信息优势方,基于信息占有的优势以及对保险人无法严格核保的预期,投保人会有为不如实告知的策略可供选择。该策略的实施,将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瞒天过海,欺诈策略得以成功实施;二是该策略因保险人的严格核保而被发现,策略预期因保险人拒绝承保或行使合同解除权而落空。因此,对于投保人而言,是否选择为不如实告知的策略,取决于保险人严格核保的行为以及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会对投保人构成一种可置信威胁。若是,投保人必不会以丧失保险费为代价换取合同被解除的后果;若否,投保人将会铤而走险,尤其是当保险人为其精心设置了“保险人陷阱”,使得可置信威胁似乎并不十分可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比较后可以发现,对于投保人而言,在保险人严格核保的情况下,选择为如实告知的策略为优。但在保险人怠于严格核保时,对于陷入“保险人陷阱”的投保人而言,则是选择为不如实告知的策略占优。
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博弈策略分析
从保险人与投保人上述博弈策略的选择中可知,保险人的最优策略选择为怠于严格核保,即“怠于严格核保+行使法定解除权”的策略选择。不过,这需要有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为不如实告知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存在。为了满足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保险人通过怠于严格核保的假象,为投保人设置了一个“保险人陷阱”,使得投保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进而铤而走险地选择了为不如实告知的策略加以应对。因此,面对保险法中的如实告知义务制度,投保人和保险人博弈的结局是形成了(不如实告知,怠于严格核保)策略组合。但是这样的策略组合严重背离了保险法的立法初衷,助长了道德风险水平的上升。以此反观,保险人行为还是否具有合理性,其如此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构成权利的滥用呢?自罗马法以来,“个人权利的行使禁止任何他人的不法干涉”的权利行使自由原则,由于有加害意思的权利行使禁止之法理的采用及在诉讼程序上的善意衡平法理的运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2]。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首次以立法形式出现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概念,该法第2条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应依诚实信用为之;权利滥用者不受法律保护。”迄今为止,理论界对于何为权利滥用而形成的理论学说主要以恶意行使说、超越界限说、利益损害说以及违背权利本旨说为代表。
1.恶意行使说。恶意行使说认为构成权利的滥用,须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界定标准。如果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具有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能被认定为权利滥用。《德国民法典》对于权利滥用的界定即采此说,该法第226条规定:“如权利的行使专以加损害于他人为目的,则不得行使权利。”[3]
2.超越界限说。超越界限说则认为,任何权利都不是漫无边际的。权利主体只能在权利的既有界限内行使权利才是正当的,一旦其超越权利界限去行使权利,即构成了权利的滥用。梁慧星先生是该观点的支持者之一。
3.利益损害说。利益损害说支持者之一的孙宪忠教授认为,禁止权利滥用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必须正确行使民事权利,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原则[4]。可见,利益损害说所界定的权利滥用是以权利行使的客观结果是否侵害了其他合法利益为判定标准的。
4.违背权利本旨说。违背权利本旨说认为,在私权利由个人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的当下,罗马法中那句经典的“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论对于何人,皆非不法”的法谚已不再能适应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权利绝对性”的思想已经过时。私权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性色彩,如若权利主体置权利的社会性于不顾即构成权利的滥用。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认为:“权利之滥用者,乃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法律赋予权利之本旨(权利之社会性),因而法律上遂不承认其为行使权利之行为之谓。”[5]
综观上述四种学说,笔者认为,从维护行动自由、惩戒不法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违背权利本旨说更能体现权利滥用的实质。另,对于权利滥用的界定采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似乎更为可行。即:从主观观之,行为人要有滥用权利的过错;从客观观之,其行为产生了侵害其他合法权益的后果。具体而言,权利人意识到权利的存在,但却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违背权利本旨去行使权利,并造成了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被侵害的后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利用权利滥用的理论来考察保险人的策略,无疑可将其归入权利滥用的行列。首先,我国《保险法》通过赋予保险人以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方式,使得保险人获得了对抗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有效手段。保险人可以通过严格的核保以及规定期限内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来规避来自投保人为不如实告知的风险。但是保险人却倚仗其所拥有的法定解除权,通过怠于严格核保的方式,给投保人设置了一个“保险人陷阱”,引诱投保人投保。将保险费收入扣除责任准备金之后用于有价证券等收益项目的投资,并于嗣后行使法定解除权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虽然受到2年除斥期间的时间限制,但在大规模保险基金聚集的情况下,仍足以产生相当可观的投资收益。保险人的此等行为严重违背了赋予其法定解除权的立法本意。其次,保险人的此等行为严重干扰了投保人的行为预期,助长了投保人故意不为如实告知义务行为的普遍发生。
如实告知制度的路径重构
以上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不如意之博弈结局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险人的权利滥用。因此,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如实告知制度的重构当属必要。而制度重构的关键之举即在于对保险人滥用法定解除权的行为加以规制,以此建立一种对于投保人的可置信威胁,尽量把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风险消弭于无形,使得双方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结局回归保险立法之初衷。
1.创设保险人的信息提供义务。保险人的信息提供义务与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不同。该义务主要是在询问告知模式下,要求保险人必须以一个谨慎承保人的标准,在其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或其他各种书面文件中将所有有关该特定险种的重要事实包含在内。否则即意味着未能体现在上述文件中的事实与该保险无重大关联或者是保险人已经经由其他途径获知。保险人因此便不能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保或行使合同解除权。在美国法院看来,要求被保险人披露保险人并未询问的事项将导致保险人合理行事以保护自己利益之义务的免除。因此,美国法院早在1934就认定隐瞒保险公司未询问的重要事实并不能够导致保险合同的无效。
2.剥夺特定情况下保险人的法定合同解除权。当保险人一如以上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滥用法定解除权为投保人设置“保险人陷阱”的话,剥夺其法定合同解除权将有效地限制其权利滥用的行为。正如斯科曼诉豪一案中主审法官阿斯圭斯所指出的一样,“投保单中的问题的构造形式可能会暗示承保人只需要有关一些问题的资料,或就某一问题他们只需要问题所限定的程度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构成对投保人在判例法上所负担的对一切重要事实进行披露的义务的豁免”[6],甚至是权利的滥用。因此,美国法院在哥伦比亚人寿保险公司诉罗杰斯一案中认定,如果保险人有必要对投保人之意思表示为进一步调查,但却疏于此项调查,法院就会认定保险人丧失合同解除权。另外,因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丧失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言关乎重大,因此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乃至受益人进行举证。如实告知制度如此重构,必将迫使保险人在合同签订之初即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严格的风险核查,否则即将面临合同解除权丧失的不利局面,使得保险人的权利负担明显加重。而如此的制度重构,也会形成对于投保人的可置信威胁。如此一来,投保人与保险人基于如实告知义务而展开的博弈也将回归保险立法的本旨。(本文作者:范玲 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
- 上一篇:小议城乡医疗保险统筹途径范文
- 下一篇:小议健康保险急诊费用分担的影响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