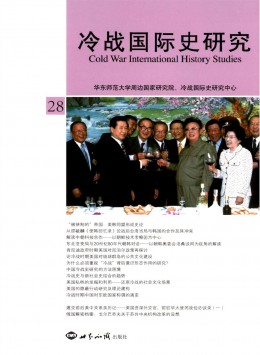战国与古希腊雕塑艺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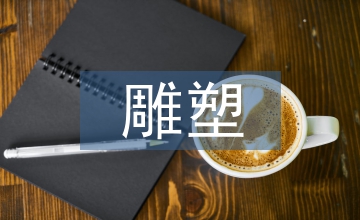
“阴阳”是借阴阳家术语,此处意思是泛指事物的两极,如虚实、有无等。诸子学说中关于此论说较多,最能体现得莫过于《老子》:“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1]“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即是“阴阳”。在老子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生、成、形、倾”阴阳协调才能平衡。他举一例解释“有无相生”的道理,“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车轮、脸盆、房间中“无”——空,才能“用”——转动、盛物、住人。只有达到平衡,世界万物才能存在而生生不息。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在他看来,一个君子是文——外在文饰与质——内在品质的平衡,否则即是或野或史,试想在那个纷争不平的年代,“文质彬彬”具有何等分量。孔子另一典型理论是关于“和”的审美取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它尽管来源于音域启发,强调的却是为建立一个正统之礼来规范人生之行为,进而为社会统治借以秩序,但这个“和”仍不失中国审美重要命题,其实质依然是在一个“度”之下的阴阳平衡。所以说,无论老子“虚实有无”之说,还是孔子的“文质”说、“和”之论其目的指向共同一点:在阴阳两极之中达到一个平衡。唯有在此之上统一,事物才得以存在,世界才能维持其秩序,社会才能有正常而合理的规范。由此,处在这个审美之上的战国雕塑的动静相依,强弱、曲直、方圆造像,并在自身的空间中达到平衡的方式是极其自然的。单看某个形体不合理,但通体的协调却是战国雕塑的客观呈现。换言之,这种形体就是战国趋向平衡审美的一个直观反映。
所谓大是指以自然宇宙为参照并与之融合,由此达到永恒的境界。它无意于实际大小,其实质在于与天地相合的状态。孔子在赞扬尧时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大,唯尧则之”[4]把他的形象比作天。对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5]的经典审美命题长期以来或以自然美注释[6]或以道德范畴论述[7],本文认为其意义在于:智者、仁者所乐并非山水之物,而在于与山水天地融合。因为“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动静在当时是哲学概念,也是事物的两极;“乐”是秩序(孔子的乐为礼),“寿”是时间。在刘向在《说苑•杂言》中解释:“智者乐水”以“通润天地之间”,“仁者乐山”以“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8]。所以,孔子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无非是在与天地共融达到永恒。如果说孔子审美还带道德约束,那么老庄之说更具彻底意义,“大”在老子理论就是“道”。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9],“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由“自然—道—天—地—人”、“无—有”这两个派生关系可知,要想获永恒或大,只有与自然融合,在“无”中才可行。《管子》更进一步推出宇宙永恒不变的是“气”,“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他进而指出气无处不在。天论是天上,大海,山都充满了气。“气道及生”一句点明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根据所在。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诸子为社会合理秩序著书立说,其共同点是以自然宇宙的运行为终极依据。也就是说,把大而永恒的自然存在和社会活动、政治事务、人的规范一一对座,这是综合的认识方式与极其感性思维的结合,溶于战国治世哲学的审美也必将具有这等气质。固而,作为审美反映之一的战国雕塑形体既是综合的结果,又是一种感性的方式塑造。另外,对大而永恒的追求,对气的感知造就了战国雕塑张扬的律动感。
战国文献及典籍中有许多这类描述,在美术上影响深渊的莫属于《易传》与《庄子》。《易传》中有:“立象以尽意”与“观物取象”说。前者见《系辞传》:“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11]在此指出立象设卦旨在“尽意”、“尽情”。而其后点明了立象以尽意的特点:以小喻大——“其称名山小,是取类也大”;而意旨深远——“其旨远”;语言含蓄而显明——“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观物取象”是《系辞传》关于伏羲氏创八卦的传说:“去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天下,俯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心通神明之往,以类万物之情”。[12]依此,作八卦是天地万物之象,而非某个具体事物,它强调所通的是万物共性之情。在此,我们无须讨论“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与后代意境说的前后因缘。但可以明确的是此二者包含有明确的审美超越精神,它要求艺术不是表现某个具体的事与情。它指向的是整体的(自然世界)事或物,而表达综合的意与情,那种以物取物,近浅的意象显然不是战国审美所提倡的。庄子《逍遥游》中许多诸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一切都来源于其“坐忘”之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13],这是一种极端自由之境,最终到达“至美至乐”,也就是说,在庄子看来“至美”是在完全自由的境界达到的。“超越——自由”的审美意识蕴涵给战国雕塑强烈的指导,它强调了以普遍意义(意境)及精神(意、情)作为艺术目的,指出了一种基于个别事物之上的整体自然的关照,弘扬了自由的艺术创作手段。由此,战国雕塑形体既自由的表达又含有普遍的因素;既超越个别事物,又超越了某类事物(动物/人),达到了一种共性的形体。
一如战国审美影响了战国雕塑形体,古希腊美学对古典时期雕塑形体亦产生了巨大作用。古希腊的审美也同中国战国时代相似,深深包含在哲学之中,所不同的是这些审美话语变得更富有逻辑且更清晰明了。有四位西方先哲我们必须提到: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由于立脚点的不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同一个命题:和谐,它开启了西方美学的起航灯,对雕塑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以四点阐释:
其一,数,代表人物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毕达哥拉斯基于哲学的研究引伸到审美领域。他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14],数是万物的来源,万物就是它的模仿品。由此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认为:美由是数及数量关系的和谐演化而来的,而人的形体美是这种和谐的数比关系的结果,通过研究音乐的实践使他们更坚定了数及数比关系的对立统一的组合产生了和谐[15]。需指明的是毕达哥拉斯之数与战国时代中国关于数的认识有巨大差异。后者是以比喻与联系为中心的概念因而具有某种神秘色彩,而前者尽管也有涉及数字的含义[16],然而其重要特征却清晰显示:“数是万物和谐之源”的解释影响到雕塑就是一种具有分析而又有理性特征的形体。由探讨数量关系的分配注定了一种既清晰明确又冷静思辨的图象。他们以脚长为基本单位计算人体,以人体各部横截面与长度之比为基本模式,甚至细化到手指的精确计算确实给了我们惊讶!由此,我们说理性、分析的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形体是“数的和谐”的外在反映。
其二,对立统一,代表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基于“世界源于火”的论断[17],他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丰富产生的”[18]。赫拉克利特的美学对雕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以对立为前提而回归于统一,这种动态的和谐使得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形体摆脱了早期古风时期——略显平直的造型——逐渐向更自然而富有张力的形体转化,现在我们见到的典型的S型雕塑样式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不同中求统一的审美化身。
其三,理念集中体现于柏拉图的审美论述中。在他设计的理想国中,柏拉图坚定地认为理念是先于现实而存在,客观的个别事物是由理念派生出来的[19],对现实持有虚幻、相对的观念而对理念永恒的理想真实的认定更使他坚信:艺术与美是对理想世界的一种模仿。[20]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具有超越现实事物的意义,它是一个具有恒定概念的理想。这种理念与中国战国时代为求治之序而向宇宙寻找的终极依据有某种相似之处,它给了古希腊古典时期雕塑极大的规定性,正是柏拉图理式的和谐存在,西方二千多年前的雕塑既塑造人物,又有取舍,取共同之美而舍个性之丑。显示了理性而相对写实的特征;既刻画现实又含共同的特征,呈现了一定的程式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的程式化正是柏拉图理念和谐的直接体现,正因此使得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形体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美而具有永恒意义。
其四,整体集中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和谐思想中。作为古希腊思想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基于哲学上宇宙统一性的思考,提出了形式整一形态的和谐。他的总体美学主张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调纯形式之美,指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提出完整性构成整体性,尤其是强调“艺术创作高于自然‘是在模仿给定的实在事物时要把它理想化’”[21]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创作高于自然的论证毫无疑问对雕塑形体的理性特征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亚里士多德对“纯形式化”(秩序、匀称、明确)的倡导对古希腊后期雕塑形体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指导性的影响,因此,其后期的雕塑越来越多注重外表的形式,形体逐渐脱离程式化而转向具体化的塑造,换言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谐是古希腊雕塑由古典转向希腊化的美学根源。综上所述,古希腊古典时期雕塑形体的分析、理性的特征、程式化倾向与当时的美学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以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是此时雕塑形体产生的内因之一,而雕塑形体是其审美的物化载体。
东西方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轴心时代”的雕塑,它们提供了一种精神——超越与永恒——的当代指导。超越是不尽的探索和宽广的胸怀。战国时代和古希腊时期雕塑在超越具体达到差异外化,正是艺术多样化的基本表现。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总是纠结或者在意某种形式是基本艺术素养的缺失。我们常常听见类似“民族精神”、“民族特色”的话语,殊不知,“可能性”的不尽探索是艺术存在的基本方式。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的融合和对话中,总是强调“自己”势必失去艺术的基本动力。甚至可以说,包括两千多年前战国雕塑与古希腊古典雕塑所呈现的人类雕塑仅仅是艺术的一个个视角,而非全部,更不能说从古至今雕塑的总和就是“雕塑艺术”。或许,以一个平和的心态看待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作品,感知其中蕴含的生命灵动更有价值。永恒是由“破”走向“立”的人性关爱。无论“气象飞动”的战国雕塑和“理性和谐”古希腊雕塑有多大的差别,其根本却指向超越具体人或物,走向人性深处的永恒。这种永恒既是作品本身传递的气质,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艺术是人与世界沟通基本方式之一。包括雕塑在内的艺术在经历二十个世纪之后不断“破”,在当代,世界或许需要的是“立”——基于个体生命境遇的真实体验。此“立”不是指固定,而是生命与世界的沟通交流方式——参与与表达。这是对基本的艺术规律尊重,更意味着对暴力思维的离弃,这对于当今世界艺术,尤其是中国更有价值。(本文作者:江林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 上一篇:水利设施的重要性范文
- 下一篇:小议象征主义对当代雕塑的启发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