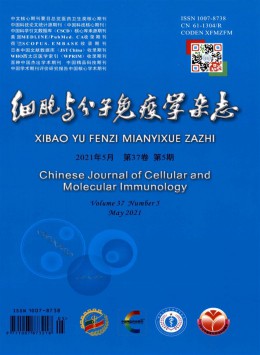克隆电影艺术的身份叙事探讨

摘要:克隆题材的科幻电影融合了神话原型的虚构性与当前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伦理价值反思,而此类叙事的互文性与自我指涉性则解构了故事的现实性,却又戏仿了历史文本的经典性。叙事主体的自我意识与文本话语之间的情感疏离造成了克隆个体对身份意识构建的无所适从,而电影叙事再语境化则消弭了传统叙事强调的神话原型与寓言性所导致的人类主体与克隆之间个体差异的修辞陷阱,并依托国际主义叙事策略创立了身份叙事的“第三空间”与文化差异的共存共荣。
关键词:身份叙事;神话原型;戏仿;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特别是克隆电影融合对社会现实的戏仿性和神话或寓言元素,通过蒙太奇、拼贴画与滑稽戏仿等叙事手法呈现作者的创作意图。J.G.弗雷泽在《金枝》(1890)中将神话与图腾追溯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相似律”和“触染律”并藉此剖析了神话原型的起源,而诺斯洛浦•弗莱则在《批评的解剖》中将神话原型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阐释。本文将借鉴原型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科幻小说中原型意象与叙事结构,阐述电影文本间身份叙事的影响焦虑症以及彼此间的互文性戏仿。詹姆斯•怀勒于20世纪30年代执导的哥特式影片《科学怪人》将神话或寓言意向推进新纪元,而肯尼思•布拉纳则于20世纪90年代忠实地将科幻小说《弗兰根斯坦》搬上荧屏并藉由克隆人他者的视角反思人性与艺术的审美价值,但近年来影片《逃出克隆岛》(2005)、《别让我走》(2010)和《屠魔战士》(2015)则戏仿他者化的身份叙事并超越了文本美学价值的界限,从而奠定了此类题材狂欢化的哥特式风格。
一、身份叙事的时空焦虑症
小说人物的身份叙事不在于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反思,而是存在于个体的叙述视角,制约着读者对此作出或同情或厌弃的心理反应。读者对人物的情感或生活场景深入了解之后,因为担忧其他剧中人物没有像叙述者那样耐心潜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就倾向于选择与其一致的立场身份对待周围的世故人情。影片《科学怪人》的叙述者医学狂人弗兰根斯坦将观众引入怪诞的神话梦境,而妄图创造人类的病态心理或动机将赋予其上帝创世的身份,显然与神话原型相悖,但通过叙述者的视角读者却感受到与文本的逻辑悖论似曾相识的亲近或怜悯之情。叙述者的时空焦距精心掌控着主人公的信息呈现方式,而影片的情节布局虽由全知视角聚焦却通过主人公的视野感受外界并感知弗兰根斯坦的情感变化。内视聚焦点的选择创造了让读者移情主人公性格的变换并藉此产生了怜悯之情,希望心灵瞩目的剧中人物能获得命运之神的眷顾。缘于剧中内视点的存在和聚焦,观众就不会与主人公的言行产生隔阂并在延续同情之时明晰他的缺点,从而避免了影片中单纯的审美价值评判。除此近距离聚焦的内视角之外,全知视角的叙述者也时而脱离剧情而站在观众的角度远距离审视并评判影片人物形象,如片头制片商毫不隐讳的警示之语:“卡尔•雷米尔先生觉得影片播放之前做好予以善意警告,即将讲述的故事涉及一个名叫弗兰肯斯坦的科学怪人,他寻求创造一个依照自己形象而设计的人而不是选择依赖上帝”。而这使观众震惊或惊骇的亵渎上帝之举则诱导观众近距离地进入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并见证他的真正动机。面对主人公唐吉珂德式的幻想与冒险,影片塑造了弗兰肯斯坦的授业恩师沃德曼博士智者的形象并让其不时对这一疯狂的创造人类计划指点迷津,而这一桑丘•潘沙式形象的出现将使主人公禁锢在伦理评判的籓篱之内直至其能够幡然悔悟。叙述者的讽喻式评介使影片产生了布斯所谓的“同情的笑声”,而观众与剧中人物形象的心理距离或情感隔阂也被不同叙述声音掌控了,“我们的距离—不管是视觉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被层层的转述声音和思维之间视角的微妙变化、被所给的或故意未给的信息所控制……从技术角度来讲,同情的产生和控制是通过进入人物内心及与人物距离的远近调节来实现的”[1](26)。情感反应机制的产生类似于戏剧独白的无限展演,在此剧情之中性情偏执的医科院学生弗兰肯斯坦无视伦理界限而执意创造新人类,而观众则寄托于他的未婚妻、朋友或老师的迷津劝诫,并以文本复调的形式展现了社会话语对个体的影响焦虑。人类制造的怪物盲目服从动物的本能和丛林法则,而他的造物主和同谋者则变身为温文尔雅的道德伪君子对自己的疯狂懊悔不已并坦然接受周围人物的善意和温情。此时的观众虽深知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却依然选择站在了弗兰根斯坦的立场,而这则源于影片藉由叙述者视角的缘由而实现的信息共享的身份叙事的构建。此时源于社会经验的价值判断将因主人公的悔过自新而产生戏剧反讽的效果,而影片针对弗兰根斯坦的求知欲望而运用的戏仿手段造成了他的疯癫与观众的理智之间的情感疏离与认同的缺失。布斯认为,“只有心智幼稚的读者才会真正与人物融为一体,完全失去彼此的距离感,因而也失去了所有的艺术经验的机会”[2](200)。叙述者内视点的聚焦造成部分人物主体身份的缺失而变为迎合观众情感期待的戏剧性戏仿,而他者化怪物审美聚焦的忠实再现则要等到更为贴近小说文本的电影《科学怪人之再生情况》的面世并将身份叙事的复调性与互文性完美融合。这种内视点的聚焦制约了观众在剧情中的道德立场,并通过彼此的共享策略而与主人公成为情感相通的密友,创造了超然于主流意识之外的同谋关系的幻觉。布斯却强调布莱希特式的戏剧展演过程的情感疏离,而观众也将因弗兰根斯坦性格方面的缺陷而无法实现身份的认同感,但同情他的记忆创伤和人生悲剧并希望能藉此避免重蹈主人公的覆辙。但观众何以在布拉纳执导的影片中产生对弗兰根斯坦行为的伦理价值质疑并与其创造的怪物建立同情纽带呢?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认为,行为主体既受到主流话语的制约,却又享受着行为者身份自由的幻觉,而文学艺术的价值评判功能则藉此控制观众的身份立场,不仅会激发他们的怜悯之情,还能净化情感并移情于行为主体的社会角色。主人公创造的怪物虽曾努力构建自我的身份叙事,学习语言知识与体验人类情感,甚至希望拥有朋友或伴侣的关怀,不同程度地触及了观众的身份认同并将自我意识投射于此剧情人物身上。观众由怜悯之情转变为叙事身份的强烈认同与自我的文化认同息息相关,而认同的效果更是源自于行为主体的身份性差异。劳拉•马尔维(LauraMulvey)利用拉康的心理镜像理论将电影叙事视为观众凝视客体行为并获取身份认同的自恋性快感,超越了布斯所谓的成熟的读者会与小说人物保持审美距离的观点并将他们视为异质化的群体,而观众的主体性则会与叙事结构中特定的异性角色分工导致的性别身份立场相互认同。[3](117)无论是怀勒还是布拉纳,他们所改编的科幻性影片都无法摆脱男性主人公与女性形象凝视与被凝视的心理镜像的窠臼。弗兰根斯坦与沃德曼博士所代表的男性形象承担着积极主动的凝视者形象,而伊丽莎白与卡洛琳等则变身为消极被动的客体意象。作为叙事行为的聚焦点,弗兰根斯坦作为凝视者是电影剧情的诱因,主动地审视女性作为男性力比多客体的性欲意象并通过伊丽莎白自我欲望的镜像反衬男性的本能欲求。马尔维将理想观众视为叙事立场的认同者,“男性偷看者被引进电影,窥视容易引起性欲的女性形象……它意味着一场电影对一个男性来说具有双重愉悦,视觉愉悦和叙事愉悦。对一个女人来说,它提供了与一个女性人物、一个由摄像机框定的形象、一个图像及一个男人注视对象的认同”[1](36)。但此种过分关注男性观众认同的叙事聚焦忽视了观众根深蒂固的文化身份的主体性,而男性与女性人物形象针对叙事主体性的竞争则因其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性而不得不转而聚焦马尔库塞笔下的叙事主客体之间的身份差异。然而,在迈克尔•贝与马克•罗曼内克分别执导的影片《逃出克隆岛》和《别让我走》中,前者的男女主人公林肯与乔丹和后者的剧情叙述者凯茜将马尔维对观众身份认同的心理镜像彻底击碎。无论弗兰根斯坦眼中的怪物还是林肯、乔丹与凯茜所代表克隆人类,他们都因其特殊性而被主流话语将指涉性的外在品质置换为行为主体内在性的情感反应机制,而这种貌似公正、客观的价值判断则被迫陷于行为主体、能指与他者的纠缠中,将任何异质化因素纳入了文本话语的运营机制。而弗兰根斯坦怀抱娇妻时的反思或者猎杀怪物的弥留忏悔,抑或是凯茜凝视恋人汤姆献祭生命时的怅然若失,都在颠覆者镜头聚焦点的全知视角以及其佯装的故事情节自我指涉的客观性。剧情的主观叙述性假借主人公之口突显了文本隐含的伦理判断和观众期待的叙事声音,而故事结局之巧妙也将剧情的后现代式的开放性则诱发了观众微妙的心理期待和社会责任感。
二、叙事主体的身份危机
叙事主体将文本的历史语境视为贯穿社会写实主义所遗留的历史残片并击碎了文本批评的作者意图,而结构主义者所推崇的语言结构的共时性形态差异最终为德里达的“延异”所替代,而且“此在”本身也成为跨越过去与未来并突显时间差异的指涉性幻象。改编自玛丽•雪莱经典科幻小说的电影情节通过截然相反的结局颠覆了善与恶之间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也驳斥了贝与罗曼内克如上帝般随意掌控文本的权力。此类将克隆人或个体他者作为叙事主体延续了历史文本的互文性戏仿,而《逃出克隆岛》与《别让我走》所置换的他者化视角的内视点解释了历史文本对作者的影响焦虑症。布雷德伯里指出,互文性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漂浮的能指时代与一个戏仿与拼贴、疑问与引用的世界,充斥着粘连的文本单细胞网络、哲理性思考、人性悲剧与感伤情绪并扮演着讽刺或幽默的滑稽角色,而这种本文并置的双声或复调的杂糅结构突显了作者的语义或价值观方面的写作意图。[4](271)德里达曾抨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认为如果凭藉排除疯癫的主观性策略人类理性时代就会自我构建的话,那么历史文本的本源性与经典的叙事就会丧失权威性特权,但彼此却都认同历史文本的差异性不可简化为纯粹的单一性叙事中心的观点。[5](42)因为经典“存在”的瞬间性作为叙事主体的排他性结构试图在语义符号周围建立自我意识的界限,并清除了文本叙事在此前或之后构筑的能指性标识。如此一来,叙事主体的本源性即被主流话语赋予了神秘性,而符码结构的差异则变身为叙事性强加的文本幻象。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文本作为主观性建构,背负着叙事主体强加的文本价值观,而不是现实主义式的真实反映,并通过对目标文本的解构与戏仿转而强调文本的自我意识与叙事主体身份焦虑的涤荡。德里达的叙事“补充性”(supplementarity)概念为读者提供了与历史叙事的本源性相对立的权力机制,断绝了文本主体赖以存在的形而上的线性结构与排他性意识,并补充了叙事他者的身份缺失现象或隐藏的语境。上述影片中被主流话语排除在外的他者化故事补充并颠覆了常规叙事,而文本的阐释更是与科幻小说《弗兰根斯坦》,特别是近百年以来此类题材的影视改编背后所隐现的道德伦理的演变密不可分。怀勒与布拉纳的影片强调了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人类对科技与知识的疯狂欲求对伦理价值的毁灭性影响,并将叙述的内视点置于科学狂人弗兰根斯坦的角度反思生与死的生命奥秘。反观贝与罗曼内克的影片,叙事主体的聚焦点放在了社会他者的身上,突显了主流话语对他者化个体意识的关注,更加注重人性或个体身份的人文探求。但斯图亚特•贝亚蒂耶执导的《屠魔战士》更侧重主人公亚当充当人类救世主的玄幻性与好莱坞影像效果,而欠缺细腻的对人性身份的文化思量。个体身份作为想象性的意象,支撑着主流话语的运行机制并承载着诸如战争与冲突等社会现实经验,而此类认同的纯粹性则迫使其清除内部非整体性或非主流的价值体系并使主人公亚当他者身份的逐渐边缘化。玛丽•雪莱经典小说的影视改编过程中,主人公弗兰根斯坦所代表的个体意识凝视着镜中的自我意象,并将其创造的他者化形象的身份特殊性或者灵魂的缺失视为邪恶的动物本能的体现,正如怪物对人类造物主的诘问,“我懂说话及阅读及思考并懂得人的作风……你给我这些情感,却不叫我如何运用”。作为社会的他者化意象,怪物拥有生前的社会记忆、怜悯之心及憎恶之情,而这些皆源自人类对自我或内心恶魔的敬畏或恐惧并将之视为天使或撒旦的载体。霍米•巴巴谈到旅行理论时称,社群的时空迁移在书写中呈现双重性叙事,而个体行为者既是民族主义教学的历史客体,也是生产意义的主体,赋予自我身份意义的同时也抹去了本民族的先验性或主体的存在痕迹并表现为不断重复与再生的过程。[6](297)同样作为社会他者的林肯与乔丹所代表的克隆人被人类科学家圈禁在神秘岛,并被告知他们是地球污染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在克隆过程中植入了类似的社会记忆并随之接受学识教育和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而最终的命运却是为母体提供替代性器官。反观凯茜代表的黑尔森克隆学生,他们作为社会边缘群体同样承受主流话语的影响,虽心有不甘却自愿为病痛中的人类献祭生命。克隆性他者面对主流话语的影响焦虑却选择了不同的实现身份叙事的方式,因为叙事主体的身份取决于主流话语权并决定知识与真理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他者的克隆群体通过神秘岛或黑尔森的学识教育认同了主流价值观,并逐渐被陌生化与边缘化而成为基于某类特殊的自然性特征而衍生的想象性的“他者”。他者身份的典型化则依赖林肯与凯茜等人物形象参照外部社会对其自我镜像的反应而构建并认可了权威机构预设的自我行为的反常性与差异性。身处流散困境的边缘个体最终将“从文化的帷幕后面‘整体性’地走出来,在殖民者的强力下被继承碎片,镶嵌在自身的价值承诺和其所生活时代的文化争端之中,并由此着床和深陷于殖民者打造的关系网络之中”[7](236)。他者化个体的叙事身份呈现出碎片化与断裂性特征,比如影片人物林肯与乔丹身份意识的觉醒过程以及反抗邪恶科学家梅列克博士的身份操控时,他们同样也接纳了统治阶层的话语并寻求机械师麦克的善意引导直至逃离生天并重见光明。克隆他者无法操控或重建自身所代表的文化与意识的运行机制,因主流话语的影响而变为身患失语症的他者而造成了集体的自卑情结,即使逃离克隆岛也将消弭于主流话语控制的“文化杂种”的身份意识。影片人物凯茜所在的黑尔森学校却倡导克隆学生限制性地接触人类社会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但对文化习俗的接纳并未塑立其独特的身份意识,反而阻碍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在与人类接触的过程中从未完全抵制话语的影响焦虑症,而是选择鹦鹉学舌式地关注电视或周围人群的行为举止。事实上,文本叙事强行植入主导型话语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个体对话语权的反驳或遗弃,无论是《逃出克隆岛》中主人公的革命性反叛还是《别让我走》中对话语权的顺服。他们为此而采取的颠覆性策略则是选择对强势文化进行滑稽性戏仿,而诸如待人接物、友谊与爱情或者酗酒寻欢等日常行为无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模仿,却又在自我意识的意象中形成颠覆性变异或者构成霍米•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自我”与“他者”们之间中心—边缘的对立性关系通过神秘岛的强力统治或黑尔森的话语权控制将克隆性他者的独立思想与自我意识排除在外,并刻意地忍受他们对主流话语的颠覆性变体与“第三空间”带给林肯、乔丹和凯茜们的身份自主的想象性快感。身份叙事反对传统叙事将神话与民族历史作为集体记忆使身份合法化的策略,而是选择与那些异质化的故事相共存的国际主义身份并且无需排除其他的群体或者寻觅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人类的历史就仅在于将具体的民族叙事转变为人类群体的整体叙事即可。
三、结语
当代学者詹姆逊称,当前的社会体制已经丧失了保存传统的能力,并开始生活在永恒的现时与持续的变化之中,终将会磨平各类社会形态的历史记忆,而历史意识的缺失与空间层次等级的抹平将时空压缩为平面化的共时性并因经历多样化的他者化差异而自鸣得意。[10](179)电影剧本对小说《弗兰根斯坦》的改编以及《别让我走》将故事置于历史语境,但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性时刻提醒观众当下时代的紧迫性,并通过集合了历史意识的叙事文本以集体记忆的方式融合了现实的社会经验。这种颠覆线性时间的历史意识将激活历史文本的叙事并将其置于当下的社会经验,而贝亚蒂耶的《屠魔战士》可谓此类电影文本的典范。影片将主人公亚当置于启蒙时代科学狂人弗兰根斯坦创造怪物的再语境化,而后追随莉奥诺王后率领的石翼兽天使抵抗纳比利斯王子代表的恶魔军团毁灭人类的阴谋,为剧情蒙上了神秘的玄幻性,却不时跳转至医学博士韦德小姐研究克隆技术的现实场景。这种针对现实经验对历史文本的再利用将会形成互文性自我指涉,反映了影视文本时空压缩的再语境化并造成了叙事在时间与空间的线性逻辑层面的凝滞与颠覆。文本叙事的时空共时性将互不所属的符号能指拼凑成众生喧哗的认同体验并将观众变身为拉康所谓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丧失了以同质化的线性时空意识经历文本语义的鉴别力并陷于永恒的现时状态。
参考文献:
[1]柯里,马克.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Booth,Wayne.TheRhetoricofFiction[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1.
[3]Mulvey,Laura.VisualPleasureandNarrativeCinemainContemporaryFilmTheory[M].LondonandNewYork:Longman,1996.
[4]罗斯,玛格丽特.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M].王海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Derrida,Jacques.WritingandDifference[M].TransA.Bas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8.
[6]Bhabha,Homi.NationandNarration[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89.
[7]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Lyotard,Jean-François.TheDifferend:PhrasesinDispute[M].Trans.G.VandenAbbeele,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8.
[9]Jameson,Fredric.PostmodernismandConsumerSocietyinModernism/Post-modernism[M].Ed.P.Brooker,LondonandNewYork:Longman,1992.
作者:李厥云 杨花艳 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