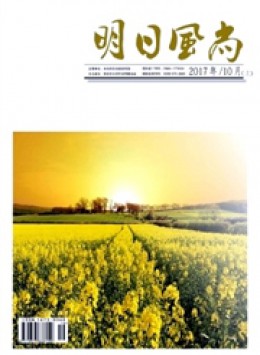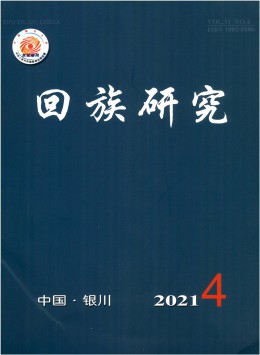族群文化研究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族群文化研究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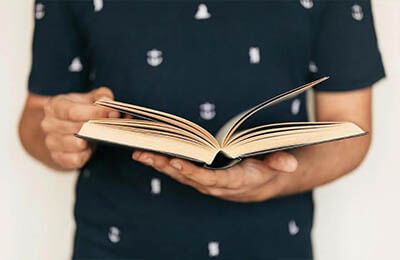
第1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文化适应;多维模型;族群关系
【作 者】张劲梅,心理学博士,昆明理工大学讲师。昆明,650093;张庆 林,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北碚,40071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号】1004-454X(2008)04-0082-006
Multidimensional Acculturation Model and Ethnic Croups’Relationship Researches Abroad
Zhang Jinmei,Zhang Qinglin
Abstract:Multidimensional acculturation model includes dimensions o f host and non-dominant group members’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The implicat i 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 not only consists in a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 ing of acculturative process,but also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on of et hnic groups’relationship through a study on the 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 of h ost group members and non-dominant group members
Key words:acculturation;multidimensional model;ethnic gro ups’relationship
在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各族群的相互交往、族群成员间相互接触、各种民族文化的相互 碰撞是必然现象。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接触所导致的群体及其成员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变 化被称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文化适应表现出两个要点:一是文化适应产生的条件是各文化间持续和直接的接触或相 互交流;二是文化适应的结果是接触的人产生了文化或心理现象的某些改变。文化适应包括 两个层面,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和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群体层面的文化适应包括社会 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而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包括认同、价值 观、态度和行为能力的改变,即个体所经历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新环境的最终适应①。心理 学 领域的文化适应主要以个体层面为主,研究者们提出了文化适应的模型理论并且进行了实证 调查。文化适应多维模型是在一维和二维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的实证研究少于另 外两个模型,但是其理论和实际价值不容忽视。
一、多维文化适应模型
一维模型最初是由帕克和米勒(Miller)在1921年提出,而后得到戈登(Gordon,1964)等人 的进一步发展②。戈登的一维模型把文化适应中的个体看作是处于一个连续体中,一端是 保 持原文化,一端是原文化的丧失而接受主流文化,在这一连续体的中点上就是双文化现象, 即个体既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又接受了基本的主流文化。但是戈登认为双文化状态 是暂时的,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原有的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被主流文化中 的这些方面替代,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受到原文化的影响就越小,而个体文化适 应最终的结果必定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③。
二维模型把移民本族群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为作为独立的维度进行描述。作为二 维模型的开创者,贝瑞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面临两个基本问题:1.是否趋向于保持本族 群文化传统和身份。2.是否趋向于和主流群体接触并参与到主流群体中。通过个体对这两 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y) 分为四类,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 alization)④。所谓文化适应策略就是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与新文化直接接触过程中面对 新 文化冲击和文化变迁所采用的态度或应付方式。当非主流群体中的个体不想保持对自己文化 的认同但寻求与其他文化的日常交往时,就会采取同化策略;当个体注重保持自己原文化而 同时避免和其他文化交流时,采取的是隔离策略;如果个体既保持自己的原文化又保持和其 他群体的日常交往时,个体采用的是整合的策略;而个体如果既没有保持自己文化的兴趣又 不想和他群体有联系,个体采用的策略就是边缘化。贝瑞认为个体最为理想的文化适应策略 是整合,而最为消极的策略是边缘化。一些对贝瑞四类文化适应策略的研究也证明个体最为 偏向的是整合策略⑤⑥,采用整合策略的个体所经历的压力也比采用边缘化策略的个 体要少。⑦
但是,对非主流群体来说,文化适应策略采取的前提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但事实上主 流群体可能施加某种文化适应模式的影响从而限制了个体的选择。因此,这引起了多维文化 适应模型的提出。
贝瑞也在原来的两维模型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成员文化适应的 影响。主流群体珂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取向会表现出四种态度:多元文化主义,熔炉主义 ,隔离和排斥⑧。当主流群体要求非主流群体采取同化策略时,称为“熔炉主义(melting
pot)”;当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强加分离策略时,称为“隔离(segregation)”;强加边 缘化策略时称为“排斥(exclusion)”;而整合策略的取向称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 ralism)⑨。
布瑞斯(Bourhis)等人也认为二维模型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适 应取向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国家或主流群体采取的一些整合政策对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 应取向具有重要影响⑩。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布瑞斯(1997)提出了一个文化适应的多维 模型,并命名为“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the interactivea cculturation model)。该模 型试图整合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主流群体的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所持的态度,以及文化群 体中人际和群际的关系。
首先,布瑞斯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贝瑞的二维模型的第一个维度是测量移民文化 认同,测的是态度,第二个维度是行为倾向,虽然和前者有所差别,但是还是态度的不同类 型。实际上,前者和本群体文化认同的价值有关,而后者和与他群体的跨文化接触的价值有 关,因此,布瑞斯修改了第二个问题,把“是否值得保持和主流群体的关系?”改为“接受 主流文化是否有价值?”。而且,他认为原来贝瑞划分的边缘化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文化适应 取向,即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因为有些移民把自己从原文化和主流文化分离,可能 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被两个群体所排斥,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个体而不是归 属于移民群体或主流群体的成员。他们拒绝归属于某个群体,而且也倾向于把他人看作是个 体而不是群体的成员。同时,他认为这种移民可能更会出现在崇尚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 的价值观取向的文化中。
此外,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包含了主流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倾向维度。主流群体成员的 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他们对有关移民文化适应的两个问题的态度:1、是否可以接受移民保 持自己的文化传统?2、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体的文化?根据主流群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 答,主流群体可能表现出5种文化适应取向:
当主流群体成员既接受和尊重移民保持原有的传统文化,又赞成移民接受重要的主流文 化特征时,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种整合的取向。
如果主流群体成员把自己和他人定义为个体而不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如移民群体 成员或主流群体成员,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体的个性和成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身份,或保持 原文化和接受主流文化,那么采取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策略。
如果主流群体成员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而期望移民为了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而 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那么就是一种同化的策略。
如果主流群体成员赞成只要移民保持和主流群体成员的距离就可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 ,因为他们不希望移民采用、“污染”或改变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种隔离的策略。而且本 质上,该策略仍然是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
当主流群体不能容忍移民保持原文化,也不允许移民采用或改变主流文化,就是一种排 斥的策略。其本质仍然是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如下图所示:
布瑞斯模型的意义在于对贝瑞的模型进行了补充,把主流群体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纳入到 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关注了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群体的影响。虽然多 维模型变量多过导致研究复杂,目前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显著少于二维模型,但是多维模型的 理论和研究意义不容忽视,尤其是对族群关系研究的启示。
二、文化适应多维模型与族群关系的理论假设
族群关系的变化实际上会受到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裹有的是直接 发生作用、很容易观察到,有的则是间接的、隐藏在其他因素的背后,很容易被忽视。而且 经常是各种内因、外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B11。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反映了 其中的 心理因素和主流群体对待其他族群的宽容度,涉及了两个族群相互融入和相互接纳的态度和 方式。
文化适应多维模型提出非主流群体和主流群体间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的冲突和一致直接影 响了两群体间的关系。当主流群体成员和非主流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较为一致时, 两者的关系趋于和谐,而当处于不一致的情况时,两者关系趋于产生矛盾和冲突。
布瑞斯图解说明了主流群体成员和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会导致怎样的族群 关系B12:
从图表可以看出,当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采取的文化适应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当主流群 体和移民群体成员都偏向于整合策略时,那么就可能产生和谐的状态。当两个群体的文化适 应取向不一致时,例如移民群体想要整合,而主流群体却采取隔离的态度,就会产生不和谐 和状态。
一致和不一致的文化适应取向导致了移民个体和主流群体成员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在社 会心理层面上,这种关系结果涉及了族群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族群态度和刻板印象、文化 适应压力、以及在诸如就业、教育、政策和司法公正等方面的歧视。
正如上图所示,移民和主流群体文化的关系是处于一个连续数轴上,和谐的关系为轴的 一端,问题的关系位于中点上,冲突的关系在轴的另一端。
当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成员都采用整合、同化或个人主义的文化适应态度时,他们之间 的关系是协调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在大部分领域中两个群体间会存在积极的族群关 系。例如,就社会心理层面来说,这种积极的族群关系包括了积极有效的言语或非言语跨文 化交际、较少族际紧张形势、相互间积极的族际态度和刻板印象、低文化适应压力、且主流 和移民群体成员间几乎不存在歧视现象。
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取向如果不一致,就会产生另外两类关系结果:问题关 系或冲突关系。
当两个群体对文化适应取向存在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时,两者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 其中两种常见的问题关系结果是因为移民群体成员偏向同化取向,而主流群体成员却宁愿移 民采取整合的策略,或者恰恰相反,移民期望整合,但是主流成员坚持同化策略。这两类问 题关系结果会引发两个群体的交流失败,引起消极的群际刻板印象,导致歧视行为,产生尤 其是移民成员的中等程度的文化适应压力。当处于整合或同化取向的主流社会中的移民群体 成员采用边缘化或个人主义策略时,问题关系结果也会出现。同样,偏向于个人主义策略的 主流群体成员和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群体身份的移民(不管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是整合、同化 、分离或边缘化)之间也会存在问题关系结果。
采取分离策略的移民与多数主流群体成员之间会产生冲突关系,尤其是那些采取隔离或 排斥态度的主流群体成员。采取隔离和排斥策略的主流群体成员与移民之间易于产生冲突关 系,而且排斥者比隔离者与移民的关系更可能更消极。除了与移民之间的交流障碍,排斥者 和隔离者更容易对移民产生更消极的刻板印象,而且更容易在诸如就业、住房等领域更加歧 视移民。此外,排斥者最可能发动对移民的种族歧视袭击,组织政治活动诋毁、驱逐移民。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可能经历更多的文化适应压力。而采取分离态度的移民最可能抵制,甚 至报复主流群体的迫害。因此,排斥性的主流群体成员和分离性的移民最可能出现最多的族 群冲突。
但是,布瑞斯等提出通过国家多元文化的整合政策可以削弱族群关系的冲突程度,相反 ,种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可能加剧族群关系的冲突。而同时,布瑞斯的模型表明,即使国家政 策反映了多元文化意识或公民意识,主流群体中仍有一部分人可能保持隔离或排斥的态度。 同时主流族群也可能影响国家采取的整合政策,主流族群的文化适应取向与其对国家意识形 态的支持相对应,例如具有整合文化适应取向的主流成员可能支持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因此 ,正是国家整合政策、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三者的结合导致了族群关系 的结果。对此,李凯德(Liebkind,2001)评论认为该模型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考虑了具有不同 移民和整合政策的国家中移民和主流群体的交往问题,从而强调了文化适应过程中族际关系 的性质B13。
简而言之,多维模型反映了主流族群与非主流族群各自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对两者族群 关系的影响。当主流族群倾向于采取一种基于对非主流族群文化认可而允许其融入主流群体 的策略、或强调移民的个体性而不重视其族群属性的策略,而同时又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 一致时,就可能产生和谐的族群关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与移民的取向不一致 ,而同时主流族群又不认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许其融入,那么就可能导致两族群的关系 出现问题或发生冲突。
三、多维文化适应模型与族群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前来说,虽然多维文化适应模型更全面的剖析了文化适应的现象,但是由于纳入的变量 过多,所以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之二维模型的相关研究较少。
运用布瑞斯的交互文化适应模型进行的有关研究证实了这个模型对族群关系的预测。巴 雷特(Barrette)等使用布瑞斯等所编制的主流文化适应量表(host community acculturatio n scale)和移民文化适应量表(immigrant acculturation scale)对巴黎郊区大学的学生进 行调查。结果发现来自于法国主流群体的大学生最趋向的文化适应策略是整合和个性化,最 不趋向的是隔离、同化和排斥策略:而北非裔移民大学生更偏向整合、个性化和分离策略, 同化和边缘化是采取最少的文化适应策略。分析结果显示,采取整合和个性化策略的主流族 群和北非裔大学生认为自己和其他族群关系融洽,而采取隔离和排斥策略的主流族群大学生 和采取分离策略的北非裔大学生趋向于认为自己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和冲突 B14。
而且该研究还发现主流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移民被尊重的地位,亚裔移民比北非 裔移民更被尊重,因而法国主流大学生对前者更倾向于整合和个人主义的态度,而对后者更 倾向于同化、隔离和排斥的态度,这似乎证明了梅的设想:当主流群体平等地看待移民时, 采取的是更为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而如果主流群体认为移民文化次等或劣等,那么采取的 就是消极的取向。
多维文化适应模型也被用来研究原住少数族群与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以及关系。有研究 发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大学生主要采取整合和个性化策略,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以色列的 原住少数族群)比俄罗斯裔和埃塞俄比亚裔的犹太移民表现出更多的隔离和排斥取向。犹太 移民和以色列阿拉伯人都很少采取同化取向。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采取整合和个性化策略的大 学生包容族群差异,具有安全感,没有社会强势意识。整合和个性化策略持有者不仅不会感 到受到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威胁,而且会被认为是以色列的永久公民和工党的支持者,而不被 认为是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相反,采取同化、隔离和排斥策略的个体会感到不安全,较少 包容族群差异,更易于具有社会权势意识。而且除了感到被以色列阿拉伯人所威胁外,他们 回避与俄罗斯裔和埃塞俄比亚裔移民的亲密关系B15。
对德国主流成员和移民(学生)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某一族群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移民 与主流成员策略偏向的相对一致,两者对族群关系都具有预测能力。而总体上,整合策略与 两个族群间较为积极的关系有关,而两个族群间文化适应策略偏好不一致产生了消极关系结 果B16。
此外,也有研究显示两个族群都采取整合策略对移民和主流族群成员的族际态度具有积 极影响B17,而采用同化策略的主流族群成员和采取整合策略的移民之间的关系更可 能出现问题B18。
四、多维文化适应模型对族群关系研究的意义
目前多维文化适应模型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且不可否认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很多 ,因此并不可能把主流族群和非主流族群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的一致与冲突看作是唯一或最 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可以认为的是,不同族群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族 群关系表现出不同结果。因此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可以部分反映族群关系状况。但是究竟主 流群体和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族群关系的变异,这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探索。而且目前的相关研究多数仍然是以学生为研究对象,那么运用到普通人群 中,研究不同阶层、文化程度、年龄等等的人群,多维模型究竟又具有怎样的预测效度,这 也需要采集不同样本进行研究。
总之,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不仅是测量主流群体和非主流群体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的理论 依据,同时也可以被用以预测族群间的关系结果。而该模型更大的意义应该在于通过研究影 响族群关系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向,在进行族群关系预测的基础上,可以建构干预措施,改变 族群间的不良关系,从把出现问题和冲突的关系改善为和谐一致的状况,从而真正实现当今 多民族和多文化国家所倡导的多元文化和谐社会。
注释:
①Berry,J.W. et al.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n and applicati o 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217-218,273-274.
②Flannery,W.P.,Reise,S.P.,Yu,J.,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ac cultu ration models [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1,27∶1035- 1045.
③Bourhis.R.Y.,Mooese,L.C.,Perreault,S.,Seneacal,S.,Towards
an i 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J],Internatio 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1997,32(6)∶369-386.
④Bersry,W.J.,et al.,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 c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Vniversity Press.1999∶278.
⑤Barrette,G,Bourhis,R.Y.,Personnaz,M.,Personnaz,B.,Accultura tio n orientations of French and North African undergraduates in Paris[J],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4,28∶415-438.
⑥Bourhis.R.Y.,Dayan,J.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 towards Israeli A rabs
and Jewish immigrants in Isra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4 ,39(2)∶118-131.
⑦Berry.W.J.,Acculturation: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relations,2005a,29∶697-712.
⑧Berry,W.J.,Poortinga,Y.H.,Segall,M.H.,Dasen,P.Cross-cult 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M],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354-357.
⑨Berry,W J.,Acculturation,in Friedlmeier,W.,Characanrath,P.,&
Schwarz ,B.(eds.)Cultural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Importance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to thc Social Sciences[M],NY,Psychology Press. 2005b∶298.
⑩Bourhis,R.Y.,Mooese,L.C.,Perreault,S.,Seneacal,S.,Towards
an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J],Internat 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1997,32(6)∶369-386.
B11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465.
B12Bourhis,R.Y.,Mooese,1.C.,Perreault,S.,Seneacal,S.,To war ds an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J],Int 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1997,32(6)∶369-386.
B13Liebkind,K.Acculturation.In Brown,R.& Gaertner,S.L. (eds.)Blac 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Intergroup Processes[M],Oxford,Blackwe ll.2001∶386-406.
B14Barrette,G.,Bourhis,R.Y.,Personnaz,M.,Personnaz,B.,Ac cult uration orientations of French and North African undergraduates in Paris[J],I 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4,28:415-438.
B15Bourhis,R.Y.,Dayan,J.Acculturati on orient ations towards Is rae li Arabs and Jewish immigrants in Isra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 gy,2004,39(2)∶118-131.
B16Zagefka,H.,& Brown,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lturation
st rategies,relative fit and inter group relations: immigrant-majority relations
in German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2,32(2)∶171-188.
第2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摘要】无论是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还是出于弘扬本民族文化的考虑,旅游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都是不争的事实。文章针对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通过田野调查法,运用旅游情景下的族群认同测定模型这一动态系统,分析目的地族群认同在受到外部经济、文化环境与内部族群认同成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变化。研究发现:吐鲁番葡萄沟在长期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互融合中,旅游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助推作用,民族认同感得到提升。
【关键词】旅游;族群认同;影响;田野调查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5.06.00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为一种普遍的消费行为。旅游的发展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族群传统文化的保护、族群认同重构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碰撞等,尤其是族群认同问题受到人类学、旅游学等方面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本研究基于旅游情景,考量族群文化、族群认同的变化,对发展地方经济和弘扬民族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针对吐鲁番葡萄沟这一地区的族群认同研究,也符合“一带一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发展经济的理念,体现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共赢的精神。
一、对于族群认同的研究综述
“认同”原本属于哲学范畴,后来在心理学中被频繁应用。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而今,社会科学的学者从各种视角研究民族内部的认同感,“认同”一词便被普遍应用起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族群认同必须在民族互动中才能得以产生,在与外界隔离的孤立的群体中不会产生族群认同,而旅游的过程恰恰实现了这种民族之间的互动。旅游通过经济活动的形式不断改变着目的地族群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族群文化也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影响了族群社会的环境系统,从而导致族群认同发生改变。在本研究中,把族群认同认为是族群的身份识别与确认,也就是指族群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依附[2]。
二、研究背景
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族群认同的影响受到国内外旅游人类学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目的地族群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认为旅游的日益发展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族群认同产生影响,但是对如何测定旅游情境下族群认同变化这一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并且目前针对旅游对新疆地区某个旅游社区族群认同影响的个案还尚未有学者进行研究。
目前,以旅游情景下目的地族群认同变化规律的研究最多。吴其付研究发现,民族旅游既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民族的文化认同[3]。陈刚在研究中发现,泸沽湖摩梭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交流和融合加强,当地居民的族群认同被强化[4]。黄瑾则在对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的研究中发现,随着旅游的发展,居民可以利用屯堡文化获得经济利益,从而族群认同就被重新建构起来,族群意识重拾并且被强化[5]。以上学者的研究都强调了旅游对民族认同的强化作用,体现出旅游与族群认同之间的正相关作用。周丽洁则从旅游与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旅游发展能使社区自发地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6]。区别于前者的是,孙九霞选择了三个个案进行对比分析,她认为,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旅游开发强度的目的地社区,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7]。那么,针对吐鲁番葡萄沟这一旅游社区,旅游与族群认同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维吾尔族的族群认同?
三、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的测定
综合人类学、旅游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本研究主要是根据陈修岭提出的旅游情境下的族群认同测定模型[8]分析旅游情境下族群认同的变化。模型以族群认同成分为基点,以族群认同理论为依据,以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要素为情景,从而进行构建。族群认同的成分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态度、族群归属感和族群卷入(文化实践和社会参与)等不同的维度,是动态的多维度的结构[9]。因此,本研究把握的一个理论方向,就是必须把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放在一个情景中系统化地进行分析。族群认同的成分,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族群其认同状态直观体现的参数。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在特定情景下族群认同感的强弱变化。
影响族群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旅游情景下的族群文化变迁。在旅游目的地社区,通过旅游者和参与到旅游中的当地居民的接触与交往,外来文化与族群文化不断地交互影响与融合,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旅游文化。这种具有多元化形态的旅游文化不断渗透到当地族群社区,改变着族群原生文化,甚至引致族群认同重构[10]。
四、 田野调查
第3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开幕式上,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教授和《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分别致辞。顾功耘指出,政治学是华东政法大学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日前中国社会处于重要的转型期,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和命运,尤其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与探讨。在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比较视野下的民族与族群政治研究”学术研讨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政治学介人民族研究的一种必然结果,政治学与民族学的紧密联系,对于未来的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政治学研究,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研讨会从民族与族群政治基础理论的宏观层面、制度机制的中观层面,以及现实民族问题的微观层面进行了两整天的大会讨论与交流。学者们各自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同时围绕议题展开深入的对话。
1.民族与族群政治的基础理论研究 在民族与族群政治的基本理论环节,严庆教授探讨了族性与族群政治动员及相互关系,提出如何调整族性在国家政治中的效应的问题;常士間教授指出,我国“两个共同”的民族政治理念及独特模式在中华民族复兴与国家建设上具有重要价值,其特征是由内及外实现价值的政治整合;叶江教授从社会认同的视角出发,指出在我国“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虽然曾导致阶级问题扩大化,但却建立了一种超越各民族本身更高的认同,提出目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实质应该归纳为“各民族在自身民族群体认同基础上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在民族及民族主义理论环节,朱伦研究员认为民族主义源于自由主义对于治理需求下政治场域的划分,指出应从公民、地方社会共同体及民族共同体三个层面建构国家;刘泓研究员梳理了民族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理论的关系,对是否存在系统和规范的民族主义理论提出质疑;高奇琦副教授论述了阿甘本政治哲学思想对民族理论的启示,总结指出民族问题上存在着无公民身份的少数族群和有公民身份的少数族群,他们分别面临着公民权问题和例外状态下的潜在侵犯问题。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族群政治环节,王建娥研究员考察了国家建构过程中少数民族与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互动博弈的过程;马俊毅副编审考察了不同国家差异化的民族概念及形成过程,对于中国的亚国家层次民族概念主张称之为“族元”(national ethnic-unit);姚尚建教授对族格理论做了补充解释,认为在中国,民族政治发展是承认民族族格之后,以国家和民族交互发展实现国格与族格的内在融合。
2.民族与族群政治及制度模式研究 佟德志教授总结了当代西方主流民主模式下包容族群政治的制度探索及相关问题,包括个体权利和群体权利,多数制与比例制,同化共识、交叠共识、底线共识、协商共识等内容;高春芽副教授论述了西方族际政治的协和民主模式及其特点、优势;田钒平副教授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中要重视共性文化的根基和纽带作用;王剑峰副研究员将各国治理族群冲突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即同化与吸纳、排斥、多元主义;杨仁厚教授指出,应加强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建构性研究并继续完善这一制度;张殿军副教授指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应该是权力而不是权利,目前自治权的一些规定存在着模糊性,应进一步完善;周少青副研究员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效果进行了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的研究;游腾飞博士比较论述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美国的族裔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同;杨友孙教授指出我国的民族权利保障和民族政策的发展完善应该引入社会融入的视角。
3.移民与城市民族问题研究 在移民与城市民族问题研究中,余彬博士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对于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功能重置进行了研究;阎照祥教授对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与爱尔兰不列颠主流群体的暴力冲突进行了论述;陈玉瑶博士论述总结了法国移民问题与移民政策的演变;来仪教授对我国城市民族问题的现状和特
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良警宇教授对流动的少数民族纠纷的内在发生机理及具体动因进行了研究;郝亚明副教授对于西方族际居住隔离研究进行了论述和总结;梅祖蓉博士对美国黑人的权利运动做了历史回溯与研究。
4.文化、宗教、人类学及相关研究 王金良博士对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回溯与论述;张三南副教授运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现代化背景下客家民居与人伦关系的变迁进行了田野考察与分析;赵光锐博士对西方的藏学研究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观念史的梳理;刘琪博士对“切糕”事件进行了人类学分析。此外,于红副研究员对土耳其民族理论家的奥兹基瑞姆的民族主义研究进行了介绍;王坚论述分析了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在过度发展后走向了政治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过程;包胜利副研究员研究了蒙古国民族主义的态势及其对中蒙关系的影响;章远博士对于东盟在区域宗教问题治理中的角色拓展进行了研究。
对于本次研讨会的学术讨论,《民族研究》编辑部副编审马俊毅作了总结。她指出,“比较视野下的民族与族群政治研究”的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作为亚群体的民族、族群的认同和政治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拓宽民族理论的研究视野,突出其民族政治学的特质;可以更深刻地剖析我国的民族和族群政治,在概念、学术话语上与世界接轨。第三,政治学应该加强对民族与族群政治的研究。我国建构现代多民族国家过程相对顺利的转型经验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应该作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此外,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高奇琦指出,比较政治学十分注重研究方法,并且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系统而科学的方法,将其引入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研究十分必要。
不断借鉴、汲取多学科的前沿成果、方法,使民族理论研究日益趋向国际化、跨学科性、学术前沿性及创新性,这是民族理论学科和本次会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鉴此,在闭幕式上,《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提议,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建立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设立“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论坛”,明年将择定相关主题继续研讨,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响应。
第4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民族认同;少数民族;高中生;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1 — 0077 — 03
1 引言
认同的建构作为青少年的首要任务,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还包括对本民族成员的感知和概念。〔1〕民族认同对少数民族高中生极为重要,由于在他们的生命阶段,种族划分作为其首要的构造,并且潜移默化中强烈地影响其日后发展的多个方面。Phinne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行动,过往的研究都关注于狭义的本民族认同,〔2〕更广义上的民族认同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个体对自己既作为单一民族的成员同时也作为国家民族的成员身份的自我确认,表现为对本少数民族和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义务感。〔3〕民族认同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过分极化的民族认同常常会诱发其产生偏离常态标准的行为,同时导致该群体的狭隘思想的形成,严重影响其日后的行为塑造。而降低问题行为的发生,促使少数民族高中生适应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应试图探寻少数民族高中生中华民族认同的根本诱因及其内部的心理加工机制。少数民族高中生处于生理和心理成熟的过渡期,随着生理的成熟,其行为变化和心理发展都相应地呈现出动态的特征,其民族认同的过程定然受到个体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国外的研究借助观点采择的理论,指出美国少数民族青少年认同过程中的三个阻碍因素,并且提出了少数民族高中生认同的五步干预模型。同时,国外针对来自相同区域和相同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种族人群进行了民族认同问题的相关探讨,〔4〕对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国内对于此类研究的深入性不强,由于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认同状况将会影响群体行为,因而对于本民族或中华民族越认同的个体在民族冲突情境下越容易出现积极行为。此类相关研究过多地关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的研究,但是很少将亚文化因素作为考虑的重要指标,往往造成研究的片面。由于少数民族高中生作为特殊群体,其自身面对强烈的外部竞争力,内心极大的挣扎和不平衡感致使其对本民族群体的疏离及民族认同的降低,自身亦矮化为“亚文化”群体,可能导致其民族概念淡薄,归属感较低,因而必然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其自身的心理品质的影响,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促进少数民族高中生对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与此同时,国外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实行以“强化认同”为指导思想的多元文化教育,这一启示性的举措,对于国内学者试图深入全面研究众多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推进制定系统、科学的中国化的方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伴随着心理学视阈下的文化研究逐渐在少数民族研究中崭露头角,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社会适应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当少数民族学生脱离自己的母体文化群体进入校园后,必然要面临着来自与原来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有较大差异的主流文化的考验和民族认同的困境。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少数民族高中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其外在的行为表现,以整群抽样的方式发掘不同种群的内在心理潜质,对嫩江流域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同予以深入考察。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齐齐哈尔地区的在校高中生进行抽样,随机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回收少数民族高中生问卷187份,汉族高中生问卷610,少数民族高中生问卷回收率为18.7%。剔除漏答、错答问卷后,得到实际有效问卷148份,有效率为79.1%。其中,男大学生73名,女大学生75名;高一学生54名,高二学生94名,其中达斡尔族44人、满族35人、回族24人、蒙古族21人、朝鲜族10人、柯尔克孜族10人、鄂温克族2人、鄂伦春族2人,所有被试年龄为17.36±0.77岁。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民族与性别变量间样本差异不显著(Pearsonχ2=9.519,p>.05),表明此次抽样的样本分布较为均衡,抽样较为合理。
2.2 研究工具
(1)中华民族认同问卷,〔5〕由秦向荣(2005)根据翻译国外量表,参考国内涉及民族认同的调查问卷所编制。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修订其中部分题项,将“华人”修改为“中国人”,重新建模进行因素分析。本量表涉及认知、评价、情感、行为等四个维度,共21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6级评分的方法。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837,各维度的α系数都在.90以上。
(2)民族认同问卷,〔6〕由秦向荣(2005)根据翻译国外量表根据翻译国外量表,参考国内涉及民族认同的调查问卷所编制。本量表涉及认知、评价、情感、行为等四个维度,共29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6级评分的方法。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834,各维度的α系数都在.90以上。
2.3 数据统计
使用EXCEL2003进行数据录入,通过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F分析、偏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各维度在性别、民族间的差异分析
各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变量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显示各维度性别差异不显著,在本民族认同的认知、情感、行为维度中少数民族男高中生得分略高于女高中生,而在民族认同评价维度以及中华民族认同的所有维度中,少数民族女高中生得分略高于男高中生,总体而言,表明少数民族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的民族认同的发展状况较为均衡。同时,各少数民族高中生在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各维度F分析差异不显著。
3.2 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间的相关情况
本研究通过对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各个维度进行计算后,将研究转化为显变量的研究。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间的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民族认同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各维度间存在正相关,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水平。
3.3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针对少数民族高中生,进一步以中华民族认同作为因变量,对民族认同作为自变量的预测效果进行回归分析,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的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民族认同维度中的评价、情感、行为共能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总分的51.4%。回归系数R为.717,回归方程:中华民族认同=45.831+.351×评价+.171×情感+.268×行为,回归方程有效(F(4,143)=37.811,P
4 分析与讨论
4.1 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性别和民族属性对民族认同的影响
由于国内外在性别与民族认同关系问题上的研究结果尚无定论,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嫩江流域的亚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高中生整体的民族认同得分在各维度上男生与女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在民族认知、情感、行为维度少数民族男生高中生得分上略高于女生,而女生在民族认同评价维度上的得分要略高于男生。尽管本研究与国内的一些研究并不一致,例如,李红梅(2009)认为蒙古族高中生男生比女生有着更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是王亚鹏(2003)认为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并没有性别上的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要考虑地域以及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本研究取样中的少数民族多数是传统的“渔牧、狩猎”的民族,男性对于征服自然的先天优势通过历史沿承积淀下来,从而影响到现如今少数民族男性高中生心理与行为的表现,又由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优势文化的渗透,导致少数民族高中生原有的民族意识重建。基于此,研究又试图探寻民族属性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各民族间的民族认同差异并不显著,这与国外的相关研究存在相应的契合,在对于亚裔美国青少年群体的民族认同的研究中,这些群体可能由于轻微的文化倾向,使得民族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微弱地减少,从侧面揭示出文化因素对于民族认同的深刻影响。由于各少数民族高中生自身所处的“双文化”或是“亚文化”的背景使得少数民族高中生彼此的风俗习惯以及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具体表现在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满族等民族之间颇为密切的历史渊源以及他们对于萨满教、共性图腾的信奉。随着历史的推演,进而推动各民族间的融合,这是现阶段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积极认同形成的强烈信号,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建立最佳的社会交流和形成积极的群体意识以及推动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实时性研究提出新的启示。
4.2 民族认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
少数民族高中生在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显著地相关。研究将关注点放在探求亚文化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并且试图探寻少数民族高中生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诱因。同时,研究也关注不同少数民族在各外显变量的差异。本研究显示少数民族高中生具有较高的本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具有高度的中华民族认同;这一结果与多数国内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结果相一致,〔7-8〕但与国外提出的对一种身份的过强认同会削弱对另一种身份的认同的观点相悖,即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黑人、拉美人以及白人对国家认同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9〕这一结果表明国外的种族主义的歧视较为严重,削弱其公民的整体归属感。而较之国外所谓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仅指人数上的劣势,对于其权利没有削弱,而是尽可能予以保证,且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政策的支持和重视程度也较高。然而,结合嫩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而言,“流人文化”以及“闯关东”移民活动,促进了本地区对于中原文化的汲取,加速了其由过去纯粹的民族文化向多元共存的民族文化的演变,并且由于世居嫩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性格豪爽、热情好客也使得本地区与各民族之间和谐发展。综上种种,促使其产生对于本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强烈的归属感,同时对于其本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的积极塑造也具有有效的促进作用,进而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GarciaColl, C.G., Crnic, K., Lamberty, G.,Wasik,B.H.,
Jenkins,R.,Garcia,H.V.,&McAdoo,H.P..Aninte grative model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competencies in minority children 〔J〕. Child Develop ment,1996,67:1891–1914.
〔2〕Phinney J.S., Lochner B. T., and Marphy P.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ts . In: Stiffman AR, Davis LEed 〔J〕. Ethnic is suesin adoles centmental health.London:Sage,1990:53-72.
〔3〕陈谊,张庆林,史慧颖.民族认同与少数民族高中生问题行为〔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来康复,2007, 1(07):10640-10643.
〔4〕Mark H. Chae and Pamela F. Foley. Relationship of
Ethnic Identity , Acculturation ,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g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Americans 〔J〕.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2010,88:466-476.
〔5〕〔6〕秦向荣.中国11至20岁高中生的民族认同及其发展〔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7〕万明刚,王亚鹏.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J〕.心理学报,2004,(01):83-88.
〔8〕史慧颖.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族认同心理行为适应研究〔D〕.重庆,2007.
第5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因此,同时具备“认同感”与“认同行为”之义。在“认同”概念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将“认同”概念运用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并衍生出对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层次、维度等问题的深入研究。1996年,DavidY.H.Wu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一文中,指出,“凯斯在总结东南亚一些民族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即把文化作为一种原始的解释性特征保留下来,同时也显然考虑到相反的事实,就是在结构互动过程中,文化内容与族群联系在一起常常承受着意义上的变更。”[1]之后,卡拉(J.Carla)和雷格奈德(J.Reg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菲尼(J.Phinner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2]国外对族群认同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主要对民族认同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民族认同的结构、民族认同的发展、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实证研究。尤其在民族认同的发展问题上,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论解释少数民族认同和适应发展的过程。[3]菲尼(J.Phinnery)发展了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提出个体的族群认同主要经历了弥散性阶段、排斥性阶段、延迟阶段和整合阶段。70年代格罗斯(Feliks•Gross)提出了一个黑人族群认同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即前遭遇阶段、遭遇阶段、浸入和浮现阶段、内化阶段、承诺与信仰阶段。[4]然而,国内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定性研究仍然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主流,尚且缺乏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进行系统地实证研究。佤族是云南省独有的一个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与萨尔温江之间的山地,分属于缅甸与中国,云南境内佤族现有人口35万多人,仅占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2.76%。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推进力而势如破竹冲向全球的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冲破了传统的封闭性,极大地拉近了各个民族、各个族群之间的距离。同时各种差异直接碰撞,直接对抗,从而导致了新的矛盾和冲突。”[5]因此,佤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及文化融合的状况如何、他们的民族认同又与哪些因素相关,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入研究,对于促进佤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良往与相互融合、促进西南边疆的和谐稳定及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本研究采用了代表性抽样的方法,抽取了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三所中学的437名中学生。施测时实际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7份,有效率97.11%。在所抽取的437名学生中,其中男生206人(41.7%),女生231人(52.9%)。高中生222人(50.8%),初中生215人(49.2%),并且少数民族聚集区35人(8.0%),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15人(3.4%)。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处于中缅边境,与缅甸隔江相望,是我国佤族最聚居的区域之一,受主流文化影响不多,而佤族中学生是思想最活跃、人生观正在形成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文化与民族认同也代表了佤族民族认同状态的趋势。
(二)研究工具及数据分析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参考Phinney的民族认同四维度理论及其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MEIM),自行编制《佤族民族认同调查问卷》,采用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本研究分为两个分量表,即“本民族认同问卷”和“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从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四个维度入手,分别对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进行分析。从对问卷所做的因子分析来看,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小于.01,拒绝零假设;KMO的值为.878,在0.8<KMO<0.9之间,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sanalysis)和平均正交旋转法(Equamax)对问卷进行结构分析,本民族认同调查量表与中华民族认同调查量表均自然归类得出4个因子。由此可见,因子分析的结果与研究者的构想相吻合,两个分量表及其总量表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最终问卷整体信度(Cronbach''''sAlpha)达到0.954。数据分析是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对数据进行了均值分析、单元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目的在于探索佤族中学生对民族认同的认识、情感、评价和行为,并分析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结果
(一)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总体状况从整体上对佤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结果显示,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各维度均值M在2.8699~3.9697之间,标准差SD在.31108~.63541之间。可见,佤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总体上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但对本民族的认同要高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且在行为维度上的得分偏低。
(二)双重民族认同的相关及差异检验佤族中学生既是少数民族成员,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民族认同存在身份的双重认同,用Pearson相关考察分量表及其相应维度之间的相关,并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两者是否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为.406,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0,即认为佤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在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且本民族情感和中华民族情感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但本民族认知和中华民族认知、本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评价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三)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差异比较民族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受到不同背景变量的影响,包括正影响与负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级、社会文化环境、语言熟悉程度设定为可能影响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自变量,并采用单变量方差来分析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
1.性别从表3可知,性别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只是男生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平均得分都要高于女生。从四个维度来看,在行为维度上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46<0.05),而在认知、情感和评价维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2.年级在本民族认同上,高中生(N=225)和初中生(N=215)没有显著差异,F(1.130),P=.051>.05。对维度的比较发现,初中生与高中生在中华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行为维度上均有显著的差异性,高中生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要显著地高于初中生。
3.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对佤族中学生的生长环境的考察,研究结果显示,佤族中学生所在中学的环境在本民族认同(F=42.828,P=.000<0.001)和中华民族认同(F=52.232,P=.000<0.001)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县城中学生的民族认同得分要显著地高于乡村中学生。4.语言熟悉程度从表6来看,汉语的熟练程度对本民族认同没有显著的影响,F=.769,P=.512<.05,且在四个维度上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中华民族认同上存在着显著差异,F=5.776,P=.001<.01,并且在中华民族认知(P=.001<.01)和评价(P=.000<.001)两个维度上差异性显著。从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语言的知晓程度来看,佤语的熟练程度对本民族认同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反而在中华民族认同上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F=4.763,P=.003<.01)。
四、讨论与分析
(一)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总体状况在“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中,民族认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本研究将民族认同的结构划分为四维度: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其中,认知维度是个体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承认及其对自己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评价维度,即个体对本民族的积极评价和民族自尊心;情感维度,对自己所属民族群体的情感上的联系和依恋;行为维度,对自己保持本民族的行为习惯、文化、语言及其在民族群体面临困难时积极为本民族效力的承诺。[7]本研究结果表明,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均值在“3.5”左右,尚处于一种相对良好的认同状态,不具有明显的“种族中心”的倾向。但是,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要稍微强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且在中华民族情感维度上的得分偏低(M=2.8699)。“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8]我国的佤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边疆,与缅甸接壤,属于典型的跨境民族,在族源、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同一文化民族或族群。[9]由于经济、文化和婚姻的原因,佤族中学生在日常生活接触到境外的同族群体更多,而接触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机会反而更少,边民的认同更多的是族群的原生认同,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相对弱了。
(二)佤族中学生双重民族认同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还表明,佤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反映了佤族中学生在认同本民族的同时,更多地将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民族统一体,从内心深处真正认为自己是该民族统一体的一员,而不是把中华民族视为“他民族”。因为佤族“和其他55个民族同属一个层次,他们相互结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这个多元统一体有个凝聚的核心,就是华夏族团和后来的汉族……”。[1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佤族中学生对自己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不存在冲突,说明佤族中学生既一致地认同本民族,也同样认同中华民族。但是,从四个维度来看,本民族认知和中华民族认知、本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评价之间呈现负相关性,出现双重身份认同理论(即线性两极模型和二维模型)负相关现象,且对中华民族认知和评价上的得分均高于对本民族的认知和评价。显然,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及日益普及的汉语教学,使得佤族中学生对于本民族的认知和评价在逐渐地减弱,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越来越少的了解,甚至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已经失传了。这种民族认同上的差异也迫切要求国家日益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倡导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政策,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保护与教育。
(三)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目前,国内外对于性别与民族认同之间关系研究上存在着差异,在很多民族认同的研究中,性别不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11]本研究结果表明,佤族男生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女生,但并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由于佤族世居于云南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边远山区,自狩猎时代以来,男性就一直在社会生活、宗教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佤族女性则处于追随者的角色。这种历史缘由使得佤族社会的男性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为强烈,更倾向于维护本民族社会的独特性。同时,佤族男性更多地接触外面的社会,而女性更多从事一些家务,即使中学生也如此,因此,佤族男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也相对要强烈一些。一般而言,年级越高,其与主流文化和汉文化接触的时间也越长,因而高年级的同学也就能比较全面而理智地看待民族文化,而年级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可能主要是以接触汉文化的时间和年龄因素为中介变量对民族认同产生影响的。[3]但本研究却发现,佤族高中生与初中生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从四个维度来看,佤族中学生在中华民族认同评价和行为维度方面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高中生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初中生。这说明,随着年级的增长,佤族中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评价上日趋理性化,对中华民族的认知程度和评价程度也更为积极、主动。研究还表明,佤族中学生的居住地、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其民族认同也产生影响,县城中学生的民族认同得分要显著地高于乡村中学生。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族群比较是群体成员获得积极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可能会影响到对内群体(即所属群体)的认同。在汉族人口比例多的地区(如县城)的佤族中学生同汉族之间的互动较多,而乡村地区却是佤族人口比例较大的聚居区,聚居于此的佤族中学生则更多地接触本民族群体,对本民族认同更强烈,而对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也就相应多一些。汉语的熟悉程度在本民族认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中华民族认同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由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佤族中学生接触汉族文化的机会比较多,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接触也比较频繁,被试的佤族学生(95%)基本上都能很熟练地使用汉语。汉语熟练程度越高的佤族中学生接触汉文化就越多,对汉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也了解更多,因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更高。从佤语熟悉程度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来看,佤语熟悉程度越低的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反而越强,在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得分就越高,这说明对佤语或佤族文化知晓程度越低的学生接触汉族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更多,更倾向于认同中华民族。
第6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民族识别;族群;民族;族群认同;民族认同
【作 者】覃乃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4-454X(2009)03-0022-010
From Ethn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al Identity:Third Research on Guangxi's National Recognition in Mid and Late 20th Century
Qin Naichang
Abstracts:This paper argues that ethnic groups are biased toward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 is emphasis on the political concept. It has forme d 12 ethnic groups historically in Guangxi, each of which has a common historica l source, inter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national recognition, these groups became a nation, which forced them from ethn 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this national identity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ethnic identity.
Keywords:national recognition; ethnic groups; nation;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一、族群与族群认同
族群概念来自西方,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20世纪60年代广泛运用于国际人类学界 ,其概念最初由台湾学者译进,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开始引用“族群”一词 。①目前,族群概念与民族概念一样,被我国学者频繁引用。
对于族群的定义,国外学者各有说法,其中对我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定义 :“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徙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 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此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性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 为族群”。②
我国的学者也给族群下了各种定义,如“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制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 渊源(世系、血统、体质等)和文化(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 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③④“所谓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 为我 的一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对他“自觉 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⑤“族群的含义可以理解为:1.属于人类群体分类中“ 族类 化”的概念,它所指的群体有一个名称(符号);2.这类群体的区别基于体貌特征(种族 ) ,民族(国家、祖籍地、族体)归属,文化习俗,语言,历史和祖先记忆,等方面 的显著不同;3.其成员在心理、感情和价值观念上通过感知他者在上述要素方面的与己不 同 而自我认同;4.一个这样的群体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维护群体的边界,同时排斥异己群体 ; 5.通常被指称在一个社会中居于文化上非主流地位、人口规模属于少数的群体,包括移民 群 体“。⑥“族群不仅指亚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泛指所有被不同文化和血统所造成的被打 上 烙印的社会群体,是人类社会群组层次划分之一种,以生物性和文化性为代表”。⑦“族 群 兼具“种族”、“语言”、“文化”含义,本质上是家族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 象征体系的核心部分,以默认或者隐喻的方式在族群乃至国家的层面上演练原本属于家族范 围的象征仪式,并且通过构造各种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加以巩固“。⑧
综合各种族群的定义,不难看出,一是涉及了血统的因素,即族群与人种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是强调了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族群也是社会文化涵化的群体,这也是族群定义所要 阐释的关键。
关于族群概念在我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是20世纪80 年代以后,人类学与 民族学一样是获得恢复的学科,它们都在建立自己的学科特色,其中人类学强调的是文化与 社区的研究,剔除了民族学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具备了比较广泛的研究空间和学术取向,所 以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进入90年代后,我国学者在阐释民族概念和进行民族研究时,无论 如何尽力摆脱整个苏联民族理论框架的影响,都不能尽如人意。在摆脱斯大林民族定义束缚 的探索上,许多学者更多的是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除此之外一时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民族定义。族群概念一开始就强调文化因素,淡化政治色 彩,这多少让处于困境中的许多学者给了某种暗示,使他们意识到,要探讨真正的民族定义 ,必须跳出以往的政治场景,在纯学术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才能有所突破,而族群概念的出 现正是这一突破口。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更加加深了一些学者对斯大林的民族观,特别是 其民族定义的置疑,认为在当前西方国家借助人权、民族自决等旗号颠覆、分裂别国的情况 下,淡化民族问题的政治色彩,抑制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强调文化因素、淡化政治色彩的族群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符合 了部分学者的思想。
二、关于“民族”与“族群”的争辩
同样是作为人们共同体的阐释,族群概念在我国广泛传播的同时,出现了两者或是彼取代此 ,或是互为补充,或是各自独立使用的讨论。其焦点是在两个概念的界定上,一是学术性的 识别,一是国家的确认。许多学者认为,“民族”侧重于政治层面,而“族群”侧重于学术 层面。如“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学术性,使用范围十分宽泛;民族强调的是其政治性、法 律性,使用范围相对狭小”。⑨“族群是情感――文化共同体,而民族则是情感――政治 共 同体”。(10)“‘族群’概念使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使用于 ‘族群’的政 治定义”。(11)“‘族群’是籍于文化传统与血缘联系的人们共同体,划分主要 是文化因素, 侧重民间的界限划分;而‘民族’则要经过政府识别,是普遍、典范的概念”。(12 )有的学者 认为,学术界研究“族群”是可以的,但用“族群”称国内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容易在 现实中引起混乱。(13)有的认为,民族始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政治成为理解其 实质的重要切 入点。在对待“族群”与“民族”的问题上,必须严格遵循“学术自由”和“现实政治”区 别对待的原则。(14)
从以上可以看出,族群主要是指具有多种“自然文化”特征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更多地涉及 了共同体的政治地位,与国家和政府的“民族识别”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正是因为民族概 念与族群概念两者含义的侧重点不同,又由于他们在概念及内涵上的相似性,使得在运用上 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主张用“族群”概念取代我国现行的“民族”概念的学者认为,族群强调的是文化的因素, 从学术的角度上考虑,更加符合国际的研究和我国的实际。民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今 民族主义盛行,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出发,必须要淡化民族概念的政治化因素,从而避免我国 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应该从国家的战略角度和政治角度出发,朝“去政治化”和“强文化化 ”的方向努力,“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称谓,并把56个‘民族’改为‘族群’”,认为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妥善解决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15)应该严格区分上 位“民族”( 国家民族)概念与下位“民族”(国内族群)概念,“现代中华民族是处于上位的统一国家 民族,由处于下位的56个国内族群平等组成,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各个族群在更高层次上 的统一体。”(16)
主张两者可以并行通用,相互补充的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既要符合当今国际潮流 ,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族群作为一个国际学术用语,具有浓厚的学术渊源和研究价值,而我 国的民族概念也是经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建国后的民族识别 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更是为其形成积累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实基础。两者在 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综合两者研究,可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新中国 成立以后,经过民族识别,把全国的民族定为56个,但是,“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只有56个 族群,这也是说研究中国的族群,离不开民族这种划分,‘族群’与‘民族’可并用。”(17)
有的学者认为,“‘族群’和‘民族’既不是对等关系。也不是广义和狭义的关系”,“‘ 族群’概念应该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因为,在中国,“民 族”是“要经过政府识别,要享受优惠政策,民族自治地方可享受自治权利”的,“是普遍 的、典范的概念”,而“‘族群’探讨的是特例的、变迁的现象”。(18)
反对“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的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探索与研究在我 国进行了近百年,由最初的“舶来”发展成为后来的“中国化”,在我国具有了深厚的现实 基础和历史意义,符合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和谐发展,无论是学术层面、政治层面 ,还是现实的生活层面,民族一词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因此,如果用“族群 ”取代“民族”来统称我国的各民族,在现实中会引起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我国社会 主义政权的巩固。中国的民族理论就是中国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 适合中国实际的民族理论,“中国的‘民族’概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相关论述与 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而确定和使用的概念,有它自身的特点,没有必要为了与国际接轨而用 ‘族群’概念替代”。(19)“将‘ethnic group’同时译为‘族群’和‘民族’ ,或者用‘族 群’取代‘民族’,甚至将‘族群’概念随意运用于各类社会群体,都不是明智和科学的态 度。”(20)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情实际,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无论是意识形态的还是社会制 度的,都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结果不同于外国正是由自身的国情特 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识别尽管有不完善之处,但是也不需要西方的族群理论框架来重新 括套甚至重新识别各民族。所以,“在‘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中,将‘族群’概念及其 应用泛化于社会群体范围不是本土化,而将‘族群’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和既定的‘民族’ 概念也不是本土化。”不应该用族群取代民族,“削足适履于自身”。(21)“用 ‘族群’概念 置换‘民族’概念,一则不妥,二则不能”,“硬性的置换,很可能在相关领域造成难以整 合的混乱”。因为,“族群”主要以文化要素为指标,“文化及其概念”的“非确定性”也 导致了“族群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清晰及非确定性”,而“民族”一词“已经成为了一个极 为重要的约定俗成的关键概念,无论被使用于哪一个系统,都是一个清晰、恰当、便用的表 述,不会衍生歧义”。(22)
三、广西历史上的族群与族群认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经过民族识 别,将“布壮”、“布土”、“布曼”、“布傣”、“布衣”、“布雅伊”等不同称谓的僮 族统一称为僮族。1965年10月12日,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把“僮”改 为“壮”,“僮族”改为“壮族”。同时还确认了瑶、苗、侗、仫佬、毛难(1987年经国务 院批准改为毛南)、京、彝、仡佬等民族,加上汉族和回族,广西共有12个世居民族。据20 00年人口普查,全自治区共有4723.61万人。
那么,这些民族是否经过识别以后才形成并生活在广西的土地上呢?不是的。他们自古以来 就生活在广西这块土地上。如果说经过民族识别以后他们才称为“民族”,或者说是政治的 原因他们才成为民族,那么,在民族识别以前,他们就是在文化上各具特征、各自内部认同 的人们群体,这种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族群”。当然,按照族群理论,这些人们群体还 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族群,但是,为了便于叙述,我们仍以12个大的族群分别加以叙述,并暂 且以“民族”分别称之。这里记述的重点是这些族群各自共同的历史来源。
(一)壮族
壮原为“僮”。僮的称呼初见于宋代。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广西路经略安抚使 李曾伯在给宋理宗的《帅广条陈五事奏》中,有宜州(今宜州市)有“撞丁”的记载。元明 以后关于僮的记载越来越多。《元史•刘国杰传》有“庆远诸僮人”之记载。元代虞集《广 西都元帅章公平瑶记》有“若所谓曰生瑶,曰熟瑶,曰撞人,曰款人之目,皆强犷之际也。 ”明嘉靖《广西通志》卷五十三载:“庆远,南丹溪洞之人呼为僮。”到民国时期,自称布 僮的有宜山、罗城、柳城、柳江、融安、永福、马山、鹿寨、象州、河池、南丹、贵县、武 宣等十多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僮人。
僮源自古代的西瓯、骆越。先秦时期,广西的主要居民被称为西瓯、骆越,他们是壮侗语族 诸民族的先民。据《汉书•南粤王传》南越“西有西瓯”、晋人郭璞《山海经注》“郁林郡 为西瓯”、《旧唐书•地理志》郁平县(今广西玉林市玉州区西北)“古西 瓯骆越所居”等 记载,西瓯、骆越的分布大体上以郁江、右江为界,郁江以北、右江以东地区为西瓯,郁江 以南、右江以西地区为骆越,其中郁江两岸和今贵港市、玉林市一带是西瓯、骆越交错杂居 的地区。也有人认为,西瓯即骆越。
瓯、骆名称在历史上消失之后,出现过乌浒、俚、僚、亻良、僮等称呼。乌浒之名最早见于《礼记 》,后在《后汉书•南蛮传》中说有十多万乌 浒人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年)为郁林太守 谷永招降之事。俚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当时交趾征侧征贰反,合浦俚人亦 揭竿而起,三国时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俚分布于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横县)、高 梁(今广东省阳江等地)五郡,占地数千里。僚的称呼始见于三国,到隋唐时扩大到岭南十 二郡。在《南史•兰钦传》中,陈文彻兄弟被称为俚帅,而在同书的《欧阳危页传》中,又 把陈文彻称为俚僚人的首领。东晋裴渊《广州记》中把俚僚并称。《隋书•南蛮传》则进一 步说明百越是俚僚的祖先。亻良的称谓最早见于晋人左思的《三都赋》,文 中把亻良与乌浒并称 ,到明代,《明实录》说:亻良人分布遍及粤西 诸峒。清人李调元《粤风》里收有亻良歌和僮歌 ,亻良歌是典型的壮族勒脚歌,说明亻良人即是僮人。
(二)汉族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进攻岭南,进一步加强了汉族与岭南西瓯骆越的融合。
东汉之后,中国历经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的分裂、南北朝对峙,北方战乱不休,南方相对 稳定,中原大量汉族南迁进入岭南地区。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大量流民南迁入岭南。《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说:“天下大乱,中 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
宋元时期政治动荡,中原战乱频仍,大批汉人南迁。特别是皇年间镇压侬智高起义和北 方 战乱宋室南迁后,迁入广西的中原汉人较历代更多。过去很少有汉人迁入的桂西偏僻地区, 也有汉人的踪迹。
明初实行卫所制,大批军籍汉族移民广西,如广西桂林卫所军士合家属约5万人,世袭为屯 兵,加上柳州卫所的军籍移民,他们后来成讲汉语桂柳话人口集团的核心。这一时期汉族进 入广西的特点是二次移民,即在华南东部地区及珠江三角洲形成的广府人、客家人、福佬人 等在清初到清中叶溯西江而上向广西境内迁移,使桂东南、桂南一带成为广府人、客家人和 福佬人的重要分布地区。就一般而言,明清以前,汉族入桂者多为屯戍、躲避战争和自然灾 害及被流放者,大多属被动原因,因而数量较少,其中有不少汉人融入当地原住居民;明清 时期,有大量汉人因从事开垦、经商、手工业自觉入桂,他们来的不仅人数多,而且一旦立 足便迅速发展,在长期的交往中有不少原住民族失去本民族的特点,融入汉族之中。
(三)瑶族
名称最早见于《梁书•矣钻传》,元代被称为带侮辱性的“”。新中国成立 后改为“瑶”。
秦汉时期(公元前3世纪初到2世纪),瑶族先民主要集中在湖南湘江、资江、沅江流域的中 、下游和洞庭湖一带。后来,因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压迫,逐步向南迁徙。隋唐时期(六至十 世纪初),瑶族主要居住地在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澧阳、熙平等郡,即湖南大 部分和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等地区。从宋代开始,瑶族逐渐从岭北向岭南迁徒,南宋时桂 林附近的县已有大量的瑶人居住。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说:“瑶之属桂林者,兴安 、灵川、临桂、义宁(治所在今临桂县五通镇)、永宁(治所在今荔浦县花贡乡境)诸邑, 皆迫近山瑶。”据《元史•顺帝纪》记载,元朝时瑶族已经分布于桂林地区、柳州地区和桂 平、平南等桂中桂北地区。清代瑶族继续大批南迁广西,形成了“岭南无山不有瑶”的大杂 居、小聚居的局面。有一部分瑶族经过广西迁到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四)苗族
苗族和瑶族是同源民族。早在公元前三世纪,苗族先民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湖南省洞庭湖地 区。后来由于民族压迫等原因,他们溯沅江而上,向西迁徙,来到湘西和黔东的“五溪”地 区。以后,他们不断向西迁徙。约在宋代,他们陆续迁到贵州南部、云南西南部和广西北部 地区。在广西,他们最初迁到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的元宝山周围。另一部分则沿着黔南不 断向西迁徙。到明末清初,一部分迁到南丹县山区,有一部分则从黔西南迁到今隆林各族自 治县境内的德峨山区。
(五)侗族
侗族属古越人的一个支系,自称“金”。汉文史籍中,多将侗族地区称为“峒”、“蛮峒” 。隋唐时期,在桂北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始设“羁縻州郡”。到清代,称谓才从“峒”演 变为“侗”。
宋代,聚居在今湘黔桂交界地区的一支骆越人,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 了一个自称为“仡伶”的人们共同体――侗族。《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说:乾道七年(11 71年)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老学庵笔记》卷四说:沅、靖等 州,有仡伶,“男未妻者,以金鸡羽插髻”,“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 人吹笙在前导之。”这些称谓、姓氏、居地、习俗都与侗族有关。伶是侗族的称谓。道光《 龙胜厅志•风俗》说:“伶与侗同。”
(六)仫佬族
仫佬又称木老、木娄、姆佬,传说他们的祖先来到现居住地定居时是操西南官话的,因与当 地土著僚人妇女通婚,生下子女,生活习俗随当地土著人,语言也发生变化,称母亲为姆佬 ,元代,仫佬族逐渐从僚族分化出来,明代以罗城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 ――仫佬族。
(七)毛南族
毛南族,在汉文史籍中,有“茅滩”、“茆滩”、“茅难”、“冒难”、“毛难”等写法。 清乾隆年间,“毛难”才正式在碑文中出现,但这时还不是民族称谓,而是作为地名、行政 单位的名称出现的。毛南族的形成与仫佬族相类似,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湖南、山东、福建 等地迁来的汉族与当地土著僚人妇女通婚,明代在茅滩(或作茆滩、茅难、冒南、毛难)这 一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毛南族。
(八)回族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元至元三年(1337年)波斯人伯笃鲁丁从金陵(今南京)到广西 任粤西廉访副使,后代定居桂林,改为白姓,此后子孙繁衍,逐渐分散到临桂、永福、灵川 等地居住。其他各姓回族,也在元、明、清时代,先后从外省或是从征,或是经商迁来桂林 定居。其他各地回民大多系明、清两代先后从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南、云南 等地迁来。其中马姓一支于明末由河北宛城来到广东韶关,然后迁入广西。李姓是在清朝杜 文秀起义后,从云南迁来的。
(九)京族
京族过去称为越族,1958年后改称京族。京族是明代因越南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自正德年间 (1506―1521年)陆续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到今防城港市江平镇巫头岛,后又逐渐向氵万尾、山心、谭吉3个岛上发展。
(十)彝族
自称“诺濮”、“诺苏濮”等,1964年统称彝族。彝族是从唐宋时代开始从 云贵高原迁入今 广西西部地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一带的彝族,传说早在唐、宋时代由云南的东川迁来 ,先到宣城、曲靖(均属云南),然后分两支,一支经贵州的罗平、兴义,渡南盘江进入隆 林;另一支则继续往东,经贵州的兴仁、安龙、册亨,渡南盘江进入今田林县的旧州一带, 到明代才迁到隆林。另有一说是明末清初参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以后,经云南富宁 迁入广西百色、凌云,最后进入隆林德峨。那坡县城厢境内者祥、达腊、念必等村的彝族, 有说是从四川,有说是从云南、贵州迁来;迁来的时间,有说是三国时代,有说是明代,也 有说是清朝乾隆年间,但以明代的说法较多。
(十一)水族
族称最早见于《宋史•西南诸夷传》中“水曲”一语。水族是明代在宋元时期的“抚水州蛮 ”和“环州蛮”的基础上形成的。水族形成后,在广西的一部分,后来可能迁去贵州,或融 合于壮族。今广西境内的水族,有一部分是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从贵州迁来的。
(十二)仡佬族
自称“图里”、“牙克”。唐宋史书中,有“仡佬”、“葛佬”、“仡僚”等称谓。其先民 是古代僚人,统称为“僚”。新中国成立后称仡佬族。广西的仡佬族是清雍正年间从贵州迁 来的,主要分布在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德峨、蛇场等乡。
四、民族识别: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
主体在广西的壮族、瑶、仫佬、毛南、京五个民族,除瑶族的名称在历史上就比较统一之外 ,其他四个民族的名称,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从未得到过统一。经过民族识别,族称才 第一次获得统一。
(一)壮族名称统一
壮族有1548.9万人口(1990年),其中90%以上分布在广西,其余分布在云南省的南部和广 东省的北部。根据汉文史书记载,在岭南地区有乌浒、俚、僚、亻 良等族称,皆壮族先民的称 谓,但也不排除包含了其他民族的泛称。这些族称如此之多,是因为他们长期分散居住和方 言的差异,于是汉族封建文人或以地名称之,或以特殊风俗习惯称之,或以其方言特征称之 ,或以其自称音译称之,因而出现许多同音异写的族称。但这些族称之间都有密切的渊源关 系,而且上同西瓯、骆越,下同今天的壮族都有密切的渊源相承贯连的关系。南宋时,史书 上称广西一带自称为“布壮”的群体为“撞”或“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称庆远、 南丹溪峒之民呼为“僮”。李曾伯给宋理宗的奏折中称宜山一带的族体为“撞丁”,他在《 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中说:“在宜州则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义效、 撞丁共九千余人”。朱辅《溪蛮丛笑》中指出南方溪峒的少数民族“有五:曰苗、曰瑶、曰 僮、曰仡佬”。明清以后的文献上对壮族的族称“僮”、“僚”等多写成反犬旁,带有侮辱 性。
由于壮族居住的地域辽阔,而且多是山区,交通不便,加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长期 采取“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挑拨民族内部的关系,制造民族内部纠纷,因而 壮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统一的机遇,因而表现在族称 上,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自称。其中在红水河、龙江、融江流域,主要包括今宜州、南 丹、罗城、忻城、柳城、柳江、鹿寨、象州、武宣、来宾、贵港、马山、都安、融安、永福 、阳朔、临桂等20多个县(市)的壮人多自称为“布壮”;在广西中部和北部的宜州、南丹 、河池、来宾、龙胜、都安、柳江、柳城、上林等地壮人多自称“布越”、“布雅依”、“ 布依”;在广西南部和右江流域的钦州、南宁、百色等地区的壮人多自称“布土”;在左、 右江一带及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壮人自称“布侬”;在今广西的龙州、钦州、防 城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壮人自称“布傣”。此外,还有自称“布曼”、“ 布沙”、“布岽”、“布陇”、“布偏”、“布闪”、“布爽”、“布僚”、“布斑”、“ 布板”、“布诺”、“布央”、“布那”、“布峒”、“布天保”、“布隆安”等等。在壮 语中,“布”、“濮”是人的意思,壮族所有的各种自称中,都离不开“布”这个总的称呼 。“布壮”译成汉语即为壮人,“布土”即为“土人”,“侬”、“岽”壮语中为森林,“ 布侬”、“布岽”即为“山林中的人”。“曼”、“斑”、“板”壮语为村子,“布曼”、 “布斑”、“布板”意为住在村子里的人或乡下人。而所有这些自称,大都与壮族所居住的 自然地理环境和壮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有关。解放后,50年代初期,在中央访问团的帮助下, 壮族地区开展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同时开展了民族识别。根据共同语言和生活习俗等特 征,广西、云南、广东等省境内各种自称的壮人自愿统称为壮族。这是壮族名称的第一次统 一,它对壮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壮族人民的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 利的。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民族同化、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使许多壮族人民的民 族意识已蒙胧,开始时不少壮人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是壮族,认为自己是“讲壮话的汉人” 。随着民族平等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和民族科学知识的宣传,许多人才改变了看法,要求承 认自己为壮族。
关于壮族各支系的自称和他称,廖汉波先生做了个统计,见下面各表①:
壮族原称“僮族”,由于“僮”字为多音字,一念“同”,二念“状”,而且含义不大清楚 ,容易引起误会。1965年,总理倡议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僮族”称 为“壮族”。以“壮”为健壮、茁壮的意思,意义好,又不会使人误解。这一建议完全符合 壮族人民的心愿,得到了壮族人民的拥护。1965年10月12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更改僮族 及僮族自治地方名称问题给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委 员会的批复》,将原“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广西僮族自治区”改为“广西壮族 自治区”,1965年,云南省“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改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 省 “连山僮族瑶族自治县”改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1965年11月3日,中共广西壮族自 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正式发出改名通知。这一字的改动, 更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各民族的团结。
(二)仫佬族名称的确定
仫佬之名,最早见于《新元史》记载的“木娄苗”①,明清以后,相继以“穆佬”、“木 老”、“木佬”、“姆佬”、“木老苗”、“伶”、“犭令”、“犭令僚”等名称 见于史册。而当地壮族又称他们为“布谨”。“姆佬”在仫佬语中为母亲之意,因此很多学 者认为,汉族文人依此用汉字记音为“姆佬”,并将这一称谓记载下来,相沿至今。而其他 称谓大体上是“姆佬”一词的不同汉字记音。
在广西,“仫佬”族称之出现,最初见于清嘉庆年间修《广西通志》转引《粤西丛载》记述 明成化年间,封建统治者强迫仫佬人改装的一段记载中:“天河獠在县东,又名姆佬……” 。接着在后来编修的地方志书中,陆续有所记述。如《大清一统志•庆远府条下》说:“姆 佬即僚人,服色尚青,男衣短裤,老者衣细褐。女则短裤长裙,宜山、天河有之。”《新天 河县志》说:“天河县……多夷种,而处四境者,又各不同,东则伶獠,名曰姆佬。”《宜 山县志》说:“宜山姆佬即僚人,服色尚青……”。这些记载,诸多出于统治阶级封建文人 之手,他们往往在族名偏旁加上反犬予侮辱和歧视。不过,文中提出伶僚“名曰姆佬”的论 点,为进一步探讨仫佬族的来源提供了线索。解放后,经过民族识别,族称正式确定,统称 仫佬族。
(三)毛南族名称的确定
“毛南”族的族称,在汉文史籍中曾有“茅滩”、“茆滩”、“茅”、“茅难”、“冒 南”、“毛难”、“毛南”等不同的写法。“茅滩”、“茆滩”等作为地方名称,早在宋代 即已出现。元代仍称毛南族居住的地区为“茆滩”、“茅滩”。明清两代,史籍中关于“茅 滩”、“茆滩”的记载也不少,这时期的“茅滩”或“茆滩”已不仅作为地名、山名、圩名 ,而且作为行政区域单位的名称。清乾隆年间(1760―1795),“毛难”之名才正式出现在 碑文中,1935―1942年编的《思恩县志》和《思恩年鉴》中,又将“毛难”写作“冒南”。 可见,“茅滩”、“茆滩”、“茅”、“茅难”、“冒南”、“毛难”等名都是“毛南 ”族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种文献中的同音异写,反映了这个族体族称(因住地而得名)发 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周围壮、汉等族人民习惯称他们居住地区“毛难”居民为“毛难人”。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经过识别调查,正式称他们为“毛难族”。1986年,尊重该族人 民的意愿,把“毛难族”改为毛南族。
(四)京族名称的确定
京族的祖先是从十六世纪开始陆续由越南的涂山(今海防市附近)等地迁来的。新中国成立 初期被称为越族,1958年5月1日建立东兴各族自治县(1979年1月改为防城各族自治县,199 6年成立地级防城港市时撤销)时,根据其历史、语言、文化特点、生活习俗和本民族的意 愿,正式定名为“京族”。
各民族名称的统一和确定,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 力。
民族识别,使这些人们共同体的族群身分同时又具备了民族的身分,使他们从族群认同走向 民族认同。必须指出,这种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注释:
①乌小花:参见《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②转引自祁进玉的《国内近百年来民族和族群研究评述》,《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 期。
③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④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⑤郝时远:《Ethic group(族群)辩》,《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6期。
⑥转引自乌小花的《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⑦转引自王东明的《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社哲版),2005年第2期。
⑧周传斌:《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⑨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10)参见纳日碧力戈的《现代背景下的族群构建》第12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11)参见马启成、白振声主编的《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第102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5年版。
(12)乌小花:《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3)转引自王实的《“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南民族学院 学报》,2001年第6期。
(14)李红杰:《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 群”》,《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15)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和“文化化”》,《民族工作研究》2004年第5期。
(16)转引自王实的《“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南民族学院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17)陈志明:《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18)乌小花:《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9)金炳镐、都永浩:《“三个代表”思想与民族理论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2 001年第3期。
(20)沙力克:《“族群”与“民族”的国际对话》,《人民日报》,2001年11月2日。
(21)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 第5期。
第7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的重大问题分析汤法远 (6)
民族政策宣传面临的新形势与应对策略红梅 (11)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影响研究邓思胜 王菊 (16)
民族自决理论及其中国实践邓立群 (21)
新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特色论——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系列之一黄仲盈 (25)
电视仪式:电视人类学研究发展王清清 (34)
标识与符号:“物”的人类学研究吴兴帜 (39)
民族地区贫困村寨参与式发展的人类学考察——以广西龙胜龙脊壮寨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为个案廖杨 (45)
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集体表象阎莉 莫国香 (51)
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兼论“无国籍女人”的身份罗柳宁 (57)
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结构分析韩鼎 (62)
广西汉族“壮化”现象个案研究——以东兰县花香乡弄兰村为例马世英 梁世甲 (67)
岑毓英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贡献初探——岑毓英研究之三施铁靖 (74)
岑大将军崇拜初探许方宁 陈曦 朱广 (82)
祛魅:刘三姐形象的历史演化任旭彬 (88)
推行拼音壮文步履维艰的反思覃德民 (97)
壮族与客家族群互动中的语言关系罗聿言 袁丽红 (106)
明清时期两广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其影响滕兰花 (112)
峇峇娘惹——东南亚土生华人族群研究梁明柳 陆松 (118)
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看铜鼓的厌胜功能陈金文 (123)
艺术化生存的淡化与侗族歌师的精神皈依——侗歌艺术传承研究系列(七)张泽忠 韦芳 (134)
略论晚清时期桂东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高茂兵 刘色燕 (141)
对民族经济学研究“冷”与“热”的思考王建红 (146)
民族地区农地保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探讨李凤梅 (151)
文化视野中的水族经济行为蒙爱军 (159)
岭南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研究严雪晴 (165)
从自然资源因素看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广西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原因研究之一邵志忠 (172)
文化品牌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马翀炜 马骏 (179)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村寨居民交际和社会认知能力研究李星群 (184)
乡村旅游语境中民间艺术的在场与形变——基于湘西德夯苗寨的个案研究吴晓 (189)
新世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李荣启 唐骅 (194)
傣泰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研究领域的新贡献——评黄兴球《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何平 (202)
瑶学研究的新力作——评玉时阶、胡牧君等著《公平与和谐:瑶族教育研究》俸代瑜 (204)
全国报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满达日花 (206)
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挑战——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研究之一覃彩銮 (1)
制度安排与族群认同——民族区域自治视阈下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因素分析程守艳 (10)
多民族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文化基础构建张文静 杜军 (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概念在我国的历史演变——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二黄仲盈 (19)
“”、“”的国际化路径研究李捷 王婷婷 (25)
文化全球化·文化安全·文化自觉陈蕾 (37)
“民族社会问题”涵义探讨陈纪 (41)
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及预警调控研究张劲松 (47)
共生互补视角下中国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特点岳雪莲 (55)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熊晓辉 (60)
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地区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其前瞻讨论周建新 覃美娟 (65)
关于壮族经济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覃乃昌 (73)
气候灾变与乡土应对:龙脊壮族的传统生态知识付广华 (84)
方块壮字文献生存及传承状况调查分析——以龙州、象州、忻城三县为例黄南津 高魏 琼华萍 (93)
论开发壮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动因、平台和主体谭国志 谷中原 (99)
汉、壮接触诱发的语言变异的机制李心释 (104)
明清伏波神信仰地理新探王元林 (112)
瑶族史诗《密洛陀》的认知语言学视角谢少万 刘小春 (120)
中国京族研究综述黄安辉 (125)
仫佬族族源新探温远涛 (131)
从“八百媳妇”到“兰那王国”名称变更考释——泰国古代北方泰族国家变迁新探饶睿颖 (136)
论广西桂柳运河沿岸地区商业系统的空间结构唐凌 (142)
新时期广西百色现代物流业发展研究蔡旺 (148)
民族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制度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徐成波 (154)
不交易的“交易者”广西隆安县南圩镇亥日的“牛中”黄兰 (161)
近代广西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分析(1877~1931)——基于海关贸易档案的考察吕兴邦 (167)
新、马、泰、越经济发展与环北部湾少数民族地区的对策白爱萍 (177)
边疆文化旅游开发与文化安全张春霞 (185)
旅游小城镇社会空间问题研究——以漓江流域阳朔、兴坪、大圩调查为例范文艺 (192)
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保持——以壮族布洛陀文化为例李志强 (197)
涵摄中国传统文化,拓展中国人类学研究——评覃德清著《民生与民心——华南紫村壮汉族群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龚树排 (201)
《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评介汤夺先 (203)
全国报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 (205)
新中国民族团结的理论与实践李富强 (1)
民族自治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族际政治互动分析汤法远 (7)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自治权王乐宇 (13)
试论民族法学的性质、理论体系及其调整对象郑毅 (19)
关于“”问题的几点思考贾春阳 (27)
族群动员:一个化族裔认同为工具的族际政治理论严庆 (35)
中国民族社会结构:“民族分层”抑或“民族内部分层”陈怀川 (42)
“文化民族性”的三种解读理路与情感重构解丽霞 (48)
“民族信仰”定义及其特质探析——基于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特质及当前“民间信仰热”的反思和晓蓉 (55)
传统民间信仰的生态蕴涵及现代价值转换张祝平 (63)
从狂欢到日常:牛哥戏与乡村文化生活的变革王易萍 (69)
岭南文化的起源与壮族经济史——壮族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覃乃昌 (74)
壮汉文化冲突与壮族民间长诗许钢伟 (80)
壮族传统水文化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付广华 (86)
例论壮、岱、侬等跨国民族的认同状况——以广西那坡县念井村为例罗柳宁 (95)
广西金秀花蓝瑶族源:东来说莫金山 赵乙生 赵贵坤 (101)
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仪式的审美人类学考察雷文彪 (110)
首届“全国瑶族文化高峰论坛”综述谷家荣 (115)
土司文化:民族史研究不能忽略的领域成臻铭 (120)
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宏贵 (129)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蓝武 (134)
国家认同的隐喻:广西左江流域伏波信仰与班夫人信仰共存现象探析——广西伏波信仰研究系列之一滕兰花 (141)
远谋与近虑的兼容——对“驱准保藏”前后清朝西南边政决策调整的透视马国君 (147)
黎族“禁”习惯法的演变韩立收 (156)
加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思考陈光良 (16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边贸县减贫的影响分析——以云南省勐腊县为例庄天慧 张海霞 余崇媛 (166)
农村产业转型与农民角色变迁实证研究——以湖北高家堰土家族为例向丽 (172)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广西为例伍梅 (178)
我国宗教旅游利益相关者及其协调机制初探高科 (184)
韦拔群与东兰红色旅游整合开发李燕林 朱瑞平 黄松 (191)
研究壮族的“他者”和壮族作为研究的“他者”——杰弗里·巴洛以及他的壮族研究金丽 (195)
广西民族研究学会、广西壮学学会“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付广华 覃彩銮 (200)
全国报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 (205)
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郝亚明 (1)
关于中华民族构成的思考罗械杰 (6)
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国家行动——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一覃乃昌 (12)
“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严庆 青觉 (22)
作为民族志的个人叙述——从一位昆人妇女的生活史谈起张丽梅 胡鸿保 (30)
网络日志:一种“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可能巴胜超 (35)
经济消耗与社会构建——箐口村哈尼族丧礼的经济人类学阐释郑宇 谭本玲 (40)
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国经验30年(1978-2008)祁进玉 (47)
20世纪前半期中山大学与西南民族调查刘小云 (53)
反刍与探赜:壮学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契洽——侧重于近代壮族边疆区域社会史的分析覃延佳 (60)
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结构及其特点梁庭望 (66)
历史文献中的沙人——少数民族支系研究之一颜洁 (77)
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研究回顾与展望邓金凤 (88)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麦思杰 (96)
菲律宾伊戈洛人与中国仡佬族的关系何平 (105)
宋自杞国索隐白耀天 (110)
壮族与客家杂居的空间结构分析——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一袁丽红 (119)
从汉、壮民族接触看平话的变异类型李心释 (127)
试论右江革命根据地中的“共耕社”生产模式陈一榕 梁玉珍 (133)
我国西部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王月 张跃平 (138)
毛南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现实难题与对策黄润柏 (144)
试论南汉宋朝时期岭南的开发雷学华 陈晓燕 (150)
明清民国粤港核心城市组合变化与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结构——粤港商业经济对广西经济辐射的研究之五黄滨 (157)
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合理性探讨李昕 (165)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甘明 刘光梓 (172)
文化景观遗产及构成要素探析——以广西龙脊梯田为例王林 (177)
桂台农业旅游竞争与合作模式研究韦复生 (184)
旅游展演艺术研究述评魏美仙 (192)
黑衣壮:“我”的表述与建构——兼评海力波《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吕俊彪 (197)
壮心、壮志与壮学——评《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吴秋燕 (203)
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付春 (1)
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张建军 (9)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实践——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二覃乃昌 (20)
人口较少民族的法人类学探讨朱玉福 宋才发 (29)
民族乡的性质及其为什么不能成为一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因周全琴 (38)
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韦小鹏 徐杰舜 张艳 (44)
身份·参与·书写——家乡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困惑毛伟 (52)
本土知识与人类学传统张永宏 (58)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侯豫新 (65)
民族志的“真实性”彭兆荣 谭红春 (71)
族群身份之论争: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郝瑞与李绍明的论争分析王菊 邓思胜 (78)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台湾语言生态——基于“族群政治”分析视角陈颖 (85)
结构主义神话学评析韩鼎 (91)
来稿须知 (70)
壮族织锦技艺廖明君 (F0002)
卷首语 (I0001)
论岑毓英施铁靖 (98)
社会学视角下的布洛陀文化——对壮族乡村和谐社区建设的思考吴德群 (108)
壮族麽教与壮族师公教的比较研究莫幼政 (113)
《三千书》新探何明智 (121)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余益中 刘士林 廖明君 (124)
推进教育公平 和谐发展瑶族教育玉时阶 (131)
从瑶族石牌律看法律的起源莫金山 陈建强 (139)
多族群杂居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以贺州大盘村为个案——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二袁丽红 (146)
中国传统民族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和谐发展黄家莲 (153)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文化力因素李德建 (158)
晚清广西城市居民消费探论侯宣杰 (164)
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反思——以中国瑶族盘王节为例谭红春 (172)
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的内涵界定及其框架模型构建黄松 (179)
旅游中的民族文化整合与传承——以阳朔“印象·刘三姐”为例范文艺 覃德清 (184)
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文化认同——以羌族旅游为例吴其付 (191)
多民族文学史观视野下的壮族文学——评《壮族文学发展史》的分期、体例与文学史理念龚树排 (199)
第8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音乐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7.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14
自1980年Ethnomusicology被引入中国并被翻译成“民族音乐学”以来,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本文中,在未明确音乐人类学名称前,均用“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来指称Ethnomusicology所对应的中文翻译,以避免先入为主的误解)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1],但是仍有诸多重大问题尚未得到最终共识,其中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问题位居前列。30多年来,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出发,围绕着究竟是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或者其他学科名称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甚至是繁琐的讨论,这些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毫无疑问,学科名称的不确定势必极大的影响该学科的发展,目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现状正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仅在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更是极大的影响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2],众多研究者一直以来也在不断呼吁甚至提出批评,要求尽快明确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
作为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无疑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原因,音乐学界许多研究者将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人类学的替代名称使用,排除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存在,混淆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学的关系。可见,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名称之争,归根到底,是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的字面翻译、及其与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理论研究和实践相对应的问题,其实质在于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状况出发,判定本学科究竟是人类学理论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还是民族学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由于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而民族学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上位学科,因此,本文尝试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关系这一在以往研究中从未出现的全新角度,来分析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以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确定作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
人类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叶启晓在对多种人类学定义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给出人类学的定义为:人类学是“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以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两个视角,从个体、群体和整体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类起源和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体质、文化和社会 “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相互关系的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演进、特征与规律性及人类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综合性实证科学”[3]。与人类学相类似,民族学的定义也很多,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民族学学定义为:民族学是“以民族和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份、起源、分布及相互关系,比较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探索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4]。
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下位学科,因此,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内容多有重叠,由上述两者的定义也可略见一斑。但两门学科也有很多不同,最主要表现在作为上位学科的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广博而宽泛,而下位学科的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则专向和深入。由于人类学研究内容十分宽泛,因此关于人类学学科分支的方案有三四十种,但不管何种分科方案,民族学都是作为人类学下位学科存在的,与其并列的学科包括:人体学、考古学、史前学、工艺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神话学、等[5]。
从微观的角度,可以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人类学研究的跨度包含自人类产生以来至目前的全部人类群体;民族学则是专门研究民族的学科,所研究的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等,但却很少涉及人类早期的原始群。人类学以不同尺度的人类群体为基本单位,其研究涉及人类起源进化、人类体质特征、以及人类文化的全面内容;民族学则以民族或民族共同体为基本单位,以现代民族为主体,开展民族识别、某民族或诸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在文化研究方面,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往往拓展多个族群文化的比较研究,或深入到很小的人群中去探索文化的共性和深层次问题,注意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互通性和共同性,多以整个人类的文化为背景进行综合性人类群体研究,不仅关注某时期的文化特征和这些文化因素的横向联系,更注重这些文化因素产生的历史源流和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民族学的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那些构成民族特征具有显著特点的文化,侧重于某时段某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并展开同时段的横向比较。另外,民族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人类学既包含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包含社会科学的研究,或者说人类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综合性学科[6]。
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研究中,与多门学科结合形成了若干交叉学科。民族学在其他学科中应用形成的交叉学科如:地理民族学、旅游民族学、历史民族学、生态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等;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更多,如:经济人类学、工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这两门学科在音乐学中应用形成的交叉学科即分别为: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民族学。
二、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了解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不同之处,再来通过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历年来研究成果的文献研读,分析目前为止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看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在音乐学中的运用。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跨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跨度极大,包含从人类生涯开端到目前为止的全部人类社会各种群体的音乐行为,相关的研究成果早已经出现,如1989年的《原始音乐研究综述》[7],对19世纪以来原始音乐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评述。类似研究成果还在不断增加,这突破了民族学基本不包含原始群的研究范围,具有强烈的人类学特征。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单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有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研究活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不同尺度的人类群体为单位,比如某一村落、某一城镇、某一县城、某一更大范围的区域,或者因为、音乐关系(如某种乐器、某种民歌)、人口迁移、甚至建筑特色等原因形成的某一范围内的人类群体,等等,也就是说具有灵活可变的特点,即前述人类学定义中所说的“个体、群体和整体”。并且,深入某一小群体内,针对某一小群体甚至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事件研究其音乐文化活动,正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例如:《区域音乐文化的主体——乐人个案研究——以庆阳唢呐艺人马自刚为例》[8]、《音乐事项个案研究——2003年12月2日晚,丽江古城四方街的“甲磋”》[9]、等。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要研究音乐本体,但更主要的是研究音乐的发展传承、音乐所涉及的人群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研究音乐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变化、人在其中的作用、音乐文化对其他人群直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举不胜举。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尤其关注在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的背景下,音乐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状况,如《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10] 、《原生与再生——豫中笙管乐班的传承与变迁研究》[11]等。可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早已突破了民族学的范畴。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经常采用人类学与民族学共有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法、民族志方法、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方法等,但也借用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典型的研究成果如《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2]、《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下)》[1314]等。同时,两种源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当代音乐人类学中有更加广泛运用的趋势,一是全貌观,更强调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研究人类音乐,二是文化相对论,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并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音乐及其文化,如《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15]等。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属性:与音乐学一样,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也属于人文学科,其学科研究活动中既有社会科学的特点,也有自然科学的特点,社会科学的特点很明显不需赘述,自然科学方面的特点,如对于乐器制造工艺的研究,对于歌唱发声的研究,等等,成果如《满族萨满乐器研究》[16]、《中国民族唱法音色的声学阐释——以女声为例》[17]等。因此,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属性与人类学综合性的学科属性相类似,而不同于民族学的纯粹社会科学学科属性。
上述从研究跨度、研究单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来简单概括和分析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状况,能够为确定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奠定基础。
三、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人类学
从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跨度、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还是其学科属性,历史及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的实际状况都毫无疑问的显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不是民族学基本理论而是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并取得成果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比民族音乐学或者音乐民族学更能体现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音乐人类学无疑应当替换民族音乐学成为Ethnomusicology的当之无愧的中文译名,从而体现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名实一致。
实际上,国外的Ethnomusicology本来就是典型的人类学在音乐学中运用的学科,除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作为佐证外,仅从新版格鲁夫音乐词典关于Ethnomusicology研究人员的描述就可看出:“(Ethnomusicology的)研究人员接受音乐或(和)人类学训练”[18],可见实际的Ethnomusicology研究并非其词面所表述的民族学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而是人类学在音乐学中的应用。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这组略显复杂冗长的词汇改为音乐人类学了。
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得到确认,那么,民族音乐学又该做何处理?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是Ethnomusicology1980年从日本按照英文词汇的顺序转译过来的,殊不知,Ethnomusicology本来就是“杜撰”而成[19],该词汇的词面意义根本不能包含其所指称的相应内容,因此按照词面顺序进行直接翻译成民族音乐学导致了中文译名的歧义,进而导致了30年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在中国混乱。1985年乔建中等就已从Ethnomusicology中文翻译的角度指出民族音乐学应改为音乐民族学[20]。
通常,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分析民族音乐学的字面含义: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和语言学的角度。从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看,如果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交叉产生的学科,那么按照学科分类和命名的基本原理,一门学科在另一门学科中应用形成交叉学科,其命名规则为应用到的学科名称在前,应用的学科名在后,例如:文献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形成的学科命名为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在影视学中的应用形成的学科命名为影视民族学,其他例子如前文中提到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各种学科中应用形成的大量交叉学科。因此,民族音乐学就应是音乐学在民族学中应用形成的学科,应归属于民族学之下,这显然与一直以来学界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解和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情况全然不同,故而从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来理解民族音乐学名称是无法正确解释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合理性的。
杜亚雄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名称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偏正短语,由定语+中心词构成,定语又称修饰语,对偏正短语的核心即中心词进行限定和修饰,因此,民族音乐学这一词汇中的“民族”是用来修饰“音乐学”的[21]。照此理解,民族音乐学实质上就是各民族的音乐学,而世界上所有的人群都有相应的民族归属,因此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学科的每一个方面就完全等同,既然民族音乐学不可能替代音乐学,那么民族音乐学也就根本没有实际的存在价值。
可见,采用上述两种角度来理解,民族音乐学都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学科名称。尽管民族音乐学在国内使用了30多年,并被音乐学界所广泛接受,但从严谨、科学的角度出发,民族音乐学应被完全替代。具体方式为:在其研究内容的维度看,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人类学所替代;在学科应用和交叉的维度看,音乐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民族学所替代。音乐民族学将音乐人类学中与民族学相关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而其学科位置则归属于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从而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上下位学科关系相一致。在王耀华和乔建中的《音乐学概论》中,正是采用此种学科归属的方法[22],很好的解决了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关系问题。
以往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中,支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往往仅认为应以音乐人类学代替民族音乐学,对于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去向则没有研究或者没有说明,使得音乐学界很多从业者和研究者误认为要消除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从而对音乐人类学名称产生抵触。而按照上述音乐民族学归属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安排,能够避免音乐学界对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学科消逝的忧虑和误解,有利于融合音乐学界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认同,也有利于音乐民族学回归其正确的学科位置并促进音乐民族学学科的正常发展。
结语
现在来反思过往30年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可以发现,我们其实不应过于纠缠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本身,而是应着重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实际内容。著名音乐人类学家洛秦就指出:“如果充分认识了学科的性质,了解了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产生的背景及其变化过程,学界对这些都有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认同和共识,那么译名或称谓的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23] 。外国人喜欢用单词的组合创建新的词组,很多时候是个人喜好,具有极大的随意性,Ethnomusicology的“创造”就是典型例子。国外对于Ethnomusicology的使用也曾经有过很多争论,因为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已远远超过Ethnomusicology原意所涵盖的范围[2],但若进行替换也存在很多问题,只不过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使用罢了,但其对应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是毫无疑问的。Ethnomusicology的“杜撰”,再加上1980年引进国内时的字面翻译,仿佛是为我国音乐学界设置的一个陷阱,让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及相关研究陷入其中,不仅浪费了研究资源,更极大的阻碍了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分析相关研究,能够看出一个趋势,即2000年后,尽管仍有一些分歧,但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24]。洛秦在2010年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更进一步从13个方面分析指出音乐人类学名称的合理性[25],是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总结性成果,自此以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正式确立已呼之欲出。
在此背景之下,音乐学界的从业者应理解国际国内音乐人类学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应再背负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历史包袱,反复纠缠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应齐心致力于音乐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教育的开展,从而紧跟音乐人类学国际研究的前沿,促进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全面发展。
作者说明: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基金项目编号:13SA0030。
[参考文献]
[1]王一平.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双重难题——跨学科、跨文化的困惑[J].音乐探索,2011(1):6-9.
[2]洛秦. 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J].音乐研究,2010(3):49-59,124.
[3]叶启晓. 诠释人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
[4]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简编版,第6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2011:3392.
[5]同[3],68.
[6]同[3],76.
[7](美)布鲁诺·奈特,赵仲明译. 原始音乐研究综述[J].中国音乐,1989(2):29-32.
[8]板俊荣,伍国栋.区域音乐文化的主体——乐人个案研究——以庆阳唢呐艺人马自刚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3):81-86.
[9]杨波,陈铭道.音乐事项个案研究——2003年12月2日晚,丽江古城四方街的“甲磋”[J].中国音乐,2007(2):47-55,63.
[10]郑海燕.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M].柳斌杰,邬书林,阎晓宏.中国图书年鉴 2005.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508.
[11]方墨涵.原生与再生——豫中笙管乐班的传承与变迁研究[J].中国音乐学,2010(1):47-53.
[12]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1月1日.
[13]齐琨.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J].黄钟,2010(3):139-148.
[14]齐琨.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下)[J].黄钟, 2010(4):105-111.
[15]杨殿斛.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8(1):8-18.
[16]刘桂腾.满族萨满乐器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17]吴静.中国民族唱法音色的声学阐释——以女声为例[J].中国音乐学,2007(4):53-60.
[18]C Pegg. Ethnomusicology: Introduction[EB/O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10-13]. http:///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52178pg1#S52178.1.
[19] 王耀华,乔建中. 音乐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50.
[20] 乔建中,金经言.关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建议[J].音乐研究,1985(3):96.
[21]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J].中国音乐,2009(3):38-43.
[22]同[19],11.
[23]同[2].
第9篇:族群文化研究范文
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受众
受众,指的是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网民。受众从宏观上来看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上来看有体现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多样性的人。受众的特点包括:规模的巨大性,在人数上超过大部分社会群体;分散性,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异质性,即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受众既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对象,对传播过程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受众的需求,受众对媒介信息内容的选择性接触活动等,都对大众传播的效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需要探讨的是针对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的电影受众。众所周知的是,好的电影受众,能够充分咀嚼出电影当中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并且通过理性的分析和评价,发掘出电影当中最闪光的部分,并且通过网络、书报等各种途径对电影中的闪光点进行较好的传播,让普通大众在他们的评价和分析当中获得帮助,从而更好地理解电影、欣赏电影。由此看来,不同类别不同题材的电影产品需要不同的受众,才能够获得较好的鉴赏和传播。在我国的电影市场当中,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属于较为稀缺较为罕见的电影品种,因此需要的是具有一定的电影鉴赏能力的受众,这样才能够将这一电影队伍发展壮大起来。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一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的受众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探讨。
1.壮族人或者亲属中有壮族人的人群是首要受众
对于一些具有少数民族特有性质的文化产物,由于其中所携带的民族文化特性,从而直接吸引了与该民族存在一定血缘联系的人群。容易让人们理解的是,这些人从这些特定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物当中所感受到的民族认同感和巨大的心理共鸣,是保证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产物继续生产并且持续发展的最初原动力和最初目标。由此可见,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的首要受众,一定是该民族的族人,或者是在亲属当中有该民族人的人群。相应的,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的首要受众,一定是壮族人或者亲属中有壮族人的人群。由于这些人本身所携带的壮族文化特征,并且在人类共有的民族荣誉感、自我认同感的引导之下,让他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很容易对与壮族相关的产品具有非常浓厚的好奇心和文化兴趣。也就是这种民族感情的驱使,这些人群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由自主的寻找与壮族相关的一些产品,品味他们,从而满足他们内心对自我文化的认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人群长期处在壮族的民族文化氛围当中,对于电影产品当中所涵盖的壮民族特有文化具有相当高的敏感度,能够非常轻松地从电影当中获取到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也能够更加透彻地对其进行理解。
2.对壮族文化有所了解和研究的专家学者
说到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有一个人群是我们不可以加以忽视的。那就是对相应民族文化进行专业研究的专家学者。这些人不一定本身具有少数民族血统,但是在多年的深入了解和钻研之下,一定是对该少数民族的文化有着相当高程度的了解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普遍趋向于对那些与自身相关的事物产生较高的兴趣,因此钻研少数民族文化的专家学者们,就更容易对相应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物产生接触了解的愿望。具体的说,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叫容易吸引到研究壮族文化的专家学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是他们接近壮族文化的一个捷径,特别是在排除了语言障碍之后,他们可以更好的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环境来对壮族文化特征进行接触,并且随着电影的剧情发展和主题表达,更好地理解壮族文化当中最显著、最普遍的价值观,进而更好地理解壮族文化。也是由于他们之前已经有的研究,他们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电影中所传递的壮族文化,使电影获得更理性的鉴赏和理解。
3.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文化感兴趣的人群
在人类的大多数活动当中,由兴趣产生的驱动力是驱使人们产生许多行为的最根源的因素。不难理解的是,人们通常会很容易在对某一事物产生兴趣的情况之下,开始关注与之具有关联的事物。因此在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的受众当中,相当一大部分的受众是由那些对壮族,或者壮族文化具有兴趣的人。这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持续搜寻一些与壮族相关的产品,用以将自己与壮族文化之间建立起更多的勾连,进而进一步了解壮族相关的信息。因此经过译制的壮族民族语电影,对于那些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文化感兴趣的人群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接近壮族文化的机会。像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这种类型的电影当中所包含的浓郁的壮族文化气息,对于那些对壮族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说,语言的译制扫除了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巨大障碍,给予了他们一个绝佳的机会从最真实的角度来观察壮族文明当中最本真的成分。这一点,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综合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知道,由于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殊性,这些产品需要一些特定的受众群体来对其进行较好的鉴赏和监督。而在广大的电影受众当中,壮族人或者亲属中有壮族人的人群是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的首要受众。另外,对壮族文化有所了解和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适合加入到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的观看群体当中来。最后,那些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文化感兴趣的人群也是壮族民族语电影译制产品较合适的受众。
[1]张允.新疆柯尔克孜语电影译制产品受众及市场研究[J]电影文学.2011.13
[2]张允,蒋雪娇.维吾尔语电影译制产品受众及市场调查[J]当代传播.2011.03
- 上一篇:债务危机案例分析范文
- 下一篇:生物质燃料技术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