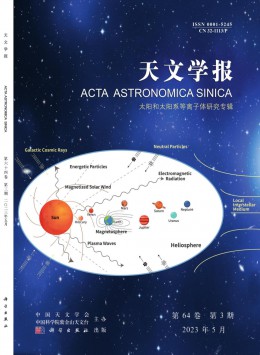天体物理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天体物理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天体物理范文
位于智利阿塔卡玛沙漠中的阿塔卡玛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阵列(ALMA),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地面射电天文望远镜兴建计划,由66座小型望远镜组成一个毫米波及次毫米波段的干涉仪,可视为次毫米波阵列的扩大版,是研究早期宇宙遗留辐射、恒星形成与演化、行星系统、星系甚至生命起源的利器。
该计划的三个主要合作伙伴分别为北美、欧洲及东亚地区团队。凭借以往研制射电望远镜仪器设备的经验,台湾中研院天文所于2005年和2008年先后受邀加入其中的日本计划(ALMA-J)与ALMA北美计划(ALMA-NA),负责组装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荷兰及英国所提供的接收机模组,使成为完整的接受机前段次系统为其提供及组装测试信号接收机前段次系统。该所科技人员与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在台中合作成立东亚接收机前段整合测试中心,不但成功提前完成原本负责的所有东亚团队17套信号接收机前段次系统,并协助北美与及欧洲团队另外完成9套前段次系统的组装和交付,保证了这座望远镜在2013年3月正式完工并运行。
到目前为止,ALMA机构已两次向全球天文研究学者公开征求观测计划书,分别称为Cycle 0与Cycle 1。在总共征得2000余份观测计划书中,只有300余份通过严格的审查。观测计划通过审核与否,主要是由审查委员会按送审计划的科学价值加以评量。台湾在此激烈的竞争下,总共通过了20余份计划书,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天文学上最终极的观测挑战之一是以相当于事件视界的角解析度来直接观测到黑洞及其周围情况,这对于研究广义相对论强场效应、黑洞边缘吸积盘及外向流过程以及黑洞的自旋等都开启了新的窗口。
台湾中研院天文所同时拥有SMA与ALMA的使用权,这两个阵列若联合成为一个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系统(VLBI),可望达到数微角秒的角解析力。目前已知有两个超大质量黑洞,即位于银河系中心的SgrA*和M87的核心,其尺寸大得足以使用次毫米波段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系统进行解析。因此该所提议,再增加一座射电望远镜,与SMA及ALMA相结合,组成一个纵跨地球南北表面的超大射电天文望远镜,可望达到几十万分之一角秒的解析力,将能做到对黑洞“剪影”的成像。这是仅使用由SMA及ALMA组成的单一基线所不能做到的。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于2011年同意,将ALMA-北美团队建于新墨西哥州的12米口径Vertex原型望远镜提供给台湾中研院天文所的研究团队。台湾科学家建议,将这座望远镜移至北极圈内格陵兰海拔3200米高的峰顶上(该望远镜也被更名为“格陵兰望远镜”),与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史密森天文台、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及座落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海斯塔克天文台等共同组成面向北天球的超大“北天次毫米波VLBI”,在次毫米波段用极高的角解析力来观测M87星系巨大黑洞和喷流发源区。该计划的准备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参与制作天文观测仪器
除了上述种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外,台湾科学家目前与日本、韩国及欧洲航天局共同商议,参与由日本主导的下一代“宇宙学与天文物理太空红外望远镜计划”(SPICA)。该望远镜口径3.5米,整座望远镜温度由冷却系统降温至5K,其工作波长范围在5~210微米。SPICA的口径与之前的赫歇耳红外天文望远镜相似,但凭借较低的工作温度,可以降低背景辐射而大幅提高系统灵敏度。预计SPICA将在2020年以后发射升空,比美国的新一代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太空望远镜要晚。虽然两者在短波长范围至25微米都有观测能力,但是SPICA在波长大于20微米的区域有^佳的探测能力,并且是唯一能观测至210微米范围的太空望远镜。此外,SPICA具有较大的视野、图像能力也较佳。
SPICA的科学目标主要有三项:研究行星系统的形成与演化,包括原行星盘中的气体(包含水)与尘埃与行星演化的关系、岩屑盘的矿物学、外太阳系气体行星的大气以及柯伊伯带天体的组成;星际尘埃中的生命循环,包括在银河系与邻近星系的气体与尘埃的物理与化学、尘埃的矿物学、超新星残骸中的尘埃演化以及在早期星系中星际尘埃的来源;星系的形成与演化,包括活跃星系核与大量恒星形成在不同宇宙时间与环境的关联性、恒星形成与超大质量黑洞的同时演化、恒星形成及星系质量蓄积的历史与大尺度结构的关系、宇宙红外线背景的物理。
SPICA规划搭载4个观测仪器。台湾中研院天文所将参与日本宇宙科学研究所负责研发的中红外相机与光谱仪(MCS),包括一个中解析度光谱仪和一个高解析度长波长光谱仪,能够在12~18微米提供解析度在20000~30000的光谱,以及一个能够在5~40微米提供16个不同波段图像的广角相机,其滤镜组包含一个光栅棱镜,以在全波段提供低解析度的光谱(R=50~200),包含不在光谱仪范围内的5~12微米范围。
其他重要科研成果
除台湾中研院天文所外,岛内一些高校如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新竹交通大学、成功大学等也在开展有关天文及天体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包括:发展张弛程序,研究星系中央气体盘在棒形旋转体驱使下的演化过程;发展一个小波程序,分析哈伯太空望远镜中的第二代广角行星相机(WFPC2)和红外线照相机(NIC-MOS)所观测到的资料;研究磁气流,发现小波转换和重建技术可应用在观测旋涡状星系的构造上;发现在洛斯比(Rossby)数值小于1的情况下,热对流在径向方向的波长会缩短,热对流的效应会受到在径向方向磁乱流,和热辐射的双重破坏而削弱;发现环绕在白矮星的吸积盘内,热对流效应完全被破坏而消失,造成热传导几乎由磁乱流所传递;探讨X风流体的热结构问题,计算出电子游离比、温度及化学成分在X风发源地8000AU(日地距离)区域内的分布;根据估算类似木星的外太阳系行星,如果离母恒星在0.04AU以内,轨道离心率在0.2以上,这个巨大行星半径最后会超过潮汐半径,气体会通过L1点离开这个行星,同时会渐渐地远离母恒星;分析彗星微尘,研发一套能够用来分析万亿分之一克(10-12g)大小的微尘极灵敏质谱仪;发现在内在切变力对星系自旋的影响存在条件下,相对较易测量的星系自旋场可用来重建潮汐切变力与质量密度的初始值;提出一个自由参数a的二次方程序,发现a值为0.17(4σsignal);发展复杂而健全的非球形动力模型,显示由此模型得出的数值与比用球形动力学算出的标准质量函数,更符合N个天体模拟所得结果;发展以切变力测量为基础,包括质量重建与发现星团演算法的弱透视分析计算程序;以松弛法及高阶戈多诺夫法(Godunov)编成的高效能气体动力程序,模拟星系盘面上促使棒状结构形成的密度波,并将此程序应用在3kpc旋臂问题及NGC5248的模拟上;藉由极大阵列望远镜(VLA)、超长基线波干涉仪望远镜(VSOP),观测星系中心大质量黑洞SgrA*的电波源的结构,了解活跃星系核的超光速运动、吸积盘的运转情形,及中心大质量黑洞SgrA*与银河中心气体可能发生的交互作用;利用观测类星体在可见光波段与氢原子气体的分布情形不同,了解邻近星系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受到潮汐作用而膨胀的巨大外太阳系行星所发展的模型,可解释为什么截至目前为止,在天文学家已发现的70多个巨大外太阳系行星之中,尚未有任何轨道半径小于0.07AU的行星。
2006年,台湾科学家梁茂昌参与的国际天文研究团队,首次成功观测到距离地球约63光年远的狐狸座外太阳系行星(HD189733b)大气中存在着生命之源――水。
赫比格-哈罗天体(HH object)是年轻原恒星在两极方向产生喷流的一系列的块状云气。2009年,台湾中研院天文所李景辉等人使用次毫米波阵列望远镜,观测到源自于一颗邻近年轻0级原恒星的HH211赫比格-哈罗天体,拥有一对高度准直的喷流,不仅显示出喷流内的内震波,而且在原恒星的两侧都可以看到喷流至少1次的摆动,相对于原恒星呈现反射对称,完全符合喷流的理论模型。
次毫米星系出现在宇宙大爆炸之后20到60亿年间,地球上所看到的其实是早期遥远的宇宙所传来的图像。中研院天文所王为豪2010年运用最新升级改良过的次毫米波阵列望远镜,观察到新的次毫米星系,并推测此类星系的数量可能超过之前天文学界的估算。
暗物质是宇宙中的一个谜,由于无法被可见光所探测,所谓暗物质粒子的存在迄今无法证实。中研院天文所人员参与一组国际研究团队,利用日本斯巴鲁望远镜观察25个大质量星系团,藉由引力透镜来详细测量这些星系团的暗物质空间分布,在2010年首度证实天文学界目前对暗物质的主流预测模型。
该研究人员还利用日本的朱雀号X射线观测卫星,对位于Abell 1689星系团最的高温气体进行温度测量,结果发现高温气体存在一个各向异性的温度分布,显示星系团会藉由加热而成长,而触发加热机制的是气体掉入星系团内所产生的能量,至于这些气体的来源,则是位于星系团外被称为“宇宙网”的细丝状大尺度结构,说明镶嵌着这个星系团的大尺度结构会影响星系团的成长。
自1998年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的现象以来,天文学家一直就测量大尺度宇宙结构的方法,致力寻找更完美的技术。2010年,台湾中研院天文所张慈锦与彭威礼等人利用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的绿堤望远镜进行观测,成功研发出通过测绘太空中极遥远的氢气体所发出的射电波,测量不同星系内的氢气体分布,最终绘制出“宇宙网”图像的新技术。与先前使用可见光观测所绘制的结构图详加比对,吻合度相当高,验证该方法的正确性。藉此,科学家将能更深入地探索宇宙中的暗能量及其本质和特性。
行星如何形成是天文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台湾天文学家高见道弘、金孝宣、周美吟等人2011年利用日本斯巴鲁望远镜,成功地在距离地球460光年的银河系外金牛座RY恒星附近搜さ奖怀莆“原行星盘”的尘埃气体云。研究人员成功地在波长为1.65微米的近红外波段取得一张金牛座RY星图像,与其他许多在较长波段观测的原行星盘图像相比,这里盘面辐射的光偏离恒星中心位置,原因是些近红外波段的辐射是从盘的表面层发出的散射光,为金牛座RY星原行星盘在垂直方向结构提供重要特征线索,对行星形成过程的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些活跃星系核喷出的强力等离子体喷流范围可长达千万光年,远比星系本身还大,并且速度高达光速的99%以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家一直无法解开这些喷流如何被加速到接近光速之谜。2012年,台湾科学家利用欧洲VLBI网,首度发现在室女座星系团中的巨型椭圆星系M87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所产生喷流的自行速度变化的失落环节。原来在黑洞附近喷流刚开始产生时速度并不快,但在距离黑洞约1万到数十万黑洞大小的空间区域内,由于磁流体力学的作用,喷流不但发生形状上的变化(趋向束状),还历经了由低速(光速的1%)加速到高速(光速的99%)的过程。
第2篇:天体物理范文
【关键词】油田;物业;管理;措施
一、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业主满意度
要从狠抓思想观念的转变入手,积极教育和引导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服务第一,业主至上”的思想,坚持“服务是岗位、服务是市场、服务是效益”的理念,努力把“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落到实处,这些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具体工作之中。
建立和落实领导责任机制,层层签订各类责任状,使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进一步明确担负的责任,形成一个纵向到底的管理责任体系。物业与业主、社区及驻矿单位的互动明显增强,增进彼此解,促进相互支持。强化从严治企,重点推行问责制,对于因服务质量等问题引发投诉的,要对职工予以警告处分和通报批评,并附之以经济处罚,在职工队伍中引发深刻反响,促进正气的树立,行为的规范。加强对小区管理的监督检查,实行每月定期检查、随时抽查相结合,打分排名,奖优罚劣。进一步加强“440”服务网络建设,做到快速反应,处理认真,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定期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使小区环境和绿化美化有所改善。组织召开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联席会议,研究落实齐抓共管、群治群防措施,加强保安力量,配备专用警车,强化值勤巡逻,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安全感,促进平安矿区建设。
二、树立责任至上理念,努力提升物业管理和服务水平
做为服务型企业,要的产品就是服务,对于企业和员工来讲,服务是市场、服务也是饭碗。业主就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要必须树立责任至上的服务理念,时时处处、真心实意地为业主着想,切实把不断满足业主的需要当成要不懈的追求,真正把“服务第一,业主至上”、“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落到实处。进一步落实问责制,完善责任体系,严格责任追究,着力推进“责任物业”建设。
要进一步加强“440”服务网络建设,策划组建“440”指挥中心,提高服务投诉、应急事件的协调处理能力和效率。加强应急维修服务的管理,明晰工作界面,明确责任界限,加大回访力度,提高维修工作质量。在专业化重组的基础上,要加强保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增加并更新巡逻警车数量,与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加强联系和协作,保障小区监控等物防技防措施的正常运行,务必在年内实现小区治安的根本好转。
要进一步坚持“目标从高、要求从严、质量从优”的原则,着力推进物业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严格执行矿区服务事业部《物业管理和服务工作标准》,加强走动式管理,不断形成按标准做事,按制度管事的局面。加强物业与业主的联系,定期开展活动,真正发挥业主大会、小区管委会的作用。继续做好星级小区评比工作,促进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和不断提升。
三、加强企业管理,提高运行质量,保障工作目标全面实现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向管理要效益是要公用事业单位尤为重要的生存之道、立业之本。因此,要下功夫开展好“基础管理年”活动。
要积极筹措资金,加强投资管理,搞好矿区环境建设和生产设施维修改造。在项目安排上,要区分轻重缓急,从职工群众要求最紧迫、受益最直接的实事做起,集中有限的资金,优先解决与矿区居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矛盾和问题。投资重点向“示范小区”建设上倾斜、向改善基层生产条件,特别是小区物业工房建设上倾斜、向节能节水项目上倾斜、向平安矿区建设上倾斜。努力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要的“只见补丁,不见新衣”的问题,尽力做到办一件事,成一件事,落实一个项目,解决一个问题。强化招标、合同、概预算管理,坚决按程序办事,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管理,机关和基层共担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确保实现理想的投资效果。
加强预算管理工作,全部收支都要纳入预算范畴,严禁资金在体外循环,发挥预算管理的预警机制,超前发现和及时避免经营风险。加强成本管理,从严控制成本费用,严格执行《定额标准》,成本费用支出要逐级审查把关,实现非生产性费用压缩10%的目标。加强物资采购管理,减少中间环节,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成本。加强收费管理,加大收费稽查的力度,将收费指标与二次分配挂钩,水电回收率要不断提高。要加强物业企业劳动人事管理,压缩非生产人员,以低成本用工为原则,扼制人工成本的快速攀升;改革分配机制,二次分配向苦脏累险的岗位倾斜,用分配机制促进职工的合理流动;严肃劳动纪律,规范劳动用工和薪酬支付行为。加强信息化工作,积极摸索“数字物业”的建设。继续认真组织实施好“管理工作千分制考核”,促进管理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加强幼教管理,与知名幼教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突出办学特色,塑造公办幼儿园的新形象,努力吸引生源,增加收入。以业主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培育新的物业服务能力,拓宽市场空间,提高经济效益。
四、健全体系,落实责任,夯实质量安全环保和节能节水工作基础
第3篇:天体物理范文
一、集多人的力量优化备课环节,提高备课质量。
教师的业务水平直接影响着授课质量,教研活动为教师的学习提供了机会。利用网络上大量的教育资源,我们可以学习、利用并为我们的教学服务。教师可利用各网站提供的教育论坛、聊天室进行交流,对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剖析,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物理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增加教师教研活动的机会,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
二、教学媒体从单一媒体向多媒体转变,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一)物理概念是从大量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不容易理解,难于记忆,所以更难应用。而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水平。即发挥图像、图片、视频、音频、文本等多媒体功能,结合传统教学媒体,通过力、热、声、光、电等形式为学生提供生动形象的感官刺激,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二)实验能力是中学物理教学中必须培养的一项重要能力。要求学生明确实验目的,理解和控制实验条件,在理解的基础上独立完成有关实验;会使用相关的实验方法;会正确使用相关的仪器;会观察、分析实验现象;会处理实验数据,并得出结论。信息教育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在整合物理学科教学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视频实物展台、多媒体投影仪等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媒体,在物理实验中具有直观形象、化小为大、化远为近,改变时空、动静变化、快慢可调、重复再现等特点。
三、节约时间,提高课堂效率。
在上习题课、复习课等专题性课程时,需要复习提纲、知识网络、练习题目、试卷分析等内容,将其制作成课件,直接展示在屏幕上讲解,可以节省抄题、解答过程和板书的时间。解答过程的展示可以规范学生的答题步骤,也可以提高课堂效率。
四、多媒体教学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不足之处。
多媒体不是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是破解教学难关的万能工具。多媒体教学不管发展得多完美,都存在不足。加上各门学科也有独特之处,以实验为主的物理学也不例外,且高中物理更抽象、逻辑性更强,而多媒体教学虽然功能强大,但若应用不当会适得其反。
(一)多媒体教学本身的不足
1.多媒体不能完全代替教师
美国《教育周刊》提出:问题不在于电脑进不进课堂,而在于教师和学生使用它做什么。美国的儿童电脑教学课程专家毛尔科维奇说:“先进工业国如美国和德国,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电脑可以代替教师。到了最近,他们才逐渐明白,人才是最好的教育工具。并认为,成功的教学要由多样因素结合。就像学游泳,不能单靠游泳池,也不能单靠水,还要有好老师。”多媒体只是辅助教学,而不是代替,否则教师将成为多媒体技术的奴隶,起不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因此,必须摒弃“多媒体万能观”,它仅仅是促进教学目标实现的手段,绝不是教学的归宿。
2.多媒体教学容易导致信息容量过大
多媒体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能不能被学生消化、吸收、内化为知识,则不得而知。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适量的教学信息,才会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信息密度是有限度的,它受课堂教学时间、学生素质、知识难度等方面的影响,信息量过多过滥,会造成无效信息的增加,学生学习负担的加重,获取信息难度的加大,处理信息能力的减弱,课堂教学效率的降低。课堂教学信息容量大,显示速度快,教学节奏快,不能给学生充分记笔记和思考消化的时间,记忆停顿太短,导致刺激不够,印象不够清晰,甚至使学生把握不住课堂教学的重难点,无疑给学生的学习增加了难度。
(二)物理学科的特点使物理教学不能依赖多媒体教学
1.多媒体不能完全代替物理实验
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离开实验,物理科学就不会产生,也无从发展,因此中学物理教学中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虽然多媒体技术可以逼真、贴切地模拟实验,可以没有误差,没有失败的风险,可以随意控制实验的速度,但是物理学毕竟是一门实验科学,学生对事物的认识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实事求是。如果完全用模拟实验来代替物理实验,教师就成了机器的操纵者,学生就成了实验的看客,这不仅会影响学生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及协调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还会直接影响对物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长此以往,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极为不利,同时也不利于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的形成,不利于学生科学品质的养成。“活动是认识的源泉,智慧从动作开始”,因此,在物理教学中要尽可能地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亲自体会感受。
2.多媒体教学不利于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4篇:天体物理范文
ISO9000质量认证与管理体系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并实施的一项国际标准,此概念在1994年首次提出,而后在世界各国普遍推广与运用,该标准有助于各种类型的企业有效建立并运行其质量管理体系,我国在引入该体系之后随即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将其转化为通行的国家标准,而后,各行业结合自身实际将其进一步转化为行业标准。长庆油田物业管理公司应该采用并规范地导入物业管理ISO9000国际标准质量体系工作,通过该标准的实施实现物业管理各个部分的标准化操作与经济效益的提高。油田企业通过建立和实施物业管理ISO9000国际标准质量体系可以为其带来如下几方面的益处:1.增强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定位。物业公司由于其性质比较特殊,提供的是无形的劳务与服务,所以更应该以顾客为中心,物业公司应该通过各种措施与方法去了解和满足顾客需求,尽可能超越顾客需求,在此基础上,采用各种措施测量顾客满意程度,搜集各类反馈意见,不断提高服务定位。2.强调公司最高管理层的直接参与。公司最高管理层往往是政策措施的直接制定者,要想让所出台的政策符合实际,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必须要求最高管理层,即政策制定者直接参与物业公司的质量管理活动,从公司层面与物业管理实际制定出切合实际且颇具可行性的标准化管理体系相关对策。3.明确界定不同层次人员的职责权限。界定不同层次人员的职责权限有利于从诸如教育、培训、技能和经验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统筹兼顾,满足和明确各类人才的需求,并充分加强对各类人才的管理,充分调动各方人员积极参与到整个物业管理标准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二、物业管理标准化体系的构建
如上所述,长庆油田物业管理在导入并构建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步骤:1.聘请顾问。ISO质量管理体系诞生的时间并不长,在我国开始采用的时间更短,同时,ISO标准的建立必须与本企业的实际紧密结合,否则非但不能起到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反而会有碍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总之,物业企业导入ISO9000标准体系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环节,必须聘请资深的物业管理行业的专家,必须具备标准体系与物业管理两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管理经验,才能很好地指导物业公司建立切合自身实际的物业管理标准化体系。2.抽调业务骨干送外培训。在聘请顾问与专家建立了符合长庆油田物业管理ISO9000标准化体系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标准化体系如何运行的问题了。要保证该体系能够沿着符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轨道顺利运行,长庆物业企业必须建立对干部与员工进行有关ISO9000专业管理知识与基本理论的培训制度,定期展开相关理论知识的培训与训练。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强与外界的联系,积极吸收其他物业管理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强该系统与本公司的契合,还必须抽调业务骨干送外培训,培训结束后回来之后必须在全公司进行经验介绍与汇报。3.建立两阶段服务质量测评标准。第一阶段应该毫无疑问地进行顾客感知质量测评,要想获得顾客的真实感受与评价,必须设计出合理、科学的问卷与调查机制,即“真话表露机制”,因为业主对物业评价的高低,可能与其物业费的缴纳额度存在关系,所以站在业主的角度来考虑,既要保证其说真话,又不至于承担更高的物业管理收费。第二阶段是对物业企业及其组织支撑进行质量测评,即设计出合理的指标体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等综合实力进行测评,完成两阶段测评后,对物业公司的得分进行加权平均,然后提交认证机构进行考评,根据得分不同划分出不同的档次。企业的综合得分可以用下列方法计算求得。式中:OSQ——组织支撑质量,即上述第二阶段所衡量的内容,其权重为0.3;CPQ——顾客感知质量,即上述第一阶段所衡量的内容,其权重原则上为0.7;SQ——物业企业综合管理服务质量。通过计算,可以较为直观地获得不同物业管理公司的综合管理服务质量的高低,审查组在综合评比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其他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如业主投诉率、小区入室盗窃等的发生率、刑事案件的发生率等)的基础上,形成物业企业服务质量评价报告,上报认证机构,由认证机构审核、查验相关证件之后,授予物业管理标准化等级。4.监督检查。一般情况下,监督检查机构应该自物业管理企业获得证书之日起第八个月开始进行第一次监督检查,以保证物业企业在获得相关认证之后仍然继续保持优良的服务水平,以后每隔12个月进行一次例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获证物业单位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顾客频繁投诉无果等情况的必须严肃处理,如果被查物业企业逾期不改的话,要考虑取消其认证资格。认证机构再进行监督检查的过程中,对相关信息必须保密,以维护物业公司的形象,保证物业公司在积极改正上述问题之后可以继续为广大业主提供优质服务。
三、结束语
第5篇:天体物理范文
1 油田财务管理现状
1.1 财务管理工作不被重视,财务管理意识薄弱 一直以来,财务都被简单地看成是记账的账房先生,目前油田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大多仍停留在记账、算账、保障等浅层次,成为会计工作的附属品,主要是处理企业对外联系,涉及对内需求管理少,并没有体现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价值。同时在部分管理人员眼里,财务工作并不重要,财务工作人员可有可无,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碍事。他们不会对财务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有过多的要求,将财务人员隔离在企业运作之外,直接免去了财务管理的实际职责。
1.2 财务管理思想、理念落后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财务管理涉及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以资金的流动形式反映出来,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账房先生的存在。然而目前我国油田实行的财务管理体制依旧沿袭计划经济形势下的部分模式,财务核算工作还是围绕生成计划目标进行,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与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符。
1.3 财务管理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财务管理是一项需要专人专干的工作,不仅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非常高,能够处理财务管理相关工作,还需要具备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职业操守。但是目前油田企业财务从业人员在专业知识这块存有欠缺,部分人员甚至在职业操守上出现偏差,做假账的现象时有发生。
1.4 财务数据与实际生产数据存在脱节现象 目前油田企业很多方面的信息都存在不透明的现象,油田企业各个部门都对信息有所保留,提供的信息带有水分,造成整体财务数据失真,通过财务核算的数据与企业实际生产数据有出入,甚至严重不相符,影响了油田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失去财务管理的意义。
1.5 财务管理体制陈腐 目前我国油田企业财务管理依旧沿用过去那套传统的管理制度,无论是关于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管理还是从业资格管理等,依然呈现金字塔结构,办事效率低,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等体制呈现的问题都制约了油田企业工作效率的提高,无形中增加企业管理成本,成为制约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关键点。
2 改进油田财务管理的策略方向
2.1 破旧立新,改变传统财务管理理念,进行财务管理转型 财务管理并不仅仅能对企业生产进行核算,而是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每个环节。这就需要企业加大对财务管理的投入,高度重视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改变传统的财务管理思想,积极走出去,学习先进的财务管理经验,不断进行管理创新,以全新的管理意识和工作方式,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实现财务管理对企业经营全方位的监控管理,从“核算型”财务转变为“经营管理型财务”。
2.2 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 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是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形式相辅相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序进行。要实现财务管理职能,油田企业需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财务管理体制建设,把成本控制作为财务管理的重点工作,引导企业节能降耗工作的开展,形成成本节约的意识,把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心转移到资金的运营管理上,逐渐形成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模式。
2.3 重视财务管理系统建设,提高实际应用水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油田企业已经应用了多套财务管理软件。从实践来看,由于石油企业单位数目庞杂,各单位的技术水平、管理模式、市场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财务管理软件应用上,要多走“量身定制”这一模式。如何调整现有管理模式,将以往好的管理思想植入财务管理软件系统中,对财务管理软件系统进行后期改造以适应企业的管理现状与管理要求,将是财务管理软件系统实施成功与否和发挥财务管理效益的关键。
2.4 实现财务管理与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结合,追求效益最大化 对于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来说,资金管理是企业良性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如何在自助理财前提下基于安全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对企业资金进行运作实现利益最大化,成为每一个企业都在考虑的问题。而财务管理不仅能对企业生产进行成本核算,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对企业利润的增加进行预测、控制和反应,达到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效果。这就需要油田企业重视财务管理的作用,允许财务管理直接参与企业资金运营过程。
第6篇:天体物理范文
关键词:油田;物理管理;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现代油田的建设也在迅猛发展,良好的油田物业管理水平对保证油田生产、促进工作和谐稳定环境的营造起到积极地作用。通过目前油田物业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解析,提出可行的对策,有利于促进油田物业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
一、油田物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没有健全的体制。油田的物业管理部门大多数是由油田后勤系统职能转化而来,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并没有与商业化的物业管理形成良好的对接,仅仅是一个摆设部门,仍从事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后勤保障工作,没有系统性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说就是盲目服从上级从属机构的安排,指哪打哪,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缺乏商业物业管理中的服务意识,并没有明确的职业归属感。这就造成了目前油田物业在服务系统上管理一片混乱,并且停滞不前,没有发展性。
(二)没有明确的定位。油田生产历来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体制,这就让物业管理部门对自己的职能定位不清晰,既跑去做生产工作,又同时兼任物业工作,并且往往重生产、轻物业管理,两头忙,但是两头都没忙好,这样既制约了企业的生产又没有做好物业管理的本职工作。
(三)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由于一般油田都远离城市,往往是自成一个系统,这就要求企业不得不考虑为解决大多数职工的生活问题而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建设自身的社会服务系统。但同时又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各种配套设施都不能很好的完善,只能做到基本解决生活问题的层面,有些比较老的油田,在设计之初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很多配套设施从设计到施工都不是很完善,并且,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重复的投入建设,不仅仅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还给物业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严重影响物业管理部门的服务质量。
(四)物业管理队伍人员素质层次不齐。在上面的描述中提到,油田的物业管理部门是由后勤部门转化而来,这就造成多数油田目前的物业管理队伍女多男少,学历普遍不高、技术水平不高的现状,对于一些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在培训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年纪大,学历低造就了他们的接受能力较差,观念更新速度较慢,影响了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
(五)职工及其家属的思想亟待改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油田职工的各项生活开支,包括住房、生活服务等都是由企业在负担,这种福利政策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到目前还有油田企业在负担职工的一部分生活开支,因此,对于现在物业管理部门的收费行为,很多职工及家属都不是很能够接受,这就使得油田物业管理商业化的进程不太顺畅。
二、油田物业管理中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建立物业应急安全管理队伍。在油田物业管理中,安全始终是一项关键性的问题,关乎养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为了保证人们健康、高效的生活,必须提高油田物业管理水平,打造物业应急安全管理团队,专门针对油田物业管理中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应急处理,进而降低安全隐患的滋生,提高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在通信设备方而,为保证油田区域与外部的联系与通信,管理人员应及时对通信设备进行质量检验,对设备的性能进行安全检查,禁止出现通信设备瘫痪的状态。此外,为了提高物业管理的安全,应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针对紧急状态下的安全问题进行罗列与规范,分别在制度之中予以体现,强化安全管理责任制,实现权责的明细化,采取24小时轮班制,及时对安全隐患予以消除。
(二)建立严格的物业收费标准。为了提高收费水平,解决物业费收费难的问题,应建立完善的收费机制,建立完整的物业费收费体系,强化监管、质量考察与问题反馈等收费机构的重要职能,严格按照统一的收费标准收取物业费,在物业费清单上罗列每平方米的收费单价,对每家每户的房子大小进行标注,进而表明物业费的总额,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与管理下,能避免矛盾问题的滋生。
(三)建完善的物业服务体系。油田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应充分考虑住户的实际需求,深入到住户之中,与住户及时沟通与交流,通过住户的相关反馈,能够让物业管理部门对相关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强化主动服务,转变传统住户投诉的方式,物业管理部门应做到主动出击,从中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分别就小区内的房屋质量、环境卫生、绿化以及安保等问题进行调查,应具备前瞻性,提前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预测,不要等到东窗事发才予以处理,为时己晚。此外,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应及时对物业管理人员的素质予以重视,当住户来反映相关问题时,住户情绪激烈,应及时安抚,而不是比住户的情绪更激烈,甚至还会出现打架斗殴的情况,使问题更加恶化。
三、结语
在油田物业管理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对正常的物业管理工作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这就需要全面油田物业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更加的细心周到,从而全面提高油田物业的管理效率及服务质量,将油田物业管理工作的软实力发挥到极致,从而促使该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参考文献:
第7篇:天体物理范文
关键词:油田 物业 管理
一、引言
油田物业管理走进电子信息化时代。数字管理平台的投用,可使企业的生产运行管理、服务质量监督、处理用户报修投诉更加方便、快捷、直观。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就可以一览热网、污水站运行情况,全面了解所属单位员工服务执行情况。
二、油田物业管理的注意问题
什么是战略?战略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谋求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全方位的综合因素出发,对自己的生产经营和资本运营所做出的总体谋划。战略管理的基本内容是:指导企业全部活动的是企业战略,全部管理活动的重点是制定战略和实施战略。而制定战略和实施战略的关键是对企业内外环境条件进行分析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企业战略目标,并使三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所以说,企业战略管理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在保持这种动态平衡下,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和企业使命。可以说,一个不重视战略的企业永远不可能做强,也形成不了核心竞争力。
振兴公司是我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第一家成立的物业管理企业,公司近些年来结合企业实际制定的发展战略是:以品牌服务为主导战略,以低成本运营、市场开发为基础战略,以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科技创新为保障战略。并加强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变化的跟踪,对战略目标和具体战略措施随时加以调整,做精做强主营业务,积极培育辅业项目,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高效快速发展,努力实现打造石油系统一流物业管理企业的战略目标。
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是做好人才工作的三个关键环节。在这方面,企业必须打破等级界限,打破专业界限,多渠道发现人才,真正做到识才用慧眼、用才有气魄、爱才动真格,使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形成大力培育人才、广泛吸引人才、珍惜和用好人才的环境和气氛。振兴公司在人才培养培训方面从两个环节入手,收到了较好效果。一是加强对高级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复合型技术人员的培养。鼓励技术精湛的老师傅与青年工人签订师徒合同,传授经验,同时加强多面手人员的培养,使他们在各个工种间可以进行轮岗操作,做到“精一、通二、会三”。二是广泛开展技术培训,提高操作人员的技能水平,举办各工种技能培训班,提高技术水平和实际能力。
三、油田物业管理的发展模式
1.走“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之路,广开财源
服务市场不发育、物业管理收入来源不足是独立工矿企业物业公司生存发展的最大障碍。拓宽收入渠道,弥补经费不足,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多元经营”的经营策略。油田矿区开展多元经营有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发展居住小区的社区服务业大有可为。独立工矿区因远离城市,许多社区服务项目无法依托城市供给,因此物业公司可以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家政服务、养老服务、餐饮服务、商业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家庭装饰服务、房屋出租等内容,既可以方便居民的生活,又能增加收入来源。
2.走精干高效之路,实现管理手段现代化、服务方式社会化。
在实行物业管理的初级阶段,物业管理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不高、以自我服务为主。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物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尤其是信息化已经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物业管理行业也不例外。在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形势下,物业管理如果不摆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管理模式,不用信息技术提升管理手段,仍然采取封闭式的自我服务方式,物业管理公司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难以生存。
3.走规模化发展之路,是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的必然选择。
像石油企业这样的独立工矿区,居住区分散、规模相对偏小,物业管理机构往往按居住区设置,造成物业管理资源分散,成本偏高,形不成规模效益。随着服务市场的发展、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竞争,通过兼并、重组,走向集约化、规模化是物业管理发展的趋势和生存之道。深圳、上海等地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独立工矿企业必须适应规模化发展的要求,对物业管理机构有计划的进行合并重组,以发挥规模效益。
4.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努力造就高素质的物业管理人才队伍。
青海油田物业管理的人员大部分是过去从生产一线分离出来的老弱病残和闲散人员,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已不能满足新形势要求。油田物业管理必须按照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和专业化、社会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重视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素质优良的物业管理人才队伍。
5.物业管理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
新世纪里,市场意识和市场竞争,对于物业管理行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物业管理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走进市场参与竞争。因此,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在国内物业管理规章制度不断健全、物业管理市场容量不断扩展的机遇下,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服务平台,才能获得市场。
四、结语
因此,油田物业管理企业必须要做好短期和中长期战略规划。主要内容有品牌定位、目标市场、发展规模、人才储备、服务方向、企业核心竞争力等。同时,物管企业的战略规划还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性、整体性及目标性。既要做好中长期战略规划,使企业的战略规划能增强企业品牌的生命力,也要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强势品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第8篇:天体物理范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会调节天平,会测出固体和液体的质量,会正确地记录测量值.
2.会用量筒测液体的体积,会正确地观察和读数.
能力目标
1.培养观察能力
观察天平的构造、观察天平的最大称量和最小称量,观察砝码(每个砝码的质量以及盒内砝码组成)
对比观察量筒和量杯的区别,观察量筒和量杯上标有的单位,它的最大刻度是多少?它的每小格表示的体积是多少?
2.培养实验能力
德育目标
培养学生认真操作,自觉遵守操作规范的良好习惯.
通过天平的使用,使学生提高对平衡美、对称美的欣赏能力.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主要目的是练习使用天平称质量.通过实验培养学生使用天平的技能,同时,进一步使学生对质量的单位形成具体观念.对于称固体的质量.教材中之所以选择三个体积相同的木块、铝块、铁块让学生称量,是为了与下一节内容衔接,为学习密度知识作准备.
教法建议
本节是实验课,因此本节课的教学方法应以实验法为主.
教学设计示例
一、本节重点、难点分析
1.天平的使用
上节课学生已初步了解了天平的基本构造和使用方法,但是由于天平是比较精密的仪器,而且又较难掌握,因此本节课应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进行规范操作上.
在天平调节前,首先应让学生明确,未经调节的天平是不平衡的,称出的质量也不准确,因此必须事先将天平调平衡,在天平调节环节中,边讲解、边示范、边对学生进行指导,在调节天平中应要求学生按照以下顺序进行:(1)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2)观察游码和标尺,认识最小称量值,将游码拨到零刻度线;(3)观察天平初始状态,确定调节螺母的移动方向;(4)进行调节,判断是否平衡,再调节,直至平衡.
天平一旦调节平衡就不能再移动位置,否则应重新调节,这个问题一定要向学生讲清楚.
2.量筒和量杯的使用
使用前一定要指导学生认真观察量筒,观察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弄清量筒(杯)的单位,并找到它标在仪器上的位置.
(2)弄清量筒(杯)的最大刻度和最小刻度.
(3)测量时应把量筒(杯)放在水平台面上.
(4)观察时,液面如果是凹形的应以凹形液面底部为准,若是凸形的,要以凸形液面顶部为准,读数时视线应与液面相平.
二、课时安排1课时
三、教具学具准备
托盘天平、砝码盒、烧杯、水、墨水瓶、木块、铁块、铝块、幻灯片、投影仪、视频
四、师生互动活动设计
1.认真观察天平(复习),认真观察量筒和量杯,首先是整体观察,观察它们的构造,然后对比观察,观察它们构造的不同点,最后细致观察,观察它们上面标有的单位,观察最大刻度和最小刻度.
2.实验:测量固体的质量.
3.实验:测量一定体积的液体的质量.
4.讨论测量液体质量的方法.
5.讨论测一张邮票质量的方法.
五、教学过程设计示例
(一)引入新课
方案一:复习提问引入新课.
1.什么叫物体的质量?它的单位是什么?
2.实验室里测量质量的仪器是什么?
3.天平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最后落实到实验课主题“今天我们就学习使用天平测量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方案二:教师将一些邮票、丝线、大头针、食用油实物展示给学生(也可展示图片),提问“如何称出一张邮票的质量?一卷丝线的质量?一个大头针的质量?一勺食用油的质量是多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入新课.
(二)新课教学
1.练习天平的调节
(教师可将幻灯片投影到屏幕上,或使用视频,演示天平的调节.)
把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向学生指明:放天平时,要合理安排实验中各种仪器在桌面上的合理布局,仪器的摆放位置应便于操作,实验过程中不能再移动天平,否则需要重新调节.
指导学生观察游码、标尺,认识最小刻度值,并把游码拨到零刻线的位置.
把游码拨到零刻度线,观察一下指针偏向哪边,确定螺母的调节方向,再调节.
学生练习调节天平,教师巡视指导.
调节天平的操作结束后,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归纳总结出“在调节天平过程中,若指针偏向标尺右侧,就需要将平衡螺母向左端旋动,若指针偏向标尺左侧,则需将平衡螺母向右侧旋动.
明确:所谓天平的平衡,就是调节横梁螺母观察天平指针的摆动是否相对分度盘中间位置静止或等幅摆动.
2.实验:练习使用天平测量固体的质量
提问:用天平称量物体的质量时,被测物体应放在哪个盘里?砝码应放在哪个盘里?用什么方法拿取砝码?
明确: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调节天平先让天平平衡,而当在左盘里放入被测物体时又破坏了这个平衡,再通过加减右盘中的砝码和移动游码使天平再次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此时右盘中砝码的总质量数加上游码在标尺上所对应的刻度值就等于被测物体的质量.
注意:放入被测物体后,使天平再次达到平衡的过程中只允许加减砝码和移动游码,决不允许再旋动平衡螺母.
引导学生设计测固体质量的记录表格
长方木块(g)
长方铝块(g)
长方铁块(g)
学生测量开始,教师巡视指导.
提醒学生实验时,要爱护仪器,小心谨慎地操作,认真进行测量,细心真实地记录测量结果,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
3.实验:用天平称液体的质量
用天平称液体的质量时往往需要称一定体积的液体的质量.这时就需要我们测出液体的体积,测液体体积的仪器是量筒或者量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量筒和量杯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1)量筒和量杯的使用
教师利用实物介绍什么是量筒,什么是量杯,然后让学生观察它们的构造,并指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
请同学说一下量筒和量杯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它们上边都有刻度,每隔一定数量的小刻度就有一个大刻度,上边标着数值,最上边标有字母ml.老师讲解“ml表示毫升,1毫升是1立方厘米”.
由学生归纳总结量筒和量杯的不同点.
这时教师用投影仪打出量筒和量杯的画面让学生观察(投影片应做成复合片,可以复合不同的液面,复合人观察时的视线),以强化学生对量筒(杯)的认识.并请学生说出投影幕布上所显示的量筒、量杯的最大刻度和最小刻度值.
请同学们往量筒中倒一些水,观察液面形状,使用量筒测液体体积时,应注意:
①液面的形状是凹形的.
②用量筒测液体体积时,要以凹形水面底部为准,视线要与凹形水面底部相平.
③要把量筒(杯)放在水平桌面上观察.如果量筒中装入水银,则液面是凸起的,观察时应以凸形液面顶部为准.
教师打开投影仪,用复合片显示几个不同位置的液面,让学生练习读数(包括凸形)
(2)测量液体的质量
在教师指导下启发学生认识用减液法测一定体积的液体质量的方法.具体步骤是
①在烧杯内倒入一定量的液体(体积数应大于要求测的液体体积),用天平称出烧杯和液体的总质量,设它为
②将烧杯中的液体倒入量筒中,使量筒中液体的体积达到要求的体积值,比如100ml.
③用天平称出烧杯和烧杯内剩下的液体的质量,设它为
④100ml液体的质量就等于减
(3)引导学生设计用天平测液体质量的记录表格
空烧杯的质量(g)
烧杯和水的质量(g)
水的质量(g)
学生开始实验,教师在同学中间巡视、指导.
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把桌子上的所有实验器材整理好,并摆放整齐.
(三)总结、扩展
请同学们回答“想想议议”中的问题.指出我们无法直接用天平称出一张邮票的质量,但我们可以称出若干张相同邮票的总质量,用质量数除以张数就是一张邮票的质量.
介绍“累积法”.
学习长度测量时,测一张纸的厚度使用的方法和测一张邮票的质量的方法是相同的.虽然一个是测物体质量,一个是测长度,但思路一样,都是用累积的方法.
提问“今天的实验中称的木块、铁块、铝块,体积大小是相同的,但它们的质量是否相同?水、酒精的体积都是100ml,但它们的质量是否相同?从测量值可以看出不相同,这是为什么?请同学们回去考虑.”为下一节课“密度”的教学打下伏笔.
探究活动
质量测量精确度
【课题】调查质量测量的精确度
【组织形式】学生活动小组
【活动流程】
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
【参考方案】
各种质量的测量工具的不同场合下使用其精确度,例如托盘天平测量中药的质量、物理天平测量金的质量等.
【备注】
1、写出探究过程报告.
2、发现新问题.
自制测量工具——天平
【课题】自制测量工具
【组织形式】学生活动小组
【活动流程】
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
【参考方案】
可选择各种方便易找的材料制作天平,与实际天平对照,努力改进,提高精确度.
【备注】
第9篇:天体物理范文
从那时开始,人们知道了关于中微子的很多东西。对中微子性质新的理解总会使人们对于整个基本相互作用领域带来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费米最早的简化模型的尝试直到今天标准模型的建立,中微子的许多信息从加速器、反应堆,以及后来从太阳系和大气环境实验研究中大量地积累起来。而今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中微子只有三种,它们具有极其微小的质量,而且通过振荡彼此转换。
近年来中微子物理的突破性进展主要来自天体物理。特别是人们发现中微子在宇宙膨胀中不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且通过它们与其他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引力,对于宇宙演化有着很多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宇宙膨胀历史的研究,对于不同能量和时空标度的中微子的性质提供约束。而检验中微子性质的巨大舞台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微子宇宙学。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是理论与实验粒子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研究的交汇点,在这个迷人的领域中,不同背景的专家们找到了共同语言。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天体物理学的一个活跃的分支。如果说20年前,中微子宇宙学还处于早期阶段,理论家们还只能满足于数量级的估算,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的观测手段给出的结果要求细致得多的理论分析。
本书从中微子的方方面面对宇宙的历史给出综合介绍。作者们撰写本书的指导原则是力求阐述所涉及中微子现象的主要物理思想,而不是罗列数不胜数的繁杂现象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主要的关注焦点是标准中微子宇宙学。
全书内容分成7章:1.中微子物理基础; 2.标准宇宙模型概览;3.宇宙早期的中微子;4.MeV阶段的中微子; 5.宇宙微波背景时代的中微子;6.最近的时代:中微子和结构形成; 7.宇宙学中微子之今天。
作为宇宙学、天体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这本自成一体的专著中,作者们把中微子在宇宙学中作用的各个方面汇集一起,从中微子物理基础开始,清晰地阐述了标准宇宙学模型和膨胀宇宙中的统计力学,按照编年顺序介绍从很早开始到今天中微子的历史。这部新颖而丰富的著作无疑会引起在天体物理、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领域从事理论或实验研究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极大的兴趣,对于相关领域更广泛的读者,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