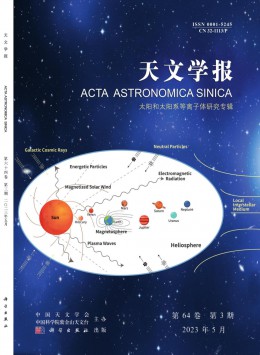天体物理学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天体物理学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ISSN Print: 2161-4717
ISSN Online: 2161-4725
Aims & Sc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IJAA) is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publication and public discussion of high quality original research in all the fields of astrophysics and space sciences and related technology. All the manuscripts must be prepared in English and are subject to a rigorous and fair peer-review process. Generally, accepted papers will appear online within 3 weeks followed by printed hard copy.
The journal publishes original pape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fields:
第2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吸积盘是围绕中心体转动的等离子云,这些等离子云逐渐螺旋式下降,被巨大天体吸积,比如黑洞。黑洞是恒星崩塌时聚集成的高强度引力场。这些崩塌的恒星周围是事件视界,在此边界以内的光无法逃离。吸积盘朝事件视界的方向转动时,为宇宙中最亮、最活跃的电磁辐射源提供能量。
银河系中央存在一个巨大黑洞。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黑洞位于人马座,便将此黑洞命名为“人马座A*”。人马座A*的引力质量为太阳的400万倍。然而,围绕该黑洞的吸积盘的等离子体螺旋下降到此黑洞时辐射效率异常低,也就是说,等离子体释放出的辐射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吸积盘的活动那么慢呢?”论文第一作者马修・昆茨提出了问题。马修是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方向的助理教授,也是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的物理学家。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和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詹姆斯・斯通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论天体物理学学科负责人艾略特・奎塔特考虑了人马座A*超高温黑洞吸积盘的特性。他们认为,该吸积盘的等离子体不仅温度极高,而且异常稀薄,这导致它们之间不会发生碰撞。也就是说,等离子体内的质子和电子的运动轨道很少出现交叉的情况。
缺乏碰撞能力是人马座A*黑洞吸积盘区别于其他吸积盘的显著特征。其他吸积盘也环绕黑洞转动,辐射更多且更明亮,亮度越高吸积盘内的等离子体越容易碰撞。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曾将吸积盘的碰撞过程用许多公式呈现出来,这些公式将等离子体视为导电的液体。但是昆茨教授指出,“这种模式不适用于环绕超大黑洞的吸积盘”,因为这些公式无法描述内部不发生碰撞的黑洞吸积盘变得不稳定且呈螺旋形下降的过程。
为模拟人马座A*黑洞吸积盘的转动过程,昆茨教授及其合作者不再运用先前的公式(那些公式将相互碰撞的等离子体的运动视为一种宏观渗流)。相反,他们采用了一种物理学家称为“动力学”的方法,系统追踪这些不会相互碰撞的单个粒子的运行轨迹。为了实现这一方法,昆茨教授、斯通教授及哈佛大学讲师白雪宁共同设计了Pegasus计算机编码,并用它生成了一套方程式,能够更好地模拟超大质量黑洞吸积盘的运行状态。
第3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早在1915年,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此后这一直是我们理解宇宙的理论基础。按照广义相对论,宇宙只能收缩或者膨胀,不可能稳定不变。那么宇宙究竟在收缩还是在膨胀呢?如果膨胀,其速度是否恒定?是在减慢或是还在加速呢?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威尔逊山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投入了使用,天文学家们发现几乎所有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他们发现当光源远离我们而去时,光的波长会被拉长,而波长越长,它的颜色就越红,这被称作“红移(redshift)”现象。目前对红移现象的解释为:速度造成红移。比如,当一辆汽车向我们奔驰而来时,它的喇叭声尖锐刺耳,因为汽车的高速运动使声波波长被压缩,波长变小,听者接收的频率变高。相反,当汽车离开我们飞驰而去时,它的喇叭声则低沉幽缓,因为汽车的离去使声波波长被拉长,波长变大,听者接收的频率变低,简称多普勒效应。20世纪初,天文学家斯里弗对旋涡星云光谱做了多年研究,发现了谱线红移现象。在斯里弗观测的基础上,哈勃与助手赫马森合作,对遥远星系的距离与红移进行了大量测量工作,发现远方星系的谱线均有红移,而且距离越远的星系,红移越大,于是得出重要的结论:星系看起来都在远离我们而去,且距离越远,远离的速度越高。这被称为哈勃定律(Hubble’s law)。他认为:整个宇宙在不断膨胀,星系彼此之间的分离运动也是膨胀的一部份,而不是由于任何斥力的作用。这一发现直接导致俄裔美国天体物理学家伽莫夫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提出。伽莫夫认为,我们的宇宙诞生于约137±2亿年的一次大爆炸,宇宙开始于高温、高密度的原始物质,最初的温度超过几十亿度,随着温度的继续下降,宇宙开始膨胀。星系天体的退行原因正是这次宇宙大爆炸的冲力导致的。
从此之后,天体物理学界一直都认为宇宙是在以一个恒定的速度膨胀,直到天体物理学家萨尔・波尔马特、科学家亚当・里斯以及物理学家布莱恩・施密特这三位科学家于1998年向外公布:宇宙的膨胀速度不是恒定的,更不是越来越慢,而是不断加速,即越来越快。他们通过寻找太空中的标记,研究宇宙膨胀问题。这些标记就是爆炸的恒星――1A型超新星。由于其非常亮,超新星被用来确定距离。只要找到足够的1A型超新星,就能测量它们的亮度。亮度较高的超新星距离比较近,亮度越来越弱的超新星,一定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亮度很低的超新星,距离就很遥远了。1A型超新星同时有个重要的特点,它们爆炸的亮度都是相同的,超新星的光度曲线普遍都具有一个相同的光度峰值,这使得它们可被用作辅助天文学上的标准烛光。这是因为它们形成的过程都一样,每个1A型超新星都是在相同质量时爆炸。因此,宇宙各处都有相同的亮度和可见度。三位科学家找到若干个1A型超新星,并测量它们远离我们的速度。通过比较不同时空的超新星的位置和年代,便能计算出宇宙的膨胀是否在变慢。他们得到了惊人的结果:宇宙的膨胀速度并未变慢,反而是正在加速。这一惊人的发现意味着,宇宙不会停止膨胀,反而在不断加速膨胀。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这个结果的出现直接撼动整个天体、物理学界,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宇宙大爆炸所产生的冲力在引力的作用和牵制下,星系天体的退行速度应该渐于趋缓直至稳定平衡,可是这三位科学家的发现却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相互矛盾,如何解决、诠释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呢?物理学家们认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宇宙之中存在着一种与引力作用方向相反(反引力作用力)、至今人类还没有发现的神秘力量!物理学界把这种与引力作用方向相反、至今人类还未知的神秘作用力称为“暗能量”,并且认为,正是这种“暗能量”推动星系天体快速膨胀退行。宇宙膨胀的这种加速度暗示,在蕴藏于空间结构中的某种未知能量的推动下,宇宙正在分崩离析。这种所谓的“暗能量”占据了宇宙成分的绝大部分,含量超过70%。它的本质仍然是谜,或许是今天的物理学面临的最大谜题。因而现代天文学认为:我们的宇宙最初的膨胀是由于最开始的大爆炸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物体由于具有惯性,而在原始大爆炸之后继续膨胀。后来,由于物质之间的万有引力的作用,这个膨胀开始变慢,可是在大约100亿年前,宇宙中的“暗能量”在与万有引力的交锋中占据上锋,于是宇宙的膨胀又开始加速了。
第4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1983年出生,2006年获南京大学物理系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学习。2008年赴英国留学,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剑桥大学天文和宇宙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描述宇宙起源的完整理论,它应该可以被所有的人所理解和掌握,而不仅仅是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它也意味着,人类理性获得的巨大成功,和人类透析上帝思考的伟大智慧。
――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
浩渺的宇宙,总是激起人们无限的遐想与追问:宇宙从何而来,宇宙如何演化,宇宙将走向何方,在宇宙中我们是否是孤独的人类?要找出这些神秘问题的答案,只能诉诸于复杂和抽象的物理理论,以及精确的实验技术。当我在灿烂的星空下仰望苍穹,心中升起种种猜想和疑惑时,一条世界重大科技新闻,将我的目光和兴趣聚焦到了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
在南大确定研究方向
1998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2个研究组,通过对超新星光度距离的研究,发现了宇宙暗能量的存在。通过分析,他们发现,距离太阳系远处的超新星,正加速向我们离去。从1929年起,哈勃(Edwin Hubble)就告诉人们,远处的星系正向我们退行,即宇宙在膨胀。然而由于万有引力,物质之间会不断地吸引,以及塌缩。因此,人们认为宇宙即使膨胀,也应该减速膨胀。然而,1998年的发现却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预期:星系正在加速向我们离去,宇宙在加速膨胀!
那么,是什么神秘的物质驱动宇宙加速膨胀的呢?这便是举世闻名的“暗能量问题”。
2002年,我进入南京大学学习。南大的学风很好,较少受到社会上浮躁之风的影响。上大学期间,物理系组织的针对本科生的报告,我基本上每一次都去。南大物理系的优势在于凝聚态物理和微电子物理(应用物理),所以报告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对于天体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学方面的报告,却非常少。
凝聚态物理的报告,比如纳米科学、晶体生长、磁性材料等等,其实很有意思。坦率地说,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我总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研究的。直到2004年,一次报告将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这一年,美国宇航局和普林斯顿大学的WMAP卫星实验组,了该卫星测量宇宙学基本常数的数据,确定了宇宙中暗能量占74%,暗物质占22%,可见物质只占4%。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李小源研究员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杜东生研究员作了一个“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的科学”的报告,介绍了国际上这方面的前沿进展。他们将微观世界的基本粒子和整个宇宙的演化相联系,解释当今宇宙的星系、星系团结构是如何和宇宙及早期的微观世界的动力学相联系的。那个晚上精彩的演讲,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于是便认准了我感兴趣的领域。南京大学离紫金山天文台(办公楼在南京市的北京西路,观测站在紫金山上)不远,陆院士领导的天体物理研究组每周都有讨论,我争取每周都前往参加讨论,虽然那时候对宇宙中结构形成还不是很清楚,但对于暗物质和暗能量问题已有一定的了解。
我决定在毕业以后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理论所”)去攻读理论天体物理学研究生。让我感到庆幸的是两件事:(1)我在大学第四年期间,已经把研究生的理论物理学课程全部跟班学习了一遍,并且参加了考试,其中有一门还得了满分。这让我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有了一定的基础;(2)由于当时成绩还可以,我被保送进入理论所读硕士研究生,这使得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和思考一些专业问题。如果没被保送而需要参加统考的话,我会花费很多时间去准备“考研”。我面试的时候,理论所在全国一共招收20名学生,如果我没记错,我当时面试总成绩是99分,排名第一。我后来见到了李淼教授(弦理论专家),我还跟他讨论过一个面试时我遇到的量子力学的问题。
难忘中国科学院
我到了中科院理论所之后,并没有直接进入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而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学习广义相对论的唯一性定理的知识。后来事实证明,这部分时间花得不是很值当,因为该理论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没有太多可以开拓的空间。我还在宇宙的扰动理论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成效也不是很大。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被人们非常好地发展起来了,可做的新东西不多。这时我开始逐渐地思考,以后的研究该怎样定位,怎样才能做一些有新意,比较独特的研究。
暗能量的理论问题,人们尚未把它搞清楚,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于真空能(Vacuum Energy)的本质还不甚了解,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基本的量子场,或者是由某种时空几何决定的。这其实是当今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头号难题。因此,在没有基础理论上取得根本进展的前提下,人们试图去构造一些唯象(即现象学上的解释)上的模型,去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当然,这些模型目前都只是唯象上的近似,并非已经得到公认的基础理论。但是研究它们,对于天文观测也是一种促进,因为你知道了不同的模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宇宙观测的预言,可以期待着在天文的一些观测上得到验证或排除。
我花了一段时间研究了全息暗能量,探讨了它在观测上的一些可能的预言,以及利用当时最新的天文观测数据(超新星、微波背景辐射等)去限制了这个模型,并且首先用统计学上的贝页斯证据(Bayesian Evidence) 去计算了它与宇宙常熟模型的之差等等。后来,在美国洛杉矶2008年初举办的“暗物质与暗能量”会议上,我应邀报告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觉到,要真正地探究这些宇宙中的神秘物质,找到宇宙的起源与结构形成的一些实验上的关键证据,必须掌握丰富的天文观测资料,并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方法。在这方面,国内的研究实力很有限;应该说,不仅是中国,整个亚洲在这方面的研究都非常薄弱;于是,当2008年初我拿到一笔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时,我决定赴剑桥大学留学。
英国的留学生活
能来剑桥大学,实属幸运。剑桥有一个研究实力很强的天文研究所(我现在所在的研究所),几乎在相关的领域,研究所都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比如唐纳德・耶丹・贝尔(Donald Lyden-Bell)(星系、黑洞、广义相对论)、马丁・里斯(Martin Rees)(宇宙学、星系)、安德鲁・费边(Andrew Fabian)(X射线与黑洞)、罗伯・肯尼卡特(Rob Kennicutt)(恒星形成),以及我后来的导师乔治・艾夫斯塔修(George Efstathiou)(宇宙学)。就算是一些资历较浅的研究员也相当知名。另外,离研究所不远,还有另外2个研究所:霍金的“理论宇宙学中心”,以相对论和宇宙弦(Cosmic String)的研究而出名;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天体物理研究组,以发现脉冲星和开创射电天文学而闻名。这些单位之间经常会有一些讨论。
这几年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宇宙微波背景的研究(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以及星系和星系团等宇宙中大尺度结构的形成的研究。为什么人们要研究这些东西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试图去了解宇宙中结构的形成,即我们所观察到的星系团、星系、恒星系统,究竟是如何演化来的,即动力学上是如何形成的。因此,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要素是必须要了解的:星系和恒星体统形成的初条件是如何,以及动力学方程是怎样的?而宇宙之所以复杂,就是在于动力学上,有一些很复杂的、尚未被科学家搞清楚的物理学过程(比如重子物质如何与暗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等等),这会给研究结构形成的动力学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所采取的办法主要有2个:一是观测上要掌握大量的实验资料,尤其是对不同种的星系和恒星系统的资料都要掌握;另外,在理论上,通过数值模拟,可以计算那些不同的微观机制(比如上面提到的相互作用),究竟会对最后形成的星系和恒星系统有多大的影响,从而通过与观测对比,确定下来可能的机制。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的一些对星系的速度场的研究,主要遵循的是这个思路。
另外,对于结构形成初条件的观测,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方面的观测量,会直接影响到对早期宇宙初条件的限制。它所发生的物理学过程是这样的:宇宙在极早期由于量子效应会产生一些时空上的量子涨落,而这些涨落经过宇宙的演化会“进化”为宇宙中不同物质密度的涨落(比如光子、可见物质,以及暗物质等等)。那么通过对于这些物质涨落能谱的观测,我们就可以推测在宇宙的极早期,究竟是哪些量子效应在起作用,从而对宇宙的起源问题给出一些有意义的启示。这对于理论物理学家会是非常感兴趣的内容,因为理论物理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大统一”问题(Grand Unification Theory),就是要去寻找能够统一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力,以及引力的基本理论,而这种理论描述能量极高的物理,而通常的地面的加速器提供不了这么高的能量。但现在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却有可能在宇宙中,找到验证这些理论的办法,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沿着这条线,我也持续在做一些研究工作。
由于卫星、地面望远镜等天文观测手段的不断加强,有一些领域不断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它们有可能在未来提供一些解答难题的关键性的实验证据,比如:
1.再电离(Reionization):宇宙中的原初星系是如何形成的。
2.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s):验证广义相对论,寻找引力在早期宇宙的效应。
3.太阳系外行星问题(Extra-solar Planet):太阳系外的行星,它们的环境如何,有没有生命的存在等等。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很宏大,都不是人们在几年内就能够轻易弄明白的,因为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如果能够被观测到,都意味着天文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时刻思考着宏伟的物理图像,并且时刻注意这方面的观测和实验上的突破与新的证据,以及理论方面的进展。
我时常在想,怎么样才能真正地认识大自然,了解大自然。我逐渐找到了一条方法论,就是去认识大自然的结构,认识大自然的动力学过程。浩渺的星空,就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探索的空间,给了人们以“重新发现”大自然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文学是一门有着无穷宝藏的的学科,而人类就像是在捡着贝壳的孩子,去试图勾勒一片大海的美丽图景。
第5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1、文学类:比较文学、古典学、语言学、哲学、神话学、视觉环境学。
2、社会科学类:人类学、历史与文学、社会学、心理学。
3、科学类:应用数学、天体物理学、化学与物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4、工商管理类:金融与经济学、建筑学考古学、生物化学、神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临床医学。
(来源:文章屋网 )
第6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北极星总是坐落在北极的上空,这是因为它与地轴成一条直线。在夜晚的天空中找到位于小熊星座的北极星,你便可以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确定方向。
为了测量北极星的质量,德国波恩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Hilding Neilson和同事对它的脉冲进行了分析。
研究人员注意到,这颗恒星在大约4天的周期中会变亮和变暗,他们同时还分析了周期长度的变化。与其他恒星一样,北极星由包裹着一颗内核――这里是发生核聚变的地方――的气体所构成。
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引力将最外层的气体向内牵引,北极星在其表面下形成了一个不透光层,从而使其亮度变暗。随后光线便会在不透光层下聚集,并像水蒸气顶锅盖一样推动不透光层。最终光线加热不透光层,导致其膨胀并更为透明。北极星也就变得更大更亮,直至外层气体向内塌陷,进而再次开始新的循环。
然而这4天的脉动并非恒定不变的:1844年便大约比现在慢了12分钟。并未参与此项研究的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的天文学家David Turner,之前曾与同事对截至2004年的北极星脉冲历史记录进行了汇编。如今,Neilson和同事又将过去10年的观测结果加入其中。这一漫长的记录表明,从1844年至今,北极星的脉冲每年变慢4.5秒钟。
这一变化率意味着恒星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Neilson和同事推测,如果北极星是一颗更老的恒星,正在熔化或“燃烧”氦核,那么它的脉冲则因为缩减得太快而无法匹配标准的恒星进化模型。Neilson说:“只有当恒星正在失去大量质量时,这一矛盾才能够得到解决。”北极星的这种质量损失会使积聚的光线冲破不透光层,并减缓恒星的脉冲速度。
研究人员认为,北极星每年损失的质量大约相当于地球的质量,或不足其自身质量的一百万分之一。研究人员在于2月1日出版的《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第7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据国外媒体报道,早在1572年11月,丹麦天文学家和占星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发现了仙后座中的一颗新星,它是400年来能用肉眼看到的最亮的超新星,并被命名为“第谷超新星”。现在,由美国宇航局(NASA)的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通过多年收集到的数据显示这颗破碎恒星的残骸在高能量的伽玛射线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这一发现的研究报告发表在12月7日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这一发现为天文学家提供了另一个了解宇宙射线源头的线索。宇宙射线是亚原子粒子,主要由质子组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宇宙空间运动。宇宙射线的源头及其加速到如此高速的机制一直是长期存在的谜团,因为穿越星系的旅途中,带电粒子加速通过银河系时很容易被星际磁场偏折,这使得它们的轨迹被搅乱,科学家无法追踪到它们的源头。该研究报告的首席作者、意大利巴里大学和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的弗朗西斯科•焦尔达诺(Francesco Giordano )说:“幸运的是,宇宙射线撞击星际气体和星光时产生了高能量的伽玛射线辐射,这些伽玛射线直接从源头到达费米太空望远镜。”
更好地了解宇宙射线的源头是费米伽玛射线太空望远镜的主要目标之一。费米上的大视场望远镜(Large Area Telescope,LAT)会每三个小时对整个天空扫描一次,逐步建立起一个不断深入的伽玛射线天空。由于伽马射线是能量最高、穿透力最强的一种光线,从辐射源直线朝我们而来,因此,它可作为粒子加速的路标。此项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美国Kavli粒子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所(the Kavli Institute for Particle Astrophysics and Cosmology,KIPAC))的天体物理学家斯特凡•芬克(Stefan Funk)说;“这种检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支持超新星残骸可以使宇宙射线加速的观点。”
1949年,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 )表示,能量最高的宇宙射线在星际气体云磁场会加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天文学家发现超新星残骸可能是最佳的宇宙射线加速地点。当恒星爆炸时,它会转化成一个超新星残骸,爆炸冲击波范围内的高温气体迅速膨胀。科学家预计冲击波前两侧的磁场可以捕捉它们之间的粒子,相当于亚原子乒乓球比赛。合著者之一、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巴黎第七大学(Paris Diderot University )的梅莉塔•纳曼•果多(Melitta Naumann•Godo )说:“一个超新星残骸的磁场比地球的磁场弱得多,但它们扩展成一个广阔区域,最终跨越数千光年,它们对带电粒子的形成起主要的作用。”带电粒子来回穿梭于整个超新星激波,并在每次穿梭时获得能量。它们最终摆脱其磁约束,逃脱超新星残骸,最终自由漫游于星系之中。费米大视场望远镜的持续观测对这种情况提供了额外的证据。许多年轻的残骸,如第谷,往往比老的残骸产生更多的高能量的伽玛射线。斯特凡•芬克补充说:“伽玛射线的能量反映产生加速粒子的能量,我们预计年轻的残骸内有更多的宇宙射线不断发展到拥有更高的能量,因为冲击波和它们的紊乱的磁场变得更强。” 相比之下,老的残骸具有较弱的冲击波,不能保留能量最高的粒子,大视场望远镜没有检测到相应能量的伽玛射线。
1572发现的“第谷”超新星是天文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颗超新星连续15个月可见,挂在天上没有移动迹象,表明它远远超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范围。现代天文学家估计,该超新星残骸距离地球9 000光年至11 000光年远。经过两年半时间的观测,大视场望远镜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十亿电子伏特(billion electron volt)的伽玛射线辐射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区域原来是“第谷”超新星的残骸,为便于比较,可见光的能量约2电子伏特至3电子伏特。KIPAC的研究生基思•贝茨托尔(Keith Bechtol)是注意到它们的潜在联系的研究人员之一,他说:“我们认为,‘第谷’超新星残骸闪光可能是费米一个重要的发现,它可能是我们确定一个光谱特征表明宇宙射线质子存在的最好的机会。”
该科学小组的模型以大视场望远镜的观测结果为基础,连同地面基础设施、无线电和X射线数据映射的高能量万亿电子伏特(trillion electron volt)伽马射线。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被称为介子产生的过程最好解释这种闪光。1)接近光速运行的质子碰撞到较慢移动的质子,这种交互作用创建一个不稳定的粒子―介子,它的质量只有质子的14%。2)在极短的时间内,介子衰变成一对伽玛射线。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残骸内的某个地方,质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的速度,然后与慢粒子相互作用产生伽玛
射线。
第8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1、文学类:文学、比较文学、古典学、语言学、东亚学、近东学、印度学、哲学、英语、非洲学与非洲裔美国人学、神话学、条顿民族学、建筑艺术历史、罗曼斯语文学、斯拉夫语文学、视觉环境学、性别研究;
2、社会科学类:历史、人类学、历史与文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历史、社会学、环境、自然科学与国家政策、心理学;
3、科学类:数学、物理、应用数学、天体物理学、化学、化学与物理、生物化学‘人类进化生物、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机体进化科学、人类发展科学、人类物理、工程技术、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统计;
4、研究生专业:工商管理、金融与经济、建筑、经济、化学工程、电子工程、教育、计算机科学、考古学、生物化学、人类学与地理、神学、法律、美术、现代史、人类语言产生研究、自然科学、心理研究、数学及电算、工程学、社会科学、数学、生物科学、临床医学、管理、物理、音乐、哲学、政治学。
(来源:文章屋网 )
第9篇:天体物理学范文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站报道,一组志愿者日前借助美国宇航局进行斯皮策空间望远镜数据的检查,在我们的银河系银盘结构中发现了超过5000个“气泡”结构。这是年轻高温的恒星“吹出”的尘埃和气体气泡结构,这些气泡说明这些位置正有新生的恒星诞生。
超过3.5万名“公民科学家”翻遍宇航局斯皮策望远镜的红外波段观测数据,他们参与的是一项旨在从海量数据中帮助科学家们找出这些气泡结构的志愿者参与项目。到目前为止这些志愿者们找出的气泡结构已经超过了之前被发现的气泡结构总数的10倍以上。
艾利・布列斯特(Eli Bressert)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博士研究生,在设在德国境内的欧洲南方天文台以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攻读专业课程,他是有关这一研究的论文合著者,他们的论文已经被提交给《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他说:“这些发现让我们感觉银河系在恒星新生方面似乎是一个比我们原本认为的更加活跃的星系。银盘就像香槟酒一般,到处都是泡沫。”
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计算机程序很难准确地从图像中识别出这些气泡结构。但是对于这些暗弱纤细,有些地方破缺的环状体,人类的肉眼和大脑却能进行非常精确的识别,于是“银河系项目”(Milky Way Project)应运而生。它邀请广大公众参与到这些图像的识别工作中来,并且为了确保准确率,规定必须经过5名参与者确认,某一被认为是气泡结构的图像才能被确定并编目。借助一种复杂的画图工具,参与的志愿者们可以在斯皮策望远镜拍摄的大量红外图像中任何他们认为是气泡结构的位置上做上标记,并随后移交给下一位志愿者重新检视并进行判断。
罗伯特・辛普森(Robert Simpson)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天文学博士后研究员,他是银河系项目首席科学家,同时也是这一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他说:“银河系项目是一项尝试,即将斯皮策望远镜获取的海量美丽数据提取出来,并让信息的提炼工作变成一种公众参与的有趣的事情。”
所有这些数据都源自斯皮策望远镜的GLIMPSE和MIPSGAL两个巡天项目。这些巡天获取的数据覆盖了天空中一道狭长区域,宽130度,而高度仅有2度。如果你伸出手对准夜空,你的食指的宽度大致就相当于这2度的张角。这两项巡天项目都覆盖了银盘区域,并直指银河系的核心。
志愿者们标记出的气泡结构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距离的远近不同,以及当地气体云团实际大小和形态的差异。这些结果帮助天文学家们更加精确地在银河系中确定恒星诞生的位置。目前正在进行探讨的一项课题是“触发式恒星新生”,即由于大质量恒星的爆发压缩周遭气体尘埃云,导致在这些区域出现物质聚集塌缩形成新生恒星。
马修・帕维奇(Matthew Povich)是这份论文的合作者之一,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是一位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天文与天体物理学博士后研究员,他说:“银河系项目的成果显示这些气泡中超过2/3拥有等级结构,在较大型的气泡内部或四周几乎都发现了较小型的气泡。这证实了新一代恒星的诞生是受到了较大型爆发事件的触发和影响。”
而这些气泡的不同分布同样暗示了银河系的精细结构。比如说,一些气泡数量突然上升的区域恰好和银河系的旋臂位置相吻合。或许最大的意外在于靠近银河系中心的区域气泡数量竟然相对较少。布列斯特说:“我们原本以为星系核心位置的恒星诞生密度是最高的,因为那里的气体密度最高。但是这项研究的结果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