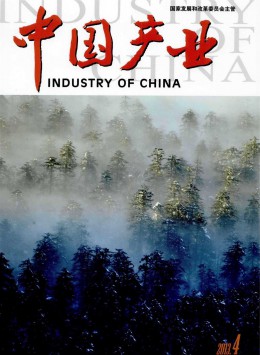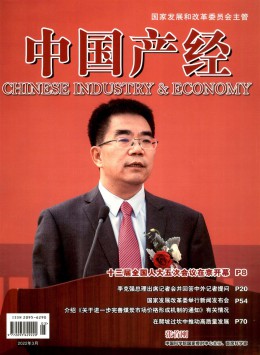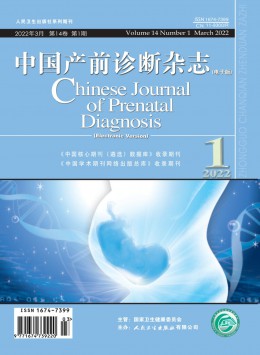国产刺客题材电影叙事策略探析

关键词:刺客题材电影;情节;人物;叙事话语
除《秦颂》《荆轲刺秦王》《英雄》等刺秦三大部外,国产刺客题材电影还有《刺秦王》(严幼祥,1940年)、《大刺客》(张彻,1967年)、《六刺客》(郑昌和,1971年)、《女刺客》(屠忠训,1976年)、《刺客》(苗述,2013年)、《大刺客之鱼藏剑》(韩凤泉,2015年)、《刺客聂隐娘》(侯孝贤,2015年)、《刺客记忆之血月》(陈保文,2016年)、《清宫大刺杀》(华山、程刚,1978年)等不少作品。国产刺客题材电影表现刺客群体的悲剧人生,涉及对人性与政治的反思、对封建与集权制度的考察,对儒、道、佛、法各家思想的运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之相应,无论是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还是叙事话语,刺客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也呈现出多元多貌的动态发展趋势。
1情节设置:杀与不杀的纠结
刺客题材电影归属历史大类,历史题材电影的情节设置在史事依违、结构编排乃至整个的体类判定方面是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与弹性的。刺客题材电影中的题材,大体都有史实依据,导演们多半也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处理这类题材,因为学者们通常认为:真正的历史剧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艺术表现的基础上,发展历史的精神,寻求古今之汇通,具有一定史事性的戏剧”[1]18;“所以它应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凸显历史精神、认清民族立场、张扬文化价值、提升哲学内涵、营造诗意氛围。而这重大的使命最好能通过最具感染力的悲剧来实现。”[2]与此相应,刺客题材电影也多采用传统戏剧式的结构。曾经实在,但不等于不可以后来想象,而中国式的悲剧,向来都是悲喜交加的。所以《秦颂》虽有高渐离与秦始皇这两个真实的名字与荆轲刺秦余绪的历史踪影,具体情节却多为虚拟构想甚至荒诞不经,说什么羸政与高渐离同吃一母乳汁长大,说什么高渐离为求速死而强奸栎阳公主,没想到瘫痪的公主反因此站立起来,这样的政治寓言既晦涩难懂,又多少有点鄙贱污秽。这种任意的改编有助于艺术真实的表达,但有时也难免生硬。如苗述《刺客》的结尾,设置有楚王预派三千死士潜入宫中的情节,这样的情节其实经不起推敲:雷靠死拼就可以闯入魏王宫中?而魏宫中楚王正向魏王献媚,魏楚两王对外面的急战居然全无察觉?如果没有惊惮的护卫,魏王早已被雷所杀,又何须动用三千死士?潜伏一人尚且不易,何况三千死士?在其余卫兵起来之前,正好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供两兄弟格斗?魏王、楚王的品性与真实目的,甚至魏、楚、秦三国战事及其余人事都飘忽不定,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演绎导演事先定下的关于刺客悲剧命运的主题,但这些直奔目的的急切表达难免生硬僵化。在结构的编排上,刺客题材电影秉承传统戏剧式结构,或有意尝试罗生门式叙述技巧,或刻意淡化故事情节。《荆轲刺秦王》有编年版,有人物版,以人物言行间繁复的戏剧化矛盾来强化电影的悲剧意味。赵姬为秦灭燕而出谋划策,但不能眼看着秦国的军队攻打赵国的都城,因为她是赵人,赵是她的祖国。赵姬以为有了嬴政,“百姓就不用流血”,但当她看到秦的军队“把人绑在房梁上吊死,绑在桌子上射死,把村庄夷为了平地,城池烧成废墟”,便质问嬴政:“你跟那些王有什么不同?”但她终归救不了赵国,也改变不了嬴政。嬴政的矛盾是更根本的矛盾,电影说他以非秦后裔的身份率领秦军一统天下,原本是赵的后人而执意要灭了赵国,他一统天下让百姓安宁的目的或理由结果却演变为一路残杀,民怨沸腾。因为从小被逼过独木桥,他也让嫪毐过独木桥,在赵姬的请求下本打算放了赵国的小孩,可小孩唾面的举动又触发了他潜藏在骨子里的对赵国人的仇恨,最后将这些小孩全部活埋。处置生父吕不韦更是其人格分裂的集中展现。吕不韦说:“杀了我就是告诉天下人你不是我儿子,也只有杀了我才能告诉天下人你不是我儿子,因为儿子是不会杀自己父亲的。”嬴政说:“我不杀你,只要你告诉天下人我不是你儿子,等天下大定……”吕不韦反问:“天下不定,就没有父亲了吗?”这个时候司礼在旁反复提醒:“秦王嬴政,你忘记了秦国历代先君一统天下的大愿了吗?”吕不韦不得不悬梁自尽。吕死后,秦王叫了一声父亲,然后诏告天下,吕不韦叛逆,夺取封侯,诛灭九族。这个弑父情节,虽有司马迁所作的一点点近乎传说的记载,在电影中,却是被刻意强化后用来消除一统天下的历史包袱尤其身份障碍的。嫪毐的临终挣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直白:“交通外国,莫非你不是赵国的奶水喂大的?谋反,我谋反,你才是真正谋反。
当年秦异人在赵国作人质……可怜啊,一个号令秦国上下公卿百姓,统领秦军扫灭六国的竟不是秦人后裔,这还不是谋反?”一统天下是为了天下安宁,非秦后裔不能一统天下,所以天下未定,不能有吕不韦这样的非秦父亲,所以口口声声说不能杀他,最后还是逼他自杀并诛灭九族,这样的逻辑悖论又何尝不是历史与人性的悲剧?当秦王说“只要六国还在,战争还不会停止,天下就永不得安宁,百姓就永不得安宁,六国是一定要灭的”时,燕丹回了一句:“你怎么不说,只要秦国还在,天下就不安宁?”知微见著,也许就这么一句,足见《荆轲刺秦王》比其它刺秦电影更具悲剧性。作为刺客的荆轲也有矛盾的言行:他不分青红皂白刺杀盲女一家,为救偷食小孩却宁受胯下之辱;他说自己杀人,尤其杀天真无辜的女童,是罪人,最终又为了六国儿童免被无辜杀害而行刺秦王。电影的叙述也留了一点悬念给后来补叙,盲女也曾尝试杀他,并问他的名字,说杀人的人也有名字。荆轲坦言:“我是荆轲”。这样一来,名字既是荣誉,也可能成为负累。而荆轲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成为荆轲自己及后人当然也包括导演不断思索的问题。就连那个秽乱后宫、私生孽子的嫪毐,在电影里也以前半生猥琐如小丑,刑前凛然若丈夫的矛盾言行,展演着爱情与政治、名称与实际之间的多重背反。“人都以为我是贪恋富贵才惹来杀身之祸,其实只不过是你想作我的女人,我想做你的男人,夫妻一样过日子,要在民间这算什么,偏你是母后,这就难了,来世吧。不哭,一哭,倒像是咱们错了。”“不杀我的门客我就降!”嫪毐的儿子也是太后的儿子,不但不能享受王子的待遇,反被活活摔死。《荆轲刺秦王》就是以这种种冲突来结撰戏剧式的情节结构的。《英雄》以罗生门式的方式拼接了四个刺客的三种刺秦故事。一是无名自述利用情感纠葛一一击杀长空、飞雪、残剑以取得接近秦王十步机会的故事。二是秦王不信,推测真相:长空、飞雪主动献出生命让无名获得接近秦王的机会,残剑则为了飞雪也自动消失在无名剑下。三是无名再述超乎秦王想象的真相:残剑要无名为了天下放弃刺秦。最后无名击而未杀死于秦军箭丛,飞雪知刺秦未果挥剑刺残剑,残剑甘愿受死,飞雪随之徇情,长空封剑,秦王成就一统霸业。第一个文本强调为情所困、因情而死,情同时下的狗血剧,不乏世俗的市场。第二回故事以自杀方式获取刺秦机会,是荆轲以地图与人头使秦刺秦的翻版,是对传统叙述样貌与侠义精神的秉承。第三种叙述纠结于刺客内部的杀与不杀、无名刺秦时的实杀与假杀、秦王处决无名时的不忍与忍,凸显天下一统对人心的压力,也为无名背后的刺客留有死与不死的选择。就这样,《英雄》把荆轲刺秦的复杂心绪与可能行迹及多元结局分给四名刺客来承担,这种集成式的构想与编排可以尽可能满足全球时代与商业语境下不同观众与评论家的期待与允诺,虽然这部电影不乏虚假的撒谎、低级的挑拨与粗俗的报复。相较于《英雄》对故事的强情节化处理,《刺客聂隐娘》是有意淡化情节,追求抒情化、诗意化的表达效果的。故事平铺直叙、人物恬淡庸常、场景和缓琐碎、语言零散片断,完全不同于一般武侠片的固有风格,以致于大家认为这是票房失利的重要原因。[3]但这种以诗化思维、诗化场景、诗化语言呈现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性人伦的古老方式却为刺客题材电影的发展另辟了新境。
2人物塑造: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刺客题材电影是径以刺客形象的塑造为目的的,刺客形象的定位离不开历史渊源,更关乎时代背景与导演喜好,但终归要通过外在的形容、动作、言语与内在心志情怀来展现,故演员的选择也至关重要。从《刺秦王》中王元龙饰演的荆轲,到《秦颂》中葛优演的高渐离,从《荆轲刺秦王》中张丰毅演的荆轲,到《英雄》中李连杰、甄子丹、张曼玉、梁朝伟等扮的近乎无名的众刺客(无名、长空、飞雪、残剑),刺秦电影中的刺客形象由强转弱,由集中转分散。1940年公映的《刺秦王》以《史记》为蓝本,但加赋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相较于“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刺客形象,由军校出身以粗犷硬朗著称的王元龙饰演的荆轲形象被重构为为国家而死的民族英雄,从而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与价值。电影还虚构了荆母、可卿与胡姬三位女性形象,荆母为了坚定荆轲刺秦的决心毅然自戕,可卿的相知相恋最后也让位于报国救国,就连秦王身边的胡姬也成了正义联盟的情报员。诚如论家所言:她们“颠覆了传统的‘女为悦己者容’的女性形象,而以主动型的为救国牺牲和奉献自我的新形象呈现”[4]。《秦颂》选用喜剧名星葛优演高渐离,一开始就将高渐离的定位偏向为优伶而非刺客,而他的对手秦王嬴政却由柏林电影节的影帝姜文扮演,在视觉上就无法构成势均力敌的对抗,整部电影的悲剧意味也因之消减。或许这个形象猥琐、性格怪诞、行为疯癫、欲望张狂的艺人、臣子、友朋、亲人有助于说明人心的一统远难于疆土与政制的一统。人性的复杂在《荆轲刺秦王》的一众形象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与《秦颂》相比,荆轲与秦王的对比刚好掉了个头。在电视剧《水浒传》里把宋江演得哆哆嗦嗦、奴气十足的李雪健把嬴政也演得身形猥琐、性格扭曲,这个喜怒无常的秦王时常有放浪形骸的形容动作与歇斯底里的声音气息,完全颠覆了叱咤风云、伟岸高峻的传统始皇形象。而张丰毅演的荆轲倒是既伟岸坚毅,又慈眉善目,既孤傲清峻,又恬退隐忍。
他如巩俐演的赵姬、王志文演的嫪毐,周迅演的盲女,都有助于落实导演表现复杂人性的期待。《英雄》里的刺客,堪称华语明星的大组合,但这个大组合反倒模糊与分散了刺客的形象。在这个多元的组合里,有人坚持传统,反抗暴政,为知己者死,为悦已者容,有人幡然醒悟,由职业杀手变为劝谏天下安宁的和平使者、支持天下一统的国家英雄。这种多元组合既可以顾及到不同读者的认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意识形态的论议与风险,但隐含叙述者的倾向还是趋于和平与一统的,有论家说:“张艺谋并没有以英雄的个体身份与社会理想的对立来结构整个文本,而是让英雄从与社会的对抗中逐步走向与社会的和谐,从而消解了英雄的对抗性身份,建构英雄的规划性身份,让英雄获得与社会和谐一致的新生过程。”[5]台湾学者南怀瑾说圣人是要承担天下的烦恼,英雄则是将自己的烦恼给天下人承担,这种将帝王将相视为社会,又将英雄归顺于这种社会的作法,与其说是建构,不如说是消解。陈道明演的秦王,在《英雄》里端居王坐,以言语与无名相交,无异于明察秋毫的老吏与温顺睿智的教主,那些不可规避的私欲与暴力都被粉饰干净,而没有异议的秦王也刷新了我们对历史的成见。总言之,相较于《大刺客》(张彻)《六刺客》(郑昌和)《刺客》(苗述)《大刺客之鱼藏剑》(韩凤泉)等近于传统观念的人物形象,这几部刺秦电影中的刺客与国君形象都没有陈陈相因,而是力求有新的创制,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电影人物形象的长廊。《刺客聂隐娘》则更以其女性与人性的回归重塑着刺客的形象。电影中,聂隐娘去除了小说中的“玄幻之术”与“奇异之能”,也没有现代武侠剧中精彩纷呈的武打场景,连身份,也由《太平广记》中的“豪侠”转而为“刺客”,意在强调她的刺杀任务,而这身份与任务,又被置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情感纠葛之中,目的在于“为观众展现作为侠女的聂隐娘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矛盾情感,表现聂隐娘作为‘人’的一面”[6]。“人”的回归,就是主体意识的回归,这无疑是刺客题材主题的一大进步。
3叙事话语:淡妆浓抹总相宜
刺客题材电影在影像呈现方面或简古或铺陈,或宏大或细切,或急促或舒缓,讲求意象意境。就视觉形象而言,郑昌和的《六刺客》中将刀光剑影置于大雨滂沱之中,血溅飞沙,仍属经典武侠场面。周晓文的《秦颂》以土黄为主色调,显现出古旧的历史感,还让秦王面对滔滔黄河作沉思之状,这是导演探寻中华“黄色文明”之源的有意安排。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中则极力还原或描摹那个时代的本真状况,无论山川风物还是服饰道具,都力求表现那个时代的纷乱仓促和那个国家的糙砺粗豪,许多镜头都是灰头灰脑的,不少人物言行笨拙、形象污秽,包括大英雄荆轲,这样的处置意在表现开天辟地的艰辛与气魄。与《荆轲刺秦王》只有一个生得比较干净的盲女不同,张艺谋的《英雄》极力使用洁净的服饰,打造精美的画面。张艺谋最钟情于色彩的运用,在《英雄》里,色彩参与叙事、塑造人物、隐喻情感,与精巧玄幻的动作一起,展演着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中国意境的中国功夫。电影以无名、秦王、残剑、观众等不同视角分段叙事,导演刻意用不同色彩来区分不同的叙事单元,将情节、人物、场景与情感意绪都揉合进作为视觉标志的色彩里。第一单元的叙事由无名自述击杀三大刺客的过程,以红色为主色调(杀死长空片断是黑色调)。红色象征欲望、仇恨、暴力、血腥、迷乱、死亡,合乎刺客“反常”的身份目的、郁暴的行为风尚与惨烈的悲剧命运。第二单元叙述的是秦王的推测,用蓝色调。蓝色偏冷偏静,象征宁静、深邃、忧郁、理智、隐秘、等待。秦王认为无名之所以能获得刺杀的机会,是因为长空、残剑与飞雪主动牺牲了自己,这种牺牲是冷静理智而又大义凛然的,颇近《大学》所言七证之修:知、止、定、静、安、虑、得。也利于表现秦王的沉着缜密。第三种叙述是真实的故事:三年前,残剑与飞雪曾联手刺秦,但在见到赢政时残剑收手,现在无名以精准的剑法游说他们,残剑依然以“天下”劝阻无名,得知无名失败,飞雪怒刺残剑,残剑承受,飞雪自杀,两人身着白衣。
白色明亮,象征纯洁、优雅、神圣、庄严、正直、和平,在西方可视为结婚的喜庆,在中国却用于哀悼死亡。与残剑、飞雪纯洁的生死爱恋及以天下苍生的幸福安宁为已任的神圣使命也是相合的。开头结尾叙事者所在的现实场景及无名自述杀死长空的断落多用黑色调,黑色肃穆、阴郁、机械、刚健、孤独、寂寥,合于秦的铁血冷酷,历史上的秦王朝原本也是崇尚黑色的。不同叙事单元里的色彩都经过导演的精心设计,色彩的变化,构图的经营,成为电影造型的重要手段,四大色调标识四种叙述的场景、情绪与意义。梦幻的服饰,再加轻柔的动作,置之于洁净的环境中,以慢镜头特写推出,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琴馆、书房中,在大漠、秋林里,在小亭、镜湖上,雨珠滴剑、水袖弹箭,黄叶飘旋、红裙漫舞,踏步成纹、一飞冲天,翩若惊鸿,婉如游龙,极尽意境之美。山水、琴韵、棋品、书法、武功,一统于道,一统于意念,这也是导演张艺谋为简洁直观地展示中国文化而作的尝试。相较于《英雄》的铺陈与夸饰,《刺客聂隐娘》显得格外简淡与玄远。它没有新奇的手法,没有尖锐的冲突,没有耀眼的画面,节奏缓慢,影调阴暗,语言简古,声音低沉,不会给你太多感官的刺激。电影有大量长镜头、空镜头、静止的镜头。长镜头减省镜头个数与情节密度,利于表现广远深邃的场景与独立苍茫的意绪。空镜头下的湖光山色、白云飞鸟、茅屋青烟也适于表达出尘之想。对人物细节与各种器物的摄取则近乎静止。这些延宕故事节奏的镜头,给人物性格、志趣、言动的转变以逻辑的依据,也给沉静淡雅的风格塑造以时空的保证。与叙事舒缓轻柔相应的是语言的简省与古雅。电影多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语言,导演侯孝贤说是有意参考原著中的语序与句法,采用古老的词汇,以适配古朴淡雅的风格。便是这样的词汇,也少之又少,作为主角的聂隐娘,从头至尾也不过十几句台词,甚至两人决斗而不说一句话的场景,也类似于《世说新语•任诞》篇所载恒伊为王徽之吹笛而不交一言的故事,简省的语言不受爱热闹的观众欢迎,但有利于表现导演心中的神韵。影调的阴暗与时间、地点、景物、光线有关,电影表现的时间多在夜晚、凌晨与秋冬之际,所选地点多在室内、山洞、荒谷、空林,所摄景物多帘幕、烟雾,好褐色、黑色、背影、侧光。也喜欢用封闭的构图与不同于常规比例的银幕,以构建隐忍静穆的侯氏电影风格。
4余论
内容与形式实难两分,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与叙事话语都隐含着叙事倾向。《刺秦王》赋予刺客以国家民族意识。《荆轲刺秦王》倾向于人性的思考,注目于自我的分裂。《英雄》试图作文化的反思,也有冲突与矛盾,但努力让这些冲突走向一统与和谐。为了票房,也为了海外观众肤浅却直观的中国文化需求,张艺谋把所有能想到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元素都放到《英雄》里,并且尝试为动荡世界所希翼的和平提供强权保证。这样一来表层的矛盾虽然是秦王该不该杀的问题,深层矛盾却在阐释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刺客聂隐娘》也涉及思想与制度的问题、但更倾向于艺术与生命的展现与思索。电影对集权制度的忧惧,对政治逻辑的批判,都以人性的回归为指向,而归隐即是对政治工具的逃离,即是人性的回归、生命的觉醒。所以说,内容关乎形式,形式即是内容,叙述过程中,满溢着叙述的声音。作为传统题材,刺客电影有许多可资借鉴的资源。司马迁《史记》曾专辟《刺客列传》,载录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等人的事迹,再加历代文人诗赋、优伶剧艺递相展现,使刺客题材日渐成为文艺专宠。诸如曹植《白马篇》、王维《少年行》、李白《侠客行》、唐传奇《聂隐娘》、元杂剧《赵氏孤儿》、明清《三侠五义》《水浒传》等,莫不秉承传统侠义精神。光由《史记•刺客列传》等改编而成的刺客题材戏剧便蔚为大观。据刘永辉《刺客人物改编戏剧简表》,传世有元杂剧李寿卿《说专诸伍员吹箫》、杨梓《忠义士豫让吞炭》,明杂剧叶宪祖《易水寒》、茅维《秦廷筑》,清杂剧四费轩主人《豫让报仇》,清传奇徐沁《易水歌》,及存目杂剧元无名氏《乔风魔豫让吞炭》、明王元寿《击筑记》、清管世灏《吊荆卿》等。[7]直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高渐离》等,还借古讽今,以刺秦故事批判政府的对内专制与对外妥协。电影是最新的也最具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但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离不开对传统的承袭。刺客的形象、行踪、处事的原则与目标极具传奇性和戏剧性,刺客题材自然也成为电影艺术青睐的对象。所以刺客电影蔚然成风,刺秦故事尤为显著。当然,时代与局势不一,可以依凭的技术艺术手段与主创者们的眼界胸襟意识也不一。所以刺秦三大部、《刺客聂隐娘》,乃至《十月围城》,各有千秋。除了取法传统以外,刺客题材电影的发展理当比较与借鉴国内外武侠片、犯罪片、武士片等刺杀类电影的经验与教训,使其题材范围更加广阔、主题思想更加现代、表现手法更加多样。
参考文献
[1]吴玉杰.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剧的艺术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刘伟生.影像屈原的建构与批评[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5(2):76-82,88.
[3]吕新阳.《刺客聂隐娘》票房失利归因[J].电影文学,2016(17):47-49.
[4]金舒莺.政治和商业的互动:论《刺秦王》影片的人物形象重塑和想像[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5(2):79-82.
[5]赖翅萍,陈汉云.崇高与崇高的暖昧———《英雄》的意识形态分析[J].社会科学家,2003(11):138-141.
[6]权亚楠.《刺客聂隐娘》的人文情怀[J].电影文学,2016(20):98-100.
[7]刘永辉.《史记•刺客列传》到“刺客戏剧”的嬗变[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1):48-54.
作者:刘伟生 王艺璇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
- 上一篇:谈物联网技术与 LTE无线通信技术范文
- 下一篇:空间装置在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