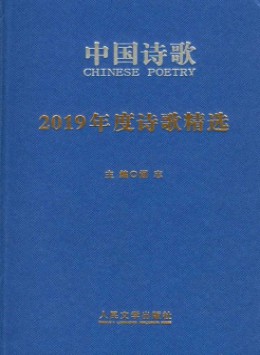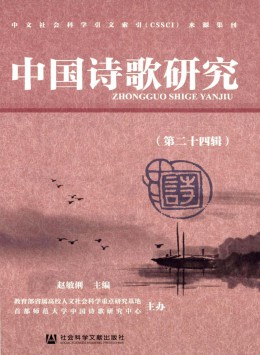诗歌叙事学的界定与确立

随着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迅速发展,小说结构以及叙事技巧研究的重要性很快就在20世纪60年代的小说批评理论研究中显现出来。之后,叙事学理论广泛地应用于小说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研究而不是诗歌研究。尽管不少学者已从不同视角将其引入诗歌研究,但其研究仍然局限于小说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由于受到诗歌研究应该注重形式研究而不是主题研究这一理念的影响,认为诗歌应该从新批评的视角进行解读。换言之,叙事学和诗歌研究没有理论上的结合,诗歌研究主要还是本体研究,因为学者们不是关注诗歌的内容、背景以及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共谋,而是关注诗歌的连贯性、节奏感、隐喻等特征。不过,诗歌研究已开始从新批评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开始接纳包括叙事学在内的理论视角。遗憾的是,没有确立和发展诗歌叙事学。
诗歌叙事学的界定
普林斯和热奈特叙事学定义以及其与结构主义的联系,暗示学者将综合考虑叙事学与诗歌叙事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为诗歌叙事学的最终确立奠定一个科学而又合理的基础。可惜,目前无人界定诗歌叙事学,也无人系统地提出诗歌叙述行为以及其与叙述者意义联系密切的叙事理论。学者们仅从叙事学的视角下归纳和总结了叙事诗歌的一些具体的叙事特征,尚未将之理论化。虽然他们在叙事诗的叙事形式、叙事结构、叙事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和主张,但是这尚未揭示出叙事诗内部制约诗歌叙事的普遍规律,也未能界定诗歌叙事学。为此,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对诗歌叙事学进行界定。首先,它是一种科学而又系统的叙事诗歌研究理论,关注叙事诗歌文本的性质、形式以及其内在规律、诗人、文本、读者,和叙事诗歌内在及外在机制相关的叙事性,但这还依赖于诗歌和叙事有机结合;其次,它的重心在诗歌叙事话语分析,诗歌叙事行为及其本身所隐含的叙事意义和效果,以及其支撑的“叙事在场”的基础和诗歌所讲述的故事[1]。
诗歌叙事学的确立
首先,通过拓展叙事诗歌元素及其相互关系和叙事规律以及在同一理论和概念框架下探究一个叙事诗歌文本和另一叙事诗歌文本之间在结构方面的区别以构建诗歌叙事语法;其次,研究中心也转到诗歌结构特点及其读者阐释之间的相互影响,转到深入探究与某些意识形态模式有关的主体研究。笔者把诗歌叙事分为四类以关注诗歌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及诗歌的内、外部研究。
第一,着力构建叙事诗中所讲述的故事的叙事语法,着力探究事件的功能、叙事的结构规律以及诗歌和诗人的叙事性,也着力寻找故事发展的逻辑等问题。当然,要继续开展诗歌叙事学方面的研究或者探索诗歌以及诗人的叙事性等问题,就得摈弃普洛普等人提出的将叙事学的研究局限于小说叙事的研究传统观念。为此,诗歌叙事学研究得从理论上关注叙事诗,而对于其它叙事媒介则极少论及,因为诗歌叙事学需要花很大篇幅来表述诗歌叙事行为、歌人以及诗歌文化背景之间微妙的联系,而不是其它“无法讲述故事”[2]。
第二,展开研究诗歌叙事话语,因为叙事话语既存在于小说文本,又存在于诗歌文本。凯南说过,“除了作者的风格、语言以及各自的媒介以及符号系统之外,不同的体裁也可以讲述相同的故事”[3]。因此,诗歌的叙事话语应该包括诗人的写作风格,诗人创作诗歌所采用的语言以及诗人为了推动故事发展而从其它学科中引入的各类媒介,因为它的形成在于诗歌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它是诗歌产生意义的途径。然而,研究的重心是叙事诗中叙述者的聚焦叙述。不论叙述者的聚焦是在叙述语言本身还是在其叙述者所依赖的媒介,学者们探讨诗歌文本的时候都可能忽略诗歌语言本身。除了诗中的叙事视角和引言之外,他们很少关注措辞、句型、拼写和语音、衔接和过渡以及叙述故事与叙事话语之间的差异。这一缺失会使诗歌叙事学很难将叙事学和诗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这就是探索诗歌的叙事行为、诗歌叙事的不确定性以及诗歌中受到诗歌意义复义和内容复义的影响之后的叙事确定性是否可能存在等问题以及深入研究诗歌的叙事话语的有效途径。其实,这个研究还得把诗歌叙述者在诗歌事件叙述中所起到的叙述作用、组织作用以及评价作用也需考虑在内。它既可以把叙事诗中所叙述的故事转化为既定诗歌中的叙述话语,也可以把自己凸现为诗人意识形态以及其创作意图的化身。由此说来,如果叙述者是同叙述者,其叙述过程以及人物刻画过程可能被视为诗人与读者的文本交流过程;反之,如果是异叙述者,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其叙事话语属于本真叙述还是戏仿叙述,因为后者强调通过“叙述者的在场”来颠覆诗人的创作意图[4],从而削弱诗歌叙事的可靠性。这就是巴特所说的,“操纵文本意义和控制文本的书信之神”[5]。
第三,研究诗歌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技术化的重要性,要同等对待这两个方面。前者是诗歌所述故事的表层和深层研究,它体现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重要理念。不过,由于诗歌叙事高度依赖诗歌艺术性,诗歌故事结构尚未引起诗歌理论家的高度关注。后者则在叙事论文和专著方面表现突出,探讨诗歌叙事技巧的共性,呼吁诗歌研究从阐释诗人以及诗歌本身转到阐释读者,从叙事的共时叙述换入历时叙述,以探明诗歌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何影响和推动叙事结构的发展,从关注叙事的形式结构转入关注叙事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此外,后者研究还注重阐释叙事诗歌的重要性,注重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和理念来探索诗歌叙事技巧中叙事规律的稳定性,倡导诗歌读者、社会历史背景以及跨学科研究,旨在通过借用其它学科的学术理论成果和研究视角来克服诗歌叙事学研究的困难,挖掘出叙事诗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以及审美效果以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诗歌美学和诗歌叙事学的研究领地。
第四,研究关于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在叙事诗中的主要功能的相互关系。长期的诗歌研究和诗歌批评实践让部分诗歌理论家隐约感觉到后者可能会取代前者而独立存在。其实不然,二者应该会共同存在,相互补充。当然,二者从诗歌叙事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上来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别。前者针对于构建诗歌的叙事语法、叙事修辞以及叙事诗学,而后者则转向具体诗歌文本的分析、解读和阐释。在后者看来,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要审视诗歌产生的背景才能真正解读诗歌语言。其实,前者解读叙事诗歌的叙事语法以及叙事诗学时,未考虑诗歌的背景,而后者则力图弄清楚诗歌的背景。
然而,虽然学者们对语言学和叙事学意义上的语法之间的区别与差异有着清楚的理解,但是对如何合理地构建诗歌叙事语法和解读诗歌文本的各种背景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构建诗歌叙事语法以及叙事诗学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就没将诗歌的各种背景考虑在内。这就使得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具体诗歌文本的分析,既不区分叙事诗歌的叙事语法和诗学和社会历史背景,也不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结果,前者显得保守,后者显得过时。其实,“一种价值的不准确性与另一种价值的准确性共存”[6]。诗歌叙事学里,注意到的不确定性以及注意不到的确定性也一样。
叙事学以及诗歌研究在中国多年的发展,已为诗歌叙事学及其系统科学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任何一种想要阐明诗歌方方面面的理论反而只会准确地阐明另外一种理论的方方面面,因为任何一种绝对化的理论反而导致其相对化。诗歌叙事学的确立也不例外,跟其它理论一样,它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也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只要学者们不断地为诗歌叙事学开疆辟土,不断凸现诗歌叙事学在诗歌研究中的理论导向作用,诗歌叙事学就会取得更大发展。因为,传统的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叙事学在小说中的应用关注得越多,学者们对其在诗歌中应用越是好奇。这必然会使诗歌叙事学成为推动诗歌研究和叙事研究走向叙事理论新领域的必然趋势,用它去揭示和阐明诗歌内在本质的叙事规律及其深层问题。(本文作者:罗军 单位: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 上一篇:儿科教学中PBL教学法的应用范文
- 下一篇:儿童护理中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