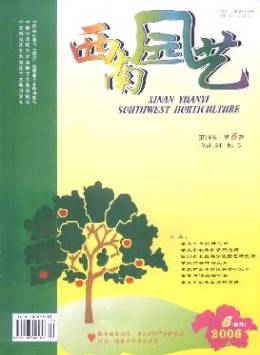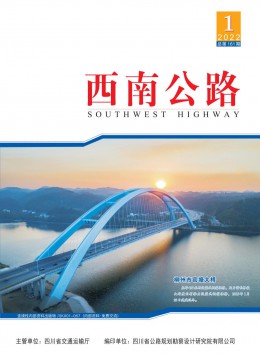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与现代文学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与现代文学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现代中国学界对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进行了一定发掘整理,不少现代作家与文学研究者也将边地歌谣与现代文学进行对照,期望以此丰富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在现代文学语境中,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样式丰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共性,具有质朴灵活的表现形式、执着求真的美学风格等特点。它是西南边地传统文学的代表,也起到沟通主流知识界与边地、少数民族、民间、民间文学的媒介作用,并由此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现代文学。
关键词:西南边地;民间歌谣;少数民族歌谣;特点;充实丰富;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是多元文学,包括民族多元、地域多元等。作为一个远离中原的多民族文化区域,西南边地及其文学也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边地主要指西南地区多民族共存的区域。据《史记》、《华阳国志》等记载,西南地区在古代就生活着多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古“西南夷”区域。“西南夷”文化区域大致包括今天云南、贵州两省及四川省大渡河以西(原民国时期西康省),并向南延展至中南半岛北部、向东延展至湘西地区(雪峰山以西)。这个区域自古以来被视为中国的边疆,也是大西南地区的外围部分,被视为“西南边地”。西南边地有悠久和独特的文学传统。在现代文学语境中,西南边地传统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对话、互动使双方都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使中国文学的内涵显得更为丰富。西南边地传统文学主要包括(口传与书面的)神话、传说、歌谣等。其中,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具有独特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近现代以来,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逐渐被主流学界注意,如20世纪20年代的“歌谣运动”就特地收集与整理了不少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据统计,在“歌谣运动”前期,《歌谣周刊》收录的一万多首歌谣中,仅云贵两省就贡献了两千多首[1]。至抗战及战后,西南边地歌谣更是得到多方关注,不少边地歌谣被搜集成册并公开出版,如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陈国钧的《贵州苗夷歌谣》等。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现代西南边地民间歌谣、少数民族歌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它不仅是西南边地地域文化、文学传统的结晶,还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心、主流”文学之间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边地文学传统、少数民族文学传统为主流文学话语所感知,并对主流文学产生某种反作用力,从而进一步充实了现代文学。
一、现代文学语境中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的几种形式
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历史十分悠久,但由于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它在历史上较少受到官方及主流知识分子注目。直至“五四”前后,特别是北京大学掀起“歌谣运动”风潮之后,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才逐渐被“主流”较为系统地了解。可以说,成文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在现代是以“被发掘”的被动态势进入主流学界视野的,它们基本上都经过了知识分子的翻译与改写。翻译与改写自然有力度的区别。若按“被翻译与改写力度”由弱到强的线索来考察现代文学语境中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它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
1.主要是指深入边地的知识分子采集的、大致上还保留着本来面貌的边地少数民族歌谣。
如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9年成书,恰逢抗战,至1947年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有41首湘西苗族歌谣,这些歌谣被翻译为汉语,同时都标注了苗语读音和直译读法。陪同凌纯声在湘西进行苗族调查的湘西人石启贵于1940年编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书中也收录了大量湘西歌谣。与此类似的是,抗战期间内迁到贵州的大夏大学教授陈国钧等人编成的《贵州苗夷歌谣》,以及贵州本土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杨汉先著成的《大花苗歌谣种类》、《威宁花苗歌乐杂谈》等文(收入吴泽霖、陈国钧编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在云南,张静秋的《云南僰民唱词集》、薛汕的《金沙江上情歌》等则对云南(主要是滇南、滇西)少数民族歌谣进行了收集、整理。在西康,刘家驹(格桑群觉)整理康藏民歌并将之翻译成汉语,并于1948年编成《康藏滇边歌谣集》(西康知止山房,1948年)出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边地歌谣是被零散收录的。如北大《歌谣周刊》收录的几千首西南边地歌谣。沈从文将湘西歌谣整理成《筸人谣曲》,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将湘西、贵州、云南歌谣整理成《西南采风录》等。这类歌谣并未在搜集和刊出的过程中被大幅度改写,总体而言,它们大体上保持了边地少数民族歌谣的原生态面貌。
2.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在原生态歌谣基础上改写的边地少数民族歌谣。
在这些经过改写的歌谣中,较广为人知的是光未然改写云南彝族歌谣而成的《阿细的先鸡》。光未然坦言,原作的一些内容“也是经过了我的苦心经营”[2]。光未然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将少数民族歌谣“文人化”的做法,但大致上保留了原作的味道。与光未然相比,有一些知识分子对边地歌谣的改写就是更为纯粹的文人化改写了。如云南作家赵银棠将纳西族歌谣改写成五言旧体诗:“上峰三峰雪,/下峰三峰柏。/柏雪常相思,/相思情脉脉。”[3]230-231除了形式上的改写,另有一种改写是吸收歌谣的内核之后,将歌谣的叙事原型和美学传统融入到新的创作中。如云南诗人梅绍农的叙事诗《奢格的化石》,取材于云南彝族传说(以歌谣形式流传于民间),诗人将民间歌谣转化成新式白话诗。沈从文也曾将湘西苗族、土家族歌谣改写成新诗,如《乡间的夏》、《镇筸的歌》等,他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湘西歌谣的形式改写楚辞(《还愿》)和《诗经》(《伐檀章今译》),以此让边地歌谣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从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屡屡“被改写”来看,可见歌谣内蕴着文学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所以它才能不断被发掘和改造。
3.主要是指作家或模仿边地歌谣创作的、或生造而成的“陌生化”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
这些歌谣大多散落在新文学作品中,读者一看到这类歌谣就知道它们与边地有关,而实际上它们却不在边地流传。如沈从文《凤子》里镇筸女子所唱的歌:“谁见过天边有永远的虹?/问星子星子也不会承认。/我听过多少虫声多少鸟声,/谎话够多了我全不相信。”[4]这首歌很可能就是沈从文虚构的,因为镇筸(凤凰)苗族并没有这样的山歌(无论是沈从文的记录还是凌纯声等人的田野调查都没有录入类似歌谣)。《神巫之爱》、《龙朱》等文中几乎是西洋歌剧形式的歌谣更只能归结为沈从文的“再创作”。另有一些与边地真实歌谣相近,但也可推论出是作者生造的歌谣。如马子华小说《月琴》出现的那首:“阿妹,/哥哥真想你,真想你!/请个画师来画你。/把你画在月琴上,/抱着月琴如抱你。”[5]《月琴》最早收录在马子华1936年的短篇小说集《路线》中,该篇小说典型地“表现出马子华早期小说创作的特色”[6],即往往如其他年轻左翼作家的作品一般沦为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的“急就章”。这篇小说虽以故乡为表现对象,但当时马子华并没有切实的边地底层经验,他早期主要生活在省城昆明,并在上海创作,这种歌谣只是为了增添“边地风味”而已。当这些“生造”歌谣出现在小说、散文中,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以供唱或颂的边地歌谣,而是为现代文学作品增添边地风味的佐料。当然,这类歌谣的生成基础仍是边地传统歌谣,只不过它们与原生态歌谣有较大差别,有时就难免变得陌生,以至于让人不敢直接断定是否就是实际存在的边地歌谣。仅从上述歌谣形式来看,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是十分丰富的。当然,多样的边地歌谣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西南边地这个文化区域的独异性。
二、现代文学语境中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的基本特点
西南边地歌谣虽繁杂,却是杂而不乱。无论在整体上、形式上还是思想内容、审美取向上,现代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都可概括出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
1.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共性。
西南边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各有不同,但西南边地不同民族从古至今就相互交流、融合,这也形成了西南边地文化的地域共性特点。地域文化共性使不少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超越了民族之别而成为地域性文学。如刘兆吉《西南采风录》收有云南曲靖的一首歌谣:“隔河望见妹爬坡/桃红带子顺地拖/有心等哥站着等/无心等哥快翻坡。”[7]110《贵州苗夷歌谣》也收有十分类似的一首贵州安顺一带的仲家(布依族或云南壮族的旧称)歌谣:“老远望见姐翻坡/情姐主意等情哥/有情有义坐起等/无情无义快翻坡。”[8]黔西与滇东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这首歌谣在不同民族之间流传,可见它已经是一种地域性文学了。甚至有的歌谣超越了民族和国界,成为某种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的经典性文学。如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流传的“松帕敏”长诗。张镜秋曾将其译成汉语,并命名为《天王松帕敏奇遇唱词译》。张镜秋在“注”里说明:“松帕敏系为四大佛典之一。”[9]164据相关研究者考证,这些歌谣“故乡在印度,是佛教之风把它的花粉播撒到这里来了。”[10]总体而言,西南边地歌谣体现了这个文化区域的文化共性,它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态共同培育而成。
2.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具有质朴、灵活的表现形式。
朱自清认为,歌谣有“自然民谣”与“假作民谣”之别,后者往往向着“高雅”或“文人化”方向发展,而自然的民谣一直保持“单纯质朴”[11]。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就是典型的“单纯质朴”歌谣,即使被改造成“文雅”的或“现代”的诗词形式,它依然保留了质朴的本性和形式。如赵银棠将纳西古歌改为旧体诗词,遣词造句尽量向“雅驯”靠拢,然而“女儿爱戴花,戴花会情郎”[3]235等句仍是典型的纳西族民间用语。边地歌谣的质朴深得沈从文推崇,他也从这种质朴里吸取营养,“用笔写出来的比较新鲜,俏皮,真实的话”[12]。同时,边地歌谣在成文形式上十分灵活。如1936年贵州作家寿生指出流传在贵州的一些歌谣有共同的“歌母子”(母题),在传唱过程中人们可以随性更改,因此就生成了多首歌谣:(一)买米要买一斩白/连双要连好角色/十字街头背锁链/旁人取消也抵得!(二)买马要买四蹄白/联双要联好角色/那年那月犯了岔/旁人耻笑也值得[13]!这种质朴、灵活的歌谣形式十分普遍。所以即使被改写为旧体诗词或现代诗,这些“歌谣诗”在遣词造句上仍保留了鲜明的西南边地民间和民族色彩。
3.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具有执着求“真”的特性。
西南边地远离中原,西南边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往往保持着不受汉儒思想束缚的初民色彩。因此,在此文化土壤中生成的边地歌谣相对内地文学来说,也就保留了更为“真”的一面,同时更为执着地追求“真”。最能体现边地歌谣追求人性本真的是情歌。西南边地情歌文化特别发达,在现代成文的一些西南边地歌谣集中,情歌占有很大比重。如《西南采风录》收录各类歌谣771首,其中情歌就有641首。陈国钧《贵州苗夷歌谣》把贵州苗夷歌谣分为七类,情歌一类在数量上远超其他六类之和。刘家驹《康藏滇边歌谣集》原本就叫做《西藏情歌》。在情歌中,边地人民毫不掩饰对原初生命意识的追求,也不压抑对两性结合的渴望,更表达了对世俗束缚的蔑视与反抗。当边地男女相遇,女子爱慕男子时不用掩饰自己的情感:“君细腰,眼睥睨/妾一见倾心,神魂飘荡/侬心陶醉,精神错乱了呀/真个白嫩的皮肉儿!”[9]9-10当两者得以结合,则满心高兴地唱:“好女好男好风光/好女今晚配好郎/好日好时生贵子/好心好意比鸳鸯。”[7]520如果恋爱婚姻受到束缚,边地男女更会勇敢地喊出反抗的呼声:“怪七怪八怪我娘/拿我八字许配郎/等到三年我大了/只有随我不随娘。”[14]可见,边地情歌“既不同于剥削阶级仿作中的那种无病呻吟,也没有市民阶层所编俗曲中的低级趣味,所表现的感情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真挚,那样的深沉,这些作品与地主阶级文人扭捏做作的‘情诗’和小资产阶级虚夸、矫饰的‘爱歌’不能同口而语。”[15]当然,现代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仍有很多值得剖析的特点。只不过总体来说,鲜明的西南边地地域性、质朴与灵活的表现形式、执着追求“本真”的思想内涵与审美风格等算是其基本特色。当这具有边地色彩、少数民族色彩的歌谣遇到现代文学,它就对现代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三、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遇
近现代以来,随着歌谣运动及类似歌谣采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边地、边地少数民族及其文学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呈现出更为客观、立体的一面。同时,歌谣采集活动还促使现代文学从边地歌谣中汲取“民间”、“蛮夷”的活力与养分,以此丰富现代文学的内容、形式与美学风格。
1.现代中国从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中发现了西南边地的“人”。
历史上,西南边地一向被忽视,边地人往往被视为非人的“蛮夷”。而歌谣运动重新定义了“民”的含义,边地少数民族也被纳入现代中国“民”的范畴。徐新建指出:“大体而论,在民国前期中国歌谣学的相关研究中,‘民’的含义与以下几组命名关联:民间、民众;平民、乡民;俗人、蛮人。”[16]作为“蛮人”、“乡民”的一部分,边地少数民族在“五族共和”或类似政治表述中没有一席之地,却在歌谣运动等文学语境中受到了重视。凌纯声在调查湘西苗族时明确认识到“(苗族歌谣)或为表现内心现象的抒情歌,或为表现外界现象的叙事歌。……其内容虽似浅薄粗野,然很值得我们深刻的注意,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他们的情绪生活,有一种直觉的觉察。”[17]这里虽还有“我们”与“他们”之分,但已经看出“我们”确认“他们”也是有喜怒哀乐的“人”,“他们”的情绪也值得“我们”去注意。黄钰生在给《西南采风录》作序时也讲述了自己对边民的真切感受。边民和他一路同行一路高歌,虽身负重物一步一喘仍歌声不绝。黄说这并不是因为边民“非人”,而是因为他们以歌声来分担劳累,唱歌之后“也觉得在绵绵长途上,还有同伴,还有一样辛苦的人。他们所唱的歌,与其说是情歌,不如说是劳苦的呼声。”[18]若没有发现这些歌谣,有几个人能知道边民也是挣扎在劳苦的底层呢?薛汕更是把边地歌谣当成“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他从边地歌谣里看到了活生生的边地民众。边地民众“正如金沙江上的青年男女,充沛着丰富的生命力一样……他们用火热的感情,毫无顾忌地使山光水色,为之一变,使茂林巨石,为之动容……假如有人想抹杀他们的这些真实,甚至侮辱了他们,他们绝不是只晓得沉湎于私情,不晓得是非的。”[19]边地歌谣凝结了西南边地民众的喜怒哀乐,采集歌谣也就是把这喜怒哀乐给“采”出来,并把真实存在却几乎不为人所知的边地少数民族展示给世间:西南边地少数民族也是活生生的人。若没有这些歌谣,边地少数民族留给现代“中国”的印象或许只是面目模糊或狰狞的,如野兽一般的蛮夷罢了。只有在边地歌谣中,边地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才有了更为客观、立体的面貌,才能使“中心之国”更为平实地看待边地。正如林同济在认识到真实的“苗夷”之后呼吁:“让我们大家不要无条件地摆出高等民族态度,动不动就高喊要‘同化’这些苗民!”[20]
2.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发现了“边地”和“边地文学”。
刘兆吉在谈及民歌研究时不无遗憾地说道:“记载西南几省尤其是黔、滇民歌的,可说是太少了,这实在是一种憾事。”[21]这其实反映出以滇黔为主的西南边地文化区域被忽视的现实。对西南边地歌谣的采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从北大《歌谣周刊》所收录的西南边地歌谣到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民间文艺》等收录的西南边地歌谣身上,这个文化区域逐渐受到外界的认识和重视,特别是这些歌谣采集者将少数民族歌谣翻译成汉语并集结出版,这就使得在以往中国文学范畴里模糊不清、甚至被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以“汉化”的姿态进入主流视野。这些“汉化”的原生态边地文学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发现了一种“异域情调”文学,另一方面以这种“异域”文学来观照自身、充实自身。比如闻一多以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来考证伏羲女娲神话就是典型例子。在《伏羲考》中,闻一多特地强调中国西南各族洪水故事、瑶族图腾舞乐等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对中国神话考证的积极作用。这些被闻一多作为观照资源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大多是流传已久的口传文学,歌谣是这些口传文学的重要载体,其中的洪水神话更是西南边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学、边地歌谣一个重要主题。从闻一多等人对边地歌谣的重视来看,边地歌谣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正如胡适所言:“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22]这就可看出,边地歌谣使中国文学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扩大,同时使其内涵更为充实。
四、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
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与现代文学的相遇影响了现代文学的方方面面,两者之间的互动更是使现代文学扩展了创作视野。可以说,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在新时代为新文学不断提供营养。
1.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为现代文学的西南边地书写、少数民族书写提供了某种文化、文学原型。
如沈从文《月下小景》写苗族青年男女在山洞中幽会之后服毒殉情,按照作者的解释,殉情的原因在于当地一种古老的风俗:女子不得嫁给夺取了其初夜的男子,必须要嫁给他人。但《月下小景》对“夺取初夜”与殉情之间关系的描述并不一定依据现实习俗,而是从某种古老习俗、传说中脱胎而来,其中的要点就在于“被迫嫁人”这个“原型”。实际上,湘西苗族婚恋歌谣里一直存在“被迫嫁人”与“反抗被迫嫁人”这个母题,沈从文极有可能在无意识中化用了这一原型。在这里,可参考一首古老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对苗族祖先姜央娶亲过程的描写。史诗叙述:大洪水过后,人类都灭绝了;姜央被天神命令娶自己的妹妹,以重新繁衍人类;妹妹不同意天神的安排,姜央就想了一个办法意图困住妹妹:“聪明的姜央,来到小桥西,编了九个铁笼子,捉来九只土画眉,放进笼子里,叫妹妹去取。”当妹妹被笼子困住后向姜央求救,姜央说:“我娶你作妻,答应不答应呢?答应才救你。”[23]这首古歌一方面反映了远古时期的兄妹通婚风俗;另一方面其实描写了苗族“抢亲”习俗的源头,即姜央对妹妹的刁难便是远古苗族男子抢夺女子的手段。“抢亲”在后来不再盛行,但“抢亲”及“反抗抢亲”故事却在苗族口传文学中流传,故事中具体的主人公及行为已经不限于姜央及其妹妹,而是成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学原型:被迫嫁人、进行反抗。那么,回到《月下小景》的“被迫嫁人”这一主要结构,可发现小说所述的“规矩”女子必须离开与自己过“初夜”的男子实质上就是女子被迫离开情人而嫁给抢亲者:这可能就是“姜央妹妹必须嫁给姜央”这一传统文学原型的再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还影响了现代文学西南边地书写、少数民族书写的文学形式与审美情趣。
比如在作品结构上,边地歌谣与现代文学的边地书写之间便有某种呼应。以马子华《他的子民们》对比彝族民歌《阿细的先鸡》,会发现该小说与彝族创世歌谣的内在结构有一致性:《阿细的先鸡》包括“创世记”、“开荒记”、“洪水记”、“谈情记”和“成家记”,恰好是彝族对本民族历史的理解;《他的子民们》的主体结构包括“自在生活、土司压迫、反抗土司、反抗失败、逃进深山”这与歌谣中彝族在创世纪与开荒之后,遭遇洪水、躲过洪水,然后在山上繁衍的结构是一致的。这类“走出困境”式的故事原型不止存在于《阿细的先鸡》中,更几乎是西南边地不同民族创世神话的共同主题,这无形中就影响了包括《他的子民们》在内的部分现代文学作品。除了结构上的联系,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也在文学形式与审美风格上充实了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西南边地书写有一个特点,即作品中常常混杂不少边地歌谣,这些歌谣带给文学作品以别样的风味。如埃德加•斯诺和周辂等人的“马帮文学”加入云南歌谣,使“马帮文学”呈现出某种边地传奇色彩;沈从文构建湘西世界总要写男女对歌,“对歌与音乐的插入,使沈从文的神话传说故事洋溢着少数民族的浪漫与绚烂,也使故事充满着独特诗意和韵味,从而呈现出沈从文小说的优美的风格。”[24]更有一些边地新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文学发生期的边地诗歌)直接就脱胎于歌谣,这使新文学与边地传统文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如贵州《铎报》1919年6月刊登的《销国货歌》不乏“国货劝他销/偏说恐惹祸/比如我的房/空起我不坐”[25]等句,这些句子与边地民间歌谣并没有很大区别,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看成边地新诗诞生期的独特风格。可以说,边地歌谣使现代文学边地书写、少数民族书写的文学母题、文学结构和审美风格都呈现出独异色彩。正因为如此,现代作家笔下充满活力与生机的西南边地艾芜绚丽的滇缅边境、沈从文冲淡的湘西世界、蹇先艾沉重的黔北民间、周文残酷的川康雪地、马子华奇诡的热带滇南以别样的风姿为“老气沉沉”的“旧中国”及中国(中心之国)文学注入了一股“野蛮人”的新鲜血液。而且,边地歌谣不仅充实了现代文学创作,它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面貌,一些学者在考察边地民间歌谣与其他口传文学之后就提出“中国文学并不缺少英雄史诗”等观点①。当然,某些边地歌谣是否该被归为“史诗”暂且不论,但它毫无疑问是边地民族文学传统、边地生存经验的结晶,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3.除了与文学创作的直接互动,在边地歌谣中还可看到边地“民间”之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歌谣运动”目的之一是知识分子为了确证自我与“民”的身份,这种确证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认定有一个属于“民”的生存空间它与“庙堂”相对,也与知识分子构建的“知识广场”相对,它被称为“民间”。陈思和指出“民间”具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它产生并存在于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位置。二是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是它的内涵十分复杂,“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织,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形态[26]。现代新式知识分子在确证“民间”之时,往往有“改造”大众与民间的动机。作为“乡民”、“土人”生活的区域,无论是地缘上还是文化上,西南边地都是典型的民间。作为“民间”的一部分,边地歌谣以“民间文学”的面貌为现代知识分子所认识,于是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边地作为解读与“改造”的“民间”对象。在这层意义上,西南边地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左翼话语的“阶级”及1942年延安讲话之后的“人民”等现代文学关键词紧密相连,也就与现代文学、现代中国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看来,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体现了自由也蕴含着糟粕,他们从歌谣里看到启蒙的迫切性;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体现了“人民”的智慧与苦难,它是“人民文学”的一部分,还可从中延伸出“阶级斗争”的多种解读。有学者就此认为,对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来说,“民间文化形态总是与知识分子已有的价值系统发生碰撞。这种冲撞使知识分子对现实思考的深度有了历史纵深感”;对沈从文等坚持“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是“把自己融于民间的文化世界中,以‘下层人’的眼光去理解社会、人生、政治,去体悟民风民情,把自己的心交给那一浸润着民间文化精神的大地,叙说‘乡下人’的心理内涵、生命渴求与行为方式。”[27]总而言之,无论是何种立场的现代知识分子从民间去观照现代中国、现代文学,他们都不可能绕开西南边地这个典型的“民间”。西南边地和边地歌谣如其他“民间”及“民间文学”一般,从中可看到“新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27]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文学是多个文化区域、多种文化形态共同塑造而成的多元文学。仅就现代文学而言,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多元传统,在新的时期又有新的多元内涵,所以绝不能以单一观念(如以中心话语遮蔽边缘话语、以雅文学遮蔽俗文学、以汉族文学遮蔽少数民族文学等)去认识现代文学。民间与官方及知识广场的关系、雅俗文学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等,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需要理清的要点。在理清这些关系之时,重视歌谣(包括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在内)等民间文学传统,这有助于研究者以承认并尊重多元的态度去认识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下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样式纷繁、特点突出,重视并探讨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歌谣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也是“重审”现代文学的一个角度。唯有认识到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性,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阐释才不至于落入“一言以蔽之”的笼统概括中。
参考文献:
[1]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385.
[2]光未然.阿细的先鸡解题(代序)[M]//光未然.阿细的先鸡.昆明:北门出版社,1944:16.
[3]赵银棠.玉龙旧话新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4]沈从文.凤子:在栗林中[M]//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359.
[5]马子华.月琴[M]//马子华.他的子民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7
[6]吴重阳.边地民族生活的绚丽画卷:论马子华的小说创作[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7]刘兆吉.西南采风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110.
[8]陈国钧.贵州苗夷歌谣[M].贵阳:文通书局,1942:222.
[9]张镜秋.云南僰民唱词集[M].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164.
[10]王国祥.傣族长篇叙事诗与佛教[J].华夏地理,1981(3).
[11]朱自清.中国歌谣[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9.
[12]沈从文.乡间的夏(镇筸土话):话后之话[J].国语周刊,1925(5).
[13]寿生.莫把活人抬在死人坑[M]//寿生.寿生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51-52.
[14]陈国钧.贵州苗夷歌谣[M].贵阳:文通书局,1942:78.
[15]张景华.论《西南采风录》的情歌文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
[16]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M].成都:巴蜀书社,2006:40.
[17]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76.
[18]黄钰生.序[M]//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2.
[19]薛汕.序[M]//薛汕.金沙江上情歌.昆明:春草社,1947:5.
[20]林同济.千山万岭我归来[J].战国策,1940(13).
[21]刘兆吉.西南采风录的经过[M]//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2.
[22]胡适.复刊词[J].歌谣周刊,1936(1).
[23]马学良.苗族史诗[M].今旦,译注.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247-248.
[24]杨剑龙.神话传说故事与少数民族文化:读沈从文作品[J].民族文学研究,2012(1).
[25]毛宅三.销国货歌[M]//尹伯生.贵州新文学大系(1919-1989)现代文学卷(下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384.
[26]陈思和.民间的浮沉[M]//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7-208.
[27]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作者:彭兴滔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