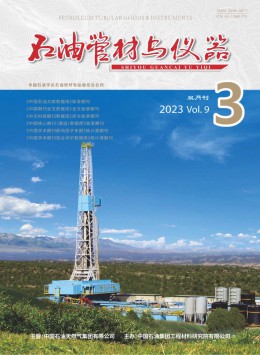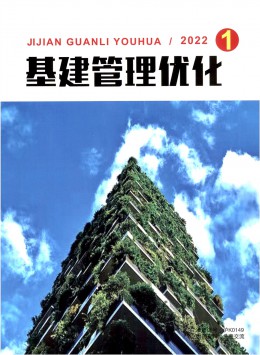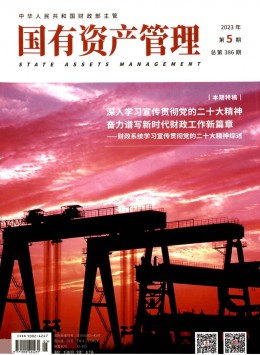有关植物的诗歌精选(九篇)

第1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关键词:曹植 白日 意象 特点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 白日”意象
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被称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在诗歌中大量使用“美女”、“少年”、“云”、“风”、“飞蓬”等意象,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多有研究。同时,曹植诗歌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白日。“白日”意象本身的原型含蕴十分单一,但是一旦诗人将自身情感注入其中,在诗歌中势必会呈现出多种复杂的意蕴,这也展现了作者精湛的艺术表现力。
曹植诗中“有‘白日’意象的诗共五篇,分别为《箜篌引》、《赠徐干》、《赠白马王彪・其四》、《侍太子坐》、《名都篇》……曹植以‘白日’入诗,不仅是诗人对曹操在世时他‘贵公子’般生活的怀念和留念的体现,更是他后期内心生活悲苦、政治失意的一种淋漓尽致的宣泄。‘白日’还表达了曹植对时光匆匆流逝中自己却功业未立的哀叹”。①本文主要探讨曹植诗歌中的“白日”意象的特点。
二、曹植诗歌中“白日”意象的特点
(一)移情性
所谓“移情”,“指人在聚精会神中关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品)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②“日”仅仅就是“太阳”的意思,而正是由于移情手法的运用,诗人将自己内心中的不同感受倾注于“白日”意象中,这也就使得曹植诗歌中的“白日”意象有了不同的含蕴。太阳光芒四射,给人以朝气蓬勃之感,使人充满希望。曹植在《名都篇》中所描写的京洛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主要是歌颂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诗中“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虽是一种对时光易逝的感慨,但基调仍是十分积极乐观的。散发着灼热光芒的太阳本应给人以乐观积极的印象,但是由于观察者自身的情感的消极而使得代表着勃勃生机的太阳充满了抑郁暗淡。“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赠白马王彪》)的“白日”一片惨淡,毫无生气,是由于同胞兄弟被害,路上又被迫与诸侯王分开走,曹植“思郁以纡”。诗人内心悲愤,因此看到的太阳暗淡凄凉,没有光彩,这集中抒发了曹植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并且对那些挑拨他们兄弟感情的小人大为痛斥,表达出对手足情深的任城王的深切怀念。同样,诗人的朋友徐干才华横溢却不得重用,于是曹植在《赠徐干》中用“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来表达因对朋友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思念而引发的对时光易逝的慨叹。曹植其他诗篇中的“太阳”意象也有此意。《杂诗七首・其一》首句“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写的是登台时的情景,惨淡的日和高台上的“悲风”相互映衬,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凄凉和苍茫之感,也比喻当时朝廷政治气氛险恶阴惨。《情诗》中“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薄薄的云层遮蔽了日光,一阵阵凉风吹起诗人的衣衫,写出了一派凄清的景色,其中寄寓着诗人压抑、忧郁的心志。既是写情,也是写景,达到了物我同一。
(二)多义性
多义性是指寓“情”于景中的“情”是多方面的。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其实是作者与读者在文本当中的潜在对话,读者的接受活动被看作是文本含义的具体化和再创造过程。③西谚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中国也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古语。由于关照的角度和读者自身文化素养以及生活体验的不同等原因,对于同一首诗,同一个意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悟,甚至,对于同一个意象,诗人本身就寄寓了多种复杂的感情在里面。徐干是“建安七子”之一,善诗赋,好文词,但一生坎坷不遇,贫贱可怜。《赠徐干》是曹植悯其不遇,勉其待时的劝慰之作。首句“惊风飘白日”,李善评说:“夫日丽于天,风生平地,而言飘者,夫浮景骏奔,倏焉而过,余光杳杳,似若飘然”。风惊、日飘,一方面是诗人对时光易逝的感慨,另一方面也与诗人对朋友的思念密切相关:正是对朋友的思念导致诗人神情恍惚而主观上产生的光景西驰的感受。一首《赠徐干》即包含着诗人悯朋友之不遇、对朋友的思念以及感慨时光流逝等多种情感寄托,同时,同一首诗不同的人也有其他的理解。有学者(韩涛)认为“这首诗是作者以朋友的身份劝说徐干出仕的,所以诗写的真挚热情,喻之以理,动之以情,很有分寸。”他认为首句“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则是以比喻的手法,说明东汉王朝就像惊风吹拂下的白日一样快要落山了,而曹家的天下就要建立起来了,把天下的大趋势告诉了徐干,以封建士大夫最珍重的友情来感化徐干,让他出仕,和自己一起共举大业。《侍太子坐》写于曹植竞争太子之位失败之后。曹丕当上太子,曹植心里十分压抑苦闷,但却不得不参加哥哥“清醴盈金殇,肴馔纵横陈”的游乐宴飨之事。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之下,曹植内心充满了份孤独苦闷的失落感。“这首诗表面上一派欢乐景象,其实是以乐景写哀情。其中‘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既指现实中大雨过后,太阳普照大地,‘白日’也喻指曹丕,形容他当上了太子后光芒四射,足以‘曜青春’”。
第2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第3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关键词:情诗;植物;巫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19-01
《诗经》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最早的植物图谱。《诗经》305篇,其中记录植物达140多种,内含草类85种,木类58种,比如《周南・关雎》、《周南・卷耳》、《周南・葛覃》、《周南・桃夭》、《周南・]q》中的荇采、苍耳、葛蔓、桃花、]q,《召南・采蘩》中的白蒿,《卫风・氓》中的桑树,《卫风・木瓜》中的木瓜,《王风・丘中有麻》中的大麻,《小雅・采薇》中的薇菜等等,这些植物意象在诗歌中频繁出现,显然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兴”是《诗经》主要的艺术手法之一,朱熹《诗集传》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用一物引起他物,从而触动诗人的感情。而对兴的用法解读一直以来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兴仅仅作为发端,与下文所咏内容仅有艺术形式或情调上的联系,与意义无关。也有的认为兴与下文有意义上的联系,暗含了一定的寄托关系,能起到烘托渲染的作用。从文学表现手法的角度来说这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不分对错,难以区分,我们在这里试图绕过艺术特征的角度,从原始先民的意识形态来分析《诗经》中的植物兴象在诗歌中的作用。
一、巫术的产生与应用
上古先民处于混沌和懵懂的状态之中,生产力水平和科学知识的极度落后和贫乏,使其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极少的了解。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是神秘的,充满了魔力,甚至是恐惧。当面对大自然的灾害,如地震、洪水,或者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而无能为力的时候,先民就幻想出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加以膜拜,巫术也便随之出现,并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但由于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处于最初发展的阶段,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和感性材料,还不能将自身与自然界截然分开,在感知自然时,认为人和物之间都是有灵性和感应的,因此他们经常借助于人们所熟悉的某种具体的形象表达特定的情感体验,进行巫术活动,很多物象便被赋予了巫咒的意义。《诗经》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巫术的影响。
二、植物性巫术在情诗中的具体表现
《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和挫折,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诗中提到的众多植物意象便是发咒者意志和欲望的自我中心性投射,其中的大部分是表现追求爱情和思恋怀人的。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d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思恋不已,却又追求不到。诗中三次提到荇菜,难免显得繁冗,而从巫术角度来看,通过荇菜的强化作用建立起信心,形成心理上的暗示,并深信通过自己的诚心祷祝就会达成心愿,更显得合理。
再看《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P。我姑酌彼金,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矣,我马矣。我仆j矣,云何吁矣!”女主人公反复采摘卷耳却始终不能装满一小筐,可见女主人公根本无意采集卷耳。后面又提到“金”、“兕觥”、“马”、“仆”等器物,不可能是一个远离丈夫独自生活的女性所能有的,如果把这些作为祷祝的礼仪用品来看待更为合适。因此女子借采摘卷耳是为了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认为这些承载了巫咒的植物,有助于自己愿望的实现。
还有《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木桃”、“木李”在上古都被看作男女之间表达爱慕之情的信物,在这里并不是简单的投赠之物,而是被施用了巫术借以表达“永以为好也”的美好愿望,希望可以使恋情长久不变。我们且不管咒术是否真的能实现,最起码已对发咒人来说有相当的心理效应。
《诗经》中这样的诗还很多,比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兮”、“野有蔓草,零露”,《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王风・采葛》:“彼采葛兮”、“ 彼采萧兮”、“ 彼采萧兮”,《召南・坑忻贰罚骸坑忻罚其实七兮”、“坑忻罚其实三兮”、“坑忻罚顷筐I之”,诗中所涉及到的植物被多次提到,显然是借助巫术的力量帮助其增强信念,实现愿望的的一种方式。
诗经中还有一部分巫咒是用来表达不满和反抗的。比如《王风・中谷有》:“中谷有,缕淝矣。有女仳离,其叹矣。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中谷有,缕湫抟印S信仳离,条其啸矣。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缕涫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即益母草,诗中多次用干枯衰败的益母草的形象表现女子的悲惨遭遇,写女子被丈夫抛弃,恨自己命运不济,遇人不淑,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予以控诉。在现实障碍和困难无法克服的情况下咒语便成了超现实的极端形式,表现更为激愤的感情。
三、植物的内在意蕴
可见,植物在诗中的出现是相当频繁的,并且都承载着某种巫咒意义,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植物可以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同。
众所周知,原始先民主要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虽然到商周时期,已经过渡到农耕社会,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采集劳动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在物质生产中仍是不可缺少的一部风。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会不可避免的经常提到最为人们所熟悉和了解的,与采集有关的各种植物意象。另外此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社会分工,男子从事农耕,女子从事采集,在农业生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女子处于一种辅助和补充的状态,更多时候植物成了女性符号的隐喻象征,因此在诗歌创作,尤其是在表现男女恋情的作品中植物的频繁出现就很正常了。
第二,与植物本身的特性有关。
上文提到了《周南・关雎》中的荇菜,从其植物特性来看,荇菜属于浅水性植物,叶片小巧别致,花朵呈鲜黄色,花多且多花期长,经常用作点缀水景的佳品。而且根茎可以食用,可做蔬菜来煮汤,柔软滑嫩,在上古是美食。可见荇菜不仅是一种外观非常美丽的植物,而且还有实用价值,这种特点正好暗合了“淑女”外貌美丽,品行贤淑的标准,所以在诗歌中用来表现女子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而借用巫术追求心上人的作用也就很明显了。
再比如《王风・中谷有》中的益母草,是一种中草药,嫩茎叶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多种营养成分,有活血祛瘀,名目益神的功效,还可用来医治女性疾病,养生育子,与女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连。诗中多次提到益母草的枯萎,隐喻了生命力的消退和营养的损耗,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憔悴的女性形象,用于表示被夫抛弃的悲伤女子是非常合适的。
参考文献:
[1]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4.
[2]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陈子展.《诗经》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4]孙作云.《诗经》研究[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第4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关键词:傅玄;曹植;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7-0001-01
女性历来都是文人骚客笔下不朽的主题,文人们总是大费笔墨去描绘她们的一切。傅玄与曹植也是如此,在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各种类型的女性亭亭玉立的站在那里,妖娆多姿,争相媲美。
一、世俗女性与梦幻佳人
傅玄是魏晋时期创作女性诗歌最多的作家,他对于女性创作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傅玄虽“善言儿女”,可他诗歌的独特性却不仅仅停留在抒写女性优美迷人的单一方面,而是把笔墨触及到下层的妇女,去细细的描摹她们的悲剧性命运,有一种想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大量描写来来引起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之意 。他诗歌温柔、美丽、婉约之间总是带有平民女子得心酸和悲苦之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直面生活的残酷面,体味平淡人生的喜怒哀乐。比如他的《豫章行・苦相篇》,诗歌描写一个命运悲苦的女性,诗人认为生为女子本为苦相,可是她并不被珍惜,长大后出嫁到遥远的他乡后只能沉默、谦逊的生活,可是命运的魔爪还是会袭击她本就柔弱的身躯,就算自己极力用最卑微的姿态去乞求着男子的爱,可依然逃不掉旧不如新残酷现实。在傅玄其他的诗歌,如《明月篇》、《秦女休行》中的女性也是如此,她们的泪水、心酸、悲哀袭击读者的思维,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她们九在墙脚低低的抽泣。
曹植的作品和傅玄有很大的不同,曹植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其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有38个,可是描写可望不可触及的梦幻佳人形象有23次之多,其中神女为8个,而让普通大众根本不可以想的上层佳人形象就有15个,这和傅玄大量模仿汉乐府去创作的下层阶级女性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在曹植的《杂诗・南国有佳人》,在他笔下的女性不仅具有高层次的美,更加具有很深的内涵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个犹如三月桃花般明媚的女子在眼光下微笑,和普通大众是完全不一样的。她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犹如落入人间的天使。这和傅玄笔下的绝望女性有着本质的区别,毕竟傅的创作是以对女性的一种关怀和同情出发,而曹植想表达的则是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向往之情,在曹植的名作《美女篇》中写到“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他将女子置身于万条绿丝飘荡的丛林中,突出了女子柔美的身段和优雅的步调,接下来费了很大的笔墨去些女子身上的配饰:“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我想这样一个华丽、高贵的女子,她只能在男性的梦幻里飘摇,是她们终生追求的一种理想而已,与傅玄作品中充斥着被抛弃,被束缚的没有自由的女性形象有很大不同,当我们在感叹傅玄诗歌中女性的“藏头羞见人”或是 “跪拜无复数”时,曹植所创造的这种女性形象,完全犹如一片在天际飘飞的美丽云彩,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站在人间去张望她们的风采。
二、女性悲剧命运中“局外人”和“剧中人”观念
如果说作品都是凝结了创作者性格、激情、社会阅历、创作风格的结晶,那我认为曹植和傅玄创作女性形象的不同与其在作品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傅玄和曹植相对而言,傅只能是个二流的诗人,而曹植在文学史上确算的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行於言”,它指的是评论一首诗的好坏,最少有个标准:那就是诗歌中的感情充沛力是否能充分的感染读者。对曹植和傅玄诗歌感发生命的厚薄和深浅而言,在这里用“局外人”和“剧中人”来比喻也许是合适的。傅玄虽然用汉乐府的题材写了很多关于女性的诗歌,可是总体来说,他的诗歌没有曹植那种强烈、深沉、充沛的感情,比如他入选《诗品》的《杂诗》虽然也是直抒胸臆之作,但是并没有直接深入到感情悲苦的情面上去,而是选用了大量的形象来堆砌,在这些方面他和曹植的诗歌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当然这肯定和傅当时所处的的社会背景以及他本人一惯喜欢用文学揭露社会现象的创作目的是很有关联的,这和他作为一位很有名的政治家的身份有很大关联。曹植则完全可以说是“剧中人”,他把自己所有的生命都融入在他创作的每一个人物形象中,这和曹植本身的悲剧命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她写的女性就隐含着自己对于人生的体验,在一个又一个拥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的佳人外表下包裹着的其实就是曹植自己的灵魂,是他自己对命运不公平的一种呐喊,是他本人一种血的呼唤。
三、结语
从傅玄的诗歌中我们能读出婉约那根主弦,但更能体味他诗歌中包含着的心酸,整个作品风格弥漫着愁绪和悲苦。而创作目的完全曹植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他诗歌中无望的悲哀和哀叹诉说着对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
第5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摘 要:约翰·邓恩是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先锋代表,其爱情诗也因独特意象的运用受到追捧。爱情诗《歌》中邓恩巧用各种意象,产生陌生化效果,增强诗歌的艺术感。
关键词:《歌》;意象;陌生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1.引言
约翰·邓恩(1572-1631)是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先锋代表,他的作品主要包括诗歌、书简和布道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爱情诗歌。多恩的爱情诗歌独辟蹊径开创了诗歌先河,充满奇特的意象,给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
诗歌意象以语言为载体,是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诗歌的灵魂和生命。而诗歌的创作就是诗人将客观事物转化为意象,使主观情感通过具体的意象生动地再现。在诗歌创作中,邓恩对诗歌的意象进行创新,摒弃了陈腐的比喻,运用新奇的意象,通过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拉长了审美的时间,给诗歌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效果,产生陌生化效果。
2.意象的陌生化效果
第一个对“陌生化”理论进行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虽然没有正式提出“陌生化”,却使用了“惊奇”、“不平常”、“奇异”等说法。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言的就是一种陌生化手法。正是因为通过这种陌生化手法,将平常熟悉的事物变得不寻常,变得奇异,从而使读者有惊奇的。同时,“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由什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sky)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最先提出。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强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17世纪诗人评论家约翰·德莱顿(JohnDryden)在1693年评论邓恩时写道:“喜用玄学,不仅在他的讽刺诗中如此,在爱情诗中也如此。爱情诗本应言情,他却用哲学的微妙的思辨,把女性们的头脑弄糊涂了。”在爱情诗《歌》中,邓恩借助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如奇特的意象和夸张等使行文达到一种妙不可言的效果。这与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达成某种契合,它们都侧重感觉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并强调艺术技巧在增强可感性上的重要地位。
《歌》是一首爱情诗,在这首诗中,邓恩对女性的朝三暮四和见异思迁进行了讽刺。这一主题在艺术创作上十分常见,但在《歌》中邓恩巧妙借助多种艺术手段让陈腐无趣的主题改头换面,赋予语言新奇感和惊奇感。邓恩主要借助奇特的意象进行创造性地破坏,将《歌》中熟悉的事物和情感陌生化,使该诗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诗人在第一小节中将多种奇特的意象“陨星”、“人形草”、“魔鬼的脚”、“美人鱼歌唱”和“风”并创造性地将它们组合。这几种意象看似毫无关联,“陨星”属于现代科学的领域,“人形草”和“风”属于自然科学,而“魔鬼的脚”和“美人鱼歌唱”则为古代神话传说。这几种看似毫不相干的意象组合到一起,使人摸不到头脑。诗人为何要选取这几种相隔甚远的意象?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恰恰是这几种奇特的意象和意象的奇妙组合体现了诗人的智慧所在。
实际上,邓恩巧妙运用这几种意象表述了一系列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将不可能具体化。就“陨星”而言,没有人可以抓住一颗陨落的流星。“人形草”指的是“蔓德拉草”,这种草的草根形状极像人体,下部劈开,像人的两条腿。因外形与人相似,诗人将“人形草”比喻成女人,但让一种植物孕育胚胎却是极度不可能的。一般认为,“魔鬼的脚”状如鸭掌,整个脚掌连在一起或者状如牛羊等的蹄子。世界上没有人有足够勇气接近魔鬼,将魔鬼的脚劈开。因此,该意象再次传达出一种不可能。“美人鱼歌唱”则指的是希腊罗马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上女妖塞壬(Siren)唱的歌声。塞壬可以发出美妙动听的歌声,航海者听到后会被歌声迷住,触礁遇难或者受到蛊惑,流连忘返,不思行进,最后饿死在海上。因此,没有人可以听到塞壬的歌声而不受蛊惑。“风”这一意象出现在很多诗歌中,但在这首诗中,“风”这一意象使用的目的却打破了常规和人们惯常的思维。这一意象表达了一种不可能。虽然风可以将散播种子,传播花粉,促进植物的生长,但却不可能让人的地位提升。
由以上可以看出,诗人抓住了这几种意象的共同点,即完成这几种事情的不可能性将科学领域的意象与神话中的意象巧妙结合。但同时这些由普通语言构成的意象所代表的含义却打破了常规。“陨星”是一种平常的自然现象,它代表着稍纵即逝的时间概念和人们许下的美好愿望,但在这首诗中却表达了一种不可能性含义。因此,该意象打破了常规,使整首诗变得独特而新颖。虽然国内读者对“人形草”不熟悉,但是对类似人形的植物,如人参等却很了解。人们惯常的理解是人参代表着长寿健康。但邓恩将这一意象的含义陌生化,让植物孕育生子。在很多读者看来,这种思维方式不可接受,这也是邓恩在新批评以前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但他对意象的奇妙运用,他“古怪”的思维,却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正是他的诗歌吸引越来越多的注意力的原因。他打破常规,提出让植物孕育后代,这挑战了人们的传统惯常的思维,创造了奇特的艺术感觉。在表达不可能时,人们惯常思维是摘星星,摘月亮这样的行为。而邓恩却使用了神话中“魔鬼的脚”这一意象。这一意象首先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人们会使用“魔鬼”这一意象来说明邪恶势力和黑暗。而具体到魔鬼的某一个部位,是非常人所能及的。因此,该意象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陌生、分辨不清的感觉,造成陌生化的效果。“美人鱼歌唱”的意象取自希腊罗马神话,它常用来指蛊惑人心的事物。在《歌》中,这一意象却表明了一种不可能的情况,了人们对该意象的惯常理解和常规认知。总之,这几种表达不可能的意象的选取打破了人们的常规认知和感受,使人们产生新的审美体验。
与此同时,这几种意象的奇特组合,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拉长了审美体验。现代科学中的“陨星”,自然科学中的“人形草”和神话中的“魔鬼的脚”和“美人鱼歌唱”被糅合在一起,现代的理性和古代的迷信思想进行碰撞。反常规的组合一开始让人感觉摸不到头脑,但随着认识的加深,却让人感受到了其中的艺术感觉和艺术之美。
诗歌中各种神奇意象的奇特组合打破了人们惯常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将诗歌语言与普通生活中的语言区分开来,赋予诗歌一种特殊的气氛,使读者产生新奇的、非同寻常的审美体验。
3.结语
约翰·邓恩的爱情诗《歌》能够与众不同、个性鲜明,一系列奇特意象的应用和组合是一个重要原因。《歌》中的意象不仅产生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加深了审美难度和审美体验,而且意象为主题服务,烘托了诗人对不忠实于爱情的痛恨和怒斥。由此可见,运用意象含蓄地表达爱情比直白的表达方式更耐人回味,也更具艺术上的可读性和审关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刚.诗歌语言的陌生化[D].华中师范大学,2002.
[2] 李正栓.奇想怪喻,雅致入理[J].北京大学学报(语言文学专刊),1997.
[3] 李正栓,吴晓梅.英美诗歌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 李正栓.玄学思维与陌生化艺术——约翰邓恩《跳蚤》赏析[J].名作欣赏,2005(8).
第6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关键词] 威廉·布莱克;泛神论;动植物意象;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11—04
布莱克从幻觉中构建了一整套专属神话体系,其预言式的短诗中充满了神秘主义的不可理喻,尤其是他对于宗教的态度自相矛盾,前后冲突。例如1974年《欧洲:一个预言》中反复出现耶和华的崇高形象,充满智慧的老人在天上望向混沌灰暗的人,目光充满怜悯,大量诗作和版画都明显源于圣经的描述;然而另一方面,布莱克却又常常在诗歌中批评教会和宗教制度,例如《天真与经验之歌·扫烟囱的孩子(二)》中的诗句“因为我显得快活,还唱歌,还跳舞,/他们就以为并没有把我害苦,就跑去赞美了上帝、教士和国王,夸他们拿我们苦难造成了天堂。”这已经明显具有了现实批判的意味。两种极端态度的并行在布莱克后期诗歌《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变得越来越晦涩而难以解读,但是如果对布莱克早期简单明快的抒情短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进行细读,甄别其中含混的修辞意义就会发现,布莱克诗歌的宗教影响,圆融地统一在一种独特的泛神主义体系中,终其一生也不改其志。
泛神主义最明显的特例就是多神论。威廉·布莱克固然也赞美上帝,但却并不影响他将羔羊和孩子们放在与上帝同样的高度,例如他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羔羊》
《天真之歌》中的《羔羊》,往往与《经验之歌》中的名篇《老虎》形成对比,不仅同为罕见的扬抑格形式,而且以两种不同的动物,描绘了刚刚开始的工业时代的人类精神状态。羔羊、小孩和“他”是诗集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布莱克为这首诗所配的蚀刻画上,画着孩子和一群羔羊,诗歌以孩子和羔羊之间的对话形式展开。孩子和羔羊的意象,实指和虚指并存,也可以认为是天真与宗教的象征;而“他”则是造物主,是上帝,是“创造了你的人”。《羔羊》一诗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中,孩子不断追问羊羔:“小羔羊谁创造了你”;第二节中,孩子自问自答地告诉小羊羔,是“他”创造了你。“他”是谁?“他”是作为牧羊人和造物主的上帝;“他”是羔羊,在基督教传说中为洗清人类罪恶而被牺牲的羔羊——基督·耶稣;“他”是小小孩,是一份天真、更是宗教赋予的最高意义。《天真之歌》就是为“天真”所唱的一曲颂歌。
这首诗被称为“预言诗”,诗中大量含混(ambiguity)手法增加了诗行的多重理解。例如开头句“小羔羊谁创造了你”,刻意略去了标点,使原文的断句出现了歧义。原文是“Little Lamb who made thee”,既可以断句为“Little Lamb, who made thee?”(小羔羊,谁创造了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带有定语从句的名词短语“Little Lamb who made thee”(小羔羊创造了你),暗指上帝就是创造万物的小羔羊。再如第二节第八行“咱俩的名字跟他一样”,原文是 “We are called by his name”。这个句型同样有歧义,既可以理解为“咱俩的名字跟他一样”,也可以理解为“以他之名,召唤我们”,这是教士们受命去传福音时常说的一句话。再如全诗结尾反复吟唱的“小羔羊上帝保佑你”,原文是“Little Lamb God bless thee”,同样有两种断句方式:“Little Lamb / God bless thee”(小羔羊,上帝保佑你)或者“Little Lamb(Lame) God /bless thee”(小羊羔般的上帝,保佑你呀)。在原文中,为了音调的和谐,句尾的Lamb往往被读成了Lame(原意为“蹩脚的”),形容上帝并非万能。这样一来,结尾句就由原先甜美的祝愿,变成了宗教讽喻。
《羔羊》运用威廉·燕卜荪《含混的七种类型》中的第二种含混,即“上下文引起的多种意义并存,包括词的多义和语法不严密产生的多义”,拓展出两种对立的意义。这是含混作为修辞的本源属性,而且由含混构成的不确定性甚至能够颠覆了原本的力量对比关系。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 : 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沈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第10页。“当我们一方面研究字面意义,另一方面又研究比喻意义时,我们的研究模式仍然停留在语法层面;但是当我们无法用语法或其他语言学手段来确定两种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兼容的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占主导地位时,我们的研究模式就进入了修辞学层面。” 如此一来,羔羊变成了上帝,上帝便成了羔羊,正如诗中所说的:“他变成了一个小小孩。”于是,小孩、羔羊和上成了神一般的存在,是各自不同而又合为一体的神。千万不可将这三者的关系理解为类似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因为在威廉·布莱克看来,虽然他的诗中大量存在“上帝”或者大写的“他”,但是“谁能在万物中看出无限,他就看到了上帝;谁只在万物中看出分类图解,他就只能看到他自己……万物存在于这个永恒的世界,而与基督教的前世毫无关系。” 威廉·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张德明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第40页。这也就是说,布莱克笔下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义中的上帝,而是所有神灵的代称,这是泛神论的基本特征。
如果说《羔羊》中的羔羊、小孩和上帝,都是由天真和经验抽象出来的“道成肉身”,是多神论的具体表现,那么威廉·布莱克更多的短诗则不是塑造抽象的神祗,而是回归泛神论本源的“万物有灵论”,直接从动植物崇拜中寻找精神慰藉和指引,例如“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梁宗岱译)就是著名的范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毒树》这首以植物为题的诗歌。
《毒树》出自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中的《经验之歌》,传统上认为它们以具体的自然植物为意象,描绘了抽象的人类罪恶。即“压抑的愤怒”带来的毁灭。《毒树》一诗采用了四音步(杂有三音步)抑扬格、双行押韵的诗歌格律,这种格式往往用于童谣或者基督教赞美诗。“毒树”之名,并非表示“有毒的树”(a poisonous tree),而是和“milk tree”(乳胶树)一样,意指“为提炼毒物而栽培的树”(a tree to produce poison)。诗中描绘了“我”的愤怒幻化成一棵树,所谓的自制和隐忍都是虚伪,“虚假的阳光”和“我的泪水”把这棵树“照耀”和“浇灌”,只为最终结出有毒的苹果,毒死我的仇敌。此诗指向的主题并非愤怒本身,而是对愤怒的压抑,间接瞄准了基督教隐忍之说。布莱克认为这种隐忍,压抑了人性,结果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灾祸。诗歌原名“基督徒的自制”(Christian forbearance),后来才改为“毒树”(A Poison Tree)。这样的传统解读固然解决许多问题,却也无法解释这个故事结局的预言性,无法解释敌人吃了苹果而死去这个结尾的特殊含义,也无法匹配诗中“毒树”和“苹果”的关系。诗歌中,人的行为是逻辑的,可以理解的;而树的发展则是神秘的,不可预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否可以用“祈祷”这种仪式作为平行的原型结构来勾画人与树的关系。诗中“我”受了委屈之后,便“怀着疑惧,早早晚晚,/用我的泪水把它浇灌;/我又带着诡诈的微笑,/用虚假的阳光把它照耀。” 威廉·布莱克著,张德明译《毒树》,引自《外国诗歌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189页。英文原文是“And I water'd it in fears, /Night & morning with my tears; /And I sunned it with my smiles /And with soft deceitful wiles.”张德明的中文翻译中将“in fears”翻译为“疑惧”体现了对于这首诗歌基于一神论的传统解读,以毒树象征嫉妒和仇恨,而“疑惧”就是人类因为道德感或者对于宗教审判的担忧而对内心阴暗面的反省。然而,如果从泛神论的角度来解读就会发现,“in fear”还可以用来表示对神的“敬畏”,“in fear of God”(敬畏上帝)这个短语本来就是牧师用来劝谏教众信服上帝的常用口语词组。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毒树就不再是指一切阴暗的意志,而是成为了和上帝一样的神灵。以植物为神是万物有灵论最为常见的隐喻。诗中的“我”并非“怀着疑惧”而是“怀着敬畏”来浇灌毒树,其中所有表示浇灌的描述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诗行“我怀着疑惧,早早晚晚,/ 用我的泪水把它浇灌;/ 我又带着诡诈的微笑,/ 用虚假的阳光把它照耀”可以解读为:“我”满怀敬畏之心,日日夜夜向小树苗诉说悲伤、分享快乐并以“带有一点点欺瞒”(soft deceitful wiles)的忏悔赢得了神的偏袒,于是毒树的神灵便赐下个“苹果发红光”,帮助“我”消灭了仇敌。这种崇拜模式与原始部落崇拜图腾,祈求自然界的神灵赐与力量,消灭其他部落的敬神仪式原型构成了平行结构。只有从毒物即神灵的意义上来解释“我”与树的关联,诗歌中仇敌吃了苹果死去的结局才不显得突兀。
运用万物有灵论的人类学诗学观来解读毒树的象征意义,诗歌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立体。传统观点仅仅认为这首诗歌批判了隐忍对人性的压抑,但其实诗中同时还流露出反对唯理性论的意味,认为非理性的偏爱和理性的选择一样,都能改变人生命运和社会版图。
如果对诗中的苹果进一步剖析,就会发现其表面上是指圣经中伊甸园禁果(forbidden apple)的传说,即基督教中的人类原罪(sin)的象征,似乎圣经中原罪的根源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而在诗中却是人类对负面情绪的压抑。但是“苹果”的意象更有可能指的是《荷马史诗》中 “不和的苹果”(Apple of Discord),象征古希腊多神世界的“众神之争”,而这正是圣经反对得最为激烈的异教学说。事实上,无论《羔羊》中三位一体的假象,还是《毒树》中代表“众神之争”的苹果,都暗示布莱克试图从学理根源上批判基督教制度,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泛神的、万物有灵的统一存在,教会占据了诸神的伊甸园,而三位一体正是多神论向一神论过渡的特殊形式,这种典型的泛神论发展为一神论从而使人类受到思想束缚的观点,虽然并不为宗教研究学者们所认同,但却是布莱克思想体系中不可撼动的基石,这一点在《爱的花园》中表现得最为明确。
诗歌延续了《经验之歌》常见的宗教主题,质疑教会割裂了世俗与上帝的对话,而不是充当二者之间的沟通的使者,批判了教会对人类心灵的束缚和对追求快乐的灵魂的扼杀。“爱的花园”应该是指伊甸园。诗中显然布莱克并不认为上帝创造了伊甸园;正好相反,伊甸园先于上帝而存在,花园中的树、蛇、花、果原本都是各自的神灵。夏娃听了蛇的宣道,吃掉了代表自由意志的苹果,获得了泛神论中的“神性”,成为了异教徒之后,便被逐出了伊甸园。这首诗歌中用词往往都具有多重意味,例如“教堂”一词,原文是“Chapel”,本身就有两个意思,既是指礼拜堂,又表示殡仪馆,与后文的墓地遥相呼应。问题在于,这是谁的花园?谁的坟墓?原本诸神的花园变成了一神教的伊甸园,而教会制度扼杀“鲜花无数”。尤其是诗中写道“这座教堂把门统统关上/ 门上写着‘禁止’两个大字”(王佐良译)。英文原文是“And the gates of this Chapel were shut,/ And Thou shalt not, writ over the door”其中“Thou shalt not”是指门上的装饰画绘中有“禁止”纹样,是摩西“十诫”的句式。威廉·布莱克诗中多次提到“十诫”对人类灵魂的束缚,《爱的花园》里,“穿黑袍的教士们……还用荆条捆起我的欢乐和欲望”,同样也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化成了尤理生“嫉妒的锁链”3(P19)。
布莱克诗歌的主要中文译者张德明教授在对威廉·布莱克诗歌的研究中提到,布莱克“砸碎……理性的锁链”与“恢复尤理生的重要地位”之间的矛盾,是“因为神话的根本特征正在于它的非理性矛盾。” 张德明:《人类学诗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第339页。这是比较经典的基于一神论观点而对布莱克本人宣称的“砸碎……理性的锁链”的理解。布莱克晚年的长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深刻地批判了尤理生“只允许一种命令,一种欢乐,一种欲望,/ 一种诅咒,一种重量,一种尺度,/ 一个国王,一个上帝,一种法律。”3(P44)可见他并不是反对有神论,而是反对一神论;砸碎的并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锁链”,或者说是“嫉妒的锁链”,其实质是以更为宽容的泛神主义来反对一神论的专制性,而未必是反理性的。
T·S·艾略特将威廉·布莱克称为“天才诗人”,认为布莱克诗歌中具有“所有伟大的诗歌中所共有的独特性”。布莱克用以建构自我幻觉世界的泛神主义观与以斯宾诺莎“自然即神”或者黑格尔“理性即神”的泛神论并不一样。这两种布莱克时代盛行的泛神论观点都是物质和理性的,而诗人并不像哲学家那样关注什么是神,也并非从神的本质与相中寻找意义,诗歌更关心泛神论对一神论世界观及其制度的突破。可以说,人类学家们基于原始思维而提出的万物有灵论或者“互渗律”是一神论之前的泛神论,而布莱尔式的泛神论则是一神论之后的泛神论。按照列维·斯特劳斯对于神话的归类,泛神论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回顾式的,目的借助遥远的往事建立某种传统的秩序;二是前瞻式的历史,目的是将往事变为一个刚露头的未来的起点”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658页。。布莱克式的泛神论因为其前瞻性而具有了“预言诗”的气质。同时,对其泛神主义观的剖析,也不是为了对于布莱克诗歌提供一种解读方式,而是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在含混中构造多重理解,甚至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中,模糊了对立双方的主从关系。布莱克泛神论在诗歌中的广泛运用本身,事实上已经具有了解构的萌芽。
第7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不光人有笔名,好些个花花草草、蔬蔬果果也有听上去冠冕堂皇诗意盎然不知其究竟为何物的笔名,只不过植物自己没法给自己起笔名,都是光给自己起笔名还觉得不够过瘾的人为了营造不同的表达需要给天真的植物们安上去的。
年少时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诗,老读到一种叫做忍冬的植物。譬如,他常常把忍冬作为时光的纹理之中清晰的纹路之一:
……停摆的钟,
纠缠成一团的忍冬,
竖立着愚蠢雕像的凉亭,
黄昏的背面,鸟的啁啾,
塔楼和慵懒的喷水池,
都是过去的细节。
(博尔赫斯《失去的公园》)
再譬如,他曾经忍冬为要素之一给诗歌下了一个很“发生学”的定义:
秘密水池里
流水的循环,
素馨花和忍冬的香气,
安睡的鸟儿的宁静,
门道的弯拱,潮湿
――这些事物,也许,就是诗。
(博尔赫斯《南方》)
我当时认定忍冬是一种稀罕的异域植物,它的字面意思注定了它和博尔赫斯隐忍、克制的文字之间的联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国内的诗人都喜欢拿“忍冬”这个词来点染一种含蓄、内敛的精神,这几年有一套很不错的诗歌丛书就叫“忍冬诗丛”。但这忍冬其实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它就是俺们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银花,大江南北很多地方都一嘟噜一嘟噜地长着,开的花不但香,还可以入药,药铺里俗称“二花”。你瞅瞅,“金银花”里的“金银”俩字太经济主导,“二花”里的“二”字老让人觉得很二,所以,要把它捣鼓进诗里面,还真得用“忍冬”这个艺名。
也是在年少的时候,看翻译过来的很多欧洲作家的书,总看到三色堇这种不知所以然的植物,看名字觉得很“本真”、很单纯明快,符合我对欧洲青年的想像,怨不得意大利人把它作为思慕和想念之物,波兰人更是把它定为国花。多年后我无意中发现,原来如此异域如此翻译腔如此文艺的三色堇,竟然就是俺们祖国任何一个小公园里都泛滥成灾的鬼脸花,我小的时候,每逢五一十一被学校抓到公园去暴走一圈之后,都免不了要被老师逼迫着写荷花鬼脸花的作文,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对那些一脸讪笑的鬼脸花的愤恨之情。
最近的一次被植物的笔名忽悠是和烹饪有关。我娘子酷爱钻研厨艺,前段时间经过网上网下地认真揣摩,决定大规模地自己动手做泰国菜。难为她居然从各个犄角旮旯的商店、超市搜罗来了许多泰国菜专用香料,可最后还是缺一样很重要的佐料,名唤罗望子。听听,多诗意的名字啊,好像一个轻解罗衣的泰国妹在纱帐里望着即将宽衣上床的兀那贼汉子。俺们一开始猜测这是一种极其稀罕的泰国本土植物,所以才被汉语赋予了高度化的想像之名。可能由于这种植物所具有的异域想像性,19世纪以来的很多西方诗人都在诗中提到了它,在汉译里,我们也都把它翻成“诗死人不赔命”的罗望子,比如,波德莱尔用罗望子写过的《异域的芬芳》:
……那绿色的罗望子的芬芳――
在空中浮动又充塞我的鼻孔,
在我的心中和入水手的歌唱。
德语诗歌怪杰特拉克尔也写过:
傍晚来临的时候,
一张蓝色的面孔悄悄离你而去。
第8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关键词:滋味说;内涵;价值
前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被誉为齐梁文苑诗坛“奇葩双树”之一的钟嵘《诗品》,第一次较为具体地提出了“滋味说”这一诗学体系,并形成特定涵义的审美理论。
关于钟嵘《诗品》的研究历来的学界还是研究得非常多,通过对中国知网键入“钟嵘《诗品》”的检索显示有793条记录,(不包括日韩等国学者的研究)。虽不及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那么多。但其分别从①钟嵘生卒年问题、②三品不公和陶诗出于应璩、③《诗品》与《文心雕龙》文学观异同的论争、④“滋味说”及其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细致研究。而“滋味说”作为钟嵘《诗品》中重要的理论,学界对其展开的研究层次大抵停留在①“滋味说”探源、②“滋味说”内涵③“滋味说”的接受以及影响、④“滋味说”与中西诗学的比较异同等方面。而针对前三个层次的研究,笔者认为学界对“滋味说”的真正内涵以及内在的统一完整性是没有做出准确合理的把握,使得“滋味说”在接受诗学上和历时层面上的影响没有充分体现,从而对“滋味说”的重要价值产生了遮蔽。
针对于此,笔者试图从理论重读、文本分析以及接受诗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对“滋味说”的真正内涵加以厘清,从而展现“滋味说”在接受诗学上和历时层面上的影响,进而为我们正确了解和认识到“滋味说”的重要价值提供一种可能。
一、“滋味说”溯源
“味”的概念起源于饮食,先秦时期,味的含义主要是指味觉及其所带来的生理,与声色等而视之。《吕氏春秋・仲春纪・》:“故耳之欲无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无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皇帝,其欲桀纣同。”这说明味只是一个表示生理感受的词语,还没有同艺术联系起来。但古人又认为,饮食之味实蕴有审美的因素在内,《说文解字》训“味”为“滋味”也,“滋味”不仅指咸、酸、苦、辣诸般味道,还特指能引起人的愉悦心理的味感,这种味感里面即包含美感的成分。《论语・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是以“肉味”来比喻音乐有韵味,孔子把听乐时心理上所产生的美感与甘美的肉味在生理上所获得的加以类比,认为前者超过了后者,并对音乐有如此大的美感效力感到十分惊奇。孔子已经初步感觉到诗歌、音乐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开了后世以“味”即以美感论诗乐的先河。自魏晋以来,“味”开始同诗歌等文学创作发生了直接关联,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第一个明确地用“味”来说明艺术感染力的是陆机的《文赋》,把“味”引进了文艺鉴赏的专论中,他说:“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陆机之论,应是从《乐记》之文中获得启示,用肉味来譬喻诗文,雅而不艳,他认为只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既有美质又有文采的文章,才能产生真味、余味,给人以美感。《文心雕龙》也多次使用“味”这个词。
钟嵘所提出的“滋味”,是以生理上的味觉感受比喻精神上的审美享受。这一点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传统上的拟人化、形象化、比喻化,把文学与自身和生活密切联系起来。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滋味说,一方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同时也具有非凡的创造性。钟嵘改变了“味”或“滋味”仅仅是作为一种印象式、片面化的文学理论批评词汇出现的局面,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诗歌领域什么是“滋味说”,怎么样的诗歌才有滋味,诗歌有什么滋味能给人审美愉悦等一系列问题,展现了“滋味说”作为诗评原则、审美标准、创作方法三个维度里的和谐统一。使“滋味说”真正的成为一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范式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
二、“滋味说”内涵
钟嵘在《诗品序》中对其“滋味说”有专门的文字论述。如下: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以上文字显示了诗具有滋味,那么它在内容上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能够指说事情,摹写形状,穷尽情感,描写物体;在艺术手法上是采用兴、比、赋,适当酌情的加以运用,主张“风力”、“丹采”的结合,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审美感受上是能够带给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审美愉悦。据曹旭选评《中日韩<诗品>论文选录》一书,《1980年以后中国钟嵘<诗品>研究概观――以“滋味说”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直接论述“滋味说”(有时亦表述为“诗味说”)的主要论文如下所述:
1、吴调公《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及其美学思想》
2、李传龙《论钟嵘的“滋味”说》
3、高起学《浅谈钟嵘的诗味说》
4、武显漳《浅谈钟嵘的“滋味”说》
5、陈建森《钟嵘的美学思想“滋味”》
6、郁源《钟嵘<诗品>“滋味”解》
对以上80年以后学界对钟嵘“滋味说”研究成果的罗列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滋味说”相关论文的第一个共同点是把“指事造型,穷情写物”作为“滋味”的根本;各家论文的第二共同点是认为作诗要斟酌运用兴、比、赋三义的手法,并使“风力”与“丹采”融为一体,即“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这是构成“滋味”的两个要素。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滋味说”内涵中包括了钟嵘在诗学理想中所遵循的诗评原则、审美标准、创作方法三个维度里的和谐统一。
(一)、“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
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地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章学诚称之为“诗话之源”。“滋味说”在《诗品》中的提出与阐释,其首先应该作为一种诗评原则在《诗品》中得以彰显。“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体现在了对诗人的品评中。
《魏陈思王植诗》说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于五言诗最推崇曹植,《诗品序》誉为“建安之杰”,“文章之圣”,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建安风骨中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其诗歌具有充实的内容、饱满的情感和文质彬彬的特点。从钟嵘对曹植的评价上看,其表明了钟嵘对曹植诗歌中展现的骨气、词采、情感、文体的赞美,深度符合了“滋味说”中要求指事穷情、丹采风力的原则。而在评价中品诗人张华时说:“其体华艳,兴托多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犹恨其儿女情多,少风云气”。评价中品诗人刘琨时说:“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评价下品诗人孝武帝时说:“雕文织采,过为精密”。评价下品诗人惠休时说:“惠休,情过其才”。以上这些对诗人的品评都把“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在内容和形式、情感与词采上加以扬弃。
由此观之,“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自始至终、潜移默化的贯穿了钟嵘《诗品》的始终。
(二)、“滋味说”作为一种审美标准
虽然“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在钟嵘《诗品》一书中得以提出和遵循,但是在“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的同时,其作为了一种审美标准在《诗品》中有所体现。
钟嵘认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最好的诗歌,换句话说,一首诗歌能够带给人无极的滋味,心动的感觉,这才是最好的、最具美感的诗歌。这便是钟嵘对诗歌的审美标准。魏晋时期,玄学兴起,玄言诗成为了当时诗歌创作和思想的主流。但是钟嵘认为此时的诗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对玄言诗的批判,反映了钟嵘对诗歌应具有“滋味”的审美要求。而为了客观的评价玄言诗以及倡导良好的诗风,因此钟嵘提出“滋味说”对诗歌应该呈现的美学风格和美感要求提出标准。
“滋味说”作为钟嵘品诗的审美标准其间已将鉴赏者和接受者作为诗歌本体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里的“味之者”、“闻之者”无疑指的是鉴赏者和接受者。从接受诗学的角度讲,“滋味说”不仅应该作为钟嵘对诗歌的审美标准,更应该在鉴赏者和接受者这里进行传释活动。所谓传释活动就是指中国古典诗里(作者)传意和(读者)应有的解读、诠释的活动。在这种传释活动中,将“滋味说”的审美标准上升为普遍读者的审美标准以及不仅仅是限于五言诗的审美标准。
(三)、“滋味说”作为一种创作方法
“滋味说”的内涵里还包含了一种诗歌的创作方法,具体体现在“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曹旭说:“此言酌用赋、比、兴以为作诗之法。仲伟总览五言创作,独抒己见,绝无依傍而开唐宋诗法者”。可见钟嵘认为诗歌的创作是兴、比、赋的合理运用,并且在诗歌内容上注入风力,在词采上加以润饰,这确实充满了一种独创性和深刻性。而究其产生的原因也与当时的诗歌创作形式密不可分。
在钟嵘时期的齐梁时代,沈约等人提出的声律论正是方兴未艾的时期,声律论在当时的诗坛已成为诗歌创作的“圣经”。“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而钟嵘认为“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因此,钟嵘反对这种伤害诗歌“真美”的创作方法,转而提出“滋味说”,对创作具有诗味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创作方法。
同样“滋味说”作为一种诗歌的创作方法,在传释活动中也应该被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诗歌创作方法。
三、“滋味说”的价值
上文从三个角度抽绎出“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审美标准、创作方法的体现,实际上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滋味说”的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对总体上把握“滋味说”的内涵,充分认识到“滋味说”的价值是尤为不足的。如要真正廊括“滋味说”的价值我们还应该把诗评原则、审美标准、创作方法三方面在总体上加以把握。
“指事造型,穷情写物”作为“滋味”的根本,其代表了最根本的诗评原则;“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构成“滋味”的两个要素,其代表了最主要的创作方法;“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又代表了最高的审美感受。但我们割裂其中的任一方面来谈“滋味说”似乎都不妥。因为“指事造型,穷情写物”的诗难道不是“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诗;运用了赋、比、兴,文质彬彬的诗难道不是“指事造型,穷情写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诗。同理如果一首诗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那么它也一定是“指事造型,穷情写物”的,运用了赋、比、兴,采用了风力和丹采结合创作手法的。
由此,“滋味说”是一个独立而完整并且系统地诗学体系屹立于中国千古诗话的源头,而且深远影响到后世的诗论。诸如唐代司空图的“韵味说”,宋代严羽的“妙悟说”,苏轼的“至味论”,清代王士G的“神韵说”,乃至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都在不同程度上从钟嵘的“滋味说”中汲取了养分。在此“滋味说”真正的价值便得以显现。(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项目基金: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钟嵘“滋味说”的内涵及价值项目编号:CX2015SP178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著:《诗品》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
[2]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3]曹旭: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9篇: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
关键词:《诗经》;植物;爱情;
中图分类号:I06 文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006-01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全面而浪漫地展现了从远古到春秋漫长历史进程中华夏文明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容。这一扎根于农耕生产背景下的文学瑰宝,在它最早最本色的演绎中,充满了先民们对大自然的感怀与歌唱,缤纷多样的植物则成为情感抒发的载体,留下了不可缺少的篇章。“清人顾栋高《毛诗类释》对《诗经》中记载的植物加以注释的有:谷类24种、蔬菜38种、药物17种、草37种、花果15种、木43种。”这些数据足见植物内容在《诗经》的重要地位。同时在这部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中,爱情作为自古以来人类情感和社会生活的热门主题,也占有相当大的篇幅比重。王宗石在《诗经分类诠释》中提到,《国风》中的爱情诗共有52首。这类诗多以植物为比兴,用或婉约或直白的语言,抒发男女内心最纯真自然的情感,本色流露,毫不虚浮做作。
一、草木花朵之纯真
《诗经》中常见的植物意象有飞蓬、木槿、桃花、、木瓜、芦苇等。下面将结合具体篇目对草木花朵进行浅析。
《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飞蓬”即蓬子菜,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于山野,茜草科,入秋根枯拨落,随风卷飞,故名“飞蓬”。在这里用“首如飞蓬”比喻妇人因丈夫不在,不常梳洗而蓬头散发的样子,《毛传》曰:“妇人夫不在,无容饰。”“飞蓬”一用,将女为悦己者容表现得自然贴切,思妇形象具体生动。
《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舜”即木槿,落叶灌木,花五瓣,有红、白、淡紫等颜色。在这里,用仲夏夜的梦之花――木槿花来形容同车姑娘的美丽容颜,那白里透红的漂亮脸庞跃然眼前,梦幻而又美好。
《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可以想象,在那葱葱郁郁的桃花林中,出嫁公主的红润脸颊与盛放的花儿交相映衬,新婚的喜庆全然展现在一片红艳的花海之中。
《周南•》:“采采,薄言采之。采采,薄言有之。采采,薄言掇之。采采,薄言捋之。采采,薄言之。采采,薄言之。” “”即车前子,多年生草本植物,乡间田野很常见。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全诗只是反复吟咏“”,就已经韵之悠扬。
《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美人送我以木瓜,我投之以佩玉。在那个时代,爱情是这样的朴素而真挚,定情信物不是俗气的钻戒房车,只一个来自田间的香木瓜,就能给人以浓浓的温暖和快意,自然并幸福着。
《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蒹葭”即芦苇,想象那岸边青绿的芦苇在轻轻摇曳,似在向流水诉说着不尽的思念。一幅静谧却又灵动的画卷怎能不教人沉醉。
《诗经》中以大量植物为比兴载体,将自然之物拟人化,将人之情感自然化,使草木花朵等意象在表达爱情这一主题的反复吟咏或简单直叙中变得纯真且富有生命力。
二、男女爱情之自然
作为人类情感的永恒主题之一的爱情,在《诗经》中也被表达得自然悠扬,混然天成,毫无矫揉造作之迹。那时候的爱情,既有“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邶风•静女》)的暧昧朦胧,又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的豪迈热烈。那时候的爱情,与金钱、地位都无关,不需要金银首饰房子车子,田间的“木瓜”、道旁的“彤管”、岸上的“蒹葭”,采摘下来就是有心人的定情信物,幸福就是这样简单自然。
且《诗经》爱情诗题材丰富,细腻入微,有《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追求过程中思慕之情;有《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热恋中的欢爱之情;有《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暂别后的相思之苦;有《卫风•氓》:“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情感破裂后的悔恨之苦。
爱情的圣洁、美好、纠结、苦痛,都在《诗经》中以原生态手法得以阐释,那些花木映衬下的情感,或热烈或深沉,或直白或婉约,不变的是那份朴实率真与清新自然。
三、花木爱情之碰撞
《诗经》中草木花朵等植物意象,多寓意美好、圣洁、如意、幸福。《诗经》中如痴如醉的恋爱男女和相思相守等爱情状态,也都与快乐、纯真、自然、清新有关。二者的碰撞不是简单的“美丽邂逅”,而是共同审美体验下的“命中注定”。
《召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就有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的一语中的:“桃花色最艳丽,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则有郑玄《毛诗郑笺》所解:“华以喻女之颜色。”《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亦有王夫之《诗经稗疏》引萧炳曰:“其花虽不雅,而亦鲜媚。以比美女之颜,所谓朱太赤、施粉太白,在红白之间也。”可见以草木花朵喻恋人爱情之妙,古人皆明察也。爱情是人类最自然纯真的情感流露,植物亦是大自然最缤纷的生命形态之一,《诗经》爱情诗中对草木花朵的描写与吟咏,既是对大自然美好景物的热爱,更是将这种直观的审美体验与对恋人对爱情主观的情感诉求融于一体,物我合一,情于景醉,使得花木的美丽变得丰富而有内涵,恋人的容颜变得自然而又圣洁,爱情的滋味变得具体而有情调。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道:“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草木之物、繁花之景等外在的情境都与人的心灵相通,和人的情感结合为有机的整体,在本真的审美共性下将爱情这一主题演绎得自然纯真,《诗经》中花木与爱情的碰撞,就是主观与客观的激荡,人心与自然的合唱。
参考文:
[1]布莉华、刘传.中的植物文化[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5,(3).
[2]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毛苌、毛亨.毛诗故训传[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方玉润.诗经原始[M].中华书局,1986.
[5]姚际恒.诗经通论[M].广文书局,1977.
[6]郑玄.毛诗郑笺[M].学海出版社,2005.
- 上一篇:土木工程类毕业论文范文
- 下一篇:内部员工管理办法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