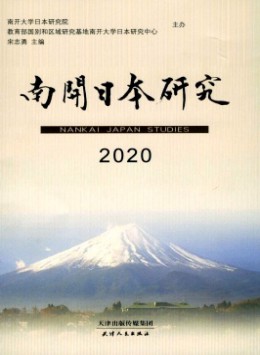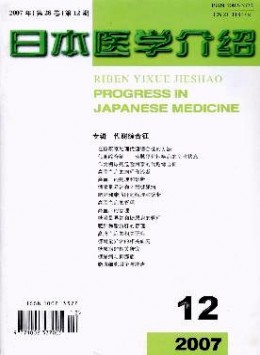日本传统文学物哀美意识研究

摘要:“物哀”美意识是日本美的源流,其发展而成的“物哀论”是对日本文学民族性的概括总结,也是日本文学独特性的体现。它通过对文学价值取向、审美判断、创作与接受心理的影响,深刻参与到日本传统文学空间的建构。本文探究“物哀”美意识如何在自然、宗教、文化的多重因素中创生,如何在不断的审美超越中建构文学这一自由的生命形式,又如何在二战以后的历史阶段受日本社会意识形态西化、审美情趣异化、创作视角内化的多重压迫下消解了物哀美的韵味,造成这一传统文学理论的解构。
关键词:物哀;日本文学;文学空间;建构;解构
美意识,是“在主观与客观志向相关并使主体与客体能动与受动相互反转的创作或鉴赏经验中,将创造性对象规定与接受性的自我反省二者的动态平衡作为肯定基准,而对带有情绪性出现的对象的主客融合状态作出直观判断的意识作用”。[1]“物哀”(mono-no-aware)是日本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所形成的独特美意识。这种美意识从上古时代的《古事记》《万叶集》等作品中萌生,至中世的《源氏物语》成熟,经近世传统文学的锻造,渗透到日本人的文化基因,浸润着日本文学创作、接受的全程,成为决定其审美情趣的根本要素,呈现出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稳定性。而在日本文学步入现代之后,这种美意识之于文学的影响受到诸如意识形态西化、审美情趣异化以及创作视角内化的挑战,逐渐走向衰微,并参与到日本传统文学在后现代背景下的转型与解构。这一过程,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学所遭遇的一场重大危机,也是对后现代主义图景下的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种警示。
一、“物哀”美意识在日本古代文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创生
“物哀”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师本居宣长所提出的文学理念。本居宣长受《古事记》影响,认为文学应从儒家道德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关注并尊重人本身的情感,进而提出“物哀”的概念。他在《紫文要领》和《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中强调:“‘物哀’就是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就是从自然人性出发、不受道德观念束缚、对万事万物的包容、理解与同情,尤其是对思恋、哀怨、忧愁、悲伤等刻骨铭心的心理情绪有充分的共感力。”以物语和和歌为代表的日本古代文学的创作宗旨就是“物哀”,作者只是将自己的观察、感受与感动如实表现出来,从而寻求审美共鸣及心理满足,其作品中并没有启示、教诲、引导的功利目的,而读者的阅读目的也是为了“知物哀”,“知物哀”既是文学修养又是情感修养。这一文学理念与江户时代之前,长期占日本文学评论史主流地位的“劝善惩恶”论有着根本不同。“劝善惩恶”论建立在中国儒家的道德学说基础上,在文学评论中强调伦理纲常,文学主题与表现很少脱离道德的评判与约束,人伦关系被稳定地置于艺术创作与审美的核心地位,而创作者及接受者的情感则处于次要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钟嵘在《诗品》中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咏。”这些表述情感之于文学创作的作用都与“物哀”有所接近。但中国的“物”更强调的是无情之物,其情由观者借其自身遭遇处境所赋予。进一步说,这种情是基于道德纲常、理想志趣之上的伦理化的情,具有社会性。而物哀中的情则主要强调与人的理性、社会道德观念相对立的自然感情即私情。所以,中国的感物之情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日本的物哀之情则发乎情、止乎情,乐而淫、哀而伤。此外,物哀与中国明清诗论中的“情景交融”也有差异。差异在于“情景交融”强调审美主客体关系,主体使客体诗意化、审美化,从而实现主客体的契合与统一,达成中和之美。物哀更侧重于作家作品对人性与人情的深度理解和表达,并特别注意读者的接受效果,即“知物哀”。因此,物哀从文学角度肯定了文学对人性与人情的滋润与涵养的功能,具有东方温润、细腻、绵长的文化色彩,并由此打破了儒学传统对日本文学的道德束缚,确立了日本文学美意识的民族性。
二、“物哀”美意识成为日本传统文学空间建构的美的根基
法国文学批评家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认为文学空间的生成与构筑依存于作家自身对生存的体验和感悟,并非是一种独立于其生存体验之外的景观、场景或幻象,更非标示时间在场的固化场所,因此,文学空间是一种内在的、深度的、孤寂的、多维的体验空间。从日本近现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物哀”透过文学空间建构所呈现的传统美意识在近代的发展与变化,以及这些文学作品所赋予“物哀”精神的近现代意义。其中,川端康成、渡边淳一的作品最具代表性,不仅富含日本本土文化风情,也渗透出人类共通的本能情感体验。在人类共通的本能情感体验中,最具感知力的是男女恋情。叶渭渠指出:“‘物哀’的思想结构中,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渡边淳一的“不伦”小说更具物哀文学气质。与“以伦理道德的善”来评价文艺美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学评论观不同,“物哀”的文学评论观是以“知物哀”为善的。本居宣长受《古事记》影响极大,而《古事记》是日本最古老的文学,叙述了神道教的起源,即极度的自然崇拜,在自然崇拜中,不受后来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追求作为自然之物———人的本能释放。《源氏物语》中绝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是“好色”者,都存有不伦之恋。由此而引起的期盼、思念、兴奋、焦虑、自责、担忧、悲伤、痛苦、绝望都是可贵的人情。衡量的标准是出自真情,只要是出自真情,皆无可厚非,即属于“物哀”,都能使读者“知物哀”。从这个角度来讲,不难理解受“物哀”论影响下日本文学“不伦”主题的出现、风靡,以及在日本社会受到的理解和包容。因此,物哀美所依存的文学空间是一种充满悲剧意识的文学再构,一切美的体验实现在以悲剧为创作结构的文学空间建构中,同时,由于这种悲剧评价跳出了“将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的一般标准,着眼于从个体极其狭小的自我关照的视角去内视与感知其由本能欲求所带来的冲突与悲恸,这种悲哀之感由于空间的狭仄,而迸发出浓烈不散的哀伤气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具有一般悲剧的共同本质,也是必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物哀美的民族性经由文学空间的悲剧性得以确认和深化。
三、“物哀”美意识在日本现代社会的文化异化过程中解构
“物哀”作为一种美意识,在日本传统文学空间的建构中起到了奠定基调的作用,推动了日本传统文学民族特色的传播。但是,在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中我们发现,以物哀为表征的日本文学传统空间正在逐渐被解构,这种解构的力量既存在于内部又来自于外部。在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生存以及如何生存成为一种问题,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受到多重冲击,进而影响了文学空间的稳固性。这些冲击及其对传统文学空间的解构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二战之后,日本社会迫切的西化愿望。日本人世界观的历史性演变,是在其执拗地保持着本土世界观的基础上,反复多次地使用外来体系“日本化”所导致的。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化的根本是由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者哺育着的。西方文化已经深入滋养日本的根,两种文化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复杂的化合”。二是物哀中“哀”不断异化为颓废与无聊,成为颓靡的表征,表现为“无聊文学”的出现。无聊文学表现的是“对无聊的小人物及其‘无聊’的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这些真实的描写在读者心中酿造成同样‘无聊’的心情和气氛;人物对‘无聊’的种种反应也是‘无聊’”。与“物哀”所代表的纯粹日本韵味和鲜明的民族特性不同,“无聊”虽然是一种心绪,并且日本文学向来强调内心情绪的传统,但无聊的心绪是基于年轻人过度专注个人存在空间,在物质富足条件下,精神世界愈发贫乏的危机。在文学作品中,极端颓靡的表征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死亡,成为当代日本所遭遇的真正危险。这种审美意识大大背离了“物哀”美意识的审美初衷,叶渭渠指出:“‘物哀’所含有的悲哀感情,绝不是对外界自然压抑毫无抵抗力所表现出来的悲哀,它经过艺术锤炼,升华为一种独特的美感。因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美意识,一种规定日本艺术的主体性和自律性的美的形态。这就是通常称作悲剧的美形态。”将这种具有悲剧力量的文学审美追求异化为“无聊”“颓废”甚至“死亡”,不仅丧失物哀的韵味,而且对物哀论的存在空间进行了消解。三是文学创作主体文学视角的“内向化”。这一方面源于日本文化的内指性,一方面是目前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中的多数,热衷描写“日常生活”“恋爱”或内心风景,面对社会和世界,以“被动姿态”从事创作不仅限制了文学的自我超越,也限制了文学的批判力量。所以,当代日本环境下,基于物哀美意识所构建的传统文学空间正在逐步解构,大江健三郎总结了日本现代文学长期陷入低迷的原因:“在严肃文学中,已找不到当今日本的知识阶层(包括我国多数大都市大学生)———日本人的新类型。”[2]即日本现代文学对日本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日趋下降,日本文学失去了主动姿态和创作主题。传统的物哀美意识一直渗透并伴随着日本传统文学空间的建构,参与着社会文化的生成与反思,借此传递着日本美的意蕴,然而,面对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文学让出了文化空间的中心位置,日本传统文学空间更是在文学精神空泛化与文学理论多元化的双重夹击下不断萎缩,在崩溃与再生的文化结构中日渐衰弱,成为现代日本文学的一种显在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大石昌史,梁艳萍,谢同宇.“日本美意识”与“场的逻辑”:通过“心”的“相关”“反转”构造阐释“物哀”[J].外国美学,2013.
[2][日]黑古一夫.论日本现代文学1987年的“转型”[J].日本研究,2007(3).
作者:冯露 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 上一篇:传统文学创作意境研究范文
- 下一篇:小学数学“对话教学”的实施策略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