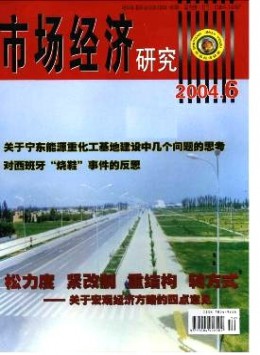市场经济对乡村典型的政治影响

乡村典型作为政治橱窗里的展品,为获得推展乡村典型政治的势能,经常被以理想纯化的宣传推至很高的地位,以突出其政治追求的崇高性和超越性,却难免经常出现人为拔高脱离实际的情况。而乡村典型也善于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如南街村毫不讳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宏图大略,而华西村宣称“看社会主义”则要到华西,这样的说辞确有一定的经济成绩作支撑,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却难掩其乌托邦色彩。乡村典型作为市场主体要生存下去,当然得“做事时自有妙法”,高调的理想正可以被编织成遮掩实利追求的迷彩服,一方面自我圣化其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一方面雇佣大量外村廉价劳动力,以纯粹的市场逻辑悄悄置换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想,风生水起地玩转市场和意识形态。这当然也是因为在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新时期,村庄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经济理性就不太可能创造出显赫的经济成绩以晋升为乡村典型,而缺乏光鲜经济成绩的乡村典型也会失去立身之本,备受质疑。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被认为超越一般乡村社会的乡村典型,也直言不讳对于利益的追求,如天津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上世纪80年代说出“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话,既含蓄又直白地道出了乡村典型生存的潜规则和硬道理。所谓“向前看”就是要认真学习时政,熟知国家方针政策,把准政治脉动,走对政治路线,看似乡村典型的政治追求,实是其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准确把握,是经济理性的体现;而“向钱看”可看作对于经济中心的粗陋解读,是乡村典型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理性的必然体现。在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下,市场理性必然主导乡村典型的运行逻辑,只是过于直白的利益观使得作为典型支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崇高性荡然无存。乡村典型政治的理想仅是装点乡村典型的美丽花边。因而,被寄予政治厚望的乡村典型颇为吊诡,乡村典型所实际展现出来的东西和人们意图通过乡村典型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之间不可避免出现鸿沟。
市场经济所培养的理性精神还会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对于树立乡村典型工作方法的深刻反思。一直以来,由于乡村典型政治能营造出一种浩大热烈的浪漫主义的动员氛围,被好大喜功者当作理想的工作方法。但乡村典型政治对权力的依赖和对示范可能性的主观认定,必然带有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刻板的官僚主义的特征,形式重于内容,很难有实质性作用。而市场逻辑的优势就是不拘一格的灵活性[3],会自动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摒弃任何形式主义,从而削弱对于乡村典型政治的工作方法的理想化期待。在市场经济下,乡村典型不仅要看起来很美,而且不能造成东施效颦的恶果,否则,乡村典型政治很难行得通,乡村典型也免不了遭到最终被抛弃的命运。如小岗村经验能帮助大多数农村解决温饱而被普遍仿效,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红极一时的乡村典型,却也只是纯粹的农业典型,因此大包干在大邱庄和华西村等具有工业基础的明星村庄照样行不通。这些村庄继续原来的集体管理体制,以便把分散的稀缺资源集中起来办企业,发展村庄经济,为中国农村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些村庄也成为更受推崇的典型,其发展经验受到青睐并无不妥,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被以“农业学大寨”的方式在中西部乡村强制推行的时候,成功者凤毛麟角,失败者满目疮痍,不但没给中西部乡村带来发展,留下的债务一度成为束缚这些地方发展的沉重包袱。所以,乡村典型虽甚合某些人之理想,也能激起农民之向往,但在一个具有更多自主选择权的时代,农民会以自己的经济理性加以评判,如果乡村典型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那么,乡村典型政治只能徘徊在大多数村庄之外,不得其门而入。
市场经济的法治导向对乡村典型政治的人治导向的制约
理性经济人对于利益的全力追求会打开“潘多拉魔盒”,放大人性中邪恶的一面,所谓“利之所存,行之所尚;利之所去,行之所息”。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其健康运行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须以明确的规则约束人们的行动,保证竞争规则的公平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引导人们确立合理的行为预期,所以,市场经济即规则经济,它内在地要求规范有序。经济活动作为人类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经济规则具有统率作用,“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成熟最权威的规则,不仅是经济运行的依据,也是政治运行的依据。因此,法治是现代人类经济、政治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而乡村典型政治可谓中国人治传统的现代翻版,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受到法治的制约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检视当代中国乡村典型政治的历史,单以树典型而言,就充满了偶然性。树典型虽是政治所需,却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多取决于领导人的喜好,具有明显的人治特征,成为运动式治理的手段。“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的三十年典型史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小岗村在时期,实际上是缺少集体主义精神的落后典型,谁能想到它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并成为三十年来最有影响的乡村典型之一?小岗村人在按下血手印的时候可谓诚惶诚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以及大包干在北京报“户口”受挫时,都给安徽省委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小岗村的大包干也被“冷处理”了,可干三到五年看看[5]。小岗村没成为反面典型已属幸运,岂敢妄想成为登堂入室的正面典型。邓小平的一番话解了安徽省的围[6],竟使得小岗村咸鱼翻身,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典型。1998年和2008年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了强调改革的意义和彰显改革的成就,两次造访小岗村,也让小岗村更加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上,小岗村不要说同沿海发达地区比较,即使和安徽省其他地方相比,本来自然条件较差的小岗村的先发优势很快荡然无存,除了一张“血手印”,鲜有引人瞩目的创新成绩称得上典型的地位和荣耀,甚至一度成为“落后标本”,仅剩下忆苦思甜的功能,常令参观者失望而归。作为改革典型的小岗村历史使命业已完成,“典型不再”亦是人之常情。可为了保住小岗村典型,只得以各种无偿援助、凌空蹈虚的宣传、政策优待(如很早免除农业税和获得各种援助)和四星级“政治”旅游景点来维护典型形象[7],就乡村典型政治而言完全是逻辑悖论。由此可见,树立和宣传小岗村典型不是“制度”、“标准”等客观因素在起作用,而是“人”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小岗村是老典型了,在小岗村问题上须照顾一些老领导的感受,导致落后也能当典型的情况出现。在以规则统率一切的市场经济时代,终究难以消除人们对其资格的拷问,因为人们对于典型还是有着类似于“标准”与“规则”的共识性要求。
乡村典型政治由于不会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框架把身份平等和发展权平等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在规则之下公平竞争,往往成为乡村典型的经济和权力的积累机器,实际在刻意对村庄进行身份切割,以政治庇护造就乡村典型的不败金身。这般形成的乡村典型被拿来运动式治理乡村,要求全国乡村学典型,即是以两类乡村之“异”而求乡村之“同”,清楚暴露出乡村典型政治的非制度化和非专业化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以及不稳定性的人治特点,难以推动乡村善治。此外,在市场经济下,乡村典型领导人借着村民自治和企业管理的名义更有效掌控村庄经济政治资源,容易成为集美德能力于一身的克里斯玛权威,为村庄的人治提供了条件。某些村庄领导人甚至蜕化为“红色堡主”,导致普通村民某种程度上的人身依附。禹作敏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8]。村庄政治病变为家族政治,异化为“圣人治村”,典型村庄似是村庄能人打造的“羊的门”。村民们都努力表现自己对他们和村庄的忠诚。恩宠与排斥相结合的德治模式有效实现了对于村民的规训,实现了村庄治理的权力技术与村民抑制改造自我的自我技术的一种特殊结合[9]。这样的乡村典型稀缺民主和法治的基因,即使拥有漂亮的经济成绩单也不能使其获得示范引领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对乡村典型保守性的挑战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经济则代表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市场主体为了完成交换实现利益最大化,会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打破从村庄到国家的所有层次上的割裂封闭状态。物的交换也必然带来附着在物上的文化交流,使文化管理或主动或被动地放松,由此带来的思想冲击会呈现破窗效应,推动多元化的观念市场以及自由、平等和竞争的开放社会逐渐形成,部分社会成员会选择新观念取代旧观念,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观念形态发生变迁,打破传统社会对教条和权威的盲目崇拜。这使得封闭保守的乡村典型面临新挑战,进而冲击乡村典型政治。
乡村典型保守性的表现之一是乡村典型作为先进模范,也是既得利益者,尽力维护其所代表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这是因为该模式帮助乡村典型获得特殊的政治地位,被视为存身立命的政治资本,却也成为它的沉重包袱,使它不能正视社会的转型和挑战,不但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怠于改革创新,相反却更愿意极端化其模式,以为非如此则不足以彰显特色、巩固地位,对其他村庄的新模式则态度消极,抱有戒心,甚至加以压制。且不说“”期间,“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因为不学大寨很显然意味着另搞一套,不仅是对大寨至上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也会使大寨模式遭到质疑和动摇,所以,当万里来到安徽决定不学大寨的时候,遭到了大寨的指责和“中央的阻力”[10]。这样的典型情结在改革后亦复如是。以改革著称的小岗村在以激烈的按血手印的方式分田到户后,因创建出一套新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成为名扬一时的典型。可这种体制只能解决温饱,难以带来富裕,所以村中有人希望重新集体化,像绝大多数明星村一样,借助集体力量整合资源,发展非农经济,改变落后面貌,做一个名实相副的典型。可这个想法出来以后,立即遭到反对,理由很简单,小岗村是大包干典型,再回到集体经营,那小岗村还是小岗村了吗?[11]此外,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管理体制和华西村的家族式管理体制虽饱受诟病,但两村皆以典型之名博取政治优待,以企业之实虚化村民自治,还不断强调其社会主义“特色”,占据政治意识形态高地,拥有不俗经济实绩,呈现绚丽的红色文化,岂能随便革新?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焉有不变之理?
乡村典型保守性的另一表现是乡村典型刻意隐瞒与粉饰村庄真相,意图展示完美的典型形象,却与时代格格不入,愈显保守落后。笔者多次调查曲折发现,小岗村虽小,村内矛盾却大。两位大包干带头人冲突尖锐,连上级领导也摆不平,需要驻村干部来维持平衡。当然,为了典型和上级的颜面,在宣传的时候这些都被“和谐”掉了,只是“择其善者”而登之。《小岗村调查》的作者在小岗村调研时遭到了当地的种种阻挠和非难。笔者在华西村的调研虽未遇到麻烦,却要不找不到村民,要不找到的村民总是说着千篇一律的话,和宣传材料没什么区别。这种封闭保守仅能让人看到乡村典型表面的浮华,难以了解真相,既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开放社会背道而驰,也让真心学典型者不得要领,乡村典型政治又如何发挥作用?实际上,在当前高度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条件下,资讯极其发达,很难筑起完全屏蔽村庄真相的防火墙,透明、公开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而典型村庄的政治却似乎总有着难言的禁忌。事实上,人们对于乡村典型总有这样那样的疑问,却罕见公开及时的回应。乡村典型缺少竞争更新机制,更看重典型的身份,与现代社会的精英式选择标准格格不入,似乎一朝获取即终身拥有,虽然有的典型实在不堪。不过,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开放社会的氛围下,仍受传统惯性影响的管理体制对现实反应的迟钝,以及意识形态也对保守的乡村典型政治有点厌倦了呢?
经济现代化对乡村典型政治的弱化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能够快速推动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另一面则是农业小部门化,即“随着经济增长,农业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经济地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农业增长对整个经济系统增长的贡献、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系统总产出的份额以及农业获取社会生产所需稀缺资源的能力都不断下降[12],自然表现为乡村社会边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82年最高,为33.4%,到2010年降至10.1%[13],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迅速转型。因此,乡村典型的示范功能错位,示范空间逼仄,示范对象衰落,自然会弱化乡村典型政治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乡村典型的非农化特征非常明显,少数村庄抓住经济转型的契机,以工商业率先致富获得典型称号,却是非农化的乡村典型。除了小岗村因率先大包干成为农村改革典型外,其他村庄中只有率先致富,才具备成为乡村典型的物质前提,而要率先致富就必须摆脱农业束缚,走工业化道路。从华西村网站的主页被命名为“江苏华西集团•中国第一村”可知,华西村实已不是乡村,而是一个大型经贸集团,村域经济以二三产业为主,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1%,农业比重低,务农人数少。江阴市2011年批准华西村正式更名为“华西新市村”,尽管称谓改得比较晚,但其管理方式早已由村庄向城市转变[14]。像南街村等也是如此,残存的农业微不足道,仅剩下点缀功能,徒具农村之名,却有城镇之实。即使以农为主的小岗村,也在竭力追求工业化,发展旅游业,到处招商引资[15]。根据产业分工,农村是农产品生产地,城市是非农产业聚集地。可现实却是,乡村是农业的领地,本应树立农业生产和组织创新的乡村典型,可现实却是非农化的乡村典型大行其道,俨然构成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悖论。大多数乡村徒生羡慕之情,却无从模仿,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非农化门槛日高,动员中西部农村不顾条件学习工业化的乡村典型办乡镇企业,实有误导之嫌,乡村典型政治的效率越高,贻害反而越大。
农业小部门化的另一面则是乡村社会边缘化和空心化,这会使得即使真正切合农民需要的乡村典型的影响力也会因此下降。市场要求农民作为自由劳动力从农户和村落共同体中分离,从而瓦解农村社会特别是村落共同体,“而且,市场力量对共同体的敌意和瓦解,虽采取解放农村自由劳动力的激进姿态,并不能遮掩它是要求经济从社会脱嵌并以市场自由规则支配社会的组成部分”,甚至“釜底抽薪,彻底摧毁共同体及其规则”[16]。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在收人差距的推拉作用下,城市犹如黑洞吸走了农村的资金和人才,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已上升到49.68%,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13.46个百分点[17]。其结果是农村精英人物和青壮年大量出走,村庄萧条无人气,留守农村的多是老人、妇女及儿童,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有限,政治态度消极冷漠,连接农民的纽带渐渐松垮,农民生存状态原子化,村庄公共生活衰败。没有了最起码的人力资源和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何谈学习乡村典型?因此,城市化虽没有完全消灭农村和农民,但导致了农村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乡村典型自然难免被边缘化。乡村典型政治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呼风唤雨,其经济社会基础是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后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当农村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的时候,乡村典型政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必然变轻,逐渐被边缘化。也许某位学者对乡村末世景象的描述看似夸张,却恰成最佳注脚:“农民,这个被现代化工具宣判了死刑的阶层……在最后的日子里,老农们显得十分平静。猪圈、牛栏拆除了。古老的农具变卖给收藏家了,锄头上的泥土已经清洗,高高地挂在了墙壁上。”[18]此时,谁还有多少兴致来谈论乡村典型政治呢?
乡村典型政治集中经济政治资源推出亮丽的乡村典型,引导乡村发展,鼓舞乡村精神,提升国家形象。但乡村典型政治的逻辑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市场逻辑耦合,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存在巨大冲突,因为有的乡村典型很多时候凭借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左右逢源,予取予携,经常能够轻易获取普通村庄难以奢求的稀缺资源,非常规实现经济发展,其真实的经济发展路径与其所示范的经济发展路径大相径庭。相比绝大多数普通乡村脚踏实地依靠自身努力发展经济,乡村典型即使经济“高效”也难以激发其他乡村的模仿而继续其“政治神话”。乡村典型政治历经市场经济的反复淘洗,作为意识形态花边已失去其原本该有的一抹亮色,似乎还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从而消解了乡村典型政治的多种可能性,如此的乡村典型政治又何以为“典”,怎能行“治”?看起来,乡村典型政治收敛于市场逻辑大概是二者当下博弈的必然结果。(本文作者:董颖鑫 单位:巢湖学院乡村治理研究所)
- 上一篇:农村复垦工程的经济效益研讨范文
- 下一篇:市场经济环境下创新人才培养路径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