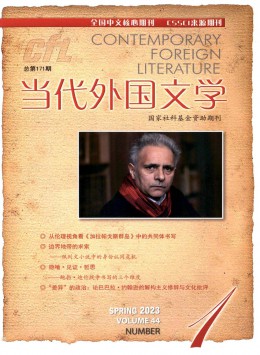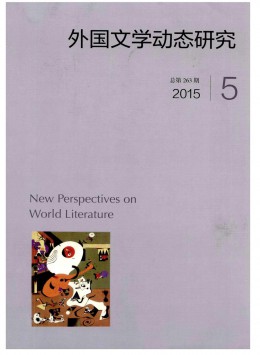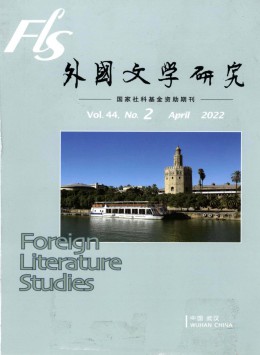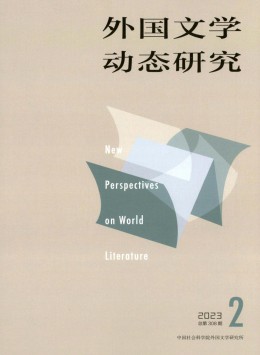外国文学教育价值观

一、概念辨析:何谓“价值观教育”
在研究展开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什么是价值观教育?传统上,价值观常被化约为“思想品德观念”或“道德观念”。因而价值观教育也就被推理为教育教学领域通常所说的“德育”。然而推究起来,二者却迥然有别。价值观(values)是“个体对事物及意义评价的观念系统,即推动和指引人们采取决定和行动的价值指向和标准。在心理学中,价值或价值观是比‘态度’(atti-tude)‘、信念’(belief)更宽泛的概念,通常指人生观的核心内容,为人生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2]而德育是“旨在形成受教育者一定思想品质的教育。”[3]“我国教育界一般都认为,学校德育主要有四部分组成,即,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4]可见,价值观教育比德育更着眼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它远非以实用目的和制度规范为圭臬,而致力于更宽泛意义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的引领。价值观教育侧重的是如何对世间万物和潜在影响自我行为的因素做出评价,德育关注的则是从社会伦理层面规范和协调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虽然一个人的价值观与他的道德观念必然会有交集,但本文认为,价值观教育更关注“精神自我”,德育更偏重“社会自我”。[5]
不得不说,外国文学[6]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比一般文学类课程更需要价值观教育的充分施展。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学自源头之一古希腊以来,就开始高度关注人本,以探求人生价值、丈量人在世界的位置而为文学目的之一,及至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奠定西方文化第二根基后,西方文学更是被引向深邃的精神层面,广泛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以灵性生命和精神呼吸划定人存在的维度。尽管沿着这条脉络,文学的发展不乏畸变,但无可否认的是,对生命和世界的意义与价值的终极关怀,始终回荡在西方文学的心府,无论时代怎样更迭,文学形式怎样流变,价值观探究始终是西方文学的灵魂。当然,西方文学所热衷思辨的价值观,绝非超验的抽象概念,而是灌注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价值观教育本质上乃是关于文化认同的教育……在这里,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活中参与性地、体验性地继承与发展某种或某些特定文化的过程。”[7]高校外国文学教学通过文本层面的意义解读和文化层面的观念传导,而使学生近距离体验了异质文化。因此,对于价值观教育来说,外国文学课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更在于提供了文化接触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文化的差异在对照中彰显,不同的价值观也在交锋中碰撞。外国文学课的一项重要功能正是引领学生辨别、体验、吸纳异质文化的价值观之精粹,将人类思想的宝贵积淀传承下去,同时也丰富、延展、调整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二、回溯生成体系:价值观教育的前提与方法
明晰了“价值观教育”的概念后,就抵达了问题的根本:究竟哪些才是需要我们积极认同的西方价值观之精华?我们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外国文学作品中浮现的林林总总的价值观?本文认为,西方文学具有特定的生成体系,必须将其置入所由来的文化语境,才能理解和评价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这首先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前提。当然,进入他者的文化语境并非易事,且不提我们主体的修养学识怎样,单就我们的阅读对象而言,同样的语义单元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下,意义完全有可能大相径庭。而且当代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早就指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8]这似乎使跨文化的阅读更面临尴尬的处境。但布鲁姆并非意在终结阅读活动,而只是指出阅读和写作必定是创造性的,诗(文学)的意义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背离前辈中产生。我们认为,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接受也是如此,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期待与原作者的绝对契合,同时,倘若我们能够深入探察西方文学的源头和承继嬗变,厘清各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精神,捕捉诸多观念生成的因缘际会,并以文本本身为根基,那么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学所蕴藏的价值观念是完全可能的。众所周知,西方文学历经数千年演进,其内在的观念意识、价值准则等等也在屡屡进行着确立、突破、回归、重建等各种尝试。但总有一些文明的酵素沉积下来,酿造了西方文化传统最基本的精神理念,比如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终极关怀等等。
这些观念虽然在不同的历史话语中一再地被质疑、检验,甚至弥散不见,但它们的身影又屡屡重现,从未寂寞。即便在后现代思潮泛滥之际,本质主义的一切乃至意义、价值、真理本身都遭受了抛弃和解构,一个有意味的事实却是,那些被质疑和消解的观念、精神本身,却并没有真地死掉。[9]所以,本文认为,上述这些价值观念尽管有着芜杂的内涵和波折的接受史,却基本可以视为西方文化中最具生命力、最值得继承的精髓。而即使那些卷起千重硝烟、甚至饱受诟病的极端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我们认为,也应当看到它们所独具的意义,那就是,它们抒写了高度的批判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本质上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其实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没有对理性、个人、人本、自由精神的高度推崇,是绝不会诞生这种批判意识的。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牵绊,我们在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往往又面临着对上述价值观的审读困境。例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自由”精神是对人性和个体性的极度维护还是对人的社会性的颠覆、僭越?怎样评价那些被极端化的个人主义英雄?个体的反叛在多大程度上是正义的?宗教之爱与人本关怀是否具有不可挣脱的悖谬?悲观主义与颓废主义、非道德化等等,是富于意义的反思和批判,还是精神的逃避和沦陷?我们认为,这些富于争议且反复回荡于西方文学的问题,无不与价值判断相关,每一重尖锐的思辨,无不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必须将这些观念、概念、问题放到西方文化系统内仔细辨析,才能理解它们的真实指向。
譬如,如果从道德说教的逻辑看,则无论爱玛•包法利或是安娜•卡列尼娜都不足为训,她们无疑拆卸了传统道德的篱栅,成了可怕的纵火者。然而倘若能从爱玛的迷梦透视出她对庸碌环境的极度抗拒,从她“堕落而不以为堕落”的义正词严倾听出作者深深的反讽和叹息,则她才既不会被简单地冠以骂名,也不至于被奉为冲破藩篱的勇士。没有对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全面反思、没有对西方女性地位的历史性审视、没有对西方文学叙事方式之幽微的关注,则这个人物必定要惨遭道德之刀的屠宰,而且注定要丧失其伪浪漫主义反叛的悲剧内涵。同样,于连(司汤达《红与黑》)、阿乐哥(普希金《茨冈》)、布兰德(易卜生《布兰德》)们也都在演绎着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叛,同时也在试探着自由的限度,经历着“浮士德难题”的磨砺。那么如何看待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群体性,讲究集体利益为先,重视德性修养,“从文化上讲,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也极不发展。”[10]而且,“个人”首先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有其尊严和权利的个体,而是相对于整个等级制而言的渺小存在物,[11]如此看来我们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个人主义”,就缺少古希腊以来就受到推崇的价值维度———“个人主义”代表着高度的人本关怀和对制度与积习的积极反思,而并非等同于自私自利主义。我们略以数例为证是想表明,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价值观的考量不能一概本土化,要评价某个观念,不能止步于词语标签,而要追问概念背后的观念体系。
三、结语:主体价值观的重建
外国文学教学实践证明,对他文化的评介、传播难免要面临价值观的冲突碰撞。往往,即使我们很仔细地追溯了某些价值观的来路,也未必能认同那些观念本身。我们认为,既然价值观教育关乎文化认同,那么多元文化接触中出现的抵牾、排斥、质疑实属正常。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照单全收,而是要辨析不同文化观念的精微,只有从各自内在的文化逻辑出发,才能洞观异文化价值观的真髓。倘能如此,也就达到了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的,那就是,通过主体的判断而包容、吸收异质文化的思想精华,从而丰富、调整、重建主体的价值观。
- 上一篇:戏曲表演艺术研究范文
- 下一篇:民间剪纸艺术思路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