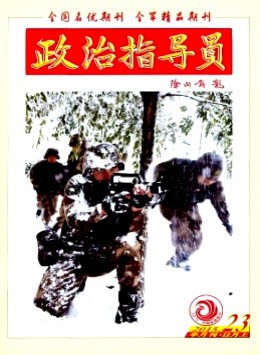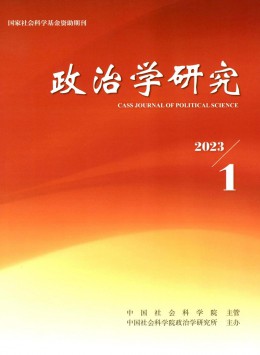政治风险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第2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政治稳定风险主要指的是有关政治统治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其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政治安全、政治稳定和政治冲突。
1、政治安全从本质上而言,人类政治学研究就是一个追逐政治安全的历程。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对被统治阶层而言,它存在必然意味着风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政治权力具有原罪。古今中外政治学家的研究其实大都耗费在探究如何去减少这种原罪上,经过他们的探究,逐渐发现政治权力之所以“恶”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统治权力的不受约束,所以政治学家们希望以民主的手段去代替专制主义统治,这在西方政治史上表现为民主与专制的长期斗争过程。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早期,在王权政治或者宗教政治形态下,“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们拥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这种任意杀戮的权力就将风险带给其治下的所有臣民。为了保证民众的安全,政治学者思考出对君王的权力的制约的方法,从而发展出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对王权进行制约,保证王权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发展出议会制度,以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制约王权;发展出选举制度,以定期选举取代世袭制,使得权力的专断可能被减到最小;形成理性的官僚体制,从而保证政策的稳定和理性;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强大公民自治组织的进行自我管理,以此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从而也达到了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的目的。在民主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之后,出于对担心民主的过度强大也可能会造成政治的不安全的顾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埃德蒙•伯克,约翰•密尔和托克维尔等政治学家都对“多数人暴政”保持着强烈的警惕,他们害怕当民主制的政体中出现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往往会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而这种压迫甚至比我们之前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处在比其他任何迫害都更为悲惨的境地。而苏格拉底被民主所诛杀,中国的运动式政治民主等事实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来看,完善的民主制度相对地更有利于安全的实现,当然,当然究竟哪一种更为安全的政治模式会出现,我们都在期待。
2、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主要是针对统治政权而言,主要探讨的是政治统治权威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如果大量出现民众对既有政权机构的不认同甚至反抗行为,则意味着政权面临被瓦解和倾覆的风险。对此讨论最早的讨论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统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关系的论证,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合法性的基础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基于系统分析理论,他提出了特定性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的丧失,即意味着政治成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认同的丧失,从而产生政治不稳定。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进而他提出了“合法化危机”是影响政治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的三个著名的公式:社会不满=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度=社会不满/流动机会,政治动乱=政治参与度/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意味着政权统治的不安全。这些为我们探讨政治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理论支持和分析框架。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政治学家有关政治稳定论述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与中国政治实际,发展出了中国政治稳定的相关理论。他们将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和伊斯顿等人关于政权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的讨论应用于中国政治实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红利的共享使得政权获得了长期的合法性认同,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基于亨廷顿观点的基础上对政治稳定的讨论,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在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处理上,首先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没有走上类似苏联解体的道路,从而实现了政权的长期稳定。对“中国模式”与中国政局长期稳定之间关系的讨论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分析认为中国模式的魅力就在其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及对外开放等。正是在这样的“中国经验”支持下,保证了中国的长久稳定,而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当然这一判断是否准确,相关讨论还仍在继续。
3、政治冲突当代政治冲突的研究是从对西方政治学者及其学说的引介开始的,早期主要涉及科塞、达伦道夫、李普塞特等相关学者的论说,近年来的引介主要涉及爱德华•A.杰简哈根的需要层次理论在政治稳定上的应用、柯尼欧曼尼斯•S.考特索基斯的社会融合与政治稳定的研究、特德•罗伯特•盖尔的政治镇压模式视角对政治稳定的研究、歇尔•狄龙的政治受挫模式下对政治稳定的探讨、克雷斯汀•亚历山大•达文波特基于冲突边界控制模式对政治稳定的研究等。这些理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政治现实,认为虽然政治冲突对政治安全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只要冲突是在可控的限度内,就可以将人们积压的不满情绪有序的释放掉,进而会有益于政治安全;有的政治学家甚至认为,适当的政治冲突可以起到对政治系统的新陈代谢作用,从而有效的保证正字系统的良性运转,所以对待这样的政治冲突行为应该少用和慎用政治镇压等极端性惩罚措施。这些理论就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西方各国近些年的政治事实也证实了这些理论的效用,其有效的化解了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如受中东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美国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等示威游行活动,它并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在被迫停止后,美国的政治生活依然正常运转。中国关于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在诸子百家时候就开始了,主要集中在治与乱的讨论上,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自诸侯出”,认为不管是君王、大臣还是民众,只有大家能各安天命,特别是臣子和民众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可以化解政治冲突,保持政治安全;韩非子在《韩非子•扬权》中提出,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持政”,则必然导致政治冲突的产生;老子在《道德经•三十六章》中指出,要做到减少政治冲突就要做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要轻易的使用武力,以无为之法治民,无为方能大为,从而实现政治的长治久安。周代开始的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被认为是化解王权继承中的冲突与斗争的一种优选方式。但是古代的政治冲突的讨论更多的是一些意见,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真正系统化的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见于当代学者王浦劬教授提出的“心理对立说、价值对立说、资源争夺说、环境互动说等理论中。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阶层差距的拉大,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就为政治冲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从这些冲突的事实出发,政治社会学者更多的活跃其中,于建嵘在对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理论、斯科特的“生存伦理”理论、查尔斯•蒂利的竞争性抗议、反应性抗议和主动性抗议理论以及李连江等人的“依法抗争”理论进行批判性吸纳的基础上,提出了“抗争性政治”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政治冲突的类型。他认为上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化解政治冲突风险的有力途径,但由于维稳是国家的“刚性需求”,它不停的挤压着民众的上访空间,从而使得上访的功效在不断递减,由此,他呼吁一种“韧性维稳”机制的建立来化解政治冲突。当然这一类政治冲突正如于建嵘等人所言的那样往往只是涉及个人利益,因而其政治效用是有限的。而最近几年的一些政治冲突如乌坎事件、新疆7•15事件,3•1等冲突事件则已经开始触及到政治选举、民族分裂和宗教斗争等政治命题,所以相应的政治冲突理论研究的需求已经产生。
个人命运主要是对政治生活中个体生存层面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的探讨,这些研究最早主要散见于历史学、野史轶事、文学作品中。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中很早就有“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智慧,认为从政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尤其是开国功臣,往往会因为功高盖主而被杀戮,“功成而身退”才是他们规避风险的良策。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经记载:范蠡离开越国之前,曾给文种写过一封信言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嘴,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即认为文种继续待在越王身边必然面临被杀害的风险,文种没有听从其建议,而范蠡的预言在不久之后就被应验。所以中国古代文人面对政治的诡秘和凶险,总结出了“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逻辑,可谓良苦用心。作为君王或者领导人,他们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仅就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领导人而言,如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枪杀,美国总统林肯和约翰•肯尼迪被谋杀,印度两任总理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和拉吉夫•甘地也都遭到暗杀,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被刺身亡,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执行绞刑死亡,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被乱枪打死,除此之外,其他受到监禁和判刑的领导人还有许多。这些领导人在位时都曾经权力巅峰的弄潮儿,而最终却一个个落得不可善终,足见政治之凶险于政治精英而言可能更甚。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个人命运与政治的关系则表现的更为明显,处于治世,则可以养家糊口,享受天伦之乐,处于乱世,则命如草芥,而这种可能只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真正的政治事实却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了近现代社会,因为民族国家对整个社会规划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增强,如果国家政策失当,民众面临的政策性风险境则更为明显。正是基于此,徐友渔在谈到精英外流时认为“精英们移民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他们凭经验和遭遇认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太多,未来是不确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动和决断做出合理预期的”,与其说精英们不爱国了,不如说精英们非常务实,只要他们在国内能感觉到安全,他们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去国外发展,他们之所以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过上“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担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权力机关剥夺;在从事经营活动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动时,不必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就可以顺利进行;在遇到麻烦时,可以指望廉洁奉公的警察或是独立审判的法院”的生活而已。基于以上判断,学者们得出了个人政治安全感的获得必须依靠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化进程需要再进一步积极推进论断。
二、风险的政治学化研究
与上文提到的对政治生活中风险的研究不同的是,也存在一种以政治学化视角切入而对风险展开的研究,笔者之所以认定其为政治学化的研究,是因为其只是把风险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对某种类型风险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做了些相关性的探究而已,并没有真正形成对风险的政治学讨论,但是其毕竟使用了一定的政治学分析工具对风险进行过研究,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风险的政治学化研究,以区别于本文所要主张的风险政治学的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环境或者生态风险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的探讨,形成了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另一种是探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风险社会阶段,各种频发的风险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结构的影响与挑战,形成了风险社会理论中有关研究的部分。
(一)绿色政治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对自然造成了大量的破坏,空气污染、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锐减和气候变暖等环境灾难日益严重。基于此,有别于环境工程、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从政治学视角切入,对环境和生态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环境恶化对政治系统造成的挑战以及政治系统所应该做出的反应和调整。与生态学和环境工程等学科注重对自然生态的研究不同的是,绿色政治着重考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探讨了人口与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政策的调整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罗马俱乐部给出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倡一种零增长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科尔曼的《生态政治》一书中则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指出在集权主义的权力集中模式下,参与型民主方式对生态的改善必然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他提倡以社区治理的社群主义模式来对抗集权主义,从而实现生态政治的目标;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提出了有关气候政治的四点建议:第一,把气候变化与日常生活勾连起来;第二,坚持气候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第三,实现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合,集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第四,把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结合起来。之后很多学者都进入了这一领域,形成了大量的著作和成果,其中比较优秀的有安德森的《政治与环境:关于生态危机的读本》、卡普拉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托卡尔的《绿色的选择》等等。这些学术成果的研究与绿色政治运动是同步的,随着这些理论研究的进展,绿色政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纷纷崭露头角,有的进入议会,有的甚至成为政治官员。绿色政治的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郇庆治主持翻译了丛克里斯托弗•卢茨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穆勒—罗密尔《欧洲执政绿党》、默里•布克金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的《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约翰•德赖泽克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等,从而引导了中国大陆绿色政治研究的风潮。而国内其他有关绿色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生态智慧的挖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态理念的阐释等方面。而在政治生活层面,面对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政府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政府执政的基本理念之一。
(二)风险社会视角的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主要由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是以反思性现代化作为其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的,……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即他们认为风险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其“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所以现代风险,即人造风险,往往是因现代化而发,官僚制、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民主政治、现代科技等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风险产生的根源。这些理论中从政治学角度对风险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贝克对现代风险分配的阐释上,他认为风险“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事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他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在这个风险定义的基础上,他认为风险社会一个是以风险的暴增和累加为特征的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对政治系统提出了挑战和要求,而风险对政治系统的影响要体现在风险的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后果上,“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向重叠”,从而提出了有关风险分配的命题。如果说政治就是有关分配的问题,那么贝克认为财富分配的利益政治和坏处分配的风险政治在分配逻辑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风险也依照阶级模式进行分配,但是其分配逻辑是刚好倒过来的,财富在上层集聚,风险在下层集聚,财富的贫困与风险的累积实现了重叠,从而加剧了阶级的分化结构。进而他认为,这种风险分配的不平等结构是以风险感知、处理和转嫁能力的不平等为根源的,所以“那些发现自己作为风险制造者而处于公众声讨中心的人,竭尽全力通过在工业中逐渐制度化的“反科学”的帮助来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并试图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祸根。”从而可以逃避对风险的责任承担,就产生了风险责任规避逻辑。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风险分配逻辑:风险分配也遵守一种“飞去来器效应”,即因为风险作用方式的无序性和超时空性,那些早先在风险中获利者,最终可能也必须承担风险的后果。从而形成了风险分配的两种逻辑,而正是这两种逻辑的作用,使得在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机制,当民众在政治议题中要对风险责任进行明确化时,却遭到现有政治系统的歪曲与打压,于是,在民意无法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民众就在在现有的正式结构之外发展起来一些专门针对风险议题的社会运动,人们通过示威、游行、静坐和拒购等政治活动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政治议程或因此而改变。吉登斯从社会构成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知识三者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从传统过度到现代。社会在去传统化的之后,社会结构出现了变迁,从而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敏对这个失控的世界,可以采取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方式走一条风险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来控制和化解风险,其思路和贝克的观点大同小异。贝克和吉登斯被认为是风险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制度安排需要调整,这种调整过程更多的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下的职能转变。至于新的制度安排,则往往是在现有制度无法承担的新的职能的地方出现,未来时代原有的性质的机构可能会被更多的被直接参与决策的自主性制度安排所替代。很多的溢出现有制度框架的社会运动、游行示威,新的政治团体,论坛,甚至暴力行动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三、批判与讨论
上文笔者分析了与风险相关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此处笔者将对这些成果进行必要的讨批判性讨论:
(一)政治风险理论批判
政治安全理论探讨的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做可能遭受的政治风险,政治稳定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探讨国家政治权力可能遭受到的不安全影响,政治冲突理论则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一定的政治框架内各种政治团体之间的斗争与妥协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风险理论的研究,对于人们在面对捉摸不定的政治权力格局调整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人们规避政治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从上面的理论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政治风险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目前研究仍然不是很深入,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政治安全的现实需要,所以进一步的研究正在被期待。虽然政治风险学重要,但是其自身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一,研究对象局限于机构或者个体在政治生活中面临到的风险,没有讨论人们面临的其他风险;其二,在研究视角上,把政治生活中的风险看作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缺乏对风险作为内生变量视角的考察。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风险不仅仅限于政治风险,除去此之外,还有自然风险、科学技术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等等,而面对如此多的风险,如何保证人类生存的安全。故探讨一种更为宏观的能统一各种风险理论的理论研究势在必行。
(二)对风险政治学化理论的批判
1、绿色政治理论批判绿色政治学坚持的是以环境为中心,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它有利于人们在政治活动中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安全的目标,这对于解决因为现代化的高度发展而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而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管是深绿政治还是浅绿政治的提出都主要是针对人类行为的任意性和盲目性而提出的,其只是把目光放在环境问题上来进行思考问题,所以难免具有一下缺陷:其一,其具有明显的道德呼吁和宗教“启示录”色彩,在面对受强大利益驱动的环境破坏行为时,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往往难以实现,在而今道德和宗教衰微的情势下,更是如此;其二,自然中心主义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与人们的基本理性常识相背离,从而在根本上很难被人们接受,从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得势来看,就可见一斑;其三,过于注重环境要素的考量,较少考虑到影响人类安全的其他要素,因而总是被批判为“片面的真理”。
2、风险社会理论批判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当代社会研究风险的重要理论之一,表现了比较强大的生命力,自其产生开始,就广受关注。有甚者因为其中涉及到了风险的分配问题、风险社会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变革等政治命题,就按照政治是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概念来比对,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开辟了风险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其研究的明显不足体现在:其一,在横向层面上,只是将风险看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他们将社会风险与工程风险、自然风险割裂开来,只进行社会风险的研究,而忽视自然风险和工程风险的研究;其二,在纵向历时性层面,把目光放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研究上,即认为在后工业化时代有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从而忽视了对以往社会形态中风险现象的研究;其三,风险社会理论中涉及到的政治学的部分内容,只是论及到了风险社会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类型的风险所引起的相应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并没有对其它社会形态下的风险和对其它类型的风险进行过相应的分析。可见,其研究更多的是一种风险的社会学研究。
3、风险政治学化研究的分析绿色政治注重探讨人类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风险的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则从不仅探讨人类行为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风险、也探讨了人类对自身造成的风险,从而使得人类对风险的研究更为全面,尽管如此,两种理论的缺陷依然明显:第一,两者都预设了自然环境风险的终结,认为人类已经战胜了自然,并且人类已经反客为主,具备了危害自然的能力,而这一点显然是欠妥当的。即使是在这些理论的发源地的达到国家,地震、飓风以及其它自然灾害的发生依然是不可测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地认为我们已经战胜了自然风险。退一步再说,就算是我们认为人类现在已经具备了足以和自然抗衡的能力,甚至有了破坏自然的能力,但是这仅仅是在地球范围,如果将跳出地球范围,将视野延伸至整个宇宙范围,那么一个我们无法预料的陨石随时都可能让整个地球毁于一旦,我们又何所谓战胜了自然呢?所以这一假定最多只在地球上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少数领域中存在,超出这个范围,就面临着错误的同化。第二,绿色政治和风险社会理论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都具有局限性,只把某一种类型的风险或者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风险作为研究对象,使得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受限而效用大打折扣。绿色政治只研究环境领域,风险社会制把后工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而整个人类所经受的风险又岂止如此呢?所以,一种对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风险的统一理论的研究变得非常必要。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初步探讨,我们发现了两种与政治学相关的风险研究成果,它们在风险治理的实践中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体现了一定的解释力和优越性,但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些理论的不足与缺陷,以便为新的理论的产生提供基础。政治风险理论探讨的是政治权力或者政治体系所造成的风险,是把政治看作风险产生的外生性变量来看待;风险政治学化理论考察的是由一些类型的风险所引发的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系统的回应,把风险看作是政治结构变革的外生性变量。所以两者都具有共同的欠缺:对风险与政治的研究都互把对方看作外生变量来展开研究,而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即对风险的内部政治结构的讨论。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逻辑起点。
四、风险政治学的建构
在对现有的政治学视野中的风险研究成果进行探讨和批判之后,笔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尝试———风险政治学研究。下面主要对这一范式的问题意识、研究逻辑,和分析框架做概括性的论述。
(一)问题意识
理论建构之所以必要往往体现为现实的焦虑与不满,否则再完美的理论也可能会沦为无病,所以好的理论的产生必然基于明确的现实问题。风险与人类相生相伴。在古代社会中,自然中的毒蛇猛兽、地震火山、疾病瘴气随时可能取人性命,部落与国家间的战争与仇杀让导致生灵涂炭,君王与当权者的暴政会民不聊生。这些风险不仅在现代社会依旧存在,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又带来了新型的风险,诸如染色馒头、地沟油油条、瘦肉精猪肉,避孕药的黄瓜、硫磺熏姜、塑料奶茶等等;人在旅途,可能面临车祸、动车事故、桥梁垮塌、船舶沉撞等威胁;住在家中,所住的房子可能是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工程,也可能在睡觉时房子被强拆;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呼吸到有毒气体;更有甚至,一次核泄漏事件则会让我们的家园寸草不生。总之,风险与人类如影相随。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这样认为:既然风险对人类而言的是“坏”东西,只要是思维正常的理性个体,必然以趋利避害为取向,当他们面对上述风险时,正常反应是避之惟恐不及,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另外一番场景: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人们并不会因为车祸的可能而不出门,不会因为存在有毒食物就不吃饭,因为空气污浊而停止呼吸,因为手机、电脑的辐射而停止使用它们。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人们却会因为饥饿而去抢劫和犯罪,他们似乎并不害怕被逮捕和判刑;没有学历和权势的妇女为了养家糊口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好像她们并不在意性病和艾滋病的感染;士兵们清楚地知道战场上的冲锋可能会中弹而亡,但是他们仍然选择战斗,似乎并不害怕死亡。于是,种种违背常识的现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是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和不在乎,而不是极力的规避和逃离。当然,对此每一个学科都会形成自己的解释和判断,而政治学对此当作如何解释呢?如果说政治学就是对分配问题进行研究,而风险政治学就是对风险的分配问题进行探究的话,那么从政治学角度出发,对人们面对风险之时的所作所为进行阐释的话,这就涉及到风险分配的问题,由此,可以提出一个理论预设:一定存在某种原因使得一些人群承受和容忍了那些本该无需容忍的风险。就将一个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难题转化为一个政治学的理论命题:风险的不公平分配格局为什么会被人们容忍和接受的?换句话说,就是风险的不公平分配格局是如何被合理化的?当然,由上面提到的悖论现象可以引发出的问题会有很多,但是为了保证本项研究主题的单一性和明确性,本文只选择这一命题展开讨论。
(二)回应与展开
在对上文提及的问题进行尝试性回答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风险本身的特性进行认识,继而尝试性的提出一个势科学视角的分析框架:
1、风险界定对上面提到的问题要尝试进行回答,首先有必要对风险本身的特性进行认知:(1)就风险是的时空关系而言,它不但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就时间范畴而言,它不仅仅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在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也并没有消失,反而似乎越来越多。(2)就风险的存在形式而言,风险不仅仅是一种是实体性存在,也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所谓实体性,即其作为一种危害的趋势的实在性,所谓关系性存在主要体现为与人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人来孤立的探讨风险,是无法给其定性的。(3)就风险的行为逻辑而言,风险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趋势,。说其是一种趋势,是因为危害并没有发生,即它只是一种危害的可能性状态,而不是一种危害的事实和结果,如果把风险看作是一种危害的事实的话,那么风险也就不能称之为风险,而是灾难或灾害了;他也是一种事实,即一种趋势的事实,这种事实是确实存在着的。(4)就风险的存在状态而言,风险是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是对风险施加者和风险承受者之间的一种方向性关系状态的概括,风险的这种特性是风险区别于其他现象的重要特征。风险是复杂的,它不仅是长时段、跨空间、方向性存在,而且能将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我们该如何对其展开研究和分析呢?理论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就事论事的经验对比和街头巷议的泛泛而谈,就在于其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系统性。人类社会至今所进行的理论抽象无非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哲学抽象,一种是数学抽象。对于人文社会学科而言,面对人类社会的各种研究对象,我们的“每一次概念化都要以某些哲学承诺为基础。[23]”所以,往往更多采用的是哲学抽象的方式展开研究。但是哲学抽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理论建构和逻辑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最小分析单位———概念,往往是一个在操作层面无法再继续细分而展开讨论的“空壳”,从而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往往沦为“概念的旅行”,作家创作成了作家自己在不断编造新概念和去解释和代替旧概念的过程,而学术对话则成为作家之间互说黑话的“概念战争”或是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争夺活动。到了近代,出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学术研究变为纯粹的“语言的游戏”,这种现象就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缺乏切实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很难搭建起共同探讨的对话平台和行业评价机制,因而很难实现学科的自主和自强。而自然科学在面对各种自然现象时,则采取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抽象,数学工具的引入和使用,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了极强的可操作性,得以搭建起良好的分析平台,从而实现了自身学科的繁荣和对话的可能。可见,面对不同的分析对象,人们所所采取的分析手段也有所不同。而就风险研究而言,风险既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物”的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事”的存在,针对风险的这一特性,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综合采用哲学抽象和数学抽象两种方式来对其展开研究,一方面满足这一分析对象的特性,另一方面取两种学科之所长。
第3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私人风险;公共风险;政府职能;市场经济;风险机制
中图分类号:F045.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07-04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问题,涉及到一系列具体问题,包括政府与市场如何分界、政府与市场各有什么职能或功能、政府职能如何转型等等。
我国经济学引入了西方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归政府治理,如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效应、垄断、收入分配不公、信息不充分、经济波动,等等;政府的职能在于向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如法律制度、国防,等等。市场失灵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对我们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相当启发,但是,这种启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不少局限性。
十多年来,刘尚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风险理性、公共风险、私人风险的角度,阐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他认为,政府职能取决于公共风险,而不取决于市场失灵;“在市场经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实质上是不同性质风险的归宿划分。私人风险与市场相匹配,公共风险与政府相匹配。这种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应当说是一种有效的选择。这已为中外社会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明。”[1]
笔者认为,刘尚希同时厘清了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范围和功能,是一种理论上的突破,非常值得关注。但也留下不少重要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比如,如何从一般风险理论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有什么样的具体特征、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有哪些具体内容等等。
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也是社会建构的主观现象。风险是日常生活的概念,也是科学的概念。一般风险理论起源于保险学,在一般风险理论中,风险可以分为机会风险和损失风险,机会风险指可能获利也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形,如、投资等;损失风险指不可能获利只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形,如地震、传染病、环境污染、社会骚乱等。不同语境下,人们总是灵活地使用风险概念,有时指机会风险,有时指损失风险;有时指损失的不确定性,有时指损失本身。笔者从事过保险行业,对一般风险理论有一定了解。在学术研究中发现,如果我们从一般风险理论考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有很多新的认识。
二、政府与市场的分界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动,比如衣食住行、就业、投资、创业、消费、休闲、选择生活伴侣等等,在一定准则内,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那样做,不管怎样,都会有不确定性的后果,可能对自己有利,也可能不利。这些有着不确定性后果的活动,都属于私人风险。概而言之,私人风险包括身、心、名、利四个方面。身指身体健康、人身自由、人身关系、感官享乐等,心指个人的心境、信仰和精神世界,名指人们通过交际、言论、结社、竞选等活动所追求的社会名誉和地位,利指人们所追求和享有的财产。
私人风险基本上是机会风险,其主要特征是:风险因自愿行为和选择而发生;风险的有利以及不利后果由私人承担;私人有能力判断风险的概率以及损失、收益的大小;私人有能力管理和控制风险;可以通过契约方式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某些风险;常常可以获得与风险有关的信息;风险一般是可接受风险。这里所说的私人,包括自然人,也包括非属于政府的各种社会组织,例如家庭、企业、社会团体等。
无数的无限多样化的私人风险治理活动就构成了市场。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互为风险,互为机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都是以风险为核心的。在市场中,每个人都是风险人、经济人、理性人。市场的范围,就是私人风险治理,就是人们的自主选择行为。市场的功能和意义,就是使人们能够通过平等的自由的交易活动,去实现私人的生活计划和目的,获得身心名利的综合发展,获得幸福。当然,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当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市场和私人风险治理天然地与公民自由权有关。公民没有自由权,也就根本谈不上私人风险治理,个体生存就缺乏意义,社会发展也必然失去动力和活力。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了市场机制,公民有了私有财产权、自由就业权、生产经营自等等。应当看到,很多改革措施是一种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进步。
人们的生活中必然面临着战争、地震、传染病等风险,这类风险是损失风险,是公共风险。其主要特征有: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都可能受到风险的侵害;每个人都需要风险治理的保护,都有受益权,在受益权方面没有排他性;个人在享有风险治理利益方面没有竞争性,某个人的受益并不减少他人的受益;风险不是个人冒险行为的结果;个人无法预料、抵御和逃避风险;个人难以获得与风险有关的信息;风险是个人难以承受的。
市场和社会个体是无法有效地应对和治理公共风险的,公共风险只能由政府进行治理。政府就是一个社会的保险公司,“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各种‘保险’,社会成员所缴纳的税收本质上就是一种‘保险费’。”[2] 这也意味着,如果政府治理公共风险的效果不好,或者收取“保险费”过高,社会成员将会以一定方式重新选择政府。
划分公共风险就是划分政府职能。考虑逻辑合理性和政府运行实践相关性等因素,公共风险可以分为以下互相关联的六大类型:
第一,政治风险。指政治性的社会对抗的风险,包括普通社会成员破坏法治、反对国家权威的风险,也包括行政、司法、立法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破坏法治的风险。
第二,经济风险。指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系统性的风险。市场要素配置失衡、信用恶化等多种因素都可以形成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会带来生产及交易活动停滞、通货膨胀、失业、财产贬值、资源浪费等恶果,并引发其他公共风险。
第三,公众风险。指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风险,主要包括生活及生产经营活动、犯罪、危险物品、科技成果使用、产品消费、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传染病等等。
第四,个人风险。指与社会成员基本的教育、养老、救助、医疗等保障有关的风险。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并非由于个人的主观原因才陷入需要政府帮助的困境。如果政府对一些社会成员不提供基本的保障,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会成为整个社会的风险源。政府提供有关保障,主要是出于现实主义的保护社会的需要,而不是福利、伦理、人道主义。
第五,涉外风险。指与国际关系有关的风险。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更加安全,都可能对内对外隐瞒自己的风险,向他国输出风险,防范他国风险的输入,限制他国风险治理的能力和效果,当然,也都希望进行风险治理合作。
第六,国防风险。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就是治理公共风险,人们所说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在主要方面也就是治理公共风险、提供公共安全的职能。
上述六类公共风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所规定,政府治理这些公共风险,也就是在履行宪法。
有观点认为,政府具有为公民增加福利的职能,这是一种模糊的观点。政府的职能是将公民通过纳税而转移的风险集中起来进行治理,为公民自己增加自己的福利提供环境支持。西方理论认为,“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3]这实际是在强调公民福利的增加,主要应通过私人风险治理来实现。
以公共风险治理为标准,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履行职能方面还存在以下两大问题,需要切实加以解决。
第一,越位问题。越位是指政府职能、政府行为超越了公共风险治理的界限,政府之手伸的太长、太多。国有企业是政府在市场中的越位和延伸,但是多数国有企业不具有治理公共风险的属性,应当退出市场。文化、体育、高等教育等事业没有公共风险属性,原则上不应当属于政府职能的范围。公共风险治理如果具有全民、全国地域的属性,则应成为中央政府的职能,否则,则应成为地方政府的职能,中央政府不能越位。“三公”费用等公共财政开支很少涉及公共风险治理问题,原则上应当取消,至少应当大幅度削减。对不涉及公共风险的事项,政府不应当设置行政审批及许可,已经设置的应当尽快取消。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备案制、行政检查等方式,对有关事项进行监督、管理和规范。
第二,失位问题。失位是指政府治理公共风险有不足,有缺失,政府之手还没有伸到位。在个人风险治理上,政府的很多工作还没有到位,还没有建立全面的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如何治理各类公共风险,特别是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经济风险,政府还缺乏经验,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在治理政治风险、公众风险方面,很多时候还不能严格依法办事。各类公共风险治理都与政治体制及政治理念高度相关,我们的政治体制及政治理念还有不少与公共风险治理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能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调整。
三、风险理念的实证研究
上述分析是逻辑上的演绎与归纳分析,也是符合生活常识与历史事实的,能够初步说明机会风险-私人风险-市场的对应关系,以及损失风险-公共风险-政府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预设前提是人类具有将机会风险及损失风险“分而治之”的风险理念与本能。要从根本上说明有关问题,无疑需要对这种风险理念和本能进行科学实证分析。
幸运的是,有不少科学研究能够支持我们所需要的实证分析。风险认知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大众完全懂得对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进行归纳和区别。在一项对694名北京市居民的调查中[4],居民所认为的“高风险因素群”是国内动乱、经济风险、食品安全、能源风险等,这些风险都是公共风险,而不是私人风险。在一项229人参与的研究中[5],所列出的46种风险有公共风险,也有私人风险。参与者所认为的对社会而言的高风险因素,大多为公共风险,国内动乱和核战争被认为是最高风险;所认为的对社会而言的低风险因素,都属于私人风险,如登山、滑雪、辞职等。在一项2 133个有效样本的研究中[6],北京等三地公众对15种风险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了排序,排序有着明显的公共风险与私人风险之别,而且公共风险的社会危害性普遍高于私人风险。其中,三地公众一致将核泄漏、传染病、地震这三种公共风险视为社会危害性最大的前三种风险,而普遍将房价上涨、看病难、贫富加大这三种私人风险视为社会危害性最小的三种风险。
风险认知研究涉及到个体对风险的分类、趋避倾向等问题。美国学者斯塔尔在1969年就指出,公众对自愿活动风险(如滑雪)的可接受程度,大约是非自愿活动风险(如食品添加剂)的1 000倍[7]。很显然,私人风险都是自愿活动风险,公共风险都是非自愿活动风险。中外学者进行的风险认知研究,对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特殊的意义,说明人类追求私人风险自治的自由,并且组成政府治理公共风险,是一种风险理性,是一种本能。
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人类为什么懂得区别对待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呢?人类的风险理性是怎样形成的呢?有什么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呢?
刘尚希非常重视将其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上,他在2010年指出,“风险理性是基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经验积累而形成”,包括个体风险理性和公共风险理性,前者使个体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后者“为集体成员提供一种社会化的预警机制,通过集体行动,最终‘沉淀’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制度,以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8]
笔者认为,刘尚希所言的“风险理性”也可以称为“风险应对机制”。人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为了应对各种生存压力,适应严酷的风险环境,进化形成了复杂的风险应对机制。现代人都有一个“石器时代的脑”[9],这个脑实际上就是形成于上百万年的石器时代的风险应对机制。在文明进化过程中,新的刺激因素使得风险应对机制不断丰富、完善,这些因素包括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群体规模扩大、生存风险环境变化、科技发展、个人与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多样化,等等。
风险应对机制体现在基因和文化中,包括神经生理机制、心理机制、行为模式、社会制度等内涵,具有风险感知、风险识别、风险转移、风险选择、风险沟通、风险处置等功能,涉及个体行为以及社会机制的复杂多样的趋向和选择,如个体与群体、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约、奖励与惩罚、利己与利他、理性与冲动,等等。例如,人们总是本能地计算风险和收益,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总是选择以较小的风险避免较大的风险;为了应对某些重大的个人无法应对的风险,人们愿意与他人进行合作;为了个人或群体的安全,人们可能主动增加其他个体或群体的风险,会对违反合作规则以及制造风险的人进行告诫、惩罚和报复;对某些可以控制和预料的风险,人们愿意自行冒险,并独自享有冒险所得利益;在防范风险、获得安全方面,人们有“搭便车”的心理,也有反对“搭便车”的心理;如果人们的行为客观上会使他人减免风险或责任,人们可能放弃该行动,或者要求他人做出补偿;能够给他人和群体带来安全、减免风险的人受到群体的尊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不增加个人风险的情况下,人们愿意告知他人有关险情,或者救助他人脱离风险。我们所探讨的很多经济学问题,都与这些风险应对机制有关。
人类的风险应对机制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和统一解释,对经济、宗教、政治、伦理、法律等现象有着根本性的支配作用。只有从人类的风险应对机制出发,也就是说从人类行为科学出发,从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和语境出发,我们才能透彻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经济学问题。
四、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市场经济
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规律或市场机制。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机制主要有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由于这几个机制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从风险机制出发定义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每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一样,都遵循着一定的风险应对机制。市场如同生态系统一样,具有自稳定、自平衡、自发展、自淘汰的机制及功能。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被否定和打击,政府完全取代了市场。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时间并不长,市场机制只是初步建立,还很不健全,很多制度性历史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总的来说,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就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问题。从市场机制的基本定义出发,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制度环境。制度环境问题主要是法治问题,市场经济天然地是法治经济,法治为市场运行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制度支持和环境,使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利害得失风险能够进行某些分析判断。
法治对市场经济的支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立法。法律为市场主体从事市场行为提供工具、手段和界限,这些法律主要是有关的民事商事法律。二是执法。政府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平等地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提供支持和服务,严格监督市场行为,惩治违法行为,不能通过市场寻租谋利,不能违法获取税费等利益。三是司法。对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以及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判。缺乏立法,市场经济就不会发达;执法不严,市场经济就变成违法经济、权贵经济、诈骗经济;司法不公,市场经济就会变成暴力经济。我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曾经十分发达,但是一直无法发展成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其原因就是缺乏法治,这个历史教训不能不吸取。
第二,市场主体。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要对自己行为的利害得失、风险后果承担经济责任,正因为如此,市场主体才可能审慎地进行风险选择。
政府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如政府采购,政府才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运动员”,成为市场主体。然而,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对自己行为利害得失的风险后果常常可以不承担经济责任,也没有政府破产制度,政绩考核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各种因素使得政府实际上成为十分活跃的重要的市场主体,出现了大量的“县长经理”、“市长经理”现象。很多地方政府不当地运用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积极地卖地、发债、招商引资、投资兴建公共工程、扶持企业和产业发展等等,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宏观上也带来了一些全国性的经济风险。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政府退出市场主体的位置。
第三,产权制度。市场行为的前提之一是,市场主体必须明确可以支配哪些资源和利益,可能的风险损失范围有多大。这个前提实质上就是产权制度问题,就是所有制问题。没有产权,就不存在风险选择问题,也就没有市场。产权不明确,交易风险就会加大,交易也难以操作,交易成本也会增加;产权就难以流转,市场也难以活跃。科斯的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着深刻的风险理念,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广义地说,资源、劳动力、货币、技术、管理等市场要素,都属于产权的范围。中外经济发展史证明,市场配置产权的效率和效果要好于政府,产权私有化的效率和效果要好于产权国有化。我国的国有企业占据着大量的资源,而且每年都不断消耗着大量的资源,但是其效率和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需要进行改造。我国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也不是一种很有效率的土地产权制度,也应当进行改造。
第四,风险机制。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行为及其后果,供求关系、交易价格、交易方式等等,都存在着多样性、选择性、不确定性,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和博弈,这些都是风险机制的具体表现。风险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权配置才能最优化。
我国的市场经济具有强烈的行政垄断成分。行政垄断排斥了市场行为所应有的多样性、选择性、不确定性,排斥了风险机制和竞争,也就破坏了市场机制和市场功能。行政垄断企业以固定价格提品,使得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垄断企业在经营方面很少存在风险,即使亏损了,也会获得大量的政府补贴。私营资本不允许进入垄断行业,也就排斥了竞争。由于缺乏竞争,行政垄断企业也就缺乏创新与降低成本的动力。行政垄断企业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了一般市场主体,造成社会不公平,也造成企业产品价格虚高,给一般市场主体的经营带来了困难。因此,我们应当打破行政垄断,允许私营资本进入某些行业,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以促进产权配置最优化。
参考文献:
[1] 刘尚希.公共支出范围:分析与界定[J].经济研究,2002,(6):77-85.
[2] 刘尚希.税收“用之于民”,故“取之于民”[J].中国税务,2006,(8):1.
[3] 埃尔金.新论[M].周叶谦,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9.
[4] 钱洁凡,孟耀斌,史培军.北京城市居民风险认知状况调查[J].中国减灾,2009,(12):26-27.
[5] 谢晓非,徐联仓.一般社会情境中风险认知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学,1998,(4):315-318.
[6] 刘岩,赵延东.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J].社会,2011,(4):181-183.
[7] 伍麟,张璇.风险感知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式[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5-102.
第4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从中央和地方两个不同的政治关联层次出发,利用2010―2014年中小板民营企业的相关数据,对政治关联与财务风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分析了地区发展程度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地方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更高的财务风险,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这一相关关系被加强。本文结论为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政治关联 财务风险 民营企业
一、引言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截止到2013年末,我国私营企业占所有企业法人单位的68.3%,小微企业法人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95.6%。中小私营企业生命周期短,财务风险问题一直是很多学者的关注点。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被选为中央或当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形成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现象。作为中小企业的重要竞争力,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方方面面,包括财务风险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政治关联的研究起源于1974年Krueger的开创性研究。Faccio(2006)认为,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减免;王珍义等(2011)认为,政治关联可以使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促进了企业的创新。Fan等(2007)发现当CEO有政治关联时,会成为政治家达成自己目标的工具,被政府“掠夺”;陈和平等(2015)认为政治关联公司更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盲目投资。
因此,政治关联在企业中既可能扮演“援助之手”的角色,也可能是造成负面影响的“掠夺之手”。为了更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对中小民营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我们需要展开讨论:第一,现有的文献没有区分政治关联的层级。中央与地方政治关联提供给企业的资源是不同的,对企业的要求也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会给企业的财务风险带来不同的影响;第二,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中的政府官员对企业的要求也有所差异,会影响到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能力。
本文从不同的地区发展程度和不同层级政治关联的角度出发,考察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能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具体深入的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不同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中,地方政府会在税收、审批、资金支助等方面向企业提供制度性资源(赵峰等,2011),使其在当地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企业也需要帮助政府官员实现政治业绩,推动其在官场上的晋升(李建等,2012)。由于GDP增长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官员为了晋升纷纷在GDP上大做文章,促使政治关联企业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投资等方式提高当地GDP。李传宪等(2013)指出,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有更多的过度投资行为,损害企业的价值。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拥有地方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更高的财务风险。
企业家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有利于帮助企业获得产业内信息、产业外信息,获得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机会(李建等,2012)。但是不同于地方政府官员对GDP的追求,在我国处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央官员更提倡企业健康发展,树立民族品牌,对于企业的干预程度相对较小,企业能够健康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企业中央政治关联与财务风险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地区发展程度对竞争战略选择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土地财政来获得收入,对于地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高;而发达地区地方官员会更重视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获得政绩,以谋求晋升,因此也会对当地的经济进行更多干预(田伟等,2009)。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会对政治关联与财务风险的关系进行强化。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政治关联”的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数据库。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选取2010―2014年间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有缺失或异常的样本,得到截面企业数量为593,观测值为2 965的面板数据集。
(二)研究方法
1.模型设定。本文研究民营企业家不同层次政治关联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影响的调节作用,因此分别设定回归方程:
Riskit=α0+β1Politicalit+γControlit+εit (1)
Riskit=α0+β1Politicalit×Developmentit+β2Developmentit+γControlit+εit(2)
模型(1)用来验证不同层次政治关联与财务风险的关系,模型(2)研究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2.变量选择和说明(见表2)。
(1)被解释变量――财务风险(Risk)。现有研究中对财务风险的衡量方法有很多,本文所采用的是目前财务预警中运用最广的,由美国学者Altman提出的多元Z值判定模型,判别函数为:
Z=1.2×X1+1.4×X2+3.3×X3+0.6×X4+0.99×X5
其中:X1=营运资金/资产总额;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X4=权益市值/负债账面价值;X5=销售额/资产总额。Z值越低,表明企业的财务风险越高,越有可能发生破产。
(2)解释变量――企业家政治关联(Political)。本文主要借鉴巫景飞等(2008)对企业家政治联系的分类和测量方法,采用对Wind数据库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信息进行赋值,对企业家政治关联的编码所参考的指标如表1所示。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简历中,如果认为符合该条目则编码确认为1,否则编码为0,然后逐项相加,编码分值越高越说明该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程度越高。
(3)调节变量――所在地市场化(Devindex)。按照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选择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北京、天津、山东八个省市为市场化进程发达地区,并编码为1;而其他地区则为不发达地区,编码为0。
(4)控制变量(Control)。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对企业财务风险有较大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控制了其他一些可能影响政治关系发挥作用的因素。
四、实证结果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3提供了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和中央政治关联最小为0,最大均为4,均值分别为0.7319和0.2310,说明不同企业间企业家政治关联差异较大,并且拥有地方政治关联的企业数量更多。表3也给出了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二)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上页表4中汇总了样本相关性分析结果。除了政治关联之间,其余各变量间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下,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解决指标之间的共线性,本文将指标逐步纳入回归方程。
(三)实证结果分析
1.企业家政治关联。表5汇总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中小板上市民营企业中,企业的地方政治关联与财务风险之间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也就是说,地方政治关联越强的企业,财务风险越高,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就越大,这与假设1吻合。而具有中央政治关联的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风险却没有显著的特征,这与假设2吻合。
2.地区发达程度的加强作用。单独带入地区市场化指标进行回归时,地区市场化程度与财务风险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负相关关系。从表6可以看出,地方政治关联与地区市场化变量的乘积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企业的财务风险负相关,同时,变量的系数相较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有所提高。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说明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与财务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起到了加强的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地方政治关联越密切,企业的财务风险越高。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定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选用了企业的财务杠杆率作为财务风险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再次对H1、H2和H3进行验证。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说明本文模型设定及实证结论较为稳健。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六、结论
实证结果发现,地方关联的企业普遍会在政治关联的影响下有更高的财务风险。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政治关联对财务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强烈,为企业经营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治理具有一定政策意义:单一的GDP增长指标考核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使得其引导政治关联企业进行更多非经济的增大企业风险的投资发展决策,这虽然在短期上能够对GDP做出贡献,但是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损害了企业的价值。X
参考文献:
[1]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
[2]Goldman E.,J.Rocholl and Jongil So.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Allocation of Procurement Contracts[J].Review of Finance,2013,13(5):1617-1648.
[3]王珍义,苏丽,陈璐.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以外部融资为中介效应[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5):48-54.
[4]Fan J.,T. J. Wong,and T. Zhang.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Corporate Governance,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2):330-357.
[5]张雯,张胜,李百兴.政治关联企业并购特征与并购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13,2(16):64-74.
[6]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7]李传宪,干胜道,何益闯.政治关联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3,(5):63-86.
[8]李健,陈传明,孙俊华.企业家政治关联、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价值――基于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2,15(6):147-157.
第5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双边关系;OFDI;一带一路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84-08;中图分类号:F732;文献标识码:A
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称“一带一路”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时,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创新合作模式。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经济发展潜力巨大。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1%。
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更多的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包括了少数发达国家及众多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遭受着政治局势不稳定、法律制度不健全、恐怖主x盛行的困扰,一些国家与中国还存在地缘冲突。中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是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亚洲、欧洲、非洲等65个国家,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也考察与东道国文化差异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是否有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母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对投资安全提供保障,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存在政治风险高、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特点,本文试图探讨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否推进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分析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如何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
一、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国内外学者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多,但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抑制母国对其投资(韦军亮、陈漓高,2009[1];王海军,2012[2]);另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政治风险高的国家(Ramasamy et al.2012[3])。Buckley et al.(2007)根据我国1984―2001年的OFDI数据进行回归,指出我国的OFDI除了更倾向于流向与本国距离相近、文化相似、市场大、资源丰富的国家之外,还更加偏好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我国OFDI政治风险偏好可能在于寻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韦军亮、陈漓高,2009[1];杨娇辉等,2015[4])。Kolstad 和Wiig(2012)通过引入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与制度质量的交叉项,发现我国的OFDI更加偏好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制度质量差的国家。[5]
在研究OFDI影响因素中,文化差异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随着Kought & Singh(1988)在Hofstede(1980)提出的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基础上构建了文化距离指标[6],Ronald Inglehart 基于世界文化价值观调查(WVS)结果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研究文化距离对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受到关注。许和连和李丽华(2011)[7]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6个国家样本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表明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文献发现,文化距离既会给OFDI带来外来者劣势,也会带来外来者优势。Kang & Jiang(2011)[8]认为文化距离是一个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障碍,从而影响OFDI的区位选择,然而在研究中国对东南亚、东亚OFDI时发现中国倾向于向文化距离较远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綦建红等(2012)研究中国2003―2010年对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四种方法计算文化距离,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OFDI不是简单地负相关关系,而是U型关系。[9][10]
另外,随着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不断深入,外交活动、政治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理论上,母国政府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为对外投资提供安全保障,现有的研究也表明投资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张建红、姜建刚,2012[11];潘镇、金中坤,2015[12])。潘镇和金中坤(2015)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现中国的OFDI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国家。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研究认为双边良好的外交活动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宗芳宇等(2012)研究指出双方投资协定(BIT)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但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还比较困难,本文借鉴国际上运用广泛的事件数据分析法,运用归一化处理,定量衡量双边关系。
目前的文献缺少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而且现有研究没有将双边关系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2003―2014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两条线,采用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双边关系及其他控制变量来比较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OFDI的影响,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风险防范提供建议。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43个主要国家,主要是基于投资规模、国家重要性和数据可得性三个标准。截止2014年底,中国对上述43个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占到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977%。本文根据以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为指导,并参考国家前沿战略支撑平台“一带一路”数据库(),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以色列、斯里兰卡;“丝绸之路经济带”: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希腊 、塞浦路斯、立陶宛、土耳其、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捷克。
在面板数据模型回归方式的选择上,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显著,但是模型中含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地理距离、文化距离),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会删除重要解释变量。然后在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如表1所示。为得到稳健型结果,本文选用面板矫正误差(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 model简称PCSE)方法。
本文的基准模型采用投资引力模型,在投资模型中加入所需研究的变量,具体模型构造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东道国,t表示年份。
(二)数据构造及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OFDI)。由于被解释变量不能为负值,而OFDI流量有负值的情况,目前主要的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以OFDI存量为被解释变量,二是通过公式 转换(Busse 和Hefeker, 2007)。本文选取OFDI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既解决了负值问题,又避免了流量数据短期内波动很大的问题。
2.解变量
政治风险(PRI)。本文选取美国著名的政治风险测定服务公司PRS (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 )集团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定期的政治风险指数。PRS将政治风险分为12个维度,分别是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回报、内部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事干预政治、宗教参与政治、种族关系紧张、法律与秩序、民主责任、,并依据规则对12个维度分别打分。PRS的政治风险指数涵盖140多个国家1984年以来12个维度的数据,将12个维度的分数相加得到综合政治风险,分数越高,风险越小。本文对原数据取倒数后乘以100,所得PRI越大,政治风险越大。
文化距离(CDI)。Hofstede(1980)提出文化的四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个人主义、男性/女性度。Kought 和Singh(1988)在Hofstede提出的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提出测量文化距离的公式: 。CDj表示中国与第j个国家的文化距离,Iij表示第j个国家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Iic表示中国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Vi表示所有国家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方差。
双边关系(BIL)。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从狭义上看是政治关系。潘镇、金中坤(2015)[12]定义政治关系为国与国之间出于维护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往来,扩大国际影响等战略考虑而结成的政治上的亲疏关系。张建红、姜建刚(2012)[11]分析研究了高层互访、双边冲突、建交时间和友好城市等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门洪华、刘笑阳(2015)[13]指出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为双边关系提供制度化的框架,中国将伙伴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的建交时间受东道国独立时间的影响,国家间的双边冲突具有偶发性,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与中国发生双边冲突的国家很少,本文在确立双边关系这一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未选用建交时间、双边冲突。
本文采用与对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的三个概念来量化双边关系:一、高层互访(VIS):借鉴张建红、姜建刚(2012)[11]方法,国家最高领导人(主席、总统)互访的得分为2,其他领导人访问的得分为1,访问包括第三国会晤,以特定年份访问次数乘以得分来衡量;二、伙伴关系(FRI):一般伙伴关系得分1,全面伙伴关系得分为2,战略伙伴关系得分为3,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分为4;三、友好城市(CIT):以该年度两国省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存量来衡量。双边关系BIL=VIS+FRI+CIT。其中:
VIS=该国当年与中国高层互访次数/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高层互访次数最大值。
FRI=该国当年与中国伙伴关系得分/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伙伴关系得分最大值。
本文选取友好城市作为衡量双边关系的一项指标,但是人口越多城市数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的机会越大。定义:相对友好城市系数=友好城市数/该国总人口。CIT=该国当年与中国相对友好系数/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相对友好城市系数最大值。
3.控制变量
国民生产总值(GDP)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地理距离(DIS):两国首都地理距离。地理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双边进行经济贸易时成本的大小。中国对东道国出口(EXP):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对东道国出口与OFDI正相关,项本武(2007)利用引力模型对2000―2001年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OFDI和进出口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更加倾向于出口创造性。贸易依存度(YCD):东道国与所有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衡量一国的开放程度。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开放程度越高,越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YCD=(进口+出口)/GDP。自然资源(RES):在对外直接投资文献中,解释中国OFDI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Buckley et al., 2007),Aleksynska 和Havrylchyk(2012)[14]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越多的国家,FDI流入也会增加。对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中国,寻求东道国自然资源可能是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用燃料、矿石、金属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来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研究中国对“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投资选择的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分别回归。回归方程(1)―(3)为全样本,来自“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回归方程(4)―(6)的样本来自“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简称“一路”;回归方程(7)―(9)的样本来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简称“一带”。为解释OFDI倾向于高政治风险国家的现象,本文引入双边关系与政治风险、自然资源与政治风险的交叉项。相关变量中心化后,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10,从而排除了多重共线性。
(一)全样本分析
本文方程(1)中PRI的系数为1046,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OFDI有促进作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一般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CDI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显示与东道国文化差异抑制我国的OFDI,与已有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许和连、李丽华,2011[7];綦建红、杨丽,2012[9])。BIL系数为3875,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双边关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有显著正影响,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东道国投资。 首先,中国跨国公司在决定对外投资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导向。我国为了加快“走出去”战略,制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别产业目录》中国家的选取原则也依据与中国双边关系来选取:一是周边友好国家;二是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的国家;三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四是与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其次,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降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良好的双边关系能促进母国通过外交渠道对东道国施加影响,保护投资者利益。
理论上,考虑到投资安全性,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越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本文得出相反的结论,为探究原因,方程(2)引入交叉项BIL×PRI,系数为-7446,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双边关系与东道国政治风险是替代关系,政治风险的效应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而降低,揭示了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是我国投资高政治风险的国家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显著影响OFDI且可能影响PRI效应的变量是自然资源,方程(3)引入交叉项RES×PRI,系数为3249,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中自然资源与政治风险是伴随关系。说明样本中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有较高的政治风险。
方程(1)结果显示GDP系数为负,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对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有负效应。可能原因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需要资金和技术。其他控制变量中,DIS系数在5%水平下为负,说明与东道国地理距离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有负作用。EXP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效应。YCD系数在1%水平下为正,表明东道国贸易越开放,越有利于我国对其投资。
(二)“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比分析
“一路”与“一带”的回归结果在PRI、CDI和DIS上有显著差异。方程(4)―(9)中,“一路”样本国中PRI在1%水平上显著檎,而“一带”样本国中, PRI系数不显著。“一路”和“一带”沿线国家PRI平均值分别为166和134,说明“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政治风险高的特点,而“一带”国家政治风险较低。“一带”沿线国家包括少数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和少数发达国家,平均而言政治风险较低,所以PRI显示为不显著。“一路”样本国中CDI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一带”样本国中,CDI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在“一路”上表现出外来者劣势,而在“一带”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綦建红等,2012)。方程(4)―(6)中DIS系数不显著,方程(7)―(9)中DIS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理距离阻碍我国对“一带”沿线国家的投资,而对“一路”国家影响不大。“一路”国家多为亚洲国家,我国OFDI发展初期较多投资于东盟等邻近国家,样本“一路”中21个国家投资总量占“一带一路”样本43国总投资的70%以上,相对“一带”国家而言,发展较早,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投资的发展,地理距离的消极作用逐渐淡化,不再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交互项PRI×BIL的系数在“一路”和“一带”样本中分别为-15779和4244,但在“一带”上不显著。表明在“一路”样本下双边关系对OFDI的效应随着政治风险的增加而减小,“一路”国家政治风险较高,当发生高风险政治事件时,本国政府基于好的双边关系鼓励企业投资的作用减弱。而“一带”样本中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低,BIL对OFDI的促进作用不突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面板数据,利用PCSE模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和特点。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国家呈现出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特点;(2)本文选取高层互访、伙伴关系、友好城市三个指标,运用归一化原理,计算出双边关系系数,验证了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文化距离在“一路”上表现出外来者劣势,而在“一带”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地理距离虽然阻碍我国OFDI,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阻碍作用减弱;(4)双边关系对OFDI的效应在“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表现为随着政治风险的增加而减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显著。
本文结合国际商务和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作出以下几点贡献:首先,本文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到东道国投资的促进作用,并采用适当方法将双边关系量化,以前的研究都采用如建交时间、高层访问、友好城市、BIT等单一因素,稳健性较差,完善了国际商务研究中双边关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其次,本文研究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对“一带一路”OFDI的影响,得出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减少东道国政治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实证研究中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给出新的解释。此外,本文进一步比较了我国对“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投资的差异,“一路”国家普遍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而“一带”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低、与我国文化差异大。我国对“一路”国家投资表现为政治风险偏好的特点,文化距离阻碍我国对“一路”国家的OFDI,而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我国对“一带”国家投资中,东道国政治风险影响不显著,文化距离在“一带”国家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地理距离有显著阻碍作用。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级体系和投资保险制度。从实证结果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但东道国政治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提前做好风险预警是保障投资安全的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不可避免会遇到来自东道国的风险,比如战争、政治暴乱、征收及国有化,投资保险有利于减少风险发生后的损失。二、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与东道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积极与东道国建立伙伴关系,结成友好城市、签订有利于保护投资和贸易的合作文件,如《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三、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减小对化石能源进口的依赖。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中国对“一路”国家OFDI显示出明显的资源寻求取向,并且往往需要承受高的政治风险,投资安全问题突出。四、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修建港口、基础设施,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修建铁路,出口高铁,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去。
参考文献:
[1]韦军亮,陈漓高.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9(4):106-113.
[2]王海军.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2(1):110-116.
[3]Ramasamy, B., M. Yeung and S. Laforet,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1): 17-25.
[4]杨娇辉,王伟,王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颁布的风险偏好:悖论还是假象[J].国际贸易问题,2015(5):133-144.
[5]Kolstad, I. and A. Wiig,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1): 26-34.
[6] Bruce Kogut and Harbir Singh Source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3):411-432.
[7]S和连,李丽华.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1(17): 154-156.
[8]Kang, Y. and F. Jiang, 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1): 45-53.
[9]綦建红,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J].经济地理, 2012(12): 40-46.
[10]綦建红, 李丽,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 2012(12): 137-147.
[11]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12): 133-155+160.
[12]潘镇,金中坤.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财贸经济, 2015(6): 85-97.
[13]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65-95,157-158.
[14] Aleksynska,M.,and O.Havrylchyk.FDI from the south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and natural resource[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2,29:38-53.
第6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联系 财务风险 民营上市企业
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的关系是非市场环境的最主要构成部分。任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非市场环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和政治经济的融合,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产权保护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企业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府干预比较多、市场信息还不够透明、资本市场缺乏效率,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治联系被当成了制度环境的重要的替代机制。
与民营企业的政治背景要靠企业控制人投入成本自主建立和经营不同,国有企业普遍具有政治联系,而且国企的政治背景通常是“免费”的,这使得国企高管不会刻意重视政治联系的作用,其对国企的影响不会有很大差距。因此,本文仅选择我国上市民营企业作为政治联系研究的对象,探讨政治联系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分析民营企业控制人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以期得到更为显著的研究结果。同时,也能对民营企业理性看待政治联系,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具有更为针对性的参考意义。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在资源分配方面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控制着一方经济命脉。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政府干预、金融业竞争与市场化和法律制度的限制。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民营企业想要从政府手中低成本地获得稀缺资源,得到更多市场机会,便会对其产生依赖,这种依赖主要通过企业对政治联系的渴望体现出来。企业控制人希望通过建立政治联系,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互利关系,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采取主动,获得更有利的市场竞争力,如此一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就可能降低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活动带来的财务风险。
根据委托理论,被委托者对企业贡献越大,越能受到委托者更多的赏识,同时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无形中培养了企业管理层激烈的竞争环境,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会让企业管理者自愿地投入更多精力到企业经营中。但是在企业高管知识、能力背景相同的情况下,为了在竞争中有突出表现,企业高管会挖掘一切可利用的政治联系谋求企业发展,企业因此随时受到政治联系的影响。从侧面来说,在企业管理者通过建立政治联系以期在竞争中胜出的同时,也会有利于企业财务风险的降低。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在民营上市企业中,企业实际控制人、董事会和经理人的政治联系能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二)政治联系特征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虽然虚拟变量法在研究政治联系时得到广泛应用,俨然成为学者们衡量公司政治联系的最主要方法,但是,它只区分了政治联系的有无,并未考虑我国的制度背景和政治联系方式。
在我国,政治联系按性质可以分为政府官员型和代表委员型,不同性质的政治联系所接触的政治环境存在差异,政治联系人能获得的政治信息也不同。政府官员型政治联系人曾任职于政治部门,其人脉关系能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帮助企业赢得政治补贴、税收优惠等经济利益;而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人能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提出有利于企业的诉求,同时,能更及时地将新的政治策略反馈到企业中,有利于企业控制人优化相应的经营决策。而且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能直接影响政府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其效果具有外在合法性,因而也应该能对财务风险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认为这两种政治联系方式都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并能有效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水平,并提出假设2:
H2: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和政府官员型政治联系都能有效降低民营上市企业财务风险。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本文收集了2012―2015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数据,并对样本做了如下筛选:①剔除ST、*ST样本企业;②剔除高管背景难以判断的样本企业;③剔除相关研究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④剔除2008年间已经退市或者新上市的企业。在进行以上筛选后,剩余397家样本企业。本文所使用的控制变量所需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和《锐思RESSET金融数据库3.0》,同时也参考了新浪股票等互联网信息。
2.变量选择。
(1)被解变量――财务风险。目前,国内外在研究企业财务风险时,普遍使用Edward Altman的Z得分公式(Z-Score Formula)进行预测。但由于中西方的会计准则的差异,国内外的企业在会计信息处理和财务报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不同,Z得分公式没有考虑企业的现金流量以及一些表外预警指标,该模型在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分析时,会出现较大误差。
周守华、杨济华等(1996)在Z得分公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得到了更符合我国国情的F分数模型,引进现金流量的相关项目,使得数据处理更加全面,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企业是否存在财务危机。故本文采用F分数模型度量企业财务风险,具体公式如下:
F=-0.1774+1.1091X1+0.1074X2+1.9271X3+0.0302X4+0.4961X5
其中:X1=(期末流动资产-期末流动负债)/期末总资产,X2=期末留存收益/期末总资产,X3=(税后纯收益+折旧)/平均总资产,X4=期末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期末总资产,X5=(税后纯收益+利息+折旧)/平均总资产。其中,X5测定的是企业总资产在创造现金流量方面的能力,利息是指企业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后的余额。
(2)解释变量――政治联系。本文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PC1)、董事会的政治联系(PC2)和总经理(包括CEO、总裁、执行总裁)的政治联系(PC3)三个变量分别表示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同时,利用虚拟变量法对三个变量进行赋值。从企业控制人政治联系特征来看,本文将控制人的政治联系划分为两部分:政府官员型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虽然虚拟变量法已成为衡量政治联系最主要的方法,但它把不同层次政治联系都赋值为1,没有考虑政治联系强度,结果略显粗略。本文分别利用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进行赋值,进一步考虑政治联系的影响力和政治联系的层级,具体见表1。
(3)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考了陈丽君(2012)在企业控制人政治身份与财务风险控制研究中使用的控制变量描述:
成长性(GROW):本文用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企业成长状况,具体表现为第t年的营业增长率=(营业收入t-营业收入t-1)/营业收入t-1,成长性较好的民营上市企业往往更注重企业财务风险,对风险的估量和防范更加全面。
资产期限结构(AM):本文所说的资产期限结构,即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百分比。当企业资产期限结构越大,表明企业固定资产比重越大,流动性风险就会相应增加。
资产负债率(LEV):该变量表示为企业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当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往往企业偿债压力越大,企业财务风险越高。
(二)实证检验。
1.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1)企业政治联系。从2012年至2015年,我国377家A股民营上市企业中实际控制人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平均数量为236家,每一年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企业存在政治联系,而且有政治联系企业的数量逐年增长,这意味着我国政治联系在民营企业中的存在现象极为普遍,民营企业控制人对政治联系的关注和建设也越来越多。同时,企业高管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均数比例占到0.53,远远大于企业高管曾担任政治官员的比例,这说明,相对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代表型政治联系是民营企业控制人获得政治联系的主要途径,换而言之,企业获得代表型政治联系更容易。当然也存在一些企业既有高管人员曾为政府官员,又有高管曾经或现在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见表2。
(2)企业财务风险。根据我国上市企业的实际,F分数模型的临界点为0.0274;若某一特定的F分数低于0.0274,则将被预测为破产公司;反之,若F分数高于0.0274,则公司将被预测为继续生存公司。见下页图。
2012―2015年间陷入财务困境或有潜在财务风险的样本企业数量远低于50%,且数量逐年下降,这表明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在2012―2015年间发展状况良好。但是从上页表2可以看出,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的数量比例远不如被预测稳步发展的企业的数量,这表明政治联系并不是唯一控制企业财务风险的手段,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其他环境影响的变化更显著。
2.回归结果及其分析。为了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3报告了具体回归分析结果。为了区别于F分数模型的F分数值,表3中回归分析的F值以F*表示。由表3可知,模型一F*统计量为63.383,在1%水平上显著,且调整后的R2为9.43%,故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效。
考察表3中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可知,度量政治联系的变量PC与F分数值在5%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说明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能够有效帮助企业降低财务风险,本文的研究假设H1得到证实。进一步考察其他解释变量发现,GROW、Am、LEV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43、-1.084和1.034,对应的显著性检验的P值分别为0.022、0.000和0.000,均小于0.05;由此可知,除了政治联系之外,企业成长性(GROW)、资产期限结构(Am)和资产负债率(LEV)都能对企业财务风险(F分数)产生显著影响。其中高成长性和高负债的企业面临更高的财务风险,而资产期限结构则有助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水平。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分析结果,我们对政治联系方式同时采用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衡量,也使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采取赋值法还是虚拟变量法,政府官员型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的系数都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和政府官员型政治联系都能有效降低民营上市企业财务风险。故此,H2得到证实。同时,分别对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研究可以发现,在虚拟变量法下,政府官员型政治联系的关联系数绝对值大于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的关联系数绝对值,而在赋值法下,结果刚好相反。但是赋值法下模型的R2较虚拟变量法下有所提高,f明赋值法下对财务风险的拟合度较优。综合这两点,在研究政治联系性质与企业财务风险关系时,采用赋值法结果更准确。根据赋值法的结果可以发现,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略高于政治官员型政治联系。
上述分析表明,在研究政治联系与公司财务风险时,政治联系可以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但政治联系性质的不同对企业财务风险影响稍有不同,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略高于政治官员型政治联系。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2012―2015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在民营上市企业中,企业实际控制人、董事会和经理人的政治联系能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并且将政治联系进一步分类之后研究发现,虽然政治官员型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都能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但代表委员型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略高于政治官员型政治联系。同时,研究还发现,政治联系对财务风险影响的系数都不是很大,说明政治联系对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相当有限。这就意味着,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能一味地依赖于政治联系,而忽略了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我们认为,政治联系虽然给企业赢得了政策支持和廉价的公共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但作为企业控制人,合理的企业决策才是企业规避风险的重要环节。只有在强化企业风险控制意识、建立完善的风险规避制度后,政治联系才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Z
参考文献:
第7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政府审计风险的产生存在着客观条件与主观原因。其客观条件是:(1)经济环境的复杂化,使得审计范围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财务审计,使得传统的审计技术、审计方法受到挑战,审计作业风险显现。(2)我国《宪法》赋予了政府审计组织审计的独立性,然而现行的体制安排造成审计独立性的制度性缺损。审计人员在履行其宪法责任时往往遭遇来自同级党政部门的体制隶属关系上的干预,政府审计组织被动屈服导致政府审计违宪而产生政治风险。(3)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构成政府审计机关的审计行为外部约束力量,必然形成法律风险。(4)社会公众对政府审计的期望与政府审计能够发挥的作用之间矛盾也越来越大,这种社会期望正逐步演变成一种社会性“审计疲劳”,审计面临社会压力的信用风险。主观原因方面:(1)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不够,在审计工作中因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而产生的审计方法、审计程序等方面的失误,带来审计风险。(2)由于政府审计直接涉及经济活动,利益的诱惑与讨价还价已成为政府审计工作中无法回避的隐患,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尤其是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时,过多地考虑个人或小集团的私人利益,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监督机构,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和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政府审计风险的影响也是深远而重大的。对于政府审计而言,审计失败带来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将影响到依赖和利用企业编制的会计报表作为决策依据的企业管理当局――国家、企业投资者、以及债权人、消费者、企业职工等。然而,由于政府审计工作长期低调和体制性口蔽,其风险问题无从谈起,对其的关注、研究也是从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目前,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与风险要素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且基本上是对国际公认的社会审计风险模型的简单改良,与中国政府审计风险的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指导性较差。本文在风险因素识别基础上,构建政府审计风险模型。通过对审计风险模型的分析指出风险的控制措施,以此促进政府审计机关的制度建设和责任规范,进而指导政府审计实践。
二、审计风险构成要素分析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对构建政府审计风险模型提供框架性的思路指导。我们可以把政府审计风险视作一个系统,政治风险、组织风险、执行风险、文化风险构成了系统要素,而系统又是开放的,它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转换,所以,外部的环境对审计风险也有影响作用。
(一)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政府审计风险由于审计文化中群体共同的价值观、精神、道德观、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作用,审计组织在同一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全体成员则具有一种强烈的一体感,这就非常有利于审计组织内部人员的协调一致。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也比较容易消解。审计文化渗透到其他各个系统,其优化功能可以有效降低组织系统风险;组织系统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组织系统风险,同时可以对政治风险起到一定限制作用,政治风险具有和审计组织系统风险同向变动的特点;在总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政治风险、组织系统风险和能接受的审计执行风险呈反向变动,政治风险、审计组织系统风险越小,可接受的审计执行风险越大(见图1)。
(二)从要素与系统的关系有政府审计风险系统论认为,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有机组合构成了整体,各个部分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而反作用于整体,部分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体的变化。在政府审计风险的几个风险要素中,政治风险、审计执行风险、审计组织系统风险和审计文化风险属于内部风险,对政府审计风险起决定作用。环境风险属于外部风险,对政府审计风险起影响作用。对于政府审计机关来说,政治风险和环境风险属于不可控风险,组织系统风险、审计执行风险和审计文化风险属于可控风险,因此,审计机关只有着力于降低这三种风险,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审计整体风险。
(三)从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看政府审计风险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开放的,它同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当它与其它系统相互作用时,并不是代表孤立的要素本身,而是作为整体的要素与环境发生作用。环境系统具有多层次性、多方面性,环境系统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结构机制充分显示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有些外部环境因素具有一定的刚性,对于政府机关来说来说是比较难改变的,只有去适应它才能进行正常的审计活动。
三、政府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
社会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是基于财务报表审计的特点,与社会审计风险自身的特征相适应,而我国政府审计风险是系统性风险,不仅仅是财务报表审计的风险,它在政治系统、组织系统、执行系统、文化系统都存在风险,审计环境的复杂化又加剧了风险的产生,政府审计风险是这几种风险合力的作用。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政府审计风险可用下图(图2)表示:
基于这几个因素,本文构建的我国政府审计风险模型为:
第8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模糊综合评价 国际工程项目 政治风险
中图分类号:F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2-058-03
政治风险作为国际工程项目实施中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中的一种主要风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国际工程项目往往投资及规模巨大,风险一旦产生,将给承包企业带来无法承受的损失。因此,研究政治风险的产生及影响,建立政治风险识别和评价模型对国际工程项目的有效管理和承包商的投标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常见的国际工程项目风险识别评价模型主要有:期望值法、专家经验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BP神经网络综合评价法等。国内许多优秀的学者运用这些理论在国际工程项目风险评价方面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而针对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在这里提出一种针对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的方法,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项目决策和实施提供参考。
一、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一)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概念及类型
对于政治风险的概念和涵义,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基点有不同的理解。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是指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因国家决策或行为、社会事件或社会条件变化而造成工程承包商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它是一种国家风险,国际承包工程系统将政治风险分为战争、内乱、政权更迭、国有化没收外资、拒付债务、政府干预等。
从政治风险的作用范围来看,可以把政治风险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两大类。其中宏观政治风险作用于项目所在国家所有的承包企业;而微观政治风险则作用于项目所在国家的某些承包企业;同时,从政治风险所产生的原因上来看,政治风险又可以分为由政府决策和行为引起以及由社会事件和条件变化引起两大类。所以,又可以将政治风险分为以下四种主要类型:(1)政府宏观政治风险;(2)社会宏观政治风险;(3)政府微观政治风险;(4)社会微观政治风险。
政府宏观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对国家内所有跨国承包项目实行征用、没收、国有化或限制承包企业本金及收益汇回等。社会宏观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权更迭、内乱等。政府微观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府非法解除项目协议或违反合同条款、选择性征用和国有化、实行歧视性扣押或税收等。社会微观政治风险主要包括针对性的恐怖袭击、针对性的罢工、抗议示威等。
(二)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随着现阶段国际形势的相对稳定,战争已是极其偶然的事件,内乱也只在极少数国家出现;而国际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使得东道国公开征收和国有化国际工程项目以及针对承包企业完全的外汇管制等现象不再常见。选择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关键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本文以政治风险概念界定为基础,剖析造成造成国决策或行为、社会事件或社会条件变化的原因,注重评价效果以及评价效率,选取的评价指标尽量为国家本质内在并且不会随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国际工程项目本身的特点参照上述原则,建立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二、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一)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结构
模糊数学综合评价能够将事物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量化,通过运用数学知识科学分析多个因素对评价对象隶属等级关系进行综合性评价,是一门应用十分广泛的科学分析工具。国际工程项目主体之间在语言、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带来了项目实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治风险评价因素的复杂性、评价标准存在的模糊性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适用性非常契合。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能够使得定性和定量因素相结合,解决政治风险评价信息量大的问题,评价结论可信。具体评价过程如下:
1.根据专家意见针对项目实际结合国际工程项目特点对各个指标进行定量估算,建立评价指标集和评语集以及各指标权重分配模糊向量A,表示如下:
U={u1,u2,…,um};V={v1,v2,…,vn};A={a1,a2,…,am}
其中,m、n分别表示指标项目数和评语等级数,向量A满足■ai=1。
2.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集U中各影响项目政治风险因素的权重ai(i=1,2,…,m),具体做法如下:
(1)根据专家打分,将各指标按影响程度作两两重要性比较。设评判指标集合为T={t1,t2,…,tn},设判断矩阵aij(aij>0)代表ti对tj的重要性。判断矩阵aij的标度方法选用1~9比例标度法。
(2)使用根法计算下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权重值,具体做法如下:
先对上一部种判断矩阵aij中各行元素的乘积,记为Mi=■aij;然后求Mi的n次方根,记为wˉi=■;接着归一化或正规化处理wˉi,处理公式为wi=wˉi■wˉi;最后检验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值是否满足一致性,若满足则以此作为该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权重值。
3.对每一个影响因素根据评判集中的等级指标进行模糊评价,得到项目政治风险评判矩阵R,表示如下:
4.进行各评价指标权重分配模糊向量A与对应的模糊评价矩阵R之间的模糊矩阵合并运算,得到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评价指标综合评价模糊向量B,经归一化处理后得Bˉ,表示如下:
B=A×R={b1,b2,…,bm},Bˉ={bˉ1,bˉ2,…,bˉm}
(二)仿真实验
以某个跨国公司在非洲某国的一个国际工程项目为例,利用本文提出的评价方法进行项目的政治风险评价。根据9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就文章提出的指标结合工程所在国家实际进行打分,令评语集为{最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大风险、适中风险、较小风险},量化专家评分后得到一级评价指标权重为:(0.20,0.18,0.21,0.17,0.11,0.13),二级指标权重为:
(0.35,0.33,0.32,0.45,0.55,0.21,0.20,
0.28,0.31,0.30,0.30,0.40,0.50,0.50,
0.60,0.40)。
1.构建二级指标评判矩阵,有:
S=0.25 0.22 0.18 0.25 0.100.30 0.25 0.22 0.12 0.110.20 0.25 0.25 0.15 0.15
2.分别对二级评价指标进模糊变换,有:
R1=W1×S1=(0.35,0.33,0.32)×
0.25 0.22 0.18 0.25 0.100.30 0.25 0.22 0.12 0.110.20 0.25 0.25 0.15 0.15
=(0.25,0.24,0.22,0.18,0.12)
同理,有:
R2=(0.23,0.21,0.24,0.19,0.13)
R3=(0.21,0.23,0.22,0.18,0.14)
R4=(0.21,0.24,0.25,0.16,0.14)
R5=(0.20,0.19,0.26,0.20,0.17)
R6=(0.24,0.21,0.25,0.17,0.13)
于是,有:R=
0.25 0.24 0.22 0.18 0.120.23 0.21 0.24 0.19 0.130.21 0.23 0.22 0.18 0.140.21 0.24 0.25 0.16 0.140.20 0.19 0.26 0.20 0.170.24 0.21 0.25 0.17 0.13
3.进行一级指标模糊综合变换,有:
B=A×R=
(0.20,0.18,0.21,0.17,0.11,0.13)
×0.25 0.24 0.22 0.18 0.120.23 0.21 0.24 0.19 0.130.21 0.23 0.22 0.18 0.140.21 0.24 0.25 0.16 0.140.20 0.19 0.26 0.20 0.170.24 0.21 0.25 0.17 0.13
=(0.22,0.22,0.24,0.18,0.14)
(下转第62页)(上接第59页)
由于■bi=1,其中(i=1,2,3,4,5),故无须归一化处理。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此国际工程项目的政治风险等级为一般。
三、结束语
政治风险是国际工程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本文针对政治风险评价,提出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方法,运用模型进行仿真实验,证明该方法在有效评价政治风险方面可靠、可行,可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项目决策和实施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徐阳.国际承包工程面临的风险及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1(1)
[2] 胡文发.基于BP算法的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级模型[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6(4)
[3] 邵军义,董坤晗等.国际工程项目风险评价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1(2)
[4] 林飞腾,侯渡舟.国际工程承包中的项目风险模糊层次分析[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
[5] 朱毅,李吉勤,魏焱等.基于总承包商视角的EPC国际工程风险因素分级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2(5)
[6] 李寿双,周双庆.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法律应对——以国际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为例[J].学术论坛,2003(5)
[7] 杨学进.浅析国家政治风险评价对象[J].中国经贸,2001(5)
[8] 杜栋,庞庆华,吴炎.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社,2008
第9篇: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评估准确评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魏明禄,丁烈云.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及其规避[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许迈进,章瑚纬.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3][4]张增莲,编著.风险评估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