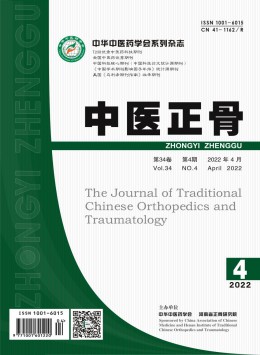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精选(九篇)

第1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8日作出(2003)刑监字第155号再审决定,以原二审判决对刘涌的判决不当为由,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了该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12月18日至22日在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再审被告人刘涌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了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一、二审确认刘涌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妨害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定罪准确,原一审对各罪的量刑适当,二审除对伤害罪的量刑外,其余各罪维持一审的判决正确,对伤害罪的改判有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二审判决中对再审被告人刘涌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及决定执行的刑罚部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维持原二审对刘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判处的刑罚;对刘涌被判处的各罪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再审被告人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敛的全部财物及其收益,依法追缴;供其犯罪使用的工具,予以没收。判决宣告后,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死刑执行命令,当即对刘涌执行了死刑。 作为一起涉黑案件,该案的首犯刘涌可谓"罪行累累"。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活动27起;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之前,实施违法活动4起,共实施违法活动31起。其中,直接参与或者指使、授意他人故意伤害13起,致1人死亡,5人重伤并造成4人严重残疾,8人轻伤;指使他人故意毁坏财物4起,毁坏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33090元;非法经营1起,经营额人民币7200万元;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6起,行贿金额人民币41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95000元,行贿物品价值人民币25700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 275 497元;指使他人妨害公务1起;非法持有枪支1支。但是,在这些犯罪中,涉及死刑的罪行只有故意伤害罪。至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94条的规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该条还规定,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因此,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是刘涌被判死刑的法定理由,真正致刘涌于死地的是故意伤害罪。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在判决上的差异,也主要是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认定和量刑。 根据我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关于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则认为,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刘涌直接或者指使、授意他人持刀、持枪实施故意伤害犯罪,致1人死亡,5人重伤并造成4人严重残疾,8人轻伤,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不具有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刘涌所犯多起故意伤害罪中,最具争议的是发生在1999年10月的故意伤害(致死)罪。法院的判决书指称,1999年10月,被告人刘涌得知有人销售"云雾山"牌香烟,影响其经销同种香烟后,指使程健去市场查看并"收拾"销售"云雾山"牌香烟的业户。同年10月15日上午,在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农贸大厅,经程健派人指认,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及李凯(同案被告人)等人对销售"云雾山"牌香烟的业户王永学进行殴打,宋健飞并威胁他人"看谁还敢卖云雾山烟"。王永学因右肺门、右心房破裂,急性失血性休克合并心包填塞而死亡。刘涌涉黑案的第二被告宋健飞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与其直接参与了对被害人王永学的伤害,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无关系。在这起犯罪中,被告人刘涌是否指使了对被害人王永学的伤害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刘涌在侦查阶段对这起犯罪作了多次供认,但在审判阶段提出,自己的供认乃是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结果。公安机关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也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点之一。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宋健飞等人殴打王永学,系为了刘涌的利益,在刘涌的指使下所为,刘涌应为此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被告人刘涌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公安机关在该案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第2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关键词]故意伤害;盖然性故意;具体性故意
【中图分类号】G640
一、 故意伤害罪主观罪过立法概述
(一)我国故意伤害罪立法概述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一般认为,故意伤害罪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①故意伤害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行为人对自己的伤害行为以及行为会造成的伤害结果具有认识,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伤害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②关于故意的具体内容是抽象的笼统的故意伤害他人还是具体划分为致他人轻伤的故意,重伤的故意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论文将重点分析这争议问题。
(二)外国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立法状况
西方国家关于故意伤害行为较我国规定比较细致,表现在伤害种类划分为数个罪名以及刑罚设置这两个方面。例如德国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有伤害罪、危险伤害罪、严重之身体伤害罪、伤害致死罪;法国刑法将有关伤害的犯罪分为酷刑及野蛮暴行罪、暴力罪和威胁罪,在这三种犯罪之下,又进一步作了更细的划分;韩国刑法中伤害的犯罪包括伤害罪、尊亲属伤害罪、重伤害罪、尊亲属重伤害罪、伤害致死罪、暴行罪、尊亲属暴行罪以及特殊暴行罪。③
由此可见,外国刑法对于故意伤害行为严格区分了主观故意内容,并依据主观伤害他人轻重程度结合伤害结果,分别进行刑法规定与刑罚处罚。而我国刑法不论故意的具体内容,将伤害结果造成的轻伤、重伤以及死亡结果全部规定在一个刑法条文之中,同外国刑法条文相比,具有一个法条包含多个伤害故意、多个伤害行为和方式、多个伤害结果、多个因果关系、多个量刑档次的特点。
二、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分析
(一)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的争议观点
在理论界,就故意伤害罪主观罪过形态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故意伤害罪中的故意是概括的故意,不区分伤害故意是轻伤的故意还是重伤的故意,只要行为人具有伤害他人的盖然性故意,无论是轻伤害故意还是重伤害故意,都符合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故意要素。
(二)各观点评析
对故意内容不做区分的概括的故意与具体的故意是理论上存在着的主要争议观点,但是都存在着各自的利弊。
盖然性故意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证据认定简单容易,容易实现法律形式上公正--相同危害结果得到相同判决,但是盖然故意不利于实现实质的法律公正。
具体故意说主张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进行具体区分,并依据主观故意设立普通伤害罪、重伤害罪以及伤害致人死亡罪。此观点侧重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险性,追求实质上的法律公正,但此观点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存在着弊端,可能会导致违背刑法理论现象的发生。例如,如果行为人以轻伤害他人的故意,实施了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只造成了他人轻微伤害结果甚至无任何伤害结果,则行为人将构成普通伤害罪的未遂,但未遂不等同于不构成犯罪,这样我国刑法将主观恶性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危害行为也纳入了犯罪刑罚领域,有悖于刑法本质。从实践层面分析,形式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故意内容难以取证,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只有行为人即施害人供述这一情形下,我国证据法规定在此情形下不能采信任被告人供述,现实中,行为人也很少会供述不利于自身的主观方面的犯罪证据。因而在取证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增大了司法机关的任务,容易导致案件拖延,降低了司法效率。
三、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之完善
由上述可见,盖然的故意与具体的故意二者存在着各自的利弊,在理论上与司法实践方面可以取其优点,避其缺点,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笔者认为原则上应采取盖然的故意,需要注意的是本人所主张的盖然性的故意并非第一种观点的故意,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依据故意伤害结果对行为人予以刑罚处罚,而是将故意伤害结果同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故意内容将结合,以伤害结果同主观故意内容一并作为量刑依据。此种故意是在肯定我国现有刑法条文基础之上,加入主观故意内容的量刑因素,结合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及伤害结果双方因素对行为人予以定罪量刑。这种故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着其合理性。
首先,这种故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体现,行为人的入罪量刑既考虑了行为人主观故意态度,又结合了危害行为所造成了客观危害结果,在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又兼顾了施害人的权利。这种故意与盖然性故意相比,加入了行为人主观罪过这一考量因素,具有更合理性。
其次,以伤害性结果为入罪主要因素的故意,有利于解决具体故意的理论与现实不一致的难题。具体的故意会出现轻伤害的故意未遂形态,这一现象只存在于理论探讨层面,在实践中几乎不具有存在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依据这种故意此行为将不作为犯罪处理,行为人主观上仅有轻伤害他人的故意,客观上未造成轻伤害以上结果,不作为犯罪处理。
再次,此种故意在司法实践层面也具有合理性。第一,以伤害结果为主要入罪量刑因素的故意,主观故意内容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处于次要地位,较具体故意相比,减轻了司法机关的举证责任,即司法机关可以依据行为人使用工具、打击部位、个人状况以及有无预备行为等进行综合评断。第二,此种故意以危害结果为主要考量因素,使相同危害结果得到相同判决,实现了形式正义,同时还考虑行为人主观恶性,从主客观双方面对行为人定罪量刑,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综上所述,此种故意对我国传统的盖然性故意进行了补充与完善,更科学的对故意伤害行为人进行主客观评析,使行为人的定罪量刑更加合理,但是此种故意仍然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对伤害结果的倾向性考虑,加之主观故意内容认定的不易,司法实践中难以做到主客观合理兼顾等问题,因而,对于故意伤害主观故意在刑法定罪量刑中的地位仍需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处版社2011年版,第763页。
②冯胜:《故意伤害罪疑难问题研究》,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5页。
③段长寅:《论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认定与量刑》,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8页。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2]马克昌:《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曾宇、胡君旸:《对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的理解与认定》,《中国检察院》2009年第3期。
[4]杜文俊:《故意伤害罪的二重的结果加重犯性质探究--以故意伤害罪的比较法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
[5]田宏杰:《故意伤害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法学家》2001年第4期。
第3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关键词:间接故意犯罪 犯罪未遂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出有意识地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的犯罪是间接故意犯罪。间接故意犯罪有无犯罪未遂?这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张。
一、间接故意犯罪与犯罪未遂的观点
1、外国法学家的观点
旧中国法学家曾介绍说,意大利刑法理论否认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而荷兰、挪威、德奥等国的法律解释则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日本刑法学者大场茂马、泉二新熊等以及旧中国法学家王觐等,也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苏联刑法理论基本上倾向于否定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其中,一些刑法教科书认为,受犯罪构成主观因素限制,间接故意犯罪逻辑上可能存在未遂,但在事实上很难确认,因此事实上只能对直接故意犯罪中的未遂加以惩罚。另一些专著专论则批评说,间接故意犯罪在实际上和逻辑上都不可能存在未遂。例如,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伊宁认为,在间接故意犯罪的场合,既然行为人不希望发生犯罪结果,那么“从逻辑上”看,他也就不可能去预备实施或企图实施犯罪。刑法学者库兹涅佐娃也曾明确指出,间接故意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不可能存在未遂。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看,1958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和现行的《苏俄刑法典》均以第15条第二款规定:“凡直接以犯罪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如果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进行到底,就是犯罪未遂。”这就从强调犯罪未遂必然存在犯罪目的的角度,否认了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苏联的司法解释更明确了这种观点,例如,1975年6月27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故意杀人案件审判实践的决议》中指出:“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第十五条的内容,杀人未遂只能存在于直接故意中。也就是说,当行为人的行为证明,也预见到会发生死亡,而且他也希望发生这种结果,只是由于不以犯罪人意志支配的原因,而没有产生致命结果时,才可能有杀人未遂。”
2、我国法律界的观点
我国刑法学在五十年代对此问题基本上未展开研讨。但当时也有个别刑法教科书曾提出了间接故意犯罪不可能存在犯罪未遂的观点并有所论证。《刑法》颁行以来,这个问题逐渐引起我国刑法理论界的关注。从发表的论著看,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的见解,两种见解又都是从间接故意犯罪有无犯罪目的来论证它有无未遂的。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观点一般认为,间接故意并非一概有犯罪目的和未遂,在实施非违法犯罪的行为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间接故意犯罪无犯罪目的也无未遂;在实施某种违法犯罪行为而放任另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间接故意犯罪有犯罪目的的也有未遂,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所放任的结果,就是间接故意的犯罪目的,如果该目的未能实现,就是间接故意犯罪的未遂。例如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本来放任被害人的死亡,只是由于抢救及时才未死亡,就应认定行为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未遂。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即使实施合法行为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犯罪未遂。例如,开枪打兔子而放任旁边的小孩,一枪打去击中小孩但未中要害,小孩没死,这就应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不是伤害罪。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无未遂的观点认为,间接故意犯罪无犯罪目的因而也无未遂,因为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犯罪行为达到的危害结果,而间接故意是“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目的;由于某种原因间接故意对结果发生与否都无所谓,都在其放任的主观意思内,因此结果没发生时就不能说是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没有“得逞”,所以间接故意犯罪也就不存在未遂问题。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否定间接故意犯罪存在未遂的观点较占优势。
笔者也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没有未遂,但是认为从间接故意犯罪没有犯罪目的的来论证它没有未遂是不妥当的。间接故意犯罪之所以不存在未遂,是由其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的特点及犯罪未遂的主客观特征决定了的。
二、犯罪未遂的特征及其与间接故意犯罪的关系
1、犯罪未遂的特征
犯罪未遂主观特征的含义,是行为人造成特定的犯罪结果或完成特定犯罪行为的犯罪意志,因其意志以外原因的阻止而未能实现,这是未遂客观上不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反映。间接故意犯罪主观要件的特点,并不表现为一定要造成特定犯罪结果的犯罪意志,即不是希望、追求特定结果的心理态度,而是表现为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造成的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放任”的心理态度,即听之任之,发生与否都可以的心理态度。这样,行为人所放任的危害结果未发生时,这种结局也就是行为人放任心理所包含的。放任心理由其所包含的客观结局的多样性和不固定性所决定,根本谈不上“得逞”与否;“得逞”与否只能与希望的心理相联,即只能与追求特定犯罪结果发生或特定犯罪行为完成的心理相联。可见,间接故意犯罪在主观上不符合犯罪未遂所具备的主观特征。
犯罪未遂的客观特征,就是着手实行犯罪后未齐备犯罪既遂的客观要件,具体看或为未造成特定的犯罪结果,或为未完成特定的犯罪行为,这是主观犯罪意图“未得逞”的客观表现。间接故意犯罪由其主观“放任”心理地的支配,而在客观方面不可能存在未齐备犯罪既遂客观要件的情况。以间接故意杀人为例,或死、或伤、或无任何实际危害结果,这些结局都是放任心理所包含的内容。在徒有行为而无任何实际危害结果的情况下,这种结局也符合其放任心理,因而不能把此结局视为故意杀人“未得逞”,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在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这种结局不是齐备了故意伤害罪的要件、而是未齐备故意杀人罪要件的未遂,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只能认定是齐备了故意伤害罪的要件而成立故意伤害罪;只有造成死亡时,才能够认定是齐备了故意杀人罪的要件而成立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
上述间接故意犯罪主客观特征的统一,决定了间接故意只能是造成了为刑法所惩罚的实际危害结果时,才能构成犯罪,危害结果符合什么罪的构成要件就成立什么罪。而不可能存在以不齐备特定犯罪客观要件为标志的“犯罪未遂”。
2、间接故意犯罪与犯罪未遂
对于理论上和实践中经常研讨的涉及间接故意犯罪有无未遂的案情,笔者认为,运用上述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都可以说明它们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其一,行为人为了实现一个非犯罪的意图,而有意放任某种犯罪结果的发生。案例一:某甲持枪打猎,看到地上有只野鸡,但近处有一小孩在拔草,甲明知自己枪法不佳,若开枪有可能打死小孩,但他为了不放过这只野鸡,遂不顾小孩死活,开枪射击,结果未打中小孩或打伤了小孩。有的主张间接故意有未遂的论者,认为这时甲应负间接故意杀人罪未遂的责任。其二,行为人在实现某种犯罪意图时,放任了另一种犯罪结果的发生。案例二:财务人员某甲贪污了大量公款,他得知上级部门近期要来查账,遂决定放火烧毁财务室以灭迹。在预定放火的当夜,有一人睡在财务室里间值班。甲知道放火可能烧死值班人,但他因急于灭迹而对值班人的死活持放任态度,放火烧毁了财务室,值班人在火起时惊醒,跳窗逃了出来。有人主张,这种案件的行为人除应负贪污、放火的刑事责任外,还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其三,行为人对他人实施伤害行为,而放任对方死亡结果的发生。案例三:被告人某丙在保外就医期间,身带尖刀外出游逛。在拦路抢走一顶军帽后,又遇见工人某丁。因丁看了他一眼,即喝令丁站住并斥问“看什么?”丁答:“我以为你在这儿住。”丙一面说:“谁在这儿住!”一面拔刀猛刺丁的腹部一刀,尔后扬长而去。丁身受重伤,被路人急送医院抢救无效,幸免于死。法院对丙以间接故意杀人未遂处理。理论上也有造成对这类案件以间接故意杀人未遂定性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上述三种案件里的行为人以间接故意杀人罪的未遂论罪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并不具有追求他人死亡这种唯一结果的心理态度,而是具有放任多种结局的心理态度。案例一和案例二里,行为人具有放任他人的死、伤、不死不伤三种结局的心理态度;案例三里,行为人具有放任他人死、伤两种结局的心理态度。从客观上看,在放任多种结果局的心理支配下的行为,不能笼统地讲就是杀害性质的行为,而要结果客观结局来确定其行为性质(例如案例一里,若根本未射中小孩,就不能讲开枪就是杀人行为);而客观结果是未造成死亡,案例一和案例二里可能是也未造成任何伤害。如果认为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对上述案件以杀人未遂定罪,那就是无视行为人主观放任心理所包含内容的多样性结局,而人为地将之限制为单一的死亡结局,并以此种错误的主观要件来认定客观行为的性质,这样定性显然不符合间接故意案件的客观事实,有悖于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要求。笔者认为,应该按实际危害结果解决上述案件的定罪问题。即在案例一里,造成死亡即定间接故意杀人;造成伤害即定间接故意伤害;未死未伤的不认为是犯罪。在案例二里,如果值班人未死未伤,行为人只对贪污、放火行为负刑事责任;如果造成值班人死亡或伤害,则同时又构成间接故意杀人或间接故意伤害,其放火行为构成的放火罪或毁坏财务罪与间接故意杀人或间接故意伤害是竞合关系,应从一重罪处断。在案例三里,仅造成伤害就定故意伤害罪;造成死亡就以间接故意杀人定罪。应当强调指出,我们主张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而按实际危害结果定罪,这决不是客观归罪,而恰恰是坚持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客观归罪是片面地甚至仅仅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而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罪过及有何罪过,因而它是主客观相脱离的;而在间接故意犯罪情况下,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对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以及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都持放任态度,即都不违背其主观意愿,这样,客观上发生死亡结果就定故意杀人罪,发生伤害结果就定故意伤害罪,当然都是主客观相一致的。
三、司法实践中的理论运用
研究刑法理论问题必须注意到它与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的密切关系。我国刑法理论界近几年才有人提出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主张,这种主张的出现与司法实践及有关立法紧密相联。具体讲,主要是近年来实践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动辄行凶、捅一刀或打一棍遂扬长而去、不计后果的案件,其中有不少无法认定为希望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杀人,而确实是对死、伤结果抱着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客观上虽然没有造成死亡结果却造成了伤害甚至终生残废的严重后果,再考虑到犯罪动机、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手段等一系列情节,某社会危害性确实相当大而应予以严惩。但是如果结合行为人间接故意的心理和实际的伤害结果定罪,就只能定为故意伤害罪。按照刑法的规定,一般的故意伤害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有期徒刑,重伤害最高也只能判七年有期徒刑,这种刑罚幅度显然过轻,不能适应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这样,有些同志就试图通过把间接故意犯罪解释为有未遂的办法弥补立法以的这一缺陷,以便将上述危害很大的情况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适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幅度予以严惩,避免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时的量刑畸轻。应该承认,这种主张的着眼点,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刑罚与犯罪危害程度相适应的需要。但是,在发现立法不能适应司法实际需要时,不是科学地指出立法缺陷以促进法律的完善,而是背离我国刑法的基本原理,把间接故意犯罪解释为存在未遂以解决量刑的需要,这种态度和研究方法是不妥的。应该指出,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注意到了故意重伤害法定刑过低的缺陷,并在1983年9月2日颁行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决定》中对之作了必要的修改,提高了情节恶劣的故意重伤害的最高法定刑。这样,对情节恶劣的间接故意致人重伤案,认定为故意重伤害就完全可以解决罪刑相适应的需要。立法的这一重要修改,也使得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主张基本上失去了解决司法实际问题的实际价值。应当充分注意到立法修改对刑法理论研究的影响。
由上可见,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主张不符合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和原理。进一步分析,这种主张的适用至少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两个弊端:首先是导致刑事责任不合理的扩大和加重。所谓扩大,是指会把本来不应为罪的未发生任何实际危害结果的间接故意认定为间接故意犯罪未遂而处以刑罚;所谓加重,是指会把本来应该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罚的间接故意犯罪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加重其刑罚。其次是会给司法实践中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人为地造成困难,并易于导致轻信口供。本来,没有造成任何法定危害后果的间接故意行为不为罪,造成伤害后果的间接故意构成故意伤害罪;而按照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的主张,前者要定为间接故意伤害未遂或杀人未遂,后者要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这样司法机关就难以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去证实行为人具有这种特定的犯罪故意及其行为具有这种特定犯罪的性质,就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根据被告人的口供定性,这样确定的案件就很难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参考文献:
1、许鹏飞《比较刑法纲要》
2、王觐《中华刑法论》
3、(孟)孟德金《苏联法总论》
第4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一、结果加重犯的行为特征
1.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但造成了结果加重。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加重结果不是由于基本行为造成的,则不成立结果加重犯。
2.行为人对基本犯罪一般持故意,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首先,行为人对基本犯罪一般持故意,但也有少数情况是对基本犯罪持过失(参见刑法第132条)。其次,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如果对加重结果没有过失,则不成立结果加重犯。其中,部分结果加重犯对结果只能是过失,如故意伤害致死,行为人对死亡只能是过失,如果对死亡结果持故意,则成立故意杀人罪。部分结果加重犯对加重结果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如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属于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结果既有可能是过失也有可能是故意。这需要根据犯罪的性质、法定刑以及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理论。
3.刑法就发生的加重结果加重了法定刑。所谓加重了法定刑,是相对于基本犯罪而言,即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高于基本犯罪的法定刑。如果刑法没有加重法定刑,结果再严重也不是结果加重犯。例如:妇女致其重伤的,由于刑法加重了法定刑,属于结果加重犯;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致其重伤的,因为刑法没有加重法定刑,故不是结果加重犯。
由于刑法对结果加重犯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故对结果加重犯只能认定为一罪,并且根据加重的法定刑量刑,既不能以数罪论处,也不能按基本犯罪的法定刑量刑。
二、加过加重犯的基本犯罪
行为人必须实施基本犯罪且该犯罪引起加重处罚的结果构成结果加重犯。因此基本犯罪是组成结果加重犯的基石。基本犯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一般认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为实害的结果犯,但是随着立法的发展,行为犯也可以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另外,危险犯也能够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但是中国刑法中,只有刑法第123条第2款规定的结果加重犯包括基本罪为危险犯的情况。
1、基本犯罪客观特征。基本犯罪的危害行为,可以说又是引起加重结果的行为,研究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是研究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基本犯罪的行为也是结果加重犯的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自然具有重要的刑法理论意义。
2基本犯罪主观特征。基本犯罪的主观特征所研究的问题是,除基本犯罪的罪过形式包括故意外,还应否包括过失。亦即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罪的罪过形式是否仅限于故意。
从理论上讲,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的罪过形式不应包括过失,亦即基本罪为过失犯的结果加重犯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理由如下:
(1)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与重结果的结果犯没有本质的区别。
(2)承认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只有在承认对加重结果既无故意又无过失的偶然的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才有理论意义。
(3)在实务上,承认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极易扩大被告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甚至将不是被告人行为引起的结果即与被告人的过失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仅有偶然联系的结果归属于被告人承担。
综上所述,中国刑法没有基本犯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三、我国刑法规定结果加重犯的具体条文
结果加重犯通常是依据分则条文规定确定的,即是法定的。常见的故意犯罪的结果加重犯,包括: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致人重伤的、死亡的;非法行医致人重伤、死亡的;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死亡的;绑架致人死亡的;拐卖妇女、儿童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放火、爆炸、投毒、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破坏电力设备等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生产销售假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生产、销售劣药后果特别严重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劫持船只、汽车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法规实施造成严重后果的;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造成被组织人重伤、死伤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客观上不能退还的;不征、少征税款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对加重的结果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过失的。常见的过失犯罪的结果加重犯,包括:危险物品肇事后果特别严重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后果特别严重的;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对加重结果一般是过失的,但是个别也有故意的,如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从表面上看,结果加重犯又构成了伤害、杀人、毁坏财物等罪,但是法律上认为是其基本罪行导致的结果,不作为独立犯罪评价,而是作为基本罪行的加重刑罚的后果,不数罪并罚。而仅仅作为加重某一罪法定刑的情况。在理论上,认为结果加重犯是实质的一罪,即一行为犯一罪。
四、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建议
第一,针对我国刑法总则部分关于结果加重犯并没有设立一般性规定而导致实践乱作一团、五花八门的状况,我国完全可以效仿那些对此在总则部分设立专门条款的国家。
第5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关键词:竞技体育;竞技比赛过失;竞训监管过失;纯粹的竞赛过失;故意的竞赛过失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2-0029-07
Abstract:Negligent injury accidents occurred in competitive sports frequently, and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crime or not, which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riminal law scholars.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is much inadequacy in the research that if the negligence behavior constitutes an offense or not. There are simple classifications on the negligent behavior in competitive sports: according to the main body, it is divided into negligence injury behavior in competitive games and supervisory negligence injury behavior in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by the subjective attitude, it is divided into willful negligent injury behavior and pure negligent injury behavior. If the competition negligence meets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criminal law, it shall be recognized as a crime; supervisory negligent injury behavior in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should be convicted as a crime in terms of the reality, law, and in theory. Pure negligence behavior shall not be characterized as a crime due to Tolerance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justifiable cause of weakened responsibility
竞技体育通过正式的比赛规则,以击败对方运动员来体现利益价值,彰显人类的体力与智力之美。竞技体育避免不了激烈的身体对抗,运动员受到身体伤害的事常有发生。针对这一情况,在建设法治社会大背景下,如何规范这一“暴力性正当业务行为”是体育立法亟需关注的事。当然,竞技体育过失行为的定性问题,既关系到体育立法的完善,也涉及到刑法中罪与非罪的界定。但由于我国刑法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还不够充分、深入,立法有所缺失,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提供明确的执法依据。
现阶段,我国关于竞技体育领域的过失行为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竞技体育中发生的严重的过失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究竟该如何界定行为性质?罪?非罪?行为实施人的主观心态该如何认定?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刑法界尚没有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论证;二,未划分竞技体育过失伤害的类型,并对每个类型应当如何认定进行详细、深入地探讨,进而确定区分罪与非罪的依据。
1 类型界定问题
对于竞技体育过失伤害行为类型的界定问题,可以从主体、行为人主观心态两个方面来考虑。按照主体划分为竞技比赛过失伤害和竞训监管过失伤害;按照行为人主观心态划分为:故意过失伤害行为和纯粹过失伤害行为。
1.1 竞技比赛过失伤害行为和竞训监管过失伤害行为
在展开探讨之前,需要明确两种行为的内涵:竞技比赛过失伤害行为指的是参赛人员在参与竞技比赛或者正规训练过程中,违反竞技规则而造成的过失伤害行为。竞训监管过失伤害则是指竞训监管中监督人、管理人等运动员之外的其他人员,因违反注意义务而引发的过失伤害行为。
就竞技比赛过失伤害行为的定义来说,其具有时间、空间、身份三种属性。从时间上来讲,过失伤害行为必须发生在比赛持续期间,比赛开始前、结束后的过失行为不在此范围。这是对过失伤害行为时间线的界定,令人不能忽视的是,时间点的问题应当如何界定。时间点有两个:一个是中场休息时间,当然通常情况下,这个时间段出现过失伤害行为的可能性较小,笔者认为中场休息时间发生过失伤害行为,因缺乏竞技体育最显著的特征――对抗性,因此它不属于竞技体育过失伤害行为范畴;另一个时间点是比赛中止或结束的哨声响起时,比如在NBA赛场上经常会出现压哨球,压哨球计不计分要根据裁判的判断,同时依靠现代技术,做出最终决定,但是最终决定也往往存有争议。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过失伤害行为属不属于体育竞赛中的过失伤害行为?又应当如何认定?笔者认为比赛中止或结束的哨声响起时发生的过失伤害行为,应当属于竞技体育过失行为范畴,即使该行为发生在哨声结束后较短的时间内,也应当看作是竞技体育行为的继续,并做出相同的判断。从空间上来说,行为发生的地点必须是赛场或者训练场上,发生在两个场地之外的过失伤害行为应按照现有刑法来界定,不涉及竞技体育过失伤害行为。此处需要强调的是训练场也属于过失伤害行为发生地,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训练场是赛场的延续,在正规的训练过程中,也具有竞技体育的特点。从身份来讲,笔者认为过失伤害行为的主体,大多数情况下是运动员自己,但是特殊情况下,也包括裁判员。比赛过程中,裁判员是中间裁判者,没有真正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身体对抗中。但是当出现裁判员出于特殊原因而放任故意的过失伤害行为,将之认定为过失伤害行为的共犯比较符合体育和刑法精神。
竞技体育中,教练员、领队等人员负有一定注意义务,他们在安排平时训练时,应综合考虑运动员的身体状况、比赛时间等多种因素,合理安排训练时间、时长和力度,以确保运动员在比赛时能够保持最佳状态,确保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如果教练、领队等人员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采取了不科学、违反人类生理规律的训练方法,造成运动员受到严重伤害甚至导致终身残疾,这就属于第一类竞训监管过失伤害行为。竞技体育中还存在第二类竞训监管过失伤害行为,竞技体育赛事的设备、场馆管理员、维修员疏于对自己监管的人员的监督、培训或者对自己监管的场馆以及设备的检查、维修,而导致发生过失伤害行为。例如,因未做好安保工作导致在大型比赛中发生踩踏事件;再例如在足球比赛中没有及时发现、更换、维修已坏掉的球门,造成运动员受伤。
1.2 纯粹过失伤害行为和故意过失伤害行为
纯粹的竞赛过失伤害行为,指的是运动员实施了符合竞技体育要求的行为,无意间给对方造成伤害,这种伤害虽不违背竞技体育精神,但却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外。故意的过失伤害行为,是运动员在没有伤害对方的心态下,故意实施违反竞技规则的行为,造成严重伤害。若故意实施违反竞技规则,又希望出现伤害结果,则属于严重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在竞技体育比赛中,这两种情况均常有发生,尤其是在需要激烈身体对抗的竞技比赛中,比如篮球、摔跤等。值得强调的是,故意的过失伤害行为从性质、危害、影响上来看,明显要比纯粹的过失伤害行为严重的多。实施故意竞赛过失伤害行为的运动员大多是为了给团队、个人争取时间或者有利的条件,又或者出于战术的安排限制对方队员的发挥,行为本身虽然违反了竞技规则,但是没有伤害故意。美国NBA篮球联赛中曾一度风靡的“砍鲨战术”①,就是一种典型的“故意过失伤害行为”,采用这种战术,运动员、教练员本质目的还是为了赢得比赛,不具有伤害故意,之所以会实施这种战术,多数是基于对自身技术的自信或者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可以避免伤害结果。
2 竞技比赛过失行为、竞训监管过失行为之刑法探讨
2.1 竞技比赛过失伤害行为犯罪化的法理依据
目前我国刑法界对犯罪的构成要件采用三要件说: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该当性即所发生的事实与刑法条文规定的内容要相一致,主要包括行为主体、危害行为、犯罪对象、危害结果、因果关系几个要素。违法性要求犯罪行为必须是违法的行为,且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即不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被害人承诺等。有责性是对实施了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行为人有非难和谴责的必要,需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犯罪故意或者过失等方面考察。另外,有责性要排除违法性认识和缺乏期待可能性两种情形。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竞技体育中过失伤害行为有符合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存在。首先,从该当性上来说,即使我国现有的刑法法典及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竞比赛过失伤害行为的具体条文,但是根据刑法原理,没有特殊法应当适用一般法,也就是说没有关于竞技体育过失犯罪条文,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对一般过失行为该当性的规定,就应当按照一般过失行为来处理。其次从违法性来说,竞技体育虽存在一定风险,但若不将那些故意实施名为“战术”实为危害行为的情形确定为违法行为,那么竞技体育就丧失了体育本质精神,容易让赛场陷入无序化。最后,从有责性来看,赛场上的运动员、裁判员显然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能力,过失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若是存在故意,那就必须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2.2 竞训监管过失行为犯罪化的依据考察
竞训监管是为了控制、降低竞技体育的风险。竞技体育活动本身具有高风险性,监督者、管理者的责任是在训练或比赛时,能确保运动员及其观众的安全。监督者、管理者没有尽到监管、管理责任,造成运动员或观众受到严重伤害,刑法应对存在监督过失、管理过失的主体依法追究其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竞训监管过失行为犯罪化的依据可以从现实依据、法律依据、理论依据三个方面展开。
2.2.1 现实依据
无数个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于体育比赛来说,监管体育设施,培训管理人员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1991年,雷丁足球俱乐部因纵容足球流氓的暴力行为而被诉至法庭。2014年,NBA联盟调查NBA球星保罗・乔治在比赛中重伤断腿事件,并最终认定是篮球架离底线太近而导致其受到伤害。1991年-2014年间,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来统计因管理、监管过失而造成的伤害事故,但却能从报纸、网络上找到大量的案例,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监管过失造成的损害后果已经相当普遍,且社会危害性严重,刑法应进行有效的规制。另外,众所周知,为了配合职业运动员大量、超乎常人承受能力的训练,体育部门或者俱乐部都会聘请专门的教练员、营养师等专业人员,来为运动员制定合理的训练计划、方式和配套的饮食,以保证运动员的身体状态。比如说NBA球星詹姆斯训练跑步用太空跑步机、布泽尔在水中训练,都是为了将训练伤害减到最小。教练员或者营养师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原因造成运动员在训练中受到伤害,也是没有尽到监管、管理责任的行为,同样要受到刑法的规制。没有刑法的保护,竞技体育参与者便如同蒙住眼睛走高空钢丝,内心的恐惧可能不在于坠落,而在于不知何时会坠落。设置刑法的初衷,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预防、为了震慑,对竞训监管来说,将竞训监管过失纳入刑法规范范围内本质的目的是为了震慑监管者、管理者,以使他们能够恪尽注意义务、监管义务,进而维护体育竞赛秩序,弘扬竞技体育精神。
2.2.2 法律依据
刑法处罚非常严厉,关系到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因此适用刑法有着严格的标准。适用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那么探讨竞训监管过失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就应当在现有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中,寻找可以适用的法律条文。
根据刑法适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竞训监管过失行为犯罪化的法律依据首先应当考虑是否有具体罪名可以适用。笔者认为,竞训监管过失行为可以适用我国刑法典第135条规定的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根据该条文规定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设置该罪的目的主要预防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中出现如踩踏事故、看台垮塌、球迷斗殴等大规模的人身伤害事故。根据条文的描述,竞技体育比赛属于大型群众性活动,竞技体育比赛中的管理者、监管者以及安检、紧急预案落实执行人员则是直接责任人员和分管的其他责任人员。若竞训监管过失行为符合此条文规定,即具有该当性,则可以适用该条文对管理者、监管者进行处罚。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只有在体育竞赛进行时才能够适用135条的情形,而前文中提到的训练场上发生的竞训监管过失行为不能够适用该条文。没有特殊法,则应当适用一般法条,即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第235条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是一般法条,也是兜底条款,它的适用范围比135条要广泛。135条没有涉及到的训练场上,因教练员、营养师的不科学的训练方式、饮食方案,致使运动员遭受到身体伤害的,应当适用233条、235条。综上,竞训监管过失行为犯罪化具有刑法的法律依据。
2.2.3 理论依据
在刑法理论上,负有义务的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自身义务,需承担刑法责任。竞训监管过失行为,属于不适当履行义务的情形。在竞技体育中,教练员、领队有管理运动员的义务,安保人员有管理、维修、养护竞技场馆、设备的义务,体育行政部门有监督竞技体育参与者的义务,俱乐部中高层管理者有监督教练、领队的义务。作为义务承担人,必须尽到注意义务,选择适当的方式履行自身义务。根据《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的规定,教练员、领队应当科学训练运动员,合理安排训练比赛的时间,确保运动员的身体健康状况。若教练员、领队没有遵守上述义务,制定了不科学训练方法,致使运动员身体受到伤害,教练员、领队则存在管理过失。体育局或体育运动队的领导应当定期听取教练员、领队的汇报,纠正其不科学的训练方法。若体育行政部门领队不及时纠正教练员、领队不科学、非人道的训练方法则存在监督过失。
3 纯粹竞赛过失伤害行为、故意竞赛过失伤害行为之刑法探讨
刑法理论上故意与过失,是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所持有的心理状态,故意是明知道自身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仍希望或者放任这一结果发生;过失则分为两种:一种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其行为的危害结果,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另一种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预见到了危害结果,出于自信认为可以避免危害结果出现。过失犯罪的处罚要比故意犯罪处罚的轻,且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予以处罚。
笔者认为纯粹的竞赛过失伤害行为,属于竞技体育自身风险,应当排除在犯罪圈之外。故意过失伤害行为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量刑中应考虑主观恶意、后果严重程度、危害影响等因素,适当减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3.1 纯粹竞赛过失伤害行为的非罪依据
3.1.1 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张明楷教授也指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刑法学家李斯特称刑法为两刃之剑。刑法是我们惩治犯罪的最有力的手段,是其他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要求了刑罚不宜广泛的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出现了其他法律不能调合的社会矛盾时才可借助其帮助实现管理目的。因此,不能一出现违背管理目的的行为就考虑使用刑罚手段予以打击,而是应该要抑制对刑法的使用。在司法环境中,我们也要考虑在“慎刑”或“少刑”的基础上做到有效预防与控制犯罪。
竞技体育以其强烈的对抗性、观赏性唤起人们心中的激情,才使得人民对其狂热。美国NBA联盟,不仅以精彩的篮球比赛吸引力全球球迷的眼球,更与其他的行业相结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产业,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市场不断完善,竞技体育行业逐渐走向成熟,促使各项竞技体育规则的完善,同时法律方面也逐渐健全,专门体育法及行政规章相继在各个国家出台。在竞技体育中,行业规则应当是规制竞技体育的主要手段,以确保竞技体育的对抗性、可观赏性。只有在超出行业规范的范围时,才考虑适用刑法。
在竞技体育领域,过多适用刑法,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首先,过失犯罪率飙升,震慑、预防效益甚微。竞技体育中,过失行为造成伤害的情形特别多,尤其是在需要身体激烈对抗的项目当中,过失伤害更不可回避。将纯粹过失伤害行为定性为犯罪,不仅会导致过失犯罪率飙升,更是会影响到刑法的权威性,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其次,掣肘竞技体育行业的发展。刑法过多参与,会严重影响到教练员的战术安排、运动员的临场发挥,进而降低竞技体育的对抗性、可观赏性,也就违背了近代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长此以往,整个竞技体育行业将无法健康发展。最后,容易矫枉过正,最终导致竞技体育行业无序化。刑法过多参与,严重排斥行业规则的适用,久而久之,行业规则就会出现过多依赖刑法的现象,竞技体育就会陷入无序化状态,更不利于体育领域行业规则的自身完善。因此,不将纯粹竞赛过失伤害行为定性为犯罪,更符合刑法谦抑性原理。
3.1.2 存在违法阻却事由――责任能力减弱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辨认能力是指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的认识能力。 控制能力是指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如果不能辨认和控制能力,即使他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比如说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杀人就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刑事责任能力减弱者,其刑事责任也要相应地适当减轻。责任能力减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辨认能力减弱或者控制能力减弱甚至两种能力均减弱,等于行为人已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或者虽能认识到但无控制能力,或既无认识也无控制能力。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通常处于责任能力减弱的状态中,这可以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得以论证。
首先,生理学角度。根据调查:篮球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需要跑5~10公里,能量消耗上,血乳酸含量可达到7~9 mmoL/L,平均有氧代谢的产能是最大耗氧量的70%,ATP-CP和糖效能供能约占总供能的85%,有氧代谢和糖效能供能占总供能的15%,同时还会大量消耗谷氨酸和Y-氨基丁酸,来保持神经中枢系统的兴奋和抵抗能量消耗带来的疲劳。
其次,心理学角度。根据德国学者莫拉卡的研究表明运动员在竞技比赛中,身体的血尿素氮、血清肌酸激酶、尿胆原等元素多少会发生变化,导致运动员注意下降、精神分散,甚至不能有效的控制自己的身体,很容易出现过失伤害。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高风险性。在强度较大或高水平比赛中,运动激烈,运动员身体极度亢奋,精神状态亢奋,心率加快,随之而来一系列心理反应,甚至会导致运动员视觉模糊、昏迷、休克等症状。
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身体、精神都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生理各数据异于普通人,心理也感到极度疲劳,此时运动员对自身行为的控辨能力都会有所下降。若还按照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要求处于极度亢奋的运动员,显然不合适。竞技体育中,暂停和中场休息时间都是为了让运动员身体和精神获得暂时的缓解和放松,避免达到极限之后给运动员身体造成伤害。纯粹的竞赛过失伤害行为并不违背竞技体育规则和体育精神,竞技体育允许这样的行为存在。笔者认为,在探讨竞技体育过失伤害行为罪与非罪问题时,不可以忽视一个大前提,即刑法是为竞技体育服务的,不是限制和阻碍竞技体育发展的,刑法的介入只能是为了惩罚犯罪,而不能广泛地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可观赏性。刑法又是最为严格、严厉的法律,适用其要格外小心注意,不满足或不完全满足犯罪的构成要件,就不能以犯罪论。纯粹的竞技体育过失伤害行为, 虽然从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上来说,其满足该当性和违法性,但并不满足有责性――因为运动员在运动中存在责任能力减弱的情况,因此应当排除在犯罪之外。
3.2 故意的竞赛过失伤害行为的定罪依据
如上所述,运动员为了给团队或个人争取时间或者有利的条件,又或者出于战术的安排,故意违反竞技规则,过失造成了其他运动员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行为。故意的竞赛过失伤害行为发生重伤、死亡的后果,应当定罪处罚,理由如下:
3.2.1 违背竞技体育规则和体育精神
刑法介入社会调整之中的前提是社会规则遭受到了破坏,且运用其他规则已经丧失了评价效益或规范能力,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适用刑法这一“恶法”来规范。在竞技体育领域里,如果有违背竞技体育规则的行为,应当首先考虑由竞技体育规则来规范,而故意竞赛过失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竞技规则的调整范围,仅用体育规则已不能完全评价行为人行为的恶劣程度。
故意竞赛过失伤害行为最重要的一个构成要件是:故意违反竞技体育规则。从行为人心理状态上来讲,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状态是故意,明知其行为违背体育竞技规则而实施。竞技体育中,为赢得比赛胜利可以适当使用战术,但是这些战术应当在尊重体育比赛规则和体育道德的前提下开展,比如遵守比赛规则、尊重对手、反对欺骗、耍花招、暴力等。而诸如篮球比赛中关键时刻为了阻止对方投篮故意打手犯规,足球比赛中为防止对方进球故意铲向对方运动员小腿……这些行为即使也被某些运动员或教练员称之为“战术”,却违背了体育规则和体育精神,应当严厉禁止这种“战术”的滋生和泛滥。
但是,这些手段虽然卑劣,却必须承认运动员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比赛,而不是伤害对方运动员,其对伤害结果持否定态度。不排除有运动员为了伤害对方运动员而恶意犯规,这属于故意犯罪的范畴,并不是故意违反规则过失伤害的行为。定罪量刑时,应当考虑行为人彼时的心理状态、危害后果,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3.2.2 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如上文所述,责任能力减弱是违法阻却事由。那么故意违反竞技规则过失伤害行为符不符合责任能力减弱条件呢?笔者之所以将纯粹过失伤害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是因为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处于一种极限的状态中,其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和辨认能力都受到了影响。而在故意违反竞技体育规则过失伤害行为中,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可能跟纯粹过失伤害行为是一致的,但是,纯粹过失伤害行为人遵守了体育规则或过失违背规则意外造成对方受伤;而故意违反竞技规则伤害行为,违背竞技规则的主观状态是故意。等于说纯粹过失伤害行为和故意违反竞技规则过失伤害行为的行为人,身体状况可能是一样的,对违反规则及造成严重后果的控制和辨认能力是不一样的。故意违反竞技规则过失伤害行为的行为人是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性质、意义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有能力予以控制――不实施,却仍实施了这种行为,认为不会对对方运动员造成任何伤害或者轻信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够轻易避免。综合考虑故意违反竞技规则行为人的心理,就不难发现其不符合责任能力减弱的条件,也就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4 余论
4.1 故意竞技过失伤害行为的误区
在定性故意竞技过失伤害行为时,非体育专业学者可能会无法理解该行为与故意犯罪之间的区别。刑法中对故意主观状态的定义是:行为人预见行为的危害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前文已有提到在竞技体育中,不排除出于伤害目的的、故意违反竞技规则的情况,此种情况即属于刑法中的故意犯罪。但是故意竞技过失伤害行为与刑法中的故意存在很大区别。区别一:故意竞技过失伤害行为发生在竞技赛场上,对其定罪量刑需要考虑竞技体育的特殊特征,如维护竞赛秩序、体育精神等,而一般故意犯罪则不需要考虑。区别二:故意犯罪中行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是希望或者放任,故意竞技过失伤害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否定态度,其故意心态仅存在于违反竞技规则。区别三:行为目的不同,故意犯罪行为人的目的是实施犯罪、达到犯罪目的,故意过失伤害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比赛或者为个人、团队争取有利条件或时间。从主观恶性上来说,前者的恶劣程度更加强烈,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因此,在量刑时,故意竞技过失伤害行为应当根据行为性质、危害结果综合考虑,适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4.2 竞技体育过失犯罪理论证据收集问题
刑法的定罪量刑需要证据,刑法上的证据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形式有书证、物证等。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众所周知,过失犯罪在司法实践当中,取证非常困难,把过失犯罪放置在竞技赛场上,取证问题无疑难上加难。由上述论证可以知道,文中可以过失犯罪定罪处罚的竞训监管过失行为和故意竞技过失伤害行为,主要定罪的依据是行为人的过失心理。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意外伤害、过失伤害、故意伤害就是取证的重点、难点,尤其是在故意违反竞技规则过失伤害行为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过失还是故意心态实难取证。但是竞技体育的优势在于,大部分重要比赛都能够实现同步录音录像,而且技术也日臻完善,这就有利于司法人员通过不断重复观看行为发生时的情况而作出判断。此外,笔者认为建立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裁判队伍,对刑事取证大有裨益。仅有这些技术手段,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刑法证据学对此做进一步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
5 结语
细化分析竞技体育领域过失犯罪,不仅丰富了我国刑法理论体系,有效地控制犯罪圈的大小,防止矫枉过正致使过失犯罪率飙升;且能够维护竞技体育现有规则,有助于竞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刑法理论界对竞技体育领域刑法理论的探讨仍需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在法学与其他刑领域的交叉地带,也需要刑法学者们跳出已有的思维框架,运用自身严谨的刑法法律逻辑思维,考证需要刑法予以规范的情形。
注释:
①砍鲨战术(hack-a-Shaq ):由小牛队前主教练老尼尔森发明,即采用犯规战术对付奥尼尔,减少“鲨鱼”投篮命中的机会。由于罚球是奥尼尔的“死穴”,所以“砍鲨”后,他虽然获得了罚球的机会,但是命中的可能性非常小。 砍鲨这个词在奥尼尔在NCAA打球时就有媒体报道。
[HT5H]参考文献:
[1] 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1.
[2]熊晓正,郑国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形成、演变与重构[J].体育科学,2007(10):90.
[3]陈兴良.正当化事由研究[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2000(3):80.
[4]王桢.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刑法规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4(4):17-22.
[5]石泉.竞技体育刑法制约论[D].长春:吉林大学,2004.
[6]王军仁.刑事责任能力的幅与度[J].法学论坛,2011(2):
[HJ2.05mm]126-132.
[7]张伟东, 熊正英, 李振斌.运动训练对优秀男子篮球运动员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4):86-90.
[8]王骏.竞技体育行为刑事正当性问题探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5):70-72.
[9]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53.
[10]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89.
[11]贾健,刘红建.论体育犯罪所侵犯的同类法益[J].体育与科学,2012(6):35-39.
[12]莫洪宪,郭玉川.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入罪问题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4):70~76.
[13]米希尔, 蒂姆, 玛丽.体育法[M].郭树理,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30.
[14]赵龙.竞技体育的刑法基础价值理念探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10):70.
[15] 陈兴良.规范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22.
[16] 韩玉胜, 沈玉忠.监督过失论略[J].法学论坛,2007(1):42-51.
第6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内容提要: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该款规定的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有人认为是八种犯罪行为。但是从文义解释、《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犯罪行为说”的弊端以及“罪名说”能满足实践需要四个方面可以证明,“罪名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立足成文刑法的特点,站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上去理解现实中存在的值得科处刑罚却不能解释到《刑法》第17 条第2 款中去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规定的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还是八种犯罪行为,学界仍不无分歧。
一、“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之争
关于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之犯罪的范围,1979 年《刑法》第14 条第2 款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条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引发了诸多质疑,主要表现在对“杀人、重伤”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含义和范围理解不一。对于前者,一种观点认为仅指故意杀人罪、故意重伤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既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重伤罪,也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重伤罪;对于后者,有学者认为是指1979 年《刑法》分则第6 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有学者认为是指1979 年《刑法》分则第2 章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6 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还有学者认为是指故意实施的相当于1979 年《刑法》第14 条第2 款列举的杀人、重伤、放火、惯窃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1]针对1979 年刑法对该款的规定失之于概括的弊病,在取消类推制度而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思想指导下,1997 年《刑法》取消了原条文中的“杀人”、“重伤”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表述,在第17 条第2 款,把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明确列出。鉴于此款生成的上述原因以及新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学界自然认为此款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八种具体犯罪(即罪名) 。[2] “罪名说”由此产生。
然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个案似乎使“罪名说”面临尴尬。①例如14 岁少女实施运输的行为,15 岁少年实施绑架人质撕票、拐卖妇女、儿童后又致其重伤、死亡行为等等,这类未成年人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主观恶性极大,情节严重,给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运输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贩卖小,而绑架人质撕票和拐卖妇女、儿童过程中又故意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重伤、死亡的社会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单纯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有学者认为对这些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仅与法理不符,也有违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和立法精神。于是,理论上有人提出:《刑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的是八种犯罪行为而不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2002 年7 月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上述疑问时作出了如下答复:“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对于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伤害行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都应负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只有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才负刑事责任,绑架撕票的,不负刑事责任。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该刑法解释性文件就是采取了“犯罪行为说”的观点,犯罪行为说由此似乎占得了优势地位。有学者对“犯罪行为说”从学理上进行了论证,认为如果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所实施的某种行为包含了《刑法》第17 条第2 款中规定的八种犯罪行为,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3]
二、“罪名说”应予坚持
“罪名说”是基于立法本义和立法精神所作的解释“, 犯罪行为说”是基于司法实践的考量所作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犯罪行为说”的观点值得商榷“, 罪名说”应予坚持。
(一) 文义解释的观点
在《刑法》第17 条第2 款“犯⋯⋯罪”的格式中,只有最后一项是完整的罪名(即“投毒罪”) 。但是从汉语习惯和法条用语上看,“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等七项犯罪应是省略了“罪”字。也就是说,该款规定的应是八种犯罪的罪名。因为在刑法用语中,“犯”一般与罪名搭配,而“实施”一般与具体行为搭配。如果该款要表明的是八种犯罪行为而不是八种犯罪(罪名) ,法条的表述应是“实施⋯⋯犯罪(或行为)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这样的话,法条所规定的就是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罪名。
也许有人会提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是存在于刑法规范中的客观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制定刑法规范时的主观意思或立法原意。文义解释的结论也许符合立法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但解释者的根本标准,是解释时的人民意志而不是刑法制定时的人民意志。如果人民意志发生变化,即立法当时的人民意志不能表现解释时的人民意志,就必须通过解释来使之变更。因此,为了使《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规定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必须对其作出扩张解释,即在现实的条件下,该款所使用的文字失之于狭隘,不足以表明刑法的真实(客观) 含义,必须扩张其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因此,宜将该款规定解释为八种具体的犯罪行为,这样,不仅使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包含了“罪名说”所主张的八种犯罪,而且扩大了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这样才符合正义的要求。
“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最终由目的解释决定取舍。”[4]因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动机(耶林的观点) 。[5]如上文所述,依据文义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和扩张解释得出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去寻找《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立法目的,只有在正确理解和领会该款立法目的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该款的真实含义。
(二)《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
在精神状况及智力正常的情况下,年龄是衡量自然人刑事责任能力有无及大小的关键因素。《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规定是为了限制已满14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这一点勿庸置疑。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但是,“刑法的目的,不只是狭义地保护法益,同时也要保障行为人的自由。换言之,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一方面是保护法益免受个人侵害,另一方面是保护法益(行为人的自由) 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4] (35)也就是说,法益保护原本就包括了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从实质上说,该款的确立是在刑法的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的指导下进行的,进一步而言,该款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妥协。
在法益保护(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折中和调和) 的指导下,还需要明确《刑法》第17 条第2款在确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负刑事责任范围时所采用的具体标准。这一点在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应对刑法中规定的危害性质明显和危害很严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6]有人认为,已满14周岁未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确定,既考虑了犯罪的严重性,又考虑了犯罪的常发性; [3] (188) 还有人认为,能列入《刑法》第17 条第2款的犯罪应当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具有强烈的反伦理性。[7]这三种观点都强调应当列入《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但是显然都认识到,鉴于这个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和认识能力的特点,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不能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于是,分别提出了第二个标准,即:危害性质明显、常发性和强烈的反伦理性。笔者认为,强调危害性质明显或者强烈的反伦理性是适宜的,因为这个标准意味着这个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应该能够认识到此类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常发性只是强调犯罪的多发性,有些犯罪如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并不具有常发性,但具有强烈的反伦理性,其危害性也易于为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所认识。如果强调犯罪的常发性,便会将这部分犯罪排除在外,显然是不妥的。
考察1979 年《刑法》第14 条第2 款的司法适用过程,也许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1979 年刑法施行过程中,就不断有一些司法解释陆续地把一些未列明的犯罪解释到1979 年《刑法》第14条第2 款规定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中去。例如,1984 年11 月14 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否负刑事责任问题的电话答复》将具有严重情节的罪纳入其中;1992 年5 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应当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将具有严重情节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纳入其中;1992 年12 月1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第3 项将盗窃数额巨大也纳入其中;1995 年4 月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备、电力煤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应否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将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备罪和破坏电力设备、易燃易爆设备罪纳入其中。这些司法解释的出台,无不显示了人权保障向社会保护的低头。1997 年《刑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引下,将1979 年《刑法》所采用的列举加概括的规定方式改为列举式,彰显了新刑法典对人权保障的强调和对司法机关随意解释的限制。
综上所述《, 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规定,既考虑到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又考虑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在这个前提下,以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强烈的反伦理性为标准确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将该款规定解释为八种犯罪,虽然不能说是详尽无疑没有缺憾,但相对于下文将要论述的“犯罪行为说”所导致的弊端,是极具合理性的。
(三)“犯罪行为说”的弊端
将《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规定解释为八种犯罪行为,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这里所说的犯罪行为是事实学或者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还是规范学或者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故意杀人的行为不一定构成故意杀人罪,如在闹市区开枪杀人是故意杀人的行为,却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也不一定构成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而是可能构成其他诸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妨碍公务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等等。相关的司法解释似乎支持这种认识,例如2003 年4 月1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的《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指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依此观点,以放火方式毁坏财物的,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以爆炸方式实施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易燃易爆设备的,分别可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在拐卖妇女过程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应定拐卖妇女罪;后迫使的应定强迫罪;故意造成被强迫的人重伤、死亡的应定强迫罪;等等。如此,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被极大地扩大了,甚至不能确定有哪些犯罪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因为一个犯罪学或者事实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可以成为很多犯罪的犯罪行为(刑法学或者规范学意义上) 。如果这样理解“犯罪行为说”,将极大地破坏《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甚至使该款的规定形同虚设。
如果将“犯罪行为说”中的犯罪行为理解为规范学或者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那么意味着《刑法》第17 条第2 款中规定的故意杀人行为将构成故意杀人罪,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将构成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因为八种犯罪行为不包括绑架行为,因此,刑法对绑架行为不予评价,但对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按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因为规范学或者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必然是具体犯罪的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说”和“罪名说”的结论将不存在差别。如此,“犯罪行为说”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可见,坚持“犯罪行为说”的结果,要么是不合理地扩大了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不当扩大处罚范围,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因而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要么是使其没有存在的必要。“犯罪行为说”的弊端也从反面证明了“罪名说”的正确。
(四)“罪名说”能够满足实践需要
为了符合正义的要求,坚持“罪名说”的观点,必须对构成要件进行合理的、实质的解释。唯此,才能基本满足司法实践中追究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强烈的反伦理性的犯罪的刑事责任的需要。
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对《刑法》第17 条第2 款所规定的八种具体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应作如下理解和适用。
1. 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已满14 周岁未满16 周岁的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一是触犯《刑法》第232 条、第234 条第2款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二是触犯法律拟制条款的情况,即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论处的情形,例如《刑法》第238 条第2 款规定:非法拘禁过程中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247、248、289、292、333 条均属此类情况;三是属于想象竞合的情况,例如以故意决水的方法杀人或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如果是已满16 周岁的人实施的,应构成决水罪和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然后按照想象竞合的情况处理,但是因为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不能构成决水罪,故只能评价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属于此类的情况还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等等。第三种情形下只有在主观上具有伤害或者杀人的故意时,才能分别以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并不是严格的具体罪名,只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犯,但这不应影响我们将该款规定认定为八种犯罪的罪名。类似的立法例见诸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 条第2 款采用的也是列举式的规定方式,其所列的20 种情形既有完整的罪名(包括这些犯罪各种危害程度不同的情形) ,如第105 条的杀人罪、第111 条的故意严重损害他人健康罪、第131 条的罪、第162条的强盗罪等;也有某些罪名的严重情形(将较轻的情形排除在外,通常表现为将较轻的量刑幅度排除在外) ,如第167 条第2 款的有加重情节的故意毁灭和损坏财产罪、第213 条第2 款和第3 款的有加重情节的流氓行为罪。[7] (737)
2. 罪。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除了可以构成《刑法》第236 条规定的罪外,对于实施《刑法》第240 条第3 项规定的奸淫被拐卖妇女的行为、《刑法》第241 条第2 款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并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刑法》第300 条第3 款规定的组织和利用会道门、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女的行为、刑法第358 条第1 款第4 项规定的后迫使的行为等,均应以罪定罪处罚。
3. 抢劫罪。《刑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的抢劫罪包括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刑法》第263 条规定的抢劫罪;二是《刑法》第269 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三是《刑法》第289 条规定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情况;四是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第四种情形需要着重作出说明。其实,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8]但是对其理由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解释:第一,抢劫罪原本就是一个小类罪名(虽然不是刑法典中明文规定的) ,其中既包括普通的抢劫罪,也包括抢劫特定对象的抢劫罪,比如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抢劫公文、证件、印章罪等,这是法条术语的客观含义可以包摄的内容。而决定这些具体的抢劫罪中哪些属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的主要标准是《刑法》第17 条第2 款的规范目的。第二,《刑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负刑事责任范围的标准是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强烈的反伦理性,因而决定了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属于该款规定的犯罪。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依“罪名说”的观点,《刑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的是八种具体犯罪,如果对抢劫罪作出如上解释,使该款中既包括具体犯罪也包括类罪,造成混乱。笔者认为,刑法解释的目的是使法律的适用更能符合法条的客观、真实含义,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法益。对抢劫罪作出如上解释既没有超出法条的客观含义,又有利于保护法益,因此具有合理性。事实上该款规定的内容并不是严格的具体罪名,例如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就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
4. 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14 条将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及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列规定,并且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说明立法者认为这几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当。《刑法》第17 条第2 款将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作为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而没有将决水罪列入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漏。但笔者认为,这个立法上的不足完全可以用合理的解释予以弥补。如前文所述,已满16 周岁的人实施决水行为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时,属于想象竞合犯的情况,应按决水罪定罪处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决水行为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时不能构成决水罪,但符合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罪的犯罪构成,完全可以按后者定罪处罚。
5. 贩卖罪。《刑法》第347 条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而第17 条第2 款只将贩卖罪作为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依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把其他犯罪列入其中。
余论
本文是基于解释论得出上述观点和结论的,也许现实中仍然存在值得科处刑罚却不能解释到《刑法》第17 条第2 款中去的行为,但这是成文刑法的特点所致,是保障自由的代价,是刑法的保护机能对保障机能的妥协。鉴于《刑法》中有许多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强烈的反伦理性但却未被规定在《刑法》第17 条第2 款中去的立法现实,从立法论的角度来考量,将来在对该款作出修改时,应该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予以扩大。
注释:
①之所以使用“似乎”一词,是因为笔者认为这种“尴尬”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可以通过对“罪名说”或者犯罪构成的解释而得到合理的解决,后文对此将有详论。
[1] 赵秉志. 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 [m]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234 - 238.
[2] 高铭暄. 刑法专论(上编) [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07.
[3] 张明楷. 刑法学[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89 - 190.
[4] 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4.
[5] [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09.
[6] 高铭暄. 刑法学原理(第1 卷)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646.
第7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重新审理等多个程序,控辩双方以及不同审判机关的主要争议点都是围绕量刑情节展开的。量刑情节是反映罪行轻重以及行为人的再犯罪可能性大小,从而影响刑罚轻重的各种情况,是选择法定刑与决定宣告刑的依据。在我国,量刑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人民法院通过正确认定和评价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依照刑事法律关于各种刑罚方法的适用权限和适用条件的规定去裁量刑罚。量刑被称为刑事正义的一半工程,和定罪同等重要,以往采取的是“估堆式”的量刑方法。[1]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呼唤“精细化”的量刑方法,因此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李飞故意杀人案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行为前、行为中、行为后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逐一分析影响该案量刑的各个情节。
一、行为前阶段
第一,构成累犯。这是本案在行为前阶段最为重要的一个法定从重情节,即被告人2006年4月14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8年1月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这一点,在各个诉讼环节控辩审三方均不存在争议。但我们也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在裁判理由中的表述是“李飞虽系累犯,但此前所犯盗窃罪的情节较轻”。我们认为,在本案中“累犯”是作为一个法定从重情节存在,其前罪与后罪并非同种罪名,因此所谓“前罪所犯情节较轻”并不能影响后罪的处罚。
第二,犯罪目的与动机。通常情况下,故意杀人罪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出于报复,有的出于贪财,有的出于,等等。[2]虽然在理论上动机并不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成立,但是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具体到该案,也是最终导致案件改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环节认为从案件的起因和性质看,该案属于民间矛盾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实际上,被告人李飞和被害人徐某某经他人介绍,曾建立恋爱关系,后因经常吵架在案发前已经分手。2008年4月至8月两人在一起只有短短四个月,很难说有深厚的感情,但同时这样短的时间也很难堆积重重矛盾,事实上被告人也主要是由于怀疑其被停止工作与被害人徐某某有关,而非因感情问题与被害人发生争吵、直至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因此我们认为,被告人性格中的鲁莽、偏执、多疑等因素是最终造成一死一伤危害结果的主要原因。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被害人无明显过错的情况下,由被告人单方挑衅所引发的矛盾是否能够认定为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民间矛盾”,关于这些问题,下文将结合有关司法解释进行深入分析。
二、行为中阶段
第一,从犯罪手段和过程看,被告人深夜破门而入,系不法行为在先,即使被害人徐某某有过激语言,也不宜认定为徐某某有过错,况且被害人已经死亡,在案没有证据显示徐某某曾经有过激语言,足以导致双方矛盾激化,仅有被告人单方的辩解不以采信。
第二,被告人对两名被害人的打击部位为头部且实施了二次打击行为(第一次击打徐某某头部20余下,后再次击打徐某某头部并致其当场死亡;击打王某某头部、双手等部位数下,后又再次击打王某某头部并致其轻伤),且作案工具为铁锤、可见被告人主观上欲将被害人置之死地。
第三,被告人对与本案无关的人——被害人徐某某的表妹王某某实施犯罪行为(受害时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年人)。
三、行为后阶段
第一,将被害人徐某某、王某某、学徒佟某的手机带离现场,虽然被告人供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被害人报警,但也在客观上妨碍了被害人打电话求救,延缓了伤者的治疗。
第二,被告人李飞的母亲梁某某代为赔偿被害人亲属4万元,但并未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从实际情况看,被告人没有进行任何赔偿,被告人的母亲梁某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期间(一审、二审均未赔偿),经法院做工作,才对被害人亲属表示同情和歉意,并筹措现金人民币4万元交到法院,代为赔偿被害人亲属,但并未获得被害人亲属谅解,也没有完全达到被害人亲属的赔偿要求。(见下表)
四、综合评价
该案的难点是“在一个犯罪人同时具备从宽情节和从严情节时如何综合全案进行处理”。法院经过重新审理后给出的改判理由是:本案系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案发后李飞的母亲梁某某在得知李飞杀人后的行踪时,主动、及时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李飞抓获归案;李飞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抓捕时,顺从归案,没有反抗行为,并在归案后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在本案审理期间,李飞的母亲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李飞虽系累犯,但此前所犯盗窃罪的情节较轻。
同时,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编纂的《刑事审判参考》在详细分析该案例时,引用的司法解释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9]217号)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
对于《纪要》,我们认为在适用时要注意大前提和小前提,前者是立法背景,后者是适用范围:一是要注意到《纪要》适用的大前提是“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该《纪要》的出台背景是当时农民间因生产生活、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内部矛盾激化为刑事犯罪的情况比较突出,审判机关从加强对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维护农村和整个社会稳定的角度所提出的一些处理原则,并不具有普适性。从该案目前能够公开查询到的材料看不出来案发地点是在农村,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也看不出是在乡务农的农民,因此不属于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范围。二是要注意到“民间矛盾”的限定范围。《纪要》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此可见,这里所说“民间矛盾”的起因一般是“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突出特点是矛盾具有双方性,即双方当事人存在利益纠结,因此,不应当任意扩大解释,如前文所述,该案的案发原因是被告人疑心单位停止其工作与被害人有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上门滋事、单方挑衅所引发的,我们认为不属于《纪要》所说的“民间矛盾”。综上所述无论是“大前提”,还是“小前提”均不具备,因此引用《纪要》作为量刑的依据欠妥。
对于《意见》,我们认为对被告人适用死刑时不能先顾及从宽情节,后顾及从严情节,而要严格按照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进行综合评价:《意见》第28条规定,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从表一、表二、表三看,被告人兼具多个从宽与从严情节,且各情节之间相互交织,不能简单的折抵,而应当考虑不同情节的地位与作用。在这里,应当充分注意到刑法典在故意杀人罪量刑上的立法原则: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立法要求司法机关在量刑时要正确区分情节严重的杀人和情节较轻的杀人,以便准确选择相应的法定刑幅度;[3]二是在法定刑顺序上,是由重到轻排列,而不是由轻到重排列。[4]这也反映出立法对于故意杀人罪在刑罚选择适用上的倾向性。具体到该案,无论是行为前,还是行为中、行为后的各个情节看,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告人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理由如下:被告人仅因怀疑其被单位停止工作与前女友徐某某有关,不分青红皂白,半夜闯入徐某某的卧室,持足以致人死亡的铁锤分别打击徐某某和王某某头部数十下,并当场造成一死一轻伤的后果。其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极为恶劣,所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且系累犯,无论从责任刑的角度还是从预防刑的角度看,都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即判处死刑。
此外,我们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应当成为犯罪分子的“免死牌”,在考虑和谐因素时要兼顾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利益诉求。因此,采取“死缓+限制减刑”的方式能否平复被害人亲属的愤怒,获得其理解,能否真正实现“案结事了”,需要个案考量:在充分赔偿并获得被害人亲属谅解的情况下自然无可厚非,反之,即使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看,也不应过度考虑被告人亲属的感受,而忽视被害人亲属的感受,毕竟,被害人亲属已经承受了亲人被犯罪行为致死的伤痛,如果“报应心理”得不到充分的照顾和释放,必将成为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该案暴露出来指导性案例的一个缺陷,即片面追求言简意赅而使得一些看似可有可无,但仔细推敲后却有可能影响量刑的情节在指导性案例的叙述中反映不出来,案情描述过于简单,这使得指导性案例对司法实务部门的指导、借鉴意义大打折扣。其实,“‘相同’是从来没有真正有的……在真实里,永远只有或多或少,较大的相似性及不相似性。”[5]因此作为比较基准——指导性案例,其基本案情、裁判要点、裁判理由的表述必须精准,才能便于司法人员在适用时得出准确的比较结论。但鉴于指导性案例本身篇幅不可能太长,因此我们建议司法机关在指导性案例的同时,能够以适当方式公布详细案情、诉讼过程、办案效果,[6]以便于司法人员和社会公众能够综合全案作出准确合理的判断。
注释:
[1]参见杜飞进等:《为了公正高效和权威——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载《人民日报》2012年9月28日、10月1日。
[2]参见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410页。
[3]根据司法实践,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主要有手段残忍的杀人、不计后果的杀人、后果严重的杀人等;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主要有当场基于义愤的杀人、因被害人长期迫害的杀人、机遇被害人请求的杀人,以及“大义灭亲”的杀人等。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757页。
[4]同注[2],第411页。
第8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死刑的适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死刑又是一种无法补救的刑罚,即使是冤错一件、一人,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的后果,带来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我们认识到审理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应当慎之又慎,绝对不能容许出任何差错。在死刑案件的二审和复核过程中,严把死刑案件的质量关。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人,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论罪不应当判处死刑或者虽然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是可不立即执行死刑的案件和犯罪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坚决地发回重审或者改判。
经过分析,发回重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此外,有个别案件因原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侯,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改判的原因比较复杂,经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排除或者阻却了死刑的适用:一是根据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和社会危害程度,论罪不应当判处死刑,而一审判决犯罪人死刑。二审严格把握死刑的裁量标准,予以改判。二是犯罪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或者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当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没有予以认定,或者虽然认定,但没有对犯罪人从轻处罚的。这里包括从犯、自首、重大立功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和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后又积极实施救治被害人的、归案后认罪态度好以及犯罪人属限定责任能力的人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三是一审判决定罪不当而导致适用死刑不当,而予以改判的。四是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犯罪,但是,要判处犯罪人死刑,证据尚有缺陷或者说证据存在瑕疵,致使对犯罪人适用死刑下不了决心;并且,发回重审也无法补充新的证据,为了慎重,在裁量刑罚时留有余地而予以改判的。
通过对死刑案件改判、发回的原因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严格适用死刑,就必须明确适用死刑的标准。否则,就谈不上严格适用死刑。而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准确把握适用死刑的标准的问题。
关于适用死刑的标准,刑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笔者认为,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通过对犯罪分子的主观动机、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结果的考察之后作出的判断,通常理解为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三者的统一。主要是指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才能适用死刑。为了保证只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适用死刑,刑法分则在规定死刑的犯罪中,对于适用死刑的情节都作了明确、严格的限制。如,危害公家安全的犯罪必须是“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适用死刑;又如,重大刑事犯罪中,只有“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等等。除了总则和分则对死刑所作的明确、严格的规定之外,刑法在总则中还规定了若干从轻处罚的情节,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这些从轻处罚的情节适用于刑法分则中的任何犯罪以及任何的犯罪人。因此,又从另一方面对死刑的适用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刑法规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是指犯罪人只要存在这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便应当毫无例外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人,只要存在这种情节,首先就应当排除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另一类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是指犯罪人只要具备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便应对犯罪人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就是说,犯罪人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由于存在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也有排除适用死刑的可能性。
除了刑法明确规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之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影响法官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的情节,俗称为“裁判情节”或“酌定处罚的情节”。这主要的有因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或者因被害人的严重过错引起的刑事案件等。案件的起因是复杂的,这要求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于具有可以排除或阻却适用死刑的情节时,对犯罪人就不适用死刑。
二、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刑事诉讼证据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证据的客观性。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第二,证据的相关性。证据的相关性又称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存在某种联系,正是因为证据与案件之间存在的联系,才能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际意义。第三,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为了从重从快的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人们在“严打”斗争中摸索出“两个基本”的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从分”。“两个基本”的原则的适用,对于排除枝节情节的干扰,快速审理大批刑事案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两个基本”的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和赞同。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死刑是一种无法补救的刑罚,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的马虎。任何一点粗心大意、任何一点的疏忽,都可能酿成错案、冤案。因此,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应当树立“铁案”意识,把审理核准的每一件死刑案件都办成“铁案”。为了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两个基本”的要求,而是应当“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我们就应当认真、严格的审查案件的事实、证据:必须认真审阅全部案件的卷宗材料,认真查找案件存在的疑点和问题;必须提审被告人,耐心听取被告人的辩解和要求,从中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必须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案件的事实、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必须到发案地,认真核实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客观真实,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必须查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法庭调查、质证。通过认真细致的审核,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决不放过任何影响案件的蛛丝马迹。在查清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之上,再依照刑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准确地评判。如果案件存在无法解释的疑点,决不草率下判。
三、常见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
(一)故意杀人案件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一种侵犯公民生命权利的严重犯罪,是所有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危害程度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刑法分则对故意杀人罪规定了最为严厉的刑罚。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规定的刑法分则中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排列顺序,一般都是按照由轻刑到重刑排列。但是,对于故意杀人罪,法定刑的排序则是由重刑到轻刑排列。即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首选法定刑是适用死刑,体现刑法对故意杀人这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案件从重打击的方针。犯故意杀人罪只是在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考虑排除适用死刑。因此,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的数量在所有犯罪中一直占第一位。
但是,并非所有的故意杀人案件都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案件,特别是因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或者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这些案件虽然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案件的起因不同,犯罪动机的卑劣程度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不一样,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适用刑罚时就同样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适用死刑一定要慎重。也就是说,对于故意杀人的犯罪人是否适用死刑,不能单纯从是否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上考虑。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据有关统计,由于民间纠纷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的死刑案件,一直占全部故意杀人犯罪死刑案件的60%左右,占所有死刑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这类故意杀人犯罪案件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些是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案件。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故意杀人案件的情节、后果、手段一般,其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因此,对这一类案件适用死刑一定要慎之又慎,要与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有所区别。如刘某故意杀人案:犯罪人刘某夫妇与被害人夫妇都在农贸市场卖肉,一天,有顾客来买排骨,刘某的妻子因自己摊上的排骨已卖完,便介绍左边摊主卖给顾客。被害人之妻因此降低价格叫卖,但顾客嫌被害人摊上的排骨不好,仍然买了左边摊位上的排骨。为此,被害人的妻子指责刘某的妻子,继而发生争吵、厮打,二人均受轻微伤。被人拉开后,被害人的妻子将刘家摊位上的猪肉全部掀到地上。市场治安科明确“各自看各自的伤,最后凭法医鉴定结果再行处理”。但是被害人夫妇拒绝接受调解,在当天和次日强迫刘某拿出360元给被害人的妻子看病,并殴打了刘某夫妇。刘某多次找公安机关反映请求解决,并拒绝了被害人“私了”的要求。被害人得知刘找公安机关后,扬言“黑道白道都不怕,不给我媳妇看好病绝不罢休。”第三天下午,被害人夫妇又逼迫刘某雇车随被害人夫妇到医院拍片检查,结果无异常。被害人仍然继续纠缠。刘某恼怒,掏出随身携带的剔骨刀将被害人杀死、将被害人的妻子杀成重伤。然后自杀未遂。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本应判处死刑。但由于本案事出有因,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和矛盾的激化有一定的过错,并有悔罪表现,因此判决刘某死刑缓期执行。一审判决后,刘某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以刘某在公共场所有预谋的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理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认为,被害人一方虽然有一定过错,但是刘某用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报复被害人在民事纠纷中的过错,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检察机关抗诉有理。决定撤销原判,认定刘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报请最高法院核准。最高法院经复核认为,刘某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严重后果,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情节严重,并且没有任何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是,刘某并不是属于那种罪行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犯罪人:一、从案件的起因看,是因生产中的纠纷没有及时处理好而使矛盾激化引发持刀杀人,这种起因不属于泄愤报复;二、从案件矛盾发展过程上看,被害人一方殴打刘某、多次逼迫刘拿钱看病、当刘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后又对刘威胁,对引起矛盾的激化有严重过错,刘因此而作案与无端杀人的案件有区别;三、有关机关没有及时处理并保护刘某免受被害人的欺负,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有一定的责任。基于以上原因,一审判决对刘某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无不当,不属于判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失当。最高法院决定撤销二审判决,判处刘某死刑缓期执行。从对上述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到,第一、案件的起因和被害人的严重过错是排除和阻却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重要情节;第二、死刑缓期执行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构成“量刑畸轻”。又如,商某故意杀人案。犯罪人商某的丈夫无端怀疑自己的孩子是商某与他人所生,经常打骂被告人,从而导致夫妻矛盾激化。商某乘丈夫不备将丈夫杀害。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二审认为,犯罪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是,考虑到本起案件是因家庭纠纷引起的;同时,考虑到案件的起因,是由于被害人心胸狭隘,无端怀疑并经常打骂被告人,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具有较严重的过错。因此,虽然依法应对犯罪人适用死刑,但不必立即执行,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审理故意杀人案件时,要严格区分直接故意杀人和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虽然都是故意杀人,但是由于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人在主观上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因而主观恶性大。而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人在主观上并不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而是对被害人的死亡采取的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相对于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小一些。所以,在刑罚的裁量上应当有所区别。如严某故意杀人案,犯罪人严某与被害人发生口角纠纷后,在十分气愤情绪下,不顾被害人在车前阻拦,驾驶汽车以每小时15.36千米的速度行驶,导致被害人被车推行十余米后被扎死。作案后,严某投案。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人严某犯故意杀人罪,依法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投案自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审认为,本案犯罪人明知被害人在拦车的情况下,驾驶汽车向前行驶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仍然驾车向前行驶,导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间接故意。虽然,对犯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人,刑法规定首先考虑死刑,也就是说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是,鉴于犯罪人具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同时,基于该案是因家庭纠纷引起的;犯罪人在主观上又是属于间接故意心理态度,因而依法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死刑缓期执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法,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这在理论界或司法界都是没有歧义的。因此,我们在考虑死刑的裁量时,适用死刑缓期执行时,不需要有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换言之,如果犯罪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时候,法官就应当考虑排除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正是因为如此,法官在考虑上述案件的处罚时,鉴于犯罪人具有一个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和两个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对其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二)故意伤害案件
故意伤害犯罪与故意杀人罪比较,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要小。但是,由于故意伤害犯罪特别是重伤害犯罪也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暴力性犯罪,历来也是适用死刑较多的犯罪。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或者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据此,犯故意伤害罪适用死刑有两种情况,一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二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1、关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在处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的时候,要严格区分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一是要严格区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故意犯罪,都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情况下,犯罪人主观方面只有伤害的故意。对于致人死亡的结果,不是犯罪人在主观上予以追求或者放任的的结果。因此,致人死亡的结果是犯罪人过失所致。而直接故意杀人,犯罪人在主观方面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并积极追求死亡的结果发生。二是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二者的共同点,也都是故意犯罪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二者的区别在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只有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对于他人死亡的结果,既不希望、也没有放任,是一种过失的心理状态。而间接故意杀人,犯罪人不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而且对死亡结果的发生采取放任的心理态度。三是要正确理解立法者制定刑法时的立法本意。根据刑法的规定,虽然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都是故意犯罪,刑法规定的最高的刑罚都是死刑。但是,正是由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不同,从而社会危险性的程度也不同。因此,立法者对这二种犯罪的处罚的严厉程度也大相径庭。表现在刑法规定刑罚的顺序上的不同。故意伤害罪,刑法是从轻刑向重刑的排列顺序规定刑罚的;而故意杀人罪,刑法规定首先考虑死刑,并以从重刑到轻刑的排列顺序规定刑罚。法律规定表明,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适用死刑,从立法的精神看,只有对那些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适用死刑。如赵某故意伤害案,犯罪人赵某酒后好打人骂人,一天,赵某在同村村民沈某家喝了大量白酒后回家。其母亲见其酒喝多了,责怪赵某不该喝酒。赵某恼怒将自己家里的木椅打坏。其母亲便拿着坏椅子找到沈某,指责沈不应该给赵喝酒。赵认为母亲使其没有面子,待其母回到家后,赵不顾他人的劝阻,对母亲拳打脚踢。赵某被人拉开,母亲离去后,又追上前对母亲拳打脚踢,致其母脾脏破裂,因大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法院认定赵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二审认为,赵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但是,考虑到本案是因家庭纠纷引起,赵某酒后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等情节,对赵某不必立即执行死刑。因而改判赵某死刑缓期执行。
2、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应当注意的是,在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时候,既不能仅仅看犯罪人的行为是否致人重伤,也不能仅仅看其行为是否特别残忍或者仅仅看是否造成严重残疾。而是应当将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和造成严重残疾者三者联系起来,只有在同时具备这三种情形时,才能对犯罪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否则,将会扩大打击面,有违立法本意。
关于故意伤害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加以规定,在一定的时期造成处理此类案件的标准的不统一。最高法院1999年召开的济南会议上,确定统一参照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来认定故意伤害是否造成“严重残疾”。“工伤标准”将残疾分为十级。其中的一、二级为特别严重残疾;三至六级为严重残疾;七至十级为一般残疾。因此,参照“工伤标准”一至六级伤残为“严重残疾”,主要表现为被害人身体器官大部分缺损、器官明显畸形、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造成严重并发症等等。
关于特别残忍手段。在故意伤害犯罪中,不是对所有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犯罪人都可以适用死刑。根据刑罚234条第2款的规定,具有特别残忍手段是对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犯罪人适用死刑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什么是特别残忍手段?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在刑法学界的学术著作中也不多见。根据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用凶器划割他人面部,致人容貌毁损;用浓硫酸、硝镪水泼洒在他人面部,致人容貌毁损;挖掉双眼;砍断双腿;挑断脚筋;持利器刺、割他人数十刀;用钝器打、砸他人,致人多处骨折、损伤等等。当然,具体案件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具体的特别残忍手段也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需要在审判实践中,通过考察犯罪人故意伤害他人的手段是否凶狠毒辣以及严重程度加以判断确定。
(三)抢劫犯罪案件
第9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论文关键词 聚众犯罪 转化犯 刑法
一、转化犯的概念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上看,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人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者转化为更加严重的犯罪,从而应当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或者应当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情形。”?其中也就包括非罪向罪的转化。例如:根据《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有关于转化型抢劫的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269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标准的;(2)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而司法实践上,由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大量存在非罪行为转化为犯罪的情形。
关于转化犯的特征,也有多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转化犯应当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转化犯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类型或者形态。转化犯是以特定的法律表述形式,规定本条的犯罪必须依照另一条文的犯罪定罪处罚,转化犯必须由法律特别规定是其得以成立的外部条件。二是转化范围的特定性。即转化犯是非罪(一般违法行为)向罪的转化,此罪向彼罪的转化,轻罪向重罪的转化。三是转化条件的法定性。转化犯的成立是以特定的条件为基础的,罪向非罪的转化、此罪向彼罪的转化都必须具备法律明文规定的条件。”
二、聚众犯罪中的转化犯
关于聚众犯罪的转化犯,有学者认为,“罪数判断标准是构成要件标准说,即确定罪数的标准应当是所符合的犯罪构成的个数。行为人的犯罪事实符合一个犯罪构成为一罪,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为数罪。在聚众犯罪中,行为人在实施聚众危害行为的同时,又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符合两个以上犯罪构成的,应当以数罪进行并罚,但是如果其他犯罪行为与聚众犯罪之间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或者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构成聚众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牵连犯,应当按照牵连犯择一重罪处断。”?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出现的典型聚众犯罪的转化犯有第289条规定的“聚众‘’”行为和292条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的转化问题。
(一)聚众“”的转化犯
我国《刑法》将聚众“”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本条并没有规定为一个单独的罪名,对于“”行为具体罪名的认定,需要依照行为人实施的具体行为的具体后果分别确定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是抢劫罪。从其实质来看,上述立法属于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转化犯的一个典型规定,由聚众“”行为向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成立转化犯,属于从一种罪向另一种罪的转化。所谓聚众“”,是指首要分子聚集多人,实施“打、砸、抢”的行为。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聚众”,即就是首要分子聚集多人实施的行为;二是具有“”的客观行为,即行为人针对人或者财物实施的暴力殴打、抢劫财物、毁坏财物等行为,此时对“”行为不单独定罪,而是以行为人在聚众“”中造成的后果予以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1.聚众“”致人伤残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在聚众“”中是否包含致人轻伤的情形。根据《刑法》第289条规定“致人伤残的”依照《刑法》第234条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根据2002年12月1日公安部颁布的《交通伤残等级鉴定标准》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损伤所致的人体残废包括:精神的、生理功能的和解剖结构的异常及其导致的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能力不同程度丧失。”并根据不同的伤残情况评委为一至十级。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对于故意伤害轻伤案件,仅作法医学鉴定;而只有对以经法医鉴定为重伤的,才要求出具相关的伤残等级鉴定。故一般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致人伤残的”一般仅指致人重伤的才构成。
所以笔者认为,从转化犯具有的轻罪向重罪转化的趋重性特征上看,在聚众“”中致他人轻伤的行为不应当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因为故意伤害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聚众“”的行为无论是触犯了《刑法》第290、291条规定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还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交通秩序罪,其法定刑都和故意伤害规定的法定刑相当,甚至更重,此时,以故意伤害对其行为进行处罚并不符合聚众犯罪中转化犯趋重性的特征,也利于准确、有效的打击犯罪。所以,对于聚众犯罪中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情形不应直接转化为故意伤害罪,而是应当优先考虑以其他的聚众性犯罪予以定罪量刑;只有在其行为不符合其他聚众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情形下,才可以直接根据《刑法》第234规定以故意伤害(轻伤)对该行为定罪量刑。
2.聚众“”中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问题分析
这里的核心问题涉及聚众毁坏财物时是否转化为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时是否转化为聚众哄抢罪、聚众犯罪时是否对一般的参与人员进行处罚。根据《刑法》第289条规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对于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263条以抢劫罪定罪量刑。但笔者认为,对于聚众“”中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时,可以直接根据《刑法》第275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量刑,因为对于聚众“”中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由于行为人实施该行为时更多的是一种发泄,并没有“非法占为己有”的主观目的,此时如果转化为抢劫罪,并不符合抢劫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方面的犯罪构成,所以一概以上述规定处理并不符合我国的刑法理论。
对于聚众“”中抢走公私财物的行为,虽然有学者认为应当根据《刑法》第268条规定的“聚众哄抢罪”定罪量刑。但笔者认为,由于“聚众哄抢罪”财物和故意毁坏财物两者之间在主观目的上截然不同,聚众哄抢财物行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该行为也同时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而由于聚众哄抢财物罪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0年,而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则最高则可以判处死刑,所以根据转化犯具有的轻罪向重罪转化的趋重性特征上看,为严厉打击该类犯罪中其组织、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对于该类行为应适用《刑法》第263条的规定转化为抢劫罪。同时,上述条文中明确规定只有“首要分子”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对于一般参与人员,并不适用相应的转化犯的规定,此时,可以直接适用《刑法》第268条规定的“聚众哄抢罪”定罪量刑。
(二)聚众斗殴罪的转化犯
我国《刑法》第292条第2款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界一般认为“这是一种转化犯的立法例,是最为典型的聚众犯罪的转化犯。”
1.聚众斗殴罪转化犯的条件
本罪规定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最高法定刑为有期徒刑10年。一般认为,所谓“聚众斗殴”,是指双方或者多方人数均在三人以上以暴力手段的相互攻击人身的行为,聚众斗殴罪本身包含了致人轻伤的结果。但是,在当聚众斗殴罪中实施了暴力致人重伤或死亡等超出正常的“聚众斗殴”的范畴时,由于该罪和故意伤害(重伤)、故意杀人罪中的主观上具有对他人身体进行伤害的主观故意,但其行为的结果和危害程度已经超出了聚众斗殴罪所能涵盖的范围,造成了致人重伤或死亡危害结果,此时构成聚众斗殴转化犯的前提条件。
- 上一篇:关于学生会的述职报告范文
- 下一篇:安全作业管理的重要性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