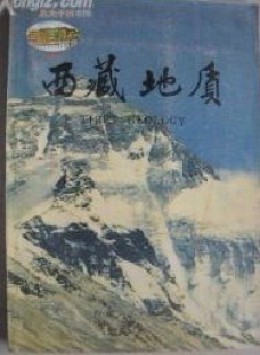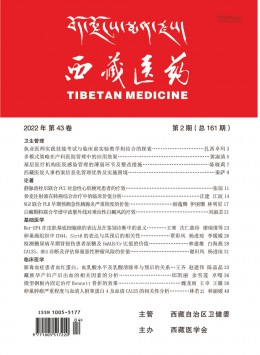西藏茶文化探析

西藏传统社会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政治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嘎•洛桑赤列(1981)认为,政治利益的角逐直接反映着宗教教派利益的冲突,宗教教派间的矛盾也体现着对政治领导权的争夺。因此,研究茶在西藏治理中的功能,应该至少涉及宗教与政治的多个方面。实际上,茶在西藏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与其在西藏传统生活世界中发挥的功能是紧密相关的,有研究者“通过‘茶’在藏族生活中的语言学地位证实茶在藏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2]。因此,我们假设:在生活世界中实现的作为文化的社会凝聚功能成为茶在治理中功能发挥的基础,也是重要体现,而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又成为其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功能升华。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
宗教政治传承中的茶
宗教政治的传承有一个相互衔接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有多种因素介入,其中包含有茶的内容。最主要的是法主身边的“司茶侍从”常常会被选入宗教政治系统核心集团之中。在帕竹噶举的传承中涉及了在法主身边司茶的侍从。当时因帕竹一系在康、藏都有众多僧众,即使一些小事务,上师都需要亲自处理,护持两部法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帕竹的僧众提议应有一人主持事务。后与法主请示,提议一位曾在法主身边任司茶侍从的人担任,法主同意,命此人担任法座,即后来的京俄法主(京俄意为眼前),是朗氏家族第一个由知事僧人担任帕竹法座的人。①在地区的治理中,有万户长一职,对万户长的选择是格外重要的。京俄曾有一位司茶侍从担任过洛扎雪寺的堪布,被称为堪布仁钦坚赞,担任过万户长。期间,一个名叫多吉贝的人被委派为司茶侍从,大小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被京俄派到内地办事后,得到皇帝和上师的喜爱,赐给他世代管领帕竹万户的权利。他返回乌斯藏后于阳木虎年修建了雅隆南杰和乃赤康,并担任万户长13年。在香巴噶举历史中,相传穹波南交功德无量,他广收门徒弟子,智慧空行母普贤女前来赞颂道:“你的门徒最终达到八万,你最后的弟子为六人,你最终享寿一百五十,你最后升入极乐净土。”于是,穹波南交在10日上午宣布召开大法会,召集了所有弟子门徒,熬茶布施。在法会上他交代了诸多身后事宜,对6大弟子寄予厚望,强调弟子们要团结一致,服从6人的领导。[3](P323-325)在诸如此类的法会上,“熬茶布施”是必须的环节,平时的说法法会也必然有此环节。在说法时,听法僧众都以锦缎为坐垫,每次法会时大量煮茶,一般在五十大包以上。因此寺院中的用茶量也以法会期间最盛。《颇罗鼐传》记载,颇罗鼐晚上梦见一位白脸的妇女告诉他,天亮后早动身行程,路上见着吃的,不管好坏全都掺起来,自己要吃,也要给别人吃,这样缘分才好,否则不会有什么好运气。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一个少女提着一桶牛奶走来,颇罗鼐依梦中的指示,把牛奶据为己有,然后随从拿来一箱好茶,搅到牛奶里去,屯氏首领的奴仆拿来盐巴也掺了进去……总之凡是吃的都掺到一起。颇罗鼐先喝了三碗,屯氏、江洛坚巴、白策巴、白席巴、嘉康巴、吉甫唐巴等人也喝了下去。喝过这种混合物的人都很富贵,当时没喝的后来遭遇到了不幸。因此,传记中写道:“像这样的因缘,真是命中注定的。”[4](P201)通过这段记载可以发现,在颇罗鼐逐步走向宗教政治的核心领域过程中,“天赋神眷”的宗教政治观发挥着一定作用。梦境传达了神的意旨,而颇罗鼐很好地遵奉并实行了意旨,从而保证了他以后的大有作为,得到神佛保佑。而分析梦的实现过程发现,除了“一箱好茶”之外,其他见到的可吃之物,包括牛奶、狗的剩食、野牛角里的酒、吃剩的碎野驴肉、刚死去老狗的肋骨均非颇罗鼐随身携带之物。茶是颇罗鼐出行携带之物,而且数量较大(一次就用掉一箱),一方面表明当时茶叶对社会上层出行的重要性,包括对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两个层面;另一方面通过“天赋神眷”,表明茶已经成为神旨的一部分,由于颇罗鼐出行随身带有大量的茶,因此,即使没有其他可吃之物,茶也必在其中。无论是纯粹的宗教内部的上下传承,还是政治系统管理人员上下传承(如万户长),亦或是召开各种各样的法会都涉及西藏自身茶文化的内容,这种文化摆脱了纯粹的文化形式,上升至一种宗教与政治的判断、识别和传达精神意旨的重要手段(政治的与宗教的),这种手段进一步交织运用(即把政治与宗教相结合)即发展成为整合社会治理的社会外在强制力,而超越个人的命令或意志。这一作用长期以来在西藏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宗教活动形式出现的“入藏熬茶”现象中蕴含的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交叉意义深刻阐释了这一作用。
入藏熬茶
“熬茶”也称“熬广茶”,是藏、蒙古、土、纳西等信仰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各民族的一项宗教活动,是到寺院礼佛布施的俗称。主要流行于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与茶有着密切的联系,酥油茶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日用品,而藏传佛教则成为推动西藏茶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5]“入藏熬茶”约起源于16世纪末,随格鲁派在蒙古地区传播而渐盛,早期常与西藏教派斗争、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入藏熬茶”者人数不等,少则十几人,多者数百,甚至上千人。布施物品有各种牲畜、金银、绸缎、茶叶、各种工艺品等。清政府统一西北后,封建主入藏熬茶现象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10人以上要有请票程序,由驻藏大臣给予执照方可以实行。“入藏熬茶”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成为西藏之外藏传佛教信徒与西藏藏传佛教相互联系、有机互动的重要文化力量。这种宗教文化现象以“熬茶”为名,表明了茶事活动在藏传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信徒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成为重要的宗教仪式。另外“,入藏熬茶”也成为一种政治角逐的手段。噶尔丹策零曾多次请求“入藏熬茶”,被清政府拒绝,期间双方多次发生战争。吕文利、张蕊在《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一文中详细考证了有关细节,认为其中都有一定的政治意图。尤其对清政府而言,既把握了噶尔丹策零的政治意图,又对其展示了权威,同时也进一步笼络了僧俗领袖,增强了其归属感。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通过“入藏熬茶”也增加了西藏与其他省份的贸易往来,对推进经济互动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乾隆八年(1743),噶尔丹策零多次命人向颇罗鼐刺探,试图拉拢。十一月,策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试图探听颇罗鼐振兴黄教(藏传佛教的格鲁派)经验,被拒。接着又提出:准噶尔地方无好额木齐(医生),噶尔丹策零吩咐他们来藏熬茶事毕,将好额木齐与通经典之大喇嘛延请一位带回。对此,颇罗鼐答道:“汝等欲请好额木齐与通典大喇嘛,并未奏请大皇帝谕旨,此事我何敢专主?”(《清高宗实录》)。噶尔丹策零,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借熬茶事由,其他部族力量会向清中央政府提出一些请求。此次是噶尔丹策零请求派遣好的医生和僧侣(喇嘛),但颇罗鼐非常坚决地予以回绝。这是一种政治手段,即传达一种信息: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一切事务具有绝对权威。颇罗鼐诸如此类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树立与维护非常多。清中央政府对此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清高宗实录》中多处记载了相关情况。乾隆九年(1744)元月,在给颇罗鼐的谕旨中曾褒奖颇罗鼐在对待“准噶尔之人入藏熬茶”中所采取的恰当措施“,甚属可嘉”。清政府的嘉奖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准噶尔入藏熬茶者在临别的时候表达恭顺且兵戈永息之意,“群生亦皆乐业”,并诚恳表达了“结信于大皇帝”之愿望。颇罗鼐在此时再次传递了清中央政府的无尚权威,“大皇帝包容四海”,对待各方各族均一视同仁,对来熬茶者格外加恩,赏马驼、路费等等诸多信息。
赐茶
传统社会中西藏治理的路径是众多而复杂的,除了以上分析的形式外,还有一种最为直接的“政治对宗教的治理术”,即运用赐茶方式来加深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间的联系与纽带。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清朝统治者在与蒙藏上层人物的政治互动中,茶叶成为赏赐和馈赠的重要物品,也就是成为了恩威并施政治手腕中的“恩施”内容。茶往往比金银和其他财物更具有重要意义。明朝实行“群封众建”、“宽容优抚”的政策,对藏传佛教各派领袖进行分封,允许他们按级别定期朝贡,并给以高于朝贡的赏赐。进贡的物品包括铜佛、铜塔、犀角、珊瑚、左髻、毛缨、刀剑之类。朝廷赐给黄金、白金、锦帛、法器、鞍马、茶、米等物。这一政策对藏族地区大小僧侣领袖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通过贡赏得到了丰厚的经济赏赐,也维系和加强了自身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有利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明史•西域传》记载了噶玛巴第五世黑帽派活佛于1406年朝贡时,享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币四十五表里,法器、茵褥、鞍马、香果、茶米诸物毕备。”[6]1408年,明朝遣使来迎请格鲁派领袖宗喀巴,赏赐各色丝绸、彩绫、水晶念珠、金刚杵、茶叶等近二十种物品。这种“厚往薄来”的治理政策刺激了西藏寺院僧侣与内地的联系。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入贡不过三四十人,景泰年间(1450-1457)增到300人,到天顺年间(1457-1464)猛增至二三千人,每年朝贡二三次。弘治年间(1488-1505),朝贡人数剧增,入贡者一次多达三千八百余人;嘉靖十五年正月(1536年2月)一次最多达四千一百七十余人。除有名望的僧侣朝贡外,寺院也组织僧团朝贡,从而获取赏赐。《明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麦思奔寺(哲蚌寺)朝贡;景泰二年(1451年)些腊寺(色拉寺)朝贡;成化六年(1470年)葛丹寺(甘丹寺)朝贡;成化十六年(1480年)扎矢论卜寺(扎什伦布寺)朝贡。每次朝贡都是带着丰厚的赏赐而归。《明代宗实录》载:景泰年间藏僧“贷买和茶至万数千斤及铜、锡、磁、铁等器用”[7]。通过朝贡争取到了明朝政府的恩赐,为寺院提供了物质保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寺院经济的发展。清政府时期,继续推行厚赏政策。《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记:1653年2月18日赏赐50两金制茶桶两个、金盆两个、银茶筒八个、白银一万两等。1674年,康熙皇帝在赏赐五世达赖的物品中有重达135两的金曼陀罗、百两重的金锭、银茶筒和元宝410两等。康熙皇帝曾规定由打箭炉税收项下,每年拨给达赖喇嘛白银5000两,拨班禅茶叶50大包。
《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西传》中也有相关记载。作为历世班禅中第一位进京向皇帝祝寿的班禅喇嘛,六世班禅巴丹益希在进京前的1748年10月,皇帝遣使臣送了大量资费,包括:诵经费黄金29两2钱,僧茶费白银1000两。僧茶费成为皇帝特别关注的重要资费,并且数额巨大。这些表现了当时的几种社会现象:一是茶在西藏高层僧侣中极为重要;二是“僧茶费”已经成为一种僧侣日常消费的代称;三是清政府对西藏寺院与僧侣的用茶极为重视。雍正二年(1724),鉴于达赖喇嘛每年派人到打箭炉,沿途征收“鞍子钱”,清政府决定每年赏赐给达赖茶叶五千斤、班禅二千五百斤,每年由打箭炉拨运,此外并给运费银二百两。这些茶由边茶商人采办,实际约为5000斤至15000斤。这些赏赐大大超过达赖于各地所收的“鞍子钱”,同时要求达赖停止在上述地区征收“鞍子钱”。赐给达赖、班禅的茶叶称为“赏需茶”,每年由边茶商人采办。《雅安县志•盐茶》中记载:“赏需茶单年三百包、双年二百包,由道署领价。赏给达赖喇嘛茶七十五包,包重五十斤,除折扣核减,实领银三百四十五两,另由地丁坐支。”每当清政府举行各项大典及蒙藏上层朝贡时,茶叶常常是重要的赏赐品。历代清帝逝世、西藏各大寺庙大做法事,清政府则赐以大量茶叶等赏项。如雍正帝逝世时“,颁赏三大寺熬茶银三千两、大小哈达各三百根,茶八百甑。其余寺庙只给银三千两,小哈达三千根,茶八百甑。盖遵旧例以为布施资福也。”[8](P176-177)此外,清政府历任驻藏官员均在赴藏前在打箭炉等地购备茶叶等物、以备沿途和至拉萨时对藏族上层的馈赠,这已成为一种惯例。道光时期,姚莹在《康輶纪行》中说“:赏需以茶为主,然后杂以它物。余计半年之用,市茶百八十包。从行诸人亦各买数十包而行。”除了直接赐茶外,清政府还向西藏高层赐予大量的饮茶用具,这些器具多为金银或美玉制成。如崇德八年(1643),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除令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等人口悉诸多内容外,“外附奉金碗一、银盆二、银茶桶三、玛瑙一、水晶杯二、玉壶一、镀金甲二、玲珑撒袋二、雕鞍二、金镶玉带一、镀金银带一、玲珑刀二、锦缎四,特以侑缄。”在与噶尔马书中同样有“银茶桶二”,与昂邦萨斯下书中有“银茶桶一”等之说。[9](P2-4)另外还有“银茶筩(筒)”、“嵌绿松石珊瑚金茶筒”、“金茶筒”等制茶、存茶用具。[9](P13-15)20世纪初叶,仅拉萨三大寺的佛事活动所需赏赐茶量已经非常之大。当时三大寺有寺僧1.65万人,最低年需茶叶两千余包,酥油17.5万余斤,粮食、服装、柴、盐等生活大量开支不计其数,年共需大洋174.5万余元,宗教开支占全藏各项开支的69.5%。[10](P283)这些均由政府贴款补助。
抵御印茶
除宗教与政治以某些方式结合起来维护统治模式外,茶也渗透入其他形式的政治治理之中,其中重要的一种是茶叶政治的尝试:抵御印茶。英国在印度扶植茶叶发展,并大力推进茶叶公司建设,开展机器生产。印度茶叶公司数量,1924年为140家,资本总额为3960万卢比,1934-1935年为672家,资本总额为16920.2万卢比,生产规模以及生产效率均有了很大提升。但针对印度茶业的机械化过程,国内较长时间持一种不屑的态度。以世界茶业鼻祖自居,认为中国茶的香味为最好,印茶只能贩运到英国销售,而英国人也不喜欢。[11]但面对严峻形势,有人开始觉醒,相关报纸刊物上介绍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国茶业的文章不断增多,《申报》等许多报纸不断宣传机器制茶的优点。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命率团考察了印度茶业,回国后写了《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一书。在南方涉及边茶生产与贸易的许多地方设立茶叶人才培育机构,如1909年湖北设立的茶业讲习所,1910年四川灌县创办通省茶业讲习所,1923年云南设立的茶叶讲习所等等。一些茶叶公司相继成立,并购入机械,向机械化生产过渡,涉及藏茶生产的是四川雅安川藏茶叶公司。与此同时,在与中国茶叶的竞争中,英国采用多种手段在国际、国内市场中打压、排挤中国茶叶。把中国内地所产之茶掺到印茶之中,再以印度茶的名义在英国各地出售。英国还诬蔑中国绿茶不卫生,营养价值低。[12]印茶入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抢占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国美国以及其他海外市场,如澳大利亚和俄国市场份额;二是向中国内部大量倾销茶叶;三是侵入康藏边茶市场。四川、云南所产边茶大量运销西藏,这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增加国家财源,强化政治统治,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英国利用印茶入侵西藏茶叶市场,实质是企图以印茶倾销西藏,达到驱逐边茶,进而达到侵略西藏的目的。在印茶一步步紧逼下,国际市场中,中国茶叶市场份额逐步萎缩(见上表)。这是以茶为纽带的抵御印茶入侵的宏观背景。输藏边茶生产经营方式长期处于封建的手工作坊阶段,而新兴的资本主义茶产业在印度、锡兰等地逐步兴起。1840年前后,印度已经相继成立了五十余家茶叶公司。1881年成立了“印度茶业联合会”,并在产茶区设立分会,联合会旨在加大对茶产业管理以及对茶叶的种植、制造、采摘进行科学研究。印茶产量因之得到迅猛发展。1950年,印茶出口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印度茶业快速发展是和英殖民者侵略野心密切相关的。“英人海斯汀任印度总督时,看到这种情形,就企图将印、锡的过剩之茶,千方百计设法倾销于康藏,欲削弱我国在藏之势力。”[11]早在1869年,英帝国主义分子枯柏在《由中国到印度之游记》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印茶销藏可带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收益。
俄国人居涅尔在《两藏记述》中也指出,英国人强行在西藏销售印茶是把实际政治政策问题与商业掠夺结合在了一起。[8](P224)经济掠夺是政治掠夺的先导,甚至二者在印茶入侵西藏过程中同时实现。光绪十九年(1893年)签订《藏印续约》,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军武装侵略拉萨,签订《拉萨条约》,已经明显表现出英国要强行在西藏开展印茶侵略的目的。1908年,印度事务副大臣在致外交大臣函中直白地表明了印茶在西藏的销售是英国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抵制印茶的入侵虽然主要表现在几个历史人物身上,但总体而言是当时清政府与西藏当局的一个共识:捍卫内地输藏茶叶,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抵御经济侵略。如川边镇守使张毅在《请改由川边印发茶票案》中写道:“查边茶额票十万张,现极力提倡保护,以杜印茶栏入。”表明抵制印茶入侵西藏已经是川边防卫中的重要内容。据赵尔丰分析,②《藏印通商章程》虽然当时尚在谈判之中,但从长远看来,印茶向西藏的入侵已不可避免。因此,他呼吁以四川茶业为主的边茶供应产地迅速采取自强之策,通过改良、整顿,提升竞争力。他指令雅州、清溪等地方官员召集各县茶商,探讨形势、妥筹对策。最后选择了筹设“边茶公司”的道路。这一设想虽最终未见大的成效,但却成为中国边茶,尤其是与西藏相关的茶产业发展的重要事件。标志着中国茶产业的一种自强、自救、自我发展的探索历程。面对英帝国主义及印茶的大规模入侵态势,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张荫棠在致电外务部时再一次提出自己观点,力主改变藏政,维护主权,抵制印茶入侵。在当时形势之下,清政府意识到整顿西藏政务的必要性,西藏一旦失去,其毗邻的川、滇、甘、青也将难保。鉴于此,光绪三十二年四月癸卯(1906年4月29日),命张荫棠整饬西藏事务,严惩贪污腐化、鱼肉藏民人员。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张荫棠又提出“治藏刍议十九条”、“治藏大纲二十四款”,进一步实施治藏政策,涉及政治模式、税赋管理、人口流动管理、军队设置及管理、建筑交通、教育设施、矿产开发、农业种植、风俗文化等方面。其中在农业种植方面包括了种植茶树以及抵制印茶输入两项重要内容。在《中英印藏通商章程》的谈判中,他不遗余力地抵制印茶侵藏,主张对入境印茶采取重税政策。张荫棠坚持重税印茶,其用意显然并不在于多征税收,即使对印茶征再多的课税也无法弥补英国经济侵略给西藏带来的损失,因此,其用意在于抵制英帝国主义的双重入侵。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张荫棠在《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中写道“:茶宜自种也。西藏向销炉茶,运道艰阻,炉茶市价一钱三分,至藏须购至二两五六钱。现在印茶力谋进藏,印度报纸载三十二年(1906年)由噶大克运至后藏茶值卢比三十二万,将来可望畅销。印茶无税,运费较轻,炉茶万难相敌;而藏民亦岁失运茶脚费数百万。查四川从前不准茶种至藏,系为保护炉茶起见,今时移势变,似宜以炉茶茶种输藏,教藏民自种。查大吉岭、哲孟雄一带均能种茶,则西藏卓木、工部等处土性亦想能种。藏民素嗜炉茶,印茶苦涩,一时未必能广销,但价廉,贫民乐于购用,数年后习惯自然,茶利必尽为所夺。若以炉茶茶种输藏自种,茶味不殊,而市价稍平,雅州茶利或犹可保。至打箭炉茶税,或应豁免或应酌减,以轻成本;并修道路以利转运,而省运费。”[14](P275)这是张荫棠在奏折中提出的十六条之一,也是张荫棠主张让西藏自种茶的最鲜明表达。从中可发现当时四川向西藏输入茶叶的诸多问题,如交通不便,税费过高,造成茶叶入藏后价格过高,社会底层茶消费受到抑制。另外,“查大吉岭、哲孟雄一带均能种茶,则西藏卓木、工部等处土性亦想能种。”这一表述体现了当时清政府对西藏的农业,尤其是种茶方面没有系统调查,所以,张荫棠只能对西藏自种茶的可能性进行推测。他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即印茶价格便宜,目标客户为社会底层百姓。事实证明了张荫棠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事实上,张荫棠在光绪三十三年上半年已经草拟了一个具体草案来应对西藏受到的印茶威胁,其中包括在西藏种茶。在《咨外部为西藏议设交涉等九局并附办事草章》(1907年5月)中,张荫棠已经提议在西藏设盐茶局,作为九局之一,专门负责茶盐事务。“盐茶局应办事宜。总办二员,委员八员,文案四员。由四川采办茶籽,教民间自种;派人往四川、印度学种茶制茶之法。凡种茶宜于天气暖热之地,山沟岩间,当先从拉萨、工部、巴塘毗连貉貐野人一带和煦之地试种。设官运茶局于打箭炉,务轻成本,照市价除运脚平沽,以抵制印度茶入口。又须分小包零卖,或每包一加刚,或两包一加刚,以便贫民零买。”[14](P253)张荫棠的计划已经相当成熟与周全,除了让西藏自种茶叶外,他还注意到了社会底层茶叶需求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应对印茶入侵的重要举措,最大程度减少印茶以廉价争取到的目标客户。
总体而言,张荫棠所主持的种植茶树行动是在西藏植茶的前期尝试,为新中国成立后实现西藏地区大面积植茶做了有益的探索。这也表明当时张荫棠已经注意到西藏植茶的可能以及自身产茶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茶对西藏政治及百姓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发展西藏的茶事业能够一定程度推进西藏社会发展,并对抵御外敌产生良性影响。二是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印茶向西藏侵略打开了通道,如何更加有效地抵御印茶入侵,自产茶是一条最好的选择。三是自产茶是最大程度减少四川茶向西藏输入诸多弊端影响的最有利最直接措施,从而成为抵御印茶入侵的最有力武器。因此,张荫棠在大力推进尝试茶树种植的同时,也采取各种措施联合各种力量共同抵制印茶的入藏过程。赵尔丰与张荫棠力主抵制印茶入侵,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均体现了维护自有统治、捍卫政治利益、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实现了以茶为纽带的政治凝聚功能,联合了各阶层力量。虽然这一功能的实现并未真正改变时局发展,但至少表明了以茶为纽带的各阶层、各民族在国家危难面前能够表现出一种政治向心力:一致抗外。清政府推进的抵制印茶的政治策略,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光绪十八年,驻藏办事大臣升泰在《复赫税司政函》中表达了西藏地方政府请求清中央政府严禁印茶入藏的态度。甚至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呼吁制止印茶销藏,并请求清政府配合行动。[8](P233-234)西藏地方政府之所以竭力抵制印茶入藏,归结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印度及锡金的亡国之痛深深警示了当政者。二是印茶的入侵将直接打击川茶、滇茶等入藏茶的发展,这对西藏财政会产生一系列恶性影响。三是边茶贸易催生的西藏各阶层的饮茶文化直接影响着西藏人民饮茶口味的选择,印茶在侵藏初期未能通过西藏人民的口味关。[15]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西藏地方政府在面临危难之时,能够主动向清政府求援,并与清中央政府全力配合抵御外来侵略,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现象的一道美艳风景,也成为茶在西藏传统社会中西藏治理功能发挥的重要体现。
结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西藏茶文化不仅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了西藏治理的重要内容。研究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看清历史中的诸多现象与问题。正是这种清晰的认识让我们发现,小小的茶叶曾经在西藏社会和宗教政治中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发挥过如此大的作用,茶文化是西藏社会秩序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西藏茶文化中的诸多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已经逐渐被淘汰出了日常生活范畴,但有许多内容仍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与生活,对这些内容不能简单抹杀,也不能随意全盘沿袭,而应该以传承发展与创新的态度去认真研究,使其在西藏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繁荣中发挥积极向上的作用。(本文作者:赵国栋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法学院)
- 上一篇:小议微网络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范文
- 下一篇:探讨中英茶文化的差异性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