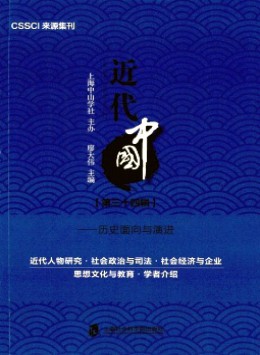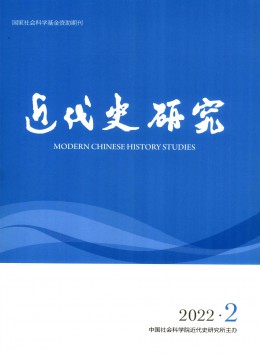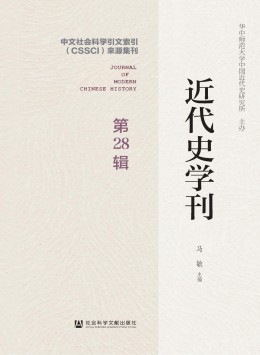近代汉译法学书籍出版研究

【摘要】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等外国人和中国知识界人士,成为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汉译法学出版领域整体呈现书籍数量多且主题丰富、出版时间与地域分布不均衡、出版机构类型众多、出版活动与时局走向紧密相连、出版质量参差不齐等特点;汉译法学书籍大量出版,助推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关键词】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出版史
晚清时期是近代西学东渐的早期阶段,所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汉译法学书籍格外引人注目。学界关于晚清汉译法学书籍的研究成果,多以历史学、法学和翻译学等学科为侧重点展开论述,鲜有从出版的角度进行探讨。考察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概况和特点,客观评析其历史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近代中国出版史的研究。
一、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概况
鸦片战争前,从事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活动的多为个人,且缺乏系统性的译介成果,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纵观整个晚清时期,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的主体逐渐由来华传教士等外国人变为中国知识分子。1862年,清政府设立同文馆,揭开了官方吸纳在华外国人翻译出版西方法律和法学书籍的序幕[1]。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和法国人毕利干(A.A.Billequin)等。1864年,在丁韪良的主持下,同文馆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国际法的中文译著,“于泰西各约俱备志之”[2]。丁韪良于1869年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后,又先后翻译出版了《星轺指掌》《公法会通》等西方法学书籍。傅兰雅自1868年起被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在近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主持翻译并出版了多种法学书籍,主要有《法律医学》《各国交涉公法》《公法总论》《邦交公法新论》等,其中包括我国第一本专门论述国际私法的译著——《各国交涉便法论》。毕利干于1866年来华,在同文馆任教期间,翻译出版了《法国律例》,这是《拿破仑法典》的第一部中译本。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翻译出版西方法律和法学书籍的任务,基本上都由来华传教士等外国人负责,中国人仅作为助手,一般采取“西人与华士同译”的办法,先是西人“逐句读成华语”,“华士笔述之”并将初稿加以改正润色,最后由西人核对后出版[3]。如在翻译出版《星轺指掌》的过程中,由联芳、庆常完成初稿,复经丁韪良审核。随着各类新式学堂的增多,以及清政府陆续选派人员出国考察、游历和留学,当时的中国积累了一批熟习西学的人才。19世纪90年代末以后,包括国内新式文人、留学生和上层统治精英在内的中国知识界,成为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的主力军。1900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的热情。除了官方机构——修订法律馆,留日学生团体、国内民间出版机构等是晚清最后十年间从事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的主要力量。1904—1909年,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修订法律馆翻译出版了几十部外国法律。商务印书馆是晚清民间商业出版机构的代表,1907年编译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几乎国内每处官署都订购一部,“销数之多,仅亚于教科书”[4]。1900年,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译书汇编社”,翻译出版了大量近代西方和日本法律文本和法学书籍。1905—1906年,“湖北法政编辑社”翻译出版了《法政丛编》,共24册,其中涉及法学的书籍有18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
二、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特点
1.出版数量和主题丰富从具体的学科分类看,法学和政治学有一定的区别。田涛、李祝环在《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述》一文中列举了晚清引进的外国法学书目,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很多属于政治学书籍,所以该目录值得商榷。经笔者统计,晚清时期共出版汉译法学书籍342种,这一数字远高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社会科学类译著;所涉及的类别十分丰富,既有法律文献汇编和专业的法学著作,也有法学教科书、工具书等基础类书籍;专业覆盖面较广,包括法学理论、法学史、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多个主题。其中关于国际法(包括国际法理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译著最多,达65种;关于国家法、宪法的译著次之,有47种之多(见表1)。
2.时间与地域分布不均衡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在时间和地域上呈现一种集聚性特征,分布极其不均衡。首先,从时间分布上看,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数量虽不断增加,但主要集中在1900—1912年,多达323种,占总量的94.4%。以甲午战争为界,中国译介出版外国法学书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初兴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在各地设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和译书机构,并延聘外国人为译员,翻译出版欧美国家的法学书籍;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末至1912年清朝覆亡的繁荣时期,得益于官方、民间各类出版机构的支持,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法学书籍的译介出版事业迎来了繁荣发展,其中日本法学书籍所占比重最高。其次,从地域分布上看,国内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地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上海、北京和东京出版的书籍数量位居前三位,分别有123种、101种和67种。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通商口岸,较早地受到西方的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较其他城市而言较为开放、进步,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涌现出许多知名的翻译出版机构,因而成为近代西方法学知识传播的前沿地带,所出版的汉译法学书籍也最多。在北京出版的百余种法学译著,主要依赖洋务运动期间同文馆等新式机构及“新政”期间修订法律馆所进行的译书工作。此外,甲午战后国人留学日本成为热潮,在东京的留日学生怀揣着“救亡求强”的爱国热情,积极向国内译介日文法学书籍,使得东京成为海外中国人出版法学译著最多的城市。
3.出版机构类型众多晚清时期开展翻译外国法学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有多种类型,其中以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为主,教会机构和国外(以日本为主)机构作为有效补充。官方机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中央政府部门,如修订法律馆、农工商部印刷所等;二是政府设立的译书机构,如同文馆、保定官书局等。出版数量最多者为修订法律馆,达69种(见表2)。民间机构则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新式知识分子设立的译书社、学社(会),如译书汇编社、丙午社等;二是国内的民营商业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三是国内的私人书坊,如浙江桐乡汪氏求是斋等。此外,国内一些新式学堂也参与了译书活动,主要为了满足自身对于法学教科书的需求,如江西公立法政学堂于1911年出版了由曾有澜、潘学海翻译的《日本帝国宪法论》。
4.出版活动与时局走向紧密相连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活动,与清政府内外政策及政治局势的走向密切相连。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面对外敌入侵,亟须了解国际的交往惯例。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后,翻译出版的西方法学书籍大多涉及国际公法领域。1900年之后,清政府实行“新政”,进行官制改革,新设了民政部、商部、法部等中央政府机构,并由修订法律馆有计划地译介欧美、日本等国的法律文本和法学书籍,尤以民法、商法、刑法、宪法、国际私法类居多。1900—1912年是晚清出版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国内民间出版机构和留学生团体抓紧时机,与官方机构相呼应,翻译出版了大量法学书籍。晚清时期外国法学书籍的翻译出版,一直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和支持,在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双重推动下,这一出版活动日益兴盛。
5.出版质量参差不齐鸦片战争后,国内开始引进新式机器铅印和石印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雕刻和木活字印刷术,装订方式也由线装转变为平装、精装为主的近代图书形制。然而,晚清汉译法学书籍的质量仍参差不齐,主要体现在编辑过程和翻译内容上。早期翻译出版法学书籍的任务主要由外国人承担,诸如丁韪良、傅兰雅等深谙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在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时十分谨慎,采取以“意译”为主的翻译方式,力图将西方法学术语与汉语词汇相对应,对后者或进行引申阐述,或赋予新的含义;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与中国助手详加校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译著的质量。然而仍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汉语词汇并不十分了解,如中文水平不高的毕利干,所翻译的《法国律例》内容极为难懂,该书虽由官方出版,但流传范围和影响力很小。直至19世90年代末随着国内民间出版机构的兴起,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留学生广泛参与,充分理解这一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5],外国法学书籍的翻译出版质量才得到了快速提升。此外,晚清时期翻译出版的法学书籍在装帧设计上比较单一,如在封面上只是用大号黑色字体突出书名、出版者和时间,未综合运用“文字、图形、颜色和材质四类视觉元素”[6]。
三、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出版的历史影响
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大量出版,不仅促进了中国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和法学知识的普及,而且对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点,学界已有详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有力地助推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一个持续升温的图书出版热点。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对当时的国人而言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传播法学知识和法律观念的载体。晚清时期,一种外国法学书籍常有多种译本,由国内多家出版机构竞相刊印。如丁韪良翻译的《公法会通》,有同文馆本、益智书会本、北洋书局本、制造局本、美华书馆本等多个版本;日本学者笕克彦所著的《国法学》有陈时夏译本、熊范舆译本,1907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丙午社出版。晚清时期外国法学书籍一书多译、一书多版的现象,使国内形成了新的出版热点,繁荣了图书出版市场。第二,加深了报社与图书出版机构之间的共融共生。晚清时期报社与图书出版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报社刊布广告代售图书,或兼办译介法学书籍的业务,而图书出版机构在译书的同时也发行一些报刊。如金粟斋出版的所有法学译著,都在《中外日报》上刊载了广告;南洋官报局除了主办《南洋官报》,还翻译出版了《国际中立法提纲》;译书汇编社不仅翻译出版日本法学书籍,而且经营发行《政法学报》。晚清时期报社与图书出版机构之间共融共生,业务相互交叉,使得报刊出版市场和图书出版市场呈现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晚清时期,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共同参与翻译出版外国法学书籍的活动。对于清政府而言,译书只是为了发挥其“工具性”作用,为外交和内政提供参考;而中国知识界将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作为融入世界大潮、实现国家富强的一种途径,契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因而相较于官方,民间的出版活动更为活跃,产生的社会效用更大。许多知识分子在西学书籍的启蒙下,或积极倡议变法,或走向革命,催化了晚清社会的激烈变革。考察晚清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情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出版活动及社会变动的深层次内涵。
|参考文献|
[1]田涛,李祝环.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述[J].中外法学,2000(3):355-371.
[2]张德彝.航海述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5]姜海英.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文图书外译刍议[J].出版广角,2020(5):89-91.
[6]杜妍.书籍封面设计中视觉元素的运用与思考[J].出版广角,2020(17):83-85.
作者:崔嘉欣 宋永林 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 上一篇:数字化下的书籍装帧设计美学范文
- 下一篇: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特点与技巧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