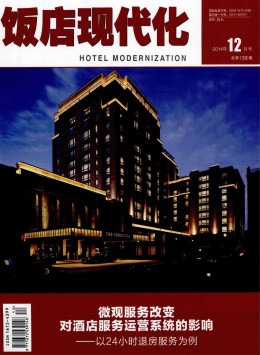现代化语境下电影解读

摘要:文章以宁才导演拍摄的影片《季风中的马》为例,对影片草原人物塑造、民族文化诠释表征所体现的现代性、民族性冲突,城市、草原二元对立,两个空间话语权力的争夺,牧人身份认同危机等内蕴进行探讨,从而对现代化语境下的蒙古族电影进行解读。
关键词:蒙古族电影;现代化;认同危机;话语争夺
1《季风中的马》的草原特写
1.1现代化下的草原人镜像
“广义的现代化是指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剧烈变革。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大转变中,无论少数民族本身是否选择现代化,他们都会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潮流。”[1]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全球化的主要特征,面对草原的沙化和城市的冲击,影片中不同的人物进行了不同的选择,体现了城市和草原彼此间的拉力与推力。1.1.1故乡草原的守望者影片的男主角乌日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传统牧民,他热爱草原、眷恋五畜,即便曾经“骑快马走三天三夜都走不到头”的草原因旱灾和雪灾已变得“像一张破羊皮”,邻里芒来、胡尔查等人都搬到城里生活,他始终不忍离开草原,记忆中水草丰美、万马奔腾的草原令他魂牵梦绕。影片从外貌、穿着、动作、语言、心理等多个角度对他进行了刻画:看到马儿和牧场被铁丝网禁锢,乌日根义愤填膺;听到再也不能放牧的消息,无所畏惧的他却泪流满面;而当看到妻子到路边卖酸奶的举动和城市里的一切,乌日根实在难以忍受,甚至会忍不住发起脾气。对城市百般抗拒的乌日根,是蒙古草原和游牧文化坚定的守护者。乌日根最为尊敬和信任的前辈道尔吉,则是一位善良朴实、充满智慧的老人,影片中他的三次出现都为乌日根拂去了内心的阴霾。为了生计,乌日根最终不得不选择妥协,将故乡留给梦乡,和妻儿一起到城市生活。放了一辈子牧,从没离开草原,也舍不得离开草原的道尔吉老人,和老马萨日拉,成了草原最后的守望者。1.1.2草原、城市的游离者和乌日根的坚定乃至倔强不同,乌日根的妻子森吉德玛虽然也舍不得毡包和家园,疼惜自己的牛羊马儿,但面对举步维艰的生活,她劝丈夫一起搬到城里开个奶茶馆,“总比靠天活着好”,或者干脆到公路边卖起了酸奶。贤惠的森吉德玛,没有像传统的蒙古族女性那样,一味地屈从于丈夫的压迫。她既能理解丈夫的悲痛,又能独立而不失理智,彰显了新时代蒙古族女性的光辉形象和提倡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色彩。呼和是牧人的后代,也是影片中最小的人物。他生长在草原,也深爱着草原,熟知饮马、看羊、熬茶等活计,勤劳懂事的他是父母的得力帮手。但同时,呼和也急切地盼望着能继续去城里上学,辍学一周的他因落下了课业一再痛哭。城市和草原文化,同时交融于其身心。影片中再三出现的陶高,亦正亦邪,既有工商文明熏陶下的狡猾,又没有彻底失去草原文明浸染下的良善。陶高似乎在城市和草原间活得游刃有余,同时又像是两者间的一座沟通之桥。此外,在草原上出生、在城市里卖画的画家必力格,为了生存和名利,一再强调自己是“布尔只津•必力格”,是作为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为祖先画像。起初,面对前来请求帮忙打官司的乌日根,必力格傲慢回应“我为什么要管你们那些无聊的事,坏自己的前程”,最后他被乌日根的执着坚守深深感动,骨子里的草原情也被唤醒。影片里着墨不多的队长、乡长和警察,虽然都讲着蒙古语,但显然已经成为了官方话语的代言人,既转达不收牧业税的喜讯,又转达全面禁牧的噩耗。1.1.3城市文明的代言者在草原劳伦斯葡萄酒厂工作的赵长江来自南方城市,却又向往草原。城市里的浓烟和喧嚣让他身心不适,草原的安宁和牧人的淳朴令他倍感温暖。影片中,赵长江对森吉德玛好得令人感动,关心她的同时为她介绍了很多来自城市和工业文明的产物。当赵长江向森吉德玛示爱,表达想和她一起在草原上生活时,却遭到了坚定的拒绝,最终悻悻离开。由此可见,宁才导演对影片中每个人物的刻画都颇为用心,没有一个角色十全十美、非黑即白,因而使得影片更加真实动人。
1.2草原文化的符号化诠释
蒙古草原是马背民族生命的魂,草原文化则是他们灵魂的根。《季风中的马》中,在内蒙古草原上长大的宁才导演通过电影语言对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均进行了适度的自我阐释,从而避免了被过度误读和猎奇。影片中的人物多身着蒙古袍,讲述着流利的母语,有着意蕴丰富的蒙古名字。诺甘西里草原上,敖包、牛羊马、勒勒车等一应俱全,展现了真实的草原蒙古人家。女主角森吉德玛,时而在毡房里熬着奶茶,时而做着蒙古面片,时而在搅奶桶中搅拌牛奶。此外,牧人们拾牛粪、割羊皮,叩拜火神、用奶祭天,彼此敬送砖茶,捧着五彩哈达吟唱牧歌为马放生,就连送人银碗时,都谨记放些奶食不送空碗的礼仪。此外,祝词、长调、马头琴等民间文学和民族音乐的出现更为电影的情感表达增色不少。这些蒙古族经典意象和民俗文化的自然流露,增加了影片的审美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陌生化的期待视野。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作为一种‘场域’,是通过‘符号系统’建构而成的。”[2]宁才导演在电影中勾勒的这些形象和意象,是蒙古草原最具代表性的符号,系列符号建构了草原这一天人合一的传统空间。与代表城市空间、现代文明和主流文化的拖拉机、皮卡车、秧歌、迪斯科、菜市场、红绿灯、柏油路、楼房等符号形成了鲜明对比。除此之外,电影中富有草原特色的对话俯拾皆是,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当赵长江向森吉德玛表达爱意时,她回答:“人怎么能见马就骑呢”,对丈夫的爱和对家庭的守护可见一斑。当乌日根看到趾高气昂的必力格,愤怒地对陶高说他“其实他是一匹骟马”。而从影片的第85分40秒处开始,道尔吉老人富有哲理的关于马和牧人关系的一段话,则是电影的主旨与升华。这些对话都没有离开一个形象———马。如同影片《季风中的马》中道尔吉大叔在放生仪式上对马的赞颂,牧人将马这非凡的生灵视为神圣的长生天的恩赐,“它的双眼如晨星般闪亮,它的四蹄如烈火般迅疾,它如兄弟一样与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建造过家园”。马是电影《季风中的马》的线索,更是蒙古族的象征和蒙古族最鲜明的符号。牧人与马,亲密相连。面对妻子卖掉老马筹集儿子学费的建议,乌日根声称“那就把我也卖了吧”。萨日拉曾因敏捷迅疾闻名草原,为乌日根带来六次冠军和无数荣誉,也为他带来了毡包和妻子,那也是牧人记忆中草原最美的时光。如今,萨日拉日渐老去,草原也日渐荒芜。当马儿在城市中受到侮辱,牧人同样在城市面临挑战。在必力格的画卷中定格的骏马,恐怕会成为日后城市博物馆里展示草原文化时的代表之作。
2《季风中的马》的内蕴解读
2.1草原、城市空间对立
2.1.1草原的消解
“现代性意味着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传承方式的制度化与科层化。对于少数族群来说,最大的冲击无异于将族群中的每个人从原来的对本族文化的无条件的非理性的认同中分割出来,纳入到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秩序之中。”[3]蒙古人尊崇“从自然中来,回自然中去”,草原也长久保持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图景。然而席卷草原的工业化浪潮却加速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水、草、人命运相连,草原变得面目全非,草原上的生命也都面临生存危机,游牧文化在哀怨的马头琴声中陨落。曾经草原,只能在心中重构。电影《季风中的马》开篇就用一组长镜头缓缓地向观众展示了被沙化吞噬的草原,视觉冲击直观有力。影片中,小呼和在荒漠般的草原上念起了《蒙古人》:“那飘着袅袅炊烟的蒙古包啊,是我出生的地方;那辽阔天际的绿色草原,是我生命永恒的家园。”往日草原和今日沙地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片段,兼具讽刺和悲剧意味。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影片中那偶尔闪现的绿色草原,都是通过乌日根的梦境出现。同时,在影片中,放牧被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昔日的牧场被网围栏割据。乌日根在不解中感叹:“过去牛羊满山遍野,草原还是绿绿的。可现在我放几只羊,怎么就破坏草原了?”
2.1.2城市的丑化
电影《季风中的马》中,城市仿佛是个恶魔般的存在,不仅拥挤而喧哗,人性也遭到了挑战。草原上长大的必力格在城市变得傲慢又自私,声称自己是黄金家族的后裔,却丢失了草原人应有的谦卑和善良;和卖酸奶时绝不贪便宜的森吉德玛相比,当乌日根和王老板买卖马儿时,帮忙翻译的陶高在他们讨价还价中的一番作祟败露了他作为小商人的油滑狡黠。而当来自城市的放着意大利歌曲的货车停在蒙古包前,赵长江一行人下车后敲锣打鼓扭着秧歌问候牧民时,森吉德玛和萨日拉都被吓倒在地。这一片段,象征城市对草原的剧烈冲击。对于乌日根而言,城市的喧闹嘈杂、人们的趋利虚伪让他恐惧,他只能通过酒精缅怀草原,认为“在草原上饿肚子都比在城里好”。而自己心爱的尊贵的马儿在城市受到比被惨杀更糟的“大罪”,更是加重了他对城市的厌恶。影片中,城市一再被丑化恶化。甚至就连来自城市的赵长江,都渴望逃离那个让他无比头痛的“到处都是楼房、机器和人”的城市。
2.2身份认同危机和话语权力争夺
2.2.1个体内部解读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拉康等都曾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进行过阐释。身份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每个生命存在的意义。电影《季风中的马》中,城市草原的二元对立和时空区隔,导致草原人在失落的草原和陌生的城市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感受到激烈的文化冲突,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产生了迷惘和危机。草原成了乌日根等牧民再也回不去的精神原乡,而城市的表象和内核都与草原相悖,乌日根不知道连汉语都不会讲的自己,该怎样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昔日的草原骄子、当代的马背英雄在城市中渺小而卑微。福柯在《话语的秩序》提出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将人形成为“主体”的最具权力的方式。”[4]权力决定话语,话语决定主体性。主体性和话语的争夺也意味着权力的争夺。影片中,深处边缘的草原人和草原文化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彻底失去了主体性和话语权,如同电影的开头,牧人在祈福仪式中的颂词渐渐被淹没在音量越来越大的英语、日语等混杂着各种语言的广播中。
2.2.2整体、外部解读
当回溯蒙古族电影的诞生发展,将《季风中的马》置于其中,对于身份认同和话语权力的解读则不尽相同。蒙古族电影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所拍摄的具有自我阐释意识的“马上动作片”。此前的影片大都是广义的蒙古族题材的作品,其中,1942年上映的《塞上风云》是中国第一部蒙古族题材也是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1950年上映的《内蒙人民的胜利》则明显带有“十七年”期间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刻痕,这一时期的电影多是以草原为背景进行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与民族团结的光荣礼赞,蒙古草原、牧人生活只是作为世外桃源,为电影谱写的“红色”主旋律点缀,民族话语被主流话语遮蔽,影片彻底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20世纪80—90年代,具有鲜明民族书写和文化寻根意识的蒙古族电影滥觞,影片“去政治化”和“去公式化”特点尤其明显,其中塞夫、麦丽丝执导的《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影片将目光放置于蒙古族金戈铁马的历史现场,对马背英雄进行史诗般地歌颂和追忆。此外,汉族导演拍摄的《黑骏马》《猎场扎撒》等影片以外来者的视角展现了蒙古高原和游牧生活,丰实了蒙古族题材电影。到了新世纪,蒙古族电影的内容题材、技术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且多次获得部级乃至世界级的奖项,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关注到草原影像。同时就蒙古族电影创作队伍而言,涌现了宁才、巴音、哈斯朝鲁等一大批优秀的蒙古族导演,建立了老、中、青为一体的蒙古族导演、编剧、演员群。此外,使用母语对白也成了蒙古族电影的日常。进入发展高峰的蒙古族电影,在描摹古今蒙古大地、牧人内心悲欢的同时丰富了全球电影,在探寻商业性的同时保持着本真的民族性。因此,就《季风中的马》等蒙古族电影的拍摄、上映,和宁才等蒙古族导演关于民族现状的特写而言,则是一种拥有高度自我认同感、民族责任感和自我阐释权的体现。他们的电影叙事从对历史的追忆转变为对现实的关注,从对民族英雄的颂赞转变为关注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力争在现代性中书写民族性。宁才导演曾经说自己“心之所向,魂之所系”都是草原,在他的心中有着深深的原乡和草原情结。“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荣格使用,“情结是构成人体结构的一个个独立的单元,是潜意识的。”[5]在草原情结的内驱下,作为一个蒙古族的“文化持有者”,宁才导演并没有沉浸在对草原的诗意描绘,而是直面现实,通过影片讲述和追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文化自觉观念鲜明。因此,《季风中的马》虽然基调悲凉,整部影片没有沉浸在一味的悲痛和回溯中,结尾终是开放式的。如同道尔吉老人所述:“马就是马,是蒙古人骑的马,它可不是蒙古人最终的理想,我们只是骑着它实现过理想。没有马并不可怕。你想想,你不想去的地方,马能把你驼去吗?你想要去的地方,一定要骑马才能去吗?”
3结语
总之,在全球的电影市场中,蒙古族电影如同那草原上的马头琴般,悠扬婉转地讲述着民族的传统和现在、欢乐与悲伤,并在回望和审视中思考和探索着民族的未来,彰显了蒙古族电影人的责任与情怀。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以《季风中的马》为代表的蒙古族电影所投射的草原人的怅惘与彷徨、草原生态文化的嬗变与挑战,以及以城市与草原两个空间为代表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种种纠葛和其话语与权力的争夺,则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与此同时,蒙古族电影也有着制作成本不充足、题材相对同质化、影片观众较单一、批评队伍不健全等问题需要改善,期待蒙古草原和蒙古族电影的未来,都能够丰饶而美丽。
作者:乔亚楠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 上一篇:问题驱动的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模式探索范文
- 下一篇:电影产业链中的衍生品版权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