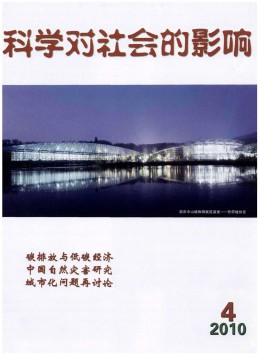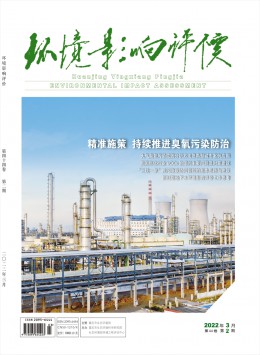影响中国文学外译因素的考察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影响中国文学外译因素的考察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引言
中国文学,无论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千百年来负载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滋润着中华儿女的心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重建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承担着重塑与建构中国形象的神圣使命。近年来,经过多方努力,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国家影响力的中国文学还未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还很长,并且中国文学在向西方译介与传播的过程中一直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据相关研究统计,在跨越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方书籍近10万册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相反,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籍却不足500本。数字上的鲜明对比引发学者们对比和探讨中外翻译中内容的选择、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翻译观和翻译策略选择等翻译的根本性问题并产生质疑和争议。“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包括翻译界、翻译研究界对翻译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较多的误区……看不到翻译作为一个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实质。”(1)从当前实际情况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是由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逆势”行为,既有语言形式、功能以及地位方面的不对等,又有文化方面的天然差异——文学表达和叙事方式的陌生化以及迥异的文化价值观,这些都构成了中西文学之间阅读交流的鸿沟。译者可以克服语言表达上的障碍,却很难在翻译过程中弥补文化方面的差异。翻译的“文化转向”表明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两种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沟通的行为。的确,从本质上看,翻译是一个辩证的系统活动,即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系统工程,影响文学外译诸因素之间始终处于相互联系和运动之中,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相交错,环环相扣,辩证而有序地统一于一个有机系统中。任何文学翻译实践活动或翻译实践的评介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就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然而,目前国内对于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仿佛进入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逻辑矛盾之中。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存在于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的主要争论的焦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外译作品的选择,经典文学和大众文学孰为轻重;二是翻译理论和翻译主体的确定,是以国内译论和翻译家为主还是西方译论和汉学家为主;三是翻译策略的取舍,以归化策略为主还是异化策略为主。本文拟就上述看似两难问题做一辩证考察,并尝试提出能更好译介中国文学的路径和策略。
一、外译作品的选择: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应齐头并进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作品选择方面一直存在一个两难选择:是选择面向“小众”的传统经典文学,还是倾向受众面更广的通俗大众文学。这看似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两难选择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伪命题,对外译介首选最优秀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经典文学代表着中国文学的精华,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直接反映。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我国首先向世界系统推介中国文化典籍的“大中华文库”重大出版工程的原因。另外,“熊猫丛书”也值得推介,它是一套中国官方主导对外译介的高质量的英语版中国经典著作、传说、史集。至于有人质疑“熊猫丛书”的影响力,甚至认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里永远属于边缘化和小众化的存在。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这样的论断。暂且不论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存在状况是“边缘化”还是“小众化”,不妨先问一问我们自己:“中国文学”在国内当下的生存状况又是怎样的呢?难道不也是处于“边缘化”属于“小众化”吗?试想一下,一国文学在母国的接受情况尚且如此,又何来底气要求异国读者必然对中国经典文学热烈接受和积极欣赏呢?因此,即便是真的达到了“小众化”也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推广效果,不必妄自菲薄,失去了文化自信,陷入民族虚无主义就更加不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因此,中国传统经典文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都诠释着中国文化与中国价值观,无论多么“曲高和寡”,都是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对外译介。事实上,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不分国界的,也是能够赢得读者青睐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克诺夫出版集团出版并能有比较好的销售业绩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不能否认,“严谨的输出导向和活泼的需求期待之间存在缝隙,导致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常常过于死板紧张,缺少灵活变通。”(2)严谨的“学院”式的对外译介在对外于大众文化交流、对于国外普通读者来说就不见得有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同时,过于重视经典作品的对外译介,相应地就忽视了大众文化的传播。汉学家杜博妮曾经指出:“中国政策制定者对文学译本的实际读者缺乏重视,而只关注专业读者的可接受性。”(3)的确,不能因为过分注重经典文学的对外译介而忽视了通俗大众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现代消费社会,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成为大众青睐的对象,而严肃文学和后经典文学受到很大冲击和挑战,当代普通读者会觉得它们太远离现实而对之敬而远之。从大众文化层面上看,普通读者所关心的并不是成体系的学术问题或无休止的创作经验漫谈,他们所关心的是文学是否有趣味性、体验性或实用性。换言之,他们重点关注是否适合自己的阅读习惯和欣赏风格。其实,对于带着固有文化习惯以及阅读习惯的人在接触和欣赏异域文化时,需要有一个由易到难、由体验到对话、由乐趣到思想的渐进过程。只有在充分了解潜在的阅读对象的成长环境、文化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表达方式、思维习惯的基础上,再精心选择那些能展现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引起精神共鸣的或者与西方读者切身利益、生活相关的中国优秀文化作为“好的故事”向外国读者“讲述”,对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言,必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引起普通大众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唤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才能使中国文学的推广和接受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因此,在确定中国文学外译内容上,应该“双管齐下”,让经典文学和通俗文学“齐头并进”,这样既能让不同目标读者群各取所需,又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中国文化。
二、译者和译论主体的确定:以中国译论指导中国译者的文学外译实践
目前存在于我国翻译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翻译的职业化,甚而由于当代作家外语(主要是英语)水平存在着短板,很少有作家再涉足翻译。翻译一旦职业化和工具化,图书市场的畅销与营利便主导着一切。文学的商业化意味着不要经典,舍弃精神,那么由谁来继承百年翻译史的两个优秀传统——对精神和经典的追求?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尤其是近代翻译实践中,出现过很多优秀的翻译家,从林纾的开山翻译之作,到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学的译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苏联革命文学的翻译,都体现着翻译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诸多文学大家同时也是翻译家,诸如鲁迅、傅雷、钱钟书、李健吾等都具备一丝不苟、恪尽职守和精益求精的文学翻译精神,使得近现代的文学翻译作品在思想性和美学高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因此,中国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文学家应该继承前辈这种“思想启蒙”和“经典传承”的精神,负起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重任,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内在的主观能动性,构建并承担起多种特定的译者身份——既是外译内容的筛选和推荐者,也是中华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融合与协调者,更是中国文化的阐释者和传播者。不过,有学者以读者接受为考量,主张以国外汉学家为译者主体,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阐释、折中与重写,译者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更要对得起读者”。(4)很明显,不少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的时候是以读者接受为第一考虑要素的。为读者翻译的观点当然无可厚非,没有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作品的译介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要想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不能一味地以西方读者的接受性为考量。市场销量和畅销书排行榜的确是译者应该关注的,但对翻译求“真”的本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是对外译介活动中需要重点考虑的。事实上,比较而言,西方翻译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更多关注译本的可接受性,而中国本土翻译家更注重忠实于原文。有人担心为了保持真实性不对原著进行适当删改会造成目标语读者阅读、理解和接受上的障碍。此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无须过于担忧,原因就在于文学既有其民族特性的一面,但也有人性共通性的一面。从人类认知和体验的一般规律来看,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认知经历,在与自然界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拥有相似的生命体验,以表现人类生命与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从而也就有许多相同的主题和感悟,因而文学作品是可以“通约”和“互赏”的。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文学由于发展时间的原因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就一定比世界其他文学低一级,更不能以克服差异为借口在文学翻译中在不尊重原著的情况下进行随意删改,从而削弱了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意义和价值。在翻译理论的认识方面,有学者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译论要比西方译论至少落后二十年,还有学者甚至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翻译界,很少或几乎没有本土原创性理论,没有产生过国际上公认的中国翻译理论家,从而导致了中国翻译研究在国际上几乎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5)对此种论断,翻译家许渊冲先生颇不以为然,认为中国本土有很好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指出《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乃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源头。许先生翻译的中国古代散文、诗词、戏剧等14部重要作品均是根据中国译论翻译出版的,“每本译著都有一篇后记——‘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6)许渊冲把《论语》的说法和文学翻译相结合,提出了“知之、好之、乐之”的“三之论”,用来衡量译文质量的优劣。译文的最低要求是“知之”,即被读者知道和了解;译文的中等要求是“好之”,即被读者喜爱和接受;译文的最高要求是“乐之”,即能使作者感到愉悦。“三之论”关注的是译文被读者接受的程度。国学大师钱钟书提出的“化境说”认为“文学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7)同时,当代翻译领域的实践者如刘宓庆、许钧、谢天振等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中国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中国视角的思考与总结,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事实上,在改革开放40年的翻译发展历程中,中国译学界辛勤耕耘,在翻译理论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并呈现出“中国根基、世界眼光、跨域融合和创新精神”(8)等特征。这些在翻译领域辛勤耕耘的先行者对翻译理论的阐释和翻译实践,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实践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认真学习和运用的。
三、翻译策略的取舍: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到底是忠实于原著因而更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还是为了让读者接受考虑从而较多地使用归化翻译策略,这是翻译界甚至整个学术界争议颇多的一个话题。有学者认为,诸如莫言的小说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之所以在全世界传播和产生影响,“主要归功于像葛浩文这样优秀的目标语国家的翻译者”(9)。且不说这样的论断是否过于武断或者对国内翻译界是否公允,因为中国文学外译成功与否确实离不开像葛浩文这样优秀的目标语国家的翻译者,但要说“主要归功于”像葛浩文这样的优秀译者,却未免把其他方面的努力都最小化了。还有学者主张“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进而据此对以忠实性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提出质疑,甚至将之视为“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10)。试问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何在?又把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置于一种怎样的位置呢?事实上,这样的论断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初衷相去甚远,是不值得鼓励和提倡的,一些研究者就对这种过分归化的翻译策略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批评,认为西方读者从这样的译本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11)作家高尔泰也无法认同和接受葛浩文的在他看来比较“随意”的翻译方式,认为“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等于阉割”。(12)以上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免过于绝对。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删改,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主要是看译者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目的对原作进行了删改,进而思考和研究这种删改带来了怎样的效果。一部作品无论怎么删改,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产生误读,更不能有意误导读者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因此,对一部翻译作品的评价,首先要看在译介过程中是否“把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译介出去”(13)。中华文化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在译介过程中丢失了文化价值观,那么这种译介过程中的删减就是必须禁止和杜绝的。相反,如果不损失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传达,又能更好地让西方读者阅读和欣赏中华文化,那么这种删改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实际上,在具体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更多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是非常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出于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也是推崇异化的翻译策略的。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根茨勒认为译文应该“保留源语文本的陌生化表现手法,如果源语文本中的表现手法在第二语言中已经存在,译者就要构想出新的表现手法”。(14)国内一些学者同样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陈琳等强调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这与异化翻译策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意指“避免将文本归化成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内容,而是将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保留即异域化……使翻译审美主体和审美接受者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提高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其本质是“违背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特别是审美接受者的期待规范,造成陌生化效果”。(15)文学甚至文化的传播乃是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译文的可接受性和读者的反应是衡量译文质量优劣的一个标准,但不能就此贬低以忠实性为原则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观念,质疑经典文学的译介,从而否定对传播中国文化付出的努力,对中国政府主导下的主动译出模式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这么做是不负责任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文学翻译的方法和策略的取舍上能反映出翻译过程中对语言文化异质性的态度。即便是在翻译策略方面颇受争议的葛浩文,也直观地给出了自己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看法:“我们选择作品来翻译时,不能仅仅以我们自己文化里通行的文学标准来判断,而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评估他们的作品。”(16)就大环境而言,由于汉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力尚不够强大,因此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传播与接受必然会遇到障碍,必然是一个漫长过程。弱势文学比如中国文学要想顺利译入到强势文化中并被读者所接受和认可,根据目的语的语篇规范,对原著进行适当删减,用比较流畅的译文翻译,让读者阅读起来比较轻松,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也是文学译介和传播开始阶段的折中之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加,中国本土翻译者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时会更多地保留中国的特色文化,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接受中国,真正地做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无论是某些个别文学出版社的撤销、某些丛书的停止出版还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数量和销量的低迷,都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必然遭遇到的暂时困难和挫折,不能为此就否定了社会各界为此付出的努力,更不能堵死了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探索之路。我们能做的是对过去的做法进行适当反思,对不足之处进行调整,为更好地译介中国文学探索更加畅顺之路。
结语
依据德里达的观点,翻译乃是一种必要的然而又无法真正完成的任务,这一悖论性的局面构成了翻译的永恒处境。目前存在于中国文学外译中的看似两难的命题其实是何主何次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在中国文化外译过程中,到底如何“选择”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我国当下对文学乃至文化“走出去”的一系列探索,都应当以反映和体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前提。虽然目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存在删节和改译等违背翻译忠实性原则的问题,但应该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出发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存在于中国文化外译中的“时间差”和“语言差”这两个因素。“语言差”存在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西方国家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读者数量是不多的,而能从事中国文学译介的汉学家更是屈指可数;“时间差”则意味着中西双方对彼此的文化了解时间长短的不对等,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译入”明显长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认识”。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在积极推进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时,现阶段不宜贪大求全”(17)。总之,应从不同层次和多重视角来考察文学译介与传播的效果,而不能只聚焦于某一个方面,尤其不能对其缺陷进行无限放大进而否定其合理性。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影响力的增加,中国文化会被更广泛地传播和接纳,中国文学外译的动力也不断加强,异域读者会更加渴望再现文学魅力的原汁原味的译本,从而对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提出更高的要求。
作者:王倩 张绪忠 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