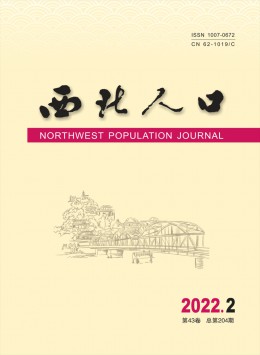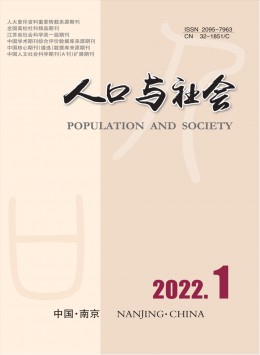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创作文化价值取向

[摘要]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较少民族面对着相比于其他少数民族而言更为尖锐的文化冲突和更为复杂的文化选择。新时期的土族作家文学处处体现着在民族传统和现代性二者之间徘徊不定的文化价值取向矛盾,一方面,对民族失落传统的追寻、对民族主体的确证成为这一时期土族作家创作的重点;另一方面,土族作家对现代文化价值观也表达出了渴望与困惑相交杂的复杂态度。而要走出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两难抉择,仍需作家继续探索,突破局限、重构立场。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家文学;土族;文化价值取向
一、新时期土族作家文学发展概述
文学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信息与精神世界,呈现着民族特有的审美倾向、地域环境和思维哲学。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和积累时期,在1949年以后,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开始进入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在1979年后逐步转向了蓬勃发展和兴盛阶段。土族是中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人口排名首位的民族,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土族作家文学曾有一段相对沉寂的状态,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寥若晨星,董思源是其中唯一一位坚持文学创作的作家。这一时期的土族作家文学仍处于萌发阶段,当时的写作者多为业余作家,诞生的文学作品也较为不成熟。但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土族作家文学进入了发展的繁荣期,逐渐形成了一支相对成熟的作家队伍。新时期以来,土族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成熟的作家队伍。20世纪80年代以来,鲍义志是土族文学史上影响力最为广阔的作家之一。鲍义志从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之后也一直佳作不断,体裁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剧本和报告文学等。其中,小说集《呜咽的牛角号》是土族作家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作品集。小说《水磨沟里最后一盘水磨》曾获1987年《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山丹奖”,后又改编成电视剧获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骏马奖”。1991年获“庄重文”文学奖,这是至今为止土族作家获得的最高文学奖项。祁建青是一名军旅作家,主要创作散文和诗歌,他的散文集《玉树临风》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另外,李占忠、刁桑吉和祁进城也是20世纪80年代较为活跃的作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土族作家文学渡过了上一个高峰期,一些新生的文学势力蓄势待发,师延智、阿朝阳、阿霞等作家开始有新作问世。师延智和阿朝阳同属“河煌文社”成员,都擅长创作诗歌和散文。而阿霞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大多收录于2000年出版的诗集《我的河流》,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土族诗歌集。进入21世纪,出现了更多的优秀作家,文学作品的质量也有显著的提升,土族作家文学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在国内乃至国际都有着更新的探索。衣郎是诗坛颇有影响的诗人,曾在2009年与斩获“骏马奖”的祁建青一同作为代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李卓玛的长篇小说《泪做的仙人掌》,是土族历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得春则在美国出版了土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MongghulLivesinEasternTibet(《激情彩袖》)。从拉开土族新时期文学创作帷幕的鲍义志,到活跃于1980年代的作家祁建青、李占忠、刁桑吉、祁进城,再到1990年代的师延智、阿朝阳、阿霞,以及21世纪以来出现的衣郎、李卓玛、李得春等作家,土族作家文学一直延续着一条完整而顺畅的脉络,没有陷入沉寂。土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特征与其他大多数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类似。首先,它们都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积累、萌生,最早由民族内的优秀知识分子发起先声,往往会出现一个或数个创作成果较为突出、影响力较大的作家,进而带动一批乃至一代人的文学创作热情;其次,民族的作家文学也深受其民间文学的影响,早期很多成绩斐然的优秀作家,同时也从事着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整理工作;最后,在创作体裁方面,便于抒情达意的诗歌与散文的数量和质量往往超过注重情节的小说,尤其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速度是较为迟滞的。但乐观的是,无论是土族还是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其作家文学都在不断取得显而易见的成绩,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逐渐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新时期土族作家文学的题材包含着诸多方面,如追溯族源、文化寻根的历史题材;展现民俗、反思传统的民族文化题材;怀乡抒情、表达忧思的乡村-都市题材,等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的背后,体现着作家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对生活的理解,更深层地反映出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正如李长中在《在历史记忆中重构传统———当代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论》一文中所说:“新时期以来,本土/全球、传统/现代、边缘/中心等的碰撞渐趋加剧,时代精神与民族意识的彼此碰撞,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短时期内的难以兼容,城市化进程与民族传统社会秩序的矛盾和冲突等问题的层累,导致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处境比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更为严峻、更为恶劣。”[1]人口较少民族面对着更为尖锐的文化冲突和更为复杂的文化选择,而这样一种文化上的矛盾与忧思,贯穿于新时期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始终。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在民族传统和现代性二者之间徘徊不定的文化价值取向迷思。
二、传统:守望与反思
全球化与现代性带来的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在物质上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环境受到了直接的影响,民族传统也随之面临解体。这种被客体化和边缘化的处境,导致人口较少民族普遍陷入一种身份上的焦虑。新时期的土族作家文学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其间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为土族文化带来一种“文化撕裂”,传统民族文化的弱势和边缘地位导致文化存续上的危机感的产生。因此对民族失落传统的追寻、对民族主体的确证成为这一时期土族作家创作的重点,其本质上是为了构筑民族集体记忆、修复文化创伤,乃至建立族群自我身份认同。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追寻族源、文化寻根主题作品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是怀恋乡村、追忆民俗的作品的不断产生。有关土族族源的探究,学界有着诸多的争论。其中“吐谷浑说”为更多的土族民众所接受,“吐谷浑王国”也成了土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不可磨灭的情结。如师延智在《彩虹:在中国辽阔西部的高崖上》一诗中曾写道:……吐谷浑和他的儿孙他的部落/站起/站起/站起/在高头大马上,/在狂风暴雪中,/在生肉白酒中……/舒展狂悍不羁的辽阔生涯,/研磨坚韧苦难的大生命/吟唱悲怆的长调和英雄的史诗/也吟唱凄婉粗放的爱情和浪漫传奇……[2]诗人将浪漫的诗意和丰沛的情感融于诗行,对民族历史的自豪与无限深情溢于言外,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被唤起对民族的眷恋与骄傲之情。而以怀乡之情为主题的作品,多见于阿霞的诗作。如《柳湾:陶的歌声》一诗中所写:青海之东,湟水逶迤/陶的碎片编拼神秘音符/在河流的波纹间飘扬/梦呓和哭泣的姿势/已不能辨认/谁的梦如此纷乱/谁的哭泣如此伤悲双耳的陶聆听着久远的记忆/泥土的脚步/在陶的年轮中浮现/故事没有始终卷唇的陶诉说着/陶前凝望的眸子/水的倩影和泪珠交叠/铜镜里第一根白发/光芒如炽流泪的手,握不住分离的消息/陶啊,柳湾的河流间齐声歌唱的陶/湮没了往昔的马蹄声/梦中的心事不曾消解……[3]诗人阿霞生长于民和官亭的山川大地之间,接受着地域民族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润,在她的文字之中,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渗透极深,即便是细微之处也有着充分的表达。由于目睹了本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摇摇欲坠的现状,一些作家也开始反思民族文化中的弱点与不足。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就是描写女性苦难、批判陈旧习俗的作品。鲍义志的小说中就包含着对女性生存和命运的关注和描写。如在小说《菊香》中,就塑造了菊香这一传统而又善良的女性形象。菊香的丈夫因偷情而受伤残疾,而她仍恪守妇道,照顾残疾的丈夫和婆婆,在两年里不离不弃地照顾两个病人,因而被乡里树为先进典型。而当她决心与丈夫离婚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时,反而招来了人们的责骂和污蔑。小说着力描述了在传统观念压迫和限制之下女性的悲苦命运和沉重的道德枷锁,体现了对民族文化中落后观念的批判与反思。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审视、捍卫和追溯,构成了新时期土族作家“文化寻根”的基本策略。而这样一种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一批土族作家面临社会变迁、时代更替时的抉择。传统文化生活成了他们修复创伤、寄托心灵、建构认同的“精神原乡”。
三、现代:切望与困惑
当现代性溶解空间的差异而将各民族人民纳入全球同一交往、碰撞的共时框架,少数民族就已经失去了居住地地理位置的封闭性与边缘性。[4]当现代性裹挟着纷杂多样的观念与信息渗透而入、席卷而来之时,人口较少民族更易陷入对文化转型的犹疑和迷茫。土族居住于青海地区,长期与当地的多种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因此形成了柔韧、包容的民族性格。对于崭新的、异样的外来文化,土族人尚且能以包容兼蓄的态度理性看待,而非一味地抵抗。然而,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对于文化根基较为薄弱的人口较少民族而言,这一过程更是充满了“断裂”的痛苦和无所适从的困惑。一方面,人口较少民族迫切期待依靠现代性转型来寻求民族文化发展途径,使民族文化恢复生机;另一方面,又难以在迅疾的现代性潮流袭来之时立即找到自身的立足点,往往是被动地接受改变与冲击。胡艳红在《土族作家文学研究》这篇论文中曾对土族作家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民的现代性渴望和忧虑”做了论述。论文着重分析了当代土族作家笔下的“商品经济弄潮儿式的土族新农民形象”,并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退伍军人或者是高中毕业生”[5],他们接受过较为系统的现代化教育,视野较为开阔,对城市生活中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着深切的向往,因而选择了经商,参与到改革开放进程中,自觉追求现代化;另一类则是出身于贫瘠困苦的土地之间的普通农民,随着现代化进程推动生产方式的进步,这些依靠传统耕作方式的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为了维系生存和改变命运,他们选择了“进城”。这些农民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主要体现在年轻人的婚姻爱情选择、生产生活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城市的向往等方面。而在此种追逐时代潮流的过程中,也随即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乡村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却还未能重新建构,农村暂时没有一柄尺度合适的价值标尺”[5],因此,传统美德的丧失、拜金主义的盛行,如此等等,弊端也依次显现。土族作家们一方面对努力追求现代化的举措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也对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予以揭露和批判。文学作品是当下时代与生活的反映,是作家依据自己的感受与理解对自然形态的生活真实进行艺术加工后的艺术真实。在当代土族作家笔下所构建的“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局面,直接指向土族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取向的徘徊不定。一方面现代性能够为本民族带来经济、物质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精神上的迷茫。究竟是乘着时展的巨轮悍然前行,还是转回原地寻求传统文化的荫蔽,土族人无疑面临着文化上的两难抉择。
四、探索:调整与重构
民族文化从不会一成不变,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前发展,当土族作家文学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的两极之间时,一批土族作家与学者也开始思考本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应当成为共识的是,民族文化课题必然不能长期囿于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拉锯战,民族文学乃至民族文化要取得发展,应持续保持探索姿态,调整文化结构,重构本民族文化立场。笔者于2018年7月曾赴青海省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情况进行调研,期间调研团队对青海当地的几名土族作家和学者如祁建青、阿朝阳、衣郎、李卓玛、东永学、毕艳君等作了访谈。在谈及对土族文学创作发展前景的认识时,几位作家、学者所表达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普遍提到了作家应当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根基、立足于当下的时代现状、立足于真实的地域生活,探索将本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有机结合的连接点,创作出真实反映本民族思想感情、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土族文学评论家毕艳君曾说:“民族文学的出路,都在于要坚持自己的本心。民族文化如果丢失了自己的本土文化和本土特色,完全随着城市化发展而被卷入现代化进程里,那样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淹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如何去结合自身的民族性与现展,如何反转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去表达自己真正要表达的内容,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我认为作家不能只是局限于对本民族的关注与表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一定要寻找到多元文化的结合点,然后再加上文学的表达,才能找到更好更远的出路”。被访的几位土族作家也不约而同地认为,民族文化的呈现不是流于表面符号化的堆砌,将民族文化内化为自己的民族情结,并通过文学技巧和艺术手段将民族情结以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是每一个民族作家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能力。而面对当下文化错综交杂的状态,土族作家也将致力于追求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为创新的写作内容。正如《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价值取向书写困局》一文中所说:“当代民族文学应勇于突破地域政治想象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局限,走出过去偏狭的立场,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习惯,在深度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体悟本族文化在现代性转型阵痛的同时,借鉴外在文化的合理因素,从现代性现实出发,在深入思考和广泛对话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可以充分表述自己意愿、把握自我主体的文学场景。”
[参考文献]
[1]李长中,代娜新.在历史记忆中重构传统———当代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论[J].民族文学研究,2015(6):37-48.
[2]师延志.玫瑰•家园[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4.
[3]吉狄马加.最后净土的入口:中外著名诗人眼中的青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214-216.
[4]徐休明,宋宇.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价值取向书写困局[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24,127.
[5]胡艳红.土族作家文学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4:33,37.
作者:杨易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 上一篇:儿童课本剧艺术语言表达表现形象化应用范文
- 下一篇:浅谈课堂有效实施民族音乐教学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