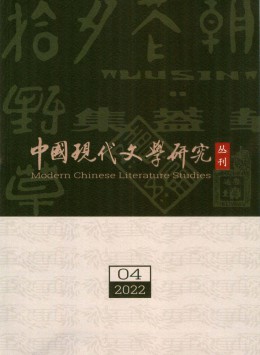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性

摘要:现代文学史料是回归文学现场,揭开历史真相的钥匙和路径。重视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必须重视现代文学史料真假的鉴别和史料价值的判断,在此前提和基础上要对现代文学史料善加保管和利用。在实际工作中要区分现代文学史料原始形态的真实性和现代文学史料内容的真实性,对现代文学第二手史料也应当加以重视。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料;价值;鉴别;利用
一、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价值
现代文学史料,是与现代文学事件、人物、活动等直接相关或有某种联系,在现代历史过程中遗存下来的,能够帮助后人认识、解释、重构现代文学历史的资料或实物。它既有当时的文字资料,如当时的书报期刊、信件和文件等,也有一些实物,如作家等使用的生活资料或历史事件遗迹,同时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后来回忆的一些回忆录、调查报告也包含在内。现代文学史料是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基础,没有完整、翔实的现代文学史料作支撑,任何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都只是编写者的主观臆测,就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经不起仔细推敲和考证。现代文学史料是我们拨开历史迷雾,回归现代文学历史现场,揭开历史真相的钥匙和路径。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价值再怎么说也不过分。如冰心丈夫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任职情况常被人误传,早在1942年王森然《冰心女士评传》》中就有“适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文藻博士”一句,认为冰心丈夫吴文藻是“法学院院长”。而据现代文学史料学者张先飞教授考证,吴文藻并没有担任过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他在燕京大学工作时,曾在1933年短暂担任过文学院院长,后在1935、1937年担任过社会学系主任。这些都清楚地记录在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的年刊《社会学界》(1927―1938)上,依据这样令人信服的原始史料,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工作经历才能不被后人曲解和误传,从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对作家冰心的研究[1]。对于那些已经有历史定位的现代文学史料,我们要善加保管和利用,对于那些现代文学史料价值和意义一时难以确定的原始材料,也应该做好标记,先行妥善保管,待有条件时再重新进行审核鉴别,不能扔在一边不管不问,更不能随意处置或者丢弃,因为这里面或许会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原稿,就是被其秘书田家英从废纸篓里捡回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叶永烈《和他的秘书们》一书记载:1963年,在为编辑《诗词》一书时,田家英拿出一首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看毕,哈哈大笑:“嗬,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写得还可以,收进去吧。”原来,1949年4月,当时已经由西柏坡迁至北平香山的,得知解放南京的喜讯,欣然命笔,写下一首七律。大抵写毕又不甚满意,揉成了一团。幸亏田家英细心,保留了的手稿。自从《诗词》印出,这首七律广为流传,脍炙人口。[2]如果没有秘书田家英的史料意识和重视史料价值的思想,今天我们就看不到的这首《七律》,不仅现代文学史上少了这样一首大气磅礴、结构精制的诗作,对作为诗人的的研究也会缺少一份重要的史料。曹禺著名剧作《雷雨》的首演,学界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4月27―29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公演[3]。但研究者刘克蔚通过查找史料进行考证,提出《雷雨》首演不是在日本东京,而是于“1934年12月2日在浙江省上虞县的春晖中学”[4]。但学界对此论断和相关史料并没给予重视。另一研究者刘家思在对已有史料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又多方寻找其他相关史料,从当时报纸刊登的演出新闻,到当年春晖学校留存的毕业生名单和现今仍健在的当事人等处入手,拓展史料研究范围,终于发掘出有说服力的真实史料,可谓“人证”“物证”俱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雷雨》首演确实如刘克蔚所说是在“春晖中学”[4]。这为纠正以往现代文学史在《雷雨》首演上的错误和偏颇提供了重要史料基础。
二、重视鉴别现代文学史料的真伪
鉴别史料的真伪是文学史料整理工作的第一步,对于现代文学史料来说自然也不例外。面对浩如烟海的现代文学史料,什么是“真品”,什么是“赝品”,需要史料工作人员睁开他的“慧眼”、小心甄别。若稍不留神,可能就会鱼目混杂,良莠不分,让“假的”成了“真的”,这会给以后的史料整理、汇编、存档、使用等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有鉴于此,史料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完善的专业知识、系统的理论素养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一些史料的真伪在没有鉴别之前,不能轻易使用,否则张冠李戴,误导他人,更有甚者,可能造成混淆黑白、颠倒历史的恶劣影响。王世儒《对〈致刘震东便条〉的几点质疑———兼评〈先生传〉一书的史料真实性问题》一文给史料工作者敲响了警钟,也引发了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的深思。正如该文作者王世儒所说,《致刘震东便条》虽然“系过录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所藏历史档案的卷宗之内,自然可以看作是与史事有关的一篇文献。但是由于这一《便条》的署名是英文拼音LaoTingLi,一时尚不清楚是否为的又一别署,只得暂付存疑,有待考证之后,再作定论”[5]。但是,在便条的真伪鉴别和定论没有出现之前,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编辑出版《全集》时,这一《便条》“已被以《致刘震东》为题,作为的信札之一,收录到《全集》书中了,而且也未说明必须收录的理由”[5]。该文又谈到张次溪编写的《先生传》一书中,却有“所谓英文拼音LaoTingLi即是的署名,以及关于《致刘震东便条》始末由来的记述”[5]。尽管此书出版较早,是在1951年由北京宣文书店出版的,但其记述经认真阅读,内容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自相矛盾,更让人吃惊的是,和已有相关史料比对,《先生传》书中一些叙述竟然不顾历史真实,完全是凭空杜撰,如该书编写者张次溪绘声绘色叙述的在北京被军阀特务拘捕、审讯的情节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在那个时间段,正在苏联,正如王世儒所说“历史事实确凿证明,1924年5月至11月期间,身在苏联,中间从未回国”[5]。所以,对此便条真伪和其来龙去脉,仍然有待史料工作者继续寻找史料,方能解开历史之谜。
三、两个概念:“现代文学史料原始形态的真实性”和“现代文学史料内容的真实性”
广东省档案局朱荣基《对档案史料真实性问题的我见》一文对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者很有启发和鉴别意义。他将人们一般意识中“档案的真实性”,细分为“档案的真实性”和“档案内容的真实性”两个概念,并进行了比较,认为“档案是客观历史活动的产物,它不是人们在立档之后主观臆造的东西。因此,它本身的客观性是确凿无疑的”。“档案的真实性”,就是指档案最原始地记录了档案形成者历史活动客观过程的这种性质。而“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则是“档案形成者对于历史事实的态度,也就是档案的内容对于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解释是否符合、能否正确反映当时现实的真相”。“作为档案形成者的原始记录,档案的客观存在,是真实的;但是,即使是原始记录,其内容对历史事实真相的反映,却是有真有伪。简言之,‘档案的真实性’,是指原始记录的客观实在性;‘档案内容的真实性’,是指反映历史事实真相的真伪性。”[6]这篇文字有力地廓清了人们对档案的一些错误认识,从而推动了档案理论建设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开展。现代文学史料的主要形态,也是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作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者,也可以借鉴这种两分法。将现代文学史料真实性分为“现代文学史料原始形态的真实性”和“现代文学史料内容的真实性”。现代文学史料中的文字资料和实物,只要是真正的“历史遗存”和“原始形态”,都被认为具有“真实性”,但这种史料内容是否和历史现场相符合,是否与历史真相一致,则要结合其他史料进行认真的鉴别和考证。因为即使是当时的历史文献和资料,由于记录人或撰写者或当事人本身的原因(或对当时客观事实不清楚,或为了某种目的有意或被迫隐埋、歪曲历史真相),也可能使得历史文献、史料中的内容虚假、不真实。这就需要后人小心求证,认真甄别,不可以被这些内容中不真实的史料蒙蔽了双眼。作家师陀在1943年3月曾写了一篇通讯《华寨村的来信》,文章中有“……今且行矣。江南秋老,夫复何言”等语,表面上看是记录其在河南老家乡村间苦闷心境的文字,其实这篇通讯是师陀为了能在上海落脚,躲避敌人的搜捕,而有意制造的“烟雾弹”,给敌人一种自己已经离开上海、回了老家的错觉[7]。如果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者不去追根究底,不向作家本人考证,是不会发掘出这一历史真相的。
四、运用现代文学史料应注意的问题
在鉴别现代文学史料真伪的前提下,在去除“伪史料”的基础上,对真正的现代文学史料的运用要谨慎。史料工作者和研究者容易犯的错误,第一是夸大其辞,将史料在佐证某一历史现象和事实时的作用夸大,或用较少的史料,甚至以孤证去说明问题,从而让史料显得“力不从心”。梁启超曾赞扬顾炎武,说其“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言”[8]。此赞语应该成为现代文学学人和史料研究者的座右铭。学者黄平认为关于“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新时期文学”关系的最早论述出现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他说“在十一大报告中发现‘新时期’第一次出现,最早的不是徐庆全。其实并不是什么生僻的材料,就在洪子诚1999年第一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是笔者所见在当代文学研究范围内,对于‘十一大’与‘新时期’的最早论述,也沉淀为当下学界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常识’”[9]。而蒋守谦却用自己早在1995年5月20日发表在《作家报》上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一文中对“十一大”与“新时期”关系的论述来进行反驳[10],孰是孰非,不言自明。第二是对第二手史料重视不够。对于和历史事件、现场、人物、活动等直接相关的史料,常被认为是第一手史料;反之,与其联系并不紧密,只有间接关系,或仅有某种牵连的史料,常被称为第二手史料。人们往往重视第一手史料,而对第二手史料却不够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如战乱、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原因,再加上现代文学史料大多是以纸张为介质的,许多人物、事件、活动等的第一手史料不足或严重缺乏或已经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二手史料的利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还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它们的分类标准也是相对的,需要根据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具体条件进行分析。在一种情况下是第二手史料,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变为第一手史料。只要能够还原历史现场,揭示历史真相,任何史料都是极有价值的,因此不应该厚此薄彼。“文学史叙述的主要任务,是使过去的历史得以复活。”[11]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管第一手史料还是第二手史料,只要能“胜其任”,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分轻重。
参考文献:
[1]张先飞.王森然《冰心女士评传》考释及其他[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11):170-181.
作者:张纪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 上一篇:卫生纸造纸机真空系统节能降耗范文
- 下一篇:戏曲元素对小提琴艺术的启示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