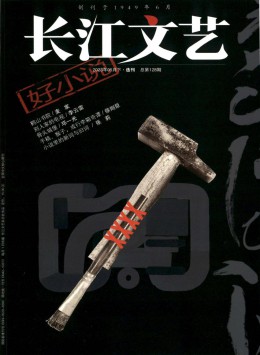文艺功利观的反思

随着文艺的发展和各种体裁的完整化,文艺的功利性开始提到理论的层面进行探讨。早期的论述仍将文艺的娱乐功能放在首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主张文艺的功能就是快乐:“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而且认为:“不应追求一切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2]苏格拉底则是将美善统一作为文艺的最高功用:“每一件东西对于它的目的服务得很好,就是善和美的。”[3]8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早期文艺功利观的集大成者,他在《政治学》中指出:“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1)教育,(2)净化,(3)精神享受,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4]古罗马的贺拉斯也认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5]古代哲人所提出的不论是“高尚”也好,“服务得很好”也罢,还是“对生活有帮助”等,其实,已将文艺的功利性加以明确指出,只不过更多是精神与审美方面的,尚未政治功利化而已。
我国将文艺功利观与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的论述比较早的是古代的大音乐家师旷:“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左传•襄公十四年》)就是说,早期的诗歌具有对政治进行批判箴谏的价值功用。这就是孔子后来提出的“兴、观、群、怨”中之“观”,因为统治者从中可以考察政事措施之得失,“以补其政”。这一点对后世也有长远影响。“箴谏”在后来发展为讽谕说,影响更为深远。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贯穿文艺发展史上的功利观,始终在政治道德教化作用和娱乐消遣作用互相排斥或互相影响的关系上左右摇摆。拿西方为例,前者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他认为诗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崇高的”“政治和道德信仰”;诗是使“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的“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6]等,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后者如意大利的卡斯特尔维屈罗,他就明确反对文艺的教化功能,“诗的发明主要是为着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一般人民大众”,“主要地为娱乐、而不是为教益”[3]194。这种种观点虽相对立,但因站的角度不相同,也大致反映出文艺发展的价值规律,即文艺功利观的多层次化、多阐释化与多元化,都从不同角度指明文艺功利观的社会内涵与审美内涵。
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我国,由于社会的激烈动荡,文艺功利观的天平明显向政治化倾斜。高倡文艺具有认识现实功能的梁启超,同时也极力夸大小说的价值功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7]当然,这里梁启超用一种偏激的语言,目的是达到一定的修辞效果。但在改良运动时期,将文艺纳入政治功利性体系的急切性和紧迫性也显而易见。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普利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他十分重视文艺的功利性。这对后来的列宁、斯大林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列宁,他的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要像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著名论断;他的关于列•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评论,都在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大旗上标示了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20世纪30年代苏联“拉普”派文学和我国的左翼文艺运动,都是文艺政治功利观的最好体现。发展到的经典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以鲜明的无可辩驳的政治功利色彩,取得了文艺功利观的正统地位。历史实践证明,在波谲云诡的革命时代,鲜明的政治功利观配合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事业,促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顺利发展,其历史价值和地位是难以抹杀的。
观念反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人类因为在其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所以我们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性,并感觉到必须维护它。”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说过:“我是欲望的主宰,而你是欲望的奴隶。”这些都说明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就是能够将自身的意志和思想投射到所有对象上,使整个可以反思的对象成为“人化的自然”。西方哲学家大多是通过对人性的经验事实的描述,来建构其社会功利观体系的。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把人看成“能感受到刺激的生物、知觉的感受者”。边沁更是明确地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功利原则承认人类受苦乐的统治,并且以这种统治为其体系的基础”。因此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求乐避苦,人的行为目的不外乎追求幸福和快乐,行为对象是那些能带来幸福的外物,也就是利益(功用)。而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人性是“人———自然———社会”相关联统一的产物,是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的统一。人性是在社会生活中成熟并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是人性的主要表现。人身上的自然性也是以社会化了的形态呈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功利观也是放置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来全面考察的。不仅对无产阶级文学如此,就是对古希腊神话,对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也都是如此。比如恩格斯就特别喜爱《德国民间故事》一书,并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它的价值功用,就在于培养人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们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8]401。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说得更为具体:“所谓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即是使艺术作品具有评判生活现象的意义的倾向,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乐于参加社会斗争的决心,是在社会上大部分人和多少对艺术创作真正感兴趣的人们之间有着相互同情的时候产生和加强的。”[9]829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概括地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归根结蒂取决于他的内容的比重。”[9]836
文艺的功利观并不等同于文艺的政治观,尽管其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以我国的古代文论为例,可以明显看到一条文艺功利观逐渐趋同于文艺政治观的传统。孔子曾提出诗歌有着“兴观群怨”的功能,但他要求学生学诗的最终目的却又是“事父事君”。这可以说是在自觉地倡导并实践着文艺为政治伦理化服务。即使孔子的文艺美学观点,也是从政治主体之美出发,如他所赞的《韶》是歌颂舜的音乐,是对仁德为本的“揖让”政治的肯定。至于商鞅提出的文艺要为耕战服务,韩非提出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些主张,也都强调着文艺的工具角色。而产生于汉代的《乐记》,则受董仲舒所宣扬的神秘化和政治化了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论的影响,提出了“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记•乐本篇》)很明显地把乐(文艺)看做是与礼相配套的,是与政和刑同样重要的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之后像刘勰的“原道宗经”;孔颖达的“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梁肃的“文章之道与政通”;韩愈的“文以载道”;李觏的“治物之器”;直到顾炎武的“明道”、“纪政事”等,一条政治工具论的主线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非常清晰的。正如刘淮南先生所指出的:“文艺的政治功能也就被更加狭隘化、极端化了。”[10]
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在阐释文艺功利性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属于艺术的独特的审美属性。即在文艺创作中,艺术家不应当把倾向特别指点出来,也不必要把他所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要让它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流露出来,而且“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8]462。所谓“隐蔽”,就是把作者的见解隐蔽在艺术形象之中,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去体会。读者从作品中体会出来的内涵越多,得到的审美享受也越多,从而艺术价值也就愈高。艺术的消费者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独特的审美渠道,来走进艺术世界,从而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并精神变物质地去改造自我、改造世界。因此文艺的功利性不是直接的、实用的,而是间接的、精神化了的。
文坛走向
从苏联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政策,到我国的“左翼”文艺运动、的《讲话》,以及建国后的历次文艺斗争和争鸣,文学艺术的政治工具论,始终是革命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期,文艺功利性的外化、物化,乃至政治化,参与整个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论家,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功利性都有精辟论述。但文艺毕竟是文艺,随着那个斗争年代的过去和新时期的到来,我们强调其功利性,更多地是看其作为文艺本质属性的存在,对整个现存社会的整合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主义文艺2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即过去实用的政治功利性已开始转化。这是一个新的趋向,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有两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走向。第一个走向是文艺市场功利观的形成。文艺市场是社会主义文艺传播中的重要途径。我国现阶段的文艺市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即以商品形式向人们提供文艺产品和文艺服务的场所;通过文艺市场可以让文艺产品的艺术价值,达到文艺传播的目的。文艺市场的建立,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文艺功利性的直接化和物态化(比如说消费者须用货币的形式来交换接受文艺产品的权利)。其实这不是问题之所在,就是在古代艺术产品的消费也是要付费的,只不过渠道不同罢了。文艺市场化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沟通,特别是强调了接受者(消费者)在整个文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接受者不是被动地感知对象,而是整个文艺创作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是阅读和产生意义的基本要素。事实上,没有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完全无视接受者的存在。“每一部文学原文的构成都意识到它的潜在的读者,都包含着它写作对象的形象。”[11]不论是书刊市场、影视市场、还是音像市场、演出市场等,文艺产品的生产者始终将消费者作为自己进行全部创作活动中最重要的伙伴和参照系。这从理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上,从社会主义对文艺的要求上,都是无可厚非的。文艺市场功利观的形成,是社会和文艺发展的大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完全不必惊叹。我们惊叹的可能是来自另外一面,就是文艺世俗化、文艺弱化的倾向,这是发育尚不太成熟的文艺市场功利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我们认识到文艺世俗化倾向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曾长期生活在宗教般的社会氛围中,被政治功利性熏陶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后,渴望“潇洒走一回”,渴望尽情地享受人生,满足不能满足的欲望;因此,世俗化倾向在冲击传统的经院哲学和保守观念方面具有一定作用。[12]但对创建精神文明,重塑民族灵魂,特别在弘扬崇高的艺术精神,确立主流审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诸方面,又有值得我们思考和担忧的一面。
第二个走向是接受体验功利观的形成。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潜在的功利,或者说是无功利的功利,但与我们所说的审美的超功利性又有着质的不同。审美的超功利性追寻着审美“意义”的形成,即从物态化的功利性转入精神的功利性。但接受体验的功利性,则只是沉溺于所谓的体验“过程“,不去进行话语“意义”的追寻。比如无情节、无主题,乃至无结构,包括一些“另类”文艺、网上虚拟文艺等。好像只有如此,才可拒斥“媚俗”倾向,才称得上真正的文艺或“纯文艺”。如果说世俗文艺还重视一些感官的体验的话,那么这一类文艺似乎连感官的体验也不屑一顾,只能是一种“接受”,使传统的接受只剩下一个无规则“游戏”的外壳罢了。当代文坛这些种种不同的文艺功利观,是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期下所遇到的新问题,但又是文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前,我们仍处在一个社会体制的转型期,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泥沙俱下,必然会使一些原先我们就倍感困惑的文艺功利观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掘进与重建
社会主义文艺的功利性,完全不排除文艺的娱乐功能;恰恰相反,“寓教于乐”说,既是文艺接受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功利性的基本要求。其实,任何社会形态的文艺都具有功利性,只不过是间接功利与直接功利的区别罢了。我们所说的“超功利”、“无功利”不过是相对而言,绝对的“超功利”、“无功利”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仍然反对“急功近利”式的功利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这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当代社会,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对于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处理好舆论导向与文艺的特殊表现、精神内省与政府管理、文艺自律与社会制约的辩证关系,包括对主流文艺思潮的监督与改善,营造宽松的文化环境;处理好文艺的娱乐功能、宣泄功能与社会批判功能的辩证融合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功利观应该充分汲取和正视市场经济所给精神文明带来的一些暂时的负面效应,既肯定在艺术生产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有机沟通可以刺激艺术生产的良性循环,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黄色的、粗糙的、格调不高的文艺作品往往能获得比高雅之作更好的经济效益。这就说明文艺消费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提高。“媚俗”文艺的后果,则是为低劣文艺提供了市场,诱发了一些文艺家和书商的私欲,使文艺界的精神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这都印证了实用功利观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弊端。因此,高尚的精神需要弘扬,高雅的艺术作品需要扶持,应成为我们重建健康纯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功利观的必要措施。掘进与重建需要开阔的视野。
总之,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当代中国的文艺事业也呈多元化、多极化、多媒化的趋势,网络文化、影视传媒的冲击,以及“纯文学”的再度复兴,使文艺的“功利性”问题更加敏感与突出。通过对社会主义文艺功利性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文艺功利性的特殊表现,在社会主义文艺宏观的理论框架下,主观的无功利性与客观的功利性,显在的无功利性与隐性的功利性,形象的无功利性与抽象的功利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现代社会和新时期文学对我们以新的要求,也是文艺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的真切呼唤。文艺就是文艺,在它真正而全面体现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质时,其价值才能同样得到真正而全面地实现。(本文作者:李建东 单位:南通大学)
- 上一篇:小议马尔库塞视域中艺术的政治潜能范文
- 下一篇:艺术设计的全球化研究范文
相关文章阅读
精选范文推荐
- 1文艺
- 2文艺作品意识形态
- 3文艺作品的价值
- 4文艺作品的特征
- 5文艺作品的要求
- 6文艺作品赏析
- 7文艺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 8文艺创作人才工作计划
- 9文艺创作总结报告
- 10文艺培训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