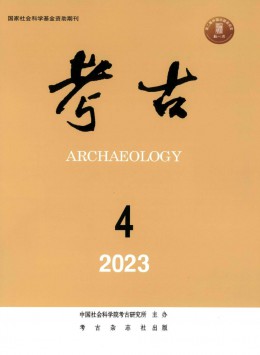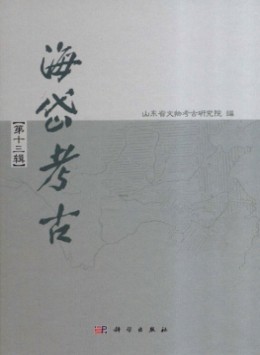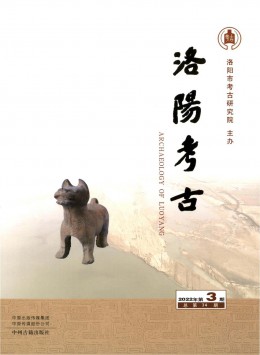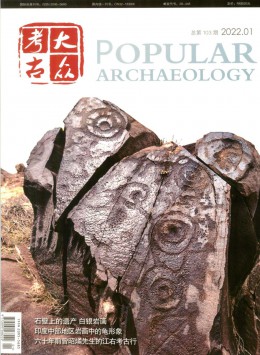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2009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发起,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科技与考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和融合”的研讨会。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的30余名著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在回顾了中国科技考古的骄人成绩外,还谈到了科技考古所面临的困扰。主要包括科技考古没有“名分”,研究人员面临申请科研项目和经费的巨大困难,也不能作为一个专业招收合格的研究生,没有项目、样品、经费和人才支撑的科技考古工作处处举步维艰(3)。
科技考古涉及到多学科交叉,这自然会涉及到研究项目申请时学科定位的尴尬问题。而且学科交叉所参与的学者本身专业背景不同,关注的问题也会存在差异。以往,当考古学者有求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时,科技人员往往作为陪衬或辅助人员参与考古项目,比如年代测定或环境研究。而其成果也常常被作为研究报告的附录以供参考。而对考古学感兴趣的科技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未必受到考古学者的同等关注甚至获得业内的认同。结果,科技手段可能并未能够恰到好处地用到解决考古学的重大问题上。
中国科技考古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像当代欧美考古学那样,像过去的类型学和地层学方法那样,将各种科技手段作为常态或规范研究程序来解决各种科学问题。这样科技考古不再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成了考古学的规范程序。考古学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纳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过程,而科技手段的发展和提高与这门学科发展息息相关。这首先需要考古学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而科技工作者也要了解考古学探索的方向和难题所在。如果两者对对方的想法了然于胸,并对考古学探索目标能够达成共识,这就能拧成一股力量来推动科技考古研究的进展。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培养各种跨学科的复合型考古人才,不必再像现在,考古与科技仍是两张皮,考古学家只考虑器物和年代,让科技专家做些辅的检测工作,这样的合作难免貌合神离。
本文想对科学技术融入考古学的历史过程作个约略的回顾,并对科技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科技考古并非是用拿来主义,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手段简单撮合的问题,它还涉及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设计。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将科技考古常态性地融入所有分析研究之中,使得科技考古最终成为考古研究的主流。
历史回顾
考古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这门学科最早是在西欧确立的。考古学是从古物学脱胎而来,其形成过程受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影响很大。地质学的均变论为生物进化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进化论的普及才能使考古学这门学科突破六千年的圣经纪年,进而探究人类漫长的史前史。为了探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地层学和类型学便成了确定人类文化遗存年代的主要手段。汤姆森的三期论首先确立了一种不求助于文献的独立断代方法,成为考古学与古物学的分水岭。
在考古学发展的初期,困惑学者们的主要问题是考古遗存的年代。因为不知道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或它们孰早孰晚,考古学的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于是,在绝对年代测定出现之前,考古探究的主要精力大多集中在年代学问题上。而解决的办法采取了两条路径,首先就是汤姆森根据器物的材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前后,确立了石、铜、铁的前后发展阶段。而后,汤姆森又根据器物的形制或风格,将青铜时代的石器以及将铁器时代的青铜器和石器区分开来。其次,就是借用地质学中的层位学方法,确定物质遗存埋藏时间的早晚。
在放射性碳技术出现之前,欧美的类型学发明了器物排列方法(seriation)来为遗址和墓葬相对时代排序,同时采用交叉断代的方法,将没有文献的欧洲史前阶段与有历史纪年的埃及编年史联系起来,在欧洲和近东建立起一个大致推算的绝对年表。此外,从1905到191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利用冰川湖泊纹泥和孢粉建立起大约12,000年的绝对年代,并将其与历史纪年联系起来。1894年起,美国天文学家安德鲁•道格拉斯开始研究太阳辐射对地球气候和树木生长年轮的影响,这一方法在1912年开始用于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史前遗址中建筑木料的绝对断代,将该区域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后来,西北欧利用橡树年轮将当地史前史上溯到公元前8000年,而德国利用松树年轮,将当地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0,000年(4)。
考古学的革命性变化发生在1950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的放射性碳断代方法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绝对年代的测定方法。这一科技成就是二战美国军用核技术的一个副产品,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全球适用的断代技术。之后,该方法对其他放射性断代方法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裂变径迹法、铀系法、钾氩法等测年方法纷纷问世。再加上含氟量、黑耀石水合法、古地磁、电子自旋共振、热释光、光释光等等不同测年技术的诞生,为考古学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测年方法。这些方法不但将考古学家从类型学断代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他更加重要的问题,而且精确的年代测定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加细致观察和分析文化的变迁,探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原因。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探究主要局限在探究谁、何物、何时与何地等问题,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则提出了为何和如何的问题。新考古学对文化历史考古学描述性和编年学方法表示不满,认为考古学不应局限于历史学的描述和编年,必须像科学一样来探究造就文化变迁的原因。新考古学提倡在考古分析中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以明确的问题导向提出假设,用严谨的科技分析手段来进行检验。过程考古学采纳了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从文化功能观和人地关系来观察文化的变迁,将文化看作是人类对局部环境压力所做的功能适应。于是,文化变迁的动力被认为主要来自生态环境的影响。于是,环境考古学成为过程考古学的主要方法。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比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与国家起源等战略性课题,成为考古研究的基石。在这一研究取向的激励下,各种科技手段蓬勃发展起来。这些科技手段的运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地学,涉及地质学和土壤学的环境研究;植物学,涉及利用植物、孢粉、植硅石、树木年轮对生态气候的重建;动物学,涉及哺乳动物、鱼类、贝类、昆虫等生物链的重建;人类,涉及墓葬、病理学、食谱和遗传学的研究;器物和原料,涉及石、陶瓷和金属等工具的生产和使用。
环境考古环境考古是考古科技中多学科交叉表现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它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比如,以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研究为例,考古学家需要有详细的动植物知识,对气候条件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并要掌握人类生计和食谱的信息。如以文明兴衰研究为例,环境研究可以为玛雅文明、复活节岛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提供深入的洞见。环境考古首先在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冢研究中开启先河,随后在瑞士的湖居遗址和北美的贝冢研究中采纳。1949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对中石器时代斯塔卡遗址的发掘采取了环境重建的方法,为在欧洲推广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榜样。目前,环境考古是考古科技的一项主要目标,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从全球气候到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的昆虫和细菌。正如美国考古学家丁考兹(D.F. Dincause)所言,环境考古的意义在于,如果不了解自然和生物学背景,就无法了解人类过去生活的各种状况(5)。
环境变迁与气候密切相关,更新世是冷暖交替剧烈的冰川时代,这种气候环境对人类起源和演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冰川后期的气候变迁与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关系密切。虽然长期的气候变迁十分重要,但是短期波动对人类生活也影响巨大,特别是以特定农作物和牲畜为生的农业社会。
地貌和土壤对于重建古环境十分重要。地表的土壤堆积、岩石露头和河湖水源的分布决定了动植物的类型和分布,以及人类觅食活动及农耕活动的条件。但是,目前土壤的分布以及农业经济的潜力可能与古代不同。土壤科学需要勘查地层的剖面,以分辨被侵蚀活动或后来土建活动所掩埋的古代地面。特别当人类不断砍伐山上的森林以拓展耕地,水土流失就会掩埋河谷底部原来的农田和聚落。分辨不同类型土壤,也能够了解人类对环境的扰动。比如褐土是林地环境的典型土壤,只要林木生长,土壤就十分稳定。但是伐林开荒后,降雨的淋滤过程会导致土壤退化,结果变成贫瘠的不毛之地(6)。
植被是区域环境变迁的一个很好衡量指标,除了充分利用大型植物遗存如种子、木头和叶子外,孢粉和植硅石被广泛用来重建古环境的变迁。而动物群一直是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收集和分析各种动物的骨骼,并统计它们的数量。最初,动物群研究纯粹是从年代学和气候环境角度来分析的,后来这些材料成为研究人类生计和经济变迁的重要内容。考古学家研究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季节性变化和丰富程度,以了解古代人群的觅食策略和聚落形态,这种研究对于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经济过渡尤为关键。当一处遗址或一个区域的植被历时变迁被构建起来之后,加入动物群、聚落分布和器物工具等资料,就能对该地区古代人类的生计和物质文化功能做出比较准确的解读,并能够重建人类经济、技术和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的具体演变轨迹。但是,动物群分析需要仔细研究动物骨骼的堆积动力,不能将它们看作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这就产生了埋藏学和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领域,将人类活动与自然动力比如食肉动物造成的骨骼堆积区别开来(7)。为了从遗址中尽可能提取所有动植物材料,浮选法或水洗法被用来收集微小的植物种子和小动物骨骼。浮选技术的应用,对农业起源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在对伊朗阿里科什遗址发掘之初,认为植物遗存很少,人们生计仍然以狩猎采集为主。两年后采用了浮选技术,从整个文化层中发现了四万颗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彻底改变了对近东农业起源的认识(8)。而区分野生动植物物种和驯化物种也是一个需要用特殊方法分析的领域,因为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不可能通过鉴定少数样本的特征就可以获得对这一过程的充分认识。
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开始加大对水生资源的利用。到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鱼类和贝类成为广谱经济的主要利用对象,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大量的贝丘遗址。鱼类的骨骼较小,需要通过水洗来收集。与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相比,鱼骨保存的几率要低得多。因此有可能低估一个遗址中对鱼类资源的利用。许多鱼类都有耳石,能够留存下来以供鉴定。有些鱼类如鲶鱼鳍的椎骨,能用显微镜观察其生长线以估算其年龄及其大小。从一些鱼类可以推断其栖息地的水域环境,甚至捕捞的季节(9)。有些海滨和湖畔的贝丘遗址几乎都是由贝壳堆积而成,贝类作为食物资源的潜力比较容易计算,由于其卡路里能量较低,所以虽然其看似数量巨大,但是可能仍不足以作为主食或全年供养较多的人口。一头赤鹿提供的卡路里相当于52,267只牡蛎或156,800只蛤(10)。不同贝类栖息地的水深,可以指示捕捞的范围和强度。贝壳生长线的观察,可以指示是全年还是季节性采集。比如,对丹麦一处贝丘遗址的观察发现,中石器时代先民主要在春天捕捞牡蛎,而新石器时代先民捕捞的时间更长,一直延续到夏天(11)。但是,有时在内陆遗址发现一些贝壳,则未必作为食物。大的贝壳会作为容器和工具,甚者作为仪式用的号角。小的海贝常常被用作装饰品甚至货币。周口店的山顶洞出土了用作饰件的海蚶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6800多枚产自南海的海贝,三星堆祭祀坑也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贝类显然是远程交换的奢侈品,具有特殊的文化或宗教象征意义。昆虫在指示环境变迁、过去人类的生活条件、食谱和健康方面信息具有较大的潜力。
人类骨骸更新世的古人类骨骸极其珍贵,可以提供人类起源和体质进化、物种差异的信息。全新世人类骨骸出土成倍增加,过去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一般观察一下性别和年龄,现在采用高新技术,考古学家可以从人骨中直接获得其当时生活状况的信息。
首先,通过检测骨骼中的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可以了解古代人群的食谱。比如碳同位素13C/12C比值可以指示主食的类型和来源,氮同位素15N/14N比值较低指示农业为主的经济,而比值较高指示一种以海洋资源为主的经济。而微量元素锶则是素食和肉食比例的有用标志,这种测定往往可以在没有其他动植物遗存的情况下,直接了解人类的生计及经济形态的转变。
其次,人骨的病理学和法医学研究可以了解过去人群的身高、营养状况、劳动强度、暴力创伤、寿命和疾病。理想的话,病理学研究与其他考古信息结合起来,可以详细重建过去人类生活状况的细节。有时,单一遗址就能提供经济变迁的重大信息。比如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边的阿布胡赖拉遗址起先由狩猎采集者居住,后来由新石器农人居住,于是对这两个阶段的人群能够直接做病理学的比较。证据显示,新石器时代妇女,因长期跪着碾磨谷物,导致关节炎和膝盖和拇趾的损伤。此外,长期负重、暴力和战斗也会留下过量运动导致的损伤(12)。
还有,遗传学的DNA技术利用分子钟来破解人类的遗传密码,它不仅可以区分性别,而且可以追溯现代人的起源、族群的渊源和迁徙,因此可以解决物质文化无法分辨的族群问题(13)。线粒体DNA可以追溯母系的渊源关系,而Y染色体可以追溯父系的渊源。DNA技术近二十多年来成果斐然,为了解现代人的起源和扩散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就被认为可与人类登陆月球相媲美。
器物、原料和工艺岩石学方法可以分析石、玉和陶器的成分和结构,这些岩石和陶片的切片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知道组成的矿物以及地质来源。金属器物也能同样做金相学的显微观察,了解金属生产的主要阶段,以及区分细微的铸造过程。它还能揭示铜器是否经过冷加工处理或低温退火处理。对铁和钢的金相分析,可以识别锻铁和渗碳,了解金属冶炼的工序,并揭示古代工艺的无数奥秘。
痕量元素(trace elements)是指器物或原料中的微量杂质,采用光谱测定法(spectrometry)可以加以探测和测量,它们对于追踪原料产地极其有用。这种方法在特征化(characerisation)研究中十分关键,这是一种为石器、玉器、矿石和陶土原料产地提供个别“指纹”的方法。此外,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技术、等离子发射光谱法和粒子诱发X射线荧光分析(PIXE)都是一些无损伤的探测技术,可分析少量样本中的痕量元素。对于了解古代人类的生产活动、交换、贸易,这些技术能够提供极其重要的信息。
考古学家现在常常采用微痕分析来了解石器的使用痕迹、骨骼上的工具切痕或动物齿痕,以了解工具如何使用,以及人类对肉食的利用。比如,美国考古学家发现非洲早期人类遗址和周口店遗址中的一些动物骨骼上,石器的切痕总是覆盖在动物的齿痕之上,表明这些动物并非是古人类自己猎获的,而是通过尸食或腐食来获得肉类。微痕观察后来衍生出器物的残渍或残留物分析,通过生物、化学(如气相色谱)、免疫、微观形态观察等多种现代手段识别石器和陶器上残留的古代DNA、淀粉颗粒、植硅石、蛋白质、脂类、炭化物等,以了解工具使用的对象和人类的生计。比如,加拿大考古学家托马斯•洛伊(T.H. Loy)采用免疫学方法,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史前遗址出土的石器上分辨出十几种动物的血渍(14)。我们曾将跨湖桥遗址出土带有锅巴的陶片,请复旦大学拉曼光谱实验室检测其化学分子结构,结果发现了脂肪和植物的残渍,表明当时可能采取一锅煮的烹饪方式(15)。现在,磷酸盐分析被用来分辨不利骨骼保存土壤区域的人类居住和活动区,因为人类和动物的脂肪、骨骼和粪便分解后会留下大量的磷酸盐。
现在,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经涉及到各个探索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只是一组方法中的一部分,获得的信息需要解读与整合,以求重建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场景和过程。所以,这需要问题指导下的探究和理论指导下的阐释,作为将不同科技领域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的纽带和桥梁。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真正的科技考古应该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合,这是当代考古学的魅力之一。我国一些学者坚称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类型学和地层学,目前许多学者从事的工作仍然是对器物的分类、分期和分辨考古学文化。其实这些都是二战前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研究范例,因为当时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对考古发现断代和编年,所以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二战以来,考古学与史前学无论在目的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变,考古学家已认识到、并努力克服先前工作中的缺陷,这就是:缺乏知识训练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分析缺乏缜密性,以及阐释方法上的主观性。目前,这门学科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对方法问题的日益关注,并对早期研究结论的怀疑。在研究技术上,则越来越多地从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中吸取方法和手段,并在研究分析上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在考古学术圈里,人文科学已经与实验科学建立起更为稳固和融洽的联系(16)。
科技手段毕竟是各种不同的方法,如果考古学目的是要了解过去,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希望了解什么信息。当今的考古学可谓十分庞杂,林林总总分为不同时段和不同探索领域的专攻。传统考古学仅限于编年学目的,从现在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来看已经显得过于狭隘。过去,中国学者将考古学定位在历史学,希望以地下之材补充文献资料的欠缺,现在来看这样的定位和视野也已过时。当代考古学意在揭示存在于一定时空里不同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并远远超越了文献记载和关注的范围。
作为研究手段的科技方法,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与方法密不可分,理论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设法采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它。如果一位考古学家缺乏理论指导的探索性思维,就不会意识到新技术对他的分析有什么用处,也不会积极开发新技术来解决新问题。同样,一位科技专家分析陶瓷、玉器或金属的成分,如果他不了解并设法去解决考古学探索的问题,对检测结果可能也就只能就事论事。
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为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见下图)。问题和理论主导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指导寻找哪些考古材料或样本;方法和技术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要求采集样本。这三个方面都是彼此衔接,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特定的问题意识,方法的选择和好坏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只能是挖到什么就收集什么材料。这样的发掘往往以典型、罕见、精美和完整的器物为目标。有了理论和问题的指导,采用哪种方法以及创造新方法就有了明确目标,而且田野发掘也对寻求和收集的材料有了明确的选择和要求。所以,在田野发掘中为特定测定技术如碳十四或孢粉采样,必须谨慎和缜密地进行。发掘和记录也必须留意每件器物和每处遗迹的空间位置,以求重现遗址的原貌。
为此,在科技手段日益渗透到考古分析各个领域中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同步增强理论指导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与对科技专家而言同等重要。中国学者向来鄙视理论,认为理论是个人的成见,是将主观想象硬套到考古材料之上的做法。这种将考古学看作是一种“材料科学”、并让材料自己说话的研究其实是很成问题的。正如伦福儒和巴恩所言,虽然考古学研究人类的过去,是一门历史科学,但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材料并不会直接引导我们去思考什么问题,发现的物质遗存自己也不会说话,是现实中的我们赋予其意义的。在这点上,考古学的实践更像科学研究,需要像其他自然科学专家一样收集材料和证据,做实验,构建假设用来解释材料,并用更多的材料予以检验,从而提出一种最佳陈述。考古学家的历史重建也是通过相同的途径才能取得,这种历史图像并不能现成地从材料中自动显现出来(17)。
当今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使得考古学家不仅需要不断增加和改善本学科的技术和方法,而且需要熟悉和掌握那些看起来与自己研究领域毫不相干的科技方法。与其他学科发展一样,考古学的专业化和分工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对于这种学科交叉的趋势,需要从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并列,转向跨学科研究一体化的协调与合作。后者才是科学考古学的最终目标。
皮埃尔•德•拜勾画了多学科向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渐进过程,在他看来,只有当不同学科的合作达到可以说是高度综合的程度,才算是真正的跨学科阶段:
(1)不同学科的学者各自研究同一课题的不同方面。
(2)各门不同学科的学者同时研究同一个问题,并协调各自的工作和成果,并在综合这些成果之后,寻求某种程度上的统一。
(3)研究者共同研究同一个课题,比较各自做出的假设,以批评方式相互评估各自的方法,以求获得一个共同的结果。
(4)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以便更好地认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18)。
在学科交叉的初期,考古学家常常会将其他领域科技专家的工作看作是辅的。在这种低水平的交叉研究阶段,考古学家求助于“辅助”学科,向其他学科专家索求一些资料和帮助,而这些专家也不亲自参加考古调查,甚至对考古研究不感兴趣。将这种学科交叉,称之为“辅助”科学也许是恰当的。但是,在学科交叉中,考古学家更愿意与对考古学感兴趣的专家合作。因为,考古学对他们探索的问题也许同样是一门“辅助”学科。著名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曾对旧石器考古学的学科交叉有一个经典的见解,他说:“在我们自己的学科内,没有哪一门学科是‘辅助’主要学科的,所有学科都是相互辅助的。我们认为,外行的‘咨询’专家是不能胜任的。这个队伍的所有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提及的三个主要学科的专家,即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同时通过能相互熟悉其他学科的问题,并且习惯于进行长期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研究‘整体’,而不是研究的专业划分,这是首要的问题”(19)。博尔德的见解应该适用于所有学科交叉的考古研究领域。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指出,要使考古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性学科,需要对事实真相的锲而不舍的、系统地研究。并且为重现过去的整体面貌,在研究中采取历史批判主义的原则,审视所利用的一切材料,对原始材料的价值和可靠性做不断的检验。今天,考古学已成为了如此广阔的天地,以致考古学多数部门都趋于专业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支团队能够涉及所有方面。因此,当合作研究需要完全不同的学科参与时,这样的协作就会出现困难。理论上说,学科交叉是一项集体的任务,但是考古学的综述则总是一个人的工作,尽管这种综述是建立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个有能力的考古学家不仅必须精通本专业的方法,而且必须受过历史学家的训练,并且对共同合作的其他学科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自己的阐释和综述中,正确地、批判性地运用这些学科提供的研究成果。但是,具备这种广博知识,有能力进行大范围综合的专家并不多(20)。因此,中国的科技考古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结
最近几十年,见证了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与此同时,研究材料也越来越广,种类也越来越繁杂。这使得考古学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发掘比原来更为缓慢,这样才不会遗失和疏漏土壤中包含的任何材料和信息。于是,我们看到,发掘工作过去只不过是挖土的活儿,现在就其需要的细巧和精密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二是我们可以从每件器物上获得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随着考古科技的发展,它正在用比原来少得多的材料做比原来更多的事情。
与此同时,考古学理论也蓬勃发展,引导着考古学家不断探索的新方向。正如巴恩所言,考古学变得像一块海绵,浸泡在各个学科组成的整个海洋中,不断吸收各种理论观念和技术的片段。然而,在考古学的发展中,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并不平衡。由于技术没有国界和阶级的归属,大家都很愿意接受和学习,但理论则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个人的标签。学者选择理论犹如选择党派与信仰,意味着隶属于某个群体或派别。因此,我们会发现,采纳新的理论,要比借鉴新技术和新方法困难得多。比如,我国有些学者对新考古学的理念并不认同,但是在推进新考古学习用的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上却十分积极。然而,虽然采用了与国外相似的方法和材料,但因理论指导和问题意识不同,研究成果也就大不相同。因此,考古学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单凭提升技术就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家自身的观念和指导思想会对这门学科的发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法国史前考古学泰斗莫尔蒂耶为旧石器考古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脾气很坏,经常出言不逊。他主办的刊物总是诋毁其他学者,偏袒自己的学生和盟友。他对所有的新理论都嗤之以鼻,确信任何与他看法不合的理论都是错的。而欧洲史前学者因信服莫尔蒂耶这样有影响学者的见解,长期阻碍了对旧石器时代墓葬、洞穴壁画和尼安德特人的研究(21)。
在上述伦福儒和巴恩所提出的理论观念、方法技术和发掘材料的三角关系中,理论观念显然处于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考古学的发展,首先是观念、理论和看待过去的历史,其次是方法技术和研究问题的历史,最后才是材料发现的历史(22)。为此,我们应该始终在思想观念上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样考古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探索性和不断有新发现的学科,而不是仅仅靠运气来邂逅重大发现的经验性实践和一门仅凭材料积累为特点的学科。
注释:
(1) 王昌燧:《学科进展与展望:蓬勃发展的科技考古学》。《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2) Green, K.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3)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科技与考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和融合” 研讨会会议纪要》。2009年10月25日。
(4) Kuniholm, P. Dendrochronology and other application of tree-ring studies in archaeology. In Brothwell, D.R. and Pollard, A.M.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2001.
(5) Dincause, D.F. Environment Archae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Barham. A.J. and Macphail, R.I. (eds) Archaeological Sediments and Soils: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Management. Lond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Conference, 1995.
(7) Lyman, R.L. Vertebrate Taph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Hole, F., Flannery, K.V., and Neely, J. A. The Prehistory and Human Ecology of the Deh Luran Pain. Ann Arbor: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1996, no. 1.
(9) Brinkhuizen, D.C. and Clason, A.T. (eds) Fish and Archaeology: Studies in Osteometry, Taphonomy, Seasonality and Fishing Methods.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S294, 1986.
(10)、(17)、(22)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1) Stein, J.K. (ed) Deciphering a Shell Midden.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2.
(12) Roberts, C.A. and Manchester, K. 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Brown, T.A. and Brown, K.A. Ancient DNA and archaeologist. Antiquity 1992, 66: 10~23.
(14) Loy, T.H. Prehistoric blood residues: detection on tool surfac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species of origin. Science, 1983, 220:1269~1271.
(15) 陈淳、潘艳、魏敏:《再读跨湖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
(16)、(20)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考古学和史前学》。《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 皮埃尔•德•拜:定向研究。《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2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数字技术;教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2]《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第3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 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著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p#分页标题#e# 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著。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著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著。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著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 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p#分页标题#e# 三、结语 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在上世纪百年历程中已经取得较大成绩,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文献学的不断跟进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已经深入影响了学术界的基本观念,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几大学科中汇成了一股整合性较强的学术力量,为神话考古学和考古神话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和文化起源神话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带有鲜明的学科特性与综合性,因此,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显得极为艰难,尤其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带来了困难。一方面,考古学与文献学在所属学科研究中具有自己的学科取向,同时兼具文献处理与考古实物求证的不确定性和争鸣性;另一方面,神话学受制于多种理论流派,往往更看重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既简便,而且认可度也更高。这也反映出当前神话学者尚未取得太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一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价值观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也难以得到公认。 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拓展,学科融合的努力在部分学者的研究实践中获得了可喜成绩。应该说,借助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新成果,系统、全面地厘清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神话考古研究正在展现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这一研究方法,将引领神话从诗学的高贵与玄妙,转向史学的古朴与敦实,渺远的人类童年记忆,也因之而变成可信的历史影像。
第4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一、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 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 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 结 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 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及随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第5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按认识规律和内在逻辑,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系统、全面地揭示出来,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学一级学科内各专业在校本科生
本科阶段非考古专业的考古学研究生
地方文博单位的业务人员
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
以1970年代中期为界,之前,中国考古学处在一个波浪式的发展阶段。
之后,中国考古学则进入一个持续发展时期。
-田野考古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内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来,各文化区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的建构,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轴和中心任务。
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顺应和指导了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这期间,各大区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学文化得以面世和确立。
以五大区系为例-中原、海岱、环太湖、江汉、燕辽地区。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学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国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问题。
此后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增多。
稍前,张光直在北大、山大举办的系列讲座,介绍了“聚落考古”等欧美考古新观念。
在欧美“新考古学”的影响下,关于国内考古学所处阶段、存在问题的讨论。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办法”正式颁布。
随后,以区域调查和田野发掘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得以开展和实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为主的各大区系,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起来。
此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即从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为中心、以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环境、资源及其互动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考古研究转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会,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门类的新资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进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种有用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续的工作中,获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会的信息和资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内容,就是上述新发展和新情况的具体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进展迅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进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的理解、支持和实践。
区域系统调查,在全国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予以调整和完善。
考古发掘方面的变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会考古研究,体现在考古发掘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可以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发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获资料均为考古学研究之基础。
在上述坚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综合性的考古学研究得以向更为宽广的领域拓展。
第6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计算机技术;考古学;文物保护
现代计算机技术发展极快,不仅在管理、教学、医学、生产等活动中有了广泛的应用,还涉足到考古学,成为了文物考古与文物保护领域中的一种常用探测、管理手段。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的时间很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文物考古学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文物鉴别、文物保存、文物修复以及考古资料管理整理。下面对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文物保护领域中的应用作详细论述。
一、计算机技术在考古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这里的考古资料又指文物信息,文物考古必须借助信息资料,如果信息资料缺少,考古依据也会随之丢失,最终导致考古无据可循。所以在文物考古中,行业人员除了要重视考古技术之外,还要重视考古资料。为了确保考古资料的管理质量,常常会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国内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数据库,后通过管理数据库来管理考古资料。数据库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情报检索系统
20世纪80年代,国内某省某考古研究院研发并建立了一套“考古文献情报检索系统”,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考古文献数据库。早期,该系统能够在考古资料管理模式下正常运行,为考古文献资料管理提供便利,但后来该系统受到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的冲击,到今天已经不再使用。
2、考古资料信息管理系统
考虑到人工管理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还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对考古资料信息的需求,所以国内某某省文物管理部门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门用来管理考古资料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后期发展中不断对该系统进行优化、完善,使其不仅能实现信息管理,还能进行报告编辑,为考古资料管理事业的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条件。
3、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的出现时间为上世纪60年代,是一种基于地理信息管理技术、计算机技术下的空间数据管理系统,能为考古学遗迹查找、探测提供帮助。国内历史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考古时会应用到该系统,利用该系统具备的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来获取文物的空间信息,定位文物。
二、计算机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除了文献资料管理之外,考古研究与文物探测中也会应用到计算机技术。考古研究领域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研究法是文物考古研究领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原理是先将搜集得到的相关资料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纳,后结合归纳结果,对搜集到的各部分资料相互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类型学研究中,最终得到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受研究人员经验丰富性影响,研究人员经验越丰富、研究水平越高,则得到的分析结果越可靠。要提及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多是由研究人员对资料进行分析,主观性强,所以分析得到的结果也具有片面性特点,可能会出现分析失误问题。如果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处理,可有效避免文献资料主观性分析,克服分析结果片面性难题。
2、不同单位间的排序和分期研究中的计算机技术
目前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往往是以一二组典型器物组合或几件典型器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质变环节上的特征为标准,判断其他组合或器物与其相似程度的高低,或与其共存关系的有无,建立一个遗址、一个墓地或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由于考古学意义上的分期其时间跨度多则几百年,少则几十年,所以属于这种分期意义上的同属一期的遗存之间,亦存在着绝对年代的差别。当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向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内部的结构发展时,就会发现属于同一分期之内的各遗存之间的相对关系,其排列的序列等问题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计算机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1、计算机断层摄影
计算机断层摄影主要有: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X一CT)、超声波计算机断层摄影(U-CT)及利用核磁共振的计算机断层摄影(NMR一CT)。由于CT技术的“透视”能力,使我们能对三维物体的内部结构进行精确描述,从而可以定量测定密度分布。
2、计算机辅助文物修复设计
传统的文物修复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文物修复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物修复者的素质。面对巨大数量的需要修复和养护的文物,传统的手工作坊式技术、短缺的修复人才与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十分不相适应。引人现代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技术方法,是文物修复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3、有限元分析法
有限元分析法是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是离散化,即化无限为有限,以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从物理上看,一个由无限个物质微元和结点构成的连续体,可以近似地用有限个在结构点处相互连结的单元所构成的组合体来代表。从而,可以把对连续体的分析变为对单个单元和它们的组合问题的分析。
四、结束语
计算机技术在现代考古学与文物保护领域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其不仅可单独在考古文献资料管理中应用,还能与其他同类技术相结合,形成一种新技术在考古研究中加以应用,为考古学的发展以及文物保护事业的进度提供源动力。在本篇文章中,笔者重点探讨了计算机技术在考古文献管理、考古研究以及文物保护三项工作中的应用,强调了计算机技术对考古学的作用于影响,得出了相关结论,希望对同行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腾铭予.计算机与考古学─―计算机技术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的应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3)
第7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地区的BuracaGrande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和Font-Juveanal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和1100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1]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Downes,J.LingaFiold,Sandwick,Orkney.GlasgowArchaeologyResearchDivisionReport1995.
[3]Buntintg,M.J.,Tipping,R.“Anthropogenic”pollenassemblagesfromaBronzeAgecemeteryatLingaFiold,WestMainland,Orkney.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001,28:487-500.
[4]Figueiral,I.Terral,J.-F.LateQuaternaryrefugiaofMediterraneantaxainthePortugeseEstremadura:charcoalbasedpalaeovegetationandclimaticrecostruction,QuaternaryScienceReviews,2002,21:549-558.
[5]Heinz,C.,Thieabault,S.CharacterizationandpalaeoecologicalsignificanceofarchaeologicalcharcoalassemblagesduringLateandPost-GlacialphasesinSouthernFrance,QuaternaryResearch,1998,50:56-68.
[6]Proesch-Danielsen,L.,Sandgren,P.Theuseofpollen,magneticandcarbonanalysesinidentifyingagriculturalactivityandsoilerosionfromtheNeolithictotheIronAge–astudyoftwolakesedimentcoresfromJearen,South-WesternNorway,EnvironmentalArchaeology2003,8:33-50.
[7]Dumanyne-Peaty,L.LateHolocenehumanimpactonthevegetationofsoutheasternScotland:apollendiagramfromDogdenMoss,Berwickshire,ReviewofPalaeobotanyandPalynology1999,105:121-141.
[8]Pitkaenen,A.,Huttunen,P.A1300-yearforest-firehistoryatasiteineasternFinlandbasedoncharcoalandpollenrecordsinlaminatedlakesediment,TheHolocene,1999,9,(3):311-320.
[9]Adams,J.M.,Faure,H.PreliminaryvegetationmapsoftheWorldsincethelastGlacialMaximum:anaidtoarchaeologicalunderstanding,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1997,24:623-647.
第8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一级学科 挑战 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
第9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46-02
自1995年至2005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呈现出了较多新的特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何种特点?在比较研究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状况?本文通过对发表于国内各类刊物上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归纳起来,其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样化
在十年里,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大约有400篇。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其基本研究态势则表现为,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就研究的广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且在研究的历史阶段上也以先秦时期为主。而这十年研究,则不仅涉及主要思想家或思想著作的政治思想研究,而且还涉及儒、墨、道、法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如兵家、纵横家等的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先秦以外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研究,还涉及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专题的研究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就研究的深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这种研究深度的加大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注重对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发掘,如靳平川的《论韩非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线索》,另一方面则对政治思想做哲学高度的反思和考察,如王楷模、张师伟的《政治思想一般性质的哲学分析》。就研究方法来说,则表现为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仅涉及文献研究法,还涉及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此外,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
(二)研究体现出的冷静思考与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浓厚
由于,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经受过西方现代科学思维和方法的熏陶与训练,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方式的锻炼,因而在考虑问题时更加倾向于理性化思考,再加上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发展,学者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就显得比以往更加成熟,同时也更加冷静,而不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粗略勾勒上。因此,这就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发展,也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研究的鲜明特点。例如,学者张分田的《关于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就体现出了,张分田先生对于民本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冷静理性反思。在该文中作者就指出:“在治学中,笔者发现一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即规范性、制约性、批判性思维很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而相关理论通常都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规范性很强这个特点正是经过历代统治思想代言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形成、发展并广为扩散的。民本思想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1]可见,张分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三)研究以凸现时代价值为主流
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章都富含有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当前时代价值与意义的讨论。这些讨论,要么是通过古今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进而来凸现出当前时代价值取向,如徐惠茹的《“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要么是通过对古代政治思想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挖掘出蕴含时代价值的精神与思想资源,进而能够利用那些对当前时代有借鉴意义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苑秀丽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文章中,以凸现时代价值的研究占有主流地位。
(四)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重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整体上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体现为二者的并重。在综合研究上,既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探讨的,如曹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也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探讨的,如徐大同的《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还有对中国古代政治观进行研究的,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等。在专题研究上,既有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如王宏玲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也有对治国方略探讨的,如刘长江的《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还有对法治思想进行研究的,如江伟的《试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传统法治观》等。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得到了展开。
二、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比较研究方面来说,它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体现,同时也是构成整个研究基本状况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比较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也有利于认识研究呈现出的基本状况。
(一)比较的正当性问题
这主要是涉及占有主流位置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正当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该问题的两类质疑,即:“一是历史向度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二是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2]对此,学者任剑涛在其文章《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对这两类质疑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和逻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辩护的理据,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实践展示的未来前景具有的显示人类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潜力。”[2]180由此,任剑涛对该问题做出了比较有自洽性的说明。同时,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比较的合理定位的见解,即需要两个内部条件和两个外部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说具体是:“其一,我们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价。其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心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进行仔细的解读和分析,进而对于政治思想的历史延续、文本对比和个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2]182而外部条件则是:“一方面是现代的政治理念的认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态的树立。”[2]182这样,他就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而有说服力的阐释。
(二)具体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近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的比较研究情况,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进行梳理。
首先,从形式上划分,可以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纵向与横向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就共时性、横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主要涉及中外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有:任剑涛的《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薛丽蓉的《中西方传统民主观比较》、胡健的《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黄杨的《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郑慧的《中西平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差异》等;同时,这也涉及相同历史时期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的比较,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寿建纲的《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比较》、晓林的《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比较》、刘艳琴和席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等;此外,这还涉及具有相同或相异政治思想的比较,如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同一性简论》和《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赵玉芝的《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刘重春的《试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国家思想之区别》等。就历时性、纵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既涉及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的比较,如张志泽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之比较》,也涉及具有延续性或历史继承性的思想的比较,如汪高鑫的《论董仲舒对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王克奇的《墨子与老子、孔子、韩非关系论》等。
其次,从内容上划分,可以分为人物、著作、政治观点或主张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就人物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来说,涉及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程朝阳、李永伟的《柏拉图、孔子之理想等级社会比较初探——谈“贤人政治”》和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治国主张比较研究》;涉及孟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王显峰、高剑平的《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老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国治的《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墨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振武的《亚里士多德与墨子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涉及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比较的,如孙晓春的《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涉及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黄旭东的《中西古代政治意识文明论——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涉及管仲与梭伦比较的,如李怀国、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之比较》;涉及卢梭与戴震比较的,如胡建、汪震宇的《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等。就著作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是白真清的《从和看中西专制主义》。就政治观点或主张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如陈开先的《民本与民主——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温志强的《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仲崇盛的《伦理国家与道德城邦——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比较》、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政体理论比较研究》、马小红和于敏的《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等等。
参考文献:
- 上一篇:戏剧美术教学设计范文
- 下一篇:大一心理健康教育总结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