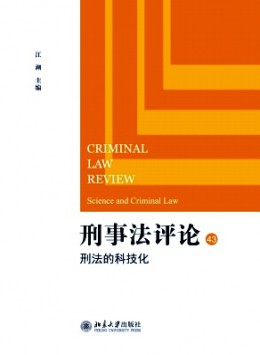刑法法律条例精选(九篇)

第1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无变革。此处以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为比较对象,探索它们对唐律的主要变革及其原因。
一、体例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体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主要是:
1.卷条的变革 卷条是我国古代法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卷条数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法典内容的繁简。一般来说,多易繁,少则简。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定本时为五百条、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载:“(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一卷条数比以往之律大为减损,故《旧唐书·刑法志》说,凡削烦去蠹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诏长孙无忌等撰编律疏,《唐律疏议》,即为三十卷,条数依旧。宋刑统为五百零二条、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条是把唐律的职制律与斗讼律中各一条分为二条,此与现传《唐律疏议》一致。宋刑统在卷条安排上与唐律的主要区别是,变动了一些卷中的条目数。变条数的卷有五,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变动情况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条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条,刑统移末条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条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条,刑统移前四条入上卷。”②还有卷九、十也有类似情况。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条,刑统前移入上卷一条,后移入下卷四条。”③卷条的位移,说明卷中的内容有变,宋刑统就是如此,下文会涉及此。
大明律虽仍为三十卷,但仅有四百六十条,比唐律少四十条。不仅如此,在卷条的分布上,大明律也与唐律有较大的区别。大明律的名例律为一卷,四十七条;唐律则为五卷,五十七条。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条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条则被十一律分享。从这一区别也可见大明律在体例上与唐律有较大区别。
大明律例卷条情况更接近于大明律。它有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条。这四十七卷除增加了律目、图、服制、总例、比引条例等共十一卷外,还把大明律中的一些卷一分为二,如名例律在大明律为一卷,而大清律例则为二卷。其条数比大明律的少二十四条。其中,吏律少四条,户律少十六条,兵律少四条。
从以上三部法典的卷条状况来看,宋刑统与唐律的差异很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比较接近,而与唐律有一定距离。
2.篇目结构的变革 唐律的篇目结构比较简单,仅分为十二篇,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以后唐高宗时撰修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只是在律条后附以“疏议”,起到阐发律意,使人明了的作用,并无更复杂的内容。
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篇中分门,每一门中含有数条律条。共有二百十三门。《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名例律有二十四门,卫禁律有十四门,职制律有二十二门,户婚律有二十五门,厩库律有十一门,擅兴律有九门,贼盗律有二十四门,斗讼律有二十六门,诈伪律有十门,杂律有二十六门,捕亡律有五门,断狱律有十七门。其次,在律条后附以令、格、式、敕条和起请等法条。宋刑统是宋代刑律统类的简称,故除律条外,还附有上述一些法律形式中的相应条款。《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七,起请条三十二。”唐律则无,只是在“疏议”中引用令、格和式的某些条文,来说明律条的内容,与宋刑统另附在后并成一种综合性法典的形式不同。最后,唐律中的“疏”与“议”总是连在一起,不单独存在。宋刑统则常把“疏”与“议”分列,各自阐述自己的内容。其中,“疏”的内容为律条文,“议”的内容为解释文。后者更近似唐律中的“疏议”。《宋刑统·擅兴律》“私有禁兵器”门的“疏”说:“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注云,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与律条无异。“议”说:“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此是对“禁兵器”的解释。尽管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但总体结构仍无重大变化,仍为十二篇,连篇名及排列顺序也与唐律同。
大明律篇目结构的变化较宋刑统要大。因为,它打破了唐律十二篇目的框架,仿效元典章,改用七篇,除首篇仍为名例外,其余六篇均按中央六部官制编目,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故近代学者沈家本评说:大明律“以六曹分类,遂一变古律之面目矣。”④此外,大明律还模仿宋刑统篇下分门的做法,在除名例以外的其它六篇中皆设若干目,并在每一目中又含若干律条。目的分布情况是:吏律中有职制和公式两目,户律中有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和市廛七目,礼律中有祭祀和仪制两目,兵律中有宫卫、军政、关津、厩牧和邮驿五目,刑律中有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和断狱十一目,工律中有营造和河防两目。一目为一卷。每目中的律条不等,如吏律职制目中有十五条,而公式目中却有十八条。
尽管大清律例比大明律少了二十四律条,但篇目结构仍袭大明律而成,变化甚微,主要是:一是在律条后附了例条,有的数量还较多,超过律条。如《大清律例·名例律》的“五刑”条,律条仅为六条,而附例文十八条,大大多于律条。二是在律条中附有注。此注的作用类似唐律中的“疏议”。如“五刑”条规定,“赎刑:纳赎,收赎,赎罪。”在纳赎后有注:“无力依律决配,有力照律纳赎。”在收赎后有注:“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在赎罪后亦有注:“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律赎罪。”经过“注”的说明,把纳赎、收赎和赎罪都区别开了。
以上三部法典的篇目结构显示:宋刑统虽有改变之处,但仍离唐律不远;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十分靠近,但均离唐律较宋刑统为远。
法典的体例只是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与法典的息息相关,可直射内容的轮廓。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体例的改动程度,与它们对内容的改动程度一致。
二、一般原则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把一般原则规定在名例律中,但它们又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取消一些原则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取消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唐律疏议·名例》“皇太子妃”、“官当”、“除免比徒”等条规定的一些原则均被废除。其中,有的是因为已被其它规定所取代,如“皇太子妃”条中确定的“上清”已被“取目上裁”等规定代替,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易起反作用,如“官当”条规定以官品代罚的原则不利于治吏,故弃而不用;有的是因为不适时,如“除免比徒”规定以除名、免官比照徒刑的原则已不适应明、清的情况,所以也在废除之列。
2.合并一些原则 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合并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宋刑统·名例律》“老幼疾及妇人犯罪”条把《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和“犯时未老疾”两条中规定的原则都归并在一起,既规定各种老、小和疾人员犯罪可享受赎、上清、不加刑等特殊处理及不适用这些附加条件,又规定了老疾人员犯罪时年龄、条件的折算方法。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把《唐律疏议·名例》中“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和“死刑二”五条,合并为“五刑”一条,内容基本相同,都规定唐律中五刑的刑种、刑等等。经过合并,唐律中一些较为相近的内容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既避免了条目内容分散的情况,又可使阅律者便于查找。
3.修改一些原则 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的有些原则还被大明律、大清律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首先,续用原律条名,但改动其中的某些内容。大明律和大清律都在名例律中设立“无官犯罪”条,与唐律同,但内容有别。《唐律疏议·名例》“无官犯罪”条规定:“诸无官犯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其有官犯罪,无官事发;有荫犯罪,无荫事发;无荫犯罪,有荫事发:并从官荫之法。”由于明代不用官荫法,故《明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删去有关官荫的规定,为此薛允升有过评论。他说:大明律的“无官犯罪”条“与唐律略同,惟明代并无用荫之法,故律无文。”⑤大清律例除续大明律的修改外,又作进一步改动。《大清律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规定:“凡无官犯罪,有官事发,犯公罪要在处笞、杖以上的,才可“依律纳赎”;“在任犯罪,去任事发”,犯公罪须处笞杖以下的,也要“依律降罚”等,均与大明律有异。还有“以理去官”等条也属此种情况。其次,律条名与内容均有变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皆在名例律中没有“亲属相为容隐”条。与此条对应的是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条,除条名有异外,内容也有所变动。《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明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扩大相隐范围,把“妻之父母、女婿”也列入大功相隐范围,对此薛允升也有评说。他说:大明律的规定“与唐律大略相同,惟妻之父母之女婿缌麻服也,而与大功以上同律,唐律本无此层。”⑥大清律例的规定同大明律同。还有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立嫡子违法”、“赋役不均”等条也属此类情况。
4.增加一些原则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取消、合并、修改了唐律的一些原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原则。宋刑统通过“议”的形式,把原来唐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定,穿插在法典中。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名例律中非是个别,在此仅能举例说明。《唐例疏议·名例》“称反坐罪之等”条规定:“诸称‘反坐’及‘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宋刑统·名例律》“杂条”门不仅照用唐律的规定,还用“议”规定了新:“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流以下止是杂犯,不在除免、加役之例。若至绞,即依例除名。”“七品以上犯在枉法,仍合减科。男夫犯准盗,仍合用荫收赎。”“称以盗、以斗减一等,处同真犯。”吴兴、刘承干在校勘宋刑统与唐律以后也认为,以上内容“唐律无。”实属新增而为。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则在名例律中增加专条,增添新原则。此两律均新设“职官有犯”。“天文生有犯”条,对文职官与天文生的犯罪,作了新规定,采用特殊处理,皆为唐律所无。还有“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犯罪得累减”等条,也是如此。
法典中一般原则的规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国情的变化和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反映,它的改变意味着国家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也随之有变。另一方面,它是法典内容的核心,它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法典内容的变化。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在不同程度上对唐律一般原则的改变,不仅告诉人们宋、明、清与唐的情况与国策不同,也预示它们在内容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变革。
三、罪名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是刑法典,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大量袭用唐律规定的罪名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作了变改。变改情况主要有以下四大类。
1.改变罪名 这是指改变唐律设定的一些罪名。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原罪名的内容基本没变,但称谓有变;二是原罪名的称谓没变,内容有变。宋刑统在名例律的“十恶”中把唐律的“大不敬”罪名改为“大不恭”。原因是为了避讳。“宋避翼祖讳,易‘敬’字作‘恭’”。⑧但内容仍依旧。宋刑统还扩大“恶逆”罪的范围,把道士、女冠和僧、尼杀师主行为也归入此罪。《宋刑统·名例律》“杂条”的“议”规定:“杀师主入恶逆”。此被认为是“唐律无。”⑨纯属宋刑统之为。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也有上述情况。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设有“诈为制书”罪,但内容有别。区别有二:一是后者的用刑重于前者,用斩代绞;二是后者无“口诈传”的内容(前者有),仅指制书诈传。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都设定“不应为”罪,与唐律的“不应得为”有一字之差,但内容无别。
2.归并罪名 这是指把唐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罪名归并为一个罪恶名。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有。宋刑统由于采取了篇下分门的形式,一门中往往有数条律条组成,罪名也随之合几为一,故归并罪名的情况在宋刑统不属个别,在此仅举一例证之。《宋刑统·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中规定的脱漏增减户口罪是把《唐律疏议·户婚》中“里正不觉脱漏增减”、“州县不觉脱漏增减”和“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三条中规定的里正、州县不觉脱漏或妄脱漏增减户口三罪合为一体而成,内容基本没变,都把里正、州县官脱漏或增减户口的行为作为惩治对象。大明律与大清律例的律条皆少于唐律,其中有一部分也是采取归并方式,故也存在归并罪名情况。如《明律·职制律》“弃毁制书印信”条规定的充毁制书印信罪是《唐律疏议·杂律》中“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和“亡失符节求访”四条中规定的弃毁符节印罪、弃毁制书官文书罪,官物亡失簿书罪和亡失符节求访罪等组合而成,内容相差不大。对此,沈家本说:“唐目‘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亡失符印求访’四条,并在《杂律》中,明并为一条,改入此律(职制律)。”⑩罪名者因此相应合并。大清律例的此条情况同大明律。归并以后,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的一些罪名外延扩大,内容也相应增加。同时,罪名数量也跟之减少。
3.增加罪名 这是指增加了些唐律所没有的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根据本朝代的统治需要,增加了些唐律没设的罪名。从这些罪名的来看,主要是调整民事关系和打击有损专制统治的行为两大类。《宋刑统·户婚律》的“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皆是新增。《刑统跋》说:这些条目都属“唐律无”。⑾其中的内容均与经济民事法律有关。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一方面增加一些有关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如它们均在户律中新增了“盐法”、“私茶”、“匿税”等条,严禁私营盐、茶和匿税不纳等行为,违者都要受到处罚,以此来保证国家对盐、茶的专营和税收的收入;另一方面还特别增添了一些有关打击有损于专制统治行为的内容,仅在吏律中就设有“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擅勾属官”、“奸党”、“交结近侍官员”等条,对官吏的活动作出新的限制,并惩治违犯者,以此来强化专制统治,维护皇帝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经过增加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内容得到了更新。
4.弃去罪名 这是指弃去唐律规定的一些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把唐律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弃而不用。宋刑统的内容基本同于唐律,弃去唐律罪名属于个别情况。《宋刑统·诈伪律》“诈欺官私取财”门把《唐律疏议·诈伪》中“诈取官私财物”、“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和“诈除去死免官户奴婢”条中规定的罪名集于一体,独不见“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条中规定的罪名。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弃去唐律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仅在户婚律中就有不少。《唐律疏议·户婚》“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已删去不用。
罪名是唐律和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罪名的变化标志着这些法典内容的变化,而且罪名变化得越多,内容也就变化得越大,这是一种正比关系。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通过改变、归并增加及弃去唐律罪名的方式,变革自身的内容。其中,宋刑统的变革的幅度不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变革幅度较宋刑统为大,变改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改革唐律内容方面,步子迈得比宋刑统要大。
四、法定刑的变革
法定刑亦是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刑法法条皆有罪名和法定刑两大部分构成。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变革唐律罪名的同时,还变革了其中的一些法定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换刑 就是用唐律规定的五刑中的某种刑罚取代其它刑罚或用其它制裁方式换代五刑。宋刑统与大清律例中都有换刑的规定。宋刑统有关于折杖法的规定,即用杖刑来代替除死刑以外刑罚的执行。《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对折杖法作了具体规定。适用折杖法的也不乏其例。《宋刑统·厩库律》“故杀误杀官私马牛并杂畜”门规定:故杀官私马牛者“决脊杖二十,随外配役一年放”;故杀官私驰骡驴者“决脊杖十七放”等。大清律例中有用罚俸代笞的规定。《大清律例·名例律》“文武官犯公罪”条规定:“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文武官犯私罪”条也有类似规定。此外,大清律例中还有用鞭责代笞杖的,条件是旗人犯罪。《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唐律中无这些换刑的规定。宋刑统、大清律例通过换刑,把原五刑的执行灵活化了,尽管它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灵活也是对五刑制度的一种变革。
2.两刑同罚 就是把两种刑罚同时适用于一种犯罪。唐律仅在个别情况下使用两刑同罚,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则广泛使用两刑同罚,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徒、流中加杖。《清史稿·刑法志》载:大明律规定“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具体适用的犯罪也不少,在此仅举一例。《大明律·刑律》“诬告”条规定:“若囚已决配,而自妄诉冤枉,摭拾原问官吏者,加所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清律例中有关徒、流加杖的规定与大明律同。此外,还有刺字与徒、流并用的。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在刑律的“白昼抢夺”条中规定: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计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伤人者,斩。为从各减一等。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两刑同罚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唐律一罪一罚的定制,亦是对唐律法定刑的一种变革。
3.增加新刑种 唐律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另附以没官、连坐等。唐后在此以外,另增加了一些新刑种,主要有:
①杖死。这是一种用杖处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唐律规定死刑为二,即绞和斩。宋刑统认可杖死也为死刑。《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准“十恶中恶逆以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应合处绞、斩刑自今以后,并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
②刺字。这就是过去的墨刑。唐律废而不用。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皆有关于使用刺字的规定,主要适用于一些与盗有关的犯罪。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均在刑律的“窃盗”条规定:窃盗“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
③充军,这是一种将重犯押至边远地区服若役的刑罚。它常适用于一些死罪减等者,用刑很严。《明史·刑法志》载:“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都有关于充军的规定。《大明律·名例律》“杀害军人”条规定:“凡杀死军人者,依律处死,仍将正犯人余丁抵数充军。”充军还有与杖并用的。《明律·兵律》“宫殿门擅入”条规定:“入皇城门内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大清律例对充军作了规范的规定,包括充军的里程发遣部门等。《大清律例·名例律》“充军地方”条规定:“凡问该充军者,附近发二千里,近边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发四千里。定地发遣充军人犯,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抚定地,仍抄招知会兵部。”律中多处适用充军。《大清律例·户律》规定:“诈称各卫军人不当军民差役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其它的不再赘列。
④凌迟。这是一种用刀脔割罪犯使其慢慢痛苦死去的酷刑。此刑在辽时入律,明清都沿用,适用于一些最严重的犯罪。《大明律·刑律》“谋反大逆”条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杀一家三人”条规定:“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大清律例的规定与以上同。
此外,还有枭首等,在此不一一罗列。以上这些刑罚皆为唐律无,也不列入五刑范围,成为一种五刑之外的律中之刑。为此,薛允升很不满意。他说:“唐律无凌迟及刺字之法,故不载于五刑律中,明律内言凌迟、刺字者指不胜屈,而名例律并未言及,未知其故。”“复枭首、凌迟之刑,虽日惩恶,独不虑其涉于残刻乎。死刑过严,而生刑过宽,已属失平”。⑿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刑制的改革不仅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唐律的框框,还有用刑渐重之势。除折杖法外,无论是两刑同罚,还是增设的新刑种,均酷于唐律规定的五刑。用刑是用法的测量计,用刑渐重直接反映用法的加重。它可帮助人们知晓宋、明和清刑事立法的概要和趋势。
五、变革的原因
既属上层建筑,又是国家意志,它的变革必有多种原因,唐后对唐律的变革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1.情况的变化 法律是一种应时性很强的统治工具,社会情况的变化是对其进行变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法律不适时,就会变成具文,失去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唐律的内容虽然很周全,集了古者立法之大成,但是唐后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有些内容不同程度地落后于现实,有的甚至已无存在的意义。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便本能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立法权,删改损益唐律的内容,制订新律,以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在这方面,有关民事方面的内容十分典型。唐律定本于唐前期,其中有关经济民事的规定以当时施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出发点,并以维护、执行这些制度为目的。可是到了宋、明、清,一方面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早已废除,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很大,资本主义萌芽也已露头,唐律中原有的一些规定显然已经过时。因此,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删去了唐律规定的“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目,废弃其中无用的内容。同时,根据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新增了一些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打击破坏经济秩序和有损正常民事活动的犯罪行为。宋刑统增设“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中的一些内容都直接有助于调整公民的财产关系,以适应当时日益发展的继承和典卖的需要。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特别设立“盐法”、“私茶”和“匿税”等条,确立国家对盐、茶等的专管和对税收的严格控制严惩违犯盐、茶法和税收规定的犯罪行为,维护当时的经济秩序。这些都是唐后社会的必然产物。唐律制订时,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其它一些内容的变革也都与社会情况有极大的关系,在此不一一列举。
2. 立法经验的结累 立法是一种国家职能。由统治者主持制定,因此他们的立法经验对立法的关系极大,它也是法律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注意前人立法之得失,并根据本朝代的特点,变改唐律一些内容,使之更好地为己所用。我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三典”之说。《汉书·刑法志》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但以后的立法实践所产生的效果却各不相同。商鞅用重法,秦国大振。秦朝用重法,二世而亡。汉、唐初用轻法,得人心,国兴民安。南朝梁武帝用轻法,“每年数赦,卒至倾败”。⒀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前人用法的经验和教训,并正视了自己所处的条件,认为虽是新邦,仍需用重典。历史上也有他们用重典治国的记载。《宋史·刑法志》载:“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这在宋刑统中亦有反映,用杖死这一酷刑就是一个方面。朱元璋执政后,也主张用重典。他曾说:“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⒂大明律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者,故新增之刑无一轻于五刑,且全为酷刑。大清律例与大明律相差无几。因此,薛允升在比较了唐、明律后认为,大明律有重其所重之处。其实,这一“重”正是明初的统治需要,因为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大明律重典治国,明初的政权会得到巩固并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会有较大吗?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明律相对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不能简单理解为“重”,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否则,历史将会改写。当初用重典,既是统治者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总结和借鉴前人立法经验的结果。
3.立法技术的提高 立法是一个把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技术很重要。高的立法技术,可使制订的法律准确地反映统治阶级的要求,符合的需求,并为司法提供正确依据。相反,法律就会歪曲反映统治者的意志,甚至破坏法制的协调,造成法制混乱,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我国古代的立法者大多重视立法技术,立法技术也因此而不断提高。从唐律到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体例的发展和变革过程,可以看到一个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唐律十二篇,内容简要明了,而且名例列入篇首,集中了前者立法之精华,立法技术高于以往。但宋的立法者并没停止不前,他们制定的宋刑统在篇下分门,分门别类,还在律条后附以其它法律形式的相关内容,以类相聚。这给查律者带来方便,易查易找,一目了然。宋刑统在立法技术上确有高于唐律之点。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不仅一改唐律的篇目结构,还减少律条,使用较少的律条规定一样需要的内容。另外,它们还在篇目下分条,既有律篇下分条的长处,又有宋刑统篇下分门的优点,使这一体例更接近于刑法典章、节、条的体例结构。明、清又在立法技术方面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立法技术的提高同样成为变革唐律的一个原因。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虽对唐律进行了变革,但仍保留着唐律的指导思想和大量的内容,唐律的处处可见。另外,它们的变革也是以唐律为基础的变革。没有唐律,不可能有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这从又一个角度证实唐律的深远影响和它在我国古代立法中的重要地位。
①②⑧《宋刑统》第514页,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下同。
③《宋刑统》第515页。
④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1129页,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下同。
⑤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名例律》“无官犯罪”条。
⑥《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
⑦《宋刑统》第518页。
⑨《宋刑统》第519页。
⑩《历代刑法考》第1830页。
⑾《宋刑统》第508页。
⑿《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五刑”条。
⒀吴兢:《贞观政要·赦令第三十二》。
第2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法外用刑与《大明律》的修订
有明一代,《大明律》是根本大法。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花费三十年时间修订完成。朱元璋修订《大明律》的过程显得有些矛盾。朱元璋显然非常重视法律。在大明皇朝正式建立之前一年的十月,他就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开始《大明律》的修订工作。新年,大明朝建立,年号洪武。洪武元年正月就有《大明律》正式颁行天下。但是朱元璋对这一版的《大明律》并不满意。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不断地组织官员对《大明律》进行修改。他自己也对律法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他和刑部的官员一起学习《唐律》,和修订《大明律》的大臣一起,对律文进行仔细的推敲。据说每一条律文拟定,他都让臣下挂在墙上,几经斟酌,感觉妥当之后再写入《大明律》内。明代中后期,天下官员多说《大明律》难学难懂,有一位叫唐枢的官员就让大家学习太祖朱元璋,说太祖皇帝当年就是用心来学习律意,设置律条的,天下官吏如果能和太祖一样用心,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抱怨呢?总之,朱元璋本人对于律法的修订是尽心尽力。几次三番修改之后,直到洪武三十年,也就是朱元璋去世的前一年,他总算认为《大明律》已经达到精良的程度,宣布《大明律》最后修订成功,颁行天下。
但是,一方面是对法律精益求精的追求;另一方面,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朝却充斥着法外用刑。也就是说,朱元璋如此重视律法,但在他自己却并不依据《大明律》来进行司法。知道朱元璋的人可能都了解,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以法外用刑,而且是用酷刑著名的。苏州的姚叔闰和王愕,被朱元璋知道有才,被征入朝廷做官,这两个人不想去,结果不仅本人被杀了头,全家都被抄没。朝廷的御史,因为处事不公,被“墨面纹身,挑筋去指”。洪武朝著名的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中牵连人数之多,用刑之惨烈更为令人瞩目。时人记载,洪武朝甚至有“剥皮实草”、“铲头会”等匪夷所思的酷刑。而且朱元璋对这些法外用刑和酷刑的行用并不隐晦。他甚至将这些案例汇编成册,以《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逆臣录》等颁行天下,周知官吏百姓。
这样的矛盾行为该如何解释呢?朱元璋自有分说。首先,他说明自己也并不愿意法外用刑,酷刑天下。他这么做,实在是迫不得已。天下初定,乱臣贼子多,作奸犯科者多,所以一方面以严刑酷法进行惩治,另一方面也需要以严刑酷法的行用警示天下。其次,他认为自己作为开国之君,经历丰富,人情练达,所以在严刑酷法的使用中能够掌握分寸,不至冤滥天下。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即使法外用刑,也可以保证公平和公正。他修订《大明律》的目的不是为他洪武朝的统治,而是为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做安排。他认为后代的皇将从深宫之中长成,对于天下大事的了解不足,对人情世故的掌握不够,在阅历上和能力上都无法和自己比较。这样的皇帝如果法外用刑,行用严刑酷法就比较危险。此外,这样的皇帝也不具备修订精良法律的能力。朱元璋说,古代以来,制订法律的人,都是朝代的建立者。这是因为每个朝代的开创者看的人多,经的事多,对于法律的理解就更为深刻。因此,他用三十年时间修订一部《大明律》,为后世准备一部“永久之法”,是为后代的皇帝尽自己的责任。
基于以上的原因,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正式颁布之时,朱元璋宣布取消一切严刑酷法,规定后代皇帝以新定《大明律》为依据行事。他还明确规定后代不准修改法律,如果有大臣建议修改《大明律》的,要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最后修订的《大明律》总计460条,先列“名例”各条,作为总则,之后按照国家行政规制,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进行分类,分别有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有明一代两百多年,《大明律》没有任何改动。
条例的出现和汇编
《大明律》虽然精良,以一个一成不变的法律来治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仍是件难事。《大明律》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也日渐明显:情重律轻或情轻律重,旧的律文失去效用而仍然存在,新的罪行出现而得不到规范。这样的情况下,条例开始在司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条例是什么性质的法规呢?《大明律》规定,法司定罪必须引用律文,如果《大明律》缺乏对应条文的,司法官员可以引用相关的条目作为量刑定罪的依据,但是必须上报刑部进行讨论,再报皇帝予以确认这一司法的有效性。如果法司认为这样的案例具有一定典型性,就会对案例进行抽象,形成相对简单的条文,奏准皇帝,通行天下司法官吏,在司法中予以运用。这就是条例。
举个例子。弘治年间,江西有个犯人江缘一,向母亲索要银两还债,母亲吴氏不同意,江缘一遂恶言相向,肆意辱骂,并将银两搜出取走。其母受气不过,自缢身亡。事发,将江缘一问罪。 但是《大明律》内并没有直接的威逼父母致死的条目。只有“骂祖父母父母”一条和“威逼人致死”一条最为相关。其中前者规定,子孙骂父母祖父母者,绞。后者规定,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绞。法司引用子骂母律,定拟绞罪上报。刑部会审,认为引用不当,而且罪行重而处置过轻。认为如此穷凶极恶之人,不得保全身首。因此建议比照子孙殴祖父母父母一条的律文规定,将其斩首,并决不待时。这一决定得到皇帝批准,并由此通行天下,今后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的,均按这一事例定罪上报。
在明朝的前期,新的皇帝即位之后,都有将前朝条例废除不用的规定,明朝立国一百多年后,弘治皇帝即位,不仅不再取消前朝的条例,而且开始对既有的条例进行整编。弘治十三年(1500),以弘治《问刑条例》命名的明代第一个条例汇编正式颁行,条例总数二百七十九条,与《大明律》并行使用。这一条例汇编,在嘉靖和万历年间,分别有再次的编订,吸收新的条例。比如上述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一条,直接编入了嘉靖《重修问刑条例》。起初,《问刑条例》是单独编排的,万历十三年,修订万历《问刑条例》382条,这回刑部将条例编入《大明律》,分系于各法律条文之下,形成《大明律例》,颁布问刑衙门,永为遵守。
在《大明律》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条例的出现和行用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大明律》的内容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调整。而从条例到《问刑条例》,其实是一个立法的过程,是条例正规化的关键步骤。在条例的行用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实质的,皇帝仍具有关键的作用。皇帝的审核批准是一个必经的步骤。当条例进入《问刑条例》,司法官吏引用《问刑条例》中包括的条例时,就相当于引用律条,不再需要上报皇帝。也就是说,从条例到《问刑条例》,皇权对于司法的影响实际上有所弱化。
律法的应用
律法被赋予相当的重要性。从明朝初年开始,朝廷就要求百司官吏熟读《大明律》,通晓律条的意义,并据此处理相关事务。为了落实这一目标,都察院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员分别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进行每年一次的考察,官吏中读《大明律》不通的,要扣俸禄,甚至要被降级处理。明代有专门的司法机构,从最基层的知县开始,到府一级的推官,到省级的按察司,到中央的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专门处理司法的事务,但是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员。从理论上说,每个进入仕途的官员均有可能在某一阶段就职于司法机构,处理刑狱之事。因此,以上的规定,是针对百官的要求。
有明一代,无论是府州县还是中央刑部,司法官员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均需引用《大明律》的条文。缺乏相关律文的则引用条例。司法官员审理过的案件多有审核的步骤。以明代最基层的司法官员——县官和府一级的推官来说,除了杖罪以下的案件之外,其余审理过的案件都需要逐级上报。隋唐以后逐渐形成以笞杖徒流死为主的五刑惩治体系,杖罪以下的案件,也就是罪行最轻的案件。上报的案件都要以规范的司法文书格式出现。从目前看到的明代司法文书比如《四川司法档案》来看,这样的文书大概由三个方面组成:招由栏、议由栏和照由栏,分别由“问得”、“议得”和“照出”引出。其中招由栏主要记录案件的起因及受理依据及经过,相当于犯罪的招供记录。议由栏的主要内容是根据罪情,引用相应的法律进行定罪。照出栏中则交代与案件有关之事物或措施等。
嘉靖中期,四川夔州府梁山县贵溪里的陈林,充当本县永丰仓和儒学仓的仓库管理。按照规定,他应该按期将永丰仓的收支出纳情况记录清楚,如有将库存解送上级衙门的情况,则需要及时填写相关文书。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陈林不知何故,没有及时将有关文书送报,而且拖延时间长达十个月以上。夔州府因此将陈林问拟杖罪,并上报四川布政司。其中的司法文书中第一部分为“招由”,具体交代陈林的罪状。第二部分为“议得”,引用律文定罪:“陈林所犯,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有《大诰》减等,杖七十。系民,审稍有力,和候申详允示,纳赎完日,省发宁家。”“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是《大明律》中的律文,按律文规定,陈林应该杖八十。但是在具体的发落中,还有一些因素起到作用。首先是《大诰》减等。《大诰》就是上文提到的明太祖朱元璋时期颁布的《御制大诰》,一共三编。朱元璋为了鼓励大家学习《大诰》,曾经在洪武年间规定,犯罪的人家如果存有《大诰》一书,可以罪减一等。洪武以后,百姓人家存有《大诰》的其实不多,但是“有《大诰》减等”,却在司法实践中保留下来。“稍有力”是指陈林家里财力状况还可以,比“有力”差一点,比“无力”强一些,仍有实力赎罪,赎罪之后陈林就可以出狱回家。如果陈林家里财力不行,属于“无力”,那么陈林就要被杖责七十。这一文书的照出部分,交代陈林的诉讼费用为银一钱,赎罪的银两是一两三钱五分,两项费用须一起交到夔州府的永安库。
第3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关键词]亲属相盗,亲属关系,礼法之争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6-0042-08
一、导论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亲属相盗是指法定范围内亲属之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彼此窃取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或多次窃取对方的财物。亲属相盗这种侵犯亲属之间财产利益的行为,始终受到刑法和伦理的双重评价。对亲属相盗如何惩罚,涉及家庭伦理和刑法处罚的轻重。
学界对亲属相盗罪的研究,多集中在亲属相盗在现代刑法中的缺失、亲属相盗在两大法系的比较,外国亲属相盗罪的规定对当前中国的借鉴、现代亲属相盗犯罪的本体论、亲属相盗的基本理论等方面。如鲁昕对自秦律以来的“亲属相盗”的立法进行了梳理,认为当前中国刑法中应重新思考设置亲属相盗罪名①。同时,有不少硕士论文对现代亲属相盗问题与两大法系做比较研究,从亲属相盗的身份犯、犯罪主体、刑事责任、刑罚、犯罪手段、犯罪情节、犯罪客体、犯罪要件等方面分析,提出对当前中国亲属相盗立法完善的建议。
不过,对晚清民国时期亲属相盗罪的立法和司法变迁,学界尚乏整理。清末修律时期的“礼法之争”对亲属相盗罪名的存废,法理派和礼教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故本文专注于这段时期该罪之变迁。
“亲属相盗”律肇生于秦代,完善于唐律,分为两条:“盗缌麻小功财物”律和“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经宋改名为“盗亲属财物”律,也将人盗己财物放进其中。进而到明律中,唐律两条真正合并为一条“亲属相盗”律,而至清律中最终完善。
在此有必要比较“亲属相盗”律在唐律和清律中的量刑轻重,从而说明自唐至清“亲属相盗”律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首先来看“凡盗”(普通盗窃)和“强盗”的规定:唐律“窃盗”条:
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②
唐律中“盗缌麻小功财物”条,比照凡盗,盗缌麻、小功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杀伤者,各依本杀伤论。而清律中“亲属相盗”律,卑幼盗窃尊长、尊长盗窃卑幼,期亲亲属减凡人五等,大功亲属减凡人四等,小功亲属减凡人三等,缌麻亲属减凡人二等,无服亲属减凡人一等,并免刺面。“若行强盗者,尊长犯卑幼,亦依强盗已行而得财,不得财,各依上减罪;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不在减等之限。若有杀伤者,总承上窃、强二项。各以杀伤尊长卑幼本律,从其重者论。”①清律中“亲属相盗”律的刑罚较唐律较轻,这与明清时期更加注重维护家族利益,强调家族和睦有关,故明清律中“亲属相盗”条刑罚较唐律变轻。正如沈家本所云:“旧律亲属相盗,罪比凡人为轻,以亲属有同财之义而宽之也。”②清律中“亲属相盗”律的量刑虽较唐律轻,但延续了中国传统亲属法文化的特色——自西周以来形成的宗法制和“亲亲”“尊尊”的家族社会。
二、清末修律时期
(一)立法上的突破:1911年《钦定大清刑律》的颁布
在清末修律时期,清廷为了满足新刑律不能立即颁布的情况,对《大清律例》进行修改,颁布了《钦定大清现行刑律》。《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之“亲属相盗”条延续了《大清律例》中的规定,仅改变了刑罚种类。
1907年《大清新刑律草案》第361条:
于本支亲属或配偶者及同居亲属之间犯第349条、第350条、第357条之罪者,免除其刑。于其余亲属间犯前项所指之罪者,须待告诉始论其罪。非亲属而与亲属为共同之犯,不用前二项之例。③
本条针对“亲属相盗”律进行了修改,亲属范围发生了改变,本宗亲属、配偶或同居亲属,不再处刑,而是免除刑罚。除上述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盗窃犯罪,须告诉才能论罪。如果亲属与非亲属的共同犯罪,不适用前两项之刑罚。
清廷为了让《大清新刑律草案》顺利地通过,按照编查馆奏请各省督抚和中央各部堂官写签注,上奏对《大清新刑律草案》的意见。清廷将学部和部院督抚大臣的签驳,连同《大清新刑律草案》发交给沈家本和法部修改。沈家本和修订法律馆在修改中,“于有关伦纪各条,恪守谕旨,加重一等”,然后送交法部。法部尚书廷杰在正文后又加上《附则》五条,明确规定:“大清律中,十恶、亲属容隐、干犯名义、存留养亲以及亲属相盗相殴并发冢犯奸各条,均有关于伦纪礼教,未便蔑弃。”④在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10年2月2日),同时印刷《修正刑律案语》,此书是对《大清新刑律草案》签注意见的回复。《修正刑律草案》第380条:
于本支亲属、配偶者、同居亲属之间犯第366条、第376条之罪者,免除其刑。于其余亲属间犯前项所揭各条之罪者,须待告诉始论其罪。非亲属而与亲属为共同之犯,不得依前二项之例论。⑤
《修正刑律草案》上奏,不但没有消除争论,反而引起了更大争论。劳乃宣以《修正刑律草案》违反礼教为由,向编查馆上奏《修正刑律草案说帖》。其中对亲属相盗律提出:
旧律亲属相盗,罪比凡人为轻,以亲属有同财之义而宽之也。草案第32章第366条及第376条为盗窃之罪,其第380条云:“于本支群亲属配偶者、同居亲属之间犯第336条及第376条之罪者,免除其刑。于其余亲属之间,犯前项所揭各条之罪者,须待告诉始论其罪。非亲属而与亲属共犯者,不得依前三项之例论。”即与亲属相盗旧律大致相同,可无庸另辑。⑥
沈家本针对劳乃宣提出《沈大臣酌拟办法说帖》,对此予以回应:“亲属相盗,并在酌量减轻之列,应于《判决录》内详定等差,毋庸另立专条。其关乎殴尊亲属者,修正草案内已定有明文矣。”⑦
可见,沈家本和编制局致力于寻求传统律学与现代法的平衡,维护刑法草案中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不否定“亲属相盗”的合理性,《大清新刑律草案》规定了亲属相盗的罪名,只是没有详细规定罪刑之减等。而劳乃宣等也不全部否定传入的近代刑法法理,但坚持伦常。认为“亲属相盗”律合乎中国传统风俗,不能混淆中西法律文化的特质和差异,故要予以维持此律,劳乃宣认为“即与亲属相盗旧律大致相同,可无庸另辑”,这一点与沈家本的“亲属相盗,并在酌量减轻之列,……毋庸另立专条”是一致的,两者在“亲属相盗”立法的具体处理方式上达成一致,即“毋庸另立专条”。
宣统二年十一月,劳乃宣以资政院议员身份,邀请105名亲贵议员,向资政院提交了《新刑律修正案》,提出修改、移改、复修、增纂有关礼教条款13条又2项。但对“亲属相盗”没有提出新的质疑。资政院对议员评议审查修改,不但未采纳劳氏修正案,连原案中的《暂行章程》也被删除。然后将此修正案交资政院议场由议员议决。①双方主要针对无夫奸和子孙对尊长的侵害是否适用正当防卫而争论,没有涉及亲属相盗,在《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②中仅有汪荣宝提出观点,没有人对此条产生异议。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谕将新刑律总则、分则及暂行章程颁布。其中第381条:
于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亲属之间犯第367条及第377条第1项之罪者,免除其刑。对其他亲属犯前项所列各条之罪者,须告诉乃论。前二项之规定于非亲属而与亲属为共犯者,不适用之。③
本条几乎完全继承了《修正刑律草案》第380条。
《修正刑律草案》的“亲属相盗”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首次将“告诉乃论”的理论运用于“亲属相盗”中。同时,“告诉乃论”范围不仅仅包括亲属相互间的犯罪和危害较轻的犯罪,并将现代职业伦理纳入规范视野,如“关于名誉信用安全及秘密之罪”。同时增加了告诉权人范围、告诉权行使的条件、告诉权消灭的事由等等。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旧律中亲告罪与近代西方刑法中有很大不同,如何将旧律的亲告罪在新式刑法典中有效移植和借鉴是很困难的事情。《大清律例》中亲告罪只有七个④罪名:“别籍异财”“妻妾殴夫”“奴婢骂家长”“骂尊长”“骂祖父母父母”“妻妾骂夫期亲尊长”“子孙违反教令”。可见,清律亲告罪的适用范围极其狭窄,亲属相盗不包括在内;清律中亲告罪的告诉主体很狭窄,一般仅为被害人,亲告罪仍依据尊卑、亲属关系来量刑。而到了《钦定大清刑律》不再局限于亲属相犯和危害较轻的罪刑,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定,亲属相盗方被规定为亲告罪。这也是移植西方刑法理论的一大后果。
清廷覆灭,《钦定大清刑律》没有施行。入民国,《钦定大清刑律》稍加改动,变为《中国民国暂行新刑律》继续适用。
(二)司法实践:固有法的延续
清末十年的传世司法判例中,发现的亲属相盗案件极少。有一件记录在《塔景庭案牍》中⑤,韩张氏为其弟张腊生拆洗棉袄,发现其中有一张当票,是张占熬失窃之物。而张腊生说张庆元之子张长庚托其代为保管。而张长庚坚决否认。张腊生年仅十四岁,当票来历不明。当票被发现之后,张氏没有给失主张占鳌,而是交给东家刘义限,刘义限再交给张占鳌。张占鳌没有按照族规,邀请本族长辈来处理此案,而是直接到县衙禀告。此案没有做最后的裁判,县官许文濬仅将当票收官,传张腊生、张长庚、韩张氏到案审判。
此案是本宗亲属之间的盗窃,但是盗窃事实没有查清,亦没有作出判决。但是县令有理由怀疑这是一起亲属相盗案件,处理的办法,是传其到案,以待审讯。该案似乎透露出在州县一级发现案件是亲属相盗的性质,且情节轻微,一般不会直接判决,而是促进案件在宗族内调解。
从现在能看到的这则清末州县审理的“亲属相盗”案来看,“亲属相盗”律的适用在清末似乎处于较为尴尬的局面。因为“亲属相盗”的处刑更在“凡盗”之下,故盗窃财物的价值不大时,处刑不会太重。而且州县官会考虑到,如果对此类案件率以判决刑罚处罚,容易增加亲属间的矛盾。从维护亲族内的和睦考虑,州县官宁可调解敷衍了事。加之整个清末修律时期,立法者对亲属相盗争论很大,法理派坚持废除亲属相盗,没有必要另立专门的法条,到后期则与礼教派达成了妥协,亲属相盗不为罪。只有在亲属告诉,才论其罪。如果是亲属与非亲属合谋一起盗窃本家亲属,则不适用本条规定。
朝廷的争论,是否直接影响了下级州县审理“亲属相盗”案件的态度,现在还缺乏更多的史料加以证明,但若各州县都与上引句容县令的态度相同,则“亲属相盗”案件在更多的时候都适用调解,即使是亲属告诉,州县也懒得去做审理和定罪判决。
三、北洋政府时期
(一)立法:继受法的延续
北洋政府建立伊始,为解决无法可依的局面,直接将《钦定大清刑律》改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作为全国刑事立法。《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81条:
于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亲属之间犯第367条及第377条之罪者,免除其刑。对其他亲属犯前项所列各条之罪者,须告诉乃论。前二项之规定于非亲属而与亲属为共犯者,不适用之。①
本条完全承继了《钦定大清刑律》第381条。亲属范围限定在直系亲属、配偶和同居亲属之内,亲属相盗不负任何刑事责任。而上述范围之外的亲属相盗,要定罪量刑,但须有人提起告诉乃论,在诉讼程序给予限制,不告不理,告诉才受理。再有,如果本条前两款如果是非亲属和亲属共同的犯罪行为,不适用本条的规定,即不适用亲属相盗的定罪量刑。
1915年《修正刑法草案》第394条:
于直系亲属、配偶人或同居亲属之间犯第381条之罪者,免除其刑。对于其他亲属犯第381条之罪,须告诉乃论。本条之规定,于非亲属而与亲属为共犯者,不适用之。②
此条较《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81条几乎没有改变。
1918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第368条:
于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亲属之间犯本章之罪者,免除其刑。③
此案较《修正刑法草案》少了后两款,仅规定直系配偶、配偶或同居亲属之间犯盗窃罪,免除其罪刑。不再限定须告诉才受理,也不再限定亲属与非亲属为共同犯罪时,不适用此条的罪刑。只要非上述亲属范围之间的盗窃,就要定罪量刑。
1919年《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第347条:
于直系亲属、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之间犯本章之罪者,免除其刑;于其他亲属之间犯本章之罪者,须告诉乃论。④
即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共财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不定罪量刑。同时恢复了《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删除的“告诉才受理”的规定。
综观北洋政府时期亲属相盗立法,延续了晚清刑事立法规定,即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亲属之间犯盗窃案件,均免除其罪刑,这项规定体现了重视亲情和家庭,废除旧律中分尊卑区别对待的量刑方法,即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盗窃,不为罪,目的是:“要使亲属之间有更完全深厚的关爱或情感。理由不外两方面:一是认为人性本来如此,人都是先爱亲属而后才爱他人。对这种人性只能顺应,不能违逆。二是认为应当如此,只有善加保护培养人类这种最本能最自然的爱,才能保护和发扬人的善端或善的萌芽,才能使人们推亲爱于社会。”⑤因此,北洋政府时期刑事立法部分延续了传统律学重视亲情和血缘伦理的法文化,但同时,亦也对一定亲属范围外的盗窃行为进行惩罚,很大程度延续了《钦定大清刑律》的条文。
(二)司法实践:对立法的补充和解释
查《大理院判决例全书》《大理院解释例全文》,有关亲属相盗的案件较少,与北洋政府时期刑事立法继续延续晚清刑事立法有关,即将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亲属之间的亲属相盗处理,这是因为上述亲属之间关系密切,故仅定罪而不量刑。而其他亲属间的盗窃行为需要亲属告诉乃论,即使亲属向审判机关告诉,方才定罪量刑。
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实践对“亲属相盗”进行了补充和解释。如统字第548号解释例①说明亲属相盗的条件,必须是同居亲属,方能为亲属相盗。今有广西宜北县母乙子甲二人,就养于丙,称为义子,尚未改姓。后母子二人与丁密谋盗窃丙家财物,并藏于戊家。但大理院给出了最终的答复,甲与丙不是同居亲属,更无血缘关系,故不能按《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81条第1项定罪量刑。又有九年上字第288号判决例②一案中,同居之侄子看望其叔,见其叔探亲未归,便将房门扭断强行进屋,掀开柜子大肆行窃其叔衣服,仍以亲属相盗论。此案中侄子虽未与其叔叔同居而住,但适用《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81条第2款之规定,为亲属相盗罪。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一)立法:“亲属相盗”罪在近代中国刑法中的定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法典成为立法工作的中心议题。司法部对《刑法第二次修正案》进行修改,到1928年《中国民国刑法》第361条:
于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共财亲属之间犯本章之罪者,得免除其刑。亲属间犯本章之罪者,须告诉乃论。③
此次刑法典中亲属相盗罪继承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规定,即亲属相盗在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共财亲属之间实是免除罪刑的,且须告诉才受理。可见,亲属相盗的立法精神一脉相承。
1933年《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初稿》第310条:
于直系亲属、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之间,犯本章之罪者,得免除其刑。前项亲属或其他五亲等内血亲或三亲等内姻亲之间犯本章之罪者,须告诉乃论。④
此条第1款延续了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之规定,而第2款又增加了前项亲属或其他五亲等内血亲或三亲等内姻亲之间犯盗窃罪,须告诉才受理。这样规定是进一步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和团结,包括四种亲属:配偶、血亲、姻亲、同居共财的亲属之间的盗窃,都是告诉才受理,即不告不理,无形之中扩大了亲属相盗的亲属范围。
1934年《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第344条:
于直系血亲、配偶或同居共财亲属之间,犯本章之罪者,得免除其刑。⑤
此案又取消了告诉权的问题,延续了《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亲属相盗罪适用的亲属范围: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共财的亲属。
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24条:
于直系亲属、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之间,犯本章之罪者,得免除刑。前项亲属或其他五亲等内血亲或三亲等内姻亲之间,犯本章之罪者,须告诉乃论。⑥
最终,中华民国刑法典沿用了一直自《钦定大清刑律》的规定,即一定亲属范围的盗窃罪,均免除其罪。这个范围一直限定在直系亲属、配偶或同居亲属。超出上述这个范围,须告诉乃论。而民国学者郭卫认为“得免除刑”的“免”字,免或不免,都应该由审判官酌定情节而判定之。“其所以增冠一‘得’字,以此项情形原不一致,容有不可恕之情节时,不能不予审判官以自由裁量之权。如被害者不愿犯人受刑罚,原可不向法院告诉也。”⑦此处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被盗窃的物体虽为直系亲属、配偶所监管,但所有权人是其他人。二是所窃之物所有权属于直系亲属、配偶所有,其物寄存于外人之处。此两种情形究竟能不能适用免除条文。郭卫认为:“查日本大审院判例系严格主义,谓虽亲族之所有物,于亲族以外占有之场合而为窃取之时,与普通窃取罪同。”⑧日本法有丈夫将他人存放不允许通融之金元,妻子知道此事窃取,日本刑法认为此是窃取他人物品,不是亲属相盗案件。与之相反,北洋政府大理院之解释则采“宽宥主义”,儿子明知父亲保管他人物品,而又窃取他人物品,使其脱离父亲监管,仍以亲属相盗论。对于第二种情况,所窃之物为直系亲属或配偶寄存别人处,是否属于亲属相盗,南京国民政府刑事立法没有给予考虑,郭卫认为此处应采取“严格主义”,以普通盗窃论。
综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立法者致力于亲属相盗罪的承继和移植近代西方刑法理念,同时基于维护部分传统亲属法伦理,维护家庭和睦关系。
(二)司法实践:最高法院判决例、解释例对立法的补充
查《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刊》和《最高法院判例汇编》,记载了两件亲属相盗的案例。
1.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刑事上字第509号判决例①解释了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即所盗窃之物体是否移入自己权力支配之下为标准,若已将他人财物转归自己所持,即成立盗窃罪。如果盗窃成功后将所盗之物遗弃逃逸,则罪行成立与否并无关系。此案中钟祝氏与钟发宝是继母子关系,但因钟发宝之父钟正谦与钟祝氏正在诉讼离婚,尚未确定,但已经与钟发宝分产析居,不再是同居共财之亲属,故此案不属于亲属相盗案件,属于普通盗窃案件,二审法院对此作出有罪判决。该案钟祝氏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日即旧历七月十三夜间雇佣钟凤祥、钟仕昌、钟章元、钟海方等到继子钟发宝田中偷盗稻谷,后经钟发宝集合村内众人阻止钟凤祥等,闻声逃走。其所遗留割稻子的器具均由钟发宝携带回家。钟发宝的田地已属于自己所有,不属于原有家庭的共同财产,已分家析产。故钟祝氏纠集众人盗割钟发宝所属的田产,是否构成盗窃既遂,最高法院认为“应以所窃之物已否移入自己权利支配之下为标准。若已将他人财物移归于自己所持即应成立窃盗既遂罪,至其后将已窃得之物遗弃逃逸与罪之成立无关”,②做出了盗窃罪既遂的判决。但因钟发宝与钟祝氏母子关系没有消灭,因其父亲与继母钟祝氏没有解除婚姻关系,最高法院考虑双方平日关系和钟祝氏的教唆犯罪情节,依照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77条的“犯罪之情状可怜恕者,得酌减本刑”,结合刑法第90条判处钟祝氏犯教唆盗取罪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两年。钟凤祥非出于自己犯意,被钟祝氏教唆,最高法院撤销了第一审判决,认定其犯有盗窃既遂,同时参考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90条缓刑规定,判处钟凤祥有期徒刑六月缓刑两年。此案中首先明确了不是亲属相盗,是普通盗窃,清晰地界定普通盗窃和亲属盗窃,进而在判决例中明确规定已分家析产,不再同居共财的亲属相盗是普通盗窃,纵使因生父与继母正处于离婚诉讼之中,自己与继母的亲属关系在法律上没有消灭,亦不能影响亲属相盗的关键条件——同居共财,故解释例进一步补充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亲属相盗立法。
2.最高法院在二十年四月十四日非字第59号判例:“犯罪时之法律,较裁判之法律定刑较轻,自应适用犯罪之时法律。直系亲属犯盗窃罪,既在刑律尚未失效期间,自应适用刑律免出其刑之规定处断。”③此案是最高法院对原审法院所判郑齐偷盗其父郑富田的财产及手枪套之刑罚做出的撤销规定——撤销原判关于窃取郑富田财物部分及刑之执行部分,郑齐窃取郑富田财务部分免诉。郑齐在民国十七年旧历正月盗窃其父亲大洋三十元,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即国历九月七日)又窃取其父亲的两个手枪套。郑齐盗窃父亲大洋三十元,因为当时尚未颁布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依照该刑法第2条规定“犯罪时之法律与裁判时之法律遇有变更者,依裁判时之法律处断。但犯罪时法律之刑较轻者,适用较轻之刑”。故将1912年4月29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81条第1项免除刑的规定,与1928年7月1日颁布《中华民国刑法》第367条和第337条第1项的刑罚相比较,可推断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刑罚较为轻,故用此律第338条第1项的规定免除其刑,撤销一审法院运用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37条第1项判决七月二十四日郑齐盗窃其父两个手枪套的犯罪行为,连带在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颁布前的偷盗大洋三十元犯罪行为的两个月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决定民国十七年(1928年)旧历正月郑齐盗窃父亲郑福田的大洋三十元免除处罚,而对1928年9月7日盗窃的两个手枪套另行审判。故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充分注重犯罪行为发生时间刑法适用,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相盗”的司法实践已较为稳定。最高法院又通过判决例和解释例补充亲属相盗立法,明确已分家析产的亲属相盗不能免除其刑;虽同为亲属相盗行为,但盗窃时间相隔很长,出于不同的两个犯罪故意,不以此罪来概括,应为两个盗窃罪等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相盗立法部分延续了中国古代亲属相盗的立法精神——维护家庭和睦,减少因盗窃而引起的纷争。司法实践亦延续了此种立法精神,但并不完全一致。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例、解释例弥补缺失,进而实现了立法与司法的融合,继承了部分中国传统固有法的亲属法伦理——家庭和睦,又移植了近代刑法的“告诉乃论”理论。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亲属相盗立法完成了中国传统固有法到近代刑事立法转向,并最终定型。
五、结论
(一)中国传统亲属法伦理的延续
盗窃罪从春秋时期以降,“亲属相盗”的处罚思想是体现了西周以来的“亲亲尊尊”的礼治思想,由“礼”来限制犯罪行为。自秦入律,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在唐律中成熟,宋代将唐律“盗缌麻小功财物”和“卑幼将人盗己家财”合并成一条“盗亲属财物”律,进而明律变为“亲属相盗”律,一直沿用此律到清。明清律中“亲属相盗”的量刑较唐律中较轻,重在维护家属之间的和睦,故从秦律开始就对亲属相盗减轻处罚,而明清律处罚更为减轻,这都表明了“亲属不分财”,亲属有同居共财的美德,而不明确界定家庭成员间的财产界限,故对亲属相盗减轻处罚,甚至有时不处罚,在宗族内部处理(常常干脆不罚),将处理权交给宗族。可见,亲属相盗从秦律开始就坚持自西周形成的宗法制——亲属之间的团结、和睦,经清末修律、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亲属立法亦部分维持了这种立法思想。同时,亦抛弃了尊卑有别的量刑原则,不再区分尊卑,只要发生法定亲属范围内的盗窃,做同罪同刑。
清末修律时期,“亲属相盗”律没有另立专条,法理派与礼教派达成一致,没有在此条过多纠缠。双方关于“亲属相盗”律只经历了一个回合,以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认为:“即与亲属相盗旧律大致相同,可无庸可辑。”①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认为:“应于《判决录》内详定等差,毋庸另立专条。”②而双方在“无夫奸”和“子孙违反教令”两条进行了激烈争论。反过来,沈家本与劳乃宣在“亲属相盗”立法中达成一致,不是因为在立法理念上趋同,而是因为沈家本坚信“折中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之最新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传之礼教民情”③的修律思想,即将寻找中西大同法规、最新学说和礼教民情三者的平衡点,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现实的法律近代化道路。沈家本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律学教育,后积极学习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个人主义和尊重人格,致力于中国传统律学和近代西方法学的融合,不否认中国传统律学中合理之处,旨在运用西方法学与中国律学中的相似之处,来解释传统律学,使其符合社会思潮,亦不触犯礼教派所坚持的“礼教民情”。这种“从传统中寻找近代的因子,再加以改造;对于传统文化,非徒以保存‘国粹’,而系以科学方法揭开‘国粹’之真相,自有利于新法律文化的嫁接。”④以减少对外来法律文化的抗拒。另一方面,沈家本为了使《大清新刑律草案》顺利通过,也充分考虑了礼教派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将中国固有的亲属法伦理与近代刑事立法的平权立法结合起来,沿用了亲属相盗的立法。虽没有立“亲属相盗”专条,但延续了部分中国传统亲属法伦理。
随着进入民国时期,社会风气强调平等、自由,原有旧律亲属法伦理所建立异化的等级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逐步消失,民众心理逐步受到近代西方法学思潮的影响。立法宗旨和司法实践随着时间推移达到一致,刑事立法强调血缘关系和家庭和睦,亲属之财界限不明确,故只定罪而不量刑。而司法实践很少出现亲属相盗的案件,即使出现,亦是为了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犯罪形态等问题,从而补充亲属相盗之立法。由此可见,亲属相盗从秦代入律,经清末修律的大变革,直到民国时期,其维持家族和睦的亲属法伦理一脉相承,维护了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家的观念。
(二)“亲属相盗”之亲告罪性质
另有,自从清末修律开始,亲属相盗成为亲告罪,一改旧律中不定为亲告罪的规定。晚清民国时期的“亲属相盗”罪是出于考虑刑罚权在家庭范围内的克制。因为盗窃罪本身就是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但亲属相盗是家庭范围的犯罪,这就存在家庭日常管理和国家管理之间的矛盾。如果国家强行介入家庭管理范围,则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但如果不介入家庭领域,又会影响社会秩序。所以,晚清民国时期立法者将处罚权交给受害人,让其决断。受害人如果认为受到了伤害,如不诉诸法律,不能维护自己权利,则可告诉;如果受害人认为家庭和睦第一,财产权并不重要,则可不。这样兼顾了亲情和血缘关系,又实现了刑法的惩罚和震慑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罚权的适用。
随着西法东渐,人们思想受到人格独立和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结构亦从大家族转为小家庭。故近代中国刑事立法亦从家族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开始注重人格独立。同样,原来亲告罪是综合考虑社会秩序和亲属关系,后转向个人权利和自由,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之间权衡。如果二者发生冲突,不再以单一的社会秩序作为标准来定罪量刑,而是将二者利益比较的任务交给受害人,让其凭借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决定是否告诉。其中标准就是受害人衡量告诉与否,是否给自己带来新的伤害,或是能弥补先前盗窃行为对自己造成的损害。
有学者认为:“民国亲告罪制度,是国家为了防止受害者因遭受二次伤害或加重伤害,及保护受害人切身利益得到救济,允许受害人对侵害行为选择告诉或不告诉的刑事制度。”①而晚清民国时期“亲属相盗”罪的变迁正是西方亲告罪进入中国刑法的一种具体表现。
【作者简介】张亚飞,男,1981年生,山西临汾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
The Evolution of the Larceny Between Relatives
in the Modern Chinese Criminal Law (1902-1949)
第4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目前东亚多数地区的刑法,主要受到19世纪以来,德国的刑法理论与刑法规范的影响。关于德国刑法制度如何从习惯法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的刑法典,并成为影响目前许多国家刑法体制的参考典范,在东亚地区尚缺乏相关研究文献。{1}德国刑法学大师冯·李斯特(Franz von Liszt,1851-1919)在其《刑法学教科书》中曾说,《卡洛林那法典》的内在价值实际成为300年德国普通刑法的存在与发展基础。{2}因此,研究《卡洛林那法典》的内容及其时代意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德国刑法在近代的发展
在中世纪的德国地区,今日刑法的规范范围仅具私法的性质,当时的人认为杀人或窃盗等行为是发生在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私法关系,统治高权并不介入加以处理。德国法理学及刑法学教授拉德布鲁赫教授(Gustav Radbruch, 1878-1949)在《卡洛林那法典》一书第6版导论中提到,当时的人将今日的犯罪行为当作是加害人对于被害人的伤害。因此,刑罚是从被害人的观点出发,只要加害人愿意付一定的金钱,赔偿被害人或其家属损害,政治高权者并不介入此种纠纷或对于行为人加以制裁。这种现象主要因为15、16世纪的德国为封建社会,尚没有现代国家型态出现,当时的人民面对私人间恩怨纠纷,往往透过决斗的方式解决,牵涉命案的纠纷往往还被认为是习惯法或私法的范畴。当时的封建领主并不认为杀人等行为要用法律规范。{3}当时的人认为杀人或窃盗等是一种地区和平被破坏问题或纯属于私人纠纷的问题。{4}拉德布鲁赫教授在《卡洛林那法典》的导论中强调,在当时,被害人如果没有勇气对加害人诉讼,加害人不会受到任何处罚。纵使被害人或其家属对于加害人提起诉讼,只要加害人找到人共同保证其是清白、无辜的,并协助加害人通过一种宣誓仪式(Reinigungseid),加害人也会受到无罪判决{5}。纵使加害人被确定有罪,也只需对被害人或其家属给予损害赔偿。{6}
拉德布鲁赫教授举例说明,在16世纪德国地区曾发生一件杀人事件,被杀者的寡妇仅从加害人处取得10个钱币(Kronen)赔偿,加害人未受任何其他制裁,因为被杀害者是个整日无所事事的人。{7}
分析1532年在德国帝国议会通过的《卡洛林那法典》的219个条文,可以发现这个条文在体例的完整性上比不上公元7世纪的《唐律》或者同一时代的《大明律》,但是它却能响应中世纪末期德国地区,由于人口的增加,农民战争、宗教战争所造成社会不安的需求。当时德国面临宗教改革,许多人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四处流窜形成一个营利的犯罪团体。{8}另外,当时德国地区也面临帝国皇帝与地方领主权力关系发生变动的时刻,这个时期也是很多德国地区人民到意大利北部学习罗马法的时刻。《卡洛林那法典》及当时许多地区类似的刑法典就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出现。关于神圣罗马帝国与当时德国地区的统治者,如何于中世纪末期,逐渐立法以统治的力量介入原来被视为属于私人跟私人间的纠纷私斗,在本文作者出版的《德国法制史—从日耳曼到近代》一书中对于德国各地区当时出现的各种地区和平协议(Landesfrieden)有详细描述。{9}
根据拉德布鲁赫教授在《查里五世刑事法院条例》(Die Peinliche Gerichtsordnung Kai-ser Karls V. von 1532,又称Carolina)一书导论提到,《卡洛林那法典》被订定之前,德国地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被处罚,可能依据习惯,可能依据统治者或审判者的任意意志,一般人民对于自己何时及如何被处罚是不确定的。{10}而在同时间,到意大利学习罗马法的德国人,开始思考什么才是适当的法并尝试启动订定明确法规范的行动。{11}
在中世纪末,可以发现德国地区有许多将犯罪行为立法加以处罚的尝试,例如1466年的《Ellwanger Halsgerichtsordnung》 、 1485年的《Nurnberger Halsgerichtsordnung》以及1506年的《Maximilianische Halsgerichtsordnungen》 、1507年的《Constitutio Criminalis Bam-bergensis》 、 1516年的《Brandenburgische Halsgerichtsordnung》、 1530年的《Die Reich-spolizeiordnungen》及1532年的《卡洛林那法典》,拉丁文又称为《Constitutio CriminalisCarolina》 ),其中《卡洛林那法典》影响最为深远,这个法典在当时又被称为《查里五世刑事法院条例》。{12}除了各种跟当代刑法有关的规范开始被订定为成文法之外,神圣罗马帝国也在1495年成立帝国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 {13} 。
《卡洛林那法典》通过后,德国地区才逐渐将许多犯罪行为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中决议的《卡洛林那法典》并不像现在德国的联邦法般具有优先于地方法规的效果。由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区域领主们对于由帝国议会主导的《卡洛林那法典》草案具有疑虑,担心如果这个法案通过,地区的习惯法或地方法的影响力将减少,因此不愿意通过此一法典。后来帝国议会作出所谓“Salvatorische Klau-sel”的决议,决议《卡洛林那法典》仅在地区没有习惯法或者地区法时才能适用,也就是仅具有次级的规范效果后,《卡洛林那法典》终于1532年在里根斯堡( Regensburg)举行的帝国议会通过。{14}
《卡洛林那法典》直到1848年还被当时德国的历史法学派的开创者,冯·萨维尼(V.Savigny)称赞,认为这是在18世纪最被重视、重要的法律。{15}这个法律的重要性一直维持到18、19世纪之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区域领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国家之后,许多区域领主开始将启蒙时期的刑事立法精神用以规范各种侵犯他人身体的行为或维持地区秩序的行为。在19世纪,刑法普遍被认为是一个需要透过国家的明文规定,才能够将国家的刑罚权加诸于人民的法规范,自此刑法被理所当然的认为属于公法的领域。从冯·李斯特1881年出版,1931年由Eberhard Schmidt教授修订第26版的《刑法学教科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卡洛林那法典》对于德国地区的刑法的影响一直维持到启蒙运动时期,也就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左右。启蒙时期的刑事立法开始贯彻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基本思想,也就是以保障个人自由、反对法官擅断、废除刑讯、废除或限制死刑、强调国家的刑罚目的、限制教会或纯精神的行为要求等。{16}启蒙运动引发德国刑法科学的发展,当时的刑法学学者于当代最常被提起的是费尔巴哈(P. J. A. Feuerbach,1775-1883)的刑罚理论。{17}费尔巴哈的影响一方面因为他在1801年完成的《德国刑法学教科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参与1813年《巴伐利亚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因此成为德国刑法在19世纪刑法立法的先驱者。他主要推动一个自由化、理性化的刑法观,这个刑法观在19世纪的刑法立法发展中被接受,也成为德国帝国刑法典的核心价值,并被20世纪继受德国刑法体系的国家的刑法典所接受。{18}
二、《卡洛林那法典》在帝国议会订定过程及其在当时帝国区域内的效力
《卡洛林那法典》最先是由Johann Freiherr v. Schwarzenberg(约1463-1529之间)所草拟的,{19}Johann Freiherr v. Schwarzenberg同时是1507年“Bambergische Halsgerichtsord-nung”的订定者。{20}今日我们所称的刑事诉讼法或刑法在15、16世纪的德国通常被称为Halsgerichtsordnung(可以翻译为死刑的法院规则)。在1485年前后的Nuenberg以及1515年、1540年今日的奥地利所在的Niederoesterreich等地区都有类似的立法。“ Hals”一词在中世纪代表一种跟身体或生命有关的重度刑罚,Gerichtsordnung指的是有关法院组织法。Hasgerichtsbarkeit(又称为die Blutgerichtsbarkeit或die peinliche Gerichtsbarkeit)在当时主要是处理跟谋杀(Mord)、强盗(Raub)、窃盗(Diebstahl )、强制性交(Notzucht)、谋杀小孩(Kindesmord)、同性性行为(Homosexualitat)、女巫或魔术行为(Hexerei、 Zauberei ),这种法规主要牵涉死刑的执行。相对于死刑的法院规则,在当时各地区存在有所谓的低级法院规则(die Niedere Gerichtsbarkeit),这是中世纪当时一种处理比较轻的犯罪行为的审判规则,也被称为所谓的“Patrimoniale Gerichtsbarkeit”。这种审判层级主要处理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型犯罪行为,主要是透过罚钱或者轻微的身体刑罚(leichteren Leibstrafen)对于行为人加以处罚。
1495年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决定设定一个处理一般人民与区域领主之间或贵族之间的纷争的法院,帝国法院的设置开启订定神圣罗马地区全体适用法律的呼声。{21}1498年在Freiburg的帝国议会中,与会贵族与区域领主共同决议,要订定一个规范犯罪处罚程序的法规。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作出这个决议后,整个立法工作进行了近30年,经过4次草案的提出,终于1532年在里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中订定了《卡洛林那法典》{22}。这个法律能够通过,主要是在帝国议会中,有人提出所谓“Salvatorische Klausel”的共识,就是指这个法律在神圣罗马地区仅有次级规范的效力,它不能高于神圣罗马帝国各区域领土中的习惯法或其他由区域领土的统治者所制订的法律。{23}
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决议《卡洛林那法典》的次级效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德国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并非像我们一般想象的帝国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时帝国皇帝的影响力不大,帝国内部的区域领主随着宗教改革与宗教战争逐渐取得统治地区内的立法权及其他主导权。在1648年“30年战争”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更是逐渐式微。帝国中的区域领主在17世纪下半叶,逐渐取得强大的统治权力。{24}
三、《卡洛林那法典》的结构与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
(一)《卡洛林那法典》的结构
《卡洛林那法典》总共有219个条文,{25}这个法律的内涵虽然有当代实体刑法的规定,但它主要的规范在于刑事程序法的规定。除此之外,也有当代法院组织法及行刑法的规定,从它的名称《Die Peinliche Gerichtsordung Kaiser Karls V》就显现出这是一部规范重罪的法律,因为Peinliche一词在当时社会表示跟生命或身体有关的刑罚。{26}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以刑事程序法为主,实体法及刑罚执行法为副的法规范。
《卡洛林那法典》在条文结构上也没有总则、分则的区分,也没有看到章节的区分。在219个条文中,程序法跟实体法是混在一起规范的,整个法律并没有完整的概念与体系。这样的法律跟当时已经存在的中国明朝的《大明律》或者清朝的《大清律例》已经有了总则、分则的概念(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的分类)相比较,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法律。{27}
《卡洛林那法典》219个条文中,第1到105条以及175条到219条主要是今日刑事诉讼法或程序法的规定,106 -175条之间主要为今日有关实体法的规定,其他则为今日刑罚执行法的规定。在这个法律中我们尚未看到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相关规定,甚至可以在第24条看到允许审判者在审判时,进行类推适用的规定。《卡洛林那法典》第24条规定中提到,在遇到相类似的案件时可以类推适用相类似的规则处理,因为要将所有不法行为均加以规范是不可能的。{28}《卡洛林那法典》第13条规定“法定刑罚”限制法官任意决定刑罚的方式。{29}
(二)《卡洛林那法典》中有关刑事程序法的规定
一般德国刑法史的书籍分析《卡洛林那法典》时会分成前言、程序法与实体法内涵加以分析。{30}《卡洛林那法典》的“前言”( Vorrede)主要说明为什么要订定这个法典,强调订定这个法典是由所有的身份等级们,例如选侯(Churfuersten)、诸侯(Fuersten)及身份等级(Staende)等共同的意思所决定的。透过“前言”可以了解1532年前后,神圣罗马帝国中皇帝、选侯、诸侯及各种身份等级在帝国议会的角色与关系。在“前言”中还特别强调这个法律主要希望透过有经验的人与研究者一起共同讨论确定,究竟哪些事情应属于刑罚的对象,那些行为可以被正当化(Rechtsfertigungen)以及如何做才能公平。“前言”同时宣示这个法律的效力,不会取代旧的传统及合于公正的习惯。{31}
许多刑法史研究者认为《卡洛林那法典》主要是一个刑事程序法规范,事实上,它还规范现代刑法各论的行为、刑的执行及监狱管理等有关的事项。下面主要分析《卡洛林那法典》中跟刑事程序法比较相关的规范。
1.关于刑事诉讼启动的规定—职权主义(或纠问制度)及告诉主义
在《卡洛林那法典》中对于刑罚的追诉主要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由被害人发动的途径(第11条),另外一个可能则是第6条所规定以职权介入刑罚的追诉。《卡洛林那法典》第6条条文标题标示着“依职权介入刑罚追诉”(Strafverfolgung von Amts wegen)。{32}此一规定提到,如果有人做出不法行为(Ueblthat),因此被传说或透过可靠的指控,法官应该由公权力介入,进行刑事追诉。第6条特别要求法官有义务对于谣言中的不法行为进行调查,了解它的真实性。另外,第11条则允许被害人,私人提出追诉(Strafverfolgung aufAntrag)。而为了保障被追诉者的利益,《卡洛林那法典》第12-14条规定有关保全的制度(Sicherheitsleistung)《卡洛林那法典》第12条规定,如果个别个人要对他人提起刑罚的追诉时,必须负起担保责任(Verhaftung und Sicherheitsleistung)。{33}
一般刑事诉讼法的学者会特别说明,职权主义后来成为现代法制国家中犯罪追诉的主要原则,也就是由国家机关,本于职权发动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34}今日我们会以为国家追诉犯罪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德国法制发展史,由统治者基于职权追诉犯罪却是在中世纪末才逐渐形成的制度。在中国《唐律》、《大明律》中是否有所谓的职权主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在《唐律》502个条文中可以看到有少数条文或特别规定“父母告乃坐”。{35}
当代刑事诉讼法学者对于《卡洛林那法典》中关于刑事追诉的规定,往往以“纠问主义”( Inquisitionsprozess)称之。所谓“纠问主义”乃是指刑罚的诉讼程序由审判者从头到尾,依职权负责调查原则。{36}这个制度从13世纪末开始逐渐在欧洲大陆发展,并在欧洲社会运作了几百年,一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有相关论著讨论在审判过程中,如果审判者同时负责作出裁判并同时要担任原告的人,但制度却又要审判者同时考虑被告是否被冤枉。这样的制度设计对于犯罪被追诉者是否公平值得怀疑。因为审判者此时同时为提起追诉程序的原告,又身兼裁判的权力。在欧洲,对于“纠问制度”的挑战开始于19世纪,主要的挑战从法国开始。法国在19世纪中开始调整刑事诉讼制度,将检察官起诉的制度引入刑事诉讼程序,自此,在欧洲大陆各国的刑事诉讼法逐渐设计出检察官与审判法官并列的制度。检察官负责案件的侦察以及犯罪证据的搜索,并作为案件的起诉者,法官则居于中立的角度,依原告与被告所提出的证据作出审判{37}。
1877年德国的《帝国刑事诉程序法》( Reichsstrafprozessordnung)引进为被告的辩护制度,规划了由法官、检察官及辩护人所组成的刑事诉讼制度。而当代刑事诉讼的制度认为检察官的角色不仅要对于犯罪者加以追诉,他的重要角色也在于不要让无罪的人受到国家刑罚的追诉。{38}台湾的刑事诉讼法从2003年开始受到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引进所谓“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制度及犯罪协商制度,德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逐渐减弱。事实上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度也受到美国法的影响。台湾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让我们看到法律制度在不同时代变迁的痕迹。{39}
2.将审判者(Urteiler)与法官(Richter)的传统功能加以改变合并的规定
《卡洛林那法典》第1-5条主要规范参与审判者的角色。在第1条中我们看到有关法官(Richtern)、审判者(Vrtheylern)及其他参与审判者的角色(gerichts personen)的说明。透过第1条的规定,清楚地看到中世纪的德国审判制度中,法官(Richter)与审判者[Urteiler)的角色是分离的,法官主要做诉讼的进行的主导者,但不决定审判的结果。在法条中特别强调由贵族及具有知识的人参与审判的工作。《卡洛林那法典》从第62条开始对于法院审判的活动,包括告诉人如何在法庭中提出他人犯罪行为的证明(第62条),哪些人不可以到法庭作证(第63 -67条),证明提出的格式(第70条),审判的速度(第77条),审判的结束,公开审判的原则,如何作出裁判及法审判时,法典如何被参考、使用,法庭中参与审判的人数,刑讯如何被运用等均加以规定(第78-104)。{40}
3.有关刑讯制度(Folter)的规定—有嫌疑犯罪行为之处理
中世纪之际,德国传统刑罚制度中对于一个人是否犯罪,主要跟据“神判”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犯罪。所谓“神判”制度,例如要求被控告者走过烧红的铁板或者丢入水中等方式,来证明其是否犯罪。{41}
从当代人的眼中看《卡洛林那法典》中的规定,刑讯制度(Folter, peinliche frag)是一件惨忍不尊重人权的规定。但是从当时人的角度来看,《卡洛林那法典》的规定限制了刑讯使用的范围,仅在为了取得犯罪者的自白并有可疑的犯罪形状才可以进行刑讯。在《卡洛林那法典》第8条规定,为了了解犯罪的真相,何时可以使用刑讯(Folter)。但《卡洛林那法典》对于刑讯使用的范围,例如方式、时间以及次数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仅在其第58条中规定,由法官依据理性判断来决定。这样的规定对于犯罪者的人权的保障非常不足{42}。
《卡洛林那法典》中在多处规范使用刑讯的可能,尤其是关于在哪些情状下,为了确认与采证犯罪行为以及有关证明力的问题部分作了许多有关刑讯的规定,例如《卡洛林那法典》对于可疑的犯罪型态区分为直接的可疑情状与间接的可疑情状。所谓直接的可疑情状,例如在第29条规定,在窃盗发生情形下,有人的东西被拿走,而身上藏有该样东西的人将成为最有可能的犯罪者,这时候为了要查出真相,可以对之加以刑讯。另外,第26条规定,在有人被杀死的情况下,那个跟死者有冲突的人,将被怀疑可能是他谋杀死者,那么也可以对这样的嫌疑者进行刑讯(第26条Verdacht bei Zweifelsfaellen)《卡洛林那法典》第33条规定,在规范对于谋杀案件嫌疑犯处理的方式时提到,在有人被谋杀时,如果有犯罪嫌疑人被看见他在死者死亡期间,衣服上染有血迹或手上拿有武器或者死者有某些东西在他身上被发现时,那么他将被告发并因此可以对他刑讯(第33条Beson-dere Verdachtsgruende,Mordverdacht) 。{43}
为了确定犯罪的真相,《卡洛林那法典》在第22条规定如果没有嫌疑人的自白或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行为,那么不可以对于行为人进行身体的刑罚(第22条Verbot peinli-cher Bestrafung ohne gestaendnis oder Tatnachweis) 。《卡洛林那法典》中规定许多关于不同犯罪型态中的犯罪嫌疑(Tatverdacht),从第32到44条都是规定不同犯罪的嫌疑状况。例如第32条规定有关危险恐吓的嫌疑(Verdacht bei gefaehrlicher Drohung);第33条规定有关谋杀的嫌疑行为(Mordverdacht);第35条规定可疑的杀婴行为(Verdacht auf Kinstoe-tung);第37条规定可疑的混合毒药行为(Verdacht der Giftmischerei);第38条规定可疑的强盗行为(Raubverdacht);第40条规定可疑的协助强盗或协助窃盗行为(Verdacht derBeihilfe bei Raub und Diebstahl );第41条规定可疑的纵火行为(Verdacht der Brandstif-tung);第43条规定可疑的窃盗行为(Diebstahlsverdacht);第44条规定可疑的魔法行为(Verdacht der Zauberei)。
从上述条文,我们可以看到《卡洛林那法典》不如同一时代中国的《大明律》或《大清律例》体系完整,但是,在关于如何确定一个人有无犯罪部分相对于《大明律》或《大清律例》有更为细致的规定。相对于当时的中国传统法律对于实体犯罪的详细规范,《卡洛林那法典》似乎比较注意到犯罪调查过程中的严谨性。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卡洛林那法典》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还是有所不足。不过,有关人权保障的思考虽然在欧洲从启蒙时期被提出,希望节制国家面对人民权利时的力量,但是,人类开始真正落实人权保障的理念,应该是起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提醒我们,新的理念要落实需要长时间的讨论与社会共识。
《卡洛林那法典》对于刑讯制度的节制并未能节制德国地区有关女巫追索的审判程序(Hexen Prozessen)及对异教徒的迫害。德国地区到了18世纪中,才开始有学者对于刑讯制度提出质疑。{44}刑讯制度在德国普鲁士1740年才受到节制。当时对于所谓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例如谋反或者想要谋害君主等行为(Majestaetverbrechen, Landesverrat)或者严重的谋杀行为(Mordtaten)还允许运用刑讯。{45}德国到19世纪刑讯制度才逐渐消失,汉诺威地区在1822年消失,瑞士有些省份在1850年才消除。
4.有关自白的规定
除了关于刑讯制度及对于特定犯罪的嫌疑处理有详细的规定外,《卡洛林那法典》还详细规定各种犯罪行为的自白,对于自白的方式也有详细的规定。在第56条规定中强调纵使犯罪嫌疑人在受到刑讯对于他的犯罪自白了,法官仍需要再仔细地确定犯罪行为的所有过程,以便了解真相。法官甚至需要在刑讯后几天,当刑讯的感受逐渐消失后,再度在刑讯的空间之外,对于被指控犯罪者确定他的自白{46}。
《卡洛林那法典》也在第48条到53条及第60 -61条中针对个别犯罪行为的自白加以详细的规定,并指示审判者在不同的犯罪类型对于犯罪者的自白应该进一步如何确定。例如在第48条规定有关谋杀嫌疑犯的自白的处理(Gestaendnis des Tatverdaechtigen beiMord),在条文中强调在谋杀行为的犯罪嫌疑人经过刑讯承认他的行为并记录后,审判者还是要很详细地问他为何他要进行谋杀行为,他的行为在哪一天?哪一个时段?在哪里如何结束?有无人帮忙他进行谋杀?在哪里埋葬被害者?用什么样的武器杀害被害人?他是否有拿被害人身上的东西或钱财或者犯罪嫌疑人如何处理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否被出卖或者有交给他人或者藏起来等问题。
又例如在第51条规定如何处理纵火的自白(Gestaendnis bei Brandstiftung),在条文中特别说明对于纵火犯自白后,仍旧要特别问他为何要纵火?在那个时段?用什么东西起火?从谁那里?如何?在哪里取得起火的东西等问题,从何时开始应该问那些事情(第51条)。
另外在第52条规定对于施展魔术的人的自白要如何处理(Gestaendnis bei Zaub-erei),例如要对于为何施展魔术,以及其他各种情境等事项加以询问;例如详细地了解跟谁,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如何及何时为魔法的施展,用哪些语言或道具。如果指证者提到犯罪自白人有将某些东西埋起来或者收藏起来,那么要去查清楚埋藏或收藏的东西在哪里。甚至应该问自白者,他的魔法从何人处学习的?他如何会有机会碰到教他魔法的人,甚至要问他是否对其他人施展魔法,且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损害(第52条)。{47}
5.对于审判记录的规定(Protokoll )
在《卡洛林那法典》中,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规定类型就是第181到189条有关如何进行审判记录的记载。在第181条的规定中,详细规定法庭的记录者应该如何针对审判程序进行记录(Verhandlungsprotokoll ),例如法庭的记录者(Gerichtschreiber)应该在有关刑罚的审判事项中,将所问的问题与回答相关的事务分别且详实的记载,例如控诉者指控的重要事项的记载。第182条规定对于被控诉者的回答的记录,例如关于在哪一天,那个时段,哪些人参与审判加以记录。记录者必须也要签名(第182条Protokoll ueber dieEinlassung des Angeklagten)。在第183条规定,对于控诉者的陈述要加以记载,例如如果被控诉者否认他被控诉的行为,要如何记载。控诉者如何更进一步地将他所控诉的行为加以证明。另外,在第184到189条分别规定,关于证明记录(Beweisprtokoll)、自白记录( Gestaendnisprotokoll )、否认记录(leugnungsprotokoll)、主张阻却违法理由的记录(Protokollder vorgebrachten Entschuldigungsgruende)、依职权提起控诉的记录(Protokoll bei Anklagevon Amts wegen)以及关于记录的形式的规定(Form des Protokulls)。{48}
(三)《卡洛林那法典》的有关刑事实体法规定
《卡洛林那法典》中程序法与实体法是混合规定的,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前后次序或章节。另外,在实体法的规定中,看不到类似当代多数国家刑法典中区分总则、分则的体例。下面将针对法典中有关实体法的规定加以分析。
《卡洛林那法典》在第106条到180条之间规定今日在许多国家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各种犯罪类型,不同于现代刑法分则中将犯罪类型主要区分为侵害国家法益之罪(例如台湾的刑法分则第1-10章)、侵害社会法益之罪(刑法分则第11-21章)、侵害个人法益之罪(刑法分则第22-35章)。《卡洛林那法典》中有关犯罪类型的规定是分散的,没有清楚体系(至少从作者的观点看)。另外,《卡洛林那法典》中多数的规则还是以描述性( Erzaehlende Form)方式规范犯罪行为,缺乏抽象性的规则。{49}
《卡洛林那法典》中有关犯罪行为的各种规定(今日被视为刑事实体法)包括下列几种犯罪类型:
1.关于规范亵渎宗教或者追索女巫或魔术行为的处罚
《卡洛林那法典》有关刑事实体法的规定大约开始于第106条。第106条是规定有关亵渎神的刑罚(Strafe fuer Gotteslaesteerer),在条文中规定,如果有人对于有无限权力的神或者神的母亲圣母玛丽亚有亵读或不敬的行为(Schendet),那么应该由下级的法院或其他公职人员跟法官及审判者提告,并依据帝国的法律对之加以处罚。这个处罚包括对于身体、生命的处罚,处罚的方式主要依据亵读行为的情形决定。第107条规范对于假的宣誓的处罚(Strafe fuer Meineid),条文中规定如果有人作假宣誓,那么他举起来宣示的两个手指头将被割断(abzuhawen),如果因为某人的假宣誓让他人受到刑罚的制裁,那么作假宣誓的人也要受到那个人一样的刑罚处罚。第109条主要规定对于施展魔术者的处罚(Strafe fuer Zauberei ),该条文规定,如果有人透过魔术伤害他人或者使他人受到不利益(Nachtheyl),那么将受到生命刑而且要用火烧来执行死刑(Strff mit dem fewer thun)。
当代刑法通常对于施展魔法的行为顶多以“不能犯”加以处理,但在16、17世纪的德国地区这样的行为却可以被处以死刑。有关对于魔术行为或者女巫追索的处罚,在德国地区直到18世纪才逐渐消失。在同一时期中国传统的法律中有两条跟施展魔术相类似规定。《大明律·刑律一·贼盗门》“造妖书、妖言条”律文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另外,在《大明律·刑律二·人命门》“造畜蛊毒杀人条”律文中规定:“若造魔魅、符书咒诅,欲以杀人者,各以谋杀论。因而致死者,各依本杀法。欲令人疾苦者减二等。”《大清律例》中也有相同的条文。这两个条文在中国继受德国法律体制之后才消失。{50}
2.对于与性有关的犯罪的规定
《卡洛林那法典》在第116-123条中规定类似当代许多国家刑法分则中所谓妨害风化章、妨害性自主章以及妨害婚姻与家庭章的犯罪行为。分析《卡洛林那法典》中与性有关的犯罪类型,可以看到下面几种类型:
(1)违反自然的性行为的处罚(Strafe fuer widernatuerliche Unzucht)
《卡洛林那法典》第116条所谓违反自然的性行为,包括人与畜的性行为,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间发生的性行为。根据该条规定行为人应该依据古老的习惯被烧死(mitdem fewer von leben zum todt richten)。
(2)发生在一定亲属间之性行为处罚(Strafe fuer Blutschande)
《卡洛林那法典》第117条禁止任何人跟他的一定亲属发生性行为,这些亲属例如继女(Stiefftochter)、媳妇、继母等。根据规定这样的行为将依据祖先及帝国所书写的法律处罚。
(3)诱拐行为的处罚(Strafe fuer Entfuehrung)。
《卡洛林那法典》第117条禁止诱拐有配偶或未婚的女性,如果违反女性的配偶或未婚女性父亲的意思,加以诱拐,纵使该位有配偶之女性或未婚女性是出于自愿的,其配偶或未婚女性的父亲均可提出控诉。
(4)强制性交的处罚(Strafe fuer Vergewaltigung)。
《卡洛林那法典》第119条规定对于强制性交行为的处罚。此条文规定如果有人对于有配偶的女性、寡妇、未婚女性利用暴力及违反她的意思发生性行为,那么有可能被用剑分尸执行死刑。
除了上述几种跟性行为有关的处罚规定外,第120条规定婚外性行为的处罚,第121条规定拥有多个妻子的处罚(Strafe fuer Bigamie),第122条规定让自己的配偶或子女从事性行为者的处罚(Sttrafe fuer Zuhaelterei)、第123条则规定关于皮条客的处罚(Strafe fu-er Kupelei)。
3.对于各种伪造行为的处罚
《卡洛林那法典》第111-113条主要规定伪造铜币的处罚(Strafe fuer Munzfaels-chung)、伪造文书的处罚(Strafe fuer Urkundenfaelschung)、伪造度量衡的处罚( Strafe fuerMassfaelschung ),条文中虽然规定对于犯罪者处以身体刑或生命刑,但关于处罚的刑度均未很明确地加以规定。条文中仅提到如果是伪造货币要看哪些货币被伪造,是否被使用并造成他人的不利益等都是考虑处罚的标准。如果情境严重,可以处以用火烧的死刑(第111条);另外,对于伪造度量衡者,严重且恶意的行为者,也可能判处死刑;情节不严重的可能将他逐出该地区或者处以其他身体刑(第113条)。
4.各种有关杀人的处罚规定
《卡洛林那法典》对于杀人罪作很多细微的规定,从130条到138条分别规定用毒药谋杀人的处罚(Strafe fuer Giftmord)、杀婴的处罚(Strafe fuer Kindestoetung)堕胎行为的处罚(Strafe fuer Abtreibung)、以药物杀人的处罚(Strafe fuer Toetung durch Medikamente)。另外,第135条规定对于自杀行为的制裁(Sanktionen bei Selbstmord),第136条规定动物伤人的行为(Strafe fuer Tierschaden),第137条规定对于谋杀或杀人行为的处罚(Strafe fu-er Mord und Totschlag),第138条规定有不可归责的事由杀人行为的处罚。
5.各种有关窃盗(Diebstahl )的处罚规定
《卡洛林那法典》从第157-175条规定各式各样窃盗的行为处罚。第157条规定秘密的窃盗、公开的偷窃、潜入他人住所的窃盗、在田野的窃盗行为(167条)、窃盗木材的行为(168条)、池塘或溪水中鱼类的窃盗行为(169条)、在教堂的窃盗行为(171条)、对教堂中被祝祷的器物的窃盗处罚(第172条)。{51}
四、《卡洛林那法典》中刑罚的残忍性与恐怖性
从《卡洛林那法典》法典有关刑事实体法的规定,可以看到当时对于许多在今日看起来属于轻罪的行为会以非常重的刑罚加以处罚,例如对于神或宗教器物的亵渎或偷窃行为可能被处死刑。《卡洛林那法典》对于各种死刑或者身体刑的执行方式有详细的规定,刑罚可以分为死刑、身体刑、监狱刑等。下面分别说明这种刑罚的内容。
1.死刑的执行
《卡洛林那法典》在第192条说明死刑的执行方式。死刑分为7种方式。
(1)火烧(Zum fewer):用火活活烧死。
(2)用剑刺死(Zum schwert):用剑活活刺死。
(3)将身体分成四份(Zu der Viertheylung):将身体分成四份切割并将四份的肢体放到四个地方街道上,挂在公共的地方示众。
(4)轮刑(Zum rade):将人绑在大轮子上,透过转动让身体分碎,也要将身体部位挂在公共场所。
(5)吊刑( Zum galgen):将人用锁炼加以吊死。
(6)淹死(Zum ertrencken ):将人活活淹死。
(7)活埋(Vom lebendigen vergraben):将人活活的埋葬。
而在《卡洛林那法典》第194条甚至规定,审判者可以决定,对将被处罚的人,在死前用烧红的铁钳加以撕裂(Zangenreissen )。我们从上面这些关于死刑执行方法的规定,可以了解到当时刑罚的残忍性与恐怖性。不过,拉德布鲁赫教授在他的导论中提到,由于当时的人生活在死刑经常公开执行的情境中,再加上生活的恶劣状况,使得他们对于挂着的尸体或者公开陈列的尸体基本上没有特别的感受,几乎是习以为常。{52}
2.监狱刑
《卡洛林那法典》仅在第195条中规定何时将犯罪者放置于监狱刑。条文特别提到对于那些被指控的人,为了避免他们继续进行犯罪,在他们没有交出保证金之前,为了保障一般人民及地区的安全,因此要将他们关在监狱。这个简单的的规定,显现出当时监狱刑显然还不是一种重要的刑罚方式。
3.身体刑
《卡洛林那法典》在第198条说明各种身体刑的执行方式(Urteilstenor bei Koerper-strafen),主要方式有下面4种。
(1)割舌(Abschneidung der Zungen )割舌的执行外,还有所谓用热的铁器在身体烙印的刑罚。
(2)断指(Abschlagen der Finger):透过切断两只手的指头,处罚行为人并让他赎罪。
(3)割耳朵(Abschneiden der Ohren):割两只耳朵。
(4)杖刑(Rutenschlagen )。
上述4种身体刑在执行完毕后,被处罚的人都可能被驱逐离开该地区。我们从《卡洛林那法典》的规定,可以看到已经不同于中世纪那种以赔偿金(Wergeld)及罚金制度或私人之复仇及和解的方式来处理杀人、伤害等犯罪行为。从条文的结构与内涵看,今日很重要的自由刑(监狱刑),在当时并非重要的刑罚。自由刑仅是在犯罪者是危险时,暂时加以管制的制度或者代替其他刑罚的功能(参考第11、216条)。欧洲社会一直要到1595年到1597年间在荷兰Amsterdamer的Zuchthaeuser设置后,才开始以自由刑(监狱刑)逐渐取代身体刑。{53}
五、《卡洛林那法典》在德国刑法史上的意义
《卡洛林那法典》是德国进入近代以后的第一个重要法律,这部法典是一部同时包含程序及实体法的刑法法律,它是德国现代刑法学发展的基础。{54}在《卡洛林那法典》被订定的同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许多这种同时具有刑法与刑事程序法性质的法律,另外,在同一时期,德国各地区也出现所谓的警察立法(Polizei Gesetzgebung)。虽然《卡洛林那法典》的“Salvatorische Klausel”约定,使得当时各地区的地方法律优先《卡洛林那法典》的适用,然而由于许多地区的地方法律是以《卡洛林那法典》作为它们的参考模板,因此,它在德国各地区的法律实务上有真正的影响力,当时的人将它视为共同的刑罚法源。{55}
1844年在曼海姆的高等法院的律师Gastav (v.)Struve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19世纪当中,而我们的刑事诉程序法与刑法还是已在16世纪出现的《卡洛林那法典》的基础上。”{56}《卡洛林那法典》除了影响当时德国地区的许多地方法律,同时也影响着奥地利地区、波兰16世纪的诉讼程序规定。{57}
《卡洛林那法典》第219条规定,在诉讼实务上遇到疑难杂症时,可以向上级的审判机关或大学法学院请求提供意见。这个条文让地方的审判者面对审判困难时,可以将案件相关文件移送到各大学法学院,请相关的研究者提供咨询意见。这个制度在德国地区,一直到了16、17世纪仍继续存在。这种由大学法学院提出鉴定书的制度,使得德国的法学者对于审判实务有强大的影响,同时也拉近了德国法学院中的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距离。将审判文件送到大学法学院请求鉴定的制度,后来因为地区领主的财政无法负担大学法学院鉴定书费用而逐渐消失{58}。
《卡洛林那法典》是一部承先启后的法典。本文作者在《德国法制史-从日耳曼到近代》一书第二编第五章曾经特别说明,从《萨克森宝鉴》的记载,可以发现12、13世纪的德国地区,并没有一个类似现代刑法体系般有系统的刑法原理存在。另外,罪刑法定主义之观念“Nulla Poena sine lege”的观念在12、13世纪的德国地区也尚未出现。{59}《卡洛林那法典》中,则可以看到某些规定已具有现代刑法理论的影子,例如关于紧急避难的规定、帮助犯的规定,还有有关归责事由的规定(第140-142、177、179条)。{60}不过《卡洛林那法典》在第105条中还规定类推适用之可能{61}。
从《卡洛林那法典》第104条规定可以看出有一点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的想法,至少关于死刑的处罚,已经规定要先有法律的规定才能作出死刑的审判结果。第104条中规定:“如果有人依据我们共同书写的法律,杀害他人,那么法官将依好的习惯或规范同样对他处以死刑。但,如果皇帝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于某种行为人加以刑罚,而且帝国中其他规范也未规定要对该行为处以死刑,那么仅可以对该不法行为者,处以身体刑,让他至少可以继续活着。”{62}
另外,在《卡洛林那法典》中,可以看到法典中提到故意的观念,虽然何谓故意还不是很明确。{63}而在第179条则明确规定,对于因为年轻或其他身体精神的衰弱,无法对于自己所进行的不法行为有所认知者,应该依其情形,经过咨询后,决定如何处罚。第164条还明白规定对于那些14岁以下的窃盗者不应该处以死刑,仅处以身体刑{64}。我们从这些规定中,看到现代刑法的某些观念已经在《卡洛林那法典》有了雏形规定。
六、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卡洛林那法典》的内容并透过它说明德国刑法在近代的发展历程,目的在于探讨当代影响东亚各国刑法典与刑法学非常深远的德国刑法与刑法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可以了解到德国刑法体制在《卡洛林那法典》存在的16世纪还是处于习惯法与体系尚未完整的成文法状态。与此相应,刑法学学说也尚未发展出一个近现代的体系。
本文延续作者在《德国法制史—从日耳曼到近代》及《传统家庭、婚姻与个人、国家—中国法制史的的研究与方法论》两本书的研究目标。在这两本书中,均呈现作者想要透过比较法制史,寻找德国法制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路径以及清朝法制的没落因素,并进而找出法律制度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局限。
第5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本文所提及的“大清刑律”,是指1911年1月25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刑律》。此部法律,学术界另有《大清新刑律》和《钦定大清刑律》之说[1]。
本文所指的“大清刑律草案”,是指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等于1907年10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和12月30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奏的大清刑律草案总则和分则。广义上的“大清刑律草案”,按照日人冈田朝太郎的说法,有“六案”之多[2]。本文所言“大清刑律草案”,专指1907年的“一案”,“二案”则以“修正刑律草案”称之,其余草案概不涉及。
本文所研究的“大清刑律草案签注”,是指修订法律馆上奏大清刑律草案后,按照立法程序,朝廷下宪政编查馆交中央各部院堂官、地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征求意见。从1908年到1910年,京内外各衙门陆续上奏对大清刑律草案的意见,这些意见被称为“签注”。一份完整的签注奏折应该包括对草案发表整体看法的原奏和所附的对草案总则和分则逐条发表意见的清单,即所谓的“签注原奏”和“签注清单”。应该指出,自1907年刑律草案上奏后,社会各界对草案发表了大量的意见,各级官员上呈的奏折也不少[3],但除了上文所限之外,均不在本论题研究范围之内。
二、关于草案的立法目的
关于草案的立法目的,亦即修订《大清律例》的动机和原因,领事裁判权问题被置于了突出的地位。1907年修订法律馆上奏刑律草案的奏折中,认为《大清律例》应予修订的原因有三,“曰毖于时局,曰鉴于国际,曰惩于教案”,其中第一点就是领事裁判权问题,其他两点也都与外交有关。可见,追求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核心的国际平等,至少在表面上的确是草案的一个主要立法目的[4]。
对于草案的这样一个立法目的,山东、东三省签注给予了明确的赞成和支持,如东三省签注就指出,“世界大同,文明竞化,均以法律之大同觇权利之得失,向以我国律例与欧美异宜,故各国之有领事裁判权载在约章,遂为放弃主权之缺陷。今以立宪之预备改订法律,果能变通成规、集取新法,使各国商民之在我领土者均以诉讼为便,则宣布实行,或有更改旧约与各国跻于同等之一日”[5]。但更多的签注,虽然也认为“原奏所注意者只收回治外法权一事,自是今日急务。…今欲收回此权,则于旧律之有碍治外法权者,自不能不酌加修改”[6],“凡关于国际交涉之失败,无不缘于中律不同之故,是则修订法律实为至急切要之图”[7]。但在对于如何修律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修律如何处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对于如何修律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学部签注和安徽签注以日本为例,指出了军事因素的作用更甚于法律因素。“收回治外法权,其效力有在法律中者,其实力有在法律外者。日本改律在明治二十三年,直至明治二十七年以后,各国始允其请,是其明证”[8];“考领事裁判权,西人初行于土耳其,继行于我国,又继行于日本。惟日本已与各国改约撤退,实由军事进步,非仅恃法律修明已也”[9]。所以领事裁判权的收回,主要依靠的是国家力量的强大而非法律与西方国家的齐同。“外人所以深诋中国法律必须改订者,约有数事:一刑讯无辜、一非刑惨酷、一拘传过多、一问官武断、一监羁凌虐、一拖累破家,果能将此数端积弊严禁而国势实力日见强盛,然后属地主义之说可以施行,外人自不能干我裁判之权。并非必须将中国旧律精义弃置不顾,全袭外国格式文法,即可立睹收回治外法权之效也”[10]。
基于上述观点,许多签注指出在法律上维持本国的风俗礼教与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并不矛盾,草案应当处理好内政和外交的关系。“我国今日改定刑律,于中国纲常伦纪大有关系者,其罪名轻重,即使与各国有所异同,似亦无碍于收回此项法权也”[11],“以法律论,必实行于本国而后能见信于外人,若专务文明之名,于本国历史人情风俗习惯一切相违,窃恐人民至成都不及,非徒无益而转有损”[12]。
即使但就法律而论,许多签注也对草案的相关规定是否有利于收回领事裁判权提出了质疑。如草案总则第二条:“凡本律不问何人于在中国内犯罪者适用之”;第八条:“第二条第三条及第五条至前条之规定如国际上有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仍从条约法规或惯例办理”。草案第二条规定贯彻了刑法的属地主义原则,但面临着如何处理各国以条约获得的领事裁判权这一事实问题,草案在立法理由部分认为本条对外国人的适用范围为:“第一、无国籍之外国人;第二、无特别条约之外国人;第三、条约改正后之外国人”[13],同时草案第八条对属地主义作了限制,在国内法上实际上承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河南签注第二条意见认为,如此规定则收回领事裁判权仍是一句空话,“如理由内所揭之三项,则此条仍属具文。盖修改刑律应以撤去领事裁判权为惟一之目的,中英中日等条约载明: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刑法改同一律,一俟妥善即允弃其治外法权。其治外法权即指领事裁判权而言,…今乘修改之际必万汇群智互相讨论以臻妥善而期必撤去不合作延宕之笔希望之词。日本改良法律,虽与各国订约议定五年后裁撤,然亦止形诸约文,未尝载诸理由。…而第八条又谓:如国际有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仍从条约法规或惯例办理,直承认其永远享有领事裁判权,尤欠斟酌。拟请更订此条,将第八条删去,并理由亦不必赘列三项致受人以柄” [14];两广签注第八条也反对予国际惯例以优先权,“更定刑律本为收回治外法权起见。释文谓因国际条约而限制刑法全体效力者即领事裁判权是,然则今日所注重以收回领事裁判之权为第一要义也。今本条谓如国际上有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仍从条约法规或惯例办理,夫特别条约转为国际而设,自不能不按约处断,若惯例则所包者广,凡有办过旧案几无一不可成为惯例矣。释文谓暂准各国领事有裁判权系不得已办法,并非常制,不知我以为非常制者难免他人不指为惯例。即此两字恐生无数葛藤,安能事事磋商,辩其为是惯非惯?倘执此条争论,则全部刑律将成虚设,所关非细,似宜再酌。”[15]
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角度出发,邮传部也对草案第八条关于优先适用国际法之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的规定表达了强烈的异议,“本条规定,在立案者本意,系为防止本律与国际法之冲突而设。不知刑法与国际法本自截然两物,各有独立性质,牵此入彼,实为大谬。…故照国际普通法,外国主权者代表者均不受内国刑罚制裁,然各国不以此种条文加入刑法,即如日本新颁刑法。…观此则本条之设,不诚为多事乎?且以国际条约与法规惯例并举,在学理上亦有未妥。夫国际上舍条约惯例即无所谓法规,盖条约惯例为国际法之大源故也。不宁唯是,此条若作为正文颁出,与中国国权体面大有损伤,何则?领事裁判混合裁判等特别条约,只成为国际条约上之权利,与内国法律上之权利,固自有间。若为内国法律付与之权利,则不因开战而消灭,若仅为条约上之权利,则开战时可以失效,今将变条约上之权利而以刑律规定之,与我国所损滋多,是亦不可以已乎?至于惯例两字,尤数荒谬。…此条为各国所无之条文,流弊甚大,非削去不可”[16]。可以看出,邮传部对于国际法的了解,远在修订法律馆之上。
即使从今天眼光看,草案此两条规定确实有欠斟酌,有在国内法上自丧其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嫌疑和危险。似乎这个问题在草案编拟之初就有人提了出来,但草案编纂者不以为然,这导致了第二条实际上仍然是具文,而且在国内法上予以承认。对于不平等条约,草案居然认为神圣,“第一项虽不问何人,然国际公法之原则至尊,为神圣不可犯侵,则刑律不能一律适用,自不待言。又国际公法之原则,有治外法权之人不能适用本律,如第六条所定者是。”河南签注认为,新刑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如果在新刑律中明白承认领事裁判权的存在,那修律何益?领事裁判权是西方以强权用国际条约的形式取得的,是一个事实存在,但不能在国内法上予以承认。但最后这个意见并没有被采纳,相反修订法律观认为河南签注“故作背驰之论,系属有意吹求,应请毋容置议”[17]。修正案第八条改“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为“特别成例”,但无实质内容的变化。提到了邮传部的签注,但未采纳其删去此条的意见。相反予以批驳,认为“邮传部签注以为舍条约惯例即无法规,悉属错误”;“本条即为声明此项限制而设,并非牵国际法入于刑律之内”;“今特定此例于国权国体并无损伤也”。《钦定大清刑律》第八条只做了文字上的修饰,导致就法律上而言对外国人的管辖仍是一纸空文。在当时已经能够区分治外法权(即今日的外交豁免权)和领事裁判权之不同的情况下,草案仍然在国内法上承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存在,这的确和沈家本一再宣传的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说法大相矛盾,由于沈家本在草案中没有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解释,今天我们无法揣测他老人家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想的。这也使我们怀疑,沈家本主持清末修律,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要收回领事裁判权吗?
立法目的上的偏差,遂导致了草案分则第三章关于国交之罪的规定。对于此章规定,众多签注提出了异议。如广西签注以前几年的租界苏报案、李鸿章在日本被刺案为例,说明草案关于国交之律中将外国君主等同于本国君主、外国代表等同于尊亲属而予以刑法上的保护是错误的[18]。两广签注反对草案第107、108条在刑法上置外国君主皇族与中国帝室同等看待。“今以外国君主大统领同于乘舆,外国皇族同于帝室,若有危害不敬,科罪惟均。非特中国臣民心理有所不安,即稽诸列代典章,似亦无此律法。…夫尊君所以劝忠敬上,所以正乱,似未可内外无别视为同等。此律务当酌改或竟删除为宜”;反对第109条杀伤外国代表按杀伤尊亲属之例处断,“今以外国代表等于父祖,若有杀伤即照此律处断。非独骇国民之视听,抑恐贻笑与外人。纵非谓其罪质相同,与以某律论者有别,而查其文义,实无殊科。恐不足以餍人心而昭法守”;对于第110条侮辱外国国旗罪和第111条滥用红十字作为商标罪,两广亦认为应属国际条约的范围,“似不宜搀入刑律致有阻碍”[19]。邮传部则认为第112条中国臣民聚众以暴力潜窃外国领域罪一条,“中国臣民下须加入“无故”二字或加“未得国家之同意”数字似较妥当[20]。陆军部举日本刑法和国际公法两例说明,对第110条侮辱外国国旗罪定罪应与限制,“似本条应添国旗章以堪为国家代表者所揭之旗章为限,并须外国政府请求然后论罪。对第112条,则以“英人以东方公司墟印度,即得印度然后归诸英国国家。虽非暴力,其为潜窃外国领域无疑,故无人从而罪之者”为例,认为本条无任何意义反而有害,“凡中国臣民潜窃外国领域者云云,此条为吾国现行刑律所无,亦为各国刑律所不载。…则本条有同虚设且恐适招外交上之结责,似宜删除”[21]。
本章国交罪的规定问题最大,一共十三条,在1997年刑法中找不到类似的一条。如1997年刑法有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罪但没有侮辱外国国旗罪,原因就在于这事关国际关系,刑法只涉及国内事务,而不规定国际关系,更何况也不能把侮辱外国国旗定为犯罪。至于滥用红十字作为商标罪国际上并没有定罪,更属草案编纂者的首创,本条草案立法理由云:“滥用红十字之记章以为商标亦足生列国之异议,而有害国交之虞者。故特为加入,将来各国刑典上必须有之规定也”。基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现实,适当的规定国交之罪以防止类似因义和团运动而导致的外交纠纷和战争而危害国家利益,亦无不可。但把外国君主视同本国皇帝、外国代表视同父母,确实有伤民族感情,也丧失了国格、人格,确实有点类似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友邦惊诧”卑躬屈膝以媚外的味道。至于把国际上都无先例的“滥用红十字记号作为商标”定为犯罪予以处罚,则和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一样有领世界潮流的意思,并信誓旦旦的表示他国一定会跟风,这就有点自不量力了。
草案第三章关于国交之罪,尽管众多签注提出异议,如外国君主不能等同于本国君主、外国代表不能等同于尊亲属、侮辱外国旗章定罪应以外国代表所揭者为限、滥用红十字记号作为商标不应入刑律、中国臣民聚众以暴力潜窃外国领域不应入律定罪、外国开战须不在中国境内者方可布告中立等,但修正案全未采纳并予以批驳[22]。相反,本章由原案13条扩充为修正案的19条,其规定之详尽、罗列之明晰、对外国及外国人权益保护之周密,令人叹为观止。在对外交往中,法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对于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给予打击是应该的(即第四章关于外患之罪),但一味的为了国家间的“友好”而做出一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措施和规定,就不合适了,草案第三章关于国交之罪即是如此。1997年刑法中即无此章规定的内容。这一方面虽充分暴露了草案半殖民地法律的特色,但另一方面实与编纂者的立场和见识分不开。许多条款,签注认为既然国外都没有规定,如滥用红十字记号作为商标、中国臣民聚众以暴力潜窃外国领域,自不应入律。案语却认为“关于国交之罪名,系属最近发达之理,不能纯以中外成例为言”。战火烧到了中国国土之上,中国竟然可以宣布局外中立,如有违反即应定罪量刑,这哪里是中国自己的法律,俨然是在为侵略者张目。本章许多规定,毫无道理,编纂者却动以外交为名予以辩解,以外交上的损失和危害来说明罪名的必要性,恰恰犯了他自己所批评的“牵事实于法律之中”[23]的错误。第三章的规定是刑律草案最大的败笔。
除了表面上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以外,实际上草案还有一个主要的立法目的,那就是服务于当时的立宪运动。这一点,沈家本等上呈草案的奏折中讲的不是很明显。东三省的签注奏折则首先把修律和立宪联系在一起,“中国法律至唐较为完备,相沿至今,代有损益,而宗旨不甚悬殊,则以政体未尝变易也。然条例日繁,罪名日重,其意原以惩奸禁暴而干大辟犯科条者岁有所增,所谓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非治本之道也。今既屡颁明诏预备立宪,而法律实为宪政之根据,自应力扫严苛一以公理为衡,删除繁细系以简赅为断。若仍本见行律例以资参考,则必扞格不入而签注不胜其繁。详译总则草案之宗旨,大抵以生命为重、以平均为义。以宥过为本旨,故过失皆得减刑,以人格为最尊,故良贱无所区别。约举数端,皆于立宪政体适相吻合。盖法律之源,本于道德,而行此律者亦必以道德之心使吾民有耻且格以渐几于无过之地。此立宪之先声、寰球之公理也”[24]。1910年宪政编查馆核定刑律草案时,更是把是否合乎立宪制度作为衡量草案的一大标准,甚至提到了保护人权的高度,“揆度时宜,今学校教授已不用科举旧法,且兴办女学,凡所谓国民教育者皆力行之;军队则用外国编制战术,交通则用铁轨轮船,凡此之类,不胜枚举。亦如夏葛冬裘,因时而变。现在朝廷博采各国成法,预备立宪,其要旨重在保卫人权。《钦定宪法大纲》所有臣民权利义务,均逐一规定,旧律之与立宪制度背驰之初,亦应逐加增损。上年臣馆奏定禁止买卖奴婢之律,即本此意。盖必用宪政同一之法律而后可保臣民之权利以尽义务。刑律不改则国民主义无由赞助,练兵兴学阻碍多段,是欲北辙而南其辕,与吏书而掣其肘。非特无成且将生患。此新律所之宜行者一也”[25]。1911年朝廷更是以立宪运动的原因而硬行把还没有履行完立法程序的刑律草案仓促颁布,“据宪政编查馆奏,新刑律分则并暂行章程,资政院未及议决,应否遵限颁布,缮单呈览请旨办理一折。新刑律颁布年限,定自先朝筹备宪政清单,现在开设议院之期已经缩短,新刑律尤为宪政重要一端。是以续行修正清单亦定为本年颁布,事关筹备年限,实属不可缓行。著将新刑律总则、分则暨暂行章程先为颁布以备实行,俟明年资政院开会仍可提议修正,具奏请旨,用符协赞之义”[26]。
在赞成新刑律草案者看来,收回领事裁判权与服务于立宪运动两者并不矛盾,相反还相辅相成。法律制度的齐一和政治制度的齐一会把中国推进到世界大同的境地。而反对新刑律草案的签注,多对草案偏重外交而不顾及内政给予了强烈批评,“或谓前年荷兰海牙保和会以我国法律不同,抑居三等,因将以此收回治外法权,故改用洋律、译从洋文。而窃思治外之道,基于治内,内治而后外可得治。今不明其政刑以讲求治内之道,而先驰其政刑以冀收治外法权,恐治外之权未收,治内之纲纪先堕。…然则法律之事文义之间,宜就地方之情形、人民之资格酌定之,不必舍己芸人自取扰乱”[27];“总之,现时法律不能不采取新说,以期便于交涉,亦不能不兼顾内政,使无越于礼防。本此旨以决从违,则施行自无所扞格”[28]。而反对新刑律草案的人中,不乏在政治上赞成和积极支持立宪运动的中央部院堂官和地方督抚,但在签注草案时,完全无人将新刑律的制定与国内的立宪运动相提并论。看来,政治运动和法律运动,并不总是同步的。
三、 关于草案的立法宗旨
草案的立法宗旨涉及如何处理中国现行刑律和西方刑法理论原则的关系,一般而言,不论最高统治者确定的“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稗治理”[29],修订法律大臣自称的“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30],还是签注所讲的“修改本国之法,则贵乎汰其恶者而流其良,采取外国之法尤贵节其长而去其短。必求无偏无倚、知变知通”,[31]“处新旧递嬗之交,定中外大同之法,岂可得与民变革者,故不妨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要不出“会通中西”的宗旨和原则。但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草案还是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呢?
这原因就在于“会通中西”的宗旨和原则实在太大了,完全可能出现偏于西方和偏于中方这两端的局面。沈家本自己就曾经承认过1907年的刑律草案,“专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为宗旨”[32]。而赞成草案者,则主张“不在枝节上之讨论,而在根本上之解决”,“刑法之变革,先由报复时代进于峻刑时代,由峻刑时代进于博爱时代。我国数千年来相承之刑律,其为峻刑时代,固无可讳,而外人则且持博爱主义,驯进于科学主义,其不能忍让吾国以峻刑相残也,非惟人士为之,亦天道使然也。…论者不揣改订刑律主义之所在,而毛举峻刑时代之习惯,瑕指而瘢索之,毋拐格不相入也。故为今日中国计,既不能自狃于峻刑主义,则不能不采取博爱主义”[33]。山东签注认为中国法律处于峻刑时代,与西方的博爱时代相比,中国法律落后了,应该像西方学习。承认中国法律落后于西方一个多时代,与那些认为中国旧律本极精详、只是因社会的变化而不得不有所修改的观念,的确不同。前者已经不把两者置于同等文明的层次上来理解,而后者竭力把两者置于同等地位来看待。这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和关键问题之所在。许多签注奏折首先着眼于此,也是感觉草案在这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今日改律之要,当删繁减轻。减轻一节,已经明谕罢除凌迟枭首等刑,而且停止刑讯整顿监狱。朝廷仁厚恻怛之至意,已为各国所同钦、万民所共仰矣,要在内外刑官实力遵行。至于删繁一节,前此修律大臣奏请删定现行法律,实为扼要办法。拟请饬下该大臣将中国旧律旧例逐条详审,何者应存、何者应删,再将此项新律草案与旧有律例逐条比较。其无伤礼教只关罪名轻重者,斟酌至当择善而从;其有关伦纪之处,应全行改正。总以按切时势而仍不背于礼教为主,限期修改成书再行请旨交宪政编查馆核议后恭呈钦定颁行海内,庶几收变法之益而不贻变法之害。”[34]
“中国治民之道,断不能离伦常而更言文明,舍礼制而别求教化。今徒骛一时之风尚,袭他国之名词,强令全数国民以就性质不同之法律。在执笔者以为,时令既趋于大同,法典宜取乎公共。不知师长去短则可,削足适履则不可。若以中国数千年尊君亲上之大防、制民遏俗之精意翻然废弃而不顾,恐法权未收,防闲已溃,必致奸慝放恣不可收拾。” [35]
“国法与天理人情相表里,中外风俗互异,刑律自难强同。近来国界交通,时异事殊,更有不能不变通之处,然取人所长,补我所短,必于中国风俗不相背驰始能行之无碍。若风俗如此而刑罚如彼,遂纲目俱备适成一家之言而与人情不相洽,必于天理失其中,即为国法所不容。”[36]
“庶于斟酌轻重之中,仍寓权衡缓急之意。盖此次改订宪章,故应博采东西各国律法,详加参酌,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乃可收变法而不废法之效。”[37]
“总之,刑法变更可以与时为进止,不容削足而适履。纲常名教断难自弃,防闲除恶惩奸,尤宜加重刑典。若徒摹文明,概从宽滥,且恐法权未握,内溃先形,驯至不可收拾。”[38]
“总之,内政外交必须兼权而并顾,新说旧教均宜舍短而取长。必期经训之留贻与法律之制定不违不背无党无偏。”[39]
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许多签注批评草案盲目追求所谓法理上的正确。因而出现了一些完全不顾及本国国情、纯属“食洋不化”的规定。
如草案第27章关于堕胎之罪的规定,这一章的内容在旧律中除了因奸有孕而堕胎致身死者有规定外[40],其他是没有的,所以草案的立法说明是“堕胎之行为戾人道害秩序损公益,本案故仿欧美日本各国通例,拟以适当之罚则”,可见其来源基本出于西方法律。但西方法律禁止堕胎主要基于基督教伦理,况且法律应否禁止堕胎,在西方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堕胎本身并非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由于医学的不发达而缺乏避孕的意识和措施,一个已婚妇女怀孕频繁致一生可生育十几个孩子,这不仅给个人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困难,而且人口的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山西签注认为,“本章规定原为保全人道起见,但中俗妇女最重名节,因奸有孕、畏人知觉私自堕胎或处于不得已之行为,事属秘密,检查不易;况今年生计艰难,各省溺婴之风未熄,其戾人道伤天彝较堕胎尤为过之。草案竟未议及,似觉疏漏”[41]。所谓溺婴成风,除了重男轻女的因素外,主要还是生计艰难、被逼无奈而为之。实际上,草案禁止堕胎而不提溺婴,并非如山西签注所云疏漏,只能理解为溺婴已经属于杀人罪的范畴了故不在关于堕胎之罪章中出现。在视溺婴为杀人之罪的情况下,草案全面的禁止堕胎,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现实,与个人、家庭和国家社会也不利。相比于今天的中国政府,顶着西方国家对“强制堕胎”无理指责的压力而坚持计划生育之国策,草案第27章关于堕胎之罪完全是一个“食洋不化”的典型。
又如草案第三十章关于略诱及和诱之罪,仿照西方法律的规定仅将拐取未满二十岁男女视为犯罪,许多签注则认为犯罪对象应该包括二十岁以上男女,尤其是妇女应予特别保护。“两广、两江签注质问被害者为二十岁以上男女是否处罚,湖南签注以原案不罚此种犯罪”[42],江西签注认为不应该将关于略诱及和诱之罪定为“须待告诉始论”的自诉罪,被略诱或被和诱人在婚姻继续之间其告诉不应该为无效[43]。在众多签注的质疑下,修正案将“凡用暴行胁迫或伪计拐取未满二十岁男女者为略诱罪”改为“凡加暴行胁迫或用伪计拐取女子或未满二十岁男子者为略诱罪”。但同时认为,“不知被害者为二十岁以上男女,原案并非置诸不问,此种犯罪应据第343条第一项[44]处断。盖诱拐罪与逮捕罪有别,既逾二十岁则有独立之资格可为逮捕罪之被害者而不能为诱取罪之被害者。第中国妇女与外国之妇女地位略有不同,兹从多数签注之意见删去女子年龄之限制”[45]。虽然按照多数签注的意见,删去了略诱罪中犯罪对象中女子年龄上的限制,但它所谓中外女子地位不同的理由却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之所以要对二十岁以上的女子予以保护,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女子自身的原因,还不如说是由中国略诱罪自身的犯罪特点所决定的。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与西方国家已经相差无几甚至还有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但1997年刑法第243条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妇女作为犯罪对象仍然没有年龄上的限制。这说明,在中国之所以不能在略诱罪中限制犯罪对象的年龄,并非由于犯罪对象自身的弱点需要特别保护,而是与中国经济文化的特点以及此类犯罪在中国的特点所决定的。即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拐卖妇女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因而需要予以特别打击。对于两广签注主张移送略诱之人于外国者应处极刑的意见,修订法律馆也不以为然,“查本章之罪在外国颇少,盖外国警察制度完备、户籍等法周密,检举犯罪自易,故不必科以重刑。新律实施之日,中国各种制度当以渐臻完备,科以原案所定之刑并非过轻”[46]。而立足于清末之时,从长远看,这种现象在中国之所以较外国为多,主要还是由于中外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从近期看,所谓新律实施之时制度逐渐完备的想法也是一厢情愿。所以对于这类犯罪,既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根除,那予以严厉打击以保持高压态势的思路也是正确的。草案对犯罪现象产生根源的分析不对,相应的处置也自然难以有针对性。历史的事实是,自古以来,略卖人口之事在中国屡有发生,历朝、历代政府都将之定为性质很严重的犯罪予以严惩。草案虽然也规定了略诱和诱之罪,但第332条将已满二十岁的男女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内,削弱了对妇女的特别保护。第338条又将此罪定为自诉罪及成婚者告诉无效的限制性条件,不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关于这一点,看一看1997年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至第二百四十二条关于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罪的相关规定[47]就明白了。1997年刑法本罪是有死刑条款的,而草案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显然对此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
另外,草案第306、307条规定了决斗罪,立法理由谓:决斗仅只两人,彼此签押并汇集多人临场以为佐证,与械斗微异。可知草案规定的决斗罪专指欧洲式的决斗,很多签注对于草案不规定中国盛行的械斗之罪而专言欧洲盛行的决斗之罪表示不解。两广签注认为,“查中国闽粤江楚等省,只有聚众斗械而无两人决斗之事。既属欧洲盛行,自难保中国之民不无仿效,着为定律,未尝不可。然械斗乃现时所有,似未便不言械斗而专言决斗,仍宜明定械斗专条以警悍俗”[48]。但修正案没有理会签注意见,《钦定大清刑律》仍然空悬决斗罪而无械斗罪的规定。近一百年过去了,草案所规定的决斗罪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相反械斗、打群架倒是屡见不鲜。不规定中国盛行的械斗之罪而专言欧洲盛行的决斗之罪,是草案“食洋不化”的又一例证。而第345条将僧道列为“因其职务得知他人秘密无故而漏洩”的犯罪主体,显然脱胎于西方基督教中基督徒习惯于向神父牧师作“忏悔”而来,两广认为“漏泄他人秘密之事,不必定为僧道等类之人。此系从理想中悬拟而立”。但两广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张(tension)问题就一直是导致中外冲突和国内重大事变的一大根源,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一直让“历史的创造者”煞费苦心。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从追求大变、全变的“百日维新”到稍后的清末新政,解决之道大致不出“中体西用”的范畴,尽管西用的概念(西用、西器、西学)从兵器、军工、经济等物质的层面一直延伸到到官制、法律、宪政等制度层面,中体的概念(中体、儒道、中学)则从“文物制度”一直缩小为纲常之道。这说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思想革命”彻底反传统之前,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上,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试图通过不断重新解释和划定“中体”、“西用”的范围和界限来解决它们之间的紧张。趋势是西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而中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断缩小,最后退守到精神领地以安身立命。因此,就清末修律时的情形而言,一方面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的惩处祸首、清政府决定新政和预备立宪,拒绝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势力已经基本扫荡已尽,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已经进入了涵盖政治制度在内的全面阶段,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已经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思路和方法,所谓“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另一方面“中体西用”仍然是国人面对中西文化交融所采取的基本价值判断和解决方略。视向西方学习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不具有独立的终极价值。纲常之道作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仍然被主流思想所信奉,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质疑儒家的义理文化。既要向西方学习以变革中国,又要维护和不悖于中国的伦理道德。江西巡抚冯汝骙在签注草案第十五章时反对过多采用日本法律的语言和结构,但不反对有选择的采用其内容。“今草案多用日本文法,如本章之提起公诉时效、罹精神病,与夫散见各条之犹豫行刑、假出狱暨笃疾废疾之视能、听能、语能、机能之类,常人似未易明瞭。…揆时度势,欲保法权,端在参量中外之情,酌定轻平之典。但与各国通例,当采其意而勿袭其文。凡官吏审判悉准新章,而律令体裁无改旧贯,复使宽者不流于纵,简者不失之疏。庶于折衷至当行之无弊益。”[49],这段话和沈家本的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在表面上,“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是大家的普遍追求。问题在于,如何折衷才能至当?所以个人认为,评价清末修律和礼法之争的得失,主要不在于评价他们的立法原则和法律精神,主要应该看他们在斟酌中西时的分寸和方法。这一点,两江签注可以给我们以启发。[50]
草案总则第50条涉及宥恕减轻的规定[51],它摒除了《大清律例》关于“老少废疾收赎”的相关规定[52],许多签注批评草案删除了废疾、笃疾宥减的规定而加入了原本不宥减的聋哑者,并且对老人犯罪的宥减过严。两江签注则认为,“是外律专有严于中律处。然中律废疾、笃疾律注均指瞎目折肢而未及聋哑,外律则只言聋哑而不及瞎目折肢。窃谓…废疾收赎本近乎宽,…今本条删去废疾收赎一层,未为不可。似宜仍用笃疾之律或添注聋哑兼病者亦包在笃疾之内,庶较周妥。至七十以上为古稀之年,中国本恤老之意,犯罪时从宽恕。外国则谓老者经验知识较少者为多,不应有犯罪之事,其罚与壮者同。至昏耄不明则精神作用不完全归之颠狂一门云云,所议亦尚近情理,此本条所以规定八十以上。岂但人至八十犯罪究不多见,或七十以上得减本刑一等,八十以上减二等,似亦平允”[53]。签注认为,中律有中律的道理,外律有外律的道理,用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到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扬长避短,从而提出了去废疾、留笃疾并把聋哑归入笃疾以及七十以上得减本刑一等,八十以上减二等的主张。两江的这一签注之所以值得认真考虑和省思,是因为个人感觉这才是真正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之道。草案在立法说明中,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心态,自然就无法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草案总则第十五章规定了包括公诉时效、行刑时效在内的时效制度[54],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很多签注都看不明白,也招致了很多的批评[55]。两江签注第69条对于这样一个崭新的法律名词和制度,使用了《大清律例》中的许多条款来予以说明:虽然名词是新的,但名词里面所蕴含的内容在旧律中是有的。“至于名词之间,即律法期于大同,字义亦颇简赅,自无妨照用,不必更易”。一个完全陌生的制度,由于使用了熟悉的材料来加以解释而变得好懂了。同时签注虽然明确赞成公诉权时效的规定,但也同时认为“各项年限,似可略为加展,以平起诉者之心,请再酌定”。如果联系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你会惊叹于两江签注在斟酌中西方面的到位和准确[56]。
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人们只有在连续的历史中才能获得方向感。骤然的制度变革,会让人们不知所措,从而本能的抵制这种变革。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崇拜浓厚的国度,如何在新旧之间搭起桥梁,如何让人们更容易的接受新生事物,是改革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中国历史上改革者多会用“托古改制”之法,甚至康梁变法时也要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改革家,原因就在于它迎合了国民的心理,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虽然“托古改制”可能会给改革带来某种类似“龙种变成跳蚤”式的不良后果,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度,揆诸国情,仍不失为一种推进改革的好办法。草案虽然在每一条款下也多有沿革的说明,但多是材料的堆砌,没有能够与新条文的解释有机结合,从而无助于人们对新条文的接受。相反草案中对旧制度的不时批评还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说明草案的编纂者们一再强调领事裁判权问题对中国的危害,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而不得不采纳新的制度这一“托洋改制”的改革策略并不成功。在当时的情况下,两种策略应该并用,但前面应以“托古改制”为主起到铺平道路的作用,后面再辅以“托洋改制”的压力。前拉后推,方是近代改革者成功的两大策略。
除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之外,草案的另一个宗旨就是“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从草案立法说明看,所谓“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就是要把那些在西方法律中还没有规定、但在学术界已经得到讨论并出现主流观点的学术思想也规定在中国的刑律草案之中。按照这一宗旨,草案作出了如下规定:
总则第十一条、第四十九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57]。草案“理由”部分认为,确定个人开始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有两个标准,“辨别说”依据一般人形成辨别是非能力的年龄确定,“感化说”依据一般人还可以教育感化的年龄确定。草案认为“感化说”是最先进的,当时西方各国主要采纳“辨别说”已经落伍了,“此说至近年已为陈腐,…以是非善恶之知与不知而定责任年龄,不可谓非各国法制之失当也。…故本案舍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用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58]。近一百年后,草案所舍弃的“辨别说”仍然是中国刑法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原则,就世界范围看,“感化说”也没有成为主流。
分则第三章关于国交之罪。此章共十三条的规定也是各国刑法典所无的内容,但草案认为“近年往来日就便利,列国交际日繁,本章所揭皆损害国家睦谊而影响及全国之利害者,特兹设为一章,是最新之立法例也”[59]。其中对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60],“理由”部分指出,“滥用红十字之记章以为商标,亦足生列国之异议而有害国交之虞者,本案故特为加入,将来各国刑典上必须由之规定也”[61]。宪政编查馆核定此章时认为,“国交之罪,凡对外国君主、大统领有犯,用相互担保主义,与侵犯皇帝之罪从同,此泰西最近学说,各国刑法尚无成例,中国未便独异”[62]。虽然各国法律并没有相应规定,但考虑到当时晚清的特定时期,把有可能引起外交纠纷的行为,如杀伤外国领导人、外交使节等定为犯罪予以处罚,也未尝不可。但那依据的仍然是中国自己的情况,并非此乃什么先进的立法主义。至于将滥用红十字作为商标等行为也定为犯罪,认为它也会有害国交,那就有点“杞人忧天”了。近一百年后,中国刑法典中仍然没有半句关于妨害国家之罪的规定,世界各国刑法典中也不见此内容。
自清末开始的中国近代化,其主要命题就是向西方学习,这是由历史发展的形势所决定的。因此,晚清刑事法律改革,移植西方的刑法制度是必由之路。问题只在于斟酌中国的国情背景,移植的多或少以及是否得当。如果说从这一角度出发,尽管我们认为刑律草案在斟酌中西文化方面有欠适宜,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作为草案的一个立法宗旨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话,那“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作为一个立法宗旨就值得怀疑了。以晚清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教育文化程度方面的巨大差异,移植西方“行之以久”的法律制度已感不甚适应、吃力得很,如果再把那些在西方也还没有形成制度、仅仅限于学术界讨论的学说观点也规定到中国刑法典中,那中国刑法的法律“文本”,岂不是与中国犯罪状况的“实际”差得更远?如果再认为首创了世界最先进的立法主义,相信各国立法会“跟进”,那简直就是“呓语”了。二十世纪初期修订法律馆诸人的心态,与二十世纪中期大跃进时期“赶美超英”的口号一样的幼稚可笑,只不过一个是出于敌对状态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个则是屈服状态下迷失了自己的“西施效颦”。对于这样的立法宗旨,人们有理由予以批判。
注释:
[1] 今从朱勇老师的意见,以《大清刑律》称之。见朱勇:《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页。
[2] [日] 冈田朝太郎:《论改正刑律草案》,留庵译自日本《法学协会杂志》,第29卷第3号,译文载《法政杂志》第一年第二期。
[3] 如宪政编查馆特派员杨度、日人冈田朝太郎、德人赫善心、宪政编查馆参议、资政院议员劳乃宣、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御史胡思敬、署邮传部右丞李稷勋、法部郎中吉同钧等。
[4] 关于晚清法律改革的动因,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与收回领事裁判权有直接关联。而我的看法是:1902年中英商约谈判时,张之洞主导制定了《马凯条约》第十二款关于英国有条件放弃治外法权的承诺,其目的在于推进国内向西方学习的进程;1907年后张之洞又否定了“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说,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沈家本过于“西化”的法律改革模式,以维护“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思路。这一过程表明,领事裁判权问题始终只是晚清主持改革者推进法律变革的手段。事实上,晚清法律改革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新政这一整体政治局势的,它本身并没有自己额外的起因和目的。而礼法之争中,就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系问题的辩论表明,法理派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修律本身并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在礼教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法理派本身又不敢正面否定礼教文化的情况下,只好拿“危机论”(即领事裁判权问题)作为推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手段。这本身表明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是认同和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精神和原则的,他们希望用西方法律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此,清末修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不过是手段,法律的近代化才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的不相协调,是导致晚清刑事法律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对此问题,本论文初稿第一章中原有专节论述,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学术争议,定稿时还是“忍痛割爱”了。如阅者有兴趣,可参看笔者的两篇文章:《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中的危机论——以沈家本眼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为中心》(《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5]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942页。
[6] 《学部奏折》。
[7] 《湖南奏折》。
[8] 《学部奏折》。
[9] 《安徽奏折》。
[10] 《学部奏折》。
[11] 《学部奏折》。
[12] 《安徽奏折》。
[13] 《大清法规大全》,政学社印行,台湾考正出版社1972 年影印本,第1942页。
[14] 《河南签注清单》。
[15] 《两广签注清单》。
[16] 《邮传部签注清单》。
[17] 《修正刑律案语》第二条。
[18] 《广西巡抚奏折》。
[19] 《两广签注清单》。
[20] 《邮传部签注清单》。
[21] 《陆军部签注清单》。
[22] “陆军部签注谓本条国旗国章应以国家代表所揭者为限并须外国请求然后论罪。查各国风俗,对国旗及国章均拘特别之敬意,即系私人所揭之旗章,苟加以侮辱行为,往往起其国民之愤,牵动外交。故本条不加制限…本条乃为预防牵动外交而设,彼此各有取义,无庸强同也”。“两江签注谓本条似应列诸商律,罚金之数亦尚需厘定。查本条之罪,系属有碍国交,其性质与商业行为不同,不得移入商律”。“陆军部签注谓此条为中外刑律不载,又各国刑律纯以属地主义为准,中国法律不能实施于外国之领土。查关于国交之罪名,系属最近发达之理,不能纯以中外成例为言”。“两江签注谓外国开战须不在中国境内者方可布告中立。查局外中立之布告,但须战争之事中国全未加入即可发表,不必论其战争之在内在外也。”——以上相应见《修正刑律案语》第117、118、119、121条。
[23] 《修正刑律案语》第十五条。
[24]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941页。
[25] 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宪政编查馆大臣、和硕庆亲王奕劻等《为核订新刑律告竣敬谨分别缮具清单请旨交议折》,见《钦定大清刑律》卷前奏折。
[26]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见《钦定大清刑律》卷前谕旨。
[27] 《都察院奏折》。
[28] 《江苏巡抚奏折》。
[29] 《德宗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7 年,第577页。
[30]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为刑律分则草案告成缮具清单折》,见《钦定大清律例》卷前奏折。
[31] 《安徽巡抚奏折》。
[32]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编定现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础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52页。
[33] 《山东巡抚奏折》。
[34] 《学部奏折》。
[35] 《直隶总督奏折》。
[36] 《陕西巡抚奏折》
[37] 《湖广总督奏折》。
[38] 《浙江巡抚奏折》。
[39] 《湖南巡抚奏折》。
[40] 其规定的着眼点也非禁止堕胎而是惩处奸夫,见《大清律例》“威逼人致死条”,载田涛、郑秦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440页。
[41] 《山西签注清单》第27章。
[42] 《修正刑律案语》第349条。
[43] 《江西签注清单》第338条。
[44] 初草第328条第一项(修正案第343条)“凡私擅逮捕或监禁人者处三等以下有期徒刑”。
[45] 《修正刑律案语》第349条。
[46] 《修正刑律案语》第350条。
[47] 1997年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48] 《两广签注清单》第306、307条。
[49] 《江西签注清单》第十五章。
[50] 两江签注是被修订法律馆归入赞成草案者之列的(“八月间臣馆先将修辑现行刑律赶缮黄册进呈。维时京外各签注陆续到齐,其中如农工商部、奉天、山东、两江、热河均在赞成之列”——《法部尚书廷杰等为修正刑律草案告成敬缮具清单折》,见《钦定大清律例》卷前奏折。),由于没有原奏,我们无法得知两江方面对草案总体倾向性意见,但根据其签注清单来看,主要以西方法律为标准,对于草案多数条款给予了明确的赞成意见,,即使对于有不同意见的条款,语言风格也比较温和,也是就事论事,没有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来讨论。
[51] 第50条:凡聋哑者及满八十岁之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
[52]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大清律例》(法律版)第106页。
[53] 《两江签注清单》第五十条。
[54] 第69条:凡提起公诉权自犯罪行为既终之日起算,于左列期限不行者则因时效消减:一、应死刑者十五年 二、应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应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 四、应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 五、应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 六、应五等有期徒刑者以下刑者六月。
[55] 《热河都统签注清单》第十五章:“今此章所言时效者,名词新异,语复拗折,虽详译二三千字,愈诠愈晦,令人不易索解,不如暂行删除或另订简明章程以资遵守。”
[56]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57] 第十一条:凡未满十六岁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命以感化教育。第四十九条:凡十六岁以上、二十岁未满之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
[58] 《大清法规大全》第1949页。
[59] 《大清法规大全》第1992页。
[60] 第一百一十一条:凡滥用红十字记号作为商标者处三百元以下罚金。
第6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前 言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内容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根据现代法学理论,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是不允许类推的存在。那么什么是类推呢?类推是“对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适用现行刑事法律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处断。”①一般认为类推构成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因此现代刑法理论基本上把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行和类推的适用对立起来,类推适用问题逐渐成为主张罪刑法定原则的国家刑法研究的禁区。在我国,适用类推也被视为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1997年颁布实施的刑法为了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严肃性,也废止了1979年刑法第79条的规定。虽然各国竞相废止类推的规定,但是法律上的类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对类推问题的否定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类推问题。本文意图通过对我国1979年刑法第79条的规定,对新刑法存在的与原刑法第79条规定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评述,说明把类推问题扩大化的危害,说明对类推问题的简单否定对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影响。
总 论
一、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问题
(一)依据79年刑法条文对原刑法类推问题的分析
原刑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人们所认为的我国原刑法中类推,就是这条规定使人们认为我国原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原刑法为什么要规定这样一种“类推”制度呢?对此,当时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犯罪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其方式方法,要求用一部刑法典把已经发生的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犯罪都包罗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制裁犯罪,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罪刑擅断,为完成这样的任务有条件的保留类推还是必要的。人们还进一步论述了我国刑法中的类推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指出类推制度是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或者例外,我国刑法规定了类推制度就表明我国刑法不主张绝对的罪刑法定。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原刑法中的类推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提出,原刑法第79条所规定的制度只是在形式上和一般类推有些相似而已,在我国原刑法中并没有规定什么类推制度,原刑法中第79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司法实践中类推适用的限制。在这里原刑法从两个方面对类推制度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1、原刑法规定的比照定罪的前提是原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而不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社会危害行为。
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原刑法第79条的规定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分析,而要全面理解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实质内容,我们必须从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说是罪刑法定主义开始。
“所谓罪刑法定主义,就是说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什么刑罚,都要预先由法律加以规定。”②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 自我国79年刑法颁布并实施以来,刑法理论界一致认为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所谓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刑法所特有的并贯穿于整个刑法之中的,人们在认定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如何惩罚犯罪的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作为这样一种原则又怎么能允许有什么例外和补充呢?如有例外,说明它并没有贯穿于整个刑法之中,就不能称其为基本原则;如需补充,则说明其内容尚不完整,一个不完整的原则又怎么能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呢?有人还把罪刑法定原则作了相对与绝对的划分,并把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归之于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那么作为一种相对的允许变通的主义,其内容尚不足以确定,又怎么能称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呢?所谓有例外的、需要补充的以及相对的罪刑法定根本就不是什么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不是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它们无非是为了适应某种理论学说的需要人为创造出来的,它的意义也无非是为司法实践中的罪刑擅断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从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原刑法的体系中,第79条规定的制度服从并表现了罪刑法定原则,为罪刑法定原则服务,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摆正原刑法第79条所规定的制度在原刑法中的地位,并且把它严格限制在罪刑法定原则之内。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我国原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而是一种更为严格更为科学的罪刑法定主义。它不仅和罪刑擅断相对立,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还有自己特殊的含义。原刑法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明确具体的规定了什么是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各个刑种如何适用,各种具体犯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从表面上看,这些规定和一般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没有什么区别,也是要求罪、刑都必须由法律预先明文规定,但是由于第79条规定的出现,原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有了更为实际的意义,也有了更加有效的实现的保障。原刑法的体系对罪刑法定原则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第一、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任何一种行为,即使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就不能把它作为犯罪行为并追究刑事责任。这只是一般理论上的罪刑法定的正面意义,一旦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已经明文规定某种社会危害行为是犯罪行为,即使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或者说规定的还不是十分具体,也必须考虑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的这种明文规定就是多余的,就不应该有这种规定。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但是它同时也隐含法有明文规定必处罚之意义,只是这一意义由于原刑法第79条的规定而进一步明确了,对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已经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予处罚同样有悖于我国原刑法就已经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第二、我国原刑法中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只有在某种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具体量刑幅度都有明文规定的时候才能对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仅有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的明文规定而没有刑法分则的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呢?这就产生了原刑法第79条明文规定在刑法总则中的必要。如果没有原刑法第79条的规定,将产生一对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是要求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是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罪刑法定从何谈起?一部刑法把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一切犯罪都包罗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制裁犯罪,防止放纵罪犯,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防止罪刑擅断,必须在刑事法律中明文规定类似原刑法第79条的制度。
我们说我国原刑法第79条的规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类推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新的具有其完整内容和体系的制度有着自己特殊的规定性。类推适用于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制度则适用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这里有两个明显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原刑法第79条适用的只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而不是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刑事法律是一个外延更大的概念,它包括刑法分则还有刑法总则以及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刑法分则只是刑事法律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对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适用原刑法第79条的规定,只能对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而刑法总则或者有刑罚规定的其他法律、法令已经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适用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制度追究刑事责任。在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也没有明文规定,就是法无明文规定,如果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有了明文规定,仍然是法有明文规定。第二个地方是原刑法第79条所规定的制度适用的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而不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第二犯罪是违反刑法规定的行为,即具有刑法违法性;第三犯罪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根据这三个基本特征,要把某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还必须以其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为条件。在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必须有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的明文规定,否则就没有刑事违法和应受刑罚处罚两个要件。
关于我国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特殊性以及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在我国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制度中的意义,我们还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严密的分析论证。比如刑法总则中第10条是对犯罪概念的规定,对此我们分两个层次作进一步的说明。
1、我国原刑法第10条规定了犯罪的概念,“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有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第13条有类似的规定,只是措词有些改动)我们能不能在司法活动中仅仅根据这一条规定来确定某种行为是犯罪行为还是一般违法行为呢?显然不能,虽然刑法总则第10条十分明确地列举了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提出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但是这种列举只是从几个方面揭示了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含义,用它来代替各种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描述是很不够的。“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这句话中的“法律”一词不应仅指刑法分则的规定,而应当包括全部刑法典和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同理它也不应仅指原刑法第10条本身,不能依原刑法第10条的规定确定某种行为是否犯罪。原刑法第10条只说明那些类的危害社会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没有具体的犯罪构成的描述,也就不可能据此把任何一个具体行为认定为犯罪。社会危害性虽然是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基础,但它并不能代替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如果把该条法律规范中的,对危害社会行为的种类表述作为该种类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依据,就混淆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
2、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我国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制度应该仅适用于刑法总则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已有明文规定而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那么刑法总则第10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在原刑法第79条中处于什么地位呢?能否属于刑法总则已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呢?所谓犯罪的定义或者概念是对犯罪的刑法理论意义上的概括,是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总标准,对定罪与量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具体说明某种具体行为的性质。依据它能够否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不能肯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依据它能够推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不能确定某一行为的犯罪性质。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还需要将犯罪的定义或者说是概念这个犯罪的总标准具体化,而犯罪构成正是这个总标准的具体化。我国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制度是对具体犯罪适用刑罚的制度,它适用的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定罪量刑,不是笼统的犯罪概念意义上的犯罪。也就是说即使你认为根据刑法总则第10条关于犯罪的概念已经可以把某一行为视为“犯罪”,也还是不能把它视为刑事法律已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还必须另有其他具体的法律规范把该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在原刑法的体制下,如我们不能直接以刑法第10条关于犯罪的概念为根据决定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一样,我们也不能直接以该条法律为根据决定适用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制度。
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在这里说明。刑法分则已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和刑法已经明文规定为犯罪的犯罪,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意义不尽相同。因为刑法分则是专门规定罪状和法定刑的,作为刑法分则已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直接适用其定罪量刑;刑法是一个更为广泛意义上词汇,不仅包括刑法分则,还有刑法总则和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对于这些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为犯罪的犯罪,其定罪与量刑还必须结合刑法分则的条款,否则就将影响刑法适用的完整性。对于刑法总则或者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和刑法分则的结合,没有原刑法第79条做中介,其结合也是不完整的,而且极易被人忽视。另外,刑法分则已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和刑法分则已经明文规定为犯罪的犯罪实际上也是两回事。刑法分则已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是罪状和法定刑都已明确的犯罪,刑法分则已经明文规定为犯罪的犯罪实际上是刑法分则仅把它规定为犯罪的犯罪,是刑法分则中仅有罪状方面规定的犯罪,且不说其没有法定刑的明确规定,就是罪状方面的规定也是不完整的,刑法分则仅是把某一行为规定为犯罪,关于其他一些问题则需要借助另外一些刑法条款包括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法令的具体规定。原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原刑法第138条规定:“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对于这一法律规范,就不能看作刑法分则已有明文规定的犯罪,直接引用它去适用刑罚,但却应当把它视为刑法分则已经明文规定为犯罪,去适用该刑法第79条的规定,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
从法律规范的性质上说,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制度是对特殊性质的犯罪适用刑罚的实体性和程序性限制,这种犯罪的特殊性仅在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
2、依照原刑法第79条比照定罪的案件,必须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由于类推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待类推只能加以限制,我们刑法第79条规定的制度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对类推进行有效限制的制度。原刑法第79条除了规定只适用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而不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外,还规定依照原刑法第79条比照定罪量刑的案件必须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核准程序意味着终审判决确定以后并不立即生效,还需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层报过程中,任何上一级人民法院都有权予以否决,这一过程足以防止比照过程中的罪刑擅断。在另一方面,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决生效,这种情况仅相当于最高司法当局对个案的一种有权解释。各级人民法院依据原刑法第79条对案件做出的判决,将推动其上级法院系统直至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核准程序。核准程序将有利于国家最高司法当局了解基层司法活动,从实践中汲取经验,推动司法解释工作及时有效的进行。在英美法系国家不强调实行严格的成文法律,主要通过程序法实现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判例是英美法系国家重要的法律渊源,某一判例的最初出现也是对事前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做出判决而成为判例。判例的产生和依我国原刑法第79条规定做出的判决相比,甚至没有必须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的限制性规定,但是没有人将英美法系称为罪刑擅断的法律,似乎也没有人将英美法系称为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我国不实行判例法,但也不能否定英美法系国家也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立法上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意义,但是依原刑法第79条做出的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生效以后,其他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在办理相同性质的案件时能不进行参照或者比照吗?按照原刑法第79条比照定罪的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以后,称其为判例或者司法解释又有何不可呢?最高人民法院对错误核准的判决可以在下次核准时及时纠正,这是一种动态的监督,提供了及时改正的条件,也就使我国原刑法第79条的适用比判例和司法解释有更为严格的限制,也比它们更为灵活有效。
原刑法第79条和一般的类推最大的区别在于,类推从总体上罪刑擅断的一部分,对类推必须实施严格限制。但是我们在反对类推或者更精确的说是限制类推的时候,也要反对扩大类推概念的外延,因为将对类推的限制都能被认为是类推,那么对判例和司法解释不也可以被认为是类推的另一些表现形式吗?
新刑法所废除的实质上是原刑法规定的对类推进行严格限制的制度,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刑法是一个决定定罪量刑的法律,它的规定性必须严格和具体,彻底的废除类推甚至将对类推进行限制也作为类推废除,刑法分则就只能是孤立的僵硬的罪状和法定刑的堆砌。即使承认立法类推仅否定司法类推,但是面对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固定的有限的预先规定的法律条文又怎么应付的了?比如我国现行刑法中众多诸如“其他方法”、“其他手段”、“情节严重”的词语,这些词语出现在刑法规范中,或是作为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或是作为重罪与轻罪的区分尺度,难道都要等有了具体司法解释时都能适用?且不说司法解释也有类推的嫌疑,对这些无法计数的情况,司法解释根本无法应付。
(二)依据法学理论及实践对1979年刑法类推问题的分析
我们从原刑法第79条规定与整个刑法体系结构的关系出发,论述了原刑法第79条的规定在法律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明确它和类推的不同性质,我们有必要从法学家论述的在原刑法中,所谓类推制度的必要性入手说明我国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原刑法颁布实施以后,为了解决原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和原刑法第79条之间的所谓矛盾,法学家们从理论上提出了新中国刑法保存类推的理由。诚然,在社会上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犯罪,形形色色,多不胜数并且不断的发生新的类型的犯罪,不可能以一部刑法典包罗无遗,但是以此为理由并不足以说明类推制度在原刑法中的必要性,也不应成为我国原刑法在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以后可以规定类推制度的根据。
第7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一)
“罪刑法定主义”,也叫“罪刑法定”原则,就是指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得处罚”。它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首先提出来的,最早见之于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权宣言》。一八一年《法国刑法典》第四条则把它具体规定为:“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法律未规定之刑罚处之”。
这项原则的确立,目的在反对封建裁判的武断和专横,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但是,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它就成为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一个“民主”招牌和“法制”幌子。
旧中国伪《中华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在一九二八年“修改理由”中又说:“本条为刑法之根本主义,不许比附援引,即学者所谓罪刑法定主义。凡行为受法律科处者为罪,否则,不为罪是也”。但是实际上国民党伪政府不仅没有按照它的规定去做,反而大搞法外制裁,滥施刑罚。他们在伪刑法最初公布的一九二八年就颁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宣布共产党员的“宣传行为应以反革命治罪条例办理”,但仍佯称其镇压革命“依法”。到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制定了所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总方针,秘密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就没有通过什么立法手续,即付诸实行了。随后,他们又颁行了《修正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国家总动员法》、《妨害国家总动员惩治暂行条例》、《惩治盗匪条例》、《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以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多如牛毛的反动法令。这些仍旧不能满足其镇压革命,打击人民的需要。于是蒋介石就索性亲自训示其特务、打手,对共产党员“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疯狂地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把他们刑法中标榜的“罪刑法定主义”抛到九霄云外。这固然是其反动统治的本性所决定的,但也说明反动统治阶级所认为的“罪和刑”,是无法事先规定得完全无遗的。
再如清末的沈家本等,他们最早主张抄袭外国“罪刑法定”、废除中国“比附”(即类推)传统制度,但在其《奏进呈刑律草案折》中却写道:“兹拟删除此律(即指比附),于各刑酌定上下之限,凭审判官临时审定,并别设酌量减轻、宥恕减轻,以补其缺。虽无比附之条,至援引之时,亦不致为定例所缚束”。这也清楚地说明《清新刑律》尽管明文废除了“比附”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主义”,但实际上仍准“临时审定”,“援引”,不要“为定例所缚束”。沈家本等回避不了在删除“比附”之后所面临的严酷事实:“人情万变,断非科条数百所能赅载者”,“如一事一例,恐非立法家逆臆能尽之也”。于是他们又提出了“酌定”,“补缺”,以收“法律之用简可驭繁”的改良办法。(以上均见其《奏折》)但他们为什么又要确立“凡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见《清新刑律》第十条)的“罪刑法定”原则呢?据说是为了“立宪”,怕实行“比附”有涉“司法而兼立法”的嫌疑。谁都知道,清朝本系帝制,“朕即国家”,皇帝握有立法、司法和行政一切大权。司法和立法又怎么能分得开呢!清末刑法制度上的这个改变,同样也只是为了标榜民主,掩人耳目而已。
中国剥削阶级刑法如此,外国资产阶级刑法也不例外,就以首倡“罪刑法定主义”的法国来说,也是名为“法定”,实有“类推”。比如法国刑法典第二七八条规定:“没有固定住址和职业的人,乞丐和流浪者,如果身边被发现有一百法郎以上的物品,而不能说明其来源时,则应受惩罚”。这种法定的“事实类推”,实际上否定了它的“罪刑法定”。同时也暴露了“罪刑法定主义”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严重问题,结果导致立法上以“罪刑法定主义”作幌子,实际上以“事实类推”搞武断专横。美国一九三九年颁行的《国防通则》第四条也是这种“事实类推”的另一个实例。即“被告人和另一个人来往,有合理的根据想到对方有承担援助敌人的义务时,即应对被告加以惩罚,只有他一定证明并没有威胁到国家安全时,才得免受惩罚”。这何止是“推定”,已经是“想定”了。因此,我们在看待资产阶级的法制时,不能只看他们的动听口号,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们的具体行动和实际做法。决不可被他们虚伪民主蒙住我们的眼睛,好象“罪刑法定主义”一定就比“法律类推”要民主一些,其实并非如此。
与此相反,有些国家能够面对犯罪现象的复杂现实,立足于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就不采取“罪刑法定主义”。比如,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一九二二年《苏俄刑法典》第十条就明确规定了“个别种类犯罪行为,如果本法典没有明文规定的,它的刑罚或者社会保卫方法,可以比照在犯罪的重要性和犯罪的种类上同刑法典相类似的条文,并遵照本法典总则的规定来决定”的类推原则。以后,在一九二四年《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第三条和一九二六年《苏俄刑法典》第十六条,又一再重申和确认。
为什么“罪刑法定主义”实际上行不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不能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客观需要。这是由于再详备的法典,也不可能把极为复杂的社会犯罪现象概括无遗;任何立法者都不能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犯罪,制定出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全能法典。就拿我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一部刑法《宋刑统》来讲,仅其《编敕》即多达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条,仍然还有“有司引例以决”的类推制度。且法越定越多,又会造成“法密则国无全民”的恶果。我国刑法规定了有控制的“类推”原则,而没有采用“罪刑法定主义”,道理也就在这里。如果硬要把我国刑法所屏弃的“罪刑法定”说成是应当遵守的原则,则不仅是强加于法,而且对于同犯罪作斗争也是十分不利的。彭真同志在关于刑法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对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严格限制了类推的应用,规定类推的使用应一律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问题很清楚,对“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如果采用“罪刑法定主义”,那就只好不予处理,任其逍遥法外了。但是从我国刑法和上述说明中,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有些犯罪,如“军职罪”和医疗事故等,还没有规定到刑法里,这些犯罪是客观存在的,或者是可能发生的,只是由于经验不成熟,或者还没有看准,而未加规定,但是只要它一旦发生,并造成严重后果者,就不能不采用有控制的“法律类推”原则,给以刑当其罪的严肃处理。否则,就有损于我国刑法的“极大的权威”。
第8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关键词]人情;循吏;《大清律例》;关系
一、人情、循吏与《大清律例》简析
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追求。在我国古代,公平正义蕴含在天理、国法、人情之中,但彼此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公正蕴含于人情之中。
传统人情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其内涵必然与儒家经义相符。儒家文化以仁和礼为核心,礼又忠(尊尊君为首)和孝(亲亲父为首)内容,受此影响,传统人情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人之情感。同时,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两千余年间,儒家经义逐步融入国人的生活中,成为日常的风俗习惯和道德准则,在此意义上,传统人情则是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人情世故。
在我国古代,循吏主要记载于“二十六史”的“循吏传”。通过研究历代正史“循吏传”,循吏具有依法行事、履行职责、严于律己、清廉、为政宽平、政绩卓著、为百姓所爱戴等品质。《清史稿・循吏传》序文记:“明史所载,以官至监司为限,今从之”,在清代,监司指府州县的长官;《清史稿・循吏传》共记载循吏117人,其中,102人担任过知县,51人担任过知府,55人担任过知州、同知或通判,依据清代的官吏等级,清代循吏多为低级别地方官;可知,清代循吏是依法行事、履行职责、严于律己、清廉、为政宽平、政绩卓著、为百姓所爱戴的低级别地方官。
《大清律例》是我国的最后一部封建法典,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大清律例》以《大明律》为蓝本,其各篇以六部命名,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其下包涵职制、公式等三十门,共四百三十六条;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的增减修订,又称“五朝会典”,至《大清现行刑律》颁行方被废止。
二、人情与《大清律例》
在我国古代,缘情制礼,因礼制律,人情与法律的关系便是礼与法的关系。人情与法律,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存有冲突。
在我国古代,人情与法律的和谐,即“合情而又合法”,表现为礼与法的融合。至清代,礼法高度融合,人情溶于法律,人情即法。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使得司法实践中,不免“合情不合法”或者“合法不合情”。体现在《大清律例》中,人情与法律的和谐指对同一法律现象无相异的规定,以不孝罪、留养制度、亲属相犯和恤刑为代表;人情与法律的冲突指对同一法律现象有相异甚至矛盾的规定,以复仇和赦免为代表。
《孝经》记载“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1)”,在我国古代,不孝是最大的犯罪,人情与法律的和谐首先表现为不孝为罪。
《大清律例・名例・十恶》记载:“七曰不孝。谓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奉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称祖父母父母死。(2)”可知,清代不孝罪体现在:日常不顺父祖;冒犯(触犯父祖名讳或状告、咒骂甚于杀伤)父祖;父祖被囚或丧葬期间有违礼法。
日常之不孝,体现在:《大清律例・户律・户役》“别籍异财”、“卑幼私擅用财”2条;《大清律例・礼律・仪制》“僧道拜父母”、“弃亲之任”2条;《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子孙违反教令”条。
冒犯父祖,体现在:《大清律例・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谋杀故夫父母”、“尊长为人所杀私和”3条;《大清律例・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妻妾殴故夫父母”、“父祖被殴”3条;《大清律例・刑律・骂詈》“骂祖父母父母”条;《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干名犯义”条。
父祖被囚或丧葬期间之不孝,体现在:《大清律例・礼律・仪制》“匿父母夫丧”、“弃亲之任”2条。
若说不孝是对孝的违犯,为亲复仇则是对孝的一种极致表现,是人情与法律冲突的典型。在我国古代,因孝悌而复仇是一种高尚伦理。
复仇,体现于《大清律・刑律・斗殴》“父祖被殴”条:“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不告官)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杀死者,勿论(少迟,即以擅杀论)・・・・・・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本犯拟抵后,或遇赦、遇赦免死,而子孙报仇,将本犯擅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3)”此条与《大清律例・刑律・人命》“谋杀人”条的规定有所冲突。此外,源自晋朝的“移乡避仇”,《大清律例》则不在提及。
《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存留养亲”条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笃废),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养)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军犯准此)。(4)”存留养亲是为体现统治者对孤寡老弱的矜恤,是人情与法律和谐的又一体现。
除却不孝为罪、存留养亲,人情与法律的和谐还体现在亲属相犯方面。所谓亲属相犯,为《大清律例・诸图・丧服图》确定的五服亲属,包涵亲属相告、亲属相盗、亲属相殴、亲属和亲属相杀。
亲属相告,体现在:《大清律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条。
亲属想盗,体现在:《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亲属相盗”条。
亲属相殴,体现在:《大清律例・刑律・斗殴》“妻妾殴夫”、“同姓亲属相殴”、“殴大功以下尊长”、“殴期亲尊长”、“妻妾与夫亲属相殴”、“殴妻前夫之子”6条。
亲属,体现在:《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娶亲属妻妾”条;《大清律例・刑律・犯奸》“亲属”条。
亲属相杀,体现在:《大清律例・刑律・人命》“夫殴死有罪妻妾”、“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2条。
此外,亲属相犯还体现于《大清律例・刑律・骂詈》“骂尊长”、“妻妾骂夫期亲尊长”2条。
在我国古代,严格遵循法律,依法断案可能招致舆论的非议,相反,曲法申情之举则可能被视为德政。恤刑和赦免便是统治者为体现其仁慈之心而对犯罪者的法外施恩,其中,恤性是人情与法律和谐的体现,赦免是人情与法律冲突的体现。
恤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老幼妇残以及贵族官僚的矜恤,体现于《大清律例・名例律》“应议者犯罪”、“应议者之父祖有犯”、“犯罪得累减”、“老小废疾收赎”4条和《大清律例・刑律・断狱》“功臣应禁亲人入视”、“老幼不拷讯”2条;二是刑讯过程中的慎刑,体现于《大清律例・刑律・断狱》“凌虐罪囚”、“决罚不如法”2条。
在我国古代,皇帝至高无上,其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赦免是皇帝的专有权力,是人情与法律冲突的典型。赦免,体现在:《大清律例・名例律》“常赦所不原”、“流犯在道会赦”;《大清律例・刑律・断狱》“赦前断罪不当”、“闻有恩赦而故犯”。
三、人情与循吏
据词义分析,循吏的重点在“循”不在“吏”,“循”有顺着、遵守(6)之义,故循吏的重点在于遵循何种规则。颜师古在《汉书注》注道:“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6)”,可知,循吏除遵循法律,还因循人情。
受儒家文化影响,我国的传统人情,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存有冲突。人情与法律相融合,人情即法,遵守法律便是因循人情;人情与法律相冲突,循吏大都以情变法,曲法申情,或直接依儒家经义断案。由此而言,循吏的一大特色便是因循人情。
在“二十六史”记载中,循吏大都政绩卓著,循吏的因循人情便体现于其政绩中。在清代,官吏的政绩主要体现在重农、教化和理讼三方面,循吏的因循人情多体现于教化和理讼,而理讼往往也起着教化的作用,故循吏多缘情理讼。
四、《大清律例》与循吏
根据上文的论述可知,人情与《大清律例》相融,有和谐也有冲突,而循吏多缘情理讼。故,以人情为核心,可以将《大清律例》与循吏相链接。
人情与法律和谐时,人情即法,循吏理讼时因循人情即是遵守《大清律例》;人情与法律相冲突时,循吏理讼多曲法申情,抑或依据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或儒家经义断案。
参考文献:
[1]孔子撰,陈书凯译.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
[2]田涛,郑秦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3]李伟民主编.法学辞源[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4][东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注释:
(1)孔子撰,陈书凯译.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第116页.
(2)田涛,郑秦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3)田涛,郑秦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68页
(4)田涛,郑秦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99页
(5)李伟民主编.法学辞源[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3178页.
(6)[东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23页.
第9篇:刑法法律条例范文
内容提要: 日本刑事判例制度不仅对刑事司法发挥重大作用而且还影响立法,这种判例制度对于解决立法滞后与现实活发之间的矛盾发挥着重大作用,相应地,司法中以判例实质地创制法规范等做法也可能一定程度上消解罪刑法定原则。日本的刑事判例制度给我国目前的有权司法解释模式提供了启示,如重视法律的权威性等。应当借鉴该判例制度构建我国的“一元个体判决式”的刑法解释模式。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中国有权刑法解释模式是二元一级抽象式的解释模式,笔者认为该解释模式具有相当的不合理性⑴,应予改变。而如何改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对此,借鉴他国的经验,不失为一条捷径。中国与日本同属亚洲国家,有很深的文化方面的联系,因此了解日本的有权刑法解释模式,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日本,判例,尤其是最高裁判所(即最高法院)的判例,对司法具有重大的作用,无论是刑事司法还是民事司法都是如此。那么,这种判例对司法的作用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刑事方面,它是具有法规范的性质,还是仅具有参考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与中国现在的状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对此问题的研究,当有益于我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选择。
一、日本刑事判例的性质
(一)刑事判例对司法的作用
在日本,存在着大量的判例,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对判例的研究。一方面,学校教学中,老师在研究判例,学生也在研究判例。笔者参加过日本一个大学关于刑事法的研究会,其内容就是研究刑事判例。通过对判例之事件内容、判决及其理由的分析,提出应该研究的课题,并制定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研究判例,通过判例的研究,为自己的裁判提供参考。这种判例研究的广泛性在日本是一个应被注目的事实(尤其对中国人来说)。也就是说,学界在研究判例,其目的是通过判例把握司法机关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司法机关也在研究判例,以确定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判决方式,或者援用案例,或者做出不同的判例,以表明司法者对法条的理解。
日本的判例作用如何?在表现形式上,日本有判例集,有判例六法⑵。但在判例的性质上,他们不承认日本有刑事判例法,即判例不是法律,如对相同问题所做出的判例就可能是不同的⑶,它对以后的裁判只有参考作用,而不是必须遵循的法规范。也正是因为如此,对同一的现象,不同的裁判所之判例会有不同的结论,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如日本在共谋共同正犯问题上,就既存在着肯定说,即将共谋者作为共同意思主体,依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将共谋者全部作为共同正犯;也存在着否定说,即认为共谋者没有实行行为,不能成为正犯,共同意思主体说是团体责任而与现代个人责任原则相背离,因而共谋者不能成为共同正犯⑷的争论和不同的判例。
(二)判例与解释的关系
从前面所描述的日本判例的作用来看,日本的判例在性质上应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即司法者通过具体的判例,表明其对具体法律条文之内容的诠释。这种解释性在判例之判决理由部分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⑸。从这个意义上说,判例是法律解释的表现之一。如果说,解释学是法律解释的理论表现的话,判例就是法律解释的司法表现。解释学以理论的方式,描述立法的应有内容,判例就是以判决的方式,确定立法的应有内容;解释学以理论的方式影响司法,若司法采用某种理论主张,就会使该主张通过判例得以在司法中实现;反之,判例也以其内容反映着司法者的理论主张,并通过判例研究影响着解释学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判例与解释关系密切,判例与解释学具有互动的关系。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判例就是法律解释,只是解释的方式更加独特。也正因为判例是解释而不是法律,所以判例作为具体的司法判决,对当案有法律效力,除此之外,它不再具有对任何事件的法律效力;它可以被他人参考却不能引用作为有效判决的根据,判例不是立法。
(三)判例之解释与立法的界限
如果前面的观点被认可,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判例是对法条的解释,它只对当案有效,对其他案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判例,尤其是日本最高司法机关(最高裁判所)的判例对司法的影响不可小视,一个判决,完全可能成为被诸多司法者实际上援用的裁判根据。例如,在有了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的裁判之后,现在的日本司法机关就将多数过去作为从犯或教唆犯处理的参与共谋的共犯者都作为正犯处理⑹,可见其判例作用之大,虽然这只是参考,但其作用之大,对司法影响之深远不容低估。
由此也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判例之对法律的解释影响如此之大,那么判例之解释与立法关系如何?如何划定判例与立法的界限?该问题应该说既重大又复杂。说其重大,它涉及判例是否法律的问题,说其复杂,是由于判例之对立法的解释既是有效的,又是解释,解释不是法律自身,而是对法律的理解,这种理解既可能符合立法意图也可能违背立法意图,但它又是有效的,不管它与立法意图之间的关系如何,只要判决生效,该判例对立法的解释就会发生法律效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判例之对法律的解释与解释学之对法律的解释又是不同的。
一般说来,一个判例只是一个法官或几个法官在案件裁判过程中对案件所涉及的某具体法律条文的解释,无论这种解释如何进行,其界限都应该是法律规定本身,即法律解释应以法律之语言表述中所具有的内容为限,如果法条的语言中没有的东西,无论以何种理由将其解释出来,其解释都是违法的。若以判例的形式做出,该判例本身是否合法就是值得研究的。但由于日本是法官解释法律的模式,即法官通过判决表现出对法律的理解,虽然这样的解释只对当案有效,不具有强制其他法官遵行的效力,但对于当案来说,无论这种解释是否为他人所认可,都是有法律效力的,除非通过启动上诉的诉讼程序来提出自己的诉求,而无论这种要求是何种观点,也要通过上诉审的法官对法律的理解来形成判决,而且只要判决生效,作出该判决的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就是有权的也就是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当然,法条本身的内容含量,直接受制于法条的语言表述,而语言表述的意思又是可以有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同样的言词概念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例如,财物概念的具体内容,在电发明之前,其内容中不包含着电力,但电力被发明之后,将其包括在财物中并未超出财物之概念的范围,如日本依据财物在刑法中的意义,将电力解释为财物,成为盗窃罪的对象⑺,就是法条言词的开放性导致的结果,这种开放性使其具有立法当时不可能设想到的对后世的适应性,这样依判例的法条解释是合法的。但如果将法条言词中未必包含的内容解释出来,并制作为判例,其合法性就存在问题。例如,日本刑法对共犯的规定共有6个条文,分别对共同正犯,从犯(即帮助犯)、教唆犯等进行了规定。而正犯是实行犯(一般的概念),非实行犯不能作为正犯在一般观念下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在于,一般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不是法定的概念定义,司法中就有依据解释改变其内容的可能性。而共犯中的共谋共同正犯问题就是其适例。如果将正犯理解为实行犯,共谋者是否实行犯应该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即“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者,全部是正犯”的立法规定,表明实行犯罪的主体是二人以上,他们应该至少分担了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否则不能成为正犯,因此,若只有其中的一人或部分人参与实行,而未参与实行的共谋者,按立法的语言表述,无论如何无法将其作为正犯⑻。而日本在判例上却具有将共谋者作为正犯的明显倾向⑼。虽然有学者会认为这种判例已经不是刑法解释的问题,它超出了解释的权限,实际是在创设新的规范,但如果其在判旨中所作的解释是能够被他人所接受的,虽然这样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法条的语义,但是否就意味着是立法,是司法者对立法权的侵入,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司法解释的界限并不是一个可以直观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二、立法滞后与现实立法之矛盾与解决方式
从以上对日本判例之应有性质及实际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某些判例所具有的实质上的立法性质,是与某些实际问题解决之需要分不开的。日本之所以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是为了处理某些实际上应该处罚的在犯罪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⑽,如策划、领导者,他们不参与具体行为的实施,但他们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实行者还大,仅作为帮助犯(不具有教唆性时)处理,显然放纵了犯罪。而这类问题显然又是立法时立法者所未预料到的。立法时,立法者是将已经预料到的事项,依据一定的立法原则规定在刑法中,但至少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立法不可能完全满足司法实务的要求:其一,社会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必然要带来对司法的新的要求,而在变化之前,立法者无法预见到其后的情况,于是形成立法与现实需要的不相适应。其二,立法疏漏。立法者无论是通过何种模式选择出来的,他们也还是人,而且即使选择的模式是能够想到的最合理的,都未必保证所选举出来的人是无例外地最优秀的人,因此也就具有人的特性,包括人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是人的弱点,既然人不是神,要求立法者将所有的社会需求无例外且准确地反映在法条中是不可能的,也就是立法疏漏不可避免,要求一部法律可以概括所有的社会生活状况,没有遗漏,实在是强人所难,因为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对人总不能提出象神一样的要求。其三,语言限制。意义的表达通过语言,但词不达意绝非限于语言低能者,在某些场合,语言难于准确表达思想是不可避免的,尤其象立法这样的规范性语言,其表达的意思与立法思想不完全相同也属不得已。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导致立法不能完全符合现实要求,也就是立法滞后。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出现立法与现实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现实。前面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的问题,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立法滞后所导致的问题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既然立法滞后不可避免,也就存在一个解决方式的问题,因为不可能对这样的问题视而不见。作为具体的解决方式,应该有很多可能性,比如:其一,制定抽象度极高的刑法,使其有任意解释的可能性;其二,随时修正立法,使立法符合现实的要求;其三,承认判例法,以判例来补充立法等等。这样的方式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解决现实问题优先,让法律适应现实。还可以有其他方法,如其四,容忍某些应予处罚的行为存在于处罚范围之外,这是法律原则的坚持优先的方法。两类解决方法都必然伴随着相应的弊端。其一的方法使立法失去规范性,因为有任意解释余地的法律实际上没有订立任何确定的规范,实质也就不具有实在的法律的性质,因为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确定性应该是其内在要求,任意解释的可能已经使法失去了确定性,它不是法律,而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立法者与司法者的任性。其二的方法会使立法失去稳定性,并由此导致法之权威性的丧失,随时变动的法律不会让人产生信仰是不言而喻的。其三的方法涉及到立法权的行使问题。如果立法权与司法权合而为一,可否保持立法者对司法者的限制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⑾因此,前一类方法,在民主国家存在无法达到保障人权,无法实现立法目的的障害。其四的方法,放任某种行为或某些行为存在于法律调整范围之外,以确保法律的权威。但是如果这种或这类行为对社会危害很大,不予处理显然不符合立法目的。设定刑法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把危害社会达到一定程度、社会无法容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处以刑罚,以使社会及其构成成员的公民得到有效的保护。在一个国家中,公民有享受和平、安宁、有序的生活环境的权利,除非是他们选择了放弃这样的权利,否则他们的这种权利应由国家来实现,相反,他们没有忍受侵害、让侵害者肆意的义务,否则就是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失职。可见,无条件的坚持后者也不可取。
这是否说明已经使问题陷入两难境地了呢?回答是肯定的,两者必取其一,但取何者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难题。当然,也存在折衷的方式,即两方面均不能绝对化。对于前者,法律必然有一定抽象性,有解释的余地,但不能任意;立法要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但法律不可能食古不化,不是金科玉律,有改正的余地;不能承认判例法,但判例的解释对法律的作用不容低估。也就是尽可能的使危害社会的严重行为有规制的方式。对于后者,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别公正而维持法的稳定性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两者各走极端,结果只能更坏。因此,全部问题是要把握其量的限度。而其量的限制必须以现代社会之主体——公民——之利益的最大保护(包括犯罪者、被害人、社会公众等)作为衡量标准。在此前提下,必然存在着选择。那么,由谁来选择?应该是社会的主体——公民。当公民选择了某种方式后,对其所带来的对自己的不利后果,自然应该承担,即忍受。当然,公民的选择方式是前提,这涉及到社会体制问题;公民是否真正的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是否选定了真正表达意愿的形式;是否有监督这种形式不发生质变的有效方法等等,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但有一点值得说明,这就是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社会的方式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以及人治或法治的具体形式。
三、从日本立法与判例现状引发的对中国立法与判例的发展方向的思考
(一)中国的立法与判例的现状
首先看中国的刑事立法。新中国真正意义的刑事立法应该说是以1979年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的。截至2006年上半年,在20余年的时间内,制定出了两部刑法典和20余个单行刑事法规,并对1997年刑法以直接修订的方式进行补充,已经通过了六个刑法修正案。可以说,中国的刑法是在不断的修订中被适用的。从刑法的立法现状,可以概括出中国刑事立法的几个特点:其一,立法多变。在21年间制定了两部刑法典,两部法典制定时间的间隔只有17年半。其两部法典之间的立法活动也未停止,从1979年刑法制定后的不满3年就开始以特别刑法的方法对其进行修定,共有24个各类决定和补充规定作为对刑法典的修正和补充。1997年刑法制定之后,只过了一年,就继续进行修正,制定新的特别刑法或修改刑法条文。其立法进程表现了中国刑事法立法多变的状态。其二,解决现实问题优先的立法倾向。立法之所以多变,是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之需要分不开的。1979年以来的20余年,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导致1979年的刑法迅速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修改法律并不是唯一的途径。例如,关于两个严打决定是否完全合适,笔者认为值得研究⑿,有些问题通过刑法典是否完全不能解决?也未必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在24个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原刑法典所规定之犯罪的刑罚调整,即加重处罚力度,而这种程度的加重是否完全必要也不无值得研究之处。不可否认,有些原刑法中未规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值得用刑罚处罚的行为,有犯罪化的必要是事实,但仍然存在一个选择问题,即解决现实问题优先还是保持法的稳定优先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无条件地选择了前者而完全将后者牺牲掉了。其三,立法的情绪化倾向。在各种立法中,反映出立法者并未对所立之法进行非常缜密的思考和论证,往往就事论事,也少考虑各种法律和条文之间的协调。例如,关于惩治税收犯罪补充规定中对发票性犯罪的立法规定,关于严打决定中对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立法规定,关于1997年刑法中许多条文间法定刑不平衡的立法规定⒀等,其重要原因,就是急于解决现实问题,而少有冷静、理智的思考,导致立法的情绪化。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几个特点,导致1997年刑法虽然是经过全面修订,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再看中国的判例。只要有裁判,就会有判例,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判例是很多的。同时,最高法院、各省级高等法院等,也在有意地编制判例汇编,如最高法院有判例集,精选各种有代表性的判例予以。从所公布的各种判例来看,中国的刑事判例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判例少有判决理由。在中国的刑事判例中,其内容主要包括:案由、事实、适用法条、判决。而在判决中,为什么该事实符合所适用的法条的规定,却没有充分的理由阐述。当然,这不是说裁判者没有选择法律适用的理由,即为何将该事实认定为某罪的理由是存在的,但并未将其在判决中明示或者充分地表达出来。其二,判例不是明显的解释法律的形式。不能否认,将具体的事例依具体的法条做出裁判,这种裁判本身就表明了司法者对法条解释的倾向,即表明了解释的结论,但由于少有判决理由叙述,因此还不能说是一种解释,因没有解释的过程。当然,司法者有裁判权,即有依照法律裁判案件的权力,但如果裁判不附理由,如何将具体的事例判定为符合抽象的法律规定,就显得有些武断。因此,很难说中国的判例是一种司法解释的形式。其三,司法者对判例的援用主要是模仿。上级法院的判例,尤其是最高法院选编的判例,对下级司法机关的裁判是有影响的,但由于判例少有判决理由,难于作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因此下级法院对其的援用很难援用其判旨,而是模仿其判决结论,即对同类案件,参照最高法院的判决总是保险的。而这种援用的效果,不是增强了由法官解释法律的意识,而是引导其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直接将最高法院的判决结论作为现成的模式进行运用,这种方式有使法律解释程式化,而失去其应有的追求法律解释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适应社会生活复杂状况的价值之嫌。
(二)中国刑事立法与判例对罪刑法定关系的评价
1997年刑法的一个重大成就,是罪刑法定的立法化,该立法表明中国承认并且坚持罪刑法定主义。因此,无论是刑法规定还是刑法解释,均应遵循罪刑法定的要求就是必须的。关于罪刑法定的内容,其谚语式的表述,源于费尔巴哈用拉丁文的表述,即“法无明文不为罪,不处罚”⒁。如果只从形式上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判例都是符合罪刑法定要求的,或者说,中国的立法状况正是为了达到这一要求而为,中国的刑事判例有事由,有法条,也符合形式上的罪刑法定主义的规定。但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形式,或者说主要的不是形式。如果赞同罪刑法定原则是以民主主义、保障人权为思想基础⒂的原则的话(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就会由此推导出对刑事立法的一系列要求,包括法律的相对稳定、罪刑均衡、规定明确、实质合理等。如果按此要求来评价中国的刑事立法,其结论应该是其立法并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20年的立法历程表明法的不稳定,其制定法的状态在明确性与罪刑均衡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即立法与罪刑法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从司法方面来看,如果判例不能明确判决理由,使判决不免有武断之感,而这样的判决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的要求也就不无值得研究之处。因为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立法原则,也是司法原则,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所及覆盖立法与司法,若在司法中未能反映或未能全面反映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很难说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得到了实现。总之,就中国现在的立法与司法状况来看,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的评价未必是全面肯定的。
(三)日本的立法与判例所给予的启示
从前面所简单介绍的日本的立法与判例来看,不能说他们是完全值得赞同的。例如,立法近百年不变,将法律看得如同神圣一般,这在树立法律权威方面虽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在立法的许多方面已经不完全适应现实状况时,仍固守旧法不作变动,法律的权威固然树立了,但现实问题的难于解决,立法滞后严重的状态如何解决似乎也难说毫无问题。同时,相应存在的在司法中以判例实质地创制法规范等做法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是不无值得研究之处的。
但通过前面对日本的判例状态的分析,对照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的状况,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一,重视法律的权威性。法是规则,而规则需要遵守,遵守的前提是对规则的认同。对普通公民来说,这种认同一方面来自于对法律的理解和对其合理性的赞同,另一方面来自于法的权威性,因为没有权威的法律即使被认为是正确的,也难于得到普遍遵守。而权威性是要求其有相对稳定性的,如果法律朝令夕改,它只能成为规避的对象而不会成为信仰的信条,不会产生权威。因此,法律的权威性来源于法律的稳定性,如果法律多变,还未等普通公民了解,法律已经变动,法律何来权威,于是,就变成权威在立法者而不在法律本身,而立法者的权威是人治的表现而非法治的表现。法律的权威很重要一点是来自法的稳定是没有疑问的。日本做到了将刑法神圣化的程度,修订案制定了近30年也未能通过立法⒃,就是法律权威神圣化的结果。其二,判例成为司法解释的重要手段。司法者对法律如何理解,对法律的适用关系重大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正是司法者在适用法律而不是其他人。而判例作为司法者对法律解释也没有疑问。法律的抽象性和社会上发生事件的复杂性要求对法律的解释,司法人员对法律的解释虽然也可以通过司法者的学术文章或其他形式反映出来,但最基本的形式还是通过判例,判例正是司法者对具体法律条文之理解的最集中表现。而这种解释虽然对裁判者来说是有一系列根据,但对于他人来说就只能通过判决来了解,因此判决理由应是判例的必不可少甚至是核心的内容。对判例的研究应该主要是通过判决理由来了解判决的根据。因此,使判例成为司法者对法律解释的重要形式应该说意义重大。它可以成为学界与实务界交流与互相影响的具体形式,也可以成为民众对法律理解的根据之一,同时可以形成法官的权威。其三,有助于司法者素质的提高。在判决中叙述事由、事实和引用法律是比较容易的,但提出判决理由就涉及对法律的理解,而这种在判决理由中提出的对法律的解释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就更加明显和重要。这种要求,就促使司法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与能力,以适应裁判案件中说明判决理由,即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要求,而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在司法中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一环。最后,为法律的修订准备素材,通过其对法条的理解,以判例为媒介,也可以通过司法与学界的交流,使法律的内涵得到充分的体现,更明确地框定其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也就比较容易发现法律的真实漏洞,为法律的修订准备素材。法律需要稳定,但不是千古不变。而变动应该特别谨慎也是没有疑问的。在判例的研究表明在司法中确实无法解决某类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提出是否修订法律的问题,而法律的是否修订又存在着多种价值目标的选择。这样,法律的相对稳定才可以达到,法治的目标才有可能在刑事法之领域得到实现。
转贴于 四、中国有权刑法解释模式重构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国现在的有权刑法司法解释模式,是存在问题的,不适应法治国家对法律正常运行的需要,应予改变。而改变的方向,笔者认为,应该设立“一元个体判例式”刑法司法解释的模式;司法解释就是法官就个案作出的解释而只对当案有效;对个案解释的借鉴形成的司法常例可以达成全国范围内的司法平衡。
(一)解释模式:一元个体判决式解释模式
如果刑法的解释是就具体案件的裁判需要而对抽象的法律进行解释,其解释的模式就只能是一元、个体、判例式的司法解释模式而不能采用其他的模式。
1.一元:只有法院具有解释刑法的权力。前面已经说明,只有法院是具有裁判权的司法机关,刑法的解释是对刑法具体规范的应用,是让具体的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律规范,这样的权力只有法院拥有才是正常的。既然立法者无法制订出一部不需要解释的刑法典,刑法就需要解释,而解释的目的就是要使具体的案件情况符合刑法条文的抽象规定,这样的工作只能是法院来作。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解释,法律的抽象规定是难于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判的,因而对法律进行适用解释是法院的常规工作,是裁判的必须。而其他机关,因为不具有裁判权,具有法律的解释权是不可思议的,不能想象,不具有裁判案件的机关,不管是何种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对法律的具体适用进行解释。
2.个体:只有法院中法官具有司法解释的权力。这是指法院解释刑法的权力不是由作为一个机关的法院行使,而是由作为具体案件裁判者的法官行使,这是由解释的基本价值决定的。要使抽象的法条适用于具体的刑事案件,抽象的解释难于担当此任,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这种具体分析,不具有案件处理职责的法院(作为机关的法院)是难于胜任的,法院可以做到的是制订比法条具体一些的抽象解释,即法条规定的细化,但细化的法条也并不能一概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因而个体的解释只能是法官的解释。而且,由于司法解释是为了个案的裁判,而个案的特殊性——世界上难于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要求对法律的解释不是针对一般进行而是针对具体的该当案件进行,抽象的解释就难当此任。在此过程中,“判断某项决定是否正当,第一种可能的认识根据是法感。”⒄也就是法官依据常情常理对法律的理解,也可以称作法伦理。“具有支配力的法伦理之来源有:宪法中的基本权条款,其他法规范以及支配司法及行政行为的法律原则、交易伦理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制度;最后,向来的惯行也是来源之一,只要它是通行的价值观的表现。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并非不受任何限制,但这种限制主要不是外在的法律规则的限制,而是时代的限制,即“在形成和发展个案规范时,法官必须受法律所确定的目的、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法律的体系及其——于一特定历史时点中的——思考模式之拘束。”⒆这也可以说,法官的解释并非是法官的任性,而是法官依据当下的时代特点,对法律的价值进行的选择,以使抽象的法律在适用解释中反映出时代所要求的公正。
3.判决式:以刑事判决中的判决理由说明解释的内容。刑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的解释,而解释具有分析说明之意⒇,而对法条的分析或说明,是难于用对法条细化的方式进行的,一方面,对法条细化式的解释,难于具有分析说明的功能,只是硬性的规定,不符合解释的要求;另一方面,解释是对法条语言文字依据立法精神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离开具体的适用该法条之事实是难于说清的。因而,解释是针对具体事例的解释,是对具体案件如何应用以及为什么应用某法条进行判决的分析说明,这样的分析说明也就只能在具体的刑事判决中出现,这种在判决中以判决理由的形式对法条的解释,是具体的,符合解释的要求;同时要求这样的司法解释,也就是以制度的形式要求法官提高业务素质,增强责任心的具体方式。在这种解释模式之下,对法条的解释是每一个法官(具有裁判权)的自然权力,而解释的方式就必须是说理的,这种解释以判决的形式出现是符合解释的基本要求的。“很多我们以往认为,只需以单纯涵摄的方法,将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归属到先经必要解释的法律规范之构成要求之下,即可解决的案件,事实上,当我们将该当案件事实理解为法律构成要件所直射的事实时,已经带有价值判断的性质,或者,其本身已然是一种有评价性质的归类行为。将‘评价’视为个人立场的抉择的行为,对之无从为合理的论证,这种意见在学界迄今仍居支配地位。”(21)因而,抽象的解释难于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判,法律解释是也应该是法官针对个案的对法律的解释,而法官的裁判依据如果要为他人知晓,就必须在判决中说明其理由,在个案中的判决理由也就必然具有法律解释的性质。
(二)解释效力:司法解释是法官就个案作出的解释而只对当案有效
与我国现在司法解释的效力不同,如果说我国现在的有权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全国司法机关一体遵行的话,一元、个体、判决式的司法解释之效力就只是对当案有效,而对其他法官的判决不具有法律效力。这种解释的效力使解释只是对法律的解释,而且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而不是具有一体遵行效力的具有准立法形式的解释。这种解释的效力之特点,一方面是还解释以真正解释的性质,不再使之成为立法;另一方面,也是还解释以具体性,即分析说明为什么将具体的案件事实适用于相关的法律以及如何适用。其实,无论何种罪名,只要作为一个统一的罪名,其必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的内涵之确定,一般说来,依据立法意图是可以有较为统一的把握的,而且这种把握一般说来,只要不是特殊的情形,也并不是困难的;但对于这种规定性的外延来说,不通过具体事件的分析,是难于进行的,因而在判决中针对具体事件的分析解释其适用具体法条的理由,应该成为解释法律的基本形式。
同时需要指出,对法律的解释以个体判决式的方式进行,由于是充分说理的,也就容易得到对方的理解或提出反对的理由,使我国现今正致力进行的抗辩式的庭审模式在法律的适用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模式的实施,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判决理由的说明,就使法官必须要给判决一个能够让人信服的理由,如果其判决理由是难于服人的,就给检察机关的抗诉和被告人的上诉提供了理由,因而说明法官难于胜任裁判的工作。这种解释法律所带来的附随效果,也会促使法官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三)解释效果:对个案解释的借鉴形成司法常例
以上说明一元个体判决式的司法解释模式之解释的效力只及于当案而不具有统一的效力。但这并不是说明这样的解释对其他案件的裁判是绝对没有作用,毋宁说,这种作用是相当明显的。由于法官所作出的司法解释是有理由说明的,如果其说明可以服人,当然也就可以被其他的法官所接受;如果是不充分服人的,可以由其他法官进行修正,反过来这种修正也可以促使原判决的法官修正自己对法律的解释,达到理越辩越明的效果。“无论是立法者的决定,抑或是法官的决定,如果在多数有关的各种利益中,它优先选择保护那种明显比较重要的利益,它就是可以被正当化的。”(22)而这种选择只有在对具体案件裁判的理由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说明。同时,如果司法对法条适用都是附理由的,法官之间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就会对法律的解释达成共识或者形成争议,诉讼过程的进行,也就成为辨别法律意蕴的过程。理是越辩越明的,法律的蕴涵就会在诉讼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越来越明确、具体,并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同时,对法律解释的接受,会使个体的解释为其他法官接受而形成司法常例,即对于某种合理的解释为其他法官接受后,其他法官对同类案件进行同样的裁判,从而形成常例。这种司法常例的形成,也就会促使一国之内司法的统一。
当然,在个体判决式司法解释模式之下,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与高等法院,并非在司法解释方面无作为余地,恰恰相反,如果法院选择部分有价值的判决予以公布,形成判例,其对司法机关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样的判例并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官必须遵行的准法律,对法官来说,它只是一种参考,但由于法院的选编,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选编法院的立场或倾向性,法官如果没有充分的可以反驳判例之理由又不赞同判例的解释,就有可能在二审中承担败诉的后果;如果法官有充分的理由反驳判例,就是刑法解释的发展,是对法律的更合理的适用,达到用法律解释提升法律价值的效果。在这种解释法律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将抽象的法律用解释将其具体化,并尽可能在不违反法治原则的情况下通过解释使法律达到合理的效果;同时,“法官必须做的并不是确定当年立法机关的心中对某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想的,而是猜测对这个立法机关当年不曾想到的要点——如果曾想到的话——立法机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主观意图。”(23)这样的法律解释不仅可以充分地使法律的内涵得以被充分发现,而且如果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法律可能的意蕴,仍然不能使法律达到合理的效果,就说明立法的规定是存在不周延的,这样的解释的充分进行,也就具有为法律的修订提供参考的作用。
总之,一元个体判决式的刑法司法解释模式,符合解释的意义,有利于解释的合理,可以促使法官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便利于国民对法官判决理由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使诉讼过程不但是认定事实中控辩双方发挥作用的场所,也在解释法律过程中有发挥自己见解的余地(在控辩双方的辩论过程中,其各自的观点对法官也是有影响的),从而提高诉讼的质量,还可以为尽可能用足法律,并在此过程中发现法律的不周延,从而为法律的完善提供素材。
注释:
⑴关于该解释模式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李 洁:《中国有权刑法司法解释模式评判》[J],《当代法学》2004年第1期。
⑵《判例六法》是日本法律汇编形式的书籍,以在各法条后附相关的判例为其特征。
⑶参见[日]中山研一等:《しヴィジォニ刑法(1)共犯论》[M],成文堂1997年版,第73-74页。
⑷同前注⑶,第75-77页。
⑸如日本对电力是否可以作为财物的问题,就是通过判例中的判决理由的部分予以确认的。参见[日]《判例六法》[M],有斐阁2001年版,第12-14页。
⑹同前注⑶,第71页。
⑺同前注⑶,第71-72页。
⑻同前注⑶,第71页。
⑼同前注⑶,第72页。
⑽同前注⑶,第75页。
⑾[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页。
⑿两个严打决定的主要内容是加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与经济犯罪的法定刑,而这样的加重法定刑是否完全必要?笔者认为,有些就未必是必要的。例如,对流氓罪的法定最高刑增加到死刑,就未必是合适的,这从1997年刑法在分解流氓罪之后,对分解出来的四个罪名所规定的法定刑均无死刑就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明问题。
⒀这样的情况在1997年刑法中并非个别,例如,有客体相同或相似而性质不同的情况,象盗窃与侵占;有危害相同或相似而刑不同的情况,如交通肇事罪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之刑罚的明显失衡;有实害犯与危险犯之刑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如涉税类犯罪就存在这样的情况。
⒁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M],成文堂1991年版,第58页。
⒂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⒃日本在1974年制定了刑法修正案,至今尚未通过为正式立法。
⒄[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⒅同前注⒄,第7页。
⒆同前注⒄,第23页。
⒇《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6页。
(21)同前注⒄,第2页。
- 上一篇:木偶奇遇记读后感范文
- 下一篇:周末时光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