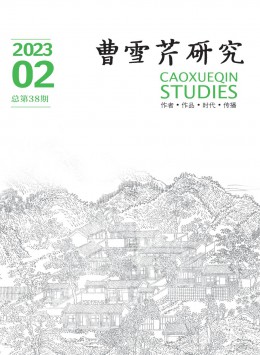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 ;风格;艺术手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码:1674-3520(2014)-02-00217-01
0.序言。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觉得,曹雪芹非常熟悉他周围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又很善于塑造人物形象,所以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
李妈妈的可厌,赵姨娘的无识,夏金桂的凶泼,晴雯的尖刻,贾政的道学,贾环的下贱,贾赦的尴尬,薛蟠的任性,迎春的懦弱,妙玉的孤高,袭人佞巧----但是作者又并非让读者鄙视这些人,以这些人为戒。他写湘云的天真,贾母的慈爱,宝钗的贞静,黛玉的多情,熙凤的才干,探春的敏慧,李纨的贤淑,贾兰的好学,也并非让读者赞扬这些人,以这些人为模范 。他平心静气,以客观的态度给了每个人物一种性格。因此让我深深被她们吸引,为她们欢乐、为她们悲伤而不能自拔。
1.《红楼梦》作品的整体风格。
红学家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的风格。把《红楼梦》和我国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加以比较,《水浒》是愤慨当时政治腐败,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儒林外史》中“牢骚则或过之”。他认为:“含怒气的文字容易一览而尽,积哀思的可以渐渐引人入胜;所以风格上后者比前者要高一点。”
红学家李辰冬认为《红楼梦》人物描写的根本特点,是作家所持的无褒无贬的严格的客观态度。关于《红楼梦》的风格,李辰冬认为它是属于“诗的金刚杵”而不是“美的风格”,而不是美的风格。“美的风格”,修辞学家有法分析,人们可以模拟;诗的风格,不但无法模拟,修辞学家也无用武之地。换言之,就是一种为技巧的,一种为天才的”。我认为《红楼梦》的风格没有一点润饰,没一点纤巧,并且也不用比拟,也不加辞藻,老老实实,朴朴素素,用最直接的文字,表现事物最主要的性质。
2.《红楼梦》的人物语言特点。
李辰冬对《红楼梦》中人物语言的充分个性化和《红楼梦》语言风格的特点作了高度评价:“将中国一切语体文的小说与《红楼梦》比较之下,就知道他的文字更较成功,其成功之由,因作者确实地向自然语言下功夫,且因善于移情关系,能体会每个人物应有的言谈与语调,所以贾母有贾母的话,熙凤有熙凤的话,黛玉有黛玉的话,宝钗有宝钗的话,刘姥姥有刘姥姥的话,总之,因性格与年岁的不同,言谈的腔调也同时而异。”
第八回宝玉与宝钗互识锁、玉之后,黛玉也来到梨香院。其中有两个细节完全是由人物的对话组成的,曹雪芹既没有写人物的眼神表情,也没有写人物的心理感受,然而各个人物的思想感情都跃然纸上了。而且随着对话的进行,读者的思想感情也和人物一样在一张一弛地活动着。黛玉本来是去探望宝钗病情的,可是一见宝玉先她而来,就“半含酸”地来了那句顶门针:“我来的不巧了”。这就逼出了宝钗的发问:“这话怎么说?黛玉接着把弓拉得更紧了,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虽然只说了句“我更不解这意”,言下之意却是“你必须把话说清楚”。黛玉“间错开了来”的话显然是在强词夺理,但却将拉满的弓又松弛下来。至于对雪雁说的那一席话,显然是在借槌敲鼓,当事者的宝玉、宝钗都听懂了,但一个不敢反诘,一个无法反诘。读者为她的“情”所动,因而也就原谅了她的“无理”。“有情”与“无理”都体现语言之中,然而形象的美却突破语言的外壳,由流动着的画面来显示的。
“曹雪芹风格之所以伟大就在这里;仅仅几句话,不但表现了他的人物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人物的“‘形’‘声’‘色’”。他的文字从日常语言中来的;然而比日常语言还要流畅,还要自然。
3.《红楼梦》人物性格塑造。
现代作家张天翼说过,小说的实际描写表现出:“这一双男女之所以特别相爱,仿佛有缘分似的,这缘分不在外物,而在他们自身。这是由他们各人的性格,兴趣,见解,生活态度等决定的。”
宝钗:深通世故,“能够博得上上下下各种种人的嘉奖和赞美”的人物。她是个“极实际的人”“能够面面圆通,处处得利”。但是这个“最正派不过的小姐”的思想言行跟贾宝玉却“有点格格不入”。而林黛玉则从来不对贾宝玉讲究那些“仕途红济”之类的话,也不懂行什么世故之类的东西,她看重的是真正的爱情,在观园里只有她是唯一能够了解、同情贾宝玉的人。宝哥哥认为红尘生活是可爱的,不可爱的是那安排红法尘生活的力量。四十四回凤姐泼醋,先下手打了平儿,接着贾琏也上来踢骂,夫妻都拿平儿煞性子。对这一薄命女儿横遭荼毒和蹂躏的命运,宝玉无比同情,亲自为平儿熨了衣裳,洗了手绢。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引起宝玉深切的同情,“平儿理妆”这件事使宝玉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发展,宝玉性格中的叛逆因素,显示着璀璨的光辉。
4.《红楼梦》同样以细节取胜。
杰出的作品,总是以细节描写取胜的。《红楼梦》在细节描写上,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丰厚的艺术遗产,滋补着我国的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红楼梦》的情节就装在这些细节里,随着细节的不断流动而移步换形。它不仅体现出一种动态的美,而且在动中显示着情节,和情节交融在一起。
比如第二十九回里写贾母领着女眷们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作为贺礼送的一盘法器中有一只金麒麟。平庸的作家可能会在这只金麒麟本身大作文章,写它的来历,写它如何金璧辉煌等等。曹雪芹却避开了这种不足以表现人物典型性格的物的描写,而去写各个人物对这只金麒麟的反应:每个人物所说的话都富有个性特点,而且都是形神兼备的“这一个”。宝钗的话正如探春所说,表现了她“有心”;而探春看出宝钗“有心”,却又表现了她的“敏锐”;宝玉的话说明他不拘细事;黛玉的话体现了她的“尖酸”;宝钗装作没听见,又显得她胸有城府;宝玉“揣着”又“掏了出来”,掏出之后又“揣了起来”,表现出他与黛玉、湘云之间那种微妙的感情和关系。一个细节写出了四个人的性格特点。
《红楼梦》细节描写的艺术手段是丰富多彩的,但丰富多彩之中却显露出一个总的特色,这就是重视白描,不事夸饰,看似平淡无奇,想去却是逼真的,令人感到意在言外,余味无穷。
参考文献:
[1]李辰冬,红楼梦研究,1942,正中书局。
[2]张天翼,贾宝玉出家,红楼梦人物评论集,1945,东南出版社。
第2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续写小说从来都是后辈作家向前辈致敬的一个重要方式,当《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之后,时至今日,续写《红楼梦》的冲动依然在一代一代作家中传递。这里面可能有作家逞才使气的成分,但是对《红楼梦》的热爱,对《红楼梦》的尊敬恐怕才是这样一种冲动代代不衰的重要原因。汪对《红楼梦》显然是充满尊敬的,这从《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中体现出来的对作品的熟悉,对小说微妙之处的理解中可以看到,不过,汪对《红楼梦》的敬意却以一种不敬的方式体现出来――他不是续写《红楼梦》,而是以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重新进入原著的很多情节之中,以事件当事人的口吻,重新演绎这些情节,其中还不乏以事件当事人的口吻表达出的对原著情节的批判。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演绎方法,就使得汪对曹雪芹遥远的致敬带有了解构的成分。而且,这种解构是彻底的,它不仅指向了《红楼梦》文本本身,也指向了关于《红楼梦》的研究。
一
《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的叙事者很特别,是《红楼梦》原著中的主人公贾宝玉。这个特别的叙事者是以当事人的口吻叙述自己的往事。这样,《我和她们》的叙事内容虽然是在原著《红楼梦》的叙事情节之间穿插往返,但是,这个特殊的叙事者就使得《我和她们》的叙事内容相比较《红楼梦》就更具有可信性――还有什么人的叙述能比当事人的回忆更具有权威性呢?这样,小说作者汪其实就有了更大的权力――他可以借助他笔下的这个虚构的主人公对原著发表任何意见,而汪也的确这样做了。所以,小说就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犀利的解构图景――针对《红楼梦》这个文本的解构。虽然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充分体会到汪对《红楼梦》的敬意,但是汪对《红楼梦》的解构也同样充分而犀利,小说以贾宝玉的口吻对《红楼梦》的小说整体架构和众多小说细节都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红楼梦》中有一个重要的二元对立结构,就是木石前盟和金玉之盟。木石前盟暗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宿命性关系,而金玉之盟则强调了贾宝玉和薛宝钗夫妻关系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结构的整体架构之下,小说衍生了悲喜交加的众多情节,甚至围绕《红楼梦》的很多研究、评论也都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整体架构之下进行的。可是,在汪看来,这个二元对立结构是可疑的,他借助对贾宝玉衔玉而生这样一个传奇细节的质疑,展开了对小说中木石前盟的解构。《我和她们》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通过理性分析,成功消解掉贾宝玉的先验神圣性。但是,从宝玉含玉而生这个细节在《红楼梦》小说中的重要性来看,《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对贾宝玉出生的分析不仅仅是要解构贾宝玉出生的神话,更重要的是解构掉全书赖以成立的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架构。当汪借助贾宝玉之口对石头的来历产生怀疑的时候,其实怀疑的不仅仅是这块石头是否是贾宝玉出生时口含着带来的,更重要的是,消解了前面关于顽石补天、绛珠仙子报恩这样一系列神话传说,自然,也就对小说中一直强调的木石前盟构成了解构。
在对木石前盟进行解构的同时,汪还解构了弥漫于《红楼梦》之中的宿命感。宿命感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特色。借助小说中宿命感的不断表达,使得小说在前半部描述贾家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时候,就已经若隐若现地呈现出悲凉的色彩。当小说暗示贾宝玉便是下凡的神瑛侍者,而林黛玉便是下凡报恩的绛珠仙子的时候,小说的宿命感便已经呈现,因为绛珠仙子已经表示要用眼泪偿还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这其实就暗示了宝黛二人的悲剧性结局。《红楼梦》的宿命感不仅在宝玉、黛玉的命运上呈现出来,而且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这种宿命感另外的重要表现方法就是利用的谶语、谜语、隐语。小说第五回就借助贾宝玉梦游幻境, 借助幻境中“金陵十二钗” 这个册子,预告了小说中十二位女子的命运。在小说第二十二回,贾政携家人做灯谜,小说先是不露声色地叙述,描述几位女子做灯谜,其谜底分别是爆竹、算盘、风筝等物。接着,小说写道贾政心内活动,“娘娘所做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做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所做风筝,乃飘飘浮荡之物。惜春所做海灯,一发清净孤独。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1]事实上,从小说叙事的最终走向来看,几位女子所做的灯谜,也都暗合了她们最终的命运。
可以说,《红楼梦》中有颇多此类伏笔,或者可以说成是草灰蛇线,利用诗词、情节暗示着此人之后的命运。这种写法在某种程度上对众多文字游戏的爱好者有一种迎合,但是同时,不可否认,这些情节客观上也都使得小说带有了强烈的宿命感,使得贾家即便是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时刻,也都带着悲凉之气,从而使得《红楼梦》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某种悲凉之味。虽然众多论者对《红楼梦》中这样草灰蛇线的宿命感的表达津津乐道,但是汪似乎对此并不认同。借助对贾宝玉出生时口含的石头的质疑,从整体上对笼罩全书的一个宿命性意义的表达构成了质疑。
面对《红楼梦》中不太合乎情理的一些具体细节,《我和她们》的叙事者贾宝玉也直接对之展开分析、批判。在第五章《晴雯,晴雯,我的花神》中,小说对《红楼梦》原著中晴雯怒斥坠儿的情节进行了批判,因为坠儿偷了平儿的镯子,《红楼梦》中,晴雯怒斥坠儿,并且“取出枕边的一丈青(簪子),朝坠儿手上乱戳”。对这个细节,《我与她们》进行了批判,“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亲眼所见,晴雯并没有拿簪子乱戳坠儿的手,晴雯可不是凤姐,凤姐才拿簪子扎丫鬟呢。我知道的,晴雯没那么狠,她只是狠狠地扇了坠儿一巴掌。”[2]
对于原著《红楼梦》的这种批判,叙事者并不局限于细节分析,甚至还对一些重要情节进行了批判分析。比如,原著中描述贾宝玉与薛宝钗的结合是在林黛玉重病之时,并且因此而导致了林黛玉的死亡,但是在这部书中,叙事者贾宝玉回忆与薛宝钗的结合,是在林黛玉死亡之后才进行的。叙事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红楼梦》原著设计贾宝玉结婚这个情节的不合理:首先,贾家作为诗礼簪缨之族不可能做这么下作的事情;其次,薛宝钗作为一个大家闺秀,极其自重的一个人也不会如此自降身价配合做这样的事情;最后,贾宝玉如果发现中了调包计,没有娶自己深爱的林妹妹,肯定不会认同或者配合这个调包计。无论批评的指向是曹雪芹,还是高鹗,其实作者都是从可能性这个角度,对《红楼梦》原著中的情节疏漏,或者是不合常理的地方展开了批判。
无论是对小说整体架构、风格的质疑,还是对小说具体细节的批评,《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都已经对《红楼梦》的书写构成了解构,而小说以贾宝玉的口吻对这些地方进行解构,更是给这种解构带上了某种权威的色彩。当然,这种解构,其实也在同时表明了汪关于文学的某种立场,那便是小说的依据应该是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作家的主观随意的情节设置。小说的可能性是指小说中的事件未必是历史中一定发生的,但是,应该是可能发生的,也是可以发生的。当曹雪芹以一个神话开头,然后用神话直接来照应小说中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违反了生活本身的可能性,而有些机械降神的味道,至于利用谶语、谜语等情节来强调宿命感,更是和生活的必然可能性没有关系。所以,对此,汪显然是不满意的。汪借助叙事者对《红楼梦》中具体细节的批判,更可看出他对小说应该遵循生活可能性的强调,他对《红楼梦》中晴雯戳坠儿这个情节的批判,对贾宝玉中了调包计娶了薛宝钗这样情节的批判,所依据的,都是生活的可能性。
二
《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一开始就引入了原著《红楼梦》。接着,小说中的叙事者,即贾宝玉说,这部《红楼梦》勾起了他的叙述欲望,因为这是关于他们贾家的一部书,所以,他想要写一写自己的故事。这个叙事开头,已经决定了《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叙事的重心所在:首先,这部书仅仅选择和贾宝玉有关的情节展开叙述;其次,点出了这部书选择的叙述点,只选择原著讲述得相对粗疏的地方,这一点就使得本书更富有了特殊的意味。众所周知,《红楼梦》问世以来,引起了太多人的兴趣,以致形成了“红学”,而“红学”集中讨论的地方,也并不是小说中明确点出的部分,往往是原著有意无意语焉不详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讲,《我和她们》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带有了文学批评、学术研究的意味。这就使得《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这本书不再是一部单纯的小说,而是打破了小说和理论研究的界限、带有强烈的《红楼梦》研究气息的小说。
借助贾宝玉这个人物,汪展开了他对《红楼梦》的解读和研究。而且,就小说看,汪对《红楼梦》的分析和解读是全方位的,既有对原著中语焉不详的某些知识、信息的考证,更有对小说中细微之处的领悟,对小说中人物微妙态度的把握。可以说,在这些研究、考证上,汪集中展现了他对《红楼梦》理解的过人之处,也向曹雪芹致以一个作家的遥远的敬意。小说在一开始,就考证了贾宝玉的名字:
宝玉,俗名,不过是个俗名罢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名、乳名、奶名。说到这儿,问题就出来了。那么,我的大名,雅名,或学名叫什么呢?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似乎回避了,或者忘记了这一点,反正他没有说。他不说,我就得说一下了。
……到了我这一代人,就是玉字辈儿了,如我的堂兄贾珍、贾琏……那我的名字也当然是玉字旁的,且是单字。好了,不必再绕弯子了,就直说了吧,我的名字叫――贾瑛,是的,贾瑛就是我的大名。[3]
这种考证和研究涉及更多的地方还是对小说中细微之处,小说中人物微妙态度、立场的分析。在《我和黛玉的爱情故事》这一章中,作者还分析了凤姐对黛玉和宝钗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凤姐在黛玉和宝钗之间,挑选一个和我在一起的话,凤姐的第一选择肯定是黛玉,于是当着众人的面,尤其是宝钗也在场的时候,她跟黛玉开了那么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你吃了我们家的茶,可是要当我们家媳妇的。这样的玩笑话嘛,由凤姐这个贾府的当家人口中说出,大家也就未必真的只把它看成是一个玩笑了,至少会有人在心里琢磨了,比如我,比如黛玉,比如宝钗,我们三个人都会这么想,莫非此乃凤姐的一个暗示,抑或是她有意跟大家发出的一种信号?若如是,这究竟是凤姐本人的意思,还是她巧妙地传达了长辈们的意见呢?[4]
上述两个例子,确如《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的叙述者所言,都是《红楼梦》原著中语焉不详的。在这些地方,汪以原著主人公的立场,设身处地地代入,分析《红楼梦》中含而不露的微妙之处,显然,在这些地方,这些叙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叙事,而构成了对《红楼梦》原著的评论。换言之,汪在这个地方已经成功消解了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和小说的分野。关于评论与文学分野的解构问题,是解构主义批评家的一个重要课题。著名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哈特曼成功消解了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的界限,他指出,“应当把批评看作在文学之内,而不是在文学之外。”因为就文学事实来看,批评和文学是统一的,“在艺术家的劳动中,批评活动在一种与创作的统一中,找到了它的最高的,它的真正的实现。”[5]毫无疑问,在《我和她们》这部小说中,小说借助小说形式展现出的对《红楼梦》的认知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小说叙事范畴,但是又以完美的小说形式呈现,体现了批评和文学的统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是一部打破了评论与小说界限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别开生面之作。
当《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的叙述不再局限于对情节的原创性构造,而强调对批评和文本的统一,强调对《红楼梦》文本进行不同角度的重新阐释、解读,强调对原著的批评的时候,小说也对既有的许多《红楼梦》研究的固定结论构成了消解。从《红楼梦》问世到今天,围绕《红楼梦》已经产生了“红学”,当然,关于这部书也形成了许多固定的结论,比如对小说中各个人物的评定,等等。当汪在这部书中围绕曹雪芹叙事相对粗疏的地方展开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围绕评论较多的地方展开,这样,借助小说叙事主人公贾宝玉,作家汪表明了他对很多红学问题的观点,从而也对既往的很多《红楼梦》研究的固定结论做出了自己的批评和解构。
受阶级论解读方法的影响,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家多赞扬黛玉,批评宝钗,但是在《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这部小说中,叙事者在赞扬宝玉和黛玉感情的纯真和他们品性的纯正之余,也并没有贬低宝钗,相反,还大大地赞扬了宝钗。作者没有囿于既有的红学评论对宝钗、黛玉的近乎定式的看法,而是详细分析小说文本,分析文本细节,提炼出自己的独到结论,从而颠覆了传统的对黛玉、宝钗二元对立式的认知看法。通过细致地分析、描述,《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解构了传统红学研究的很多固定结论,呈现了《红楼梦》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三
文学在本质上来说属于语言的艺术。如果缺乏好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小说题旨再高深远大,恐怕也会行之不远。所以,对于小说来说,叙事语言极其重要。这个恐怕也是众多续写《红楼梦》的作家拼命模仿《红楼梦》叙事语言的原因。或许,这些作家并没有超越《红楼梦》的梦想,但是,都想在最大限度上与《红楼梦》相像。如此,在小说的外部形态――语言――上下功夫,让小说语言和《红楼梦》接近甚至一致,就成了小说家本能的选择。但是,问题是,现在对几百年前的语言的模仿,究竟能否达到当时的神韵?即便和当时语言极其相像,是否还有意义?
对此,法国新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指出,叙事语言的模仿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语言环境,很难让写作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即便模仿极其逼真,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模仿的语言已经根本不具有所模仿语言在当时所具有的意义。[6]汪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与阿兰・罗伯格里耶相通的,他要以贾宝玉的口吻写一部和《红楼梦》有关的书,但是,他却没有遵从“惯例”,从模仿《红楼梦》的语言开始,而是完全采用了现代白话文。对于习惯了“惯例”的读者来说,此处可能会有不适应――古人用现代语言描述自己的生活,但是汪却尊重了一个基本的现实,现代作者已经不可能在语言叙事上与几百年前的曹雪芹完全相像。与其非驴非马,不如率性写出带有这个时代特征的自己的语言特色。
但是,汪此举并非说明他没有在小说叙事语言上下功夫。如前所述,对于小说而言,符合生活的内在可能性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这也是汪反对充斥于《红楼梦》的各种预言、谶语的原因。因为这些预言、谶语不是从生活的逻辑延伸,而是突兀而起。同样,对于小说语言来说,也存在一个符合生活内在可能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汪下足了功夫,在《我和她们》这部书中,重点写了秦可卿、袭人、晴雯、黛玉、宝钗等几个人物,而这几个人物的语言也各具特色,各不相同。比如,小说写到,当黛玉、宝钗等人都看到袭人将来可能会成为贾宝玉的妾,“黛玉就时常开袭人的玩笑,动不动就直言不讳称袭人好嫂子……而黛玉却不罢不休,不依不饶笑道,说什么丫头不丫头的,我只把你当嫂子对待,而且是我的好嫂子。相比起来,宝钗姐姐就巧妙得多。有一回,我母亲打发丫头给袭人送来了两碗菜,袭人受宠若惊了,说这多不好意思呀。宝钗姐姐抿嘴一笑接道:你这就不好意思了?日后还有更不好意思的等着你呢。”[7]这段描述,就把林黛玉的直率而无心机,同时又有些刻薄,宝钗心思缜密,用语委婉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汪的小说没有模仿曹雪芹当时的叙事语言,但是在叙事精神上,在对人物精神的把握上,他显然是和《红楼梦》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只是汪对《红楼梦》原著精神的某种承续,很难说是有所创新的话,《我和她们》小说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合理的方向上,对《红楼梦》情节的延伸。这就需要作家对《红楼梦》的情节有深入、深刻的了解,从而在合理的方向上展开合理想象,对《红楼梦》的情节展开延伸。在这样的语境下,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更要符合小说中此时、此地的心态、立场,更需要符合生活的内在可能性。在这方面,《我和她们》的语言就显出了作者的独具匠心之处。《红楼梦》中的晴雯是贾宝玉的大丫头,因为性傲,且姿态妖娆,为王夫人及其他婆子不喜,所以,在查抄大观园之后,晴雯被赶回家。贾宝玉思念晴雯,偷偷跑出贾府,探望晴雯。《红楼梦》中对这一段细节描写并不繁复,晴雯除了对贾宝玉表示自己和贾宝玉原本清白,却枉自担了狐狸精的虚名,有冤无处诉之外,还与贾宝玉换了内衣,以表示不愿枉担冤名。在《我和她们》中,叙事者展开延伸,先是就晴雯的枉自担了狐狸精的虚名展开叙述,“是啊,我知道你很冤枉的。我长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很后悔的……我真的后悔了,很后悔当初没有跟晴雯甜甜蜜蜜地好上一场。可能那时候我跟晴雯的思想是一样的吧,以为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长着呢。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想我会不管不顾,和晴雯有一个更甜蜜的故事的。”[8]在两人互换内衣之后,汪增加了两人互诉衷肠的情节。这个情节的展开毫无疑问是合理的,因为《红楼梦》的两人互换内衣的情节其实已经暗示了两人并非简单的主仆关系良好,也并非简单的晴雯赌气,其实是两人早已情愫暗生,只不过没有挑明,或者说两人没有明晰地意识到而已。在《我和她们》中,小说让这个情节自然延伸,同时,晴雯在此时的语言,也没有了在大观园时与贾宝玉的撒娇赌气,而是真情毕现,也完全符合了此时一个濒临死亡的陷于爱情中的年轻女子的心态。
《我和她们》的白话文叙述,从续写《红楼梦》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红楼梦》的一种反叛――直接从小说叙事的最外部形态的背离。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传统的续写《红楼梦》著作的一种解构。但是,从小说叙事的精神来看小说实质上是和《红楼梦》一脉相承的,作家正是在把握了《红楼梦》叙事精神的基础上,用现代语言,对《红楼梦》语焉不详的地方,阐释、分析。
《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是关于《红楼梦》的一部书。从这本书的书写,从汪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红楼梦》的熟稔程度,从作者借贾宝玉之口表达出的对《红楼梦》很多细节的理解,我们当然很明白地可以看到,这是汪作为一位作家向前辈作家的一个遥远的致敬。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红楼梦》很多细节的精妙的理解,其实正是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良苦用心的理解。当然,当汪借助叙事主人公贾宝玉自由穿梭在《红楼梦》设定的场景中,对《红楼梦》的很多情节以当事人的口吻发出自己的理解时,我们发现,汪也顺便完成了对《红楼梦》文本的解构。同时,当汪以小说的形式谈论“红学”问题,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汪对红学研究的一个创造,它解构了小说和评论的界限,使得《我和她们――贾宝玉的自白书》既有小说的细节塑造与情绪感染,也有着学术研究的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从而让这部书也成为了打破评论与小说界限的有关《红楼梦》的别开生面之作。
注释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62页。
[2]汪:《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3]同上,第17页。
[4]同上,第223―224页。
[5][美]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纽黑文1980年版,导论。
[6][法]阿兰・罗伯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第3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成就最高的伟大作品之一。正如鲁迅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①如果说《红楼梦》对贾府衰败过程的描写,使读者看到的主要是人生黑暗的一面,那么《红楼梦》所塑造的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则表现了时代的希望和人性的美好。可以说《红楼梦》在揭露黑暗的同时,赞美了光明;在表现衰败的同时,写出了新生力量;在诅咒腐朽的封建社会的同时,更拥抱了新的时代和人生。这正是《红楼梦》远远高于当时一般世情小说的独特成就。而这一切,集中反映在《红楼梦》众多人物形象之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身上,鄙人就此浅谈一下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贵族公子。作为四大家族之首贾家的公子,宝玉的人生道路,应该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封建社会男子最看重的仕途上,表现了极强烈的叛逆性。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这充分显示出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在“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贾家,贾母、贾政等统治者本来对宝玉寄予很大的希望,盼望宝玉读书、中举、扬名显赫,成为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可宝玉却走着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成为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这种新生力量正是黑暗社会中依稀可见的光明。从《红楼梦》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宝玉平时最懒于与士大夫诸男人如贾雨村之流交谈,最厌恶世俗礼仪,当贾府的重要亲戚王子腾过生日时,贾母命宝玉前去拜寿,他却私下里极不耐烦地抱怨:“一年四季闹生日闹不完!”这种“贺吊往返”,在封建社会是关系到家族的荣辱休戚的大事。对此,贾宝玉却毫不热情。可见贾宝玉是极不愿意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道路。
贾宝玉还富有平等的思想。他从不以“主子”的身份自居,有时甚至甘愿为丫鬟当“仆人”。 例如:晴雯和宝玉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丫鬟和主子,但宝玉从没把晴雯当丫鬟看待。晴雯对宝玉也是格外亲密,这是因为晴雯最欣赏宝玉的是他不以封建主子自居,并且宝玉从不把她们当下人看待。她们与宝玉在一起也从不感到约束,还可以自由自在的任其所为,宝玉有时还喜欢为她们“服劳役”,“折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自由、平等的思想,其实质,正是对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秩序”,有两个重要的支柱,一是等级制度,一是男尊女卑。贾宝玉在反对等级制度的同时,对男尊女卑的腐朽传统更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在《红楼梦》一书中,他不只一次的说过:“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他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混浊”。②宝玉的这些惊世骇俗的思想,正是他反对男尊女卑传统道德观念的彻底性,这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贾宝玉还以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作为一个封建宗法制度下豪门贵族的子弟,他的婚姻应当以“门当户对”为前提,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决定。那么“金玉良缘”,既是门当户对的象征,也是封建大家庭家长意志的体现。但是,贾宝玉完全无视这些封建教条,他把与自己有共同思想、志趣相投的的林黛玉视为红颜知己,把自己全部的爱情都给了“木石前盟”。而“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正是封建礼教与反封建礼教的对立。因此,贾宝玉的爱情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而宝黛的爱情及其悲剧,虽然表明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和新生力量的弱小,但却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显示出人性与真情的美好,也是现代爱情婚姻制度的雏形;宝黛的爱情及其悲剧,既是对毁灭纯真爱情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最强有力的控诉,更是对封建礼教叛逆者坚贞爱情的赞美。《红楼梦》正是塑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样的关键人物,才使整部小说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成就最高的伟大作品。
从《红楼梦》成书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学”。并且这么多年来,红学的发展又经历了种种曲折和成就。但由于《红楼梦》本身的博大精深,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认识也将会不断深化,可是依然会有分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只是《红楼梦》在思想内容以及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独特成就永远都会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第4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关键词: 《红楼梦》 人名绰号 隐喻 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扛鼎之作,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知名度,准确自然地翻译这部文学著作对传播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中,作者曹雪芹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常常将人物形象和人名、绰号联系起来,使《红楼梦》中人名和绰号不仅具有称谓功能,而且映射人物的性格、命运,甚至揭示了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主题。这些人名和绰号负载着巨大的信息量,无形中已经成为寓意深刻的文学隐喻,它们的翻译准确与否关系到作品主旨的传达,可谓意义重大。
一、《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机制
隐喻是指将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映射或婉转的表达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言语行为,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1]。《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也是如此。小说中具体的人名、绰号投射到抽象的人物性格命运、作品主题之上,两种概念之间形成映射,构成了隐喻的概念:人名是人物,人名是主题[5]。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丫鬟的名“紫鹃”。“紫鹃”可以引申到杜鹃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杜鹃鸟“惯作悲啼”,被认为是替亡魂诉说冤情。唐代以后,杜鹃鸟就被称为“悲鸟”、“怨鸟”,成为哀婉、纯洁、至诚、悲愁的象征。而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是哀婉、悲愁的,作为丫鬟的紫鹃对林黛玉至忠、至诚,一生为其殚精竭虑。曹雪芹利用人们对杜鹃鸟认知来映射小说中紫鹃的性格命运,恰到好处。在对“紫鹃”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的发生依赖于特定的文学语境——《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涉及人物个性命运、作品主题等内容。特定的文学语境是人名、绰号隐喻赖以生成的基础,人名、绰号隐喻中的目的域就蕴含在《红楼梦》的文学语境之中。同时,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环境,《红楼梦》所处的大文化语境——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也是《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所处的文化语境。曹雪芹巧妙地利用人名、绰号在文化语境中具有的普遍内涵传达特定的文学意图,使人名、绰号升华为人名、绰号隐喻。
总而言之,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中,作者曹雪芹是以汉语文化语境为媒介,精心设计完成了人名、绰号对人物形象、作品主题的映射。在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和理解上,汉语文化语境和《红楼梦》本身创设的文学语境缺一不可。
二、两个英语译本隐喻翻译赏析
文学作品写作和阅读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过程。只有当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表达的主题被读者准确的理解,两者的交际才算顺利完成。相对日语和韩语而言,英语的文化环境与中文的文化环境差异较大,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面对的困难也就更大。我们就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看看前辈翻译工作者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中,流传广泛的是包括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译本《红楼梦》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处理人物的名称:音译、音译加注释、意译。他们大量运用音译法翻译书中人名、绰号。音译法是杨译本对人名、绰号的翻译的主流方法,对于《红楼梦》这本著作来说,音译法远远无法承载人名、绰号中蕴含着的丰富信息。与杨译本相比较,霍克斯译本《红楼梦》的好处就在于大规模的采用了意译法。意译法主要被应用在书中群体人名的翻译中,主要包括奴仆群体,演艺群体,僧道神仙群体。比如奴仆群体中“花袭人”这个名字取自诗句“花气袭人知昼暖”,意为花香袭人,取名者贾宝玉喜欢用香木花草为他的贴身丫鬟命名,赞扬她们的外貌或品性。同时“花袭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人物的性格也很契合,“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霍译本将“袭人”译为“Aroma(芳香)”,既揭示了主人宝玉的情趣,又显示出了人物本身的性情,是相对较为成功的人名隐喻翻译。但是霍克斯译本对书中上层人物如贾宝玉、柳湘莲、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的人名主要采用音译法。这种译法上的区别固然可以让读者间接体会到小说中人物的地位尊卑,从而更好的理解整部小说。但是有得必有失,这些书中上层人物名字的隐喻义也丢失了,而这些人物恰恰是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他们的名字变成了简单的代号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了。
三、《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策略
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相对音译法而言意译法更能将《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体现出来。但是《红楼梦》中人名、绰号隐喻丰富多变,在采用意译法时,我们也应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是用人名和绰号来映射书中的人物或书的主题,人名、绰号及其意义就是喻体,人物和主题就是目的域。隐喻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隐喻是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表现,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同一个目的域,不同民族使用的喻体可能不同,而同一个事物或概念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投射的目的域也可能不同。我们可以根据原文中的喻体和目的域在其他语言的文化环境中的认知情况为《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选用不同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
首先,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已知的、熟悉的经验和感受去理解和体验未知的、陌生的事物,即用隐喻传言达意,这是人类隐喻认知的共性[2]。这反映在隐喻上,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对于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或概念会产生近似的联想,比如提到“黄金、珍珠”,人们都能联想到它们背后的“珍贵、价值高”等特点。当这样的事物或概念作为喻体出现时,即使所处的文化环境并不相同,不同民族的人还是能够理解隐喻的含义。因此,当《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中的喻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相似的隐喻含义时,能够引发相同或相似的联想时,我们可以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喻体。比如霍克斯译本中将探春的绰号“玫瑰花”直译为“The Rose”,同样也能体现绰号中的隐喻含义,即探春虽然是个富家小姐,外貌明艳娇贵,十分讨喜,但个性十分鲜明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接近的。
其次,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固然存在普遍性和相似性。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差异,不同民族的人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其隐喻方式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2]。其中一种情况是两种文化面对同一事物或概念可能都存在隐喻,只是隐喻的喻体不同,这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认识同一世界不同角度。如针对心慌的情绪状态,英语中有“have a butterfly in stomach”,汉语中则有“怀里揣着个兔子”与之对应。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译者应尝试将原文中的喻体换成适合于目的语文化中的喻体,进行喻体意象转换。我们可以从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部分人名和绰号隐喻的成功意译中汲取一些经验,如图:
“紫鹃”被译为“Nightingale(夜莺)”而不是英语中与其对应的“cuckoo(杜鹃鸟)”,是因为“cuckoo”在英语文化中除了指杜鹃外,也有疯人、狂人、傻事、丑事的意思,可以说英语文化中的“cuckoo”背离了汉语文化中杜鹃忠贞、执著的象征意义。而“Nightingale”在英语中象征对高洁美好的执著追求,与中文里的“杜鹃”相似,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原著意思,但也相去不远。这些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都是译者充分了解相应的人物形象,理解了这些人名、绰号的隐喻含义,同时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下努力寻找合适的喻体的成果。
最后,直译保留原文喻体形象和进行喻体形象转换这两种意译策略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中并不总是适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毕竟和原语言的文化环境有着诸多差异,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并不总是具有与目的域对应的合适的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采用直接翻译隐喻义的方法。比如《红楼梦》中李纨的两个丫鬟素云和碧月,“素”是指白色,“碧”是指青色,喻意清白,而名字中的“云”和“月”也是高洁而清冷的,这两个丫鬟的名字隐喻了她们的主人李纨寡居的身份和其贞洁、清白的人生追求。这两个名字的隐喻的形成和理解都非常地依赖于中国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环境中找到两个合适的喻体来表达这隐喻中的目的域,所以霍克斯在翻译这两个人名时,选择了直接将能表达出隐喻义的词语作为人名的策略,译为“Candida(心洁,清白等[拉丁语])”“Casta(清廉,纯洁,贞洁,虔诚等[拉丁语])”这种翻译策略基本能够表达出隐喻义,但人名、绰号经过这样的翻译后已经缺乏隐喻的含蓄意味,文学上、艺术上的美感被大大削弱,但是这也不失为一种补救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这种方法,同样也不能忽视文学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语境,在众多目的语词汇之中选择最具美感、最适合作为人名的词语。比如在霍克斯译本中,“霍启”译为“Calamity(灾祸)”,虽然将人名的隐喻含义“祸起”体现了出来,却没有美感,而且也不符合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因为霍启作为甄家家奴,主人是不会给他起寓意不吉的名字的。像“霍启”这样的隐喻都是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立足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翻译为其他语言具有一定难度,很难找到可以作为人名的相应喻体,若直接用隐喻含义翻译人名又容易和汉语文化语境产生冲突。这时我们可以采取音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论在保留原著魅力还是在方便读者阅读方面都存在不足,所以在意译法能够翻译《红楼梦》人名、绰号时,我们最好还是采用意译的手段。
正如翻译家奈达所言:“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用目的语民族能够理解的方式体现原作的文学精髓和文化底蕴的翻译,才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要立足于隐喻本身的具体情况结合作品文学语境、原语言文化语境、目的语文化语境,选择最为合适的译法,“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是《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成功翻译的保证。
参考文献:
[1]束定芳,汤本庆.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J].外语研究,2002(02).
[2]王黎.从认知角度看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
[3]刘法公.谈汉英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中国翻译,2007(06).
[4]肖坤学.论隐喻的认知性质与隐喻翻译的认知取向[J].外语学刊,2005(05).
[5]肖家燕,庞继贤.文学语境与人名隐喻的翻译研究:基于《红楼梦》英译文的个案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5).
[6]金娴.《红楼梦》霍译本中的人名翻译及其对文化的“传真”[J].文教资料,2010(01).
[7]李占芳,杨春红.《红楼梦》人名、绰号翻译与人物身份构建[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第5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人名;语义流失《红楼梦》中究竟出现了多少人物,颇难做出准确的统计,总之有三四百人。名字取得好、有意味颇费了曹雪芹一番巧思。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就曾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曹雪芹给《红楼梦》人物命名的思路大致有三点。第一,隐名于音,顾音思意。《红楼梦》中许多人物都是利用谐音命名,隐名埋姓于音,音义结合,妙趣横生。小说一开头,出现了两个对比性的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这是两个典型的中国式名字,作者却用以表明自己的某种创作思想:“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第二,人名预示了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或结局。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表明了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悲惨命运深深叹息的感情。第三,人名揭示了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名字,对他们的性格特点做了介绍。透过这些介绍,我们可以明白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和看法。
霍译本的译音部分。红楼梦中的人物名称大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包括人物的性格、命运、家族关系,社会地位等,而谐音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尤其在人物的命名中。通过音译来完整表述人物特征,是任何译者都无法承载的。霍克斯在处理这些姓名翻译时,采用的是汉语拼音方案。但他并非全部采用译音法,而是按人物身份的尊卑、职业生涯、名字性质等情况,分别采用译音法和译意法。小说中社会地位高的人物和具有人身自由的人物等,其名字一般都采用译音。但是,采用译音法所翻译出来的译文,难免会有原文内含信息丢失的情况出现。这里,通过语义成分分析的方法来列举。例如,贾政 ,音译为Jia Zheng ,在红楼梦中,贾政,这个人物一直积极地投身于权利斗争之中,实为一个悲剧人物,一个伪君子。因其对应的姓名含义应是 “假正(经)”,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因此,译音法在这里产生了相应的语义失落。我们来看《红楼梦》重要人名双关语的翻译,通过比较,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造成的语义流失:
(1)主要人名双关语原名 霍译本 语义子项甄士隐
(“真事隐”) Zhen Shiyin
(序言Zhens―another wordplay―Who are a sort of mirrorreflection of the Jia family) +Male,+true facts concealed贾雨村
(“假语存”) Jia Yucun
(序言Jia... a pun on this other jia which means“fictitious”) +Male, +untruthful meaning秦钟
(“情种”) Qin Zhong
+Male,+love species秦可卿
(“情可倾”) Qin Keqing +Female, +love can be poured, +tenderness贾敬
(“假敬、假经”) Jia Jing +Male, +not worthy of respect, +prude贾赦
(“假色”) Jia She +Male,+pruriency,+ posturing,+indecent贾政
(“假正经”) Jia Zheng +Male, +take part in politics, +pedantic,+decayed,+tortuous,+ hypocrite,+double faced贾琏
(“假廉”) Jia Lian +Male,+ corrupted, +lust贾宝玉
(“假宝玉”) Jia Baoyu +Male, +precious jade
林黛玉
(“玉带林”) Lin Daiyu +Female, +Umberblack dye jade王熙凤
(“显赫的凤凰”) Wang Xifeng +Female, +Splendid Phoenix,+ Pungent,+ shrewd,+be smooth and slick李纨
(字“宫裁”) Li Wan +Female, +plain silk, + ascetic, +good wife and mother元春
迎春
探春
惜春
(“原应叹息”) Yuanchun
Yingchun
Tanchun
Xichun +Female,+should be worth a sign, +unfortunate, +show profound sympathy for their fate
以上人名均为谐音双关,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霍克斯充分认识到“甄士隐”“贾雨村”这两个关键人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用注释加以说明。但更多的则是采用译音法译出,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考虑到西方读者没有这种命名习俗故将此类双关语用非双关语译出。例如,宝玉的四个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她们四人的姓名放在一起的含义是“原应叹息。”她们出身显赫但最终都无法逃出命运的捉弄。这样处理的缺点在于它无法很好地将双关语的深层含义表述出来,致使西方读者无法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艺术感受。
(2)次要人名双关语翻译原名 霍译 语义子项娇杏
“侥幸” Lucky +Female, +lucky, +uncertain of one’s fate, +Impermanence of things霍启
“祸起” Calamity +Male,+ disaster caused by him英莲
“应怜” Yinglian +Female, +poor people, +should take pity on her冯渊
“逢冤” Feng Yuan +Male, +suffer injustice张如圭
“如鬼” Zhang Rugui +Male, +evil like ghost, +led a life as a worm詹光
“沾光” Zhan Guang +Male,+benefit from them, +good at flattering单聘仁
“善骗人” Shan Pingren +Male, +good at deceiving, + greasiness卜固修
“不顾羞” Bu Guxiu +Male, +regardless of shame吴新登
“无星戥” Wu Xindeng +Male, +no principles, +unfair戴良
“大量” Dai Liang +Male, + large quantity, +numerous戴权
“大权” Dai Quan +Male,+powerful,+authority卜世人
“不是人” Bu Shiren
(序言a name that could be roughly anglicized as Mr Hardleigh Hewmann) +Male, +unworthy of life,+hardly human, behave like a human being王仁
“忘仁” Wang Ren +Male, +ungrateful, +devoid of gratitude
霍克斯在翻译这部分人物姓名时则是将大部分译为非双关语,对出现频率较少的个别人名采取译意,以双关语译双关语,处理手段令人称赞。但那些采用译音的人名都无一例外的丢失了内在信息。例如,甄英莲,谐音为“真应怜”,暗示她的悲惨命运,她本是乡绅甄士隐的女儿,原为富家小姐却连遭厄运。而与她形成对比的一个人物就是娇杏(“侥幸”)。她本是英莲的丫鬟,最终却过上贵妇的生活。她们的姓名都暗示了各自的命运和特征,但音译后对英语读者而言只是一些普通的人名,谈不上任何特殊含义,以上提到的种种信息就此丢失。另外,詹光(“沾光”)、单聘人(“善骗人”)、卜固修(“不顾羞”)等均是贾政身边的幕僚,他们的名字都代表其本性:阿谀奉承、八面玲珑、恬不知耻。这些深藏在名字当中的文学隐喻,在音译之后就不可能传达作者的良苦用心了。
霍译本《红楼梦》对人名的翻译中存在许多信息丢失,这种语义流失必然会影响到英语读者对于这本小说的理解和鉴赏。但是瑕不掩瑜,霍克斯的译名无论在拼写、语音、语义甚至语种的选择上都经过精雕细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合理性和艺术性,整个译本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我们借鉴的艺术品。参考文献:
[1] 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 Books,1977.
[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王金波,王燕.论《红楼梦》地名人名双关语的翻译[J].外语教学,2004(4):5357.
[4] 夏廷.《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人物姓名的翻译策略[C].刘世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2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35154.
第6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影视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必然具有商业性、大众性和娱乐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为迎合高收视带来的高收益,降低新剧本创作带来的风险,许多影视剧创作者开始翻拍经典,拍摄了众多的名着改编题材影视剧,例如以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笑傲江湖》(2013)等。在电视荧屏狂轰滥炸的包围下,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形式的名着改编进行审视。随着电视剧领域市场化的深入,影视剧创作逐渐显示出脱离精英化趋向娱乐化的趋势。刘彬彬在其《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一书中曾提出,当前的电视剧改编应归纳为三类:“照编法”、“整编法”和“创编法”。“创编法”电视剧比较着名的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宰相刘罗锅》等,虽为“戏说”,却是大众文化的优秀产物,传播健康向上的大众审美。“创编”虽有戏说的成分,但这不代表所有脱离原着精神的戏说作品都有艺术价值,这需要我们区别对待。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之首,历年来不乏对其进行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戏曲,都演绎出了対《红楼梦》不同的审美。为更全面的分析影视剧改编过程中的得与失,笔者选取了影视剧改编中最经典的87版《红楼梦》和2010年的新版《红楼梦》为比较研究对象,试图从经典入手,观照当代影视剧改编中的不足,窥见名着题材影视剧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87版《红楼梦》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组织摄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吸收众多红学家的思想精华,历时三年拍摄完成。在内容上,87版红楼梦仅选择以曹雪芹所着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为蓝本,创作了电视剧的前29集,而后7集则是根据前八十回中曹雪芹所着的伏笔、脂砚斋的点评以及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内容的研究进行创作的。导演王扶林将主流思想及个人的创作风格与《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相融合,创作出了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电视剧作品。在演员选定上,87版《红楼梦》更是举全国之力,创大规模海选的先河,这些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演员,在电视剧播出后,因他们深入人心的形象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87版红楼梦凭借优秀的创作思想和演职员的共同努力及卓越的后期制作,成为观众心目中《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中不可超越的经典。
新版《红楼梦》在创作风格上沿袭了李少红导演唯美的创作风格,力求展现一种浪漫高雅的诗意景象,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着,全书一百二十回,学术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先生所着,后四十回遗失,现今流传的《红楼梦》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历年来为红学家争论的热点,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基本上继承前八十回的悲剧精神。并且历代续作版本层出不穷,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流传至今,可见高鹗的续作同样具有艺术价值,需要进行辩证的阅读分析。所以在进行影视剧改编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就成了首要问题。87版《红楼梦》只选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着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删改。突出的删改情节有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颇有文采的“海棠诗社”以及与秦钟相关的章节等。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和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内容的影视表达需要借助一定水平的特效技术,但在当时八十年代的影视剧制作条件下,电视剧制作还不具备这种先进的技术,并且这些章节的浪漫主义风格有悖于八十年代我国总体的历史环境。另外,有关秦钟的章节也被认为涉及以及封建的文化糟粕,自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但最可惜的删改内容莫过于“海棠诗社”———“海棠诗社”的有关章节是大观园最繁盛时期的章节,也正处于林黛玉文采诗情的顶峰时期。“海棠诗社”的内容最终还是因资金和技术等因素被迫撤出了电视剧的拍摄计划。但对于87版《红楼梦》,最为观众期待和关注的还是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解读。87版《红楼梦》抛弃高鹗所着的后四十回,采用了众多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结局的安排上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在高鹗所着《红楼梦》后四十中,探春远嫁镇海总制;黛玉听闻金玉成姻,焚稿断情悲痛而死;金玉成姻是贾母等人在宝玉疯癫的情况下施掉包计所致;宁府虽遭抄家流放,但最终两府却是“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大团圆结局;而宝玉最终是在中魁之后随僧道出世。而在87版《红楼梦》中,探春是作为北静王的义女远嫁和亲的;黛玉是梦见宝玉客死他乡伤心惊惧而死的;金玉成姻是奉元妃旨意而行的;荣宁两府最后落得满门抄家,家破人亡;宝玉在被救出铁槛寺后归于“白茫茫厚地高天”的精神放逐……这些情节都与高鹗所着后四十回有较大差距。编剧周岭先生曾说,87版《红楼梦》是“根据人物发展、情节推进的自然逻辑,根据原着前八十回正文的伏线,根据现在能看到的脂砚斋批点的版本,根据《红楼梦》学术界多年研究成果,尽可能合理地把八十回以后部分构想出来。
黛玉“焚稿断痴情”的缺失,使得87版《红楼梦》还是使观众觉得若有所思。可见,忠实于原着,不仅仅在乎他的内容,还要重视继承原着中深刻的民族文化,不能将名着的影视剧改编视作一场学术盛宴,太过追求学术研究还是会脱离群众的审美要求,得不偿失。相比之下,2010版《红楼梦》在内容上相对于87版《红楼梦》更加符合原着的内容设置,但缺少了87版《红楼梦》对原着的思考与探索。2010年《红楼梦》完整地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为实现影视剧整体的情节紧凑与连贯,只在少数情节上略作调整。李少红也曾指出她的拍摄原则是“只有删减,没有杜撰”。2010年版《红楼梦》一经上演,被许多红学家赞为是“非常忠于原着”的影视剧改编版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比87版《红楼梦》与2010版《红楼梦》的结尾之后,观众更加倾向于老版《红楼梦》对结尾的诠释,认为这其中蕴含着众多红学家的智慧,更加贴近曹雪芹先生对《红楼梦》的结尾。新版《红楼梦》这种照搬原着的方式不免使观众产生肤浅之感,并且高鹗所着后四十回中的大团圆结局确实不符合曹雪芹先生在前八十回中的描述,从这一方面来看,新版《红楼梦》对后四十回的解读确实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思考。何为名着之“忠诚”?刘彬彬在《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中,对“忠实于原着”的内涵有具体的界定,即“忠实于改编者对原着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着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对于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来说,还应忠实于电视连续剧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另外,改编还应当忠实于改编者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意向,使作品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的生命活力,以此促使改编题材影视剧的长盛不衰。
第7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电视剧;人物;比较
中图分类号:J99
曹公笔下的《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也是我们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对经典文学名著的改编,新旧版电视剧《红楼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塑造的人物形象通过屏幕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不尽相同,观众对其也是褒贬不一。
一、贾宝玉
贾宝玉是主要中心人物。他叛逆、大胆,追求自由与平等。在他的眼里,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的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是贾氏家族寄予众望的继承人。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鄙视功名利禄,痛恨“八股”这些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生活的道路,否定封建社会主义秩序,但贾宝玉的性格又有些趋于消极。
87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由欧阳奋强来扮演。人们对于87版欧阳饰演的宝玉有些不满,是因为欧阳这张娃娃脸不能演绎出书中那个但欧阳奋强与生俱来的“憨”将宝玉的痴态演绎地恰到好处,反而把宝玉给演活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看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87版中的宝玉“目若秋波”,他的叛逆,他的大胆,他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内心,都饱含在他那既有神又有情的双目中。
新版中小宝玉纯真可爱,大宝玉痴情风流,虽更能符合观众内心对宝玉形象的期待,但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内容,只是很机械地通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来展现人物性格以及内心世界。剧中大量的旁白也使观众的注意力并不完全在人物的演绎上,而是兼顾多方面来对人物性格以及内心世界进行理解。
二、林黛玉
林黛玉,一个才华横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曹公深爱他笔下的林黛玉,爱她的笑和泪,爱她的喜与悲。她美丽才高,不为世俗所容。她的外貌体现了她多愁善感的个性与诗人般高贵的气质,更体现了悲剧之美。黛玉与宝玉一样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批判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的话来劝宝玉,因而被宝玉视为“知己”。
87版《红楼梦》是大家公认的经典,这主要归因于已故的演员陈晓旭把林黛玉表现的生动而贴切。她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对林黛玉骨子里的精神的阐释。林黛玉特有的柔弱美、病态美,被陈晓旭演绎地淋漓尽致,她那似喜非喜、深情凝驻的眼神;她那柔情似水,忧郁细腻的表情;她那纤纤瘦影,楚楚动人的体态,无一不撩动着观众们的心。但缺乏些许对林黛玉内心的表达,影响了人们对黛玉的全面认识。
新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表演清淡如白开水,表情言谈起伏都不大。她的眼神没有内容,只能通过两行清泪来表现黛玉伤感忧郁的气质。虽没有太多的表现,但好在自然平稳。
三、王熙凤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塑造的一个很成功的反面形象。她生性尖酸,个性泼辣。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弄权作势,两面三刀。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阴险的阶级本质。但不可否认的是,王熙凤确实很能干,荣府上下大小事务都由她说了算。凤姐的性格,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又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87版《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由邓婕饰演。因邓婕具有四川人特有的泼辣味儿,与王熙凤的俗称“凤辣子”相吻合。她所扮演的王熙凤,丹凤眼,柳叶眉,俊俏之中透出狡猾之态、刁钻之貌、凶狠之气。因其曾学过川剧,举手投足之间都有浓厚的戏曲痕迹,所以扮演的王熙凤一角俊美中带着成熟与干练,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邓婕说:“演《红楼梦》不光靠一张脸,还要熟读《红楼梦》,热爱《红楼梦》,勤学苦练,别无他径”。
新版《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由外形漂亮乖巧,气质温顺平和的姚笛扮演,饰演钗黛二角都颇为合适。她所饰演的王熙凤表演痕迹较重,感觉吃力,缺了点“辣味儿”。没有完全展现凤姐的阴险狡诈、八面玲珑的特点,生气时怒目圆睁的样子倒多了几分可爱,似乎有些驾驭不了王熙凤这个角色。
87版《红楼梦》上演后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剧中的演员将原著人物演绎的活灵活现,几乎达到了与原著人物神韵合一的境界,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而在新版《红楼梦》里,演员扮相戏剧味十足,但表演相对平淡,大量的旁白和配乐的运用,分散了人们对表演的关注度。翻拍旧剧现已成为潮流,旧版经典剧作给观众带来的审美惯性,以及现代各方面技术水平提高的条件下,新剧在真正拍摄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忠实原著人物、升华原著人物并超越旧版人物塑造这一大挑战。
参考文献:
[1]姜维枫.试论《红楼梦》影视剧改编中对黛玉性格的把握[J].红楼梦学刊.2009(5).
[2]重拍电视剧《红楼梦》的讨论[J].红楼梦学刊.2002(3).
第8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 饮食生活 清朝贵族
中图分类号:K8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3-
一、引言
中国饮食之讲究精细者莫过于历朝历代的宫廷与贵族们,烹饪技艺也在当权者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过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清代是封建官僚体系之集大成者,它沿袭并发展了前代奢侈的贵族饮食生活,而红楼梦正是描写盛清时期当权者们的腐朽奢侈生活。
二、红楼梦中的饮食描写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总所周知,《红楼梦》中主要描写的金陵望族的贾府,里面的重要人物如贾母、宝玉、黛玉、宝钗和王熙凤等人个个娇贵无比,他们的饮食生活真可以说是穷极奢华。
写吃,《红楼梦》是最特殊的一部。这部书中写吃喝,不仅用的笔墨多,而且精彩,全书中写了多次筵宴,含意深刻而又意趣横生,在写吃喝的笔墨运用上,也是独一无二。
第三十四回中,宝玉被打了个半死,躺在炕上不能动弹。袭人到王夫人屋里去禀报宝玉的伤情,王夫人叫带回两瓶香露去给宝玉吃。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而这两种饮料,均向皇帝进宫过,可见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高级饮料。王夫人问想吃什么,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么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儿小莲花儿的汤还好些。”贾母听到,便一叠声地叫人做去。莲叶羹,论用料,并非最贵重,费的工夫,也不算最绝。然而,用薛姨妈的话说“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
再看第四十九回,作者用很多笔墨,写那些侯门小姐围在一起烧烤生鹿肉吃,津津有味,亦兴致勃勃。这个情节写得十分精彩。吃,是为了填饱肚子或者是为解馋,于这些人都已是不相干的了。他们此举都不是口腹之需,而只是好玩,于吃中表现的,是一种情趣。第八回中写到,薛姨妈进京宝玉去看望,姨妈留饭,除拿出糟鹅掌鸭信等南方风味的菜肴招待,还做了酸笋鸡皮汤,宝玉大喝了两碗。酸笋是西南地区各省人民喜欢吃的一种素菜,不但在京城是罕物,即使在江南也是不多见。由此可见,红楼中贵族的奢华生活。
贾府的奢华可以从《红楼梦》情节上体现出来。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贾母命熙凤用茄鲞喂她。姥姥吃了两口,味道甚佳,便请教说:“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可谓贾府的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无独有偶,有一天宝玉问晴雯:“今儿我在那府里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奶奶说了,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别提。一送了来,我知道是我的,偏我才吃了饭,就放在那里”。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给我孙子吃去罢。”她就叫人拿了家去了。一碟子豆腐皮包子何以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原来这种包子不寻常,远非肉包子可比。其高贵之处首先在于豆腐皮的制作特殊,首先将做豆腐的原汁豆浆煮沸,不加凝固剂,使之冷却,漂浮在锅面上的脂肪和蛋白质会结出一层皮来,然后把它挑起晾干,才能得到一张豆腐皮。
《红楼梦》中,粥饭和菜肴种类繁多,如粥有碧粳粥、鸭子肉粥、枣熬粳米粥、燕窝粥、红稻米粥、腊八粥和江米粥等。饭有白粳米饭、碧粳粥和绿畦香稻粳米饭等。《红楼梦》中的菜肴,主要有腌胭脂鹅脯、酒酿蒸鸭子、糟鹅掌、火腿鲜笋汤、酸笋鸡皮汤和虾丸鸡皮汤等等。汤羹种类繁多,营养价值丰富。而且从饮料方面看,红楼梦中提到的也是数不胜数。在茶方面,提到的就有两百多处。
《红楼梦》对贵族家庭尤其是贾府的饮食生活作了传神细致的描写,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独特的《红楼梦》饮食谱。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期,正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中国的饮食文化再“康乾盛世”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城市中北销南运的小商摊贩人来客往,酒店、茶楼鳞次栉比,形成了风味殊异、各具特色的贵族们的饮食文化。
三、清朝贵族对饮食的要求
饮食,往往蕴涵着中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借吃这种形式,表达了丰富的心理内涵,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的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是社会意义。
清朝贵族们对饮食要求特别严格。从造型上出发,到原料加工上,从味道到意趣,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为了口味得到保证,烹饪菜肴除了注意严格的选材之外,在烹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精细加工,特别是火候和口味,都有严格的标准。而且每次烹饪的肴馔,经常要将使用的原料和调料记录,菜肴要“色香味形”俱全。经分析,主要五个方面的讲究。
一是讲究奢侈。贵族们既有山珍海味,又有天底下的稀世珍品供品尝,可以说是汇集了天下美食,奢华之极令人瞠目结舌。
二是讲究精细。贵族们的饮食追求精致、精美,为了满足生活上的享受,他们对饮食的外在要求也及其高。
三是讲究味道。味道是饮食重要标准,贵族们的饮食讲究口味的独特性、多样性、丰富性。
四是讲究营养。营养是饮食的前提条件。贵族们的饮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饮食营养,保证贵族们的健康体魄。
五是讲究意趣。“意”用今天的话理解就是“意味”之意;“趣”,情趣也。“意趣”主要指心灵活动的内容。
贵族们不仅享用着精致、奢华的佳肴珍馔,而且特别注重在吃的过程中,受用无限意趣,以获得更多的精神愉悦。
四、结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此这般居上位者享尽富贵,居下位者吃尽苦头。本文通过描述荣国府过的如何奢华、如何豪贵的生活,展示了清朝贵族们的奢华生活,分析了他们对饮食的奢侈要求。在这奢华豪贵背后,间接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凄苦生活。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8年版.
[3]徐悦.红楼梦中的养生术.科学之友.2008(6).
[4]金兰.近三十年红楼梦饮食文化研究综述.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8(4).
第9篇:红楼梦人物性格分析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主义;分析
【分类号】I207.411
1 独特女性意识
《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是在清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显示出一片平和的景象,女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始觉醒,这一现象往往反映在各类文学作品里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表现。受宋明理学中思想家王阳明著名“心学”的影响,众多学者纷纷开始为女性抱不平,文学作品中纷纷显现出诸多女性意识突出的女性角色。传统理念中关于女性一直是一个附属品的存在,人们忽视女性自身的追求,罔顾女性自身的优秀品质,无视女性对于社会作出的种种贡献。对于女生的歧视无论是裹脚还是三妻四妾制度,都严重压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期间,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凭借其独特的创作手法融合了传统文学以及当时较为先进的创作理念,塑造出一个个融合实际的性格鲜活的人物角色,赋予了小说新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将当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巅峰。
首先,《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代社会中男权政治的霸权统治,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生活现状,进而表现了女性在传统思维禁锢下,三从四德等腐朽意识的捆绑下,不甘被奴役、被统治、被封闭的现状,力求冲破当代封建思想中男权统治的堡垒,充分寻求自身价值,张扬女性个性,施展女性抱负的女性意识。
2 对女性的崇拜思想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惊世骇俗的女性崇拜思想与历代小说中女人祸水论大异其趣。《红楼梦》中所塑造的那种至纯至美、灵透唯美与清新圣洁的众多女性形象也是其他小说都无法模拟与超越的。《红楼梦》对女性才智的赞美讴歌颠覆了刻板教条,超越了世俗功利,完全是精神性的、对性灵的抒写和象征性的表达,真正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可谓境界出新、立意出新。可以说,《红楼梦》改写了中国主流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缺席的状况,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尊重女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然,《红楼梦》中的女性观绝不仅仅停留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迫切要求女性解放这一观念上,而是上升到启发引导女性自尊、自爱、自信,拥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人性角度。它极力赞美女性,否定了父权制的道德准则,讥讽了男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世间的污浊,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女性独立形象的审美缺席现象,也继而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社会价值。此外,《红楼梦》中作者最钟情的女子是林黛玉,这位绛珠仙子贵情尚真,“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可以说,她的重情和真实被作者视为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3 女性悲剧制度文化
本质上来看,《红楼梦》的女性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很多的文学家们试图揭示悲剧的本质,也都有过精辟的见解,代表人物有尼采,在他看来,希腊的艺术兴盛正是来自希腊人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大文豪鲁迅也认为,悲剧的本质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们其实都赞同悲剧实际上就是再现人生的毁灭,和西方不同的是,悲剧没有降落到强大的男性身上,而是由弱小、可爱的女性来承担,这又是何等的国家的悲剧。
《红楼梦》中女性悲剧的空间载体,内容及形式都不同,例如,迎春悲在家中,妙玉悲在庵中,林黛玉有爱无婚姻,晴雯等又展现了底层人的悲剧。实质上,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类似。上至贵妃,下至仆人,她们上演着感情、政治、家庭、文化的悲剧,共同编织出国家的悲剧,最终结果也只有自取灭亡。
曹雪芹对女性悲剧描写的淋漓尽致,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连带引发国家、社会悲剧的思考。表面上看,小说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实则描述了四大家族的悲剧,进而引出民族与国家的悲剧本质。只有细细品味,才能窥探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在看似盛世的朝代,清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灭亡的危机,只不过众多的女性担当了这个社会、民族的牺牲品,是国家悲剧的开始。然而,最可悲的是,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末日中天,反而乐在其中。小说中描述的很多女性都很优秀,实际上越是这些优秀女性被毁灭,越是体现了小说的悲剧价值,悲剧的思想也越是明确,越是引发人们的思考。
4 女性主义写作策略
可以说,题材的私人化是女性主义写作策略,而这一特征又鲜明的表现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从女性角度出发,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遮蔽已久的女性生活状态,进而把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价值等同于崇高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传达出日常生活才是人类生存本质的女性化概念。例如,第七回,周瑞家的给各位小姐送官花,迎春和探春在下棋,惜春和智能一起玩笑,黛玉和宝玉在解九连环;二十一回中,描写了宝玉一早来看望湘云、黛玉,湘云为宝玉编头发。这些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描写地细致入微。而《红楼梦》对人物的塑造,就是在这生活的描写中表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红楼梦》的旷世之处,不仅表现为历来被世人所仰慕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令人惊叹的是其突出的女性崇拜情结。它撇开“女性为祸水、为贱类”的偏见,公开地赞美女性、歌颂女性。这样的诗意表达既区别于历代小说,同时也在价值上独占鳌头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珍贵清奇的宝玉。值得我们品读学习。
参考文献:
[1]翁礼明.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J].江西社会科学,2004,09:127-130.
[2]李玉靓.《红楼梦》译本的女性主义色彩[J].青年文学家,2013,01:154-155.
- 上一篇:教师精准扶贫帮扶范文
- 下一篇:农村婚庆典礼主持词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