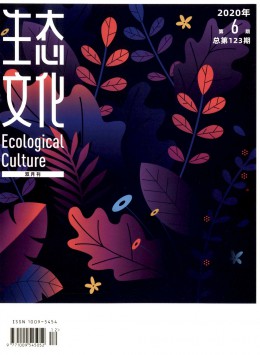文化混杂在现代白话文中的作用

摘要:清末至“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无论在语言层面还是在文化价值层面,都是一种混杂的文化行为。只是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以“归化”或“异化”的方式,强调了某一方面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文化混杂”的翻译实践为白话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而且由翻译带来的文化重构,为白话文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气候。
关键词:翻译文学;归化翻译;异化翻译;文化混杂;现代白话
一、“本色化”的基督教翻译文学
除了作为基督教传教蓝本的《圣经》,英国作家班杨的《天路历程》也是流行世界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为面向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传教布道,《天路历程》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方言本与官话本,其中都使用了“本色化”的翻译方案。所谓“本色化”,就是“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变迁的过程”[3]2。1865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Muirhead)在北京重译的官话本之所以成为“最流行、影响最广泛的白话译本”[4],与其通俗的“本色化”翻译方案不无关系。第一,宾威廉保留了自己在1853年翻译的文言本图案,从人物到背景,把富含西方基督教含义的图画替换成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元素图画;第二,更重要的是,此版本的语言载体是中国北方地区广泛使用的官话白话;第三,译者在每卷结尾处都用俗话、白话自行创作一首带有基督教劝勉性质的诗歌,总结说明此卷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创诗歌和来自原文的译诗,除有少量几首遵循了中国古诗的格律规则,多数诗歌摆脱了中国古诗规范的窠臼,属于典型的欧化白话诗。例如,在1866年《续天路历程官话》中出现的译诗片段,已和“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十分相近。整体来看,《天路历程》的官话白话翻译是一种归化翻译,而这种归化翻译从语言形式到图画等副语言形式都混杂了许多异质因素。与其说宾威廉的“本色化”翻译造成了文本变迁,倒不如说是由于“文化旅行”而造成了一种“文化变异”。这种“变异”,既不同于源语文化,又有别于目的语文化。这种“文化混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源语文化的意义。无论是官话白话的使用,还是混杂出现的欧化词汇和句式,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向文化程度不高的受众传播基督教教义,这也在客观上丰富了白话文现代化的资源。
二、严复和林纾的“归化”翻译
在语言形式方面,严复和林纾的翻译都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归化翻译,但二者的“归化”却有许多不同之处。翻译内容上,严复虽不是以翻译文学著称,但是他翻译了震动中国思想界的《天演论》,在翻译理论方面,他倡导的“信”“达”“雅”成为影响翻译文学至深的诗学原则。就“中学”而论,严复博得美名离不开其古雅的桐城文风,其译著《天演论》取“雅”而舍弃“信”和“达”。从严复和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通信上看,严复曾反复谦虚求教于吴汝纶,请其修改《天演论》文稿。严复此举的目的在于顺应其目标读者———士大夫阶层的阅读口味。耐人寻味的是,也许是受佛经翻译的影响,对西学知之不多的吴汝纶却对翻译的“异化”规则颇为熟稔。严复对《天演论》中来自西洋古书的引喻做了汉语归化处理:“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5]1413。对此,吴汝纶则强调异化处理: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占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故非赫氏所及知……[6]1560严复显然接受了吴汝纶的建议,但对于汉语没有对应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术语,严复既没有保留原著词汇,也没有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而是采取了仿照原文自造新词的“异化”策略。严复拒绝使用当时比较流行的日译词汇,而是自创了许多新词,但现代汉语中却很少保留下来。吊诡的是,严复眼中的“西学”近乎完美,但他却用“归化”桐城古雅文风的译笔来译介异质性的西方思想学说,这点看似十分矛盾。而胡适对严复的这种翻译策略解释为“不得已的办法”:“当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7]115。另一方面,严复未经科举,一直未得朝廷重用,在以科举取士、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封建中国,这无疑是严复的一大心病。由吴汝纶书信观之,吴对严的境遇颇感不平:“以执事兼总中西二学,而不获大展才用,而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事”[6]1560。因此,严复的古文翻译有以桐城文笔博取士大夫阶层赞许进而通过社会高层传播社会思想学说之嫌。简言之,严复的“归化”翻译只是在文体形式上借用了符合中国古典诗学原则的桐城文笔,其真意却在于推行异质性的西方社会思想学说。虽然严复的“天演”思想在上层建筑的深层结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巨大影响,但也只是在文化环境上为现代白话文的深化创造了条件,其译词并没有丰富白话语言。林纾的“归化”翻译在文体形式和内容上显然不同于严复的翻译。首先,在文体形式上,由于林纾本人不懂外语,对于原文的理解主要依靠口译中介人,所以,他的翻译近乎是一种以文言改译的创作活动。虽然林纾不排斥直译的方式,但他的译文经常意译、译述结合甚至有大幅度的改译、改写,对原文的偏离之处,远远多于严复的翻译。林纾关注的重心显然倾向于译本,这也给了他发挥文言文笔功底的空间。他的翻译不只是简单顺应文言文故有的语言规范,而且创造性地发挥了文言文的简洁和动感之美,略去了西方文字笨重呆滞、繁文缛节。有时不免有所误译,成为新文学精英诟病之处,但并不能掩盖林纾古文翻译的精彩。例如,以“惟以此衣上渔夫,其状当奇劣,然思之未敢出口”[8]19对照原文,便会发现,林纾行文之简,令人称奇,英语短句Imustacknowledge(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仅以“当”字表达。不可否认的是,林纾的创造性翻译屡屡流露出欧化语法挑战和冲撞文言文故有句法的痕迹,新文学话语叙事在挖掘白话语法资源的时候却忽视了这一点。其次,与严复传播西方思想的翻译不同,林纾向国人介绍泰西文学,以改造本土文化为目的。他的归化翻译经常是对原文进行节略、改写、增衍,不但以中国古典小说的体式和语言来归化和改造西洋小说,还常把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社会伦理比附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这种由文化价值观念上的混杂而导致的翻译严重变形,显然是受到了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实学”翻译的影响。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利时学者AndréLefevere指出,导致文学翻译改写的诗学原则之一是翻译作品的主题必须和目的语的社会价值系统相关[9]26。林纾以本土文化“孕化”西洋文化,致使很多爱情主题的小说带有中国传统道德色彩,这种文化变体兼具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体验。简而言之,一方面,严复的“归化”翻译以高雄古雅的桐城派文言文为语言载体,意在向主流文化精英传播异质性的社会学说,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认知,为白话新文学的成长作了文化铺垫;林纾的“归化”翻译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以古典传统文化为中心,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将西方的文学观念悄然地植入读者脑海,从观念上改变了国人对小说的偏见,为新文学造就了准读者和作者。另一方面,严复和林纾的“归化”翻译混杂的“异化”成分,诸如直译外来专有名词、自造新词、欧化句法的使用等,为白话的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也是值得重视的。
三、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翻译
的失败让维新派精英认识到政治重构必须从启蒙大众做起,而文学是社会启蒙的利器。为改造国民性,尽快提高国民政治意识,达到“新民”之目的,梁启超把译印西方政治小说作为文化参与政治介入(PoliticalEngagement)的首选。他把《译印政治小说序》作为他翻译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序言,以欧洲各国及日本为例强调政治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彼美英德法奥意日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10]172。以翻译政治小说作为“新民”的手段,就要使用大众的语言。晚清民初,由维新派提倡的“诗界革命”“新文体运动”及“小说界革命”等白话运动初见成效,各地已出现通俗文体的白话报,这为白话翻译政治小说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梁启超于1898年在《清议报》第一期开始连载自己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接着又翻译《十五小豪杰》并连载于《新民丛报》2卷24号。这两部小说都使用了杂糅部分文言的通俗白话,这在当时主流文化仍以文言行文的背景下,属于难能可贵的“异质”翻译行为。《十五小豪杰》(转译日本作品)的前4回采用了白话翻译,《佳人奇遇》整篇用半文半白的俗话翻译而成。但这两部翻译小说通篇都间杂着文言赋诗,人名地名也都以中国本色的词汇创制。《十五小豪杰》在体式上还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翻译的方式上,这两部小说以意译为主,翻译中附有作者评论或长段注解。与严复不同,梁启超受到日本文体改良的启发,认为由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是文学进化的一大关键,他翻译这两部政治小说,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为了白话文写作实践。对于核心的政治词汇的处理,梁启超直接使用了许多日本翻译的西方词汇,诸如“社会”“议院”“自由”“权利”“国家”“国民”“立宪”等等。这些词汇有些原本是日本从中国古代汉语中借用,但再次引入中国的译作之中,经过跨界旅行,已具有现代含义。不难看出,“议会”“权利”“自由”“民政”“独立”等词汇,表达了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情怀。小说还常以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影射当时的满清社会,这种带有类比性政治重构的翻译,和林纾以儒家道德、忠君思想来“孕化”西方社会伦理和人文传统的“归化”翻译是截然不同的。整体看来,梁启超采用了文白夹杂的语言、章回体格式等“归化”手段来翻译政治小说,以争取底层社会的读者,以利于宣传民族独立和君主立宪政治构想,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新民”目的。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翻译不仅开启了白话翻译小说的先例,还带动了社会谴责小说、虚无党小说以及鸳鸯蝴蝶小说的写作高潮,为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他的“归化”翻译是一种混杂了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变异文本,他翻译的政治小说常以书中的西方或日本社会与当时中国社会做类比,实际上是把西方的政治观念做了本土化处理。这一点也体现了“新民”的政治教育以本土文化主义为本位。学习西方列强的政治文化正是为了改造国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摆脱西方的侵略和控制。
四、《新青年》的“异化”翻译
无论出于何种翻译目的,清末的翻译文学都出现了以中国本色文化“孕化”外来异质文化的倾向。“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则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学翻译,在语言载体、翻译选材、翻译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以“异质性”的策略表现出“新”的面目。首先,最有特色的是,新文学精英借“《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⑵,文学启蒙是从用白话翻译入手的。《新青年》之所以占据了白话文运动开风气的地位,是因为其无论是在理论建设还是在白话实践方面,同期其他杂志都是难以超越的。同时期的《东方杂志》等刊物也刊载了文白夹杂的文学翻译,但这些杂志都没有提出白话文改革的理论性口号。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义》发表以后,陈独秀才充分认识到白话文乃为文学革命必要部分,并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此二文是白话文理论建构的革命性纲领。理论摸索的过程中,陶孟和与钱玄同提议《新青年》模仿留美学生主办的《科学》杂志,采用“左行横迤”排版格式、采用西式标点和句读、模仿欧式句法的主谓宾结构,这些建议都被陈独秀采纳。与清末的文言翻译相反,这种异质性的白话翻译以“差异”挑战以至颠覆故有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带有强烈的破坏性。意大利后殖民文化学者LawrenceVenuti指出,原文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通行的文化原则才能存活⑶。用语言来表现差异,以胡适、陈嘏、刘半农和周氏兄弟等为代表,他们是《新青年》白话翻译的重要践行者。胡适用白话翻译了俄国作家泰莱夏甫的小说《决斗》,此译和陈嘏用白话翻译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弗罗连斯》一同刊载在《新青年》2卷1号上,掀起了《新青年》白话翻译经典的热潮。需要注意的是,《新青年》的文言翻译文学要远远多于白话翻译,即使是白话翻译也经常是文白间杂,其他栏目的文章基本都使用文言文。以刘半农的白话诗歌翻译为例,译诗混杂了大量的文言词汇,也常借用古典诗词格律及体式,文言味道比较浓厚。如:“我昔最惧死,不愿及黄泉。自数血战绩,心冀日当天。日当天,血腥尽散如飞烟。”[11]其次,直译是《新青年》翻译的又一“异化”特色。意译曾是林纾和梁启超青睐的手段,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认为:“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12]50意译和直译关系到翻译的“通顺”和“忠实”,为“忠实”采取直译,有时就要舍弃“通顺”。《新青年》的读者张寿朋对周作人直译诗歌颇有微词,认为胡适译诗符合读者预期,而周作人译诗“中不像中,西不像西”⑷。读者难以接受风格迥异的白话译诗,体现了时代的诗学原则对读者欣赏水平的限制。周作人在给读者的回信中批驳了清末翻译的“融化”之说,认为翻译最好“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⑸。直译是造成偏离主流诗学系统的异化方式之一,“译文越接近原文的措辞,对读者来说就越显得异化”[13]129。周作人的直译正是通过竭力保留源语言的词句顺序,造成对目的语主流话语文体的偏离,对抗主流话语的“归化”翻译,进而达到改造目的语文化的效果。再次,选材之“异”。《新青年》的选材经历了从翻译“欧洲经典”到“弱小民族国家”文学作品的过程。1915年11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3号、4号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倡议以翻译世界大文豪的作品进行思想启蒙。创刊之初的《新青年》翻译了许多经典作品。但是,从4卷开始,《新青年》展现了自己独有的特色,杂志的翻译和创作都明显转向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弱小民族”的作品。据赵稀方统计,自4卷1号至9卷4号,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弱小民族”文学16种,俄国作品8种,鲁迅翻译俄国作品2种[14]225。施莱尔马赫认为,“异化翻译的首要机会出现在外语文本的选择上,译者可以通过翻译那些遭到排斥的文本,在英语中重构外国文学律典,抵抗英美文化中的主流话语。”[15]129同理,《新青年》通过选择当时主流文化认为比较边缘的“弱小民族”文学,不仅影响了杂志自身的翻译选材,而且引起了中国文坛在1920年代翻译俄国和“弱小民族”作品的热潮,在文化重构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小说月报》在沈雁冰的倡议下,1921年出版了“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东方杂志》与《新青年》论战后,于1920年开始改版,也翻译了大量俄苏作品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述的各种异质性翻译,都可以看作《新青年》翻译文学对“陌生化”手段混杂的运用。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把“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解释为:“要审美主体对受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支持的习惯化感知起反作用……使审美主体即使面临熟视无睹的事物时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感……”[16]339《新青年》翻译文学运用“陌生化”手段首先表现在其语言注重传达“异国情调”(Foreignism),挑战读者熟知的文言审美体验。例如,杂志从1卷至3卷英美文学作品和部分非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现的;翻译作品中常混入不做翻译的外语词汇,甚至有的文章题目直接是外语。其次,《新青年》翻译文本的“陌生化”还经常表现在古语、白话文、源语言、造词的混合运用。以诗歌翻译为例,上文刘半农的译诗就是混合了古词、新词、半白半文语言、格律诗的体式、英语对照格式的变异体;陈独秀翻译的美国国歌《亚美利加》[17]则使用了文言古体诗的形式,以文言为主、混杂白话新词、配有英语对照。总之,这种“陌生化”的文化变体的文学翻译,以“异质性”的语言、文体形式和价值主题,挑战了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体验,为白话文的现代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五、结语
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在巴赫金“复调”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引用了生物学词汇“混杂性”或“杂交”(hybridization)来研究殖民地国家的文化混杂。但他本人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明确定义,DavidHuddart将霍米•巴巴的“杂交”理论总结为“混杂性是说不同文化间不是分离迥异的,而是相互碰撞和交流就导致了文化上的混杂化”[18]114。清末至“五四”期间,中国输入外国文学的个体经验当然不同于后殖民话语中第三世界国家文化殖民经验,但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概念,对翻译研究却不无启示。用“归化”或“异化”翻译来定义清末至“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只是体现了翻译强调了某一方面的文化价值倾向。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在文化价值方面,各个时期的翻译都体现了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混杂。综上所述,翻译行为不是一种单纯的“归化”或“异化”,而是一种混杂的文化行为,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强调的文化价值不同。清末至“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不只是在上层建筑的表层———字、词、句、语法等语言层面为白话的现代化提供了必要资源,更重要是在上层建筑的核心层———翻译所强调的文化价值层面,为白话文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作者:侯杰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 上一篇:艺术院校单簧管乐团的组建与训练范文
- 下一篇:诵读法在辞赋文学教学中的作用范文
相关文章阅读
精选范文推荐
- 1文化与乡村旅游
- 2文化与传播论文
- 3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
- 4文化与历史的关系
- 5文化与城市的关系
- 6文化与广告
- 7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
- 8文化与旅游
- 9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 10文化与艺术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