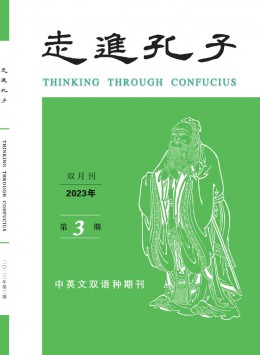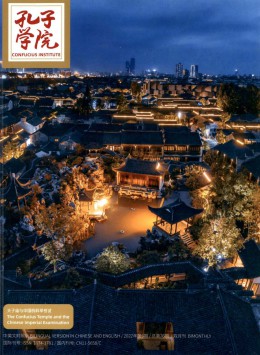孔子删诗说精选(九篇)
第1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关键词:张西堂;《诗经六论》 ;学术价值;历史局限
张西堂先生(1901~1960),关于《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诗经六论》 这部书中。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说明了《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府总集,讲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诗经》的编订、体制,还有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关于《诗经》的著作不是很多,《诗经六论》被当作进行《诗经》学习和研究的必读书目。现在随着对《诗经》不断深入的研究,这六篇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似乎已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如站在作者发表的那个时代来看,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从我们现在研究《诗经》的角度综合来看,其研究成果也不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本文拟从这六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角度,对其加以介绍和说明。
一、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学术价值
《诗经》是中国的乐歌总集。张先生从一般诗歌的起源,诗三百篇的采删,风歌之绝非徒歌,古代歌舞的关系,古代“诗”“乐”的关系来证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并用《墨子・公孟篇》中“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来说明先秦的人认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全都可以弦诵歌舞。此书中说《诗经》是中国先秦以前的乐府。认为其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来自各地民歌。张先生列出了其认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的四个理由,并依次做了说明:
首先,由诗三百篇的收集看来,他用孔子“反鲁正乐之时,年以六十有九,而钱此言诗,皆为三百”说明诗不是孔子所删。诗三百篇应当是经过最有关系的乐师的搜集或被以管弦或变为
乐歌。
其次,由风诗之绝非徒歌看来,张先生分了四层来说明,墨子《困学纪闻》十说中,风诗文体最近于二南,与大小雅相似,风诗的“风”只可释为声调,《论语・灵公篇》从旧曲的流传,风诗的体制和声调的意思,与所谓郑声之乱雅,都足见风诗并非
徒歌。
再次,从古代歌舞的情形来看,古代社会歌与舞是分不开的,张先生分别从古代的乐舞,歌舞,歌诗,乐器四点来说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
最后,由古代“诗”“乐”关系看,古来“乐”本无经,所以乐歌就是诗。张先生认为,只要这四个理由有一个成立,都足以证明《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我们现在都认为《诗经》时代是诗乐舞一体的,这就说明诗三百的确是一部乐府总集。从春秋时期人们的用诗情况就能证明这一点。张先生关于《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虽然不是他的创见,但经过他的论证分析,其观点更可信。张先生采用引用举例的方法对《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去认识,了解《诗经》产生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了解研究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也能更加清楚《诗经》并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人的作品。
针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张先生认为其理论依据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最深的根源应该出自广大群众的最底层”。 因此他着重分析风诗。张先生把《诗经》的思想内容分了四类“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关于恋爱婚姻的诗歌”、“关于政治讽刺的诗歌”、“史诗及其他杂诗”。立论基础是阶级性和人民性,尤其强调人民性。他认为《七月》最具有人民性,而《良耜》是毫无人民性的。在对政治讽刺诗进行分析时,张先生还提出《风》主要是来自劳动人民最底层。在提到《召南》的《甘棠》,《卫风》的《淇奥》时,张先生说“这些诗所歌颂的人物必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物,所以不管他们是封建领主或是士大夫阶级,歌颂他们的诗得以流传至今日”。可见他不仅是强调其人民性,同时对诗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是可信的。张先生列举了大量的《诗经》作品,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通过微观分析来剖析《诗经》的内涵,后世许多文学史都沿用了这种抉微入里的分析方法。
在对《诗经》的艺术表现的研究中,张先生从“新的文艺理论及名额表现方法的角度来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分为八项:
一、概括的书写,
二、层叠的铺陈,
三、比拟的摹绘,
四、形象的刻画,
五、想象的虚拟,
六、生动的描写,
七、完整的结构,
八、艺术的语言。
对于一些思想性强的诗,如《七月》等诗也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分析。并引用汤姆生的《论诗歌源流》,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考虑《诗经》的层叠铺叙。在形象的刻画和想象的虚拟两部分中,引用了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说法并与唐、宋诗词做了说明及对比。关于《诗经》的篇章结构和修辞格等也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引用郑玄,挚虞,孔颖达,朱熹,郑樵、姚际恒等人的说法,来说明“不应当将赋比兴也当作诗体”。他认为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写作方法,比是用另外一种事物作比拟譬喻的写作方法,兴是即兴的唱出。兴而比就是比,兴而赋就是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对赋比兴的定义基本上是与张先生一致的。在这八项艺术表现,张先生每一项都举了几首诗,都做了详细的阐释。并从修辞学,典型形象,结构特点等角度进行分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确实是一种很难得的新方法。
在《诗经》的编订问题上,张先生主要讨论了采诗说和删诗说。张先生从旧说开始一一进行辨析。关于采诗说,张先生列出了古籍所载的八种说法,从《礼记王制》到《文选三都赋序》,都说有采诗之事而采诗之人不同,甚至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都不一致,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张先生认为:“采诗之官,古时固然没有,然而搜集当时诗歌的却一定另有人在,这应当就是当时的太师,其后以讹传讹,才发生了巡行采诗等等臆说。”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张先生列举了赞成删诗说和反对删诗说两种观点。张先生对这些观点加以抉择、剖析和论证。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朱彝尊已指出“取其可施予礼仪”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毫无可疑的。张先生又用《桑中》等诗不可施予礼仪,却没有被删去,进一步说明《史记》的说法不可信。由此,张先生得出结论,现在流传的《诗经》,本是当时乐师采集入乐的乐歌,在孔子时,它在合乐演奏的过程中就已经编订流传,不是孔子编订的。关于孔子删诗说,张先生也持以反对意见。
对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主要讨论的南、风、雅、颂的定义和区别。张先生认为“南”应当从《风诗》中分出来。他举了六种对“南”的定义,甄别之后认为:“南”是一种曲调,是南方之乐,由一种乐器而得名。关于“风”张先生共举了十二个说法,从《毛诗序》到顾颉刚,他比较赞同“风”是一种声调。后来的学者都赞同张先生这种说法。关于“雅”张先生举了七种说法,他自己比较赞同“雅”也是一种乐器,大小雅可以从音来区别,他不赞同“诗之正变”之说。关于“颂”张先生认为《颂》之声较《风》《雅》较缓,且与一种叫做“”的乐器相关,也因此得名。张先生的结论是这四者皆因音乐而得名,其体制就是以音乐为诗的形式。张先生对《诗经》体制的研究紧扣音乐二字,说明了其立足点是正确的。南、风、雅、颂是乐调,大体上也为大家所认同,当然他认为南、雅、颂为乐器,似尚可商榷。然谓“颂”即“”即“钟”还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张先生赞同《释文》中取消大、小序的说法。针对《毛诗序》的作者,张先生列了十六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驳斥。为了证明《毛诗序》之谬妄,张先生将前任的说法归纳为十点:①杂取传记②叠见重复③随文生义④附经为说⑤曲解诗意⑥不合情理⑦妄生美刺⑧自相矛盾⑨附会书史⑩误解传记。张先生这些材料和观点,有力的批驳了《毛诗序》,给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启发。关于《毛诗序》是否村野妄人作,还有待讨论,张先生所列材料已经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有利于后人的探索。
这六篇论文中,张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的的传统,用了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在关于孔子删诗说,诗经的体制、《毛诗序》的作者等都用了罗列比较法,先罗列历代有影响力的说法,进行梳理分析,对各家说法提出意见,最后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以诗证诗法,张先生说“以诗三百篇证诗三百篇”“以本经证本经”。在分析“南”与“风”的不同和“说雅”中都用了这种方法。从《诗经》文本中寻求解释和答案,避免了随意曲解,很值得我们学习。张先生这种朴实,严谨。扎实的学风,是我们后代做学问应该学习的。
二、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历史局限
张先生这篇论文可能是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品尽可能的用“人民性”作为其理论武器,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张先生用了新的文艺理论和方法来对《诗经》的作品进行分析,这是很可贵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理论界特别强调古代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一片文学作品的标准。把人民性作为研究《诗经的思想内容》的标准是基本没有错,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理论之中。如《良耜》、《鸱枭》,如果只用这个理论就给它们定性的话,似乎有些偏颇了。由此可见,张先生在使用新理论上还是比较生硬的。
同样还有“典型形象”的理论。对“典型形象”的理解也是过于简单的。与孙作云先生有关《诗经》的研究相比,就可以看出区别。孙先生除了用传统的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音韵学进行考证以外,也用了大家已经熟悉的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的方法,在用这种新方法时也不给人生硬感。
参考文献:
[1]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
[2]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
第2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关键词:《关雎》 思无邪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关于《诗经》的形成,说法不一。有“王官采诗说”,有“孔子删诗说”。按照后一说法,《诗经》是孔子从先秦三千多首诗歌中删减编撰出来的。我倒是愿意相信后一说法。这似乎为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找到某种逻辑。孔子在《论语 为政》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就是说诗歌的思想要纯正,也就是没有邪念、没有杂念。孔子究竟是在什么语境里说出了这番话,我们无法知晓了。按照“孔子删诗说”,我们不妨做如下推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老师,“诗三百”是怎么删减出来的?孔子回答:以思想纯正为标准,“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也就是说,“思无邪”是孔子删诗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被收录进了《诗经》,不符合的不予收录。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孔子把它放在《诗经》篇首的用意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关雎》是“思无邪”的最好例证,那么,《关雎》是怎样体现“思无邪”呢?
我们先来重温这首两、三千年前的爱情诗,看看它是怎样体现“思无邪”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d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不用怀疑,这是一首爱情诗。但却不是爱情当事人写的爱情诗,而是作为第三人的诗人记录下的一对男女青年的求爱场景,如同一位高明的摄影师拍下的一组“凤求凰”的动人场景。
首先,诗歌开篇就创造了一个热烈激昂而又温馨纯美的意象,为诗歌主旨的表达做了一个很好的艺术铺垫。整个故事都是在“雎鸠”的爱情奏鸣曲中拉开序幕的。象大雁、天鹅一样,雎鸠也是一种爱情鸟。自然界中似乎只有鸟类的爱情符合人类爱情观。那就是两情相悦、彼此爱慕、终生厮守。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写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为什么他不在地面上找一种动物来象征爱情呢?因为在鸟类之外,他实在找不到另外的动物可以用来表征人类的爱情。狮子老虎行吗?显然不行。老虎是独行侠,遇上谁就是谁,露水之欢,事后不负责任。狮子是群居动物,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人类的爱情是排他的。“老鼠爱大米”?更加不行。因为人类的爱情是“两情相悦”,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老鼠啃大米的声音与雎鸠的“关关”情歌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即为人类爱情故事的展开作了艺术铺垫,也为整个作品的风格定了基调。不难想见,春和景明,岸芷汀兰,草木繁茂,清流婉转。进入了恋爱季节的鸟儿们春心勃发,悦耳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就在鸟儿们的爱情奏鸣曲中,人类的爱情故事拉开了大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该是一个怎样的爱情场景呢?
其次,诗歌展现了至纯至美的爱情场景。《关雎》所表达的爱情却是至纯至美的。爱情这个主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因为它表达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对此,人人都懂。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极易受到“污染”而丧失其纯洁性。如果你是个亿万富翁,你很难判断人家是看上了你还是看上了你的财富;如果你位高权重,你很难判断人家是看上了你的权力地位还是看上了你。当今社会,当一个人的权力越来越大或财富越来越多时,女人离他越来越近,但爱情离他越来越远。因爱而爱的爱情才是纯洁的,因欲望驱动、阴谋驱动的爱情则是不纯洁、甚至是邪恶的。即便在遥远的上古时代,财富、社会地位同样在左右着爱情和婚姻。如《诗经 鹊巢》正是反映了富、社会地位对爱情婚姻的干预。《诗经 鹊巢》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情感上原本另有所属的,是“百两御之”、“百两将之”、“百两成之”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造成了“鹊巢鸠占”的现实,这让爱情的当事人该是怎样的黯然神伤。在《关雎》展示的场景里,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没有权力的威胁、物质的诱惑。我们没有听到“君子”在说“我爸是李刚”,也没有听见“君子”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有的只是心灵的碰撞和对知音的寻觅。我们看到的是“君子”对爱情的真诚、耐心与执着,是对“窈窕淑女”的人格尊重。
从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看,《关雎》对爱情场景的展现也是美轮美奂的。诗歌的作者如同一个高明的电影导演,在雎鸠的爱情奏鸣曲声中,巧妙地运用镜头在“窈窕淑女”和“君子”之间进行画面的反复切换。一会儿是楚楚动人的“窈窕淑女”,一会儿是“寤寐思服”的君子;一会儿是“窈窕淑女”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d之”,一会儿是君子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在这些画面的反复转换过程中,我们虽看不到女主人公的面部表情,听不到她的只言片语,但我们从诗人反复咏叹的“参差荇菜”里不难体会出女主人公的心境。荇菜的参差不齐不正隐喻了她此刻心潮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心理状态?哪个女子不怀春。面对这样一个多情君子的真诚表白,姑娘早已是春心激荡,不能自已。只是姑娘家的害羞和矜持让她一时还不能对君子的追求做出回应。这反倒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时,男主人公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更让我们仿佛从《动物世界》里看到鸟儿们为了爱情时而展示华丽的羽毛,时而放开美妙的歌喉,时而交颈高歌,时而凌波起舞的动人场景。真是真挚热烈、美不胜收。
其三,诗歌的场景展现和情感表达尺度适中。正如孔子在《论语・八佾》里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符合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
我们先看诗歌的情感表达。喜怒哀乐,人之常情。但情绪的表达要适中。儒家的先贤们曾以人的情绪变化为例来阐述中庸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就个人的修养而言,情绪的控制是多么重要。情绪极端,乃小人之举;情绪适度,才是君子之风。《关雎》中的君子乃真君子也。尽管他的求爱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窈窕淑女”的积极回应,尽管爱情的烈火使他“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但他独自承受着爱的煎熬,而没有因爱生恨,更没有情绪的极端表现。对他人,没有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对自己,也没有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相反,他对淑女的追求表现得极有分寸:热烈而不犯粗鲁,执着而不失理性。他“哀而不伤”,今天的追求没有结果,明天依然去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相比我们所熟知的古往今来种种“因爱生恨”、“寻死觅活”的爱情悲剧,《关雎》所表现的对爱情的尊重,实在是可以为万世垂范。
再看看《关雎》的场景表达。不用说,《关雎》是一首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男欢女爱,天经地义。但是,对情爱描写尺度的把握,既涉及到不同社会阶段的伦理规范,又涉及文学作品的审美格调。孔子说“食色性也”。但这个论断还没有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动物穷其一生都在忙乎两件事:食与性。前者是为了维护生命个体的存在,后者则是为了种群的延续。但动物有性无爱、有慈无孝。人类的爱情则不同。它基于性而高于性。《诗经》中有大量描写爱情、婚姻的诗篇。这些作品对情爱的表达虽远没有达到现代文学作品中“丰乳肥臀”的直白程度,但也到了接近“淫”的边缘了。如《野有死麇》描写是男女青年的野合,“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这样情爱场景的展示几近现代电影中的“”了。《桑中》描写的是男主人公从多名美女处渔色后的自鸣得意:她们“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似乎,美色是他的战利品。这就显得格调不高了。《坑忻贰访栊吹氖桥主人公孤独的思春哀鸣。她连具体的恋爱对象都还没有,但面对树上成熟的梅子被人采走、越来越少(寓意着她的同龄伙伴一个个被人迎娶),眼看着自己就要成为“剩女”,她焦虑地呼号着“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求我庶士,迨其谓兮”。少女怀春,无可厚非。但这种“傻大姐”似的嚎叫也实在缺乏审美价值。品读《关雎》,我们既看不到“君子”伺机渔色的企图,更体会不出任何宽衣解带的暗示。在它所展现的爱情场景中,女主人公矜持而含蓄,男主人公热烈而有度。它让读者的情感随着“君子”时而低徊舒缓、时而激越奔放的琴瑟钟鼓声超越了物欲的羁绊。不论她的社会地位如何,一个能被音乐征服的女性该是怎样的高贵?尽管直至诗歌的结束,这场真挚而热烈的求爱都没有明确的结果,但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关雎》给它的读者留下了无限广阔而美好的想象空间。
第3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关键词: 宋咸注本 《孔丛子》 古本 改变
今所见《孔丛子》版本较多,但尚无较好的精校精注本可兹借鉴。《四部丛刊》本《孔丛子》本据宋宋咸注本所定,为今所见最古的《孔丛子》定本,且其注此本时又多参古本,因此我们研究《孔丛子》即以《四部丛刊》本为据。其脱落部分,则参照《续修四库全书》宋咸注本和吉林大学出版的明程荣《汉魏丛书》本。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水经注》,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以及《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所引《孔丛》文字,有很多并不见于宋咸注本《孔丛子》,《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小尔雅》佚文数则,亦为此本所无。结合上文所证此书唐、宋志中所载书名的变化可知,宋咸以后的《孔丛子》版本,与当时他所见到的版本及其以前的版本,应是有所不同的。故《孔丛子》在流传过程中必有版本上的变化。为研究方便,我们将宋咸注本前各书所引的《孔丛子》版本称为古本,而宋咸注本后的各《孔丛子》版本统一称为今本。我们在将唐、宋类书所引《孔丛子》与今本进行比较时,发现古、今本有许多差异之处,由于宋咸最早注《孔丛子》,且以后历代翻刻板多据此本,故我们有理由认为此古今变化必为宋咸所为。下面让我们尝试探讨宋咸对古本《孔丛子》的改变情况。
一、删削
《水经注》云:
“《孔丛》曰:‘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邱封五十余所,人名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
《艺文类聚》和《北堂书钞》皆引伍辑之《从征记》云:
“《孔丛》云:‘夫子之墓方二里,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之,今盘根犹存。’”
而今本《孔丛子》并无此段文字。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考证:
“《提要》云:‘《水经注》所引与全书不类,且不似孔氏子孙语,或道元误证,抑或传写有讹,以他书误题《孔丛》欤?’然《书钞》九十四引伍辑之《从征记》:‘《孔丛》云:“夫子之墓方二里,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之,今盘根犹存。”’《类聚》四十引《从征记》同,足见《孔丛》有叙夫子墓说,而与此证所引互有详略。此但至泗水止,诸孔氏封以下,乃别有依据,郦氏连言之,若与《孔丛》言为一条耳。”
《太平御览》卷九五二引书云:
“《孔丛子》曰:‘夫子墓方一里,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殖之。’”
如果《太平御览》所引《孔丛子》不是采自《从征记》,则宋人所见版本或与伍辑之所见版本同。因此,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的考证无疑是正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怀疑《水经注》所引此佚文或为误引,但《水经注》卷六又引《孔丛子》却见于今本,因此证明《水经注》所见《孔丛子》应该不同于今本。由此足证唐人所见《孔丛》版本,与今本《孔丛子》必有所不同,即今本《孔丛子》在内容上已发生了一定的删削。这种版本上的前后变化,始作俑者应是宋咸无疑,而宋咸自己对此也毫不隐瞒,如在今本所见的《进〈孔丛子表〉》中,宋咸云:“因以史隙,辄然管窥。取诸史以究寻,用群经而忝验。即指归而斯得,复删定以无繁。”在《注〈孔丛子〉序》中有言:“所得本皆豸亥鱼鲁,不堪其读。臣凡百购求以损益补窜,近始完集。然有语或浅固,弗极于道,疑后人增益乃悉诛去。义例繁猥,随亦删定。”结合上文所证看,宋咸表、序中所言不妄,亦足证今本《孔丛子》即出宋咸删削。而由《孔丛子序》宋咸云此书“非诸子之流”看,其所删削标准可以想见。
试以《后汉书》、《太平御览》和今本《孔丛子》所见相同材料比较而观,以进一步考察宋咸对宋本的改变。
《太平御览》卷四五七《谏木孔丛子》“又曰”条引《孔丛》佚文:
越饥请食于吴,子胥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仇雠之国,非吴丧越,越必丧误。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五湖九江、越十地以有吴哉?今将输之粟,是长仇雠,财匮民怨,悔无及也。”
此材料不见于今本《孔丛》,但今《吴越春秋》卷第九却见此文,原文远较《太平御览》所引《孔丛子》佚文为长,故只能略引一二比较之。如《孔丛子》佚文“越饥请食于吴”一句,《吴越春秋》为:
十三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蒙子之术,所图者吉,未尝有不合也。今欲复谋吴,奈何?”仲曰:“君王自陈越国微鄙,年谷不登,愿王请籴,以入其意。天若弃吴,必许王矣。”越乃使大夫种使吴,因宰皮求见吴王,辞曰:“越国下,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乏,道荐饥馁,愿从大王请籴,来岁即复太仓。惟大王救其穷窘。”
《孔丛》佚文一句话,而《吴越春秋》却铺衍成一大段文字,更具故事性与曲折性。因此,《孔丛子》所记肯定不是采自《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长攻》与《说苑・权谋》亦皆记此事,与《吴越春秋》相仿,可知此材料的最初来源当为先秦无疑。现在比较一下四书所记伍子胥的进谏以考察《孔丛子》佚文的最初来源。《吕氏春秋》中子胥谏曰:
“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地邻境,道易入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五湖九江、越十七厄以有吴哉?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误。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雠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此者吾先王之所以霸。”
《说苑》中子胥谏曰:
“不可,夫吴越接地邻境,道易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有越,越必有吴矣。夫齐、晋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吴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阖闾之所以霸也。”
《吴越春秋》所记子胥谏言不仅更加详细,而且加上了子胥与伯的争辩,以及吴王采纳伯建议同意与越粟的细节。由结构的缜密与情节复杂看来,《吴越春秋》当然比《吕氏春秋》与《说苑》更为繁复。而由记叙材料的风格看,《孔丛子》佚文显然与《吕氏春秋》更为接近。因此,《孔丛子》此条佚文应由《吕氏春秋》简略脱化而来,此不惟证《孔丛子》佚文所记材料实采自先秦,而且或许因为此佚文所含王霸之气不合儒道,故而为宋咸所删,因为《太平御览》编者尚见《孔丛子》中有此佚文。今本《孔丛子》虽不见此文,但由今本相近的材料叙述风格看,此佚文前或后当有孔氏之评论应是无疑的。我们可于《后汉书》中找到其蛛丝马迹。《后汉书・儒林传》有孔僖与崔评论吴王夫差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耳。’”由崔答语“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以及孔僖“书传若此多矣”看,二人所论必为夫差前兴后衰之事,即与此条佚文关系极大。故此佚文当系于孔僖下。孔僖曾为汉东观兰台令史,一代名流,今本见记季彦事极多,续《连丛子》者决无对其父孔僖事弃而不录的道理。此文见于《太平御览》而不见于其后的宋咸注本,故此佚文必为宋咸所删。
再如《太平御览》卷四五七:
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仇由君大悦,除道将内之。赤章曼枝谏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之,不可内。”不听,遂内之。曼枝因以断毂而驰至齐,十月而仇由亡。
《韩非子・说林下》亦录此文:
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悦,除道将内之。赤章曼枝谏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大也以来,卒必随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听,遂内之。曼枝因以断毂而趋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
比较二书所引此材料,似乎《孔丛子》佚文更合春秋叙事古义,如其云“不听”,而《韩非子》却云“仇由之君不听”,可见《孔丛》佚文省略了主语,此用法多见于《韩非子》前的先秦史书。可见称引此文的应为韩非之前的孔氏子孙。
又《太平御览》卷四八九引《孔丛子》佚文:
窦皇后弟广国曰:“姊去我西时,与我诀于传舍中,沐我而去。”
《汉书》卷六十七《外戚传》亦见此文:
曰:“子去我西时,与我决传舍中,丐沐沐我,已,饭我,乃去。”
又《太平御览》此卷又引《孔丛子》佚文一则:
成帝遣定陶王之国,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诀。
此则亦见《汉书》卷九十八《外戚传》:
(王凤曰:)“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於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诀。
比较可知,《孔丛》佚文非袭于《汉书》,而实为局外人闻而转述口吻。如此看来,必是东汉孔氏子孙将此事系于孔氏后人而缀补之。结合《孔丛子》内容看,最有可能是《连丛子》之《叙世》篇中的佚文。《御览》所引《孔丛子》材料,还有很多并不见于今存宋咸注本。如《太平御览》卷四五七所引“智伯欲伐仇由”事、“秦穆公以女乐二八与良宰遗戎王”事、“越饥请食于吴”事等,皆不见于今本《孔丛子》。此足证《水经注》与《从征记》中所引《孔丛》之文字,虽不见于今本,然决非误证所致,而实为古本《孔丛》的原始材料。这就证明一个问题:今本《孔丛子》显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润色甚至删削,此加工显然是《太平御览》成书之后的事情。成书早于宋咸《孔丛子》注本不足百年的《太平御览》,其所录《孔丛子》与宋咸《孔丛子》注本文字上的差异,足以证明《孔丛子》版本在此期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历代史书或目录书中,皆未见宋咸前有人校注《孔丛》的记载。因此,今本《孔丛子》与《御览》所引版本比较所见的变化,必出于宋咸之手无疑。
二、修改
《太平御览》卷八十三所引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太甲修政,殷道中兴,号曰太宗,《孔》所谓‘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谓之明王’者也。”今本《孔丛子》则云:“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古今文字稍有差异。《太平御览》引于《帝王世纪》,故其必不会对此引文作简引或缩引的改变,则此必为宋咸对古本的修改。此为宋咸对古本《孔丛子》的又一改变方式,如《文选》卷二七王仲宜《从军诗五首》引《孔丛子》:
赵简子使聘夫子,夫子将至。及河,闻鸣犊与窦准之见杀,回舆而趣。为操曰:“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
《孔丛子》卷二《记问》:
赵简子使聘夫子,夫子将至焉。及河,闻鸣犊与舜华之见杀也,回舆而旋之。息邹,遂为操曰:“周道衰微,礼乐陵迟。……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
《文选》李善注:吾与狼狈见圣人之志。
今本《孔丛子》: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
《文选》注所见《孔丛子》版本,显然较今本近古,且有春秋史书简洁、凝练之风格。以上所举二例,皆为诗歌或诗评,它书转引不会有改编引用的可能,这种语句与文词的修改只能出自宋咸之手。
《文选》李善注引《孔丛子》,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孔丛子》有的基本相同,未见有较明显的变化。《太平御览》成书早于宋咸《孔丛子》注本成书,《太平御览》所见《孔丛子》本当与唐本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将《文选》注与二书一块比较,也可以看出唐本《孔丛子》的情况及宋咸对它的改变。《文选》卷一引《孔丛子》:
古之帝王功成作乐,其功善者其乐和,乐和则天下且由应之,况百兽乎?
《太平御览》卷六二四则曰:
古之帝王功成作乐,其功善者乐和,乐和则天下且犹应之,况百兽乎?
今宋咸注本与《文选》注引完全相同,可见今本的确保留了古本的某些风貌。然而,如果进一步比较看,有的材料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文选》卷五十四:
苌弘语刘文公曰:“孔子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貌也。”
《艺文类聚》卷十七引:
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貌也。”
《太平御览》卷三九六:
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也。”
而今宋咸注本则为:
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
唐前本较唐本与今本较为简练,如唐前本无“吾观”、“其状”等限定修饰语。而今本同唐前本“形貌”者,亦证唐前本在今本中的痕迹并未完全消失,而唐本无“貌”者,证宋咸校《孔丛子》时,必据古本对唐本中的舛误又有所修正。当然,唐人对古本《孔丛子》也有修改,如《文选》卷一与卷三十五引《孔丛子》中的遗谚为“尧饮千钟”,而《艺文类聚》卷二十五、卷七十二等与《太平御览》多次引此条皆为“尧舜千钟”。《文选》注中二次引用皆为“尧饮”,可知并未误引,而今本亦为“尧舜”,因此“尧舜”必为唐人所改无疑。再如《文选》卷五十八注引:
鲁人有仪公潜者,砥节厉行,乐道好古。
《太平御览》卷四O二引:
鲁人有公仪潜者,厉节行道,恬于荣利。
今本所见与《文选》注引同,而续修四库本则为:“鲁人有公仪潜者,砥节厉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由此比较所知,《太平御览》所引必将“砥节厉行,乐道好古”二句合为“厉节行道”,则其所见本已有较多脱落或舛误。今续修四库本与《文选》注本的相同,则说明唐本材料曾以不同的方式流传至今。入唐后《孔丛子》版本的变化,多为古书流传中的脱落、误刻等常事,而宋咸注本中虽有不小的变化,但也的确保留了古本《孔丛子》的许多风貌。又《太平御览》所记《孔丛子》文字,多见于今本《孔丛子》,有的篇段大同小异,然有的篇段文字上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太平御览》卷三六九:
《孔丛子》曰:“子高游赵,还鲁,平原君客邹文李节与子高别。文节流涕交颈,子高抚手而已。”
《艺文类聚》卷二九云:
《孔丛》曰:“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李节者,与相友善。及将还鲁,诸故人诀既毕,文节送行,三宿。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
《孔丛子》卷四《儒服》:
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季节者,与子高相友善。即将还鲁,诣故人诀既毕,文节送行,三宿。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
《太平御览》所记《孔丛子》之文字,远较今本《孔丛子》所记简洁、精炼;于情节曲折,则今本显远胜于《御览》所录之《孔丛子》。这其中的异同当然有转引者的改变,但也不能排除宋咸改变的可能性。再如今本《孔丛子》卷一《记义》篇,有“孔子昼息于室而鼓琴”事,曾子答孔子“汝二人孰识诸”问时,今本为“曾子对曰:‘是闵子。’”而“是”作为判断系词出现,应是较晚的事情,孔子时尤不当有此用法。如《论语》、《孟子》中的“是”皆未有此用法即可证。而《御览》卷五七九引此段文字时为“曾子对以闵子”,无判断系词“是”。可知《御览》所引较宋咸注本近古,而今本《孔丛子》中的文字显然已被宋咸窜入了宋人语气。当然,也不能排除由于宋咸所见《孔丛子》已为残本,他才有於改编之余又有整理、修饬的可能。如《毛诗正义》卷一之三孔颖达注疏:
《孔丛》云:“唐虞之世,麟凤游於田。”
今本《孔丛》:
(孔子)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孔颖达所引古谣谚,至宋本已成为格式工整的楚歌体,这种变化肯定出于宋咸的改编。《毛诗正义》卷五至二:
《孔丛子》云:“卫人钓於河,得鳏鱼焉,其大盈车。子思问曰:‘如何得之?’对曰:‘吾下钓,垂一鲂之饵,鳏过而不视。又以豚之半,鳏则吞矣。’子思叹曰:‘鱼贪饵以死,士贪禄以亡。’”
今本《孔丛子》卷三:
卫人钓於河,得鳏鱼焉,其大盈车。子思问之曰:“鳏鱼,鱼之难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对曰:“吾始下钓,垂一鲂之饵,鳏过而弗视。更以豚之半体,则吞之矣。”子思喟然叹曰:“鳏虽难得,贪以死饵;士虽怀道,贪以死禄矣。”
今本显然不如孔颖达所见唐本凝练、古朴。《毛诗正义》卷十七之一:
《孔丛》云:“魏王问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无故有谷,乃云天雨,反以亡国,何也?’曰:‘自古及今,未闻天下谷与人。《诗》美后稷能太教民种谷,以利天下。若中山之谷,妖怪之事,非所谓天降祥也。’”
今本《孔丛子》卷五:
魏王问子顺曰:“寡人闻昔者上天神异后稷而为之下嘉谷,周以遂兴。往者中山之地,无故有谷,非人所为,云天雨之,反亡国何故也?”答曰:“天遂至神,自古及今,未闻下谷与人也。《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谷嘉以利天下。故《诗》曰‘诞降嘉种’,犹《书》所谓‘稷降播种,农植嘉谷’。皆说种之,其义一也。若中山之谷,妖怪之事,非所谓天祥也。”
子慎即子顺。此处比较易知,宋咸非仅删改而已,文字的脱落或补加在此是有迹可寻的。如“周以遂兴”与《诗》、《书》所引,定为宋咸以己意妄补。而“《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谷嘉以利天下”后半句不仅有增补的痕迹,而且有文字错乱的迹象,《汉魏丛书》本《孔丛子》为“种嘉谷以利天下”可证。另外,今本“非所谓天祥也”与孔颖达引比较,显然脱落了“降”字。
三、调整
宋咸对《孔丛子》的文字或章节还作过重新的调整和布排,宋咸在其《序》中亦对自己调整古本章节的行为供认不讳。如《孔丛子》卷一《论书》题下宋咸注曰:“《论书》者,盖仲尼与诸侯弟子析白《尚书》之义。然自子张问圣人受命、有鳏在下、子夏问书大义凡三事,旧在《嘉言》篇,臣咸今易之于此,首庶一贯焉。”其次,上篇之《叙世》记述孔氏子孙由孔鲋至子丰,与下篇所记子和、季彦、仲渊等正好承代相继,此证上篇中《叙世》与《连丛子》下本属同卷,后来编书者将《与子琳书》与孔臧赋并列,而将记子和、季彦等之事别列成为《连丛子下》。如宋咸《孔丛子后序》云:
详孔臧续《连丛子》二篇,至《与子琳书》而止。自《叙世》而下逮季彦卒,悉孔氏之后人术。
由宋咸之语可知两点:一是《连丛子》非孔臧作之而为其续之,且至《与子琳书》止;二是季彦卒事本来是在《叙世》中的,且《叙世》为后人又续。另由今《连丛》皇甫威明与仲渊问答时有“今观《连丛》”语,仲渊时既已有《连丛》书,则有关仲渊材料必为后人又有增益。这样看来,今所见《连丛子下》完全可以归入《叙世》内,《连丛子》成书过程就可由此而见:古《连丛》亦为二篇,东汉孔臧续之,至《与子琳书》止;其后孔氏后人又续《叙世》,内容至季彦卒。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孔臧续《连丛》至《与子琳书》,则次续篇应在《连丛》最末;《叙世》又为后人续之,则此篇又在《与子琳书》后,今所见《连丛子》章节排列,必为宋咸注书时调整无疑。
参考文献:
[1][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6:2101.
[2][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732.
[3][唐]徐坚等著.初学记(第一册)[M].中华书局,1980.1:32.
[4][唐]虞世南辑.北堂书钞[M].中国书店出版社,1989.7:357.
[5][宋]李等.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2:390.
[6]周生春注.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7]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M].中华书局,2000.
[8]汉书百衲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9]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第4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关键词]述而不作 方法论
《论语.述而篇》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其中“述”是阐述、叙述的意思,“作”是进行新的创作之意,“述而不作”是指只阐述、叙述前人的理论、学说,而自己并不进行新的创作、提出新的见解的意思。新的创作不仅只是局限于文字上的,也指制度等方面的。《汉书.儒林传》中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究观古今之篇籍,……于是叙《书 》则断《尧典 》,称《乐》则法《韶舞》,论《诗 》则首《周南 》。……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这里,班固把“述而不作”理解为只是叙述而不进行自己的创作。这种理解,从班固开始,延续至今。虽然,也有其他诸多的理解与解释,但这一解释一直占据主流。例如,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说:“述者,传于旧章也;作者,新制作礼乐也”;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 》、《书 》,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 ,而未尝有所作也”;至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将“述而不作”译作“阐述而不创作”。
“一句‘述而不作’,成为孔子一生治学特点的权威概括 ,也演化为某种扎实、不尚空言却也带有保守、无创新意向的学术风格”[1],后来却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根据孔子的记述,殷朝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们根据历史记载和《论语》中的相关言语,还是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时期乃至后世,人们一向都不太重视立言,人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转·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与范宣子的一段对话,穆叔对范宣子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没有办法的最后选择,人们首先选择的是要向古圣贤学习,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为圣人们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让后代的人觉得他们的言语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时候广招门徒,史书记载孔门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艺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来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编撰教材来传授弟子,他所编写的《诗》、《书》、《礼》、《乐》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的,《诗》本来有三千多首,经他删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诗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作为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为什么自己不独创呢?因为在他看来,先王之道已经很完备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论传达出来就行了,只是当时世道混乱,“礼坏乐崩”,本来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们忘记了,因此他才会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来教授弟子,好传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贡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说,只是为了教授弟子才去说那么多话。在孔子生前,他并没有自己的专著,《论语》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为其编撰的。
孔子不注重言还与他的教学思想有关。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学成后对社会有所贡献,他更多地是从修身即道德方面来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只要道德修好了,学不学文都无关紧要,只是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才去学文。从他对学《诗》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诗》的目的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兴、观、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还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更可以看出他“学以致用”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学那么多的诗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应用,学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之后,相传子夏传经,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都是来传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样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几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兰陵著书立说,他对为什么要学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经无所不包,只要学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说荀子的思想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脉相承的。
但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后世的情况与前代已经很不相同了,古先圣贤的言论似乎已经不能包罗一切了,怎么办呢?于是后世的人们不断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从“十三经”的确立便可以看出古人的思路。孔子时代,并没有自封为圣人,《论语》成书后也没有很快成为经典,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才将《论语》连同《孝经》一起列为经典,才有“七经”说,唐代又发展为“九经”,宋代有“十二经”,将《孟子》列入经典后,便有了“十三经”之说。有了这些经典之后,历代的儒生们便有了“述而不作”的条件和依据。他们只要去注释经典即可,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不敢任意去表达,只是在注释的时候才阐发出自己的思想。注释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先是前代人的注,可时间久了,前代人对经典的“注”后代人看不懂了,于是后代人便去再注释前代人的“注”,这便是“疏”,经历代人的努力,便有了“十三经注疏”。可以说,在几千年的时间中,“我注六经”一直成为中国人著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经学的繁盛也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有关,既然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都这么做了,后世的人还有谁敢不去照办呢?只有那些离经叛道的人才转向文学的创作,转向诗词歌赋和小说的写作,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述而不作”作为一种学术风格或方法论,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借鉴它,学以致用,注重实效;另一方面,对前人的理论、学说进行解释和说明,本是个人的学术自由,可是如果学术界普遍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对我们的学术进步、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利的。因为这不利于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和激情,不利于解放人、开发人。
第5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周穆王时代乐歌证补
《毛传》成书及定型考论
《诗经》“荒”的义项初探
《小雅·北山》“旅”字考辨
《诗经》叠字计量研究
源于《诗经》的组合式复音词
叠音词的陆性与水性
《诗经协韵考异》版本考辨
袁枚对孔子《诗》说的批评与改造
徐干《中论》引《诗》略考
论焦循的《诗》学思想
“兴”字本义及因变考
刘歆《诗》学观探微
《艺文类聚》引《诗》堪比
论杜丽娘习《诗》的反理学意义
民国时期的赋、比、兴研究
《诗经·商颂》的语言之美
《诗经》的语言研究仍有可为
《诗经》编集过程中的传播问题初探
浅谈《国风》情诗的界定与分类
论《毛诗序》女性礼教体系及其影响
“采诗观风”及其意义的再探讨
《左传》赋诗、引诗与春秋解《诗》之学
《韩诗外传》所勾勒的孔子诗教观
陈奂《诗毛氏传疏》初刻本的文献价值
清儒三家《诗》辑佚观念论略
欧阳修《诗本义》学术渊源略考
关于吕祖谦对于《诗序》的态度问题
刘瑾《诗传通释》的撰述体例与解经方式
元代《诗经》学著作对《诗集传》的校勘价值
王逸引《诗经》释《楚辞》考论
韦昭《国语解》引《诗》笺补
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究
谢康乐山水诗引《诗经》典故类析
《全三国文》征引《诗经》文献研究
“毛诗名物图说”与“毛诗品物图考”异同论
《四库总目》对《诗集传》的误评述论
苏轼转化《诗经》“思无邪”为“思无所思”的断思
《诗经正义》江西南昌府学雕本及断句本试阅一卷
朱熹“以《诗》说《诗》”之经典还原论及其意义
“诗际幽明”:王夫之《诗经》学诗学观管窥
毛传郑笺对《诗经》中复现词语的释例发微
论《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伊尹、尹吉甫家世生平和《诗经》编订考
《诗经》中双音象声词的语义构成及其形义特征
西周铭文、《费誓》与《江汉》《常武》的互证研究
第6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形容孔子的成语集锦
[钻坚仰高] 原形容颜渊对于孔子之道的赞叹,后指努力攻读,深入研究,力求达到极高水平。
[至圣先师] 至:最。旧时特指孔子。
[子曰诗云] 子:指孔子;诗:指《诗经》;曰、云:说。泛指儒家言论。
[笔削褒贬] 笔:记载。削:删改。古时在竹简或木简上写字,写错要修改时就用刀削。原指孔子作《春秋》,用文字来评文论物的好坏。也指用文字褒扬、贬斥人或事。
[道大莫容] 原指孔子之道精深博大,所以天下容纳不了他。后用以正确的道理不为世间所接受。
[孔席不暖] 指孔子急于推行其道,到处奔走,每至一处,坐席未暖,又急急他往,不暇安居。
[孔席不适] 指孔子急于推行其道,到处奔走,每至一处,坐席未暖,又急急他往,不暇安居。同“孔席不暖”。
[刚毅木讷] 刚:坚强;毅:果决;木:质朴;讷:说话迟钝,此处指言语谨慎。孔子称颂人的四种品质。
[孔情周思] 指儒学的思想、情懆。孔,孔子;周,周公。
[不悱不发] 悱:心里想说而说不出来。发:启发。指不到学生想说而说不出来时,不去启发他。这是孔子的教学方法。
[不愤不启] 愤:心里想弄明白而还不明白。启:启发。指不到学生们想弄明白而还没有弄明白时,不去启发他。这是孔子的教学方法。
[周情孔思] 周公、孔子的思想感情。封建社会奉之为思想情操的楷模、典范。
[配享从汜] 旧时以孔子门徒及某些所谓“名儒”附属于孔子者一并受祭,称配享从汜。
[先圣先师] 旧时尊称孔子;也称周公和孔子或孔子和颜渊。
[梦见周公] 周公:西周初著名政治家,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原为孔子哀叹自己体衰年老的辞句。后多作为瞌睡的代称。
[上智下愚] 智:聪明;愚:笨。最聪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孔子认为他们都是先天决定,不可改变。
[孔孟之道] 孔:孔子;孟:孟子。指儒家学说。
[东观之殃] 孔子任鲁司寇时,杀少正卯于东观之下。后用以指杀身之祸。
[三节两寿] 旧俗对于塾师,逢端午节、中秋节、年节及孔子诞辰,塾师生日,均各加送束脩一月,称为三节两寿。亦用以泛指节日和生辰。
[三盈三虚] 盈:满。虚:空。指孔子的满门弟子,被少正卯讲学所吸引,多次离开孔子之门。形容讲学效果好,影响大。
[诗云子曰] 《诗经》所说和孔子所言。二者均为历代儒者遵奉的信条。因用以泛指儒家言论或经典著作。
[黔突暖席] 原意是孔子、墨子四处周游,每到一处,坐席没有坐暖,灶突没有熏黑,又匆匆地到别处去了。形容忙于世事,各处奔走。
[孔席墨突] 原意是孔子、墨子四处周游,每到一处,坐席没有坐暖,灶突没有熏黑,又匆匆地到别处去了。形容忙于世事,各处奔走。
第7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关键词:诗话 诗言志 适理 雅正 尽善尽美 《济北诗话》
《济北诗话》是日本五山诗僧虎关师炼(1278-1346)所著,是其二十卷文集《济北集》中第十一卷。这是日本首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在日本诗话史上的意义与中国的《六一诗话》较为相似。虎关师炼曾以诗文著称,对汉文、汉学涉猎颇深,其在日本五山文学中,特别是在五山时期的汉文学创作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虎关师炼对中国的文学典籍有着较为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对于中国的诗文他不仅有深刻清晰的认识,同时还有着自己独到的感悟见解。这在《济北诗话》中就有较为鲜明的体现。
《济北诗话》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十一则。其完全继承了中国诗话的体制特色:即以一条一条长短不一的、互不相关的、随笔式的条目连缀而成。其记述内容上也较为驳杂。《济北诗话》中记述的内容涉及了中国的诗人、诗歌、诗论等诸多方面。当中评述论及的便有周公、孔子、陶渊明、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韩愈、韦应物、贾至、王安石、梅尧臣、杨万里、刘克庄、朱淑真等数十位中国诗人,并涉及到了《诗人玉屑》《古今诗话》《城斋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等数部中国诗话著作,另外,当中还涉及了《梵网经》《广灯》《起世经》等佛门经典。短短三十一则,寥寥数语,却语涉颇广。极为鲜明地反映出虎关师炼对中国诗文以及诗论思想涉猎之广、之深。
虎关师炼曾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中以诗文创作著称,其一些诗作几乎可与中国诗作相比肩。同样,虎关师炼在诗文理论方面的心得体会也应被人重视。《济北诗话》中记述了虎关师炼对于中国诗人、诗歌以及诗文创作上的种种体会和认识。通过分析《济北诗话》中涉及的诗学思想、文学观念,有助于了解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及其文学观念。
一、诗歌观
《济北诗话》开篇第一则:
或曰:“古者言:周公惟作《鸱^》《七月》二诗。孔子不作诗只删《诗》而已。汉魏以降,人情浮矫,多作诗矣。而诸?”予曰:“不然。周公二诗者,见于《诗》者耳,竟周公世,岂唯二篇而已乎?孔子诗虽不见,我知其为诗人矣。何者?以其删手也。方今世人不能作诗者,焉能得删诗乎?若又不作诗之者,假有删,其编宁足行世乎?今见‘三百篇’为万代诗法,是知仲尼为诗人也。只其诗不传世者,恐秦火耶。周公单二,亦秦火也耳。不则,何啻二篇而止乎?世实有浮矫而作诗者也,然汉魏以来,诗人何必例浮矫耶?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皆形于绪言矣,传记又可考焉。‘浮矫’之言,吾不取矣。”
首则便为诗文创作正名,驳斥了“周公惟作《鸱^》《七月》二诗。孔子不作诗只删《诗》而已。汉魏以降,人情浮矫,多作诗矣”的观点。在其看来,周公和孔子二位圣人诗作必定不少,大概缘于秦火而不得传世。不能因此而认为诗创作之多源于汉魏以来“人情浮矫”的风气。毕竟诗文创作体现的是“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绝不是“浮矫之言”。
在虎关师炼看来,诗歌创作在根本上秉持着诗以言志的思想,具备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这种诗歌观正是源自《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一开篇便阐明了《诗经》在诗歌创作史上的典范地位,并表明了其所认同的“诗言志”的诗歌观。诗歌观是诗人创作诗歌时最重要的理念和理论基石,秉持着怎样的诗歌观,影响甚至决定着诗人的诗歌创作。虎关师炼在清楚地点明中国诗歌典范的同时,也凸显着他对于诗歌的认识:即用于言志、用于教化。这一认识正与中国儒家的诗教观相合,这也正是虎关师炼所秉持的最基本的诗歌观。
在一开始便开宗明义点明自己的诗歌观念后,紧接着,虎关师炼又先后从更为具体的角度阐明了作诗须重视的一些因素,如“适理”“雅正”之论,即用以进一步表明虎关师炼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具体要求与内涵。
赵宋人评诗,贵朴古平淡,贱奇工豪丽者,为不尽耳矣。夫诗之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适理而已。……达人君子,随时讽喻,使复性情,朴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适而已。……圣人顺时立言,应事垂文,岂工朴云何然?则诗人之评,不合于理乎!
“m理”之论表明虎关师炼对诗歌创作中内质的重视。“圣人顺时立言,应事垂文”点明了诗歌的最佳源出即在于应运而生,也就是触物感兴,只有这样创作出的诗文才能言之有物、言之合理。“达人君子,随时讽喻,使复性情,朴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适而已。”言有物、言合理才是诗歌创作需要秉持的根本核心,而不应该舍本逐末,仅注意到形式上的平淡或奇工。诗歌高低更多的在于当中表现的“志”、抒发的“情”。
夫诗者,志之所之也,性情也,雅正也,若其形于言也,或性情也,或雅正也者,虽赋和,上也;或不性情也,不雅正也,虽兴,次也。……其思念有正焉,有邪焉,君子之者,去其邪,取其正,岂以其无事忽焉之思念为天,而不分邪正随之哉?……况诗人之者,元有性情之权,雅正之衡,不质于此,只任触感之兴,恐陷僻邪之坑。昔者仲尼以风雅之权衡,删三千首,裁三百篇也。后人若无雅正之权衡,不可言诗矣。
“雅正”之称,强调诗人作诗时要以雅正为权衡。《诗》有六艺,风、雅、颂、赋、比、兴。“六艺”从形式到思想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发展的基础。正是以《诗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雅正观念自古传承于诗歌创作之中,成为了诗歌创作最重要也是最正统的创作理念。《诗经》中的“风”与“雅”体现出的是诗歌创作应该包含的艺术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中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与“风雅精神”的主张相同,虎关师炼在这里也鲜明地指出诗人作诗要“去其邪,取其正”,秉持“雅正之衡”,不能“只任触感之兴”而陷于“僻邪之坑”。虎关师炼提出的诗歌“雅正”观也正是得于《诗经》中的风雅精神。在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中,诗歌出于性情兴感,是诗人抒发感情与心怀自然而然地流露,而这些流露出的情感表现在诗歌中时却是要合于“雅正”的规范。“雅正”的重要性被虎关师炼定位到了“后人若无雅正之权衡,不可言诗矣”的高度。可见,在创作诗歌时,诗人必须要以“雅正”为权衡,以确保诗作之正。
另外,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观念中,周公和孔子等圣人的观念与创作是其所重视并极力推崇的,而被视为中国诗歌典范的《诗经》也同样受到了虎关师炼的关注。其主张的“学道忧世、匡君救民”的诗歌创作观,以及对诗歌“适理”“雅正”的强调都彰显出其诗学观承续自以《诗经》为诗歌典范的诗歌观。这也展现出虎关师炼作为一位日本的h诗创作者在诗学源出上的选择与自信:汉诗创作并非学于中国当代(日本五山时期时中国大致处在宋代),而是本于诗歌创作的源出――《诗经》,表明其在诗歌学习上的正统性与传承性,内含着在日本的汉诗创作是与中国的诗歌创作同源而出亦可并肩而立的思想观念。
二、“人才”观
在《济北诗话》中,虎关师炼多次提及诗人之才。在其看来,诗人有“上才”“下才”之分,才能高低不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人诗歌创作的成就。
诗贵熟语,贱生语,而上才之者,时或用生语,句意豪奇;下才惯之,冗陋甚。
又,“李、杜无和韵,元、白有和韵,而诗始大坏者”非也。夫人有上才焉,有下才焉。李、杜者上才也,李、杜若有和韵,其诗又必善矣,李、杜世无和韵,故赓和之美恶不见矣;元、白下才也,始作和韵,不必和韵而诗坏矣,只其下才之所为也。……夫上才之者,必有自得处,……下才之者,少自得处,只是沿袭、剽掠、牵合而已,是杨子之所谓“大坏”者也,只其下才之所为也。宁赓和之罪哉?
虎关师炼认为诗人才学能力的高低深刻影响着其创作出的诗歌的优劣。严羽《沧浪诗话》便有“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论述,正式指出写诗的才华是一种特殊的才华,跟学问高低没有关系。这份才能并不是单靠后天的学习就可以达到的,而是和与生俱来的天分相关。基于对诗人诗才的认识,虎关师炼指出“上才”诗人“必有自得处”,而“下才”诗人则“少自得处,只是沿袭、剽掠、牵合而已”。“自得”是触物而能感兴,并实现自我创造,最后在发言为诗时能“适理”且合于“雅正”。好诗并不会受外在形式体制的约束而变成坏诗,同样坏诗也源于诗本身的不佳,而不应牵连到诗歌体制、体裁的好坏之上。明确诗人的上才、下才之分,有助于客观地认识诗歌中不同的体制、题材、语言、韵律等因素的作用。可以说,诗歌的好坏不能归咎于其所使用的体制、题材、语言、韵律等因素之上,在虎关师炼看来,诗人才能的高低才是根本决定性因素。所以,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中,便以诗人的才能为根据来反驳中国诗话中类似“李、杜无和韵,元、白有和韵,而诗始大坏者”的思想观点。
三、诗评观
《济北诗话》中多处记述了对中国诗歌的品鉴与批评。虎关师炼在对中国诗的品评论述中多主张秉持“尽善尽美”的标准。虎关师炼的品鉴虽深受中国诗评的影响,却也没有完全以中国原本的品鉴马首是瞻,而是在了解中国诗评的同时,或认同或反对,却都充分表达了虎关自己的观点和喜好。
欧阳文忠公称赏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山谷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或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缘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矣系于人。”予谓,二联美则美,不能无疵。……二公采林诗为绝唱,我只以其尽美矣、未尽善矣言之耳。《古今诗话》曰:“梅圣俞爱王维诗有云:‘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善矣;夕阳迟则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也。如杜甫诗云:‘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此了无瑕h。”如是诗评为尽美尽善也。
在虎关师炼看来评诗既要重视“美”又要重视“善”。“美”在于诗中的辞藻、韵律;“善”在于诗从内容情感到形式体制的完善。在品鉴诗歌上,总是要将这两方面都重视起来。对于中国诗歌的品评虎关师炼常发自己的品析感触,有赞同亦有驳斥:
《遁斋闲览》云:“凡咏梅,多咏白,而荆公诗独云‘须捻黄金危欲堕,蒂团红蜡巧红装。’不惟造语巧丽,可谓能道人不到处矣。”荆公此诗,丽则丽矣,“能道人不到处”非也。……遁斋过称,可笑矣。
“可笑矣”一语在《济北诗话》中数次出现,虎关师炼对中国诗歌、诗人、诗评的批评具有自己独到的感悟。这些感悟的表达一则出于虎关师炼对中国诗文的熟悉,一则也表现着他对自身汉诗文造诣的自信。能这样态度鲜明地反驳中国诗评以及诗论;能观点明晰地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是《济北诗话》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又深刻影响着日本之后的诗话创作,让日本诗话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好议论并能不拘囿于中国诗话的创作特色。
四、结语
《济北诗话》是日本第一部独立创作而非编纂的诗话著作,当中记述了不少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观念。从这些记述来看,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更多地受到中国的“诗言志”“风雅思想”等诗教观的影响。在他看来,诗歌用以抒怀言志,更是用于匡君救民。诗歌创作绝不是文人的游戏,它有着极为严肃的社会功用。在诗歌品鉴上,虎关师炼力求“尽善尽美”,并以自己独到的感悟品鉴着中国的诗歌、诗论。通过对《济北诗话》的浅析,可以大致分析出虎关师炼所秉持的关于诗歌的创作观、鉴赏观等,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位汉诗文才能不输中国诗人的日本诗人。
参考文献:
[1]蔡镇楚主编.域外诗话珍本丛书二十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马歌东编选校点.日本诗话二十种[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3]蔡镇楚.诗话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4]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5]徐毅.《济北诗话》的诗学价值[J].科教文汇,2008,(7):217-232.
[6]黄威.论宋代诗学思想对日本《济北诗话》之影响[J].船山学刊,2009,(4):162-164.
[7]段丽惠.《济北诗话》的“立异”与儒家价值理念[J].船山学刊,2009,(7):102-105.
第8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古音学是一门研究汉语上古音的学问。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当中,上古音到底属于哪一时段的语音,学界还有些分歧,流行的说法认为上古音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但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段时间太宽泛,上古音应该仅限于周秦时期,不包括先周时代以至远古时代的语音(刘晓南,2007:135)。本文依据清代学者研究上古音使用的材料――《诗经》等先秦韵文和《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采用刘晓南先生的说法。古音研究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末,郑玄的“笺”、“注”或刘熙的《释名》里,一再提到“古音某,今音某”的语言现象。古音研究的真正开始是在宋代的吴域和郑痒,但他们受制于《唐韵》分部的影响,又加上对古音研究的指导思想没有脱离“叶音说”的窠臼,因而缺乏科学价值。到了明代的陈第明确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说法,建立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改,音有转移①”的正确语音历史观,古音研究的科学时代才算开始,但陈氏考察古音拘泥于只言片字缺乏系统性,因而古音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时期是在清代,表现为名家辈出,如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等;成果丰硕,据耿振声先生统计可达167种②。为近现代古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清代的古音研究做一个全面的鸟瞰,以便同行们参考。
二 古音理论研究
清代之前古音研究形成了两种指导思想。一种以朱熹为代表的“叶音”说,主张用今音改古音以求得读古书的和谐,其精神内核是古今音不变;另一种以唐代陆德明、宋代吴域、明代陈第为代表的“音移”观,主张语音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有古音今有今音。
清初顾炎武继承了“音移”观的指导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语音发展的阶段理论,顾氏认为:《诗经》“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其后“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辞赋日繁”“休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堪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唐时以诗赋取士,其书一以陆发言《切韵》为准”,“至宋景佑之际微有更改,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③。顾氏的这一理论为自己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并且影响了其后的江永、段玉裁等人;
江永在继承了顾炎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倡导“审音”理论。他主张对上古音的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的材料作科学的区分。在江永之前,许多古音学家不区分材料的不同时代,对材料的真伪也不做科学的考证,把《诗经》、《楚辞》甚至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统统混杂在一起。对此,江永明确指出,古韵研究的材料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至于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与上古音相互比较,以究明其源流变化,不能作为对上古音分声定韵的依据。同时,江永十分重视对中古音的研究,认为中古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去认识上古音的韵部。这一点,得到戴震的支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戴氏认为上古韵部的材料传世的比较少,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来断然决定上韵部的分和合是不够的,因此,中古音的研究对上古音的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戴震认为《广韵》是中古音的代表,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不同可以帮助我们对古音作出更加精细的研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他精心研究古韵并做出了九类二十五部的细致划分。同时,建立了韵类的“正传”、“旁转”的理论,所谓“正传”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同一韵部的内部转变,第二种是统一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第三种临近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旁转”是指上述三种“正传”之外的情况,这种理论为后来孔广森的阴阳对转理论开了先河。
孔广森,山东曲阜人,是戴震的弟子,他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明确建立了阴阳对转理论。孔广森把古韵分为十八部,其中阴声韵九部,阳声韵九部,分别构成九对阴阳对转关系:歌元、支耕、脂真、鱼阳、侯东、幽冬、宵侵、之蒸、叶谈,他利用阴阳对转的理论来解释《诗经》押韵和谐声中的一些现象。例如:《诗经・邶风・北门》押敦、遗、摧,可是敦字属真部,遗、摧属脂部,这就叫脂真对转。孔氏的这一理论对其后的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古音构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古音研究方法
清代的古音研究方法虽然主体仍是前代的系联法,但大有改进,表现在系联对象的扩大,归纳结论更加科学仔细,同时,还开创了“审音法”、“古音构拟”法。
首先,顾炎武提出归纳古韵第一步要“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将平水韵中已经合并的韵分开,恢复《唐韵》的原貌,“所谓一变而至鲁”,第二步“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归纳《诗经》、群经的用韵,而将《唐韵》重新分合,“所谓一变而至道”,从而使得“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④同时采用“诗韵系联”、“谐音系联”、“离析《唐韵》”等多种方法,广求证据,讲求事物条理,愈祥博愈好的朴学风范。顾氏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被清代音韵学家所采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运用。
其次,江永在顾炎武开创的科学方法基础之上,明确倡导“审音法”,这种方法提出从事古音研究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运用的材料做出科学的划分,不能把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和后代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作为考查古音的依据,考察古音的材料依据只能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作为参考佐证之用。
“古音构拟”法是章黄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黄之学”是指由清末国学大学章太炎(1869-1936)、黄侃(1886-1935)师生二人所创立的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一个学派。它是东西文化碰撞的结果,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朝“朴学”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原始母语思想。在研究语言文字方面,把研究音韵作为首位。章太炎说:“董理小学,以韵学为侯人。⑤”研究音韵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构拟我国古代的语音体系,从而为探求语源服务。在探求语源上,章黄以《说文》和《广韵》作为工具,“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拟构上古语音体系中,声母二十一纽,古韵二十三部;黄侃在《音略》中拟构的上古声母是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
四 古音韵母研究
清代古音研究家们依据《诗经》等先秦韵文、《说文》的形声字,采用系连法归纳古韵部。首先,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作《音学五书》⑦分古韵为十部,如下:
(一)东、冬、钟、江;
(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
(三)鱼、虞、模、侯;
(四)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萧、宵、肴、毫、幽;
(六)歌、戈、麻;
(七)阳、唐;
(八)耕、清、青;
(九)蒸、登;
(十)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顾氏分类大体沿用了《唐韵》的韵目,但并不受其约束,如入声韵不一定与阳声韵相配,每个韵的字也不硬性配入某部,如“支”半入“支脂”半入“歌戈”等等。他这种做法从其《音学五书》“叙”表达的思想来看,大体有一种复古的倾向性。如:“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对此,江永给予了批评,他说:“音之流变已久,休文亦据今音定谱为今用耳。如欲绳之以古,‘风’必归‘侵’,‘弓’必归‘登’,‘宜’必归‘歌戈’,举世其谁从之?”⑧
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等逐步有所修正。江永撰《古韵标准》以正顾氏之讹阙,分古韵为十三部,他把顾氏第四部“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分为两部,“真、谆、臻、文、殷、魂、痕”为一部,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仙”为另一部,口侈而声大,“先”韵一半从前一般从后,界于二者之间;第五部“萧、宵、肴、毫、幽”中的“萧、宵、肴、毫”为一部,“幽”并“尤、侯”为一部;第十部中的“侵”单独为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部分用字,“添、咸、衔、严、凡”为另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另一部分用字。
戴震作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十分强调“审音”在古韵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的不同借此对古韵做出了更加精细的划分,得出古韵九类二十五部⑨,阴、阳、入三个大类的韵部互相配合,如下表:
(一)1、阿2、乌3、垩
(二)4、膺5、噫6、亿
(三)7、翁8、讴9、屋
(四)10、央11、夭12、约
(五)13、婴14、娃15、厄
(六)16、殷17、衣18、乙
(七)19、安20、霭21、遏
(八)22、音23、邑
(九)24、腌25、叶
其后,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和江有诰分为二十部,章炳麟分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均在其前辈分部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换韵目,大同小异而已。
五 古音声母研究
清代古音声母研究的成就突出体现在钱大昕、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著作中。首先,钱大昕(1728-1804)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中,得出有关古声母的的两个重要结论:①古无轻唇音,即三十六字母“非、敷、奉、微”四个轻唇音,在上古要分别读为四个重唇音“帮、滂、并、明”。②古无舌上音,即“知、彻、澄”三个舌上声纽,上古分别读为“端、透、定”三个舌尖音。此外,他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音韵问答》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里又说古音“影”、“喻”、“晓”、“匣”四母多相混,而与“见”、“溪”诸母没有明显的区别。其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上卷《古音“娘”、“日”二妞归“泥”说》一文中提出“泥、日”两个声纽上古应读做“泥”,在《新方言》卷十一里又说:“‘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上古声母无正齿和齿头之分,其弟子黄侃从《广韵》中考定上古有十九个声纽,如下表⑩: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学者看重。
六 古音声调研究
古音声调研究方面,清代学者也作了许多努力。段玉裁具有开创之功,首先提出上古声调和《广韵》不同,汉初以前的汉语没有去声,只是到魏晋以后,许多原来上声、入声的字才转变为去声,因而,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入三声,这一见解当时许多学者并不赞成,但近现代许多学者如章太炎、王力等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江有诰对上古声调的研究也卓有贡献,一开始他认为古无四声,反复推敲之后,他认为古人确有四声,并作了《唐韵四声正》这部专著,并指出四声与韵部的搭配并不一致,有些韵部四声具备,而有些韵部只具备三声(平、上、去)、或两声(去、入),或一声(平),对入声进行了专门研究,做成了《入声表》,得到段玉裁的高度评价。王念孙关于上古声调的主张大体与江氏相同,既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但黄侃作《诗音上作平证》则认为上古声调只有平、入两个声调,可谓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七 小结
清代是我国训诂学的鼎盛时期,许多学者用力于以音求义,音韵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对前代作品的注释、补订,还是独立创制,都有很高的质量,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一般只能从古文献中构拟出一个系统,研究资料、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开拓,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如古代声母、声调问题,尤其古汉语的音值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的去研究。
参考文献: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刘晓南.汉语音韵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史存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清代古音学》见《王力文集》[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5]高本汉著、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6]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7]李方桂.上古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第9篇:孔子删诗说范文
一、 主张“文理一物”与“博文约礼”
关于主张文理关系,历代大儒已多有论述。周敦颐将“文以明道”改为“文以载道”,已经“为以后的理学家确定了与古文家不同的关注中心,从而形成了与古文家截然不同的文道论。”(《中国文学批评史》182页)沿此方向,程颐的“作文害道”说和朱熹的“诗文妨道”说,可谓已将“道本文末”的思想发挥到极至,而王阳明则进一步发挥,提出文道同体说。(《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第6页)
从本体意义上讲,此处的“理”与前述的“道”是同一概念。王阳明认为;文是发见出来的理,理是发见不出来的文,文就是理,理就是文,文理本是一物。这事实上可以理解为其心学,‘心即理’学说在文学层面的阐释。在王阳明看来,所谓“作文害道”、“诗文妨道”说仍属于“文”、“道”二本说,即文学创作有两个本体。这种说法本身就意味着提倡“道”的同时也承认了“文”的存在,而承认“文”的存在就有使文学陷入“纯文学”即“虚文”的危险。鉴于“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 ,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纵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 (《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第56页)的弊端存在,王阳明提出了文理“只是一物”、“博文即是惟精”“和约礼即是惟一”的说法。在儒家文化中,“博学”本指的是对典籍与历史的学习,“约礼”本则指的是礼仪与道德的实践,一向被看作是两种不同活动。王阳明则认为,博文的确是指对经典的学习,但经典本身即是天理的表现,因此学文仍然是学习天理,所以在他看来,“活动的方式可以多样而博,但所有的活动的内容则都是以特定方式学存天理,这种博实际上与约并没有根本差别。”(〈有无之境〉第285页)所以王阳明关于文学本体的基本态度就是,理就是文,文就是理,文理本一物,博文与约礼本也只是一物。
二、 主张“去文求实”与“删繁就简”
王阳明认为文理本同一,文只不过是理的外在显现,不赞同过度夸饰的文风,在他看来,文理本同一,文本是理的昭示,对文的过度敷演反而会使人心迷惑,犹如给理蒙上了面纱让人不知所措。所以孔子删六经并非如后人所言是有意著书立言,给世界增添学说;恰恰相反,孔子是出于求实的目的,提倡简字去文,扫除世上那些迷惑人的东西,从而使人‘反朴还淳’。孔圣人是在“删经”而非“增经”――这无疑是对今人追求著书立说,为文呈奇斗艳行为的讽刺,从而给当时那些不求实务而整日逐泥于虚文却自诩为遵循孔子“立言”之训的人以釜底抽薪一击。在他看来,所有汲汲于追求“文”的举动都是虚的,都是不必要的。甚至,他进一步否定了文体的差别,(《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第10页)
王阳明认为史用说事的方式来说心,经用讲道的方式来说心,二者只是形式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是他文论观第一点文理一物的具体表现,换而言之,即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文这个本体的存在,又何来关注文的技巧、方式、优劣之说呢?文本不存在,文体的差别当然也不存在了。那么,世人所关注的所有关于文的好与坏的评价标准、作文的技巧与方法、文体的差别等等都只不过是虚妄的幻象罢了,过多注意这些,反而“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所谓”,因此他主张“去文求实”“删繁就简”。
三、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
王阳明特别重视戏曲即文的作用,他认为戏曲堪与古乐相比,都具有教化人心的能力。在他眼中,韶与九变等经典之作也不过是一出戏罢了,如若将今天戏曲中的‘妖词淫调’去掉,去其粗,“只取忠臣孝子故事”,留其精未尝就不是今天的韶,未尝就不是今天的九变。所以他积极的利用“文”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
他非常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并将其诉诸实践,将其因势利导的应用于对学生的教育中。正如前文讲述经和史的关系一样,在王阳明眼中,戏曲和诗歌地位上也是没有区别的,二者只要能传道、传理、传心,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就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这充分展示出他对文学社会功用的重视。
- 上一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 下一篇:电子商务的行业分析范文
相关文章阅读
精选范文推荐
- 1孔子
- 2孔子世家
- 3孔子儒家思想的利与弊
- 4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
- 5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 6孔子删诗说
- 7孔子名言
- 8孔子启发式教学
- 9孔子启发式教学思想
- 10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