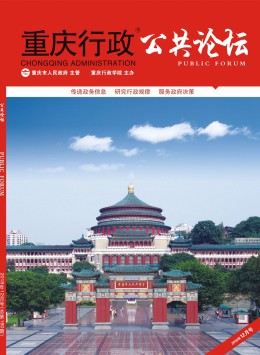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1.“设定”可以分为广义上的设定和狭义上的设定两种。《行政处罚法》第二章标题上的“设定”是广义上的设定,而具体条款中的“设定”是狭义上的设定。对行政处罚狭义上的设定,系指在上位法尚无对行政处罚作出设定的条件下,下位法率先对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作出规定。对行政处罚的规定,系指在上位法已对行政处罚作出设定的条件下,在上级规范性文件所设定的处罚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再作具体的规定。广义上的设定包括狭义上的设定和规定。所以,行政处罚设定也包括广义上的行政处罚设定和狭义上的行政处罚设定两种,广义上的行政处罚设定包括狭义上的行政处罚设定和行政处罚规定。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基本相同。
2.行政处罚设定权,是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创设行政处罚规范的权力。从本质上看,行政处罚设定权就是一种创设行政处罚的权力,它可以使本来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行为,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规定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而行为人就有可能受到相应处罚。设定是一种立法活动,是一种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活动,设定权属于创制性立法。规定权是在罚则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罚种和幅度内结合实施的需要,对罚则的规定加以具体化,属于执行性立法。设定是从无到有,规定是从有到具体,是对已有的设定进一步具体化。这一观点排除了行政处罚设定具有广义上的设定的观点。认为行政处罚设定就是一种立法活动,仅指从无到有的创制活动,不包括规定权。综上,不难发现分歧在于行政处罚设定权是否包含规定权。“设定”一词是《行政处罚法》首次提出的,虽然“设定”的通常含义是创设与规定的意思,但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用语,其具体意思必须放在具体语境中,结合《行政处罚法》的体系进行分析。
在《行政处罚法》中共有11处“设定”,分别是第1、2、4、9、10、11、12、13、14条和第二章的标题。通过对《行政处罚法》具体法律规范上的分析和把握,显而易见“,设定”有别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在我国法律规范中“,规定”一词大量存在,比如《立法法》中就有66处之多。通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在一般意义上,“规定”既包括“设定”(创设新的法律规则),也包括对已有的法律规则作出“具体规定”。所以,这时的规定反而包含设定。具体分析《行政处罚法》中11处“设定”可以发现:首先,作为第二章的标题,统领第二章的全部具体内容,其中的“设定”是否包括规定呢?《立法法》第54条规定:“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可以通过章的设置情况,了解到法律的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法律的章是具体法律规范的高度概括,它有助于人们透过纷繁冗长的法条文句迅速抓住该法条的核心规范,也有助于人们提纲挈领地把握该法条的整体内涵。因此,章是对其统辖下的具体法律规范的高度概括,虽然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但也只是主要内容,并不是具体条文的全部内容,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讲,《行政处罚法》第二章标题中的“设定”一词并不必然包括“规定”。其次,设定权属于立法权,是国家机关行使立法权的表现。而规定权只是对已有法律规范的具体化,没有创造性,不属于立法权的范畴。虽然在设定具体行政处罚时,也会有处罚内容的具体规定,比如处罚幅度,但这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设行为,是设定权的一种具体表现。设定权表现内容的“具体规定”不是规定权。另外,一部法律即使把其他法律内容原封不动地纳入自己的条文中,也属于行使了规定权。当然,前提是其内容不与高位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冲突。《行政处罚法》从第10条到第13条规定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定权,这可能是一部分学者坚持设定权包括规定权的原因之一。但从法学原理出发,既然《宪法》赋予了一些国家机关可以在不与高位阶规范性法律文件相抵触的情况下,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因此,即使《行政处罚法》不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的处罚规定权,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也当然地享有相应的行政处罚规定权。而行政处罚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充分考虑我国当时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状况、各级执法部门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法治建设的需要,所以才特别作规定。而且,具体分析《行政处罚法》第10条到第13条可以发现,“设定”与“规定”、“具体规定”是明显不同的。“设定”在行政处罚法中始终是指设定权“;具体规定”是指规定权“;规定”既含有设定权也含有规定权。《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了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第7款则是为了防止现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处罚的遗漏和预防今后立法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处罚措施而设定。所以该处的“规定”含有创设的意思,包含设定权。所以,《行政处罚法》中的“设定”仅指从无到有的设定权,不包括规定权。
二、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性质
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性质,通说认为,行政处罚设定权属于立法权范畴。行政处罚的设定是指国家机关依照职权和实际需要,在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中,自行创制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其特点是,国家机关依据职权自行创设,属于立法权的范畴[8]。立法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创制法律规范活动。行政处罚是具有制裁性质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处罚,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或者权利能力被剥夺或者受到限制,或者行政相对人被强制要求履行义务。拥有行政处罚设定权即可以自行创制设定行政处罚,从而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对于哪些违法行为应处罚、实施什么种类的处罚、在某一种类中实施什么程度的处罚、由什么机关去实施处罚、该机关依据什么程序去处罚、受处罚人不履行义务时如何去强制执行、受处罚人在处罚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等等,这些无不涉及权利义务关系[5]61-62。所以,设定权是通过创设行政处罚的方式,调整社会权利义务关系,属于立法权范畴。正因为如此,行政处罚设定权通常由立法机关行使,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不得行使,以防止这些国家机关和组织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设定行政处罚,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例如,《奥地利行政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只依法律实施;在德国,设定权集中在联邦议会,联邦政府和各地原则上不能超越联邦议会规定的原则另行设定新的行政处罚;在美国,处罚的设定权由国会行使;在日本,设定权主要集中在国会,内阁及内阁各省非经法律的特别授权不得制定罚则;在意大利,设定权只掌握在国会和20个地区议会手中,地区议会的规定不得设定;在新加坡,设定权集中在国会,行政机关只能依据议会的法令规定处罚的具体标准。
三、行政处罚设定行为
第2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壹、前言 法律是以建立并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为目的,在此理念下所形成之创作物,而此并非只是社会共同生活所期待或允许之「行为计划(Verhaltensplan)或「行为建议(Verhaltensvorschlag),而是一种具有「可实践性(Durschsetzbarkeit)与「可强制性(Erzwingbarkeit)之行为规范。因此,法律所建立及维持之法律秩序,是一种经由外力强制的他律作用所形成,其与经由个人道德或社会伦理之自律作用所形成的伦理秩序,显有不同。 以刑法规范与刑罚制裁而言,其虽是国家维护社会治安,强而有力的法制,但绝非治安的万灵丹,是一种基于理性考量不得已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刑罚的强制制裁,动辄剥夺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与人权人道密不可分。德国刑法学家Gallas氏即言:「刑法的制裁作用,并非一种实现正义的绝对目标,而祇是一种以正义的方式达成维护社会秩序目的时,不得不采用的必要手段而已。因此,自宪法保障基本权的精神,刑法的运用应在必要及合理的最小限度内为之。此一刑法谦抑的思想,实为贯通刑事法领域的基本理念。刑法之所以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于一定的犯罪行为,有效发挥刑罚制裁的作用,实系因其具有保护法益的功能。处罚犯罪与保护法益具有一体的两面性,而本于刑法谦抑主义及保护法益的关联性,可谓为刑罚的存在与正当化的依据之所在。德国的刑法学界更直认刑法就是一部「法益保护法,如果没有法益保护的必要性,自无刑罚的需要性可言。然而这一刑法立法的特色,面对社会的急速变迁与现代犯罪多样化的情势,面临着许多发展上的挑战。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侵害公共生活秩序的现象很多,几乎在民法、行政法的领域,均可发现法律的规范与处罚的效力;而其中刑法要加以处罚者,则以侵害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基本法益与价值为限,并非以每样不法的行为,做为处罚的对象。然而,民刑法与行政法之间,如何分工对抗违法的任务?就一项违法行为是否应或宜处以刑罚?或者课以行政处罚,即为已足?这是关系到立法者是否认定该项行为其有「犯罪性而定,属于刑事犯与行政犯区别的问题。究竟一个行为是否应该或者适合以刑罚为后盾,或以行政处罚为当,其间的取舍有无理论的根据,或者完全依靠政治利益做决定?是为刑法立法论上,应以探明的课题。为明了刑事犯与行政犯区别的问题,宜先探究刑事不法及行政不法之义涵,以下即从制裁法之体系,说明两者之意义。 贰、刑事不法及行政不法在制裁法体系之意义 (一)制裁法体系概说 法律既为一种具有「可实践性与「可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任何具有「禁止(Verboten)或「诫命(Geboten)内容的法律,均须设有制裁条款的规定,而作为违反「禁止或「诫命规定时之公权力制裁的依据,以发挥其规范的功能。透过这些公权力制裁的手段─「制裁法(Sanktionsrecht)而树立禁止规范与诚命规范不容违反的权威,建立并维系杜会共同生活所必需的法律秩序。 制裁法因其制裁权之依据、制裁手段与制裁对象之不同,可区分为下列三种: 1、刑事罚法:针对一般人之犯罪行为,而以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没收、号夺公权等「刑事刑罚(Kriminalstrafe)为制裁手段之刑法。 2、秩序罚法:针对一般人之秩序违反行为,以罚锾、勒令停工、停业或歇业、撤销许可等「行政罚(Verwaltungsstrafe)或「秩序罚(Ordnungsstrafe)为制裁手段的「行政罚法或「秩序罚法。 3、纪律罚法:针对公务员之违法失职行为,而以撤职、休职、降级、减俸、记过、申诫等「纪律罚(Disziplinarstrafe)为制裁手段的「纪律罚法。 其中纪律罚法,在台湾地区现行法制中因制订有「公务员惩戒法,属于行政法之领域,且与刑法有明确的界限,无需加以详细探讨。有问题者,乃刑事罚法与秩序罚法之界限。就某一制裁法而言,于如何条件下, 其应属刑事罚法抑或属于秩序罚法;或者于如何情形下,其应采取刑事刑罚的制裁手段抑或秩序罚的制裁手段。在探求此等问题之前,宜先对于制裁法体系中之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之概念有所厘清。 (二)刑事制裁法 刑事制裁法系规定刑事司法制裁之法律,此等法律规定之制裁权乃基于 「国家主权(Staatsgewalt)之发动而形成之「刑罚权(Strafgewalt),由隶属于司法权之法院,以刑事司法审判之方式,使用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事刑罚为制裁手段,行使刑事制裁权。由于此等制裁手段中,有极为严厉的生命刑与自由刑,对于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之剥夺或限制,既深且钜,在民主宪政国家大多将刑事制裁权授由独立审判的法院行使。 刑事制裁法在立法体例上,除采以一部具有系统性之独立「制典(Kodifikation),即刑法典加以规定外;尚分散规是在此一制典外之刑事单行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财税法、卫生法或环境法等罚则中。前者系规定犯罪与刑罚之主要法律 (Die srtafrechtlichen Hauptgesetz),故称为「主刑法;后者则居于辅助地位,辅助前者共同发挥刑法之规范功能,故称为「辅刑法或「附属刑法(Nebenstrafrecht)。 事实上,就刑事立法技术而言,不可能亦不必要将所有刑事制裁条款毫无遗漏地规定在一部主刑法法典中。故大陆法系多数国家之刑事立法体例系将犯罪之一般共通要件,以及各种主要的犯罪行为,汇编成一部具有系统性之「制典,以作为刑法规范的主要法律。再分就特定事项,制定个别的刑事单行法,以补刑法法典之不足。不论是主刑法中所制裁之不法行为或者辅刑法中以刑事刑罚所制裁之不法行为,皆为具有「刑事不法(Kriminalunrecht)本质的犯罪行为,或称为 「可罚行为(Die strafbare Handlungen)。从刑法犯罪理论以观,其所制裁之犯罪行为乃指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Tatbestandsm??igkeit)、「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与「罪责(Schuld),而应科以刑事刑罚之刑事不法行为。行政机关对于这些犯罪行为,仅能居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告发人之地位向检察官告发,经由检察官之侦查,提起公诉,并由法院审判。即使在辅刑法中,行政机关亦不能因此等犯罪行为规定在其行政主管业务有关之行政法中,而回径行依法处罚。因为,辅刑法所规定处罚的犯罪行为,仅是立法技术上或立法 体例上,规定在主刑法法典以外之法律中,而与主刑法法典所规定处罚之犯罪行为,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其在行为本质上成在法律效果或定罪科刑之法定程序上,均无不同之处。故附属在主刑法法典以外之辅刑法所规定处罚之犯罪行为,其本质上亦属刑事不法行为。对于此等本质上亦属刑事不法的犯罪行为之处罚,自无必要另外制订一套原理原则以为适用。 (三)行政制裁法 行政制裁法系规定以罚锾、勒令停工、停业或歇业等秩序罚为手段,而赋予行政机关裁决权与执行权,以科处「秩序违反行为(Ordnungswidrigkeit)之行政法。行政制裁权乃属于行政机关,其基于行政权之发动所为的制裁,与司法机关行使之刑罚权,迥然有别,其制裁之行为在「不法内涵(Unrechtsgehalt)上,显较刑事制裁之犯罪行为为低,在本质上亦仅属「行政不法(Vewaltungsunrecht),而非属刑事不法。 行政不法因其不法内涵远较刑事不法为低,可授权行政机关裁决并执行之,而不必经由法院依刑事诉讼法之程序而为审判。一方面,法院因为不必负责对于此等不法内涵较低之不法行为之广罚,故可集中其力量,做好犯罪行为之审判工作,以发挥刑事司法之功能;另一方面,则因制裁程序之简易迅便.各类不同之行政机关,均可据之以制裁与其行政业务有关之秩序违反行为,而使行政权得以发挥其建立并维持行政秩序之功能。 行政制裁法因系由行政机关管辖,且使用秩序罚作为制裁手段,并非如刑事制裁法系由司法机关管辖而使用刑罚作为制裁手段,自不适用刑法总则规定之处罚犯罪行为之原则,亦不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之程序以为处罚。故行政制裁法除分散于各形各色 行政法之实体制裁规定外,仍须有一部规定完整之处罚总则与处罚程序之法律,以作为各种行政机关科处秩序违反行为之总则与程序之依据。 参、刑事犯与行政犯区别之理论 (一)概说 在制裁法的体系中,对于不法行为既有刑事不法及行政不法之别,而形成不同之制裁法系统,从而刑事犯与行政犯(Straftaten und Ordnungswidrigkeiten)即应有所区别。对此一问题,学理上有本于传统的「自然犯与「法定犯的概念,即罗马法所谓「mala in se与「mala prohibita的观念,认为刑事犯是属于自然犯,也就是指一个实质上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违法行为,因侵害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为一般社会正义所不容者;而行政犯乃属法定犯的性质,其行为在本质上并不违反伦理道德,但是为了因应情势的需要,或贯彻行政措施的目的,对于违反行政义务者,加以处罚。 从刑事犯着重于伦理的侵害性观点,与行政犯着重于行政技术秩序的观点而言,两者在本质上具有「质(qualitative)方面的区别,为学说及判例所肯定。然而此等理论随着福利国家理念的发展,有许多社会保育行政、经济行政的措施,虽然假借行政管理的方式进行,但其内容却与国民全体的福祉息息相关,而逐渐产生社会伦理的感情。立法上许多诸如环境行政刑罚、经济行政刑罚及卫生行政刑罚之类的特别刑法或行政罚则的运用,使得原有的刑事犯与行政犯的区别界限,亦发生动摇,两另有「量(quantative)方面的差别理论出现,影响刑事犯基本概念的体系[12]。 对于行政犯明确设定定义规定的的立法例,首推德国一九六八年五月甘四日公布,并于一九八七年重新修正公布的秩序违反法(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其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违反秩序之行为,系指该当可处以罚锾的法律构成要件之违法与可责之行为。然而,法规上形式的定义,却无法解决,立法者在何种情况之下,对于一项违法的行为,应该规定处以刑罚或者处以行政罚,甚至于均不予处罚?其判断有何理论上的依据?这些问题也关系到,由于当代社会变迁的需要,为了经济行政、交通秩序、环境行政的目的,而增加「行政刑罚(Verwaltungsstrafe)或行政附属刑罚(Nebenstrafe),以致行政犯之立法愈益扩张范围,而形成刑法的肥大症(Hypertrophy)[13],影响刑法的体系功能。在此,有从刑事犯与行政犯的定义理论,加以探讨的心耍。以刑事犯与行政犯区别的理论而言,大抵可分为「质的区分说、「量的区分说及「质量的区分说。 (二)质的区分说 传统的学说从二十世纪之初起,倡导「违法性质区分说(Unrechtsqualit?t),以学者Frank,Goldschmidt,M.E. Mayer,Erik Wolf,Ebhard Schmidt等为主要代表[14]。依照性质区分说的见解,一般刑事犯或司法犯(Justizdelikt)是指具有特定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而行政犯(Verwaltungsdelikt)则指对于行政作用秩序的维持,违反服从义务的行为而言,也即行政犯仅关系于「行政利益的侵害,而非「法益侵害的问题。从而,行政秩序犯的处罚意旨,乃是一种「义务的警告(Pflichtenmahnung)与刑罚之具有「伦理、社会的非难性,性质迥异[15]。 法律哲学家Erik Wolf从价值论哲学的立场,对刑事犯与行政犯价值判断的区别问题,认为:刑事犯牵涉的是个人权益及文化的损害,而行政犯则牵涉特别性的社会损害。因此,刑事犯是有关「正义价值(Gerechtigkeitswert)的行为,行政犯则是一种有关「福利价值(Wohlfahrswert)的行为;前者应属司法管辖,而后者则属行政权力管辖的对象[16]。 违法性质区分理论曾经深远影响德国法制,对于刑法上的「轻微犯(Bagatelldelikt),「违警罪(übertretung)与行政犯之区别,提供判别的理论依据,更由Eberhard Sch midt予以发扬光大,而应用于经济刑法的立法之中[17]。德国于第二次大战期间,政府曾颁行各种财经管制法令,战后为了稳定经济秩序,重新整理法规体系,于一九四九年制定新设计的「经济刑法(Wirtschraftsstrafrecht),就应受处罚的经济、犯罪行为,采用「混合的构成要件(Mischtatbest?nde)的立法方式,依行为事实的内容,合于该法所定的构成要件,堪以认定为犯罪时,则科以刑事制裁;反之,如认定性质仅属行政目的者,则祇系行政违反而科以行政罚锾(Geldbu?e)。从而在传统的刑事犯与行政犯之间,产生中间类型的「行政刑法或「行政刑罚的概念[18]。在此意义之下,行政刑法(经济刑法)概念上实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行政刑法是指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制裁的部份而言;广义的行政刑法则兼指构成行政秩序之违反,应受行政罚锾的情形在内。其间的区别,端赖实质的违法性质的区别去认定[19]。 德国联邦法院判例,曾经明采实质的违法性质区别理论,认为:「刑法上的违法,是属于一项特别伦理价值的判断;而行政上的违法,则是属于单纯不服从行政命令的事项(BGHSt 11,263ff.,264)。从「质能及「价值区分的法理观点,奠定了行政犯的概念体系。 至于日本,往昔主要理论见解亦从「伦理价值论出发,配合「自然犯与「法定犯对立的观念,而认为刑事犯是思于自然犯的范时。如学者美浓部达吉认为刑事犯的本身即含有社会的罪恶性,国家法律加以规定的用意,并非在于创设其行为的当为性,做为法律禁止或命令的基础,而仅是在于宣示各种罪恶性的行为,应得的罪刑而已;盖自然犯本身,不待国家法令的规定,而依其自身的伦理意识与社会价值观念,本可认识其违法性,而求免于罪戾。反之,行政犯乃是法定犯,其行为本身初不含有反道义性、反社会性,仅因法规加以禁止或命令的结果,始拟制予处罚效果[20]。 然而传统理论对于当代立法的发展,却仍未能自圆其说。一方面在法律思想上,由于福利国家理念的实现,个人、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协同存在关系的形成,使得刑法保护法益的观念,也产生质与量的变化;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许多与社会福利及重大民生有关的行政管制事项,也有升高其法益地位的现象;而国家司法除了保障正义的任务以外,也有追求民主福利的使命。他方面在实际立法上,为了强化大众生命与健康的安全,也将许多抽象性的危险行为,提升到刑事犯的范畴,例如交通运输的安全罚则、医疗卫生罚则、环境刑法等等;并且为了有效保障民生经济秩序,轨许多传统犯罪类型的准备行为,也从中间类型的规定,例如属于诈欺罪前阶行为的骗取手段的构成要件(Erschleichungstatbest?nde)正式纳入诈取国家补贴的经济犯罪的立法规定之中,上述行政犯与刑事犯中问类型的「法定犯(行政刑法)应运而生,使得上述性质区别理论的界限,发生动摇[21]。 (三)量的区分说 量的区别说又可分成两派,一派是否认一切区别意义,另一派则是承认以「行为之轻重作为量的区别。 1、否认一切区别意义说 主张此说之学者有Wachenfeld及Berolzheimer,其主要见解认为行政不法亦含有「法益之侵害或危险,故否认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区别意义[22]。 2、以行为之轻重程度为区别标准 此说亦根本否认行政不法行为与刑事不法行为间有任何「质的差异,而认为至多仅在行为违法性之轻重程度不同,而具有「量的差异而已。换言之,此派学者认为行政不法行为祇是一种比犯罪行为具有较轻的损害性与危险性的不法行为,或者是在行为方式上欠如同犯罪行为的高度可责性的不法行为,行政犯或违警犯在事实上即是一 种「轻微罪行(Begatelldelikte)[23]。 主张此说者在德国早期系以Fritz Trops为代表,有不少学者持相同或类似之见解,如Ernst Beling、R.von Hippel、H.Mayer、W. Sauer、P. Bock elmann、H.H. Jescheck、Welzel等。以下仅以Fritz Trop、H.H. Jescheck、Welzel三人之论述为代表: (1)Fritz Trops之见解 氏认为一切刑法规范皆应以「可罚的行为为其统一的基本概念,行政刑法乃是刑法之一部分,而非行政法,因而在刑事类型化的基本原则上行政犯同样受其支配。申言之,行政犯与刑事犯皆系受刑罚科处之可罚行为,在构成事实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方面全然无异,就此概念已是否定二者间有何质的差异。同时,行政犯与刑事两类犯罪规定,在保护客体(Schutzobjekte)方面,根本欠缺实质的区别,至多不过程度之差异而已。就法益概念以论定实质违法性,其概念并不确实,实际上某些行政犯之违法要素在刑事犯亦复常见。反之,在刑事犯方面,有些违法类型究系侵害何法益,往往不甚明了[24]。 (2)H.H. Jescheck之见解 氏认为秩序违反行为即为行政不法行为,对于秩序违反行为之处罚,系因对保护法益或行政利益的相当程度之攻击危险性,其公共秩序之保护,以国家压制性的制裁即为已足,并以这些观点与 「契约侵害(Vertragsverletzung)及 「警察违反(Polizeiwidrigkeit)相区别。秩序违反之危险性程度比刑事不法行为要来得轻微,其对所保护之行为客体(Handlungsobjekt)的妨害,大都是轻微的。而秩序违反行为与刑事不法行为更重要的区别是在于其缺乏「高度的行为者节操之非难性(hohe Grad von Verweiflichkeit der T?tergesinnung)。此种非难性在刑事不法行为上,却同将重大杜会伦理之非价判断正当化。秩序违反行为并以罚锾来主张其仅系一种「激烈的行政命令(Verscharfer Verwaltungsbefehl)或者「特别的义务敦促(besondere Pflichtenmahung),而未达「无法忍受的风俗违反性。故不可以为秩序违反规范不含法益的保护。秩序违反行为亦非「与杜会伦理无关的懈感(sozialetish farblose Lassigkeiten)。从而秩序违反行为与刑事不法行为之区别,并非本质上的差异,而是程度上差别。故立法者对刑法核心以外的部分,依实证的观点加以决定,不法行为究应列入制裁法体系?或者对之以完全无压制性的制裁[25]。 (3)Welzel氏见解 氏认为并无所谓自然的,或者自然法的「犯罪构成要件(Deliktstatbest?nde),将刑法的核心部分视为自然法是不合理的。刑法典核心部分的重要历史性本质,与人类本质的历史性不可分割。从刑法的核心部分开始,有一条逐渐微弱,但决非消失的实质不法长线,一直延绩到与核心部分远离的轻微犯罪,即使秩序违反行为,亦与此一长线联结一起。国家订立命今与禁止规定,并非要求市民服从,而是在于有「法的价值状况(rechtliche wertvollen Zustand)或事象(Vorgang),或者阻止一个非价情事(Sachverhaltenwert)[26]。 不仅学界理论的转变,联邦宪法法院亦改采依违法内容情节的轻重,做为判别标准的倾向,而认为行政犯所显示的违法内容,是较刑事犯为轻微的看法,且将「情势配合原则、「法益衡平原则及「度量理论引进于「法律法益与「行政利益的区别思考之中[27]。从而,德国的立法及法律见解,遂渐改以「行为的危险程度(Grad von Gef?hrlichkeit)做为该行为可罚性(Strafwürdigkeit)判别标准。准此,则行政犯的情节也非完全「无视于社会伦理的评价(sozialethisch farblose L?ssigkeit)[28]。 (四)质量的区分说 此系质的区别说及量的区别说之综合见解。此说认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两者不仅在行为的量上,而且在行为的质上均有所差异。刑事不法行为在质上显然具有较深度的伦理非价内容与杜会伦理的非难性,而且在重土具有较高 的损害性与杜会危险性;相对地,行政不法行为在质上具有较低的伦理可责性,或者不具有杜会伦理的非价内容,而且其在量上亦不具存重大的损害性与杜会危险性[29]。 Robemann、Roth及Herrmann氏即谓「观察秩序违反的实质扩充后,不能再主张法益保护应保留在刑法内,因为现代的秩序违反法,已逾越单纯行政不服从而扩及于法益保护。亦即,秩序违反法已将其所规定的不法行为,从法益的危险变为法益的妨害。由此可知,在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业杜会中,国家行政的顺畅机能,在经济、交通及一般社会国的保护领域内,都被评价为法益。从而,一般的秩序违反法亦构成法益保护。故任一秩序违反,将如同刑法构成要件保护之法益受到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系不可或缺之个人及其团体的利益,其在人类杜会中之所以被侵害,乃因维持和平秩序之必要性未为组成份子共同接受。而秩序违反法所保护者,虽系在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中,轻微或者欠缺杜会伦理根源,但仍不可放弃的价值。属于刑法核心领域的所有重要不法构成要件,皆具相当的杜会伦理不法内涵。相对的,秩序违反的核心领域仅为罚锾构成要件,其侵害并非违反伦理基本价值,而是有助行政顺利完成其任务的利益。故刑事不法与秩序不法间,法益侵害的「界限领域(Grenzbereich),其实质意义的特征,乃量的区别而非质的区别。刑事不法行为与秩序违反行为,经由伦理非价内涵的程度,而加以区别。秩序违反仅及轻微不法内涵事件,其在一般杜会上并无刑罚价值[30]。 事实上,对于一个不法行为的评价,当然应该质与量兼顾,否则可能顾此失彼,而无法明确而妥善地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在质与量兼顾之情形下,从事不法行为的评价工作时,应依据下述四个标准而决定[31]: 1、不法行为在伦理道德上之非难性。此乃对于不法行为本身的价值判断。 2、不法行为所破坏与危及之法益的价值与程度。此乃对于不法行为所生结果的价值判断。通常法益的价值乃依法益在杜会秩序与杜会共同生活中的地位来决定,如专属法益高于财产法益。 3、不法行为的杜会危险性,此亦即是国家对于该不法行为加以制止的必要性。 4、刑罚之无可避免性。 依据前述的四个标准而认定某一不法行为具有较高度的杜会伦理可责性,且自其所侵害或其危及的法益具有重大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因而,务必深具伦理非难性的刑事刑罚以作为反应手段,冀求有效地阻止此一不法行为。在此种情况下,让不法行为即具有刑罚之无可避免性。某些不法行为虽然其伦理非价内容并不很高,但却可能造成甚为严重的后果,对于社会共同生活具有很高的危险性,如不少经济违反行为,基于经济安穿秩序维护之必要,而赋予此等不法行为刑罚的法律效果,则此等不法行为亦具有刑罚的无可避免性[32]。 肆、结论 刑事犯与行政犯的区别界限问题,从刑法的角度观之,实质上涉及一项行为,是否因为违法而具「有可罚性或「应刑罚性(Strafwürdigkeit)认定问题[33]。在社会福利国家的理念之下,行政秩序的违反,也并非绝对与社会伦理的价值无涉。盖人民相互问对于法律的信赖,与守法的修养也是最基本的工商社会伦理。如德国Jescheck教授所言,两者之间的差别,仅是危险程度的考量而已。这种见解为德国联邦法院接受,立法者在核心刑法的范围之外,亦得依据实务的观点,就运法行为的危险性,决定其处罚的手段,或者甚至是否设定禁止的处罚等问题,宜从社会需要与政策的观点,予以考量。然而一旦立法者选择了处罚的立法方式,行政犯与刑事犯则各有其概念体系与适用法则,不能因界限在「质能上没有绝对的分界,贸然认为刑法的规定得毫无限制的适用到行政犯[34]。 行政犯处罚规定并非刑法犯罪概念结构的一部份,其立法的原则,包括:处罚法定主义原则、责任主义原则、共犯及法人责任的规定等等。然而刑法理论上的研究,如德国学者Lange所见,主张行政违反行为的「故意必须以违反规范的意识做为前题,与刑法上的「故意可能具有双重的地位关系,亦颇值注意。有关违法性认识与责任的基 础,是否行政犯与刑事犯亦有统一性的理论基础,则是值得详加探究的问题[35]。 综上所述,吾人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之区别,似可采质量区别说。即在判断违法行为时,应加入社会论理价值之因素,打破所谓「核心领域及「边界地带之界限,成为由刑罚到行政秩序罚之间的光谱式之型态。并应综合以下六种可能影响不法行为轻重之因素决定:一、非难性之程度;二、危险之程度;三、法益之侵害;四、发生之频率与数量;五、制裁制度之特性;六、权力分立之理念[36]。 林山田,「论制裁法之体系,载于氏着「刑事法论丛(一),一九八七年五月,页189。 Wilhem Gallas, Beitrag zur Vergrechenslehre, 1968, S. 4. Otto Harro, Rechtsgutsbegriff und Deliktstatbestand, in:Heinz Müller-Dietz, 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 K?ln, 1971, S.1 林山田,「使用刑罚或秩序罚之立法考量,刑事法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期,1990年2月,页1。 吴耀宗,「武器管制法制之研究,1993年4月,页113以下。 林山田,「刑法通论,1988年5月,页9-10。 林山田,前揭书,页62-65。 吴耀宗,前揭书,页116。 林山田,前揭文(注1),页193。 吴耀宗,前揭书,页117。 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六十九年第十卷第一期,页4;苏俊雄,「从刑事犯与行政犯之理论界限论刑法修正之问题,『法学论丛,六十五年第八十一及八十二期,页74-77。 [12]田中二郎,「行政法总论,『有斐阁法律学全集,页404-425;上揭拙著,页74以下。 [13] Baumann /Web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9.Aufl. 1986, S.38. [14] Baumann /Weber, a.a.O., S.39. [15] James Goldschmidt, Das Verwaltungsstrafrecht, 1902., Maurach/Zipf Lehrbuch AT 1, 6.Aufl. 1983, §8 Rdnr.26 ff. [16] Erik Wolf, Die Stellung der Verwaltungsdelikt im Strafrechtssystem Festgabe für R. v. Franf, Bd II, 1930, S.516. [17] Ebenhard Schmidt, Problemdes Wirtschaftsstrafrechts, SJZ, 1984;Straftaten und Ordnungswidrigkeiten Erinnerungen an die Arbeiten der Wirtschaftsstrafrechtskommission(1947-1948), in Festschrift für Adolf Arndt, Frankfurt 1969, S. 415ff. [18]行政刑罚由于使用 刑罚之刑名,属于特别刑法之一种,由法院审理而非由行政机关为处罚主体,不宜认为系行政罚。参照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八十九年八月修订七版,页379。 [19] Ebenhard Schmidt, a.a.O. [20]美浓部达吉,「行政刑法概论,昭和十四年,劲草房刊行,转引自苏俊雄,「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区别理论对现代刑事立法的作用,刑事法杂志第37卷1期,1993年2月,页29。 [21] 苏俊雄,前揭文,页28。 [22] 郑善印,「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区别-德、日学说比较1990年四月,页129-130。 [23] 林山田,「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刑事法杂志第20卷第2期,1976年4月页38-39。 [24] 韩忠谟,前揭文(注11),页56-57。 [25] H.H. Jescheck,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 Teil , SS.45、46. [26] 郑善印,前揭书,页119。 [27] BverfGE, 8,197(201);22,49(78ff.) [28] H. Jescheck, Das deutsche Wirtschaftstrafrecht, JZ 1959, S. 461. [29] 林山田,前揭文(注23),页120。 [30] Robemann/Roth/Herrmann, 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Kommentar. 2 Aufl., 1988, SS.7-9. [31] 郑善印,前揭书,页145。 [32] 林山田,前揭文(注23),页44-45。 [33]对于刑法上的观点,就轻微的案件,是否认定其有「可罚的违法性的问题,学者及实务界已多有讨论。参见甘添贵,「可罚的违法性之理论,1992年最高法院院学术研究会,可罚违法性理论与司法实务研究讨论会资料料;洪福增,「可罚的违法性的理论,收录于「刑法理论之基础。 [34]苏俊雄,前揭文,页29。 [35] Jescheck, Neue Straf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 ZStw. 98(1986), S.12;Lange, Der Strafgesetzgeber und die Schuldlehre, JZ 1965, S.73.;Lange, Nur eine Ordnungswidrigkeit?, JZ 1957, S.233. [36] 洪家殷,「论行政序罚之概念及其与刑罚之界限,东吴法律学报第9卷第2 期,页104以下。
第3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关键词】: 行政公告 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的告知
一、源自现实的问题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本条例所列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
《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以及保护期满的中药品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指定的专业报刊上予以公告。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定期发布药品质量公告。药品质量公告应当包括抽验药品的品名、检品来源、生产 企业 、生产批号、药品规格、检验机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内容。
某市卫生局对该市纯净水市场中不同品牌的饮用水进行了大抽查,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公告了抽查结果,其中被认定存在质量问题的生产厂家认为,卫生局在抽查程序违法且没有合理和 科学 依据的情况下,公告抽查结果,影响了该厂的声誉,致使其市场占有量明显减少,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故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1]
笔者以上所罗列的现实 法律 规范和案例,旨在表明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发布有关行政权行使信息的法律现象。我们姑且将这种以公告形式实现行政目标的行为称为行政公告。然行政公告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否有足够的法理支撑、应具备哪些构成要素等问题,都有赖于对行政公告的分析和论证。
二、行政公告释义
行政公告并非法律概念,充其量只是法学概念。受研究者兴趣偏好与精力所限,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对行政公告的专门研究非常匮乏,[2]行政公告作为普遍存在的行政法律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含义
纷繁复杂的行政公告现象背后,其共性在于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所赋予的职权,通过公告形式来实现预期的行政目标。据此,行政公告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履行职权,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通过公告形式,将与行政职权行使相关的信息向社会公布的一项行政法律制度。
首先,行政公告只是对一定法律现象形式上的概括,而不是性质上的厘定。现行行政法学研究,都是在界定行政主体行为内容性质的基础上,对形式上具有共性的行为作归类研究。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都是在界定其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这种本质属性基础上,对形式上具有共性的法律现象的概括。而行政公告不是对其意指的法律现象性质上的概括,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特定行政目标的纷杂法律现象形式上共性的概括。这表明,行政公告作为法学概念,与现行行政行为具体范畴和种类是不同层面意义上的所指,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行政公告是履行行政职责的表现。依行为性质的不同,行政机关可以有民事主体、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甚至是刑事责任主体的不同身份。行政法所关注的只是行政机关以行政主体身份出现时所表现的权利义务状态。本文的行政公告,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时的公告,虽以公告方式行为,若不是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行政职责,则不在行政法学研究领域范围内,也不是本文所指的行政公告。
(二)种类
不同形态的行政公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法律性质、救济途径等可能存在差别,对不同形态的行政公告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划分,是非常必要的。基于前文是从形式上界定行政公告,以行政公告内容的形式特征为标准,对行政公告进行类型化分析是可行的路径。[3]据此,行政公告可以分为:
1.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告
它是指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将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报纸、新闻媒体、特定公共场所张贴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布的一种行政公告。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规范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特定性,通过对每个被规范对象的具体送达不具备现实性与可行性,故只有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布。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所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向社会所发布的公告。
2.行政处理公告
它是指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将其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行政处理由于涉及特定的当事人,应该遵循政府行政相对性的要求,不得对社会公开,这是公民隐私权保护的需要。然原则依托例外而存在,在特定情况下,因某种因素的介入,行政处理决定可能会丧失“私”的特性,而必须向社会公开。虽然行政处理公告的法理根基、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现实中不乏行政处理公告的现象。如:《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对单位和个人的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
3.其他行政信息公告
从广义上来理解,一切有关行政权行使条件、范围、过程、内容以及后果等因素都可称之为行政信息。但行政法所指的行政信息,应是与行政权行使直接有关的信息。其他行政信息公告是指,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将除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处理决定之外的,其他直接有关行政权行使的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布。这类行政公告在法律实践中非常普遍,如药品监督行政主体公布药品抽查结果等。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其他行政信息公告的规定,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三)相关概念辨析
行政公告作为行政目标实现的手段,它与其他行政手段或者行政法律现象之间的异同比较,有利于其自身内涵的界定和阐释。
1.行政公告与行政行为的告知
依通说,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该行政行为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包括拟制行政行为的依据、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的告知。[4]作为向相对人告知一定的内容,行政公告与行政行为的告知具有一定的重合之处,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既属于行政公告范畴,也可以划归行政行为告知的范畴;且两者之间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呈现性质上的一致性。[5]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1)对象和表现形式不同。行政公告是行政主体通过报刊、新闻媒介、公共场所布告等可见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有关行政信息的活动,它的表现形式一般是书面的。而行政行为的告知中,如拟制行政行为依据、陈述意见机会等,都是通过口头或书面向特定相对人进行告知。
(2)内容不同。行政公告的内容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其他行政信息,而行政行为的告知内容包括拟制行政行为的依据、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等。前者较概括和抽象,后者较为具体和细化。
2.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当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时,行政主体可以用公告形式向相对人送达行政处理决定。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一定期间,视为送达。它与行政公告存在以下差别:
(1)性质上,行政公告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行政目标的各种法律现象形式上的概括,不能反映这些法律现象的本质属性,不同的行政公告有不同的法律性质。而公告送达是程序性法律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
(2)内容上,行政公告的内容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其他行政信息;而公告送达的内容是行政处理决定,至少在现今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语境下是如此,而不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送达。[6]
(3)对象上,行政公告的对象可以是特定而具体的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非特定的社会公众;而公告送达,在一般情况下,其送达对象为具体、可数的行政相对人。
三、行政公告的性质
本文是从形式上对行政公告内涵作了界定,然真正决定行政公告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法律救济途径等根本性问题的是行政公告的性质。所谓行政公告的性质,是指行政公告是否属于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现有权利义务状态的行政行为范畴。行政公告包罗万千,不同种类的行政公告有不同的性质。
(一)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
判断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其形式是其次,关键在于行为内容能否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行政公告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取决于行政公告具体内容是否对相对人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变化。一般而言,具备行政行为属性的典型行政公告有以下几种。
1.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
基于不同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行为可以有不同种类的划分。在非行政规范性文件领域,根据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有惩戒效果,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与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前者主要指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7]
之所以将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具有惩戒性质决定的公告,纳入行政行为范畴,而否定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公告的行政行为属性,是因为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现例举法律实践中的具体情形阐述如下。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本条例所列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据此,财政行政主体可以公告其作出的处罚、处分决定,该行政公告将对相对人现有权利义务状态产生影响,其缘由为:
(1)从立法意图来看。一般而言,行政处罚、处分决定只需送达相对人即可,行政处罚、处分决定无需、甚至不得向社会公开。立法者之所以赋予财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基础上,公告该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权力,使社会不特定公众知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存在以及所受的不利制裁,从而影响相对人的良好声誉和形象,其目的在于加强财政行政主体的管理力度以及行政权行使的有效性。故从立法意图来看,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公告具有影响相对人人身权的目的,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8]
(2)从公告的内容来看。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意味着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行为作了违法性的宣告和确认,这不仅可能对相对人的财产权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对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只局限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特定范围内。而通过公告行政处罚、处分决定,使得原本不知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其他社会公众获知该信息,使得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了新的不利影响或者扩大了原有的不利影响范围,这符合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2.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
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处理之外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是否会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没有统一的类型化标准。对于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信息只能作个体化分析,视其具体内容而定。一般而言,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在实践中有以下两种常见形式:
(1)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相对人若有违法行为,法律一般是规定了实体性内容的制裁措施,或者追加规定行政主体可以将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所作的制裁措施通过公告形式,公之与众,作为加重处罚。但有时,法律也会赋予行政主体可只公布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本身,而无需公布对违法行为所作的制裁决定。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虽然,这种公告行为可以理解为强制执行措施的一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将对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不利影响。这类行政公告因其具有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现实性,而被归入行政行为范畴。
(2)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一般而言,行政检查结果只是行政主体作出实体性裁定的基础。但有时候,法律授予行政主体可以公开行政检查结果,而不作实体性裁定。此时,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开,就可能影响到被检查人等相对人的权益,该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告就具有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此类行政公告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负有保证公民生活安全责任的行政主体,通过对有关公民生活安全的物品的监督和检查,向社会对其监督和检查结果所作的公告,如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质量监督部门、药品监督部门等对食品、生活用品、药品等是否符合相应质量、安全要求等检查结果所作的公告。如:《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定期发布药品质量公告。药品质量公告应当包括抽验药品的品名、检品来源、生产企业、生产批号、药品规格、检验机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内容。
(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
当行政公告不会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效果时,就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对象的不特定性,其公开方式只能选择公告的形式,以行政公告为载体。但是,实际上对相对人产生规范性约束的是该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行政公告本身,行政公告只是作为该规范性文件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或许有人会质疑,没有经过行政公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行政行为效力所具有的可分性表明,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有不同的效力,且效力发生的时间也不一致,[9]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只是一种附属性的程序行为,其本身不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10]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2.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告
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由于并不包含对相对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对该处理决定的公告,不会对相对人的人身权造成不利影响,类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法律实践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这种行政公告形式。如:
《煤炭法》第26条规定,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届满或者经批准开采范围内的煤炭资源已经枯竭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注销并公告。煤矿企业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经核查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吊销并公告。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1条规定,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应当向社会公告。
《专利法》第55条规定,专利局作出的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登记和公告。
3.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
除了对行政违法行为和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告之外,对于其他信息的公告,一般都不会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具备行政事实行为属性。如:
《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发布公告。
《防洪法》第25条规定,防洪保护区是指在防洪标准内受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
《执业医师法》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准予注册和注销注册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告,并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汇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四、行政公告的适用条件
现代 法治社会中,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影响他人 法律 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依据。[11]无论是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抑或作为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由于都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但行政公告的性质不同,即是否会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差别,其适用条件也不同。
(一)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适用条件
1.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适用条件
政府行政的相对性,以及过罚相当原则所要求的相对人不因自己违法行为而受到过度的不利影响等决定了,针对特定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一般不得向社会公开。但当有其他因素介入,经过利益衡量之后,可以允许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公开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具体而言,以下情况可适用行政公告:
(1)作为行政执行措施时。通过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使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的相对人的声誉等权益受到减损,给予其较大的压迫感,从而促使其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从这一层面上,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有作为行政执行措施的作用和属性。但若将所有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定性为行政执行措施,那么将导致这类公告游离于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之外,使得不具备行政公告条件的行政公告逃避司法权的监督,因为对于行政执行措施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若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是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情况下使用时,其就属于行政执行措施,否则就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相对人对此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2)行政处理决定本身的适用范围具有不特定性时。行政行为的执行力一般限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对于非行政行为当事人不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但是,某些特定情况下的行政处理决定,虽然其相对人是特定的,其内容却具有扩散性,导致了行政处理决定的适用范围具有不特定性和扩散性,要求非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予以执行。此时,该行政处理决定就须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不特定主体广为告知。这种公告形式在实践中并不鲜见:
如《招标投标法》第53条规定,投标人因违法行为而被取消参加今后招投标活动资格的,行政主体在作出取消其资格的决定后,应将决定公告。
《 金融 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受到开除或者撤职纪律处分的,由 中国 人民银行决定其终身不得在金融机构任职,并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
2.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适用条件
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主要包括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和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其有严格的适用条件限制,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之一:
(1)作为行政执行措施时。对于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主体一般应给予实体性的行政处罚或者处分,而不能只公告该行政违法行为。倘若违法行为相对人不履行处罚或者处分决定,那么行政主体可以采取公告该行政处罚、处分决定本身,或者只公告该违法行为相对人的违法事实,而不公告处罚、处分决定,以作为行政执行措施,督促相对人履行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义务。[12]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2)公共利益介入时。行政主体因履行职权而作的行政检查,一般只涉及特定的相对人,无需且也不能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但是,当行政主体所进行的检查或者其公布的检查结果,关系社会不特定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时,也即当该行政检查或者检查结果有公共利益因素介入时,行政主体应该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其检查情况。[13]如食品卫生监督主体对市场上特定食品的检查结果、质检部门对市场上关涉公民人身安全的生活用品等的检查结果,就应该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适用条件
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公共行政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者大众福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是公共行政的概念属性和功能属性。[14]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虽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但由于也属于行使行政权力的积极行为,行政权的公益性决定了其仍然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适用条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是其对外生效的前提条件,未经公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所以,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是制定主体的一项义务,只要存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其必须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2.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告适用条件
此类行政公告的适用条件应该是当该处理决定的内容有必要使社会不特定公众知悉,以便作为社会公众今后行为的指向或者借鉴的,行政主体才可以用公告形式公布该行政处理决定,否则不得公告。如:《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以及保护期满的中药品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指定的专业报刊上予以公告。
3.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适用条件
根据行政效益的要求,基于行政成本的考虑,该类行政公告的适用也应具备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在行政信息会对社会公众造成影响,确有必要时,行政主体可以公告,行政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发布公告。
五、行政公告的救济
作为行政目标实现手段的行政公告,由于其只是对众多法律现象的形式概括,作为独立的行政手段尚未得到明确和重视,行政法学界关注较少,行政立法和司法实践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认识,关于行政公告的救济,是一个有待规范的问题。
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制,均是以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为标准,来界定是否将行政行为纳入各自的救济体系。所以,应根据是否具有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属性,分别论证行政公告的救济途径。
(一)具有行政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的救济
属于行政行为性质的行政公告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以及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对于这些行政公告,由于其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且针对特定的相对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相对人若认为该行政公告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若认为该行政公告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15]
(二)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的救济
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由于它不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效果,所以此类行政公告不应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系。但必须注意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模糊状态的行政公告的救济问题,因为,行政事实行为存在向行政行为转变的可能。由于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标准,两者之间存在一些模糊、变动不居的状态。[16]在界定此类行政公告的救济途径时,必须坚持以最大限度保护相对人权利救济为原则,尽量将有争议的行政公告纳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体系。我们须确立这样的观念,即使是事实行为,若造成人民权利侵害或负担,而产生除去义务或损害赔偿义务时,则不应只视为事实行为,而应允许相对人提起救济。[17]
注释:
[1]类似案例可参见王国和等:《对一起因大桶饮用水质量公告引起行政诉讼的思考》,《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00年第2期。
[2]就笔者的阅读范围,无论是教科书体系,还是专著体系,尚未有对行政公告的专门论述,甚至没有出现过行政公告的提法。有关学术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关于行政公告的研究 文献 也非常鲜见,只有学者张晓玲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 版)》2003年第6期的《论行政公告》一文。
[3]当然,行政公告还有其他分类标准,如以行政公告的内容性质为标准,行政公告有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与非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之分;以行政公告是否可以救济为标准,可将行政公告划分为可救济行政公告与不可救济行政公告等。但是,这些标准是建立在形式标准之基础上,没有对行政公告进行形式上的划分之前,就以行政公告的实质作标准进行的划分,有本末倒置之嫌。
[4]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行为的告知》,《法学》2001年第9期。有学者将行政行为的告知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中,详见孟昭阳、赵锋:《论行政告知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也有学者将行政告知等同于说明理由制度,见张引、熊菁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应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5]关于此点,请见本文第二部分“行政公告的性质”的相关论述。
[6]其实,抛开学界对“公告送达”的传统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行为,无论是从实质层面,抑或从形式层面上来说,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送达行为,因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普遍适用性决定了其无法通过个体的直接送达方式,而只能采取公告送达。
[7]当然这里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仅指纠正相对人违法行为措施之外,对相对人追加的不利处理,不包括对违法行为本身所作的纠正措施,如因相对人违法而需撤销其行政许可证,那么这个撤销决定虽然对相对人来说具有惩戒性质,但其属于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本身所作的纠正措施,不属于这里特指的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
[8]或许有人会将对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公告理解为行政处罚、处分的执行措施,督促被处罚人、被处分人依法及时履行义务,但即便如此,该执行措施也会对相对人产生新的影响,它与其他行政执行措施不同,其他执行措施只是单纯的对执行行为内容的实现。
[9]对行政机关本身来说,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和行政处理的成立时期一致,行政处理一旦作出立即生效。对当事人来说,行政处理只在行政机关使当事人知悉时起才能实施,即行政处理只在公布以后才能对当事人主张有效。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应分对行政机关本身和对当事人而不同。
[10]这也符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中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可诉的要求,如果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告将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将导致该行政公告具有可诉性,必然导致公告所内含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具有可诉性。当然,行政公告主体、程序上的违法是否可诉,是否影响行政公告的效力则是另外层面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11]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2]在日本就存在作为间接强制执行方式的公布违反事实措施,即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13]利益衡量的裁判方法理论要求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根据权利重要性等标准,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详见[德]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 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12~321页。行政主体在此个案中,类似法官的角色,应运用作为裁判方法的利益衡量来决定是否进行公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公告。
[14]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3页。
[15]如在日本,对于公布违反事实措施,可以提起撤销诉讼。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第4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关键词〕 科技行政处罚,科研不端行为,具体行政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5-0137-03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科技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的科技行政管理职能不断扩展,科技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权范围不断增大,科技行政法随之产生并得以快速发展。在我国,1993年7月通过、2007年12月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基本法律。此外,还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包含的条款,初步形成了包括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管理和科技进步奖励在内的科技行政法规范体系。由于科学技术活动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的特点,因此与一般行政法相比,科技行政法规范整体上表现出“探索性、激励性、社会性的特征”,并且“多以激励性手段进行调整”。〔1 〕 (P254-256)尽管如此,行政处罚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在我国科技行政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行政处罚的涉案也变得复杂多样,例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科研不端行为的行政处罚问题,撤销奖励和追回奖金等行为的法律属性问题,等等。因此,探讨科技行政处罚的法理,分析我国现行科技行政处罚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对于我国科技行政法治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根据科技行政法规范和行政处罚法,所谓科技行政处罚,是指科技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科技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惩戒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其目的是使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进行科学技术活动,维护良好的科技行政管理秩序。它包括:1.科技行政处罚的主体。在我国,作为科技行政处罚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各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其他行政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科技行政处罚中的当事人。科技行政处罚中的当事人是指承受科技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3.科技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科技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科技行政管理秩序尚未构成犯罪或虽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且应给予行政制裁的行为,是科技行政处罚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4.科技行政处罚种类。有关法律规定了行政处罚的责任形式。主要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撤销登记。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与繁荣,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各种损害或破坏科技行政管理秩序的违法现象也大量增加。一方面,科技行政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专业性,要求加强科技行政处罚的力度;另一方面,执法者违法行为的广泛与严重,则要求加强对科技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当前,我国科技行政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科技行政处罚的运行过程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有关违反科技行政法义务的罚则规定不足,甚至存在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形。例如,科学技术进步法授权行政机关对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但对于拒绝接受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督检查的组织或者个人未规定法律责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34条赋予行政机关对一些侵权行为处以罚款的行政裁量权,但有的地方性法规却赋予行政机关对同类行为单处或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权力,①不仅改变了行政裁量权的范围且有违行政处罚法有关行政处罚种类设定的要求。
其次,对科技行政处罚的种类认识不够。诸如“责令改正”、“限期改进”、“撤销奖励和追回奖金、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取消优惠待遇和奖励”、“取缔”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一些地方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识不一,有的认为属于行政处罚,有的认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也有的认为属于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之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这导致同一行为在适用法律规范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上的混乱:认为属于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应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要求;认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主体无疑应接受行政强制法调整;而认为属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仅受有关行为法的制约。
第三,针对科研不端行为,科技行政法律法规大多只规定了处理的原则、方向而缺少惩罚细则。有的部门规章,如《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虽然较为详尽地规定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查处,但它仅适用于归口某一部委管理的某一类项目,不能及于其他项目或归口其他部委管理的同类项目,适用范围有限。此外,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行政处罚,也存在处罚对象过窄的问题。例如《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均规定了通报批评的处罚形式,但该处罚仅适用于科研不端行为人和科技奖项推荐者,未及于科研不端行为人所依托单位和科技奖项申请者,致使后者或者未因此受到任何行政制裁,或者只承担“撤销奖励,追回奖金”的法律后果,难以达到惩戒作用。
行政处罚是制约行政违法行为的主要手段,因此规范行政处罚,是约束科技行政违法行为的有力保障。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路:
(一)强化科技行政处罚立法。科学技术活动具有专业复杂性、探索前瞻性、风险隐在性、不可预见性等特点,如何将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和法律运行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设计出既较好体现科学活动的内容和过程,又不失行政处罚基本属性的科技行政处罚体系是未来立法或修法的重点。首先,应当增设违反科技行政法义务的行政处罚责任。科技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义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即作为义务、不作为义务和容忍义务。拒绝接受依法进行的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督检查的行为即违反了容忍义务,对此,也应像惩戒弄虚作假行为一样,设定行政处罚责任。其次,有关立法应当阐明科技行政处罚的事实要件、责任标准和处罚形式。对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形,则应根据立法法应予撤销的规定处理。
(二)厘清科技行政处罚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界限与区别。除了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以及撤销登记等行政处罚法和科技行政法规范明文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外,有关“责令改正或限制改进、撤销奖励和追回奖金、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取消优惠待遇和奖励、取缔”等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表面上看来,这些行为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是不同的,例如责令改正、限期改进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规定的撤销奖励、追回奖金,位于法律体系中的“罚则”或“法律责任”项目下,而科学技术进步法第59条规定的取消优惠待遇和奖励则位于“第六章保障措施”,不属于“罚则”或“法律责任”部分。一些地方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表面上的差异仅将前者视为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但是,认定“其他行政处罚”的标准不应该是形式标准,从根本上说,判断一项具体的行政处理措施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关键在于该行政措施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根据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处罚是一种以惩戒违法为目的的具有制裁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制裁性体现在:对违法相对方权益的限制、剥夺,或对其科以新的义务。〔2〕 (P201 )在科技行政法规范中,责令改正或限期改进往往与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合并适用,其目的是命令违法行为人履行既有的法定义务,纠正违法,恢复原状,并非惩戒。〔3 〕 (P2 )“撤销奖励和追回奖金、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取消优惠待遇和奖励”这些行为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实质上是行政主体对已经成立的给予奖励等具体行政行为因在事后发现相对人不具备给予奖励、奖金、优惠待遇的条件的撤回,是行政主体对自己业已作出的前一行为的收回,体现为对自己行为的修复,〔4 〕 (P77 )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也不具有制裁性,不属于行政处罚。至于取缔,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行政机关针对特定非法组织或者特定非法行为作出的旨在解散或者消灭此种组织或者行为的非单个性的行为,是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集合。〔5 〕 (P30 )换言之,取缔本身应是一种科技行政目标的表达,具体的取缔措施可能既包括行政处罚,又包括行政强制措施, 还包含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有关取缔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的问题要视其采取的具体行政处理措施而定。〔5 〕 (P30 )如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23条在取缔社会力量“无证设立的奖项”过程中,采取了没收有关组织用于非法活动的工具、财物、没收非法所得的方式,该没收行为即属于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时应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要求。
(三)统一和细化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行政处罚。首先,应当在国家层次上制定一部统一的规范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对预防、查处科研不端行为的组织、原则、程序、罚则进行统一、明确的规定。其次,应阐明政府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规制的具体行为形式,例如是采用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合同还是行政指导。如果国家机关与科研人员之间是行政合同关系,当科研人员发生科研不端行为时,行政主体一方有权单方面决定解除或撤销该合同。解除撤销合同也是制裁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6 〕 (P66 )但是,如果科研不端行为人违反了有关科技行政法规范直接规定的义务,或者违反了科技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设定的命令或禁止义务或行政许可,为了确保行政法上义务的履行,就可能受到行政处罚。例如,科学技术进步法分别规定了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不得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第44条、55条),对此规定,若某机构或个人有违反的情形,即符合应受处罚的要件,应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第70条、71条)。第三,有针对性地设定行政处罚种类,拓展应予处罚的对象范围。科研不端行为人或其所依托单位往往能够从申请的项目、获得的奖励中得到一定的精神性利益和经济利益,这是他们实施科研不端行为或纵容这种行为发生的重要动机之一。为此,为达到教育和防止再犯的目的,有关立法应当设定针对科研不端行为人或其所依托单位的精神性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能够增加行为人的违法经济成本以及限制其从事相关活动的权利和资格的处罚形式,例如警告、通报批评、罚款和限制或剥夺从事科研活动或教育活动的资格。对在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方面大致相当的应给予行政处罚的科研不端行为,不论实施者是科研不端行为人,还是其所依托单位,也不论行为人是科技奖项的推荐者,还是科技奖项的申请者,均应给予行政处罚。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前述《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规定的针对科研不端行为人和科技奖项推荐者的通报批评的处罚形式也应扩及于科研不端行为人所依托单位和科技奖项申请者,包括外国组织和个人。当然,整体而言,科研不端行为人或其所依托单位违反科技行政法义务的责任究竟是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或行为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尚需有关的立法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方面进行细化,有关罚款的数额、行为罚的期限与违法情节、获取非法利益等方面的关系还需要制定专门规章予以明确。
注 释:
① 参见《河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33条。
参考文献:
〔1〕 倪正茂. 科技法学导论〔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3〕 杨建顺.正确理解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关系〔N〕.中国医药报,2005-06-04.
〔4〕 胡建淼.“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2005,(1).
第5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内容提要: 可罚性不应被还原为其他犯罪成立要件的要素,应成为犯罪成立的独立要件;可罚性的内涵除包含客观处罚条件与客观不处罚条件外,还应包含预防必要性因素;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具有平衡罪刑关系和作为与刑事政策沟通节点的功能。
在德日犯罪论体系中,传统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是由构成要件该当、不法和有责构成的三阶层体系,可罚性并不是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但一直以来,也有很多刑法学者对于可罚性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可罚性应属于刑罚阻却事由,有且只有阻却刑罚处罚的性质,但却并不是犯罪的成立要件,因此,事实上将可罚性排除出了犯罪论体系⑴;也有的学者认识到可罚性与犯罪成立具有内在的联系,但认为可罚性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于是将可罚性内化为构成要件该当、不法和有责的内容,也即将可罚性还原到原有三阶层体系中,维持了三阶层体系的稳定性⑵;还有的学者不但主张可罚性与犯罪成立具有关联性,而且进一步主张可罚性应成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从而突破了三阶层体系,构建了新的犯罪论体系。⑶持该主张的学者通常认为“可罚性,是特指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可罚性,即‘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它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之外,对行为进行的“值得处罚”这种实质的评价,因此,可罚性是继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之后的第四个犯罪成立要件。”⑷
一、德日犯罪论体系中可罚性的发展变化
在德日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作为颇多争议的问题之一,可罚性理论一直在犯罪论体系的边缘徘徊。早在李斯特时代,可罚性即已经为理论界所论及。李斯特在其《德国刑法教科书(第2版)》中将“作为可罚的行为的犯罪”作为犯罪的第四个标志,尽管没有明确使用可罚性(Strafbarkeit)一词,但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客观的可罚性条件,仍然是可罚性的问题。及至当代,有日本刑法学者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可罚性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即把可罚性评价视为犯罪论体系上的一个评价阶段。日本学者庄子邦雄认为:“应该与刑罚权的发动密切相连来考虑‘犯罪’的实质,在刑罚权发动时才认为成立犯罪……,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和有责的行为,并且是具备可罚性的行为。”⑸日本学者松原芳博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不仅是决定行为的犯罪性的条件,而且可罚性不属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内容,应当在犯罪论内部确立可罚性独立的体系地位。他还进一步将作为范畴体系的可罚性与作为包含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责任的全体的可罚性区分为狭义的可罚性与广义的可罚性。⑹日本学者板仓宏则进一步将可罚性区分为当罚性与要罚性。他认为,当罚性是实质的可罚性,它说明行为本身受处罚是相当的;而要罚性则是基于预防犯罪的目的,说明刑罚的必要性。⑺
德国刑法学家施米德霍伊泽明确将可罚性作为第四个犯罪范畴的标准。“这种客观的刑事可罚性的条件,‘另外还是犯罪行为的特征’。这些条件必须在具体的犯罪行为的构成中,附加在行为构成性的不法和行为构成性的罪责之上,以便在构成行为的刑事惩罚性方面,为有关的犯罪行为提供基础。”⑻德国刑法学家洛克辛则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可罚性问题。洛克辛将客观处罚条件作为其犯罪论体系中的第五部分即其他处罚条件,与行为、构成要件、违法性和答责性并列。而且在答责性部分创造性地将预防必要性引入了犯罪论体系⑼。洛克辛认为:“对于罪责这个各种刑罚必不可少的条件,总还必须补充进刑事惩罚的(特殊或者一般)预防必要性。因此,罪责是和预防必要性相互限制的,然后才能共同产生引起刑罚的行为人个人的‘责任’。这种把传统的罪责范畴与预防性目标设定相结合的做法,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⑽基于对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考虑,洛克辛把他的刑法体系称之为“目的论和刑事政策性的体系”。“建立这个刑罚体系的主导性目的设定,只能是刑事政策性的。刑事可罚性的条件自然必须是以刑法的目的为导向。根据这个观点,支持这个传统体系的基本范畴,就作为刑事政策的评价工具表现出来了,从而,这些范畴本身对于一种目的论体系来说,也是不可舍弃的。人权与法治国和社会国的基本原则会在刑事政策评价中被接受,并且将通过其超国界的适用而成为‘欧洲刑法的基石’。”⑾尽管洛克辛的目的论体系将预防必要性与责任纳入到同一位阶,统称之为答责性;而将传统意义上的可罚性内容,即客观处罚条件与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归入其他处罚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洛克辛还是将可罚性正式归入了犯罪论体系中来,可罚性成为了最终确认犯罪的必要环节。尽管洛克辛将预防必要性作为答责性的内容,但就与刑罚论的关系而言,预防必要性也应该属于可罚性的范畴,其意义相当于板仓宏提出的可罚性的分支之一——要罚性。因此,洛克辛通过其新的刑法体系继承并发展了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拓展了可罚性的内涵,即除了包含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之外,还包涵了预防必要性的内容,从而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思想引入到刑法犯罪论中。
从上述可知,在德日刑法学者的理论中,可罚性的范畴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变化。但德日学者也有殊途同归之处,就是将预防犯罪的目的性需求引入到犯罪论体系中。尽管可能使用不同的称谓,但至少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提倡将可罚性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引入犯罪论体系;二是可罚性的内涵得到了丰富。洛克辛更是从其目的理性刑法理论出发,重构了犯罪论体系。可以说,其最大的创举之一就是改造了责任论的内容。“洛克辛将预防因素引入责任层次是责任观念的一个重大改变。洛克辛认为自己的研究就是为了改变自古以来德国刑法学被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方法所支配的局面,将刑法学的研究转到以刑事政策和预防为指导的方向上来,而这个转变的最大困难就在于责任论。因为责任主义一方面具有制约国家刑罚权的自由主义、法治主义的机能,另一方面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还具有使观念论的赎罪正当化的意义。如果要实现对于责任的改造,一个途径是坚持责任主义的制约机能,放弃责任主义的报应思想,从而在预防的意义上重新构建责任概念,这个重新构建的责任概念就是答责性。”⑿
对于学者担心的引入可罚性会破坏法的安定性问题,洛克辛认为:“承认缺乏预防的刑罚需求可以阻却责任,并不会造成法安定性问题。因为这并不是法官自己对刑事政策的想法,而是以现行法为基础来确定是否有预防需求。亦即缺乏预防需求的阻却责任事由必须以实定法为根据。同样,法治国罪责原则的保护功能也不会由于把预防需求的必要性纳入负责性而受破坏。因为刑罚以罪责为前提,无论有多大的预防需求,也不能够使刑罚制裁合法化。这个预防必要性,仅意味着对‘刑法干预’做进一步的限制。这是由预防必要性的要求来限制有罪责行为的可罚性。”
将可罚性作为独立的要件予以了确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关系,而将刑法与刑事政策沟通,也成为了当代刑法理论的主流思潮之一。
二、罪刑关系与可罚性的目的追求
可罚性之所以命运多舛,除了德日犯罪论三阶层体系自身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之外,可罚性在一定程度上连通了犯罪论与刑罚论这两大相对独立刑法理论部分,会使得犯罪论作为独立的封闭的体系的特征受到冲击,也是许多刑法学家排斥可罚性的重要原因。从古典刑法学开始,犯罪论与刑罚论就被认为是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罪与刑成为了刑法的两极,对于行为的评价、定罪是犯罪论的任务,而如何处罚则是刑罚论的任务。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没有犯罪也就没有刑罚,犯罪论与刑罚论相对独立,如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观点,可罚性这一与刑罚论密切相关的理论,被认为是破坏了犯罪论的体系严密性,属于刑罚论对于犯罪论的逾越,因而难于为学者所接受。
但尽管如此,不同的声音依然存在,并且随着刑法学对于罪刑关系的重新认识有了新的转机。随着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人们开始对罪刑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的认识,走向了刑罚决定犯罪而不是相反这一新的认识。也即从犯罪决定论开始步入到刑罚决定论。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举了一个例子,“想像有一个由圣人们组成的社会,一个模范的完美的修道院,在那里可能没有纯粹的犯罪,但是,在常人看来是很轻微的错误,在那里可能引起常人认为是一般违法行为才会引起的丑闻。因此,如果这样的社会被赋予审判权和惩罚权,它会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并按照犯罪行为予以惩处。”⒀在迪尔凯姆的论述中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逆向关系,是因为惩罚的需要才会有犯罪被认定,在此,刑罚对犯罪的认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并不是刑罚造成的,而是先于刑罚而存在,只不过是由于刑罚的采用才被人们归入到特定的类别中来,赋予其新的不同的性质。“不是惩罚造成了犯罪,但犯罪只是由于惩罚才明显地暴露于我们的眼前,因此,我们要明白何为犯罪,必须从研究惩罚人手。”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刑法理论界认识到“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的格言告诉我们,法律对某种行为是否规定了刑罚后果,是从法律上区分某种行为是否犯罪的根据。”⒂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刑法学开始重新审视罪刑关系,而作为犯罪论与刑罚论重要链接点的可罚性问题也理当被重新认识,赋予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如我国学者冯亚东教授指出,犯罪并非是由不法行为危害量的简单递增即可成立,即行为“犯罪”的性质并不完全取决于行为自身的危害性及其程度,而是还应考虑规制为“犯罪”后能够运用何种方式处罚、处罚的效果如何等因素;即除考虑行为本身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外,还应权衡行为之主体是否“应受”(必要性)和“能受”(可行性)刑罚的处罚问题——凡不应当或不可能受到有效刑罚手段处罚的行为(或行为人),便不能人罪。……在国家立法者面前,各种危害行为本身并没有一般违法和犯罪的分野——它们在总体上汇成一股恶流,危及国家和社会的生存。立法者在对“犯罪规范”进行创制假设时,其“假设”的根据为何,“犯罪”根本区别于一般违法行为的控制着眼点又在哪里?顺此思路考虑,既定的刑罚制裁体系便自然成为是否“入罪”的具体参照系。⒃那么在犯罪论体系中如何体现刑罚对犯罪的决定作用?如何体现刑罚对人罪的参照系作用呢?可罚性应当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对于刑法体系内部而言,可罚性作为关键节点之一,既可以发挥人罪的功能(客观处罚条件),也具有出罪的功能(客观不处罚条件或称之为处罚阻断事由)。将可罚’性引入到犯罪论体系中来,可以给予犯罪论定罪体系有力的支持,做到定罪有根据、刑罚有效果,避免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罪与刑的脱节问题,起到沟通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对于刑法的价值追求而言,提升刑罚论的地位并不意味对刑罚的过度追求,而是为了在刑罚发动之前把刑法价值提前融入社会化过程,以期减少犯罪发生率,实现刑法的预防犯罪功能。
在刑法理论中,对问题进行界定时通常要与刑法的目的相适应,也即在关系之内以某个标准去看待的问题。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功利的做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功利本身就是法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对于社会科学理论而言,通常是为研究目的服务的,惟其如此,研究才有意义。因为这是由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决定的。人文科学不完全是客观的,很多时候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主观的价值期待与追求。在构建犯罪论体系、界定对象本质的时候,对象是什么与对象应该是什么是同时存在的。犯罪作为社会事实的一种,属于关系范畴,刑法研究正是对于关系的认识与判断。而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其中就包含有人,尤其是立法者的需要,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本身就包含主观价值期待。在现代刑法理论从报应刑法走向预防刑法的大趋势下,可罚性的目的追求自然离不开刑法的目的追求——预防犯罪,要做到尽可能的罚有必要、罚有效果。
对于犯罪论体系而言,其有效性的最终评价标准在于实定法的实践效果,而对于效果的评判自然离不开刑法的立法目的,这也应该是一个国家刑法理论体系的目的。刑法中犯罪论的理论价值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对于刑罚适用有利与否,看是否达到刑罚的适用目的。如果偏离了理论的目的性,脱离了实践评价标准,就会丧失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功能。可以说,犯罪论理论是为了适用刑罚而设立的,也是为了刑罚服务的,这就是其目的性。因此,可以说犯罪论的目的本身就蕴含了沟通刑罚论的内在要求,将可罚性这一包含刑罚适用效果考量的要件纳入犯罪论体系中是符合犯罪论体系的目的追求的。
三、作为与刑事政策沟通节点的可罚性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指国家制定和实施犯罪对策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刑事政策的目的的形成是人们对社会上现存价值理念经过选择在对付犯罪过程中的应用。这种目的一经确立,就要在整个刑事法体系运作过程中加以体现。对于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我国台湾学者林纪东认为,“刑法之刑事政策化是现代刑事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刑事政策的观念是刑法的基础,刑法的定罪科刑,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为达到防卫社会和预防再犯的手段。刑事政策也就是刑法定罪科刑基础的政策。所以刑法的制定与运用,罪刑的确立与执行,都应由刑事政策的观点出发,以是否合于刑事政策的精神为指归。离开刑事政策的立法、裁判、执法,必是不良的立法、裁判、执法。因此刑法的研究,也不只是在法条上的咬文嚼字,更重要的是应该培养刑事政策的观念。刑事政策的研究是刑事法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和终极目标。研究刑事法而不知刑事政策,至多只看到现代刑事法的形式,而没有把握到更高一层、更深一层的灵魂。”⒄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司法与立法的重要性确实如此。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如何做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有效沟通。相对封闭保守的刑法与相对开放灵活的刑事政策在衔接上不可避免会出现时间差与速度差,这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犯罪认定精度与刑罚适用效果的损耗与弱化。罪刑规范和刑事政策是两套各具特色的独立规则体系。前者讲求形式的明确、观念的保守,较多地反映法的技术性要求;后者则在形式上灵活而包容,在观念上积极进取,较多地反映政治直观。在现实中,罪刑规范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是:刑事政策必须考虑罪刑规范所蕴含的刑法的技术性要求,而罪刑规范必须是一种把刑事政策所反映的政治直观考虑在内的罪刑规范。面对这种局面,罪刑规范与刑事政策应相互留有余地,在纯属对方的领域,应主动退出;在双方竞合的领域,应在不损害自身规定性的前提下,在彼此能够融合的领域,尽量反映对方的要求,从而结成一个开放的讲求互助的联盟,共同实现对犯罪的有效控制。⒅在此,可罚性作为关键节点的功能可以再次得以实现,在纯属于刑法领域的如构成要件该当、不法和有责的犯罪成立要件中,应避免刑事政策的介入;而在“开放的窗口”——可罚性中,刑法与刑事政策当可以相互融合,吸收对方的合理要素,一起发挥合力的作用。故而,可罚性的合理运用会在相对封闭的刑法中开拓出一个通道,通过与刑事政策的连接作用,发挥预防犯罪和限缩刑罚权的功能,实现其目的追求,这正是作为与刑事政策沟通节点的可罚性的功能。
在作为可罚性要素之一的客观处罚条件中可以明显看到刑法与刑事政策沟通的例证。在德日刑法中,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Objektive Bedinggungen der Strafbarkeit),即客观处罚条件,是指这样一些情况,“它们存在于不法构成要件和责任构成要件以外,但行为的应受处罚性取决于其存在与否。由于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不属于构成要件,因而没有必要涉及故意或者过失。”⒆从源头上看,客观处罚条件源于古代的法官或者主权者的刑事裁量权,是赋予裁判者根据特殊需要而决定刑罚权发动的一项制度设计,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出罪的功能。而这种所谓的特殊需要实际上就是基于一定刑事政策的需要。这种需要最初是源于维护贵族、僧侣等特权阶级利益的要求以及其它政治目的的需要,如军事、外交等特殊需要。例如,“德国刑法第102条以下的规定就是通过保障外交的联系和互惠来保护‘最低限度的国际接触,否则,处罚针对外国的犯罪行为就在刑事政策上没有意义。”⒇正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在现代法治原则已经广泛确立的情况下,可罚性满足了谋求一定的社会效果和刑罚效果的统治者的特殊需要。但无论如何,客观处罚条件都具有了限缩刑罚权的出罪功能,也都与一定社会阶段的刑事政策相适应。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客观之可罚性条件乃于不法构成要件之外而附加之可罚性要件,有如构成要件附加物,而成为可罚性之附带必要之要素。虽客观上并不存在此等可罚性之条件,但行为人之具有违法性与责任之构成要件该当行为,本来即属应于刑罚之可罚行为。易言之,即使不存在客观之可罚性条件,行为本来即具应受刑罚性;惟因有此附带条件之限制,而不成立犯罪。因此,客观之可罚性条件即有如一种刑罚限制事由,而把本来仅由不法与罪责即可决定之应受刑罚性,附带地加上不法与罪责以外之条件,而限制刑罚之范围。”(21)林先生在此处明确地将客观处罚条件提升到影响犯罪成立的高度上来,是犯罪成立的独立要件,而之所以要确立这一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刑罚的范围。那么为何要对刑罚的范围作出限制,归根结底是源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如果不添加要么涉及行为本身,要么涉及行为后的其他情况,给予行为以重要的构成刑罚的刑事政策的必要性基础,无论是否存在不法和责任,在一定的情况下,立法者均会否定要罚性。……从实质上看,是基于刑事政策的理由对责任原则作出限制。”(22)即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以行为之外的客观要素作为行为是否应受惩罚的一个条件,这个附加于行为的条件,通过排除或限制责任原则的适用来达到调整刑法打击范围或加减刑罚轻重以使之与当时当地的刑事政策目的相契合。刑法规定客观处罚条件,实际上就是通过将其作为限制犯罪成立的一个实质要件,以大大收缩刑法打击面,从而既可以缓和司法资源紧张与发案率高的矛盾,又可以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维持刑法的最后性和严厉性。在此,实定法之外刑事政策通过可罚性这一制度设计与实定法相互融通,使得刑法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思想,刑事政策通过刑法的适用实现其目的追求。可罚性成为了刑法的一个出口,同时也成为了刑事政策的一个人口,其沟通节点的作用应得到实质性的彰显。
同样,在作为另一个可罚性要素的客观的不处罚条件中情况也是如此(die objektiven Strdflosigkeitsbedingungen)。通常认为客观不处罚条件是因为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涉及的是与客观的处罚条件相反的情形,它指的是在不法和责任之外的与行为人个人相关的从一开始就排除可罚性或者在事后取消可罚性的各种情况。日本学者将之称为“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personliche Strdfdusschliessungsgxuende),也可以直译为“人的刑罚排除事由”。在内容上,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包含着不同性质的事情。有的是从刑事政策的理由否定有责行为和因此是当罚的行为的要罚性,有的是本身已经完全存在的要罚性必须向其他的国家利益让步(23)。对于客观不处罚条件或者是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我国刑法学者也意识到其重要意义。王勇博士提出:“在我国,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具有相当的意义。比如,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盗窃罪来说,盗窃近亲属财物或者偷拿家里的财物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于确有追究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对盗窃近亲属财物的行为,按照现有犯罪构成来说是构成犯罪的,但是为了将这种情况与社会作案相区别,我们一般求助于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来解释,认为这种情形‘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但是为什么明明已经构成犯罪却要做无罪处理,仍然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我们的理论中缺乏对刑罚的确证。如果在犯罪构成中加上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则我们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就有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也避免了犯罪标签的扩大化,维护了社会、家庭的稳定。”(24)
对于客观不可罚条件的理论依据,“一般来说,一个行为具备了事实性要件,同时也不存在着排除犯罪性事由,就意味者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在有些特殊情况下,行为必须具有可罚性,行为的犯罪性才能最终确认。通常,犯罪的认定经过上述两个过程之后即可得出结论,之所以增加可罚性的要件,事实上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这种刑事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将无需动用刑罚的事案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以表达刑法的谦抑精神,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免标签理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25)在此,学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并将其归纳为出于刑法谦抑精神和避免标签理论的考虑。对于其从刑事政策的角度予以阐释的大方向应无异议,但其归于标签理论的观点则过于牵强。对于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26)刑法给予否定的评价是符合伦理的要求的,符合对犯罪的质的评价。这样符合划定犯罪的基本原则的条件成立后,再从不同的数量出发考虑不同的法定刑就是合乎规律的。但是如果行为人盗窃的是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或家庭成员的财物,就必须要考虑其中的伦理因素。从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看,对于此类行为是持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与宽容的。如果对于这样的行为不加区分、不充分地考虑其中的伦理因素,就断然给予否定的评价、归入犯罪范畴,是不妥当的。因此,立法上划定盗窃罪的犯罪圈时应将此类行为排除在外,即使盗窃的数额达到了标准线也不应以犯罪论处。(27)这种基于行为人身份的阻却刑罚的做法,是为了维系社会的亲伦、人伦关系(28),这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符合刑法与刑事政策的目的。因此,刑事政策在此予以了肯认。虽然我国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解决的,但考虑到司法解释在我国的实际效力,实际上也是承认了可罚性这一沟通节点的作用。
小 结
可罚性在刑法之内可以起到连接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纽带作用,能够有效地缓和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紧张关系,平衡罪与刑的矛盾和脱节;在刑法之外可以起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沟通节点的效果,减轻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同步性所造成的立法与司法损耗。有鉴于此,赋予其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的应有地位并不为过,这对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效果,限缩刑事责任的范围,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⑴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M],创文社1991年版,第514页。
⑵Jakobs,AT2,10/lff,转引自[德]洛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M],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98页;参见[日]佐伯千仞:《刑法讲义(总论)》[M],有斐阁1974年版,第232页。
⑶参见[日]庄子邦雄:《刑法的基础理论》[M],日本评论社1971年版,第59页以下;[德]洛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M],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99页。
⑷参见冯军:《德日刑法中的可罚性理论》[J],《法学论坛》2000年第1期。
⑸[日]庄子邦雄:《刑法的基础理论》[M],日本评论社1971年版,第59页以下。
⑹参见[日]松原芳博:《犯罪概念和可罚性》[M],成文堂1997年版,第2页以下。
⑺参见[日]板仓宏:《当罚性(实质的可罚性)和要罚性》[C],载 《平野龙一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上卷)》,有斐阁1990年版,第116页。
⑻Schmldh·user,LBAT2,12/1.转引自[德]洛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M],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98页。
⑼雅各布斯也在其犯罪论体系中强调一般预防的作用,在其教科书中在罪责与其刑罚目的理论相一致的情况下,完全并入了一般预防的概念。Jakob,Strafrecht-Allgemeiner Teil,2 1991.转引自[德]洛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M],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⑽[德]洛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M],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⑾同前注⑽,第133页。
⑿王充/《犯罪论体系本质论纲》[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印,第83页。
⒀[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8页。
⒁同前注⒀,第87页。
⒂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⒃参见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⒄林纪东:《刑事政策学》[M],台湾地区正中书局1969年版,自序。
⒅参见张鹏:《论罪刑规范与刑事政策的关系》[C],在《严打政策法律问题研究》会议论文集,第84页。
⒆[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⒇赵秉志:《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21)林山田:《刑法通论》[M],自行出版,第293页。
(22)同前注⒆,第668-669页。
(23)同前注⑷。
(24)王勇:《犯罪构成本体论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印,第163页。在日本刑法第244条、第257条规定了配偶、直系血亲或者同居的亲属之间犯窃盗罪、侵夺不动产罪以及赃物罪的,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原对家庭内部的盗窃和侵占不进行刑事处罚,现在由第247条作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25)同前注(24),第163页。
(26)这里所指的他人应是与行为人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或家庭成员以外的人。
第6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自德国刑法学家、行政刑法之父郭特希密特(J1Goldschmidt,又译为高尔德修米德)在其192年出版的5行政刑法6(Verwal-tungsstrafrecht)著作里首次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以来,行政刑法的界域等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我国学界开始注意到行政刑法是在1989年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四次大会召开之后,但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并不多,研究水平基本处于萌芽和初始阶段[1],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行政刑法的界域等相关问题上。根据5辞海6的解释,界域一词主要是指事物的分界和区域。就法律而言,就是指法律的分界和法域,而法律之间的分界是指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规范对象。因此,行政刑法的界域也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其规范对象。
一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
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即刑事法域说、行政法域说和行政法域与刑事法域双重法域说(或独立说)[2](35页)。笔者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属于刑事法的范围。我国学者对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形式、程序、实质等法理角度作了很好的论述[3],本文试从行政刑法一词的语法逻辑的角度,结合我国法制的实际,进一步说明行政刑法属于刑法范畴,是刑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行政刑法一词从语法上讲,词根是刑法,刑法是行政刑法的中心词,行政则是行政刑法的修饰和限制成份,即定语。这从语法上可以说明,行政刑法只是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刑法的一个子部门。本文并不赞成行政刑法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双重性的法律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刑法才有-行政.与-刑法.之名)[4]的观点,因为按照此说法,行政与刑法是并列关系,那么行政刑法应该可以叫做刑事行政法了,如果这样,刑法作为保障法、后盾法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从逻辑上看,行政刑法概念的属概念是刑法,行政则是行政刑法概念的种差,刑法除了行政刑法外,还有诸如固有刑法(普通刑法)、经济刑法等,据此,也可以说,行政刑法除了其行政种差外,还具有刑法的一般属性,是刑法的一个分支。因此,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分析,可以确定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法制建设实际看,刑法是我国所有法律的后盾法、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对第一次规范(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强有力的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5]。行政刑法正是在行政法这种第一次规范的力量难以完成保护行政法益的任务时,以补充行政法规范的目的所设立的第二次规范。我国法律体系分类的标准主要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可以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第一次规范划分为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刑法作为上述第一次规范的保障法,因为其独特的刑罚调整方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将行政刑法独立,那么法律体系的分类标准又怎么确定?而且如果行政刑法要独立,则依同理经济刑法、普通刑法等势必也要独立,如此刑法作为一个传统的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将会丧失。进而推之,取消刑法这个法律部门也具有合理性,其结果是将相关的刑法规范全部在相应的第一次规范中加以规定,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法律体系建构的实际,也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划分理念相悖。从我国现有的行政刑法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以及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属于刑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不是刑法,但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刑法规范。因为无论从刑法作为保障法的特征还是从附属行政刑法规范的结构、调整方法和适用司法程序上看,皆具有刑法的基本性格,行政刑法应属于刑法范畴[6]。德国等欧陆国家之所以将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犯罪观和刑法观与我国根本不同,他们对犯罪和刑罚均作广义理解,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命令性规定的行为都是犯罪,即行政不法(行政违法)和刑事不法(刑事违法)都属于犯罪;一切具有刑罚性格的法律效果包括刑事刑罚、保安处分、行政罚等都被认为是刑罚。而我国目前对犯罪和刑罚均作狭义理解,将一般的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刑罚与行政处罚严格加以区分。如果将我国的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除了从我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上讲不通外,还势必混淆一般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行政处罚与刑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严重脱离目前我国的法制实际。因此,将行政刑法确定为刑事法域,是刑法的一个部门,既符合我国的语法逻辑,又与我国的法制实际相融。当然,行政刑法除了属于刑法的分支外,行政刑法还可以分为更小的分支,如环境刑法、军事刑法、公安刑法、卫生刑法等等,这也完全与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划分一致。
第7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内容提要: 与自然犯相比,行政犯属于犯罪中的新类型。行政犯不但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史,就其本质而言,也有着与自然犯不同的自身属性和犯罪构成。规制行政犯的行政刑法虽然与刑法的其他组成有所不同,但仍有必要承认其具有附属于刑法部门的本质属性。同时,行政犯的责任形式必须重新审视,为了应对行政犯罪,有必要对刑法典和附属刑法进行补充完善。
一、犯罪的新类型———行政犯罪
(一)自然犯和行政犯的历史流变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观念,一般认为最早渊源于古代罗马法制度。1 古罗马法中关于malain se 与mala prohibia 的区分实质上为后来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mala in se 指实质上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违法行为,这种行为因侵害了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而为一般社会正义所不容。mala prohibia 则是本质上并不违反伦理道德,而是因为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需要而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2 但真正完整提出自然犯和法定犯分类并在理论上系统加以阐述的则是意大利刑事人类学派的标志性人物加罗法洛。加氏在其经典力作《犯罪学》中详细地阐释了其自然犯和法定犯的思想。在加氏看来,各民族都存在某种具有同一性和进化性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由非基本情感和基本情感组成。前者包括祖国之爱、宗教情感、贞洁感、荣誉感等。对这些情感的伤害不被视为是犯罪,因为它们只对作恶者本人及其家庭或国家有害,而并不危及整个社会;后者主要是指利他主义情感,这是唯一对社会关系重大的情感。它包括仁慈感、怜悯感、正义感和正直感几种基本类型。3 加氏断定,在一个行为被公众认为是犯罪所必需的不道德因素是对道德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绝对表现为对怜悯和正直这两者基本利他情感的伤害。对这些情感的伤害不是在较高级和较优良的层次上,而是在全社会都具有的平常程度上,这种程度对个人适应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确切地把伤害以上两种情感之一的行为称为“自然犯罪”。4 同时,加氏把某些侵害了非基本道德情感的行为排除出自然犯罪之外,如伤害庄重、贞洁、家庭情感的行为,政治犯罪行为及某些威胁公共安宁的非政治性地区犯法行为。5
加氏的这种分类方法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感觉到它对近世各大刑法法系的影响。就现代而言,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自然犯是指无需法律规范的规定,其自身就具有罪恶性的犯罪,如杀人、放火、强奸等犯罪就是如此。法定犯是指由于法律的规定才成立的犯罪,即行为本身不具有罪恶性,只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才使之成为犯罪。6 这种分类,在德国法中大多分为刑事犯与行政犯,在法国法中大多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7 实质上,大陆法系大多把自然犯和刑事犯作同一理解,把行政犯和法定犯作同一认识。本文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认识问题的。所以,为了行文的需要,后文皆以自然犯和行政犯来展开论述,而不特别提及刑事犯和法定犯的分类。英美法系则把犯罪行为分为本质恶与禁止恶。前者指行为就其自身性质而言就是不法的,在普通法上必须给予处罚,它基本上等同于大陆法系国家所说的自然犯;后者是指违反制定法的作为与不作为,它基本上等同于大陆法系国家所说的法定犯。8 可以发现,加罗法洛后的刑法认识与加氏对自然犯和法定犯的界定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加氏看来,自然犯的存在范围非常狭隘,既不能说违背社会伦理的犯罪就是自然犯,也不能说所有违背利他情感的犯罪就是自然犯,只有违背利他情感中的正直感和怜悯感的犯罪才能构成自然犯。而后来的见解突破了这种原始的认识,赋予了自然犯更为宽广的存在空间。我们不能说加氏的纯粹见解没有价值,但这种后来对自然犯的较为宽泛些的见解恐怕更为符合刑法上的通常认识和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透析,所以,现在对自然犯和行政犯的理解更为符合法律理解的精神,更能凸显其存在的理论品格。基于如上认识,我们对自然犯和行政犯的系列分析皆是以此为基础来展开认识和分析的。
( 二)自然犯和行政犯的划分
当下国内在刑事犯与行政犯的界分上大致存在两类观点:第一种认为自然犯和刑事犯就是刑法或特别刑法上所列举的犯罪。而法定犯或行政犯则是指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行政犯可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行政法上所规定的应受刑罚制裁的行为以及行政刑罚法上所规定的应受刑罚制裁的行为;其二是行政法上所规定的应受行政罚的行为。9 第二种观点认为,违反行政法规范因而构成的犯罪,就是行政犯。刑事犯则是直接违反刑法典规范所构成的犯罪。10 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更提出区分“狭义的行政犯”与“广义的行政犯”,区分的标准在于“刑罚”与“行政罚”的观念。11 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犯界定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客观实际状况,而不能一味考虑、全盘引进西方的行政犯理论。众所周知,德日大陆刑法学中的行政犯概念具有较为宽泛的含义。这一方面是德日的犯罪概念范围过广,许多在我们视为行政违法的情况他们都是作为犯罪来处理的;与之相关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作为行政罚规定的处罚方式他们是作为刑法处罚来规定的。所以,我们认为,我国的行政犯应当这样界定,即行政犯是违反我国行政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
虽然当下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犯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且“行政犯的自然犯化”日益明显,但也决非像有的学者所谈及的那样“由于法定犯与自然犯的区别实际上是困难的,刑法解释上的实益也不大,所以,自然犯与法定犯的概念,不过是在为了尽可能说明各个犯罪根据法律被处罚的由来或者考察立法的形式之际才成为必要。”12 在概念确定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自然犯和行政犯有着诸多颇为显著的区别。
其一,在刑法机能实现上的不同取向。刑法的机能,是指刑法在社会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效果。刑法具有行为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13 虽然关于自然犯和行政犯的刑事立法都有行为规制的机能存在,但在秩序维持和自由保障机能的发挥上两者却是各有侧重。由于行政犯的立法目的重在行政秩序的维持,故其侵害的法益大多属于国家或社会的法益,而甚少涉及个人法益的维护。而自然犯的立法虽然也有秩序维持的成分,但其存在的本质主要还是重在公民人权、自由的保障上。这也无怪乎每当行政犯立法急剧增加就有学者大声疾呼:社会更需保障自由人权。
其二,在犯罪论问题上,两者的不同在于:首先,对行为的理解不同。第一,行政犯所言的行为不限于本人的行为,其代理人、辅助人或者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完全可以视为主体自身的行为进行考察和处理。这种方式较之于自然犯恐怕要走得远的多。第二,自然犯中的行为几乎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都被作为犯罪看待,在自然犯问题上,刑事立法仅仅充当留声机的功能;而行政犯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时代的不同行政取缔或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期行政管理的变化直接决定了行政犯的不同类型;在行政犯问题上,刑事立法是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主宰。
其次,构成要件层次的评价有所不同。第一,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上,自然犯大多有明确的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不需要借助于其他法律进行补充;行政犯大多为开放的构成要件,需要法律上的二次评价。即开始必须审视行为的行政违法性,最后还要考察行为的性质是否严重到了必须刑法评价的必要。第二,在违法性的评价上,主要是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对犯罪成立的意义。虽然现在对自然犯的界定已经超越了加罗法洛最初设定的范围界限,即不再单纯认为自然犯仅是对人类怜悯感和正义感的侵犯而扩大了其适用,但自然犯和行政犯的相对确定的理解仍然可以在认识论上求得存在的依据。在自然犯和行政犯的区分问题上,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违法性认识对各自犯罪成立具有不同的意义。按照通常的认识,自然犯主要与特定民族的伦理操守、道德感情紧密相关。在特定民族看来,某些犯罪是否成罪甚至根本不需要到刑法典中去寻找答案,对这些犯罪的解读用世代相沿的民族情操就可完成,这些就是所谓的自然犯。但行政犯的认知则远非如此明显。行政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伦理道德可以评价的范围,其罪与非罪的成立主要是借助于刑法和特定行政法的规定才能予以解决。即行政犯区别于自然犯的本质方面即在于其与道德生活的不相联系,而自然犯从社会伦理道德上可以合理地寻求正当的解决。简洁来说,自然犯对于自然人而言具有自发性和自然的融通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不需要进行成文法审视和判断的内容。当行为人进行自然犯罪时,违法性的意识一般不作审视或者重点审视,这种意识是被推定为已经存在的内容,只有当客观可证实的事实能够证明这种意识确实不存在时,司法者才会回过头来关注刑事违法的认识问题。而在行政犯问题上却根本不是这回事。当一个行政犯罪展现在司法者面前时,司法者是不会过度关注行为者的违法认识的。自然犯不是不审视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司法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这种认识都是存在着的,只是不需要过多的关注。而就行政犯而言,司法者却认为这种考察不属于法律上的必要措施,或者干脆就认为这种认识根本不影响违法性的成立。在对违法性认识的回答上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者间的如下区别:(1)违法性认识有无必要予以特别关注。(2)违法性认识是否具有道德伦理性。(3)违法性认识是否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的延续性。(4)违法性认识有无必要借助于成文刑法来明确和规定。
再次,在有责性的评价上不同。自然犯一般从责任能力、故意或者过失、期待可能性等方面来审视问题,而行政犯则无须全面顾忌上述情况。行政犯不像自然犯那样完美地体现主客观的联系和结合,在主观方面,除了犯罪故意或者过失外,行政犯的成立与否应当说再没有可以凭借的因素,这种状况最极端的结果和表现就是英美法上的严格责任和替代责任。甚至是在犯罪的故意或过失上,行政犯和自然犯也有着不小的区别。以单位犯罪为例,具体在犯罪故意或者过失上,很难说只有单位负责人的故意或者过失才能视为单位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在现实的司法考察中是需要总体衡量和整体把握的,只要在全体意义上体现了犯罪故意或过失的本质且具有主观要素的可归责性,单位从属人员的行为归结为单位犯罪没有其他的法律上的障碍。
二、行政犯罪的责任承担
( 一)行政犯罪的定罪依据———行政犯罪的构成
有学者认为,行政犯是指以违反特定的法规(如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为前提,从而构成的犯罪。14 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行政犯有着与自然犯不同的犯罪构成状态。
首先,行政犯的二次违法性,决定了在考量行政犯罪行为时必须同时关注刑法和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两项内容。行政犯所指称的行为必须最初违反了行政法规或者经济法规,此项条件若不具备就根本没有刑事考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还要考察这种对行政法规或经济法规的违法行为必须突破了这些法律可以包容、调整的范围,其客观危害和主观状态需要借助于更为严厉的手段,需要借助于刑法打击才能达此目的。但必须注意的是,此处所言的行政犯的二次违法性,决非是在主张双重属性说的前提下来适用的。笔者虽然承认行政犯以行政违法为前提,但行政犯本质上决非单纯违反行政法的行为。对当下有学者主张“所有的犯罪都具有二次违法性”的见解,笔者认为其认识方式和结论过于绝对,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余地。特别是在自然犯问题上,这种主张颇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按照通常的认识,划分部门法的依据是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拿自然犯中的故意杀人罪为例,第一,我们无论是在民法中还是在行政法中都找不到对故意杀人这一行为的法律调整规范,民法和行政法只有在构不成故意杀人罪的情况下才有调整“死亡事件”的可能,但这种“死亡”绝非故意杀人。第二,民法和行政法也缺乏规制故意杀人的处遇措施。一方面,刑法对自然犯的处罚规定并不都附带有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内容。以刑法第232 条的故意杀人罪为例,该条仅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未规定出现此种情况下可以或者必须民事赔偿、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另一方面,民法或行政法中从来都未出现过“故意杀人可以或必须负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规定,在实践中我们也很难想象在当今社会中故意杀人仅靠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就可解决。退一步说,现实中如有此类事实发生,我们不会认为对此类行为的解决方式是民法或行政法合理、合法适用的结果,相反倒会认为这种处理是对民法的侮辱、对刑法的挑衅。在此问题上,反对者往往会以刑法的第36 条和第37 条做例证试图反驳笔者的上述见解。的确,刑法第36 条是刑事处遇和民事责任“可能”并用的规定,刑法第37 条是刑事处遇和行政责任“可能”并用的规定。但要注意“可能”一词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刑法第36 条和第37 条针对的都只能是行政犯罪而不能是自然犯罪,“可能”一词的意义就在于此。刑法第36 条明确指出,“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才可以适用此条的规定进行双重责任的处遇,而自然犯特别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如故意杀人罪等并不一定带来经济损失,所以刑法第36 条对自然犯而言恐怕要大打折扣。同样,刑法第37 条规定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针对的对象本质上也是犯罪行为而非民事或行政违法行为。因为此类行为若构不成犯罪,刑法大可不必对此予以规定,单靠相应的民法或行政法就可解决。刑法第37 条规定的要义旨在表明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但在责任承担上可以适用民事处罚或行政罚以代替刑罚上的处遇。但注意,这种责任承担上的替代决不意味着“犯罪都具有二次违法性”。适用刑法第37 条规定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而非民事或行政违法,这种单一的犯罪行为不能毫无逻辑地进行多重意义或多重责任形式的评价,否则就直接违反了“同一行为不能多重评价”的基本原理。
其次,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决定了行政法规或经济法规具有极大的变异性,这种客观情状决定了行政犯构成要件的开放性。行政犯大多由规定此类行为的附属刑法和刑法典综合调整。附属刑法出现在行政法规或经济法规之中,它仅仅发挥其应有的指示功能,明确地指出此种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人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2 条就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野生动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与附属刑法相呼应,刑法典一方面重申了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一方面又具体规定了相应的刑罚种类和幅度。如我国现行《刑法》第341 条第2 款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虽然从形式上看附属刑法和刑法典并合适用的立法方式可谓天衣无缝,但当面对司法实践时,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实质上的严重障碍。因为刑法适用的铁则是罪刑法定原则,而附属刑法自身的规定难以实现此种要求,所以刑法典必须对刑罚打击的合理性提供实质意义的解释。于是刑法典必须明确哪些属于狩猎法规、哪些属于情节严重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事实上,也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行政犯的成立才有可能。可以看出,在此种意义上行政犯的构成要件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一方面表现在刑法必须在刑法外寻找犯罪成立的依据;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刑法外寻找的行政犯构成要件社会常态极具流变性。但我们能不能说“所有犯罪构成都是开放式的、自然犯构成要件也是开放构成要件”呢?笔者认为不能这样认识问题,其理由如下:
第一,开放构成要件有确定的含义,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开放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仅对部分构成要件作了明确规定或仅对犯罪行为作了一般特征的描述,其他要件需要法官在适用刑法条文时作出某些必要的判断、补充才能最后确定的犯罪构成。或者说,是指条文没有将犯罪构成的要件予以明白地揭示,而是需要援引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说明的犯罪构成。开放的犯罪构成主要存在于一些法定犯或行为、对象具有实质易动性的犯罪中。另外,在不纯正不作为犯形态下,犯罪构成的形式也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其中心问题是如何确定作为义务的范围。开放的犯罪构成,并不是法官对之可以随意确定,而是仍应贯彻和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对行政犯的要件的确定,法官应认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确定,不得随意补充。15 可以发现,开放构成要件主要是针对法官的判断而言的,开放构成要件的“开放性”不是表现为法官面对的已经明确的构成要素在各社会主体间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法官在多重价值判断中进行“应然”的取舍;而是表现为客观的构成要素自身在刑法范围内不能得到“实然”的认知和表现。对开放构成要件进行填充仅靠刑法是不够的,法官必须借助于其他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先在”的基础材料来完成对开放构成要素的描述,这些基础的素材对开放构成要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然犯中的构成要素一般是不需要借助于外来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进行描述和评价的,这些要素具备记述和客观判断的性质,仅凭自然的、本能的意识就可把握。所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讲,自然犯是普通人或一般理性人就可对行为作出定性分析和判断的犯罪类型,虽然这些具有通常理性的普通人不大可能对具体的犯罪罪名和刑罚量定作出较为精准的如法官那样的认识和判断。第二,如果承认所有犯罪的构成要件都是开放性的,不符合概念分类的逻辑规律。因为只有在存在本质差别的情况下才有概念分类的必要。如果赞同此种见解,就从根本上抹杀了概念分类和封闭构成要件存在的必要性。第三,认为自然犯构成要件也是开放构成要件的见解不符合事物认识的经济性目标。第四,这种见解违背了事物存在的客观状况。就行政犯而言,现实的情况虽然通常是在行政法规对已有行政违法进行规制后刑法才将其犯罪化,但也有如下情况存在,即在刑法将其犯罪化后行政法规才进行规制或者至今都没有相应的行政法规与之对应。如与79《刑法》投机倒把罪具有直接渊源关系的现行《刑法》第225 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其第4 项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也构成非法经营罪。笔者认为,当面对225 条的第4 项时,很有必要反思对行政犯概念的界定。在行政犯概念的界定问题上,有见解认为只有在违反实定行政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立行政犯,笔者认为不能这样来理解。较为恰当的解释是,行政犯应当是对行政管理秩序的侵犯。也就是说,从行政维持的见地出发来考量问题,只要行为是对行政管理秩序的侵犯并达到了犯罪化的程度,这种行为即使不能从实定的行政法中找到依据,我们仍可从应然的角度把此行为定性为违反行政法的行为。一句话,行政犯并不一定是对实定行政法的违反,但一定违反了应然的行政法,侵害了行政管理秩序。就自然犯而言,我们也不能认为其构成要件也是开放性的构成要件。如故意杀人罪,不论行为样态如何复杂,借助于通常的道德情感即使是不具有成文法认识的普通人也完全可认知行为的犯罪性,因为几千年来因袭遵循的伦理道德已经把诸如“不得杀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认识固化,对这种行为的认知是不需要借助于成文刑法的,“人、杀人、故意”是记述性的概念,是无须价值判断、无须描述的客观判断。对“人”我们仅需回答“是否是人”,没有必要考察“应否是人”的问题。
再次,行政犯客体鲜明的时代性。与行政犯相比,自然犯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自然犯伴随着民族社会意识和道德伦理而生,行政犯则是国家行为日渐成熟的产物。虽然我们也可以说在自然犯产生的不长的时期内或者同时期也已出现了行政犯的萌芽,但现代语境下的行政犯恐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伴生物。所以,与“杀人偿命”所描述的自然犯不同,行政犯侵犯的客体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性特征。这种客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生活的消长而消长,而不会像生命权、财产权那些客体一样长久保持其永恒的魅力。在这种意境下,我们不难理解行政犯都是对行政管理秩序或者是国家经济秩序的侵犯;我们也不难理解行政犯一般都是对国家或社会法益的危害而甚少波及个人的法益;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79 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为何已成昨日黄花,而在当下经济形势下,“非法经营罪”的适用仍是如火如荼。
最后,在犯罪主体的定位上行政犯与自然犯也有不同。自然犯的犯罪主体,通常的见解认为只能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在行政犯罪的主体定位上则不限于此。虽然自然人可以成为行政犯的犯罪主体,但就像有学者提出的那样:“法人可以而且只能构成行政犯罪的主体”。16
(二)行政犯的量刑依据———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抉择
首先,在已经构成行政犯罪的前提下是否都必须予以刑罚处罚?笔者认为不能把问题简单地理解为“有犯罪就有刑罚”。且不说《刑法》第13 条的但书为非刑罚化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刑法第37 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同样可以为这种处遇提供法定的理由。
其次,是对刑法第37 条的正确解读问题。在刑法第37 条的理解上,有人认为该条规定的其他处遇方式属于任意性规范,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简洁而言,即是说在无罪免刑后行为人也完全可能免除行政罚上的责任。笔者不赞同上述见解。实际上,刑法第37 条的规制对象是在构成行政违法的基础上又构成行政犯罪的行为人。这就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要面对行政法和刑法的双重审视和评价。在具体操作时只是说要优先进行刑法意义上的处理,在刑法自身范围内能够完美解决问题时就不需要进行行政法背景内的审视。但问题是,当刑法认为相关行政犯罪没有刑罚打击必要性从而不考虑刑罚打击时,丝毫无损于行政法的依法处理。因为,任何法律都有特定的规制范围和对象,超越于自身可作用的领域对其他平行法发号施令不符合宪政的精神和法律独立运作的目的。这即是说刑法只能审视行政犯罪,当刑法不作刑罚处理时刑法没有任何权力干涉或左右行政法的适用。退一步说,我们即使不论及行政法和刑法就法律部门而言的平行性,仅就公正和合理而言,在行为人已经构成行政犯罪的情况下却不进行任何法律制裁的事实恐怕无异于是对法律的一种辛辣的嘲讽。
再次,行为人在触犯行政刑法后是否可以承担刑罚和行政处罚双重责任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有学者以“一事不再理”原则否定承担双重责任的可能性。这种见解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一事不再理”作为一项诉讼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抑或是社会主义法系中都存在着。该原则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抑或是刑事诉讼中都有明确的体现。“一事不再理”的要义是对同一行为不能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独立的、分别的法律上的评价,也不能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同一性质的处罚。但该原则不排斥针对同一行为可能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法律上的处分,只要这种处理方式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就行政犯罪而言,在刑法典和包容附属刑法的行政法中均明确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和处罚且处罚方式并不矛盾的状况下,对行为人进行刑罚和行政处罚的双重处理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在我国当前的刑罚种类中,还不存在禁业限制、资格剥夺等刑罚方式的规定。针对危害严重的单位犯罪,我国刑法也仅仅规定了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罚的刑罚种类,当对这些犯罪确有禁业限制时假若不适用行政法的相关行政处罚就难以达到法律所追求的效果,如此,从公平和正义的角度计,就必须进行处罚方式的多重处遇。假如说我们的上述见解还停留在理论探讨的范围,那么刑法附则二的规定则为上述的认识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列于刑法附则二的8 项补充规定和决定被公认为刑罚处遇和行政罚处遇的典型。刑法在附则二中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下列补充规定和决定予以保留,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责任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本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适用本法规定。”另外,我国也有许多行政法明确规定了刑罚和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况,这也足以证明两者适用的并容性,而非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行政处罚只适用于违反行政秩序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17 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 条第1 款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在刑罚和行政罚并合处遇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刑罚的优先适用问题。由于行政犯罪违反的是行政刑法,其首选的责任方式必须是刑罚措施。只有在刑法作无罪化处理或免罪化处理的情况下才能径直适用行政处罚。第二,责任方式具有性质类同性时的具体处遇问题。在行政罚上存在财产罚、人身罚、资格罚等不同的处罚种类,相应,刑罚方式上也有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罚,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人身自由罚。在具体司法适用时必须注意,当用刑罚处遇时就不能再让行为人承担同样性质的行政罚;只有在没有相应性质的刑罚时行为人才必须承担行政法上的其他填补意义的行政责任。
三、行政犯规范的完善
( 一)刑法典的完善
1、刑法典总则的完善
要完善行政犯的总则性规定。在这方面要借鉴德日刑法的规定和理论研究成果,同时,要注意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协调问题。要摒弃如下错误的认识:即刑法典适用后不能再次适用行政处罚。我们必须首先追求行政犯刑事处罚方式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立足于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刑事立法,引进剥夺资格和职业禁止等内容。在刑罚种类上我国特别有必要借鉴德国的刑罚方式,引进和移植他们的资格罚、行为罚规定。从西方国家的立法例来看,资格刑主要分为四种,即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职权、亲权和职业权。常见的有禁止驾驶、禁止从事某种商业、营业活动、禁止从事某种职业以及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与之相比,我国的刑法规定存在不小的欠缺,首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只适用刑罚而不适用行政罚的现象;其次,在资格罚或能力罚上,司法机关有时即使想同时适用也存在立法上的障碍。这不但表现在刑法没有规定成体系的资格罚、行为罚措施,也表现在行政法上缺乏适用的规定。比如,我国行政处罚法上规定的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和执照几种处罚方式主要针对单位而言,缺乏对自然人本身的资格处罚方式。
2、刑法典分则的完善
法律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但法律也必须紧追不舍地与社会生活基本相适应。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尽量保持刑法典的相对稳定性,只有当确有必要时才考虑刑法典的修改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刑法典的时代性特征,对社会生活的新现象予以充分合理的关注,对确有必要的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其实这种行为的入罪化处理对行政犯罪尤有必要。反观1997 年新刑法,可以发现如非法经营罪、信用卡诈骗罪等许多新罪名都是针对近些年来新出现的行政犯罪而设的。但在完善刑法分则的方式上,我们力主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来补正刑法的欠缺,而不主张采用单行刑法的形式。之所以作如此的考虑,一方面是单行刑法自身存在着缺陷,一方面是刑法修正案与其他补正形式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
( 二)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协调
“严格追求刑法典的统一适用性,限制附属刑法的存在范围,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采附属刑法的形式”应当是我们对待附属刑法的态度。在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下可以看出,附属刑法大多只具有刑法适用的指示性功能。即,它的存在意义是且只能是指导人们在刑法典中追求定罪、量刑的解决和答案,单纯适用附属刑法不能确定犯罪的成立和量定具体的刑罚。附属刑法不能离开它所依附的行政法而独立存在。就其存在目的上,我们与其说是为了促进刑法打击,倒不如说是为了更有威慑地进行行政取缔更为符合附属刑法本来的意旨。
如上所述,附属刑法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刑法适用性,它解决不了具体犯罪的罪名认定和刑罚量定问题。在此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说附属刑法并非真正的刑法,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刑法仅仅是形式渊源的划分需要。在刑法典和附属刑法的关系上应持如下态度:
第一,附属刑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甚至随着行政管理的扩大,附属刑法也可适当扩大;但必须注意附属刑法只是表征行政法和刑法典必要衔接的桥梁或者是必要的技术性规定,其存在意义必须局限于此。那种认为附属刑法也具有实质的适用性,可以单凭附属刑法定罪量刑的观点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杜绝。因为,罪刑法定是刑法的铁则,该原则旨在强调定罪和量刑的刑法明确性,其目的即在于最大可能地保障公民基本的人权。而附属刑法都缺乏明确的罪名、罪状描述,在刑罚的规定上更是一片空白。所以,附属刑法的自身存在就决定了它只能充当部门法过渡的桥梁,而不可能像刑法典那些在刑事法领域内大有作为。
第二,必须注意附属刑法的时代性和与刑法典发展的同步性。附属刑法要发挥其刑法适用的指向性功能,就必须注意其条款规定与刑法的对应性。如果附属刑法不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就可能导致适用上的混乱。如,我国1992 年4 月3 日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 条规定:“雇用、容留妇女与他人进行猥亵活动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 条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此处的刑法是指1979 年的刑法,1997 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是流氓罪,而1997 年3 月修订的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是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两者之间风马牛互不相及,如果《妇女权益保障法》不及时作相应修改则难以适用该条规定。
注释:
1、9、11 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 年版,第140 页、第140 页、第123 页。
2 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80 年第1 期。
3、4、5[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第29-43 页、第44 页、第49-50 页。
6、8、10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8 页。
7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97 页。
12[日]川端博:《刑法总论讲义》,成文堂1997 年版,第84-85 页;转引自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8 页。
13 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6 页。
14 喻伟、聂立泽:《法定犯的认定与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00 年第4 期。
15 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0 页。
第8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内容提要: 惩罚是监狱行刑的重要内容,是监狱存在的法律属性和本质机能,但是有些学者出于进化论的需要却把其解读为类似体罚和权力的代名词。现代社会条件下监狱惩罚本身具有正义、平等、人道和秩序的价值元素,而惩罚本身具有的这些元素是对惩罚内涵和外延的自我限制。另外,鉴于惩罚具有权力的外在性和表象性,所以必须明确惩罚的客体和监狱纪律的内容和属性,并基于理性主义对其权力的扩张性进行限制。
一、问题的由来
监狱并不是与法律一起产生的,至少不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刑罚一起产生的,其一点可以证明:作为“罪恶昭彰”代名词的古代狱制如果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看,其实监狱的诞生是人类历史文明进化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监狱这个惩罚武库中的一个基本因素,确实标志着刑事司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刑事司法走向人道。”[1]然而在法治与权利至少在文本上庄重给予了宣告的当代,较多学者们极力探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罪犯权利保障与监狱改造机能的内涵和价值,以划清当代监狱人本主义思潮与专政工具主义价值的界限,以表明惩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远离了监狱的价值体系,甚至有的学者把惩罚当成了体罚的代名词。其共同忽视了一个刑事法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命题——监狱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史上即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也不是可以和惩罚相剥离的。而且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如果不把监狱惩罚的本体和边际界定,就无法可以说清罪犯权利的位置与边界,就无法对惩罚的外在权力属性进行限制。所以笔者极力想在本篇论文中尝试探讨监狱惩罚机能的本体与维度限制。
二、惩罚是监狱存在的法律属性和本质机能——对惩罚属性的再认识
我国《监狱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我国作为规范监狱行刑最为根本法律依据的监狱法以文本的形式规定了“惩罚罪犯”。对于“惩罚”的两个字眼,频繁地出现在刑罚学各种理论诸学中。有的把其作为刑罚的本质,如古典学派代表人物康德认为惩罚绝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对罪犯或者公民社会都是如此,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都只是一个人已经犯了一定的罪行才加刑于他。[2]由此可以看出,康德从绝对平等的原则出发,认为刑罚的本质就是通过惩罚来达到对犯罪的公正报应。有的把惩罚当做刑罚的目的,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在于限制和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权利,此种惩罚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以制止犯罪的发生。[3]有的把惩罚当做刑罚的功能之一,认为刑罚是对犯罪人适用的强制方法,首先对犯罪人发生作用,任何刑罚都具有惩罚的功能。[4]如日本学者宫本指出,作为刑罚,以对受刑人剥夺其财产,或剥夺其身体自由,有时还剥夺其生命为内容,所以刑罚为一种害恶,必然发生痛苦这一现实,必须率直地承认。[5]从上述的几种关于刑罚的学说中可以看出,惩罚在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中或把惩罚作为本质或作为目的或作为功能。
我国有些学者把刑罚理论中的惩罚延伸至刑罚执行的理论中,对于监狱惩罚从政治属性或者工具属性的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如我国有的学者就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监狱刑罚执行,惩罚是我们长期奉行的阶级斗争哲学的结果,具有强烈的专政含义,这些思想观念深深影响着监狱警察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在现实中就是表现为对罪犯的惩罚,惩罚,再惩罚,剥夺,剥夺,再剥夺,惩罚就是意味着罪犯只有接受惩罚的权利,就是履行义务的权利。[6]传统意义上的刑罚执行就是用单纯的政治权力至上来压抑人性,用统治者的权力武断地规训惩罚罪犯,以实现政治要求和政治价值,惩罚所体现的是将刑罚对“实为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向将来的一种“可能性的为”引申,使刑罚得到了一种任意的扩张,以及对曾犯过罪的社会公民的将来私人生活选择进行粗暴干预。[7]惩罚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毫无疑义该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报应主义,惩罚从人类的演进过程中就一直离不开精神的贬损和肉体的折磨,特别是在愚昧时代和封建未启蒙时代达到了极端。但在刑罚进化论①者眼中现代主义的法律文本竟然依旧明文规定了惩罚,而且是“为了惩罚”,此惩罚为彼惩罚吗?笔者认为监狱行刑的惩罚属性在政治视野中的解构中一定会得到毫无意义的扩张和扭曲,如果先入为主地把惩罚与有形的恶或政治性的压迫联系在一起,其本来的意义则会非理性地转为面目可憎。在政治哲学中的惩罚是与对抗反对抗中得出来的结果,政治哲学中的解析语义本来就存在着一定或极大地扩张化。而理论是在没有前提假设指导下的观察产物,不可能经由其他方法达成。[8]现代中国如果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诠释势必会得不出恰当的应然的结论。不管刑罚进化论者眼中的惩罚是何等的不应然,惩罚都是实然的存在,而且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延续下去本来的机能,但其表象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才是尤其重要的。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无论如何没有改变,法治条件下把它界定为监狱存在的法律属性和本质机能才能还它本来的面目。惩罚本来具有多重的含义,它当然具有政治的功能,即社会合法控制犯罪和罪犯的一种必要手段。
然而正如福柯指出,惩罚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这项工作只有在成为某种自然机制的一部分时才能成功。[9]在现代社会日益追求法律文本主义的背景下,立法者们把惩罚写进了法律的文本中。而“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法律语言的表述必须要考察惩罚与改造的两种机能或属性的关系才能清楚惩罚的本体属性。惩罚从监狱的诞生那天起或者说早在监狱诞生前就是抵制罪犯犯罪的一种手段,归功于近代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惩罚为了实现正义必须要对犯罪加以惩罚,在惩罚时为了防止对罪犯的憎恶过头,就必须保持对刑罚的收敛,保持罪犯间的大致均衡。于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规范确证范围内的惩罚人道化就明确了监狱惩罚的法律属性:为了表示被犯罪所破坏和否定了的法律秩序与规章制度是现实地存在的,不能允许放任那种不法行为状态,就此而言,对犯罪人的惩罚才是必要的,惩罚就意味着恢复被破坏了的法律秩序的意义上,为维护法律秩序而对个人处以必要限度以内的刑罚是正确的。[10]众所周知,改造也是监狱存在的重要机能之一,而且是刑罚执行人道化的最为重要的表象。改造一开始并不是与刑罚并存的,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改造真的是从近代学派竭力提倡而开始就有的吗?单举一例或可表明个中情形,《尚书·酒诰》中说:“毋庸杀之,姑惟教之。”“令人幽闭思衍,改恶从善”也在西周的监狱制度中得到了极力的提倡。[11]但改造的机能明显在未启蒙时代不是其主要机能,及至启蒙时代改造才广为进入现实中人们的视野。关于惩罚与改造的关系有的学者提出了“钟摆效应”的概念,来说明惩罚与改造的刑罚哲学的历史循环性,他认为刑罚哲学是一个连续体,它的一端是惩罚,包括报应、犯罪控制和强硬政策;另一端是预防,包括改造治疗等。每个时期的主导哲学就在这两个端点上产生:刑罚哲学朝着惩罚一端倾斜,矫正政策就会具有较多的惩罚性;刑罚哲学朝着预防一端倾斜,矫正政策就会有较多的改造性和人道性。[12]钟摆效应理论或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监狱行刑的刑罚哲学或理念在各个时期的关系命题,但笔者认为,改造与在我的本篇论文中想要论述的惩罚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属性上的。虽然法律文本把惩罚与改造并列于条文中告诉人们惩罚与改造都是监狱刑罚执行的机能,除此无它。但正如笔者前述,惩罚生来就是监狱的本质属性,改造是监狱在人类文明艰难史演变中嫁接而来的,是本质机能产生出来的主要功能,没有本质机能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衍化出主要功能,衍化的功能是对本质机能的必要修正和主动补充,但这一修正或者补充而来的改造机能不可能从根本上替代本质机能,本质机能是事物质的规定性,即监狱惩罚机能是监狱存在的质的规定性。这也意味着几千年来作为监狱存在的本来的内在根据虽然其属性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随着人类的工业文明和政治文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这一内涵被一些启蒙思想家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把改造的功能嫁接给了惩罚,正如格老秀斯指出:“惩罚的第一目的,就像保罗、普鲁塔克和柏拉图所说的改造,惩罚的目的就是使一个罪犯变成一个好人。”[13]
当然本文中的研究必须声明,虽然惩罚并不相当于前述有的学者把惩罚当做一种类似体罚的普遍权力,笔者也丝毫没有否定监狱的改造罪犯的功能,也不想——当然也没有否定监狱的政治属性,只是想指出刑罚哲学中的刑罚进化论的虚伪和误导,②刑罚的轻缓化和人道化不能否定监狱存在的惩罚法律属性和本质机能,而其只与刑事政策的运用以及规范有效性的维持、规范的稳定有联系。
三、惩罚本身具有的价值元素对惩罚的自我限制
监狱作为国家的政治附属物的同时是法律控制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和物质载体,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衍化过程中其存在的形式虽然从没有过改变,其作为机能的本质属性的惩罚内涵必然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惩罚经历了威吓时代的由主观到客观过渡,惩罚客观化成为威吓时代的历史成果;博爱时代的惩罚否定了国家的恣意与残酷,保障罪犯人权成为根本;科学时代的惩罚取代了博爱时代的惩罚,从以前单纯保护犯罪权利兼带剥夺和报应。因此从上述惩罚的进化史可以得出结论,惩罚即使其作为监狱存在的内在根据从威吓时代到科学时代没有发生改变,但惩罚的基本内涵和外延总是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演化。既然惩罚本身有其相当的易变性,那么国家对罪犯的现代监狱制度存在法律属性的根据——惩罚,不但是作为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最后规制手段,而且是为人类共处和谐和为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的规范性安排,这种规范性安排背后正是有了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才使得其具有自身的价值,反过来,惩罚自身具有的价值属性本身又是对监狱惩罚机能的必要限制。笔者以为监狱惩罚机能至少具有正义、平等、人道和秩序等品质,即只有正义、平等、人道和秩序等品质的具备才能算得上此种规范性的安排,才具有存在的合理必要。
正义是惩罚的内在根据。“一个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可强制实施的惩罚手段,就会被证明无力限制不合作的、反社会的和犯罪的因素,也就不能实现其在社会中维持秩序与正义的基本职能。这就解释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即所有成熟的和高度发达的法律制度都通过把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置于执法机构和执法官员的支配之下以使法律得到最大限度的服从。”[14]惩罚是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最重要的刑罚哲学,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监狱惩罚哲学在西方国家复以占为主导地位。[15]监狱惩罚和正义可以联系在一起吗?如果从前述有的学者把惩罚类似于体罚或一种政治权力和武力的规训来看肯定永远也得不出正义是惩罚的第一价值属性。康德和黑格尔等古典学派学者早在几百年前说明了这一惩罚的正义性。康德把自然的惩罚和法律属性的惩罚加以区分,自然的惩罚是由于是自身的惩罚当然不在立法者考虑的范围之内。法律的惩罚是法院加诸犯罪人的惩罚,这种惩罚应当具有正义的根据,这就是刑罚的正义性,惩罚是建立在犯罪人的行为之上,是那种纯粹司法性的立法理性所决定的,犯罪人和公民的联合体中的其他公民都必须给予遵守。黑格尔认为刑罚的正义性应当从法的辩证关系中得以阐明,尤其强调犯罪人的意志自由对于实现刑罚正义的重要性,所以法等同于正义,犯罪的不法性决定了它对正义的否定性,刑罚作为否定之否定,它肯定了法,即恢复了正义。[16]正如犯罪的本质——孤立的个人反对现行统治阶级的行为从人类历史发明了犯罪概念以来,它就从来没有过一刻的改变一样,作为对抗犯罪手段的刑罚的正义性自然也不可能发生转变。作为刑罚动态过程中的监狱行刑,其必须有一个载体来完成正义的任务,惩罚则担当了完成这一任务的使命。如果在前面动态过程中的刑罚的制定和量定是一个观念性或抽象思维的事物,③那么监狱惩罚的正义的体现则明显可以感观而且具有具体的物质性。比如罪犯入监狱前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入监狱后则为犯罪人,身份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某些自身重大权利的被剥夺,某些资格的限制,法律以这些感官的制裁来直接表明正义需要恢复。那些具有意志自由的且是因为选择意志自由而犯罪的罪犯则在面对监狱的惩罚必须反思因为不理性的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惩罚的正义另一面体现在对体罚和精神虐待的完全禁止。一个再好的监狱惩罚体制如果允许对任何哪怕是罪大恶极的罪犯进行肉体上的责罚,那都是惩罚的非正义。于是惩罚将愈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受惩罚的确定性,而不是公开惩罚的可怕场面,应该能够阻止犯罪,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17]
平等是惩罚的外在机制。平等是正义的自然延伸和必要补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有多义性的特点。正如美国学者萨托利指出,平等可以用非常实在的方法加以简单化的表述,但也可以用高度而又无从捉摸的方法加以表述。一方面,平等表达了相同性的概念,另一方面平等又包含着正义。两个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18]平等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并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理念之一,近代启蒙运动更将平等提高到与自由、人权相并列的重要地位,并从政治平等开始向法律平等转化。[19]法律对于平等也起着一种相同的双重作用,在历史上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平等方面发挥过显著的作用,法律平等所意指的不外是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方式来对待。[20]监狱惩罚的平等价值属性就在于刑罚的执行不因特殊身份或个人的政治地位而造成差异,任何被刑罚执行的对象都是因正义的惩罚需要而被放置监狱这个特殊器物之中,且在法律的文本中给予明定。当然因为平等有着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分,博登海默更注重实质的平等,他认为实质的平等使得法律的有效性便受到了这样一种要求的约束,该要求就是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待遇,而只要是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21]监狱的惩罚是一种法律的基本属性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权力的重要分配的一个方面,被法律赋予特殊法律身份的被刑罚执行的对象直接面对和感知着这种权力的平等属性,惩罚如果可以没有法律平等属性的对待则会加剧罪犯对法律权威的藐视,监狱秩序的稳定和谐势必遭到破坏。当然这里所要证明的平等必须要和刑罚执行中的个别化原则相区别,个别化指的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处遇的制度,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遇改造方式。特别是近年来学者们探讨的罪犯权利中的特许权的一些方面,这些特许权并没有较多的法律给予规定,而是监狱在行刑过程中考察罪犯的现实表现给予相应的处遇,这其实正是法律实质平等和形式平等相结合的体现。如罪犯都被剥夺人身自由在监狱服刑,这是行刑中的形式平等,任何罪犯都没有法外服刑的特权,但是法律根据重返社会的原则规定了相应的罪犯可以离监探亲,这项行刑制度并不是对所有的罪犯可以开放。一个虽然只有余刑几年的罪犯,即便因为亲人的死亡却因为常常破坏监狱秩序的稳定也无法得到这项处遇的优待,这完全体现了惩罚的实质平等性对惩罚边界的确定。
人道是惩罚的必要前提。监狱之惩罚曾经以一种血淋淋的残酷形象存在过,尽管毫无疑义现代社会惩罚已经轻缓化了,但只要惩罚存在一天,它给罪犯带来的绝大部分只能是痛苦,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把这种痛苦控制在人的尊严所能接受的限度之内,这就是惩罚的人道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道性越来越成为现代刑罚追求的价值目标。康德从“人是目的”这一原则出发,对罪犯的人格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指出行为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做目的,绝对不能只当做工具。在康德看来,人是客观的目的,他的存在即是目的自身,没有什么其他只用做工具的东西可以代替他。根据“人是目的”的原则,康德指出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而惩罚是刑法根据理性的判断而规定的,国家惩罚罪犯为了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就必须尊重人格,尊重人的尊严,这是自然法的要求。从尊重人格的观念出发,其主张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原则,绝对不允许对犯罪人进行虐待。[22]惩罚的人道性一直是中国现代监狱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却也是制约传统类型监狱向现代监狱飞跃质变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当然当下中国监狱惩罚人道性的贯彻的障碍并不在于体罚或其他不可以公开的一些物质性的因素,而应当进入某种制度层面上的解读。毫无疑问,当代现实条件下中国监狱不会或者至少很少在物质层面上会发生不人道性的情形,吃饱、穿暖等物质基础的提供对于罪犯的惩罚条件下的基本生活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随着监狱运行机制的进一步强化和执法者维法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对罪犯的致伤致残案件较以往有较大的下降。笔者以为,行刑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现实语境条件下的某些行刑制度的缺位会导致惩罚人道主义某种程度的泛政治化的口号和虚假的表象,这才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惩罚人道性对惩罚的较高层次的限制。例如,《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监狱法》规定的罪犯可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监狱对犯人的劳动主要是经非货币的实物形式作为回报,包括向犯人提供提一些日用品、假定工资,而这些微薄的劳动报酬只是象征意义,并不表明罪犯劳动就真正获得了劳动报酬权利。于是行刑实践中,大多数监狱因为劳动成本的低廉,为了经济利益,大大延长国家有关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规定,使得作为三大改造手段之一的劳动改造成为了一种绝对性的义务。而欧洲国家大多实行向罪犯劳动支付报酬的制度,例如《意大利监狱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犯人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国家关于设施外劳动时间的规定,并根据实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囚犯劳动的工种,对各类劳动人员确定报酬,该报酬平均不超过同业工人工资的2/3。”[23]实践中欧洲一些国家的劳动报酬制度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如在法国,1997年参加劳动的罪犯月平均收入达到了1790法郎(约合人民币2291),在丹麦参加监狱劳动的犯罪人每小时的报酬约为6到7个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70元),在比利时为每小时约为28到60比利时法郎(约合人民币147元)。[24]当然,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当下中国社会才刚刚脱贫,但对于罪犯劳动报酬权利的适当保证并不会造成惩罚机制的扭曲,相反这种以法律的手段给予保障会极大地证明惩罚的正义性和人道性。
秩序是惩罚的必要保障。秩序是指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无序则表明存在着断裂(非连续性)和无规则的现象,即缺乏智识所及的模式——这表现为从一个事态到另一个事态的不可预测的突变情形。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决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或“违背自然”的努力。[25]在法律层面上所要论证的是一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具有客观实在性,并具有可控制性,必须将人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从而根据社会需要建立起一套可控制的社会秩序。监狱惩罚最外向的机能和本质属性正是体现于此。刑法的最为重要的机能之一的社会保护即通过惩罚犯罪来体现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基于国家维护其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意志制定的,根据国家意志,专门选择那些有必要用刑罚制裁加以保护的法益,侵害或者威胁这种法益的行为就是对犯罪处以刑罚的根据,刑法具有保护国家所关切的重大法益功能,这是刑法存在的根基。[26]而刑法对社会秩序的保护不只是对罪犯的罪刑的量定和制裁,最终还得通过一个持续性的可以施加合法影响的东西来规范,这样社会秩序才可能最终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监狱的惩罚机能最终担当了这一切,并配以惩罚本身具有的前面论述的另外三个价值属性加上改造的修正机能一起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惩罚所具有的维护秩序的价值还体现在对改造机能的保障,集中体现在惩罚是监狱秩序本身稳定的前提。但是,反过来,监狱秩序的有序运行又是对惩罚正义、平等和人道的必要保障,即对惩罚的合理限制。监狱秩序是监狱在对罪犯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在一定政策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刑罚执行观念,有条理、有组织地安排各种行刑制度以使监狱管理、教育改造和对罪犯的奖惩达到正常、安全、良好、稳定的一种状态。在一个特殊的机构中,因为利益主体的利益存在着相对性的不平衡,如果伴随惩罚带来愈来愈多、模糊的、极为弹性的、过于宽泛的和不准确的规定导致了监狱秩序的无常性和模糊性,那么,这种监狱秩序运行状况必定会增加处于不对称地位的罪犯的危险感和不安全感。如果监狱秩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常常连最起码的监管安全都难以保证,监狱要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必定难以实现。这时监狱的秩序运行状态必须得到有效的保证,纪律的维护和保障都必须体现强制性的特征,惩罚机能的物质性体现则表现得相当明显,此时的惩罚不再是观念的、抽象的了,禁闭、限令悔过、行政处分和记过、某些处遇制度中特许权的剥夺都是秩序对惩罚的合理限制。进一步考察的话,因为如对罪犯的某种处分必然是其违反了监狱对其惩罚的某种合理性的规则,特别是在一个特别封闭的小型社会中,被聚集在一起的特殊群体会对某种现存秩序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如果秩序一旦遭到某个罪犯的破坏,那么某些潜在的秩序破坏力量可能会集中表现出来,其他绝大多数守法循规的罪犯可能会放弃对秩序和规则的依赖,那么惩罚的外在机制很可能难以得到顺利的运行,所以必须重视监狱秩序对监狱惩罚机能的限制。
四、基于惩罚具有外在权力属性之理性限制
“也许没有任何一项行动权力,包括没有任何一项在伦理上得到阐明的行动权力,能够毫无例外地和不受限制地得到贯彻实行,这些限定,也就是说,各种抽象地看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伦理价值的正确比例,在经验中才能获得,即在一种理性分析过的经验中才能获得。”[27]监狱惩罚之机能从经验的形态上来看具有外在权力的属性,而权力的属性具有相当的膨胀性和扩张性,特别是惩罚权力的属性和某种政治权力相结合,如警察的某些制裁权力相联系,那么惩罚的力度可能很难做到适度的控制,罪犯的合法权利特别是某些罪犯特别处遇制度中的权利则难以保障。根据韦伯的观点,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试图将其意志毫无拘束地强加于那些为他所控制的人,这种统治形式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它往往是统治者出于一时好恶或为了应急而发布,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近代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刑罚的惩罚属性走向人道、正义、平等的一个重要契机,刑罚作为对于犯罪的一种社会反应,属于社会行动的范畴,在古代社会受人的报复本能的制约,刑罚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活动,在近代刑罚理性化的指引下,特别是贝卡利亚把几何学的原理引入刑罚的可计算性,才使得理性主义完成了对惩罚的恰当控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贝卡利亚不像已往一些刑法学家那样只满足于对刑罚本质、目的和作用的抽象理论,他力图找到精确运用刑罚、发挥其最佳效益的规则,使其能从政治算术和刑罚力学的角度来探索这些规则。[28]在监狱惩罚机能实现的过程中,虽然我们无法找到像贝卡利亚发现刑罚能够和数学规则一样来计算,但我们当然可以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去找到限制监狱惩罚的非理性的实现,因为惩罚权力的属性具有外向性和表象性。
对监狱惩罚外在权力属性的限制必须首先明确惩罚的客体。客体是指主体中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29]惩罚的客体即惩罚的对象是指什么,这个问题的明确对罪犯权利的边界划定至关重要。一个观念的误区必须谈及,即惩罚的客体不是指罪犯,罪犯在刑罚执行权的运行机制(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中和行刑机关或执法者一起构成了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主体,只不过两个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一个为积极主体另一个为消极主体。惩罚对积极主体来说是一种职责,而对消极主体来说是一种义务,惩罚的义务内容则构成了惩罚的客体。监狱惩罚客体最主要体现为自由和某些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们之所以把监狱关押罪犯的刑罚叫做自由刑,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就在于区别其他的肉体刑和耻辱刑,监狱惩罚罪犯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就是把一定的犯罪之人置于监狱这个特殊的装置之中,在剥夺自由的前提下进行有组织的教育和改造,以便使罪犯顺利重返社会。由于罪犯自由成了惩罚的重要载体,那么和自由相关的一些罪犯权利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剥夺和限制。所以对惩罚机能的必要限制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惩罚总是和权利联系在一起的,惩罚的背面往往意味着罪犯的权利,所以明确惩罚的边界和明确罪犯权利的边界可能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犯罪人的权利是指得到法律保护的要求,当犯罪人享有某项法律权利时,监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监狱承担着满足犯罪人要求的法律义务。[30]现代法治的国家无不在相关法律文本中明确罪犯享有的相关重要权利。自由的剥夺和限制大致可以包括部分权利被暂停行使、部分只能限制行使、特定权利不能主张等三种情况,这些被限制的权利有的有法律明文规定,有的没有法律规定而因惩罚的自然属性被当然剥夺了。④因文章篇幅所限加上近年来众多学者对罪犯权利的探讨较多故本文不作过多探讨。⑤
对惩罚外在权力属性的限制必须明确纪律的属性。关于纪律的属性对于惩罚机能的限制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监狱纪律是指要求在监狱中的犯人必须遵守的禁止性规定,包括法令规则、具体命令、个别指示在内的被收容者所应遵守的一切行为规范,受刑人有服从这些纪律的义务。纪律具有系统性、成文性、禁止性和惩罚性等特征,系统性是纪律的具体内容包括违反纪律的不同情节、违反纪律的后果、给予纪律处罚的程序、对错误的纪律惩罚补救措施等;成文性是指纪律规范用明确的文字表达出来,纪律条文通常体现在监狱规则、犯人手册之类的文件和资料中,仅仅口头宣布监狱纪律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禁止意味着不允许或者禁止犯人进行所提到的事项或者行为,这是监狱纪律与其他监狱规范的根本性区别之一,也是犯人的法律义务的重要体现。[31]迫使受刑人遵守纪律的方法有强制和处罚,所谓强制是指使用警械等手段,包括预防性强制、制止性强制及镇压性强制;为了维持秩序,有必要要求受刑人遵守一定事项,如有违反便进行处罚。但处罚虽不是刑罚,它是作为罪犯的一种不利处分的行政处罚,因此,其实施必须严格依据法定的原则进行,即对该行为惩罚种类应事先向受刑人予以说明。”[32]福柯也指出,纪律带有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惩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33]从上述纪律的内涵和构成特征可以看出,纪律是监狱为了维护自身的秩序和稳定而对罪犯制订的规则,其本身虽然不是刑罚,但因为其对象的特殊和性质的特殊则使其具有惩罚的属性。监狱为了达到良好的秩序效果往往使纪律遵守变相得到执行,而且因为监狱是个绝对权力机构,纪律的推行往往依靠强大的警察权力来实施,这时如果纪律一旦成为惩罚的奴隶,那么秩序和人道的天平往往向秩序倾斜。在行刑实践中关于罪犯生活、学习和劳动现场的纪律,监狱为了强调监狱现场秩序的一致性、稳定性和严肃性,⑥罪犯的行为必须遵守上个世纪监狱的标语口号“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等诸如此类的标签性纪律训令,于是军事队列训练⑦中的规范被自然地运用到了罪犯行为的养成之中,被标签化的行为和动作成为罪犯监狱化的重要一步,不难发现纪律的规训是功不可没。罪犯在纪律的强大惩戒功能面前成了机械的受令者,以至于有罪犯出狱后写到:“在走往城里的路上(从监狱释放后),川流不息的行人和来往的汽车一样使我心惊肉跳,他们看上去像一群被人控制的癔病者,似乎各有各的打算、目的和方向……在监狱里是不会有这种窘境的,在那里,人们都排着整齐的队伍……”[34]所以笔者以为对于纪律的执行必须以明文规定为准,而且在行使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罪犯的惩戒适度,以唤醒罪犯的羞耻心而不是引起罪犯的不满反抗。特别要注意到监狱纪律的制订必须要以便于罪犯重返社会为原则,所以对那些所谓强调整齐划一的秩序完全可以适当放宽或全部废除,或者只针对某些确实需要强制性纪律制裁的罪犯。
收稿日期:2009-02-20
注释:
①所谓刑罚进化论其大义为当今的刑罚应该由适应人道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报应主义、客观主义向适应科学时代的团体主义、目的刑、主观主义进化,这是一种线性历史进化论的反应,其本质为刑罚轻缓化、非罪化、非刑罚化和非设施化。
②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即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能防止国家政权对人权的非法侵害,而且事实上,这种侵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甚至可以达到血腥恐怖的程度。具体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4.
③说刑罚制定和量定是抽象或观念性的,比如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对社会秩序破坏的恢复都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
④例如罪犯扶养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因为自由被剥夺自然在监禁期间现实生活中无法被实现。
⑤关于罪犯权利的探讨学者大多对罪犯权利的构成特征、分类和范围等作了较多的探讨,并且和罪犯的特许权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认为罪犯特许权是监狱基于罪犯的改造表现和再社会化的需要而赋予部分罪犯的特殊待遇,笔者以为这是近年来对罪犯权利研究的重大突破。具体参见柳忠卫.罪犯特许权论——以罪犯与其配偶同居权为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2008,(4).赵运恒.罪犯权利论[J].刑事法杂志,2001,(4).
⑥此处所说的秩序的一致性、稳定性和严肃性并不是指前面笔者论述的秩序是惩罚的必要保障内涵意义的相同,其指的不外是要求所有的罪犯全部必须遵守的纪律秩序具有的机械性和僵硬性,忽视了罪犯的个性化和必要的权利表达空间。
⑦现阶段我国监狱仍然实行的罪犯队列军训等军事化管理源于20世纪解放区的改造反革命犯的普遍做法以及建国后各个劳改支队是由军队或兵团建制而设立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也由军队抽调而组建,另外也受到前苏联的影响。
注释:
[1][9][17][33][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59,117,9,9.
[2][13]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424,158.
[3]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408.
[4]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45-46.
[5]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87.
[6]参见张晶.当代监狱制度的价值[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12).
[7]张峰.论现代刑罚的品质[J].河南大学学报,2006,(4).
[8][英]吉尔德.德兰逖.张茂元译.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
[10]周光权.刑罚进化论——从刑事政策角度的批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3).
[11]张风仙,刘世恩,高艳.中国监狱史[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22.
[12][15][24][30][31]吴宗宪.当代西方监狱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19,126,768-769,421,471.
[14][20][21][25][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64,308,318,227.
[16][19][26]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2-65,263,155-156.
[18][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40.
[22]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1.
[23]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4.
[27][德]H·科殷著.林荣远译.法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91.
[28]参见黄风.贝卡利亚及其刑法思想[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12.
[29]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3.
第9篇: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内容提要:限时刑法是对为适应一时的或特殊的情事而在一定时期禁止为某一行为或命令为某一行为的刑法规范的总称。通常应根据法规的目的与实质来考察限时刑法失效后是否还存在适用的合理性。委任行政规范虽不具有限时刑法之形式,但因其与空白刑法相结合即可以成为空白构成要件的禁止内容从而影响到行为的可罚性范围。如果仅仅是作为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发生变更,那么仍应适用行为时之补充规范。
限时刑法,是对为适应一时的或特殊的情事而在一定时期禁止为某一行为或命令为某一行为的刑法规范的总称。它属于一种只在一定时期实施的特殊法。当这种一时的或特殊的情事已消灭或变更,对某一行为就不再加以处罚,或者因指定施行有效之期间已终了而失效以后,对于在该法规有效期间实施的违反行为,仍可适用该法规作为处罚的根据。如果限时刑法的施行期间届满,而立法者又未再依法定手续延长施行期间,那么该限时刑法即属当然废止。①限时刑法一般都是基于立法理由的消失而失效,而不是基于法律观念的改变而失效。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4款规定:“只适用于特定时期的法律,即使该法律在审判时已经失效,但仍可适用于在有效期间实施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即是明文规定了其适用期间的限时刑法。
我国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限时刑法,但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2条第1款却对时效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该条的规定,单纯从形式上看,对于那些凡属因行为之后的法律、法规而使得该行为本应遭受的刑罚被废止的,应该一律作出免予刑事追究的决定。“可是,基于一时的情况或者为一定时期所制定的法令有很多,这种法令由于一时的情况消灭或一定期间的过去就被废止。如果根据上述原则,对废止前的违法行为不能处罚。因此,这种法令中对尽管在废止后是否也不能处罚有效期间中的违法行为就成为问题,这就是所谓限时法的问题。”②特别是在行政法规中,根据一时的需要而制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废止的法规很多,而这些法规有的是作为刑法规范本身出现的,有的是作为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出现的,因而就存在很多限时刑法的适用问题。作为限时刑法的刑法规范如果发生变更,因其涉及刑罚罚则的追及效力的问题,那么就出现了是否应适用《刑法》第12条第1款以及是否应该与其他法律规范相区别而特别对待的问题。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比较少,因而很有必要对限时刑法进行深入研究,以切实解决法律、法规发生变更后如何适用限时刑法的问题。下面笔者拟就限时刑法的含义、委任行政规范的变更与限时刑法的关系以及限时刑法的效力等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刑法学理论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限时刑法的含义
关于限时刑法的含义,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1)“最广义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不论法律是否规定特定的期间为该法律的有效期间,只要该含有刑罚内容的法律是为适应一定的情事而颁行的,即为限时刑法。如日本有学者就认为,日本经济统制法规中的刑罚规范就属于限时刑法。因为只要有一时的危险存在,即有加以应付之必要,所以日本经济统制法规并未预定有效期间。③而对该说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所谓“一时”是相对的,很难界定何者为“一时”或“非一时”,故以“一时”来定义,态度未免暧昧不确实。④(2)“广义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除设定一定有效期间的含有刑罚内容的法律为限时刑法外,为适应一时的情事而颁布的含有刑罚内容的法律也属限时刑法。当限时刑法废止后,对行为人在限时刑法存续期间实施的行为不得加以处罚。但如果是立法者法律见解的变更,那么对行为人的行为仍得加以处罚。⑤日本的判例曾采用过这种学说,如1950年4月11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认定,日本《修订物价统制令》第11条第2项将处罚范围缩小,对非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人不予处罚的规定,只是基于立法者法律见解的变更,并非法律本身的变更,不属于限时刑法变更的问题,故变更前的行为仍不得免其处罚。⑥(3)“狭义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制订刑法规范之初就预定了有效期间或事后依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了有效期间的,均为限时刑法。出于临时需要而制定的没有确定废止时间而处于迟早要废止命运的法律、法规,即没有确定期限的法律、法规,则为临时法。因战争或其他紧急事件而制定的法规,大多属于临时法。也就是说,有确定存续期间的刑事法律、法规为限时刑法,而无确定存续期间的法律、法规则为临时法。因此,对临时法与限时法要区别对待:“对临时法,不认可其失效之后的适用;而限时法并不限于从一开始就有期限规定的法令,在事后因其他法律而附加规定了期限的情况,以及被委任决定填充空白刑法的空白规范的机关事先决定该规范的效力期限的情况,也属限时法。如果没有关于追及效力的规定,则虽然是限时法,也不认可其失效之后的适用。”⑦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区别对待,是因为对于已被废止的法律只要它属于限制时间适用的法律,就属于已经失去了效力的法律;如果在限时刑法的效力期限已经届满之后,对行为人在期限内实施的行为仍适用该法律,那么就不是对法律的解释而是对法律秩序的修正;而如果运用行为之后的法律,就有可能产生延迟诉讼、免除刑罚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因其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甚至破坏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应该被允许。
如果我们以是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还是根据刑法规范的实质为标准来判断某一法律、法规是否限时刑法,那么上述学说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1)“形式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凡是没有规定一定有效期间的法律、法规不属于限时刑法,其失效之后即不可适用;即便是规定了一定有效期间的法律、法规,只要其自身没有所谓追及效力的规定,也不应该认可其失效之后的适用。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对限时刑法都未作明确的规定,因而从立法技术上看,有必要将个别的行政刑法规范明定为限时刑法。这种希望通过立法上的明确规定来解决是否限时刑法的观点尽管不存在不妥之处,但现行法律大多是以告示(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支配国民生活的,如果将个别的要求以明文的形式规定为限时刑法,那么现时的法律、法规就可能处于无法适用之境地。如经济刑法的统制机能将无法发挥,经济法规将遭到全面的破坏。⑧1935年的德国刑法草案曾明文规定在一定期间有效的法律,即使废止或变更,仍得处罚其废止或变更前的行为。⑨(2)“实质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限时刑法无须以明文规定为必要。换言之,从探究法律的实质即可知悉其是否为限时刑法,而无须从形式上规定其有效期间。其理由在于法律虽然没有预定其有效期间,但是依照超法规的理论⑩仍可以解决其有效期间的问题。对该说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如果委诸法官对个案进行判断,那么难以避免法律适用的混乱,因而处理限时刑法问题,应以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为限。(11)日本的判例就曾采用这种学说,如1950年10月11日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当某种为处理一时异常情况而制定的法规在这种异常情况消灭后即遭废止时,该法规属于限时刑法。(12)
客观地讲,“形式说”没有考虑事物的本质,只是试图从形式上讨论限时刑法的适用问题。如果采用这种学说,那么对于因为某种原因而成为附加一定时间效力的刑事法律以及出于某种原因明确规定有追及效力的刑事法律,是否承认其为限时刑法或者是否承认其适用效力就存在问题。
对形式的限时刑法在其失效后仍然承认其效力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不承认限时刑法在失效后仍能适用,那么行为人就有可能故意使对自己的处罚拖延至规定了一定时效的限时刑法失效之后,从而使自己得以免除处罚。此外,行为人在限时刑法效力期限即将届满时实施违反该限时刑法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刑罚处罚之虞,那么就会出现行为人无视法律的情形,进而使法律的权威丧失。因此,必须基于国家法律的权威性,考虑限时刑法的特别效力而强制性地适用该限时刑法。当然如果仅仅是从保护法律权威性的目的出发来适用限时刑法也不妥当,因为如果为了保持法律的权威性就认可所有的法律在失效之后仍然对在其有效期内实施违反行为的人适用,那么限时刑法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刑法》第12条的规定也就丧失了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从实质上考察限时刑法失效后仍然适用的根据问题。从实质上看,刑法失效后存在以下两种情况:(1)对长期以来刑法规定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国家不再承认其具有犯罪性。即某种行为实施当时是作为犯罪来处理的,而在刑法失效之后,不再作为具有性、犯罪性的行为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第12条的规定得以适用。(2)在刑法失效之后,行为的性、犯罪性依然存在,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在刑法失效后仍然作为犯罪来考虑,只是有可能不再被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刑法》第12条规定的精神,行为时的法律在失效之后仍能适用。限时刑法就包含在后一种情况之中。因此,基于对《刑法》第12条规定的合理性基础与限时刑法实质根据的考虑,一般情况下,国家对行为犯罪性看法的改变可以预定,但在存在所谓限时刑法的情况下,国家对法律失效后有关行为犯罪性的看法并没有改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根据法律、法规的目的与实质而非法律、法规的形式来探讨其失效之后是否还存在适用的合理性。对此,需要重点考察的是“立法者的法律性见解”或者“国家的法律性见解”(13)是否存在改变,据此判断是否限时刑法,从而决定其失效后能否继续适用。根据这一见解,《刑法》第12条的一般性规定仅仅适用于存在设置该规定的实质理由之场合,而在存在限时刑法的情况下则不适用,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所谓追及效力的场合也不适用。在考察这些特殊规定的合理性实质根据时,也不限于有明文规定的场合,对实质上与之属于相同情形的场合,必须作出相同解释。这里所说的特殊规定并非例外规定,而是注意性规定。有时尽管法律缺乏明确的形式规定,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希望立法者立法时完全没有遗漏则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此,坚持形式的限时刑法论并不具有合理性。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如果从实质上考察法律、法规失效之后的效力问题,就会发现不仅限时刑法存在失效之后是否还能适用的问题,而且其他刑法规范也存在失效之后是否还能适用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即使某一法律、法规在形式上并不是限时刑法,在该法律、法规废止之时,也可以规定在该法律、法规废止后对其有效期间实施的行为适用该法律、法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立法上可以自由地作出某种规定,而是应当从事物的本质上考虑其现实上理所当然的可能性。另外,从形式上看,作为所谓限时刑法而被规定的法律、法规,也存在失效之后不能被适用的情形。对于这种情形,即使是立法者预先作出了属于限时刑法的规定,立法者也可以在必要时修正该法律、法规而删除限时刑法的规定,对于此种情形同样应该从实质上探讨其适用与否的妥当性。
二、委任行政规范的变更与限时刑法
如前所述,尽管我国目前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限时刑法,但是当行政刑法中的空白刑罚规范发生变更之后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却与限时刑法密切相关。作为空白刑法之补充规范的委任行政规范虽不具有法律之形式,且无刑法之实质内涵,但因其与空白刑法相结合即成为空白构成要件(14)的禁止内容,从而影响到行为的可罚性范围。因此,这种补充空白构成要件的委任行政规范如果发生变更,那么就涉及《刑法》第12条第1款的适用问题。
对于如何看待委任行政规范的变更与限时刑法之间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界、司法界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肯定委任行政规范与法律具有相同的效力,认为委任行政规范变更的效果与法律变更的效果相同。如有学者认为:“所谓法律有变更,尚包括填补规范之变更,也即当作禁止内容之法律、行政规章或行政命令之变更,也属法律有变更。”(15)另一种观点是否定委任行政规范与法律具有相同的效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委任行政规范与法律的效力不同,由于委任行政规范的补充规范并非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而委任行政规范的补充规范的存在与否为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该委任行政规范的补充规范所补充的构成要件无论是主观构成要件还是客观构成要件,也无论是论述性的构成要件还是规范性的构成要件,都属刑罚法规以外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委任行政规范的补充规范的存在与否,属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充足与否而宣告是否无罪的问题,即为事实问题,而不是刑罚法规的变更或废止的问题。如潘恩培认为:“所谓变更之法律,当然以刑罚法律为限。故如事实变更……及刑罚法律外之法令变更……均不属条文所谓法律变更之范围……”(16)陈朴生也认为:“称法律有变更,系指刑法之变更而言。其所变更者,为普通刑法,抑特别刑法,则非所问。至刑法以外法令之变更,虽有影响刑法之解释……应认为事实之变更,并非本条所谓法律之变更,自不生比较适用之问题。”(17)日本学者定塚道雄的主张也与之类似:“如就日本物价统制令而言,个别统制命令的变更、废止,对统制价额的概念并无影响。虽然法律规定‘超过统制额而受领货款’与‘超过若干元受领货款’的构成要件相似,但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价格统制令的规定形式属前者。因此,纵使个别行政命令变更、废止,对价格统制令而言,不但并未变更,且仍属有效存在。”(18)
日本司法界对委任行政规范的变更是否具有与法律变更同样的效力在认识上并不一致。如日本最高法院在“大藏省果实贩卖价格统制令违反案”中认定大藏省1947年10月27日告示将果实价格统制令予以废止并非直接废止刑罚法规,继而认定指定价格告示的变更、废止不发生刑之废止的效果。(19)但是,在“道路交通取缔法违反案”中,日本最高法院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认定该案被告的行为并无犯罪后刑罚已废止而应免诉的情形。(20)一般而言,在日本,作为空白刑法补充规范的委任行政规范发生变更,如果法律无特别规定的,那么法院均认为其属于法律变更从而作出免诉判决;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那么就认为并非法律的变更从而作出有罪判决。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界的态度与日本司法界的态度相反,即我国台湾地区司法界的人士都认为委任行政规范是事实而非法律。如我国台湾地区1962年“台上字159号判决”和1962年“台非字76号判决”均认定所谓法律的变更,是就刑罚法律而言的,并以依所谓的“中央法规标准法”第2条的规定制定公布为限,而行政法规即使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但因其并无刑罚规定,因而不能理解为刑罚法律,因此,像事实变更以及刑罚法律外的法规变更,均不属于刑法所谓法律变更之范围。(21)
三、限时刑法的效力
限时刑法的效力问题是一个与刑法的溯及力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刑法的适用上,刑法既不得前溯既往之行为,也不得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刑法不后及之原则”。(22)而“刑法不后及之原则”,是指在法律废止或者停止其效力后,不再对其废止或效力停止后所发生的行为或者犯罪适用该法律的原则。如我国1997年《刑法》第452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体现的就是这一原则。这种不后及适用的原则与正在生效的刑法不得溯及既往的原则显然存在实质上的差异:前者针对的是失去效力的刑法,而后者针对的是正在发生效力的刑法。
从前述学说与判例介绍可知,对没有明文规定适用期间的限时刑法发生变更后是否仍须对行为人科以刑罚,存在相互对立的以下两种学说:(1)“肯定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某一法律虽然失效,但对行为人的行为仍有处罚的必要。其理由是:如果认为因委任行政规范发生变更、废止就可以对违反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就会导致对同种、同质的罪作出不同的判决,并可能导致违法者利用委任行政规范频变所产生的不受刑罚处罚结果,而无视法律的存在继续实施不法行为,逃脱刑罚的制裁,但其性并不因为委任行政规范的废止而消失,其违反的可罚价值并未改变,因此,若不对其予以处罚,则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23)(2)“否定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刑法之所以不处罚失效后的行为,是因为立法者认为其性已不存在,如果认为其性依然存在,那么《刑法》第12条的规定就变得毫无意义。“在把这种考虑方法更进一步之时,为了保持该法律的权威性,那就必须对所有法律均认可对其有效期间之内的违反行为在失效之后仍然适用,那就不仅仅限于限时法了。”(24)若认为失效的法律仍有权威性,那么刑法的规定同样没有意义。因此,从刑法解释学及刑事政策学的角度看,如果法律没有作特别规定,那么例外地排除《刑法》第12条的适用就属不当,且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嫌。故限时刑法的有效期过后,如无明文规定,该限时刑法就不能继续适用。也有学者因否定这种法律的限时性而一概否认其溯及力。如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任何法律到废止时为止,都是一时的法律,但一时概念本身也是极为模糊的,而不可能严格区分适应一时情况的法律与并非适应一时情况的法律,因此,根据是否适应一时情况这种模糊的、不确定的标准,确立限时法的概念,并且承认作为与罪刑法定主义相联系的原则的刑法第6条的例外,是不正当的……作为动机说(25)基础的法律见解的变更与事实关系的变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独立发生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二者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因此,该学说不仅严重损害法的安定性,而且在所谓事实关系变化的场合,没有特别规定却承认刑法第6条的例外,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26)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也赞同这种观点。张明楷教授认为:“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永久适用,任何法律都是适应立法时的情况而制定的,如果认为适应一时情况而制定的法律是限时法,则任何法律都是限时法,于是任何法律都有溯及力,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在一项法律的有效期经过之后,对在有效期内实施的行为,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有效期经过之后仍然处罚,就不能处罚该行为。”(27)
总的来看,中外学术界都比较赞同“肯定说”,但都是站在“实质说”而非“形式说”的立场上赞同“肯定说”。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主张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才可以追究法律变更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即使所谓法律变更是就刑罚法律而言的观点是正确的,委任行政规范是否就不属于刑罚法律也存在疑问。所谓刑罚法律,应包括其构成要件在内,而不是仅指刑罚而言。因为如果没有构成要件存在,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刑罚法律。因此,只有将补充规范与空白规范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刑法规范,否则该法规就无适用的可能性。补充规范既然是立法者授权制定的,那么从实质上看它也就是法律。如果仍然认其为事实,而不是法律,那么在逻辑上就存在矛盾。法院的判决通常是先认定事实,再适用法律,然后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法律作依据,那么就无法得出结论。而认为委任行政规范是事实的观点,显然是以事实为大前提,又以事实为小前提,因而不可能导出结论。由此可见,委任行政规范应为刑罚法律,而非事实。同时,笔者认为“补充规范之变更为法之变更,对刑罚不生影响”(28)的观点也不正确。因为就《刑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而言,因法律变更而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国家的违法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缘故,对行为人在法律变更后实施的行为,已没有处以刑罚的必要,所以就《刑法》第12条第1款的立法精神而言,违法价值观的改变应属法律变更。
至于将委任行政规范视为犯罪构成事实而非犯罪构成要件,即认为委任行政规范是一种具体的犯罪构成事实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因为委任行政规范本来就是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当然是一种法规,而不是行为人行为的组成。立法者既然委任行政机关制定补充规范,那么也就是承认行政机关制定的补充规范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具有相同效力,否则,现行法制既有违宪之嫌,同时也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因此,把委任行政规范看成事实的观点显然不妥。
至于在委任行政规范发生变更后行为人在此期间实施某种行为是否应当予以处罚,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刑罚的变更与构成要件的变更区别讨论,构成要件的变更通常使刑罚产生变更,“不能因为限时法概念的引入,就承认作为与罪刑法定主义相联系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的例外”。(29)笔者认为,如果只是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发生变更,那么仍应适用行为时的补充规范。理由是:(1)空白刑法一般规定的都是行政犯,而行政犯与刑事犯本质上的差异在于行政犯的伦理性要弱于刑事犯的伦理性,其所维护的伦理也往往因具有隐藏性而不为国民所认识。但是这种隐藏的伦理性,在委任行政规范发生变更后,也并不发生变更,其非难性并未丧失,因而当然也就不能免除行为人的刑罚。而刑事犯伦理性的丧失通常要经过较长的期间,国民往往在法律变更前就对该刑事犯的伦理性产生信念动摇,在变更后免其处罚自然合理合法。(2)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一般都会因为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而频繁变动,如果认为因其变更即可免除行为人的刑罚,那么就难以达到限时刑法所预期的效果。因此,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若发生变更,从创设刑法规范的本质及其精神来看,该委任行政规范仍应适用。只有这样操作,才既可以解决刑法学理论上的困难,又可以避免刑罚权操纵于行政机关之手的弊端,否则行政机关就可能借委任行政规范变更之机实施规避法律的行为。
注释:
①参见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页。
②[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郑树周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3页。
③(18)参见[日]定塚道雄:《限时法》,载日本法学会编:《刑事法讲座》第1卷,有斐阁1952年版,第65页,第53页。
④(26)(29)参见[日]福田平:《行政刑法》,有斐阁1978年版,第48页,第62页,第62页。
⑤参见[日]福田平:《行政刑法》,有斐阁1978年版,第48页;[日]定塚道雄:《限时法》,载日本法学会编:《刑事法讲座》第1卷,有斐阁1952年版,第66页。
⑥参见[日]松尾浩也:《限时法》,日本《ジュリスト》别册28号《行政判例百选》,第87页。
⑦(13)(24)参见[日]八木胖:《行政刑法》,载日本法学会编:《刑事法讲座》第1卷,有斐阁1952年版,第102页,第104页,第103页。
⑧参见[日]定塚道雄:《日本经济刑法概论》,日本评论社1943年版,第105页。
⑨(21)参见刘钦铭:《论限时之行政刑法》,《军法专刊》1980年第7期。
⑩超法规的理论,是指以自由法论或社会法论作为方法论的理论。参见[日]牧野英一:《限时法问题与新判例》,载《理论刑法与实践刑法》,有斐阁1952年版,第260页。
(11)参见[日]佐伯千仞:《刑法讲义(总论)》,弘文堂1944年版,第106页。
(12)(19)参见[日]日本最判1950年10月11日刑集4卷,第1972页。
(14)需要说明的是,有时仅仅是补充构成要件要素,但是为了行文之方便,本文中统称为构成要件。
(15)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台湾大学法学院图书部2000年版,第89页。
(16)转引自洪福增:《刑法判例研究》,台湾汉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7)陈朴生:《刑法总论》,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23页。
(20)本案案情为:被告用第2种原动机车后座载运他人,违反依《道路交通取缔法施行令》第41条的新澙县原《道路交通取缔规则》第8条的限制。但是上述取缔规则于1958年全面修改,依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取缔规则》第9条的规定,第2种原动机车已不为取缔对象。但《道路交通取缔法施行令》第72条规定,行为当时规定具有可罚性的,法令变更后仍得加以处罚。《道路交通取缔法》及《道路交通取缔法施行令》虽为新《道路交通法》所废止,但是新《道路交通法》附则第14条仍规定新法施行前的行为依前例处罚。参见日本最判1962年4月4日刑集第16卷,第345页。
(22)参见钊作俊:《刑法效力范围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23)参见[日]木村龟二:《刑法总论》,有斐阁1959年版,第36页。
(25)持“动机说”的学者认为,对于这种没有明文规定适用时间的限时行政刑法是否具有溯及力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由于国家关于该违反行为的可罚性的法律见解发生变更(即后来认为该法律规定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而废止该法律时,该法律就没有溯及力;但由于单纯事实关系的变化或者某种状态的消失而废止该法律时,该法律就具有溯及力。
- 上一篇:新兵日记范文
- 下一篇:现场生产管理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