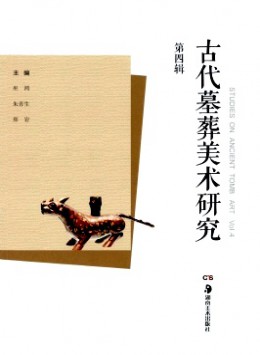古代文人文学素养与文学创作关系

【摘要】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素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的联络,作者的人格魅力在历史的评甄中被放大。基于儒家文化,符合历史规律的文学思想能够对社会起到警世的作用,从而对当时社会产生积极的正反馈或消极的负反馈的影响。尊重文人的社会地位,保持文学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统一性,对一个朝代的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古典文学;儒家文化;人格;历史
文学素养是一条路,一条文明之路。中国文学是开放和自由的,具有自我纯洁的机制。中国古代文学不限于狭义的语言表达艺术,而是一个博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系统在规范社会伦理,形成治国理念和决定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文人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传统,也有学、仕皆优而谪耀后世的普遍现象。文学素养根植于社会,而非文学本身。文学的归宿可以是政治、经济和宗教等生活的各种支配力量,也不是文学本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对文学评论家而言是再确切不过了。文学创作具有艺术性,是独一无二的。文学素养则是社会知识和创作经验的积累。文学素养有时是与社会阶层地位挂钩的,而创作灵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源于生活的体验,是不分等级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话对基层文学创作者来说也是再确切不过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文学素养与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在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中相互制约。文学创作对作者来讲是卑微的,也是神圣的。哪怕失去生命,他们也不愿封闭自己。政治家和作者的界限体现在阶层的固化上,而这种界限或隐或现都是存在的,需在阶层之间加以协调。曲折的人生经历是作者的艺术源泉。文学创作强化了作者的人格魅力,给予现实世界各种形式的思想鞭策。
文学演化为古代人们修身养性的社会载体,文人则成为古代社会树立风范的模范标杆。作者受众的群体不同,后世的历史评价也不同。中国文学的受众主体呈现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趋势。文学形成社会各阶层情感交流的社交网络,也演化成了一个从个人智慧、文学智慧到民族智慧的良性循环机制。但这种循环机制是不对等的,统治阶级掌握着社会思想的选择权。愚忠思想的存在使得主流文学思想的含蓄和民间文学思想的讽刺并存。主流文学思想的艺术形式强于内容,而民间文学思想的内容强于艺术形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知识的共享性大于思想的共享性,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或政治服务的。书院已是中国古代社会比较开放、自由的思想发源地了,书院促进了各种社会思想的交流。但是单纯依靠在思想领域,用一种思想去取代另一种思想也是不现实的。中国古代文人体味到思想的匮乏和生活的艰辛,实际上已经是在酝酿一场思想革命了。中国古代流传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开宗明义、以醒世人的,需哲人和先知的传播和坚守。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论战和屈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高贵气节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先导思想的话语权对古代社会发展是多么至关重要。也难怪汉高祖刘邦发出《大风歌》的内心感慨,乾隆皇帝为后人贡献了四万多首未名的诗篇,仍笔耕不辍。秦始皇想通过焚书建立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统一思想的社会。但事与愿违,儒家思想挣脱战火的洗礼,确立了在中国古代社会二千多年正统的地位。历史择人而居,择势而为,择理而行。如果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部社会思想的演化史,那么中国古典文学则是一部学术思想的演化史。中国古代文人把握着历史的脉搏,修订着社会伦理的标准。中国古代文人治学(学世、度人)和治世(经世、度世)的学术传统集聚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气节和人格是古代文人历史声誉的两个主要评判标准。在先秦的哲学思想中,儒家和道家的历史情结最重。儒家思想包容政治和文学,是大众、通俗的思想。道家思想凌驾于政治和文学之上,是小众、高深的思想。情感对等交流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人格内涵,即政治人格+艺术人格+历史人格的多重性。屈原是中国古代文人完美人格的化身,是中国文人乃至中国社会的精神象征。政治人格是对家国情怀的固化,艺术人格体现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鞭策。政治人格强调思想的过程和结果,艺术人格强调思想的重构和憧憬。统一的文化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外在保障。
汉朝社会的发展蕴藏着黄老思想、儒家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潜在交流,这实际上是先秦时期社会状态的一个反向的映照。以司马迁为代表,汉朝文人的历史人格最重。司马迁向世人展示了文人正直的人格与历史的是非曲直一样同等重要。汉朝帝王、政治家和文人均能较好地遵守历史的道义。汉朝也格外重视民间文学(如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汉朝奠定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但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形式催生出艺术创新诸多的历史语言的文学表达形式,如谢朓的“永明体”五言律诗[1]。文学艺术形式的完美和内容的颓靡预示了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完善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奠定了中国统一文明延续的社会制度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悠久、独特、辩证的历史智慧。唐朝制度的张力、思想的向心力和现实的差异性造就了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景象。唐朝文人是中国历史最乐观向上的文化艺术群体,具有较强的国家归属感。唐朝诗人的情感源泉比较多元化,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边塞、新乐府、山水田园和历史综合等各种创作题材。写诗体现了唐朝文人对现实的敬畏心理。虽然唐朝文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但是在唐朝文人的政治人格和艺术人格均得到尊重。唐朝文人的艺术人格最重,尤以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最具典型。他们的诗一方面再现了唐朝的繁荣景象和人们对美好社会制度的维护;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唐朝诗人卑微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无奈。晚唐诗人李商隐杰出艺术风格的回光返照,以及晚唐颓靡的诗风和诗人们对唐诗艺术形式的坚守,预示了唐朝社会制度进一步的传承与创新。宋朝社会平等、制度完善和理学的兴起[2]导致宋人思想的离心力较强。宋朝文人的政治人格和艺术人格是分离的。党争和人斗导致宋人的社会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较低。作词是宋朝文人对无助思想的一种安抚。后人将宋朝词人按情感归属分为婉约派(如李清照、柳永、晏殊和秦观等)和豪放派(如苏轼和辛弃疾等)。[3][4][5]婉约派和豪放派之争明显体现了宋朝文人社会情感和历史情感的冲突。婉约派和豪放派在艺术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婉约词更能反映当时的主流社会风气,而豪放词在思想境界上更胜一筹。宋朝文人的政治人格最重。宋朝文人的政治理念全面而深刻,如司马光的经世守世、王安石的经世度世和苏轼、朱熹的育人度人等政治理念。[6]宋朝文人有极高的政治人格和艺术人格,但宋朝官员遭受贬谪的现象较为普遍。受党争排挤的政党派核心官员创作时喜欢流露出自己的政治不遇感,如王安石[6]。而怀有历史主义情感的中间派官员,如苏轼和辛弃疾,则在作品中表现出豁达的人生态度和超常的艺术感染力。正如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按照这一思想标准,除苏轼和辛弃疾外,宋朝文人基于历史主义哲学的文学智慧普遍不高。岳飞屈死在风波亭也可谓是宋朝统治者对社会情感和历史情感的一个偏重取舍了。
元朝文人的政治人格和艺术人格均较低。科举制度在元朝的政治生活中处于有限参与状态。[7]元朝的汉族知识分子一般只能担任官学(包括书院)的学官这类中下等职务。[8]元朝的书院也只是儒学普及和汉族知识分子重返社会生活的象征性符号。元朝的文化系统是由多元化、自由的、形式主义的历史文化元素和低等级的官方附属机构组成的。缺乏高层次的文化体系的思想滋养,元朝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和凝聚力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元曲的流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元朝社会思想的游离情结。虽然元朝文人的政治人格、艺术人格和历史人格相对统一,但元朝文人的文学智慧对元朝的统治实际上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元朝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退步是元朝悲观历史主义情绪的集体表现。现代学者也对元朝给予诸多正面、积极的历史评价。[9][10]元朝的社会治理结构也是对中国大一统社会在历史上的独特的尝试。阶层固化有利于在军事层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但缺乏文人的聪明才智的辅佐和缓冲,导致社会治理效率低下[11],容易积累社会矛盾,这也凸显了社会软实力的重要性。明朝文人的政治人格和艺术人格相对统一。明朝文人的历史人格,即思想的适势性加强。也因此压抑了明朝文人的本位人格(政治人格和艺术人格),增加了中央决策者的政策偏差,降低了中央政权的领导力。明朝社会注重思想争鸣,具有浪漫主义艺术情怀。对社会伦理的重新梳理(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和对现实与思想本源的探索(如《西游记》)是明朝小说的社会主旨。明朝文人对社会的过度思想贡献,导致明人在艺术中对未来心存幻念,渴望浪漫主义的人性。明朝文人的整体文学智慧也处于杂序的状态。缺乏统一的社会思想,形成不了文化合力,无法衍生出更高级的文学智慧。明朝统治者的历史意愿和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也暴露了明朝上层建筑存在的问题。清朝通过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将全社会思想统一、固化。清朝统治集团从皇帝到官员开创了勤勉、务实的政治风气。清朝文人的政治人格、艺术人格和历史人格高度统一。清朝文人要在思想的禁锢下,发挥才智,务实进取。清朝的社会思想长期处于一种迷茫、静止的状态,清朝多诗,却诗无境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道出了晚清社会思想迷茫的堪忧境地。清朝小说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法是在曲折的生活苦难中窥视人的内心世界,更多表现出对现实的一种思想折射,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治国理念的差异形成明清小说不同的艺术特点。明朝小说具有“词化”现象,即追求生活中的人性。清朝小说具有“诗化”现象,即追求思想中的灵性。书院作为民间的思想的集散地在不同朝代的影响也不一样。但体现了一个共同点,即非正统的社会思想很难通过民间渠道传播开来。最早的书院,即唐朝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是官方修书、藏书、校书和皇帝讲经的场所。至唐末、五代时期,书院开始具备教学功能,如始建于五代的嵩山书院、应天府书院和龙门书院。[12]两宋时期书院除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教育功能,还承担了思想创新和交流的重任。[13]元朝继承并发展了南宋的书院格局,书院在消除南北文化差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14]明朝书院的思想自由开历朝之先河,不仅呈现心学与实学的论争,而且两者也从不同层面改良了传统程朱理学思想。[15]清朝书院既吸收了心学的一些优点,如重视道德教育,也拓展了实学的一些传统,如开辟了自然科学等诸多新的学术领域。[16]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官学化倾向使书院沦落为统治者巩固其政治思想的工具。理学似乎比心学更有利于思想的统一,书院的发展与理学的兴衰正相关。[17]历史的复杂性远超思想的复杂性。在自由的条件下,思想的统一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思想在政治的庇护下才能衍生壮大。在这一角度下儒学不利于知识在社会底层繁衍。心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文艺复兴思想的萌芽,但书院始终摆脱不了封建社会政体的桎梏。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思想只能寄寓在文人的作品中,依靠才气点拨人们的思维。文学是古代社会一个独立的社会元素。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潮的演变史。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活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起到理论奠基和哲学引领的作用。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根植于文化制度本身的文学智慧会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正反馈的影响,如汉朝、唐朝和清朝。根植于军事制度的文学智慧会对社会进步产生消极的负反馈的影响,如秦朝和元朝。根植于经济制度(如宋朝)和政治制度(如明朝)的文学智慧缺乏民族凝聚力(如宋朝)和社会凝聚力(如明朝),易受突发的军事事件(如宋朝)和政治事件(如明朝)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素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明显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的联络,作者的人格魅力在历史的评甄中被放大。基于儒家文化,符合历史规律的文学思想能够对社会起到警世的作用,从而对当时社会产生积极的正反馈或消极的负反馈的影响。尊重文人的社会地位,保持文学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统一性,对一个朝代的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申树斌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 上一篇:传统文化中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浅议范文
- 下一篇:教师线上课程著作权归属浅议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