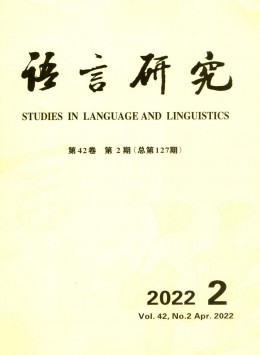语言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王夫之;语言哲学;六经;道;辞
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的王夫之,通过深入的哲学反思。将民族危亡的根源归咎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理论失误,认为是他们背经离道的学术造成了“人道不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他说:“上古以还,典礼不修而天下大乱,皆此等启之也。可无辨哉!”因此,他倡导“当以王之政典为式,诛暴禁乱。惠此小民,使之和辑。”其意在即经求治国、除暴和安民之道。以扶民族之危难。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他提出了“六经之育有大义焉”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反对理学家的“凿空立说”。正是此种切时的思想使他与同时代的顾炎武、方以智等思想家一道。确立了“即经求道”的新哲学路向。
一、六经之言有大义焉
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他在《读通鉴论》(卷六)中说:“六经之盲有大义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韫于山,珠之函于渊。不可浅而获也。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所贵乎经义者,显其所藏,达其所推,辨其所异于异端,会其所同于百王,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斯焉尚矣。”在这段对六经及其所蕴含的“大义”的总论中,王夫之明确地阐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六经之肓有大义焉”。这种“大义”就是儒家圣贤之道。道之于六经之言,如玉石之藏于山,如宝珠之蕴于深渊。不可简单获取,必须通过对语言的深度诠释才足以发掘“六经”之大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道”关系在此又以新的方式得以重现。
基于上述的思想认识,王夫之在训诂中看重的是古经文字所蕴含的“大义”,他说:“《尚书》文义多难解了。然或错综成文,而有字则必有义。”他在《春秋家说》(卷中)中说:“善治《春秋》者,先大义后徽言。求诸大义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盲:求之大义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盲,则大义蚀。而党人之邪说进。故大义已昭,信圣人焉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这即是说,研究《春秋》首先应探求其中的“大义”,然后再求之微言,如此则邪说不起:如果舍却大义而求其微盲,必致圣人之“大义”失而邪说群起。明末柬书不观、不理时政的学风导致儒术衰微而空疏之学竞起,此即明证。
第二、六经之微盲大义,“不可浅而获也”。于六经之言明圣人之道,如于山中寻玉,于渊中取珠,何其难哉!王夫之提出读经要“反复讽诵,文义固有可通者。”除了反复诵经以会通“文义”的方法之外,王夫之还要求体道者应忘掉“成见”以显六经之道,他说:“万世不易之常经。通万变而随时得中,学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习成之见,知有未至之境,则可与适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不恃个人成见。乃知有未知之道。这段文字同时也说明了有“常经”但却无“常道”的道理,六经之道“与时偕变”,不可偏执。在王夫之看来,古经所涵之道是一个向后人敞开的无限的动态过程。读者要切合现实去理解其中的“大义”,做到“随时得中”,以切实用。
王夫之从道与器的关系上提出“尽器则道在其中”的体“道”方法,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故尽器难矣,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尽器”以求“一贯”就是多识多学的归纳法,而“天下唯器”,故王夫之发出“尽器难矣”的感叹。他在评价程子读史时说:“程子自读史,一字不遗。见人读史。则斥为‘丧志’。‘丧志’者,以学识为学识,而俟一贯于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读史,则一以贯乎所学所识也。若不会向‘一以贯之’上求人处,则学识徒为。古人之学,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学识,后半截一贯,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程子之所以指责学生读史为“丧志”是因为学生读书“以学识为学识”。不求其中一贯之道。程子读史能将所学贯通起来。学识之所以能贯通,其中自有精神(道)在,识其精神即为读书之目的与效果,故日“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
第三、六经之微言大义有修德安身、经邦制远之用。于六经求“大义”目的在于致用:“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小而言之,六经之道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大而言之,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法。他说:“《易》曰:‘修辞立其诚’,立诚以修辞,修辞而后诚可立也。”王夫之将涵道之辞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联系起来。他不仅远绍《易》“修辞立其诚”之说。肯定“修辞”对人的德性的提升作用。而且进一步发展为“立诚以修辞”。“立诚以修辞”旨在强调具有“诚”的境界才可做到读经、解经不悖圣人之道、才能保证“经正”。所谓“故必约之以礼,皆以肃然之心临之,一节一目、一字一句。皆引归身心。求合于所志之大者,则博可弗,而礼元不在矣。……有志者勿惑焉,斯可与于博文之学”,说的就是“立诚以修辞”这个道理。同样,这也是他注重六经“大义”的原因,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已乱。尧舜之道,人皆可学。亦为之而已矣。”至于王者。除了个人的修德安身之外,还须治《春秋》,他说:“《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纲也。”意即《春秋》经中有经邦安国的王道在,是外王之所本。
尽管王夫之注重六经之言中蕴涵的“大义”,但并未因此而将语育简单地看作是经义的附庸。在文学理论中,他继承传统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以“文以言道”命题,将语言与形上之道连结起来。他在《读通鉴论》(卷十二)中说:“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违,下以尽己而不失,则其视文也莫有重焉。”君子之文所载即是天道。所言即是己之心志。是君子对天道的体认及其心志的统一。这里的“文”是指什么呢?他在《诗广传》(卷一)中说:“一色纯著之谓章,众色成采之谓文。章以同别,文以别同,道尽矣。”王夫之独拈一个“文”字,从其对“文”的定义可知“文”不限于六经。从他的著作来看,“文”也包括史类及前贤的涵道之作,经史并举是王夫之的一个特征。虽然王夫之称“众色成采之谓文”,但“文”决不包括佛、道之典籍。他说:“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可知王夫之所谓的“道”主要是指先儒之道统,而佛、道、法等不在其列。这一点与倡“三教合一”的方以智和偏重六经的顾炎武有很大不同。由于志趣相异。同时代的思想家所宗的典籍有所不一样。然其“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及“文以言道”之说与顾炎武“经学即经学”和方以智“文章即性道”在即经求道、反对阳明及其后学之“凿空”学风方面却不谋而合。体现了一种时代的共通性。
二、“夫道者,有事之辞”与“不凿空以立说”
王弼认为“卦辞”难以述尽“卦意”,因而提出“言不尽意”说。其旨在得“意”,但也表达了“辞”在述“道”方面的局限性。与之不同,王夫之充分地肯定了“辞”的显器呈道作用。提出“夫道者,有事之辞”的观点,明确表明了道藉辞显的语言哲学观。
1、道因言而生
“天下惟器”是王夫之最根本的世界观。“尽器则道在其中”则是他识“道”的根本方法。然而他认为要通过“述器”的语言形式才能使“器”及“器之道”体现出来,他说:“故‘作者之谓圣’。作器也;‘述者之谓明’,述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识其品式,辨其条理,善其用。定其体,则默而成之,不盲而信。皆有成器之在心而据之为德。呜呼!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辞。所以显器而鼓天下之动,使勉于治器也。”绎其文旨,大抵意谓:一、天下之器乃圣人所作,比如“弓矢”、“车马”、“牢醴”、“壁币”、“钟磐”和“管弦”等。同时也说明了王夫之所谓的“器”不但指具体的物件。而且包括六经等在内的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二、言辞的“述器”、“显器”作用。通过“述器”可以“识其品式”、“辨其条理”,从而使“器”及“器之道”“明”起来。即通过概念、判断等理性思维形式对“天下之器”进行抽象。使“道”得以呈现。这是就“辞”的“显器”功用。三、言辞的经世致用功能。人们通过言辞识器、显道达到“在心而据之为德”的道德修养目的,此乃“鼓天下之动”、成万民之德。促使人们勤于治器。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立诚以修辞”。总之,这段话表明这样的观点:圣人藉“辞”以“显器”、“明道”,藉“辞”以“鼓天下之动”、教化下民,使“道”获得普遍认可,并使“道”得以向“天下”彰明而流传不失;反过来。后人依圣贤的载道之“辞”可以指导礼乐、伦常等“器”的建构。这是王夫之借释《周易》之言通过对作器、述器、明器、成器、治器过程的描述。阐述其对“器”、“神明”、“道”、“辞”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以此来说明“辞”在“尽器则道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鉴于“辞”能够“述器”、“显器”作用,王夫之对王弼“得意而忘言”犹“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签”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并针锋相对的提出“道因言而生”的主张,肯定“言”的独立性地位,他说:“何居乎以为兔之蹄、鱼之筌也?夫蹄非兔也。筌非鱼也。鱼兔筌蹄,物异而象殊,故可执蹄签以获鱼兔,亦可舍筌蹄而别有得鱼兔之理。……故言未可忘。而奚况于象?……道抑因育而生。则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周易外传》卷六)王夫之以“鱼兔筌蹄,物异而象殊。故可执蹄筌以获鱼兔。亦可舍签蹄而别有得鱼兔之理”来反驳王弼以“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之喻“得意而忘言”具有深刻的道理。进而,他提出了“道抑因盲而生”的主张,并认为“言、象、意、道”四者之间,可以达到“固合而无畛”的相容程度,深刻地揭示了作为表意达道的“盲、象”之具本身的价值,与传统的重意以重道的本质主义语言哲学有显著的区别。王夫之在此处所说“道抑因言而生”的“生”。当然不能理解成“遭生万物”意义上的“派生”。而应当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理解成言辞能使隐藏在器中之道“彰显”出来。是从育辞的“显器”、“述器”功能而言的。如果没有言辞的“显器”作用。六经之“大义”是不会自己“明”起来的。这是就“道因育而生”的基本涵义。传统道家哲学与魏晋玄在讨论“言意之辩”的问题时。着重强调的是“意”的独立价值和“言”的工具性价值及其有限性。王夫之却突显了作为工具“盲”的自身不可或缺的价值及道对“言”的依存性。这是明末清初重器、重实的哲学思想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
2、不凿空以立说
主张“道因育而生”的王夫之自然不满佛学“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种贬低言语、文字的“凿空”作法。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言者,人之大用也,绍天有力而异乎物者也。子贡求尽人道,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竖指摇拂,目击道存者,吾不知之矣。”在这段文字中,王夫之充分肯定了“盲”在接续天道、述尽人道方面的作用及其不同于一般万物的重要性。他认为言辞可以使生生不息的天德得以彰显。子贡“求尽人道”就在于“述”孔子之言而后成;这种依言传道、借述尽道、藉文继道的方式才使得儒家道统在天下流行,所谓“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亦植立之兽”即是此理。“竖指摇拂,目击道存者”者主张以心传心、废除文字。其所谓“道”不是圣贤之道,不守教化。故被王夫之斥为“禽兽”和“异类”。针对类似的各种异端邪说。王夫之提出“斯不凿空立以说”的主张。
王夫之根据“夫道者,有事之辞”的求实精神提出“育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反对“凿空”的无实之论。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言无者激于育有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元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盲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言“无”者乃是为了破除言“有”者,把“有”说成“无”,其实天下不存在“无”。“天下惟器而已”。“盲龟无毛”,意即犬有毛,实说犬;“言兔无角”,意即麋有角。实说麇。所以王夫之说“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这个“立”就是立事、立理、立实,与“空”相对,做到“有事之辞”而不“凿空”。当然所“立”之事、理,自然不包括佛家的“佛性”和道家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先儒圣人之道统。在批评佛道的“贵无”“贵空”的思想同时。他对理学家空谈性命的饽道之论也给予了切实的贬斥,他说:“盖《易》、《诗》、《书》、《乐》、《春秋》皆著其理,而《礼》则实见于事。则《五经》者《礼》之精义,而《礼》者《五经》之法象也。故不通于《五经》之微盲。不知《礼》之所自起;而非秉《礼》以为实,则虽达于性情之旨,审于治乱之故。而高者驰于玄虚,卑者趋于功利,此过不及者之所以鲜能知味而道不行也。”《五经》微盲大义以显“理”,《礼》则纪其事以见“实”,二者相资并用而致天道于中和。而袖手高谈心性者,无实玄空;趋予功利者,又不得其中之理。欲使天道流行,必须六经兼治,不可偏废,即要有“事”。也要见“理”。不可“凿空”立说。
在哲学方面。王夫之所言的“道”、“事”主要是指先儒的王道与政事,而排除佛道的异端之道与异端之事,因此,他对前人的写景、写物而不言圣人之道、不盲立身安邦之事的诗词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文不悖道者,亦唯唐以上人尔。杜甫、韩愈。稂莠不除。且屈赢谷以为其稂莠,支离汗漫。其害道也不更甚乎?”这些言论,一方面反映了王夫之美学思想自身的局限性,但亦体现了他重视文学艺术与人类根本精神的内在联系。使文学避免沉沦于个人的情感之中而缺乏应有的人性深度。王夫之的美学思想本身非常丰富,此处仅简单地从言与道的关系角度对其作一点分析。
三、“六经责我开生面”与“推故而别致其新”
王夫之虽然坚信“六经之言有大义焉”,道行而天下无忧,但决不墨守成规、固守古人之道。他强调“诚”于古经。旨在通六经之道,以防邪说诬道。“万世不易之常经。通万变而随时得中”,他相信只有深请常经,才能通万变,以求经世致用。在“奉常以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将古人之常道与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在哲学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关于世界发展的根本看法,这一法则之于六经的诠释,便是“考古者必以其时”之说。他在对儒家经典的考辨中发现沿用下来的一些名称的意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因时为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礼记》所云‘建天官六大’之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五官’之司士。在殷则与大宰、司徒、司马、司空并列,而周则下大夫之职。殷周相踵。其异已然,况唐虞乎!”《礼记》所载官职至商而变、至周愈变,商周相沿如此,更不用说以后的各朝各代之变了。因此,王夫之要求不能固守古之礼义。他说:“天之所治,因而治之,天之所乱,因而乱之。则是无秉礼守义之经也。”所以,他反对在训诂求道时不加辨别地“以今例古”的做法,而主张在“古今语文迭变”的历史过程中。具备“考古者必以其时”的灵活性。他这种将过去与现实相结合的解释方法具有相当的自觉性。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提倡所“视域融合”的理论有可通之处。同时。“考古者必以其时”之说也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内容:圣贤们遗留下的经典文本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因之而具备了生生不息、万古长青的品质。
正是由于这种将圣贤之道与具体的历史时代结合的解释方法,使王夫之认识到“与时偕行”、“趋时应变”的重要性。但是“奉常以处变”还要做到“变不失其常”。故有“非富有不能日新”之说,他说:“盖道至其极而后可以变通,非富有不能日新。”又说:“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在王夫之的视野中只有不变的“常经”,决没有不可变通的常道“欲通圣贤之道必以。道至其极”为条件。这种对六经之道的认识达到“至其极”的状态就是“富有”。所以又说“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这种“至其极”的理想状态就是上文所说的能够通过六经之辞而体认天理流行、物我一体的“中和”境界。王夫之的“中”与“至”是有一定关系的,他说:“无方无体之中者,至足也。”“至足”或“至其极”即是“中”,达至“中”或“至其极”便可应万物、万变而不惑,辅天地育万物而“日新”,用他的道器观来说就是“治器”,用其天人关系来说就是“造天”。从文化的继承上来说就是“推故而别致其薪”。这种“日新”观体现出王夫之对人类的创造能力充满极大信心以及通经致用的时代特征。
王夫之“日新”的思想在《周易外传》中说得更具体。他说:“道因时而万殊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元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我们这里要注意:王夫之坚持“道因时而万殊也”的理论与他所反对的“凿空”立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新”是在“诚”于六经之辞与道而“至其极”的条件下,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发新的生命力。体现了六经之辞是“道”之家的语育哲学的意蕴;“凿空”立说是背离六经之辞、圣人之道而空谈性理、自立新说,是诬圣之道。不是“诚”于六经之辞求道的路向。由此可见王夫之已经具有很自觉的语言哲学思想。
第2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赵奎英明确指出: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第3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语言转向
一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存在
一般认为,哲学本体论是一种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哲学学说,关于脱离具体存在的超验存在的学说。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它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没有穷尽的指向性,其中,指向的是无限的终极关怀,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浩瀚宇宙中获得生存的归属感,古人通过存在寄希望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建立起某种终极稳定的联系,希望寻求一个超感性绝对和历史恒久的终极存在来实现生命的价值所在。“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蕴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存在论或狭义的本体论);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知识论或认识论);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价值论或意义论)。”[1]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物质,比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后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又将“火”“气”“种子”等视为当时的世界本源。由此可以得出,古代哲学家们提出的“始基”一词,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色彩,而且是感性直观的。相当一部分的思想观念或者著名学说都是属于最原始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前者属于存在论或本体论,后者属于狭义宇宙论。古代本体论思维模式关注的是对知性的追根问底和本原的探索,即是将“物理”问题转向“物理学之后”的顶端智慧的终极探索,希望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建构一个具有绝对真理价值意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这也就确立起了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探索框架和具有理性主义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这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人类的理性积累、科学知识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历史价值。古代和近代有一种本体观的形态叫“本质论”,这一理念认为本体是万事万物的内在本质和普遍的共相。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绝对观念等当作世界的本体,从中可以看出古近代对本体性的理解是本原性、本质性、基础性的,然后它符合了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理想性、现实性、有限性、指向性。人类实践的本性是建立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总是渴望着能够在最深层次的基础上认识世界、把握和解释世界,从而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哲学存在
培根和笛卡尔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开创人,在培根所有的理论哲学中,大部分的思想是他的知识方面的思想。虽然笛卡尔的所有哲学观念中,知识学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他的经典著作中大部分是属于知识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具体的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2]近代哲学能够确切的区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区分了“客观世界”和“意识内容”,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内容”上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掌握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对我们理解、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前提、基本内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认识论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而言的一个概念。认识论转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能够自觉到了“思维和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研究。也就是说,近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实现的。近代认识论思维模式把思维和存在视为探索存在问题的逻辑出发点,“思想”的主题地位得到了确立,它根本的价值就在于:以主体的人作为核心,在主客体之间探寻思想的客观性和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本依据,从而为人和世界的知识提供根本的保障。近代哲学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不管是唯理论也好,经验论也罢,最后的目的所在都是为了探索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区别就在于两者的研究方向、出发点不同而已。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开篇就明确的提出了“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3]洛克制定了经验理论体系,即主体意识原理的理论。他说道:“在我们考察那类(知识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能够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4]对洛克而言,知识的问题本质就是人的理智能力的问题。
三现代西方“语言转向”的哲学存在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把语言问题视为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来研究,是从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这时的人类也顿悟到,思想观念的经历也即是语言的经历,哲学的体验感受也即是语言的游戏,因此,语言的这种意识使得语言问题在某个世纪主体化了,并且包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等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哲学接过语言学得对象为自己的对象,但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语言学。”[5]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包括了语言论的反思方式、存在论的反思方式和文化论的反思方式。而且了解语言转向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认识研究哲学基本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脱离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进而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所要批判的。并且关于哲学家们对人类意识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把语言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现代西方哲学如此重视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即世界在人的语言之中,尽管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语言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而且是人类存在的积极世界;通过对语言的反思达到“治疗”传统哲学的效果;既从批判传统哲学和实现“哲学科学化”的角度去对待哲学语言转向,而且更加深切地从“文化批判”和“人文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哲学语言转向;语言相对于观念而言,更具有广阔的哲学反思价值尺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是哲学本身灭亡的救世主,化解了这场岌岌可危的劫难。而且这次转向有它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原因在于哲学从未消停过对存在的探索与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哲学不是对它的方向作了改变,而在于它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转变思维方式,换一种介质继续向前进。古代自然哲学为了往外寻求“始基”,而无法实现时,就转化为认识存在的精神实质。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对诸如语言的原则、性质、规范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创立一门既严格又清晰的工作语言。语言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而它的意义则是更加的难以确定,对于相同的话,相同的信号系统,不同的人对于这些持有的看法和观点是不一样的。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西方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
人是现实的存在,但是却要寻求着超验的存在,原因在于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处在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之中的。感性所把握的存在是经验的,理性所把握的存在是超验的存在。古代的本体论是人们在没有经过认识和反思的情况下而直接的追问下,所以这种幻想只能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都力图通过对求知的方法来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的研究重点在于本体论上,而不是在认识论方面,随着认识论哲学的发展,探求存在本身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模式,就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近代西方哲学对于理性和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思索,仅仅是看作能思的存在,过于局部地看重理性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能思主体的价值所在,原因也在于人类判断力、理解力的局限性、狭隘性,使得近代认识论不能走出思维主体的枷锁。在认识论哲学中,存在与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世界和主体的人相脱离,使得对哲学的追问又陷进了古代本体论那种窘境。这表明,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的缺陷就在于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历史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进而,产生了新的革命性的“语言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像传统思想家们把语言视为具有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仅仅是看作生活经验和非理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否定了逻辑在语言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如,德里达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时就把人的语言活动认为不是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认知活动,仅仅是一种非理性、非决定论的杂乱无序的活动。缺乏抽象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观,例如,胡塞尔与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性关键是以种语言交往的形式为基础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性,是一种抽象的经验和精神交往的关系。“视域融合”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文本中的作者与读者间的思想交流以及读者阅读文本的反思。所以,哲学语用学说明的语言意义不仅仅是来自于语言自身的要素以及结构框架,而且还来自于语言的使用等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第4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发展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万婕.后“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研究趋势[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第5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逻辑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 B56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07-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他的意义观在整个语言哲学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一生最主要的两本著作分别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这两本书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研究上的大转向,国内外普遍把《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作为他哲学研究的前期,主要观点是“逻辑图像论”,他的前期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发展;而把《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作为他理论研究的后期,主要思想是“语言游戏说”,他的后期思想开创了日常语言哲学的新时代。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理论:逻辑图像论
(一)逻辑图像论的基本含义
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深受弗雷格和罗素的现代数学逻辑的影响,正如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中提到:“对我思想的激励大多得之于弗雷格的伟著和我朋友罗素先生的著作”。他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学说和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的目的在于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即对这些不加以澄清就容易模糊的思想给出明确的界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立足于意义确定性的寻求,他认为人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哲学问题,是由于误解了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因此,他试图澄清语言的逻辑来指明形而上学对语言的误用。跟以往以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为目的的哲学家不同,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是消解哲学问题,这种全新的哲学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逻辑分析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用以整理语言和世界的手段,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灵魂。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集中研究了语言如何表现实在,一种科学语言的构成,以及语言和世界的“界限”等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他的“图像论”。“图像论”贯穿《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它集中代表了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基本思想。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词汇的简单叠加,命题的本质在于语词间的逻辑关联,语词通过命题建立起逻辑上的联系,语言表征意义的功能才能实现。他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在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每个命题都反映某个事实并且反应的方式类似于图像。而语言是由命题组成的,所有的命题就组成了作为整体的语言,因此语言是实在的一个图像。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时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提出图像论的灵感之源。当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时偶然在战壕里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示意图描述了一场交通事故。维特根斯坦突然想到,所有的命题也像这张示意图一样,是反映某个事实的图像。在他看来,可以将图像当作一个命题,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图像的关系,进而可以说语言与事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图像关系。
(二)逻辑图像论中语言、事实和世界的关系
关于世界的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分解成诸事实”,世界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关于人类怎样认识世界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提出了逻辑图像论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相似性,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以他的逻辑图像论勾勒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由于世界可以被看作解析成无穷数量的“事实”,这些“事实”实际成为对于严重诸词汇作为符号所要传达的现实意义的“命题”,因此语言所反映的实际是现实中的各种图像。一个“命题”反映了真实存在着的图像才有意义,语言通过完成“命题”所设定的题目、对应真实中存在的图像来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因而语言和现实具有同样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形式;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通过这种逻辑图像的建立,完成了二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所遵循的投影规则的建设。对于语言的本质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基本命题构成的。一个命题符号就是一个事实,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因此语言是实际的图像。一个命题向我们传达了事态,因此这个命题从本质上应该与该事态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逻辑,或者逻辑结构。所有的基本命题都是基本事态和基本事实的逻辑图像,命题是事态的逻辑图像。按照逻辑图像论的要求,一个图像与其所描写的事态或事实必须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反过来,一个命题只有在其是一个图像时才具有意义。
(三)逻辑图像论的实质
逻辑图像论实际上是在继承传统的符号语言学观念的基础上,以逻辑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和新的准绳,重新对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内容、联系方式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逻辑哲学论》指出“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他承认了人的主体性,没有了人的思想活动,命题、图像、语言是没有意义的,以图像形式的命题、语言是人的精神活动对事实的反应。在图像论的观点下,语言必须反映事实或与事实的逻辑相符。所以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语言的确定性,主张意义的指称论。追求语言的精确性一直是西方的传统观点,在这种影响之下,维特根斯坦和其他著名哲学家,如罗素、弗雷格一样,都追求和推崇理想的、精确的形式语言,同时认为日常语言是不精确又充满混乱的。他主张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消除由于不精确的表达而引起的哲学混乱,从而清除日常语言对哲学的消极影响。
二、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理论:语言游戏说
(一)语言游戏说的基本含义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本书时隔多年,后者可以看做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语言哲学理论的反思和深入研究。他在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的序言里写道:“当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学思考上来时,我一开始便被迫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一错误指的是他前期理论的核心――语言图像论。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几乎摒弃了图像论用“语言游戏说”取而代之。
在《哲学研究》的开篇,维特根斯坦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朴素语言,或者是原始语言。这是他前后两个阶段不同语言观的缩影,一种是奥古斯丁的图画,这是一种原始、简单的语言观,是脱离了生活的语言。另一种是建筑师和助手之间为某一目的而交流信息的对话,这是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把这两种语言都叫做语言游戏。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语言游戏做严格的定义,有时他把原始语言称作游戏,有时他又把语言和那些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成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本身具有游戏规则,即语言用法,这是一种内在构成规律,规则构成游戏本身,人们只有学会某种语言的用法才能学会某种语言。在这种语言游戏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词汇的意义是变动不定的,任何一个符号都可能代表任何一个意义,只要它在相应的环境里是这样的用法。因此,词汇含义的确在于它在一定语境里的用法,并且词语的含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字面意义来看,语言和游戏有几个特征是吻合的,首先,语言和游戏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其次,语言和游戏都趋于稳定,即在一定规则内执行;再次,语言和游戏都是被给与的,两者都要依靠公共约定进行。
(二)语言游戏说的家族相似性和日常生活性
如果说逻辑图像论所关注的重点尚局限在符号与语义之间静态的联系之中,之后以动态会话条件为研究背景的语言游戏说打破了这一局限,并通过“生活形式”为语言研究提出了更广阔的考察空间。因此 “家族相似”理论的提出则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下将各种语言游戏串联起来,对语用、语义、甚至语言的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化论述,进一步开拓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对于“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代之以一段十分形象的论述:“例如观察一下我们称之为‘游戏’的活动。我所说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竞赛游戏等。它们具备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吗?不要说它们一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否则其就不能成为“游戏”。而是要去观察,看它们是否真的有一些共同特征。因为当你仔细观察时,你虽然看不到它们全部都具备的特征,但会看到一些、且是一连串的类似和相近的地方。”“对于上述相似性,我想不到有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称呼;因为正像同一个家族中的成员间在体格、面孔、眼睛颜色、走路姿势、脾气等方面的相似那样,游戏间的相似性也重叠、交叉。我要说的是,‘游戏’本身构成一个家族。”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摒弃了图像论中那种命题图像与世界事实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而认为语言与世界事实并没有特定的一一对应,各个范围之间只有相似的某种特点,只能用“家族相似”来表达和划分世界事实。
在提出事物的“家族相似性”同时,维特根斯坦也将语言哲学的研究引入了日常生活中,他强调在研究语言时“不要去想,而要去看”,这句话并不是让人真的不要去想,而是强调不要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转而在日常生活中了解语言的用法,从实际生活中了解词语的特征与性质。
三、结语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转向,国内外学者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经过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后期并不是将前期思想全盘否定,他的前后期哲学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最为核心的转变就是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逻辑语言的确定性,追求语言的本质,后期他回归了日常语言,放弃对语言本质的追求,提出家族相似性。在分析方法上,也从早期的逻辑分析、逻辑解释澄清到后期的日常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语言描述。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维特根斯坦贯穿一生的哲学主张始终是: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任务不是提出新的命题,而是一种消解。并不管是前期的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是不变的。他始终把语言作为解决哲学问题的钥匙,哲学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语言的批判,只不过在前期和后期的批判方法和手段上有区别。
参考文献:
[1]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纪春景,谢鸿昆.试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转向[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32:11-15.
[3]林素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意义观之比较[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05.
[4]刘龙根.维特根斯坦语义理论刍议[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9).
[5]王国华.从逻辑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探讨[J].北方论丛,2008,2:57-60.
[6]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7]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第6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对于语言的意义和存在的探讨,其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最初对这个世界产生疑问的哲学家都对语言有自己的见解。西方哲学在历史上经过了不同重心的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这一转向思潮当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首先对语言与哲学的关系的历史渊源进行了简单回顾,接着分析了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理论及其所体现的哲学思路。他在语言学领域和哲学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贡献,并为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灵感与启发。
⒈ 语言与哲学
语言是一个纷繁多彩的世界,因为语言,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历史,文化和文化,甚至了解各个地域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因为语言,我们得以继承这些美好的传统和文化并继续发展我们的人类文明;因为语言,现代的我们还整日沉浸在语言带给人类的美妙当中。关于语言的奇妙,语言的起源问题,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发展或者灭亡,语言与其他学科的关联等等,除了我们的感性认识之外,一直以来都是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并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就是研究客观世界上的一切普遍规律的科学。哲学思维和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密不可分,二者的联系历史悠久,和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比,哲学思维不能脱离语言,以为思维的对象和思维的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高名凯 2010:8)。
如陈嘉映所说,人类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的好奇使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语言的研究活动,柏拉图曾评论,语言这个题目也许是所有题目中最重大的一个。他又说,“语言又与历史、艺术等不同,语言和概念的关系更为密切,乃至我们经常无法区分概念和语词,于是一切概念考察都是语词考察,语言哲学就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哲学本身了,或者说是‘第一哲学’”(陈嘉映 2003:4)。从这些分析我们得知,语言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尽管陈嘉映的论述最终回归到不宜将哲学等同于语言哲学,因为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进行观察,概括,推论,但二者目标不同,语言学家旨在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直到掌握这一机制,而哲学家是从理解语言的机制出发走向理解世界,希望有一种更深层的理解方式。
从古希腊众多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的语言思考,到中世纪热衷于宗教领域语言的探讨,集中在《圣经》的诠释,一直到近代哲学,语言学和语言思辨的发展受到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在20世纪初哲学的语言转向后,由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后,现代语言学开始形成,而对现代语言学起奠基作用的就是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
⒉ 语言学总论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索绪尔指出,
“语言学的任务是:a 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言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b 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c 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索绪尔 1983:26)。
⑴ 语言和言语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出发点。他认为,人类的言语活动是复杂的一个民族的表达能力系统,同时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领域都有联系。在言语活动中,索绪尔强调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简要说,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他潜在地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意识中。它是社会现象,也是社会的产物,不属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个别成员。言语指我们具体说的话,或者指说话者可能说出或者可能理解的全部内容。语言指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方面,言语指具体话语,是语言的具体表现(涂纪亮 1994:227)。
“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 (索绪尔1983:35)。
根据这种区分,索绪尔提出设立两门语言学,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其中,前者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后者是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的和物理的(1983:41)。虽然索绪尔强调语言和言语的这种区分,但没有将这两者完全割裂,而是也强调了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举例说明语言和言语相互依存,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如果语言离开了言语的具体表现,语言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具体存在。这种区分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有目的地展开研究,而且在互相联系的基础上能够又研究整体,这种哲学思路就是一种强调系统依赖性的相对主义,而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⑵ 能指和所指
语言单位是一种由两项要素联合构成的双重的东西。这个要素分别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符号。索绪尔提出用两个术语,分别是所指来代表概念,能指来代表音响形象。“这两个术语的好处就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983:102)。
能指和所指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的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个实体就将不存在。如果将能指和所指分开,可能会造成误解。例如,一些偏心理学的概念,“黑”、“听见”等等,就其本身而言,需要和音响形象结合起来才能有意义。但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很多现象。在他看来,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任意性的证明。
索绪尔分析道,“符号正因为是连续的,所以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1983:112)。这句话看似矛盾,但是仔细体会后就觉得不无道理。语言具有稳固的性质,始终是前一时代的遗产正是因为时间的作用,语言时时刻刻被大众使用,处于时间当中的这种连续性保证了它的不变性。符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在时间上的变化是相连的,这种变化具有必然性。因为首先,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就是说语言处于大众中,处于社会成员中,这种社会力量和集体的惰性都抑制了语言的改变,另外一方面是,语言处于时间中,因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人们可以在声音和概念之间建立任何关系,所以,符号中的两要素以不同的程度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语言在各种能够对声音或意义发生作用的力量---社会力量---的影响下也变化并发展着。这种发展是语言无法逃避的,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总能意识到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移(1983:114)。
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语言学理论,将语言看成一种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才决定价值和意义。所以这一点,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维,因为符号的概念可以延伸到各种风俗、仪式、宗教、建筑、绘画和音乐等等方面, 因此,可以说他的理论为现代符号学奠定了基础作用,并开拓了发展前景(刘艳茹 2007)。
⑶ 共时与历时语言学
从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出发,索绪尔提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既然语言符号有不变性,它就可以作为不变的固定的符号系统存在于某一时间段中,另一方面,既然它又在时间范畴内可变,就是在前后相继的时间段中不断演化。为了研究同时轴线上的语言现象和连续轴线上的语言及其变化,诞生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分别研究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
索绪尔将历时与共时研究区分开,目的就是界定语言学的内容。“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1983:143)。
这种共时性思想就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思想。语言学的研究就是符号的形式关系,因为符号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其价值完全依赖于它在符号系统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在符号系统这个结构中,价值来源于各个符号之间的关系。结构其实是一种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的成分以相互依存,相互对立或者相互矛盾的关系存在,事物的本质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正是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结构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观察事物的时候不仅是注意这一客体的存在,而是更应关注它与周围事物方方面面的关联。由此,我们才能更为全面的认识。
⒊ 结语
因为索绪尔提出的这些理论,他的语言学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心论点是: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成分完全由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界定。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此后的一些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首先是索绪尔的弟子们建立的“日内瓦语言学派”,其他主要代表还有雅各布森等积极参与的布拉格语言学派,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他们吸收了一些索绪尔的观点,并加以继承,发展或延伸,总之在各自领域都有成就都做出了贡献。
索绪尔创造了自己的语言研究模式,这为哲学研究也注入了新的动力。结构主义形式的语言学一方面强调语言返回自身,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形式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推广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批评和精神分析等各个领域中,使结构主义语言学事实上获得了一种“第一哲学”的地位。(钱伟量 2003:2)由索绪尔引发的所谓“语言学转向”,人们对语言意义和存在的问题的思索使得语言成为焦点。索绪尔的语言观不仅直接促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这些理论中体现的哲学思路,对其他人文科学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结构社会学、结构经济学和结构人类学等等用这种结构主义方式研究的领域(张一平 2006:12-17)。综上所述,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影响人文科学领域后,他的影响还会延伸到更多科学领域,为更多研究者提供灵感和启发。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
[3]刘艳茹.《索绪尔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J].外语学刊,2007(4).
[4]钱伟量.《语言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第7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着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第8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 Linguistic Prison Cell:
A Clarific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Tradition of West Philosophy
Key words: West philosophy, Beings, thoughts, language, home
Abstract: 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 philosophy could be summed up as such a standard syllogism of relation inference: because thoughts is Beings’ hom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is thoughts’ home (modern philosophy), so language is Beings’ home (the present philosophy). Now the puzzle of West philosophy is what language’s home 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9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从远古时代起,哲学问题就与语言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就成为哲学的主题。有关语言哲学的探讨,反映了哲学思想的存在须臾不能脱离语言,因为思想的对象与思想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成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1]1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2]可见,分析语言和语言现象是语言学、语言哲学的共同特点和任务,“两者不仅不相互疏离,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3]24哲学进入语言领域,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或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领域的新亮点,为语用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从共时的角度展现了语用学的跨学科性质,说明了当今的语言学研究在向其他人文学科输出思想的同时,也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本文结合顺应理论,对语言哲学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推动语用学和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4]59-61。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4]65-66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4]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5]157。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6]13。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7]577。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4]7,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8]130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8]131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4]7。“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8]132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p#分页标题#e#
1.进化认识论思想。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一书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是怎样作出贡献的?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4]55?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是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要探究语言在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必须探究语言是怎样以及为何被使用的,与人类社会和生命的进化有何相似之处。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经历自然选择和适应两个过程。选择是手段,适应是目的和结果[9]54。“顺应”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生物进化论。在生物学中,顺应指生物体调整自己以适合环境的过程,是生物体为了生存而对自然选择范式作出的反应。在进化认识论中,这种观点被扩展至人类的行为、心理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用于解释人类的学习、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增长。进化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表现为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问题求解,其目的是增长科学知识,而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文化正是这种顺应的结果之一。[8]129维索尔伦在考察语言使用中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即选择与适应的思想。认为语言使用中选择时的趋优(利)心理与自然选择的存优去劣是极其相似的。既然在语言使用中选择普遍存在,顺应也自然具有普遍性。语言顺应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
2.动态的意义观思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史上发生的“语言转向”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转到了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上。意义问题成为转向之后语言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1]38语言既是一种交际工具与符号,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特殊在者或是者。同时语言又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伴随人脑的出现而出现的。确切地说,语言,不论是作为对象工具还是在者本体,也不论其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是思维物质器官大脑的产物,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产生并决定着语言的意义。语言、思维与世界相互关联,共存于意义产生的动态演变体系之中。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和“意义用法说”,把意义归结为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6]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后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分析语言意义的基础,而且为语用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影响下,奥斯汀、塞尔等人逐步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研究意义问题,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即将语言表达视为行为方式。后来利奇[10]的礼貌原则强调从社会的角度对言语运用进行研究;而斯珀伯与威尔逊[11]提出的关联理论则强调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言语运用。这些各有侧重的研究都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言语运用的全貌。维索尔伦希望改变这种语用学研究中的传统、走出困境,因此他接受了达尔文选择与适应的进化认识论思想,从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中直接借用了“适应”观点,并对社会语言学中的言语适应理论进行借鉴和革新,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中提出了语用综观顺应论。维索尔伦的意义观从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日常语言研究中功用论的思想,用商讨性和变异性来概括语言意义的特点。同时维氏也继承了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动态地考察语言的动态功能,这与他的研究目标“语言与人类生命的其他特征的功能相关性”是一致的。[12]52-53顺应理论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顺应交际条件而对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作出恰当的选择。所以说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意义就是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通过不断选择、互动、协商、顺应而建构出来的。因此,维索尔伦的意义观关注的就是语言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这正是它与以往意义观的根本区别。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一的静止系统,而是一个与认知世界、人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的、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动态系统。意义就是在动态的选择中、在多样的语境中和交际者不同的心理认知参与构成的交互网络中生成和得到解释,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顺应和人与客观世界的顺应。维氏的顺应论完整地体现了语言即选择的观点,探求语言意义就是主动选择和社会建构的行为。
3.动态的语境观思想。任何言语交际都离不开一定的语境。交际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交际过程中,语境也随之而变。交际过程也是语境的构建过程。[13]21-22莫里斯(Morris)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使用者关系的学问。[14]52然而,纵观以往学者对语境的研究,他们都未能明确指出交际者在语言使用中的重要作用。维索尔伦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一个以交际双方为中心的语境关系顺应框架,指出语言使用者在语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交际双方作为言语交流主体平等的关系,认为语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概念[14]52;同时从顺应性的角度全面探讨了语境的本质属性:动态生成性。即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产生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由不断被激活的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相互作用而动态生成,并随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维氏指出:语言顺应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顺应既可以是语言顺应环境,也可是环境顺应语言,或者两者同时顺应,还可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15]85可见语言与语境相互顺应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所以,语言顺应的社会维度、文化维度和认知维度都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维氏把动态顺应作为其语用综观顺应论的核心。
- 上一篇:大学生考察总结范文
- 下一篇:网购消费心理学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