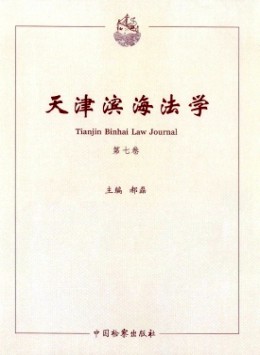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当代离婚法的改革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西方世界第一部彻底废除过错原则的离婚法案,规定夫妻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是裁判离婚的唯一理由。其后,许多西方国家的离婚立法选择不同模式的破裂离婚主义。离婚法由过错离婚主义向无过错的破裂离婚主义的迈进,超越了法系,跨越了社会制度的藩篱,成为世界性趋势。我国于1980年颁布第二部《婚姻法》时确立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裁判离婚标准,进入了实行破裂离婚主义国家的行列。
无过错离婚法的实施,也导致了一些使立法者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离婚女性的贫困化和由母亲监护的子女生存条件恶化,便是其中最具普遍性的问题。这是无过错离婚法倾向于使离婚变得更加容易,忽视了表面上是个人选择的离婚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结果。
立法上实行破裂离婚主义,只是当代离婚法改革的开端。构建将离婚的危害最小化,保障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使之不因离婚而致生活困顿的离婚衡平机制,是无过错离婚立法未来改革的目标。
二
离婚的衡平机制,以坚持无过错离婚原则为前提,在离婚的条件与程序、离婚的后果与救济等方面,突出对弱势一方当事人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特别保护。现行《婚姻法》经2001年修正后,在离婚衡平机制的完善上,取得了相当成效。它突出体现在诉讼离婚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离婚救济措施,以及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扶养和教育三方面。
我国法律在婚姻关系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上,并不追究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只看婚姻关系本身是否已经“死亡”,即“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但在离婚后果上,要对一方导致离婚的过错行为予以追究。将照顾无过错一方作为诉讼离婚财产分割的原则之一,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该项原则由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定,它与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原则一同构成在离婚财产均等分割原则之外的公平分割原则。
离婚救济,是离婚法为离婚过程中的弱势一方和因离婚而受损害一方提供救济的法律手段。我国现有离婚救济制度由经济帮助、家务劳动补偿、损害赔偿三项制度构成,其中,后两项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创设的。家务劳动补偿,主要针对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家庭事务,如扶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尽了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经济补偿(婚姻法第40条)。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夫妻一方有法律规定的过错行为,因此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要求对方赔偿自己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婚姻法第47条)。离婚经济帮助作为我国传统的离婚救济方式,不以婚姻期间一方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为条件,也不以对方有婚姻过错为必要,而以一方因为离婚导致生活困难为前提,有扶养能力的一方应从其个人财产中,对生活困难的一方给予一定的资助(婚姻法第42条)。
在离婚后子女的监护、扶养和教育的规定上,以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准则,确定了对子女的监护、扶养费给付及父母一方探望权的行使等问题。
三
“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我国离婚立法的一贯指导思想。未来民法典关于离婚制度的规定应体现这一指导思想,需在“保障离婚自由”与“反对轻率离婚”之间达成一种衡平,既要减轻婚姻失败给当事人造成的痛苦,为离婚提供体面的“丧礼”,又要考虑到离婚对家庭和子女的影响,引导当事人努力克服暂时困难,达成和解,促进婚姻的稳定。
为此,需从离婚制度的整体出发,在现有离婚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对离婚制度相关内容的完善,建立全面的离婚衡平机制。
登记离婚,是与诉讼离婚并列的法定离婚方式之一。现行离婚制度中,登记离婚的行政程序与诉讼离婚程序相比,在衡平当事人利益与保护未成年子女方面,显得较为薄弱。2003年出台的《婚姻登记条例》简化了当事人办理离婚登记的条件与审查程序。当前,离婚率的大幅攀升,登记离婚中存在的以形式上的合意损害夫妻一方和子女利益的显失公平现象说明,如果不从离婚协议的实质要件和离婚登记的审查程序两方面,对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势必造成现行两种离婚程序在体现离婚法的公平与正义方面明显失衡,致使当事人为了离婚,不得不放弃自身利益,选择较为简便但又缺乏必要限制的登记离婚程序,从而有损一方与未成年子女利益,造成轻率离婚,并最终影响人们对婚姻的认识与期待,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建议在民法典亲属编相关章节,增加规定“登记离婚的条件”,要求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必须具备双方已经就离婚后的子女扶养、财产分割、债务清偿、对生活困难方的经济帮助,以及一方家务劳动补偿等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协议内容应当有利于保护妻方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专条对“离婚登记的程序”做原则规定,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双方是否符合登记离婚条件。这对在《婚姻登记条例》中增加离婚登记的行政审查期限具有上位法的意义。
关于裁判离婚标准,现行法以破裂主义为裁判离婚的准则,同时列举若干客观外在的、证明夫妻关系确已破裂的事由的立法方式,是一种有别于彻底的破裂离婚主义立法模式的混合立法主义。民法典亲属编在破裂离婚主义原则之下,可援用现行法的立法模式,但需关注无过错离婚立法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采取相应对策,衡平离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减轻离婚对未成年子女心理的和情感的伤害,保障其日常生活和接受教育处于正常状态。
为此,在继续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前提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坚持均等分割的基本原则,同时,以照顾女方和子女监护方利益、照顾无过错方的公平原则为补充。均等分割是我国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的内在要求。否定之,则与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的基本要求矛盾,导致离婚时法律对夫妻双方财产利益保护的无序。所以,不能仅因实现公平离婚,而简单否定均等分割原则。
离婚衡平机制的强化,还有待于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民法典亲属编需针对现有各项制度的不足,作必要的增删、扩大与细化。
关于离婚时的经济帮助,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适用条件过于苛刻,受助者范围小,住房帮助的规定难以落实等问题。为此,需放宽经济帮助的条件,规定只要离婚使一方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即可要求对方给予经济帮助。法律也无须限定以提供住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为经济帮助的形式。
关于离婚时的家务劳动补偿,取消现行法上要求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限制,无论夫妻婚后实行何种财产制,只要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家庭事务,即扶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尽较多义务,离婚时都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经济补偿。
关于过错离婚损害赔偿,在我国当前建立“离婚补偿”和离婚扶养制度尚无可能的前提下,这一制度仍有存在的价值。要使之对无过错方利益损失的补救功能充分实现,需扩大其适用范围,在现有法定情形中,增加一项概括性规定“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以涵盖所有对导致离婚的,对无过错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
第2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过去这几年中发生的诸如幼师将幼儿倒置在垃圾桶、用透明胶布封嘴、提耳朵、掌掴、脚踹、用针扎、用电熨斗烫伤虐童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尽管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但是由于该规定过于笼统且缺乏相应的处罚条款,使得这些虐童案件大多不了了之。由于违法成本低廉,虐童案件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这到底是法律不完善的原因还是人为的执法不严?笔者在文中通过对刑法、侵权法以及行政法的比较分析来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现行刑法对虐童行为规范的缺失
何为虐童行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相关资料明确其定义,1975年美国制定的《预防虐待儿童及治疗受虐儿童公约》中将虐童定义为“对年龄在十八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的健康和福利监护人对其所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上的损伤、待、冷落并使其健康受到危害或威胁”[1]。其中情感虐待或冷落是指“包括不满足儿童预防、医疗、情感、教育、身体发育等方面的需要,造成儿童身心损伤,对儿童恐吓、排斥、讥讽的情感虐待与遗弃、禁闭等”[2]。定义将虐童的行为主要限定在父母这种福利监护人身上。
关于教师虐童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理论界仍存有争议。司法界则普遍认为,由于我国没有专门针对虐童行为的法律法规,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不宜处罚。即使要进行处罚,也只能从其行为的危害性出发,归入到相似的罪名中。比如在浙江温岭的虐待儿童事件中,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颜某。但是虐童行为是否真的只能通过相似罪名进行处罚,还是在现有刑法之下完全不能够进行处罚?针对此问题笔者对虐童行为可能涉及到的相关法条进行梳理。
(一)侮辱罪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侮辱罪,要求公然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众对被害人的名誉评价,不以行为人自己的感受为标准。此外,构成本罪还必须以情节严重为条件。在以上所列的几类虐童案件中,教师公然打骂学生的行为确实贬低了学生的人格名誉。在主观上,教师也存在有贬低学生人格的故意。但是笔者认为,教师在这种封闭的环境内实行虐童行为,一般情况下不会让教室以外的不特定第三人获悉其虐待行为,事实上也不希望第三人知道其有虐待行为。所以虐童行为并不能构成侮辱罪。
(二)故意伤害罪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如果追究刑事责任,必须达到轻伤以上伤害,而轻伤害的则可以由被害人进行自诉。在罗列的几类行为中,只有扎脚底和用电熨斗烫伤有可能达到轻伤以上。从教师的角度考虑,他也害怕自己的虐待行为被家长发现,因此大多数时候教师对于儿童的伤害行为是具有隐蔽性的,多数只够达到轻微伤的程度,以治安拘留来进行处罚,而现实中的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也表明了这样一种推断。
(三)虐待罪
从客观行为上看,虐待儿童的行为基本上能够被虐待罪的行为所囊括,但是虐待罪是特殊主体,即必须与被害人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共同生活的同一家庭成员。教师与学生显然没有这种特殊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虐待罪必须达到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要求虐待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因此,虐待罪不能适用教师虐童行为。
(四)寻衅滋事罪
此罪的客体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其中与虐童罪有关系的只有第一种情节。但是这种行为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抱着公然藐视社会法纪和公德,出于逞强斗狠、耍威争霸、发泄不满或开心取乐、寻求刺激等不健康动机而实施的犯罪。在温岭案件中颜某在“提儿童使其双脚离地”的这种情况下,主观上经其自己承认是一种开心取乐的态度,但是,她的行为很难定性为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影响,而且并未造成该名儿童轻伤的结果,司法机关也可能是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决定撤销案件的。
综上可知,目前我国对于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定,具有紧密关系的罪名仅有故意伤害罪和猥亵儿童罪。但是很显然,仅这两类罪名是难以概括到所有的虐童行为的。
二、国外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全方位性
关于国外的刑法规定,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德国、法国、英国的刑法。
德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虐待被保护人罪”规定在伤害罪一章下,该法条规定:
1.对下列不满18周岁之人或因残疾、疾病而无防卫能力之人实施虐待行为,或恶意地疏忽其照料义务,以致损害被害人健康的,处六个月以上十年以下自由型:(1)受其照料或保护之人(2)其家庭成员(3)受其照料之权利人(4)职务或工作关系范围内之下属。
2.犯本罪未遂的,亦应处罚。
3.行为人因其行为致被被保护人有下列危险的,处一年以上自由刑:(1)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2)身体或心理发育上的严重侵害。
4.犯第一款罪情节较轻的,处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自由刑;犯第三款之罪未遂的,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自由刑[3]。
德国刑法对于虐待行为的行为规定有三个特点:(1)把虐待行为的主体扩大至照料之人而不限于家庭。(2)处罚严重。以未遂、较轻情节为入刑点,以情节严重为较重处罚理由。(3)保护的对象范围广泛。涵盖对于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有上下属关系的成年人。
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英国刑法规定了威胁罪(assault)和殴打罪(battery)这两种罪名,适用于所有的主体。威胁罪是指故意地或者放任地引起被害人感受到立即的、非法针对其人身的暴力的行为[4]。威胁罪的要求暴力非常轻微甚至于不需要暴力,只要当事人感觉受到暴力威胁即可,甚至于带有暴力性的语言也可构成。而殴打罪,是指非法地对他人进行暴力打击的行为[5]。同样,此罪要求的暴力程度也非常的轻微。这两种犯罪的刑罚为六个月以下的监禁或者五等级以下的罚金,或者二者并处[6]。此外,这两个罪也可以通过民事侵权案件进行诉讼。
三、侵权责任法救济的限制
在虐童案件中,虐童 行为都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这种健康权的内涵应当包括心理和身体健康,但是各有侧重,一类行为是仅仅侵犯心理健康的,比如将未成年人倒置在垃圾桶内;另一类行为是既侵犯心理健康又侵犯身体健康的,比如扇70个耳光、扎脚底板。但是无论何种虐待行为均同时侵犯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权,这项权利属于一般人格权。
虐待儿童根据特征不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侵犯到完整意义的健康权和人格尊严权;第二类是侵犯到健康权中的心理健康以及人格尊严权。
(一)对于侵犯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的法条分析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侵权的主要方式包括八种,适用于虐童案件的只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这三类。其中最富有争议也是最有实际救济意义的是赔偿损失,损失可以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物质损失包括赔偿医疗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在电熨斗烫人、扎脚底这几类行为中都可以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要求赔偿物质的损失。但是这类物质损失的赔偿额非常小,因为从先前的分析可以看出,很多虐童行为造成的都是轻微伤,而轻微伤甚至不需要治疗就可痊愈。除了物质损害外,还有精神损害赔偿,但是《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规定“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虽然这一条款不可以直接解释为“如果当事人没有其他诉讼请求,仅有精神损害诉讼请求,那么法院将不予受理。”但是在实务操作中法院往往采用这种做法,这使得不存在明显身体伤害的受害儿童的损失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二)对于侵害心理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的法条分析
被虐儿童的人格尊严权毫无疑问的是受到了侵犯,并且法律也规定了当人格尊严受到侵犯时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但是问题是精神损害赔偿不能单独提起,必须以其他的请求权为基础。如停止侵害请求权、赔偿物质损失请求权等。问题在于侵害人格尊严权以及心理健康权的这类的行为中,儿童并没有遭受到物质上的损失,教师的侵害行为也没有持续性,那么就不需要请求停止侵害,只要依靠学校内部管理就可以要求停止侵害,无需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又不会予以受理。这便导致此类侵权行为不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进行司法救济,更不能提起损害赔偿的请求。因此,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制度,对于未成年人受到虐待这种情况,并不能很好的提供保护。
(三)未成年人的发展权的保护
虐待行为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都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成长,这也就衍生出了未成年人发展权的概念。《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其中的发展权,本来是一个人权上的含义,但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表述,已经对原先的概念进行了突破。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应该具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基本维度,是指在成长过程当中身体心理的健康发展,或者当出现不健康发展倾向时,有机构进行适当的干预;第二个维度是在第一个维度的基础上,未成年人应充分享有的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的条件,这种能力的发展需要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联合的形式进行。
四、国外侵权法救济
国外对于侵权法的规定,笔者选取了两个法系的代表国家,即英国侵权法和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之所以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比,笔者认为,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同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比较相似,通过德国与英国的对比,侧面上也能考察出我国制度所需增补之处。
1.主观方面。英国与德国都认为一切主体都可以成为侵权的主体,这是毫无争议的。关于主观因素,英国侵权法认为这种侵犯人身的行为必须是一种故意的行为,是指对行为有明知或者故意,而对于“故意非直接暴力未作规定”即过失行为,但是通过判例认为这种类似的过失行为也是具有赔偿性质的[7]。而德国民法典则概括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
2.客体。虐童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人身权。在这一点上两国法律也均无分歧,但是在对于具体人身权的解释上,各国不同。英国侵权法将人身作为概括的规定,这也与其侵权行为的任意性有关。而德国民法典则是规定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以及其他权利[8]。
3.行为。英国侵权法侵权行为规定的非常的宽泛,只要具有直接暴力(direct force),包括任何直接触及他人的身体都可能被认为是暴力。但是英国侵权法也认为合理的社会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对于家长的“管制权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英国法律在1987年的时候禁止所有的公立学校进行体罚,之后再1988年又禁止所有的学校进行体罚[9]。但是法律赋予家长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管教孩子。而德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必须具备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要求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质。
4.救济。英国侵权法对于侵权行为的救济规定的较为详细。分为民事救济及非民事救济。民事救济包括禁止令和损害赔偿。对于赔偿根据目的可以分为五种:补偿性赔偿、名义性赔偿、蔑视性赔偿、加重性赔偿、惩罚性赔偿[10]。其中第一种补偿性赔偿最常见,而名义性赔偿适用于未造成损害结果的侵权,通常仅处以很小的带有名义性质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则具有较高的数额,适用于指对人身尊严侵犯的行为,而且通常这种赔偿数额远远大于物质性赔偿,这也是一种非金钱的损害赔偿。
德国民法同样规定非物质性的损害可以要求赔偿。“因损害健身体、健康、自由和性的自主权而应当进行损害赔偿的,也可以因财产损害以为的损害而要求公平的金钱赔偿”[11]。主要问题仍然是精神损害赔偿,英美法以精神痛苦本身作为原告可以请求赔偿的理由,便不需要求具体的权利受到侵犯,只要具有行为即可,而大陆法系以特定权利(人格或特定之精神利益)之受害为请求依据。我国目前采取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这种做法。
5.程序。英国的非民事补偿或赔偿包括两种。一 是由国家专门基金进行管控的犯罪损害补偿机制,二是由刑事法庭发出的赔偿令,这种赔偿令只针对轻微的犯罪,并且在刑事判决之后不可再提起民事诉讼,这种赔偿令一般所获得的赔偿金额很少。
五、行政法受益对象的迁移
行政处罚是在虐童事件中运用的最多的处罚方式,其中罚款、拘留则运用最普遍。在虐童案件中,大多是由于尚不构成犯罪而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但是行政处罚的力度不够,难以对当事人的虐待行为起到相应制裁,并且对于真正的受害人没有任何弥补的措施。行政机关也不能要求当事人作出赔偿、赔礼道歉等。而国外的行政法则规定可以通过政府发出的赔偿令的形式,要求侵害人向被害人赔偿一定数额的损失。
六、总结与建议
以上对于虐童行为分别从刑法、侵权法、行政法进行比较研究,目前从我国司法现状看对于幼师虐童行为难以得到司法上的救济,要么是在部门法中缺乏相应的规定,要么是在部门法中缺乏“罪责刑”相适应的惩罚手段,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立法以及社会政府的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措施。笔者从以下三个角度提出建议。
(一)关于立法方面,目前西方国家是三做法
一是制定特别法,二是在刑法维度进行规范,三是通过侵权责任法进行概括的保护。对于制定特别法,前提是需要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鉴于我国目前社会自治组织发展水平较低,并不建议采取这种做法。第二是在刑法维度,关于何为虐童行为学界并没有公认的一个定义,那么进行惩罚的话势必会导致惩罚的范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围过宽或者过窄,其次,根据我国的传统及现状,还存在着学校以体罚的方式进行教育,且这种体罚的方式有一定的效果,而家长体罚更是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合理的,那么仍然存在处罚对象的问题。因此,通过在侵权法的角度进行规范是目前最为合理的法律选择,具体的思路为:首先将发展权作为一种受到保护的权利,列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并将发展权列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发展权受到的侵害,可以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也要参考英国刑法的家长管制权概念,进而允许教师行使这种管制权,但这种管制权的特征必须是禁止带有侮辱性的行为。
(二)以机构为对象的立法
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据笔者与幼师从业人员的交流发现,目前上海地区公办幼儿园的幼师招录要求必须幼教专业毕业,同时要求取得教师资格证,而幼师在进入幼儿园后可以通过考试的形式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编制,享受事业单位的待遇。此外,受访者认为,在公立机构中,很少出现幼师虐童的行为。在现实的案件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找到支持受访者的事实根据,虐童行为基本出现在私立幼儿园。这也在侧面反映我国目前学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特点,私立、民办幼儿园应是立法以及各种政策的重点对象。
现实行的《幼儿园管理条例》于1989年制定,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并且许多规范都没有细化,很多规范均是指导性意见,缺乏强制力和执行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也缺乏针对性,笼统的规定所有的民办教育机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专门性的以幼儿园整体为规范对象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2〕周达生,戴梅竞.现代社会病[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316.
〔3〕徐久生,庄敬华.德国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66-169.
〔4〕〔5〕赵秉志.英美刑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301,303.
第3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一、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的表现
区际继承是指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三个要素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涉及到不同法域。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定继承方面的法律冲突
我国各法域的立法中,法定继承都是主要的继承方式。不同法域的立法对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继承份额等存在不同的规定。
1、对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不同。大陆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香港在上述人员中除外祖父母外,其余均为法定继承人,同时还增加了伯、叔、姑、舅、姨、甥、侄,其法定继承人范围远宽于内地的规定;澳门地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更广,除大陆的法定继承人外,还包括兄弟姐妹的卑亲属,旁系至第四等血亲;台湾地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大陆基本一致,区别主要在于台湾民法典不承认继子女、继父母、继兄弟姐妹有继承权,不论其是否形成抚养、扶养关系。8除上述区别外,大陆继承法规定了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为法定继承人,这是大陆继承法的一个特别规定,香港、澳门、台湾均没有将其列为法定继承人。
2、对继承顺序的规定不同。大陆继承法将法定继承分为两个顺序,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同时还规定,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为第一顺序继承人。香港法律没有规定继承顺序,而是依继承人与无遗嘱死亡人之间的婚姻、血亲的远近,经济和生活上的依附程度,来确定继承遗产的顺序。澳门《澳门民法典》将法定继承分为五个顺序。第一顺序为配偶及直系血亲卑亲属;第二顺序为配偶及直系血亲尊亲属,即在被继承人没有卑亲属时,由配偶和尊亲属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第三顺序为与死者有事实婚姻关系之人;第四顺序为兄弟姐妹及直系血亲卑亲属;第五顺序为四亲等内之其他旁系血亲。台湾地区继承法的继承顺序分为血亲继承和配偶继承两种情况。血亲划分为四个继承顺序,第一顺序为直系血亲卑亲属;第二顺序为父母;第三顺序为兄弟姐妹;第四顺序为祖父母。配偶可以与血亲的任何一个继承顺序的继承人共同继承遗产,在没有血亲继承人时则单独继承全部遗产。
3、对继承份额的规定不同。我国大陆对于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没有规定具体界限和比例,而是按权利义务相一致、男女平等、赡老扶幼、和睦团结的原则,确定同一顺序继承人之间的遗产分配。香港对法定继承人应得的份额规定非常具体。当无遗嘱者死亡时,若只遗下配偶而无其他亲属,其遗产全部由配偶继承;若只遗下配偶和子女,则应先从遗产中拨出5万元,并连同自死亡之日起到遗产分割时止,按5%计算的年息归在世配偶,余下的遗产,配偶享有1/2,其余1/2由子女摊分;若无遗嘱死亡者去世时没遗下子女,而有在世的父母亲或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的子女时,则应先从无遗嘱死亡者的财产中拨出20万,连同自逝世之日起至分遗产时按5%计算的利息,一并归在世配偶;余下的遗产在世配偶可继承1/2,其余1/2由在世的父母双方平均分享;若父母亲均死亡,该一半财产可由无遗嘱死亡者的兄弟姐妹或侄甥等继承;没有配偶的,由子女、父母等继承人按血亲远近,经济和生活依赖程度确定顺序继承,在同一顺序中按均等原则分配。澳门地区的《澳门民法典》也对法定继承人应得的遗产份额作了明确规定,若被继承人仅遗有配偶,没有其它血亲,其遗产由配偶全额继承;若被继承人遗有配偶和卑亲属时,由配偶和卑亲属按人数划分等份遗产继承,但配偶的遗产不得少于遗产总额的1/4;若被继承人没有卑亲属,可由其配偶和尊亲属继承遗产,其中配偶应占遗产总额的2/3;没有配偶的,由其他继承人按继承顺序平分。台湾地区的继承法对法定继承人的继承份额也作具体规定。配偶与被继承人直系血亲卑亲属同为继承时,其应继承的份额与其他继承人平均;配偶与被继承人父母或与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同为继承时,其应继份额为遗产的1/2;配偶与被继承人之祖父母同为继承时,其应继份额为遗产的2/3;若没有其他继承人时,其应继份额为遗产的全部。
(二)遗嘱继承方面的法律冲突
我国各法域对遗嘱继承存在不同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立遗嘱能力的规定不同。立遗嘱能力是指依法能够订立有效遗嘱的能力。我国大陆《继承法》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结合其它法律规定,可认定我国大陆有立遗嘱能力人是指智力发育正常、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十八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而香港地区《遗嘱条例》规定,立遗嘱人必须已成年(军人、海员、航空人员除外),即年满21周岁,同时立遗嘱人必须头脑健全,清楚自己的财产及负担,记忆力无重大缺陷,理解力也无重大缺憾。《澳门民法典》规定,所有未被法律规定为无能力立遗嘱之人,均可订立遗嘱。并规定,亲权未解除之未成年人及因精神失常而导致禁治产之人无立遗嘱之能力。结合《澳门民法典》关于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其他规定,可认定立遗嘱能力人为精神正常的、十八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或已婚的未成年人。台湾民法典规定,无行为能力人不能为遗嘱;未满16岁者不能为遗嘱;而限制行为能力人无须法定人的允许得为遗嘱。
2、对遗嘱方式的规定不同。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我国各法域对订立遗嘱的方式均有明文规定,但规定各不相同。我国大陆《继承法》规定了五种遗嘱方式,即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以及在危急情况下的口头遗嘱,并对五种遗嘱的效力作了相应规定。香港《遗嘱条例》规定遗嘱必须以书面方式为主,主要形式为自书遗嘱,并对遗嘱书写、署名、见证等做了具体规定。原则上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在香港不具有法律效力。台湾民法典规定,遗嘱方式包括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遗嘱、口授遗嘱。并规定,各种遗嘱方式均须有遗嘱人的签名、立遗嘱的日期和二人以上的见证人。
3、对遗嘱解释的规定不同。由于订立遗嘱人多数不十分了解法律,以及由于文化水平和文字习惯等因素,遗嘱常出现难懂及易生歧义等情况,所以遗嘱解释就成为遗嘱继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大陆《继承法》对遗嘱解释未作任何规定。香港则根据英国法院解释遗嘱的有关原则规定了如何对遗嘱进行具体解释。澳门及台湾对遗嘱解释也分别作了不同规定。
二、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
(一)对各种解决方案的评析。
综观世界上各多法域国家的立法与实践,结合学者主张,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存在三种途径,即统一实体法途径、订立冲突法途径和类推适用国际私法途径。
统一实体法的途径是消除区际法律冲突的根本方法,不仅彻底消除各法域实体法之间的冲突,也使冲突法之冲突这种第二层次的法律冲突无由产生。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经济的趋同化推动法律的趋同化,各国在修改、完善本国法律时进行大量法律移植,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而我国各法域间的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也成为统一实体法制订的一个内在要求。但通过制定统一实体法途径来解决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实现中国法制的统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实现。除了台湾尚未与祖国统一外,还涉及到;一国两制“方针、两个基本法不相符的问题。故该途径在目前尚不存在实现的现实条件。
在冲突法途径方面,学者提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一种提出分别制定各法域的区际冲突法,一种提出制定统一的中国区际冲突法。关于分别制定各法域的区际冲突法,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持这样的观点。台湾在1989年颁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和1997年颁布的《台湾地区与港澳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有一些区际冲突法的内容,旨在调整其与大陆和港澳的法律冲突,但大陆及港澳均未有制定区际法律冲突法规范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问题。由于各自制定冲突规范,其规定当然各不相同,从而造成各法域之间冲突规范的冲突,使法律适用变得更为复杂,故笔者认为不宜适用。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能使各法域的法院对同一案件的审理得出相同结果;挑选法院“现象,而且可以避免区际冲突法本身的冲突和反致问题的出现,也使识别简化,同时还可为各法域实体法的统一奠定基础。且其制订不涉及各法域间存在根本分歧的实体法,较实体法的统一更易取得成功,是解决我国如此复杂的区际冲突的理想途径。但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实现也存在诸多困难。一方面,仍未解决,统一区际冲突法必须考虑到四法域的统一;另一方面,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相类似,统一后,各法域仍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除属自己管辖的事项外,无权制定直接适用于港澳台地区的法律,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只能在四地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产生,而目前难以实现这种协商。但应当看到,随着各法域的民事交往增多,在协商基础上制订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目前对于统一的区际冲突法进行前瞻性研究,仍具有相当的价值。
关于类推适用国际私法方式。纵观国外关于区际继承的法律适用,许多国家把国际私法与区际私法等同或是基本等同起来,在解决区际继承的问题上,基本上沿用国际私法中涉外继承的一般方法与原则。由于区际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性质不同,类推适用国际私法处理区际继承,本身不甚恰当,且在适用上也存在诸多困难。但在我国目前无法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的情况下,采用类推适用国际私法成为唯一的选择。
(二)当前类推适用国际私法处理区际继承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1、我国区际继承法律适用的原则
区际继承的法律适用,应依据基本原则进行。依据我国区际继承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区际继承法律适用应遵循下列原则:
(1)“一国两制”原则。“一国两制”是我国处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关系方面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是一种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中央与地方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处理冲突问题上,应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既要积极谋求区际冲突法的协调,又要保持各法域独立的法律体系。
(2)法域平等互利原则。在解决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中,平等互利原则主要表现在:首先,要求我国各法域的继承法地位平等,互相承认对方继承法在本法域的域外效力。其次,对继承人而言,平等互利意味着不同法域的继承人可以通过继承,平等取得跨法域的被继承人的遗产。
(3)保障和促进区际民事交往的原则。我国区际继承的遗产范围不但有历史遗留的财产,更有改革开放以来各法域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财产,各法域人员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财产,往往位于其所在的法域,若继承人未能取得遗产,会认为凡不在继承人所在法域内的财产,一旦成为遗产将无法继承。这种心态会导致各法域人员的交往十分谨慎,当事人将不轻易把财产带入其它法域,这不仅影响区际民事交往,也不利各法域间的相互投资与经贸发展。因此,在解决区际继承时,要坚持保障和促进区际民事交往的原则,解除各法域人员在民事交往中的心理负担。
(4)保护继承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有的法域过份限制继承人的范围,剥夺部分继承人的继承权,甚至限制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如台湾地区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66条规定,大陆地区人民为继承台湾地区人民之遗产,应于继承开始起2年内以书面向被继承人住所地区之法院为继承之表示;逾期视为抛弃继承权。第67条规定,大陆地区人民依法继承在台湾的遗产,每人不得逾新台币200万元,超过部分,归属台湾地区同为继承之人。这是台湾当局对大陆及大陆人民所持的敌对态度的反映。类似规定严重损害了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法治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不利于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故各法域均应当消除歧视性不平等的限制条款,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2、区际继承准据法的确定问题。
由于各法域在国际私法方面对涉外继承的准据法确定存在不同规定,所以在类推适用国际私法处理区际继承时,也应依据各自的规定处理。
(1)法定继承准据法的确定。在解决涉外法定继承准据法的确定上,国际上主要存在区别制和同一制两种制度。区别制也称为分割制,是指在涉外继承中,将被继承人的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动产继承依被继承人属人法,不动产继承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同一制又称单一制,是指把遗产看做一个整体,不分动产和不动产,均依被继承人的属人法。我国各法域对涉外法定继承准据法的确定采取不同制度。我国大陆采用区别制,《继承法》规定,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香港也是采用区别制,其国际私法规定,死者遗产的继承,在没有立下遗嘱的情况下,他的动产按永久居留地的法律分配,而不动产则按物业所在地的法律继承。该规定与大陆的规定一致。澳门法定继承采用同一制,《澳门民法典》规定,继承受被继承人死亡时之属人法所规范。而台湾在涉外法定继承中兼采两种制度。立法总体上倾向同一制,但在调整与大陆间继承关系时另有规定。台湾地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规定,继承依被继承人死亡时之本国法。但依台湾有关规定台湾当事人应为继承人者,得就其在台湾之遗产继承之。根据台湾《港澳关系条例》的规定,前法只适用于调整台港澳之间的区际继承关系。台湾地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又规定,被继承人为大陆地区人民者,关于继承依该地区之规定,但在台湾地区之遗产,适用台湾地区的规定。
(2)遗嘱继承准据法的确定。遗嘱继承以遗嘱内容为依据,不象法定继承因涉及多个法律导致法律冲突而需要选择准据法,遗嘱继承本身不存在法律选择问题。但遗嘱继承的实现是以有效遗嘱为前提,而法律从立遗嘱人的立遗嘱能力、遗嘱方式和遗嘱的内容三个方面确定遗嘱是否有效,故各法域间的遗嘱继承在这三个方面存在准据法确定问题,即冲突法所要确定的实际上是遗嘱效力准据法。遗嘱继承的准据法确定应从立遗嘱能力、遗嘱方式、遗嘱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准据法的确定上,各法域在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方面总体上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不同点。在立遗嘱能力方面。我国大陆对于立遗嘱能力的准据法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采用区别制,即动产遗嘱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不动产遗嘱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香港采用区别制,其渊源来自英国法,“遗嘱人住所地决定其是否有个人能力对动产订立遗嘱。”“一般认为原则上应适用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对不动产立遗嘱的能力依什么法,英国尚无权威依据,或许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澳门采用同一制,《澳门民法典》规定,作出变更或废止死因处分之能力,以及因处分人年龄而在处分上所要求之特别形式,受处分人作出意思表示时之属人法规范。台湾采用同一制,但在涉及大陆时作了特别规定。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规定,人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大陆地区人民之行为能力,依该地区之规定。但未成年人已结婚者,就其在台湾地区之法律行为,视为有行为能力。在遗嘱方式方面。我国大陆采用区别制,区分动产遗嘱与不动产遗嘱而选择准据法,香港也是采用区别制,而澳门与台湾采用同一制,统一适用立遗嘱人属人法或立遗嘱行为地法的。在遗嘱内容方面。其最主要的问题是遗嘱的解释问题,我国各法域的继承法对涉外遗嘱之解释问题没有直接规定,只对遗嘱实质要件准据法作了规定,台湾和澳门采用立遗嘱时的属人法,大陆与香港采用区别制。
3、有所限制适用反致制度。
反致是国际私法的术语,是指某种涉外民事案件,依内国冲突规范之规定,应适用某外国的法律,而依该国冲突规范之规定,又应适用内国法或他国法时,则以内国法或者他国法为本案之准据法。广义上的反致包括直接反致、转致、间接反致和双重反致。虽然在区际冲突领域探讨反致问题如同在国际冲突法领域探讨反致一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但由于我国各法域间没有统一的区际私法,各法域用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具体规定存在不同,故反致制度有其存在的基础。至于是否采用,则要依据各自的法律规定。大陆现有法律对反致没有作出规定。香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遵循英国冲突法中关于“单一反致”和“二重反致”的判例。澳门民法对反致和转致作了明确规定。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规定,依本法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时,如依其本国法就该法律关系须其他法律而定者,应适用该其他法律,依该其他法律更适用其他法律者亦同,但依该其他法律应适用台湾地区法律者,适用台湾地区法律。明确接受反致、转致及间接反致。各法域在采用反致制度时,应受到维护当事人正当利益这一原则的限制,否则,法官会因为狭义反致和间接反致最后援引其所熟悉的法院地法而滥用之,使反致制度丧失其原有意义,损害当事人利益,以致成为区际冲突调整中的障碍。
4、谨慎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公共秩序保留是国际私法中排除适用外国法的一项制度。是指如认为法院依内国冲突规范援引指定的外国法的内容有碍内国公共利益、道德准则与法律秩序时,便可拒绝适用所指定的外国法。我国各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法律冲突,特别在继承这个涉及到人身关系、物权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的领域上,冲突更为突出。故在解决区际继承的法律冲突方面,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运用可能更为重要,其频率也会更高。我国大陆《继承法》虽没有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但在《民法通则》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利益。香港、澳门对公共保留制度也有相应规定。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依本条例规定应适用大陆地区之规定时,如规定有背于台湾地区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但区际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毕竟不同,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在实际中不能滥用,否则,不仅会危害各法域的真诚合作,也不利于各法域之间的民事交往,导致危?;一国两制“的实现,所以法院在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时应从严掌握,谨慎适用。
5、积极参加有关国际公约和条约。
国际公约和条约是用于解决国际间法律冲突的重要规范性文件,“条约必须信守”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其内容对缔约各方均有约束力。通过参加有关条约,也有利于调整我国各法域之间的区际冲突。目前有关继承问题的国际公约主要有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先后制定的《关于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公约》(1961年)和《关于死者遗产继承的准据法公约》(1988年)。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已通过各种渠道加入了上述两公约,我国虽已成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成员国,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和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有关立法活动,但我国尚未加入上述两个公约。建议我国尽快申请加入该两个公约,以便于依公约的内容来调整区际继承的法律冲突。
(三)对区际继承统一冲突法的设想。
随着各法域交流的增加,区际继承越来越多,各法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制订区际继承的统一冲突法或法律协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会越来越大,这也是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最为可取的方式。
在法定继承中,采取区别制与同一制各有利弊。同一制强调继承的身份法性质,其优点是简单、方便,依同一制,被继承人在各法域的动产和不动产可合并清算,被继承人的所有债务可合并抵偿,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生前已取得的财产也可从中扣减,比较容易计算出可继承的财产和各继承人的应继份。其缺点是在实践中承认与执行可能出现困难,而且适用与遗产所在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来确定遗产的归属,不尽合理,甚至有悖遗产所在地的利益。区别制强调继承的财产法性质,采取区别制可避免同一制中所存在的执行困难的缺点,而且因不动产遗产与所在地的关系最为密切,区别制有利于维护遗产所在地的公共利益。但区别制也有缺陷,如果遗产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域,遗产继承就要受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域的法律支配,使继承关系复杂化,在法律适用上会碰到诸多困难。综合我国四法域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将来我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中,法定继承以采取区别制为宜。理由是:1、四法域中有两个采取了区别制,台湾兼采取两种制度,只有澳门采取同一制,故采取区别制,较易于统一和协调。2、各法域的属人法并不都是以住所地法为标准,故在采取同一制时,实际上难以确定属人法。3、尽管同一制与区别制各有利弊,但总体而言,区别制的优点更为重要。不动产的价值大,与所在地利益密切相关,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更符合该地的公共利益。而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有利于判决的执行。
在遗嘱继承中,应从立遗嘱能力、遗嘱方式、遗嘱内容三个方面分析。1、立遗嘱能力。立遗嘱能力属人的行为能力问题,根据国际私法一般理论,人的能力依其属人法。故笔者认为,将来的统一区际冲突法中,对于立遗嘱能力的准据法确定上,应统一采用同一制。对于属人法有的国家规定为本国法,有的国家规定为住所地法。我国各法域的本国法相同,所以在解决区际继承的立遗嘱能力方面,应以住所地法为准。但由于住所容易变更,有时还会出现住所冲突的现象,并且经常遇到根据其住所地法无遗嘱能力,而根据立遗嘱地法有遗嘱能力,此时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故应采取如下方式:一是若立遗嘱地法认为有能力,?;场所支配“行为的一般原则,认定其有遗嘱能力。二是对住所变更的情形,可借鉴英国法对连结点改变后立遗嘱人属人法的适用原则,如立遗嘱人的住所地法认为有遗嘱能力,而后来的住所地法认为无能力,应适用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如立遗嘱人的住所地法认为无能力,而最后住所地法认为有能力,应适用最后住所地法;如果根据原住所地法其有能力但未立遗嘱,后来的住所地法认为其无立遗嘱能力,则其在先取得的此种立遗嘱能力不能保留。2、遗嘱方式。主张适用立遗嘱行为地的,认为”场所支配行为“原则属于强行法范畴,自应遵循。而持适用立遗嘱人属人法主张的,则认为遗嘱制度本身要求遗产处分应充分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而且遗嘱还具有身份性,故应适用属人法。对于主张区分动产遗嘱和不动产遗嘱而分别选择准据法的,一般认为,不动产遗嘱方式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动产遗嘱方式则可在立遗嘱人属人法和立遗嘱地法之间选择适用。以上做法各有利弊。我国区际继承统一冲突法对于遗嘱方式准据法的选择,不应拘泥于一种或两种方式,不宜因遗嘱的形式要件而影响遗嘱的成立,如我国大陆继承法对于动产只规定一个连结点,造成遗嘱因其方式问题而导致无效的可能性极大。对此,可以借鉴1961年海牙《关于遗嘱方式法律冲突公约》之规定,遗嘱方式符合下列法律规定的都认为有效:遗嘱人立遗嘱地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本国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住所地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惯常居所地法;不动产遗嘱方式依财产所在地法。并且公约不妨碍缔约国现在或将来的法律所规定的遗嘱。公约采取区别制,规定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连结因素,反映了遗嘱方式准据法的扩大趋势,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3、遗嘱内容。根据我国各法域的具体情况,在区际继承遗嘱解释的准据法问题上,应采用如下原则:确定动产遗嘱解释的准据法依遗嘱人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因为对一般人而言,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是其立遗嘱时最熟悉的法律,应当是其意欲适用的法律。对不动产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其理由与区际法定继承采用区别制的理由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黄进:《区际冲突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杨大文:《婚姻家庭法领域的区际法律冲突和司法协助》,《法学家》1995年第4期。
3沈涓:《中国国际冲突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第4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民法典的内生性优势,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容易为普通人所知晓、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灵活性,这三个因素被某些大陆法学者称为“民法法系的新格言”。
(一)法律容易为人所知晓
拥有众多的成文法典是大陆法系的重要特征。法典化,就是根据某些标准对于某一部门的法律规范进行理性化、有序化和等级化的整合,使之能为所有普通人所知晓。比较法学家指出,法典本身就是作为对抗法律产生的任意性、神秘性和秘密特征[4]。曾热烈主张在普通法系统中引入法典化立法技术的英国法学家边沁指出了正义和法律为所有人知晓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必须条件之一;而为了使得法律为所有人所知晓,采纳法典化手段就是绝对必需的[5]。
法律易于为人所知晓,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典本身内在的体系性。这种体系性也影响到普通法。英国比较法委员会主席、肯特大学教授GeoffreySamuel指出:英国学者关于合同法的著作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习惯于以一般性命题的方式去阐述合同法原理。但是,这是19世纪自大陆法系“进口”的产物[6]。
法典化的重要功效之一,就在于改善主体对于法律的认知。以拥有两百多年生命力的法国民法典为例,法国国民议会法律委员会副主席XavierdeROUX曾这样指出:“民法典首先带来了法律安全,它懂得适应社会的变迁。它易于读懂,论述清晰,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民主的。它所使用的方法不仅显示出了它自身的杰出,对于立法者而言它也应该是一个典范。此外,民法典的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本在网上也可以读到。对于法学家们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是被优先考虑的首要法律工具。”[7]
法典集中了某一部门的所有法律规范,具有体系性和完备性,从而容易为人所知晓其全部内容。这也解释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初期,在法律战略上选择了法典化的道路(有意思的是,这些法典化的举措还得到了部分英美法学家们的协助)。比较法学家们对此的解释是,法典化更容易实现法律的变革和对传统的“断裂”;而在普通法系中,遵循先例原则、尊重司法经验在长时期内的积累等传统,使得法律变革通常要难得多。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其他国家在法律变革中采取法典化战略的原因:譬如作为海洋岛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进行大规模法律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借鉴同样是岛国的英国(当时是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帝国)的法律体系[8]。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易于为民众所知晓,这在大陆法系成为一项与政治民主相关的原则:法律是否是“民主”的?法律民主不仅是指法律制定和通过的程序必须是民主的(根据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代议机构,基于民主原则对法案进行辩论,最后经由民主程序进行表决通过);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求所通过的法律本身必须能为民众所知晓和被读懂。大陆法系对于后一点的重视,在部分比较法学者看来具有历史原因:在各自成形和传播的过程中,大陆法系———尤其是法国法处于共和体制,因此对于后一种意义上的“法律民主”尤为看重;而普通法系的成形和传播处于王权时代,因此对于此点并不甚在意[9]。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于法律的知晓的权利,在某些国家如法国,被上升到宪法原则的层面。法国宪法委员会1999年12月16日的一项判决指出,“法律易于为公众所知晓和读懂”这是一项具有“宪法价值的目标”,主要理由有:“如果公民对于适用于他们的法律缺乏充分了解,1789年人权宣言第6条所阐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第16条所要求的‘保障权利’都无法实现”;“对法律的了解对于人权宣言第4条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也是必要的”,因为第4条规定行使权利的界限只能由法律加以确定,第5条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法律所未禁止的行为都不得被阻止,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做法律未要求他做的事情”[10]。法国学者对这项宪法判例的分析是,法律易于为公众所知晓和被读懂,这不仅牵涉到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还涉及到“公民资格”是否能真正具有实效这一宪法问题[11]。法国宪法委员会在2005年12月29日的另一项判决中更明确指出:措辞和内容过分复杂的法律草案有可能被其宣布为违宪,这就意味着,从宪法要求的高度来看,法律本身应该是简单易懂的[12]。
法律易于被民众所知晓,这又包括两个层面:从物质层面上,法律的载体法典极大的“拉近”了法律和民众的距离;从精神层面上看,成文法典的条文本身具有清晰和易于读懂的特点。毫无疑问,法律文本中所包含的法律规范比起冗长的判决的摘要来说,要好懂得多。这些判决中所包含的规则通常还很少明确其适用领域和范围;而且,某些判决通常会引发法院嗣后的一系列解释,这更加重了其复杂性。对于一个不是专门研究法律的普通人而言,普通法系其实是很难懂的:为了从众多判决中提炼出一项法律规则,这是只有法律专家才能完成的工作。由此,如今普通法系所必须应对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法律信息的过分繁复给整个普通法体系的平衡带来了威胁———这比成文法系中的“立法膨胀”更为严重。牛津大学著名学者PeterBirks教授在其“英国私法”中指出:“在这个新世纪之初,普通法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的过分冗余(informationoverload)。”[13]另一普通法学者指出:如今的法律著作和判决都充斥着大量的、不必要的判例和学术性论述,结果是“细节比比皆是,原则却消失了……生活变成了一堆司法机构的丛林,人们却无法知晓这些机构所秉持的目的和原则。”[14]
以近代第一部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为例,其在行文风格上非常简明易懂,大量的条文可谓脍炙人口:第146条规定“如不存在合意则无婚姻”;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物的、绝对的享有和处置的权利,只要法律和条例未加以禁止”;第81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处于共有状态”;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第1382条规定“任何因过错致人损害之人应对他人负担赔偿之责”。法国民法典的这一风格在上世纪初被瑞典民法典之父欧根·胡贝尔(E.Huber)称为“大众型法典”,与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学者型法典”形成对照[15]。直到今天,法国民法典的许多条款仍然堪称立法艺术的典范:如第1375条和2805条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第1405条关于不动产买卖中的损害(lésion)的规定,第708条关于未成年人遗嘱能力的规定等等。法国民法典的风格深深影响了同为法语地区的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民法典,后者在1994年修订时,起草者仍然坚持“要使法典为所有人所知晓,尽可能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二)法律的确定性
法律的确定性,是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本身能够给法律主题提供某种明确的预期,使其在事前能够清晰地知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在成文法体系中,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以明文的方式加以规定,主体由此可以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责任,他(她)可以根据可能承担的责任来选择或者控制其行为模式。
1·事先通晓规则。法律的确定性要求法律主体在事前能够预知法律规则或者其原则。英国学者JohnBell认为,在法律渊源上,大陆法系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法典和其他成文法占有相当比重,另一方面理论和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16]。就大陆法系而言,一方面,判例在法律渊源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如今已毫无争议的称为辅的法源,但是,根据大陆法系的一般原则,法官被禁止创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典型者如法国民法典第5条的规定),法官仅在必要的时候介入,运用法律解释的技术手段来应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另一方面,创制一般性法律规则的前提条件是,法学理论已经提炼出了作为成文法核心的范畴和概念。
2·预防争端。就法的精神层面而言,大陆法系将争端的预防和争端的解决视为同等重要。就理念层面,法律固然应该组织一套对抗机制以实现其纠纷解决功能,更为重要的恐怕是确定一种和平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诉讼的大量出现不应该被视为法律辉煌之所在,而应被视为法律本身的某种失败[17]。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大量的、本应由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等)所规范的关系涌入法律所调整的领域,大量的、本应由其他规范体系消解的纠纷转化为诉讼争端,这本身也标志着社会有机体吸收和化解纠纷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的“失灵”。这在许多人极力主张“为权利而斗争”的中国,是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
(三)法律的灵活性
灵活性是法律本身适应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能力。由于新的科技和交流手段的革新,社会演进的节奏明显加快,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社会利益的分化日益加剧,法律规则也激增,这样尤其表现为法律渊源以及冲突解决途径的增加。“法律”和“时间”的关系成为当代法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18]。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法律规则变换越来越迅速的今天如何保障“法律安全”?法律如何能回应社会的快速演进?
(四)法律渊源的开放性
渊源方面的开放性是指法律本身对于其他法律渊源的进入保持开放态度,允许在适当的条件下适用其他这些法律渊源;这些除了成文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渊源包括:判例、习惯、法律一般原则、学说等。就民法典本身,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迁。以法国民法典为例,它所历经的修订是十分壮观的:这个规范的“大全(Corpus)”被保留下来了,它被“反复修订和重组,但是并没有被破坏”[19]。民法典的人法和家庭法部分(包括婚姻制度),以及继承法的相当部分内容已经被完全重新制定。就此而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1964至1977年间,由巴黎大学Carbonni-er教授所主持起草的九部法律,实现了家庭法和人法领域“静悄悄的革命”。为了应对同性恋团体的压力,民法典于1999年纳入了颇有争议的“民事互助协定(PACs)”制度,承认了同居(无论异性或者同性间)这一法律形式的合法性。另外,法国民法典中有关经济生活的内容的改革,也早已开始,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履行对于欧洲联盟的承诺—譬如为了转化欧盟1985年关于瑕疵产品责任的指令,法国民法典增订了第1386—1至1386—18条。这些改革还将持续下去:关于担保法的改革在MichelGrimaldi教授的主持下已经完成,2006年3月28日的法令在民法典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第四编“担保”,扩大了担保设立的标的(例如在库存商品stock上设立的担保)、简化了担保实现的程序(譬如承认所谓“流质”和“流抵”的合法性)、增加了新的担保形式(安慰信、独立担保、可更新抵押等);债法改革的专家报告已经完成(PierreCatala教授领导的专家小组已经向司法部提交了报告)。由此,法国民法典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纳入了从人工辅助生殖、生物证据到电子文书等在内的多项变革,如今的民法典在内容上与1804年诞生当初的民法典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
此外,在法国,民法典之外的许多单行法也得以通过,其中部分法律被纳入到其他法典之中,譬如商法典、消费法典或者货币与金融法典。譬如,就法国合同法而言,所谓的“普通法”当然是民法典,但是还有许多的判例和特别法,适用于某些群体的特殊需要或者特定地位(消费者、经营者、经销商、劳动者等)。
1·判例的重要作用。判例作用的日渐突出是大陆法系国家所出现的共同现象。以法国为例,自19世纪末期以来,判例在私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法国最高法院对民法典的许多解释,既表现出相当的实用主义精神,又不乏前瞻性和想象力。在初期,最高法院通过对部分条文的解释,赋予了其以立法者的意图之外的意义(譬如对第1384条第一款的解释);后来,最高法院揭示出部分条文具有某些通常被忽视的意义:譬如,最高法院对第1134条第三款的解释(第1134条第三款要求在合同的履行阶段必须秉持诚信(bonnefois),最高法院则扩大解释为在合同的所有阶段特别是缔结阶段,当事人负有诚信义务,以及对第1135条的解释(该条对于当事人课设了“根据其性质”、基于公平原则而产生的义务,据此法国最高法院推导出了当事人所负有的许多未曾明文约定的义务)。此外,最高法院还通过对一些过时条文进行解释,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新的需要:譬如,民法典第1121条对于为他人所缔结的合同设定了一些条件,这对于人寿保险合同的发展明显不利;第1129条要求债的标的必须特定或者客观上可以确定,这对于承认单方面决定价格的供货合同或者服务合同在理论上造成了障碍;第1142条的规定引发了债务的强制实际履行是否能适用于不作为之债的争议。法国最高法院通过其解释,都圆满消除了这些理论障碍,使得民法典能够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迁和需要。
2·一般性条款的弹性。民法典的许多条款都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特点。这种一般性表现为表述上的抽象,省略掉具体化的细节性描述。不过,这种一般性规范本身也具有灵活性,这使得判例可以通过它们来实现对民法典的调整,使之适应于现实生活。长期以来,德国民法典中的一般性条款广泛为中国研究者所注意;相反,对于法国民法典上的一般条款问题,中国学者则基本未有涉及,实际上,法国民法典也存在诸多的一般条款。譬如,从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出发,在19世纪末,法国最高法院发展出了“因物所生之责任”的一般性原则;在20世纪末,又从此发展出了“因他人行为所生之责任”的一般原则。同理,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一款(将契约类比为当事人间生效的法律)从意思自治原则出发,强调合同的绝对性效力,因而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坚持严格主义立场;其第三款要求在合同履行阶段秉持诚信原则,这一条款后来成为一系列判例革新的“温床”,尤其是诚信义务被法院扩展至合同的全部阶段,由此实现了合同关系的人性化。至于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第1135条,后来被用来补充合同的内容,尤其是为合同增加那些基于公平原则和合同惯例所衍生出的义务。
3·任意性条文的补充。民法典同时包含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不得由当事人的合意加以排除;而任意性规范则可以当事人选择适用。强制性规范往往是为了保护某种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秩序(譬如某些特别合同法对于消费者、承租人等特定群体的保护)。任意性条文则是民法典的主体规范,它具有以下功能:首先,它本身也是法律规范,由立法者基于公共利益所制定,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它,则本身也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促进———当然,当事人完全有权排除它们的适用;其次,在确有必要的情形下(譬如当事人约定的条款被宣告为无效或者被撤销),法官可以以任意性条款来直接取代当事方最初所约定的条款;再次,任意性条款可以使得当事人在缔结合同的阶段免于进入过分细节化和技术化的讨论,它也使得当事人省却必须预见到一切的负累;最后,如果当事人认为某些任意性条款并不适合或者不再适合他们之间的情势,则他们可以以合意排除这些条款的适用。由此,任意性条款为当事人留下了充分的创造和想象空间。
二、外在特征
由于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密切联系,合同法是民法典中最富有活力的部门,因此,合同法的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民法典发展变迁的缩影。合同法的开放性、平衡性和经济性,尤其反映出民法典的优势。
(一)开放性
1·针对其他法律渊源的包容性。民法典中的合同法是这方面的典型:合同法作为调整经济交易关系最为重要的法律,面对永远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的交易实践,当然也不应该“凝滞”或者僵化。以法国为例,首先是单行法的修改,譬如,1975年7月9日和1985年10月11日的法律分别修改了其民法典第1152和1231条,授权法官对于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违约金条款进行修改。其次,判例有时候可能会构建出合同法某一领域的规则(例如,前契约阶段),或者在民法典之中或之外发展出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和概念(譬如,前契约阶段的信息义务,安全义务,销售者和制造者的产品责任,合同的协议转让和解除等),或者将某一局部适用的规则扩展为一般性规则(譬如同时履行抗辩规则,exceptiononadimpleticont-ractus)。再次,交易实践为不断丰富合同法的内容,使得合同法不断接纳和确认新的交易形式(如解约条款、责任条款、安慰信、独立担保)。最后,学理界也不断将许多理论和概念体系化(合同的对抗性,实质性义务、合同群理论[20]),并不断突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如方法之债和结果之债的区分)。
2·对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在如今各国的立法活动中,比较法无疑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各主要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制度安排,这已经是各国在立法中的一项普遍做法。对于外国法的借鉴,这也是法国这个拥有悠久民法传统的国家的经常性做法。仍旧以法国法为例,譬如,在价格的确定方面,法国最高法院在审判中就曾参考了德国法和罗马统一私法国际委员会(UNIDROIT)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当时还尚未公布)中单方面确定价格的有关内容[21]。在法国最高法院近年的一些关于合同诚信义务的判决中,还可以看到普通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影响,譬如所谓的“信赖理论”[22]。
3·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迁的敏感性。作为调整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不可能自外于其他领域,不受其他领域变革的影响,或者不考虑自身对于其他领域的一项———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可能引发的后果。合同法更是如此:对于交易关系的促进、对于经济生活的良性影响,这是合同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拒绝将一方遭受的“损失(lésion)”作为宣告合同无效或者变更的原因之一,因为起草者们“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多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大量交易因一方遭受损失而被撤销的麻烦记忆犹新”[23]。在当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显然需要考虑法律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譬如,法国负责研究担保法改革的专家小组中,除了法学教授和法官以外,还有银行家、公证人和律师等实务界专家。此外,法院在做出判决时,通常也会考虑判决的经济影响,譬如,法国最高法院在为某些投资性的人寿保险合同进行定性的时候,就曾大量征询了公证人、保险公司、经济和金融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意见。另外,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的动机也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得到解释。此外,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方法也并不陌生:在合同法中,法国一些学者反对情势变更理论,也正是基于经济上的分析。据他们看来,如果经济情势的变更能经常性地导致合同的变更的话,这会危害经济秩序的稳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24](当然这一看法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平衡性
平衡性是指法律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平衡。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存在关于合同的一个普遍性的定义?比较法研究发现,关于合同这个最基本的法学范畴之一,存在着多种定义和视角。例如,在深受自由主义思想、重商传统和新教伦理影响的英国,关于合同的观念就更多的体现出经济维度的考虑;而在天主教影响深厚、重视合同伦理的法国,其关于合同的看法就呈现出相当的道德主义的特点。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扩大至伊斯兰法体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教法关于合同的理念又与前述两大法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关于最为基础、为各大法系所共有的基本法学范畴,关于其内容的理解,各个法系可能并不相同。
就合同的有关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个人主义方法、道德主义方法、连带主义方法等。就此而言,巴西的最新立法值得关注:其2002年的新法典要求“契约自由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在合同的社会功能的限度内行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普通法学者梅因就揭示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一切“进步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在当代,许多大陆法学者在更为深入地谈论所谓“法律的契约化”现象(如前所述,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家庭法、物权法等领域);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并非偶然: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重心从“法律”向“契约”的转移;法律为当事者所直接规定的联结逐渐减少,而当事者通过契约所构建的联结渐次增加;法律的调整模式逐渐从“强行性法律”向一种“协商性法律”转变。
在理念和方法论层面,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观念与普通法系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譬如,就合同的效力而言,尽管两大法系都会强调古老的拉丁法谚Pactasuntservenda(承诺应当严守),这一合同法的奠基性原则却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将合同视为“bargain”,强调双方利益或者好处的交换,两种允诺的交易,因此,合同一方可以主张“或者我选择履行,或者我选择赔偿”,任何一种方法是均应被视为可以满足对方的利益;显然,交易秩序中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可见,此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考虑是经济上的安排。由此,普通法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根据Holmes的著名论断,原则上,选择支付损害赔偿是当事人的自由;强制实际履行只是一项例外性责任形式。总之,合同法需要考虑的是交易的迅捷、便利、效率。法律经济学派的“有效违约”理论即是典型:如果违约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则应允许一方选择以支付违约赔偿而解除合同。这明显反映出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履约还是违约在这里被纯粹解读为一种利润最大化的算计,并无道义诚信等方面的考虑。
这正是许多大陆法学者明确反对将合同简约为“bargain”的原因所在。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大陆法更倾向于合同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后,才算达到圆满状态。例如,受到法国法的影响,智利法律规定“如一方未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选择强制其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支付损害赔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某些合同法制度———诸如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前的催告、约定违约金条款、合同解除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拒绝承认情势变更理论等———都反映出对于合同效力的重视:法律为债权人同时提供了多种选择,以使合同能得到履行;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法律为促使其履行合同提供了多种制度框架,以使合同不至于终止。在许多大陆法学者看来,强调对己方先前做出的诺言的信守、对于对方的合理期待的尊重,这显然涉及道德等诸多层面:中世纪教会法和宗教教义的影响,和他的交互性特征,信守承诺的骑士精神,基本的自然正义观念……由此,强调进入合同关系的双方应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善意、忠诚、合作和相互扶助等),这只有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外的其他分析框架才可以解释(道德、伦理、宗教、社会学等)[25]。法国当代影响甚大的“合同连带主义(solidarismecontractuel)”思潮,是沿袭了杜尔凯姆、撒莱、德莫格和约瑟朗等人的法社会学思考路径,反对纯粹从商业和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合同。
(三)经济性
经济性是指法律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各个环节包括争端解决环节的成本。在成文法体系中,合同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交易关系的抽象,这些规则在内容上可以成为一般性的交易条件。由此,在大陆法系中,由于完备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对经济当事者而言无需就合同的所有环节和所有事项,均制定繁简无遗的庞杂条款———这与普通法的情形有所不同;从微观角度看,这极大地节省了经济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从宏观角度看,以法典为核心的成文法体系还具有预防和避免争端的功能。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司法和诉讼程序的总运作成本(公民、企业、公立机构为律师、法院、司法专家等所负担的所有费用)约为650亿美元,大约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6%;这一比率在瑞士为0.8%,在法国为0.6%,而在西班牙仅为0.4%。此外,在美国,平均每3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的律师数量据称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这一数字在法国是1700。在美国,每年每10人中就会有一人牵涉到讼争;这一数字在法国是300[8](P106)。根据一些比较法学者的分析,这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在普通法中,当事者无法服从于成文法典,而是受制于法官创造的规则,这使得当事方对于律师具有更大的依赖;而由于当事人预先无法完全知晓规则,由于普通法的诉讼构造和法律文化,当事人也会具有更大的冲动去诉诸法院。
结论
颇有意思的是,根据位于普通法区域的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全世界,超过150多个国家占全球60%的人口采用的是大陆法体系;以制定众多法典为其标志。虽然数字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成文法体系就一定优于普通法系,但是,这起码使得我们更有理由在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坚持大陆法传统,理解法典化是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最合理选择,从而坚定地继续已颇有建树的法典化之路;而中国民法典的最终出台也必将为中国法体系的“质地”增添“现代性”。
注释:
[1]NicolasMlfessis(souladir.),.LaCourdecassationetl’élaborationdudroit[C],Economica,2004.182
[2]B.MALLET-BRICOUT,Librespropossurl’efficacitédessystèmesdedroitcivil[J],RevueinternationalduDroitcomparé,2004(4).865
[3]譬如,普通法系上的支票、融资租赁或者信托等制度,就都为大陆法系所吸收;而作为普通法系的英国在2004年通过的“住房法HousingAct)”,就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法国法的经验,要求住房在出售前必须由房屋监察员(homeinspector)签发一份“房屋信息报告”,详细报告待售房屋的法律、环境、安全等方面的信息。在美国,部分州受到了法国等国的经验启发建立了“民事公证人”制度;而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的以色列也正在准备制定一部民法典。
[4]PierreLegrand,Thestrangepowerofwords:codificationsitu-ated[J],TulaneEuropeanandCivilLawForum,1994(1).12
[5]J.Vanderlinden,LeconceptdecodeenEuropeoccidentaleduXIIeauXIXesiècle,Essaidedéfinition(M),Bruxelles,198
1967.
[6]GeoffreySamuel,EnglishPrivateLawintheContextofthCodes,inMarkVanHoecke,FrancoisOst(dir.),HarmonsationofEuropeanPrivateLaw(EuropeanAcademyofLegTheorySeries)[C],HartPublishing,2000.58
[7]XavierdeROUX,LeCodecivilresteunoutilprivilégié[J],LaTribune,2004.3-18.
[8]MichelGRIMALDI,“L’exportationduCodecivil[J],inLeCodecivil,Pouvoirs,2003(107).80
[9]AssociationHenriCapitant,Lesdroitsdetraditioncivilisteenquestion,AproposdesRapportsDoingBusinessdelaBanqueMondiale(C),SociétédeLégislationcomparée,2006.182
[10]法国宪法委员会1999年12月16日作出了第99-421号判决,针对的是即将颁布的、通过政府法(ordonnance)所完成的九部法典。
[11]V.M.-A.FRISON-ROCHEetW.BARANES,Leprincipeconstitutionneldel’accessibilitéetdel’intelligibilitédelaloi[J],DallozRecueil,2000.
[12]法国宪法委员会2005年12月29日作出了第2005-421号判决,此项判决所针对的是2006年的预算法草案。
[13]PeterBirks,EnglishPrivateLaw[M],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10
[14]E.McKENDRICK,TheCommonLawatwork:theSagaofAlfredMcAlpineConstructionLtdv:PanatownLtd[J],Ox-fordUniversityCommonwealthLawJournal,2003(3).145
[15]A.MARTIN,LeCodecivildanslecantondeGenève[C]inLivreducentenaire,1904.
[16]JohnBell,FrenchLegalCulture[M],Oxford,2001.7
[17]AssociationHenriCapitant,Lesdroitsdetraditioncivilisteenquestion,AproposdesRapportsDoingBusinessdelaBanqueMondiale(C),SociétédeLégislationcomparée,2006.89
[18]AnneGUINERET-BROBBELDORSMAN,Letempsetledroit[M],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he-Comté,2003.28
[19]Jean-LouisHalpérin,Leregarddel’historien[C],inLeLivreduBicentenaire,Dalloz/Litec,2004.43
[20]合同群(Groupesdecontrats)指基于同一总体性目的而缔结的、相互具有关联的多项合同的集合体。
[21]Cass.Ass.Plén.,1erdéc.,1995,DallozRecueil[J],1996(1).153
[22]Cass.civ.3ème,13oct.1998,DallozRecueil(J),1998(2).172
[23]F.TERRE,P.SIMLERetY.LEQUETTE,Droitcivil,Leobligations[M],8eéd.,Dalloz,2005.209
[24]J.FLOUR,J.-L.AUBERTetE.SAVAUX,DroitcivilLesobligations,L’actejuridique[M],ArmandCollin2004.410
[25]C.JAUFFRET-SPINOSI,Rapportdesynthèse-Lecontrat[C],Journéesbrésiliennesdel’AssociationHenriCapitant,2005.20
第5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内容提要: 行为能力制度依据自然人的本性设计,用于商主体时意义有限。商主体能力建立在完全行为能力基础之上,商主体之间不存在行为能力差异。每个商主体特有的组织条件和方式造就了相应的经营能力,通过机关形成与表达意思,经营范围是经营能力的外在表现,商事登记是对经营能力的确认。商法依据经营能力判断主体活动的法律效果,商法中的经营能力发挥着民法中行为能力类似功能,在商法中实际发挥制度功能的是经营能力。
在我国商法理论中,直接套用民事行为能力理论,将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制度直接应用于商主体(注:商主体是商法确认的能够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并能够独立享有和承担商事权利义务的人。有学者将广义的商主体等同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商人,即商自然人、商合伙、商法人,还包括广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本文在狭义上使用商主体概念,范围与传统商法中商人概念一致。)。一般认为,无论是民事主体还是商事主体,都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商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灭。其实,商事法律关系通过经营行为而产生,商主体是经营者,商主体的人格基础是组织体,通过内部机关形成和表达意思,这些机关都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商主体之间不存在行为能力差异,只存在经营能力差异,行为能力制度在商法中没有意义,实际发挥制度功能的是经营能力。
一、行为能力制度设计的固有逻辑
行为能力是民法的基本制度,反映不同自然人之间的差异,据以区别不同自然人行为的法律效果以维护交易秩序和生活秩序;行为能力制度设计包含了固有的逻辑结构,具备特有的制度功能。
(一)行为能力的制度演变
罗马法中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人法部分,在物法部分也有关于行为能力的特殊规定。在罗马法中,并非每个人都具有独立人格,有资格进行行为能力考量。在当时,行为能力制度作用的发挥受制于身份人格制度。罗马法中的人格是身份人格,只有同时拥有自由权、市民权、公民权者才具有完全人格,如果三种权利中有缺陷则导致人格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并没有完全从家庭中析出,合格的法律主体只有家父,家父是一个家庭的代表,依据这种代表人身份地位即可以推定家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其他家庭成员在对外关系中没有主体地位,根本不用考虑其行为能力的有无。对家庭中体力或者智力不足的人进行监护或者保佐,对于非血缘的个体进行收养。蕴含特殊行为能力的遗嘱和继承的部分则在物法中进行阐明,在契约的简单规定中对于主体的要求几乎没有明确提及。[1]罗马法的一些具体法律制度也反映了行为能力问题,比如罗马法中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制度的规定,还有患精神病的人不能为任何行为的规定。在其学者论述中,出现了相当于意思表示的萌芽,如《学说汇纂》中就出现了“意愿表示”;罗马法晚期,“合意”和“善意”概念出现。另外,也出现了“心素”意识。罗马法学家保罗在论及“丧失占有”时说:“即使在占有丧失情况下也应该重视占有人的意思。如果你就在你的土地上,但却不想占有这块土地,那么你立即丧失对该土地的占有。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仅仅因为心素就丧失占有,虽然人们不能以这种方式获得占有。”[2]从罗马法的规定来看,行为能力主要是与身体和精神状况、年龄、社会职业以及宗教、性别等因素相关,但是,行为能力的基础并没有纯化为决定人的意思能力的精神状况、年龄因素。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所为行为的法律效果区别,主要是依据身份差异而不是行为能力;行为能力普遍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个人普遍的独立人格在罗马法中并不具备。
《法国民法典》实际上确认了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建立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成为法律规范的基本单位,每个人均获得私法上的独立人格,意思自治获得广泛的空间,为行为能力制度的应用准备了前提;剔除了身份因素,行为能力制度的基础被纯化为意思能力。在私法秩序和安全要求中,行为能力制度应运而生,在行为能力的基础上重构财产、契约、家庭法运行制度。“该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一个产物,这场革命旨在消灭往昔的封建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培植财产、契约自由、家庭以及家庭财产继承方面的自然法价值。”[3]在法典结构上,法国民法典采用了“人”、“财产权及所有权的限制”、“取得财产权的各种方法”体例,在这三编中没有出现“民事行为能力”这样的标题,但在具体制度规则上完成了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在第一编“人”中,婚姻、收养、未成年、监护及解除亲权以及成年与受法律保护的成年人这些章节中都有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在第二编“财产权及所有权的限制”和第三编“取得财产权的各种方法”中,契约的订立、赠与、遗嘱以及设定抵押权这些制度中,实质上也有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
在1900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成为正式制度。当时的立法者希望通过法典编纂达到法制统一,他们要求当时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对德国现行的私法要从合适与否、内容真实与否以及合乎伦理与否等方面加以探讨,特别对于诸大法典与罗马法、德国的基础相异之处要研究其合适与否,尽可能求其均衡,从而草拟出适合于现代法学要求的草案。”[4]德国民法典中出现了很多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法律概念,其中行为能力概念出现在民法典中,第一次从形式上规定了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位于《德国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的“法律行为”章中的第一节。在德国法上,“行为能力是指法律所认可的一个人可进行法律行为的能力,即为本人或被人所为的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的能力。法律只承认具备一定最低程度判断力的人具有行为能力。”[5](p133)在德国民法中,影响行为能力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和精神状况,民事行为能力的制度功能是确定行为人行为的法律效力。
总之,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实质性规定早在罗马法中就存在,但行为能力作为抽象性的法律概念直到德国法才产生。在罗马时期,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淹没在身份制度之中,当时只有善良家父才具有完全人格,被推定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家属、奴隶则不具有完全人格,需要通过行为能力解决的问题大部分通过家庭伦理规则消化。1804年《法国民法典》确认了普遍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意思自治功能扩展,以身份来确定民事行为法律效果的做法被废弃,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建立在意思能力基础之上。1900年德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作出立法规定,使之成为正式制度。总体来说,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发展是与独立人格、意思自治相适应的。
(二)民事行为能力的制度结构
现代各国民法拥有相似的前提条件——人格独立与意思自治,对于自然人适用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自然人之间存在行为能力差别;多数国家立法中认为法人不适用行为能力制度。
对于自然人适用行为能力制度,民法以年龄、智力(精神状况)为标准将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另外,以监护和保佐、宣告禁治产制度为补充,形成行为能力制度体系。以《德国民法》为例,该法规定,未满7周岁的是无行为能力人,年满7周岁未满21周岁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年满21周岁的是成年人,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如果他们不是精神病人或者禁治产人,则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于一些特别事项,法律也有具体规定。比如结婚年龄,原则上必须达到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年龄,如果其已经年满16周岁,且其未来配偶为成年人,监护法院可以允许其结婚。关于订立遗嘱的能力,规定为年满16周岁。德国法上关于禁治产的规定也与行为能力相关。宣告禁治产的情形是:“1.因精神病或者精神耗弱而宣告禁治产的,需要被宣告禁治产者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2.因挥霍浪费而宣告禁治产的,需要被宣告禁治产者挥霍浪费致自己或者家属有陷于贫困之虞;3.因酗酒或吸毒而宣告禁治产的,需要被宣告禁治产者因此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或者致使自己或者其家属有陷于贫困之虞,或者危及他人安全。”[5](p138)其中,只有精神病人被宣告禁治产人时才为无行为能力,而当行为人是因精神耗弱或者挥霍浪费或者酗酒、吸毒而被宣告禁治产的,则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关于法人的行为能力,各国法规定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的理论通说认为法人不具有行为能力,英美国家学者也持同样立场。德国民法只对法人权利能力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其行为能力没有具体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6条规定:“1.社团须设董事会,董事会得以数人组成之。2.董事会在裁判上及裁判外,代表社团,有法定人的地位。”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民法上并不承认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它的董事会则是它的法定人。但是以瑞士民法为代表的国家则明确承认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瑞士民法典》第54条规定:“法人依照法律或章程设立必要的机关后,即具有行为能力。”[6]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中规定了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关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没有象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那样作具体划分,更没有规定作为确定其行为能力的具体标准。
(三)行为能力确定的依据
行为能力确定的自然依据是意思能力。各国民法中规定的行为能力一般都与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等个人因素相关,即行为能力确定的依据是行为人的意思能力,意思能力的有无以及大小是确定行为能力状况的关键因素。意思能力是指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社会后果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它揭示的是主体的自然属性。自然人可能会因为其身体机能,即自然人主体属性内部的因素,存在意思能力不全的可能性,这是对自然人设置行为能力的主要依据。
行为能力确定的社会依据是制度功能,行为能力制度在民事主体法中的预定功能是:
其一,构造自然人主体制度。行为能力制度是自然人主体制度的要素并与人格独立、意思自治与监护制度相衔接。所有自然人均具有独立人格,享有权利能力,可以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民事法律关系主要通过法律行为形成,法律行为是意思自治的实现形式。在市民社会生活中,要求解决各种行为能力水平的自然人参与法律关系的效力问题。各国对于行为人欠缺相应行为能力的行为一般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除非该行为人在此行为中是纯获利益的;通过监护制度解决行为能力欠缺者参与法律关系问题,保护那些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行为人。
其二,保障实质平等。平等包括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行为能力制度有利于实现实质平等。法律规定所有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样,权利能力的设定就从法律上超越了所有的不平等性,实现了形式平等;但简单一致的平等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行为能力的引入有利于追求实质平等,通过区别对待使民法上的平等达到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统一。
其三,维护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民法制度规范设置背后的价值导向是使市场中大量的交易行为处于相应的行为能力支配之下,以此获得交易安全与秩序。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他人的双方法律行为,如未成年人订立合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一方面赋予法定人以撤销权或者追认权,而另一方面也赋予相对人以催告权,这也反映了各国对相对人的保护,这种对相对人的保护是从社会利益出发的。
其四,判定具体民事行为的法律效果。行为能力从技术上设置了标准,据以确定相关当事人民事行为的法律效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一般不发生预期法律效果,其意思表示在民法上是无效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自身行为能力相应的民事行为,不得独立为重大复杂的民事行为。他们行为的法律效果可以分不同情况。通常情况下,限制行为能力人都有法定人,他们可以以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名义代为有效的法律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自己所为的纯获利益的行为也是有效的。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一般是效力待定的行为,法律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和撤销权,只要得到法定人追认该行为即有效,否则该行为无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依据自主意志产生法律效果。
二、行为能力运用在商主体制度中的矛盾
行为能力在商主体制度中缺乏存在的根基,在商主体制度适用中产生诸多矛盾。
(一)经营行为的意思能力要求高于完全行为能力
商主体的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同一性质的营业活动,是一种职业性行为。如果将经营行为放到民事关系中考察,这种经营行为属于复杂行为,对于主体的意思能力水平要求高,必须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起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排除在外。商人必须面对市场风险,其风险识别、防范、规避能力均高于普通人。所以,商人的意思能力是高于完全行为能力的专业水准的能力。
(二)商主体人格基础中不包含行为能力
商主体的人格基础是组织体,不存在生理发育基础上的意志成熟问题。商自然人的组织结构简单,一般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所拥有的商业技能为核心要素,结合少量的营业资本,简单的营业设施,提供某种简单的产品服务;从外部观察,这种商业经营行为主要是经营者个人主导的,其营业体的经营意志与经营者个人意志似乎重合;从内部观察,经营者本身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并且是按照所经营业务的要求进行专业化塑造,如理发师掌握理发技艺。所以,个人的完全行为能力已经升华为专业的经营能力。商合伙虽然具有契约性质,但是,其组织性勿容置疑,商合伙的名义、财产、经营意志的形成、对外责任等方面均相对独立于合伙人,商合伙的经营意志也是通过法定的制度性程序形成、表达,与开展经营活动的专业化要求相一致。公司经营意志通过内部机构来实现,以法人机关形成、表达和实现意志,法人机关是不存在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之分的。总之,商主体以组织体为人格物质基础,其经营意志是组织体所包含的机能,这种经营意志从来都是以完全行为能力为基础。
(三)行为能力不能满足商主体的制度功能
首先,行为能力与商人本性不符。民法中的人是市民社会生活关系中的人,自然人是民法的真正主体,其人格基础是生命体,客观上存在生理发育过程和不同的意志成熟状态,在民法上反映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商人是经营关系中的人,以营利为宗旨,以营业体为基础,其经营能力是企业设立的产物,行为能力制度与商人的本性不符;其次,行为能力制度不符合商人主体性要求。自然人主体具有伦理价值,主体之间的平等是民法基本的价值追求,民事行为能力设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差别处理并与权利能力一起解决了民事主体的实质性平等。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行为是意思自治的工具,通过保护意志自由调动民事主体积极性,凡是行为人相应行为能力范围内的行为均获得法律效力,其意义在于对自然人主体性的尊重。商法中的人是经营关系中的人,商人是工具性主体,为营利和营业而存在,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的价值高于单个商主体的存在与经营自由,商主体在经营能力范围内能够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所从事的交易符合各方利益和市场秩序,经营者在经营能力范围内部的行为才能获得法律效力;再次,行为能力不能区分商主体的行为效果。在商法中,所有的商主体都具有行为能力,无法从纵向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不能以这个标准区分商主体的行为效果。在商法中,区分经营行为不同法律效果的标准是经营能力,经营能力由企业不同的组织过程和组织状态所塑造,彼此之间存在经营区域和资质的差异,这种横向的差异由经营范围所标示,由商业登记所确认。
(四)行为能力与各类商主体均不兼容
商主体的基本分类是商自然人、商合伙、商法人,行为能力制度要在商主体制度中运用,必须与具体类型的商主体兼容。
商自然人是商人,除了要具有一般智力和精神状况外,还必须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不能以行为能力一般标准即年龄和智力状况来进行考虑,因为商人本是精明人,所有的商人在精神和智力状况要求上都高于一般的完全行为能力。在法国法中,规定未成年人也可以经商,可以依法成为商人,但是一旦经商成为商人,他的法律地位就发生变化,就会转变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未成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允许营业,被允许营业的未成年人的营业行为就是当然有效的法律行为。所以,用行为能力标准来衡量商人没有实际价值。
商合伙中合伙人同样必须是或者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才能对于自己的商事活动承担法律责任,以保障商事安全与秩序;而作为组织体的合伙企业本身,只有在将它看作单一民事主体时,才可认为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作为商事主体时,具有经营能力,以此判断其所从事的商事活动的合法性和妥当性。
商法人制度结构不能容纳行为能力。关于法人的性质主要有两种学说。第一种是法人拟制说。该说认为自然人才是权利义务主体,行为能力是自然人所特有的。法人只不过是被法律拟制为自然人以确定团体利益的归属,它只存在于法律世界,仅仅是观念上的整体,并非社会中的实体。因为法人没有实体,没有意思能力,当然不具有行为能力;第二种是实在说。该说认为,由人组成的团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体,它在法律上的人格是团体固有的,不论国家是否给予承认,它们都是存在的。团体象自然人一样,也具有思维能力。[7]实在说认为法人是实在人,也具有通过其组织机构实现的意思表示能力,所以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持实在说的学者看到了法人拥有与自然人相同的主体地位,但据此认为法人也具有行为能力则缺乏说服力。因为法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代表机构实现,不存在行为能力不全的可能性。换言之,法人代表机构做出的意思表示,从行为能力角度看全部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无从区别法人的意思效果。
总之,行为能力本是私法理论依据自然人的属性量身设计的。商主体制度中不宜完全照搬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在商事领域,行为能力的设置缺乏相应的基本功能,并且适用在商主体上也存在着矛盾。
三、实际发挥制度功能的是经营能力
经营能力对于商主体的意义类似于行为能力对于民事主体,行为能力是确定民事行为人具体可以独立为何种行为的资格,经营能力就是确定商事经营者具体可以为何种商行为的资格。
(一)经营能力的定位
商主体能力制度应该包括:权利能力和经营能力制度。权利能力确立市场准入资格,只有商主体才能从事经营行为,非商主体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权利能力与主体资格具有同一性。这样,可以将商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虽然主体资格是法律确认的结果,但是,法律并非随意赋予主体资格;法律赋予某类组织商主体资格的内在依据是其具有经营能力,只有给具有经营能力的营业体赋予主体资格才符合立法者的意旨。企业法人因为具有经营能力,都是商主体。事业单位法人需要依据是否具有经营能力区分。其中,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提供有偿服务,拥有稳定的财源,具备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具有经营能力,可以成为商主体;而行政类和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则由其性质决定不能成为商主体。机关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不能成为商法主体。《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第6条规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政府投资的中小学校不得设立商人,不得从事商行为。上列机构中在职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不得设立商人,不得从事商行为。”
对于有资格参与经营活动的商主体,具体有资格进行何种经营活动,具体经营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从制度设计逻辑上看,必须有一种制度来确定商主体具体可以为何种行为,以确定商主体具体活动的合法范围。经营能力制度解决商主体可以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以及可以为何种经营行为等问题,以稳定商事秩序。经营能力用来确认商主体具体可为经营活动的范围,具体商事活动的法律效力由经营能力来判断。
(二)经营能力的内在逻辑
经营能力依托于商主体自身的组织结构以及其财产结构,经营范围是商事经营能力的内在限制与外在表现,商事登记是对于商事经营能力的权威确认。
1.经营能力是营业资产的机能。营业资产是形成经营能力的物质基础,在经营范围指引下,企业内部的各种资产要素和人力要素按照技术规则和组织规则,进行适应性安排,形成营业体的特定机能,即经营能力。如果说商人营业的目的是营利,那么,营业体只是营利的工具,而经营能力是这种工具所具有的效能,营业体的组织目标就是形成预定的经营能力。
营业资产是有组织的财产,它不仅包括物和权利,而且涵盖营业活动积淀的事实关系(包括知名度、信誉、顾客名单及同上下游协助商的关系网络、营业秘诀等)。在这种组织化的财产中包含了经营能力。如果公司需要扩大经营范围,就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并将增加的资本转化为具体的资产,按照新增经营范围的要求进行适应性安排,形成新的经营能力。
商自然人的经营能力同样来源于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组织的简单营业体。无论是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小商贩还是手工业者,他们经营能力确定的物质基础都是场地、资金、设备以及专业的经营技能。
2.经营范围是商事经营能力的内在限制与外在表现。所有商主体均存在经营范围,以公司为例,经营范围是指公司所从事的事业范围。公司设立过程中,先要确定经营范围,再围绕经营范围配备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相应的经营能力。不同经营范围的公司,需要准备不同的条件,形成不同的经营能力。比如,经营物流业务的,必须有一定的运输车辆和必要人数的司机;经营生产业务的,必须有相应的生产线和生产工人。公司成立,意味着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应的经营能力形成并获得法律认可。已经形成的经营能力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从客观方面,经营能力是各种物质资产、人力资本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按照生产经营所要求的技术规则和管理规则安排所形成的客观能力;从主观方面,经营能力是商法所确认的一种法律资格,是合法经营的许可。在客观方面,经营能力是公司实际具有能力提供何种产品或者服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只是公司经营能力的外部标识。一般情况下,经营能力与经营范围一致;例外情况下,也会出现实际的经营能力小于或者大于经营范围的情形。在主观方面,经营能力是合法从事何种商事活动的许可,其外部表现是经过合法登记程序确认的经营范围。即经营范围确定公司具体可为何种商事活动的范围,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一般超越了公司的经营能力,从而丧失了合法性。如果公司的经营范围涉及一些特殊事项的,比如要从事银行、保险或者证券等特殊的业务,设立这些公司还必须经过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这就是法律对特殊行业的经营范围的限制。在这种情形中,经营范围既是经营能力的外部标识,也是经营能力的法律依据。
3.商事登记是对于经营能力的权威确认。商事登记是指商主体或商主体的筹办人,为了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主体资格,依照商事登记法律法规、商事登记实施细则以及其他特别法规定的内容和程序,由当事人将登记事项向营业所所在地登记机关提出,经登记机关审查核准,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的法律行为[8]。商事登记包括两个方面性质:一方面是国家对商事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而采取的公法措施;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为了获得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所实施的商事法律行为。
商事登记与经营能力确立之间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从主观方面看,商事登记具有创设效力,即商事登记是商主体成立的必备条件。登记是向商事主体授予经营权的行为,带有市场准入的性质,商事主体未经登记,不能获得合法的经营资格,因此,登记在法律效果上具有创设效力;从客观方面看,登记只具有确认效力,即经营能力的取得并不以登记为前提,登记只是对经营能力的确认。因为商主体的经营能力是由其自身的经营条件所确定的,实际的经营能力并非来源于登记,此时,登记对于商主体的意义在于通过其权威性增强私法上的公信力。交易对象依据登记的经营范围识别相对人是否具有经营能力。
4.商人机关职能是经营能力的载体。商人经营意思通过内部组织机构来实现,因此,其经营能力依赖健全的组织机构。这就像自然人要想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其自身内部器官需要比较健全。经营能力依附于商主体内部机构职能及其组成人员的任职要求。例如,公司机构一般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以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会是决策机构,董事会是执行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机构。法人的意思都是通过其机关中任职的自然人来表达。商主体内部机关通过职权职责体现经营能力,如重要事项的表决权、决策权、执行权、重要文件的查阅权以及起诉权等。这些职权职责对于公司机关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出要求:首先,任职者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次,任职者应该具有相关的专业技能。不同行业的公司要求不同,比如,对于证券公司,董事就要具备证券相关业务知识技能;对于航海公司,就要求航海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不同岗位的专业要求也不同,如股东需要决策能力,而经理需要经营能力。最后,公司任职者的消极条件,从反面保证了商主体具备正常的经营能力。
(三)经营能力的功能
1.市场秩序的预先安排。在宏观方面,通过经营能力制度,对于市场秩序进行预先安排。其基本的作用机理是:一方面赋予具有客观经营能力、能够有效提供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主体资格,确认其经营资格,并且承认其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于不具有客观经营能力、不能有效提供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拒绝赋予其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将其排除在市场之外,或者拒绝承认其经营活动的合法性。
2.商主体资格的赋予依据。从形式逻辑上看是先通过权利能力赋予主体资格,在此基础上考虑经营能力。但是,经营能力与商主体资格之间关系的实际逻辑是:人们基于营利需要,对于具有各种经营能力的营业体赋予商主体资格;当市场充满了这些营业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基本对象,为了获得效率,从技术上将这个组织体简化为一个单一化的人,赋予其民法独立人格。所以,一个营业体所具有的经营能力是其获得商法上的主体资格和民法上的主体资格的合理性基础。
3.经营行为效力的判断标准。一般的判断是:具备经营能力的经营行为具有合法性,能够获得预期法律效果;不具备经营能力的经营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获得预期法律效果。实践中的经营能力通过经营范围和经营资质表现出来,超越经营范围一般就不具有经营能力,超出经营范围的经营活动当然不具有合法性。只是在一般业务中,公司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并不一定对于相对方不利,无需由国家法律一概予以否定。所以需要容许相对人依据自身的利益立场对于合同选择解除还是维持。有些商法上的非法行为,在民法上具有合法性。如果是一般性的非法行为,仅仅涉及交易双方利益,那么,违法者仅对相对方承担私法上的财产性责任,如果这种缺乏经营能力的行为威胁了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则通过强制性规定否定其效力,并进而产生行政法和刑法上的责任。
注释:
[1][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米健.意思表示分析[j].法学研究,2004(4):30-38.
[3][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8.
[4]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2.
[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蒋学跃.法人行为能力问题探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4):143-147.
第6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关键词]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法律制度;俄罗斯联邦
[中图分类号]D951.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4-0055-05
一、俄罗斯环境损害赔偿立法体系
立法体系是指一国之内由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的法律体系。在俄罗斯环境立法体系中,“除《宪法》外,俄罗斯还制定和颁布了大量保护环境的专门性联邦法律,主要有:《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联邦土地法典》、《联邦居民卫生防疫安全法典》、《城市建设纲要》、《联邦居民健康保护立法纲要》、《联邦大气保护法》、《联邦地下资源法》、《联邦森林立法纲要》、《联邦外层空间活动法》、《联邦自然医疗资源、医疗保健地和疗养区法》、《联邦特殊保护的自然区域法》、《联邦居民辐射安全法》、《联邦水法典》、《联邦生态鉴定法》、《联邦原子能利用法》、《联邦动物界法》、《联邦遗传工程活动国家调整法》、《联邦森林法典》、《联邦生产废弃物和消费废弃物法》、《联邦关于安全使用杀虫剂和农用化学制品法》,等等”[1]。具体而言,“‘生态安全立法’在俄罗斯现行立法分类规范中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被列入涉及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调整与此相关的一些共性问题的法律部门之中;另一部分被列入涉及安全和法律秩序保障的部门法规范之中。……俄罗斯的生态安全立法概括起来由四部分构成,即:意义上的立法、经济意义上的立法、社会意义上的立法和国际意义上的立法”[2]。
俄罗斯与环境损害赔偿有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宪法明确认可了俄罗斯联邦公民享有环境权利。该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均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均享有了解有关环境状况信息的权利,均享有因破坏生态损害其健康或财产而要求赔偿的权利”;第36条规定,环境权利的行使须以环境义务的遵守为限,“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和分配由其所有者自由实施,但不要破坏环境和损害他人的权利与合法利益”。
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参加签署的关于环境保护、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的国际条约以及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优先于国内生态法适用。宪法第15条规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及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是俄罗斯联邦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规定了不同于俄罗斯联邦法律所规定的其他规则,则适用国际条约规定的规则。”
第二,《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该法是俄罗斯环保单行法的基础。其明确了俄罗斯联邦的各级机关和法人、自然人都必须遵守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该法第3条规定:“遵守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保障人的生命活动的良好条件;……利用自然付费,损害环境赔偿;……对计划中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实行生态危害推定原则;……对可能给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对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威胁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方案及其他论证文件,必须进行国家生态鉴定;……根据环境保护的要求确定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影响自然环境的容许度;……遵守每个人都有获得可靠的环境状况信息的权利,以及公民依法参与有关其享受良好环境权利的决策的权利;违反环境保护立法必须承担责任”。第4条明确规定,大气、大气臭氧层是其环境保护的对象之一。
第三,《俄罗斯联邦生态鉴定法》。该法规定了国家生态鉴定和社会生态鉴定两种鉴定形式。
国家生态鉴定是指,俄罗斯联邦被专门授权的国家生态鉴定机关对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必须进行国家生态鉴定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项目,依法进行的生态鉴定活动,它具体分为联邦级国家生态鉴定(鉴定主体为联邦国家鉴定机关)和联邦主体级国家生态鉴定(鉴定主体为地区国家生态鉴定机关)两种形式。可能对邻国自然环境造成影响,或者其实施必须利用与邻国共有的自然客体,或者其实施涉及到邻国利益的经济活动的经济技术论证材料和方案,都属于联邦级国家生态鉴定的对象。并且该法第18条第4款还规定:“鉴定委员会的国家生态鉴定结论,必须经过被专门授权的国家生态鉴定机关的批准方才具有国家生态鉴定结论的地位,方才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第30卷第4期秘明杰:俄罗斯环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探究社会生态鉴定是国家生态鉴定的补充,是根据公民、社会团体(联合会、联盟、协会等)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倡议而组织和进行的生态鉴定。其组织章程明确地将保护自然环境、组织和实施生态鉴定列为主要活动方向,其鉴定主体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社会登记的社会团体(联合会、联盟、协会等)。该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实施社会生态鉴定的社会团体有权熟悉和了解规定有国家生态鉴定要求的技术规范文件。”同时第25条第2款规定:“社会生态鉴定的结论,经被专门授权的国家生态鉴定机关确认以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此外,为落实国家生态鉴定法还专门出台了《国家生态鉴定条例》、《俄罗斯联邦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条例》、《国家生态鉴定程序条例》和《国家生态鉴定规则》等。
第四,其他与环境损害赔偿有关的法律文件。如《俄罗斯大气保护法》、《关于联邦生态基金和地方生态基金的决定》、《关于批准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的生态标准、利用自然资源的限额和处置废弃物的限额及其制定办法的决定》、《关于评价和赔偿因事故造成的环境损害的暂行办法》等。
除上述外,《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09条规定:“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和处分在法津允许流通的限度内由其所有人自由行使,但不得对环境造成损失,也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同时,民法典还就环境损害赔偿归责原则、赔偿原则、赔偿办法等作出了规定。《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专章)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生态犯罪”专章)也对环境损害作了相关规定。
二、俄罗斯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
(一)《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中的几个概念
环境污染:其性能、位置或数量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物质和(或)能量进入环境。
环境损害: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引起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和自然资源衰竭的环境不良变化。
责任承担主体:法人、自然人、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主体。
损害赔偿提起主体: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公民、从事环境保护活动的社会团体和其他非商业性团体,上述主体都有权向法院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损害赔偿的接受主体: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拥有人或者自然资源利用人。
(二)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在俄罗斯联邦,环境损害又称生态损害,其民事责任与其他类型的法律责任相比较,最大特点在于,民事责任可以与违法者的纪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同时被追究。换言之,违法行为人可以在依法承担纪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同时承担民事责任。生态损害的民事责任构成,与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一样,通常情况下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要件:有生态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生态违法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与生态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
第一,生态损害事实,是构成生态损害的民事责任的首要条件。没有生态损害事实的存在,即没有生态损害结果的产生,便不能构成生态损害的民事责任。
关于“生态损害”,俄罗斯联邦在有关的立法中分别使用了不同的术语,这几个术语虽然在具体含义上有细微差别,但其基本含义是相同的,就是指因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态要求所导致的任何环境状况恶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受法律保护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利益(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的损害和减少。人的精神损害、可得利益损失和生态本身的损失也是生态损害的组成部分。
精神损害是俄罗斯联邦生态损害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根据《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51条、第1099条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关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第2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是指公民因其与生俱来的或法律规定的非物质利益(生命、健康、个人尊严、业务声誉、私生活不可侵犯、个人和家庭秘密等)、其他人身非财产权(姓名权、作者权和其他非财产权)和财产权受到侵犯所产生的精神或肉体痛苦。
精神损害包括因失去亲人、丧失继续参与积极的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失去工作、家庭秘密及医治疾病的秘密被披露、散布不实的诋毁名誉、尊严或者业务声誉之消息、某些权利被暂时限制或剥夺而遭受到的精神体验和与致残及其他健康伤害有关的肉体疼痛,以及因精神痛苦所生疾病而导致的疼痛所引起的精神体验。它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1)精神损害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既可以表现为精神痛苦,又可以表现为肉体痛苦。精神痛苦或肉体痛苦是精神损害的具体表现形式;精神损害是精神痛苦或肉体痛苦的集中体现。(2)精神损害是因他人侵害行为而引起的。侵害行为既包括侵犯公民人身非财产权的行为和侵犯公民其他非物质利益的行为,又包括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为。(3)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是公民个人。
公民不仅可能在因环境污染而对其健康或财产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受到精神损害(产生精神或肉体痛苦),而且还可能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虽未对其个人的健康或财产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受到精神损害(产生精神痛苦)。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不仅有利于人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和身体健康,而且还可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精神需求),愉悦人的精神。自然环境一旦遭到破坏,例如绿色植物或自然风景被毁,就不可能继续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就可能给人造成精神痛苦。因此,因环境污染对公民健康或财产造成损害而给公民带来的精神损害,以及因自然环境被破坏而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是生态损害的组成部分。
可得利益又称“未能获得的利益”或“未能得到的好处”。具体而言,是指自然资源利用人可以得到而实际上却未能得到的收入或其他好处。这些收入或其他好处,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得到的,但由于环境污染,如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的影响而未能得到。例如,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亩土地可获得500公斤的农作物收成,但在环境被污染的情况下,每亩土地只能获得200公斤的收成,减少的300公斤收成即是农场主可以得到而实际未能获得的利益,即可得利益。
生态损失具体是指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损坏、毁坏、枯竭、贫瘠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或生态失调,还应包括人的寿命的减少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第二,生态违法行为,是指违反自然保护立法,对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违法行为,它是构成生态损害民事责任最主要的条件。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实施了生态违法行为的人才应当承担生态损害的民事责任。而没有实施生态违法行为的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以外,不应承担生态损害的民事责任。
生态违法行为具有三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是它是违反自然保护法的行为,即违反生态法律、法规的禁止或命令性规定的行为。生态违法行为既可以是作为的生态违法行为,也可以是不作为的生态违法行为。二是它具有违法性。无论是以“为”表现出来的行为,还是以“不作为”表现出来的行为,都必须具有违法性。三是它是有过错的违法行为,即实施生态违法行为的人主观上具有过错。
第三,生态违法行为与生态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实践中,证明生态违法行为与生态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件异常复杂的工作。其中,不仅要证明行为人――企业、机关、组织、公民个人的生态违法行为与生态损害――对自然环境的损害、对人体健康和财产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证明人体健康的损害和财产损失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四,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指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时所处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一般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状态。《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064条第2款明确规定,造成损害的行为人如果能够证明损害不是因其过错造成的,行为人可以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意味着,在俄罗斯联邦,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以外,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都要求具备主观过错这一要件。
应当指出,在《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中有例外性规定。如该法第16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和其他物质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应当缴纳一定的费用,而其缴纳费用的行为并不解除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主体执行环境保护措施和赔偿环境损害的责任。”再如该法第77条第2款规定:“由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主体造成环境损害,包括其活动方案取得了国家生态鉴定的肯定结论和取用自然环境要素的活动,由订货人和(或)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主体赔偿。”此种规定实际上是严格责任原则在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的运用。
三、俄罗斯环境损害赔偿的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
(一)实体性规定
《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3条第7款规定:“利用自然付费,损害环境赔偿”;“对不良环境影响行为收费;依照规定程序赔偿环境损害”。这里不仅规定向环境排污、造成环境不良影响的行为要承担付费责任,同时强调在损害造成之前的利用行为也要付费,即不仅仅是在造成了不良环境影响甚至严重污染时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还要求在使用之初(不论是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还是对环境自身容量的使用)就要有偿进行。这样的立法思路充分表现了“自然环境的有价值性”,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环境是自然的馈赠,可以无限、无偿加以利用的做法,进而走入了环境有偿使用的新思维之中,这样的转变对于保护环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该原则的另一亮点在于规定了损害环境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不是对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造成的公民健康和财产损害的赔偿,它是对环境本身造成损害的赔偿。它把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造成的公民健康和财产损害赔偿明确区分开来,把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与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区分开来。后者主要是指可折抵的财产损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5条将损失解释为:“被侵权人为恢复其遭到侵犯的权利而花费的或应该花费的开支,其财产的灭失或损坏(实际损害),以及被侵权人未能得到,而如其权利未受到侵犯时在民事流转通常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收入(预期的利益)。”[3]。
《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1条明确了公民应享有的环境权利。具体可分为三种:一是公民环境对抗权(或环境保护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以环境权对抗不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行为的权利,是保护环境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不良环境影响的权利。将公民环境对抗权(或环境保护权)设定为公民环境权体系中的一项权利,为公民对抗环境不法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可以衡平环境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在社会生产中的分配。最关键的是,将环境保护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确定下来,为公民环境保护提供了积极的法律依据,避免了把环境保护只看作一种义务而无法调动公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的弊端。二是公民环境知情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获得可靠的国内、国外环境状况信息及环境科学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的权利。确立环境知情权为公民环境权的实现和推动环境民主奠定了基础。三是公民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权,是指公民享有依法诉诸法院、请求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
此外,该条第2款还详细列举了公民的派生性环境权利,包括:成立环保组织权即环境结社权;获得环境信息请求权;参加环境保护会议、集会、示威、游行、纠察、签名、公决权;提出并参加生态鉴定权;协助国家保护环境权;提出环境申诉、申请和建议权;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可见,《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从国家帮助环境权的实现、采纳公民环境保护意见、提供环境权国家救济三个方面构建了环境权的国家保障体系和保障基础。
《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77条确立了环境损害赔偿应遵循全部赔偿的原则,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包括间接损失,即“因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环境损害数额,根据用于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状况的实际费用并考虑受到的损失(包括失去的应得利益),以及复垦和其他恢复工程的方案予以确定,在缺乏这些项目时,依照实施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的执行权力机关批准的环境损害数额计算表和方法予以确定”。[4]全部赔偿的具体内容是指,对于财产损失的赔偿而言,致害人除了赔偿受害人直接的财产上的损失之外,还应赔偿受害人失去的“可得利益”,即受害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的利益;对于因人身损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而言,致害人应当赔偿受害人必要的医疗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护理费、治疗期间的交通费和误工工资等。如果受害人因健康损害而残废的,致害人除了赔偿受害人必要的医疗费用之外,还应当根据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和收入减少的实际情况,赔偿受害人因残废不能工作或不能从事原有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和残废人生活补助费用。如果受害人因健康损害而死亡的,致害人除了赔偿因医治受害人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之外,还必须支付死者的丧葬费及死者生前扶养人的必需生活费用。[5]
俄罗斯《联邦生产废弃物和消费废弃物法》在监督预防措施方面规定得比较具体。如第10条第1款规定:“在实施对企业、建筑物、结构、设备及其它工程项目的设计、建设、改造、防腐和摧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未形成法人的个体企业的公民(或者个体企业者)和法人有义务:遵守俄罗斯联邦有关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的法令所规定的生态、卫生及其它要求;具备对废物的利用与无害化的技术与工艺的证明文件。”
(二)程序性规定
对环境民事损害赔偿程序作出原则性规定的是《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该法第6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职权有:……对因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环境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第11条规定:“公民有权……向法院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在第78条明确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规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自愿进行或者根据法院或仲裁法院的判决进行。”该规定明确了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解决的一种程序,显示了诉讼外途径尤其是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重要性。而且该法第78条第3款把诉讼时效定为20年。
《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损害赔偿的具体程序。依据1964年民事诉讼法典第41、42条的规定,不仅可以依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提讼,而且检察长或者国家机关、工会、企业、组织和个别公民为保护他人的利益也可以提讼。而2002年民事诉讼法典则严格限定非利害关系人的条件:检察长有权请求法院维护公民、不确定范围人的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但这种请求仅在公民由于健康状况、年龄、无行为能力和其他正当原因不能亲自向法院提出请求时才能由检察长提出(第45条);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组织和公民有权向法院提出请求,以维护他人的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但前提是该他人请求这样做,只有在该他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未成年人时,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组织和公民才可以主动提出请求。
(三)赔偿计算标准
第一,由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主体造成的环境损害,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环境损害数额计算表和方法予以赔偿;在没有这种计算表和方法时,根据用于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状况的实际费用并考虑受到的损失(包括失去的应得利益)予以赔偿。
第二,因违反环境保护法规造成的环境损害数额,根据用于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状况的实际费用并考虑受到的损失(包括失去的应得利益),以及复垦和其他恢复工程的方案予以确定;在没有这些项目时,依照实施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的执行权力机关批准的环境损害数额计算表和方法予以确定。
[参考文献]
[1] 王前军.俄罗斯的环境保护政策[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7(6):2022.
[2] 刘洪岩.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球法律评论,2009(6):7786.
[3]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M].中译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447.
第7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提存(德文:Hinterlegung、法文:consignation、英文:lodgment or deposit[1]、日文:供托),即以标的物交付于公共保管机关或保管人。提存有的是以清偿债务为目的而为之,如《合同法》第101条至104条之规定,即债务人基于特种原因,无从为清偿时,得以适合于保管的给付物,为债权人提存之,藉以免除责任。有的是为担保关系而为之者,如《担保法》第49条第3款、第70条、第77条、第78条2款及第80条。后者为担保提存,前者为清偿提存。
古代罗马法,债务于债权人受领迟延时,得抛弃给付物之占有以消灭其债务,此种方法不但对于债权人个人不利,且非所以维持国家经济之法,故嗣后罗马法对于动产,特认“公共场所提存”制度(depositum in aede publica)[2],当由于债权人年幼、失踪、尚未确定等原因而发生受领迟延(moraaccipiendi)时,债务人可将有关的给付物寄存在某一公共场所(通常为寺庙的僧侣处),以此办法履行清偿义务,并使自己得以解脱[3].近世各国法律从之,《德国普通法》、《普鲁士邦法》第1部第16章第213条以下、《奥地利民法典》第425条、《法国民法典》第1257条以下[4]、《德国民法典》第372条以下、《瑞士债务法》第92条、《日本民法典》第494条以下、《泰国民法典》第361条以下、《意大利民法典》第1210~1215条、《俄罗斯民法典》第327条可供参考。民国民法主要借鉴日、泰民法,于第 326条~333条规定了清偿提存制度。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提存制度。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第19条第4款规定:“定作方超过领取期限6个月不领取定作物的,承揽方有权将定作物变卖,所得价款在扣除报酬、保管费用以后,用定作方的名义存入银行。”是为承揽合同的清偿提存。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4条规定:“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债务人履行义务,债务人将履行的标的物向有关部门提存的,应当认定债务已经履行。因提存所支出的费用,应当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间,财产收益归债权人所有,风险责任由债权人承担。”乃对清偿提存在司法实践上给予一般性承认。1995年司法部通过的《提存公证规则》对两类提存均有详细的规定。1999年《合同法》对清偿提存也做出规定。《澳门民法》第832条~837条以提存为债之消灭方式之一。
我国法上也像多数国家一样,以提存作为清偿代用(Hinterlegungals Erfüllungssurrogat)之一种。盖债务人之给付义务,有的无需债权人之协力或受领(如不作为债务),大多则需债权人之协力,始克完成,若债权人不予协力,或债务人无从得其协力,则债务人无以按时解除债务之拘束,不利斯甚。此际,债权人固常负受领迟延责任,使债务人之责任,得以减轻[5],但给付义务,仍犹存在。一旦债权人请求,仍应履行。债务人势必常为履行之准备,且各种从义务、担保权益也不得消灭,烦累堪虞。故法律特就其中适宜于提存之债,以提存作为清偿之替代方法,令债务人毋须待债权人之协力,藉此以免其义务,而期公允也[6].
二、清偿提存之性质
关于清偿提存之性质,学说纷然杂陈。大别之,有所谓公法行为说与私法行为说两大类。以提存为公法上之行为者,所持理由亦不一致。关于提存所之允受,有谓系为公益而为之者(Kapf);有谓系为尽公法上之义务者(Endemann),有谓有强制承诺之性质者(Beer);有谓提存系公法上之契约者(L?ning);有谓提存系国家以之作为非讼事件而处理之公法关系者(雉本)[7].以提存为私法上之行为者,又分为要约说和双方行为说。前者如B?hr以提存为清偿之要约,Kohler则以之为返还请求权让与之要约。后者,又复分为四:有谓其为寄托契约者,有谓其为利益第三人之契约者[8],有谓其为准为第三人之契约者[9],亦有谓其为兼备寄托及为第三人契约两种性质之特种契约说者。我国学者大多数持“特种契约说”。[10]
与提存相关的有三个问题:①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存?②提存有什么效力?③如何提存?[11]其中前两个问题在合同法中做出了规定,司法部1995年6月 2日通过的《提存公证规则》中则有更详细的规定。第三个问题则是由《提存公证规则》加以规定的。虽然我国学者之通说以提存为私法上的特种契约,但我们认为,提存是一种需要共同参与的行政行为,由此产生的提存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保管关系(oeffentlich-rechtliches Verwahrungsverhaltnis)[12],理由如下:
第一,保管关系非必由保管合同而生。无论人们对提存的性质持怎样不同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提存是一种保管关系。保管关系在公法上、私法上都普遍存在,前者如司法机关对犯罪工具、赃物的保管,后者如质权人对质物的保管,公司对无记名股东交存股票的保管等。所以有保管合同固然有保管关系存在,但反过来,有保管关系存在,则非必为私法上的关系,亦非必由私法上的保管合同所产生。提存关系即为适例。
第二,提存机关是公法上的主体。在我国,提存公证由债务履行地的公证处管辖,倘若在债务履行地申办提存公证有困难的,可以由债务人住所地的公证处管辖(《提存公证规则》第4条,以下简称《规则》)。公证处,即公证机关,是司法机关的一个部门,是对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依法予以公证,行使公证权的专门机关。在我国台湾,则是以地方法院所设的提存所来办理提存事务(台湾“提存法”第1条);在日本,则由法务局或者地方法务局或者法务大臣指定的办事处作为提存所(台湾“提存法”第1条);在德国,提存事务由初级法院(die Amtsgerichte)和司法机关出纳处(die Justizkassen)主管(见1937年3月10日《提存条例》dieHinterlegungsordnung第1条)。作为公法上之主体,提存机关接受提存,系基于公法上之义务,而不是以私法人之资格,依意思自治而任意为之。
第三,提存机关受理提存事务,虽收取一定费用,但其主要目的,非在藉此以营利,端在维护经济流转秩序,预防和减少债务纠纷(《提存公证规则》第1条),且以公之设备以充此任,于防止提存物之毁损灭失最为适当。
第四,提存关系之产生,非由于私法上之合意,而是基于共同参与之行政行为(如同私法上之要相对人的单方行为)。提存机关收取提存物并做出处分(Verfuegung),因而也就是通过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建立了提存关系。这一行政行为包括提存人之申请(ein Antragdes Hinterlegers),以及提存机关对此申请之准许。[13]《提存公证规则》规定,提存申请人应填写公证申请表,提交相关材料(《规则》第9条)。公证处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之决定(《规则》第10条),倘若决定受理,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提存(《规则》第12~13条)。此处之申请,不是私法上的意思表示,而是公法上参与人的意思表示,缺少申请或申请在内容上与行政行为不一致时,该提存之决定是违法的[14].提存机关乃是应提存人之申请而为决定,正是从这一角度上看,提存之行为乃为需共同参与之行政行为(和企业法人设立登记、公司设立登记相类似),与狭义的单方行政行为不同。
第五,基于提存机关之处分建立公法上的保管关系,由于此一关系,不仅产生了提存人的权利,也产生了债权人对于提存机关要求交出提存物之直接权利(ein unmittelbares Recht gegen die Hinterlegungsstelle aufHerausgabe)。因此,提存关系与利益第三人之契约(Vertrag zugunst eines Dritten)甚为相似[15],但切不可因有此等权利之创设,遽认其为私法上之关系。盖以行政行为而授予相对人以利益,或为相对人设定负担,或者令相对人同时有负担或得益,甚或涉及第三人者,所在多有,非为私法上法律行为所得而专也[16].提存行为乃有涉他效力之公法上行为。
第六,提存人与提存机关之间,并无意思表示之合意,其间之纠纷纯依公法上程序解决,而非依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提存公证规则》第10条规定,公证处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不予受理的,公证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不予受理不服的复议程序。第13条规定,对不符合规定的,公证处应当拒绝办理提存公证,并告知申请人对拒绝公证不服的复议程序。倘若提存人与公证处间为私法上之契约关系,则因该契约发生之争议,按理应得遵循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事实上,在我国,则是以行政复议程序解决,足证公证处与提存人间系公法上法律关系。而且,也不能把提存等同于有公法上目的之私法行为,依照所谓的二阶段理论(Zweistufentheorie),就决定缔结私法契约的行政行为,与以私法形态缔结的契约,分别处理[17].盖于二阶段理论中所要求(第二阶段中)的私法形态的契约行为在提存中压根儿就不存在。
第七,债权人因提存人之提存,可以随时或于其向债务人为对待给付或者提供担保后,领取提存物(《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但债权人申请领取的程序仍须依照提存公证规则之规定为之。对符合法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给付条件,而公证处拒绝给付的,由其主管的司法行政机关责令限期给付(《规则》第28条第1款前句)。因此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公证处负有赔偿责任(《规则》第28条第1款后句)。此为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对债权人构成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为《民法通则》第121条之特别规定也。
综上,从提存机关之性质、提存机关义务之性质、提存之目的、提存关系发生之原因、对提存纠纷适用之程序等方面来看,提存关系的确为公法上的保管关系,且有涉他效力[18].
值得注意的是,必须把提存关系同债务人(提存人)与债权人间的具体的(或广义的)债的关系,乃至于其间抽象的(或狭义的)债的关系区别开来,不可混淆(参见图1)。前者为公法上法律关系,后者纯为私法上之关系。如果没有债的关系便不至于要发生提存关系。提存关系对抽象的债的关系常生影响,使债务人之债务消灭,但非必使具体的债的关系同时消灭。此种影响是因以提存作为狭义的债的关系中债务清偿之代用,而将彼此联系起来的。提存关系中债权人领取提存物或提存人取回权之消灭,对于狭义的债的关系中债务、债权之消灭而言,乃为法律事实,且无须债权人于领取或提存人抛弃取回权时有消灭债务、债权之意思,故为事实行为。如果承认提存人不限于债务人,有代位清偿权的第三人亦得提存人,则第三人之提存人与债权人、债务人间更有因代为清偿而形成之私法上关系。因提存而使债务消灭,犹如依法院判决或强制执行而使债务消灭一样,但不可因此谓债务关系为公法上之诉讼关系,亦不可谓诉讼关系或执行关系为私法关系。其理殆属相同。[19]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谷
三、清偿提存之要件
提存要求必须具备适于提存之物及提存原因。
(一)关于适于提存之物
我国《合同法》虽也以标的物适于提存为要件,然而只是从消极方面规定“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可以提存拍卖或变卖后之价款 (《合同法》第101条第2款)。法条既明定限于“标的物”,那么以行为为标的之债,有不需协力者,有虽需协力而性质上无从为保管者,均无提存之可能。《提存公证规则》第7条则自正面积极规定:(1)货币,(2)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3)贵重物品,(4)担保物(金)或其替代物,(5)其他适宜提存的标的物,除(4)外,皆为适于清偿提存之标的物。
适于提存之标的物,是否包括“不动产”?[20]有主张提存物应限于动产者,盖以交付不动产之义务人,得因抛弃占有而免其债务,毋庸更为提存。且提存须将给付物提交于提存机关以为保管,而不动产事实上不能交付于提存机关,于保管上殊为不利,是为“否定说”。有主张不动产亦得为提存者,盖以抛弃占有只得于债权人迟延后方得为之,若因不能确知孰为债权人而难为给付者,债权人虽未构成受领迟延,事实上仍有适用提存之必要。如认为不动产不得为提存,于债务人之保护仍有不周,且不动产亦非全无保管之方法,被保管之物体,亦不必皆须提交于提存机关,是为“肯定说”。[21]
立法例上,关于提存之标的物有限于动产者,如《德国民法典》第372条、383条;有兼及于不动产者,如《日本民法典》第495条规定:“供托要于债务履行地之供托所为之”(第1款)。“凡供托所,法令苟别无规定,则裁判所要因辩济者(按:清偿人)之请求,为之指定供托所,及选任供托物之保管者”(第2款)。梅谦次郎氏解释道:“……于本条第二项,裁判所当指定供托所,且选任供托物之保管者焉。而如不动产,本来不能移转,故其场所,毋庸指定,惟定其保管者即可。加之裁判所即以债务者为新设之保管者,固亦无妨。于此时,债务者已离为债务者之地位,更占保管者之地位,由是免其义务之后,与他人之保管其物者无异。”[22]按照梅氏的解释,甚至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债务人也可能成为不动产提存物的保管人。我国旧民法学者多取后说,当今学者则以前说为通说[23].我们认为应采肯定说,理由如下:
第一,纵在承认“占有抛弃”的法制下,因其仅于债权人迟延后方得为之,于不知孰为债权人时即无法运用;且“占有之抛弃”,虽使债务人得以免责,然抛弃使第三人得先占其物体或徒生暴殄天物之结果,不独于债权人一身为不利,而自国民经济之观点视之,亦应为损失,故亦非必为可推崇之事。
第二,我现行法上,并无“占有抛弃”制度,对给付不动产之债务进行救济,似采“不动产可提存”之说为宜。
第三,对不能提交公证处的提存物,公证处应当派公证员到现场实地验收 (《规则》第14条第1款)。经过验收的提存标的物,公证处应当采用存封、委托代管等必要的保管措施(《规则》第14条第4款)。我国《提存公证规则》的相关规定与《日本民法》第495条第2款,功能上相同,即对不动产提存设定了保管的方法。
第四,《提存公证规则》第15条,对不动产之估价,并非作为自助拍卖之预备,因为需要债务人自助拍卖的物品,限于“易腐易烂易燃易爆”等物品(《规则》第14条第5款),不动产自不在其中。何况《规则》第22条第4款所谓“提存的不动产”云云,甚为明确,将不动产排除在适于提存的标的物之外,自无理由。不过,不动产提存,非但实践中较为少见,其意义与动产之提存,不可相提并论,此则可断言。
(二)提存之原因
我国现行法上关于提存原因之规定主要规定于《合同法》第101条第1款以及《提存公证规则》第5条中。而这方面的规定存在的问题有三:一是逻辑上混乱;二是规定的原因不充分;三是措辞不尽准确。
《合同法》第10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二)债权人下落不明;(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提存公证规则》第5条则规定:“债务清偿期届至,有下列情形之一使债务人无法按时给付的,公证处可以根据债务人申请依法办理提存:(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受领债之标的的;(二)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三)债权人不清、地址不详,或失踪、死亡(消灭),其继承人不清,或无行为能力其法定人不清的。”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合同法》与《提存公证规则》在提存原因的规定上有下列差别;
①《合同法》未明确是否要求债务届至清偿期,《规则》明确要求债务必须届至清偿期;
②除了共同规定了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作为原因外,《规则》还规定了“债权人延迟受领”;
③《规则》中规定于“往取债务”中,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亦作为提存原因,《合同法》则未规定;
④《合同法》中只要求“债权人下落不明”,而《规则》中则要求“债权人失踪”;
⑤除了以债权人的死亡,且未确定继承人作为共通性规定外,对于债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于消灭时,其权利继受人不清的,规则也做出了规定;
⑥除了以债权人丧失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人未确定作为共通性规定外,《规则》还就债权人不清(死亡或消灭之外)、地址不详做出规定;
⑦《合同法》有一兜底条款“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故凡规则中明定而合同法中未列举的,皆可入于此条款涵摄之下。
兹更详言之。第一,作为提存之原因,是否以债务届至清偿期为必要?从提存制度目的以观,原在债权人受领迟延(Gl?ubigerverzug)致债务人无法清偿时,为另辟一替代途径,使之得以免除债务,故应以“债务已届清偿期”为必要。其后许多国家的立法虽然将提存之适用,更扩张及于因债权人本身的其他原因,或非因债务人之过失而不能确知谁是债权人,以致债务人不能或无把握履行债务的情形。但考虑到提存可能对债权人带来的不利,如风险移转、提存费用之负担等,加之在确定清偿期届至前,债务人本来就有义务保管给付标的物,故从利益衡量角度言,原则上自以不许其期前提存为当。况且,期前虽不能确知孰为债权人,但只要清偿期届至时能够或可能明确,则亦无提存之必要。又,我国《合同法》第71条明定,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期前履行债务,除非债权人这样做无合法利益。[24]既然提前履行,债权人可以拒绝,那么期前所为之提存,当更可拒绝。从而,现实中纵有于清偿期期前为提存者,至少于债权人拒绝领取时,其不能发生提存之效力[25],当无疑义。然而,《合同法》第10条所说:“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从字面上看,其不限于“债务届清偿期”后之拒绝受领,当还包括期前债权人之“拒绝受领”。对此应为限制性解释。
第二,《规则》第5条第1项中,“债权人延迟受领”,依一般的见解,当包括债务届清偿期,债务人为给付之提出,而债权人不能受领,或毫无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而拒绝受领两种情形。但《规则》同条项中将“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与“债权人延迟受领”相并列,从而此所谓债权人延迟受领当为狭义,仅指债权人不能受领而言。
第三,《合同法》中所谓“债权人下落不明”,和规则中所谓“债权人失踪”,其共同之处在于,债权人之为谁人,乃是明确的,惟不知其所在,从而不能对之为清偿。而且此处“下落不明”和“失踪”亦应做同一把握,即指债权人所处的一种状态。“下落不明”是指公民(自然人)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法人之地址住所变化则不包括在内:“失踪”也指下落不明,不宜把“债权人失踪”解为“权人为失踪人”,盖苟有下落不明即为足矣,至其人失踪多长时间,是否有利害关系人申请失踪宣告或死亡宣告,在所不问。
必须债权人下落不明,致使债务人无法为给付,故倘若债权人虽下落不明,但其人明确,则不得为提存。例如未成年之债权人某甲失踪,而其父母(法定人)系为明确,债务人本来就应对其父母为给付,方能产生清偿之效果,自不能为提存。纵成年债权人失踪,倘业经宣告其失踪或死亡,从而其债权应由其代管人管理或由其继承人继承者,亦不必为提存。
另外,债权人下落不明应系基于其自身之原因,而非基于可归责于债务人之原因所致。例如,债务人所雇佣的人或其辅助人等将债权人绑架或藏匿,致使下落不明,即属于债务人支配范围内之事由所致,这种风险应由债务人自负,不得为提存。纵为提存,亦无其效力。债权人,不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其地址不清 (《规则》第5条第3项),亦为债权人明确,惟因其自身原因不知其所在,从而债务人无以对之为给付,与债务人下落不明,属同一类型。
债权人丧失行为能力,而其监护人(或法定人)未确定时,债权人明确,惟因债权人方面之原因,无从对其人为给付,亦属同一类型。
第四,债权人死亡,其继承人未确定,属于债权人不清。基于此外之原因,亦有债权人之为何人不明确的,如造成他人所有物之损害,应为赔偿者,却不知物之谁属是,此亦有为提存之必要。对于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虽无死亡,然得消灭,而其权利,通常有清算组代为收取。然在营业合并或分立,无须经过清算而生组织上之变更时,往往亦会使债务人不知谁为债权人。诸如此类之债权人不清,并非客观上一般人皆不知债权人是谁,惟债务人一己主观上不知债权人为谁。因此,倘债务人略加注意,即可探明,终因其过失而未能确知孰为债权人,则不得以提存相济。此德、瑞、日民法所共认者也。[26]
综合合同法及规则中所列举之提存原因,可以按照债务人主观上是否知道孰为债权人分为两大类[27],示之如图2:
对我国现行法上(《合同法》,《提存公证规则》)的提存原因之类型化,前已述及。值得注意的是,提存制度在《欧洲合同法原则》(Principlesof European Contract Law,以下简称PECL)中被类型化为两类;未被受领的财产(propertynot accepted)和未被受领的金钱(money not accepted),分别规定于7—110条和 7—111条。
PECL 7—110条规定:(1)因为另一方当事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词芰旎蛉亟鹎酝獾挠刑逦铮τ谡加懈糜刑逦镒刺囊环降笔氯耍匦氩扇『侠泶胧┍;げ⒈4娓梦锲贰#?)处于占有状态的一方当事人可以消灭其交付或返还义务:①通过将该物品以合理的条件以另一方当事人的名义提存于第三人处,并以此通知另一方当事人;或者②通过通知另一方之后,以合理条件出售该物品,并以纯收益支付于另一方当事人。(3)但是,如果该物品易于腐烂,或其保存需费过巨,则该方当事人须采取合理措施处分该物品。通过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纯收益的方式,它可以消灭其交付或返还之义务。(4)继续占有的一方当事人,对任何合理发生的费用,有权获得补偿或从出售物品的纯收益中扣除。
第8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房屋和土地一并抵押的规定只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时的利益冲突,不是要强行扩张抵押权的效力。在因实现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一起拍卖,但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未约定的部分,抵押权人对未约定的部分不能优先受偿。关键词:抵押权效力、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合并抵押抵押权效力的范围取决于当事人设定抵押权的约定和登记。房屋和土地一并抵押的规定,只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时的利益冲突,不是要强行扩张抵押权的效力。在因实现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一起拍卖,但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未约定的部分,抵押权人对未约定的部分不能优先受偿。
一、合并抵押不成立法定抵押权
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一并抵押的,并不成立法定抵押权。所谓法定抵押权,是指不需要当事人设定抵押的合意,也不需办理抵押登记,而根据法律规定直接发生抵押效力的抵押权。观诸世界各国的抵押权制度,法定抵押权的情形主要有下列几种:
1、公法性质的法定抵押权。如瑞士《民法典》第836条规定,基于公法或其他对土地所有人有普遍约束力的,并由各地州法规定的不动产抵押权,除另有规定外,虽未登记,仍生效力。此类抵押权是为了确保国家税收等权利的实现。
2、基于和抵押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法定抵押权。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121条规定,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未成年人与受监护的成年人对监护人或者法定管理人的财产,国家、省、市镇行政公共机构对税收人员和会计人员的财产等享有法定抵押权。这类法定抵押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夫妻一方,未成年人或者国家、省、市镇等的合法效益,确保其对夫妻另一方、监护人、特殊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债权的实现。因为在上述主体关系中,夫妻另一方、监护人、税收人员或者会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另一方的财产,存在利用这种优势侵吞另一方利益从而增加自己财产的极大风险与可能,所以,法律有必要给与特殊的保护。
法定抵押权的目的在于对特殊债权给予特别保护,除特别的公法上的债权外,其原因大多在于,该债权的产生是抵押物保值、增值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该债权,就不会有抵押物的现存价值,所以,如果不规定法定抵押权,就会导致特定债权人的财产充当了其他债权人的担保,从而破坏了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且,也不利于激发债权人对抵押物保值、增值的积极性。所以,法律规定了法定抵押权,允许该债权人不经合意、不需登记,就可以获得抵押权。但是,我国土地和房屋一并抵押的规定,却显然与上述两种情况无关,它解决的不是债权和抵押物的价值的关系问题,而是土地和土地之上建筑物的关系问题。
二、房地合并抵押绝对化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土地和地上建筑关系的民法模式
关于土地和土地上建筑的关系,近代民法大致有两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模式认为,土地与建筑物是一个物,建筑物是土地的重要成分。德国《民法典》第94条规定,附着于土地上的物,特别是建筑物,以及与土地尚未分离的出产物,属于土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土地和地上物分别登记,分别流转,以至出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以日本为代表的立法模式认为,建筑物和土地是两个独立的不动产。我国台湾地区也是这种模式。由于土地和房屋在法律上属于不同的物,但事实上二者又无法分离,建筑物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土地,当土地和房屋所有权不能归属于一人时,就只能通过地上权的关系来处理,也就是通过土地所有人为建筑物所有人设定地上权的方式解决建筑物的占地问题。在当事人没有达成约定的情况下,视为已有法定地上权的设定。如我国台湾民法典第876条规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物,同属于一人所有,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为抵押者,于抵押物拍卖时,视为已有地上权之设定,其地租由当事人协议定之,协议不谐时,须申请法院定之。
2、我国采取的民法模式
我国大陆和日本及我国台湾相同,坚持认为土地和地上的房屋属于不同的物。由于我国坚持土地公有制,而房屋却一直是私有财产,土地和房屋的分离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土地公有制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坚持房屋与土地的分离,对于实现房屋的流转,维护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并且,这种土地和房屋的分离,随着房屋和土地的分别登记日益得到强化。但是,事实上二者又无法分离,如果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不能归属于一人时,就需要像台湾那样通过法定的土地权利来解决房屋所有人和土地使用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我国不但没有规定法定地上权,反而为了回避权利冲突,规定了房、地一起抵押的做汉。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3、我国采取立法的原因
立法者为什么采取这种做法,而不是法定地上权的做法来解决土地和房屋权利的冲突,不得而知。我认为主是为了方便司法。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土地和房屋在自然上不可区分,所以当权利人将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转让或者抵押时,将它们一并转让或纳入抵押,这对司法者来说操作最为简便易行。但是,这种简单的做法恐怕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当时立法者乃至整个学界对法定地上权制度缺乏深入的研究。1990年《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颁布实施的时候,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刚刚开始有限度的流转,民法研究非常肤浅,法定地上权的精湛设计对大多人来说闻所未闻。
2)、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私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私有的房屋是建立在土地使用权(类似传统的地上权)基础之上的,而土地使用权年限相比来说较短,如果在土地使用权上再设定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权,恐怕成本过高,而且,理论上也存在很多难点。
3)、当时土地使用权制度主要是解决土地的有偿使用问题,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更多的是限制。使用权流转导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所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房地合并抵押的简单划一的做法是最方便的。
4、盲目采取房地合并抵押产生的后果
这种做法显然只是掩盖了矛盾,而不是解决了矛盾。一方面,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离的现实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法律不是为此现实提供解决办法,而是不顾这一现实,采取将土地和房屋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这就造成了制度内部的逻辑紊乱。随着新建房屋的不断增多,随着房屋流转的日益频繁,我国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冲突也就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我国房地分别登记的情况下,再盲目地绝对坚持房地合并抵押的做法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无法确定土地权利抵押权设定的时间和顺位,对交易安全造成危害。房地合并抵押并没有确定房屋抵押登记或者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哪一个要优先进行,导致了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地上房屋随之抵押;其后,房屋所有权抵押的,其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随之抵押。由于两次抵押是在不同的登记机关办理的,都属于第一顺位的抵押登记。但是,二者实际上又是重复的。根据一般的登记法理,登记顺位是由纳入登记簿的先后决定的,由于这两个抵押权是分别登记在不同的登记簿上,所以,在它们之间也就不存在谁是第一顺位的问题。两次登记的当事人都有主张自己是第一顺位的理由。所以,确定谁是第一顺位的,都对另一方不公平。
2)、给债务人利用重复担保进行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实中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将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后,在房屋建成后再到房产部门办理抵押贷款。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但是,房屋抵押时,其价值的计算并没有除去已被抵押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因此,在土地使用权部分是重复抵押的,这很显然违反了《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即使我们从学理出发允许重复抵押,但是,重复抵押的进行,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只有在前抵押顺位的抵押权人获得优先受偿后才能就其余额优先受偿。所以,一般来说,考虑到后顺位的抵押权实现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前顺位的抵押权的风险,后顺位的抵押权人会提高对债务人的贷款利率,这就要求其能够明确的知晓自己作为后顺位的地位,从而注意自己的风险,适当提高贷款的利率。但是,在我国现有分别登记的情形下,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却无从知晓自己的风险。债务人没有支付重复抵押的代价,却获得了重复抵押的收益,这对后顺位抵押权人是不公平的。债务人的做法也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
3)、在当事人明确约定只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仍然强行规定房地合并抵押的做法,大大限制了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削弱了当事人的物权合意在物权变动中的作用,不利于当事人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交易生活,分配自己的交易风险。众所周知,抵押的范围是和债务人的代价紧密相关的,抵押人仅仅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还是以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一并抵押来担保债务,和债务的内容,尤其和债务人支付的利息等是密切相关的。担保物的价值越高,债权人的风险越小,主债务人承担的代价相应越小。反之,担保物的价值越低,债权人的风险越大,主债务人的代价相应增加。所以,抵押物的范围和价值是和债权人的风险、债务人的代价成正比的。在债务人的代价未变的情况下,片面扩张抵押物的范围,增加抵押物的价值,减少债权人的风险,对债务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角度来讲,对当事人未设定抵押的部分,如果承认其也属于抵押范围,是不合适的。
三、片面要求房地合并抵押,是对抵押和转让的混淆
上文已经提到,我国关于房地合并抵押的规定,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主体导致的矛盾。但是,只有在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转让时,包括当事人约定转让以及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法院为了实现抵押权而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进行的转让,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转让和抵押毕竟不同。转让是现实的转让,而抵押只是以抵押物充当债权的担保,如果到期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就对抵押物实行拍卖,以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到期债务人履行了债务,抵押权作为从属性权利,也就归于消灭,抵押物所有人可以要求注销抵押权登记。也就是说,抵押权的设定只是意味着在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变卖抵押物以实现抵押权的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权利的转移。在没有转移的情况下,所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易其主体的问题就不会发生。所以,即使我们承认房地合并转移的必要性,也并不能以此作为合并抵押的理由。更何况,房地合并转移的合理性还有待于商榷呢?
四、当事人仅仅约定就房屋或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强行规定抵押权效力扩张到未约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是对抵押权性质的误解
抵押权是一种价值权利,它所支配的是抵押物的价值。即使我们承认实现抵押权时应将土地和房屋一并拍卖,也并不能得出抵押权人可以就全部的变卖价值优先受偿。抵押物价值的实现和抵押物的价值绝对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抵押物的价值的变现需要同时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就可以违背当事人的约定,任意扩张抵押权可以支配的抵押物价值的范围。在这方面,土地上已经建有房屋但是仅仅约定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又建有房屋的处理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二者设定抵押权的合意都只是针对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二者都牵涉抵押权实现时如何避免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异其主体的问题。根据《担保法》第三是五条的规定,城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物。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单独以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也应参照此规定办理。也就是说抵押权的范围仍然是单独设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在实现抵押权,需要拍卖土地使用权时,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一起拍卖,但对未设定抵押权的部分,抵押权人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例如:当事人甲用自己建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以担保丙的债务为目的为债权人乙设定抵押权,甲乙二人约定仅就土地使用权部分设定抵押,并且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登记。现在债务人丙到期无法清偿债务,抵押权人乙主张。尽管房屋所有权部分没有约定,也没有办理登记,但根据法律规定,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该一并抵押,抵押权人应该就拍卖所得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总和优先受偿。而抵押人则认为,抵押权的范围只是针对约定抵押并办理登记的土地使用权部分,对房屋所有权,虽然可以一同拍卖,但是债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上述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决原告乙“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该一并抵押,抵押权人应该就拍卖所得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总和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五、当事人仅仅约定就房屋或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强行规定抵押权扩张到未约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是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有关房地合并转让、抵押的规范性质的误解
1、我国对于房地抵押的法律规定
检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前文已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没有涉及抵押问题,而仅仅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所以,适用这一条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另外两条所规定的情形,只是针对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情形。房屋所有权人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的,因为房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土地之上,必须有一定的土地权利基础,不能是空中楼阁,所以,为了简化房地产交易关系,法律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一并转让和抵押。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转让、抵押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必须将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和转让。
2、我国房地抵押、转让的法律分析
1)、按照法理来说,抵押、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都有一个单独抵押、转让还是房地一起抵押、转让的问题,为什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只规定房屋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猜得到。不过《担保法》此条所处的位置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解释。一般的说,条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规范总要有一个规范群,立法者不会无缘无故的组成一个规范群,规范群内部的逻辑联系恰恰可以窥出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所以,在民法解释学上,体系解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有意思的是,如果仅仅单独设定房屋或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也随之抵押的话,就是抵押权效力的扩张。本条应该规定在《担保法》第三章第三条抵押的效力一节,方才合乎逻辑。但是,本条并没放在此处,而是放在了抵押和抵押物那一节,在这一节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抵押权扩张的问题,而是什么情况下,哪些财产可以充当抵押物的问题。《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本条第二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衡量这两款,第二款仅仅规定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言外之意,对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允许抵押。但是,再回来参考第一款,如果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抵押的,那么,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就应该同时抵押。这在第三款的印证下更加鲜明。第三款针对集体乡镇村企业的体积土地使用权问题做出了特别规定,不允许单独抵押,但是,如果以企业建筑物抵押的,占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所以,我认为,主张《担保法》的本条规定扩张了抵押权的效力,可能是一个误读,本条的目的或许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划拨国有土地地用权或者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或者流转问题,而不是在于扩张抵押权的效力。
2)、房屋土地的同时抵押是不是《担保法》的强制性规定,大可怀疑。《担保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根据本条的规定,首先,房屋和土地的合并转让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引导性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特约改变这一规定。改变的方法就是为房屋所有人设定土地的承租权,使他人的房屋所有权建立在对土地使用权人的承租权基础之上,从而利用承租权机制解决房屋的土地权属问题。其次,本条明确规定了,即使为了避免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分属于不同主体所导致的矛盾,要求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同时拍卖,也并不因此就导致抵押权效力的扩张,抵押权效力仍然局限于抵押权设定的范围,对未约定抵押的部分,抵押权人并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因此,房屋和土地一并抵押的规定只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时的利益冲突,不是要强行扩张抵押权的效力。在因实现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一起拍卖,但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未约定的部分,抵押权人对未约定的部分不能优先受偿。参考文献资料:
1、新编《房地产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
第9篇:民法典保护未成年条例范文
【关键词】妊娠代孕 亲子关系 监护权人 工辅助生殖
代孕是女性明知分娩后应当将孩子交付委托代孕方而孕育孩子的行为,是辅助生殖领域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②近年来,伴随着不孕不育率在我国的日渐升高,代孕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灰色产业。代孕应否合法化以及如何处理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问题,成为人们探讨的热点问题。代孕的特殊之处在于,代孕的合法化与否并不能成为探讨和解决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的前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代孕的特别之处在于,法律即使否定了协议的效力,但仍要处理抚养权的归属问题。”即便法律完全禁止了代孕,也不得不直面黑市代孕引发的孩子身份及抚养问题。基于此,探讨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问题,以便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使其免受或少受非法代孕带来的困扰,便成为本文的主旨。
在医学上,代孕依据其受孕所需要的卵子来源不同可以被划分为传统代孕(或称部分代孕)与妊娠代孕(或称宿主代孕、完全代孕)两类。传统代孕即由代孕者自己提供卵子与委托代孕方提供的结合而进行的代孕;而妊娠代孕则是仅利用代母子宫的妊娠功能,而由委托方提供与卵子或胚胎而进行的代孕。在传统代孕中,委托一方中的男性为孩子的父亲,而代孕母亲则既是孩子的生母,又是孩子生物W意义上的母亲。由于这种代孕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简单,所生的子女监护权问题争议相对较少。所以,本文将集中讨论妊娠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问题,对传统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不加涉及。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则代孕都特指妊娠代孕。
一、妊娠代孕所生子女法律上之母亲的学术争议
理论上,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学地确定代孕所生子女在法律上的父母,因为一旦其法律上的父母得以确定,则其监护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其法律上的父母享有监护权。实践中,难点集中在对代孕所生子女之法律母亲的认定上。因为从各国代孕的医学临床实践来看,代孕的发生绝大多数是由于代孕委托一方中的妻子失去生育能力(如没有子宫或不再产生卵子等),而丈夫一方则通常能够提供健康的。这使得代孕所生子女之父亲的认定相对比较容易,而对于其母亲的认定则相对复杂。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于代孕所生子女母亲的认定问题一直争议极大。
在传统代孕中,母亲的概念没有受到挑战,因为代孕母亲是孩子生母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但是在妊娠代孕中,三类潜在的女性可能会主张亲权:代孕母亲、具有基因联系的捐卵者以及意向母亲(the intended mother)。那么,究竟谁应当成为代孕所生子女法律上的母亲而拥有对他/她的监护权呢?理论上主要有分娩说、血缘说、意愿说以及子女最佳利益说四种学说。
(一)分娩说
分娩说立足于“分娩者为母”的传统伦理与法律立场,主张任何妊娠并生育孩子的女性为孩子法律上的母亲,而不论其是否也是孩子基因学上的母亲。该观点认为,在代孕过程中,妊娠代母对于生殖过程的付出要比作为捐卵者的不育的妻子更多,面临更多危险,投入更多感情。因此,妊娠母亲有权拥有主张孩子应归属自己的机会。从医学上来说,代孕作为人类生殖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毫无风险与损害的,相反,作为人类的一种生育方式,代孕从其医学操作之始就已经为代孕母亲的身心健康注入了风险或损害,如身体上的变化、产痛、宫外孕风险、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产后、抑郁等。不仅如此,代孕过程中,代孕母亲还要为胎儿牺牲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而造成对其自身自由的削减。就此而言,代孕实际上是代孕母亲冒着生命健康与心理错落以及时间、精力等多方面的风险或损失为他人生育孩子的过程。代孕母亲是真正把孩子带到世界上的人,她更应当被认定为孩子法律上的母亲。分娩说是婚姻家庭法领域认定亲子关系最为正统的一项原则,但伴随着代孕尤其是妊娠代孕的不断出现,这一原则已越来越受到挑战。因为从孩子自身的利益考量,分娩说未必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尤其是在代孕母亲并没有抚养孩子主观意愿的情况下。
(二)血缘说
血缘说,通常也被称为基因说或血统说。该说认为,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是其法律上的父母,血缘关系亦即基因来源应当作为确定亲权关系的基础。以此为基点,与代孕所生孩子有基因关联的父母是其法律父母。该说的理论支柱在于,血缘是维系家庭成员亲情最稳定、最有效的手段,是家庭延续的纽带,以血缘为依据来确定代孕所生子女法律上的父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更符合人类繁衍的本质和人伦道德情感,更契合传统的“传宗接代”的思想。血缘说认为,为代孕提供卵子的人(有时是委托一方的妻子,而有时则是捐卵者)才应当被认为是代孕所生孩子法律上的母亲。血缘说奉行血缘主义,比较符合人之常情,但在委托夫妻中有一方无法提供生殖细胞的情况下则容易引发委托人与精卵捐献者之间对孩子亲权的冲突,从而背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目的。
(三)意愿说
意愿说,也称意思说。该说认为,应该根据当事人是否有成为父母的意愿来确定代孕所生子女的父母。依据当事人意愿来判定谁是孩子法律上的母亲,这不仅是意思自治的内在要求,而且也不违背公序良俗。而法律尊重当事人愿意成为代孕子女监护人的庄严承诺,之所以不违反公序良俗,不仅仅在于这种安排是对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更在于认可这一承诺,使得孩子被纳入到了一个愿意对其一生负责的家庭之中。但该说将“意愿”或“意思”作为确定代孕所生子亲权的基本考量,使得代孕所生子女完全成为可以由意愿或意思来自由决定和支配的合同标的,不仅增加了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基础的亲子关系之不确定性,且有贬低人类人格尊严的嫌疑;不仅如此,孩子出生后当事人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将手术前的意愿作为未来孩子归属和权利义务的依据,不容许妊娠母亲对所生孩子表达爱与奉献,也难免失之武断。
(四)子女最佳利益说
子女最佳利益说是为弥补传统的分娩说、血缘说以及甚嚣尘上的意愿说之不足而出现的一种认定代孕所生子女亲子关系,从而决定其监护权的学说。该观点主张,应当以子女利益最大化作为标准来决定代孕所生子女的亲权,在涉事相关当事人中,哪一方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最有利,则该方就应当被认定为孩子法律上的父母。在我国首例代孕监护权纠纷案的二审中,法院判决体现的就是维护子女最佳利益的精神。子女最佳利益标准产生于孩子监护权纠纷并主要强调什么对孩子而不是对他/她的父母最有利这样一个待解决的问题。②该原则之所以在各国立法中被纷纷确立并成为各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家庭法的基石性原则,除了子女作为未成年人是家庭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这一层原因外,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未成年子女是所涉法律关系中最为弱势的群体,而法律的核心使命就在于保护弱势群体以实现社会公平。在确定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方面,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合乎法律机理、体现社会公正,从而更契合立法发展方向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却不宜成为确定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的立法标准,而只宜作为适用于司法实践中的一项标准来加以衡平,且该标准本身也存在先天不足。原因在于,该标准只有在父母都确定的情况下才有适用的余地,而且完整稳定的家庭对子女身心健康极为重要,孕母和受术之夫并无婚姻关系,该标准将子女置于破碎的关系中考虑子女最佳利益,无疑是自相矛盾的。
二、妊娠代孕所生子女法律上之母亲的域外法律实践
就目前来看,各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多数国家支持“分娩为母”的基本原则,即“生下孩子的人即便与孩子没有基因联系是孩子的法定母亲”。但有些国家和地区则允许司法实践中加以灵活变通。
(一)美国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的法律规定
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没有关于代孕的法律或法令,以致有人戏称“美国规制饲养狗、猫、鱼、奇异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法律比规制用于造人的有关代孕技术与生殖技术的法律多”。但也有一些州颁布了涉及代孕的法律或法令。有些州完全禁止代孕,如华盛顿州、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纽约州等;有些州开放代孕,如弗吉尼州、俄亥俄州等。正因如此,各州对于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之亲子关系的确定问题做法不一。例如,新泽西州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拒绝执行付费的代孕协议,完全以孩子的最佳利益为基础来决定亲子关系;采取类似新泽西州立场的州还有肯塔基、路易斯安那、纽约、北卡罗来纳、俄勒冈以及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州的判例法中则包含了以代孕合同当事方成为父母的意愿为基础来决定亲子关系的诸多代孕争议。在1993年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审结的Johnson v.Calvert一案中,法院最终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以意愿为基础的亲子关系标准。法院认为,在没有孩子的生物学母亲与生母时,则倾向于孩子出生并将他作为自己孩子抚养的女性就是孩子法律上的母亲。而犹他州的法律则规定,在依代孕协议产生的任何情况下,代孕母亲是孩子法律上的母亲,如果她已婚,则其丈夫是孩子的父亲。
就目前来看,在那些已经对代孕问题进行立法的州,除了严禁代孕的州以外,其余州大都规定代孕协议有效但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而阿肯色州是唯一一个完全执行代孕协议并在孩子出生之后即赋予一方或双方意向父母为法律上的父母资格的州。就此加以推断,美国尽管有些州在立法上承认了代孕,但其立法上对于代孕子女法律上母亲的认定是坚持“分娩为母”原则的,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出于更好地保护孩子利益这一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方面的考量,美国允许司法者依具体情况加以裁断。
(二)英国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的法律规定
英国2008年修订的《人类授精与胚胎法案》在亲子关系的认定上就延续了传统“分娩者为母”的法律标准,该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正在怀有或者因将胚胎或与卵子置于其体内致已怀有孩子的女性而非其他女性是孩子的母亲。而第36条则明确规定:任何代孕协议都不能被任何订立者强制执行,也不具有对抗任何订立者的效力。据此,“依据代孕协议生下孩子的人被认为是孩子法律上的母亲,并且将会以母亲的身份被登记在出生证明上”。⑤同时,该法规定,为了保护孩子的利益,孩子出生后,交由违法委托夫妻收养,使委托者通过收养的方式成为孩子法律上的父母,以确保代孕所生子女不会被遗弃或者争抢。
(三)欧洲大陆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的法律规定
在欧洲,各国对于代孕的合法性并没有统一的立场。但无论是承认代孕的国家,还是否认代孕甚至规定代孕构成犯罪的国家,其对于代孕所生孩子亲子关系的认定标准都近乎一致,即以分娩说为标准。在否定代孕合法性的欧盟成员国当中,代孕母亲作为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定母亲的法律规则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在分娩之后,代孕母亲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法律程序(比较常见的是收养程序)将亲权转移给意向母亲这一问题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尽管都禁止代孕,但却基本都持肯定性立场。而这更多的是基于孩子最佳利益的考量。
换言之,无论代孕是否合法,在代孕的事实已经产生而无法消除的情况下,其利益更需要法律保护。各国一般都基于孩子利益的考量,而在特定条件下(如代孕母亲无抚养孩子的意愿、失踪等),允许委托人通过特定法律程序获得孩子的亲权。例如,希腊经《医疗辅助生育3089号法案》修正后,其《民法典》第1463条及第1464条也对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规定,依据以上两条:一个人与其母亲及其亲属的关系依出生之事实来确定,与其父亲及其亲属的关系依其父母的婚姻关系或通过自愿承认或经由法院判决来确定。在孩子借助医学辅助生殖由代孕母亲生下的情况下,依第1458条规定的条件,获得法院允许的人应当被认定为其母亲。在孩子出生6个月内,该J定可以被一项争夺母亲亲权的法律诉讼撤销。意向母亲或代孕母亲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来争夺母亲的亲权,但后者须要有证据证明孩子与其有生物学上的联系。在法院做出承认该法律诉讼之不可撤销的判决之后,代孕母亲是孩子母亲的事实追溯到孩子实际出生时开始。显然,在希腊,尽管代孕是被允许的,但分娩为母的传统原则依旧是受到法律尊重和强化的。
德国是严禁代孕国家的典范,其立法明确禁止代孕,违者将被科以刑罚,其民法也否认代孕协议的效力,并坚持分娩为母的传统伦理与法律原则。为此,《德国民法典》第1591条规定:子女的母亲是生该子女的女子。但出于对代孕所生孩子利益的考虑,德国并不机械死板地要求代孕母亲承担对孩子的监护职责,而是允许委托代孕者在特定条件下通过收养的方式成为孩子法律上的母亲。《德国民法典》第1741条第1款规定:“……以收养为目的,以违反法律或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参与介绍或运送子女,或以此委托第三人,或为此而向第三人支付报酬的人,仅在收B对于子女最佳利益为必要时,始应收养子女。”为此,德国修订了《收养法协议》,规定代孕子女出生后交由委托夫妻收养,以保证代孕子女能够生活在正常家庭。
在比利时,现行的法律中并没有条款规制或禁止代孕协议。然而,基于儿童尤其是未出生的胎儿不能够被作为协议标的的公共政策之考量,立法者一般都认同代孕协议是违法的。在此情况下,代孕所生孩子的法定母亲自然是其作为其生母的代孕者。而在法国,由于代孕是被禁止的,因而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争夺母亲身份的情况,分娩者被认为是孩子法定的母亲。
(四)澳洲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的法律规定
澳大利亚在决定孩子的父母时并不考虑孩子出生地国家法律的做法,也不管任何其他签发出生记录国家法律的做法,除非该记录经由澳大利亚法律明确承认。一般认为,依据《家庭法法案》,该法案中的父母一词是指孕育和生下的人,即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或母亲,而不是仅仅照顾孩子的人。这意味着,基于《家庭法法案》立法目的考虑,父、母或许应当参考存在于出生时的事实决定。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法律中的母亲身份也是倾向于分娩说的。
在新西兰,2004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对代孕实行了二分规制。该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了代孕协议的地位以及对商业性代孕协议的禁止。该法规定:代孕协议并不必然非法,但是不具有支持或对抗任何人的强制执行力……。换言之,该法尽管未明确否认代孕协议的非法性,但却明确了代孕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地位。
(五)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代孕子女监护权的法律规定
日本并没有在代孕问题上出台法律,但其对于代孕的反对却是人所共知的。在亲子关系认定上,日本一直都坚持分娩为母原则,其执法部门及司法机关无论在处理2008年的曼吉案(Manji’s case)还是在裁断2009年的母亲代女儿生育案时,都始终立场一致地坚持分娩母亲为孩子法律上的母亲,拒绝承认委托母亲为孩子法律上母亲的地位。
香港《父母与子女条例》第9条规定了人工生殖子女之母亲身份的确定,即:(1)任何正在或曾经怀有子女的女子,若是因胚胎或和卵子被放置其体内而怀孕的,则除她以外,别无其他女子被视为该子女的母亲;(2)若任何子女因被领养而被视为只属其领养父母的子女,则在此程度上,第1款对其并不适用;(3)不论该女子在胚胎或和卵子放置于其体内时是否身在香港,第1款一概适用。
总体来看,各国对于代孕的法律立场并不一致,但在代孕所生孩子的法定母亲的确定这一问题上,则近乎一致。反对代孕的国家一直都坚持分娩为母的伦理与法律原则,以孩子的生母为其法律上的母亲;而支持代孕的国家尽管对代孕比较宽容,但通常也以代孕者为孩子法律上的母亲,委托父母如需获得孩子的亲权,一般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如收养)。
三、我国妊娠代孕所生子女亲子关系标准的立法建议
伴随着我国不孕不育率的提升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医学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代孕尤其是只借助代孕母亲子宫的妊娠代孕作为满足部分不孕不育者强烈需求的产物,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灰色产业。它不仅给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尖锐挑战,亦为我国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难题。而确定代孕所生子女法律上的父母(尤其是其母亲)以解决其监护权问题显然就在其中。今后,随着越来越多非法代孕在我国浮出水面,有关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方面的纷争会越来越多,而纷争的类型也会越来越复杂。在此情势下,科学地确立代孕所引致的亲子关系以更好地保护代孕所生孩子的利益,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对此,笔者以为,在立法上,我国应当采用分娩说,坚持分娩为母的伦理与法律原则。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基于权利义务相适应角度的考量。权利与义务相适应,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内在需要。而依据权利与义务相适应原则,在妊娠代孕中,尽管代孕母亲与孩子并不存在基因上的关联,却是在孩子成功孕育并顺利出生过程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人,是真正给予孩子生命的人,其承受着从怀孕到生产这一生育过程中包括产痛、宫外孕、产后忧郁等在内的全部风险或损害,并承担了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母亲所应当承担的全部伦理义务。赋予代孕母亲对其所生孩子的法律上母亲的资格与地位,使其有机会得以主张对于孩子的监护权,无疑是对其承担生育义务的一种补偿,是使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
其次,坚持分娩为母的原则有助于防范代孕泛滥。从行为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任何的行为都是禁而不止的,因此,伦理与法律存在的意义并不是要彻底消灭这些行为,而是要将这些行为控制在人类社会发展所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以维护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在此意义上,代孕作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也是禁而不止的。但为了尽可能防范其存在与泛滥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法律必须禁止代孕,或至少是限制代孕――正如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严厉禁止商业性代孕而对利他性代孕却相对容忍一样。而坚持分娩为母的法律原则,依据分娩说来确立代孕所生子女的亲权关系,则是尽可能减少代孕发生,控制代孕的必然选择。原因在于,对于代孕委托人来说,其之所以委托代孕无非是为了获得一个与自己有基因联系的孩子并取得孩子的监护权。而立法上坚持分娩为母则使其获得孩子监护权的可能性变得不具有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其必然会慎重考量委托代孕的不确定性结果,从而理性地决定是否委托代孕,以免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最后,分娩为母的原则没有被替代的绝对必要性。从法理上来说,身份法秩序是社会公共秩序的根本,民法中有关身份法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国家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基石,而鉴于身份制度安定性之需要,嫡亲父母子女法律地位的确定标准必须明确且统一。而作为人类确认亲权关系相对最为正统的一项伦理与法律原则,分娩为母的标准尽管受到了来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飞速发展的挑战,但依旧是目前世界各国在确定亲子关系上最值得依赖的一项原则。这一原则是人类婚姻家庭伦理与法律关系的基石性原则,在维护和保障人类伦理及法律秩序之稳定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已经在维护人类身份法秩序方面被证明是最为稳固和可靠的一项原则,客观上没有绝对的必要性来寻求其他替代标准,否则,就会使人类在确定亲子关系时陷入混乱,从而冲击人类身份法秩序的稳定,妨害社会的健康发展。
当然,基于对孩子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在无法查明孩子分娩母亲或其分娩母亲拒绝抚养孩子以致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酌情判由委托代孕一方中的女性通过收养的方式成为孩子法律上的母亲,以保证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监护,但这显然只能是对分娩为母这一传统伦理与法律原则的一种补充或衡平。换言之,在代孕母亲与意向母亲及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即捐卵者)对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代孕母亲应当是孩子当然之法律上的母亲;只有在各方对于孩子的监护权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司法者判令孩子的监护权归属委托人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