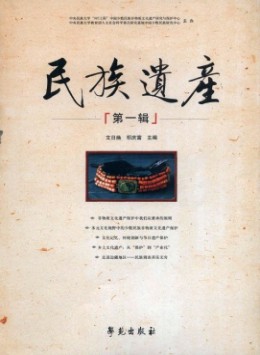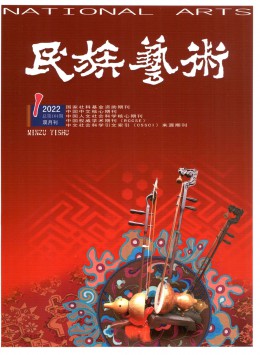民族管弦乐创作探讨

内容摘要: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创作呈现多元并存的文化景观,文章就“民族器乐剧”“主题性音乐创作”“新创作品的地域性特色”三种创作现象进行延展和探讨。一方面,阶段性记录民族管弦乐发展轨迹、追踪民族管弦乐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通过学理分析,理解当下,也指示出未来民族管弦乐创作可做可为的道路。
关键词:民族管弦乐;创作;民族器乐剧;主题性;地域性
民族管弦乐从最初的探索、创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扩充、改进,再到形成结构相对稳定、音效相对丰厚的民族管弦乐队,涉及到乐器形制、编制组合、艺术创新、价值建构、国家在场等一系列附加的文化表述,一直是学界值得深挖和探讨的话题。学者张萌在近年发表的《新时代民族管弦乐创作述略》[1]一文,系统地梳理了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历程。该文指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活跃,并呈现主题性创作繁荣、多元跨界、青年一代作曲家迅猛崛起等特征,展现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并存的文化景观。以面对这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景观,当然还应囊括更宽泛、更客观和更理性层面的思考。为此,笔者结合自己在该领域的实践,就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创作领域的三种现象进行延展,以期阶段性记录民族管弦乐发展轨迹、追踪民族管弦乐发展态势。
一、民族器乐剧
说起民族管弦乐的既定印象,定会和“音乐会”联系在一起,不论规模大小、编制繁简,抑或乐器摆位各异,演奏者在台上的固定席位演奏乐器,观众在台下欣赏乐曲,无可非议、习以为常,我们惯常的说法称作“听音乐”,而非“看音乐”。但近年有不少新创作品打破这种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固定模式,一种将剧情引入民乐的方式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创作者的视野。近年来,以“剧”冠名的作品不在少数,诸如民族乐剧《印象国乐》(2013)(图1)、民族乐剧《又见国乐》(2015)、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2017)(图2)、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2017)、多媒体民乐剧《九歌》(2018)、大型情景器乐剧《扬帆大湾梦》(2018)、跨界多媒体舞台剧《大禹治水》(2018)、音乐剧场《桃花扇》(2018)、大型器乐剧《韵魂弦梦》(2018),等等。这类新兴作品通过更多的表现手段为民乐做了宣传,许多剧目在更大范围内拓展了民乐的观众群和影响力。民族器乐剧的涌现,的确引领着各民族乐团开拓市场,但这类剧目在追逐潮流的同时,也把对这一现象的探讨推向了学术争鸣的风口浪尖。有观点认为,中央民族乐团邀请王潮歌导演创作的《印象国乐》是这一轮行业热潮的发轫,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在台上直面观众,讲述自己真实的故事,还音乐以人格特征,对民族管弦乐的提升大有裨益。该剧首演之后,音乐学家乔建中称其为国乐的新语体[2],显然,他对这一形式持“支持创新”和“鼓励探索”的态度。此后,亦有多位学者对这一创新进行肯定,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张振涛认为:“这些赋予器乐文化的立体感的现代气息,有效提升了国乐形象。”[3]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薛艺兵认为,这些作品表明艺术的创新没有定规,音乐的表演形式也需要不断创新[4]。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认为,这一系列创新之作无论还存在什么瑕疵,都能明显感受到其中无法遮蔽的闪光[5]。哈尔滨音乐学院院长杨燕迪在充分肯定这种“新语体模式”的同时,认为它还在成长中,相信会不断完善,也会继续发生变化[6]。创新必然会引起“保守派”与“改革派”的观念交锋,自然亦有许多业内人士持观望甚至批评态度,认为民乐应该固守阵地,传承几千年的文明应该谨慎对待。例如,文艺评论学者伦兵指出:“民乐‘器乐剧’究竟是新形式、货真价实还是玩概念、过度包装?这是目前‘民乐剧’演出尚未解决的问题,无疑也关系到民乐‘器乐剧’究竟能够走多远。”[7]学者刁艳认为音乐表演的动人之处“无关所谓表现形式的创新、无关你为音乐付出的艰辛、也无关音乐家的身世和故事、更无关音乐会结束后空空舞台的一地失落”[8]。另有学者在多个学术研讨场合表现出像当年孔老夫子看到“八佾舞于庭”那样“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义愤填膺,认为对待严肃音乐的态度就应该正襟危坐,甚至认为有些剧中情节与历史和现实有所偏差、尚须考证。笔者认为,对待音乐的严谨态度固然值得尊敬,但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观念亦矫枉过正,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仍值得商榷。首先,回归“民乐是什么”的问题,我们都不可否认民乐是艺术。既然艺术不是类型,艺术的表现形式本来就可以多样,可以表现为音乐会,亦可以表现为其他,那么如此说来民乐表现为一台民族音乐会还是一台民族器乐剧已然不是原则性问题,何况“严肃音乐会”(ConcertofClassicalMusic)本身就是西方舶来品,既然人们可以接受参照交响乐编制创作出来的民族音乐会,为什么不能接受类如歌剧和舞剧一样用民族器乐表现戏剧的民族器乐剧呢?其次,关于艺术和学术的区分显而易见,艺术不等同于学术。做学术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艺术创作虽然同样须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但也需要“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创新精神。换言之,艺术和学术无所谓高下,但两者实属于两套不同的评估体系,因此,把艺术作品完全等同于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并加以评判显然有失偏颇,在艺术创作中“现实”与“超现实”都只是手法,创作者有权选择适合表现自己艺术的手法。因此,比较客观的评价应该是,无论创新与否、何种形式,最重要的是“民族器乐”作为主体不应该淡化,作为支撑的依然应该是高质量的创作、高质量的演奏和高质量的表演,这一直是而且永远是评判一台民乐剧目优劣的根本标准,确切地说是评判一部舞台剧目的准绳。
二、主题性音乐创作
除去上述民族器乐“剧”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其他常规音乐会的创作与编排也更具明确主题性,音乐会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草率地仅以“民族音乐会”“民族器乐音乐会”“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印入节目单。诚如“标题性音乐”一般,音乐会名称与剧目阐述更加讲究,它赋予了听众一个大致的思想范围。这类主题性音乐会在近年频频涌现,例如《丝路粤韵》(2015)、《寻找杜甫》(2016)、《永远的山丹丹》(2017)、《高粱红了》(2018)、《七彩之和》(2019)、《中轴》(2020)、《孙子兵法·回响》(2020),等等。再具体点说,每一场主题音乐会大多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叙事结构,它更注重一场演出的文学统筹。以《丝路粤韵》为例,该音乐会以开海、祭海、远航、异域、乡愁、归来、新梦为叙事线索,分别用七个乐章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画卷;再以《高粱红了》(图3)为例,音乐会以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为叙事线索,揭示了人与自然、土地与生命相互依存的内涵。这种主题性表达的涌现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如此说来,作为音乐会形式的民乐呈现,在整体表达上确实略逊于其他舞台艺术。“民乐听韵味”的传统让创作者更注重每首乐曲个体的表达而相对忽略整台剧目的布局谋篇,策划者和表演者鲜有考虑聚焦一个主题的问题。并非说,每台音乐会都必须按戏剧作品那样以起因、发展、高潮、结局来讲述一个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矛盾冲突的故事,但是完整的音乐会,一定需要遵循某种逻辑关系,通过某种文化结构串联起来。一台优秀的音乐会一定由包含其中的优秀曲目构成,但音乐会与曲目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可本末倒置,一组优秀的曲目,即便表达了相同的主题,如果逻辑结构不合理,也未必就能够组合成一台优秀的音乐会。说起来虽有些绕口,但道理很简单——完整的剧目需要整体布局,速度的快慢缓急、情绪的跌宕起伏、结构的起承转合等因素都应考虑其中。从目前创作推出的主题性音乐会观之,完成一台音乐会整体性布局,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受制因素也很多,尤其是现代音乐作品大多采纳委约制的情况,受约作曲家大都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下独立完成单曲写作,待到作品视奏阶段已基本“定局”,回过头来考虑整体性问题确实十分受限。以《丝路粤韵》为例,该音乐会已是近些年民乐创作中比较注重整体表达的一台剧目了,策划者目标清晰,创作者方向明确,而且委约的数位作曲家均在业界有口皆碑。演奏该音乐会的广州民族乐团在技术上、作品阐释上也有目共睹,可以说是算得上良心之作了。但其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七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在发力,每一位作曲家都不甘示弱,整场下来,亢奋的点太多、高潮太密集、音响太满便成为影响整体感观的问题,因此,有时候“干货”太多也未必都是好事。在这个问题上,由一位作曲家独立完成的一整台音乐会,例如《高粱红了》,其乐曲风格和布局则更为统一。做此评价,并不是倡导作曲家今后都来创作整台音乐会,委约者今后一台音乐会只委约一位作曲家,而是应该从中看到统一性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民乐一定要向戏剧、戏曲、歌剧、舞剧的艺术创作学习,主创团队需要更多的研讨、交流,也需要更多的协作意识和协作精神。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推广,并亟待更多作曲家的认同。
三、地域性特色
立足本土、吸纳优秀的民间文化,继而创作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作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此准则也早已达成共识。近年来,因为作曲家强烈的共识,以及各省级民族乐团的崛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反映本土文化特征的作品占绝大多数。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立足本土,而是如何更好地立足本土。我们一再呼吁作曲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底怎样才叫“深”,如何才算“扎”?是不是应该像人类学者那样,研究某一文化事项,至少在自己研究对象的所在地住上一年的时间?当然,如果作曲家和创作者也能够做到自然是好事,但恐怕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大部分人抛开一切职务的、生活的、工作的琐事,离群索居、心无旁骛地在创作对象所在地住上一年。那么,我们不妨从这些较为成功的作品中汲取些许经验。“局内人”的创作立场,是一种绝对的优势,这一现象自不待言。如厦门的《土楼回响》、广东的《丝路粤韵》、吉林的《高粱红了》、山东的《大道天籁》、北京的《中轴》,细数下来,这些创作主体都在做“局内”的事,或者直接点说,在做“家乡”的事。人类学对于这一现象叫“家门口的田野”,移植到作曲家身上,暂且称其为“家门口的创作”。这些“家门口”的作品确有深意,以《高粱红了》为例,笔者认为,按照“四季”结构整场音乐会显然是基于作曲者王丹红对东北文化的深刻理解,因为那是她的家乡,充分利用家乡资源,而无须额外住上一年,这是作曲家写作家乡题材作品的最大优势,许多本土作曲家对于地方民间素材的运用都较为自如,对于民间素材没有贴标签式的移植改编,而是恰到好处地融入作品,用真实的民族器乐语言表达这一地域的文化,而非抽离出来的旋律和曲调,不是拼贴,而是将所选择的民间素材中的核心材料,打造成为具有逻辑意义的结构力的作品,让人听来既熟悉又新鲜,充满了期待。如果说,诸如《高粱红了》这样的作品是因为创作者家乡的“内力”,是局内人的立场,那么,《永远的山丹丹》(图4)则可以看作是借助了音乐学者的“外力”,是局外人融入其中的典范。曲作者王丹红在谈及创作过程时说:“在《永远的山丹丹》这台音乐会写作之初,所有采风的路线包括看哪些东西、怎么看,都是乔(建中)老师亲自安排的。”确实,作品无论是整体结构安排还是某些陕北素材的运用都非常精彩,其中的《祈雨调》《刮大风》《朝天歌》实非一个局外人对陕北音乐仅仅是信天游这样的想象就可以得来的,这一感受在此后乔建中关于该音乐会的深度乐评中亦得以验证[9]。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一“借力”的方法可以作为作曲者“采风”的一个重要路径:一位作曲家在写作一部作品的时候,最好能够寻求到一位音乐学家或者对当地民俗和文化特别了解的学者作为向导,这样的结合,一定会比蜻蜓点水式的采风能更迅速地进入角色和切入要害,继而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
四、结语
以上论述,仅从三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民族管弦乐创作领域的三种现象,也是民族管弦乐创作的三种趋势,这三种趋势为民族管弦乐的发展注入了不可低估的推动力,也引发了业界的多维思考。但从很多角度来看,民族管弦乐仍然是小众,民族管弦乐的发展,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呵护,也需要创作、演奏、评论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对待每一部新创的作品,创作者需要以开阔的胸襟来真正思考和取舍,应有海纳百川、止于至善的精神;演奏者须融入其中,真正理解作品的创作意图及其背后的文化,并在二度创作链上精彩转译;评论者更应肩负责任与担当,既不轻率否定,亦不绝对肯定,理解当下,也指示出未来可做可为的道路。
作者:杨雯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 上一篇:中小学民族器乐教学探索范文
- 下一篇:民族器乐艺术辅导教学探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