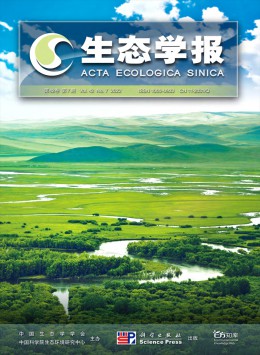生态学视域下的英汉翻译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生态学视域下的英汉翻译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生态学是研究物质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其发轫之初很长时间里被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和交叉、跨学科研究日趋成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了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容性,认为人文社会领域和自然一样,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间都发生着联系,没有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事物和现象,故而认为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遂真正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本的认识由仅仅关注认识文本内部自足性问题发展到研究文本内外部关联问题,研究的视野也随之由微观文字向宏观文化转向,人们对文本的认识,已无法将文本语言与该语言所蕴含或显现的某国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断。对于成功的翻译者来说,他不仅要作为两种语言的专家,还要是两种语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对于英汉翻译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需要不断探寻着解释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形成文化差异的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社会各层面因素影响文本文字的关系。生态学强调事物与其环境协调、互动、互相促进。在英汉翻译领域,一个成功或优秀的译作应当是不仅内部自足和谐发展,而且内部与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栖的文本。其动态性体现在这种交互作用是永无止息、不断旋螺式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或者无意义的重复。用生态学视角看待英汉翻译,为的是建立一种整体性思维。有学者为“整体性”的意义进行了阐释:“整体性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整体性不是部分的简单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动而形成的原子集合体,它有着超越部分之和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对翻译及其研究工作来说,把握“整体性”是关键。翻译活动涵盖原文本和译文本,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3方,包括语言和文化2个层面,同时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梳理和廓清这些形成翻译活动的要素的动态平衡发展,有助于建构英汉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域。
二、原文本与译文本的交互解读
原文本一经生成,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各种读者解读下成为“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消费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则文本只是完成了生产过程,惟有读者的阅读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得以生成,使文本价值得以实现。译文本的产生就是原文本蕴涵得到复活的一个过程,译文本的产生同时是对原文本的“消费”,促成原文本价值的重新生成和意义再现。译文本对原文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扩大或者新生成原文本意义。译者与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个人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译者对原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有译者的前结构参与,这种前结构大大影响了原文本意义的重现:原文作者将生活的客观信息内化于文本,译者在翻译之前先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自己的前结构对原文本进行内化,但这次内化的主体是译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体所作的“内化”经由不同文本载体产生出不同的文本接受。原文本意义和译者根据前结构而解读出来的意义不同,所以可以说,译者通过内化能扩大原文本的意义,使原文本意义更加多样。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两种理论都强调读者阅读对文本的意义,认为读者也是促成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译者作为原文本的一种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并不是被动地阅读,他是原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生态学视域下的译者已经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对原文本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而是担任协调者、统筹者的角色。多样化的意义被译者融注于笔端,形成了译文本,多样化的意义由此再传递给译文读者。由上文所述可见,译文本不是对原文本文字表达简单地“复述”,而是积极地参与了原文本的意义生成。但原文本对译文本的决定意义又不言而喻,因为译者对原文本无论如何创新解读,都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能颠覆原文本的根本主旨。“生态观认为,生物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各种要素之间进行着有序的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原文本和译文本成为两个和谐共生、交互解读的文本圈。尤其经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本、译文本共同服务于这部作品的题旨、指向,使经典作品传世;原文本、译文本形成作品的两个共生共存的表现载体,相互间发挥最佳协调效果,共同服务于作品价值的生成和阅读消费。
三、译者与译文本环境的互动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具有适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该法则而存活下来的事物才称得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种生存困境时才能够延续生命,这个原理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上已成无可辩驳的规律。英汉翻译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适应这些因素的翻译活动才能较好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成为广为接受的文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亦即拥有广大的受众。受众对译文本的消费是译文本价值的体现。如果一个译文本无法赢得受众青睐,则译文本的价值就是有限的。如今,进行英汉翻译前,译者选择要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符合本国政治环境的要求,否则译文本无法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也就无法顺利出版。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译者选择的作品可以更加多样化。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前,译者翻译的多数是苏联的作品,而且多数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作品,这符合当时“将一切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也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需;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社会来临以及价值观多元化,翻译所选择的作品样式、作品主题呈多样化,翻译不再仅限于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作品,而是面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优秀作品。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业也由政府部门主管、财政支持发展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文化市场上读者的需求是译文本得以产生和畅销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因为读者喜爱,作品很难找到出版商。除此之外,经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各学科门类及生活实用的大量文本的翻译,翻译人才的数量大大超过过去以文学作品翻译为主的翻译人才数量。“现代生态学已不仅仅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而是已成为指导人类行为准则的综合性学科,是研究生物存在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可见,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因素共同组成译文本“生态环境”,这环境中的各种因子共同作用,促成翻译的顺利进行和历史发展。只有适应这些因子,译文本才能最终实现价值。
四、名家译作对原文本和译文本环境适应举隅
译者在翻译之前,对原文本进行解读,进而通过译文本再现原文本风采,体现了对原文本的适应及对译文本所在的由政治、经济、主流价值观等组成的生态环境的适应。然而,这两种适应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生态学视域下的翻译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态学视角运用于翻译之前,人们普遍对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无法达成公论。生态学视域下翻译观可以很大程度地扩展翻译的视野,使得翻译不再拘泥于归化异化之争,而是以适应性为基础,赋予译者以协调者、操纵者的角色,译者在原文本和译文本两个文本圈间取得平衡,认为只要能达成平衡,则归化异化皆可行。这种主张是合理的,因为根据心理学上的格式塔理论,读者阅读的时候虽然会欣赏作品的字词句,但又不是拘泥于字词句,而是以整体感觉来欣赏作品,即不是从文字形式的叠加得出印象,而是在各个部分间协调、纵横、兼顾、整体认知。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要优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翻译过程中必须持有整体观念,而不能局限在字词句方面对原文本死译、硬译。死译、硬译后的作品,虽然字词句之间适应原文本,然整体效果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如,对英语长句硬译,其结果是汉语译文不堪卒读。这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的不协调翻译行为。如,英语文学对《圣经》典故的使用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不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原文本的读者对西方宗教文化相当熟悉,毋需作者赘述,而在对《圣经》文化普遍陌生的中国读者看来,这些典故犹如天外来客,中国读者不明就里。这就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的不协调的翻译行为。从格式塔心理效应来看,译文本的读者需要的是对译文本整体价值观、信息等宏观了解,译者只要在这些宏观方面能够保持与原文本一致,则不必拘泥于该如何忠实于原文本的遣词造句。即是说,译者更大的责任在于将不熟悉原文本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译文本读者所需要的所指信息显化,使之前景化,而不是仍将其作为隐含信息而让译文本读者解读困难。所以,刘士聪先生说:“将译文作为一个独立文本加以审视,审视其整体的审美效果,看其内容是否与原文相符,看其叙事语气与行文风格是否与原文一致,这一点很重要。”译者必须权衡利弊,了解两种文化的特点和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了解原文本哪些语言、文化信息是译文本读者可以无障碍地接受并且不会误读的,保留这些信息的风貌,而原文本当中对译文本读者产生障碍的信息,则需要进行明晰化处理,恰当采用释义、套用、注释等手法,这样从整体去达到忠实原文本的效果。只有这样的整体协调,才是对两种语言的“生态系统”的最佳适应,与原文本取得真正的平衡。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采用了变译的策略,许多人并不认同。然而,如果借生态学的视角来加以解释,则可发现,严复的翻译策略选择是相当理性的,其译文本体现出生态学意义的平衡观和协调观。严复的翻译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开启民智,号召人民群众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于是遵循原文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思路,在原文本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关于中国国情及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信息,使得译文本语篇更加恢弘、气势磅礴。严复的翻译,将原文本的信息型文本转化为译文本的呼吁型文本,将原文本内涵的对自然的生态选择转化为译文本内涵的对社会的生态选择。可见,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没有违背原文本的基本思想与内涵,甚至提升了原文本的内涵与意义,而且又适应译文本所在的政治环境,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因为,当时在译文本所在的环境———中国土地上,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国家独立、政局稳定,在时局动荡、民族存亡之际,普及原文本的科学知识实在意义不大,而经过严复的翻译及译文本传播,原文本的价值得到超越性实现。严复的译文本不仅适应了原文本,而且适应了译语的环境的各种因子,译文本即是在英汉两种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之间取得最佳协调关系的成果。有学者因此评论,“虽然严译《天演论》在有的方面没有很好地忠实于原作,对内容和语气都作了修改,但我们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孤立地对其做出评价,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严译《天演论》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对其不应过于苛求,应有更公正的评价。”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的小说GoneWiththeWind(傅译的书名《飘》)时,将语言大量作了中国本土化,包括在对原文本人名的翻译上,也去掉英语人名汉译经常采用的音译法,而是用典型的汉语人名二字格式或者三字格式给人物重新命名。这使得译文本读来给人恍如在读汉语原著之感,似乎不带英语著作的痕迹。当然,该译文本在翻译界引起的争议丝毫不亚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引起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傅东华译作一直是最广为接受、广为流传的GoneWiththeWind汉译本。探究起来,不难发现,傅东华译作广受欢迎的原因正在于其适应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适应了译语的生态环境,而对原文本的风采却毫无影响———因为翻译上局部的归化异化无损于原文本的思想,同时又能为译语环境所接受。王佐良翻译培根的《论读书》,影响极大。译文本无论在文采还是在思想上,都不逊色于原文本。而在具体的细节上,又可以看出译者并非惟原文本马首是瞻。例如,培根《论读书》原文本中,“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andforability.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王佐良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原文用简单的词汇和句型,以及大量省略句,而译文则文采斐然,句式整饬,超乎原文。如果仅遵从原文省略句式和平实的措辞特点,则译文会如白开水,很难在一向推崇文采的汉语文化环境下产生大的影响。王佐良在尊重保留原文本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汉语文化环境里论说散文重文采和汉语句式喜好排比和四字格的特点,使译文形式整饬,朗朗上口,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可以说,培根的这篇论说文《论读书》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王佐良的翻译。这样对译语环境和原文本风姿的双重适应和选择,即是适合了生态学的平衡、和谐理念和整体、关联思维。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充满的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信息,是汉译英上的难点。《红楼梦》英译本以杨宪益译作和霍克斯译作两个译文本最广为流传。前者以直译为主,将各种文化信息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去。这种直译法会令熟悉汉语文化的人们读来如同读原文本,较为轻松,而对于英语国家中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则会障碍重重,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中缺少汉语文化,故而无法理解文本当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后者以意译为主,将对英语民族来说很生疏或者会造成误解的信息以英语文化中可与之构成联想、意义相似的形象代替,使得鸿篇巨著的《红楼梦》不会因为太多陌生的异域文化信息的出现而阻碍英语读者对名著的理解。从生态学角度看,霍克斯很好地适应了译语主要的阅读环境,使得译语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较为和谐的互动,其译作属上佳;而杨宪益的译文会使得汉语文化空缺的外国读者云里雾里,译文和译语读者之间难以形成和谐流畅的传播接受关系,也就难以产生平衡、和谐的生态学的关系。
五、结束语
赵小兵提出,“各种关系集于译者一身,各种平衡的工作需由译者来完成,译者选择的和谐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意识。译者正确地把握文学翻译中的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把握语篇内外之间的关系,充分地考虑跨语境问题,是保证文学译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和谐一致的重要途径。译者须具有和谐的整体意识,使文学译本达到和谐的境界。”生态学的整体和谐观已经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英汉翻译工作来说,意义在于构建了生态翻译学,译者及研究者可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翻译。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只需要以生态学的眼光看待,在原文本风采保留的基础上,以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各种因子为准则,灵活运用和搭配各种译法,则译无定译。只要能协调、平衡、拓展原文本价值又吸引译语受众,甚至促进译语环境的社会变革,引导译语环境社会正面价值观念的提升,则译文本即属佳作。
作者:林福泰 单位:黎明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