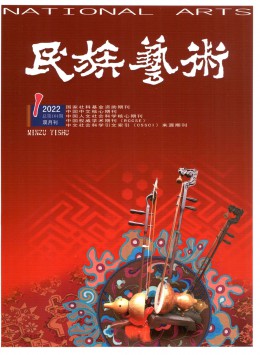民族与历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第2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在民族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能否取得较大成就或实现个别领域的突破,一方面取决于研究者对所研究民族相关材料的收集、甄别、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较为开阔的、超越所研究民族的研究视野,以及在这种视野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通史精神或通史观。
关于通史精神、通史观或“通”,自汉代开始,就不断有史家予以论述,贯穿中国史学史。司马迁著《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确提出了通古今的要求。从此,“通”作为一条著史的原则为史家接受。《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史通义》等著作的出现,表明“通”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信奉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些著作中的“通”的含义不尽相同,但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通古今的思想。不仅中国史家在著史和研究历史中注重通史精神,外国史家也具有同样的意识。施丁教授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黑格尔认为,只有对过去长时期的历史反思再反思,即“后思”,才能写出通史。正是经过“后思”,黑格尔写出了一部通古今之变的、以“世界精神”为主体的普世史———《历史哲学》。
二、通史精神在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民族史研究展示了民族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使人们更好地认识民族史的重要地位,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史研究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在进行民族史研究时,必须具备通史精神,正如周谷城所说:“通史所求者为历史自身之完整”。民族史研究中所提倡的通史精神就是渴求民族史的完整性,同时能在研究视域上有所突破。
通史与断代史、专门史的关系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相互为用的,共同发展的关系。通史是断代史、专门史的浓缩、概括,引导断代史、专门史前进;断代史、专门史则是为通史打基础,丰富通史的内容。因此,在民族史的学习和研究工程中,一定要培养通史精神,应用通史方法。
三、如何在民族研究中应用通史精神
首先,在民族史研究中要有通史修养,重视民族史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重视各单一民族史之间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和文化做出过贡献,所以中国历史不能离开民族史的内容,而民族史也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大背景而发展。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除具备专业的特殊素养外,还应具备中国史的修养和视角,要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同时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历史。关于前者,白寿彝先生以回族史研究为例指出:“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说这够搞的了,搞别的来不及了,这个想法就不对。”对于后者,白寿彝先生认为,民族史工作者虽然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收眼底,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史,至少须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既便于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也有利于深入地挖掘相关史料。
其次,应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看待民族关系。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特点,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从文献资料看,既有友好往来、和平相处的记载,但也不时见到敌视、仇杀与战争的记述。不可否认,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史上,经常充斥着争吵,乃至战争。但也应看到,各民族间也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以及民间往来等友好和融合关系,斗争和压迫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站在历史的长河里看,这一特征更为突出。以往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往往忽视民族友好和和平共处,就与未能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看待民族关系有很大关系。对此,白寿彝先生也有精彩论述:“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都是这样。”
第三,应从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与评价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以及汉化问题。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有的以及已消失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民族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少数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开发和建设中原及边疆地区,创造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方面,他们与汉族一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各民族的发展史来看,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文化载体也缺乏本民族的特色,反而充盈着汉文化特色和儒家思想。对此,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应将其放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作为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汉语、汉文尽管是汉族创造和最初使用的,但在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文化,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这种文化和思想就应视为是该民族的,而非汉族的,应视为是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第四,在民族史研究中,应把握好民族情感与宗教情感的尺度,体现科学性原则。民族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应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符合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要求。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对于从事民族史研究很重要,能够帮助研究者从深层次把握某些民族特质,而这些特质常常是非本民族成员很难领悟和把握的。白寿彝先生对从事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者所讲过的“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具有复杂性,脱离科学性的约束,就容易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容易感情用事,不能够做到以理服人。因此,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把握民族情感与宗教情感的尺度。
第3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摘 要:要从区域历史同质性、整体性历史要素和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区域开发史;充分认识这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阐述近代湘西开发引发的社会变迁;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近代;湘西;开发史;区域史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2608
一、何谓区域史视野
强调确立区域史的视野,以“开发史”为问题切入口深刻地阐述一个地方社会的近代变迁,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一种挑战性首先是必须清楚地回答什么是“区域史的视野”?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运用“区域史的视野”来议论和阐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相关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方法论和意义上予以解释与阐明。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缘于社会史研究推进的带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区别于以往仅仅关注上层政治空间与制度安排转而开始越来越关注下层社会空间与生存场景的新变化,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域转向”新趋势。史学研究中的这种“区域转向”既不是以往史学界宏观叙事模式下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拓展的一种研究范围的扩大,也不是传统地方史研究范式的翻版,而是一种包括思维方法、解释框架、叙事风格等系统要素在内的史学方法论转型。与以往史学仅仅专注于“宏观历史”的重在描述“国家、政治、时间”的“大历史”的“正史”叙事式研究不同,“区域史”关注“大历史”背景下具体“微观历史”的“民众、社会、空间”的“小历史”的解释与分析,强调社会公众、不同空间、地方经济,凸现史学研究应有的主体性、结构性和差异性;而同传统地方史的主要差别在于传统地方史往往以行政区划为依据确立研究对象范围,而以行政区划来界定研究范围往往包括若干不同显性的区域在内,实际是多个区域历史的机械相加,这与以历史同质性为特征的区域史研究有本质区别。区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的历史进程研究。它不是通史的地方化,也不是专史的地方化,同样也不是宏观主题的地方化(如“在湖南”之类),而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
所谓区域史的视野就是研究区域史所要求的思维角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有基于区域历史同质性上的问题意识,体现整体性特征的历史要素的结构分析路径和以文献与田野相结合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历史同质性是建构区域的基本廪性,也是判断确认“区域”的重要条件。区域史研究就是要在区域历史同质性中寻找课题,从其特征上发现要研究的问题,从而确立问题意识;同时,应当进一步发现影响区域整体社会变化的重要历史要素,并依循这种历史要素的自身结构来分析其在区域社会历史中的形成、特征和作用,从而反映区域社会的整体历史状况。而这样的研究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是不够的,需要把文献与田野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方能在解读“大历史”与体验“地方感”相互印证、补充,从而全面地分析和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全貌。
二、对近代湘西历史研究的学术反思
湘西自古以来就与外部地区及中央王朝存在种种历史联系,而正是这种历史联系赋予它值得关注的历史价值。然而,无论在地域范围、民族地位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湘西都不可能进入传统的正统学术探讨主流视野,因为它只是一个具有特定民族成份和特定历史影响的特定地域。所以,在传统学术的视野中湘西只能是关注这一区域以及这一区域内民族的学者的学术对象,具体地讲,对湘西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历史文化和土家族、苗族问题的学者(或者说本土学者)。经过这些学者多年的努力,有关近代湘西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著方面涉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主要有:廖极白的《湘西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论述从原始社会到1949年湘西的通史著作,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谈到历史上的湘西开发,其中关于近代湘西的开发用笔较多;游俊、李汉林的《湖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从民族史的角度叙述了近代湘西开发中的一些历史大事;游俊、龙先琼的《潜网中的企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也涉及了近代湘西的开发史实。此外,伍新福的《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陈国安的《土家族近百年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黄柏权的《湘鄂西土家族》(民族出版社,2003年)以及王跃飞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都对近代湘西的开发历史有不同程度的阐述。
第4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主流;和平相处
【作 者】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17-010
An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Mainstream of the Nation Relations
Zhao Yongchun
Abstract: Before the 1980s there were mainly two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war” proposed i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mainstream of nation relations In 1981, Bai Shouyi and Weng Dujian etc argued that the mainstream of nation relations was “History improvement promoted jointly by all nations” This new point of view received both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The controversy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ly apprehended the concept of “the mainstream of nation relations”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if we distinguish the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according to that nation relations are mainly including “war” and “peace”, “peaceful coexistence” will be Viewed as the mainstream of nation relations undoubtedly
Key words:Nation; Mainstream; Peaceful coexistence
古代史学家由于受思想的影响,多认为少数民族野蛮、落后。因此,在他们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很多战争和冲突的记载具有较强的火药味。从秦汉时对北方匈奴、鲜卑和乌桓的战争,秦对南越的战争,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匈奴、氐、羌、鲜卑、羯胡之间的相互争战,北魏对柔然的战争,唐对吐蕃、南诏、突厥的战争,宋与辽、金、西夏、蒙古的战争,明对瓦剌、鞑靼的战争,清对准噶尔的战争等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幅民族矛盾、对立和争战的图景。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家总是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各族之间的仇视、冲突和战争,认为古代的民族关系就是一种你征服我,我征服你的关系。受这种思想影响,建国前的一些学者也是将民族矛盾、冲突和战争说成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建国以后,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批判和纠正古代史学家的传统看法,提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进步。因此,他们主张在教学和论著中,少提或者不提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屠杀等等。于是,引发了有关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大讨论。
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有关民族关系主流问题大讨论,以1981年白寿彝、翁独健提出“各民族互相依存,共同推动历史前进”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为标志,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下面将这两个时期有关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一简要回顾,并提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
一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1981年白寿彝和翁独健提出“各民族共同推动历史前进”是民族关系主流观点之前,可以视为建国后有关民族关系主流大讨论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民族和民族关系史大讨论的升温,有关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讨论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并逐步发展成为学术界讨论民族关系史问题的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随着讨论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学者们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和深化,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主要有两种意见: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第一种意见认为,友好合作、和平相处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民族仇视、屠杀、战争,主要体现在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或者在某一民族统治阶级与另一民族的人民之间,但罪魁祸首是统治阶级。而各族人民之间,则是互相帮助、互相合作的。因此,他们指出,在阶级社会,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间的关系,才代表民族关系的主流,在他们之间,本质上不存在压迫、剥削、特权和不平等的关系,在某种情况下出现过的疏远、隔阂、敌视等现象,是统治阶级所制造和强加于他们的。他们认为,民族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就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这种观点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早在1958年汪锋就曾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即用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无论哪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之一。各民族人民的亲密团结、互相合作,是构成我国历史的主要的一方面。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事件,必须要记在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帐上。”①贾敦芳也对以前“往往是过多的描绘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仇杀”表示不满,指出“历史上相同的各个民族,由于剥削阶级的挑拨利用,曾经有过仇杀的事实,但更多的却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互相扶助,我们应该多多发现后者,而不应过分夸大前者”②。
到了1959年,赵华富、侯方岳等人明确提出“各民族人民的友好与合作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的观点。赵华富认为,“历史上我国各族之间有斗争,有互相歧视的现象,有互相屠杀、互相压迫的事实,但这仅仅是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即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或者是某一个族的统治阶级对待某一族的人民之间。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是友好的,他们经常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基本的方面。”③侯方岳认为,“民族间的压迫剥削、征伐屠杀和因此激起的反抗起义,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面,是次要的一面,而不是主要的一面,是比较短暂时期的支流和逆流,不是长期起主导作用的主流。”他认为,民族关系中长期起主导作用的主流,“是汉族与各族劳动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团结互助”。④陶明也指出,“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各族人民内部的联系与合作。”他说“各族人民从来就不满和厌弃民族间的混战和祖国分裂,他们深深体会到,民族间的混战和祖国分裂,带给他们的是无限的痛苦。因此,他们所迫切要求的是民族间的团结合作、祖国的统一和国内的和平,借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们对于破坏他们内部联系和合作的那种战争和压迫,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反抗,曾不止一次地共同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和压迫,以求重新建立各族人民内部的密切联系,彼此合作”⑤。
吕振羽、周乾、岑家梧等人赞成这一观点。吕振羽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在阶级社会时代,一面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统治阶级和其本民族的人民及其他各民族的人民间的关系,一面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的统治阶级或上层集团各自和其本民族人民及其他各族人民间的关系,一面是处于不同地位的各民族的统治阶级或上层集团相互间的关系,一面是各民族人民相互间的关系。”他认为“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人民在内的各民族人民间的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在他们之间本质上不存在着压迫、剥削、特权和不平等的关系,在某种情况下出现过的疏远、隔阂、敌视等现象,是统治阶级所制造和强加于他们的。”各族人民“利于彼此间的团结、友爱、互助和合作,也不断发展了这种团结、友爱和合作”,这是统治阶级禁止、离间和阻挡不了的⑥。周乾指出“各族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为了共同命运而进行的联合斗争贯穿着我国整个的历史,这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他认为“各族之间发生过不少战争,那是统治阶级的贪欲引起的,人民是不会发动战争的。”⑦岑家梧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虽然也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歧视,甚至发生各民族间的战争,但各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劳动人民之间友好合作,仍然突破了种种障碍,成为历史上民族关系上的主流。”⑧
陈永龄也赞成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族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观点。他指出“在某些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民族关系中也确曾出现过短暂的民族战争、民族压迫和民族仇杀,以及影响深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曾严重地影响,甚至破坏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这只是“民族关系中的逆流”。他认为“从历史的全过程看,统治阶级造成的消极因素是一时的、局部的;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联合和互相友好合作、取长补短等积极因素,则是长期的、主要的。”“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国所以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各族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利益一致,休戚与共,团结联合,共同战斗结成了亲密的战斗情谊。”⑨
翦伯赞在1962年曾指出“过去的史学家在论述民族间的关系时,一般都把战争作为主题,甚至只有讲到战争时候才提到民族关系,这是不对的。因为民族之间的正常的和主导的关系应该是和平相处。只有在民族矛盾发展到和平相处的关系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才爆发战争。”他认为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把各族劳动人民和各族统治者分开,是对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各族统治阶级为了便利他们的战争动员,经常挑拨种族之间的仇恨,制造种族之间的不和,在统治阶级长期的挑拨之下,各族的人民不能不受到影响,因而他们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民族偏见以及由于这种偏见而产生的民族隔阂,在阶级社会的劳动人民中也是存在的”,这就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的原因。⑩翦伯赞认为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与上述认为“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的提法略有不同。
孙伯祥也赞成各族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友好合作的关系,但他强调“团结、进步、统一是民族关系的主流”B11。还有人强调各族“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关系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B12等等,与上述提法多有相似,但也有所不同。
第二种意见仍然强调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他们认为民族压迫是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本质表现,在某些时期,民族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吴晗认为有些人“一味强调,在长期的历史关系中,各族都是友好相处的,个别的甚至说成是兄弟般的关系。这样一来,就把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民族矛盾掩盖了”,“把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民族间的战争、压迫、屠杀的史实抹煞了”,是“以今套古,把古代的民族关系也现代化了”。他指出,“片面强调和平相处是非历史主义的,同样,用相反的方法,不讲和平共处的一面,只讲战争、压迫、屠杀的一面,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说成是民族相斫史,那就更是错误的。”B13吴晗既反对片面强调民族和平相处,又反对片面强调民族战争,并没有指出二者之间何为主流的问题,但对后来一些学者坚持民族矛盾、对立和战争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多有影响和启发。
范文澜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民族斗争,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不是你打进来,就是我打出去”。“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或国家,各民族和各国家间,完全依靠力量的对抗,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狼吃羊,羊被狼吃,这是动物界的规律,也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规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并没有脱离动物界,动物界的某些生活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B14范文澜在论述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时没有使用民族关系主流的概念,但他强调民族之间不存在和平共处。
孙祚民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认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压迫和歧视的关系”,范文澜的文章发表以后,他又发表文章明确表示赞成范文澜的观点,也认为“剥削阶级统治下的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他认为“由矛盾尖锐化引起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都是大小强弱之间力量的对抗。即使在矛盾缓和时期实行的包括‘和亲’在内的‘善邻’政策,其实质也只是一种‘羁縻之道’,而根本不是什么‘和平共处’和‘平等联合’的关系。”B15
在建国后有关民族关系主流问题大讨论的第一个时期里,学者们对什么是民族关系主流问题,主要提出了上述两种观点。在这两种观点之中,虽然持“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主流观点的学者比较多,但持“民族矛盾、对立和战争”是民族关系主流观点的学者也不示弱,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前一种观点不断质疑,形成两种观点各不相让的局面。
二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大讨论进入到第二个时期。1981年,白寿彝和翁独健在前一时期讨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各民族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新观点,并逐渐赢得了多数学者的赞同,似乎为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讨论画上了句号。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仍然有人不赞成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见解,尤其是对民族关系“主流”概念的讨论,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鉴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持“友好合作”和“互相打仗”两种民族关系主流观点的学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白寿彝、翁独健等人又在1981年5月北京香山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上,提出了一种带有折衷性质的新观点。白寿彝认为,无论是用“友好合作”还是用“互相打仗”来概括民族关系的主流,“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对方的提法,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说服对方。”他认为“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说“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B16翁独健也认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B17
1984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翁独健进一步强调,民族关系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但和平与战争只是表象,主流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内聚力使各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密切。B18后来,翁独健又在他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如果说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吸取,互相依存,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伟大国家。但也应指出,在这个缔造的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很多不是和谐开展的,而是伴随着民族冲突和压迫,经过民族矛盾的发展才解决的。因此,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B19
白寿彝、翁独健提出各民族共同“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是中国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以后,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和拥护。蒋至静指出“从总体来看,中国境内各民族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国家才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之说,当是合乎客观实际的。”B20杨建新认为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一种“唇齿相依,分不开,离不得”的关系,认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就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长期联系,密切交往,相互依赖,共同发展。”B21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彭体用认为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看法的片面性,能够透过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复杂现象,揭示民族关系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自古以来,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频繁交往,相互取长补短,相互依存,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推动了各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B22。陈育宁也认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已经证明,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接触愈来愈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流,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B23杜建录通过对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的考察,认为“战争固然是西夏对外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内容,但它并没有阻挡住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各民族之间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发生战争期间,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使西夏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逐渐和内地接近,另一方面形成了既有共性又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多元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统一,这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B24彭德志也认为“民族关系总的趋势,也就是主流,应该是各民族的相互接近,互相融合,共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B25罗贤佑于2009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也赞成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B26
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段生农指出,“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和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是“属于不同范畴的另一回事”,他认为“民族间的友好合作或敌对斗争是一种历史现象,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也是一种现象。两者虽同为历史现象,但却分属不同的历史范畴,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互相取代,绝不能因为有了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这一历史事实而一笔抹煞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和敌对斗争这样的历史实事。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不能被作为民族关系的主流来看待,只能被作为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来看待。”他认为,“在我国的历史上,在民族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这一对矛盾中,所体现的各民族的友好合作,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B27
陈梧桐也认为,“所谓主流是相对于支流而言的,没有支流也无所谓主流。”他认为将“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共同促进历史的前进”说成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不一定很确切。“因为按照这种说法,人们无法理解,相对于这个主流而言的支流究竟是什么?难道说这个支流就是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或兵戎相见吗?如果说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的支流,那么离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离开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压迫和奴役的斗争,各民族所谓共同创造和发展祖国的历史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如果说民族关系的支流仅仅指的是民族之间的兵戎相见,那么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既非主流又非支流,它又该算是什么呢?”因此,他仍然认为“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是决定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因素,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中的主流”,而“民族冲突和战争”则“是我国民族关系中的支流”。B28
坚持“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观点的学者还有谷苞、吴量恺、吴泰、苏双碧等人。谷苞认为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说过头了”。他认为“在古代的民族关系中,有民族斗争的一面,也有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一面。民族斗争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要发生的事,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事,却是年年月月天天都在到处进行的。”因此,他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B29吴量恺通过对明代蒙汉关系的考察,认为“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政治上的不断联合,使蒙汉两族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和互为依存的关系”,“两族间的经济交往,是经常的、大量的,无疑是蒙汉关系的主流。”B30吴泰通过对宋辽金时期和平与战争期间对比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互相友好相处,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这时期的文明的过程中互相融合,才是各民族关系的主流。”B31苏双碧通过对“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不把少数民族(或称被统治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历代中原王朝,都和边疆各少数民族建立了一定的联系”;“长期的相处和长期的互相间的战争,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等问题的论述,得出结论说:“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各民族之间友好合作显然是主流。”B32姚爱琴主张“辩证地理解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认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广大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吸收、相互协作、相互帮助、共同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关系,这是民族关系史的主流。”B33孙进己认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共处”“平等联合”B34,与上述观点大体一致,但提法稍有不同。
持“相互压迫和歧视”是民族关系主流观点的孙祚民,也不同意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他认为白寿彝和翁独健提出的“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观点,“是在‘平等说’(孙祚民将上述认为“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概括为“平等说”)的错误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和摈弃的形势下”,“提出的另一种变相的‘平等说’”。并认为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是在回答民族关系的主流时,回答的“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是全然文不对题,答非所问的”。认为这种观点“非但不能区分阶级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民族关系的根本不同的性质,更不能揭示两种不同民族关系发生质变的条件和规律。”他仍然坚持“民族关系的主流,主要是民族间的压迫与反压迫”。B35肖黎也坚持民族矛盾、对立和战争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古代民族间的关系,绝不像某些论者讲的那么甜美和谐。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民族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和平共处’、‘平等联合’。恰恰相反,更多的却是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是不容粉饰的事实。”B36王佩环也不同意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认为,“严格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曾真正出现过‘内聚力’的吸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部反反复复、出出入入的铁与血的征服史”。B37薛虹也认为,“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基本方面是不平等的、不团结的对立关系,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并不是友好往来、团结互助的关系。”他认为“不仅侵略、征服、防御、反抗等战争关系决定着对立国家之间的民族关系是处于敌对和冲突的地位;就是贡献和册封所形成的宗藩关系,也是民族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并非是平等团结的关系;即使是和亲、会盟、通关互市等关系,也是民族羁縻政策的产物,双方矛盾缓和的表现,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从来不是基本的、经常的民族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的基本关系,只能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不是什么平等友好、团结互助的关系。”B38
王勋铭既不同意“友好合作”或“民族之间冲突和战争”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也不同意白寿彝和翁独健提出的“各民族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的‘主流’概念,不是通常所说的‘主要的’或‘大多数’的意思,而是对民族关系最一般的抽象,它舍弃了那些常见的具体的个别的现象,特指那些在民族关系的各个方面一贯起制约作用的本质内容。这种本质内容就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它构成我国民族关系各个方面、各种特征和特性的有机的稳定的联系系统。具体说,作为民族关系的‘主流’,必须具备主导性、一贯性和多面性三种属性。”按照他所确定的民族关系“主流”的涵义,他认为“各民族互相吸收、互相联合、互相依存的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他指出“这个主流犹如奔腾的长江大河贯串我国民族关系的始终(下限在新中国成立前)、渗透在民族关系的各个主要方面(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统治阶级之间的、普通群众之间的等)、各个时期(从秦汉至元明清等),它具有主导性、一贯性、多面性。这个主流把我国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共同缔造和发展伟大的祖国。”B39王勋铭虽然不同意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但他所提出“各民族互相吸收、互相联合、互相依存的关系”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似与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并无多大差异,与主张“和平相处、友好合作”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这一观点学者的也有某些相似之处。
崔明德不同意有关民族关系主流的“平等说”、“民族战争说”和“发展说”(崔明德将白寿彝和翁独健的观点概括为“发展说”)的观点,他认为白寿彝和翁独健提出的“各民族共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观点,“谈的显然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主流。他通过对西汉与匈奴的战争、唐与吐蕃的战争、唐与南诏关系的考察,认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既有阶段性的和好,也有阶段性的战争;在和好阶段,双方尽可能地采取一些措施维持较长时期的和好,在战争阶段也有积极谋求和好的活动”,“作为民族关系的双方来说,既积极谋求阶段性和好能够长期保持下去的途径,以便给双方创造稳定、发展的环境,又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谋求暂时和好或小阶段性和好,以便为长期和好创造条件。这种长期不懈的谋求和好的努力,应当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B40在上述“三说”之外又提出了“长期不懈的谋求和好的努力,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的新观点。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就民族关系整体而言,和亲是主流”B41以及“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B42的观点。
三
纵观20世纪以来的民族关系主流问题大讨论,可以看出,学者们畅所欲言,无论是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考察,还是有关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理论建设,都呈现出逐步深化之趋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勿庸讳言,讨论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学者们对民族关系主流的概念理解不同所致。
认为民族关系主流是指“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的观点,是由白寿彝、翁独健等人提出,经过杨建新、陈育宁等人的发挥,逐步走向深化的一种理论认识。这种认识得到了杜建录、彭德志、姚爱琴等大多数人的赞同,似乎成为学术界讨论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一种主流观点。但反对者则认为他们所说的“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并非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如王勋铭就曾针对白寿彝和翁独健等人提出的“各民族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观点提出三点质疑,“第一,各民族共同促进中国历史发展,讲的是多民族历史地位即历史作用问题,而不是讲民族关系本身;第二,各民族共同促进中国历史发展,讲的是民族关系的结果,它不能贯穿民族关系的多方面和始终,它不是‘流’,更不是‘主流’;第三,这种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着眼的方法,易导致人们忽略对民族关系本身具体过程的研究。这种方法得出的认识也只能是一般化的、对任何国家和民族关系都适用,而不可能是我国民族关系所特有的东西。”B43孙祚民认为白寿彝和翁独健提出的民族关系主流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说,是在回答民族关系主流问题时,回答了“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是全然文不对题的,答非所问的”,是“有意‘顾左右而言他’”。B44段生农也认为属于民族关系发展趋势的“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和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是“属于不同范畴的另一回事”。B45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质疑都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民族关系“主流”的“概念”确非指“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但王勋铭和孙祚民对民族关系“主流”涵义的理解也不尽合适。
王勋铭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中的“主流”概念,“是对民族关系最一般的抽象,它舍弃了那些常见具体个别的现象,特指那些在民族关系的各个方面一贯起制约作用的本质内容。”“必须具备主导性、一贯性和多面性三种属性。”并认为“各民族互相吸收、互相联合、互相依存的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B46说来说去,与白寿彝、翁独健等人所说的“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并无差别,实际上也是不合适的。
孙祚民认为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应该“是民族平等或者民族压迫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而不是战争或者和平占较多时间的问题。”并认为“民族关系的主流,主要是民族间的压迫与反压迫”。B47实际上,孙祚民所说的“民族平等或者民族压迫”问题,也不是民族关系主流问题,而是民族政策问题,用民族政策来概括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也是文不对题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呢?查《现代汉语词典》对“主流”一词的释义有二,一、“干流”,即与支流相对的水的干流;二、“比喻事情发展的主要方面”。B48《辞海》对“主流”一词的释义也认为是“干流”,并在“主流和非主流”条下释义说:“主流指事物的本质方面,它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非主流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它不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但对事物的发展有影响。看问题,做工作,必须分清主流和非主流,既不能把主流和非主流等量齐观,更不能把主流和非主流弄颠倒。如果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那就会犯错误。当然,在工作中,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B49
按照这种解释,“主流”的原意应该是指水的干流,与“支流”相对,引申意义为“事情发展的主要方面”,与“非主流”相对。也就是说,“主流”与“支流”或“非主流”是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陈梧桐曾指出“所谓主流是相对于支流而言的,没有支流也无所谓主流”B50,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
按照这种理解,笔者认为,要弄清楚民族关系的主流,首先要弄清楚民族关系应该包涵哪些内容?
陈梧桐认为,“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这一面之外,也存在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另一面。”即认为民族关系主要包括“友好合作”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两大方面。B51陈育宁认为,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和平形态和战争形态两种形态,战争形态包括民族掠夺战争、民族复仇战争、民族征服战争、平定民族叛乱的战争、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国内民族抵御外国异民族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国外民族的侵略战争几个方面的内容。和平形态则包括和亲、通贡、互市、开明的民族政策(一种情况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另一种情况是统治民族的羁糜政策)、会盟几个方面的内容。B52崔明德也认为“战争与和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两项基本内容”B53。这些学者均认为,民族关系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两大方面。
既然认为民族关系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两大方面,那么确定民族关系的主流就应该在这两大方面里寻找,也就是说,寻找出哪一方面是主流,哪一方面是支流。笔者认为,相对于民族战争来说,和平相处则表现为民族关系“发展的主要方面”,因此,笔者赞同翦伯赞等人提出的“和平相处”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认为民族战争是民族关系发展的支流或非主流。
这里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即笔者所说的“和平相处”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与上述各位学者所说的“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主流的观点,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处,即认为“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并非完全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因为在和平相处时期,有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但也有不友好的事情发生;在民族战争爆发的时间里,既有民族之间仇恨厮杀等不友好的现象发生,也有个别的民族之间友好现象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用“和平相处”来概括民族关系的主流更为恰当。
下面,我们以人们认为民族矛盾、对立和战争最为突出的宋金关系为例,来说明民族关系的主流不是战争和对立,而是和平相处。
首先,在整个宋金对峙时期,战争时间少,和平相处时间多。从政和七年(1117年)北宋泛海赴金谋求与金联合共同灭亡辽朝开始,到天兴三年(1234年)金朝被蒙宋联军灭亡为止,双方交往长达117年。在这117年之中,只有28年是战争时期,和平相处时期则长达89年,战争时期仅占24%,和平相处时期则占76%。从战争和“和平相处”的时间对比上看,宋金关系的主流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相处。
其次,战争时期,双方也不是一刻不停地冲杀争斗,而是打打停停,不断地进行和平谈判,积极地谋求“和”的方式和途径。宋人从战争开始爆发就积极谋求议和,不用说那些主和派,就是那些主战派也认为两国终归于和,不过希望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议和而已。金人最初企图灭亡南宋,后来看到难以灭亡南宋,也积极谋求与宋议和的方式和途径。两国均把议和作为最终追求的目标。说明,战争时期,双方并没有一刻不停地打仗,而是打打停停,谈谈打打,战争时期也有大部分“和”的时间,而且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和议。
再次,和平相处时期,双方希望和平相处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宋金双方签订和约、实现和平以后,即确立了正旦、皇帝生辰等重要节庆,双方必须派遣使节互相祝贺等交聘制度,希望双方能够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双方统治者还严格要求本国使节和人民,多言“友好”之事,不要惹事生非,尽量避免不“友好”的事情发生,就是希望使和平相处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下去。
足见,在宋金交往的117年之中,战争时间少,和平相处时间多;战争时期双方积极谋求议和;和平相处时期又都希望和平相处的关系能够长期保持下去。所以,战争和对立不是宋金关系的主流,而和平相处才是宋金关系的主流。
宋金关系如此,其他时期民族战争没有宋金战争如此激烈时期的民族关系更是如此,完全可以说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相处。
当然,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好一段,歹一段”的特点,民族战争与和平相处也会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应该说,在民族之间发生战争时期,战争无疑是那一阶段民族关系的主流;而在和平相处时期,和平相处也必然是那一阶段民族关系的主流。如果我们从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来看,和平相处仍然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民族战争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支流。
注释:
① 汪锋《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J],《民族研究》1958年第2期。
② 贾敦芳《关于研究祖国各民族历史的几点意见》[J],《民族研究》1958年2期。
③ 赵华富《为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斗争》[J],《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④ 侯方岳《对于研究各民族历史的几点意见》[J],《民族团结》1959年3期。
⑤ 陶明《试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J],《民族研究》1959年9期。
⑥ 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J],《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如何处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N],《文汇报》1962年1月26日。
⑦ 周乾《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N],《天津日报》1962年6月20日。
⑧ 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J],《历史教学》1962年9期。
⑨ 陈永龄《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J],《历史教学》1979年第4期。
⑩ 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B11孙伯祥《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J],《山西教育》1979年第2期。转引自刘先照《我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苦于理论问题综述》[J],《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
B12《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的讨论》[N],《文汇报》1962年7月3日。
B13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人民教育》1961年9期。
B14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J],《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B15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N],《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读范文澜》[J],《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B16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B17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B18李晋槐、杜少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综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B19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B20蒋至静《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辨》[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B21杨建新《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1期。
B22彭体用《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B23陈育宁《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趋势》[J],《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B24杜建录《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及其特点》[J],《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B25彭德志《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理论问题》[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1期。
B26参见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B27段生农《也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B28陈梧桐《论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合作关系形成的原因和意义:兼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J],《求是学刊》1984年第1期。
B29谷苞《论充分重视和正确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民族问题》[J],《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1期。
B30吴量恺《明代蒙汉两族的交往关系》[J],《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B31吴泰《试论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J],《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
B32苏双碧《关于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B33姚爱琴《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J],《社科纵横》2005年4期。
B34孙进己《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A],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B35孙祚民《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J],《东岳论丛》1987年第1期。
B36肖黎《也谈如何评价西汉“和亲”问题》[J],《北方论丛》1982年第2期。
B37李晋槐、杜少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综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B38薛虹《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坚持民族原则问题》[J],《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
B39王勋铭《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B40崔明德《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二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B41王连升《一部研究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著作-评<汉唐和亲史稿>》[J],《东岳论丛》1993年第5期。
B42张之恒《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A],《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C],2005年。
B43王勋铭《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B44孙祚民《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J],《东岳论丛》1987年第1期。
B45段生农《也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B46王勋铭《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B47孙祚民《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J],《东岳论丛》1987年第1期。
B48《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79页。
B49《辞海》(缩印本)[Z],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2、1203页。
B50陈梧桐《论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合作关系形成的原因和意义:兼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J],《求是学刊》1984年第1期。
第5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应当说,报告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是十分精辟的,尤其是强调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更显深刻。离开了爱国主义,所谓“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等等,都将因缺乏民族特质的整合,而泛化成人类多有的优长,无由彰显“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什么?按列宁的说法,就是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对自己的祖国的深厚感情。可见爱国主义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培育国民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是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前提,而这些舍历史教育无由。这个道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就已经提出来了。
“民族精神”的概念源于西方。在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莫泽尔发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最早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德意志人民只有在这一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才可能万众一心去实现民族统一和重新恢复其光荣与强大。该文引起了轰动,民族精神问题从此为国人所关注。随着甲午战争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民族精神问题也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关注的热点问题。1904年《江苏》就发表了长文《民族精神论》。作者指出,一个民族的兴衰最终取决于其精神的强弱,西方各国所以强盛是因为18世纪以来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关于国民精神,时人又称国魂、民族魂等。何谓民族精神?当时少有明确的界说,不过从《浙江潮》上发表的著名的《国魂篇》赞美“冒险魂”、“武士魂”、“平民魂”以及“爱国心”、“统一力”来看,时人所谓民族精神的内涵大致包括:团结爱国的精神、变革进取的精神、民主自由的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爱国主义。所以,“铸国魂”、“爱祖国”、“祖国主义”的呼声,风靡一时,成了时代最强音。《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写道:“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至于怎样培育民族精神,人们的认识相当一致,那就是要借重历史教育。上述《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认为,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少爱国心,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历史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视中国历史文化为最可宝贵的国粹与民族的根,强调要研究国学,“爱国以学”。章太炎在流亡日本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学,其目的就是要在有为的青年中传承民族的根,培育民族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初步觉醒和面临危亡的时刻,志士仁人揭出了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党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的同时,又一次揭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成熟。因时代的局限,当年志士仁人对民族精神的认知,不可能十分周全正确,但就其自觉地提出了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并作了自己的努力而言,毕竟又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在继承前人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认识。我以为,就历史教育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关系而言,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其一,历史教育是实现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固然有不同的内涵,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却是一脉相承。这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竞存于世界的根之所在。章太炎曾说过爱国主义好似庄稼,需要施肥、浇水才能成长,而历史教育就是为爱国主义施肥浇水,作培植根的工作。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所以我曾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历史教育是最基础、最有效的爱国教育。它像贵如油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中将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他们将来不论走到哪里,都怀有一颗“中国心”,而永远根系祖国,生生不已。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的学人,并没有人对他们做什么专门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志愿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冲破各种阻力,归国效力,不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吗?通过历史教育培育国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就为其他多样化、现实性的爱国教育,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承接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乏这个承接面,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有效。
其二,历史教育是实现继承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
民族精神,说到底,就是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十六大报告将之概括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它看似抽象,实际却是具体的,因为它是历史的积淀。民族精神、优良传统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欲继承首先必须要认知,欲认知便离不开历史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团结统一”为例,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逐渐形成了“大一统”观念。随着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大一统”从此也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秦以后,历代开国君主都不满足于偏安政权,而以天下统一为己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汉,所以被后人推崇,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或完成了统一大业,或安定了天下。而中国的民族心理,也习惯于把天下统一,认作是“治世”,而将割据纷争的时代,认作是“乱世”。事实上,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也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可见,统一是中国历史与人心的大趋向。与此相应,中国各民族人民都追求团结和执着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古代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常常通过联姻来沟通民族感情和发展民族友好关系。各民族都把联姻,称作“和亲”,说明彼此都珍重相互间的亲和关系。因而,“和亲”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而王昭君等历代勇敢承担“和亲”使命,并为民族间的和睦作出贡献的许多女性,也成为了各族人民共同缅怀的巾帼英雄。而从郑成功,到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再到今天党和国家为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所做和正在做的不懈努力,不都是中华民族注重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生动的历史见证吗?很显然,如果我们不了解上述的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理解“团结统一”何以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了。同样的道理,“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也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无数生动的历史实践的记录,是民族精神氤氲化育的结果。历史是最好的教师。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必须向历史请教。离开了历史教育,既无法真正了解优良的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其三,历史教育是引导国人培养历史责任感的基础。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目的是为了“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要使国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归根结底,就是要引导国人培养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这方面,历史教育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首先,一个人历史责任感的形成,有赖于具备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正确的历史观。难以想像,一个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历史感的人,会有振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可以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历史素养,以开阔视野,并养成科学的历史观,进而如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懂得“科学判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过阶段”,自觉做时代的建设者。其二,一个人历史责任感的形成,还有赖于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高的理想境界。一个目光短,思想卑微的人,不可能有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既利于国人开拓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国人荡涤胸襟,志存高远,如同志所说,学习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邓小平、等党的三代领导人历来都高度重视历史教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落实不力,多年来历史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断被削弱。商潮滚滚,人多浮躁,历史和历史教育既不能创造经济效益,自然不被重视。电视上倒有不少历史剧热播,但那是出于商机需要的“戏说”,不是真正在讲历史,许多胡编乱造,甚至误人非浅。国民的历史教育,本来主要是依赖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历史课来实现的,但现在小学是停开历史课了,中学历史课的时数也一压再压,像首善之区的北京,初中历史课将只乘下每周一节课了,聊胜于无而已。初中是义务教育,高中以后就是非义务教育了。如果学生初中毕业就去就业,他的历史知识能有多少呢?即便是上了大学,如果不进历史系,这些学生终生不再接受本国历史教育,中学学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历史知识,大概也都忘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民教育的历史教育还有多少成效是可想而知的。现在许多青少年包括大学生,“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对祖国历史知之甚少。对此,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不断提出了批评意见。不久前,一位中科院院士著文认为,建国以来教育的主要失误有二,一是重应试教育,轻能力培养;二是不重视历史教育,许多学生爱国思想淡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也著文说,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朋友曾对他讲,现在有一些中国留学生,ABC即英文很好,美元、英镑也分得很清楚,就是不懂得长江与黄河,即中国历史文化,对自己的祖国缺乏感情。中国史学会前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说得更沉重,他说: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篡改教科书,歪曲侵华历史,误导日本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我们管不了,我们中国自己的青少年总可以加强教育吧。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教育,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将来他们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篡改历史呢!耐人寻味是,戴先生说上述话后不久,就出现了个别年轻艺人因于历史无知,不自觉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事情,引起舆论哗然,网上更是一片谴责声。这不是偶然的,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反省吗!
在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国民教育”新的重大课题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历史教育的作用与地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真正加强国民的历史教育:
其一,对历史教育要重新定位。泛泛地说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凝聚力、培养爱国精神是不够的,至少还缺乏尖锐性。龚自珍说,“亡人国必先亡其史”,强调历史教育是关系国家兴衰荣辱的大事。这才是一针见血的判断。借现代的语言,我们必须明确,历史教育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应列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应当从加强历史教育入手,主管部门应加强统筹规划。
第6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应当说,报告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是十分精辟的,尤其是强调民族 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更显深刻。离开了爱国主义,所谓“团结统一”、“勤劳勇敢 ”等等,都将因缺乏民族特质的整合,而泛化成人类多有的优长,无由彰显“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什么?按列宁的说法,就是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对自己的祖国的深厚 感情。可见爱国主义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培育国民对民族历 史文化的认同感,是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前提,而这些舍历史教育无由。这 个道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就已经提出来了。
“民族精神”的概念源于西方。在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莫泽尔发表《 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最早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德意志人民只有在 这一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才可能万众一心去实现民族统一和重新恢复其光荣与强大。该 文引起了轰动,民族精神问题从此为国人所关注。随着甲午战争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 论传入中国,民族精神问题也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关注的热点问题。19 04年《江苏》就发表了长文《民族精神论》。作者指出,一个民族的兴衰最终取决于其 精神的强弱,西方各国所以强盛是因为18世纪以来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关于国 民精神,时人又称国魂、民族魂等。何谓民族精神?当时少有明确的界说,不过从《浙 江潮》上发表的著名的《国魂篇》赞美“冒险魂”、“武士魂”、“平民魂”以及“爱 国心”、“统一力”来看,时人所谓民族精神的内涵大致包括:团结爱国的精神、变革 进取的精神、民主自由的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爱国主义。 所以,“铸国魂”、“爱祖国”、“祖国主义”的呼声,风靡一时,成了时代最强音。 《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写道:“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 至于怎样培育民族精神,人们的认识相当一致,那就是要借重历史教育。上述《民族精 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认为,一 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少爱国心,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历史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 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 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 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视中国历史文化为 最可宝贵的国粹与民族的根,强调要研究国学,“爱国以学”。章太炎在流亡日本生活 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学,其目的就是要在有为的青年中传承民族的根,培育民 族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初步觉醒和面临危亡的时刻,志士仁人揭出了高扬 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党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 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的同时,又一次揭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 课题,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成熟。因时代的局 限,当年志士仁人对民族精神的认知,不可能十分周全正确,但就其自觉地提出了这一 重大的时代课题并作了自己的努力而言,毕竟又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在继承前人认 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认识。我以为,就历史教育与培育民族 精神的关系而言,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其一,历史教育是实现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固然有不同的内涵,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却是一脉相承 。这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竞存于世界的根之所在。章太炎曾说过爱国主义 好似庄稼,需要施肥、浇水才能成长,而历史教育就是为爱国主义施肥浇水,作培植根 的工作。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所以我曾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历史教育是最基础、 最有效的爱国教育。它像贵如油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中将 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他们将来不论走到哪里,都怀有一颗“中国心” ,而永远根系祖国,生生不已。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的学人,并没有人对他们做什么专 门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志愿放弃国外优厚 的待遇,冲破各种阻力,归国效力,不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吗?通过历史教育培育国 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就为其他多样化、现实性的爱国 教育,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承接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乏这个承接面,所谓爱 国主义教育,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有效。
其二,历史教育是实现继承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
民族精神,说到底,就是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十六大报告将之概括为: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它看似抽象,实际却是具体的,因为它是历史的积淀 。民族精神、优良传统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欲继承首先必须要认知,欲认知便离不开历 史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团结统一”为例,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逐渐形成了 “大一统”观念。随着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 大一统”从此也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秦以后,历代开 国君主都不满足于偏安政权,而以天下统一为己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代天 骄成吉思汉,所以被后人推崇,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或完成了 统一大业,或安定了天下。而中国的民族心理,也习惯于把天下统一,认作是“治世” ,而将割据纷争的时代,认作是“乱世”。事实上,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也 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可见,统一是中国历史与人心的大趋向。与此相应, 中国各民族人民都追求团结和执着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古代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 民族政权间,常常通过联姻来沟通民族感情和发展民族友好关系。各民族都把联姻,称 作“和亲”,说明彼此都珍重相互间的亲和关系。因而,“和亲”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而王昭君等历代勇敢承担“和亲”使命,并为民族间的和睦作出贡献的许多女性,也 成为了各族人民共同缅怀的巾帼英雄。而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可 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再到今天党和国家为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所做和正在做的不懈 努力,不都是中华民族注重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生动的历史见证吗?很显然,如果我 们不了解上述的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理解“团结统一”何以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了 。同样的道理,“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也都不是抽 象的,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无数生动的历史实践的记录,是民族精神氤氲化育的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教师。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必须向历史请教。离开了历史教育, 既无法真正了解优良的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其三,历史教育是引导国人培养历史责任感的基础。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目的是为了“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 要使国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归根结底,就是要引导国人培养热爱祖国 、振兴中华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这方面,历史教育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首先,一 个人历史责任感的形成,有赖于具备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正确的历史观。难以想像,一个 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历史感的人,会有振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可以为国民 提供必要的历史素养,以开阔视野,并养成科学的历史观,进而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 报告中所说,懂得“科学判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 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过阶段”,自觉做时代的建设者。其二,一个人历 史责任感的形成,还有赖于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高的理想境界。一个目光短,思想卑微 的人,不可能有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既利于国人开拓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国人荡涤胸 襟,志存高远,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学习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寂然凝虑,思接 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三代领导人历来都高度重视历史教育。但是,现在的 问题是落实不力,多年来历史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断被削弱。商潮滚滚,人多 浮躁,历史和历史教育既不能创造经济效益,自然不被重视。电视上倒有不少历史剧热 播,但那是出于商机需要的“戏说”,不是真正在讲历史,许多胡编乱造,甚至误人非 浅。国民的历史教育,本来主要是依赖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历史课来实现的,但现在小学 是停开历史课了,中学历史课的时数也一压再压,像首善之区的北京,初中历史课将只 乘下每周一节课了,聊胜于无而已。初中是义务教育,高中以后就是非义务教育了。如 果学生初中毕业就去就业,他的历史知识能有多少呢?即便是上了大学,如果不进历史 系,这些学生终生不再接受本国历史教育,中学学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历史知识,大概也 都忘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民教育的历史教育还有多少成效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许多青少年包括大学生,“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对祖国历史知之甚少。对此 ,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不断提出了批评意见。不久前,一位中科院院士著文认为,建国 以来教育的主要失误有二,一是重应试教育,轻能力培养;二是不重视历史教育,许多 学生爱国思想淡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也著文说,在 美国大学任教的朋友曾对他讲,现在有一些中国留学生,ABC即英文很好,美元、英镑 也分得很清楚,就是不懂得长江与黄河,即中国历史文化,对自己的祖国缺乏感情。中 国史学会前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说得更沉重,他说: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篡改教 科书,歪曲侵华历史,误导日本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我们管不了,我们中国自己的青 少年总可以加强教育吧。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教育,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历史都搞 不清楚,将来他们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篡改历史呢!耐人寻味是,戴先生说上述话后不久 ,就出现了个别年轻艺人因于历史无知,不自觉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事情,引起舆论哗 然,网上更是一片谴责声。这不是偶然的,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反省吗!
在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国民教育”新的重大课题后的今 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历史教育的作用与地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真正加强国民的 历史教育:
其一,对历史教育要重新定位。泛泛地说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凝聚力、培养爱国精神是 不够的,至少还缺乏尖锐性。龚自珍说,“亡人国必先亡其史”,强调历史教育是关系 国家兴衰荣辱的大事。这才是一针见血的判断。借现代的语言,我们必须明确,历史教 育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应列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应 当从加强历史教育入手,主管部门应加强统筹规划。
第7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尤中文集》;学术成就;治史方法;书评
尤中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为总结尤先生近60年来的研究成果,积累文化,启发后学,并以此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0周年,云南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国庆节前出版了《尤中文集》,其中汇集了尤先生除《中华民族发展史》(500万字)之外的绝大部分著作,共分为6卷。重读这些著作,关于理清尤先生史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及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从而继承尤先生的学术传统,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突出的学术成就
(一)构筑了以民族史研究为核心的西南研究殿堂
从尤先生的学术成果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以西南为中心的民族史研究。这些论著从时问而言,上起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下迄清代,纵贯古今上百万年;从空间而言,以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为中心,涉及全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以及大量跨境民族的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正确阐述了各民族的源流、民族关系,历史上各个时期统治阶级对民族地区设置的统治机构及其所施行的统治政策,并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这些著作以坚实的历史事实正确地论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一直在历代中央王朝的版图范围之内,但因历史原因,各个时期的疆域发生了具体变化,在这些地方所设置的统治机构所辖范围也时伸时缩、时广时狭。第三,校补西南历史典籍。藉由此项工目,尤先生一方面开拓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经他所整理之著作详备易读,为后学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尤先生的这些论著师从前人,又超越前人,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廓清了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漫步其构建的西南民族史学大厦,通读一部部论著,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古往今来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便清晰明了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二)构建起独具学术创见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体系
尤先生在民族史学研究中始终站在全国统一的高度来看西南、云南的史事,其论著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在论述西南各族几千年来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探讨其发展规律时,尤先生始终把西南各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客观地分析中原王朝与西南各族的历史关系。他指出从西南各族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可以看出: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西南各族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西南各族也以自己的灿烂文化,促进了汉族的发展,丰富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西南各族的许多人口不断融合进汉族的队伍中,壮大了汉族。在形成中华民族、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活动中,西南各民族是有卓越贡献的,西南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员。
(三)系统研究西南古代各族族系源流及其演变发展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西南各族族系源流及其发展演变持有不同见解,观点歧出,各成体系。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尤先生“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即把西南地区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区域的民族分布情况加以逐阶段的研究,再辅以其他论证方法,来判断各族族系渊源、发展变化及其归属”,这样,线索清晰,论证严密,见解独到而终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观点,而这也成为尤先生在西南民族史学研究中的主要学术贡献。
二、科学的治学方法
(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尤先生的史学论著都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力作。1956年,尤先生开始了以《云南民族史》为起点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此后尤先生先后为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云南民族史》、《云南的古代民族》、《云南地方沿革史》3门课程,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元明清时期的西南民族》、《中华民族史》等课程,为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中华民族史》等课程。为配合教学,尤先生最终完成了2部本科生教材、3部硕士生教材及3部博士生教材。由于经过了无数次教学过程中的检查及补充修改,因此这些著作多完备充实。以《云南民族史》成书为例,1956年秋,为配合讲授《云南民族史》,尤先生把抄录出来的资料印成了《云南民族史史料汇编》发给学生,同时边讲课边写讲稿边做研究。1957年,尤先生正式写出了《云南民族史》讲义。此后讲稿历经修改,到1980年由云南民族学院印成铅印教材。
1985年,又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再次铅印,作为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山大学等院校历史系的教材。之后先生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又多次对《云南民族史》进行了修改充实,最终形成现在的规模。
(二)宏观的视野、全局的器识是其突出的治学特点
从尤先生的学术经历来看,有一个立足云南、巩固西南,全面研究中华民族史的、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的发展过程。尤先生的研究起于《云南民族史》,但尤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只局限于云南一地,不与全国的形势相联系,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只有有了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高精尖。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先生就决定建造学问的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精”。而要构建金字塔,除了需要博大精深外,还需要从宏观、整体、系统的角度分析研究。因此尤先生逐渐将其治学视野扩大到了西南乃至全国。之后的《中国西南民族史》和《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这两部书从大西南的宏观角度探讨了西南地区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族系源流。有感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离开了汉族去研究少数民族,或者缺少了少数民族去研究汉族,都是搞不清楚的,因此尤先生在收集汉族和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资:V4的基础上又写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超级秘书网
(三)以论带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
尤先生的学术成果虽然不是直接的理论研究,但却是新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中国西南民族历史解释体系的力作,它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生产方式到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西南民族社会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从而使其西南民族史研究具有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特点。
第8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林窒壬,生于1916年3月,广东新会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1961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至内蒙古支边,从事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1979年转入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担任科研和教学工作。1990年离休后,受学校返聘,继续承担科研任务及参与指导博士研究生工作。
林纸淌谟幸欢蜒术头衔:蒙古史学会理事、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民族史学会顾问、内蒙古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被选为第五届内蒙古政协委员,1988年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5年3月,在有356万人参与投票的第五届“感动内蒙古人物”评选活动中,林窒壬入选。正如颁奖词所言:“五十多年支援边疆、扎根大草原,矢志不移、学术拓荒;三十多年潜心北方民族史,硕果累累,声名远扬!九十九岁高龄,为他热爱的内蒙古,还在执着着他的执着,梦想着他的梦想!”
他从1961年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内蒙古,已跨半个世纪,而林老也已过期颐之年。
林窒壬经世致用,深耕北方民族史,致力于民族团结,以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铸就“当代昭君”之魂,成为学术泰斗、学人典范。
披肝沥胆写草原春秋
治学的道路是艰辛的。研究历史,尤其是少数民族历史,要具有拓荒的勇气和超拔进取的精神。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林窒壬就开始进行北方少数民族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仅匈奴史资料就收集了好几箱。“”当中,这些资料遗失殆尽。 “”后,他从头做起,首先编印出版的就是《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书中选录了近百年来国内外的匈奴史论文100余篇,成为当时收录古代少数民族史论文研究最多的文集之一,奠定了他在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地位。内蒙古大学教授马骥曾透露,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抠得很细,连一句话、一个资料的出处都要找到最原始的那个东西”。 林先生治学,不仅严谨,且具有收放自如的张力,他“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并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并重”。边疆史,曾经是比较冷僻的史学门类,却也是“另一半的中国史”,正是先生的目光敏锐,论述精湛,才得正本清源;正是先生之独立思考,敢于创新,才使许多著作解决了国内外学者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其论点多为前人所未发,填补了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99年10月,林窒壬在布达佩斯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提出的“公元91年由中国西迁的匈奴人是匈牙利民族族源的一部分”论点,语惊四座,得到与会各国学者,特别是匈牙利学者的赞同。同年11月17日,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播出了林先生的演讲。匈牙利原总理、著名地理学家康德・保罗・特里基后来发表文章说:“我骄傲地承认,我们是来自亚洲的民族。”(《t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24期)
着眼历史,t望未来,才是经世致用之学。针对分裂中华民族的“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泛突厥主义的“新疆地区一贯独立论”等说法,林窒壬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深刻而精微地阐述了历史上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和亲”、北方少数民族的同化与汉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等问题,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驳斥。
先生治学,披肝沥胆,皓首穷经。学界将其研究成果分为综述、编制工具书、形成专著三个方面。就其专著而言,学术深度可以用“理论、实践与新知”来概括。仅仅就先生出版的19种著作,学界分为如下几类:历史研究类6种:《匈奴史》《匈奴通史》《突厥史》《回纥史》《东胡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工具类书3种:《匈奴历史年表》《匈奴史料汇编》《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史论类4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通论》《内蒙古民族团结史》《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文化史类4种:《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内蒙古历史与文化》《昭君文化丛书》《塞北文化》;文化选集2种:《匈奴史论文选集》《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从1977年出版《突厥史》到1998年出版《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21年,洋洋万言,鸿篇巨制,铸成了北方民族三大族系的系统工程,先生被称为“北方民族研究之纛,塞北文化探源之星”(穆鸿利,东北师范大学博导)。
正如史学界评述,林窒壬对匈奴、突厥和东胡三大族系有深入研究,堪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之执牛耳者。林窒壬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以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和雄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对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史诸问题,把握我国的现实民族关系大局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先生教学,不仅言传,更重身教。他除了在内蒙古大学授课,也经常应邀到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院校讲学。上个世纪80年代,林窒壬还受内蒙古党委的委托,在自治区厅以上干部大会上,讲民族团结历史和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的民族政策问题。如今,先生已是桃李满天下, 在2009年民盟内蒙古区委和内蒙古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研讨会暨庆祝林窒壬学术生涯60周年座谈会”活动中,他的学生、史学界同仁纷纷前来,后来者以“面对林郑像面对一部缀满注释与索引的史书”的评价来表达敬仰。
矢志不渝铸民族团结事业
林窒壬多年深耕北方少数民族史,他的研究纵横捭阖,从人类学的大视角充分阐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在我国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充满了阶级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却从未间断,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接触和影响,包含着互助、友好、合作等因素,推动着民族关系的不断改善、不断前进。匈奴文明建立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创造了中国最早的骑士文化,引发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大范围的碰撞,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多种文化风云激荡、交相辉映,铸就了灿烂的北方历史画卷。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先生与内蒙古大学的几位教师合作,写出了《内蒙古民族团结史》(远方出版社,1995年),叙述内蒙古地区古往今来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阐明民族团结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及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中的作用。该书荣获1996年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
1979年他主持编著了《昭君与昭君墓》一书,2003年担任了昭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编了五卷本的“昭君文化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分别是《昭君文化研究》《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昭君论文选》《昭君图册》,对昭君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明确提出了“昭君文化”的理念。“昭君文化”的提出,不仅提炼了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历史精神,传承了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和合”思想,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全球“文明的冲突”的层面上(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预见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即他称之为的“断层线战争”),重新重视“昭君文化”及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民心相通”的文化基因,对促进经济转型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战略布局将有巨大推动作用。而由此充实和扩展了“昭君文化节”的内容,带动了文化创意产业,也显示了其深远影响。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中华文化的深刻跃迁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契机。“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一方面,我们需要文化和艺术来提升我们民族的素质与水平;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呼唤和产生越来越多的超越本土地域性的文化成果,发出中华文明对于全球的世界性言说。
林先生知行合一,热心民族团结事业,多年来,与回族、满族、蒙古族等各民族同事真诚相处,合作共事。支边扎根到内蒙古后,更是与这里的少数民族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他教育子女,嘱咐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忠于祖国,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现在,我们看到,正是这良好的家学、家风使得他的大家庭书香浓郁、人才辈出。
第9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
一
钱穆的历史观是一种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而非一般的文化生命史观。
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对历史有较详细的定义性阐释。他说:“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又说:“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又说:“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1]”在其它地方亦有此类说法[2],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又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3]”
但钱穆不是就历史说历史。他常把历史和文化与民族联系在一起探讨。他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说:“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4]”为此,有必要知道钱穆眼中文化和民族是什么?
钱穆对文化的定义性解释颇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一是,文化是人类集体、全体生活或民族生活之总称、总体或各部门、各方面之融合,如,“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5]”“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目之为文化。……文化是指的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6]”“文化乃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把每一个民族的一切生活包括起来称之为文化。[7]”“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各配合,融凝成一,即是文化。[8]”二是,文化即是人生,是大群之人生或人生之总体,如,“文化是人生的总体相,分言之,构成此文化的也有许多体配合,如宗教、教育、政治、文学、艺术等,而政治方面又要加上军事、法律等,这一文化体系是由各方面配合而成。[9]”“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集合而成的人生,此当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10]”在上述两种解释中,钱穆也把人生视为人类的生活[11]。三是,文化是一个生命,一个大生命,如,“文化乃群体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12]”“文化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大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因此文化定有个大体系。[13]”四是,文化是一种精神共业,如,“应该说文化是人类中大群集体人生之一种精神共业。”“既说文化是人们一种精神的共业,有其传统性,因此也可说文化有生命性。[14]”这些解释并不矛盾,钱穆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文化作了定义性解释。
钱穆对民族所做的定义性解释较简单。他说:“怎样叫做民族呢?我们很简单的可以说,只要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对象、艺术爱好、思想方式,各有不同,就可以叫做异民族。”[15]他说,民族这个观念中国古代没有,是近代从西方移译过来的,中西文化的民族观有很大不同,“中国人注重在文化上,西方人注重在血统上。”近代讲民族的都注重血统的分别,而中国古人似乎并不重血统的分别,“由中国古人看来,似乎民族界线就在文化上。这是中国古人一个极大的创见,中国古人似乎早已看到将来世界人类演变,必然会有不拿血统做界线而拿文化做界线的新时代出现。[16]”在这里,钱穆突出了文化在民族定义中的决定作用。
从钱穆对历史、文化和民族这三个范畴的定义性解释来看,他用来解释历史与文化的这些概念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他用了人生、生命、经验、事业、活动五个概念来解释历史,用了人生、生命、生活、业四个概念来解释文化,在对民族的解释中,没有用较基本的概念,而是以文化来界定民族。其中,人生、生命两个概念是其共同运用的,也是其历史观中的基本概念。其它的概念是对人生和生命的规定和说明。那么,人生和生命及其关系是什么呢?他说:“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人类生命与其他生物生命不同的最大特征是,在求生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之存在,“人生正为此许多目的而始有其意义。”“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17]”人生有物质的与精神的,在精神人生中,又分为艺术的、科学的、文学的、宗教的和道德的。“人生始终是一个进展,向外面某种对象闯进而发现,而获得,而创新。……生命之实在,在于其向前闯进之对象中。向艺术闯进,艺术便是生命之真实。向科学闯进,科学便是生命之真实。若只有闯进,便是扑空,没有对象,便没有生命之真实性。照理闯进本身,使该是有对象的。人生最先闯进之途,只求生命之延续,其次闯进愈深,才始有求美求真与求善的种种对象。[18]”由此可见,人生就是生命,没有无生命的人生;但生命却不等于人生,必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的生命才是人生。而人生和生命必有一番经验、活动、生活和事业,尤其是精神上的经验、活动、生活和事业,即人生和生命的文化意义,质言之,文化的人生才是真实的生命,真正的人生是文化生命。
同时,从钱穆对这三者间相互的关系更具体和明确的阐释中,亦可看出其文化生命本体的思想,即他同样强调文化在三者中的质与体的地位和决定作用。
首先,关于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历史与文化互为作用,缺一不可;但文化是体,历史只是该体之相,即体之种种表现。他说:“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由于文化是人群大全体生活,“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19]”历史与文化“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历史,才有文化;有文化就有历史。但“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或说是现象,在现象背后则必有一体。看着种种相,自能接触到这个体。可是我们也该明白须有了这个体,才能发生种种相。”“我们可以说历史不同,就是文化不同。[20]”
其次,关于文化和民族的关系,钱穆认为,文化与民族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文化创造了民族和国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民族亦创造了文化。他说:“文化必有一体,主体即民族。如果我们说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而融成。照此说来,亦可谓文化与民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21]”不过,说民族创造了文化,这仅是从人在历史文化中的主体活动性方面来说的;至于众多个人的主体如何活动才能形成民族,还要靠文化来指导,文化创造了民族,即是从精神观念在民族形成中的决定性来说的。因此,“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某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22]”“我们可以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23]
可见,他说民族、历史、文化同一实质,实是从三者相互作用、互不可缺的关系来说的,并非是从三者的本末和体相关系说的。三者中,文化是本与体,历史与民族是末与相。当然,作为本体的文化是指精神和观念层面的文化。钱穆十分强调文化的终极精神性,虽然他把文化看成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但他说:“文化本身是精神的,仅存在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24]”文化是大群人生的一种“精神共业”。钱穆说,是观念创造了人类的一切,“当知人类一切进步,决定在其最先的观念上。观念不同,便出发点变了。出发点变了,便一切都变了。人类的一切创造,主要在其观念上,其他的进程很简单,自然会水到渠成。[25]”
而这一文化人生,即文化生命又不能是“个人”“各人之分别”“个己”“小我”“小”的,钱穆在解释历史、文化、民族时,用“我们(全部)”“大群”“人类集体”“(大)全体”“大我”“总体”“大”“共”等词对人生和生命作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词所要表达的终极意义就是指民族。脱离民族、社会和历史的个人人生和生命不是文化的人生和生命,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不能存在的[26]。故他用民族来限定文化人生,即文化生命的意义,最主要的在于它强调和突出了特殊性在文化人生,即文化生命存在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意义。“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有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分人类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中国史美国史之分。[27]”“各个群体人生,都有它们的相同处,这是文化的共相。然而各个群体人生亦有它们的互异不同处,这是文化的别相。所谓各个群体人生之不同,也可说是一种是民族性的不同。由于民族性之不同而产生了文化之别相。[28]”故他说:“文化乃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由此可见,在钱穆看来,撇开文化生命历史的民族性,单讲历史文化生命历史是空泛的、没有意义的。只有“民族”的文化生命历史才是实际存在和有意义的。他看到了文化生命历史的特殊性的根本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钱穆认为民族文化生命是历史的本体,在历史演进中起决定作用。所以说,钱穆的历史观不是一般的文化生命史观,而是一种民族文化生命史观。
二
那么,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的本质,即本体又是什么呢?是“心性”。
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其世界观的基础上的。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也是建立在其宇宙和自然大生命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从宇宙间天地万物到人生家国都是有生命的,“宇宙即不啻一生命,人类生命亦包涵在此宇宙大自然大生命中。物理神化,皆是宇宙大生命之所表现。[29]”从宇宙自然到历史人生之所以是一大生命体,在于它们是彼此依存的,“方其生,即依其他生命为养。及其熟,则还以养其他之生命。故生命乃一大共体,绝无不赖他生而能成其为生者。……则不仅一家一国一民族为群生,人之与禽兽草木同此天地同此会合而相聚,亦不啻相互为群生。此生命乃为一大总体。” [30]
“心性”则是其宇宙和自然大生命的主宰,即本体。从宇宙和自然大生命走向文化历史生命,心性之体贯穿其间,万古永存。
关于心,钱穆说,有生之物皆有心,人心源于自然,却又是一种文化心,但仍与天心相通,“而此共通之广大心,乃人类之文化心,则是后天生长的。此一个心世界,亦可称之为精神界。我们不可说此宇宙则只是物质的,更无精神存在。而此一精神界,则还是从宇宙自然界之一切物质中展演而来。故此人类文化大心,我们亦可说此乃心与天交心通于天之心。唯此由人类所创造出的精神界,即心世界,实则依然仍在宇宙自然界,物质界中,相互融为一体,而不能跳出此自然宇宙,而独立存在。”[31]心本一体,但若要象西方人作“智情意三分说”的话,则意志应作最先一分看。其次是情感,亦是与生俱来。“人类由自然人进入文化人,比较上,欲日淡,情日深,此是人生一大进步。”“理智应属最后起。应由情感来领导理智,由理智来辅成情感。即从知的认识言,情感所知,乃最直接而真实的。理智所知,既属间接,又在皮外。”[32]他又说:“心亦有其生长,亦可谓心亦有生命”,人类所创造的新的物质世界,亦是一种心的生长;“人类的心生命,乃寄存于外面之物质世界而获得其生命进展者,均在此宇宙界。凡寓人类所创造之新的物质世界中,则莫不有人类心的生命之存在。”[33]这即是说,人心创造了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之本是人心。
关于性,钱穆说,决定宇宙自然界和由大宇宙展演而来的心世界的成立、存在和变化之最高主宰和最高真理,“中国人称之曰性。中国人极重此性字,认为不仅生物有性,无生物亦有性。”万物原于天地,万物之间有一大共通,“此一大共通即是天,故曰天命之谓性。”“好生求生,此乃生命界共同之性。”“生命是一大共通,生命界之心与性,亦有一大共通。人类生命又是此生命大共通圈中一小共通。人性乃由天赋,故曰天性。人心最灵最能表现出此性,即是最能表现出此天。故曰人性善。”[34]他说,中国人为要表示其生命与禽兽草木一切生命之不同,牵连着说性命,即用心生命两字来代替生命,这便包涵着极深的思想结晶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一、人性既是禀赋于天,因此在人性之中即具有天。二、天既赋此性与人,则在天之外又别有了人。……人之所谓代表天者即在人之性,而天之所以高出于人之上者,则在天之命。”[35]所以说,“性即是一个天人合一。排除了人,于何见性,亦于何见天。欲知生命真谛,先须知此小我之小生命。此一小我之小生命,乃自外面大自然大生命中来。但仍必回到外面大自然大生命中求持续、求发展、求完成。……而大自然大生命,亦待此小我小生命为之发皇滋长。天人内外,所当合一以求。” [36]
心与性,钱穆认为性是更自然化的,属于天,由性展演出心;心则倾重于人文化的,属于人,其各有功用,“心固由性展演而来,但性只属天,而心则属于人。由性展演,乃是自然天道。由心展演,乃有文化人道。即论科学艺术亦如此。……至于人类以心交心,创出一套真善美合一调整之理想人类文化,而天地变色,宇宙翻新,其事更值重视。”[37]但他说心与性、实即人文与自然实是融通合一的[38]人生文化理想,不能有外无内或有内无外,贵能内外合一[39]正是心和性的融通与合一,才使宇宙自然和历史人生能融通和合为大生命。他说:“孟子日:‘尽心知性,尽性知天。’天由性见,性由心见,此心有明德,明明德于天下,此即由小生命扩大而为大生命。”[40]因此,心和性虽有别,但却不可分开看,心性实是一体的,一体的心性方是贯通宇宙自然和历史文化生命体的主宰和本体。
三
“心性”之体在文化历史演化中的“用”,便是心性决定论和动力论。具体说,心性对历史文化的这种“用”表现为:
首先,历史文化由心性发源和展演。钱穆说,心是广大悠久,超个体而外在的,“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41]“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42]“情感的背后便是性。唯由天赋,故称天性。情从性来,性从天来,一切人文都从自然来。”[43]“人生大道,人类文化,必从各个人之自性内心人格动力为起步。”[44]又说:“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因此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45]孔孟立教,似乎把仁义礼智看成是人类的原始本心,“此等原始本心,乃得自天赋,由自然界来,却可由于演出人文界种种事为,而发荣滋长,迄于无穷。” [46]
其次,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钱穆说,长时期历史演进中一切事都像是偶然的、突然的、意外地产生的,然而实在有一种精神在指导,即“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47]“历史文化之演进,其背后常有一抉择取舍之指针,此指针即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48]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而这个心和性,是确实会向着善而前进的,因此历史也确实会向着善而前进,文化也确实向着善而前进,……这套理论与信仰放到政治上、社会上、经济、教育一切上,来完成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领导精神了”。[49]
再次,心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演化的推动力和机括。钱穆说,“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50]讲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是一个社会背后的推动力,这是把社会的推动力看成是外在的了,“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51]又说,各民族文化体系不同,其文化力量之发现与其运使,有重外和重内、重上和重下、重大群和重个人之别;中国文化极注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重心在人心,心转则时代亦随而转,“所以各人之正心诚意,成为治国平天下之基本。……因此历代文化之进退升沉,虽其最显著的迹象必归宿到政治经济军事之基层,但求其渊源,最主要的还是在学术思想,信仰风俗,深著于人心内部之一面。”“中国人认为经济军事须由政治来领导,而政治则须由教育来领导,故道统高出于政统,而富强则不甚受重视。故在中国人说,文化之进退升沉,则只是道之进退升沉而已。今人所谓之文化,中国古人则只谓之道体。明白到此,则文化之进退升沉,其权其机括,乃在个人身上,个人心中,可以不言而喻。”[52]钱穆所以写《中国思想史》,是因他认为“此(指文化观念——引者注)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 [53]
要说心性是钱穆历史文化生命之本体,固然不错,但仍未说到尽头。在钱穆看来,心性的人文意义在于其道德性的“仁”。仁是心性之本和终极归宿;说心性创造了历史文化,实即是仁创造了历史文化。钱穆说,仁乃孔子思想之本,儒道即是仁道;孟子对仁的阐释最精到:“一日仁,人也。二曰仁,人心。三曰仁者爱人。仁为人心之同然,人心必皆仁,故仁即是人之特性之标帜。其心不有仁,即不得谓之人。心具此仁,则必爱人。”[54]宇宙造化之本体——心性,即是仁,“要之天地之道即是一个仁道,以其能生万物,又能生生不绝。既是仁,故又谓之心。人生天地间,故能具此仁心。”[55]仁虽是普存于天地万物之间的,但仁的作用主要则体现在历史文化生命的演进上,他说:“孔子当时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则礼乐之本皆在人心之仁。周公修礼制乐,治平天下。顺一家之心斯家齐,顺一国之心斯国治,顺天下之人心斯天下平,其本亦在仁。”[56]“故朱子曰:仁是天地之生气,又曰: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此心藏在人性中,则作用更大,人之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者正在此。”“人文生命,发展完成于心之仁。此心之仁,则广及古今中外之全人类而不可死。若仁心死灭,则人道亦绝。回同于禽兽。亦将不获如禽兽。”[57]
由此可见,从最根本上说,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本体论,是一种以道德性的仁为核心和本质特征的心性本体论。简言之,即是仁的心性本体论,亦可说是仁之本体论。
四
钱穆提出这一仁的心性本体论,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其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有其时代意义、文化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同时,亦有其很大的局限与不足。
钱穆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和大转型的时代(他生于1895年,1990年故去),其一生几乎经历和目睹了中国社会在本世纪的种种风云变幻。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走什么样的民族救亡和复兴道路?钱穆要回答的正是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他提出的心性本体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则是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论立足点。
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界、文化思想界对中华民族救亡和文化复兴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但总的说来其道路不外这么几种:一是完全拒斥西方文化,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吸收西方文化;三是以西方文化为本,又不放弃中国文化;四是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后两种民族救亡和文化复兴道路,即西化道路,在本世纪的前五十年成为主流。而且这一文化价值取向此后也没有根本改变。这种救亡复兴的道路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在本世纪初乃至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文化价值意义的,它肯定了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各民族历史文化生长发展中相互交流融合的必要性,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做出了贡献。但这种救亡和复兴的道路和价值取向,有着致命的缺陷和不足。它忽视了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同文化的不可替代性,看不到各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长处及其在民族文化更新中的作用。它实在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翻版。这条道路在实际上是走不通的。百余年中国社会变革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实践和世界各民族国家在近现代变革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
钱穆却一反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文化思想界的主流,提出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要走“据旧开新”的道路。“求变趋新,不该反历史。若把以往历史一刀切断,都是死灭,非新,亦非变。变与新仍须一根底,此根底即是历史,即是文化传统,即是民族之本身。只有从历史中求变,从文化传统中求新。从民族本身求新生命,仍在与古人通气之中救今之人再造。”[58]这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吸纳和融合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的道路。而史学被他视为是民族文化的根本,要复兴民族文化,就要复兴史学。他说,史学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也可以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59]又说:“欲治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主要即在其历史,昧忽其历史实迹,则一切皆于虚谈。尤其中国史学,乃更易见我所谓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所在。”[60]中国今天正处于积衰积病之中,如何起衰治病,应该有一套办法,“我们今天发挥史学,正该发挥出一套当前辅衰起病之方。识时务者为俊杰,史学可以教人识时务。史学复兴,则中国必然有一个由衰转兴之机运。”[61]而中国要复兴的史学则是一种有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和生命的史学。他说;“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我们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62]他说:“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63]由此可见,这种史学观显然是建立在其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和特征的历史观——以仁为核心的心性本体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基础上的。换言之,是其心性本体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了其史学观乃至文化观。因此,心性本体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具有批判走西方模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它看到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的意义和其自身的生命力在一个民族文化存在和更新中的作用和不可替代性。这在今天看来,确有其重要历史意义和历史文化上的理论价值。
不仅如此,钱穆的心性本体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还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同样带有“西化”的色彩。它们或者根本反对探讨历史观和历史本体问题,如各种实证性的史学。它们将史学看成是可以完全排除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的纯科学化的学科,认为史学的客体——逝去的历史是绝对独立和外在于史学主体的。那些承认历史观及其本体存在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的史学派别,则大多基本肯定和接受西方的历史唯物论或历史唯心论思想,并以西方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历史观及其本体思想进行评判。它们未能对如何将西方历史本体思想和科学的历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关思想加以融合,以创造出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史学理论真正作冷静、深入的理性思考。这两者的一个共同点是:在对中国传统史学有关历史观及其本体思想的态度和作法上是,“批”和“破”重于“承”和“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输入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之功的,对中国史学和历史理论如何适应社会变革,由传统走向现代是有理论贡献的。
但中国史学由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之路,是无法抛离传统史学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心物一原论、心性本体论和天人合一的大生命观,和中国史学的历史观及其历史本体论是融通为一的。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特点是:经史一体,六经皆史;经以论道,史以载道。钱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其以心性为本体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对此作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他反对心物两分的本体论,说:“西方有唯心论与唯物论之别。而中国则谓心物同体,心物一原。凡物各有其德其性,即其心。宇宙同体,则互显己德以为他用。非毁他德以供己用。”[64]如上所述,他认为,历史就是生命,是民族文化之生命。心性,即文化精神是历史的本体和主宰,历史只是心性之展演及其表现与成果。但“体相不二”,无历史,亦无民族文化精神。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种思想看到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主观内在的心与客观外在的物只有合一,外在的物——客体对内在的心——主体才有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他主要是想强调心性在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并要解决心物的两分和对立。同时,他反对把历史看成是历史研究主体的“心”的演绎,如他说:“当然像马克斯讲历史,他也是主张有一种指导力量的,只是此项力量是惟物的。赫格尔讲历史,则是惟心的。他们都先立定下一种哲学理论,再拿历史来证明。我们现在所讲,则要根据历史本身来寻求有没有这一种指导全部全历史进程向前的精神。”[65]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固然是错误的,但他的话却说明,他是在历史进程本身去寻找历史的本体。他还说人文从心性来,而心性从自然来,人文只是自然的产物,历史人物是自然与历史环境的产物。他说:“故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之所以分别出生在中国、印度和耶路撒冷,是因“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在内”[66]。另一方面,其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心性本体论又决定了他的史学观。他认为,史学是生命之学,史家在接触和研究已往的历史时,不仅要有史家的主体意识来体验与通达古今,还要有史家的是非褒贬和爱憎情感融入其间。史学主体也必须对历史客体有“心”的投入,才能体验和认识历史。这即是说,史学主体须要和历史主体的心相融通,史学主体的生命要融入历史的大生命之中去,历史大生命才能被我们认识和把握。不然历史便无法被我们认识,史学也成了死学问,于我们的大生命毫无意义。这既把史学主体的小生命和的历史文化的大生命融为一体,又指出了史学存在的前提——为民族文化的生长演进服务。史学不再是一堆“断烂朝报”,也不是任人随便摆弄的“大钱”,亦不是少数政治集团的“玩偶”和政治“婢女”。钱穆的这些思想在近现代史学理论中是独树一帜的,为中国近现代史学有关这一理论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钱穆的心性本体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亦有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首先,他的这一理论体现出其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和历史文化思想保守的一面。他虽然说西方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是两大体系,各有所长,但他常常贬低西方历史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褒扬赞誉有加。他爱对中西历史文化作比较,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对西方历史文化并无亲身的感受体验和深入研究,却情绪化地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从根本上比西方历史文化好,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向就是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路向。这类言论充斥他的著作之中,此不赘引。这种中国文化优越论和至上论是不可取的。其次,由于他的上述思想和为学中过分强化人的主体意志和情感,使他在探讨历史观及其历史本体论的问题时,只重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历史学中这方面的积极与合理的东西,很少考虑吸收西方的东西。同时,他对西方历史观及其本体思想的认识及批判常作一种主观臆断的说法。这便使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这实际也是他整个思想的一个特征。再者,他的心性本体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亦有其内在的矛盾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他既说人文原于自然,承认自然和历史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又说心性、精神文化和观念之类的东西是历史文化的本源、推动力和决定力量等。他虽对心物一体、人文和自然合一作了大量阐述,但他基本是从“心”这一主体方面来统摄物,以图说明两者的统一和合,他也没有探讨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主体实践活动与“心”和“物”的明确关系。因此,他并未根本解决两者存在的对立。
注释:
[1]《中国历史精神》,邓镜波学校印刷,香港,1964年增附三版,第1页,第4页。
[2]《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长春,1991年4月,第1050页,第1051页。
[3]《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10月,第1页。
[4]《中国历史精神》,第5—6页。
[5]《民族与文化》,新亚书院,香港,1962年2月再版,第43页。
[6]《文化学大义》,正中书局,台湾,1952年1月,第4—6页。
[7]《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8月初版,第13页。
[8]《中国历史研究法》,孟氏教育基金会,香港,1961年12月,第109页。[9]《中国文化丛谈)(l),三民书局,台北,1984年9月第6版,第66—67页。
[10]《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8页。
[11]《文化学大义》,第4页。
[12]《晚学盲言》(上),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7年7月初版,第185页。
[13]《中国文化精神》,三民书局,台北,1973年1月再版,第51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9月,第568页。
[14]《中国文化丛谈》(l),第51页,第52页。
[15]《民族与文化》,第35—36页。
[16]《民族与文化》,第46、45页。
[17]《人生十论》,人生出版社,九龙,1963年3月第三版,第1页,第19—20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43、546页。
[18]《湖上闲思录》,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4年1月再版,第113页。
[19]《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8页,第109页。
[20]《中国文化丛谈》(1),第29页,第32—33页。
[21]《民族与文化》,第43页。
[22]《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第31—32页。
[23]《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13页。
[24]《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0页。
[25]《民族与文化》,第51页。
[26]《民族与文化》,第41页。
[27]《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28]《中国文化丛谈》(1),第52页。
[29]《晚学盲言》(上),第55页。
[30]《晚学盲言》(上),第427—428页。
[31]《中国文化丛谈》(2),第207—217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475页。
[32]《双溪独语》,学生书局,台北,1981年1月初版,第171—172页。
[33]《中国文化丛谈》(2),第207—217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474—475页。
[34]《中国文化丛谈》(2),第218—222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476页。
[35]《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求精印务公司,九龙,1962年3月再版,第18—19页,第483—484页。
[36]《双溪独语》,第4页。
[37]《中国文化丛谈》(2),第218—222页,第477—478页。
[38]《晚学盲言》(下),第648页。
[39]《双溪独语》,第234页。
[40]《晚学育言》(上),第194页。
[41]《湖上闲思录》,第8页。
[42]《双溪独语》,第27页。
[43]《晚学盲言》(下),第641页。
[44]《双溪独语》,第105页。
[45]《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72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603页。
[46]《双溪独语》,第200页。
[47]《民族与文化》,第71页。
[48]《历史与文化论丛》,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5年9月,第58页。
[49]《民族与文化》,第87页。
[50]《中国历史精神》,阳明山庄,台北,1983年9月,第34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第》,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602页。
[51]《中国文化丛谈》(1),第106页。
[52]《中华文化十二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5年11月再版,第64—65页。
[53]《国史新论》“自序”,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1年2月,第1页。
[54]《双溪独语》,第32—33页。
[55]《朱子新学案》(上),巴蜀书社,成都,1986年8月,第245页。
[56]《晚学盲言》(下),第933页。
[57]《双溪独语》,第52页,第37页。
[58]《中国文化丛谈》(1),第173页。
[59]《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4页,第75页。
[60]《中国学术通义·序》,台湾学生书局,台北,1976年3月再版,第6页。
[61]《史学导言》,载《中国史学发微》,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9年3月,第64页。
[62]《中国历史精神》,第5页,第6页。
[63]《国史大纲》“引论”,第11页。
[64]《晚学盲言》(上),第153—154页。
- 上一篇:药学创新论文范文
- 下一篇:交通工程职称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