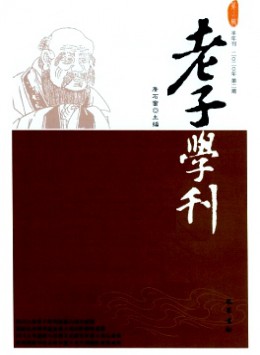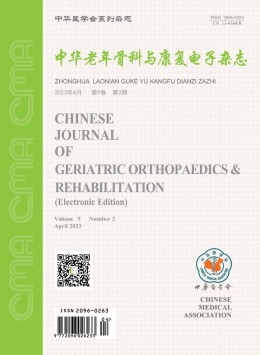老子的名言精选(九篇)

第1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1、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2、绝学而无忧。
3、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4、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5、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第2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关键词:名;道;生命践履;强为之容
近百年来,中国先秦道家语言观在一定意义上可谓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复兴。这里无意于重复著名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说的提出者对老子之“言”的解读,而是尝试着从“法自然”之“道”和行“无为”之“教”来重新把握“言”的性态、发用和方法。
一、言之“性”:“玄”
老子对语言或言语的性态的把握与他对“道”的体悟相辅相成。“玄”既是“有无相生”或“有无”同体的“道”的根本,也是与“有无相生”或“有无”同体的“道”相通的“言”的根本。
《老子》一书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段话可以说是老子论“道”的总纲,也是老子论“名”或论“言”的总纲。其中,“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通常有两种读法,一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也有两种常见的读法,一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一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在我看来,这些断句除了或者更多突出“道”同“无”与“有”的关联,或者更多突出“道”同“无名”与“有名”、“无欲”与“有欲”的关联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领会这一章中“无”与“有”、“无名”与“有名”、“无欲”与“有欲”与“道”的关系。
“道法自然”闭,“自然”之“道”自是其是,自然而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网,它永远无意于有所作为,却又无所不予成全。这种成全不是一种他律的强加,而是让天地万物自己化育自己、自己匡正自己,所以天地万物中唯一能返观自照的人也这样形容自己为“道”所成全的真实感受:“百姓皆曰:我自然。”“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闭,它“自因”、“自性”而又“无方”、“无体”——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自己是自己的根据,它显现于天地万物的“白化”、“自正”,却不为生灭不已的经验事物的任何形体和情境所牵累。就它见之于事物的“自化”、“自正”,对天地万物无所不予成全因而“无不为”而言,它有“有”的性向;就它没有边界、没有形体,永远无意于有所作为因而“常无为”而言,它有“无”的性向。“道”因为“无”的性向而显得惚恍、窈冥而难以摹状、不可形容,因为“有”的性向而显得真确、可信而可以默识冥证、勉强形容。如果把涵纳了“有”、“有名”的“无”、“无名”譬喻为天地万物的本始,那末涵纳了“无”、“无名”的“有”、“有名”则可譬喻为天地万物的生母。从“道”的无所意欲、从“道”的“无”的性向、从“道”的惚恍、窈冥而难以言喻上,可以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从“道”的有所意欲——让天地万物自己成全自己、从“道”的“有”的性向、从“道”的真确可信而可以勉强形容上,可以去观察、领悟“道”呈现于经验事物生灭过程的行迹。“无”与“有”原只是“道”的同一性向在不同角度上的两种称谓,“无欲”与“有欲”、“无名”与“有名”则是这两种性向在不同场合的随机表达。其中,“无”与“有”侧重于“道”之性本身,“无欲”与“有欲”着重于“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无名”与“有名”偏重于“道”与“名”或“言”的关系。
吊诡的是,“大道不称”、“道昭而不道”,“道”一旦被命名、被表述出来,那被命名、被表述的就不再是“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的“常道”或恒常如如的“道”了。因为言说总是起于对经验事物依类命名的“共相”意识,被命的“名”在对事物的某些特性有所敞开、揭示的同时往往不免对它的其他特性有所抽象和遮蔽。“道”这个名既然是可以称呼、可以明白说出来的有所局限的“名”,那它也就不再是与体悟中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无所局限的“常道”相称的“常名”或无所执定的“名”了。此即所谓“道常无名”、“道隐无名”。因此,老子也倡导人们“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言为念,永远无意于言。“不言”之教即“默”教,“行不言之教”亦即在“不言”之中去体会那种难以言喻而唯可神会的“自然”之“默”、“无为”之“默”。
不过,天地万物取法于“道”或师法于“自然”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已经过深地陷于文明濡染的人却不能不自觉地日损其欲念以致“自然”之“道”,此即所谓“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欲不欲”,“学不学”。这个过程,既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圣人不得已以身作则,为众人示范的过程。也是取法“自然”之“道”已臻于化境的圣人不得已以“言”启发众人的过程。所以,老子在强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后仍要去强“道”那不可道之“常道”,强“名”那不可名之“常名”。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老子》十五章所说的“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以及二十五章所说的“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老子在指出常道不可道、常名不可名后仍自觉地去强“道”、强“名”,他的所“道”、所“名”实际上还蕴涵了另一重没有明言的用意:人们切不可执著于他的所“道”、所“名”,而要透过这些强“道”、强“名”去体悟那不可“道”者、不可“名”者,此即要由“言”而“不言”、由“言”而“默”。“道”不仅“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不当名”,连提示人们“道不可闻”、“道不可见”、“道不可言”、“道不当名”的“言”、“名”也不可执,庄子后来在《知北游》里把这层意味提炼为比“有无”更彻底的“无无”。在老子那里,“言”,就它是为了引人达于取法“自然”之“道”的自觉、为了让人“白化”、“自正”、“自朴”而“有谓无谓”(终身说不可执著的话)而言,它涵贯了见之于天地万物的“自化”、“自正”、对天地万物无所不予成全的“道”的“有”的性态,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发生、措意、展开的过程。就它无所执守、不以言为念而“无谓有谓”(终身不说执著于一端的话)而言,它涵贯了无所依待、永远无意于有所作为的“道”的“无”的性态,以“不言而善应”为归着。因此,堪与“玄”道相称的“言”可以说是“玄”言,“言”的生机尽在于“无”与“有”、“默”与“言”的相即不离。
不过,老子之“道”既然不可道破,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的老子之“言”是否只是一种妄言呢?这问题把我们引向对老子之“言”的发用的注意。
二、言之“用”:言“不言”
在老子那里,“言”因着“有”或“为”的性态,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发生、措意、展开过程,又因着“无”或“无为”的性态,其发生、措意、展开终究又以“不言”为旨归。言说本身的发生、措意、展开,可谓“言”的“有”的性态的发用,言说本身以“不言”为旨归,则可谓“言”的“无”的性态的发用。正如“言”的“有”的性态与“无”的性态玄同一体,“言”的这两种发用也是“同出而异名”。不过,探老子本意,“言”的发用更重要的还在于与“言”的发生、措意、展开同时就有的“不言”。
《老子》二十七章阐示“道”的发用“袭明”时曾以举例的方式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无辙迹”的“善行”、“无瑕谪”的“善言”、“不用筹策”的“善数”不能没有行走、言说、计数这些活动之“有”,同样,“无关楗而不可开”的“善闭”、“无绳约而不可解”的“善结”不能没有关闭、打结这些活动之“有”。但对于“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这些“道”之“用”来说,重要的显然还在于人发出这些动作(“有”)时那种因任自然的“无”。正因为徜徉于尘垢之外,悠然而来,悠然而往,所以才不遗下任何刻意行走的车辙、轨迹。正因为不执著于言,所以才不留下任何概念性语词可能带来的偏于一端的瑕疵、缺点。正因为依自然之道,顺万物之性,应合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后,晓悟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所以才不用筹策等计数工具就能算尽万事万物。正因为因循事物的常情,葆全事物的天性,不强闭以为闭,不强开以为开,不强结以为结,不强解以为解,所以才不需锁、钥关闭就能不留下任何可人之隙,不需绳索打结就能不留下任何可解之处。所谓“袭明”,即是圣人深入地体察上述情形后所悟出的一个上贯宇宙下通人生的道理:因循自然。按照它去行动,就能使森罗万象和天下百姓都各得其所、各尽所长而没有一人一物不得到成全。在“道”的这些发用中,“有”和“无”始终是浑然一体的,但“无”对于“有”无疑更为根本。没有了“有”,“无”的意义无从体现,但“无”只是隐而不显,并没有与“道”相悖;没有了“无”,“有”固然还是“有”,但这是与“道”背道而驰因而充满了意欲的圭角的“有”,而不是作为“道”之“用”的不着痕迹的“有”。就“言”而言,不执著于言,才能消去概念性语词可能带来的察于一端的偏颇,才能真正对“道”有所言。“不言”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得意之后的忘言或对言的弃置,而是与“道”相称的“言”所以能发生、措意、展开(“有”之“用”)的契机。
“不言”之言或无所执著之言,是为了引导人们“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不得已才有的“言”。“言”的言外之“默”提示着人们,“不言”作为“玄”言的性态的发用之一,不是肆意妄言,它的一个当有之义是“贵言”或“慎言”。“希言自然”,即是“慎言自然”。《老子》十七章指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为什么那种百姓只知道其存在的君主才是德行最高的君主呢?那是因为在这么多的君主当中,惟有他才摆脱了肢体之欲和耳目之思的牵累,不为功绩所动,不为名声所诱,惟有他才出语谨慎,不轻易倡导,也不轻易禁止,以免搅乱百姓的心思。在他的治理下,百姓的天性没有遭到丝毫的戕贼,他们做成的每一件事,取得的每一次成功,无一不是顺着他们禀受于“天”的自然之“性”自然而然地达到的。从“下知有之”的“太上”,到“(下)亲而誉之”的“其次”,再到“(下)畏之”的“再次”和“(下)侮之”的“再其次”,是老子对君主的德行从高到低的排列,他所采用的准绳即看其是否做到了“悠兮其贵言”。在“贵言”或不轻易出言里,有一份对可体悟而不可言说者在被言说时可能毁于语言的敏感。懂得了言辞能传达的和不能传达的,明白了言辞所固有的局限,才可以免于因执著于言辞而可能带来的与“道”相违的危险,真正做到不执著于言辞。在老子的理境里,不执着于言与不轻易出言是可以相互诠释的。
耐人寻味的是,集“不执着于言”与“不轻易出言”于一身的“不言”之言,正寓托着与不可道的“常道”相称的不可名之“常名”。通常,人们都把“常名”理解为在“名”或概念性语词之上或之外的一种抽象、神秘的“名”,其实它与其说是又一种“名”或概念性语词,不如说是一种让“名”或概念性语词“使其自己”虚灵不滞的动势。对这一点,可以借助庄子在《齐物论》里谈到的“地籁”、“人籁”与“天籁”的关系来理解。地籁是自然之风游走于众窍所发出的声音,人籁是人的气息鼓荡于乐器而发出的声音,天籁不是与地籁、人籁有别的另一种声音,而是对地籁、人籁依其自然本性的没有任何意欲的成全,此即所谓“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在庄子看来,无论是风吹万窍发出不同的声音,还是人吹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都是有此窍就有此声,有此器就有此音,这些声音无一不是由于众窍和乐器自身的作用使然,是自己使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并没有谁主使其中,对它们进行发动。这种让地籁和人籁“使其自己”的动势,即是天籁,或者说其名词化的结果即是“法自然”之“道”在声音领域的别名——天籁。同样,集“不执著于言”与“不轻易出言”于一身的“不言”之言,也是自己使自己不陷于任何“名”或概念性语词可能带来的端崖,它对“常道”的特性无所抽象、无所遮蔽而“连犿无伤”。这种让“名”或概念性语词“使其自己”的动势,这种对“名”或概念性语词依其“言为心声”的自然本性的没有任何意欲的成全,其名词化的结果不正是与“天籁”相通、与“常道”相称的“常名”么?正如“无所不在”的“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一样,又如天籁也在地籁、人籁一样,“常名”并不在对“名”或概念性语词依其自然本性的没有任何意欲的成全之外另有存在,换言之,“不言”之言本身即有“常名”,深入体察任何一句自然而然地发生、措意、展开的话都可以发见玄深的“常名”的踪迹。因此,从对“名”或概念性语词无所执著的凑集结果——无所执著的言语或内蕴了“无”之“用”的“言”的“有”之“用”——上,就可以去体味不可道的“常道”的意趣。这用《老子》的话说,即是:“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并没有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切断了“名”或概念性语词通往超越的“形而上者”的道路,而是另辟蹊径,此即,从对“名”或概念性语词无所执著的“形而下”的使用中所获得的诸多意义上,即可以去体味它们曲折道出的“形而上者”的意义。
不过,对“名”或概念性语词合其自然本性的成全并不完全等同于对地籁、人籁的成全,这里还涉及对“名”或概念性语词固有缺陷的克服。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老子之“言”的方法。
三、言之“方”:“强为之容”
不以言为念不是肆意妄言。谨慎而无所执守地言,除了需对所言之“道”有非同寻常的体悟外,还需对言说方式本身有深刻的洞见。在老子看来,这种方式即是“强为之容”。
《老子》十五章指出:“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这里的“识”是“认识”,它相系于句读有则的语言,必得诉诸概念、判断、推理;这里的“容”是“形容”,它借重由概念性语词构成的具体意象而使人径直领悟某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味。如果没有概念性语词或语言,人们将无从指认一类事物中的任何事物;而如果运用概念性语词或语言,人们在对某一事物进行指认时,在对它的某些特性有所揭示的同时总会对其他的特性有所遮蔽,在把它区别于同属事物中的其他种事物的同时,总会又把它混同于同种事物中的其他事物。“道”不是某一具象的形而下的存在物,它毋宁只是一种对天地万物无所不予成全的虚灵的动势,就其“无方”、“无体”而不牵累于任何有形事物和情境而言,它是形而上的。人们耳目所及的皆是形而下的具象的存在物,对“道”的描述不能不借助对人们所熟悉的形而下者的描述,此即所谓“拟物而谈”,亦即拟形而下的事物谈形而上的“道”。形而下的事物遂成为生活在有限世界的人喻示形而上的“道”所不可缺少的“象”。如果说具象的存在物与概念性语词或语言是隔着一道沟壑的话,那末“道”便与概念性语词或语言隔着两道沟壑。通过对概念性语词或语言合其自然本性的成全而以“名”言“道”,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古代善于师从“自然”之“道”的士,其言、默、行、止无一不幽微精妙、玄奥通达,他的涵养深广博大,难以用平日使用的概念性语词直接进行准确指认,从而让更多的人领会到“道”的意趣。正因为对得“道”之士的描述不能不借助概念性语词,而这种有着特殊旨归的描述又不能不既顾及概念性语词所固有的落于一偏的缺点,又顾及人们总是惯于从形而下者去把握形而上者的习染,所以老子才勉为其难地用它们构成一个又一个意象,比如,“豫兮其若冬涉川,犹兮其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老子希望通过“强为之容”即勉为其难地对得“道”之士进行“形容”这种间接的方式,把人引向对“道”的晓悟。
对如何克服概念性语词仅仅只能部分把握形而下者的弊病这一点,庄子曾就如何描述“法道”的“事物”作出过完整、深入而精彩的展开。《寓言》篇指出:“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日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这是在说,内蕴“自然”之“道”的事物自己规定自己的性质,自己作为自己的原因,自己是自己的根据,它的“可”与“不可”、“对”与“不对”都有自己的缘由。对它来说,什么是“对”与“不对”、“可”与“不可”呢?凡是与它的自然天性相应和的就是“对”,就是“可”;凡是与它的自然天性相违背的就是“不对”,就是“不可”。事物总是自适其性,有其“对”的、“可”的道理。没有一件事物没有“对”的、“可”的道理。所以说,事物依其自然本性而存在着,有它自己的道理。言说总是在对事物的某些特性有所凸显的同时又不免对它的其他特性有所遮蔽,在把它区别于同属事物中的其他种事物的同时又把它混同于同种事物中的其他事物。不去言说事物,事物始终是完备的,这种完备的状况与对它的言说是不一致的。因此,在言说时不要执著于言语。如果说的是不执著于一端的话,那末虽然终身都在不停地说,却也未尝说过有悖于事物完备性的话。反过来,即便不曾对它有所描述、有所言说,只要始终守护着事物的完备性而使它免遭戕贼,却也未尝不是在言说,未尝不是在显示。如果能了悟到事物是完备的,同时还能对言语本身的局限不断进行反省、检点和消除,懂得说出的话应该就像“卮”这种酒器一样倾仰不定而不执一守故,那末,不论“卮言”怎样时时出现,它都会无碍于事物的自然本性,无碍于它的完备性,都会与寓于万物运作之中的“法自然”之“道”的分际相应和。除了“卮言”,还有什么话能生机永不凋谢而做到流传久远呢?庄子在这里所说的“言无言”,即是老子所说的“强为之容”,他所说的“卮言”,即是老子所说的“无瑕谪”的“善言”。而他就如何描述“事物”来提示人们如何描述为事物师法的“道”所说的一席话,则恰好是一种“拟物而谈”。
“强为之容”或“拟物而谈”对老子来说,并不仅仅是所谓言说的技巧。就它是勉强与“道”的底蕴相称的言说方式而言,它也是老子这个性情真切而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隐君子”的言说特征。《老子》一书随处可见对“道”或得“道”之“士”的形容,其中对得“道”之士的精神境界的形容最精妙的莫过于十五章和二十章,对“道”的境地的形容最出神入化的则当数十四章和二十一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嗷,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前一段文字通常被人们用来证明老子之“道”是一种精神实体,后一段文字则通常被人们用来证明老子之“道”是一种物质实体。其实,这两段话都不是老子对“道”下的定义,而是老子对“道”之“玄”——“有无”同体一的形容。“道之为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用黄克剑先生的话说都是在“拟物而谈”,是借助“有象”、“有物”、“有精”的具体事物这个意象,来形容“道”虽然“惟恍惟惚”、“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无形无体、无所意欲,却真确、可信,确凿、可靠。“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其上不嗷,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无状”、“无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也是“拟物而谈”,借助可“视”而“见”之、可“听”而“闻”之、可“搏”而“得”之、有“嗷”有“昧”、“绳绳兮”犹可“名”、有“状”有“象”、迎之可见其“首”、随之可见其“后”的具体事物这个意象,来形容“道”虽然对天地万物无所不予成全因而显得有所意欲,真实不妄,却毫无造作,没有丝毫刻意的痕迹。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对“道”生成宇宙的一种描述,而是借助能代代相“生”的生物这个意象。来形容“道”因其内蕴了“无”的“有”的性态,对天地万物无所不予成全,天地万物的“生”机尽系于对“自然”之“道”的默守。可以说,把握了老子的“强为之容”或“拟物而谈”的言说特征,就等于掌握了进入《老子》一书的钥匙。
四、结语:几点启示与评说
(一)老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文胜于质”而流于“文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礼”、“乐”起初是为了陶冶、润泽人的质朴而未免粗野的元始生命而创发的,但在后来,随着“礼乐”之“文”的逐渐隆盛和人的质朴的真性情的逐渐丧失,“礼”、“乐”失去了内在精神而成为外在的缘饰。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面前,老子选择了“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道路。老子之“道”从人得之于“天”的自然本性说起,“朴”是老子学说的一种终极性的人生价值祈向,在“朴”的导引下对德性践履的反省和匡正促成了与老子之“道”相应的老子之“教”。对这一有着鲜明的价值弃取态度的德性之“教”的倡导,是老子之“言”的始,也是老子之“言”的终。以关联着人生的终极眷注的“道”为依托,使老子之“言”自始即是在与虚灵的价值祈向相系的德性践履中才可能萌生的言语。在老子这里,纯然认知意义上的割断与人生践履之关联的“言”,或者只是与想象力和情感有关的“言”,都不是真实人生中的“言”,不是——借用现象学的术语——作为“事实本身”的“言”。老子之“言”是以德性向度上的实践理性为主导的“言”。
第3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关键词]老子;绝对的“无”;否定性的“无”;中西哲学
[中图分类号]B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2-0029-03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次将“有”与“无”作为纯概念进行专门的讨论。老子认为,天地万物这些被人们视为真实、实在的东西,都是“无”和“有”被命名后,才在思维中被建构起来的。在老子看来,“无”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绝对的“无”,一是否定性的“无”。老子还提出了两个层次的“无”之为(用):第一个层次是与“有”对应的“无”之为、之用,这是与存在、存在者(物)相关的“无”之用。第二个层次是讲人也就是主体不过分作为,要顺从自然。老子对“无”的洞见,奠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根基。
一、绝对的“无”及其作用
《道德经》第一章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一章历来被视为《道德经》的总纲。在这章中,老子首先提出了“道”和“名”两个重要概念,且将它们并列,显示了老子对“名”的重视和肯定,这与后世学者认为老子否认和抛弃“名”的说法恰恰相反。当然,老子也强调了“可道之道”即通过“名”、语言表述出来的“道”,“可名之名”即通过语言说出来的语言之“名”并不是“常道”、“常名”,揭示了知识不能得到真理即知识是相对正确的和语言与“名”的有限性特征。紧接着老子讨论的是“名”而不是“道”,这尤其应引起我们的警觉,老子对“名”的重视令我们震惊!这是因为对人来说,“道”是通过“名”来展现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真理是述说的观点是一致的。①
随之,老子接着讨论命名的“有”和“无”的问题。老子说,将“无”命名为天地的“始”,将“有”命名为万物的“母”,但“有”本身不是万物。在“道”、“名”之后,老子又提出了“有”和“无”这对重要的概念,指出它们是命名的。命名“有”和“无”的意义首先在于,有了它们天地万物才能被建立起来。老子接着写道“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所以“常无”,是用来观(观照、体认)其(无本身)玄妙性。也就是说,“无”本身非常玄妙,只有通达这个玄妙的“无”才能体认天地之始。“常有,欲以观其徼”,所以“常有”,是用来观其(有本身)的彰显性。此处,我们需注意,老子用了四个“常”字:“常道”、“常名”、“常无”、“常有”。此“常”字有真常、本己之意。由此可知,“可道之道”都不是真正的“道”,这显示了语言的局限性。所以老子的继承者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庄子・齐物论》)这是说,天地与我是并(一起、一道)生存的,万物和我都自身与自身相同的(同一性),既然是“一”的,那么能有言说吗?既然已经称谓(说了)一,这不是有言了吗?物“一”加上言说就为“二”,“二”再加上“一”就变成了“三”,即可言说的物之“二”与物自体之“一”,就是“三”。这就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即使是善巧的人也不能再得什么,何况普通人呢?从“无”到“有”就达到了“三”这种认识,自“有”到“有”也是如此!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因为根据是非的认识办法而来的(因是已)。对于真正的“名”,要注意“可名之名”即命名言说的名都不是“恒常的名”。这强调了“名”(语言之一种)的局限性。对于“常无”(真正的无、命名的无),我们要注意其玄妙性,即我们命名“无”是天地的开始,这自身是非常玄妙的,不能以客观实在性来思维它。对于“常有”(真正的有、恒常的有),我们要注意它的“徼”(收集、集置、显现)性。这个“有”不能理解为“有者”、“存在者”。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二章写道:“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足见“常有”之“有”超出具体“有者”的普遍意义。
关于“无”和“有”的问题,老子又进一步写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说,命名的“无”和“有”本来是相同而无差别的,不过一旦我们将其命名后,它们一旦“出现”即人们认识到“无”和“有”,则对它们的叫法便有所不同。另外,这里还强调了“出”这一表达时间性的概念。遗憾的是,后世学者从未注意过“出”的意蕴,没有将“出”与时间关联起来,从而认识到“出”是由于人命名了“有”和“无”,进一步研究时间以及时间与“无”、“有”的关系。“无”和“有”可以说都是玄妙不可测知的,是令人震惊和惊奇的。玄奥啊玄奥,它们是“众妙”(一切现象)的“门”。这是说,认识了“无”和“有”才能认识一切“众妙”(万物的万千现象),“无”和“有”是打开认识一切的门径,没有“无”和“有”的概念,则什么也认识不到。老子的继承者庄子在《庚桑楚》中说:“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庄子将“无”、“有”比作“天门”,即万物产生的根源。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端?他指出:“开端包含有与无两者,是有与无的统一。”②开端既不能单独是“纯无”,也不能单独是“纯有”,而是两者的统一。这与老子之意完全相同,而不是后世的中国学者所认为的老子是以“无”为开端。
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还对这个“无”给予了“妙”、“玄”的性质并与命名为万物之母的这个“有”一道,“玄之又玄”地构成了“众妙之门”。老子提醒我们要关注“无”的“妙”性,“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为什么呢?老子要我们注意什么?我们知道,“无”之所以“妙”,在于只有命名了“无”和“有”之后,才有天地的开始,才有万物的出现。这与客观主义的观点正好相反。“无”之玄奥,在于人们一旦思考它,就已经将其对象化,从而视为一物了。而我们知道,这与“无”本身是矛盾的,是自身悖谬的。按照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人类思维最普遍、最高原则的矛盾律,“无”是不能够被思考的。换句话说,不矛盾律之所以存在,也是要在命名的、绝对的“无”之后才能够出现。即命名的、绝对的“无”开出了“不”性,开出了规定性的“否定性”,有了规定性、否定性,才有万物。由于开出了万物、开出了天地,故而是“众妙之门”。按照柏拉图所言,“无”是不能被思考、不能被言说的,而我们恰恰必须先思考它、命名它,才能思考一切,甚至才能有“不”性,故而是“妙”的、“玄”的。“无”本身是什么都没有,但必须命名一个“无”,才能开出天地万物,这真是无比的玄妙。
至此,我们大体弄清了命名的、绝对的“无”之用:它开出了天地(无名天地之始)、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它是“众妙之门”,从而使我们发生惊奇,产生哲学;它开出了“不”性、“否定性”――只有命名了绝对的“无”本身,人们才能够有个“不”,它们的存在须以绝对的“无”为前见、前提;只有有了这个命名的、绝对的“无”和“有”,我们的一切思维之门才能够打开;这个绝对的命名的“无”是“无”为“无不为”的,即它的作用无处不在,它是人类思维、行动所必须依赖的一个隐含的前提。
二、否定性的“无”及其作用
老子除了认识到这种命名的、绝对的、玄妙的“无”之外,还提出了作为“有的”否定性的“无”。《道德经》第二章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这里,老子提出了相对的问题和相对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规定性的否定性。天下人之所以知道美、善,是由于有不美、不善存在。在第一章的绝对的、命名的“无”、“有”提出后,就有了对立、否定性、不性,人们才能认识作为存在者的令人惊异的现象。老子还将有无与难易、高下、音声、前后并列,显然是说现象界,即物的、存在者的现象,故此处的无,当指“有的”否定性下的概念,而非第一章的绝对性的“无”之概念。可见,老子提出绝对的、命名的“无”之后,人类的思想就可以有一个否定性的“不”的“无”。
《道德经》第十一章载:“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老子对否定性的“无”本身之用的理解。老子通过车毂、器皿、房屋的有的否定性的“无”(空),展示出了“无”本身的用处。一物之用恰恰在于其否定性的“无”之用。所以老子说:“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的即物的、存在者的用处,对人的利处,恰是以其否定性的“无”为根基的。“无”的用处是展现、隐含在“有”的利处的。
除了上述老子对“无”本身之用的提出和理解外,老子还突出了“不”性的“无”之用,也即主体性的人之用、为本身的否定性的不用、不为。《道德经》第二章载:“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三章载:“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第五十章载:“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作为特殊的存在者,人的特征在于思维、行动、作为,但老子深刻认识到了过分作为有其有害的一面,特别对于统治者而言,过分作为有时害大于利。所以老子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无为无不为”,天地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故而人们需向它们学习,有时“不为”,特别是圣人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智者要“不敢为”,更要“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后果,当我(统治者)无为的时候,老百姓就自我化育;当我好静的时候,老百姓就自我遵守法纪,顺从自然;我不过分干预,老百姓就生活富足;我不贪,百姓就自然朴素。这大有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的思想。
三、结语
可见,老子认识到了两种“无”,一种是绝对的、命名的、理论性的“无”,它是玄奥的,是人类思维的开端,是天地之始,它和命名的、绝对的“有”一起构成了“众妙之门”。只有命名了绝对的“无”和“有”,人类思维、认识之门才能打开。所以,这个“无”是理论的、抽象的概念。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人没有达到哲学、走向理性。③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老子、庄子在和西方哲学开端的同时,也开启了纯哲学思维。
如果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哲学起源于惊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惊奇乃是关于“无”的思考。依《老子》第一章之义,只有命名的“无”在并以此为根基,天地万物的种种奇异状态才能向我们而来,我们才能认识世界;但是“无”本身却是不能思考、不能言说,这多么让人惊奇!用老子的话说,“无”、“有”是玄的,是众妙之门。且仅当万物的种种奇异状态向我们袭来,与我们照面时,这才唤起了我们的一种惊奇,这才使人进行哲思,才有哲学。海德格尔说:“因为只有我们以惊奇为根基,亦即以‘无’之敞开状态为根基,才会产生出‘为何之故?’的问题。唯因为这种‘为何之故?’的问题成为可能,我们才能够以确定的方式追问根据并作出论证。唯因我们能够追问和论证,研究者的命运才落到了我们的生存上了。”④但西方哲学的开拓者之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惊奇首先应是惊奇于事物的万状。他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⑤可见老子所谓的玄、妙等惊奇性在于不合常理;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惊奇重点在追问理由和原因。这展示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趋向。
除了这种绝对的、命名的“无”之外,老子还深刻地认识到了“有”的否定性的“无”,并认为这种“无”是和“有”相生的,并为“有”之用提供保障。可见“无”对老子来说是一个主概念,其重要性是与“有”并列的,而不是“有”的派生概念。这显示了老子对“无”的高度重视。
老子还提出了两个层次的“无”之为(用):第一个层次,是与“有”对应的“无”之为、之用,这是与存在、存在者(物)相关的“无”之用。其中又区别为二:一是命名的、绝对的的“无”之用,它开启了人类思想,使人类能够认识万物,开启了规定性和否定性,开出了“不”性,使哲学得以产生。它是人类思维的根本保证之一,是“众妙之门”。二是“有”的否定性“无”之用,万物、有的事物、存在者之用恰恰是其否定性的“无”之用在保障,没有“有”的否定性的“无”之用作保障,万物之利就不复存在。第二个层次的“无”为,是人也就是主体不过分作为,要顺从自然。尤其是统治者,要充分发挥老百姓的聪明才智,自由民主,不过分干预,在必要时,还要注意“为无为”,即克制自己,不妄作为。
后世学者没有深刻理解、区分老子的这三种“无”之用,将其混为一谈,更多的是强调第三种“无为”、“无用”,将老子提出了“无”本身之用与第三种当成一回事,从而认为老子是绝对的提倡“无”为的。这对我们的行为、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我们不深入研究物之用,不重视万物之利、之用,不重视功用的一面,导致我国的自然科学、制造、技艺不够发达。
[注 释]
①④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6页、第140页。
②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智者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第4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小鸟问父亲:“世界上最高级的生灵是什么?是我们鸟类吗?”老鸟答道:“不,是人类。”
小鸟又问:“人类是什么样的生灵?”“人类……就是那些常向我们巢中投掷石块的生灵。”
小鸟恍然大悟:“啊!我知道啦!可是,人类优于我们吗?他们比我们活得幸福吗?”“他们或许优于我们,却远不如我们生活得幸福。”“为什么他们不如我们幸福?”小鸟不解地问父亲。老鸟答道:“因为在人类心中生长着一根刺,这根刺无时不在刺痛和折磨着他们,他们自己为这根刺起了个名字,管它叫做贪婪。”
小鸟又问:“贪婪?贪婪是什么意思?爸爸你知道吗?”“不错,我了解人类,也见识过他们内心那根贪婪之刺。你也想亲眼见识见识吗,孩子?”“是的,爸爸,我想亲眼见识见识。”“这很容易,若看见有人走过来,赶快告诉我。”
少顷,小鸟便叫了起来:“爸爸,有个人走过来了。”
老鸟便对小鸟说:“听我说孩子,待会儿我要自投罗网,主动落到他手中,你可以看到一场好戏。”小鸟不由得十分担心,说:“如果你受到什么伤害……”老鸟安慰它说:“莫担心,孩子,我了解人类的贪婪,我晓得怎样从他们手中逃脱。”
说罢,老鸟飞离小鸟,落到来人身边,那人伸手便抓住了它,乐不可支地叫道:“我要把你宰掉,吃你的肉!”老鸟说道:“我的肉这么少,够填饱你的肚子吗?”那人说:“肉虽然少,却鲜美可口。”
老鸟说:“我可以送你远比我的肉更有用的东西,那是三句至理名言,假如你学到手,便会发大财。”那人急不可耐:“快告诉我,这三句名言是什么?”
老鸟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徐徐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有个条件:我在你手中先告诉你第一句名言,待你放开我,便告诉你第二句名言,等到我飞到树上后,才会告诉你第三句名言。”
那人一心想尽快得到三句名言,好去发大财,便马上答道:“我答应你的条件,快告诉我第一句名言吧。”
老鸟说道:“第一句名言便是: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根据我们的条件,现在请你放开我。”那人便放开了老鸟。
“这第二句名言便是: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说罢,它边叫边振翅飞上了树梢,“你真是个大傻瓜,如果刚才把我宰掉,你便会从我腹中取出一颗重量达一百二十克、价值连城的大宝石。”
那人闻听,懊悔不已,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他望着树上的鸟,仍惦记着他们方才谈妥的条件,便又说道:“请你快把第三句名言告诉我!”
狡猾的老鸟讥笑他说:“贪婪的人啊,你的贪婪之心遮住了你的双眼。既然你忘记了前两句名言,告诉你第三句又有何益?难道我没有告诉你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吗?你想想,我浑身的骨肉翅加起来还不足一百克,腹中怎么可能有一颗超过一百二十克的大宝石呢?”
那人闻听此言,顿时目瞪口呆,好不尴尬,脸上的表情煞是可笑……
一只鸟就这样耍弄了一个人。
第5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关键词:子;长益方言;武潭话;比较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187-02
长益方言沿湘江、资江的中下游分布,以长沙、益阳两地为代表。长益方言是湘方言里的一个重要的方言片,长益片是湘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的片。
学者们对长益方言的统一认识在语音上是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无论平仄一般都念不送气清音。声母23个,韵母40个,6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在词汇上,长益方言有一批内部比较一致的特殊词汇,如崽、鸡婆子、伢子、绳子衣、禾线子等。武潭镇在长益片的分布区内,是长益方言的一个方言点。武潭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与长、益方言大体一致,但是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有一些特殊性。
一、“子”的意义在长、益方言中的表现形式和“子”在长、益方言中的使用范围
“子”的有些意义在长、益方言中的表现形式与在普通话中一致。但是区别也比较明显:
1、普通话中“儿子”、“幼小的”等意义在长、益方言中的表现形式。
把“子”称作“崽”是湘方言的一大特色,同样也是长、益方言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一说法,《方言校笺》中有谈到:“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矣。”可见,将“子”说成“崽”是古来有之的。当“子”表示“儿子”或“幼小的”之意时,在长益方言中“崽”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代替“子”,如把“儿子”说成“崽”,把“子女”说成“崽女”,把“子猪”说成“猪崽”。
2、普通话中“人的通称”这个意义在长、益方言中的表现形式。
对于“子”表示“人的通称”时,长、益方言中的表现形式有点复杂,分别用“伢子”、 “伙子”、 “老倌子”表示小男孩、小伙子和老年男子。用“妹子”、 “妹姐”、 “堂客们”、 “纸恪北硎拘∨孩、姑娘、已婚妇女和老年女性。
3、“子”作词尾使用时,在长、益方言中比普通话中的使用范围广。
普通话不带“子”尾,而长、益方言带“子”尾。这些特殊的“子”尾词可归类为:
“子”做词尾的名词:老鼠子、竹竿子等。这类带“子”尾的名词有个总的特征就是表示的都是比较小的物体,而对于比较大的物体一般不用带“子”。如不说“老虎子”、“树子”。还有些带“子”尾的时间名词,如去年子、后日子(后天)、半日子(半天)等。
“形容词性语素+‘子'尾”的名词:癫子(疯子)、驼背子(驼背的人)等。
“副词性语素+‘子'尾”的名词“:一般子、经常子等。
“量词性语素+‘子'尾”的名词:几咋子、几下子等。
(2)普通话带“子”尾,而长、益方言不带“子”尾。如“裤子”、“裙子”在长、益方言中都说成“裤”、“裙”。
(3)普通话带“儿”尾,而长、益方言带“子”尾。如“枣儿”、“饭粒儿”说成“枣子”、“饭粒子”。
(4)在长、益方言中“子”与特殊词尾“唧”构成“‘子’尾名词唧”的用法。如银角子唧(硬币)、手套子唧(手套)等。
(5)在长、益方言中“子”可构成“形容词名词子”的用法。这类形容词仅限于“死”、“瘟”这类含贬义的词,名词多是一些带有双重意思的表动物的词,它不仅表示字面意义,还借词中带有的“死”、“瘟”等带有的贬义咒骂人,以动物喻人,如:死鸡子、瘟猪子等,这类词一般用来骂人。
(6)在长、益方言中“子”与特殊词尾“婆”构成“名词婆子”的用法。如:鸡婆子(母鸡)等。
二、“子”在长益方言中的特殊语法分布情况
在普通话中,“子”随意义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词,并且不同的词有不同的语法分布。
1、作为词尾,与另一语素成词使用,用法与普通话中的“子”作词尾的用法一致。
(1)“子”加在名词性语素后时多用作主语和宾语,如:老鼠子。例句:
咯里的老鼠子真的是蛮多赖。(这里的老鼠很多。)
日日只晓得恰东西,恩真是个老鼠子。(天天这么贪吃,你真像个老鼠。)
“子”尾名词中的时间名词多用作状语、定语。
去年子,我到过昆明。(去年我去过昆明。)
咯还是去年子的茶叶。(这还是去年剩下的茶叶。)
(2)“子”加在形容词性语素后时,如:癫子。例句:
癫子有癫命!(疯子有疯命!)
嗯咯咋癫子。(你这个疯子。)
(3)“子”加在副词性语素后时,一般单独成句使用,也有些时候用作定语,修饰形容词。如:一般子。例句:
“今年子的收成还好不咯?”“一般子。”(“今年的收成怎么样?”“还过得去。”)
电脑不是一般子的方便咧。(电脑很方便。)
(4)“子”加在量词性语素后时,如:几咋子。例句:
还有几咋子桔子放在桌子上。(还有几个桔子放在桌子上。)
桔子只有几咋子了。(桔子只有几个了。)
2、特殊词“仫子”的语法分布情况。
“仫子”一词属于合成词,由两个不成词语素构成。根据不同语境下表示出的不同含义,“仫子”的语法分布情况也不同。
(1)当表示“什么”的含义时,多用作定语和宾语。作宾语时多与动词“搞”组成词组“搞仫子”。例句:
嗯仫子时候起去的,我何不晓得呐?(你什么时候起床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天还恿粒嗯就爬起来搞仫子?(天还没亮,你就爬起来干什么?)
(2)当表示心情很烦躁时,没有实在意义,多作叹词使用。“仫子”有时候也说成“仫子鬼”。例句:
仫子?嗯又蛹案瘢浚ò。磕阌置挥屑案瘢浚
仫子鬼啦!今朝子做仫子都做不好。(今天做什么都做不好,很烦躁。)
三、“子”在武潭话中的使用情况与在长沙、益阳方言中使用情况的比较
虽然同属长益片,但“子”在武潭话中和在长沙、益阳方言中的使用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用图表概括如表1:
通过表1,我们可以对“子”在普通话、在长、益方言以及在武潭话中的使用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四、结论
通过分析“子”在长益方言中的意义及语法分布,以及对“子”在普通话、长、益方言和武潭话中的使用情况的相互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长益方言中“子”的意义及语法分布的特殊性。
子”在长益方言中的意义及语法分布的特殊性使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以及悠久的发展历史、地理因素、人口因素、语言的内部变化以及不同民族的语言接触等 “子”字意义和语法分布的演化都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现在“子”在长益方言中的很多用法跟现代汉语普通话存在差异,这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分不开。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子”在长益方言与在普通话中的用法也慢慢趋向一致,在长、益方言中的使用情况与在武潭话中的使用情况存在的差异也慢慢缩小。
参考文献:
[1]侯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2]周祖谟.方言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3.
第6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老鸟答道:“不,是人类。”
小鸟又问:“人类是什么样的生灵?”
“人类……就是那些常向我们巢中投掷石块的生灵。”
小鸟恍然大悟:“啊,我知道啦!可是,人类优于我们吗?他们比我们生活得幸福吗?”
“他们或许优于我们,却远不如我们生活得幸福。”
“为什么他们不如我们幸福?”小鸟不解地问父亲。
老鸟答道:“因为在人类心中生长着一根刺,这根刺无时不在刺痛和折磨着他们。他们自己为这根刺起了个名字,管它叫贪婪。”
小鸟又问:“贪婪?贪婪是什么意思?爸爸,你知道吗?”
“不错,我了解人类,也见识过他们内心那根贪婪之刺。你也想亲眼见识吗,孩子?”
“是的,爸爸,我想亲眼见识见识。”
“这很容易。若看见有人走过来,赶快告诉我,我让你见识一下人类心中那根贪婪之刺。”
少顷,小鸟便叫了起来:“爸爸,有人走过来啦。”
老鸟对小鸟说:“听我说孩子,待会我要自投罗网,主动落在他手中,你可以看到一场好戏。”
小鸟不由得十分担心,说:“如果你受到什么伤害……”
老鸟安慰它说:“别担心,孩子,我了解人类的贪婪,我晓得怎样从他们手中逃脱。”
说完,老鸟飞离小鸟,落到来人身边。那人伸手便抓住了它,乐不可支地叫道:“我要把你宰掉,吃你的肉。”
老鸟说道:“我的肉那么少,够填饱你的肚子吗?”
那人说:“肉虽然少,却美味可口。”
老鸟说:“我可以送你远远比我的肉更有用的东西,那是三句至理名言,假如你学到手,便会发大财。”
那人急不可耐:“快告诉我,这三句名言是什么?”
老鸟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款款地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有个条件:我在你手中先告诉你第一句名言;待你放开我,便告诉你第二句名言;等我飞到树上后,才会告诉你第三句名言。”
那人一心想尽快得到三句名言,好去发大财,便马上答道:“我答应你的条件,快告诉我第一句名言吧。”
老鸟说道:“这第一句名言便是: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根据我们的条件,现在请你放开我。”那人放开了老鸟。
“这第二句名言便是: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说完,它边叫着边振翅飞上了树梢,“你真是个大傻瓜,如果刚才把我宰掉,你便会从我腹中取出一颗重量达120克、价值连城的大宝石。”
那人听了,懊悔不已,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他望着树上的鸟,仍惦记着他们刚才谈妥的条件,便又说道:“请你快把第三句名言告诉我!”
狡猾的老鸟讥笑他说:“贪婪的人啊,你的贪婪之心遮住了你的双眼。既然你忘记了前两句名言,告诉你第三句又有何益?难道我没有告诉‘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吗?你想想看,我浑身的骨肉羽翅加起来不足100克,腹中怎会有一颗超过120克的大宝石呢?”
那人闻听此言,顿时目瞪口呆,好不尴尬,脸上的表情煞是可笑……
一只鸟就这样耍了一个人。
老鸟回望着小鸟说:“孩子,你现在可亲眼见识过了?”
第7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关键词: 老子;周易;归藏;辩证思维;宇宙生成论
was the ideology of lao-zi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text of zhouyi?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deology of lao-zi was originated from guicang but not from zhouyi. the author states three evidences for his viewpoints: at first, there are more aspects putting the hexagram of kun(《坤》)in the first place while putting qian(《乾》)in the second place (which follows the order of the hexagrams' order of guicang) in lao-zi, but not in turn (which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hexagrams' order in zhouyi). secondly, lao-zi's dialectical thinking mode belongs to a mod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ancient text of zhouyi. and thirdly, lao-zi's view on the universe's generating & producing differs from that of zhouyi's ancient text too.
key words: lao-zi; zhouyi; guicang; dialectical thinking mode; view on the universe's generating & producing
《老子》五千言的思想源自何处,我看是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不是源自《周易》。理由有三。
第一,《老子》书中不见首乾次坤的思想,倒是首坤的思想明显居多。这就说明,《老子》思想与《周易》古经不是一路,而与《坤乾》相近。
古代有三部易书,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三部易书当然有不同的思想。前两部已不存在,经文是什么内容不可知晓。但是它们和现存的《周易》一个样,都有八卦和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就有卦序问题。有卦序,必然有思想。据古人说,夏易《连山》首艮。首艮有何意义,我们暂且不管。殷易《归藏》,《礼记.礼运》记孔子一段话值得重视。孔子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体会孔子语意,知《坤乾》反映殷道。据汉人说,《坤乾》就是《归藏》。
孔子所谓殷道是与周道相对而言的。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自君位继承制度而言,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从父亲的统系看,应当父死子继,从母亲方面看,应当兄终弟及(《礼记.表记》)。“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礼记.表记》)可见,殷道亲亲是以母统为重,周道尊尊是以父统为重。《周易》古经首乾次坤,显然以父统为重。《坤乾》,顾名思义,无疑以母统为重。两部易书,一个重父统,一个重母统,《老子》五千言的思想接近哪一个呢?显然接近《坤乾》。有人强调《老子》五千言重母、牝、雌,与《周易》古经之坤卦思想一致,所以《老子》接受的是《周易》古经的思想。这样说,我以为不对。应当看坤卦在六十四卦中占怎样的地位。犹如看中国封建社会对待女人的态度,不可因为中国当时除男人之外还有女人而且有些女人很优秀,就以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女权社会。只看有女人不行,重要的是看女人的处境和地位。看《周易》重视什么不重视什么,道理也是一样。说坤卦,就要看坤卦在整个六十四卦中的地位。坤卦与乾卦并列,共同居首,坤则处乾之后。乾卦辞讲“元亨利贞”。不管怎么训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简单明确是显然的。而坤卦辞则复杂得多,讲“利牝马之贞”,讲“先迷后得主”等等。都是说坤与乾比,好象牝马,牝马在马群中要受未骟牡马的管制和呵护。而且一切都居于未骟牡马之后,一定不要抢到它的前面去。总之,《周易》古经,乾坤两卦是彼此相对而言的,不可以分开理解。有人因此说乾坤看上去似两卦,实是一卦,是有道理的。
《周易》古经这乾先坤后的思想,与《老子》不同。《老子》是“我有三宝……三曰不为天下先。”(《老子》第67章),“人皆取先,己独取后。”(《庄子.天下》)。《老子》讲的居后是有普遍意义的。它主张居全天下之后,不管别人如何,自己绝不争先。《周易》坤卦讲居后不争先有针对性,它不说不为天下先,仅仅说不为乾先。它对乾而言,绝对居后。此一不同。《老子》五千言中明显有贵母、守雌的思想,《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哪里有贵母的意思!它讲“利牝马之贞”(坤卦辞)、“畜牝牛吉”(离卦辞),只是言及而已。根本没有《老子》所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的意思。此二不同。
高怀民先生《先秦易学史》说:“孔子的一生表现了乾之健,老子的一生表现了坤之顺。” 〔1〕 这话就孔、老二人一生的实践而言,可以说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就二人思想而言,则似可商榷。孔子乾之健、坤之顺都一样地强调,不分轻重而且言行一致。《老子》强调“柔弱胜刚强”,乍看,好象强调坤顺,然而仔细一想则又不然。如果《老子》以为坤应该顺乾,则“柔弱胜刚强”一语就该说成“柔弱顺刚强”。既然说“柔弱胜刚强”,就是认为柔弱作为一方,应该也能够战胜刚强之另一方。这哪里是《周易》古经六十四卦的思想!六十四卦之乾坤两卦,两条卦辞,十二条爻辞,一条用九一条用六,都是在讲乾与坤的关系,告诫人们乾坤两种精神都要有。绝不讲谁战胜谁的问题。还多少有一点崇乾抑坤的意向。《老子》强调柔弱、谦卑、居后,与乾坤两卦的思想根本不同。所以我觉得高先生说孔子一生乾健,老子一生坤顺,不甚妥当。若说孔子一生乾坤,老子一生坤乾,庶几近之。
第二,《老子》的辩证思维模式属于与《周易》古经不同的另一类。中国古代辩证思想模式是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我看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一种在六经尤其《周易》古经中,后来由孔子及早期儒家继承、发扬下来。另一种就是《老子》五千言中的。前者,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就是孔子和子思、孟子发挥的“中”的哲学。“中”的哲学最早始于尧舜时代的“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然后是殷周之际完成的《周易》古经六十四卦。然后是孔子道中庸,子思讲中和,孟子说权,完成“中”哲学体系。“中”哲学,说穿了就是辩证思想的一种中国模式。它的特点有二,一是对立统一,包括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物极必反三个意思。二是时中。前一个特点是《易》、《老》共同的。后一个特点,却只见于儒家承传的六经,特别是《周易》古经之中。时中,以承认变化为前提。时就是变化,有变化才有中与不中的问题。《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这是古今人所公认的,不须证明。《系辞传》不论是什么人作的,它说《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一段话,谁也不能说它讲的不是《周易》六十四卦的实际情况。
《老子》五千言恰好相反。它虽然也讲变化,但是它反对时中。强调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要守柔、居后,即在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中死丁丁地坚守一个方面。例如《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67章)“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76章)“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第52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26章)“清静为天下正”(第45章)“致虚极,守静笃。”(第16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第28章)“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第20章)乃至力主“抱一”(第22章)、“抱朴”(第19章)、“守柔”(第52章)。《老子》五千言最反映他辩证思维特点的是第40章的两句话:“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前一句讲事物一分为二之两面相反相成,是变化的动力,这当然是对的。后一句则暴露了老子与人不同之处:强调弱是对立两面之有意义的一面。《吕氏春秋.不仁》说:“老聃贵柔”,柔与刚是对立的,既言“贵柔”,就必轻刚。《吕氏春秋》对老子的概括,再恰当不过。《老子》思维正处于“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反面。正如金景芳先生所说,老子是半截子辩证法。 〔2〕
这样一来,则不能说《老子》五千言的辩证思维方式源自《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如果按《老子》的思想,以柔为好,则《周易》古经八卦六十四卦也就无从谈起。
若一定想说《老子》五千言的辩证思维模式与《周易》古经一个样,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老子》贵柔,守雌,居后,抱一的主张消溶掉,或者给《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加入类似的内容。而这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老子》五千言的辩证思维模式与《周易》六十四卦不是同一类。除此,我们得不出另外的结论。
第三,关于宇宙生成问题,《老子》的主张也与《周易》古经不是一路。《老子》是这样说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
又说: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
《老子》认为宇宙间一切自“无”产生。“无”是什么?依《老子》的意见,“无”就是“道”。道是什么呢?《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 者同出而异名。(第1章)
《老子》说,道有两种,同出而异名。一种叫做“非常道”,一种叫做“常道”。非常道是可以名状,有物有形,看得见,摸得到的。如《庄子.知北游》里讲的“在蝼蚁”、“在钕稗”、“在瓦甓”、“在屎尿”的道。这种道在万物之中。“常道”是不可以名状、无影无踪,看不见、摸不到的。这种道在天地之先。《老子》对于“常道”是这样描述的:
和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第25章)
其上不?,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14章)
《老子》想象的这个无名的“常道”,说来说去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无”。由此看来,《老子》的宇宙论就是:宇宙天地是被创造出来的。是“无”中生“有”。
《周易》古经六十四卦的宇宙论又是怎样的呢?按照一些人的意见,《老子》思想在《周易》古经影响下形成,则在宇宙论问题上,二者应当大体一致。然而实际上二者大体不一致。
《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不曾涉及宇宙论问题。可以这样说,《老子》五千言的宇宙论出于它自身,并非受《周易》古经的影响所致。
六十四卦卦爻辞不见宇宙论,但从六十四卦排列看出一些端倪来。它只是从乾、坤开始,一卦接一卦地讲,就是说,《周易》古经只讲“有”。“有”之前是怎样的,它不讲。根本搭不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边。有人说《老子》五千言思想受《周易》古经影响而成,这在宇宙论上是无法讲通的。
有人说《周易》古经影响《老子》,《老子》影响《易传》。画出《周易》古经—《老子》—《易传》一条线。如果事实如此,则《老子》的宇宙论一定影响到《易传》。可是《易传》的宇宙论完全是另一样。《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话既是讲八卦生成的过程,也是讲万物生成的过程。《系辞传》讲万物生成始于太极。太极之前是什么,它不讲了。太极相当于《老子》讲“一生二”的“一”,“有生于无”的“有”。如果《老子》没说“道生一”,没说“有生于无”,就与《系辞传》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段话一致了。那样,说《易传》受《老子》影响,还可以成立。
《序卦传》的宇宙论和《老子》也明显不同,更加证明《周易》经传与《老子》实非一路。《序卦传》说: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这两句话与《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意思相同,都说天地不是无中生有出来的。它根本不符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
《周易》经传宇宙论讲“有”不讲“无”,《老子》讲“有”又讲“无”。后世学者有人早已注意到这一明显差别。宋人张载说:“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正蒙.大易》)意谓《周易》经传宇宙论与《老子》是不一样的。
但是,也有人把不同的二者混同起来。周敦颐画《太极图》,作《太极图说》,给《周易》太极之上画出一个无极来,《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系辞传》本来是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而周氏平添一个“无极”。于是就和《老子》“有生于无”、“道生一”合流了。朱熹赞成周敦颐,作《太极图说解》,为周敦颐打圆场。而程颐取另一种态度。程颐是周的弟子辈,可是从来不言《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事,仿佛不知道。想必是不赞成周氏“太极”之上架“无极”的作法。
可见,古人已经注意《易》、《老》不同。有人想把《易》、《老》混合为一的努力一直未曾取得成功,却也一直不曾歇息,20世纪以来《易》、《老》合流的势头愈演愈劲,至90年代孔子、儒家几乎要被赶出易学领域,以至于竟有人一步步把《周易》划归道家,第一步把孔子与《易传》剥离开来,第二步把《易传》划归道家,第三步把《易经》也划归道家,建构所谓道家易。目前正进行第三步, 〔3〕其方法大体有三,一是置《易传》于不顾,解《经》另起炉灶。二是肢解卦爻辞的整体意义,一词一句地与《老子》挂钩。三是对待《易传》的态度,很象乾卦的“龙”,变化无定。先说“以传解经”不对,要严分经传。一边断定《易传》的思维方式就是道家思维方式,一边大讲《彖传》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和“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且夸奖说这样讲“元”字是对《周易》古经“元”字的创造性诠释。于是“元亨利贞”到底该不该讲成“大顺通,有利于占问”,经传到底该不该严分,就是问题了。
把《周易》经传思想体系主要划归道家,还有一道障碍,就是《庄子.天运》记孔、老的一段话: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也!今子之所言,犹迹也……”
孔子对老子当面说,他治《易》经已经很久了,不见效果,老子当面承认《易》是孔子研究的东西。《庄子》书寓言居多,但是说孔子治《易》经的事不至于是假。连老、庄自己都承认《易经》是孔子研究的东西。这条材料对于把《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对孔子的影响改归对老子的影响,十分不利。
今之学者有思考周全者也提出与此有关的想法,也构成持《周易》古经影响《老子》、《老子》影响《易传》主张的一道障碍。
台大教授黄沛荣先生说:
吾人研究《易》、《老》关系,于《老子》与《易传》间确实存在之某种关系,亦不可径行认定,而须再作另一层面之考察。《易传》为说《易》之作,对于卦爻辞之义蕴,自应予以阐发;换言之,影响《易传》最大者当为卦爻辞矣。是以若将某些《老子》、《易传》同受卦爻辞影响之处,误认为《易传》受《老子》所影响,势必似是而非。
黄先生接着又说:
以谦卦为例,其谦道思想一方面为《老子》所吸收而成为其哲学之一环,另一方面,谦《彖》既为谦卦之传,则其申明谦卦之义乃理所当然,自不必由《老子》转化,且谦《彖》之用语亦无承袭《老子》之迹象。 〔4〕
黄先生书原则上是赞同《老子》思想与《周易》古经有关联的,但他考虑周全,不把话说绝。他承认《易传》有直接受《周易》古经影响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这一点上我赞成黄先生。读黄先生书,我更加坚信,《老子》思想并非源自《周易》古经。《老子》必不是《周易》古经与《易传》之间一座必经的桥梁。
参考文献:
〔1〕高怀民.先秦易学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
〔2〕金景芳.知止老人论学〔m〕.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114.
第8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春秋时期的“出场费”
中国的名人广告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著名的“伯乐相马”就是名人的促销行为。苏代是纵横家苏秦的弟弟,为燕国到齐国游说时,给在齐威王面前说话很管用的淳于髡讲了伯乐相马的故事。他讲此故事的用意,尽管不在名人的商业广告价值上,却给中国广告史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鲜活的成功案例。从所述来看,卖马人颇有商业头脑,十分了解“名人效应”的作用,仅仅花费“一朝之贾”,便请到了当时的相马专家伯乐,实现了卖掉马的商业目的。
卖马人给伯乐的“一朝之贾”,在现代叫“出场费”,这也开了中国名人参与商业行为拿“出场费”的先河。
汉代女名人也做“促销女”
汉代餐饮业已很繁荣,街头酒店受到普通消费者的欢迎。这时的酒店经营者颇有创意,在店前面垒起高台,即所谓的“垆”,然后把大酒坛子放置于上,还让一名漂亮的女子站在旁边,以吸引眼球。这样的女子,在现代叫“促销小姐”。当时名声远播的大才女卓文君,便曾当过“促销女”。
据《史记》记载,当年大才子司马相如,与当时17岁的卓文君私奔后,为了谋生,在四川临邛盘了一家酒舍,开了个小酒店。司马相如洗盘子,卓文君则站到店前的酒坛旁边揽生意,“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典故由此而来。这是古代女明星参与商业活动的经典案例,现代流行的女星为某一品牌的商品站台,无非是“文君当垆”的现代版。
东晋出现的“慈善广告”
古代名人参与商业活动,并不都是商业行为,有时是一种慈善活动。有“书圣”之誉的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便曾利用自己的名家身份,为一个卖扇老妇人做好事,免费为她卖的扇子题字。
据说有一天,王羲之散步到绍兴城里的一座石桥上,见一个老妇人提着一篮竹扇,在桥头叫卖,但好久也不见有人来买。王羲之遂上前对老妇人说,如果在扇子上写上字,应该好卖些。
老妇人同意了,王羲之便在每只扇子上题写5个字。老妇人起初还有点不高兴,王羲之告诉她,你就说这字是王右军写的,每只要价“百钱”。老妇人依言说了,扇子很快被抢购一空。
唐宋流行的“商业软文”
唐宋时期,商业活动中利用名人效应现象更为突出。这一时期,请名人为商品作赋吟诗,成为一种潮流,酒、茶、食物等都曾通过名人效应得以推广。当时不少名人留下来的诗作,在今天看来都属于广告中的“商业软文”。著名诗人李白的《客中行》,就是专为兰陵出产的一种酒而写。
宋代文学家坡,从茶叶到馓子,再到猪肉,他都曾做过推广。当年海南儋县有一老妇人制作的环饼,即时称“寒具”、俗称“馓子”的一种油炸食品,非常好吃。坡被贬谪于此后,给这家铺子写了一首《寒具诗》:“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经他这么一写,这家铺子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第9篇:老子的名言范文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与文论能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家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1〕。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话语系统,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生成机制和学术规制,从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清理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基本规则,然后才可能进一步清理古代文论范畴群及其文化架构、文化运作机制和文化与文论的发展规律。由于这种文化探源式的研究,是从文化基本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入手,因而不但具有探本求源的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是一条追寻东西方文化生成运作机制和规律的切实可行的路径。从这条路径,我们不但可以比较东西方各异质文化圈的不同文化精神,而且可以总结出各类文化生成与运作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东西方文论特征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给当今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一种“活的”文化运作机制和规则。只要我们能真正认识到这种文化运作机制与规则,那么不但可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为建构新的文论体系,或者说建构一般的(或总体的General)文论体系提供若干“活生生的”学术规则和运作方式,而不仅仅是提供一堆“死的”材料和人物。作为文论史固然要借鉴古人,要研究“秦砖汉瓦”、“古希腊、罗马”、“吠陀、奥义书”等等“死的”材料,但我们更需要从生生不已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其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规则,发现其“活的”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机制。同时,也只有在探索其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机制的同时,才可能真正进行深入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真正回答清楚东西方文化为什么会“分道扬镳”的基本原因;也才可能真正认识东西方各异质文化的不同路径、文论特色及其互识的必要性和互补的巨大价值。“道”与“逻各斯”,这两个古老的术语,在中外当代学术界和文论界又开始时髦走红起来。甚至有学者将这两个术语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或专著的题目,如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TheTaoandtheLogos:LiteraryHermeneutics,EastandWest,DukeUniversityPress,1992)又如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2〕。连西方的大学者海德格尔,也对“道”与“逻各斯”情有独钟,在《早期希腊思想》(EarlyGreekThinking)一书中〔3〕,列专章讨论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逻各斯”(Logos,λσγos)。与此同时,海德格尔对中国老子的“道”也颇有兴趣。有学者指出:“海德格尔的Eregins(大道)就含有老子的‘道’的影子,是受过老子思想启发的。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与中国学人合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对东方思想有过充分的关注,对老子的‘道’大有兴趣。”〔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往往将“道”与“逻各斯”相提并论。他指出:Ereigins(大道)这个词语,“就像希腊的逻各斯(Logos)和中国的道(Tao)一样不可译”〔5〕。在《走向语言之途》一书中:海德格尔指出:“老子的诗意运思的主导词语即是‘道’(Tao),根本上意味着道路。……‘道’或许就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我们由之而来才能去思考理性、精神、意义和逻各斯”〔6〕。当代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也指出:“‘道可道,非常道’;第
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与‘言’两义,可以相参”。(《管锥编》第二册第408页)为什么钱钟书等人将“道”与“逻各斯”相提并论?显然,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确有相通之处;为什么海德格尔对“道”与“逻各斯”情有独钟?显然,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在各自的文化构成与传承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道”与“逻各斯”的相似之处及其各自在中西文化与文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道”与“逻各斯”从相似的起点迈步,却各自奔向不同的路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规则、学术话语和意义生成方式?这一点,恰恰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还是让我们从“道”与“逻各斯”的起点开始追索吧。《老子》一书开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老子》1章)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的第1条说:“这个‘逻各斯’,虽然永恒地存在着,但是人们在听见人说到它以前,以及在初次听到人说到它以后,都不能了解它,虽然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D1)〔7〕^从以上两段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第一,“逻各斯”与“道”,都是“永恒”的,是“常”(恒久)的。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之“永恒”与老子道的“常”是可以通约的,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认识到,在这千变万化的宇宙中,有一个永恒的、恒常之物,这就是“道”和“逻各斯”。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25章)“逻各斯”同样如此。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道不是逻各斯,逻各斯不是道,可是这种相异只是由于文化背景以及语言的不同,而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相同,甚至它们的超越目的也相同,它们也有相同的实词,这种实词不但超越了感官世界的变化,而且超越所有时空的束缚,超越了时空,同时也就超越了运动变化,‘逻各斯’是‘永恒’的,‘道’是‘常’的,因此,‘逻各斯’与‘道’——世界的最终原理原则,都能用实词——‘永恒’与‘常’来形容,而且,也由于这‘永恒’概念和‘常’概念而变成超越的,再进一步,唯有在这种超越的境地里,才有一种保险,保证自己在‘万物流转’中不变不动,不失去自己的存在,使自己不变成虚无,在动中不变,在毁灭中永远存在”〔8〕。“逻各斯”与“道”不但是“永恒”的,而且都是万物的本原,是产生一切的东西,是万物之“母”。此即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道”产生一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41章)“逻各斯”是万物的本质,“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D1)。第二,“道”与“逻各斯”都有“说话”,“言谈”,“道说”之意。“逻各斯”(λσγos)一词有字、语言、断言、谈话、讲演、思想、理性、理由、意见、计算、比例等等含义〔9〕,从词源上来看,“逻各斯”的词源出希腊文Legein,意为“说”(tospeak)。有学者明确指出:逻各斯的第一个意义是“言语”、“谈论”,或是说出来的一个“字”。这意义在纪元前六世纪时,是古希腊文最普遍的用法。赫氏断片(残卷)第1、第87、第108都用这种意义表达逻各斯〔10〕。老子的“道”同样有“言说”之意。杨适在《哲学的童年》一书中曾比较过这一点,他指出:这里(指《残卷》第1条)最初出现的“逻各斯”一词直译只能是“话语”、“叙述”、“报告”等等,它同“听”众相关。在这里对照一下老子的用语是很有意思的。《老子》这部我国的哲学文献也是古代的哲学诗,它一开头是:“道可道,非常道。”如译成现代汉语,这第一个“道”字显然是双关的,第二个“道”字只能译为“说出来”、“用言辞表达”〔11〕。第三,“逻各斯”与“道”都与规律或理性相关。韩非《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韩非子·解老》)韩非是最早解说《老子》的学者,他对《老子》道的理解,显然看到了道是万物之“所以然”的规律,是万理之所用。而这一点,也正与赫拉克利特“逻各斯”相似。杨适指出:“道可道,非常道”中的这第三个“道”字,作为“常道”,含义就明显地向客观的道理或规律转化去了。而这后一含义,在以后的表述中越来越清楚,并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充实。这种表述方式同赫拉克利特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的巧合〔12〕。对这一点,台湾学者邬昆如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逻各斯”的第二个含义是“理性”,赫拉克利特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把逻各斯概念提升到最高之宇宙原则,这可在许多断片(残卷)中找到(如第1、第2、第31、第45、第50、第72、第115等)。理性是万物的型式因,是万物的掌管者,是永恒的,对万物是一种共相,但仍然有能力把万物之杂多性融通为一。因此,在这些观点之下,逻各斯的意义包括了理性、艺术、智慧以及各种关系。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逻各斯的共相意义,这共相包括了原因概念。这原因概念保证了下面一项原理原则:“宇宙万物来自一体,而一体亦来自万物”。邬昆如紧接着指出,中国老子的“道”,同样具有与赫氏“逻各斯”相近似的“理性”的意义:因为中国“道”之概念有一种潜能,能统合一总之杂多性,而且使多变为一,这显然是有“理性”的意义。难怪西方学者从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之后,就一直用“逻各斯”概念来释“道”概念,尤其是他们在注释《道德经》第1章时。更觉得“逻各斯”和“道”的相同性〔13〕。尽管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有如上三点(或许还可找出更多)共同或相似之处,但为什么这种相似甚至相同的“道”与“逻各斯”,却对中西文化与文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显然,“道”与“逻各斯”在根本上有着其完全不同之处。我们更感兴趣的正是这种不同之处,因为这种根本上的不同,才使得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学术规则与文论话语。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真正寻到了中西文化与文论之根。“道”与“逻各斯”的不同之处,大致可以分为“有与无”、“可言者与不可言”、“分析与体悟”这样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恰恰是与上述三个相同或相似方面相对应的,这种“二律背反”现象确是意味深长的。限于篇幅,我们只比较论述前两个方面。我们前面说过,“道”与“逻各斯”都是“永恒”的,“恒常”的,同时又都是万物之本原,是产生一切的东西,是万物之“母”。不过,就在这相似之中蕴含着极为不同之处,那就是老子的“道”更倾向于“无”,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更倾向于“有”。也正是这一基本倾向,从起点上确定了中西方文化与文论的话语的基本方向和路径。老子的“道”,其根本是“无”。《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1章)王弼注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也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也就是说,虽然道是产生天地万物之本原,是万物之“母”,但这个本原自身却是“无”。正如老子明确指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40章)王弼注曰:“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这里,老子对于“道”的根本特征——“无”已表述得很明确、很充分了。这种“无”,并非虚无,并非真正的空空如也的“无”,而是一种无在之“在”,是一种以“无”为本的“无物之物”。老子这样描述这种“无”的情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25章)显然,这种以“无”为本的“道”,仍然是一种“物”(“有物混成”),只不过它不是具体的物,而是宇宙间“有”的本原,是万物的来源。这个本原之“无”,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14章)老子的“道”就是这样一种以“无”为特征的无物之“象”,无物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也具有某些“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特征。赫氏常常把“逻各斯”描述得似乎有些“近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的意味,他指出:“这个‘逻各斯’(λσγos),虽然永恒地存在着,但是人们在听见人说到它以前,以及在初次听见人说到它以后,都不能了解它。虽然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但是我在分别每一事物的本性并表明其实质时所说出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人们在加以体会时却显得毫无经验。另外一些人则不知道他们醒时所作的事,就像忘了自己睡梦中所作的事一样”。(D1)不过,只要我们仔细体会一下这段文字,便不难见出赫拉克利特与老子的不一样之处。老子从根本上就认为“道”就是一种“无”,所以无论谁都看不见,听不着。而赫拉克利特则并非认为“逻各斯”本身是“无”,只是人们理解力不高,不能懂得它、了解它。所以赫拉克利特说:“我在分别每一事物的本性并表明其实质时所说出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人们在加以体会时却显得毫无经验。”请注意赫氏这句话中提到的是“事物的本性”、“实质”,这个“本性”与“实质”,决不是“无”,而是“有”,是一种存在之物,是万物的“实质”与“本性”,人们听不懂的正是事物的“本性”与“实质”,而表明“实质”与“本性”的,正是赫拉克利特本人,即此段文字中的“我”。这说明至少赫氏本人是看见了或听见了“逻各斯”的,如此他才可以“分别”事物的“本性”,“表明”事物的“实质”。这就是赫氏“逻各斯”与老子“道”的一个根本区别。所以说,“逻各斯”的根本特征是“有”(或存在)。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指出:“因此,应当遵从那人人共有的东西。可是,‘逻各斯’虽是人人共有的,多数人却不加理会地生活。”(D2)赫拉克利特明确指出“逻各斯”是人人共有的,只是人们不加以理会,或没有能力去理解它,听从它,因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D123)因此,赫氏主张去爱智慧,去寻求听从和遵循“逻各斯”。他说:“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D41)“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D51)听从“逻各斯”,实际上就是遵循万物的规律,认识那驾驭一切的思想,寻求事物生灭变化的规律与本质。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必然会走向“有”,而不会走向“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赫拉克利特曾摇摆于“有”与“无”之间,他说:“任何人都不能设想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像有些人认为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那样”。((形而上学》第4卷第5章1006b)的确,赫氏常常具有辩证的相对论观点:“不死的就是有死的,有死的就是不死的。”(D62)“善与恶是一回事”。(D58)这与老子的看法何其相似。但赫拉克利特最终走向了“有”,走上了从“有”寻求万物原因和规律之途,并把这个“有”陈述为实实在在的东西——“火”。赫氏认为,万物是由“火”构成,他说:“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D30)这“火”,决不是“无”,决不是老子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无物之象”,而是“有”,是实实在在之物,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正如邬昆如指出:存在的追求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目的。若用“太初”的问题来衡量赫拉克利特,则“逻各斯”是实体,“火”是表象,那么“太初是火”或“太初是逻各斯”,有同一意义。这里的哲学方法是:抓紧逻各斯,以逻各斯为出发点,通过“思想”达到哲学追求的对象——存在〔14〕。赫拉克利特终于从“逻各斯”走向了物质实体“火”,即从“求智慧”中观察万物,从观察万物中追问原因,寻求规律,“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的事物”,(D35)“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驾驭一切的思想”。(D41)而这条由求知——观察——追问原因——总结规律的链条组成的哲学话语规则和路径,正是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基本学术话语特征。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对“有”,对“存在”的研究追问之中,建立起了西方科学理性话语和确立逻辑分析推论的意义生成方式的。而这种话语系统,正是当代海德格尔与德里达(JacquesDerrida)等人所激烈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从赫拉克利特使“逻各斯”偏向“有”而肇其端的。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正是固执于“言谈所及的东西”,才把“逻各斯”解释为理性、判断、定义、根据等,也即把“逻各斯”归约为逻辑了。正因为总是以外在的“有”,即现成存在者为取向,古希腊哲学家们(如亚里士多德)在分析“逻各斯”时就不可避免地“误入歧途”,将西方文化导向一种外在的“判断理论”——逻辑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海德格尔指出:“古代存在论在论述生长于其上的方法基础时不够源始。逻各斯被经验为现成的东西,被阐释为现成的东西;同样,逻各斯所展示的存在者也具有现成性的意义。”〔15〕因而,传统存在论的迷误就是“逻各斯”的不幸,此不幸即是:“逻各斯”沦为现存事物的逻辑了。于是乎海德格尔便力图重新审视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本源意义,企图克服和改造传统以“有”为核心的存在论,站在全新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基点上来理解语言现象,“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从而拯救“逻各斯”〔16〕。无论海德格尔能否“拯救”逻各斯,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西方文化执着(或拘执)于“有”的特征。同时也可以发现中西方文化中“道”与“逻各斯”这种“无”与“有”的特征,或许还可以发现“道”与“逻各斯”互释互补的价值。老子“道”的崇尚“无”与赫拉克利特“逻各斯”的偏向“有”,都对中西文化与文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学艺术及文论中的“虚实相生”论,“虚静”论等,显然与老子的“尚无”密切相关,“无中生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话语方式,使中国文学与文论更注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空灵和“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隽永深长。同样,“逻各斯”对“有”的探索、追问与分析,也使得西方文化与文论显得更加严密而系统,更注重逻辑因果、注重情节结构。老子的重“无”,将中国文论引向了重神遗形,而赫拉克利特的偏“有”将西方文论引向了注重对现实事物的摹仿,注重外在的比例、对称美、注重外在形式美的文论路径。老子的“道”是不可道,不可言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述了这一点。但是“道”虽不可以道,不可以言说,然如果完全不用语言文字,就根本无法论述道;而老子既然著书立说,肯定又非用语言文字来言说不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指出:“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钱钟书说:“道不可说、无能名,固须卷舌缄口,不著一字,顾又滋生横说竖说,千名万号”〔17〕。具有“大智”的老子,实际上是认识到了这一两难悖论的,他清楚地知晓,“道”是不可以言说的,但他要著书论道,却又必须以语言来表述这不可言之道,以名号来名不可名之名。老子于是迫不得已走向了“强为之名”、强为之言之途,“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25章)这种“强为之名”,实际上必然造成“道”之本真的失落。王弼注曰:“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定之所由,则系于大,大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为之名’”。显然,这种“强为之名”,是“失其极”的,老子之所以曰“强为之名”,实是不得已。不过,在这不得已之中,老子实际上闯出了一条“以言去言”之路,即通过有言,教人去认识、去领悟那无言之道,从而超越语言,直达“道”之本真。魏源《老子本义》说:“圣人知有名者之不可常,是故终日为而未尝为,终日言而来尝言,岂自知其为美为善哉!斯则观*而得妙也。若然者,万物之来,虽亦未尝不因应,而生不有,为不恃,终不居其名矣。”(《老子本义)第2章)魏源的解说是准确的,老子正是以言达到无言,以名寻求无名,从语言描述之中令人捕捉那微妙之道,去体悟那纯真之道。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说:“体不可以言说显,而又不得不以言说显则亦无妨于无可建立处而假有设施,即于非名言安立处而强设名言,……体不可名,而假为之名以彰之。”〔18〕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种“不言之教”,正是以“有言”来加以导引的,于是乎,语言便成为了桥梁与津渡,引导着人们通向“道”之本真。老子这样为我们描述那纯真之“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老子》21章)王弼注曰:“至真之极,不可得名,无名则是其名也。”这就是无名之名,无言之言。“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老子》22章)在通过有言来达到无言的津渡中,老子处处提醒人们,不要拘执于言,而要追求超越语言的“无言”;这就是后人强调的“不落言筌”,“不要死在言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意。老子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37章)道虽无名、无象、无言,但却是本真,是大音、大象,“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41章)从“无名”到“有名”,最终还是要回到“无名”,回到“道”之本真。这就是老子“道”“不可言”的特征,这种特征是言无言,以不言言之,或者说通过言说使人明白道不可言说。对这一点,庄子表述得更为明确,“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外物》)所以庄子说:“终身言,未尝言。”(《庄子·寓言》)言说的关键是直指“道”本身,而不必拘执于语言,这样就可以超越语言之拘囿,这就是庄子著名的“得意忘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海德格尔对老子的“道”的这一不可言说特征亦颇有体会,他指出:“也许在‘道路’(way),即‘道’(Tao)一词中隐藏着运思之道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如果我们让这一名称回复到它未曾说出的东西那里并且能够这样做的话。”〔19〕因此,海德格尔反对西方人将老子的“道”译为“理性”或“逻各斯”,他说:“老子的诗意运思的主导词语即是“道”(Tao),根本上意味着道路。但是由于人们容易把道路仅只设想为两个位置之间的连续路段,所以人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的‘道路’一词是不适合于命名‘道,所言说的意思的。因此他们把‘道’译为理性(reason)、精神(mind)、理由(raison)、意义(meaning)和逻各斯(Logos)等。”〔20〕看来,海德格尔已经觉察出“道”与“逻各斯”虽同为不可言说之道,但中西方的哲人们对“道”与“逻各斯”的理解与阐释是有差异的。海德格尔在《讲与论文集》中指出:“在西方思想开始之际,语言之本质在存在之光亮中偶有闪现,赫拉克利特也一度把‘逻各斯’视为主导词的光芒,接近它所照亮的东西。”〔21〕在这里,海德格尔所谓“没有人抓住它的光芒”,实际上是指出了在西方哲学史上,“逻各斯”没有被引向不可言说的道之本真——“大道”(Ereignis),而是最终导向了可以言说的理性、规律与逻辑。而这,正是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又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传统哲学对“逻各斯”的解释并没有触着其基本含义。“逻各斯”之本义乃“言谈”,传统的解释却把“逻各斯”归纳为“逻辑”,从而把语言当作逻辑的体现。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存在论的迷误就是“逻各斯”的不幸,此不幸即是:“逻各斯”沦为现成事物的逻辑了〔22〕。应该说海德格尔的眼光是极为锐利的,他的确洞察到了“逻各斯”的“惊鸿一瞥”,但也仅仅是“一瞥”而已。因为根据赫拉克利特著作《残卷)所显示,赫氏的“逻各斯”,仍然是倾向于可以言说的理性,可以认识的规律以及可以把握的外在事物。赫拉克利特曾明确要求人们,不但应当去遵循、去听从“逻各斯”,而且应当去认识、去把握“逻各斯”。他说:“‘逻各斯’虽是人人共有的,多数人却不加理会地生活着。”(D2)〔23〕“人们既不懂得怎样去听,也不懂得怎样说话。”(D19)因此他倡导人们听从逻各斯,并进而认识逻各斯。“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D50)所谓“智慧”,就是听从“逻各斯”,而“逻各斯”在何处呢?赫氏暗示,“逻各斯”就在自然之中,因此,智慧就是听从自然,认识自然。他说:“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D12)从以上论述来看,“逻各斯”是完全可以被表述、被言说的。正如赫氏所云:“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显然,“说出真理”,就是可以言说,也正因为“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赫氏才指责有些人“既不懂得怎样听,也不懂得怎样说话”。(D19)这里指责的只是人们“不懂得怎样说”,而不是指“逻各斯”根本不可说。怎样才能够“懂得说”呢?在赫氏看来,那就是去认识万物,去寻求规律,去言说驾驭万物的“逻各斯”。赫氏强调的是认识外在之物质世界,强调感官的重要性,主张从外在世界中去探寻原因,把握规律。他说:“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的事物。”(D35)“可以看见、听见和学习的东西,是我所喜爱的”。(D55)“人们认为对可见的事物的认识是最好的,正如荷马一样,然而他却是希腊人中间最智慧的人”。(D56)显然,在赫氏看来,事物是可以认识的,通过学习探索,不但可以懂得怎样“听”,而且可以懂得怎样“说”,可以把握万物的规律,“智慧只在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D41)“最优秀的人宁取一件东西,而不要其他的一切,就是: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D29)如果你要想理智地说话,就应当用这个人人共有的“逻各斯”武装起来,你就能理智地说话。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这种可以认识,可以言说的逻各斯出发,强调理性、强调万物的规律,强调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把握,于是便走向了从“求知”(求智慧)到“观察”(认识自然)再到“追问原因”和“逻辑推理”的逻辑分析话语系统,建立了以可以言说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分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正如有学者指出:赫拉克利特强调了运用“逻各斯”,亦即运用理性认识能力的重要,但他并没有走向极端而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相反,他充分肯定了感性认识的地位和作用。他对“逻各斯”的强调,从理论上看,即力图将物质性的世界运动的规律性与主观世界的运动的规律性统一起来,亦即企图把存在和思维在物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24〕还有学者指出:赫拉克利特用“逻各斯”概念,指出了“智慧”之概念,说明人类虽因愚笨而丧失了理性,但是,人之求知仍然可以在“逻各斯”的保护下,重新回到理性的怀抱中〔25〕。显然,通过“求知”去认识自然,掌握规律,从而达到“用‘逻各斯’武装起来,就能理智地说话”,(D14)这正是赫氏“逻各斯”的言说之方法。这与老子主张的“绝圣去智”(《老子》19章)“行不言之教”(《老子》2章)的“言无言”的言说方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绝圣去智”式的不可言说的方式导向了“得意忘言”,追求“不落言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化与文论话语方式。而以求取智慧、探寻万物规律为己任的“逻各斯”,推崇的是“理智地说话”的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将西方文化与文论导向了科学理性的逻辑分析话语方式,导致了西方文论那种理性的、条分缕析的系统性科学性特征。而这种科学理性逻辑分析话语,正是从赫氏“逻各斯”起步,最终由亚里士多德来完成的。恰如有学者指出:逻辑学(Logik)在希腊哲学中是关于逻各斯(Logos)的科学。希腊哲学把Logos解为陈述(Aus-sage)。所以逻辑学也就是关于陈述的科学。逻辑学从陈述方面来规定思想,也即在思想的表达中来寻找思想的法则和形式。逻辑学提供出思想的逻辑法则。人们认为,思想是以逻辑为本质的,逻辑与思想,几乎就是一回事。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逻辑和思想与源始意义的Logos和思想,相距已经不止千里了。逻辑植根于形而上学中。在希腊形而上学中,发生了从源始的Logos到逻辑的演变。这就是源始的思想的隐失过程〔26〕。海德格尔指出:“Logos成为陈述,成为真理即正确性的处所,成为范畴的本源,成为关于存在之可能性的基本原理。‘理念’和‘范畴’,后来是统辖西方思想、行为和评价即整个此在的两个名称。Physis(存在)和Logos的变化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变化,是开端性的开端的沦落。希腊哲学在西方获得统治地位并不是由于它的源始的开端,而是由于它开端性的终结,此终结在黑格尔那里最后构成了伟大的完成。”〔27〕显然,海德格尔认为,“逻各斯”成为“陈述”,或者说成为可以言说之陈述时,便意味着从古希腊哲学的“开端性”沦落,这使得与中国“道”相似的、含蕴丰富而深刻的“逻各斯”,终于沦落为关于存在之可能性的基本原理,甚至成为思维形式,成为逻辑。海氏所谓“沦落”,显然带有他主观性的贬义色彩。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古希腊哲学的“沦落”,不如说是中西文化的“分道”:或者说是中西哲学分道扬镳的肇端,“道”与“逻各斯”,正是从“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两难境地之中,各自选择了一条路,各奔前程,从而形成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文化与文论话语言说系统。这种话语言说系统,一经铸就,便成为规范文化的强大力量,具有不以某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大的约束力。尽管西方文化与文论不断有反判科学性、反叛“逻各斯中心”思潮的产生,如西方的某些宗教思想、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乃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当代解构主义大师们对“逻各斯中心论”的激烈批判,实际上都未能真正彻底摆脱西方文化那根深蒂固的科学理性的逻辑分析话语系统。就连极为睿智、洞见“逻各斯”开端性“沦落”并决心寻回“大道”(Ereignis)的海德格尔,在激烈批判“逻各斯中心论”的同时,也身不由己地重新“沦落”进了西方传统话语言说方式的窠臼之中。孙周兴在《说不可说之神秘》一书中指出:“我们也确实感到,正是在‘大道’(Ereignis)一词上,体现着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深刻的‘两难’:一方面,海氏力求挣脱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概念方式和学院哲学的言说方式,寻求以诗意语汇表达思想;而另一方面,海氏所确定的‘大道’以及相关的词语,恐怕最终也透露了一种不自觉的恢复形而上学的努力”〔28〕。为什么海德格尔最终无法摆脱西方言说方式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还没有(大约也不可能)彻底改换一整套话语言说方式,既然他终归要“言说”,要“陈述”,而且是西方式的言说与陈述,那么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沦落”:“打破了‘沉默’,终难逃被误解的厄运。诉诸言谈的东西终归要获得非生成性的本质内核。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日子里,围绕海德格尔的‘大道’思想的争辩仍将进一步展开,而此种争辩的中心题目脱不了的是:是否从‘大道’中可见出海德格尔重振形而上学、恢复哲学的‘元叙述’的努力?或者,‘大道’可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终极能指’吗?如在德里达(JacquesDerrida)那里,我们已然可见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这样一种责难了。不过,德里达本人,恐怕终究也难逃这同一种责难”〔29〕。海德格尔与德里达这种似乎在劫“难逃”的命运,不正显示了西方文化与文论话语强大的约束力么!而中西方文化与文论的这种约束力之初源,正滥觞于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老子“道”的“不可言”与赫拉克利特的“可言”,对中国与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影响是根源性的、重大而深远的。注释:〔1〕请参阅拙文《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文化病态与文论失语症》(《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2〕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台湾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3〕MartinHeidegger,EarlyGreekThinkingHarper&RowPubilishers,SanFrancisce,1984。〔4〕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3页。〔5〕MartinHeidegger,IdentityandDifference,Pfullingen,1957。〔6〕MartinHeidegger,OntheWaytoLanguage,HarperCollinsPublishers.1971。pp.72。〔7〕《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页。“D1”为柏林版第尔斯(Diels)辑《苏格拉底以前哲学残篇》的标准序数,下同。〔8〕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第189—190页。〔9〕参见《希腊语—英语词典》,李德尔与斯柯特编,牛津,1883年版。〔10〕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第180页。〔11〕杨适《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175页。〔12〕参见杨适《哲学的童年》,第175页。〔13〕参见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第181—182页。〔14〕邬昆如《西洋哲学史》,台湾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第40页。〔15〕MartinHeidegger,BeringandTime,Harper&Row,1982。中文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16〕参见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51—52页。〔17〕《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0页。〔18〕熊十力《破破新唯识论》,台北广文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8—19页。〔19〕arnHeidegger,OntheWaytoLanguage,pp.92。〔20〕MartinHeidegger,OntheWaytoLanguager,pp.92。〔21〕参见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270—271页。〔22〕上书,第58、52页。〔23〕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下同。〔24〕叶秀山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54页。〔25〕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第182页。〔26〕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109页。〔27〕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图宾根,1987年版,第102页。〔28〕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303页。〔29〕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304页。
- 上一篇:台湾名品城范文
- 下一篇:公司税务管理制度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