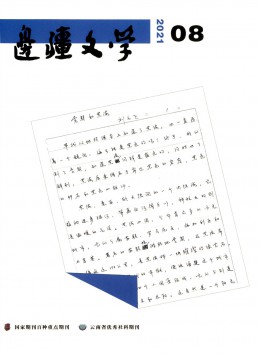文学发展论文:电影与文学发展自由之路

本文作者:石 锋 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这类文学常常以印刷的形式固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但文论家们提及“文学”时,常指向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层面以及由内容与形式所显现出的某些“本质”。还有人根据其社会功能而将文学视为某种精神特质,或仅仅表示一种运用语言的能力。由于彼此交叉又不重合的多种含义,“文学”一词常常被加上一些定语或词缀以表明所指,如现代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性、文学化等。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那里,也会出现对“文学”的不同意义或内涵的使用。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篇就提出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假设:文学行将消亡和文学既普遍又永恒。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学中不断变化的部分(前者)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后者)。那么,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否存在呢?米勒以印刷业的发展与读写能力的普及、民族文学的研究、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以及“自我”观念的确立等作为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基本特征,并以这些特征的转型或消解来昭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走向死亡的命运。根据米勒的追溯,该意义的文学得以确立也不过200余年的历史,更明确的狭义的文学观念则是近100年左右才广泛推及的。如果将这种文学观念视为以往全部文学连续性发展的成果,并将它的消亡作为整个文学历史的终结,则文学将面临的是结束历史使命,被其他人类活动取代的宿命。然而,如果仅将这200年的文学观念视为文学漫长演变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则它的结束便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文学不是走向消亡而是会有新变。的确,近两百年的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度甚至成为人类生活中主要的精神活动,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200年的时间相对于文学数千年的历史而言,实在不能算很长。当现代意义的文学确立之时,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的文学已然消亡?印刷精美的文学典籍的出现,是否宣告了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终结?当然不。既然此前的文学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芒,那么我们又为何面对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扼腕叹息着文学的衰落呢?当然,新媒体的出现使捧书而读日渐成为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并对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意味着文学样式上的改变,也动摇了此前关于文学的本质与作用等的观念。如果此时宣告文学的死亡还太早的话,那么,在这新的时代乃至未来,文学又将靠什么作为根基才能确立自身作为文学的意义?
什么使文学成为可能
米勒所论,主要围绕着导致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得以确立的几个基本要素,他并未涉及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理论,自然也不包括当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如果把文学这一概念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上,则文学成为可能应追溯至其萌生的源头。当我们弄清文学何以产生,以及其后人们为什么离不开文学,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满足人类何种需求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也许才会得出一个较明确的结论,关于文学是否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将走向消亡。关于文学的起源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就包括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和劳动说几种。且不论哪一种观念更接近历史真相,抑或历史上文学的产生本就是多源头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必是为满足人类某种需求才得以出现的。而作为长久以来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文学必然与人类的某种根本性需求相联系,这也是决定文学本质及其未来命运的关键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谓“自由自觉”,就是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不论人类目前已实现了多大程度的“自由自觉”,还要经历哪些过程才能到达马克思理想中的“人获得全面和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解放与实现自由始终是人类奋斗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以物质生产活动克服生存资料的匮乏,获得肉体生存的条件,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人类也以各种精神活动,如巫术和游戏,来克服心灵的恐惧与疑惑,进一步拓展着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赢得更大的自由。在摆脱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束缚与压抑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并确证着自己的价值与创造力,而这种确证又反过来激发人类向新的束缚挑战。因此,追求解放与自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核心动力。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关于文学起源的诸种说法,不难发现,这些学说中都包含着人类解放自我的企图。“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现实生活条件,他们企求从精神上得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模仿、游戏、巫术都是进入这个空间的途径。劳动说则具体地阐述了这种精神企求的历史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企求迄今仍然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4]正如萨特所言:“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5]人类以文学为途径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其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而文学的某些内涵及功用也相应发生着改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满足着文学用语言来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以之弥补现实的功能,这也就是米勒所说的,文学展现的“世俗魔法”[2]32。虚构,也成为很多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在现实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情感、理想、欲望等受到压抑或遇到阻碍时,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在文学的世界中释放或自我安慰,以获取替代性的和暂时的自由体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和萨特的文学自由说正指向文学的此一功能。现实主义文论的典型说以及在中国一度颇具影响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等,也无不体现出人们以文学来弥补现实缺憾的做法。当人们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时,一切规则与约束都可能激起人们冲破它的愿望,虽然这些现有的规则在最初也许就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由而设。这些规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以及一切可能成为权威和框框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具有约束力的东西都会成为自由的阻碍。而规则又总是理性的社会所必需的,要加以严格保护的,于是人们只好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渠道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和话语,总最先出现在文学艺术中的原因。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革命中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不仅仅在于形象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更表现在文艺的不合规范、非正统、非理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反叛姿态,显示出某种“离经叛道”的潜质。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之维”———审美中的想象性活动是对于人类异化的一种解放形式。文学“向既定现实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挑战的”[6]。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追求自由的目标并不一定要靠虚构来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事实或虚构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因为虚构只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才是目的。一桩真实的事件可以取得和一部小说同样的感人效果。也有很多人指出,生活远比文学虚构更富有戏剧性,更充满着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也有着实现自由的可能,虽然那常常是偶然性的和短暂的。米勒称:“所有文学作品,不论是否直接提到魔术做法,都可以视为一种魔术。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能开启新世界的咒语、戏法。”[2]32-33其实,魔术的魅力就在于使人感觉超越现实的常规,做出不可能的事(或称奇迹),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体验。文学也正是以语言的方式描述着一个个令人着迷、惊叹、神往和震撼的新世界,使现实中的不可能变为文学世界中的现实。这是文学能够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心灵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同样是人们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终于突破了文字阅读的障碍,直接以图像展现更加逼真和不可思议的魔术,于是影视作品取代了印刷文学的位置,网络虚拟世界填充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既然有比文学阅读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体验自由的梦想,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书而终”呢?
告别的是什么
米勒忧心忡忡地说:“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2]7现代意义的文学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学研究的转向和边缘化也成为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这种忧虑在文学领域早已弥漫,因为传统意义的文学的确正在淡出人们的生活。电子时代的来临宣告了“印刷时代的终结”[2]15;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书本去观看影视作品;文学刊物的发行量迅速缩减;研究性图书馆正在过时。以竹简、纸张为传播媒介的书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文字是主要的传播符号。然而,20世纪电子媒介开始抢占传统媒介的地盘。电影那种逼真、动人的影像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随着电视进驻千家万户,人们更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影像的包围之下。计算机互联网则提供了一个集各种媒介于一身的传播系统,声音、影像、文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电子媒介系统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电子文化。印刷文明并未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已遭到了电子文化的大幅度挤压。环绕于印刷文明周围的传统文化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甚至令丹尼尔•贝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7]米勒在他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中提出了“寄生”与“寄主”的文本关系。他认为,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系列“寄生”的东西,即存在着对以前作品的模仿、借喻,乃至存在着以前作品的某些主要精神。但它们存在的方式奇特而隐晦,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升华又有歪曲,既有修正又有模仿……以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又被新文本以改编的方式破坏,或者说必须适应新文本的精神基础。新的文本既需要以前的文本,又需要破坏它们;既寄生于以前的文本,靠它们的精神实质生存,同时又是它们“邪恶的”寄主,通过吸食它们将它们破坏。“寄生”与“寄主”的关系存在于一切文本,形成一个历史的链条。这种关系贯穿于整个文学过程,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关系中,也存在于不同批评文本或批评话语之间。[8]我们不妨将这种关系推广至一切文化形态之间,传统的印刷文学与当代的影像作品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一种类似的状况。影视剧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原有文学的影视形式,它有文学的话语方式和主要精神,在文化功能上也有许多一致性,然而它已成长为对“寄生物”———文学———具有一定杀伤力的新的“寄主”。
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那些久已习惯于阅读印刷书籍的人们,如米勒,自然不甘心于纸质文学被“吸食”甚至被取代的命运。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究竟以何种形式出现,是否被改写,文学的命运即将如何,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虽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文学曾一度独领风骚。在中国,还曾有以文选仕的制度,文学不仅是读书人的必修课,甚至是关乎个体安身立命与国家社稷的大事,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人类不会为任何理由而停止自己的脚步,因为追求超越与更大的自由是人类的本性。其实,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并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不会放弃每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文学与语言同在,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文学就不会死亡。旧的文学走向终点,新的文学必将出现。现有的网络文学已极大限度地拓展了创作与阅读的自由度,超文本等新的文本样式提供了莫大的意义空间。而电影与电视剧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学的变体与发展。文学在新的媒介中产生了多向度的意味,正以新的姿态进入更多人的生活。总之,用米勒的话来说:“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正在日益取代它。这不是世界末日,而只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2]17-18我们可以坦然地向印刷文学统治的时代告别,并乐观地迎接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 上一篇:传统文学论文:分析天赋与俄罗斯文学传统范文
- 下一篇:谈论对影视现象非文学批评范文
相关文章阅读
精选范文推荐
- 1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 2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
- 3文学与影视的关系
- 4文学与教育的关系
- 5文学与文化
- 6文学与文化论文
- 7文学与艺术关系
- 8文学与艺术的碰撞
- 9文学与艺术研究
- 10文学与语言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