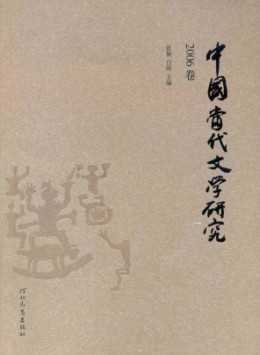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文学解读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文学解读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在当代文学教学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女性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延展开来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潮流中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等一系列紧密关联的重要现象和命题。
关键词:当代文学;新女性文学;身体写作
一、女性主义写作的意义指向
女性主义写作与女性身份认同以及女性话语表达之间的关联性,使得女性主义文学在欲望写作与身体写作的层面上有强烈的表达。因为整个人类书写的历史都浸透了男性中心主义,所以女性书写理念倡导者坚持开创一种全新的女性书写,即让写作回归女性身体,从描写女性身体的独特经验开始,让女性重建对世界的认知,让世界正视女性的存在。商品市场经济时代,女性更多地被贴上了商品的标签,或者成为各种商品的附属物,如豪车与美女,而男性成为消费者,尤以“成功’’的男性为主。商品经济取代男权文化成为女性新的主宰,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写作不无现实地具有批判意义。女性主义写作与女权主义思想之间紧密相连,它从一开始便以其对男权文化以及相关的思想观念的强烈质疑而显示着自己的价值。20世纪20年代以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庐隐的《海滨故人》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显示出了西学东渐之后在现代思想启蒙下女性意识在文学写作中最初的自觉。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表达,一方面十分注重对深深地镶嵌在封建专制体系中的男权文化思想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努力地展示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决绝抗争的勇气及其所承受的伤痛与孤独感。从长久的男权文化压制下所苏醒了的女性解放意识,具有一种强烈的对抗与批判要求,它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思想解放力量,体现出了一种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价值取向,成为那个时代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20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中,20年代的女性写作虽然数量有限,但却是最为醒目的,它激起的社会反响也是最强烈的,同时也使得女性意识的自觉与解放诉求成为三四十年代女性写作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政治解放到身体解放:复苏的女性话语表达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五四”意义层面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表达不复存在,有关女性命运及处境的描写被纳人到了阶级斗争与阶级解放的话语体系之中,对旧中国妇女命运的描写主要是揭示旧时代妇女受压迫的悲惨人生,以及在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介入下翻身获得了解放,20世纪40年代于延安解放区由丁毅、贺敬之所执笔完成的歌剧《白毛女》及60年代的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这一写作模式的最佳范本。而在这一时期,另一种有关女性面貌及命运的讲述是对新社会中全新的妇女形象的塑造,在这种塑造体系中,主要是显示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半边天等种种意义内涵。也就是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妇女解放问题以完成时的语态与方式在被描写和叙述。在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被看作是成为社会解放以及政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受压迫成为封建主义旧思想及封建制度罪恶性的一个证明,因此,革命之后的新社会中妇女不再受压迫,妇女翻身得解放,便成为必然的结局。而如果依然出现不平等的、妇女受歧视或压迫的事实,则便被看作是封建旧思想的残余,是旧制度的遗留物。言下之意,新制度中是不会产生这种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的,或者说新制度没有妇女受迫害的问题,或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在这一思想逻辑下,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对新社会妇女处境的描写完全跳出了“五四”时期与男权文化相抗争的表达方式,转而以一套全新的阶级解放的话语体系进行书写,努力展现新社会下妇女全新的精神面貌,小说《李双双》中的女主人公李双双是这一时期新政权下社会主义劳动妇女新形象的最具标志意义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女性主义思潮全面复苏与觉醒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便是王安忆,她在80年作的作品在两个层面上有着突出的意义,一是以女性个体成长体验为叙事支点的文学写作;另一个便是女性主义意识的强烈表达。前者是以《雨沙沙沙》为代表的“雯雯系列”,后者代表性的作品便是王安忆的“三恋”,即《小城之恋》(1986)、《荒山之恋》(1986)、《锦绣谷之恋》(1987)。“雯雯系列”中始终存在的便是一个成长中的女孩的叙述支点,这种个体成长体验的层层展开,形成了王安忆小说独有的沉静之美,也使得她的写作游离于“政治一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呈现出一种独有的个人风格特点。而王安忆的“三恋”则以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深人剖析,以及对性之于人生的探讨而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写作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世纪90年代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个活跃期,也是女性主义文学向纵深推进的一个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女性文学写作以其体现出的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意识而令人侧目,同时也使得女性主义文学成为彼时最为突出的一股文学思潮。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东渐有密切关联。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于80年代初传人中国,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批评思潮。正是在这一时期,以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等为代表的新女性作家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潮流。
三、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成长表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呈现出强烈的叙述“自我”的特征,作家们常常将自我对外在世界一切的感知作为叙事的主体内容,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自我体认意识。正因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常常是在一种自我心理的书写中展现个体独特的成长体验,可以说,就成长叙事而言,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成长叙事体现得最为强烈和纯粹,“成长”成为作家寻找自我、体认世界、感知时间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这在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绵绵的《糖》以至春树的《北京娃娃》等作品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陈染的写作一直是中国文学中最强烈地追寻个人世界的隐秘表达的一脉的代表。她总是活在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世界之中,从不屈服于外界的冲击和压力,也并不向自我的孤独和寂寞低头。她始终在内心的禁区中守望,不断试探内心与外部的边界所在。她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从个人的内心出发的倾诉欲望,也有不断清理个人记忆的愿望。她一面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向外部的他者发出询唤,期望得到他者的理解和认同,一面不断拒绝外部世界的冲击和侵扰,强化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孤绝感和个人世界的自主性。陈染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倾诉的特色,她总是不惮于将内心最复杂和最微妙的感情加以表达。陈染善于捕捉那种复杂、微妙和难以表达的心灵世界,她的这种表达是极具人性开掘的突破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陈染的写作标志着一个新的个人化的时代的到来。而这个时代正是今天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新的时代。个人确实得到了实现,而个人的自由也意外地变成了不受拘束的放纵的身体和急于被满足的欲望。女性得到了身体的自由,但却被消费和时尚的潮流奇观化,变成了被享用和消费之物¥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主体,它不能不在和他者的相遇之中存在。陈染的内心独白式的倾诉总是试图期待、接纳、认可他者,将自身的希望寄托于他者。但随着他者面貌的展开,她却发现他者的面貌总是破坏、侵越自我的安宁和尊严,于是个人试图逃离他者。陈染的作品不断地书写着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追溯和回忆,这种回忆成为确认自我的一种方式。陈染将童年和少女时代的经验中朦胧的、不清晰的过程通过回忆来加以展开,这种展开的目的是理解和认知自我,将我是谁的问题通过回忆再度提出来。陈染的回忆里经常有少女和成人男性接触的奇诡经验。这些经验是少女告别童年的不可逃避的过程,但这种和他者面貌的相遇却也是幻灭的过程。少女幻想的浪漫被坚硬的现实击碎,少女失掉了天真,体验了实在世界的无法消除和忽视的残酷。人脱离天真进人世界的过程是无奈,又是期望。陈染在这里提供了个体生命的最真切、最切实的表达,这种表达也意外地变成了中国告别天真、进入世界的隐喻。天真少女发现了外部与自身的疏离,发现形成的自我在外部的冲击中进退失据的慌乱和犹疑。于是,个人失掉了天真,变成了成人。陈染在这里将不间断的、绵延的回忆展开成为今天中国记忆的重要部分。它的关键之处在于陈染用小说表现的个人经验在此变成了一个社会在曲折和困扰中探求和寻找的可能性的表征。陈染自己也曾说过,一个好的作家作品,都会有“心灵自传”的成分,无论他书写社会人生什么样的话题,都会包含他自己的价值观、思想、情感和爱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人生活》可看作是作者自己的精神成长史。陈染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身体写作的特征。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私人生活》等作品中,涉及了青春少女时代的经验和极为个人隐秘的生活情史。在叙述中,陈染对青春少女性意识觉醒后既惧怕男性而自守,又渴望男性而含情脉脉的躁动不安,以及女性在生命内部重大变动时期(如初潮)、既张皇失措又甜蜜沉静的矛盾心情做了极为细腻、清晰地描述。在代表作《私人生活》里,陈染以倪拗拗这个出生在都市书香家庭的女孩子为主人公,讲述了她敏感、封闭而又隐秘的成长体验.高中老师T、邻居独居的女人禾、大学时代的同学尹楠,成为她记忆这种成长的重要节点。而在这种成长的体验与叙述中,与身体有关的性的体悟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陈染以这样的途径,找到了回到个人心灵世界的路途,由此而专注于女性自我内心世界的抒写,从而传递出对男性话语所营造的空间与生活的怀疑与拒绝。林白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中另一位颇具标志性意义的作家。林白的写作与陈染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都以一种独语体的方式对一个女性的成长在心灵的层面上进行追忆和展开。同时,林白在其作品中对热衷于对女性个人体验进行极端化的描述,专注于讲述绝对自我的故事,她还善于捕捉女性内心的复杂微妙的涌动。《一个人的战争》是部相当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借着这本小说,林白有意总结她早期的生活及创作经验,并思索一个女性为写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全书始自五六岁(叙述者)林白抚摸自己,初识身体的欲望,一路描写她的少年学习经历,初燃的创作野心,流浪四方的奇遇,一再受挫的恋爱,被迫堕胎的悲伤等情节。她最后辗转由家乡来到北京,“死里逃生,复活过来”。林白洋洋洒洒写来,颇有不能自已的时候;但全书的形式虽不够精致,仍有一股直率动人的力量。往事不堪回首,但也只有真诚地检视过去岁月的希望与虚惘,自剖年少的轻狂与虚荣,作家才能开拓出更成熟的视野。林白写自己成名心切,曾贸然抄袭了别人的作品,留下洗不清的污点;写自己一心壮游他乡,却在最可笑的骗局中失去贞操;也写自己为爱献身,几至歇斯底里的绝望。自揭疮疤,不是易事。但林白告解忏悔的动机无他:生命最绝望的时刻反而成就她对创作最深切的执着。一个女作家的成长,真是用身体来作为赌注。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写作以其强烈的女性自我表白与自我体认意识而打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回到自我个体的成长体验中去寻找自我的历史影像与心灵记忆,由此构筑女性个体历史空间成为作家们不约而同的叙事走向。的确,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正是以其强烈的自我体认而表达出对以往男权文化压制下的女性书写的拒绝与反抗,女性个体成长体验的细腻呈现,恰恰表达出的是对男权文化为代表的政治权力话语的排斥。独白的语体风格、身体感性的认知方式,都显示出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在文体层面上的大胆探索与坚决的转型。女性文学中自我言说式的心灵独白看上去将文学写作带向一个狭小的写作空间,境界与格局都十分有限,这在从王安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小说创作中便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到陈染、林白等的创作中更是走向了成熟,但正是这种带有“排他性”的自我叙述,使得女性文学写作能够远离现代以来一系列的宏大叙事命题,而这种刻意的回避,恰恰是女性写作确立自身价值体系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女性文学的写作常常与欲望写作及身体写作相关联,在她们对历史的追叙中,传统文学中的时代风云面貌被极大地淡化,一切都聚焦到了自我个体的生命成长记忆中而加以过滤和展开,身体而不是语言成为与外界世界对话的重要途径,从而使得女性文学写作中的这种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更具个人的真实性,而不是在某种现成的话语体系中来完成对世界的认知。所以,陈染、林白等人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身体写作的倾向,其内在的是一种女性写作立场的表达,这与后来卫慧小说《上海宝贝》中的那种感观化、肉体化的身体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陈染、林白等人的身体是另一种言说世界、感知历史、体验生命的方式,卫慧以及春树小说中的身体则是后工业时代的消费语境中被物化的欲望的表达,是以身体欲望的直接书写来呈现在碎片化的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陈染、林白等的文字书写则有着诗的特质,个体记忆沿着身体的点点滴滴的感知而展开,对身体记忆的追叙成为个体对生命、情感、历史、社会、人际等一切认识的重要方式。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话语体系的承载,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女性话语的体现,而对个体成长的追忆和叙述则成为女性重建自身历史体系的一种策略和g说方式。
作者:郭剑敏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 上一篇:现代职教理念下当代文学课程的应用范文
- 下一篇:比较文学的方法解读外国文学作品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