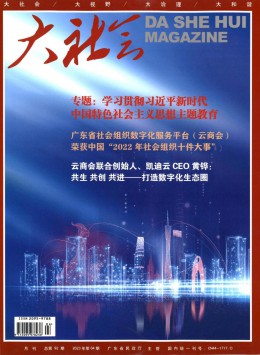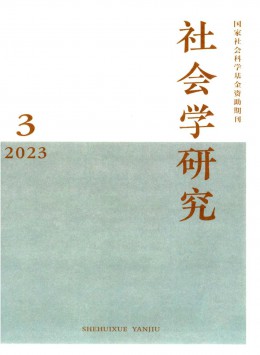社会经济损失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船舶油污损害;纯经济损失;赔偿;中国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1-0097-02
前 言
随着中国石油储备战略的实施,近年来,中国海上石油运输量迅速增加,石油泄漏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及巨大损失。据统计,自1979―1999年的二十年间,中国海域共发生船舶溢油事故2 353起,平均每3.5天发生一起,溢油量在50万吨以上的重大事故为5起,总溢油量约29 754吨 [1]。船舶油污造成环境损害或潜在的环境损害危险,使得受害者遭受收入及利润损失,这类损失大多与财产权损害无关,属于纯经济损失。关于因船舶油污造成的纯经济损失是否给予赔偿的问题,中国的司法实践及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一、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的内涵及立法论视角
之审视
(一)纯经济损失的内涵界定
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的赔偿建立在侵权纯经济损失赔偿与否的基础之上,而侵权行为所致纯经济损失赔偿在各国法律与实践中是大相径庭的。所谓纯经济损失,指被害人所直接遭受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或金钱上的损失,它并非是被害人的人身或有形财产遭受损害而间接引起的,或者说,它并非是被害人所享有的人身权或物权遭受侵犯而间接引起的[2]。由于纯经济损失具有直接性、无形性及抽象性等特征[3],各国对纯经济损失是否赔偿的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模式,除了法国等少数国家,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长期以来都对侵权行为所致纯经济损失的索赔予以限制。
(二)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公约体系中的赔偿问题
国际社会为应对船舶油污索赔问题,于1969年签订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下称CLC-69),并于1992年通过新的议定书对其进行了修改。《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下称FC-71)是对CLC-69的补充,其目的在于,减轻CLC-69给船舶所有人带来的额外财政负担,同时,弥补CLC-69不足赔偿的部分 [4]。但CLC-69和FC-71所适用的“污染损害”没有关于纯经济损失的规定,为了解决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是否赔偿、赔偿范围如何确定等问题,《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下称CLC-92)、《1992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下称FC-92)对污染损害进行了重新定义:由于船舶泄露或排放石油,在船舶之外因污染而造成的损失和损害,不论这种泄露或排放发生于何处,但是,对环境损害的赔偿,除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利润损失外,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行将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5]。但公约仅承认了对环境损害所造成利润损失的赔偿,对于其他形式的纯经济损失赔偿与否,没有明确的规定 [6]。
为了统一油污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国际法律,尤其是油污损害范围及计算方法,保护海洋环境,国际海事委员会于1994年通过《国际海事委员会油污损害指南》(以下简称《油污损害指南》);而针对CLC公约中定义模糊的问题,国际油污赔偿基金(IOPC Fund)编写了《索赔手册》[7]。指南和手册根据CLC-92和FC-92的精神,不仅规定了一般原则,更具体规定了损害赔偿范围,使得公约更具可操作性 [8]。
《油污损害指南》第3条将经济损失区分为相继经济损失和纯经济损失。相继经济损失指请求人因油类污染造成财产有形灭失或损害而遭受的资金损失;纯经济损失指请求人因财产的此种有形灭失或损害以外的原因而遭受的资金损失。相继经济损失可以获得赔偿;纯经济损失只有是油污本身引起时才能得到赔偿。仅仅证明损失和油污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不够的,只有在污染和损失之间存在合理的近因关系时,纯经济损失才能被视为由污染所引起。在确定近因是否存在时,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1)请求人的活动与污染区之间地理上的距离;(2)请求人在经济上依赖于受损的自然资源的程度;(3)请求人的业务活动在直接受污染影响地区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4)请求人自身能减轻其损失的范围;(5)损失的可预见性;(6)造成请求人损失的并存原因的影响[9]。
二、中国处理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赔偿应有的
立场
(一)原则上不支持对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的赔偿
中国民法承袭于大陆法系,不能用英美法系中的“可预见性”原理来指导中国的司法实践,所以油污损害赔偿的范围很难控制,又没有相应的立法加以规定,司法实践也少之又少。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中,对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的赔偿请求应采取原则上不予支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赋予受害人索赔权的谨慎态度,即适用“原则―例外”的赔偿原则。
首先,允许索赔纯经济损失可能过分扩大赔偿的范围,船舶油污侵权造成的纯经济损失,其索赔主体牵涉甚广,尤其在近海油污事故中,在事故发生地周围经营业务的商事主体无疑会构成索赔的庞大团体。纯经济损失的索赔将极大地稀释侵权者有限的赔偿能力,CLC和基金公约所规定的责任限额要求“当可索赔的请求总额超过限额时,要按比例降低索赔额”[10],因此,在赔偿主体的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索赔时,受偿主体越多、赔偿项目越多、数额越大,受偿主体平均获得的赔偿额越小,不利于受到油污直接而即刻损害的索赔主体获得足额赔偿。
其次,世界各国尚未设计出既能合理限制纯经济损失,又便于实践操作的规则和标准。即使通过所谓的“近因原则”加以限定,由于因果关系的确定向来标准不一,因此难以促成判决的统一,完全依赖主观色彩浓厚的因果关系判断来确定数额巨大的损害赔偿金的归属,不仅有失稳妥,而且难以令多数人信服。另一方面,基于索赔人数量、实际损害额的不确定性以及赔偿义务人对赔偿的无法预见性,油污纯经济损失的索赔很有可能在解决一个索赔问题的同时,引发相应的连锁诉讼。
最后,将于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纯经济损失,在理论界,多数学者基于防止索赔范围无限扩大及对赔偿义务人造成过重负担的考虑,主张对于故意侵权行为造成的纯经济损失索赔应予支持,因过失侵权造成的纯经济损失则不予赔偿,而实践中,故意促成油污事故发生的事件十分罕见。另一方面,与责任保险、社会保障制度将损失予以社会化分散不同,侵权行为法规制的是损害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如何分担问题,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就在于如何平衡加害人的“行动自由”和受害人的“权益保护” [11]。考虑到纯经济损失的不确定性及难以预见性,法律通过对损失的不同分类,将纯经济损失排除于损害赔偿之外,是基于对社会主体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的权衡。虽然纯经济损失价值不一定低于直接经济损失,但纯经济损失是一种脱离了受害人财产或人身而发生的不利益,它通常是民事主体生活于社会中所必须忍受的一种摩擦,否则人人将因彼此过度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胜其扰[12]。
现代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迅速,有些纯经济损失由加害人投保第三人责任险或由受害人投保意外事故险均可获得赔偿,这种方式可使损失很快得到合理的分散化解,比通过法律手段的救济更为适宜。因此,中国司法系统不必作出超前规定,旅游业、餐饮业、服务业等行业的损失可以通过保险制度予以保护,即寻找一个“深口袋”,构建一个“风险共同体”、一种“社会连带”的体系,以适应现代社会“生存权”不断勃兴的趋势[13]。
(二)例外赔偿的情形
在原则上不支持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索赔的法律环境中,渔民因船舶油污遭受纯经济损失的情形,应作为不予赔偿的例外。英国法院一直将渔民的纯经济损失作为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不赔原则的例外,其在“Land catch Ltd.V.IOPC Fund”一案的判决中这样解释赔偿渔民纯经济损失的合理性:油污虽然没有对渔民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但是渔民赖以生存的方式受到了影响,这可以视为油污造成的直接、即刻的损害,因此可以赔偿渔民遭受的纯经济损失[14]。也可以说,英国法院之所以允许赔偿渔民的纯经济损失,主要是基于政策考量,给予渔民的利益以特别的保护。对于海洋环境经济损失,美国运用Robins规则排除油污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但对以捕鱼为生的渔民,美国判例法却抛弃Robins规则,赋予其特殊的地位和待遇[15]。美国法院长期以来认为,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对捕捞海域享有某种特殊的财产权利,其所受的损害与一般公众所受的损害具有不同之处。
结语
在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中,尚不宜无限扩大因船舶油污造成损失的赔偿范围,原则上应拒绝对纯经济损失的赔偿,以适当控制船舶营运成本的增加,避免油污损害索赔多重诉讼,实现侵权者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基于政策等因素考量,应将渔民因船舶油污遭受的纯经济损失作为例外情形给予赔偿,以保障渔民的基本生存资源。
参考文献:
[1]陈安.国际商事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30.
[2]徐国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0.
[3]彭惠连,周小祺.纯粹经济损失初探[J].法制与社会,2007,(4):133-134.
[4]邢海宝.海商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8-349.
[5]罗娜,金刚.船舶油污损害中纯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问题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4):151-155.
[6]徐国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7.
[7]赖惠燕,王法利,王君玲.船舶油污损害之纯经济损失赔偿问题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6):104-107.
[8]邢海宝.海商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0.
[9]国际海事委员会油污损害指南[Z].中国海商法年刊,1994,(5):463-468.
[10]郭杰.论油污损害中的纯经济损失[J].中国海商法年刊,1994,(5):256-257.
[11]曹险峰.论“多因一果”的侵权行为――兼论多数人侵权行为体系之建构[J].法律科学,2007,(5):155-163.
[12]张新宝,张小义.论纯粹经济损失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杂志,2007,(4):15-19.
[13]林立.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30.
第2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灾害;“灾害冲击模型”;社会易损性;社会冲击性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008-04
引言
从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到2003年的SARS事件,从2008年初中国南方的雪灾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中国近年来遭遇的重大灾害事件使灾害研究和应急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地震为例,中国以全球1/14的国土面积和1/5的人口承受了1/3的大陆地震,地震造成死亡人口约占全球地震死亡人口的1/2。虽然国内对灾害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于易损性、尤其是社会易损性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灾害社会学中的“冲击论”为理论基础,以Lindell,Prater and Perry(2006)[1]的灾害冲击模型为背景,分别从社会心理、人口、经济和政治四个方面研究了灾害的社会冲击性,为进一步在中国发展灾害管理充实基础。
一、灾害和灾害易损性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定义
1.灾害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定义
早在1755年,卢梭就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指出城市人口的过度密集和初震时人口的不及时疏散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震的冲击,导致了严重的后果[2]。世界公认的第一次系统性进行灾害研究的是Samuel Prince在1920年对于1917年Halifax大喷发所进行的研究[3]。随着研究的不停的深入,人们发现“灾害兼具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学科对灾害概念的不同认知说明,即便是灾害的社会属性以及灾害的双重属性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复杂的”[4]。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弗瑞茨(Fritz)曾提出的灾害的经典定义:“灾害是一个具有时空特征的事件,它对社会整体或其分支造成威胁和损失,并最终造成了社会结构失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支持系统功能的终端”[5]。与之相似的是Kreps在1984年给灾难定义:“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爆发的事件,由于事件本身超出了人类的正常保护能力,故该事件对社会或社会组成部分造成物质性或社会性的破坏,并导致全部或部分社会功能的损伤或完全丧失”[6]。
2.灾害易损性和灾害冲击模型
灾害易损性,又称灾害脆弱性,是指影响个人或社会群里受灾概率及灾后恢复能力的特质,包含了物质易损性(physical vulnerability)和社会易损性(social vulnerability)两个类别。在易损性研究出现之前,传统的自然灾害理解范式已经不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极端地球物理事件爆发频率无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类损失却显著增加;同时,大量的事实证明,同等类型或强度的自然灾害在不同的地区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程度也不尽相同[7]。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个灾害研究中心和研究人员开始重视易损性的研究。但由于灾害冲击所造成的时间和空间因子的复杂性,如受灾范围、人口特色(性别、种族、贫富等),灾害易损性也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2006年,Lindell,Prater和Perry建立了灾害冲击模型(见下页图1),将灾害易损性和冲击性,以及两者与灾害应急管理等因素放到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其中,灾前既存条件分别是灾害的灾害暴露性(hazard exposure)、物质易损性和社会易损性。物质易损性中的实体包括人、农业和建筑[2]。人的易损性源自对环境极端变化(如温度)的敏感性,与化学物质接触和相关压力等导致的疾病、损伤和死亡。与人体类似,农业易损性主要表现在种植物对极端环境的敏感性。而结构易损性则表现为建筑物的设计和使用材料无法抵抗极端压力(extreme stresses)(如疾风、液压、地震等)或无法阻止灾害性物质渗透人们居住的建筑。社会易损性(social vulnerability)是灾害易损性(hazard vulnerability)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在自然灾害条件下的潜在损失,它涉及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状况、生存条件以及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生产能力、社会结构和秩序、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损失”[9]。具体指人的物质财产(如建筑物、家具、交通工具)、心理素质(知识、技术和其他能力)、社会资源(社区整合等)、经济资源(经济结余等)和政治资源(公共政策影响力等)的局限性。在灾害发生时,具体的灾害事件和实时应灾反应与减灾措施和应急准备一起共同产生出灾害的物质冲击。而灾害的恢复准备,实时灾后恢复再加上灾害的物质冲击一同形成灾害的社会冲击。本文基于此模型,集中探讨了社会冲击部分。
二、灾害的社会冲击
从灾害冲击模型中可以看出,灾害的物质冲击、恢复准备以及实时灾后恢复共同作用,形成了灾害的社会冲击。而在现代灾害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论是以“事件—功能主义”为导向的经典灾害流派,还是危险源分析视角下的灾害的“原因光谱”(reason spectrum),亦或是将灾害看做资源与权力分配结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人们对灾害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研究自然易损性和灾害对自然冲击,开始深入到社会背景因素分析层面,将灾害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10]。
1.对社会心理的冲击
灾害的冲击引发的社会心理反应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因素。如,灾害的发生可在短期内使得家庭或社区成员的关系更加紧密,经历过灾害的人群对灾害的认识也会使他们避免或应对未来类似灾害的能力和心理适应力有所增长。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当灾害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放到中长期的评估环境中,其消极作用便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人员的伤亡、财产的损失以及熟悉环境的破坏都对受灾人群的心理造成了消极影响。北京大学心理咨询治疗中心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几乎所有的灾民都会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其中30%的人在灾害后八至十二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处于慢性心理创伤状态[11]。
灾害对社会心理冲击的另一个体现方面是灾后犯罪率和犯罪种类的变化。如美国学者Zahran et al.(2009)发现虽然财产和暴力犯罪在灾后普遍有下降的趋势,但家庭内部犯罪(如家庭暴力等)却呈上升势态[12]。另据社会脆弱学派的社会分化命题理论,灾害对社会心理的冲击也受到受灾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在经济欠发达的中、低收入国家在灾后表现出的短期和中期的暴力冲突要高于经济发达国家[13]。
在研究灾害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时,地方知识和本土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国外灾害心理学的新近定义不难看出,对灾后幸存者的心理调节和压力减轻必须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区特征下[14],因为文化特征和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灾民对灾害的认识和在灾后寻求援助的意愿。美国社会心理学家Taylor等人发现,在美国,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灾后寻求社会支持的意愿要远远小于欧裔美国人,因为他们认为寻求帮助导致自尊的降低,而通过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能维护自己的面子,避免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15]。而在处理实际的灾后幸存者心理问题时,越是强烈的情绪,越不能忽视幸存者的文化背景,对症下药才能最有效的减轻其灾后的消极情绪,并进一步减轻这些情绪给社会其他方面,如经济和政治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2.对人口的冲击
灾害对人口的冲击主要体现为受灾地区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总量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居民职业结构的变化等。灾害社会学研究主要使用人口平衡公式,Pa-Pb = B-D+Im-OM,来分析灾害对人口变化的影响。其中,Pa(population after)和Pb(population before)分别表示灾后和灾前的人口数量,B(birth)和D(death)分别表示受灾前、中、后一段时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IM(immigrant)和OM(emigrant)则分别表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数量[16]。通过对此公式的计算,灾害对社会人口的冲击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受灾死亡人口往往高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灾后迁出人口比例少于经济发达地区。第二,灾后人口迁入和迁出的原因和特点不同。人口迁出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和工作的丧失,生活资源的缺乏和试图修复灾后心理创伤等。短期之内的迁入人口主要由于灾后恢复重建的需要所引入的各种劳动力,中长期的迁入则伴随着灾后短期内迁出的原当地居民。第三,在自然灾害比较频发的地区,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如汪志国(2008)在对安徽的灾害和人口增长调查中发现,在1910—1953年这四十三年间,安徽一共发生了两次特大水灾和一次旱灾,此时间段内人口增长率仅为全国的2/3 [17]。
此外,灾害对人口冲击的另一重要体现是灾后人口素质的下降。教育是人口素质的基本保障,当灾害对教育及相关产业造成消极影响致使教育水平和质量无法保证时,受灾地区的人口素质将经历一段时期的调整和恢复。
3.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据密歇根大学Gerald Ford公共政策学院的Dean Yang的调查,在1970—2002年间,自然灾害造成了约987 000 000 000美元的经济损失,39%的世界人口所在国家或地区的GDP在此时间段内因灾害曾下滑3%以上[18]。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可见一斑。
灾害造成的自然资产损失可以通过灾情统计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资产存量价值进行评估,进而比较准确的计算出自然资产的损失价值。但对于社会资产,包括物质资产损失、人力资产损失和制度资产损失等而言,由于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具有地域区别性和时间延续性,以及评估工作的复杂性等,对于这类损失的评估和计算难度要大得多。
在地域上,直接受灾地区遭受了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而受灾地区的临近地区可能因为人口的迁入、物资的供给等因素收到积极的经济效应。从时间上来看,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建筑物的不同程度损坏、灾害对生产资料的破坏和其他直接经济损失,这些损失一般可以通过对修复和重建的经济消耗来计算。不同于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却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统计。灾害社会学在研究灾害对经济的冲击时,一般将蒙受损失的主体分为家庭、商业和政府三个主要对象。其中,商业的间接经济损失来自于营业性建筑物的重建、员工和原有顾客的暂时或长期的失去等,而政府的间接经济损失,根据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包括灾后废墟的清理、基础设施的修复与重建,以及对受灾地区的全部或部分重新规划等[19]。从经济部门角度出发,灾后地区普遍呈现出两个趋势:第一,零售和批发部门灾后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生产和建筑部门在灾后反而出现经济效益的增长;第二,因为客源的流失和资金来源的有限,依靠小范围顾客的小型企业或小本生意比拥有较大市场(全国或全球)的大型企业或经济实体克服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要艰难的多,前者在灾难后结束经营的不在少数 [20]。
4.对政治的冲击
受灾群众在灾后往往经历心理学上划分的悲伤的五个阶段,即否认、愤怒、妥协、抑郁和接受,而在这五个阶段中,尤其是在第一、二个阶段,群众开始对政府应对灾害的不利之处、居住或受教育场所的破坏、物资发放不公平或不及时等问题进行思考和反问,进一步导致受灾地区的社会活动加剧,并最终引发政治不稳定因素。
基于上述的灾民情感反应和集中反思的几个方面,灾害对政治的冲击可以从灾前准备、救灾行动和灾后重建三个时间段寻找原因。首先,由于大部分自然灾害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政府和相关机构在灾前准备,包括灾害预警方面的工作有不小的难度,世界各国对灾害预警的研究也层次不齐 [21]。其次,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实时灾害的救援力度政府救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是决定受灾群众,甚至整个政治区域内民众在灾后产生极端情绪的主要原因。而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政府又面临救援重建资金的发放是否到位、资金和物资的分配是否公平、重建资金和物资发放过程是否透明等问题。如1989年的美国加州大地震,政府在救援过程中因为语言不通、救援经验不足等造成了某些地方的不及时或低效救援,震后对危险建筑物的不公平评估产生的在公共安全名义下的不恰当行为以及对于损害程度评估的争论、修复费用和预期能力阻碍和延误了灾后恢复工作的进行,这些都导致了灾民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并最终催生了一些新兴的组织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
结论
随着自然灾害在全球的不断发生和人们对灾害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易损性和灾害对社会的冲击日益受到重视,灾害研究的范式也面临从自然层面到社会层面的转型。但无论对社会易损性还是灾害的社会冲击性的研究,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等还需要有大量的工作投入。对于研究者而言,不仅需要用归纳法将大量真实有效的灾害数据用于灾害研究的理论发展,还需要用演绎法将研究所得用于对未来灾害数据的预测,再通过实际的检验不断的改进研究方法,最终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社会易损性和更有效和及时地减轻灾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1] Lindell MK,Prater CS and Perry RW,Fundamental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Emmitsburg,MD: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Emergency Management Institute,2006.
[2] Michael K.Lindell,Disaster Studies,Sociopedia.ISA,2011.
[3] Scanlon TJ.,Disaster’s Little Known Pioneer: Canada’s Samuel Henry Pri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
asters,1988.
[4] 陶鹏,童星.灾害概念的再认识——兼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流派及整合趋势[J].浙江大学学报,2012,(42).
[5] C.E.Fritz,“Disaster,”in R.K.Merton&R.A.Nisbet(eds.),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New York,Harcourt,1961.
[6] Kreps GA,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r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0:309-330,1984.
[7] 郭跃.灾害易损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灾害学,2005,(4).
[8] Wisner B,Blaikie P,Cannon T and Davis I,At Risk: Natural Hazards,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2nd ed.London: Rout-
ledge,2004.
[9] 文彦君.陕西省自然灾害的社会易损性分析[J].灾害学,2012,(27).
[10] Susan L.Cutter,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Hazards and Vulnerability Science,Geophysical Hazards,International Year of
Planet Earth,1,pp17-30,2010.
[11] 张素娟.从汶川到玉树管窥中国灾害心理援助[J].中国减灾,2011,(9).
[12] Zahran S,Shelley TO,Peek L and Brody S,National Disasters and Social Order: Modeling Crime Outcomes in Florida,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7:26-52,2009.
[13] Philip,N& Marjolein,R,Natural Disasters and Risk of Violent Civil Conflict,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52(2),pp.1-50,2008.
[14] 张建新.灾难心理学与心理危机干预专辑序言[J].心理科学进展,2009,(3):481.
[15] Taylor,S.E.,Sherman,D.K.,Kim,H.S.,Jarcho,J.,Takagi,K.,& Dunagan,M.S.,Culture and Social Support: Who Seeks It and W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7(3),354-362,2004.
[16] Smith SK,Tayman J and Swanson DA,State and Loc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Methodology and Analysis,New York:Kluwer,2001.
[17] 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与人口的变化[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
[18] Dean Yang,Coping with Disaster:The Impact of Hurricane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1970-2002,Research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Discussion Paper No.534,2007.
[19] Farazmand A.,Handbook of Cri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New York:Marcel Dekker,2001.
[20] Webb GR,Tierney KJ and Dahlhamer JM,Predicting Long-term Business Recovery from Disasters: a Comparison of the Loma
Prieta Earthquake and Hurricane Andrew,Environmental Hazards,4:45-58,2002.
第3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质量成本 社会经济性
目前,质量问题事件频发,使许多企业已认识到质量对经济效益尤其是社会效益的影响,在质量问题导致企业利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对质量成本认识才能成为企业经营者关注的中心。但是,理解了质量成本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掌握并成功实施和应用质量经济性思想和原理,促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容易立足和发展。有效地实施产品的质量经济性分析和管理,有力地推进企业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企业追求持续经营成功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一个企业管理有效性的重要标志。
一、质量经济性的内涵
在充分认识质量经济性的重要性基础上,普遍认为质量经济性是人们获得质量所耗费资源的价值量的度量,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较小的耗费资源价值量,其经济性就好,反之就差。就目前的理解可以把质量经济性的概念分为两种:狭义的质量经济性和广义的质量经济性,前者是指质量在形成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的价值量,主要是产品的设计成本和制造成本及应该分摊的期间费用;后者是指用户获得质量所耗费的全部费用,包括质量在形成过程中资源耗费的价值量和在使用过程中耗费的价值量。这样,我们可以用单位产品成本和分摊的期间费用之和,来反映企业某种产品的狭义的质量经济性,而用价值工程中的(单位产品)寿命周期成本,来反映广义的质量经济性。质量经济性分析的原理就是在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同时,降低质量成本。其指导思想是有效的利用资源,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满足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合格的产品决不仅限于产品按技术特征来设计,制造并达到要求,而应该在客户需要时,以合理的价格和最短的时间,能够提供给顾客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只有将质量管理和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有机的结合,质量管理在企业中才能更有效发挥其潜能,才能走得更远。
二、企业质量经济性的分析及质量社会经济性的提出
企业质量经济性在企业一般是通过质量损失或者质量成本项目的分析,以降低质量损失率或质量成本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质量成本项目基本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即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其中,预防成本是指为预防产品不能达到满意的质量所支付的费用;鉴定成本是指为评定产品是否满足规定的质量要求,进行试验、检验和检查所支付的费用;内部故障成本是指产品在交付前因未能满足规定的质量要求所造成的损失;外部故障成本是指产品在交付后因未能达到顾客满意的质量所造成的损失。因此,质量问题的分析又可归结为质量损失的分析,所以质量经济性分析就是以用户和社会需求的质量为出发点,从经济的角度分析质量问题,围绕产品的适用性和经济性,寻求质、本、利的最佳组合,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企业贴近市场与顾客,挖掘和发挥内部的积极因素与作用。质量经济性分析可以促使企业更加贴近市场与顾客,使企业能更好地根据市场、顾客和社会的需求来组织生产、确定产品档次、价格和质量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有利于企业保持质量与效益、质量与经济的相对平衡、稳定和发展。质量经济性分析通过评价企业经营运作的各个环节质量、过程质量、总体结果质量和经济效果,促使企业正确处理质量与市场竞争、质量与效益、质量供给与需求、质量与生产成本等之间的关系,科学地选择质量水平和投入费用的最佳方案与决策。
有利于企业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质量经济性分析追求的是以低的投入、低的成本获取满意的质量和尽可能大的利润。纵观从苏丹红一号、劣质奶粉、有毒大米、孔雀石绿到毒豆奶、毒饺子和“三鹿奶粉事件”到今天的乳制品行业以及双汇集团的“瘦肉精”事件,再到2012年“毒胶囊事件”、“酒鬼酒塑化剂事件”等中国质量问题频发,说明只关注企业的质量经济性已经难以解释和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深远的问题,质量问题所引起的社会损失或者叫社会成本的已引起相当的关注和研究,质量问题引发的社会经济性研究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
三、质量的社会经济性分析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任何质量事件的发生都或多或少的会引起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损失,这是企业积极进行产品研究与开发的动力,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利润水平促使企业不断的关注其质量成本问题,因此对质量问题的认识经历,从事后把关的质量检验阶段到统计质量控制阶段再到贯穿于整个产品质量产生、形成、实现的全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阶段,企业质量的经济性分析始终围绕的都是企业,从来都没有过多地关注过遭受质量问题困扰的社会受害群体和最终的承载体国家或政府,因此质量问题的社会性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或另一角度,重新审视或认识质量问题的危害,真正提高人们、企业、社会、政府对质量问题的认识,提升对质量问题的关注。
(一)质量问题所引发的企业自身的直接经济损失
任一质量事件的发生,都必然的给当事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与影响,只不过取决于问题的严重和影响程度不同,比如三鹿集团已成长为中国食品工业百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也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重点支持的企业集团,曾连续6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2007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00.1亿元。经中国品牌资产评价中心评定,三鹿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然而自从2008年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事件曝光后三鹿所有的奶粉在全国下架,接受顾客的退赔要求,全国所有的加工厂停产整顿,对于年销售额达1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三名的这样的大型乳制品加工企业来讲,其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损失是天文数字,“三聚氰胺”让三鹿奶粉轰然倒下,三鹿奶业集团的坍塌、一个民族品牌的湮灭;再如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让双汇集团一夜之间损失超百亿元,冠生园月饼事件,他们只是利用了陈旧豆沙制作月饼,被曝光以后,这个百年品牌商家一下子毁灭了;还有包括今年的酒鬼酒“塑化剂事件”更是让企业身陷危机。这且不说,伴随着企业的质量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问题的处理与善后,不仅有社会名誉的影响、品牌价值的损失,市场份额的减少,更有企业内部职工的下岗与转岗,以及内部管理结构与体制的调整有些损失不是可以以数字进行衡量的。
(二)质量问题所引发的连带行业、社会损失
质量问题的产生,一般来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会波及整个产业链条,甚至整个行业,这种影响甚至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一步的扩展和探刻。如“三鹿奶粉”事件,不仅影响到蒙牛、伊利和光明等同质化企业,更影响到奶农等养殖户以及最终端的消费人群,致使国内乳企经营困难,奶农利益倒挂,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三鹿奶粉事件由食品安全事件升级到社会安全事件,全国范围内出现倒奶、杀牛的现象,从而影响到整个产业链条。而后续国内奶粉滞销,洋奶粉价格飞涨,消费者承担了更大的付出;同样我们从后续发生的‘瘦肉精”事件看,同样引起了猪肉价格的大幅下跌和养猪专业户的极大损失,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三)质量问题所引起的国家社会的救助投入
质量问题爆发关乎国家与社会,因此每次质量事件的爆发,政府都必须为解决质量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实施相应的政策调控,双鹿事件、瘦肉精事件、毒胶囊事件、酒鬼酒塑化剂事件一样无不如此。如双鹿事件发生以后国家出台政策解决因三鹿集团等企业停产导致奶源基地养殖场(户)生鲜奶滞销问题。在奶价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启动奶农特别救助行动,给受事件影响的广大奶农提供短期补助。国家在此次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帮助奶农处理消化过剩奶源,解决奶农卖奶难,同时对这次勇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多收过剩奶源的企业,在今后企业发展中给与税收、重大项目资金、优惠信贷等方面的重点扶持。而且对所有因食用该产品受到了不同程度伤害的婴幼儿国家从财政拿出了20个亿给予重点救助,并给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上了保险,为期20年;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对这些受到伤害婴幼儿的影响和伤害可能是一生的。
(四)质量事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心灵的伤害损失
每次质量事件的发生,尤其是食品、药品、安全等关乎人们生命的质量问题,尤其是不断涌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更是使人们身心交瘁,都会引起对社会的拷问,这到底是怎么了,奶不能饮,肉不能食,药不能用,车不能坐等等,我们的社会到底还有什么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此质量事件,对使用者的身心来讲都造成了极大地影响,如三鹿奶粉事件后,查出几千名婴幼儿因食用了三鹿集团的劣质奶粉而出现肾病,超过50人因患肾结石陷人危险,2人因此而死亡,并且成千上万个家庭因食用过三鹿奶粉或其他问题奶粉而提心吊胆。孩子是父母的心肝,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伤害,人们实在难以淡忘。
(五)质量问题对我国产业进程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民族工业得以振兴,“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而频频发生的质量事件,尤其是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出现,使人们对国产食品乃至其他工业产品的信任和信心产生了动摇,尤为突出的是三鹿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上海冠生园食品事件和今年的毒胶囊事件、酒鬼酒塑化剂事件使本身就相对薄弱的国产食品信誉倍受打击;这不但使部分企业从此退出市场,而且对勉强生存下来的企业也是步履维艰。同时也对我国食品生产行业、农业产业化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制造”在境外的形象受到影响。
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损失或经济成本与企业质量成本相比是巨大的,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企业质量成本的经济性,那主要是为了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而现在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关注更为广泛的质量损失的领域,通过更多的人关注质量成本的社会性的影响,将会促使社会各方面更加深入地理解质量概念的内涵,促进我国质量事业的快速有效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
质量问题的社会经济性分析有助于企业、政府、社会正确地认识质量问题不仅仅是企业关注的利益损失,而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社会损失,这种损失是长远、深刻的,重视质量问题的社会经济性,将会使整个社会的质量意识进一步提高,促进企业和社会的质量进步。
第4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地质灾害预警 工程项目 经济效益 评价
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的投入产出与生产项目是不一致的,所以以简单的定性方法来评价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效果是片面的,不合理的。进而,寻求一种更合理、更客观、更全面地评价地质灾害预警项目经济效益的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1、评价意义
1.1、开展投资项目经济评价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世界各国项目决策的普遍趋势。通过地质调查项目评价,能识别项目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程度及对社会影响的范围,为争取国家财政支持,保障重点项目专项资金的投入提供依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为国家制定政策,进行国土资源规划、决策和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1.2、项目的评价有利于建立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的新的运行机制,完善地质调查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项目的监理和项目的后评价工作,提高项目的质量和管理水平,促使地质调查项目工作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操作规范和成果符合要求。有利于提高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1.3、项目评价在商业性投资项目中应用广泛,但在我国开展地质调查项目评价及其研究时间较短。目前,国际上也没有成熟的评价理论和方法可供直接利用。因此,进行地质调查项目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对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的实施和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同时也对公益性投资项目的评价产生重大的影响。
2、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经济效益评价方法
2.1、评价内容、指标及评价标准
2.1.1、评价内容、指标
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的实质是开展地质灾害多发区的调查,建立地质灾害预警、监测、预报系统,为治理规划、防灾减灾提供依据,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国民经济和城乡发展规划规避风险、减少损失提供参考。因此,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即指成果被经济活动所采纳,从而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贡献而产生的效益。既包括因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的实施而使受灾体直接避免经济损失而产生的直接效益,又包括因受灾体免遭破坏而避免的关联性损失所产生的间接效益。
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可根据“替换理论”,从工作区预期地质灾害损失的关系中通过替换计算获得。即将计算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替换为计算工作区预期灾害经济损失。计算公式如下:
采用效益-费用分析法,计算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效益与投资(费用)的比值。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分级及评估标准,按效益费用比的大小分别设定如表2-1。
2.2、直接经济效益计算方法
根据“替换理论”,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直接经济效益采用预期直接经济损失替换计算。因此,首先研究工作区预期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预期直接经济损失计算的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种方法。
方法一:突发性地质灾害多采用此方法
首先设定评价标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受国家经贸委的委托,曾承担制定了一个全国自然灾害分级标准(略)。
上表中增加第Ⅵ级灾害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大量存在这个级别的地质灾害。表中损失率(ρ)的含义是,灾区在灾前的所有可能成为受灾的对象(有形资产)在灾后的总实际损值(VL)与灾前的总经济净值(VP)之比。用公式表示为:
其次,确定预期灾害灾级及计算损失值。假如不进行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肯定会发生灾害。可采用两种方法来计算损失值。
一是采用经验取值法,对评价地面变形、岩土位移等灾害来讲,一般习惯于保险的做法,只设定发生了一次小型灾害(以求得最小损值)。其直接经济损失量、值从表2-2、2-3均可查到一个从0.01―
二是计算预期直接经济损失,除了查表2-2、2-3可找到灾级损失概估数外,尚可采取计算的办法求出比较接近实际的评估数。
直接经济损失一般包括资本损失、产品损失、生产损失三部分。此三方面的损失项目在未损前的净值于我国的各级统计年鉴中均有反映。前两项(资本和产品)主要是有形资产,在年鉴的固定资产及流动有形资产统计中有所反映,后一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有所反映。根据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可以计算出灾区单位面积内的有形资产净值、单位面积及单位时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它们作为基础,再和灾区面积、灾害损失率、灾害时间(平均恢复期)发生关系,即可预估出有形资产的预期损失值及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损失。估算步骤如下:
(1)求预期灾区有形资产净值
第一步,求预期灾区每平方公里的有形资产净值
根据统计年鉴及有关报表,求出预期灾区(一般是预测的危险区)的所在行政单元(如市、市区、县城、小镇、乡村等)内所有有形资产的总经济净值(VP),除以行政单元面积(m),即得行政单元每平方公里的有形资产净值VP1。
式中,DLi为第i种地质灾害对受灾地区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
方法二:缓发性地质灾害多采用此方法
采用类比法进行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
根据目前地质灾害实际情况所统计的资料进行估算预期直接经济损失。
若有些地区的灾害形成机制和灾害形成过程相似;其社会经济结构,也具有相似的统一性,即可利用类比法来根据已知地区的地面沉降有关数据,估算未知地区的地面沉降的有关数据和所造成的损失。估算公式如下:
3、结语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是一项牵涉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长期任务,希望针对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特点,设计一套可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以期为该类项目的立项、成果验收、成果使用效果的评价提供系统的分析工具。通过分析,明确地质灾害预警工程项目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找出差距与不足,保证国家专项资金最大效益为社会经济及国土资源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第5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 纯经济损失;类型化;中国民法;侵权责任法
Abstract: Pure economic loss is a kind of economic disadvantage or loss of money which the victim directly suffers, also a disadvantage imposed on victim's entire property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independence, intangibility and directness. The creation of this concept and discussion of relative theories are designed to classify pure economic loss into generally unrecoverable damages.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of damages, pure economic loss belongs to damages of property. Main cases about pure economic loss are: false statement case, cable damage case, invalid will case, oil pollution case and public facilities damage case. Other types of pure economic loss often mentioned by scholars, such as product liability, unavailability of objects, unfair competition, employee or family member's injury, and pure economic loss under contract law, can be solved by current laws. Chinese scholars not only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ing model and categorization of pure economic loss, but also initiate the analysis on difficult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dwell on them in the sight of legislation. Article 106(2)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can integrate pure economic loss concept into our current law system. With regard to the legislation of Tort Liability Law, we should conside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ovisions and the concrete categorization of pure economic loss.
Key words: pure economic loss; categorization; Chinese civil law; Tort Liability Law
纯经济损失问题起源于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是否有必要引入以及如何将其引入以制定法为主的大陆法系传统民法,是大陆法系民法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纯经济损失的概念和特征、纯经济损失的类型、纯经济损失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最后提出我国民法应对纯经济损失问题的思考。
一、纯经济损失的概念和特征
纯经济损失,又称之为金钱损失,在英文中一般表述为pure economic loss。在我国学说上,也称之为纯粹经济损失、纯经济上损失等。对于纯经济损失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立法和学说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比较认同这样一种定义:纯经济损失是受害人直接遭受的、非因受害人的人身或有形财产遭受损害而间接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或金钱上的损失[1]。该定义揭示了纯经济损失的基本特征:
1. 独立性。纯粹经济损失是“一种在任何方面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都没有关联的经济损失”(注:①1972年《瑞典赔偿法》第2条。)。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任何一种利益都以几乎无限多样的方式互相连接着。一种损失不与身体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不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只能是概念上的截取。因此,纯经济损失的独立性是指其与受害人(主张损害赔偿之人)的身体或者财产损害没有关联,而不是说与任何人身和财产损害没有关联。
2. 无形性。纯经济损失是受害人因为他人的加害行为(不仅仅是侵权行为)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不是由于受害人有形的人身伤害和有形的财产损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3. 直接性。纯经济损失是加害行为在受害人处直接导致的后果,而不是受害人的人身或有形财产遭受损害后间接引起的损失。这种直接性需要根据加害行为与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是否还有一个受到损害的“中介”来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加害人的加害行为与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还有一个受到损害的“中介”性质的利益。这种“中介”性质的利益既可能是受害人的利益又可能是他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中介”性质的利益是受害人所有,那么由该“中介”性质的利益又引起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就不是纯经济损失,而是一种间接的损失,例如由于人身遭受伤害而导致的工资利益的丧失、医疗费用的支出、受害人的抚养人或赡养人的抚养、赡养利益的丧失就不是一种纯经济损失。相反,在“挖断电缆”的案件中,由于施工者挖断的电缆属于输电公司所有而非钢铁公司所有,施工者对输电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但是并没有对钢铁公司实施侵权行为(至少根据传统民法是这样的),但挖断电缆又是造成钢铁公司损失的
直接原因,挖断电缆的行为与钢铁公司的损失之间没有涉及到钢铁公司其他“中介”性质的利益丧失,所以钢铁公司受到的损失是一种纯经济损失。第二种情况是不存在“中介”性质的利益损失的情况。在该种场合下,只需要因果关系的存在以及受害人遭受无形的、直接的经济上的不利益即可。当然,在有些案件中纯经济损失与有形利益的损失是并存的,此时需要根据上述规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 纯经济损失是加诸于受害人整体财产上的一种不利益,而非基于受害人某项具体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害而发生的。这种损失体现为受害人整体财产的变动,可以根据受害人在加害原因发生前后的财产差额来计算[2]。这种整体财产的变动与具体的财产或人身损害无关,但这并不否认受害人所遭受的纯经济损失和其所遭受的有形财产损失可以并存[3],如挖断电缆案型。
5. 纯经济损失是一个由法律工作者为了因应法律实践需要而拟制的技术概念,是对不同主体间财产和人身权利集合的人为截取,其意图是将此类损害纳入一般不予赔偿的范围。与受害人(赔偿权利人)人身和财产损害没有任何关联的经济损失在范围上和损失的计算上存在不确定性,并且这种损失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例如,道路交通事故导致道路阻塞,有人因此误了飞机、错过了商务谈判或医院急救。对这类损失予以赔偿可能过度限制社会主体的行动自由,阻碍社会生活的自如运行[4]。
二、纯经济损失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理清纯经济损失与相关概念的关系,能明确纯经济损失在损害赔偿法中的地位,有利于纯经济损失理论的发展和司法运用。学说上关于损失的分类,主要有财产上损失与非财产上损失、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履行利益损失和信赖利益损失等,以下就纯经济损失与这些损失分类的关系进行进一步阐述。
1. 纯经济损失与财产上损失、非财产上损失。财产上损失是指可以金钱加以具体计算的受害人一切财产上之不利变动,包括无形的财产损失和有形的财产损失,而非财产上损失则是指受害人所遭受的财产以外的损害,包括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很显然,纯经济损失作为一种无形的经济上的不利益当然是财产上损失的一种,是与有形财产损害相并列的一种财产上损害,即无形财产损失。
2. 纯经济损失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是我国学说上关于损失最常见的一种分类,其具体含义多被等同于所受损失与所失利益[5]。学说一般认为,直接损失又称积极损失、实际损失,是指现有财产的减损,包括既得利益的减少、财物的毁损灭失和费用(如医疗费、丧葬修理费等)的支出。间接损失又称消极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损失,即未来财产的减损。如利润损失、孳息损失等[6]。直接与间接的划分按照通常的理解应是根据因果关系,即由损害事故直接引发的损害为直接损害,非直接引发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的介入所引发的损害则为间接损害[7]。果如此,则所失利益也应为直接损失。如前所述,纯经济损失是由损害行为直接引发的损失,是一种直接损失,但与传统损害赔偿理论中的直接损失的内涵不同(注:①韩世远先生曾指出,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的分类不能够称得上是一对科学的分类,既然学说通说认为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就是指大陆法系立法及学说所称的“所受损失”与“所失利益”,我们也可以直接接受这对范畴,取代既有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习惯用语。——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14页。)。例如会计师事务所不实陈述导致股民纯经济损失的案例中,股民并没有遭受任何有形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失,其损失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其他利益遭到损害而引起的,但是这种损失却是股民积极的、实际的损失,是一种直接损失。
3. 纯经济损失与履行利益损失、信赖利益损失。履行利益、信赖利益是合同法上的概念。履行利益的损失是指债权人因合同未履行而失去的可获得的利益,履行利益的赔偿使合同达到如同被履行的状态。可见,履行利益的损失是因为债务人违反已经有效成立的合同而导致债权人正常情况下原本可以得到的利益的丧失,是一种预期利益的损失,而不是有形的既得利益的减损。所以履行利益损失是纯经济损失的一种。信赖利益损失是指由于该信赖合同能够成立而支出的诸如准备履约的费用以及导致与其他人的缔约机会的丧失等,其中有关费用的支出因为是当事人有形的既有利益的损失,所以不是纯经济损失,而缔约机会的丧失则是一种无形的、直接的财产损失,并且可以以金钱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经济损失的一种。因此,履行利益损失是一种纯经济损失,而信赖利益的损失中只有缔约机会的丧失才可以是纯经济损失。
综上所述,纯经济损失在现有损害分类体系中并无明确定位,除在财产上损害与非财产上损害的分类中可找到其明确的位置外,在其他损害的分类中,它都处于边缘的位置,与每种分类中的相应损害都存在交叉关系[8]。纯经济损失在现有损害分类体系中虽无明确的定位,但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民法尤其是损害赔偿法如何将其有机整合,是民法面临的新挑战,也是民法发展的新契机。
三、纯经济损失的类型
与纯经济损失的“类型”相近的词还有纯经济损失的“种类”或纯经济损失的“样态”,其实三者都是学说对于纯经济损失的各种表现形态的归纳和总结。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种类侧重于对纯经济损失产生的原因的抽象,而样态或类型则是对纯经济损失形态的直接描述。我国学者在研究纯经济损失问题时,一般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所用的标准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既包括对于纯经济损失产生原因的抽象,也包括对纯经济损失形态的直接描述,不一而足[9]。本文认为,不管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纯经济损失理论的发展都是通过判例而形成的,而判例是针对各种具体的纯经济损失形态的,并且各种不同的纯经济损失是否能够获得赔偿并没有统一的规则,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本文倾向于用样态或类型来概括纯经济损失的表现形态,并且用代表性的案件来命名某一类型的纯经济损失。
各国学者一般都是在侵权法的框架下来探讨纯经济损失问题,但依纯经济损失的定义和特征,合同法中的履行利益损失和信赖利益损失中的机会损失也属于纯经济损失,并且有些纯经济损失类型兼跨合同法和侵权法两大领域,因此在归纳总结纯经济损失的样态或类型时,应将合同法中的纯经济损失也纳入进来。但合同法中的纯经济损失是否应当赔偿已有明确的结论,因此,本文主要对侵权法中常见的纯经济损失类型进行概括。又因为各国对故意侵权引发的纯经济损失都判定予以赔偿,因此,下文所述只是过失引发的纯经济损失类型。
(一)典型的纯经济损失类型
1. 不实陈述案型。即专门职业者(如会计师、鉴定人等)对他人作出不符合事实的说明导致第三人损害。某上市公司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制作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而该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的不实陈述,以致公司业绩被严重夸大,吸引了不少股民前来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不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揭露存在重大不实陈述,其股票价格急剧下跌,使得购买该公司股票的股民遭受严重损失。此案中股民所遭受的损失是因会计师事务所重大不实陈述而产生的直接损失,而非其人身、财产本身遭受的损害或因其人身、财产遭受损害而引起。因此,股民所遭受的损失是纯经济损失。在此领域颇具代表性及指导意义的案例是英国上诉法院1964年判决的Hedley Byrne & Co. Ltd. V. Heller & Partners Ltd. 一案。在该案中,原告Hedley Byrne是一家广告公司,与一家名为Easipower Ltd. 的公司签约,为该公司策划一次广告宣传活动,在这次活动中,Hedley Byrne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为谨慎起见,它通过自己的开户行向Easipower Ltd.的开户行Heller & Partners Ltd.写信询问了Easipower Ltd.的资信状况,Heller & Partners Ltd.回信说,Easipower Ltd.的信用良好,并附带声明银行对此不负责任。Hedley Byrne的开户行向其转述了这封信,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证明存在不实。Easipower Ltd.后来破产,Hedley Byrne在合同项下损失达17000英镑,于是向法院诉请Heller & Partners Ltd.予以赔偿。上议院认为,因为被告银行于陈述时附带声明了免责条款,因此不对原告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它同时认为,若无该项免责声明,被告银行就应承担责任,并不因原告所受之损害为纯经济上损失而有所不同[10]。
2. 挖断电缆案型。即甲毁损乙的所有物,导致第三人受纯粹经济损失。如,农夫驾驶的拖拉机因过失撞倒了铁路桥的一个桥墩,导致桥墩维修期间交通中断,某工厂延误交货所受的损失;加工厂排放废油,污染他人养殖的虾蟹,导致供货海鲜餐厅歇业、KTV生意锐减所受的损失。英国的Spartan Steel and Alloys Ltd. V. Martin & Co Ltd.一案是这类纯经济损失的经典案例,案情如下:原告是伯明翰的一家不锈钢厂,由Midland Electricity Board供应电力。被告某施工公司在原告工厂附近挖掘道路施工,其工人疏忽大意损坏了电缆。电力公司在修复电缆期间切断供电长达14小时。原告因为停电受到如下损害:(1)锅炉中的铁块因成为废渣而减少的价值为368英镑;(2)这些铁块如果能顺利炼成,可以获利400英镑;(3)工厂因为停电不能继续营业,按往日的利润计算损失1767英镑[11]。上述第三项损失就是纯粹经济损失,并且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
3. 遗嘱无效案型。即因过失提供服务致第三人受损。典型案例是英国1995年的White.V. Jones案,立遗嘱人因为和两个女儿吵架而修改遗嘱,没有留给她们任何遗产。后来双方和好,立遗嘱人准备改回遗嘱,由于律师的过错,没有及时修改遗嘱,立遗嘱人身故后,他的两个女儿律师过失责任,并获得了赔偿。该案中女儿的损失就是纯粹经济损失[12]。
4. 油污案型。海上石油运输过程中石油泄漏常常导致海洋油污事故。一起海洋油污事故发生后,通常会导致如下几个方面的损失:(1)实际财产损失。泄漏的石油会污染渔具、船舶、码头,有时还会污染海域临近的房屋等。(2)继发性损失(Consequential damage)。这是一种由实际财产损失直接引发的收入或利润损失。最常见的情形是渔民在渔具上的污染被清除之前,或者当污染不可能被清除时在该渔具得到更换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出海捕鱼而产生的损失;还有一种情形是,渔民A与渔民B签订了租用渔民B的渔船的合同,但由于渔民B的渔船遭到石油的污染而无法出租给渔民A,由此导致的渔民B的租金收入损失。(3)关联经济损失(Relational economic loss)。这是一种由于一个受害人遭到人身或财产的实际损害后,该损害进一步导致其他人权利或利益受损害的情形。如在上例中,不仅渔民B损失了租金,而且渔民A因为没有按时租用到渔民B的渔船,他原来预期所能获得的利润也落空了。换言之,渔民A也遭受了利润损失。(4)海洋环境经济损失。这是一种因为海洋环境这一公共资源被石油污染,使有关的非资源所有人遭受的损失。如前所述,海洋油污还可能引起邻近的海鲜餐馆歇业,港口、航道关闭,海上运输停顿,前来休闲的游客剧减,当地旅游业衰退,政府税收减少等等一系列的经济损失。在这四类损失中,关联经济损失和海洋环境经济损失属纯粹经济损失[13]。
5. 公共设施损害案型。因公共设施损害而发生的纯经济损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纯经济损失类型。如因交通事故而导致道路堵塞,很多人将会遭受经济损失,如汽油费的增加、失去订立合同的机会、债务无法及时履行而承担违约责任等。更严重的是违章行驶导致桥梁、隧道毁损,因需要长时间修复而影响依赖此桥梁、隧道的人,给他们造成长期的经济损失,这些都是纯经济损失。这类损失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本类损失的初始受害人并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而是代表公众利益的市政机关或者特定公法人;二是本类损失的影响范围一般很广,如果将该等损失置于可赔偿的范围,则会引发诉讼“洪水”。因此,本类损失常常被用来作为限制纯粹经济损失获得赔偿的主要理由。
将纯经济损失与其他损失相区分的最初目的主要是对纯经济损失不予赔偿。但纯经济损失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确立了各种类型纯经济损失赔偿的规则。以上五种纯经济损失类型中,电缆案型和公共设施损害案型中纯经济损失基本上不予赔偿。其他类型中的纯经济损失赔偿也限定了严格的条件,并且不同的类型条件不一样,这也是学者基本一致的认识,即对纯经济损失应作类型化研究。
(二)关于其他纯经济损失类型
学者们还常提及的纯经济损失类型有产品责任类型或产品自伤类型、物之使用不能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雇员 和家庭成员人身伤亡类型、合同法领域的纯经济损失类型等。本文认为,这些纯经济损失类型可以适用现有的法律规范获得解决,无需不胜其烦地寻找或创制新的规则。
1. 关于产品责任案型。广义的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的缺陷或瑕疵造成产品本身的毁损灭失或使用价值降低等履行利益的损失以及产品缺陷导致他人人身、财产等固有利益的损失。如前所述,履行利益损失是一种纯经济损失,通过合同法即可得到救济。侵权法上的产品责任主要是产品的缺陷导致他人人身、财产等固有利益的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果在造成固有利益损失的同时存在履行利益损失时,是否可以通过侵权法获得履行利益损失即纯经济损失的赔偿。大陆法系的传统做法是,产品责任的赔偿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只对缺陷标的物以外的其他人身、财产损害予以赔偿。其主要依据是履行利益损失的赔偿是合同法的职责,合同法和侵权法各司其职,其界限不可轻易打破,其领域不能随意混同。其实,这种做法只会增加当事人的讼累,也会浪费珍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本文认为,既然承认加害给付时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说明合同法与侵权法的藩篱并不是不可以突破的,因此产品责任兼顾履行利益损失的赔偿未尝不可。
2. 关于物之使用不能类型。甲设在港口边的工厂部分倒塌,为避免进一步的危险,甲依政府机关命令,在港口两边用支架支撑工厂的建筑物,但该支架却封闭了进出港口的水道,致使原告乙的船无法通过水道进出港口装卸货物,因此遭受利润损失。本文认为,这种纯经济损失可以归于“公共设施损害案型”,而无需单独存在。
3. 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某商家故意低价(低于成本价)销售某商品,从而导致同样销售该类商品的商家积压商品,造成其损失。或某企业势力庞大,在行业内形成垄断,造成其它企业纷纷倒闭或严重亏损,这些受损企业的损失也可视为纯经济损失。本文认为,这种纯经济损失可由竞争法予以规制。
4. 雇员和家庭成员人身伤亡类型。雇员人身伤亡尽管不是对企业经营权的直接干扰,但将使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造成企业的利润损失。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将使其他家庭成员支出医疗费、护理费等现实财产的减少以及可得收入的减少。关于前者,还没找到相关案例予以支持,这种损失其实是很难确定的,因为企业利润的获得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某个雇员的履职不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因此企业不能以雇员的人身伤亡为由侵权人赔偿企业的利润损失。关于后者,各国已有明确的人身损害赔偿法律予以规范。
5. 关于合同法领域的纯经济损失。学界提到的合同法领域的纯经济损失类型主要有履行利益损失类型、信赖利益损失类型和第三人侵害债权类型。
如前所述,履行利益损失和信赖利益损失都是纯经济损失,但二者都可以通过已有的法律制度获得救济,履行利益损失可适用违约责任制度获得救济,而信赖利益损失则可通过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获得救济。因此,不需要再依据纯经济损失理论确认其是否可以获得救济。
第三人侵害债权有很多情形,比较典型的是第三人故意妨碍债务人履行债务而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实现。如甲为一影视明星与乙演出公司签有演出协议,丙与甲素有积怨,为了报复甲,在甲演出前一天将甲绑架,致使甲无法在演出当天表演,乙因甲无法表演而失信于大众,不但当天演出门票全额退回,为演出付出的成本无法收回,且在此后的业务开展中也遭受不利。丙的行为即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丙的行为给乙造成的损失即为纯经济损失。这种损失本质上是履行利益的损失,只是因为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不能适用违约责任制度要求第三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即使是将第三人侵害债权视为纯经济损失的一种类型,也因为这种类型的纯经济损失几乎都是第三人的故意或第三人与债务人的共同故意造成的,根据纯经济损失赔偿的一般规则都是可以获得赔偿的。
关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救济途径和方法,各国有不同的法律规定。我国现行法不承认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根据《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第三人侵害债权时,债权人只能先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然后由债务人向第三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现在正热烈讨论的侵权责任法的各个学者建议稿都规定了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如梁慧星老师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侵权责任编)第1575条(第三人侵害合同)规定:“第三人以引诱、胁迫、欺诈等方式使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合同对方当事人有权请求该第三人赔偿损失。”王利明老师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侵权责任编)第1833条(侵害债权)规定:“第三人明知他人享有债权,以引诱、胁迫等方式阻止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侵害他人债权, 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杨立新老师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55条(侵害债权)也有类似规定。虽然法工委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中没有关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规定,但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一制度应该在侵权责任法中予以规定。可以预见,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将会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得到体现。
四、我国学者对于纯经济损失问题研究的概况
纯经济损失最先是英美法上的概念,后来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借鉴纯经济损失理论对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保护进行探讨。我国学者最早专门着文探讨纯经济损失问题的是张民安先生,其发表在梁慧星主编的《民商法论丛》第25卷(2002年12月出版)上的《因侵犯他人纯经济损失而承担的过失侵权责任》一文,洋洋洒洒4万多字。其后不断有关于纯经济损失的在各种期刊上。2004年7月,中国的第一部纯经济损失专着出版,这就是李昊先生的《纯经济上损失赔偿制度研究》,全书共18万字。其后有张小义、钟洪明先生翻译的《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2005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还有张新宝老师早在2001年翻译出版的《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中有大量的关于纯经济损失的论述(注:①当然,王泽鉴先生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的两篇文章《挖断电缆的民事责任:经济上损失的赔偿》和《商品制造者责任与纯粹经济上损失》则是大陆学者最先接触到的论述纯经济损失问题的中文着述。)。之后发表的论文基本上是以上述论着为基础进行的中国纯经济损失处理模式的探讨和纯经济损失的类型化研究。前者如朱广新的《论纯粹经济上损失的规范模式——我国侵权行为法对纯粹经济上损失的规范样式》(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黄莉萍、朱娟的《侵权中纯经济损失保护模式的比较探讨》(载《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徐海燕、朱辰昊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制度研究——兼论证券市场中介机构不实陈述的民事责任》(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后者如,彭晋平的《海洋油污损害中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载《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11期),郭琛的《对我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探讨——从纯经济损失排除规则说起》(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以及前文提到的徐海燕等的文章。在类型化研究中,对于油污案 型的纯经济损失研究最为充分,有大量文章发表,这主要是因为,关于油污损害赔偿中纯经济损失是否可以得到赔偿,几个国际公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注:①国际社会为应对海洋油污赔偿问题,于1969年签订了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并于1992年通过新的议定书对其进行了修改,一般称为1992民事责任公约(英文简称1992CLC)。同时,作为对1969CLC的补充,1971年签订了关于建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国际公约,并于1992年通过新的议定书进行了修改,一般称为1992国际油污基金(英文简称1992Fund),这两个公约都于1995年5月30日生效。中国是1992CLC成员国,但尚未加入1992Fund,目前只有香港地区加入了1992Fund。
)。
随着对纯经济损失问题的认识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对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例进行纯经济损失理论分析,如王颖琼、黄长明和徐彬的《纯粹经济损失理论之践行——评〈山西日报〉巨额赔偿案》(载《时代法学》2003年第2期),周友军的《纯经济损失及其法律救济 ——“上海方舟旅行社诉东方航空公司航班延误赔偿”案评析》(载《判解研究》2005年第2辑),以及前文提及的郭琛的文章。
本文认为,关于纯经济损失问题研究的最大成果是对纯经济损失的赔偿进行立法层次的思考。因为纯经济损失的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一般不存在合同关系(注:②虽然在合同法领域存在纯经济损失,但通过合同法的相关制度可以获得救济,无需再引入纯经济损失理论进行分析。),因此学者们主要从侵权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大陆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学者们也注意到了纯经济损失问题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地位。杨立新老师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58条(纯粹经济利益损失)规定:“以故意加害他人为目的,致使他人遭受与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不相关联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前所述,各国对于故意造成他人纯经济损失的情形,都规定应予赔偿,尽管这个条文只是对这样一个规则的认可,但毕竟表明大陆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刻认识。
前文在对于各种纯经济损失类型进行探讨时,就已说明本文只是涉及“过失所引发的纯经济损失类型”。关于过失引发的纯经济损失类型,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都有所涉及(注:③油污案型的纯经济损失赔偿问题主要是在海商法中探讨,因此侵权责任法一般不予涉及。),尤其是不实陈述案型和遗嘱案型,这主要规定在专家责任制度中。如杨立新老师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三章第五节专家责任五个条文,都涵盖了这两种类型,其中第92条和第96条最为明确(注:④第92条【专家责任】以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能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专家,未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操作规程,造成委托人或者第三人损害的,应当依据本节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没有过错的除外。第96条【不实信息与不当咨询意见】负有信赖义务的专家提供不实信息或不当咨询意见使受害人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的除外。前款情形,有直接侵权人的,专家承担补充责任。)。
五、我国法律如何应对纯经济损失问题
纯经济损失虽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不是传统民法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因此大陆民商事法律中没有关于此问题的规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比较法上的考察表明,纯经济损失的保护已成为民法上的重要课题。整合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理论,对纯经济损失的保护制定基础性规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现行法律关于纯经济损失的规定
1.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之规定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学者一般认为该款并不是对权利保护的列举规定,即并不能将该款理解为“行为侵害他人财产权、人身权”,将其理解为“行为导致他人发生财产、人身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更符合立法的本意[14]。《民法通则》立法之初虽然不可能考虑到纯经济损失的问题,但该款规定也并无排除纯经济损失之本意。因此,如果要将纯经济损失问题整合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中,那么该款规定可以接纳。因为纯经济损失是加诸于受害人整体财产的损失,可以理解为侵害他人的财产。
2. 其它现行法对相关类型纯经济损失的规定
在我国现行法中,对于纯经济损失赔偿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不实陈述案型和遗嘱案型。最典型的是《证券法》第173条的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这里,即使信息披露存在瑕疵,也很难认定中介机构对投资者的财产或者人身有直接侵害行为,因此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属于纯经济损失。虽然《证券法》的该项规定主要是基于对市场安全和投资者信心的保护,而对纯经济损失是否应予赔偿并无明显的考虑,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纯经济损失给予赔偿的立法例。
另外,《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利害关系人所受的损失属于纯经济损失。还有学者提到(注:⑤张新宝老师在其向2008年12月18日在台北举行的“纯粹经济损失”国际研讨会所提交的会议论文《纯粹经济损失:在中国大陆的理论、实践及其展望》一文中提到。)《律师法》第54条(2001年版的第49条)(注:⑥《律师法》第54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是对律师虚假陈述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应予赔偿的规定,但如果仔细考察原文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该条规定的是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而“当事人”的损失本质上属于履行利益的损失,一般由合同制度来救济。前述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关于专家责任的规定倒是可以认为是对注册会计师、律师的虚假陈述或服务过失造成他人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
还有一些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司法解释也可作为对纯经济损失赔偿的依据,如[1996]第3号《关于金融机构为行政机关批准开办的公司提供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不实应当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1997]第10号《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1998]第18号《关于会计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资金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2003]第2号《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
(二)对纯经济损失引入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思考
如前所述,与合同有关的纯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合同责任制度获得救济,但大多数的纯经济损失还是适合由侵权责任法来调整。我国正在制定侵权责任法,如何将纯经济损失的概念和制度整合在侵权责任法以至整个民法体系中,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认为以下四点至关重要。
1. 纯经济损失概念引入与我国既有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冲突,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其操作性。如前所述,如果要将纯经济损失问题整合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中,《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可以接纳。纯粹经济损失概念的工具意义在于它可以将某些经济上或金钱上的不利益做出公开的利益评价,进而确认其是否可以获得法律救济。这不仅使法官适用法律有明确的尺度、判断责任有可行的办法,而且保证了裁判结果的统一性和公正性。对当事人 来说,了解纯经济损失在侵权法上一般不予赔偿可以起到息讼的作用,引导当事人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就此而言,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引入纯经济损失概念,有益于我国侵权法调整方式的进步。
2. 在调整纯经济损失时,正确处理契约法与侵权法的关系。民法对民事权益的保护,主要有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大制度。契约责任适于救济纯经济损失,因为当事人之间具有特殊关系,可以减少责任范围的不确定性,双方可以依契约条款合理分配契约上的风险。因此,纯经济损失原则上应受契约法调整。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契约的情况下,如果一方使他方遭受了纯经济损失,才可以求助于侵权法。
3. 在侵权责任法中,应考虑纯经济损失的基础性规范与具体类型的规范相结合。关于基础性规范的设置可以借鉴杨立新老师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58条(纯粹经济利益损失)并加以补充,作如下规定:第一款为“以故意加害他人为目的,致使他人直接遭受非因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而间接引起的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第二款为“因过失致使他人直接遭受非因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而间接引起的经济损失的,本法或其它法律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本法或其它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法官依据公共政策做出自由裁量”。这个基础性规范很重要,因为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运用纯经济损失的基础性规范和基本理论,对法律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纯经济损失类型进行分析。当然,对于已经有成熟规则的纯经济损失类型则在侵权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
4. 在具体运用纯经济损失概念时,还应注意两点:其一,即使一项损失属于纯经济损失,也并不表明该损失就确定地不能获得赔偿。对于那些其损失范围和受害主体都比较确定的纯经济损失,在特定情况下,并不能排除对该等损失的法律救济。其二,各种类型的纯经济损失是否予以赔偿,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需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类型化研究,以有利于司法操作,这是今后纯经济损失问题研究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2][8][10]李昊.纯经济上损失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 7,p7~8,p15,p26.
[3]靳羽.纯经济损失概念分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2):p100.
[4][14]张新宝,张小义.论纯粹经济损失的几个问题[J].法学杂志,2007(4):p16,p18.
[5]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p443.
[6]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p36.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p58.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p137.
[9]李昊.纯经济上损失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8~10.张新宝,张小义.论纯粹经济损失的几个问题[J].法学杂志,2007(4).李朝亮.纯粹经济损失初论[J/OL].
/lw/lw_view.asp?no=1929.
[1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7)[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p88.
第6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内容提要: 法经济学的一种通行观点认为,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非“真实社会成本”,而仅仅是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支付,因此原则上否定此种交易获利机会赔偿的侵权法规则具有合理性。提出该观点的早期文献系统性低估了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引发的“真实社会成本”。实际上,如果坚持使用“真实社会成本”概念对侵权法规则进行分析,最终甚至会导致对物之损害赔偿的传统规则的正当性也发生疑问。适宜的作法是放弃“真实社会成本”概念而代之以“相对社会成本”概念,原则上将成本——收益分析限定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此种思路,除第三人提供交易机会所导致的或具有合同法救济渠道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需要特殊处理外,并无效率方面的原则性理由支持侵权法一般性地排除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可赔性。
一、引言
单从语义来讲,所谓“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一概念可以指任何社会资源作为自愿交易客体的价值减损——它既包括通常被归入“纯粹经济损失”(pure economic loss)或称“纯财产上损失”(reiner vermgensschaden)的产品自伤[1],也包括因违约而导致的债权不能实现、当事人为进行缔约谈判而支出的花费等各国通常在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等制度中专门处理的问题,甚至还包括毫无疑问属于传统侵权法救济范围的物之灭失和人身伤害[2];而从最狭窄的意义上说,该概念则仅指没有任何物或人身遭到直接损害,而仅仅是(潜在)交易过程受到了第三人某种形式的干扰破坏的情形。本文所讨论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既不是最广义上的,也不是最狭义上的。具体来说,它可以用如下方式加以描述:如果加害人并未对受害人而仅仅对第三人实施毁损其物或伤害其人身的行为,但因为受害人将要或已经与他人缔结某种交易关系(或者说有偿法律行为),而使得受害人仍然因加害人的行为而损失从该交易的履行中本来能够获得的利益,那么则存在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3]。
在出现上述意义上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情形下,法律是否提供侵权损害赔偿作为救济?迄今为止,英美普通法和德国法给出的答案较为一致:至少在被告系出于过失的情形下,原则上不提供侵权法上的救济[4]。有关这种处理方式的正当性,传统的通行解释是所谓“诉讼闸门”(floodgate)理论。该理论认为:诸如交易获利机会丧失之类的“纯粹经济损失”,其发生经常具有偶然性,受害人的范围难以确定,损失大小更是难以控制。如果允许这类损失获赔,一方面会引发无数诉讼而使法院不堪重负,导致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将给被告施加过重的负担,由此有失公平[5]。这个说法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首先,现代侵权法中有很多专门用于处理损害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现成规则,如普通法中的近因(proximate cause)规则和可预见性(foreseeability)规则[6]。相比物和人身的直接损害,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或许更经常地表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这似乎很难成为对那些必然和确定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也拒不救济的理由。更何况在现实中,那些并未将交易获利机会丧失和物与人身的损害特别区分对待的法域(如法国)在实践中似乎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诉讼爆炸”现象[7],这多少让人怀疑赔偿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会鼓励滥诉的命题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其次,“诉讼闸门”理论也没有解释,何以允许交易获利机会的丧失获得侵权损害赔偿就会导致诉讼泛滥和加重被告负担,而允许其他种类的侵权诉讼就不会产生这些结果——毕竟,要论浪费司法资源,恐怕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元钱诉讼”之类小额诉讼。但现代各国法律不但没有排斥这类诉讼的存在,反而在很多情形下通过集团诉讼(class action)等制度安排为其实现提供额外便利。许多受害人本不会为之打官司的小额请求权,加起来往往就是足以导致跨国公司破产的天文数字[8],但又有谁能由此断言集团诉讼制度给被告施加了“过”重的负担,从而“有失公平”呢?这里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仅仅是:我们凭什么认为,交易获利机会丧失等所谓“纯粹经济损失”相比其他种类的损害更不值得花费司法资源进行救济?我们又凭什么认为,针对这类损害的赔偿给被告造成的负担是“过分”的?[9]
与“诉讼闸门”之类传统视角相比,法经济学的分析似乎在这个领域显示出了更大的解释力。英国学者毕晓普(w. bishop)在1982年发表于《牛津法律研究杂志》的论文《侵权法中的经济损失》(economic loss in tort)中,首次立基于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侵权赔偿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并得出了支持普通法现行规则的结论。他的思路又为大量法经济学权威学者如戈德堡[10]、波斯纳[11]和萨维尔[12]等所采用。本文将首先对毕晓普的理论进行简要介绍,然后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尝试运用和该理论相同的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交易获利机会在侵权法上的可赔性问题给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处理方案。
二、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与“真实社会成本”:毕晓普理论评析
(一)毕晓普理论的要点
毕晓普在《侵权法中的经济损失》一文中的基本论点可以概括如下:
1.法院在裁判过失案件的过程中,会对案件事实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其目标是计算事故预防措施的成本与收益。这是一种针对“社会”效益的计算,即忽视具体哪些人获得了什么,而只关注总收益是否超过总成本,即使某些人会因此处于更糟糕的境况。在这一计算过程中,重要的是绝不能计入所谓“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因为它虽然是某人的私人成本,同时却又是另一人的私人收益;换言之,由此导致的净社会成本为零[13]。
2.“在范围广泛的案件中”,因侵权行为而导致的私人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仅仅是转移支付,而不产生社会成本。毕晓普为此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假设小镇mississauga(以下简称m镇)和etobicoke(以下简称e镇)之间有一条铁路相连。铁路公司正在考虑是否安装特定的防脱轨设备,以消除装载危险化学品的火车脱轨的危险。又假设,这类脱轨事故造成的主要的直接后果就是,发生脱轨事故的小镇的人口会全部疏散到另一个小镇,为期一周。再假设该设备的安装成本为1000万美元,设备寿命为10年,而事故在不安装设备的条件下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每次造成的居民疏散费用为400万美元。显然,如果只考虑这些因素,铁路公司就不应当安装防脱轨设备。
继续假设,每个小镇都有一个屠夫、一个面包师、一个制烛匠和很多其他店主和商人(他们都是风险中立的),每人在每周都有固定的营业额。再假设(据毕晓普本人讲,“这是关键所在”)他们每人都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容纳超出其正常营业额的额外交易量,而同时除原材料之外不会产生其他额外成本。如此一来,发生在m镇的脱轨事故造成的影响就是,m镇商人在一周内无法营业,由此丧失该周本来能获得的账面利润。而同时e镇商人在该周却能使营业额翻番,由此其该周内的账面利润也会增加一倍。脱轨事故使财富从一群人手中转移到另一群人手中。假设m镇商人有权要求铁路公司,像赔偿前述居民疏散费用一样赔偿其上述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而这一损失的数额为800万美元,那么铁路公司面临的脱轨事故预期总成本就是1200万美元,这一数额大于防脱轨设备的安装成本,因此铁路公司将会决定安装这一设备。但从社会角度看,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社会福利计算得出的净损失仍然是400万美元而非1200万美元。m镇商人遭受的800万美元的利润损失仅仅是一种转移支付,由此导致的社会成本为零[14]。
3.在现实生活中,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经常可能伴随着某些真正的社会成本的产生,但是在其间发挥影响的因素十分复杂,有理由认为法院并不具备在每个个案中作出必需的技术性裁判的能力。即使法院具备这种能力,实施这类裁判也没有意义,除非经济生活中的每个潜在侵权人都能预先察知可能的法院判决对他的影响。因此,我们能够期待的通常只是大体能产生有效率结果并能给判决者提供明确指引的一套规则,而在这一方面,对于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原则不予赔偿、例外承认赔偿的英美普通法规则,至少能够和其他规则一样好地实现效率目标[15]。
(二)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第三方“真实社会成本”的界定
本文认为,毕晓普上述理论的分析思路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问题之一出在毕晓普本人视为“关键”的一个假设,即在导致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事件中,其他未受害的交易主体“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容纳超出其正常营业额的额外交易量,而同时除原材料之外不会产生其他额外成本”上。按照毕晓普的思路,如果在受害人丧失交易获利机会后,其他交易主体可以取得受害人丧失的所有账面利润,而同时又“至少在短期内”不发生“额外成本”,那么可以认为此时的“真实社会成本”为零,没有必要赋予受害人任何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恰恰是如何界定所谓“额外成本”:这类“成本”到底是只包含经营者在m镇人口疏散的一周内实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经营成本(本文称之为“短期成本”),还是同时也包含甚至在此之前很久经营者就为应付类似事故而预先支出或可能支出的成本项目(本文称之为“长期成本”)?毕晓普在文章中并没有正面回答,不过他的态度在对自己所举例子的扩展论述中可见一斑:
例2的事实同例1,唯一不同的是,商人们无法轻易地在短期内扩展服务以容纳突然增加的需求。每一个e镇的屠夫、面包师、制烛匠都必须雇佣额外的帮手,这些帮手只有在为其烦劳获得报酬的时候才肯从事工作。不仅如此,现有的工作人员也感到烦恼和过度劳累,并要求为其烦扰获得额外报酬。对于所有消费者而言,肉、面包和蜡烛的价格都上升了,无论对于平常在e镇采购的人还是对来自m镇的难民都是如此。这些事实描述了短期内真实生产成本的上升……[16]
如此看来,毕晓普所关注的仅仅是那些“代替受害人赚钱”的交易主体在事故所造成的交易获利机会丧失效应所持续的“短期内”直接产生的生产成本。只有在出现这种短期成本的情况下,毕晓普才认为事故产生了“真实社会成本”[17]。如果遵循这种思路,当然就会把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是否产生“社会”成本的问题看成一个纯粹依赖于个案案情的或然性问题:只要能够假设在社会持续期间社会总交易额保持不变,而受害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又没有在账面上直接体现出成本的增加,那么毕晓普就完全不认为存在“真实社会成本”,赋予受害人以赔偿请求权也就只会浪费加害人的防险成本和司法资源,而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效益。但这种思路显然没有考虑那些无法被直接归入某次事故持续期间的盈亏统计的生产成本,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长期成本”。让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假设毕晓普例子中的m镇和e镇除了火车脱轨事故外不可能发生别的足以导致大规模疏散的事故,此时e镇商人有什么理由在一开始就建立和维持一种“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容纳超出其正常营业额的额外交易量”的经营能力呢?比如说,e镇的屠夫为何要在三条冷冻肉生产线本已足够满足“日常”客户对肉类的需求(也即未发生脱轨事故时e镇居民的需求)的情况下购买和维持“至少在短时期内”足够同时为m镇和e镇居民加工肉类的五条生产线?e镇面包师为何要在一台小面包炉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偏偏购买一台“至少在短时期内”足够同时为两镇居民烤面包的大面包炉?e镇饭馆为何要在40平方米的经营空间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客户需求的情况下,用一座“至少在短时期内”足够同时满足两镇居民就餐机会的70平方米的平房充当铺面?不要忘记,这一类额外经营能力的取得和维持,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推论:
1.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中,受害人之外的其他交易主体为满足事故使之落空的那部分需求,不仅需要支出短期成本,而且需要支出长期成本,即必须在事故发生之前预先支出,才能期待其发挥应有效用的成本。相比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更容易被成本——收益分析所忽略;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在侵权法上是否可赔,同样会影响到这类成本的支出。波斯纳曾试图淡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虽然‘额外(交易)能力’听起来像一种浪费,但并不必然如此。多数零售企业在运营的大多数时间里都保留着一点额外能力以应付需求峰值。”[18]这种说法显然无甚说服力,因为“多数零售企业”在运营期间也同样愿意拿出“一点”资金储备以自我消化小型事故带来的损失而不是提讼,但这并不是侵权法在小型事故中拒绝赔偿的理由。这里的根本问题仅仅在于:如果我们将与短期成本变化无关的额外交易能力的存在视为单纯的既成事实,而不作为成本—收益分析中的一个变量处理,那么这种成本—收益分析就无法真正反映毕晓普理论所定义的那种“真实社会成本”的变化情况。
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不可赔的侵权法规则下(换言之,在法律放弃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进行威慑的情形下),导致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事故将会更频繁地发生,相应地受害人之外的其他交易主体就会选择投入更多成本来建立和维持更多的额外交易能力以捕捉由此带来的商机。如果再假设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几率对每个交易主体都是相等的,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社会所有交易主体都开始针对额外交易能力投入更多的成本,而这有可能大大超过社会节约的加害人防险成本。例如在毕晓普的例子中,假设e镇商人要想容纳10年内因m镇的脱轨事故而送上门来的客源,必须预先支出400万美元的成本来建立和维持额外交易能力(如更多的肉类加工生产线、更大的面包炉、更大的店面,等等),那么此时这一支出对e镇商人来说仍然是划算的,因为400万美元的投入能换来800万美元的回报。同时,由于10年内脱轨事故发生在m镇和e镇的几率是相等的,m镇商人同样也可期待从e镇的事故和疏散中获利,因此他们也会选择增加400万美元的投资。如果再考虑400万美元的疏散费用,那么在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不可赔的侵权法规则之下,社会总共将增加400+400+400=1200万美元的净成本。但与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可赔的侵权法规则相比,这种状态显然是无效率的,因为后一种规则下社会仅会增加1000万美元的净成本,即铁路公司安装防脱轨设备的费用[19]。
2.也许比第一点更重要的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受害人以外的其他交易主体为满足额外需求而支出的总成本,只能视为一种必然而非或然成本。毕晓普一再强调,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中,“真实社会成本”取决于具体个案的复杂情况,而这其实也就是说,其并不必然发生,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如果“真实社会成本”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仅限于短期成本,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将长期成本也考虑进来,就显然不能再如此认为了。实际上,企业在捕捉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带来的额外商机时投入的短期成本或者说流动资本越少,则说明该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固定资本所占比重越大,从而该企业在对固定资本进行投资时就越有可能对(至少是那些较为常规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作出反应;反之,如果企业在投资于固定资本时对商机变化问题很少甚或根本不考虑,则只能说明该企业的经营调整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控制流动资本而实现,从而甚至是那些不太常规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也很可能会导致该企业短期成本投入的相应增加:因此,社会定类型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在发生水平上的任何系统性变化,都或迟或早会导致所谓“真实社会成本”(即企业为捕捉额外交易机会而支出的总成本)的相应变化,不可能存在单纯体现为转移支付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换言之,毕晓普过分强调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的转移支付性质,是因为其一开始就片面低估了市场主体因捕捉交易获利机会而诱发的总成本[20]。
当然,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毕晓普所支持的原则上否定交易获利机会可赔性的侵权法规则一定错误——除开高昂的法律执行成本之外[21],加害人避免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的努力显然也不会是无成本的。如果采纳原则上肯定交易获利机会可赔性的侵权法规则,这些成本都将成为现实。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分困难的抉择:到底是以增加加害人防险成本的支出为代价,鼓励受害人之外的其他交易主体削减交易机会捕捉成本(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还是以增加交易机会捕捉成本的支出为代价,鼓励加害人削减防险成本呢?无论如何,我们没法先验地断定后一种方案是更佳选择。毕竟,如上文分析所显示的,交易机会捕捉成本完全有可能高于防险成本。当然,理论上最理想的法律规则是能够使两种成本之和最小化的规则[22],但这里的问题是,法院在现实中几乎完全不可能观察到交易机会捕捉成本的变化情况——单是确定因事故而转移的商机到底落到了哪些交易主体头上,就已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此处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对于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侵权法无论是全部赔偿、部分赔偿还是全部不赔偿,都无法保证削减毕晓普理论作为分析出发点的那种“真实社会成本”。
(三)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对受害人成本支出的影响
毕晓普理论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低估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受害人可能改变其成本支出状况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毕晓普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明确承认“最优结果”,即加害人和受害人都不因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而支出任何成本的状态“在受害人具有避免事故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达到”[23],因为受害人在其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不能获赔的情形下,有可能转向自行支出成本以求减少自己的私人损失。但本文认为仅仅承认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受害人是否具有“避免事故”的可能性,而在于其是否具有“避免事故给自己带来损害”的可能性。这两者的根本差别很容易理解:化工厂附近的某个住户无法独自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工厂有毒物质的泄漏,但却可以或多或少地采取措施来消除或减轻一旦泄漏事故发生时自己将遭受的损失——如购买防毒面具,或者干脆将住处搬到远离化工厂的地方。换言之,如果受害人的目标仅仅是减少自己的私人损失,那么从理论上说,他既可以选择“避免事故”,也可以选择“避免事故给自己带来损害”,前者不可行不代表后者也必然不可行。
由此,我们能得出推论:在法律放弃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进行威慑的情况下,正如第三人捕捉交易获利机会的成本是必然发生的一样,受害人为避免自己遭受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而支出某种形式的成本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尤其从长远观点来看,受害人在理论上总是会对给自己带来损失的事件作出反应以求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由此又可能带来更大的“真实社会成本”。具体到毕晓普的例子来看,假设m镇和e镇的商人都可以通过每年在另一个镇里预先购买在一周时间内以固定价格承租第二个店面的选择权(option)的作法,来保证一旦在自己镇里发生脱轨事故时,可以通过以另一个镇的店面接收本镇老主顾生意的方法来保持企业账面利润持平。假设此类因素将使m镇的商人在10年间总共增加500万美元(每年的选择权价格加事故发生时实际支付的固定租金)的经营成本,那么他们作为理性人仍然会选择这种低效的经营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可以使其在脱轨事故发生时减少800万美元的账面利润损失。又因为事故发生在m镇和e镇的几率是相等的,因此e镇商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样一来,在侵权法拒绝赔偿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条件下,社会将产生总计500+500+400=1400万美元的净成本,显然高于在法律允许赔偿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时社会将产生的1000万美元防脱轨设备安装成本。
(四)小结
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侵权法拒绝对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给予赔偿,那么无论是受害人本身支出的减损成本,还是受害人之外的交易主体支出的交易机会捕捉成本,都完全有可能超过社会所节约的加害人预防成本。如果再考虑受害人已经支出了减损成本,其他交易主体却仍然徒劳地投入交易机会捕捉成本的可能性(这主要是交易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那么“真实社会成本”无疑会更加巨大。本部分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侵权法否定对交易获利机会的过失损害赔偿能够比肯定这类赔偿节约更多毕晓普所谓的“真实社会成本”[24]。
三、问题的解决:从“真实社会成本”到“相对社会成本”
(一)物之损害赔偿案件中“真实社会成本”的确定
上文已经证明,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侵权法无论是允许还是拒绝受害人针对过失加害人的索赔请求,都无法被证明有助于节省毕晓普所谓的“真实社会成本”。那么,这种困境仅仅存在于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吗?本文的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只要我们坚持损害赔偿范围必须是毕晓普意义上的“真实社会成本”而非受害人的“私人成本”的观念,那么甚至连最普通的物之损害的赔偿问题都没法解释。
1.何谓“物的直接损害”?
假设a因过失打碎了b的一块窗玻璃。各国侵权法对此的处理方案基本相同:第一,a应当赔偿b在当地市场上购买一块新的窗玻璃所需付出的价格[25];第二,如果b能够证明自己因a的行为遭受了“间接”损失(亦即仅仅通过换一块窗玻璃无法得到弥补的损失),则可以一并请求损害赔偿。此处让我们把间接损失的赔偿留待稍后讨论,而首先回答一个问题:此时b的直接损失是什么,与此对应的“社会成本”又是什么?乍看上去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b的直接损失就是“一块窗玻璃”,而社会因事故遭受的损失也是“一块窗玻璃”,b的私人损失与“真实社会成本”完全重合,因此各国侵权法的通行处理方案完全符合“责任范围应当等于损失程度”[26]的法经济学信条。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
(1)从b的角度来看,他的私人损失显然并不是“一块窗玻璃”,而是一块已经安装在自己房屋某扇特定窗户上的玻璃能够给自己带来的效用,如遮风、采光等。至于用来购买新玻璃的款项支出,则是在消除上述损失的过程中发生的“二次损失”,它本身并不是事故直接引起的b的初始私人损失:至于“二次损失”与初始私人损失的大小,严格来说是无法进行“客观”比较的,因为二者根本不同质。只有在b实际支出款项购买新玻璃的情形下,外部观察者才有理由认为“二次损失”小于b的初始私人损失。
(2)新玻璃的价款本身是否属于“真实社会成本”?答案也是否定的。假设b是从玻璃生产商c处购买新玻璃(此处为讨论方便忽略一切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中间商业环节),则b支付的价款成为c的收益,即所谓“转移支付”。此时是否能认为,虽然c获得了支付,但同时丧失了与之等值的一块玻璃,因此这一交易只不过是“重述”(restate)了已经造成的社会损失呢?[27]显然不能。如果c不能从交易中获利(换言之,其制造一块玻璃的账面成本大于或等于其获得的玻璃价款)[28],那么他就不会从事交易;如果他不从事交易,一开始他就不会耗费原材料和人力,将这块玻璃生产出来。因此对于c而言,其因交易而遭受的损失并非“一块玻璃”,而仅仅是生产这块玻璃的账面成本,或者说为生产一块玻璃而消耗的原材料和人力。
(3)上述推论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由于c本身并不是玻璃原料的生产商,因此其必须从玻璃原料生产者d那里购买原料,而d生产原料同样也要耗费他自己的成本……由此类推,整个社会因a的行为而产生的不包含任何私人收益成分的“净”损失归根结底由两部分构成:为生产一块玻璃所必须耗费的纯粹原始状态的自然资源,和为将这些自然资源加工成一块玻璃而需要耗费的人力成本之和。如果说侵权损害赔偿额应当与“真实社会成本”而非任何私人损失等值,那么a对b的赔偿数额就不应当是一块窗玻璃的市场价格,而应当等于上述两项的价值之和。显然,在实践中要证明上述价值的准确甚或大体数目(比如说,窗玻璃市价减去它的各级生产商和销售商各自从中获得的账面利润),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如果因此就认为窗玻璃的市价可以作为毕晓普所谓的“真实社会成本”的一个“粗略”计算标准,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上文分析已经指出,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真实社会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成本的数额“很可能”小于受害人的私人损失的事实足以成为侵权法拒绝赔偿后者的理由,那么就根本无法解释,在窗玻璃案件中,同样是“真实社会成本”小于受害人的私人损失,为何侵权法却坚定支持对后者的赔偿。更何况,如果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举证难度远远大于物之损害的举证难度,那么基于和法经济学支持惩罚性赔偿相同的原理[29],我们更有理由主张,侵权法针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的责任强度即使不说应当大于,至少也不能小于针对物之损害案件的责任强度。
2.物之损害导致的间接损失:“附随经济损失”而非“纯粹经济损失”?
以上内容仅仅是针对物的直接损害的赔偿问题的分析。如果同时考虑“间接损失”的赔偿问题,那么毕晓普理论遇到的困难就几乎是无法逾越的——众所周知,“间接损失”的概念是包含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的,如果说独立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本身并非“真实社会成本”,那么附随于物或人身损害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同样也不是“真实社会成本”,为何后者在实在法上独独就可以获赔呢?[30]毕晓普本人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分是“专断的”[31],但同时又试图为之提出三点辩护。在本文看来,这些辩护都是明显难以成立的:
(1)毕晓普认为,程度严重的损害将破坏受害人自身分散损害的机制,而且附随于物理性损害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更可能在受害人一方造成投资激励扭曲[32]。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一方面,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并不见得只附随于“严重”损害的情形,如扎破车行所有的一辆自行车胎对车行来说并非多么严重的损害,但却可能导致该车行损失自行车在特定时间内的出租收益;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基本假设,受害人一方投资激励的扭曲程度并不取决于其遭受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是附随性的还是独立存在的,而仅仅取决于该损失的大小[33]。
(2)毕晓普还提出,法院只选择某些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进行赔偿,可以“粗略地”反映“真实社会成本”只是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一部分的事实[34]。这也就是戈德堡所谓的“错错得正”(two wrongs might make a right)[35]的思路。这种思路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错错真的可以得正,我们也应当根据相同的逻辑,只选择一部分物之损害进行赔偿(比如,只有年满20岁的男性遭受的物之损害可以获赔),以同样“粗略地”反映“真实社会成本”只是物之损害的一部分的事实。毫无疑问,法律的任何这种尝试都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专断。
(3)毕晓普给出的最后一个辩护是,只赔偿“间接损失”的作法有助于区分有根据的索赔请求和不真实的索赔请求[36]。戈德堡对此作了进一步补充:对于附随于物理性损害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法院可以比较容易地适用减损(mitigation)规则以使赔偿数额逼近“真实社会成本”,但对于独立存在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法院就很难确定该损失被其他交易主体通过代替受害人赚钱而被“替代减损”的程度。对于毕晓普的命题而言,且不论是否能从直接损害的真实性直接推导出间接损害的真实性,单就这个命题本身而论,实际上是个证据法而非实体法的问题,应当适用证据法规则来解决。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限制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戈德堡的命题同样没有说服力:附随性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也有被其他交易主体“替代减损”的可能性,独立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也有受害人自己减损的可能性,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受害人自己减损占据主导地位,而后一种情况下他人“替代减损”就要占据主导地位。
分析到这一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要么认为现代各国侵权法连最简单的物之损害赔偿问题都无法适当应对,要么重新检讨作为毕晓普理论根基的“真实社会成本”概念。后一个选项涉及准确回答侵权法中的“社会成本”到底是指哪些主体所发生的成本,由此对侵权法的成本-收益分析边界进行必要限定的问题。
(二)“相对社会成本”概念的提出
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简要考察一下诉讼程序问题。众所周知,典型的诉讼程序是原被告两造参加的,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和质证、法律观点的攻击与防御,都只会围绕着原被告双方的立场而展开。法官在疑难案件中进行利益衡量,进而创制判例规则时,原则上同样只能基于对原被告双方各自的利益状况作出的判断。超出这个范围,去过多地考虑第三人,尤其是那些并未参加诉讼程序的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很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有关这些第三人利益状况的各种事实由于诉讼程序设计上的局限,更难被法官全面准确地认知,由此作出的法律判断是否正确也就没有保障。如果我们考虑到司法判例和法官经验甚至在成文法的制定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7],那么那种认为法律中的利益衡量可以超越具体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利益分歧,直接以“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为旨归的思想,如果不是根本错误的,至少也是十分可疑的。
实际上,正如我们或许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甚至连“社会福利”的概念本身都不是那么无懈可击的。我们究竟应该把哪些东西看作“社会福利”?对于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包装和“开发”,我们是应当遵循开发商和经济学家的意见将之看成“社会福利”呢,还是应当遵循环保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意见将之当作“社会成本”?如果在某个侵权案件中,加害行为换来的是社会舆论的一致称赞[38],那么是否应当将这种“第三人福利的增长”包括到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去?如果说不应当,那么这种情况和毕晓普例子中的其他交易主体能赚更多钱的情况又有何本质区别?无论如何,在福利经济学至今也无法给出一个具有通用性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条件下[39],试图将原被告双方之外的第三人的福利变化情况无差别地加入成本——收益分析的衡量标准,似乎并不能得出太多有意义的结果,而这一点显然已为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所证明。
从以上分析出发,本文提出的建议是:至少在针对侵权法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范围内,必须放弃将加害人和受害人之外的第三人福利状况的变化作为利益衡量的一个当然参照指标的作法。一个真正有用的“社会成本”概念,应当被定义为加害人和受害人双方(确切地说是两个社会群体)可用金钱更方便地衡量的私人成本之和;至于第三人的私人成本变化情况,原则上不应予以考虑[40]。本文将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成本”称为“相对社会成本”,用以区别于毕晓普意义上的“真实社会成本”。只要某种侵权法规则可以减少“相对社会成本”,就可以认为社会福利得到了(相对的)改善,而并不是非要在衡量了社会中一切想象得到的相关方的福利变化情况之后,才能对某一法律规则的合理性问题给出答案。
毫无疑问,采纳“相对社会成本”的概念意味着对毕晓普理论体系的彻底否定。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和物之损害在社会福利效果上的所谓“本质区别”现在完全不复存在了。它们都是受害人私人的损失,因此原则上没有理由不认为它们属于侵权法应当关注的“损害”。“相对社会成本”的引入也使得原先我们无法解释的物之损害赔偿的正当性问题迎刃而解:在打碎窗玻璃的案件中,根本不需要考虑某个玻璃生产商或其上游生产者是否会因打碎玻璃而得利的事实,需要关注的仅仅是受害人的“私人”损害,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如果考虑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论点,即无论是物的损害还是人身损害赔偿,某种程度上其实都可以直接视为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赔偿,那么将“纯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单独排除出侵权法救济范围之外,就更没有什么道理了。无论是在物之损害赔偿的情形下,还是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赔偿的情形下,侵权法赔的都既是私人损失,又是“社会损失”;或者说,由于侵权法的利益衡量框架已经在原则上排除了对其他不相关第三人福利状况的考虑,因此这里的私人损失和社会损失是完全重合的。
(三)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作为毕晓普理论基石的“真实社会成本”概念会导致在传统法经济学框架内根本无法胜任处理的大量问题被引入分析过程,这势必引起整个分析的全面瘫痪。相对可操作的利益衡量标准是“相对社会成本”,即受害人和加害人各自支出的可以较为方便地计算的私人成本之和。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第三人的获利在任何情形下都既不能用来论证某种损害是否具有可赔性,也不能用来论证加害人注意成本的投入水平究竟是过高还是过低。
四、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赔偿的两个限制
虽然上文得出的结论是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原则上没有理由不成为侵权法的赔偿对象(具体到法教义学上,也就是在侵权法可赔损害的范围上采纳“法国式的放任原则”[41]或许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但这当然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是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就一定能得到赔偿。除了因果关系等传统上就被视为控制损害赔偿范围之利器的法律技术工具外,笔者在此重点讨论两种不应获赔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1)因第三人提供交易条件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2)具有违约责任救济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42]。
(一)因他人提供交易条件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不应获赔
尽管引发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除了非人为因素导致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外,人为导致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加害人通过侵害某人(不一定是受害人,甚至也不一定是交易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物)而导致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另一种是加害人通过向某人(同样不一定是受害人的交易相对人,也可能是其他人)提供交易条件,使其不愿意与受害人或其他相关当事人缔结或履行某种交易(有偿法律行为)而引发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前一种情况在上文中已经作了详细分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后一种情况。假设a欲将某物出卖给b,合同尚未订立,c向a提出支付更多的价金买下该物(或者单纯凭借与a的良好关系向其施压,要求a将物赠与给他),a允诺;或者,a虽然仍选择与b达成交易,但这是以b被迫提出更高的价金而实现的。在这类情形下,b无疑损失了与a签订合同本能实现的交易获利机会。对于各国法拒绝赔偿此种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规则,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
1.纳入“受害人”交易相对方利益状况的解释路径
这种解释路径将因第三人提供交易条件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视为侵权法不考虑第三人利益状况之原则的例外。具体而言,从单个案件的静态角度观察,b和c各自从与a的交易中获得的主观效用增加是无法“客观”比较的,因此决定性的考量因素就是a的利益状况。鉴于a无论如何都能从这类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中取得某种形式的福利增加[43],因此,在a与c订立合同的情形下,abc三人的整体福利水平更有可能高于在a与b订立合同的情形下的水平,而非相反。换言之,法律允许a根据其自身意愿与c而非b达成交易,更有可能达成较佳的社会福利状态。这其实也就是某些法经济学者认为此种情形中b的损失“并不对应于社会损失而是对应于社会盈利”[44]的观点的真实含义。
2.不纳入“受害人”交易相对方利益状况的解释路径
这种解释路径坚持“相对社会成本”理论排除考虑第三人(即a)利益状况的原则,直接在“受害人”b和“加害人”c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具体而言,从同类案件在社会中持续发生的动态角度观察,如果认为a选择c进行交易而“导致”b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那么就必须认为,a如果选择的是b,那么同样“导致”了c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45]。因此,适用赔偿规则的长期效果实际上就是:无论是谁获得与a交易的机会,都有相同几率被判赔。根据科斯定理[46],这一结果是否会对b和c的交易激励发生过份的抑制作用,取决于b和c之间交易成本的大小。(1)如果b和c并不处于相互可以无成本地知晓对方的存在或报价的状态(如竞标过程中),那么无论是b还是c,都很可能由于不能确定对方的存在与否和所要求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而从一开始就选择不与a签订合同。显然,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结果——b和c的潜在交易机会都因为不良的制度设计而损失掉了。(2)如果b和c处于相互可以无成本地知晓对方的存在与报价的状态(如拍卖过程中),那么只能认为b在自愿退出报价竞争时已经达到了己方交易获利机会的压缩极限,继续加价只能使得该交易对于他/她的效用转为负值,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他/她因退出而遭受的任何交易获利机会损失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总之,在c提供交易条件导致b与a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情形下,要么认为强制c对b进行赔偿的规则无法得到实际适用,要么认为其适用结果比不适用还差。
基于以上分析,无论b和c各自提出的交易条件是什么,法律只有任凭a与c达成交易而不作干涉,才能达成较佳的总体福利状态。这一点反映到法教义学上,就表现为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私法主体有权选择与任何其他人以任何条件实施法律行为,法律应当保护行使缔约自由的当事人免于因此承担侵权责任(当然,构成权利滥用的除外[47])。
(二)具有违约责任救济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不应获得侵权法救济
1.一般分析
在受害人就其遭受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具有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作为救济渠道的情形下,受害人通过违约之诉寻求救济和通过侵权之诉寻求救济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前一种情形下,受害人的合同相对方在赔偿受害人之后,可以将自己支付的赔偿通过违约之诉,或作为“间接损失”通过侵权之诉向加害人索赔,因此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诉讼;在后一种情形下,只有受害人针对加害人的一个侵权之诉。乍看上去,似乎后一种情况更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因此应当允许受害人通过侵权之诉向加害人直接索赔[48]。其实不然。在受害人直接向加害人索赔的情形下,受害人要证明加害人行为与自己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势必要证明:(a)自己与自己的交易相对方存在有效合同关系;(b)该交易相对方与加害人存在有效合同关系且加害人违约,或加害人对该交易相对方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换言之,即使在后一种情形下的一个诉讼中,法院同样要审查在前一种情形下的两个诉讼中各自需要审查的基本事实。但问题是,后一种情形下的一个诉讼只能解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至于受害人的交易相对方因加害人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仍然需要通过其与加害人之问的直接诉讼来解决。因此,如果法律允许受害人除合同救济外还可选择依侵权法向加害人直接索赔,那么在最终的社会福利状态上没有任何区别(所有事故成本最后都会传递到加害人身上),唯一的变化就是:受害人的索赔诉讼有可能变得异乎寻常地繁琐复杂,给法院和其他当事人带来各种不便(例如,受害人的交易相对方可能必须出庭作证,否则庭审查证无法进行)。基于这一理由,切断受害人向加害人直接索赔的渠道也许是适宜的。更何况在司法实践中,合同条款通常能够对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提供明确清晰的依据,从而大大节省法院确定损害赔偿额的审查成本,这一点是侵权之诉不能相提并论的。
另一个禁止受害人向加害人直接提起侵权之诉的理由或许更有意义,那便是保持法律对债权人清偿不能的风险的合理分配。毫无疑问,如果允许受害人直接向加害人索赔,那么受害人就可以借此规避其合同相对方清偿不能的风险,直接从加害人财产中获得其债权的满足。但如此一来,肯定将削弱受害人通过与交易相对方的合同安排来分散风险的激励。或者也可以这么推论:令加害人直接对受害人负侵权责任,在效果上实际相当于强制前者成为后者实现其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证人,但受害人本来是可以通过自行寻找合适的保证人(包括其现有的合同相对方)缔结保证合同来达到同样效果的。在没有证据证明实施这样一个自愿交易的交易成本的确很高的情况下,显然是通过自愿交易达成的保证合同较有效率,而法律强行安排的“保证合同”较无效率。这也正是德国学者卡纳里斯在分析三人关系不当得利时提出的论点:与第三人相比,合同当事人能够更容易地控制相对方清偿不能的风险,因为其有机会通过自行挑选合同相对方并审查其财产关系来限制风险范围,由此可以更容易地发觉后者资不抵债的财产状况,并通过相应的担保措施等对风险进行及时预防。所以,由合同当事人自行承担其合同相对方的支付不能风险更为公平。当然,的确存在一些能够证明加害人比受害人更有能力避免和分散损害的情况,如产品责任的适用领域,或英美普通法上的诈欺(fraud)等侵权类型。在这些情形中,无疑应当在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外赋予受害人以独立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处就不再赘述。
2.疑义情形:合同排除交易获利机会赔偿时的处理方案
有待进一步讨论的一种情况是:虽然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是因违约引起的,但针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赔偿已经为合同条款所明确排除。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美国的robins dry dock and repair co. v. flint案[49]:船主将船出租,租船人又将船转租,嗣后此船在船坞中修理时因船坞的过失而两周内无法使用。在租船和转租合同的条款中,都已明确规定船舶停留船坞期间租用人有权不付租金,而本案中租船人获得的转租金大大高于其向船主支付的租金。租船人遂直接向船坞,要求赔偿自己因事故而蒙受的转租差价损失。一审和二审法官支持该请求,其中二审法官明确指出加害人不应当仅仅因为存在船舶转租合同而获得利益,他必须赔偿自己给有关当事人造成的全部损害;但终审法官霍姆斯驳回了原告的请求[50]。
针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学术观点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赋予受害人以侵权法救济,否则不承担所有损害后果的加害人就不具有投入注意成本的正确激励[51]。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存在合同关系的背景下,法律是否赋予针对第三方的侵权救济无论如何都不重要,因为当事人总有机会选择通过设计适当的合同条款获得救济[52]。这里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救济条款的交易成本与司法机关因受理有关侵权诉讼而增加的管理成本之间的轻重比较,而这恐怕很难有统一明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某些作者用来支持霍姆斯判决结果的如下理由似乎是有待商榷的:如果加害人必须赔偿其造成的船主和租船人的全部利润损失的话,则会造成如下有失衡平的情形,即在船主和租船人订立合同后,如果市场上的船舶租金上涨超过合同所定额度,那么加害人就必须赔偿租船人的转租差价;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上的船舶租金跌到合同所定额度以下,加害人却无权索取租船人因加害行为而“节约”的租金差额。因此,上述规则将导致作为一个群体的加害人投入过多的注意成本[53]。该理论和毕晓普理论的共同之处——因此也是共同的软肋——在于均将第三方的额外获利视为确定加害人适宜注意水平的必要考量因素。实际上,如果这一思路成立的话,则加害人赔偿“就高不就低”的现象在单一受害人那里同样存在:假设所有权人签订了出卖标的物的合同尚未履行,则在导致标的物灭失的侵权行为发生后,如果标的物市价已经跌破合同价额,则所有权人可以索取相当于合同价额的损害赔偿;反之,如果市场价格已经上涨到高于合同价额,那么所有权人仍然可以获得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赔偿,因为各国法律普遍承认计算赔偿额时应当考虑所有权人将对买受人承担的违约责任,即市价与合同价额的差价(间接损失)[54]。可见,导致上文所谓有失衡平状况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于法律以合同价额作为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55],而非法律承认合同之外的第三方有权就其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相反,如果在确定加害人适宜注意水平的时候放弃考虑第三方额外获利情况,或者说采纳本文主张的“相对社会成本”理论,则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有失衡平的说法,因为被告赔偿水平的高低问题原则上本来就只能在与原告而非其他人的关系上进行考量。
此处或许可以考虑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允许船主向加害人主张相当于租船人转租获利的赔偿。但问题在于:船主往往难以获取有关租船人转租获利情况的准确信息,租船人也没有激励向其提供这一信息;而如果法律进一步赋予租船人要求船主返还其取得的转租获利赔偿金的权利作为补救,那么船主就会丧失向加害人主张相关赔偿的激励。为解决以上问题而在船主和租船人之间达成的任何合同都会涉及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上述替代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并不大。
结语
有关交易获利机会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毕晓普所提出并为诸多权威学者所认可的“真实社会成本”概念并不是一个适宜的分析工具。毕晓普本人的相关分析系统性地低估了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所导致的“真实社会成本”;而一旦“真实社会成本”的概念严格地按照其原初含义适用于分析中,则最终会导致任何种类损害在侵权法上的可赔性都产生疑问。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切实可行的分析工具并非“真实社会成本”,而是“相对社会成本”,或者说原则上严格限制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这一标准下,除了因第三人提供交易条件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和已经存在合同法上救济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之外,追求效率最大化的侵权法规则并没有原则性理由将其他种类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硬性排除在可赔偿范围之外。
注释:
[1]see ralph c. anzivino, “the economic loss doctrine: distinguishing economic loss from non-economic loss”, marquette law review vol. 91(2007-2008), 1086; r. joseph barton,“drowning in a sea of contract: application of the economic loss rule to fraud and negligent misrepresentation claims”,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vol. 41(1999-2000), 1793. 有必要指出的是,各国法往往对产品自伤在侵权法上是否可赔的问题给出大相径庭的答案。美国法上的“集成系统规则”(integrated system rule)不仅否定产品自伤在侵权法上的可赔性,而且进一步否定缺陷产品对其作为组成部分的机械或系统造成的损害在侵权法上的可赔性(anzivino, 1088 ff);而德国法的“同质料性”(stoffgleichheit)规则认为,只要物的瑕疵最初只影响物的一部分,而嗣后造成物之整体的损害,即视为缺少“同质料性”而认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存在(günter christian schwarz/manfred wandt, gesetzliche schuldverhltnisse, 3. anfl., vahlen, 2009, §16 rn. 23)。
[2]波斯纳法官在miller v. united slates steel corp. (902 f. 2d 573, 574, 7th cir. 1990)一案的判词中持相同看法:“(所谓经济损失)最好被称作‘商业损失’,因为人身伤害,尤其是财产损失同样是经济损失……这类损失破坏了可以而且已经被金钱化的价值。”相反看法参见bruce feldthusen, economic loss:“where are we going after junior books?”, the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12(1986-1987), p.246。
[3]这一定义排除了侵害无主物而导致他人交易获利机会受损的情形,因为被侵害物的无主性会导致一些非常棘手而又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的理论争议。
[4]在法律技术层面,英美法是通过确立过失引起的“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的侵权法规则实现这一结果的。这方面英国法的代表性案例为cattle v. stockton waterworks co., l. r. 10 q. b. 453(1875),美国法的代表性案例为robins dry dock and repair co. v. flint, 275 u. s. 303(1927).德国法则通过对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较利”(einsonstiges recht)进行严格解释而达到相同效果,siehe schwarz/wandt, anm. 1, §16 rn. pp. 96-97.
[5]如卡多佐法官就在ultramares corp. v. touche, 255 n. y. 170, 174 n. e. 441(1931)一案中认为,要求因过失而引发合同之外第三人经济损失的会计师承担责任将导致一种“在不确定的期间内针对不确定的群体的数额不确定的责任”see, victor p. goldberg, “accountable accountants: is third-party liability necessary?”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7(1988), p. 297。
[6]有关这两个规则内容的详细介绍,可参见dan b. dobbs/paul t. hayden, torts and compensation, 5th ed., thomson/west, 234 ff.现实中也的确有美国法院利用这两个规则来代替robins案所确立的“经济损失规则”处理有关案件。see ann o'brien,“limited recovery rule as a dam: preventing a flood of lingation for negligent infliction of pure economic los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31(1989), pp. 961-962, 970; victor p. goldberg, “accountable accountants: is third-party liability necessary?”,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7(1988), pp. 298-299.
[7]参见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
[8]1999-2000年的东芝笔记本事件即为典型。参见张珏《产品质量规则应与国际接轨——从东芝笔记本事件看我国市场法律体系的亟待完善》,《中国质量》2000年第3期,第45页。
[9]w. bishop,“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1982), p. 1.
[10]goldberg, "recover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in tort: another look at robins dry dock v. flint",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0(1991),p. 249.
[11]richard a. posner, "common-law economic torts: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48 [2006], pp. 736-737.
[12]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以下。
[13]w. bishop, "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1982],p. 4.
[14]victor p. goldberg, "accountable accountants: is third-party liability necessary?", the journal of legal stadies vol 17 [1988], p. 297。
[15]w. bishop, "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1982],p. 4.
[16]victor p. goldberg, "accountable accountants: is third-party liability necessary?",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7 [1988], p. 297。
[17]波斯纳也认为,如果“代替受害人赚钱”的商店不需要增加人手或者为增购货物支出溢价,则它们的平均销售成本就不会上升,由此在它们的收益增加和受害人的私人损失之间也就不会有显著的缺口。richard a. posner, “common-law economic torts: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48[2006], p.737.
[18]richard a. posner, "common-law economic torts: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48 [2006], 737.
[19]在制度经济学的语境下,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因[交易获利机会的]产权界定不清而引发的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问题。租值消散的基本理论可参见h. scott gordon,“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 vol. 53[1991], 231 ff; 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1974], 53 ff.
[20]萨维尔也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其他企业为捕捉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带来的商机而增加的生产成本将等于受害企业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换言之,此时“真实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完全重合,或者说受害企业所丧失的交易获利机会的租值将耗散到零。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注19。
[21]不过,减少法律执行成本与减少发生在当事人身上的事故成本并非同一个分析层次的目标。参见[美]盖多·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在法律规则对后一种成本的影响得到深入讨论之前,单纯以减少前一种成本作为法律规则的正当化理由似乎是不可取的。
[22][美]盖多·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23]w. bishop, "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1982], 9.
[24]有学者曾分析过企业的生产供应被切断和产出被迫减少两种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变化,认为企业由此遭受的交易获利机会丧失都构成真实社会成本而非转移支付。see mario j. rizzo, “a theory of economic loss in the law of tort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1[1982], 281. 不过该分析所举的例子都涉及有形产品的毁损或不能生产问题,和毕晓普的例子尚有区别。
[25]或者a也可以通过给b安装一块新的窗玻璃而免除金钱赔偿义务,此时购买窗玻璃的人就变成了a,除此之外社会福利状态没有任何变化。
[26]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48页。
[27]戈德堡就是如此认为的。victor p. goldberg, “recovery for economic loss following the exxon“valdez”oil spill”,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3[1994], p. 35.
[28]此处可能有人提出,c在现实中有时会做亏本生意。但如果将之当成具有普遍性的命题,那么就无法想象玻璃生产行业还能存在。还可能有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理想市场条件下,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是相等的。但如果采纳完全竞争的假设,那么也必须承认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本身就构成“真实社会成本”。关于商品价值具有趋向于其生产成本的长期趋势的经典论述,可参见[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9页以下。
[29]法经济学分析认为,无论是加害人有很高的几率逃避承担责任,还是法院在评估实际损失数额方面有很大困难,都可以成为支持惩罚性赔偿的理由。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3页。
[30]有关普通法对这两种情形的区分,参见herbert bernstein,“civil liabilit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under american tort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6[1998], pp. 111-112.
[31]w. bishop,“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1982], 11.
[32]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以下。
[33]当然,考虑到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交易获利机会都极其分散且不确定,可以认为这些交易获利机会给单个受害人造成的预期损失微乎其微,此时法律让损害留在受害人处[或者说让受害人“自我保险”[self-insurance],或许更有利于实现卡拉布雷西所谓的事故法的次级目标,即损害的分散,参见[美]盖多·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但即使在这里,决定性的考虑仍然与损害到底是附随的还是独立存在的无关。
[34][36]w. bishop, "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1982], p. 12.
[35]victor p. goldberg, "recovery for economic loss following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3 [1994], p. 36.
[37]《拿破仑法典》的4人起草小组中有3人是来自法院的实务工作者,而德国民法典第一起草委员会的11名成员中有6人是法官。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216页。
[38]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为“道德主义”[moralism],参见guido calabresi a. 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havard law review vol. 85[1972], pp.1112-1113.
[39]这就是所谓“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相关分析参见[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克劳斯·奥特《民法的经济分析》,江清云、杜涛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以下。
[40]更确切地说,这里所说的“第三人的私人成本变化”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第三人私人收益的增加。在第三人因侵权事故产生私人损失的情况下,第三人可以被视为受害人,从而将其纳入成本——收益分析的作用范围。但如果福利受损的第三人并没有被分析者视为受害人,那么在分析中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顾及他的福利状况。例如,a将b打成重伤,c目睹此事并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如果我们认为c在整个事件中遭受了精神损害,那么就应当在该案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加入c的损害;相反,如果我们不认为c仅仅因为对a的行为感到义愤就成为a的“受害人”[或者说我们根本不认为日常生活中诸如义愤之类的情感活动构成哪怕是轻微的精神损害],那么我们也不能以a的行为“民愤极大”之类理由加重他的责任。
[41]关于法国法的具体情况,see d marshall, “liabilit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negligently caused-french and english law compare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24, 749 ff.
[42]美国学者道布斯同样区分了这几种“经济损失主要类型”,see dan b. dobbs,“an introduction to non-statutory economic loss claim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48[2006], pp. 713-714.
[43]不限于“经济利益”的增加,也包括因利他主义[altruism]而产生的纯粹精神利益。对a而言,只有在其从出价更高的b处所获得的金钱利润不如从“帮助”c中获得的精神满足更有效用时,其才会选择后者而非前者。
[44][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45]这与b和c谁先向a报价无关,后报价者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与先报价者的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差别。
[46]该定理的内容是:只要产权的交易成本足够低,则法律对产权的具体配置方式不会影响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资源最优配置总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自动达成。see r. h.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1960], 1 ff.
[47]权利滥用原则的中心思想是:在特定情形下,c对b蒙受损害具有所谓“非法利益”,比如c向a压价提出交易条件的唯一目的就是让b拿不到合同而破产。“非法利益”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是不能作为收益因素考察的。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以下。此时,法律应采取特别措施[包括公法规制]阻止c的行为,这与相对社会成本理论并不冲突。
[48]bruce feldthusen, "economic loss: where are we going after junior books?", the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12 [1986-1987], pp. 250-251.
[49]robins dry dock and repair co. v. flint, 275 u.s. 303 [1927].
[50][52][53]goldberg,"recover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in tort: another look at robins dry dock v. flint"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0 [1991], pp. 251-257, p. 266, pp. 262-263.
[51]bruce feldthusen, "economic loss: where are we going after junior books?", the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12 [1986-1987], pp. 269-270.
第7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环境损失计量是企业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进行环境损失的实物量化与货币化,并对货币化的环境损失按照会计的要求进行确认与记录的过程。
环境损失计量应以环保部门公布的环境监测数据和企业从环境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环境状态数据为基础,其概念构架包括四类变量: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以这四类变量为基础,逐渐形成三个计算过程:①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②将实物型损失货币化;③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变量和三个计算过程均具有时变性,即:环境损失的发生时间及其计量过程具有时序性与动态性特征,发生空间、表现形式与计量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变化性特征。
二、环境污染计量的四类变量
1.环境污染状态。①以污染物排放量形式表现的变量,如厂区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浓度、污染物产生速度等;②企业权责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三废”的排放量等;③企业权责范围边界的污染物流出量与流入量,如环境责任主体因污染破坏造成的影响程度。污染状态变量决定了企业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变量的大小与权责份额,是环境损失计量的起点。
2.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①急性实物型损失,如有毒液体的排放导致的森林树木毁坏、有毒气体的排放导致的人员伤亡和野生动物灭绝等;②慢性实物型损失,如浓度较低的有害气体和液体,由于长时间的排放导致的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土质改变等;③尚未完全确认的实物型损失,如地表下陷、气候恶化等导致历史文物的毁损和风景资源的破坏等。其中①、②类大多是具有可视性或者是可测性的显形损失,能够而且必须计量;③类是可视性和可测性较低或很低的隐性损失,不容易准确计量。
3.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其在内容上包括伤害型损失、防御型损失等;在价值构成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计算方法上可以采用现实市场价格法;在计量模式上可选用名义货币或一般购买力计量单位,选用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
4.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实物型损失的确认:要求在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经济效益范围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及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可靠性与相关性等标准进行初始确认与再确认。实物型损失的计量:要求在对其确认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按照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准确性、一致性、有用性、可靠性与效益性等标准对引起环境损失的交易或事项进行货币化与分配,它具有间接性、异质性、模糊性、差异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
三、环境污染计量的三个计算过程
1.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实物型损失。污染破坏程度一般是用污染物浓度来反映的。该计算过程的关键是建立污染物浓度与导致各种实物型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的类型取决于环境污染的三种主要形式:①扇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多种影响,使函数表现为叠加型;②链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沿其因果链依次传递,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型;③网式影响,是扇式影响与链式影响的综合,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叠加。
2.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合理货币化是保证环境会计信息可靠的又一重要环节。该计算过程应重点考虑污染可能造成的价值损失,如水污染会造成农田污染损失,农田污染又会加剧水污染的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函数应用十分广泛。
3.货币化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企业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划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等原则的要求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其日常账务可用待摊方法和预提方法进行处理:①待摊方法。在企业发生污染损失金额较大且受害期较长时,按总损失扣除残料价值、可收回的赔偿款后的金额,借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环保赔偿款”、“应交环保税”等科目;分期摊销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②预提方法。逐期预提环境损失支出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预提费用”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预提费用”、“应付环保赔偿款”、“原材料”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还应在期末或至少每年年终,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资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减值计提准备。
四、环境污染计量模型
1.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外部负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负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成本,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负效应。
假定某社区有一大型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该社区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医药费用开支增加,如果将这种费用开支的外部负效应计入企业的总成本,它的生产量就会减少,同时污染也会减少。外部负效应产生一个外部边际成本,产品产量越大,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外部成本也越大。这时,整个社会为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社会边际成本应等于该企业的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因此,该产品的有效率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应由社会边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状况决定。显然,企业不计算外部负效应时将过度生产,从而造成严重的污染。
2.限制污染排放模型——最优排放量分析。环境污染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就是为了保持城市的环境目标值,将排入城市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在环境容量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一般来说,各种污染产生的边际损害是递增的,即污染越多,其边际损害也越大,而社会的边际收益则因污染的排放而递减。污染的最优排放量由其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变化曲线的交点所确定。当污染排放量低于最优排放量时,社会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损害,污染排放就是符合标准的;当污染排放量高于最优排放量时,污染的边际损害大于其边际收益,污染排放则是有害的。
3.环境绿化管理模型——外部正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正效应就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收益或好处。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的收益,使得其他经济主体(厂商或个人)无偿地获得额外的好处,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正效应。
第8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自然灾害 灾害经济与社会 自然灾害波及效应
一、灾情调研
(一)自然灾害综合调查的意义和内容:1.目的和意义。重大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其与环境破坏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许多重大自然灾害常常诱发一连串的其他灾害,形成灾害链。并且其发生突然,不可预测,无法控制,常常具有剧烈的消极或破坏作用。因此,研究重大自然灾害,无论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对于整个社会,都有重大意义。人类要从科学的意义上认识这些灾害的发生、发展以及尽可能减小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已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主题;2.主要研究内容:(1)灾害调查的时间尺度和灾害划分标准;(2) 关于单项灾害研究的内容;(3) 关于灾害总体的综合研究。
(二)研究创新点和社会经济效应:1.创新点:(1)全面总结了我国20世纪的自然灾害态势,研究深度从单纯灾害分布规律研究发展到灾害危险性的波及效应问题和预测性灾害风险研究;(2)对我国减灾工作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系统调研,初步评估了我国现有减灾能力;2.推广应用及社会经济效益。我国在抗灾救灾实践中,不断提高应对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借助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归纳,并构建此种波及效应产生机理的概念模型。此项目关系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减少重大灾害受损程度,降低波及程度,更好的保护大自然。更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
二、灾害经济与灾害社会
(一) 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生存条件的危害。据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中国因地震、洪水、风暴潮等突发性自然灾害共造成330万人死亡;1949-1980年,不同程度的春荒、疾病、非正常死亡等自然灾害造成48万人死亡;1980-2000年,伴随人口持续增长,受灾人口不断增加,全国平均每年受灾人口3.3亿。综合对比本世纪三个时期,基本特点是,自然灾害不仅受自然条件控制,而且与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由于自然灾害的种类不同,强度和频次,各地人口密度,防灾能力不一,所以我国人口受灾程度也有显著的地区差异。
(二)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灾害十分严重。1949-2000年,全国不同年份农作物受灾程度不已。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直接危害――影响农林牧渔等各产业的产品产量和产值,1950――2000年,每年减少粮食10%~20%,减少农林牧渔产值15%~50%;深远影响――减少农民收入,加剧贫困,破坏农业生产资源,削弱农业发展能力。
2.自然灾害对城市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到2000年城市总数达667个。受自然和人为活动的影响,我国城市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广、破坏损失重。
主要灾害为:洪水灾害――受威胁城市546个,占82%
地震灾害――受威胁城市240个,占36%
台风与风暴潮――受威胁城市343个,占52%
地质灾害――受威胁城市139个,占21%
3.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自然灾害造成的紧急损失通常分为直接经济损失(如房屋、农场品、工业产品生活用品等)、间接经济损失(指各种生产活动的经济损失和抗灾、救灾费用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一方面随自然灾害活动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增长。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总体区域上升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大幅度上升,年均达1185亿元。
三、综合减灾
面对中国20世纪严峻的自然灾害形势和减灾需求,为了保障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打破经济、发展、环境、灾害分割管理和分部门、分类减灾的传统模式,在继续加强采取多种工程性与非工程性减灾措施和途径,发挥社会减灾能力的联合作用和综合效应,以消弱致灾因子。切断灾害链,保护受灾体,增强抗灾能力,达到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直接与间接损失和影响的目的。即需要在我国专业减灾系统的基础上,充分落实和实施减灾规划,建设综合减灾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1]马宗晋,高庆华.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原国家科委记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3
[2]苏桂武,高庆华.自然灾害风险的行为主体特性与时间尺度问题.自然灾害学报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3]陈 史培军.自然灾害.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2007
[4]徐德诗.地震应急.北京:地震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第9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单从语义来讲,所谓“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一概念可以指任何社会资源作为自愿交易客体的价值减损——它既包括通常被归入“纯粹经济损失”(pure economic loss)或称“纯财产上损失”(reiner Vermgensschaden)的产品自伤①,也包括因违约而导致的债权不能实现、当事人为进行缔约谈判而支出的花费等各国通常在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等制度中专门处理的问题,甚至还包括毫无疑问属于传统侵权法救济范围的物之灭失和人身伤害②;而从最狭窄的意义上说,该概念则仅指没有任何物或人身遭到直接损害,而仅仅是(潜在)交易过程受到了第三人某种形式的干扰破坏的情形。本文所讨论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既不是最广义上的,也不是最狭义上的。具体来说,它可以用如下方式加以描述:如果加害人并未对受害人而仅仅对第三人实施毁损其物或伤害其人身的行为,但因为受害人将要或已经与他人缔结某种交易关系(或者说有偿法律行为),而使得受害人仍然因加害人的行为而损失从该交易的履行中本来能够获得的利益,那么则存在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③。
在出现上述意义上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情形下,法律是否提供侵权损害赔偿作为救济?迄今为止,英美普通法和德国法给出的答案较为一致:至少在被告系出于过失的情形下,原则上不提供侵权法上的救济④。有关这种处理方式的正当性,传统的通行解释是所谓“诉讼闸门”(floodgate)理论。该理论认为:诸如交易获利机会丧失之类的“纯粹经济损失”,其发生经常具有偶然性,受害人的范围难以确定,损失大小更是难以控制。如果允许这类损失获赔,一方面会引发无数诉讼而使法院不堪重负,导致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将给被告施加过重的负担,由此有失公平⑤。这个说法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首先,现代侵权法中有很多专门用于处理损害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现成规则,如普通法中的近因(proximate cause)规则和可预见性(foreseeability)规则⑥。相比物和人身的直接损害,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或许更经常地表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这似乎很难成为对那些必然和确定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也拒不救济的理由。更何况在现实中,那些并未将交易获利机会丧失和物与人身的损害特别区分对待的法域(如法国)在实践中似乎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诉讼爆炸”现象⑦,这多少让人怀疑赔偿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会鼓励滥诉的命题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其次,“诉讼闸门”理论也没有解释,何以允许交易获利机会的丧失获得侵权损害赔偿就会导致诉讼泛滥和加重被告负担,而允许其他种类的侵权诉讼就不会产生这些结果——毕竟,要论浪费司法资源,恐怕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元钱诉讼”之类小额诉讼。但现代各国法律不但没有排斥这类诉讼的存在,反而在很多情形下通过集团诉讼(class action)等制度安排为其实现提供额外便利。许多受害人本不会为之打官司的小额请求权,加起来往往就是足以导致跨国公司破产的天文数字⑧,但又有谁能由此断言集团诉讼制度给被告施加了“过”重的负担,从而“有失公平”呢?这里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仅仅是:我们凭什么认为,交易获利机会丧失等所谓“纯粹经济损失”相比其他种类的损害更不值得花费司法资源进行救济?我们又凭什么认为,针对这类损害的赔偿给被告造成的负担是“过分”的?⑨
与“诉讼闸门”之类传统视角相比,法经济学的分析似乎在这个领域显示出了更大的解释力。英国学者毕晓普(W. Bishop)在1982年发表于《牛津法律研究杂志》的论文《侵权法中的经济损失》(Economic Loss in Tort)中,首次立基于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侵权赔偿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并得出了支持普通法现行规则的结论。他的思路又为大量法经济学权威学者如戈德堡⑩、波斯纳(11)和萨维尔(12)等所采用。本文将首先对毕晓普的理论进行简要介绍,然后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尝试运用和该理论相同的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交易获利机会在侵权法上的可赔性问题给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处理方案。
二、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与“真实社会成本”:毕晓普理论评析
(一)毕晓普理论的要点
毕晓普在《侵权法中的经济损失》一文中的基本论点可以概括如下:
1.法院在裁判过失案件的过程中,会对案件事实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其目标是计算事故预防措施的成本与收益。这是一种针对“社会”效益的计算,即忽视具体哪些人获得了什么,而只关注总收益是否超过总成本,即使某些人会因此处于更糟糕的境况。在这一计算过程中,重要的是绝不能计入所谓“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因为它虽然是某人的私人成本,同时却又是另一人的私人收益;换言之,由此导致的净社会成本为零(13)。
2.“在范围广泛的案件中”,因侵权行为而导致的私人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仅仅是转移支付,而不产生社会成本。毕晓普为此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假设小镇Mississauga(以下简称M镇)和Etobicoke(以下简称E镇)之间有一条铁路相连。铁路公司正在考虑是否安装特定的防脱轨设备,以消除装载危险化学品的火车脱轨的危险。又假设,这类脱轨事故造成的主要的直接后果就是,发生脱轨事故的小镇的人口会全部疏散到另一个小镇,为期一周。再假设该设备的安装成本为1000万美元,设备寿命为10年,而事故在不安装设备的条件下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每次造成的居民疏散费用为400万美元。显然,如果只考虑这些因素,铁路公司就不应当安装防脱轨设备。
继续假设,每个小镇都有一个屠夫、一个面包师、一个制烛匠和很多其他店主和商人(他们都是风险中立的),每人在每周都有固定的营业额。再假设(据毕晓普本人讲,“这是关键所在”)他们每人都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容纳超出其正常营业额的额外交易量,而同时除原材料之外不会产生其他额外成本。如此一来,发生在M镇的脱轨事故造成的影响就是,M镇商人在一周内无法营业,由此丧失该周本来能获得的账面利润。而同时E镇商人在该周却能使营业 额翻番,由此其该周内的账面利润也会增加一倍。脱轨事故使财富从一群人手中转移到另一群人手中。假设M镇商人有权要求铁路公司,像赔偿前述居民疏散费用一样赔偿其上述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而这一损失的数额为800万美元,那么铁路公司面临的脱轨事故预期总成本就是1200万美元,这一数额大于防脱轨设备的安装成本,因此铁路公司将会决定安装这一设备。但从社会角度看,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社会福利计算得出的净损失仍然是400万美元而非1200万美元。M镇商人遭受的800万美元的利润损失仅仅是一种转移支付,由此导致的社会成本为零(14)。
3.在现实生活中,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经常可能伴随着某些真正的社会成本的产生,但是在其间发挥影响的因素十分复杂,有理由认为法院并不具备在每个个案中作出必需的技术性裁判的能力。即使法院具备这种能力,实施这类裁判也没有意义,除非经济生活中的每个潜在侵权人都能预先察知可能的法院判决对他的影响。因此,我们能够期待的通常只是大体能产生有效率结果并能给判决者提供明确指引的一套规则,而在这一方面,对于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原则不予赔偿、例外承认赔偿的英美普通法规则,至少能够和其他规则一样好地实现效率目标(15)。
(二)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第三方“真实社会成本”的界定
本文认为,毕晓普上述理论的分析思路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问题之一出在毕晓普本人视为“关键”的一个假设,即在导致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事件中,其他未受害的交易主体“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容纳超出其正常营业额的额外交易量,而同时除原材料之外不会产生其他额外成本”上。按照毕晓普的思路,如果在受害人丧失交易获利机会后,其他交易主体可以取得受害人丧失的所有账面利润,而同时又“至少在短期内”不发生“额外成本”,那么可以认为此时的“真实社会成本”为零,没有必要赋予受害人任何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恰恰是如何界定所谓“额外成本”:这类“成本”到底是只包含经营者在M镇人口疏散的一周内实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经营成本(本文称之为“短期成本”),还是同时也包含甚至在此之前很久经营者就为应付类似事故而预先支出或可能支出的成本项目(本文称之为“长期成本”)?毕晓普在文章中并没有正面回答,不过他的态度在对自己所举例子的扩展论述中可见一斑:
例2的事实同例1,唯一不同的是,商人们无法轻易地在短期内扩展服务以容纳突然增加的需求。每一个E镇的屠夫、面包师、制烛匠都必须雇佣额外的帮手,这些帮手只有在为其烦劳获得报酬的时候才肯从事工作。不仅如此,现有的工作人员也感到烦恼和过度劳累,并要求为其烦扰获得额外报酬。对于所有消费者而言,肉、面包和蜡烛的价格都上升了,无论对于平常在E镇采购的人还是对来自M镇的难民都是如此。这些事实描述了短期内真实生产成本的上升……(16)
如此看来,毕晓普所关注的仅仅是那些“代替受害人赚钱”的交易主体在事故所造成的交易获利机会丧失效应所持续的“短期内”直接产生的生产成本。只有在出现这种短期成本的情况下,毕晓普才认为事故产生了“真实社会成本”(17)。如果遵循这种思路,当然就会把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是否产生“社会”成本的问题看成一个纯粹依赖于个案案情的或然性问题:只要能够假设在社会持续期间社会总交易额保持不变,而受害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又没有在账面上直接体现出成本的增加,那么毕晓普就完全不认为存在“真实社会成本”,赋予受害人以赔偿请求权也就只会浪费加害人的防险成本和司法资源,而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效益。但这种思路显然没有考虑那些无法被直接归入某次事故持续期间的盈亏统计的生产成本,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长期成本”。让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假设毕晓普例子中的M镇和E镇除了火车脱轨事故外不可能发生别的足以导致大规模疏散的事故,此时E镇商人有什么理由在一开始就建立和维持一种“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容纳超出其正常营业额的额外交易量”的经营能力呢?比如说,E镇的屠夫为何要在三条冷冻肉生产线本已足够满足“日常”客户对肉类的需求(也即未发生脱轨事故时E镇居民的需求)的情况下购买和维持“至少在短时期内”足够同时为M镇和E镇居民加工肉类的五条生产线?E镇面包师为何要在一台小面包炉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偏偏购买一台“至少在短时期内”足够同时为两镇居民烤面包的大面包炉?E镇饭馆为何要在40平方米的经营空间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客户需求的情况下,用一座“至少在短时期内”足够同时满足两镇居民就餐机会的70平方米的平房充当铺面?不要忘记,这一类额外经营能力的取得和维持,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推论:
1.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中,受害人之外的其他交易主体为满足事故使之落空的那部分需求,不仅需要支出短期成本,而且需要支出长期成本,即必须在事故发生之前预先支出,才能期待其发挥应有效用的成本。相比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更容易被成本——收益分析所忽略;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在侵权法上是否可赔,同样会影响到这类成本的支出。波斯纳曾试图淡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虽然‘额外(交易)能力’听起来像一种浪费,但并不必然如此。多数零售企业在运营的大多数时间里都保留着一点额外能力以应付需求峰值。”(18)这种说法显然无甚说服力,因为“多数零售企业”在运营期间也同样愿意拿出“一点”资金储备以自我消化小型事故带来的损失而不是提起诉讼,但这并不是侵权法在小型事故中拒绝赔偿的理由。这里的根本问题仅仅在于:如果我们将与短期成本变化无关的额外交易能力的存在视为单纯的既成事实,而不作为成本—收益分析中的一个变量处理,那么这种成本—收益分析就无法真正反映毕晓普理论所定义的那种“真实社会成本”的变化情况。
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不可赔的侵权法规则下(换 言之,在法律放弃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进行威慑的情形下),导致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事故将会更频繁地发生,相应地受害人之外的其他交易主体就会选择投入更多成本来建立和维持更多的额外交易能力以捕捉由此带来的商机。如果再假设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几率对每个交易主体都是相等的,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社会所有交易主体都开始针对额外交易能力投入更多的成本,而这有可能大大超过社会节约的加害人防险成本。例如在毕晓普的例子中,假设E镇商人要想容纳10年内因M镇的脱轨事故而送上门来的客源,必须预先支出400万美元的成本来建立和维持额外交易能力(如更多的肉类加工生产线、更大的面包炉、更大的店面,等等),那么此时这一支出对E镇商人来说仍然是划算的,因为400万美元的投入能换来800万美元的回报。同时,由于10年内脱轨事故发生在M镇和E镇的几率是相等的,M镇商人同样也可期待从E镇的事故和疏散中获利,因此他们也会选择增加400万美元的投资。如果再考虑400万美元的疏散费用,那么在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不可赔的侵权法规则之下,社会总共将增加400+400+400=1200万美元的净成本。但与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可赔的侵权法规则相比,这种状态显然是无效率的,因为后一种规则下社会仅会增加1000万美元的净成本,即铁路公司安装防脱轨设备的费用(19)。
2.也许比第一点更重要的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受害人以外的其他交易主体为满足额外需求而支出的总成本,只能视为一种必然而非或然成本。毕晓普一再强调,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中,“真实社会成本”取决于具体个案的复杂情况,而这其实也就是说,其并不必然发生,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如果“真实社会成本”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仅限于短期成本,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将长期成本也考虑进来,就显然不能再如此认为了。实际上,企业在捕捉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带来的额外商机时投入的短期成本或者说流动资本越少,则说明该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固定资本所占比重越大,从而该企业在对固定资本进行投资时就越有可能对(至少是那些较为常规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作出反应;反之,如果企业在投资于固定资本时对商机变化问题很少甚或根本不考虑,则只能说明该企业的经营调整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控制流动资本而实现,从而甚至是那些不太常规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也很可能会导致该企业短期成本投入的相应增加:因此,社会中特定类型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在发生水平上的任何系统性变化,都或迟或早会导致所谓“真实社会成本”(即企业为捕捉额外交易机会而支出的总成本)的相应变化,不可能存在单纯体现为转移支付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换言之,毕晓普过分强调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的转移支付性质,是因为其一开始就片面低估了市场主体因捕捉交易获利机会而诱发的总成本(20)。
当然,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毕晓普所支持的原则上否定交易获利机会可赔性的侵权法规则一定错误——除开高昂的法律执行成本之外(21),加害人避免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的努力显然也不会是无成本的。如果采纳原则上肯定交易获利机会可赔性的侵权法规则,这些成本都将成为现实。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分困难的抉择:到底是以增加加害人防险成本的支出为代价,鼓励受害人之外的其他交易主体削减交易机会捕捉成本(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还是以增加交易机会捕捉成本的支出为代价,鼓励加害人削减防险成本呢?无论如何,我们没法先验地断定后一种方案是更佳选择。毕竟,如上文分析所显示的,交易机会捕捉成本完全有可能高于防险成本。当然,理论上最理想的法律规则是能够使两种成本之和最小化的规则(22),但这里的问题是,法院在现实中几乎完全不可能观察到交易机会捕捉成本的变化情况——单是确定因事故而转移的商机到底落到了哪些交易主体头上,就已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此处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对于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侵权法无论是全部赔偿、部分赔偿还是全部不赔偿,都无法保证削减毕晓普理论作为分析出发点的那种“真实社会成本”。
(三)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对受害人成本支出的影响
毕晓普理论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低估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受害人可能改变其成本支出状况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毕晓普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明确承认“最优结果”,即加害人和受害人都不因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而支出任何成本的状态“在受害人具有避免事故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达到”(23),因为受害人在其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不能获赔的情形下,有可能转向自行支出成本以求减少自己的私人损失。但本文认为仅仅承认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受害人是否具有“避免事故”的可能性,而在于其是否具有“避免事故给自己带来损害”的可能性。这两者的根本差别很容易理解:化工厂附近的某个住户无法独自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工厂有毒物质的泄漏,但却可以或多或少地采取措施来消除或减轻一旦泄漏事故发生时自己将遭受的损失——如购买防毒面具,或者干脆将住处搬到远离化工厂的地方。换言之,如果受害人的目标仅仅是减少自己的私人损失,那么从理论上说,他既可以选择“避免事故”,也可以选择“避免事故给自己带来损害”,前者不可行不代表后者也必然不可行。
由此,我们能得出推论:在法律放弃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进行威慑的情况下,正如第三人捕捉交易获利机会的成本是必然发生的一样,受害人为避免自己遭受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而支出某种形式的成本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尤其从长远观点来看,受害人在理论上总是会对给自己带来损失的事件作出反应以求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由此又可能带来更大的“真实社会成本”。具体到毕晓普的例子来看,假设M镇和E镇的商人都可以通过每年在另一个镇里预先购买在一周时间内以固定价格承租第二个店面的选择权(option)的作法,来保证一旦在自己镇里发生脱轨事故时,可以通过以另一个镇的店面接收本镇老主顾生意的方法来保持企业账面利润持平。假设此类因素将使M镇的商人在10年间总共增加500万美元(每年的选 择权价格加事故发生时实际支付的固定租金)的经营成本,那么他们作为理性人仍然会选择这种低效的经营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可以使其在脱轨事故发生时减少800万美元的账面利润损失。又因为事故发生在M镇和E镇的几率是相等的,因此E镇商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样一来,在侵权法拒绝赔偿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条件下,社会将产生总计500+500+400=1400万美元的净成本,显然高于在法律允许赔偿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时社会将产生的1000万美元防脱轨设备安装成本。
(四)小结
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侵权法拒绝对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给予赔偿,那么无论是受害人本身支出的减损成本,还是受害人之外的交易主体支出的交易机会捕捉成本,都完全有可能超过社会所节约的加害人预防成本。如果再考虑受害人已经支出了减损成本,其他交易主体却仍然徒劳地投入交易机会捕捉成本的可能性(这主要是交易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那么“真实社会成本”无疑会更加巨大。本部分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侵权法否定对交易获利机会的过失损害赔偿能够比肯定这类赔偿节约更多毕晓普所谓的“真实社会成本”(24)。
三、问题的解决:从“真实社会成本”到“相对社会成本”
(一)物之损害赔偿案件中“真实社会成本”的确定
上文已经证明,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侵权法无论是允许还是拒绝受害人针对过失加害人的索赔请求,都无法被证明有助于节省毕晓普所谓的“真实社会成本”。那么,这种困境仅仅存在于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吗?本文的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只要我们坚持损害赔偿范围必须是毕晓普意义上的“真实社会成本”而非受害人的“私人成本”的观念,那么甚至连最普通的物之损害的赔偿问题都没法解释。
1.何谓“物的直接损害”?
假设A因过失打碎了B的一块窗玻璃。各国侵权法对此的处理方案基本相同:第一,A应当赔偿B在当地市场上购买一块新的窗玻璃所需付出的价格(25);第二,如果B能够证明自己因A的行为遭受了“间接”损失(亦即仅仅通过换一块窗玻璃无法得到弥补的损失),则可以一并请求损害赔偿。此处让我们把间接损失的赔偿留待稍后讨论,而首先回答一个问题:此时B的直接损失是什么,与此对应的“社会成本”又是什么?乍看上去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B的直接损失就是“一块窗玻璃”,而社会因事故遭受的损失也是“一块窗玻璃”,B的私人损失与“真实社会成本”完全重合,因此各国侵权法的通行处理方案完全符合“责任范围应当等于损失程度”(26)的法经济学信条。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
(1)从B的角度来看,他的私人损失显然并不是“一块窗玻璃”,而是一块已经安装在自己房屋某扇特定窗户上的玻璃能够给自己带来的效用,如遮风、采光等。至于用来购买新玻璃的款项支出,则是在消除上述损失的过程中发生的“二次损失”,它本身并不是事故直接引起的B的初始私人损失:至于“二次损失”与初始私人损失的大小,严格来说是无法进行“客观”比较的,因为二者根本不同质。只有在B实际支出款项购买新玻璃的情形下,外部观察者才有理由认为“二次损失”小于B的初始私人损失。
(2)新玻璃的价款本身是否属于“真实社会成本”?答案也是否定的。假设B是从玻璃生产商C处购买新玻璃(此处为讨论方便忽略一切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中间商业环节),则B支付的价款成为C的收益,即所谓“转移支付”。此时是否能认为,虽然C获得了支付,但同时丧失了与之等值的一块玻璃,因此这一交易只不过是“重述”(restate)了已经造成的社会损失呢?(27)显然不能。如果C不能从交易中获利(换言之,其制造一块玻璃的账面成本大于或等于其获得的玻璃价款)(28),那么他就不会从事交易;如果他不从事交易,一开始他就不会耗费原材料和人力,将这块玻璃生产出来。因此对于C而言,其因交易而遭受的损失并非“一块玻璃”,而仅仅是生产这块玻璃的账面成本,或者说为生产一块玻璃而消耗的原材料和人力。
(3)上述推论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由于C本身并不是玻璃原料的生产商,因此其必须从玻璃原料生产者D那里购买原料,而D生产原料同样也要耗费他自己的成本……由此类推,整个社会因A的行为而产生的不包含任何私人收益成分的“净”损失归根结底由两部分构成:为生产一块玻璃所必须耗费的纯粹原始状态的自然资源,和为将这些自然资源加工成一块玻璃而需要耗费的人力成本之和。如果说侵权损害赔偿额应当与“真实社会成本”而非任何私人损失等值,那么A对B的赔偿数额就不应当是一块窗玻璃的市场价格,而应当等于上述两项的价值之和。显然,在实践中要证明上述价值的准确甚或大体数目(比如说,窗玻璃市价减去它的各级生产商和销售商各自从中获得的账面利润),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如果因此就认为窗玻璃的市价可以作为毕晓普所谓的“真实社会成本”的一个“粗略”计算标准,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上文分析已经指出,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中,“真实社会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成本的数额“很可能”小于受害人的私人损失的事实足以成为侵权法拒绝赔偿后者的理由,那么就根本无法解释,在窗玻璃案件中,同样是“真实社会成本”小于受害人的私人损失,为何侵权法却坚定支持对后者的赔偿。更何况,如果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举证难度远远大于物之损害的举证难度,那么基于和法经济学支持惩罚性赔偿相同的原理(29),我们更有理由主张,侵权法针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案件的责任强度即使不说应当大于,至少也不能小于针对物之损害案件的责任强度。
2.物之损害导致的间接损失:“附随经济损失”而非“纯粹经济损失”?
以上内容仅仅是针对物的直接损害的赔偿问题的分析。如果同时考虑“间接损失”的赔偿问题,那么毕晓普理论遇到的困难就几乎是无法逾越的——众所周知,“间接损失”的概念是包含交易获利 机会的损失的,如果说独立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本身并非“真实社会成本”,那么附随于物或人身损害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同样也不是“真实社会成本”,为何后者在实在法上独独就可以获赔呢?(30)毕晓普本人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分是“专断的”(31),但同时又试图为之提出三点辩护。在本文看来,这些辩护都是明显难以成立的:
(1)毕晓普认为,程度严重的损害将破坏受害人自身分散损害的机制,而且附随于物理性损害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更可能在受害人一方造成投资激励扭曲(32)。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一方面,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并不见得只附随于“严重”损害的情形,如扎破车行所有的一辆自行车胎对车行来说并非多么严重的损害,但却可能导致该车行损失自行车在特定时间内的出租收益;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基本假设,受害人一方投资激励的扭曲程度并不取决于其遭受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是附随性的还是独立存在的,而仅仅取决于该损失的大小(33)。
(2)毕晓普还提出,法院只选择某些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进行赔偿,可以“粗略地”反映“真实社会成本”只是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一部分的事实(34)。这也就是戈德堡所谓的“错错得正”(Two wrongs might make a right)(35)的思路。这种思路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错错真的可以得正,我们也应当根据相同的逻辑,只选择一部分物之损害进行赔偿(比如,只有年满20岁的男性遭受的物之损害可以获赔),以同样“粗略地”反映“真实社会成本”只是物之损害的一部分的事实。毫无疑问,法律的任何这种尝试都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专断。
(3)毕晓普给出的最后一个辩护是,只赔偿“间接损失”的作法有助于区分有根据的索赔请求和不真实的索赔请求(36)。戈德堡对此作了进一步补充:对于附随于物理性损害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法院可以比较容易地适用减损(mitigation)规则以使赔偿数额逼近“真实社会成本”,但对于独立存在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法院就很难确定该损失被其他交易主体通过代替受害人赚钱而被“替代减损”的程度。对于毕晓普的命题而言,且不论是否能从直接损害的真实性直接推导出间接损害的真实性,单就这个命题本身而论,实际上是个证据法而非实体法的问题,应当适用证据法规则来解决。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限制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戈德堡的命题同样没有说服力:附随性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也有被其他交易主体“替代减损”的可能性,独立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也有受害人自己减损的可能性,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受害人自己减损占据主导地位,而后一种情况下他人“替代减损”就要占据主导地位。
分析到这一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要么认为现代各国侵权法连最简单的物之损害赔偿问题都无法适当应对,要么重新检讨作为毕晓普理论根基的“真实社会成本”概念。后一个选项涉及准确回答侵权法中的“社会成本”到底是指哪些主体所发生的成本,由此对侵权法的成本-收益分析边界进行必要限定的问题。
(二)“相对社会成本”概念的提出
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简要考察一下诉讼程序问题。众所周知,典型的诉讼程序是原被告两造参加的,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和质证、法律观点的攻击与防御,都只会围绕着原被告双方的立场而展开。法官在疑难案件中进行利益衡量,进而创制判例规则时,原则上同样只能基于对原被告双方各自的利益状况作出的判断。超出这个范围,去过多地考虑第三人,尤其是那些并未参加诉讼程序的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很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有关这些第三人利益状况的各种事实由于诉讼程序设计上的局限,更难被法官全面准确地认知,由此作出的法律判断是否正确也就没有保障。如果我们考虑到司法判例和法官经验甚至在成文法的制定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7),那么那种认为法律中的利益衡量可以超越具体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利益分歧,直接以“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为旨归的思想,如果不是根本错误的,至少也是十分可疑的。
实际上,正如我们或许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甚至连“社会福利”的概念本身都不是那么无懈可击的。我们究竟应该把哪些东西看作“社会福利”?对于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包装和“开发”,我们是应当遵循开发商和经济学家的意见将之看成“社会福利”呢,还是应当遵循环保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意见将之当作“社会成本”?如果在某个侵权案件中,加害行为换来的是社会舆论的一致称赞(38),那么是否应当将这种“第三人福利的增长”包括到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去?如果说不应当,那么这种情况和毕晓普例子中的其他交易主体能赚更多钱的情况又有何本质区别?无论如何,在福利经济学至今也无法给出一个具有通用性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条件下(39),试图将原被告双方之外的第三人的福利变化情况无差别地加入成本——收益分析的衡量标准,似乎并不能得出太多有意义的结果,而这一点显然已为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所证明。
从以上分析出发,本文提出的建议是:至少在针对侵权法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范围内,必须放弃将加害人和受害人之外的第三人福利状况的变化作为利益衡量的一个当然参照指标的作法。一个真正有用的“社会成本”概念,应当被定义为加害人和受害人双方(确切地说是两个社会群体)可用金钱更方便地衡量的私人成本之和;至于第三人的私人成本变化情况,原则上不应予以考虑(40)。本文将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成本”称为“相对社会成本”,用以区别于毕晓普意义上的“真实社会成本”。只要某种侵权法规则可以减少“相对社会成本”,就可以认为社会福利得到了(相对的)改善,而并不是非要在衡量了社会中一切想象得到的相关方的福利变化情况之后,才能对某一法律规则的合理性问题给出答案。
毫无疑问,采纳“相对社会成本”的概念意味着对毕晓普理论体系的彻底否定。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和物之损害在 社会福利效果上的所谓“本质区别”现在完全不复存在了。它们都是受害人私人的损失,因此原则上没有理由不认为它们属于侵权法应当关注的“损害”。“相对社会成本”的引入也使得原先我们无法解释的物之损害赔偿的正当性问题迎刃而解:在打碎窗玻璃的案件中,根本不需要考虑某个玻璃生产商或其上游生产者是否会因打碎玻璃而得利的事实,需要关注的仅仅是受害人的“私人”损害,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如果考虑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论点,即无论是物的损害还是人身损害赔偿,某种程度上其实都可以直接视为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赔偿,那么将“纯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单独排除出侵权法救济范围之外,就更没有什么道理了。无论是在物之损害赔偿的情形下,还是在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赔偿的情形下,侵权法赔的都既是私人损失,又是“社会损失”;或者说,由于侵权法的利益衡量框架已经在原则上排除了对其他不相关第三人福利状况的考虑,因此这里的私人损失和社会损失是完全重合的。
(三)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作为毕晓普理论基石的“真实社会成本”概念会导致在传统法经济学框架内根本无法胜任处理的大量问题被引入分析过程,这势必引起整个分析的全面瘫痪。相对可操作的利益衡量标准是“相对社会成本”,即受害人和加害人各自支出的可以较为方便地计算的私人成本之和。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第三人的获利在任何情形下都既不能用来论证某种损害是否具有可赔性,也不能用来论证加害人注意成本的投入水平究竟是过高还是过低。
四、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赔偿的两个限制
虽然上文得出的结论是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原则上没有理由不成为侵权法的赔偿对象(具体到法教义学上,也就是在侵权法可赔损害的范围上采纳“法国式的放任原则”(41)或许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但这当然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是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就一定能得到赔偿。除了因果关系等传统上就被视为控制损害赔偿范围之利器的法律技术工具外,笔者在此重点讨论两种不应获赔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1)因第三人提供交易条件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2)具有违约责任救济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42)。
(一)因他人提供交易条件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不应获赔
尽管引发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除了非人为因素导致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外,人为导致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加害人通过侵害某人(不一定是受害人,甚至也不一定是交易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物)而导致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另一种是加害人通过向某人(同样不一定是受害人的交易相对人,也可能是其他人)提供交易条件,使其不愿意与受害人或其他相关当事人缔结或履行某种交易(有偿法律行为)而引发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前一种情况在上文中已经作了详细分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后一种情况。假设A欲将某物出卖给B,合同尚未订立,C向A提出支付更多的价金买下该物(或者单纯凭借与A的良好关系向其施压,要求A将物赠与给他),A允诺;或者,A虽然仍选择与B达成交易,但这是以B被迫提出更高的价金而实现的。在这类情形下,B无疑损失了与A签订合同本能实现的交易获利机会。对于各国法拒绝赔偿此种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规则,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
1.纳入“受害人”交易相对方利益状况的解释路径
这种解释路径将因第三人提供交易条件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视为侵权法不考虑第三人利益状况之原则的例外。具体而言,从单个案件的静态角度观察,B和C各自从与A的交易中获得的主观效用增加是无法“客观”比较的,因此决定性的考量因素就是A的利益状况。鉴于A无论如何都能从这类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中取得某种形式的福利增加(43),因此,在A与C订立合同的情形下,ABC三人的整体福利水平更有可能高于在A与B订立合同的情形下的水平,而非相反。换言之,法律允许A根据其自身意愿与C而非B达成交易,更有可能达成较佳的社会福利状态。这其实也就是某些法经济学者认为此种情形中B的损失“并不对应于社会损失而是对应于社会盈利”(44)的观点的真实含义。
2.不纳入“受害人”交易相对方利益状况的解释路径
这种解释路径坚持“相对社会成本”理论排除考虑第三人(即A)利益状况的原则,直接在“受害人”B和“加害人”C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具体而言,从同类案件在社会中持续发生的动态角度观察,如果认为A选择C进行交易而“导致”B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那么就必须认为,A如果选择的是B,那么同样“导致”了C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45)。因此,适用赔偿规则的长期效果实际上就是:无论是谁获得与A交易的机会,都有相同几率被判赔。根据科斯定理(46),这一结果是否会对B和C的交易激励发生过份的抑制作用,取决于B和C之间交易成本的大小。(1)如果B和C并不处于相互可以无成本地知晓对方的存在或报价的状态(如竞标过程中),那么无论是B还是C,都很可能由于不能确定对方的存在与否和所要求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而从一开始就选择不与A签订合同。显然,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结果——B和C的潜在交易机会都因为不良的制度设计而损失掉了。(2)如果B和C处于相互可以无成本地知晓对方的存在与报价的状态(如拍卖过程中),那么只能认为B在自愿退出报价竞争时已经达到了己方交易获利机会的压缩极限,继续加价只能使得该交易对于他/她的效用转为负值,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他/她因退出而遭受的任何交易获利机会损失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总之,在C提供交易条件导致B与A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情形下,要么认为强制C对B进行赔偿的规则无法得到实际适用,要么认为其适用结果比不适用还差。
基于以上分析,无论B和C各自提出的交易条件是什么,法律只有任凭A与C达成交易而不作干涉,才能达成较佳的总体福利状态。这一点反映到法教义学上,就表现为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私法主体有权选择与任何其他人以任何条件实施法律行为,法律应当保护行使缔约自由的当事人免于因此承担侵权责任(当然,构成权利滥用的除外(47))。
(二)具有违约责任救济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不应获得侵权法救济
1 .一般分析
在受害人就其遭受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具有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作为救济渠道的情形下,受害人通过违约之诉寻求救济和通过侵权之诉寻求救济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前一种情形下,受害人的合同相对方在赔偿受害人之后,可以将自己支付的赔偿通过违约之诉,或作为“间接损失”通过侵权之诉向加害人索赔,因此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诉讼;在后一种情形下,只有受害人针对加害人的一个侵权之诉。乍看上去,似乎后一种情况更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因此应当允许受害人通过侵权之诉向加害人直接索赔(48)。其实不然。在受害人直接向加害人索赔的情形下,受害人要证明加害人行为与自己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势必要证明:(a)自己与自己的交易相对方存在有效合同关系;(b)该交易相对方与加害人存在有效合同关系且加害人违约,或加害人对该交易相对方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换言之,即使在后一种情形下的一个诉讼中,法院同样要审查在前一种情形下的两个诉讼中各自需要审查的基本事实。但问题是,后一种情形下的一个诉讼只能解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至于受害人的交易相对方因加害人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仍然需要通过其与加害人之问的直接诉讼来解决。因此,如果法律允许受害人除合同救济外还可选择依侵权法向加害人直接索赔,那么在最终的社会福利状态上没有任何区别(所有事故成本最后都会传递到加害人身上),唯一的变化就是:受害人的索赔诉讼有可能变得异乎寻常地繁琐复杂,给法院和其他当事人带来各种不便(例如,受害人的交易相对方可能必须出庭作证,否则庭审查证无法进行)。基于这一理由,切断受害人向加害人直接索赔的渠道也许是适宜的。更何况在司法实践中,合同条款通常能够对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提供明确清晰的依据,从而大大节省法院确定损害赔偿额的审查成本,这一点是侵权之诉不能相提并论的。
另一个禁止受害人向加害人直接提起侵权之诉的理由或许更有意义,那便是保持法律对债权人清偿不能的风险的合理分配。毫无疑问,如果允许受害人直接向加害人索赔,那么受害人就可以借此规避其合同相对方清偿不能的风险,直接从加害人财产中获得其债权的满足。但如此一来,肯定将削弱受害人通过与交易相对方的合同安排来分散风险的激励。或者也可以这么推论:令加害人直接对受害人负侵权责任,在效果上实际相当于强制前者成为后者实现其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证人,但受害人本来是可以通过自行寻找合适的保证人(包括其现有的合同相对方)缔结保证合同来达到同样效果的。在没有证据证明实施这样一个自愿交易的交易成本的确很高的情况下,显然是通过自愿交易达成的保证合同较有效率,而法律强行安排的“保证合同”较无效率。这也正是德国学者卡纳里斯在分析三人关系不当得利时提出的论点:与第三人相比,合同当事人能够更容易地控制相对方清偿不能的风险,因为其有机会通过自行挑选合同相对方并审查其财产关系来限制风险范围,由此可以更容易地发觉后者资不抵债的财产状况,并通过相应的担保措施等对风险进行及时预防。所以,由合同当事人自行承担其合同相对方的支付不能风险更为公平。当然,的确存在一些能够证明加害人比受害人更有能力避免和分散损害的情况,如产品责任的适用领域,或英美普通法上的诈欺(fraud)等侵权类型。在这些情形中,无疑应当在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外赋予受害人以独立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处就不再赘述。
2.疑义情形:合同排除交易获利机会赔偿时的处理方案
有待进一步讨论的一种情况是:虽然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是因违约引起的,但针对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的赔偿已经为合同条款所明确排除。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美国的Robins Dry Dock and Repair Co. v. Flint案(49):船主将船出租,租船人又将船转租,嗣后此船在船坞中修理时因船坞的过失而两周内无法使用。在租船和转租合同的条款中,都已明确规定船舶停留船坞期间租用人有权不付租金,而本案中租船人获得的转租金大大高于其向船主支付的租金。租船人遂直接向船坞起诉,要求赔偿自己因事故而蒙受的转租差价损失。一审和二审法官支持该请求,其中二审法官明确指出加害人不应当仅仅因为存在船舶转租合同而获得利益,他必须赔偿自己给有关当事人造成的全部损害;但终审法官霍姆斯驳回了原告的请求(50)。
针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学术观点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赋予受害人以侵权法救济,否则不承担所有损害后果的加害人就不具有投入注意成本的正确激励(51)。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存在合同关系的背景下,法律是否赋予针对第三方的侵权救济无论如何都不重要,因为当事人总有机会选择通过设计适当的合同条款获得救济(52)。这里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救济条款的交易成本与司法机关因受理有关侵权诉讼而增加的管理成本之间的轻重比较,而这恐怕很难有统一明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某些作者用来支持霍姆斯判决结果的如下理由似乎是有待商榷的:如果加害人必须赔偿其造成的船主和租船人的全部利润损失的话,则会造成如下有失衡平的情形,即在船主和租船人订立合同后,如果市场上的船舶租金上涨超过合同所定额度,那么加害人就必须赔偿租船人的转租差价;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上的船舶租金跌到合同所定额度以下,加害人却无权索取租船人因加害行为而“节约”的租金差额。因此,上述规则将导致作为一个群体的加害人投入过多的注意成本(53)。该理论和毕晓普理论的共同之处——因此也是共同的软肋——在于均将第三方的额外获利视为确定加害人适宜注意水平的必要考量因素。实际上,如果这一思路成立的话,则加害人赔偿“就高不就低”的现象在单一受害人那里同样存在:假设所有权人签订了出卖标的物的合同尚未履行,则在导致标的物灭失的侵权行为发生后,如果标的物市价已经跌破合同价额,则所有权人可以索取相当于合同价额的损害赔偿;反之,如果市场价格已经上涨到高于合同价额,那么所有权人仍然可以获得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赔偿,因为各国法律普遍承认计算赔偿额时应当考虑所有权人将对买受人承担的违约责任,即市价与合同价额的差价(间接损失)(54)。可见,导致上文所谓有失衡平状况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于法律以合同价 额作为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55),而非法律承认合同之外的第三方有权就其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相反,如果在确定加害人适宜注意水平的时候放弃考虑第三方额外获利情况,或者说采纳本文主张的“相对社会成本”理论,则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有失衡平的说法,因为被告赔偿水平的高低问题原则上本来就只能在与原告而非其他人的关系上进行考量。
此处或许可以考虑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允许船主向加害人主张相当于租船人转租获利的赔偿。但问题在于:船主往往难以获取有关租船人转租获利情况的准确信息,租船人也没有激励向其提供这一信息;而如果法律进一步赋予租船人要求船主返还其取得的转租获利赔偿金的权利作为补救,那么船主就会丧失向加害人主张相关赔偿的激励。为解决以上问题而在船主和租船人之间达成的任何合同都会涉及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上述替代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并不大。
结语
有关交易获利机会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毕晓普所提出并为诸多权威学者所认可的“真实社会成本”概念并不是一个适宜的分析工具。毕晓普本人的相关分析系统性地低估了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所导致的“真实社会成本”;而一旦“真实社会成本”的概念严格地按照其原初含义适用于分析中,则最终会导致任何种类损害在侵权法上的可赔性都产生疑问。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切实可行的分析工具并非“真实社会成本”,而是“相对社会成本”,或者说原则上严格限制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这一标准下,除了因第三人提供交易条件而发生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和已经存在合同法上救济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之外,追求效率最大化的侵权法规则并没有原则性理由将其他种类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硬性排除在可赔偿范围之外。
收稿日期:2011-12-01
注释:
①See Ralph C. Anzivino, “The Economic Loss Doctrine: Distinguishing Economic Loss from Non-Economic Loss”, Marquette Law Review Vol. 91(2007-2008), 1086; R. Joseph Barton,“Drowning in a Sea of Contract: Application of the Economic Loss Rule to Fraud and Negligent Misrepresentation Claims”,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Vol. 41(1999-2000), 1793. 有必要指出的是,各国法往往对产品自伤在侵权法上是否可赔的问题给出大相径庭的答案。美国法上的“集成系统规则”(integrated system rule)不仅否定产品自伤在侵权法上的可赔性,而且进一步否定缺陷产品对其作为组成部分的机械或系统造成的损害在侵权法上的可赔性(Anzivino, 1088 ff);而德国法的“同质料性”(Stoffgleichheit)规则认为,只要物的瑕疵最初只影响物的一部分,而嗣后造成物之整体的损害,即视为缺少“同质料性”而认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存在(Günter Christian Schwarz/Manfred Wandt, Gesetzliche Schuldverhltnisse, 3. Anfl., Vahlen, 2009, §16 Rn. 23)。
②波斯纳法官在Miller v. United Slates Steel Corp. (902 F. 2d 573, 574, 7th Cir. 1990)一案的判词中持相同看法:“(所谓经济损失)最好被称作‘商业损失’,因为人身伤害,尤其是财产损失同样是经济损失……这类损失破坏了可以而且已经被金钱化的价值。”相反看法参见Bruce Feldthusen, Economic Loss:“Where Are We Going After Junior Books?”, The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12(1986-1987), p.246。
③这一定义排除了侵害无主物而导致他人交易获利机会受损的情形,因为被侵害物的无主性会导致一些非常棘手而又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的理论争议。
④在法律技术层面,英美法是通过确立过失引起的“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的侵权法规则实现这一结果的。这方面英国法的代表性案例为Cattle v. Stockton Waterworks Co., L. R. 10 Q. B. 453(1875),美国法的代表性案例为Robins Dry Dock and Repair Co. v. Flint, 275 U. S. 303(1927).德国法则通过对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较利”(einsonstiges Recht)进行严格解释而达到相同效果,siehe Schwarz/Wandt, Anm. 1, §16 Rn. pp. 96-97.
⑤如卡多佐法官就在Ultramares Corp. v. Touche, 255 N. Y. 170, 174 N. E. 441(1931)一案中认为,要求因过失而引发合同之外第三人经济损失的会计师承担责任将导致一种“在不确定的期间内针对不确定的群体的数额不确定的责任”See, Victor P. Goldberg, “Accountable Accountants: Is Third-Party Liability Necessary?”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7(1988), p. 297。
⑥有关这两个规则内容的详细介绍,可参见Dan B. Dobbs/Paul T. Hayden, Torts and Compensation, 5th Ed., Thomson/West, 234 ff.现实中也的确有美国法院利用这两个规则来代替Robins案所确立的“经济损失规则”处理有关案件。See Ann O'Brien,“Limited Recovery Rule as a Dam: PreVenting a Flood of Lingation for Negligent Infliction of Pure Economic Los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31(1989), pp. 961-962, 970; Victor P. Goldberg, “Accountable Accountants: Is Third-Party Liability Necessary?”,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7(1988), pp. 298-299.
⑦参见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
⑧1999-2000年的东芝笔记本事件即为典型。参见张珏《产品质量规则应与国际接轨——从东芝笔记本事件看我国市场法律体系的亟待完善》,《中国质量》2000年第3期,第45页。
⑨W. Bishop,“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1982), p. 1.
⑩Goldberg, "Recover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in Tort: Another Look at Robins Dry Dock v. Flint",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0(1991),p. 249.
(11)Richard A. Posner, "Common-Law Economic Torts: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48 (20 06), pp. 736-737.
(12)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以下。
(13)W. Bishop, "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1982),p. 4.
(14)Victor P. Goldberg, "Accountable Accountants: Is Third-Party Liability Necessary?", The Journal of Legal Stadies Vol 17 (1988), p. 297。
(15)W. Bishop, "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1982),p. 4.
(16)Victor P. Goldberg, "Accountable Accountants: Is Third-Party Liability Necessary?",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7 (1988), p. 297。
(17)波斯纳也认为,如果“代替受害人赚钱”的商店不需要增加人手或者为增购货物支出溢价,则它们的平均销售成本就不会上升,由此在它们的收益增加和受害人的私人损失之间也就不会有显著的缺口。Richard A. Posner, “Common-Law Economic Torts: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48(2006), p.737.
(18)Richard A. Posner, "Common-Law Economic Torts: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48 (2006), 737.
(19)在制度经济学的语境下,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因(交易获利机会的)产权界定不清而引发的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问题。租值消散的基本理论可参见H. Scott Gordon,“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 Vol. 53(1991), 231 ff; 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1974), 53 ff.
(20)萨维尔也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其他企业为捕捉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事件带来的商机而增加的生产成本将等于受害企业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换言之,此时“真实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完全重合,或者说受害企业所丧失的交易获利机会的租值将耗散到零。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注19。
(21)不过,减少法律执行成本与减少发生在当事人身上的事故成本并非同一个分析层次的目标。参见[美]盖多·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在法律规则对后一种成本的影响得到深入讨论之前,单纯以减少前一种成本作为法律规则的正当化理由似乎是不可取的。
(22)[美]盖多·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23)W. Bishop, "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1982), 9.
(24)有学者曾分析过企业的生产供应被切断和产出被迫减少两种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变化,认为企业由此遭受的交易获利机会丧失都构成真实社会成本而非转移支付。See Mario J. Rizzo, “A Theory of Economic Loss in the Law of Tort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1(1982), 281. 不过该分析所举的例子都涉及有形产品的毁损或不能生产问题,和毕晓普的例子尚有区别。
(25)或者A也可以通过给B安装一块新的窗玻璃而免除金钱赔偿义务,此时购买窗玻璃的人就变成了A,除此之外社会福利状态没有任何变化。
(26)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48页。
(27)戈德堡就是如此认为的。Victor P. Goldberg, “Recovery for Economic Loss following the Exxon“Valdez”Oil Spill”,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3(1994), p. 35.
(28)此处可能有人提出,C在现实中有时会做亏本生意。但如果将之当成具有普遍性的命题,那么就无法想象玻璃生产行业还能存在。还可能有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理想市场条件下,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是相等的。但如果采纳完全竞争的假设,那么也必须承认交易获利机会的损失本身就构成“真实社会成本”。关于商品价值具有趋向于其生产成本的长期趋势的经典论述,可参见[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9页以下。
(29)法经济学分析认为,无论是加害人有很高的几率逃避承担责任,还是法院在评估实际损失数额方面有很大困难,都可以成为支持惩罚性赔偿的理由。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3页。
(30)有关普通法对这两种情形的区分,参见Herbert Bernstein,“Civil Liabilit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Under American Tort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6(1998), pp. 111-112.
(31)W. Bishop,“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1982), 11.
(32)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以下。
(33)当然,考虑到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交易获利机会都极其分散且不确定,可以认为这些交易获利机会给单个受害人造成的预期损失微乎其微,此时法律让损害留在受害人处(或者说让受害人“自我保险”(self-insurance),或许更有利于实现卡拉布雷西所谓的事故法的次级目标,即损害的分散,参见[美]盖多·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但即使在这里,决定性的考虑仍然与损害到底是附随的还是独立存在的无关。
(34)(36)W. Bishop, "Economic Loss in Tort",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 (1982), p. 12.
(35)Victor P. Goldberg, "Recovery for Economic Loss following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3 (1994), p. 36.
(37)《拿破仑法典》的4人起草小组中有3人是来自法院的实务工作者,而德国民法典第一起草委员会的11名成员中有6人是法官。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 3年版,第128、216页。
(38)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为“道德主义”(moralism),参见Guido Calabresi A. 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Havard Law Review Vol. 85(1972), pp.1112-1113.
(39)这就是所谓“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相关分析参见[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克劳斯·奥特《民法的经济分析》,江清云、杜涛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以下。
(40)更确切地说,这里所说的“第三人的私人成本变化”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第三人私人收益的增加。在第三人因侵权事故产生私人损失的情况下,第三人可以被视为受害人,从而将其纳入成本——收益分析的作用范围。但如果福利受损的第三人并没有被分析者视为受害人,那么在分析中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顾及他的福利状况。例如,A将B打成重伤,C目睹此事并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如果我们认为C在整个事件中遭受了精神损害,那么就应当在该案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加入C的损害;相反,如果我们不认为C仅仅因为对A的行为感到义愤就成为A的“受害人”(或者说我们根本不认为日常生活中诸如义愤之类的情感活动构成哪怕是轻微的精神损害),那么我们也不能以A的行为“民愤极大”之类理由加重他的责任。
(41)关于法国法的具体情况,see D Marshall, “Liabilit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Negligently Caused-French and English Law Compare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24, 749 ff.
(42)美国学者道布斯同样区分了这几种“经济损失主要类型”,see Dan B. Dobbs,“An Introduction to Non-Statutory Economic Loss Claims”, Arizona Law Review Vol. 48(2006), pp. 713-714.
(43)不限于“经济利益”的增加,也包括因利他主义(altruism)而产生的纯粹精神利益。对A而言,只有在其从出价更高的B处所获得的金钱利润不如从“帮助”C中获得的精神满足更有效用时,其才会选择后者而非前者。
(44)[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45)这与B和C谁先向A报价无关,后报价者的交易获利机会损失与先报价者的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差别。
(46)该定理的内容是:只要产权的交易成本足够低,则法律对产权的具体配置方式不会影响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资源最优配置总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自动达成。See R. H.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1960), 1 ff.
(47)权利滥用原则的中心思想是:在特定情形下,C对B蒙受损害具有所谓“非法利益”,比如C向A压价提出交易条件的唯一目的就是让B拿不到合同而破产。“非法利益”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是不能作为收益因素考察的。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以下。此时,法律应采取特别措施(包括公法规制)阻止C的行为,这与相对社会成本理论并不冲突。
(48)Bruce Feldthusen, "Economic Loss: Where Are We Going After Junior Books?", The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12 (1986-1987), pp. 250-251.
(49)Robins Dry Dock and Repair Co. v. Flint, 275 U.S. 303 (1927).
(50)(52)(53)Goldberg,"Recover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in Tort: Another Look at Robins Dry Dock v. Flint"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0 (1991), pp. 251-257, p. 266, pp. 262-263.
- 上一篇:美术教育摘要范文
- 下一篇:骨折后的康复护理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