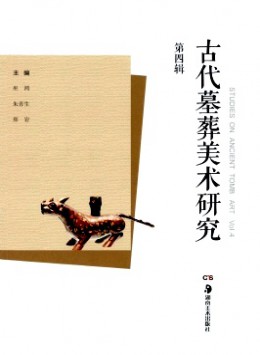古代文学传记精选(九篇)

第1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 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 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Austronesian 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 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檮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 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複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繫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 见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第2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诗经》;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今古学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70-04
在现代《诗经》研究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划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它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等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这种理论框架对于认识《毛诗》与三家诗的区别很有意义,但是对于认识它们的相同之处和进一步深化《诗经》研究却有着消极影响。
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古文与今文本指书写文字的不同,古文经就是用古文字书写的经书,是先秦旧典;今文经是用今文字书写的经书,是西汉初年用当时文字隶书所改写的经书。这两对概念在西汉初年就已形成,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作为两个学派的概念是在清朝后期形成的。大致滥觞于清初,发明于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许多学者鼓吹这种观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一些现代学者的继承和阐述,逐渐代替了传统经学研究中“汉学”、“宋学”分野的基本格局,成为研究古代经学的主要理论认识框架。
关于清末学者论述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别,周予同先生曾经归纳为13个方面,总的来说,“他们的不同,不仅在于所书写的文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书籍有不同,书籍中的意义有大不同;因之,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对于古代制度以及人物批评各各不同,而且对于经书中的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观念”。书籍不同,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和制度不同成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个学派差异的主要内容。两汉博士学官及其所传授的经书是今文学派的代表,而民间传授的《毛诗》、《周官》、《左传》、古文《尚书》则为古文学派。从时间上来看,前汉主今文说,讲微言大义;后汉主古文说,详在章句训诂。刘歆是由今文学派向古文学派转变的关键性人物。至于两派的关系,它们互相争斗,势同水火。关于传授学统,今文学派“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渊源清晰准确,所以非常可靠。清末学者很多像廖平、皮锡瑞一样,认为他们发现了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流派的划分及其斗争的秘密,为经学研究开辟了康庄大道。但我们细读有关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流派划分的著作,发现他们对于流派的划分和论述却充满了矛盾。尽管这样,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划分作为一种认识理论框架却已深入到我们现代的学术研究中。
这种认识理论框架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汉代经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不过它过度强调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对立性和斗争性,而忽视了其复杂关系。这与汉代经学学术研究的实际状况有所偏差,对我们现代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消极影响。钱穆、徐复观、李学勤等先生先后指出过这种消极影响,但这些先生的观点在《诗经》研究中反响并不大,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壁垒对立的理论框架的影响依然很深。
二、今古文与四家诗
虽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主要内涵在于经义解说的不同,但今文、古文字体的差异却是其理论的基础要素。我们先来看一下经学传授的文字问题。
在西汉初的经学传授中,无论是学官的还是流传民间的文本都存在着由古文或小篆改为今文隶书的情况,此改写过程在文帝、景帝时已结束。王国维说:“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于是鲁国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逸礼》、《书》等,河间献王也得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由于当时经传全部改写为今文,所以《史记》、《汉书》等文献特别注明这些书籍为“古文”。“古文”之名于此产生。王氏的这种推测合情合理。对于《诗经》的传授来说也是如此,在汉景帝时期,不仅三家诗,就是《毛诗》,其文本应该都已经改写为今文隶书。《史记》记载,孝文帝时朝廷听说伏生能治《尚书》,使晁错前往学习;郑玄《尚书传序》说伏生传授《尚书》的一个困难就是“重以篆、隶之殊”,伏生是秦博士,可以看出,秦代博士经书用的是秦统一的文字小篆书写,伏生在教授时改写为隶书。当然,秦国统一文字后其文献用小篆来写,当时还存在着大量的东方六国的古文文献,即使在焚书之后也有许多古文献遗留下来。汉初经学传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小篆或古文改写为隶书。这对于《诗经》、来说也是如此。对于三家诗来说,它们最晚在立为学官后改写为隶书。
对于《毛诗》来说,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域中,《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那么其书写文字就是古文。文献中对于《毛诗》是古文的说法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汉书・艺文志》中,《毛诗》很明显已是今文字书写的了。《汉书・艺文志》的书写体例是先列经书,古文经书在前,且注明“古文”;今文经书在后,因为当时书写字体为隶书.所以不着“今文”二字,经书的传记等研究著作罗列在后。《毛诗》在“诗类”目录中列在最后。“《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不注明古文,从《艺文志》的书写体例上来看,它已不是古文。王国维、徐复观先生对此都有论述。王国维指出:“《河间献王传》列举其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后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并称,其所有并称者,当以三者同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惟卢子干言‘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下列举《毛诗》、《左传》、《周礼》三目。盖因《周礼》、《左传》而牵连及之,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贯长卿之时,已不复有古文本矣。”河间献王为汉景帝第三子,毛公为其博士,《毛诗》最迟在此时改写为今文。这一派的《诗》为什么称作《毛诗》应与小毛公毛苌有关,与大毛公毛亨无关。《汉书》说:“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班固此文就是交待《毛诗》师法由赵人毛公确立,但是班固并没有说毛公的名字。郑玄在《笺》中以《故训传》为毛苌作,在《诗谱》中又以毛亨作《故训传》,关于《故训传》的作者郑玄不能确定,而且毛公成了大毛公和小毛公两个人。后来。陆机和徐整继承这种观点,认为毛公有两个人,鲁人大毛公亨和赵人小毛公苌,且都认为毛亨作《故训传》教授毛苌。《鲁诗》、《齐诗》、《韩诗》三家诗的命名都跟博士学官、传授和对《诗》注解即师法的确立有关。我们认为,《毛诗》的形成与得名应与三家诗相似,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虽不是汉庭学官,但他是诸侯学官,是《毛诗》师法的确立者,《毛诗》之“毛”即指毛苌,《故训传》也应为毛苌所作。
我们说,《诗经》在文帝、景帝时已改写为今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那就是1977年安徽省阜阳市出土的汉简《诗经》,埋藏时间为文帝十五年,其文字为隶书。文字、篇章顺序与《毛诗》和三家诗都有所不同,生、韩自强两先生认为它应该是没有被《艺文志》收录而流传于民间的一家,李学勤先生推测可能是楚国地域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汉文帝时期,民间的《诗经》都已用隶书书写,学官中的《诗经》更可想而知了。
西汉末年,古文在经典的意义上由泛指六艺为基础的儒家经典文献变成专门指代孔壁之书,即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出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和《孝经》等,尤指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和《礼记》都没有立为学官,由于《左传》、《周官》、《毛诗》等经也没有立为学官,人们往往把它们看作同一类经典。
三、今古学与四家诗
汉代经学除了今、古文问题,还有今学、古学的问题,两者关系复杂。今古学是在西汉后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施行之后,经学经过长期发展后而产生的两种观念。
《史记》中的“古文”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指文字字体;二指一种学统或流派;第三,“古文”既指一种学术传统,也指经典著作。这一经典系统包括《诗》、《书》、《春秋》等经书及其相关文献,是周朝礼乐制度的体现,也包括记载孔子弟子的文献,作为史料,它也是最可靠的。西汉初期,“古文”作为学派意义是与百家言相对的,当时没有什么“今文”学派,他们不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到了东汉古文与今文在学派意义上作为一对对立概念只局限于《尚书》研究。
两汉之际,经学研究中产生了今学与古学两种观念,并成为东汉经学研究的重要分野。古学与今学的内涵可以从多方面来看。从经典上来看,古学的经典包括古文《尚书》、《左传》、《毛诗》、《周礼》等,今学的经典包括今文《尚书》、《公羊传》、《韩诗》、《鲁诗》、《齐诗》、大小戴《礼》等。这在许慎《五经异义》中是非常明显的,前者多冠以“古”字,后者多冠以“今”字,以示区别。《后汉书》中,古学的概念也与这些经典联系在一起,今学经典全是博士学官所授,而古学则为民间传授经典,所以今学与古学可以指代博士学官与民间的经学研究。由于古学和今学的经典不一样,所以因经典的解说也就自然形成了两种学统,即博士学官派和民间经学派。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古学设立博士学官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不断斗争,但在学问上并不是壁垒森严,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借鉴,互相阐发。东汉时期,无论是今学家还是古学家,对五经都有深入研究,甚至可以说兼收并蓄。今学和古学的差异还表现在研究方法和风格上。今学以章句学为代表,文辞细碎繁冗,涉及谶纬,讲究家法;古学则注重古文字研究,侧重于从文字训诂,追求古义,讲究圆通。钱穆先生把章句和谶纬作为今学的两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抓住了要害。当然他们在研究方法和风格上的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他们也是相互影响和互相渗透的。今古学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复杂。今古学的区别正是清末学者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形成的基础,不过这一理论框架过度强调了今古学的区别性和斗争性,而忽视了其共同性。
东汉的《诗经》研究当然也是伴随着今古学观念的形成而展开的。大致说来,齐鲁韩三家诗属于今学,都是博士学官,是国家开设的课程;《毛诗》属于古学,不是博士学官,是民间经学的内容。这并不意味着,博士学官不学习《毛诗》,民间《毛诗》传授不学习三家诗。在研究方法和形式上,《毛诗》有训诂、有传,在传承中基本按照这种文体发展,而齐诗、鲁诗、韩诗在训诂、传的基础上发展出章句。《汉书・艺文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后汉书》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今学三家诗有章句之学。章句的形成与博士学官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毛诗》的传授遵循着早期“师法”,而齐、鲁、韩三家诗并没有严格地遵循“师法”。这与皮锡瑞所说的“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的结论有所不同。《汉书》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鲁诗师法形成之初只有训诂,没有传;齐诗、韩诗都有传,从《艺文志》所收书目来看,齐诗、韩诗还有诂、说、记等。西汉末年,它们都有章句,并形成不同学派家法,即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方法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的内容。如果说师法主要是解说内容方面的,那么同一师法形成了不同的家学,这就意味着在解说内容方面出现了差异,如果要严格遵照师法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毛诗》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它在小毛公形成师法之初只有训诂和传,后汉时仍然遵循这一传统。这实际上也就是古学的一个内涵。即在研究方法和风格上遵循着当初的师法。
第3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 300 万年的历史; 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 17 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 4000 年左右。从 300 万年前到 4000 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 开( 夏后启) 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 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 年,河南舞陽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25 支骨笛,据碳 14 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 8000-9000 年; 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 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
二、 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 20世纪 20 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 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 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鼍也、《诗经大雅》: 鼍鼓逢逢,蒙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3015 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三、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
第4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大禹;冉駹;羌族;巫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0033-6
汉唐文献记载大禹生于汶山郡广柔县石纽山,其地即今岷江上游汶川县域北部羌族聚居区的绵厩镇石纽山。古史传说记载大禹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暨最高巫师,后世道教巫师端公和羌族巫师释比皆奉大禹为始祖。岷江上游地区在先秦时期为古蜀人支系建立的冉駹(尨)古国所在地,冉駹的巫师在商代为商王重要的巫师贞人。今日聚居于岷江上游的羌族与古冉駹人具有重要渊源关系,并且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古老的巫文化。笔者认为,大禹、冉駹与羌族在同一地区在巫文化上呈现的重合现象,反映了三者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羌族的巫文化是在岷江上游原生并传承了四千多年的古老巫文化活化石。
一、大禹与岷江上游的巫文化
大禹是古史传说记载中黄帝与嫘祖的后裔、上古治水英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奠基人。大禹率领民众治水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不畏艰难和身先士卒的勇敢精神及其对建立国家和凝聚民族的伟大贡献,成为后世敬仰、历代颂扬的人文典范,被尊为功高盖三皇的伟大“圣王”。
关于大禹的出身地,虽然在西汉中期以前的文献中原本无明确记载,但皆公认大禹生于西羌,故《史记·夏本纪》等多篇西汉著述皆记载:“禹生于西羌”。称大禹生于汶山郡石纽刳儿坪始见于西汉扬雄收集蜀中典故所著《蜀王本纪》:“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三国志·蜀书》载蜀人秦宓称:“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三国蜀人谯周作《蜀本纪》亦记载:“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2004年在三峡库区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东汉《景云碑》,记述大禹后裔伯沇(魏唐鹏先生考证即夏王“伯杼”)循大禹之迹中兴夏朝,有:“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语句,这里的“汶川”为岷江上游别称(汉代称岷江上游为“江源”、“汶江”、“汶川”、“汶水”,非指后来才有的汶川县。今汶川县治地在汉武帝时为汶山郡治绵厩县,西晋更绵虒县名为汶山县,南朝梁时因汶山县西临汶川始更县名为汶川),证明两汉三国时期人们所说的大禹出生地石纽在岷江上游。因此,禹生石纽很可能为蜀中广泛流传的古老传说。此后,魏晋时期《帝王世纪》记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也。”东晋《华阳国志》记载:“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不敢追,云畏神禹。”唐代《括地志》记载:“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元和郡县志》汶川县条下亦记载:“广柔废县,在县西七十二里。汉县也,属蜀郡。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刳儿畔。”唐代汶川县治地在今汶川县治威州镇姜维城台地上,西汉为汶山郡治地,唐末迁维州于此,宋代置威州,至今仍残存部份唐宋夯土城垣残段。唐末五代大学者杜光庭《青城记》称:“禹生于石纽,起于龙冢。龙冢者,江源岷山也。有禹庙镇山上,庙坪八十亩。”所言江源岷山石纽亦为今汶川石纽山。直至北宋欧阳修著《新唐书·地理志》,始出现大禹生石泉县(今北川县)石纽山的说法,至南宋方出现以石泉县为汉广柔县地说法。
古史文献记载大禹治水功成后于会稽山(涂山)会盟诸侯计功。据《景云碑》记述的:“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语句,大禹曾有“汶川之会”的重大事件。按“会”的本意指盟会,《周礼·春官·大祝》记载:“四日会”,郑玄注称:“会,谓会同盟誓之辞”,又引郑司农言:“会,王官之伯命事于会”。因此,“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当指大禹在其故里石纽与诸侯进行盟誓的会盟事件。据《景云碑》前后文意分析,此四句当指伯沇(伯杼)循大禹“汶川之会”故事中兴夏王朝,从而表明大禹的“汶川之会”当为导致夏王朝始兴的重大盟会事件。结合大禹治水于“岷山导江”并最终因治水功绩而奠定夏王朝基业的历史记载,“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就应指大禹治水开始时曾在家乡石纽会盟诸侯举行盟誓,并由治理长江江源汶川(古人以岷江上游为长江江源)开始治水工程,这与治水功成而于长江下游的会稽之山会盟诸侯计功正好首尾相应。由此,汶川石纽山既是大禹故里,又是大禹治水会盟誓师的“汶川之会”所在地,在大禹治水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5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策略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随着历史和汉字的发展演变,汉字不仅记录和语言,也记录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繁体字在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记录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语言文字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而现阶段,我国大陆地区通用的文字是简体汉字。这是由于汉字在使用过程中遵从经济性原则。虽然,简体字大大提高了人们的书写速度,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汉字的发展历史。部分汉字的繁体字很容易看出字义,但是在简体字中,字义来源却无法推测。并且,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学生对繁体字的认识较少,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极为必要。探索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繁简字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汉字的认识,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1、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的必要性
1.1有利于了解汉字发展历史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人们为达到经济目的,汉字简化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虽然,简体字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但是有些简体字却掩盖了汉字的真实意义,使繁简字在对照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麻烦和错误。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能够使学生了解汉字发展的历史,了解繁体字蕴含的字义及繁简字对照的规则,使学生真正掌握汉字的字义,加强对汉字的认识,完善自身的汉字学知识结构。
1.2有利于加强汉字的影响力
虽然,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是用简体字,并且简体字的发展以成为不容改变的事实。但是繁体字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很多广告、名胜古迹、艺术作品都使用繁体字进行介绍。同时,由于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仍在使用繁体字,古代汉语课程开展繁简字教学有利于大陆地区与香港台湾交流,寻找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根源。另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韩国、越南等地越来越重视汉字的使用。因此,在古代汉语课程中开展繁简字教学有利于加强汉字的影响力
1.3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
繁体字不仅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和演变,还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重要的经典文献都采用繁体字记录。而我国大多数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对繁体字书籍也十分排斥,导致我国经典文献的阅读人数较少。开展繁简字教学能够完善学生的繁简字知识,使学生能够读懂、会写繁体字,减少阅读繁体字书籍的阻力,进而了解我国优秀的文化经典,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2.古代汉语课程中繁简字教学策略
2.1加强对繁简字教学的重视
首先,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应加强对繁体字教学的重视,认识到繁体字教学对汉字发展及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大繁体字教学在古代汉语课程中所占比重,积极鼓励古代汉语教师开展繁简字教学,并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其次,高校应积极改进教学理念,正确认识到汉字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加快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的步伐,积极引进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担任古代汉语课程教师,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提供人才保障。同时,高校应加强古代汉语教师的专业培训,组织古代汉语教师定期参加培训,完善古代汉语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增强古代汉语教学的专业性。
2.2明确教学重点
在现实生活中,繁体字被大量运用在电影字幕、名胜古迹及文物介绍中。在当今时代,开展繁简字教学变得极为必要。在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开展繁简字教学应积极明确教学重点。由于汉字的发展历史较长,汉字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形体,部分汉字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在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辨别繁体字和异体字,通过繁体字和异体字的学习,了解汉字使用和演变的规律,加强学生对汉字的了解。同时,教师还应积极引导学生区分繁体字和简体字,尤其对繁体字在简化过程中意义发生转换的汉字进行重点讲解,使学生理解繁体字的字义,提高繁体字学习的效率。
2.3改进教学方法
由于繁体字没有书写规律,只能一个个记忆,学习难度较高。因此,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应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提高繁简字教学的效率。首先,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将繁简字对照表、繁简字通论及经典文选相结合。在向学生讲解繁简字通论的基础上,让学生对繁简字进行对比,并引导学生阅读分析经典文选,提高学生使用繁体字的能力;其次,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积极采用比较辨析的方法,加强学生对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认识。为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对繁体字、异体字、简体字进行辨析,加强对汉字的认识;最后,教师应积极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加强锻炼学生运用繁体字的能力。为此,教师可以从网上下载优秀的繁体字文选,鼓励学生使用繁简字对照的游戏软件,不仅要使学生能够识别繁体字,还要使学生学会写繁体字,增强学生学以致用能力。
小结:
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要的必修课程,不仅能够完善学生的汉字学知识,有利于学生了解汉字的发展历史、加强汉字的影响力,而且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加强重视繁简字教学,积极探索繁简字教学的科学方法。为提高繁简字教学质量,高校应积极加强对繁简字教学的重视、明确教学重点、改进教学方法。完善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繁简字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拓宽汉字的影响力,而且对汉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第6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第7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认识、技术传统、传统机械
在古代,不同的文明区域有着不同的知识和技术传统。要认识中国的技术传统,首先要探讨中国的技术发展史。刘仙洲、梁思成等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开创了中国技术史研究。但是,技术史至今在中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学科①。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和现存的传统技术也就是认识或者说发现中国的技术传统,我们至今对这一传统的认识还不充分。本文从回顾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入手,进而探讨技术传统的一个认识途径——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
一、对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机械传统的的记述和传说长期流传于世,引起了历代擅长技术者和文人的注意和好奇。三国时期的马钧曾再度发明前人的指南车、翻车,明末的王徵试图复原指南车、木牛流马等。王祯撰《农书·农器图谱》,薛景石撰《梓人遗制》,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记载了他们所了解的机械。艺术家的作品也使古代机械的技术信息留存下来。比如,五代《闸口盘车图》仔细绘制了水磨图,《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船舶、车辆、桥梁等技术。
中国古机械较早地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1909年起,格里(Giles)、摩尔(Moule)、朗基斯特(Lanchester)等人先推测过指南车的传动机构[1]。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机械工程学家和文博专家开始了中国古代机械的文献研究和专题研究。1925年,张荫麟翻译了英国人摩尔的论文《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且撰写了《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刊载在《清华学报》上。1935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出版《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初步整理了汉语古籍中关于机械的记述。王振铎则根据古文献的记载,试图复原古代的机械装置。1936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汉张衡候风地动仪制法的推测》,并在北平研究院复原指南车、记里鼓车[2]。这些早期的工作开创了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1949年以后,科学技术史在中国成为一项有组织的事业,实现了初步的建制化,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3,4,5,6]。其中,刘仙洲、王振铎的工作代表了机械工程史的学术水平[7]。
1950-60年代,刘仙洲开展了机械原动力、计时器、齿轮、凸轮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于这些研究,他撰写了通史性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展史》[8,9],初步勾画了中国机械技术发展的大致脉络。书中收入了关于耧、辘轳、独轮车等方面的调研成果。后来,刘先生曾组织学者从2万余种古书中查找古机械的线索和记述,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近今来,清华大学图书馆学者对这些的资料进行了整理。
复原是古代机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振铎等长期从事古代机械史的专题研究和复原。在文献分析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地震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水排等机械装置,其主要成果收入他的文集《科技考古论丛》[10]。
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注意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这一视角,审视中国古代的机械和技术传播,同时探讨机械技术与其它知识的关系。他参考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王铃的协助下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工程分册[11]。该书初版于1965年,后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窗口[12]。
在刘仙洲之后,机械工程史的专题研究和调查工作仍有进展。同济大学陆敬严在古代兵器和其它机械装置的复原研究以及立轴式风车等传统机械的调查方面均有新的进展。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研究,西北农业大学等单位对秦陵铜车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全国的科技史家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集中展示中国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时,陆敬严、华觉明等学者,编著了该丛书的机械卷[13]。该书继承了刘仙洲、王振铎等中国学者的思路,适当参考了李约瑟和其他学者的著作,在技术内容和构造原理分析方面均有进展。
刘仙洲、王振铎、李约瑟、陆敬严和华觉明等所撰写的专著主要基于古籍的记载、考古资料和部分传统机械的调查资料。未来的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研究还可以在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发掘、整理和解读明清时期汉文典籍和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的史料;第二,充分利用现有的和将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开展科技考古研究;第三,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探讨它们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第四,开展技术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有连续的文化传统,保留了繁浩的古籍。有关古代机械的记载,散文见于多种体裁的典籍之中。然而,关于技术的文字记述或绘图大多过于简略,时常仅有只言片语,甚至找不到任何记载。考古发现能够提供某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内容显然是有限的。多数古代机械的制作材料是木、竹等不易长期保留的材料,只有少数零件是用石头和金属制作的。这使得我们在考古资料中很少有机会找到结构比较完整的机械。像古代车辆和铜车马这样的发现毕竟是少数。
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的缺憾限制了人们对机械技术传统的认识。因此,单纯基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技术史研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进一步发现技术传统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调查现存传统技术,且从科技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去展开讨论。
二、前人对传统机械的调查
中国有着连续的技术传统。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在东南沿海和一些内地城市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工业体系,而在广大乡村,尤其是边远地区还延续着传统的产业和技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既有现代的运载火箭,又有传统的耕作机具。那些现存的传统技艺是古老技术的延续,至今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机械而言,其原理、构造、制作工艺和用途基本上与古代一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为便于与现代机械区别,我们称那些遵循古代技术传统的机械为“传统机械”,它们及其相关的工匠和使用者是机械技术传统的主要载体。
只要稍加调查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传统机械和工匠的手艺中保留了完整的技术信息,其内容远比任何古籍的记载丰富得多。要想深入地认识技术传统,补充文献的不足,澄清古代机械的详细构造原理、制作工艺和使用方法,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调查研究现存的传统机械。
可以说,古人已经调查和记录了传统技术。很多技术被《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典籍记述下来,流传至今。同时,我们不难想到利用现代的条件,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和方法,调查记述传统技术,保留文化遗产。
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就开始做传统技术的田野调查,并将调研成果整理出版。20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技术给予了关注。霍梅尔(Hommel)调查了中国的若干种传统技术,1937年出版了一部专著(China at Work),其中收录了不少机械装置的图片资料[14]。尽管记述仍不够详细,但毕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的技术资料。类似的论著还有西方学者撰写的江苏传统犁、牛转龙骨水车等技术的调查报告[15]。伍斯特(Worcester)在1940年发表的论文里,描绘了在四川测绘的一种船磨[16]。这种船磨似乎已经失传了。李约瑟不仅参考了这些学者的调研成果,还亲自到乡村考察了筒车、水磨、车辆挽具等技术,为他的中国机械工程史准备了详实的资料。
日本学者对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南等地区的传统机械和相关技术做了分门别类的调查,将它们拍照、测绘和记录成册。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调查了华北和东北等地的农业机械,出版了调查报告,如中田圭治的《北支の農業と作業機具》(1940年)、二瓶貞一和松田良一的《北支の農具に関すゐ調查》(1942年),它们被当代日本学者渡部武整理为《華北在来の農具》一书[17]。这两部书内容丰富,收录了华北的各种农业机具,包括共用一根驱动轴的五个龙骨水车、驴转龙骨水车、铁匠制作的畜力水车铁齿轮,等等。书中记述的有些机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渡部武还到西南等地做了新调查,完成了《西南中国传统生产工具图录》[18]。在日本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唐立(Christian Daniels)等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制糖、造纸、榨油等技术,撰写了若干调查报告,对制糖技术的起源和明清的制糖技术均做了研究。他的调查研究汇集成《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19]。日本学者调查和测绘的机械种类多,对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机械和工具的形制描绘尤其细致。他们的调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1958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泽东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并主张推广到一切地方去[20]。在他鼓动下,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同年9月,农业部编辑了4卷本《农具图谱》,汇集了当时全国各地使用的和新改进的的各种农具,以交流改进、创造、推广和使用农具的经验,促进农具改革运动[21]。该书介绍了各种农业机械的构造特点、规格性能、使用方法、产地、造价等。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其他关于传统技术的出版物和一些独立的调查报告,比如关于立轴式风车的调查报告[22]。刘仙洲这样的机械工程史家更是重视民间技术的史学价值,对河北、山西、河南某些地方的传统机械做了调查[23]。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学术研究陷于停滞。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学术活动和研究再度兴起。20世纪80年代,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博物馆在山东、云南等省调查了多种农业技术和机械,拍摄了录象。他们征集到的传统机械陈列或保存在北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苏州丝绸博物馆也调查和征集了不少传统纺织机械,使之成为重要展品或演示工具。同时,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对传统机械做了专题调研。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考古、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了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出现了不少调研文章。研究生学位论文使调查研究工作更系统、更深入[24,25]。尹绍亭、何学惠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汇集了尹绍亭的农耕卷、唐立的生活技术卷、罗钰的采集渔猎卷等,其中描绘了很多工具和机械装置[26,27]。这套书的风格与日本学者的调查专著有相似之出,农耕卷描绘了许多耕作机械、筒车、龙骨水车、风扇车等,但很少涉及水碾、水磨、水碓等结构比较复杂的机械。
20世纪80年代,科研院所和文博部门的学者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调查、抢救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工艺。1994年成立了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在1996年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的“九五”项目“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就是该丛书中的一卷。
三、调查传统机械的经验
1991年,笔者会同冯立升、钱小康、张治中等开始了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这一工作结束后,我们在“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继续有选择地调查传统机械。1998年以来,笔者开始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合作,调查中国的力学知识与机械技术传统。
现存传统机械种类繁多,同种机械还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这方面的调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以几个人的微薄之力和有限的经费,在课题规定的有限时间内,要调查各地的各式传统机械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不得不确定一个目标适当的研究路线。
我们不是选定某一地区做多种机具的调查,而是选择若干种机械,了解它们的机构设计、材料、制造工艺和使用等技术细节,将实物的调查与走访工匠结合起来,以求在认识或发现机械技术传统方面真正有所突破。调查对象的选择取决于课题的目标。一般说来,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比较典型的、技术上特点突出的、代表传统技术水平的机械,它们大多是结构相对复杂的机械。如果某种技术濒于绝迹,就优先安排调查。中国古代的纯金属机械装置不是很多。为了反映这方面的技术,我们选择了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朝制造的浑仪和简仪。
传统机械大多属于农业和手工行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级政府的农机、机械、纺织、文博等部门及研究机构,了解传统机械的分布、制作和使用等情况,得到调查线索,初步选择调查对象和要寻访的民间匠人。例如,1993年,通过原机械工业部和连云港连云区科委,我们得知传统风车在江苏赣榆的使用情况,到海边的盐场做了调查[28]。那里的工程管理人员又向我们提供了去浙江开化县考察的线索,促成了水碓、油榨等机械的调查[29,30]。同年,根据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提供的线索,在云南省农机管理局、大理农机局、丽江农机局的帮助下,我们调查了云南的若干种传统农业机械[31]。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计量研究院、北京通州计量局的支持下,我们帮助德国合作者调查了北京通州的传统杆秤制作技术[32]。2001年,在广西民族学院万辅彬副院长的帮助下,我们到广西融水县调查了苗寨的水碾。
调查者的机械工程专业背景对深入开展工作,辨识技术细节是很有帮助的。为了比较全面地实录技术细节,须拍摄机械的整体照片和各重要结构的局部照片,测绘出机械视图,记录工匠和使用者口述的设计与制作思路、方法、选材要求、技术窍门,用摄象机拍摄机械和采访工匠的过程。比较理想的是,拍摄、记录机械的制作过程。笔者曾与德国学者合作,拍摄、记录了北京和长沙工匠制作传统杆秤的全过程和使用情况。这种少而细的做法可以为将来复制这些机械提供完整的技术信息,是对传统技术的一种抢救。
采访工匠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在浙江、云南、山东、内蒙古、北京、广西都曾采访过制作和使用传统机械的手艺人和农民。在采访之前,我们阅读了有关的文献资料,参观或测绘了实物,从而拟订出要向工匠提出的问题。否则,所提问题可能落不到点子上,或者不够深入,采访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有时,由于方言的限制,双方可能出现交流的困难。这时,就要找“翻译”来帮忙。
电影、电视等技术的传入,为我们带来了保存和表现传统技术的新手段。一些非科技史专家策划拍摄的电影、电视片或多或少地纪录了一些传统技术,或者为进一步调查提纲了线索,值得留意。例如,电影《柳堡的故事》以大量的画面表现了立轴式大风车带动龙骨水车提水的场景。立轴式风车已经绝迹,这部电影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卧轴式风车的场景出现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但镜头很少。近些年,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影视作品中偶尔也有筒车、水磨等机械的镜头一闪而过。科技史专家策划的专题片更有目的地记录了传统技术。比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刘仙洲和故宫博物院的帮助下,于1960年代拍摄了一部关于清宫机械钟表的纪录片。近来,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制作了一部包括中国杆秤制作在内的《力学考古》电视片。
实地调查所得到的丰富资料须经过系统的整理,进而与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补充,追本溯源,探讨技术的演进和传播,或进行其它视角的研究。需要查阅的资料包括地方志、正史、野史、笔记、考古报告等。我们在浙江开化县调查的两种水碓与元朝王祯《农书》所记述的“撩车碓”和“鼓碓”相符,油榨则与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记载一致。《开化县志》对水碓也明确记载。
当然,我们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知识和方法,对传统技术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比如,对一种机械做动力学、运动学分析,探讨其零件的受力状况和结构特性,推算机械的传动效率和整个装置的功效,等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传统的技术,我们可以说它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但却不可轻易地断定它应用了什么科学原理。通常,工匠们知道怎么做,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技术规则,掌握什么样的窍门,却未掌握那些经过科学家描述的原理和定律。
在调查和分析过程中还须辨识那些参入传统技术中的现代技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曾鼓励改良传统技术,发展现代技术。1950年代,中央政府更是提倡改进各式传统机械,举行过改良成果展览。随着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技术向各地传播,甚至影响到很偏僻的地区。传统机械的整体设计基本上遵循古制,但有些机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技术的影响,有的零件改用现代的材料制作,有的零件属于现代技术产品。比如,江苏赣榆风车的木卧轴被钢管轴取代,龙骨水车的木质刮水板改为橡胶板。苏州丝绸博物馆收藏的一架纺机上的一对木齿轮换成了塑料齿轮。云南、广西水车上都用铁丝来加固水轮的叶片。广西融水县杆洞乡水碾的水轮立轴上安装着现代的滚珠轴承,碾轮与轴的连接采用了现代的螺栓。杆秤加工过程中,匠人有时要借用现代的手电钻、钢锯、砂纸。现代文明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研究传统机械时,一定要区分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现代的;在总结传统技术的时候,注意把现代技术“剔除”出去。
在采访工匠时,须注意防止近代知识“窜入”口述的知识中。比如,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工匠在解释杆秤的时候,他可能要用现代力学概念和杠杆原理来解释秤的原理和刻度划分,而这些却不属于中国古代的知识传统。在采访那些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工匠时,我们就比较容易避免后世知识的混入。
四、调查中的发现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仅就若干种传统机械做了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发现超出我们事先的期望。可以说,每次调查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结束调查计划时往往又发现新的调查对象,深感意犹未尽。归纳起来,我们在江苏、浙江、云南、广西、陕西、北京、山东、内蒙古等地调查得到了如下发现:
1.机械的详细构造和不同地区机械的相似性和差别,比如石磨盘、水轮、齿轮的构造;
2.整个机械及其零件的准确尺寸参数,如水碓、水碾的尺寸;
3.零件制作的选材要求和注意事项,如用杉木制作龙骨车;
4.零部件的制作工艺和加工工具,主要是木作工艺和金属工艺;
5.零部件的各种连接方式,如榫、楔、铆、箍、销等;
6.轴承的构造以及冷却润滑方式,如浙江水碓、云南水磨中的轴承;
7.机械的控制方法,如水轮转速的控制、水磨粮斗与磨盘间隙的调节;
8.各种技术窍门,如长沙制作杆秤的秤星的方法、五味子用做涂料;
9.工匠解决技术问题的思路,如秤星刻度的划分与计算方法;
10.机械的其它用途,如水碓用于加工木粉、辣椒粉、纸浆等;
11.机械的操作要领与维护保养要求,机械的使用寿命;
12.匠人们的“讲究”,如杆秤刻度与福、禄、寿之间的关系的说辞;
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是古籍中没有或很少描述的。这类活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生动的技术画卷,提出了新的有待调查的问题、思考的线索和文献研究的方向,值得珍视。
中国已经为实现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现代化”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说,现代化就意味着掌握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传统技术被淘汰或濒于消失。社会上轻视“老古董”,有的传统技术已濒于消失。无详细记录的传统技术一旦失传,就难以挽回文化上的损失。立轴式风车的绝迹就是一个教训。调查和实录那些濒于失传的技术传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有关产业部门有责任开展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抢救、保护。国家应该建立有自己特点的科学技术博物馆,传统技术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机械工程史学者曾呼吁建立中国的机械博物馆。
五、基于调查资料的研究前景
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开展多视角的研究,包括史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探讨、技术起源和传播的分析、技术社会学的讨论、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等等。
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技术有很多一致性和相似性,也有差异。这一现象与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与不同的民族相对应。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与自己民族有关的文献资料不多甚至很少。在此情况下,纯粹的历史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技术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却是非常有潜力的。国外学者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的深入调查,较早将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到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称作“科技人类学”,强调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出路之一[33]。近年来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多少都有田野调查和文化人类学的色彩,只是深入系统的工作还不是很多。我们主张开展“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技术传统”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中国的传统机械,分析传统技术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这是认识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本文作者只是做了若干初步的田野调查,视野更为开阔的技术与文化互动的研究还有待尝试。该文旨在就教于学界同仁。
参 考 文 献
1. 陆敬严,八十年来指南车的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卷(1986)第1期,第52-58页
2. 李 强,王振铎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科技模型的复原工作,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1991年)第2期,第63-71页
3. 席泽宗,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9-43页
4.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3期,第75-76页
5. 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年)第2期第58-62页、封四,第3期第51-55页
6.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3卷(2001年)第3期,第88-94页
7. 张柏春,对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11卷(1994年)第3期,第36-38页
8.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
9.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
10. 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 part II,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2.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 陆敬严、华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 Hommel, P. R.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a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Bucks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Doylestown, Pa., 1937; John Day, New York, 1937
15. Rewi Alley and C. C. Bojesen, Agricultural Implements used in Southern Kiangsu, The China Journal, vol. XXVI, No.2 (1937), pp.87-96
16.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 part II,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412
17. 渡部 武 解説,(復刻)華北在来の農具,大日本農機具協会、華北産業科学研究所·華北農事試驗场,1995年
18. 渡部 武、渡部顺子,西南中国传统生产工具图录,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ヵ言语文化研究所,历史·民俗丛书IV,慶友社,2000年
19. 唐立(Christian Daniels),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84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具图谱,第一卷,前言,第1页,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8年
22. 陈立,为什么风力没有在华北普遍利用——渤海海滨风车调查报告,科学通报,第2卷(1951年)第3期
23. 刘仙洲,有关我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的几项新资料,农业机械学报,第7卷(1964年)第3期,第194-203页
24. 易颖琦、陆敬严,中国古代立轴式大风车的考证与复原,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25. 李克敏,张小泉、王麻子剪刀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1992年)第2期,第70-84页
26. 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下),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7. 罗钰,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8. 张柏春,中国风力翻车构造原理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4卷(1995年)第3期,第287-296页
29. 张柏春,中国传统水轮及其驱动机械,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1994年)第2期,第155-163页;第3期,第254-263页
30. 张柏春、冯立升,“南方油榨”的初步考察,古今农业,1994年第4期,第23-27页
31. 云南几种传统水力机械的调查研究,古今农业,1994年第1期,第41-49页
第8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 玄览论坛 传统文化 海峡两岸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23
Abstract In August 26, 2016 the Third Xuan Lan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Culture & Education and Nanjing Libr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focused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novation of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discuss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so on, and hoping to be useful for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uan Lan Forum.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玄览论坛”由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两馆在历史上皆源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而且积淀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更好地激活两馆雄厚的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延续两馆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两馆面临的共同课题。2011年5月,南图学术代表团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两馆商定以举办论坛的方式,搭建两岸图书馆界沟通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加强合作,增进两岸图书馆界的认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京联合举办“首届玄览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海峡两岸60多位专家出席论坛。首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并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报道与转载。2015年8月两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玄览论坛”,以“阅读经典,精彩人生”为主题,研讨经典阅读与阅读推广,力图营造阅读经典的氛围。台湾地区对玄览论坛的成功举办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已经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品牌,两岸文化之盛会。
为了巩固“玄览论坛”前期成果,进一步加深两岸图书馆界、出版界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南京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开幕,论坛设南京主会场与南通分会场。本次论坛敬邀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著名图书馆馆长与专家学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长及造诣精深的佛学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发表演讲,探讨如何将古籍焕发出现代风貌,重现经典之美,共同为此极具意义且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而努力,让古籍重现新气象、新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佛光山副主持兼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两岸图书馆界人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余人参与,并在现场交流互动,探讨典籍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期望能更好地利用两岸图书馆界珍贵资源,唤醒沉睡在库房中的古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全面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发言中首先从玄览论坛的命名出发,回顾玄览堂丛书收藏经历,向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为致敬,高度称赞论坛在继承先贤遗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中华典籍方面的重大意义。其次结合此次论坛的主题,介绍国家图书馆丰富藏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致力于文献的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采取讲座、论坛、夏令营、公开课等多种形式,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中华优秀典籍系列展,与大中小学和社会各界合作,策划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国图公开课等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以中华典籍为元素,独立开发了一百多种文创衍生品。无论是展览文创衍生品,还是各类社会教育活动,都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优秀典籍,社会反映强烈,让传统的阅读方式得到了延伸,让典籍在参观者的心中活跃起来。最后,陈力馆长对此次论坛在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加深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届玄览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单纯是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为普遍百姓所理解,让古代典籍中鲜活的正能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以文化为内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码。
本次论坛的台湾参访团团长曾淑贤馆长于开幕致词中指出,本次与南京图书馆共同举办之“玄览论坛”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了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图书馆通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以及多元活泼的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过对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通过加值运用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亦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人类的智慧,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蕴涵,尽显图书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审慎典藏维护之外,更应随时供学者研究利用,藉广流传,进而阐扬中华文化,让许多特殊又珍贵的出版品重新赋予生命,以全新面貌与当代的读者接触。曾淑贤馆长最后强调,本论坛主要价值为弘扬文化、经验分享及维系情谊,共同打造中华典籍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提升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学术进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图书馆在开幕式中互赠图书,增益馆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世纪容颜》《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集》赠送南京图书馆,相信对于祖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发展的学者专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教授慧开法师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致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一直重视阅读对提升全民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星云大师的精神感召带领之下,很早就开始在佛光山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举办读书会。慧开法师结合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指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国文字由于统一已有两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去了解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慧开法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印度学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高度赞扬与羡慕,并指出“我们推行中华文化到全世界正当其时”。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酝酿了恢复汉唐盛世的潜力,中华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国发光发热,更要影响到全世界。他盼望通过这次论坛让古代优秀思想与文化活跃起来,真正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再现中华盛世。
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五书”论,回答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展书”,通过展览的形式将深藏在库房中的典籍展示给民众;二是“出书”,有计划地将重要典籍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三是“读书”,即引导民众阅读古籍、喜欢古籍;四是“研书”,对古籍进行科学研究,将古书中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他认为真正要做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起来”,还在于第五点“用书”,即用记载在古籍中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去改变社会与人生。
第9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历史记忆;草纸;皮纸
只要一提起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一定会令人想到那位皈依基督教,为法兰克国家奠定基础的克洛维一世,以及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并重建“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的的确确,法兰克王(帝)国的历史是中世纪史学人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因为法兰克人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舞台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西欧社会由古代向中古交替嬗变的过程中,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征服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并君临西欧大陆诸民族之上,实现了西欧社会的封建化。所幸的是,在法兰克人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曾经衰落的古典文化有所复苏,史学创作也较为活跃,这为还原那段历史提供了便利。1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许多前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并非最早的原初版本,而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誊抄整理后留下的。2毫无夸张地说,古代世界的许多历史记忆都是借加洛林法兰克人之手保存下来的。加洛林法兰克人为何能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有如此突出的贡献?1西方学者做过多方面探索,如:伯恩哈德・沃尔特・肖尔茨和芭芭拉・罗杰斯认为“查理曼时代的教育改革和学术复兴大大改进了当时的拉丁语风格,激发了人们对古典学识和古代基督教加以深入探讨的兴趣,汇集了日耳曼人对以往的记忆,引入了盎格鲁――萨克逊的史学传统。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范围宽泛、关注现实、个性化的且超越地方狭隘视野的史学编纂的兴起。”2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认为“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根子扎在不列颠的土壤中。这个王朝的史学主要是在盎格鲁―萨克逊史学的启发下复兴的。”3史学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史学“繁荣”意味着更高的史学创造力,许许多多的历史记忆会由于高产的史作数量而被记载下来。另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现象是: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人主要以皮纸作为自己的书写材料,于是,笔者鲁莽地另辟蹊径,试图以书写材料为视角,揭开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贡献卓著之谜。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史学的基本任务――保存历史记忆
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记忆。古往今来,人类各个民族的历史能跨越时空存留在后人的心目中,主要归因于人类借助了语言、文字等手段对历史记忆加以保存。在古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借助语言的形式,如传说、神话、民谣、口碑等传承延续着人类的历史。然而,靠语言延续下来的历史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在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由于以讹传讹而造成的讹误现象。所以口头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后便降为了人类保存历史的一种补充形式。相较于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记忆形式,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记忆形式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量且更为准确地保存人类的历史。笔记、日记、档案、石刻、碑文、方志、历史著作等均为人类保存历史的文本记忆形式,但它们所容载的历史信息大多属于历史片断似的不完全记忆,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唯有历史著作能够更为全面、充分地反映历史的前因后果乃至细枝末节。
西方史学自萌生时期起,就与历史记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古代希腊史学脱胎于散文记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大多有闻必录,将散于民间的系谱、神话、传说记载下来,传承下去。4
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历史》)开篇之初,即已告知我们,他的写作目的在于保存和传续历史记忆,他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5及至中世纪,尽管西方史学在文笔流畅、修辞优雅方面不及辉煌的古典时代,但其保存历史记忆的基本职能却并未丧失。都尔的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的序言中写道:“尽管我言辞粗鄙,但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1我们从加洛林史家的述说中也能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如普鲁姆修道僧勒斋诺对于修史存志、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认,他曾为加洛林史家的失职无为而痛心疾首。他在《普鲁姆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写道:“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其它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其著作将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迹传达给我们,然而有关我们自己时代的事迹却(无人述说),未曾有人打破这一连续的沉默,尽管它们距离我们更近,似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人类的活动业已终止,或许人们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值得记忆,倘若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却曾发生过,那么一定是没有能够胜任其职的史作家把这些事迹付梓成书,史作家们由于粗心大意而趋向于无所作为。”2有鉴于此,勒斋诺撰写了一部能够保存传承加洛林王朝全部历史记忆的史著――《勒斋诺编年史》。
加洛林时代的史家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创作出许多记史体裁。其中在加洛林时代兴起、繁盛的年代记体裁3(annals)即因记忆备忘之需而产生。通常的观点认为最初的年代记以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形式呈现于世,之后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详实的大年代记。事实上,在法兰克王国,复活节年表仅仅是原始年代记(简短的页边注释)最主要的载体,而非唯一的载体。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同样也是原始年代记的载体,例如,在埃希特纳赫的殉教者名单上便出现了类似于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简短年度词条。4这些原始年代记完美地体现了用文字形式记载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因为这些记载在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上的年度词条诠释了殉教者、死亡者的生平事迹,保存了有关逝者的历史信息,生者能够透过它们追忆逝者,由此,对逝者的回忆和对历史的感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说上述原始形态的年代记保存的是有关个人历史记忆的话,那么修纂于修道院中的小年代记则保存了有关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这些小年代记记载的主要是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事件,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将其定性为一种只关注修史主体(修道院)自身历史的内视性文献并认为公元8、9世纪的小年代记纂修者不遗余力地修纂这种小年代记是为了构筑本修道院的历史记忆,在这些小年代记中,一些早于纂修者时代的历史信息也被囊括其中,以致人们对于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能够一直追溯至往昔的墨洛温时代,甚至一直追溯至遥远的古代。一所修道院据此能够寻找到某种历史认同感,其成员的精神情感也能找到某种历史寄托。5
在加洛林时代,许多历史著作都带有某种回忆录的味道,它们是一种以回忆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僚属、随从对昔日恩主的追忆与怀念。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属于此类作品。爱因哈德曾任查理曼的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机密政事。他在《查理大帝传》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对于先皇查理的恩宠眷顾,铭感五内,无法释怀,唯有把先皇的丰功伟业著录下来,方能报恩于万一。他在序言中写道:“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甚至单凭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动笔,那就是我所受到的养育之恩以及我与国王本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友谊,这种友谊自从我在宫廷里居住的时候起,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使这样恩遇我的人的丰功伟绩湮没无闻,如果我容许让他的生平不见著录,不受颂扬,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说我忘恩负义,对我来说则是罪有应得的。”1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也反映了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尽管诺特克并非查理曼同时代的人,但他在写作《查理曼事记》的时候,采访了其朋友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阿达尔贝尔特系查理曼妻舅克罗尔德的部下,曾跟随查理曼参加了针对匈奴人(诺特克记载为匈奴人,实际上是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据诺特克所述,他年幼之时曾住在阿达尔贝尔特的家中,阿达尔贝尔特常常向他讲述一些有关查理曼征战的轶事。2
阿达尔贝尔特的回忆成为了诺特克写作的主要材料来源。除了上述两部史著,根据英国学者罗塞蒙特・麦克特里克特的考证,“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出自美因兹大主教随从之手的那部分《富尔达年代记》、虔诚者路易宫廷图书馆管理员杰沃德撰写的《克桑滕年代记》都带有一点回忆录的味道,反映的都是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3
由此可见,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一直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在这一史学基本任务始终如一的前提下,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记忆的保存状况为何会有所差别呢?笔者以为这种差别不仅受社会文化水平、史家个人素养等环境、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书写材料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二、古代世界的两种书写材料
在加洛林时代以前,环地中海世界主要盛行着两种书写材料――草纸和皮纸。草纸是一种生长在埃及野外沼泽湿地中的水生植物,其底端的根茎宛如人的臂肘般大小,倘若要把这种植物制成卷轴,则须先把其根茎的外皮削去,然后再把它的内茎切成若干长条,之后把这些长条切成一片片薄片并排放在一起,薄片之间的边缘部分要有少许的重叠,之后再在这一层薄片上以同样的方式垂直铺加下一层薄片。然后把这两层薄片平摊在亚麻布中间,使用木槌趁其湿润用力捶打,于是薄片被压成皮片,再挤去水分并用石头等重物压,待其干燥后用浮石磨光就制成了草纸。草纸一般以卷轴的形式使用,即把多张草纸黏在一起并卷成一卷存放,使用时则把其展开。在古典时期,草纸是地中海世界最为普遍的书写材料。4根据玛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的说法,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于草纸的使用始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发现了草纸这种书写材料,此前,并无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使用草纸的记载。他们使用棕榈树叶、树皮、铅片、亚麻布片、蜡板等多种材料进行书写,但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发现草纸后,这些书写材料便统统被草纸所取代。正如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所记载的那样:“我们的文明或我们所记载的一切事情基本上都依赖于(草纸)这种纸的使用。”5由于草纸仅仅产自埃及等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墨洛温法兰克王国所需之草纸皆源自海外贸易。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格雷戈里在书中提到了南特主教费利克斯写信咒骂他的这一事实,格雷戈里以如下的话作答:“但愿当初马赛接受你为主教!因为船舶决不会给你运来油或其它商品,只会运来草纸。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地方来写诋毁好人的话,现在由于缺少草纸,你的唠叨也为之缩减了。”6可见,在墨洛温王朝的治下,马赛这一海港城市系地中海世界草纸贸易的集散地。不过,作为源自埃及的一种书写材料,草纸在低纬度地区干燥的气候条件下能够保存完好,但是在西欧这样的高纬度地区,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草纸的保存状况就不能令人满意了。由于冬季天气的寒冷,草纸的质地更为脆弱,在卷拢摊开卷轴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纸张破损的现象,而且它还会经常受到潮湿气候和霉菌的影响而腐烂变质,其记载的文本内容往往因为书写材料的毁损而丢失。罗马教廷的档案保存状况清楚地表明了草纸的这一特点,在西方社会全面使用皮纸以后,恪守传统的罗马教廷仍坚持使用草纸颁布公文,直至公元10世纪后半叶教皇档案处(papal chancery)方才使用皮纸,教皇档案处现存最早的草纸文件是公元788年哈德里安一世书写的一封信函,自此之后直至公元10世纪后半叶,仅有40份教皇训喻的原件保存了下来,数以千计的草纸文件消失得无影无踪。1
皮纸的产生要晚于草纸,它最早产生于公元前190年的小亚。据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博物志》的记载,当时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打算建立一个能够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相抗衡的图书馆,面对帕加马的竞争,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停止了向其出口草纸,于是欧迈尼斯二世被迫开始生产和使用皮纸。2
皮纸是一个宽泛的术语,不仅包含了羊皮纸,也包括那些使用牛犊、猪、兔子等其它小型哺乳动物皮革制成的皮纸。生产皮纸的过程描述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则需要具有高超的技艺和准确性,首先须把带有毛发或皮毛的皮子放在石灰水中浸泡几天以溶解皮毛和脂肪,之后挤压拧干并刮掉多余的毛发和皮脂并摊放在皮架子上晾干。当皮子被完全晾干后,再用一把半月型的刀刮皮子。之后,把皮子裁剪成恰当的尺寸并保存起来以便备用。皮纸一般以抄本(codex)的形式使用,即按照刀数(二十四或二十五张皮纸为一刀)把一张张皮纸折合在一起,再在上下两面各自添加一个或硬或软的封皮,最后缝合起来形成一个抄本――我们有时也把一个抄本称为一卷。皮纸是一种奢侈的书写材料,一本手抄本皮纸《圣经》就要耗费近250张皮子,其价格之昂贵可想而知。倘若使用皮纸来大规模地保存历史记忆,则必须有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力量作为后盾,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此劳民伤财的文化活动绝非史家个人的经济实力所能承受。由于皮纸价格的昂贵,人们被迫在蜡板上进行写作,但蜡板上的字迹易受摩擦而模糊,故而蜡板也不是一种好的保存历史记忆的书写材料。
三、加洛林时代皮纸的使用和生产
在加洛林时代,人们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皮纸。传统观点认为,由于阿拉伯人于公元634年征服了草纸的供应地埃及,影响了埃及对西欧的草纸供应,这才迫使法兰克人骤然停用草纸,转而就地取材使用皮纸。3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学者都证明了阿拉伯人的崛起并非加洛林法兰克人使用皮纸的唯一原因。4不过,不管是否出于阿拉伯人的原因,法兰克人在由文化蛮荒时代走向文化建设之际,愈益青睐皮纸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公元7世纪墨洛温法兰克君王的敕令直观地反映了他们的这一使用偏好,墨洛温王朝的中书监最早以皮纸颁布的一份敕令是公元677年9月以狄奥德里克三世的名义颁布的,而之前的敕令尽皆使用的是草纸。1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皮纸抄本要比草纸卷轴优越,因为皮纸抄本的正反两面都能摊开平放,人们能够利用皮纸的正反两面阅读和书写,而且与草纸相比,皮纸的纸质更硬,加玺盖印后不会导致纸张的破损变形,在法兰克人愈益依靠印章来鉴定和签署证书文献的年代里,皮纸方便了人们对于印章的使用。另外,皮纸抄本也使得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工作更为容易,因为抄本能够被垂直地放置在书架上。单就质量而言,皮纸也是一种较好的保存文本内容的书写材料,因为兽皮不易腐蚀,如果保持干燥和清洁,在良好的保存状态下能够存在3000年不腐,而加洛林时代距今也不过1200余年,所以在加洛林时代使用皮纸重新誊抄和书写的史作大多能够传延至今。下列这两组数据能够清楚地表明皮纸长久保存书写内容的功效。“公元800年之前的西欧大陆只有1800部手抄书籍或残篇流传了下来,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公元8世纪誊抄的。然而同样在西欧大陆,我们却拥有9000多部由抄书员在公元800年至公元900年誊抄的手抄书籍或残篇。”2加洛林时代传世的著作如此之多,甚至远远超过了之前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恐怕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当时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创造力,因为即便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下,加洛林法兰克人的文化水平恐怕也难以超越文化昌盛时期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例如,在他们所谓原创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对古典作品亦步亦趋的模仿,如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是模仿《十二凯撒传》写成的。看来,这种数量上的超越只能归功于下列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比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的书写材料――草纸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书写内容。
但从供应量和成本方面来看,皮纸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我们毋需多想,便能体会到一本由250张皮子制成的《圣经》意味着一笔多大数额的财富。正因为受限于高成本,在加洛林时代,主要掌控这一稀缺资源的是: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以及加洛林宫廷。上述都建有抄写室和图书馆,在中世纪的西欧,举凡建有抄写室和图书馆的机构一定拥有大量的皮纸,否则,抄写、保存图书的活动必然走向无以为继的窘境。另外,皮纸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书写材料,若用小刀刮掉上面的字迹,则可重新书写,图书馆中收藏的皮纸图书皆为潜在的书写材料,故而,抄写室、图书馆的所在地往往拥有较多的皮纸。
在加洛林时代,由于查理曼等帝王的鼓励和期许,许多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已然成为了帝国文化和学术活动的中心。查理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懂得“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在其当政期间,查理曼颁布了若干督促地方教士和修士发展文化教育的敕令,如由阿尔昆起草的《论学术知识的培养》(On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旨在督促修士研习《圣经》并对青年予以指导。《798年敕令》(Decree of 798)则督促高级教士(prelate)和乡村教士要为民间孩童开办学校。3无论是钻研神学,还是普及教育都离不开图书这一知识传播工具,故而这一时期的修道院大多设立了誊抄皮纸抄本的抄写室和保存皮纸抄本的图书馆,其中,圣・阿曼德、图尔、科尔比、富尔达、切尔斯、圣高尔等修道院均为当时法兰克帝国读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为了满足抄写室中的修士对于皮纸的需求,当时的修道院可能自主地生产这种书写材料,而修道院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又恰好能支撑这种生产活动。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均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修士们自己种植谷物和蔬菜,烤面包、酿啤酒、经营鱼塘、香草园和果园。尽管修士们只有在身患重病的时候,方才被允许吃肉,但奶、奶酪和禽蛋却是修士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修士们也喂养家禽和牲畜。修道院完全可以就地取材,依靠自养的牛犊和羊羔为修道院中的抄写员们提供皮纸。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料,笔者无法得出绝对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普遍存在生产皮纸的活动。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至少公元9世纪早期的科尔比修道院存在过这种生产活动,在科尔比修道院住持阿代尔哈德于公元822年颁布的一条法令中提到了一位皮纸制造者,他是一位俗人,在本院生产皮纸的活动中,负责对皮革的加工处理工作进行监督。1不仅修道院,某些主教区的大教堂也掌握了不少皮纸,如维尔茨堡主教区的大教堂,抄写室、图书馆、教育年轻教士的学校等文化设施一应俱全。维尔茨堡主教亨伯特还是一位热忱的书籍收藏者。他意图收藏富尔达修道院住持哈拉班・莫尔评注的《圣经》,于是向富尔达修道院发去了一份请求誊抄的申请函,并送去了大批空白的皮纸。2
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维尔茨堡主教区并不十分缺乏皮纸,否则,亨伯特主教也不可能如此的大方。在中央层面,以王/皇室的富有,估计建有抄写室、图书馆的加洛林宫廷同样不会缺少皮纸,宫廷用“纸”的奢华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加洛林宫廷不仅使用黄色、白色等天然色泽的皮纸,还使用一种用紫色燃料浸染过的皮纸,以彰显王/皇家的尊贵与奢华。如公元783年查理曼就曾授意宫廷抄写员哥德斯卡使用紫色的皮纸抄写《福音书》。3
四、教职人士垄断修史活动的物质基础
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宫廷对皮纸实行占有的事实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细细地梳理一下加洛林史家的身份,便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史家都是教职人士,包括以默思修道为业的修士,以教化俗人为业的教士以及那些身处宫廷,为君王效力的宫廷教士,而真正世俗出身的史家只有查理大帝的外孙,《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1人。如此不平衡的比例,难道是因为教职人士对于修史活动情有独钟,而俗人对之了无兴趣吗?恐怕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史学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功能始终如一,如此看来,古往今来之人皆有保存历史记忆的欲望和冲动,这种欲望和冲动自然也不会因为人的世俗身份而有所消减。譬如,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以及修史活动异常发达的古代中国,都存在着大量世俗身份的史家,而并没有出现修史活动被祭司、僧道等教职人士垄断的局面。唯独中世纪的西欧,教职人士垄断史坛的现象较为严重,笔者以为这种垄断不仅与教职人士垄断文化的状况有关,也与教职人士占有皮纸这一稀缺而昂贵的书写材料密不可分。无论是西方古典时代的草纸,还是古代中国的纸张都比皮纸更为廉价和普及,即便古代中国某些封建王朝施行高压专制的文化政策,但由于纸张的廉价和普及,大量的稗官野史也始终未曾断绝,从而使古代中国形成了官私并存的双轨修史格局。反观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王(帝)国,皮纸稀缺而昂贵的特点为人们步入史坛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有能力读写的普通人即便存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念头,也很有可能由于无法得到高价皮纸而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只能由那些掌握和接近皮纸资源的人――修道院中的修士、主教区中的教士以及宫廷教士来执行了。
在加洛林时代,由于拥有充足的皮纸,那些在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抄写室、图书馆中任职的修士、教士得以把本修道院和本主教区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于是,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小年代记、历代主教传、历代住持传:
《圣阿曼德年代记》(Annales Sancti Amandi)、《蒂里安年代记》(AnnalesTiliani)、《伦巴森年代记》(AnnalesLaubacenses)、《摩泽尔年代记》(AnnalesMosellani)、《伯塔维安年代记》(AnnalesPetaviani)、《给尔服拜坦年代记》(AnnalesGuelferbytani)、《纳赞里安年代记》(AnnalesNazariani)、《萨尔茨堡年代记》(AnnalesSalisburgenses)、《因沃文森年代记》(AnnalesInvavenses)、《弗洛达尔德年代记》(AnnalesFlodoard)、《拉文纳历代主教传》(Liber pontificalis ecclesiae Ravennatis)、《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GestaabbotumFontanellensium)……一些修士甚至并不以单纯保存同时代的历史记忆为满足,他们在誊抄、缮写皮纸抄本的同时,也把一些古代的史作誊抄了下来,如公元8世纪末、9世纪早期的洛斯奇修道院留存了许多载有古代晚期史作的抄本,其中就包括了奥罗修斯、尤西比乌斯、鲁菲努斯、约瑟夫斯、赫格西仆、阿米亚努斯・马塞林、恺撒、李维的作品。1在我们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古典著作中,有70位古典作家的作品,其最古老的抄本是由公元750年至公元900年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整理的。2今天我们看到的凯撒、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苏埃托尼乌斯的史作都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抄录到皮纸上方才幸存至今。在中央层面,那些在加洛林宫廷文秘机构(中书监、王室祈祷堂、王室图书馆)中任职的教士――如“天文学家”、杰沃德等人同样不会因为缺少皮纸而苦恼,他们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把其昔日恩主――加洛林君王的种种功绩以回忆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帝王传记和宫廷年代记:《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Magni)、《虔诚者路易传》(Vita HludoviciImperatoris)、《克桑滕年代记》(AnnalesXantenses)、《王室法兰克年代》(Annales regni Francorum)……无论是加洛林史家原创的史作,还是由他们誊抄的前代史作,都由于著录它们的书写材料――皮纸的不易腐烂、持久耐用而长存于世。尽管“加洛林文艺复兴”充其量不过是把处于普遍文盲状态中的欧洲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史学创造力也根本无法与古代希腊、罗马人相提并论。但在历史记忆的保存方面,加洛林法兰克人却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由于加洛林法兰克人常用的书写材料――皮纸比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的书写材料――草纸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书写内容,所以不仅加洛林法兰克人原创的史作能够传承下来,甚至许多古典史作也都是仰赖加洛林法兰克人的重新誊抄,方才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而幸免于湮灭的命运。
五、结论
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尽管西方史学在史学精神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古典史学的“人本”转变为中世纪史学的“神本”,但西方史学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功能却从未改变。自文字产生以后,人类保存历史记忆的能力便开始受制于书写材料。皮纸由于其材质的不易腐烂而成为了古代世界一种有效保存历史记忆的载体。加洛林法兰克人能够传承如此之多的历史著作,在历史记忆的保存方面贡献卓著,似乎并不仅仅是他们史学创造能力提升改善的结果。诚然,由于“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史学创造力在墨洛温时代后进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更多的人有能力从事史学创作和前代史作的誊抄,但这种有限的提升只有和他们常用的书写材料――皮纸结合起来才能起到有效保存历史记忆的作用。否则,即便如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那么出众的史学创造力,也无法把他们史作的原始版本全部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评判某一历史时期的史学状况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当时史学创造力的进步与否,对于书写材料保存历史记忆的因素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考虑。
- 上一篇:税收筹划发展前景范文
- 下一篇:总承包对分包的管理措施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