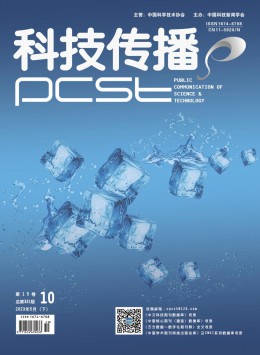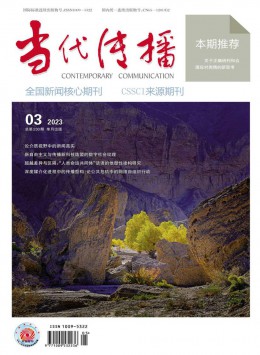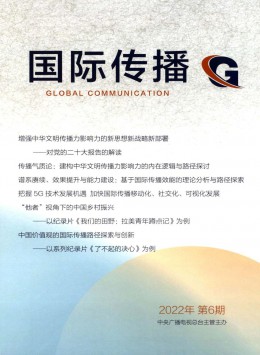传播与文化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经常听到、看到、耳熟能详的,除了研究方法、传统西方传播学理论、学派名称之外,就是一些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上的洋概念了,比如:“公共领域”、“场域”、“社会资本”、“权力关系”、“文化霸权”、“专业主义”、“符号”等。与此同时,由我们自己传播学者创造发展的土概念也逐渐开始进入研究话语并日益得到关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新闻的“双重属性”、媒介的“三角关系”、新闻记者“成名的想象”、编辑部的“象征资源”、“双重意识形态”、“权力寻租”、新闻发展的“拐点”、媒介“集团化”“招安”、“擦边球”等。跟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研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也难免会出现“谁也说不清,大家都在用”的情况。
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1971)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 [1]。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 (Morgan &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 “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 ,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修正,甚至推翻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擦边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擦边球的特殊利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注释]
[1] 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 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参见:杨击(2006)《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复旦大学出版社;胡翼青(2007)《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廖圣清(2005)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新闻大学》秋季号;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旦(200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
第2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学概论》;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149-02
传播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传入我国后,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新闻、文化、影视、广告等与传播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适应这种变化,国内不少大学的新闻学、广电编导、广播电视学等本科专业都陆续开设了《传播学概论》课程,而且基本都被列为专业核心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当前很多高校开设的《传播学概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都面临诸多困难,亟须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形式单一
传播学发源于欧美,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科渊源非常复杂。尤其是教师给学生所列的课外参考书目中那些由国外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内容可能更加艰深晦涩。在一个学期32课时至多48学时的教学时间内,学生要识记并且区分和弄懂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难度较大,往往会有畏难情绪[1]。再加上一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教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授课形式,教学手段过于单一,学生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困难重重,很容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和学生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学生觉得课程枯燥无趣,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2.理论与实践脱节
当前各高校所采用的教材,大多都是西方20世纪早期和中后期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当时这些研究成果很经典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但是很多当代新媒体传播和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传播新现象、新方法和新技巧等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却在教材和课堂教学中很少提及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即便此前的经典理论有些也很难适应和解释现在新型的传播形态,但是有的老师却基本照本宣科向学生讲授教材中的内容,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严重脱节,很难真正引起学生认真学习和钻研传播学理论的兴趣。
3.学生实践能力较差
与应用型大学设置的学生动手机会较多的实践实训类课程不同,《传播学概论》课程中涉及的理论知识很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会重点介绍传播学奠基人、传播类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相关理论。由于《传播学概论》的课程性质是纯粹的理论课,没有安排实训实践课时,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花费时间讲授纯粹理论的时间很多,学生真正动手动脑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实践分析的训练机会基本没有,从而造成学生自己应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缺乏,很难真正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实际需要。
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针对上述提到的《传播学概论》教学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授课教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解决呢?结合多年的《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以及近年来在本门课程改革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1.灵活运用教材
目前各高校《传播学概论》课程所采用的教材大都对传播学经典理论和案例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梳理,教材内容非常扎实丰富。但是,今天的传播环境和传媒生态已和多年前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传播学重点研究的都是大众传播,当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形式不断涌现,微博、微信、QQ、自媒体……这些新的传播方式都广受年轻人的喜爱。教师如果对这些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媒介不了解不熟悉不使用,就无法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自媒体存在“把关人”吗?“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时代有无失效的可能[2]?这些问题教材上也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理论给予说明,甚至很少提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但学生却是每天都在面对和接触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因此,教师必须不拘泥于教材的既有内容,既忠实于教材又敢于有所突破,既结合教材中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又参考最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当下国内外热点的传播事件,为学生进行分析和讲解,才能让课堂教学生动有趣,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2.内容通俗易懂
传播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何在消化吸收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同时,积极探索传播学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任课教师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娱乐时代的来临,学生往往注重感性的乐趣而非理性的思考,认识问题容易流于表面或过于肤浅,所以,教师要灵活结合当下的热点事件,鼓励和引导学生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比如,讲述大众传播理论内容时,可以尽量结合学生非常感兴趣又比较通俗易懂的影视作品和影视传播现象进行分析,既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又把基础理论、媒介分析、内容剖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知识,充分地向学生进行了传授,使课程内容重点突出,由生活到专业逐步引导学生的理解,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选择热点传播事件的相关案例时,需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在关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同时,要适当兼顾杂志、电影等的传播实践,以丰富案例的来源,讲授不同媒体的特性;二是增加新媒体传播案例,借以反思大众传播模式在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热荨⑹艽者、传播效果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深刻变化[3]。
3.突出专业特色
传播学教学的理论性强,实践性更强,对于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生,可以结合各自的专业特色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比如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课堂中对某条新闻或新闻栏目,运用传播学的知识进行分析和研究。新闻中采访问题的设置、新闻受众群体分析、新闻传播的效果等问题,都会大量应用到传播学的基础知识。编导专业可把作品创作和传播学教学结合起来,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让学生们自己分析某部影视剧中的经典片断,学生就会深刻理解和领会到传播效果理论、传播方法和技巧、传播符号理论等的重要作用。然后,教师再根据传播理论结合视频作品对学生的分析给予中肯到位的点评和讲解,那么学生对于学习传播学的兴趣就会大大地增加。
4.借助多媒体教学
教师在进行传播学课程教学时,不应局限于单纯的理论讲授,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将传播学涉及到的现象直观的表现出来,并通过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分析,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课堂思考和学习中。比如,借助互联网或智能手机,设置适当的课时让学生在课堂上体验多种媒介的运用方式,让学生切身认识到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与新媒体传播的不同、新媒体传播手段和方法的多元互动、媒体融合情况下受众心理的改变、“沉默的螺旋”理论为何在网络时代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失效等。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视频资料,借助影像作品直观生动视听兼备的特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比如,播放一段拍客上传到网络的精彩视频,让学生分析其传播效果和对受众心理的影响等,以此增强学生对传播理知识的认知和使用能力[4]。
5.调整开课学期
一些高校将《传播学概论》课程开设在一年级,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因为学生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思考和学习能力基础都比较薄弱,面对《传播学概论》这些枯燥艰深的理论类课程,不少学生感觉学习难度非常大,学期末挂科的同学比例偏多。笔者在早前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后,及时给学院建议,将《传播学概论》课程由一年级调整到了三年级。这样,经过前两年的大学学习,学生的独立分析和学习能力都已经得到加强,将传播学理论与本专业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能力也已基本具备。课堂上教师对于传播学理论的讲授和适时引导,学生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就大大加强,觉得传播学有趣而有用的同学数量明显增多,自觉将课堂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的学生人数也大大增加,教学效果和从前相比,得到极大的改善。期末考核时,挂科的同学数量大大减少甚至为零。
6.改革考核方式
不少高校《传播学概论》课程的考核方式使用的都是传统的闭卷考试。笔者认为,闭卷考试应与其他考核方式相结合,尤其应加大实践考核分数的力度,教师可以把实践作业的分数加入期末考试的成绩中。同时,将平时成绩计算在期末的综合评分中,平时成绩可以由学生课堂回答问题的质量和态度、课后作业比如读书笔记等的完成情况以及上课时的出勤率等构成。经过如此改革,课程的考核就能体现出较强的综合性和可操作性。总之,在期末考核时,教师应避免仅凭一份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死板而机械的作法,选择某种或几种方式结合的形式,把综合成绩作为学生《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期末成绩,这样也更容易得到学生的接受和认可,学生学习的动力会大大增强。
三、结 语
传播学是一个开放的、既注重理论建构又强调实践应用的学术领地,新媒介环境下传播学教学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传播学概论》课程的任课教师应在社会和传播学动态的发展中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能增强教学实效,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传播人才。
参考文献:
[1] 车南林.应用型本科教学背景下传播学课程转型与升级研究[J].科技传播,2016(2).
[2] 周少四.传播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今传媒,2015(9).
第3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力; 传播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8-142-001
自跨文化传播概念进入我国后,掀起了对此问题研究的热潮。跨文化传播力概念在诸多网络文献中频频被提及,百度输入“跨文化传播力”词条后,显示结果为40,600个(2014年5月)。然而在CNKI检索后对此并无相关研究与界定。所幸的是,国内有学者对其相关概念――传播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研究与含义的探讨。
一、传播以及传播力
什么是传播?胡文仲(1999)将传播定义为:“信息的传送和接受,一方发出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这一过程就是传播。”在人类社会传播中,传播又分为三种:人际、组织、大众传播。而对于传播模式,传播学界也相应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其中较著名的有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分别指Who(谁来传播)、says What(说什么)、in what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以及with What effects(得到什么效果)。之后的社会学家Jack Lyle 与M. Lyle把传播过程置于社会大环境中的考察,完善了传播的模型构建。总体来看,传播学界对于传播模式的提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基本的传播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渠道或手段、受众、效果以及环境,并且任何要素变化都会影响传播过程。
什么是传播力?国内学术界有关传播力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比如,刘建明2003年首次提出传播力概念时指出,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具体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而张春华(2011)认为,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传播力的研究大约分为以下四个角度:能力说、力量说、效果说、综合说。除了张春华所总结的研究视角之外,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如丁和根(2010)认为一个国家的传播力可以通过对外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少及强弱来衡量,郑保卫(2007)认为要提高新闻传媒业的传播力,则需通过了解受众需求、加大新闻传播渠道、加强信息报道质量;刘修敏(2012)认为电影传播力取决于对电影素材艺术性的保留和对大众迎合的平衡把握。不难看出,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角度侧重各异,大致可以归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涵盖了部分传播要素,然而相关研究对于传播者以及传播环境却鲜有专门研究。据此,笔者认为传播力既包括对传播内容、渠道、受众以及效果的综合评价,也应当包含对传播者的自身能力以及传播环境。简言之,传播的的任何基本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或手段、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以及传播环境)之一都会影响传播力的大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传播力
跨文化传播是指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或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在有着互异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地发送和接受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文化上互相联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过程。因此结合上文传播力的定义,跨文化传播力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传播的基本要素的综合考量。比如Hammer等(1978)提出的跨文化交际有效性三维度,即应对心理压力、有效交流及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之后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提出了不同标准,如Byram(1997)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提出评估指标应当包括:语言、社会语言、会话能力以及态度、知识、文化意识等内容。在国际商务管理领域,人际技巧、语言能力、异国工作及生活动机、不确定性容忍和应对能力等因素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表现(Schneider& Barsoux, 2003)。然而Helen Spencer-Oatey (2010)将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结为情感、行为、认知三个层面。
而国内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基本沿袭了Hammer, Helen Spencer-Oatey等学者的思路,并未有太多实质突破。教育领域代表观点为:语言能力、文化用语知识、目标与文化和文化意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高黎,王方,2007),国际商务领域主要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包括:跨文化沟通、跨文化适应、跨文化行动能力,文化智力、组织机构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距离等因素(吴箫,肖芬,胡文涛,2013)。
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主要适用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如有效的交流能力、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并且跨文化交际研究评估体系最终落脚点为传播者自身的因素(知识、情感、技巧)。另外,我们从“跨文化传播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身词义中也会发现二者的从属关系:传播在传播学中定义为“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而交际“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不难看出,交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属于人际传播范畴。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作为“跨文化传播力”其中一个子项-“传播者传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与跨文化传播力问题的结合,不仅对国内传播力研究中跨文化因素的缺乏补充,也使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研究不再拘泥于人际传播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更加宏观的传播方式,如大众传播中进行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50
[2]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2-61
[3]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7
[4]张春华.传播力:一个概念的界定与解析[J]求索,2011(11):76-77
[5]丁和根.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J]新闻大学,2010(4):136-142
[6]郑保卫.强化传播力彰显影响力拓展创新力提升竞争力-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传媒业发展之要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18-27
第4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广电;广电产业;法律视角
广播电视(简称“广电”)作为现代传媒的主要载体,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其新闻宣传的“喉舌”功能,从产业角度讨论广电媒体问题曾被认为“不合适宜”[1],而站在法律的层面讨论广电产业化问题更是“自不量力”。但在依法治国的策略和法治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尝试从法律的视角讨论广播电视产业化问题显得十分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广播电视的法律属性入手,在分析广电产业特性的基础上对广电产业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一、广播电视的法律释义
什么是广播电视?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结果。传播学者认为“广播电视是通过电磁波传导方式向特定范围播送音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体。”[2]从字义上讲“广播电视”应属于传播学或广播电视学上的概念,想从法律角度来说明“什么是广播电视”,确实有点困难。一个传播学概念如何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呢?这本身在法理上就值得探讨。如同“垄断”一词有不少人认为是经济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一样,同样有个疑问:“广播电视”能不能从法律角度进行界定呢?
笔者认为是可以的。所谓的法律概念无非是指“在法律上对各种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3]。一个概念只要具备了“法律上的规定”以及“权威性的范畴”两个要素就应当具有法律概念的形式特征。因为法律概念本身并不能将一定的事实状态和法律后果联系起来,只是适用法律规则和原则的前提,其功能是“将杂乱无章的具体事项进行重新整理归类的基础”[4],把某主客体、某事、某行为归入某一概念所指称的范围,界定法律的适用而已。而法律概念的实质特征就是“概念”本身,这个特征本来就需要从法律外进行抽象概括。因而,对广播电视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先看看“在法律上”有没有“假定”,是不是“权威性范畴”?再从概括的内容角度审视其法律概念的实质特征。现在就从“法律”的“权威性范畴”中来考察广播电视法律概念。
1.法律中的广播电视概念
对于很多问题我们喜欢借鉴,现不妨先从国外调整广播电视关系的法律规范中寻找广播电视的法律概念,探讨一下各国立法是如何对广播电视进行“假定”的(下定义)。《加拿大1991年广播法》对广播的定义为“利用无线或者其他通信手段为公众提供通过广播接收设备接收的加密或者不加密的节目,但不包括专门为演示而传输的节目。”《统一德国的广播电视国家条约》总则第2条就是对“广播和电视”的释义:“指为社会组织的、用电频而不用导线、或用导线,以文字、声音、图像的形式播出的各类节目。它还包括以密码播出,付费后可接收的节目以及图文电视。”[5]《美国联邦通信法》第3条第6款把广播理解为“为了公众接收,直接或通过转播,进行广播电视传播”。可见,很多国家在法律中都明确地规定了什么是“广播电视”,给“广播电视”披上法律的外衣。但遗憾的是在我国不仅没有《广播电视法》,连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中也难以找到对“广播电视”的假定。因而,对我们而言“广播电视”在某种程度上还仅仅是停留在法律之外的一个概念,也正为如此,导致了广播电视与其他概念在法律范畴上的模棱两可、权限不清(如与电信的关系),这也是从法律角度理解广播电视的意义所在。
2.广播电视的法律属性
之所以一直想把广播电视当作一个法律概念来探讨,原因就在于广播电视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或传播学俗语,它的内涵本身就具有诸多法律属性,或者说有法律概念的实质特征。首先,在“媒体即权力”的视野中,作为最主要的媒体,广播电视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是“第四种权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三权分立与制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种功能就属于法律的范畴;其次,广播电视已由单纯的“工具客体”向“责任主体”转变,人们曾经一直从一种“工具论”或“功能论”的角度来认识广播电视的本质,广播电视也同一双筷子、一台机床一样,“尽其所能、听我之命、为我所用”,但社会发展到今天,广播电视已从“工具客体”的本质中挣脱出来了,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责任主体”,是享有权利并能独立承担义务的“法律主体”;第三,广播电视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和“公益性”的要求,人们总是要用法律的理念和原则来规范广播电视的行为,如公共信条、公正原则、合法传播等等。可见,广播电视这个概念就是法律内涵的体现,也离不开法律的视线。
3.法律角度探讨的意义
为何要在法律范畴中讨论广播电视的概念呢?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想把广播电视当作法律的调整对象,不再让它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甚至居于法律之上。这也是从法律层面认识广播电视的前提,只有有了法律上的界定和界限,广电产业化才合法以及合法地产业化。
二、广电产业及其特性问题分析
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广播电视产业化的法律问题,从产业的角度分析广电产业及其特性是前提条件,只有认清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掌握其有别于他物的本质所在,才能懂得如何用法律手段对广电产业进行规范。
1.产业与广电产业
什么是产业?人们的认识水平总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对于产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产业”一词最早由重农学派提出,特指农业。在人类迈入资本主义大生产时代后,产业主要是指工业,在英文中,产业与工业的表示方式都是industry。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曾将产业表述为从事物质性产品生产的行业,并被人们长期普遍接受为惟一的定义,也正是因为“物质性生产行业”的定位,广电媒体始终没有被赋予产业的属性,而一直尊居“事业的宝座”。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服务业和各种非生产性产业的迅速发展,产业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再专指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而是指“生产同类产品(或服务)及其可替代品(或服务)的企业群在同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的集合”。[6]人们也开始对广电媒体进行重新定位,把它当作一个产业进行经营,经营的内容包括“广告经营、节目经营、信息经营、技术经营、劳务经营、混合经营”。[7]因而,可以从产业的角度给广电产业下个定义:即生产、制作、经营、播放以广播电视节目(信息)或提供广电文化服务为主的企业组织及其在市场上的相互关系的集合。同时,“‘产业’是一个居于微观经济的细胞(企业)和宏观经济的整体(国民经济)之间的一个‘集合概念’,它既是同一属性的企业的集合,也是根据某一标准对国民经济进行划分的一部分。”[8]根据现行产业的划分标准,广电业属于第三产业。
2.产业化与广电产业化
“产业化是指社会生产劳动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与社会生产活动的现代化过程。”[9] “对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一切有投入有产出、按照企业运行规则进行经营活动的事业都可称之为‘产业’,都可以推入市场。所以产业化问题,是就资源的配置手段而言的。从微观的角度看,同时也是‘企业化’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也即是‘市场化’的问题。”[10]从人们对产业化的认识,可知所谓广电产业化,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广电媒体”向“产业经营的广电媒体”过渡的过程,也就是广电媒体的资源配置及生产方式的分工化、市场化、企业化、集团化,“从单纯的文化、精神生产事业的媒介单位沿着经营合理性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渡的一种现象过程。”[11]
3.我国广电产业化问题的争论
在我国广电媒体一直强调其政治属性,对于其经济属性的“产业化问题”好像成了个“观念禁区”,十分敏感,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这种提法。在传播学界,甚至有人否认广电媒体产业化观点,也有人提出“广电媒体是产业但不应产业化”,而最新的观点是“既是事业,又是产业”[12]双重角色。而实际上,广播电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个“稀缺资源”,本身就具有产业的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还原其本来面目,按经济规律办媒体也应是“政治家办报”的内涵所在,现在最大的政治就是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应把经济规律与政治理念完全对立起来,更不能人为地扼杀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而否认广电媒体产业化。但承认广电媒体是产业而反对产业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这种观点看起来是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分析问题,却有不合逻辑不顾实际的嫌疑。从逻辑上讲,如果广电媒体是产业了,当然不存在产业化的问题,提出“产业化”是因为我国广电媒体还不是定位在产业角色的现实困惑,要还其“产业”的面目,就得讲“产业化”。“双重角色”的定位是对转轨过程中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人们对现实的一种理想的期盼,同样是徘徊于政治话语的迷魂阵中,不敢“越雷池半步”,听使行政的使唤,背着产业规律而行,最终会使广电媒体步国有企业的后尘,陷入老化、冗员、低效的泥潭。对以上几个观点的分析实际上回答了广电媒体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
4.广电产业的特性
不同的产业都有自身不同的产业属性。与一般的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农业和其他服务性的第三产业相比,广电产业是特殊的产业,其产业特性应是广电媒体属性与产业属性相结合所决定的。因而,对其属性的认识,想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产业角度分析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二是从广电媒体属性角度分析广电产业的特性。
(1)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主要体现为信息组织属性、利益组织属性以及控制对象属性。信息组织属性是广电媒体所具有的收集、加工并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决定的,它是最本质的属性,使广电媒体相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决定了广电媒体具备成为“产业”的必要条件;利益组织属性是广电媒体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首先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生存,在此基础上,广电媒体产生了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行为以及追求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运营机制。利益组织属性使广电媒体必须按照其他产业基本的生存方式生存,是广电媒体具备成为“产业”的充分条件;控制对象属性是指广电媒体必然生存于一定社会环境中并且以信息传播为功能,成为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的控制对象而被制约和监控,决定了广电产业的特性。用“‘利益—控制’平衡”模式分析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问题会发现:在这一模式中,利益和控制二者力量的对抗和平衡,造成了广电媒体的三种形态:利益力量强则形成广电产业;控制力量强则形成意识形态广电媒体;二者在某种条件下达到平衡时,则形成信息、利益、控制三种属性上都有鲜明体现的产业化的广电媒体,我国广电媒体正朝力量平衡的产业化趋势发展。
(2)广电产业的特性。a.文化性与商品性。广电产业首要的属性是其文化性,生产特定的“文化产品”。“广播电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必然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既然如此,广播电视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与文化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广电业的发展也折射出文化母体遗传因子所赋予的种种规定性。”[13]这种规定性正是广电业在发展中所应遵循的规律。当文化与技术和市场融为一体的时候,文化作为一种产业也在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又将广电媒体推向了市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凝聚着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样具有商品的属性,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文化性与商品性两者并不是广电业的“矛盾所在”,正是有“文化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才使广电媒体有商品性的属性。b.公益性与盈利性。作为“准公共产品”,广电媒体应信奉“公共信条”,创造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14]这个论述说明了广播电视业有别于其他行业。但这也只是广电产业的一个方面,广电产业更为突出的应是其盈利性,能够创造经济效益,广电产业被人称为“最后一个的暴利行业”。[15]在认识公益性与盈利性中,人们习惯把两者对立起来,总以为经济效益的利润最大化必然违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运行准则,而实际上,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只是广电业不同社会定位中的两个不同层次,两者在不同层次中要求不同,在同一层面两者的要求是一致的,没有社会效益自然就没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为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作用。c.意识形态性与相对产业性。从上文的控制对象组织属性可知,广播电视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是“权力的人”[16],总体现意识形态要求。因此,广播电视虽然具有产业属性,应按市场规律办事,但同样也有政治属性的内在要求和意识形态的运行准则,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中的规律运行,因而其产业化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不可能完全产业化,至少现在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相对的产业化。但市场具有神奇的力量,意识形态性并不能阻止广电媒体向产业的方向迈进。
三、广电产业的法律视角
对广播电视的法律释义和广电产业特性的分析之后,现在再从法律的视野来看广电产业的特性,实际上也是从广电产业的特性角度来讨论法律问题。一方面要讨论广电产业与法律规范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广电产业的法律适用问题。前者实际是探讨产业化的规范问题,后者讲的是如何在规范中进行产业化。
1.广电产业与法治
以法治业是广电产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法对广电产业的产权关系、市场关系、利益关系、经营规则进行规范,保证了广电产业的健康发展,健全的法制还为广电产业发展创造健康、公正的外部环境,法制越健全越有利于广电产业的发展。没有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不可能保障广电产业的正常发展的。以美国为例,当代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就是继承了美国法治的传统,以法治业“从一定意义上,又保证了美国的电子传播产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能居世界的领先地位。”[17]另一方面,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法治”一词又经常被理解为依法办事。广播电视产业的运行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媒体权利与广电产业权利
“权利为由法律上之力保证实现的自由。”[18]媒体为争取自由,“历经被告到原告的历程”[19]。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美国1775年的《独立宣言》、1789的《宪法》都对媒体权利进行了规定。现在国际公约和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媒体权利,确认信息自由原则。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表述:“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通过任何媒体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20]是有关传媒的国际法进行分析、解释的基础和标准。在美国,媒体权利的法律渊源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21]这条法律被媒体广泛运用而成为一把有效的保护伞,是媒体权利最集中的体现。但权利总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英国法哲学家J·边沁(JeremyBentham)和德国法学家R·耶林(RudolfJhering)所主张的“权利的本质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权利的本质可定位于正当利益,或追求正当利益行为的合理依据。”[22]媒体既是“社会公共器”也是“创利大户”,随着以信息技术不断革新并广泛应用于广电媒体,信息成为受法律保护的财产,媒体权利在产业化过程自然表现为一种产业权利,要求法律保护其产业利益,赋予法律权利,当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
3.广电产业与产权
广电产业的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拥有广播电视”,即产权问题。什么是产权?我国法学界对产权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如认为产权是所有权;产权是物权;产权是经营权;产权是有关财产的一切权利,包括所有权各项权能、现代经营权以及知识产权等。[23] “产权是具有明确归属的财产在运用中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它可以按效益最优原则进行不同安排,而这种安排将影响处于其中的不同主体的行为方式,因此产权是现代社会资源运用的规则。”[24]因而,产权问题是广电产业法律制度的基础,不同的产权制度产生不同的广电产业管理体制,也决定了各国广电产业发展的差异。在广电产业化过程,各国都以产权改革来促进产业化,也是用产权制度来保障产业化的成果。
4.广电产业特性与适用法律问题
由于广电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其产业特性决定了法律调整的方式方法与其他产业应有所不同。法虽然是“抽象的、普通的”,但不同的法律调整对象自然应适合不同的法律规范。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广电产业如何适用法律?这个问题实际包括了三个子问题,一是现行调整产业的法律规范广电产业能不能适用呢?正如上所分析的,广电产业有其特性,当然需要特别法或专项法律进行调整。但也不能排除一些法律对广电产业某一领域的适用,或者说对其个别业务的调整;二是要考虑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法的适用具有普遍性,虽然广电产业的特性对法律有特别的要求,但现行的法律却没有特别的规定,“既定法律原则”会使广电媒体产业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法律障碍;第三,实际上还得考虑法律局限性问题。在讨论产业法治时,人们常常认为法律是万能的,以法律手段代替了经济、行政及其他手段,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也违背了法治的原则。
5.广电产业法律构建问题
这是讨论广电产业法律问题的归属点和最终目的,产业特性的法律适用问题及其他法律问题最终是要通过构建广电产业法律体系来解决的。问题的对策就是立法,构建法律或重造法律。而广电产业法律体系除了上面所讨论的产权制度外,至少应包含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播电视媒体属性的法律界定;二是广电媒体的管理体制;三是广电产业的政府管制问题;四是广电产业的市场运行规则;五是广电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法律协调问题;六是广电产业发展外部法律问题。
注释:
[1]黄升民、丁俊杰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媒体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刘爱清、王锋主编:《广播电视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5页。
[3]孙国华、朱景文等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4]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533页。
[5]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法规司编:《广播电影电视法规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668页。
[6]国家体改委等编:《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7]刘爱清、王锋主编:《广播电视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330-334页。
[8]王先庆著:《产业扩张》,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页。
[9]李晓枫、柯柏龄主编:《电视传播管理实务》,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10]吴文虎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11]黄升民、丁俊杰主编:《媒体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
[12]刘宏著:《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3]黄匡宇主编:《广播电视学概论》,暨南出版社,2000年,第122-123页。
[1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5页。
[15]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财经媒体的市场空间》,载江蓝生、谢绳武主编:《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16][美]Joseph Strausbhaar, Robert LaRose著,涂瑞华译:《传播媒体与资讯社会》,亚太图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17]胡正荣著:《媒体管理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279页。
[18]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19]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体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20][法]洛特非·马赫兹著,师淑云等译:《世界传播概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306页。
[21][美]T·巴顿、卡特等著,黄列译:《大众传播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22]张俊浩主编:《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第5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转贴于
第6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 学术依赖 非洲中心性 亚洲中心性 传播理论 文化特定性 去西方化 多样性 欧洲中心主义 人性 横截性
[摘要]:本文对欧洲中心的传播知识结构加以质疑,提出亚洲传播研究中亚洲中心性的合理性。文章的第一部分对人性、文化特定性和传播的本质及其交叉加以重新阐释;第二部分接着论述了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笼统化”(totalization)和“轻视化”(trivialization);第三部分对“亚洲中心性”的元理论概念加以阐明,证明其理论必要性。本文最后提出亚洲中心性对传播学术进行“去西方化”的五条途径。它们是:(1)形成与亚洲传播讨论相应的理论认识;(2)关注于亚洲传播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3)省察地构建及批判地改进亚洲传播的讨论;(4)对“如何在亚洲文化特定性中表达和理解人性的普遍特征”进行理论探讨;(5)对理论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加以批评,并且帮助亚洲研究者克服学术依赖。
把许多不同的原生纽带混为一谈,或是把它们统统归入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范畴中,这样的做法很常见,却把我们引入歧途,非常危险……种族、性别、语言(母语)、祖籍(故土)、阶层和宗教信仰都是我们作为“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们告诉我们自己是谁,并且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资源、让我们成为自己选择成为的样子。它们各自表达了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
——杜维明(1992,p. 338)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blematizes the eurocentric structure of communicative knowledge and advocates the legitimacy of asiacentricity in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article re-articulates the nature and intersection of humanity, cultural particularities, and communication. the second section then addresses eurocentrism as ideologies of totalization and trivialization. the third section clarifies the metatheoretical notion of asiacentricity and argues for its intellectual necessity. the present article finally envisions five ways in which asiacentricity de-westernizes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asiacentricity (1) generat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at corresponds to asian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2) focuses on the multiplicity and complexity of asian communicative experience, (3) reflexively constitutes and critically transforms asian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4) theorizes how universal aspects of humanity are expressed and understood in asian cultural particularities, and (5) critiques eurocentric bias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and helps asian researchers overcome academic dependency.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0; 6(2): 1-13]
keywords: academic dependency, afrocentricity, asiacentric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cultural particularities, de-westernization, diversity, eurocentrism, humanity, transversality
引言:文化遗产是力量之源
人性深植于人类最原生的纽带中;脱离原生纽带,人类的日常存在都将失去意义。正是这种原生的纽带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实在的人类;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表达(expression)的来源”和“压制(oppression)的来源”这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反思和重铸。这正是杜维明(2007)一直希望在当今这个全球化和本土化趋势并存的年代大力推崇儒家的智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原生纽带并不只是消极地限制我们,只有顺应它们,认识到它们同时也是力量源泉, 我们才能够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中获益,因为全球趋势其实是以根植于本土为基础的”(p. 143)。我们不应该舍弃这种原始纽带,而应该将之作为文化遗产而加以转化。我们的命运可能会受到它们的控制,但是“我们也拥有对其全部或是其中一部分加以超越、解构和重建的自由”(tu,1997,p. 179)。不过,在目前的后 现代 主义、后解构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思潮中,“原生纽带”和“文化特定性”只是被看作影响人们走向社会公平和全球伦理的障碍。
本文认为,如果非西方的传播研究者们忽视了杜维明的看法,不能从非西方的文化特定性出发对传播过程及传播原理加以 总结 ,那么非西方的传播学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亚洲传播进行亚洲中心的研究对于亚洲人的共性特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亚洲人一直基于亚洲文化特点进行交流活动。但这一点被忽视了。本文希望通过质疑“非西方学术世界中的欧洲中心知识结构”、详述亚洲中心性在对传播研究进行“去西方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证实以上论点。本文的第一部分对人性、文化特定性和传播的本质及其交集加以重新阐释;第二部分对欧洲中心主义作为“笼统化”(totalization)/“轻视化”(trivialization)思想方式的身份进行了定义,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中心的知识帝国主义是世界传播学术 发展 的障碍”;第三部分对“亚洲中心性”的元理论概念加以阐明,证明其理论必要性。本文最后提出亚洲中心性对传播研究进行“去西方化”的五条途径。
人性、文化特定性和传播
lee thayer(1997)说得好,传播是“我们获得人性的过程——不管人性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p. 207)。在他看来,说话和理解的方式——即“传播”——就是做人的方式。确实,chen和miike(2008)曾假设,传播与我们做人的深层感觉密不可分。传播构建了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对于未来的展望;而与此同时,所有这些也构建了传播。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轻易地改变自己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行为。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的话,也许,没有什么比传播更难研究、更难提高了。
对人类传播进行理论总结就是对人性得以表达和理解的方式加以考察。人性得在文化特定性——而不是普遍的抽象性中得到深切体会。因此可以说,传播是人性的一种文化特定性表达。比如说,大多数基本情感(比方在这里用 英语 说“love”)也是以特定的语言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表达的,伴随着特定的经验累积。goonasekera和kuo(2000)提出,亚洲传播专家们应该探讨“探究意义的普遍性过程如何在亚洲的文化环境中进行”。他们说:
所有人都以一定的符号/意义为基础进行传播。所有人类社会都以一定的语言进行传播。人类是寻找意义、创造意义和阐释意义的生物。意义的阐释和协商是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对于人类传播活动具有中心性……意义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定义也取决于文化的条件。因此,要想理解传播的过程,研究者们必须考虑传播发生的文化环境以及文化特定性因素。(pp. xi-xii)
意义对任何传播行为来说都至关重要,总是在“日常的具体存在”中得以建构和解构。这种日常的具体存在与人类交流相连,与群体共同记忆及文化行为交织在一起。杜维明(2007)指出了意义的这种特定性本质:
意义与传统智慧密不可分;对“什么是意义”的判断通常与对“真善美”的深层感受混合在一起。意义并不要求“抽象普遍”——它甚至反而会淡化由意义编织的织物的层次丰富的纹理。意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日常的具体存在”。无论如何精心设计,一个丰满的意义也没办法分解成一串干巴巴的命题。在意义的建构过程中,总会存在语言之外的东西。语言永远无法彻底捕捉到说话的人/写作的人想表达的意义。意义可以被视成一种内心经历,即使它永远无法向外人充分阐释。与意义的阐释相伴随的“具体性”使意义无可避免地具有特定性。不过,据此而认为“意义作为本土知识的一种形式永远无法获得普遍性的特点”是错误的。相反,对在特定环境中意义中的“深度描写”极具普遍性的诉求。(p. 80)[1]
杜维明(2007)的话见地深刻,暗示意义的本质具有文化特定性,但是又可以与他人分享、具有普遍性。最具体的也可以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是,普遍性和特定性不是对立的,而是连续的。ngũgĩ wa thiong’o(1993)曾证明,“普遍寓于特定之中,特定亦寓于普遍之中”(p. 26)。因此,传播学者们没必要因为要追求人类的普遍性而回避文化特定性(miike,2006)。他们应该分析和解释,人类的共同特性是如何在文化内/跨文化传播的复杂环境中与文化特定性相互交织的。
基于以上对人性、文化特定性和传播的讨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建立世界性传播理论,传播学者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出西方和非西方的‘真理’(或者说总结概括)、从而让获得知识的人可以将之运用于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这样的看法过于浅薄。我认为,传播专家们必须考虑到“普遍性-特定性”、“抽象-具体”以及“人类共性-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交集和互动。甚至当专家们发展出看似具有综合性的“抽象”传播理论时,他们仍然不得不在更深层次上、以更为详细的方式对“具体”文化特点加以总结归纳,从而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理论(见starosta,2006)。正是这一至关重要的观点指导我们,必须对存在于非西方传播研究中的现有欧洲中心主义知识结构加以挑战和改变。
作为“笼统化”(totalization)/“轻视化”(trivialization)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
everett m. rogers(1982,1999)认为有两种长期存在的“分歧”制约了传播学术的发展:(1)人际研究和媒介研究的分歧;(2)实证主义学派和批评主义学派的分歧。这些学术分歧至今仍然普遍存在。在这一方面, 台湾 国立 政治 大学于2008年12月13-14日举办了主题为“传播研究的去西方化:何以为继?”的国际会议,意义深远。无论其研究是专注于人际传播还是媒体传播,无论其方法论是受实证主义还是批评主义的指引,绝大多数与会学者(如asante,1998,2006,2007a;chen,2002,2006,2008;chu,1988;gunaratne,2008,2009;lee,2008;kim,2002;shi-xu,2008,2009;wang和shen,2000)都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非常警惕,共同讨论了“如何对理论和研究‘去西方化’”的问题。从会议议程中可以看出,无论研究方向和方法导向如何,西方和非西方的学者们都十分关注传播学及整个人文 科学 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见alatas,2006;asante,1999;wallerstein,1997)。
就syed farid alatas(2002)看来,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是指“受欧洲唯一性和优越性思想灌输而形成的价值观、态度、观点及思想导向”(p. 761)。alatas(2002)还说,欧洲中心主义包括“从源自欧洲经验的模式、范畴和概念出发来理解欧洲以外的 历史 和社会的一种趋向”(p. 761)。maulana karenga(2002)将欧洲中心主义定义为“一种支配和排外的思想和行为;其基础是认为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以欧洲文化和欧洲民族为中心,其他所有文化和所有民族最多只处在边缘地位,甚至是毫不相干的”(pp. 46-47)。“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不应与“欧洲中心性”(eurocentricity)相混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作为一种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思想形态,是指对非西方传统中的非西方世界和人民抱有种族优越感。而“欧洲中心性”(eurocentricity)作为一种带有特定性的视角,是对欧洲文化和欧洲人进行合理的文化中心考察。不过,当地域性带上普遍性的面具,贬低非西方的想法占了上风,“欧洲中心性”就变成了“欧洲中心主义”(asante,2006;miike,2008a)。
shi-xu(2009)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并不限于西方世界。令很多善于反思的学者和 教育 家(如alatas,2006;banerjee,2009;chen,2002;chen和starosta,2003;chesebro,1996;gordon,2007b;gunaratne,2008,2009;edmondosn,2009;ishii,2008a;jackson,2002;miike,2006,2010;miyahara,2004;lee,2008;starosta,2006;tanno,1992;yin,2006,2009)感到痛心的是,很多研究者在学术上非常依赖欧洲中心、特别是欧美中心的理论发展和研究合作。其批评实事求是,非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学术的过度依赖实际上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chesebro,kim和lee(2007)指出,在chung,jeong,在chung和park (2005)所分析的在美国和韩国曾出版的关于两国的传播研究的782本书中,韩国独特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地理特点并没有在韩国传播研究的主流理论中得以体现。相反,美国和韩国两国在传播方面拥有相同的研究主题和理论概念。wang和shen(2000)注意到:“全球化趋势迫使人们不仅要直面‘他人’,而且要直面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在群体里居于什么‘位置’?我们向何处去?”(p. 26)。尽管已到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他们还是怀疑“亚洲传播学者们可能不一定对其文化中的 哲学 与传统拥有足够深刻的认识,从而了解‘自己是谁’,更不要说与传播研究相关的哲学思想了”(p. 26)。
欧洲中心学术有两个主要问题(miike,2007b)。其一,欧洲中心范式总是声称自己是“人类”范式,忽视了非欧洲中心思想的存在。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理论命题本身,而在于它倾向于单方面地设定普遍性、将一切笼统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中心主义“本质化了”(essentialize)人类经验,好像所有人都是欧洲裔、都说欧洲语言,好像所有的社会形态都仅受欧洲宗教-哲学传统的影响,好像所有人都勉强生存在欧洲历史轨迹的边缘。其二,欧洲中心范式总是因为其文化根源和文化导向而青睐某一些现象、忽视另一些。结果,欧洲中心范式忽视、低估、或者说掩盖了非西方历史文化中所包含的某些价值观和某些内容。欧洲中心理论对非西方世界缺乏共鸣,源于“笼统化”(totalization)/“轻视化”(trivialization)这两种欧洲中心思想方式。不管是那一种情况,欧洲中心学术都未能从非西方的文化特定点和传播特定点出发对非西方的人性观点和人性视角加以理论总结。
为了将不同的传播理论整合统一,robert t. craig(1999)提出一种带有根本构成性特点的元模式。他提出,“所有的传播理论都和具有普遍实践性的生活世界相关,其中‘传播’已经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概念”(p. 120)。从craig的观点(1999)看,传播理论是“一个有条理的元论证的领域,即是一个讨论对传播实践讨论的领域”(p. 120)。说得更简单些,传播理论是关于日常生活中传播问题和传播行为的元论述。如此,传播理论就是对一定的传播行为的反映、充实、批评、指导、甚至是教化。
因为未对亚洲及其他非西方文化特定点和传播特定点加以理论考察,现有的欧洲中心传播理论既不能准确地反映亚洲及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传播现实探讨,也不能全面地加以回应。更不用说对亚洲和其他非西方的传播探讨进行有价值的建设或是有意义的指导了。事实就是这样,无论那些理论是社会科学性的、阐释性的、还是批评性的。事实上,那些理论的词汇、哲学基础和历史考量,离以亚洲及其他非西方文化特点/日常具体生活为表达基础的传播理论非常遥远。这是在这种学科背景下,亚洲中心性(asiacentricity)的元理论意义在亚洲传播研究中才显现了出来。
亚洲中心性的理念及其理论必要性
最近十年中,我提出并勾画了亚洲中心性的理念,作为对亚洲传播研究进行“去西方化”以及从亚洲文化特定点和传播特定点出发探讨亚洲人性观念的一条途径(见miike,2006,2007c,2008b,2008c,2010)。我的“亚洲中心性”(asiacentricity)观点——不是“亚洲中心主义”(asiacentrism)——得益于molefi kete asante(1998,1999,2007a,2007b,2008)提出的“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如果不能领会asante的非洲中心性元理论(见jackson,2003;karenga,2008;miike,2008a),那么关于亚洲中心性的任何讨论都没有意义。asante在数年时间中提出了非洲中心性的多种定义。最近,他将“非洲中心性”定义为“一种涉及分析和实践意义的思想性质的范式,其中非洲人是现象的主体和自主者,而这些现象又是发生在非洲人自己的现实、文化形象和人性兴趣的环境之中”(asante,2007a,p. 59)。[2]根据asante(2007a)的看法,非洲中心性的工作至少有五个特点:(1)对心理定位感兴趣;(2)决心找出非洲的主体位置;(3)护卫非洲文化元素;(4)致力于语言的提炼;(5)献身于对非洲进行全新的描绘。
在仔细回顾了asante的众多著述之后(miike,2008a),我从廓清概念的角度归纳出了亚洲中心性的六个方面。亚洲中心性是(1)对亚洲人作为主体和自主者身份的确定;(2)在对亚洲世界进行知识重建的过程中,将亚洲和亚洲人的共同兴趣和人性兴趣放在中心位置;(3)在探寻亚洲思想和亚洲行为时,将亚洲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理想放在中心位置;(4)以亚洲的历史经历作为背景;(5)以亚洲语境为导向;(6)对亚洲人和亚洲现象的混乱和失位进行亚洲道德标准的批评和纠正(miike,付印中-a)。因此亚洲中心理念要求:(1)在描述中将亚洲人/亚洲文本作为主体和自主者;(2)在有关亚洲人及其经历的探讨中以亚洲利益、价值观和理想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3)在其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之语境中考察亚洲人、亚洲文本、亚洲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主体”(subject)和“自主性”(agency)这两个概念在这里有“自我定义”、“自我决定”、“自我表现”之意。主体(subject)和客体(object)的差异与“我们如何看待一个人、一份文本、一种著作”的方式有关。我们不应该先把人、文本、著作当成分析和批评的客体,然后对他们加以仔细考察;而是应该真诚地把他们视为有自己声音的主体,他们在向我们讲述关于自身文化世界的故事。“自主性”(agency)这一概念让我们注意到主动(activeness)和被动(passiveness)的差别,提醒我们发掘一个人或一个人在文本/著作中的主动性(activeness)和主体性(actor-ness),而非被动性(passiveness)和旁观者性(spectator-ness)。不仅如此,在亚洲中心性的工作中,文化“中心”的概念不应该被误解为仅是一种或多种亚洲文化的纯粹“本质”。虽然“亚洲中心性”是亚洲人的共享身份和共同表现,但是提倡亚洲中心性的人们并非意图在亚洲制造出仅有的“一个”中心。他们不是文化本质论者。asante(2007)和karenga(2002)曾指出非洲中心性的问题,亚洲中心性也是一样。作为一种思想的性质——而不是思想本身——亚洲中心性规范了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而不是“内容”。亚洲性(asianness)的问题在亚洲中心的研究范畴中居于中心位置,可是什么构成了“亚洲性”是可以继续探讨辩论的。
对于就非洲和亚洲的现象进行非洲中心和亚洲中心的研究,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误解。其一认为这种研究无益于泛文化理论建设。其二认为这种研究和欧洲中心一样,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其三认为这种研究总是与欧洲中心的方法相左。如前所述,人性的普遍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不是相对立的,而是连续的。因此,带有文化特定性的研究可以对文化普遍性研究进行补充,从而对泛文化理论发展做出贡献(chen和miike,2008)。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不是霸道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反面版本(asante,1999;miike,2008b,2008c),并不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上,更不会将自身的文化世界观定位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思考框架而强加于人。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并不否定其他文化视角对于非洲人和亚洲人的价值。要想获得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就必须根植于非洲和亚洲的文化/传播特定点。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也并不意味着总是与欧洲中心性唱反调;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不是要与其他文化中心针锋相对(asante,1999;miike,2007b,2009b)。因此,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不是民族中心主义、不是文化沙文主义、也不是文化分裂主义。
当我们将亚洲中心性的理念运用于重新理解、重新描述和重新看待亚洲文化和亚洲传播时,它就会指导研究者们将亚洲文化看成亚洲中心之慧眼和灵感的中心源泉,而不是为非亚洲中心的分析和批评提供边缘目标。换句话说,亚洲中心性坚持认为,应该将亚洲文化视为亚洲中心知识重建的理论依据,而不是非亚洲中心知识解构的文本素材。虽然以前的一些著述有相同或者类似的亚洲中心学术思路(见miike,2009a;miike和chen,2006),但是“作为文本的文化”和“作为理论的文化”(这里或者说是“亚洲声音的亚洲来源”)的区别为亚洲的新传播学术引入了新的理论视野。亚洲中心性具有理论必要性,因为要想理解、领会甚至是批评亚洲的人性观点和传播行为,理论研究者们就必须更为集中地深入亚洲文化特点及具体日常生活。
“去西方化”过程中亚洲中心性的作用
更为明确地说,亚洲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中心性在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对现有理论研究进行了“去西方化”和革新,它们是:(1)形成与亚洲传播讨论相应的理论认识;(2)关注于亚洲传播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3)省察地构建及批判地改进亚洲传播讨论;(4)对“如何在亚洲文化特定性中表达和理解人性的普遍特征”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讨;(5)对理论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倾向进行批评,并且帮助亚洲研究者克服学术依赖。
首先,亚洲中心性形成与本土传播讨论相应的理论认识,而这种本土关于传播的讨论与亚洲人实际的传播问题和传播行为相关。亚洲中心性让我们可以建设新的传播理论,从而与通过亚洲文化特点而进行表达和交流的传播语境相应。亚洲中心的必需性将可以带来众多理论词汇,这些词汇在实践上具有启发性和实用性,可以和亚洲人具体的传播经历产生共鸣。这要求本土的传播研究者进行理论总结时意识到:亚洲人是“说亚洲语言的”、“受亚洲宗教-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努力生活在亚洲历史经历中”。
west和turner(2010)将理论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概念系统,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现象”(p. 46)。因此,任何理论识的核心都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和一系列高深的命题。正如dissanayake(2007)所说,“以文化为背景的概念……包含了文化价值观、文化认识论、文化逻辑,身上都贴着源自其文化源头的标记”(p. 225)。miike(2008c,2010)特别将文化的语言、宗教-哲学及历史方面视为发展亚洲本土传播概念/命题的根本。陈国明(2004a)在其编著中(参见chen,2004b)致力于对一系列源自 中国 传统的文化概念加以整理和明确,从而推动中国传播理论的发展。我们会看到,有关其他亚洲文化的类似理论研究将在发展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比如在韩语的日常表达中,有nunchi ga bbarda和nunchi ga eupda[3]的说法;对之加以仔细分析会发现,nunchi是韩国本地有关传播理解力、敏感性和期待的本土概念。我们可以从韩国的视角建立起一种有关韩国nunchi传播的原创理论。
第二,亚洲中心性关注于亚洲文化环境中有关不同传播经历的多种亚洲声音。在亚洲中心学术中探求亚洲文化特点和亚洲传播特点,提倡将传播现象放置于文化历史的环境中而研究。因此,亚洲中心性可以更为透彻的把握和表述亚洲人在不同环境中进行传播的共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见holmes,2008)。过去对亚洲文化和亚洲传播的描述、理解和评价很大程度上更注重精英、以男性为中心、以异性恋为主导、偏向城市、而且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chen和miike,2008;goonasekera,1995;yin,2006,2009)。在亚洲传播研究方面,正在兴起的、未来的声音将更多地来自一般阶层、少数名族、女性、同性恋、以及侨居群体。以地区——而不是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将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以前对亚洲传播者和亚洲传播活动进行的本土理论总结更多地集中在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上(见chen和miike,2003;dissanayake,1988;kincaid,1987;miike,2009a,2009c;miike和chen,2006,2007)。在现有著述中,对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展示还远远不够,需要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进行大量的持续的分析(miike,2006)。
此外,要对亚洲传播现象进行更为细致切近的理解,另一条路就是利用亚洲中心的比较(比如说,亚洲的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之比较,印度人视角和斯里兰卡人视角之比较)。比如说,palencia-roth(2006)探究了菲律宾人的“kapwa”概念和儒家的“仁”,借之以理解菲律宾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自我”的概念。类似的,storz(1999)对马来语中的“budi”概念和儒家的“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们的这种亚洲中心比较激发了更多的针对亚洲人性观点的思考和研究。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以比较的方式考察了菲律宾的pahiwatig-pakikiramdam传播(见mataragnon,1988;mendoza,2004),日本的enryo-sasshi传播(见miike,付印中-b),泰国的以kreng jai为导向的传播和中国以“客气”为导向的传播,值得关注。同理,杜维明(2008)曾强调“非常严肃地将印度作为参照性社会,可以使中国收益匪浅。在理解中国自身本土传统(比如大乘佛教和道教思想)时,这种参照可以极大地拓宽中国的符号资源”(symbolic resources p. 332)。亚洲中心性的原则可以让亚洲传播学者们不再盲目地依赖欧洲中心理论,不再受欧洲中心研究进程的制约,因而不再有意或无意地从欧洲中心的角度看待亚洲文化。于是,亚洲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们将能够对亚洲传播的复杂及微妙之处有更为深入的理解。chen和starosta(2003)的话言简意赅,“一个新的中心可以让世界传播版图关注欧洲之外的东西”(p. 2)。
第三,亚洲中心性省察地构建及批判地改进亚洲传播讨论。欧洲中心的文化批评家们总是喜欢将非西方的传统看作压制的源头而加以质问和苛责,认为亚洲国家和亚洲地区缺乏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平。不过由于他们的知识说教脱离亚洲的具体日常生活,因此他们想通过这种欧洲中心的质问来产生社会变革的“正当”意图也就当然是收效甚微的了。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传播理论与传播行为不可分离。craig和muller(2007)曾敏锐地观察到,“理论总结是对日常生活中生成意义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加以正式的延伸”(p. ix),我也觉得是这样。在craig和muller看来,作为理论性元讨论(metadiscourse)[4],传播理论是与我们关于日常传播行为讨论的对话。传播理论是传播元讨论的一个开放性领域。传播的理论性元讨论和日常讨论之间的互动是源源不息的。
dissanayake(2009)指出,我们必须既把文化看成一个共享体系、也将之视为冲突之地,意义在这里得以构建、解构和重建。当然,文化就像人类一样,是活的;人们对其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必须再次强调的是,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的不同意义不是通过具有抽象的普遍性、而是通过文化的特定性而得以解构和重建的。如果不能使用具有文化特定性的语言,我们就不能推进文化变革。亚洲中心性迫切要求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们在其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对不同的亚洲文化分别加以定位,认识到他们作为群体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以更为全面的方式领悟(而不仅仅是分析)亚洲文化,倾听以前所没有听过以及被压抑的声音,通过将亚洲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理想置于中心地位从而学习其人性观点。亚洲中心的求知方式不仅仅是对亚洲文化进行描绘,而且还将重新发现、重新展示亚洲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元素,创造性地改进亚洲一些弊病陋习,向世界推出一个新的亚洲(miike,2010;yin,2009)。因此,我们是可以对亚洲传播进行亚洲中心的批评性研究的。
第四,通过对“如何在亚洲文化特定性的背景中表达和理解人性的普遍特征”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归纳,亚洲中心性将文化特定性和人类普遍性联系在一起。tanno(2008)说得很对,“我们的研究语言应该反映多样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所有的文化都会受到哲学思想、使骨肉分离之事以及增强凝聚力之传统仪式的影响”(p. 34)。亚洲中心的理论追求是要从全球视角更为全面地理解人性的多样,从而帮助我们在添加了亚洲版块之后绘制出更为完整和全面的人类传播图景(miike,2007b)。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可能要分三步完成这一极为重要任务:(1)充实不同亚洲文化中的传播概念;(2)进行亚洲中心的跨文化分析,从而对亚洲内部之异同加以思考和描述;(3)对来自亚洲文化的传播概念和来自其他非西方/西方文化中的传播概念进行比较和对比。
亚洲中心的研究事业还培育了有关亚洲世界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以本土为背景,可能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本着分享而不是强加的原则,亚洲中心的存在、认识和评价方式可以为非亚洲文化世界提供一面镜子(miike,2007a,2009b)。对于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来说,其理论事业正如immanuel wallerstein(2006)所强调的那样:
要成为一个“非东方主义学者”,就意味着要接受“必须对我们的理解、分析、价值观加以普遍化”和“必须护卫各自不同的根本,防止声称推进普遍性的外来者侵犯到我们特有的理解、分析、价值观”之间持续存在的矛盾。我们得既对自己的特点加以普遍化、又对自身的普遍特征加以特定化,这两方面须以一种持续的辩证交流的方式齐头并进。这可以让我们找到新的契合点,当然也会马上带来问题。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pp. 48-49)[5]
最后,亚洲中心性对传播理论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倾向进行批评,并且帮助亚洲研究者克服“学术依赖”(alatas[2006]语)。亚洲中心性使亚洲传播学者们可以发现前面提及的两种欧洲中心倾向,同时成为亚洲传播现实的原创理论家,而不是跟在欧洲中心传播理论后面亦步亦趋。学术依赖性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存在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alatas(2006)指出这种学术依赖性的六个方面:(1)对理念的依赖;(2)对理念媒介的依赖;(3)对教育技术的依赖;(4)对研究和教育援助的依赖;(5)对教育投资的依赖;(6)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依赖西方,采用他们的技术。当我以批评的眼光注意到这是一个麻烦而又复杂的问题时,我相信,只有当亚洲知识分子们真正拥有了亚洲中心的自觉、将其自身的文化环境转变为理念创新的宝库时,这种学术依赖才能被克服。
chen(2009)、chung和ho(2009)、edmondson(2008)、gunaratne(2008,2009)、kosaka(2008)、ishii(2008b,2009)、xiao和chen(2009)等学者最近的理论研究正是如此。他们证明了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可以对人性的本质和理想进行深刻的反映,从另一个角度为理论探索做出了贡献。gordon(2006)认为,西方传播理论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学派——过于“强调人类传播的信息方面:信息策略,信息准备,信息组织,信息传递,信息接收,以及整体的信息效应”(p. 17),未能对人和环境的因素进行充分的关注。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对“作为各种关系之中心的自我”(tu,2001)、对超 自然 和自然界的声音更为敏感,应该在传播研究的转型时期描绘出新的研究图景。如gordon(2007a)所说:
我们面临一个转型时期,不能继续仅仅将“传播”主要视作策略性的、受目的驱动的、扩张自我、保护自我的功利性信息传递行为。这种传播概念虽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妨碍我们发展更为健康的传播视角、传播态度和传播行为。我们需要的“传播”语言得少一些“自由的个人的”(agentic)、多一些“社群性”(communal)[6],少一些“阳”、多一些“阴”,少一些“影响”和“劝说”、多一些“共鸣”与“和谐”,少一些“自说自话”、多一些“对话交流。”(p. 100)
尾声:人性、多样性和横截性
hwa yol jung(1995,2004,2006,2009)曾详细阐明“横截性”(transversality)这一新概念,将之视为认识知识和伦理的一种全球方法。calvin o. schrag对这种传播理念进行了阐发,从而用以解决诸如“相同与相异”、“统一与多样”、“现代与后现代”等二元问题。与已经得以广泛使用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概念不同,“横截性”(transversality)说的是与“跨越”和“相交”有关的问题;它原本是一个几何学概念,是指一条直线与两条及两条以上的直线相交,或与一组直线相交。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一种新思路,“横截性”(transversality)是指“跨越不同文化边界的真理相交地带:这是以跨文化方式思考真理的一种方法”(jung,1995,p. 15)。因此,实现横截统一是“传播的一种成就,因为它是经历了多种不同的观点、视角、信仰体系和地域因素的结果”(jung,2009,p. 29)。“横截性”的境界就是chen(2006)所谓“道”的状态,“对真理进行民族中心主义式的垄断性思考应该停止,人性可以在不同文化的聚集体中繁衍不绝”(p. 306)。
在对人性、多样性和传播进行理论研究时,横截性观点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应该克服或者说超越打着普遍性名头的欧洲经典真理(european cannon of truth. jung,2004,p. 16)。从非洲中心的角度看,asante(2006)严肃地指出“假定……历史起源于欧洲,或者认为只有写欧洲的事情才算写历史,都是对人类学术的大不敬。当‘特定’转变为‘绝对’,我们不可避免地站在了冲突的风口浪尖”(p. 146)。虽然西方真理常常被看作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横截观点要求传播学者和研究者们仔细考察西方真理的文化特性,并且超越有关普遍真理的这种欧洲中心建构。用wallerstein(2006)的话来说,应该从“欧洲的普遍主义”转向“普遍的普遍主义”。
第二,与普遍性不同,“横截性”为同时研究探讨人类共性和多样性创造了可能。palencia-roth(2006)所言极是,与别的直线横截相交的直线本身并不因相交直线而改变轨迹:“用价值论的话来说,横截价值观是跨域两种或者更多种文化的价值观,对于不同文化来说具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又并不会转化成普遍性的价值观。一种文化横截性要想保持其横截特征,就必须保持其特定之处”(p. 38)。因此,每种文化都在维持自身历史传统之特定存在的同时,又在不同的时空下与其他文化相交汇。传播研究者们需要对人类共性与多样性的这种交汇加以解释和描绘,从而对本土群体和全球社会中的传播与关系加以思考。横截性观点要求人们既要研究特定性中的人类共性、也要研究人类共性中的特定性(miike,2007b,2008c)。
毫无疑问,人性、多样性和横截性将是未来全球传播学术的关键。传播研究的任何领域都无法拒绝人类共性和文化多样性,都必须将自身定位于这二者之间。亚洲中心的研究方法将和非洲中心及其他中心的研究方法一道,产生出具有横截性特点的知识,引领我们对人性、多样性和传播获得更为细致的领悟。亚洲中心性将在解构普遍真理、重建横截现实方面有所作为;本文即意在对亚洲中心性的这种正在出现和正在发展中的作用加以重申和展望。本文再次论述了人性、文化特定性及传播之间无法分割的联系,阐明亚洲中心性的元理论概念及其理论必要性,同时列出了亚洲传播的亚洲中心性研究对现有理论研究进行“去西方化”的五条途径。
[注释]
[1]译者注: 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是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由clifford geertz 提出的(见geertz 的著作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深度描写是指要以一个文化本身成员的视角来研究描述这个文化。与之相反,浅度描写(thin description)是传统上人类学者以自己(外来人)的视角去研究一个文化。
[2]译者注:思想性质的范式是关于思想的性质和质量的讨论。就是说asante讨论的并不是什么非洲思想本身,而是何谓从非洲人民文化为视角的思想。
[3]译者注:在韩语中,nunchi是“体会、感知”的意思,ga是“是”的意思,bbarda是“很快”的意思,eupda是“没有”的意思。因此,“nunchi ga bbarda”的意思接近于“很快心领神会”;而“nunchi ga eupda”接近于“没有领会”。其实还有“nunchi ga idda”的表达,其中“idda”是“有”的意思,和“eupda”(没有)相对。因此,“nunchi ga idda”接近于“能够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之意。
[4]译者注:元讨论(metadiscourse),或者更贴切地译为后讨论,超讨论,指的是对关于某现象讨论的讨论。
[5]译者注: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edward w. said提出的概念,是指一种始于欧洲殖民时期的思想,它将中东及远东地区视为西方的对立面,是一个神秘,怪诞,色情,缺乏人性,毫无理性的世界(见edward w. said 的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在欧美的社会及学术界中依然盛行。
[6]译者注:对于“agentic”和“communal”这一组概念,国内的翻译并不统一。此处参照邹德强等著《功能性价值和象征性价值对品牌忠诚的影响:性别差异和品牌差异的调节作用》一文中对这两个词的译法。见《南开管理评论》2007 年10 卷,第3 期第4-12 页。
[ 参考 文献 ]
alatas, s. f. (2002). eurocentrism and the rol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european legacy, 7(6), 759-770.
alatas, s. f. (2006). alternative discourses in asian social science: responses to eurocentrism. new delhi, india: sage.
asante, m. k. (1998). the afrocentric idea (rev. ed.).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asante, m. k. (1999). the painful demise of eurocentrism: an afrocentric response to critics.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asante, m. k. (2006). afrocentricity and the eurocentric hegemony of knowledge: contradictions of place. in j. young & j. e. braziel (eds.), race and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cultural amnesia in the academy (pp. 145-153).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asante, m. k. (2007a). an afrocentric manifesto: toward an african renaissanc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asante, m. k. (2007b). communicating africa: enabling centricity for intercultural engagement. china media research, 3(3), 70-75.
asante, m. k. (2008). th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frocentricit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m. k. asante, y. miike, & j. yin (eds.),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pp. 47-55). new york: routledge.
banerjee, i. (2009). asian media studies: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n d. k. thussu (ed.),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 (pp. 165-174). london: routledge.
chen, g.-m. (2002).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y. in w. jia, x. lu, & d. r. heisey (eds.),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reflections, new frontiers, and new directions (pp. 255-268). westport, ct: ablex.
chen, g.-m. (ed.). (2004a).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taipei, taiwan: wunan.
chen, g.-m. (2004b). the two face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the pacific and a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7(1), 25-36.
chen, g.-m. (2006).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what and where to now.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6(4), 295-311.
chen, g.-m. (2008). toward tran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 harmony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4(4), 1-13.
chen, g.-m. (2009). toward an i ching model of communic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5(3), 72-81.
chen, g.-m., & miike, y. (eds.). (2003).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special issu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2(4), 1-218.
chen, g.-m., & miike, y. (2008). the ferm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asia: 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j. z. edmondson, trans.). in j. z. edmondson (ed.),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pp. 62-86). hangzhou,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chen, g.-m., & starosta, w. j. (2003).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a dialogu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2(4), 1-15.
chesebro, j. w. (1996, december). unity in diversity: multiculturalism, guilt/victimage, and a new scholarly orientation. spectra: newsletter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32(12), 10-14.
chesebro, j. w., kim, j. k., & lee, d. (2007).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 in power and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china media research, 3(3), 1-13.
chu, l. l. (1988). in search of an orient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in christian academy (ed.), the world communit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vol. 2.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pp. 2-14). seoul, south korea: wooseok.
chung, j., & ho, m. (2009). public relations, i-ching, and chi (qi/ki) theory: a new model from an old philosophy. china media research, 5(3), 94-101.
chung, w., jeong, j., chung w., & park, n. (2005). comparison of curr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tatu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orea.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5(1), 36-48.
craig, r. t. (1999).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 9(2), 119-161.
craig, r. t., & muller, h. l. (eds.). (2007).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readings across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dissanayake, w. (ed.). (1988).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dissanayake, w. (2007). re-privileging asian cultural concepts: reflections on edwin thumboo’s poetry. in e. thumboo (eds.), writing asia: the literatures in englishes (vol. 1, pp. 214-226). singapore: ethos books.
dissanayake, w. (2009). the desire to excavate asian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one strand of the history.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4(1), 7-27.
edmondson, j. z. (ed.). (2008).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hangzhou,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edmondson, j. z. (2009). testing the water at the crossing of post-modern, post-american and fu-bian flows: on the asiacentric schoo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china media research, 5(1), 104-112.
goonasekera, a. (1995).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contemporary societies in asia. media development, 42(2), 21-24.
goonasekera, a., & kuo, e. c. y. (eds.). (2000). towards an asian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special issu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2), 1-123.
gordon, r. d. (2006). communication, dialogue, and transform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the pacific and a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9(1), 17-30.
gordon, r. d. (2007a). beyond the failures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y.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2(2), 89-107.
gordon, r. d. (2007b). the asian communication scholar for the 21st century. china media research, 3(4), 50-59.
gunaratne, s. a. (2008). falsifying two asian paradigms and de-westerniz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 1(1), 72-85.
gunaratne, s. a. (2009). globalization: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the bias of social science/communication oligopoly.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 2(1), 60-82.
holmes, p. (2008). foregrounding harmony: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oices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new zealand peers. china media research, 4(4), 102-110.
ishii, s. (2008a). human-to-human, human-to-nature, human-to-superna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ward developing new fields of scholarship (in japanes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view, 6, 9-17.
ishii, s. (2008b). promoting interreligious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rising rationale. human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the pacific and a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1(2), 133-144.
ishii, s. (2009). conceptualizing asian communication ethics: a buddh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4(1), 49-60.
jackson, r. l. (2002). exploring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negotiation in the academy: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vision of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3(1), 43-57.
jackson, r. l. (2003). afrocentricity as metatheory: a dialogic exploration of its principles. in r. l. jackson & e. b. richardson (eds.), understanding african american rhetoric: classical origins to contemporary innovations (pp. 115-129). new york: routledge.
jung, h. y. (1995). the tao of transversality as a global approach to truth: a metacommentary on calvin o. schrag. man and world: a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review, 28(1), 11-31.
jung, h. y. (2004). the ethics of transversal communication. 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 5-21.
jung, h. y. (2006). transversality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ex/change: newsletter of the center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6, 11-17.
jung, h. y. (2009). transversality and public philosoph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j. y. park (ed.),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and cross-cultural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hwa yol jung (pp. 19-54).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karenga, m. (2002). introduction to black studies (3rd e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sankore press.
karenga, m. (2008). molefi kete asante and the afrocentric initiative: mapping the terrain of his intellectual impact. in a. mazama (ed.), essays in honor of an intellectual warrior, molefi kete asante (pp. 17-49). paris, france: editions menaibuc.
kim, m.-s. (2002). non-western perspectives on human commun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kincaid, d. l. (ed.). (1987). 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kosaka, t. (2008).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zen rhetoric. speech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 journal of th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japan, 21, 55-67.
lee, p. s. n. (2008). the challenges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asia. in i. banerjee & s. logan (eds.),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 2008 (pp. 58-66).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mataragnon, r. h. (1988). pakikiramdam in filipino social interaction: a study of subtlety and sensitivity. in a. c. paranjpe, d. y. f. ho, & r. w. rieber (eds.), asian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pp. 251-262). new york: praeger.
mendoza, s. l. (2004). pahiwatig: the role of “ambiguity” in filipino american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m. fong & r. chuang (eds.), communicating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pp. 151-164).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miike, y. (2006). non-western theory in western research? an asiacentric agenda for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6(1/2), 4-31.
miike, y. (2007a). an asiacentric reflection on eurocentric bia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4(2), 272-278.
miike, y. (2007b). asian contributions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3(4), 1-6.
miike, y. (2007c). theorizing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 an assumptive foundation (in chinese, j. z. edmondson, trans.). in j. z. edmondson (ed.), selected international paper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137-157). hangzhou,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miike, y. (2008a). advancing centricity for non-western scholarship: lessons from molefi kete asante’s legacy of afrocentricity. in a. mazama (ed.), essays in honor of an intellectual warrior, molefi kete asante (pp. 287-327). paris, france: editions menaibuc.
miike, y. (2008b). rethinking humanity,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siacentric critiques and contributions (in chinese, j. z. edmondson, trans.). in j. z. edmondson (ed.),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pp. 21-43). hangzhou,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miike, y. (2008c). toward an alternative metathe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n asiacentric vision. in m. k. asante, y. miike, & j. yin (eds.),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pp. 57-72). new york: routledge.
miike, y. (2009a). “cherishing the old to know the new”: a bibliography of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ina media research, 5(1), 95-103.
miike, y. (2009b).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n asiacentric worldview and its communicative implications. in l. a. samovar, r. e. porter, & e. r. mcdaniel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12th ed., pp. 36-48).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miike, y. (ed.). (2009c). new frontiers in asian communication theory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4(1), 1-88.
miike, y. (2010). culture as text and culture as theory: asiacentricity and its raison d’êtr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r. t. halualani & t. k. nakayama (eds.),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crit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miike, y. (in press-a). asiacentricity. in r. l. jackson (ed.),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ident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ike, y. (in press-b). enryo-sasshi theory. in r. l. jackson (ed.),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ident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ike, y., & chen, g.-m. (2006). perspectives on asian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on: an updated bibliography. china media research, 2(1), 98-106.
miike, y., & chen, g.-m. (eds.). (2007). asian contributions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special issue]. china media research, 3(4), 1-109.
miyahara, a. (2004). toward theorizing japane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from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in f. e. jandt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global reader (pp. 279-292). thousand oaks, ca: sage.
ngũgĩ, t. (1993). moving the center: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oxford, uk: james currey.
palencia-roth, m. (2006). universalism and transversalism: dialogue and dialogic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unesco (e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ransversal values: east-west dialogue on spiritual and secular dynamics (pp. 38-49). paris, france: unesco.
paredes-canilao, n. (2006). decolonizing subjects from the discourse of difference.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1(1), 6-26.
rogers, e. m. (1982). the empirical and critical school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m. burgo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5, pp. 125-144).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rogers, e. m. (1999). anatomy of the two subdiscipline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4), 618-631.
shi-xu. (2008). towards a chinese-discourse-studies approach to cultural china: an epilogue. in d. wu (ed.), discourses of cultural china in the globalizing age (pp. 243-253).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shi-xu. (2009). reconstructing eastern paradigms of discourse studies.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4(1), 29-48.
starosta, w. j. (2006). rhetoric and culture: an integrative view. china media research, 2(4), 65-74.
storz, m. l. (1999). malay and chinese values underlying the malaysian business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1), 117-131.
tanno, d. v. (1992). the moral force of knowledge: a case for an emergent view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j. a. jaksa (ed.), proceedings of the 2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ethics conference (pp. 83-89). annandale, va: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tanno, d. v. (2008).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ethnic “text” in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m. k. asante, y. miike, & j. yin (eds.),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pp. 27-36). new york: routledge.
thayer, l. (1997). pieces: toward a revisioning of communication/life. greenwich, ct: ablex.
tu, w. (1992). core valu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fiduciary global community. in k. tehranian & m. tehranian (eds.), restructuring for world peace: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333-345).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tu, w. (1997). humanity as embodied love: exploring filial piety in a global ethical perspective. in l. s. rouner (ed.), is there a human nature? (pp. 172-181).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tu, w. (2001).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 a new perspective on confucian humanism.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 22-27.
tu, w. (2007).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a study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humanism (in korean and in english, s. na, trans.). seoul, south korea: chunho jeon.
tu, w. (2008). mutual learning as an agenda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m. k. asante, y. miike, & j. yin (eds.),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pp. 329-333). new york: routledge.
wallerstein, i. (1997). eurocentrism and its avatars: the dilemmas of social science. new left review, 226, 93-107.
wallerstein, i. (2006). 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new york: new press.
wang, g., & shen, v. (2000). east, west, communication, and theory: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searching for asia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2), 14-32.
west, r., & turner, l. h. (2010). 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4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xiao, x., & chen, g.-m. (2009).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4(1), 61-74.
第7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新媒体定义;概念;形式逻辑。
如今,互联网已经被公认为继电视、广播、纸质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手机媒体也被冠以“第五媒体”的称号。这些不断涌现的新媒体不仅改变了大众传播中的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颠覆了大众媒体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方式,而且给人类传播活动及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影响,同时也给学术理论界带来了全新的课题。“新媒体”一词越来越多的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也成为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最前沿的研究对象。伴随着新媒体系统化研究规模的展开,针对“什么是新媒体?”、“新媒体定义的依据是什么?”、“究竟哪些新兴媒体应该归属于新媒体范畴?”等基础理论的探讨,越来越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概念的定义都有它的内涵和外延。所谓内涵,就是思想的内容,可定义为“构成一概念元素之总和”或“特征的和”。概念的外延,或称指谓,是指一概念所能应用的范围,可定义为“一概念所能代表的个体和集体的总和”或“对象的和”。①从新媒体一词诞生以来,对于“什么是新媒体”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有种种解释。很多学者专家、研究人员都从不同角度对“新媒体”下了不同的定义,对新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可以说是各执一词。这使得新媒体的归属性和发展方向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术争议。早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新媒体做过这样的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还有类似的诸如“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等等。尽管这些概念已被广泛传播,但迄今为止尚无某种定义被广为认同。鉴于此,本文在列举了种种定义观点并进行分析比较之后,根据形式逻辑原理,从媒体的属性和要素等方面对“新媒体”做出全新的定义,以求抛砖引玉,丰富和完善新媒体的理论建设,促进新媒体实践发展。
一、新媒体定义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 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 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 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新媒体”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 Schramm)曾经预言: “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 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 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 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 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 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 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 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 is “new 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
第8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微信网络;用户;关系动机;信息传播模型;MATLAB仿真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11.007
〔中图分类号〕G25073;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6)11-0037-06
〔Abstract〕With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WeChat,it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diffusion and public opinions guide.This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realistic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government and other agencies.Based on complex network theory and dynamics of infectious diseases,this paper provided a modifie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el.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innovative definition of user acceptance threshold and relative motivation.It depicted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rocess curve through MATLAB simulation,and got the law of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related suggestions.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ser acceptance threshold and relative motivation had obvious effects on the width and the speed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Key words〕WeChat network;user;relative motivation;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odel;MATLAB simulation
微信作为在线社交网络的典型代表,其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地传播平台,更成为了一种人类传播方式,也是对人类交往方式的重构。在新媒体技术支撑下,微信以移动端口为基础,以手机用户为依托,以增强用户个性化体验为目标,融合了信息丰富化形态,重新整合了人们的生活圈、社交圈、工作圈,极大地满足了用户的沟通交流、信息获取、消遣娱乐等需求。相比于已有成熟研究的微博,对于微信应用的有着其独特的传播机制和传播过程。作为自媒体的典型代表,微信不仅仅是商家广告和政府的公关平台,强大的用户群自创内容及分享信息的行为极大了支撑着该平台的活跃度。于是,本文根据微信的传播特点和网络拓扑结构,以朋友圈信息传播平台为研究对象,提出用户接受阈值和关系动机影响因素,借助复杂网络理论和传染病动力学理论,基于经典的SIR模型,结合用户在信息传播过程的状态,构建适用于微信网络的信息传播模型,为在仿真环节还原真实信息传播过程奠定基础。
1相关研究
网络环境的复杂性,用户个体的差异性,使得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是极其复杂的。Web20环境下,用户的角色的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用户的生理、认知、情感都发生了变化,用户也已经从被动地接收信息到积极主动参与环境,使得环境与用户的互动更加频繁,同时有着复杂的因素影响着用户行为。英国情报学家威尔逊(TDWilson)在信息行为模式研究中给出了互联网环境下用户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逻辑框架图[1]
由图1可见,用户不仅处于特定的环境中,而且用户信息行为受到个人因素、人际关系、环境因素等的影响。邓胜利[2]在《新一代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用户信息交互行为》提出信息交互行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本身也是一个集各种理论于一身的复杂过程,它将用户、环境、内容、系统各方面整合在一起,而不仅仅考虑技术的理性因素,更要考虑到人性的感性因素。微信作为一种复杂社交系统,本文将用户的信息行为聚焦于信息的获取和信息的分享行为,作为共同的客体,借鉴以上主要影响因素,并将其分类为:用户属性和关系动机以此为构建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刻画不同变量对传播过程的影响。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最早由Kermack与McKendrick对黑死病传播规律的研究中提出的,因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及可塑性,随后学者将其应用到不同的具体研究情景下,提出了其演化改进模型,并得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Linyuan Lü等人[3]结合小世界模型,加入记忆效应、社会加强、非冗余联系人3个影响因素,定量传播概率。徐翔斌等人[4]研究了网络度分布、网络平均度及初始激活节点对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提出了改进的SIR模型;黄宏程[5]结合网络拓扑特性,引入感染用户的衰减函数提出对应的信息传播模型;还有学者对节点影响力、用户相对权重社会加强作用、个体的遗忘和回忆机制等影响因素融入到模型进行的研究[6-7]。Centola[8]实验研究结果得出聚类系数与信息传播速度成正相关关系。大量的研究工作集中网络拓扑特性对传播能力的影响,很少从用户行为动机角度量化分析影响信息传播的因素,对微信相关影响因素融入到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研究更少,当前主要有朱海涛等人[9]对微信朋友圈中的用户相似度、信息价值和信息时效性等影响构建了改进的SEIR模型。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微信网络中信息传播内在机制,本文结合微信传播特点,以微信朋友圈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用户行为动机影响因素对SIR模型进行改进,提出符合微信网络的信息传播模型。
2模型构建及仿真模拟
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微信具有小世界、无标度网络特性[10],借助复杂网络中图论理论,本文把社交网络上的用户定义为节点,用户之间的好友关系表示为节点之间的边,通过调查笔者部分好友以及好友的好友之间的关系,作出好友关系网络拓扑如图2所示:
笔者认为同一条信息在特定的情景下,不同的用户会基于不同的原因将信息传递到其朋友圈。如图2所示,用户1将信息分享到朋友圈后,只有部分好友(用户2、4、5)将信息传播下去,本文将其命名为感染者;而其他好友(用户3、6、15)并为分享该条信息,本文将其命名为免疫者。通过调查得出各好友之间的关系,用户1与用户2、5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用户1与用户4是家人关系。笔者将影响用户信息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归类为用户心理阀值和好友关系。刘行军[11]细化并实证分析用户心理对信息传播的广度及深度的传播价值。胡吉月等人[12]研究了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关系对信息传播价值的影响作用,得出大多数用户倾向于“熟人的影响力大”。基于此,结合传染病动力学理论,重构基于朋友圈传播平台下的信息传播模型。
21模型的构建
211影响因素分析
假设在初始情况下(t=0),微信网络中只有一个感染者,即第一个分享信息或者信息的用户,其他个体均为无知者。那么初始感染者个体会将信息传播给其网络上的微信好友个体,则其好友将会以一定的概率由无知者转为易感者。易感者个体同时受到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作用下,会以一定概率成为感染者。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以一定速度达到稳定状态,所有用户将不会再分享该信息。
(1)用户接受阈值。个体在接收到信息后,会因个体认知需求、情感需求、社会资本维系、自我呈现等心理动机[11]影响对信息形成判断,以作出是否接受该条信息,将信息转为接受状态的临界值称为用户的接受阈值。由此可见,每个用户有着不同的用户接受阈值。
(2)关系动机。微信是基于强关系网络建立的平台,目前,随着微信技术应用和用户需求发展,用户之间的弱关系越来越多,用户关系对用户接受信息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明显,于是本文引入关系动机,表示为用户更愿意接收并接受来自亲近的好友所传播的信息,进而成为感染者。
212SIR模型的构建
假设一个节点j在t时刻处于未知状态S,但在Δt时刻可能是接受或者退出状态,在Ia、Ib、R之间变化,在[t,t+Δt]时间段内,节点状态转移状态如图3所示:
在用户关系网络中,不考虑其好友数量和好友关系的变化影响。SIR模型将关系网络中所有的个体N分为三类:S(易感者,Susceptible)、I(传播者,Infected)、R(退出者,Removed)。其中,S在接触到传播者后会以β〈k〉转为退出者,该用户对信息并不感兴趣,即使信息多次出现该该类用户的朋友圈中,仍然不能说服该类用户关注信息;S在接触到传播者后,与信息产生共鸣,用户心理机制感知到信息对其有用,超过用户心理接受阈值会以α1〈k〉概率转为传播者Ia,将信息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S在接触到传播者后,对信息本身并没有强烈的兴趣,但是由于与传播者者的“熟人关系”,传播者的影响力仍然会以α2〈k〉概率促使未知者转为传播者Ib;信息在经用户一次分享后将不再对同一信息进行分享,传播者会以概率1转为退出者,同时信息停止传播。于是,将S作为未分享信息并不知道信息的用户状态,Ia作为因用户心理认可信息而分享信息的用户状态,Ib作为因用户熟人关系而分享信息的用户状态,R表示为不会再分享信息的用户状态。于是,SIR模型用来模拟微信朋友圈中信息的传播过程,用动力学微分方程表示如方程组(1)~(4)所示:
dS(k,t)dt=-(α1〈k〉+α2〈k〉+β〈k〉)S(k,t)(1)
dIa(k,t)dt=α1〈k〉S(k,t)-Ia(k,t)(2)
dIb(k,t)dt=α2〈k〉S(k,t)-Ib(k,t)(3)
dR(k,t)dt=α1〈k〉Ia(k,t)+α2〈k〉Ib(k,t)+β〈k〉S(k,t)(4)
k表示网络中度数,该模型中假设其大小保持不变;S(k,t)+Ia(k,t)+Ia(k,t)+R(k,t)=N,且假设N大小固定;节点状态转移过程中,是以一定的概率主动地选择是否传播信息,用户在接触到信息后,因同一因素进行传播行为的概率是统一的,且保持不变[13]。在用户心理接受作用下传播信息的概率α1定义公式如公式(5)所示:
α1=p〈D1(x1,x2,…,xn)〉(5)
D1(x1,x2,…,xn)代表用户心理接受阈值,表示用户在同时受到自身知识程度、情感诉求和社会资本维系等自身因素影响后传播信息的临界值。传播概率α1随着其心理特征的变动而变化,用户心理阈值越大,α1值越小;用户心理阈值越小,α1值越大。其次,由于“熟人关系”对信息传播具有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本文将用户分享信息的关系动机定义如公式[15](6)~(8)所示:
α2=p〈wij(α,t)〉(6)
ωij(α,t)=ωαij∑k1m=1ωαmi(7)
ωij=δijki-1+kj-1-δij(8)
其中,ωij(α,t)表示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传播关系的强弱程度,用户之间拥有的共同好友数量量化,共同好友数量越多,用户之间的关系强度就会越强。α为调节参数,ki表示节点i的度,kj表示节点j的度,δij表示i与j之间的共同好友数量。ωij(α,t)值越大,用户的关系动机越强;反之,关系动机越弱。
综上,以上两个传播概率依赖于不同的影响因素,表明了未知者转变为传播者是由不同的因素影响作用下发生的状态转移。下文中将分别针对用户接受阈值和关系动机对信息传播的影响程度作具体分析。
22仿真实验分析
本文使用MATLABR2014a对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仿真。以微信网络结构为基础,对连接该平台的所有连接节点状态进行研究。实验微信网络中未知节点、传播节点和退出节点的密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其中,根据模型特点并参考相关文献的数据设置[14],作出以下假设:初始状态网络中S(0)=199,I(0)=1,R(0)=0,相关概率参数设置为:N=200,α1=05,α2=01,β=04。迭代次数T=50则得出S(k,t)/N,Ia(k,t)/N,Ib(k,t)/N和R(k,t)/N随着时间t变化的曲线。如图4所示:
由图4可见,该模型中,未知者节点S(t)的密度在初期呈现骤减趋势,t=5时,已经接近零值,信息在社交网络中传播速度极快。传播节点在初始阶段都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t=-1时,两类传播节点都同时达到最高点,且在该点,未知节点与退出节点相交,随即两者都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并归为零。信息在扩散的初期,浏览信息的用户会迅速作出选择,随后,传播者集中分享信息,传播热度达到最高后慢慢冷却下来,信息的传播范围较小。退出节点在初始阶段迅速增多,不断上升直至达到密度1,表示所有用户接触到信息不再分享信息。
信息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会受到各种来自用户本身、好友关系强度的影响,本文将已经量化的各影响因素考虑到传播概率中,通过不同变量的初始条件,对影响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进行仿真分析,以期形象客观把握其影响过程和影响程度。
221用户接受阈值
Web20技术应用架构下,传统的社会化媒体逐渐转为新型自媒体平台,用户也由被动地接收信息到可以主动地传播信息。在信息传播链条中,大量研究已发现,用户认知、情感、自我呈现和社会资本维系等心理需求是否得到满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用户的传播行为。于是本文将作出如下定义:用户在浏览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产生共鸣,信息所传达的知识、情感、感官等要素对用户受益,用户在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并愿意分享信息的临界点为用户的接受阈值。若用户的满意度超过了该临界点,信息便得到传播,该用户转为传播状态;若是用户的满意度未达到该临界点,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下,该节点退出传播链条。在本文仿真实验中传播概率分别选取02、05、07和1,其中前3个传播概率α2=01。随着用户接受阈值不断降低,其对应的传播概率取值逐渐变大。在用户接受阈值不断降低的情景下信息传播状态如图5所示:图5传播概率α1仿真试验图
由图5可见,在传播概率α1设置为不同数值时,变化程度最为明显的是传播节点a的密度。其中,未知节点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快速减少,然后缓慢趋于零值。信息扩散的初始阶段,传播节点a的密度迅速增加,在t=1时达到最高点,随之传播信息的节点数量最终没有节点再传播该信息。且随着α1取值不断增加,其密度变化明显,但是,即使α1=09时,传播节点a的密度只是接近04,未及用户总量的一半。由此可知,即使高质量的信息,在微信网络中,该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是有限制的。在某一时间t,若有有接近1/2的用户分享某一条信息,则该条信息具有较高的价值含量。一方面,该类信息值得媒体人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该类信息的广泛传播所引发的社会效应,需要相关部门给与关注,防止舆论恶化或者传谣行为的形成。
222关系动机
微信朋友圈不同于微博,是一款集QQ好友、手机通讯录和“附近的人”3种渠道为一体的关系网络移动社交平台,具有更强的用户粘性。本文将关系动机定义为用户考虑与用户之间形成稳定的好友关系,于是,微信朋友圈作为一个较为私密的纽带,体现着以强关系为主、弱连接为辅的全方位新型虚拟社区[16]。已有研究表明,来自“熟人关系”的信息信任度会更高,本文所述“熟人关系”不仅仅指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而且包含基于互动交流形成的紧密好友关系,用户之间交流越频繁,其关系紧密度则越高,信息更易被接收者传递下去。在接收到信息,虽然未达到用户满意度,但由于与传播者有着紧密的关系而接受信息。于是将用户关系强度作为另一影响用户传播信息的影响因素。根据公式分析,用户关系越强,ωij(α,t)数值越大,则传播概率α2数值就会越高。假设传播概率 分别为:01、03、05和07四个不同的数值,α1=01,其他参数作出相应的变化
图6主要描述了传播概率α2数值的大小对传播者的影响,由于α1+α2=1-β,在α1=1时,在传播概率α2设置不同数值时,该网络中形成的效果与传播概率α2的效果类似。由此可见,用户的关系动机下,强关系网络中信息传播的效果更佳。微信朋友圈形成的在线网络中,人际关系强度越高,用户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就会更大,那么就会有越多的用户分享信息,从而提高信息传播深度,并促使信息在较短时间产生较强的传播效力。
3结论
综合以上仿真结果,本文从用户的用户接受阀值和关系动机探讨了信息在微信网络中不同影响程度,真实量化了信息在实际传播过程的动态过程,为企业、政府、媒体等机构主体有效地扩散信息和实现信息管控提供了理论基础。针对研究结果对相关部门给出以下建议:第一,降低用户接受阈值促进信息传播,用户希望所接收的信息能够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周边的好友,出于个体心理动机会自主地选择是否接受信息,因此迎合或刺激行为主体的认知、情感需求等心理,在进行商品、机构活动信息投放的同时,结合当前流行要素植入知识、情感、娱乐类等充满轻松正能量而又有“干货”的软文,用户会更容易接受从而将信息分享给周围的好友,实现二次传播。第二,充分利用微信网络中的强关系。从本文研究结论得出,关系动机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效果。而微信作为一个以强关系为主的网络系统,其网络结构中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并不断提升强关系。因此充分利用关系价值,沟通用户、建立强关系,并不断拓展与深化强关系也是各机构需要考虑的手段。
本文基于微信网络以微信朋友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微信信息传播特点,引入用户接受阈值和关系动机两个影响因素,再次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微信网络的改进的SIR模型。实验表明,该模型可以较好的描述信息实际传播过程和规律,为企业电子商务和政府舆情传播政策制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Wilson TD..Models i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1999,55(3):361-367.
[2]邓胜利.新一代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用户信息交互行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33-135.
[3]Linyuan Lü,Duan-Bing Chen,Tao Zhou.The small world yields the most effective information spreading[J].New Journal of Physics,2011,13(2).
[4]徐翔斌,李恒,王坤.Web20网络信息传播影响机制研究[J].情报科学,2015,33(8):44-49.
[5]黄宏程,蒋艾玲,胡敏.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模型分析[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6,33(9):1-6.
[6]刘东亮,黄颖,毛海宇,等.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机制研究[J].情报科学,2015,33(8):30-34.
[7]程晓涛,刘彩霞,刘树新.基于局域信息的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模型[J].计算机应用,2015,(2):322-325,331.
[8]DCentola.The Spread of Behavior in an Online Social Network Experiment Science.2010,329:1194-1197.
[9]朱海涛,赵捧未,秦春秀.一种改进的移动社交网络SEIR信息传播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16,34(3):92-97.
[10]刘颖,张焕.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微信用户关系实证分析[J].情报资料工作,2014,(4):56-61.
[11]刘行军.微博用户及其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12]胡吉月,张蔓蒂,黄如花.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关系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作用[J].情报杂志,2013,32(6):181-185.
[13]刘丹,殷亚文,宋明.基于SIR模型的微博信息扩散规律仿真分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3):28-33.
[14]王金龙,刘方爱,朱振方.一种基于用户相对权重的在线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模型[J].物理学报,2015,64(5):71-81.
第9篇:传播与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定义 传统媒体 内涵 外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和迅速普及。“新媒体”这一概念不仅在学术文章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而且逐渐融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时髦名词。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新媒体”,不仅普通使用者难下定义,就是专家学者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诸多障碍。因此很有必要加以讨论和澄清。
大相径庭的新媒体定义
一般认为,所谓新媒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已经用于公共通信方面的除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目前,对于新媒体较为流行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但是,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国内外还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新媒体的定义,了解它们将有助于对新媒体的定义加以重新建构。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个相对的概念。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
阳光卫视的执行主席兼集团行政总裁吴征给出的新媒体的定义是:是一种既超越了电视媒体的广度。又超越了印刷媒体的深度的媒体,而且由于其高度的互动性、个人性和感知方式的多样性。它具备了从前任何媒体都不曾具备的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
若干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新媒体有过一个定义,即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美国俄裔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认为。新媒体将不再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的媒体,而不过是一种与传统媒体形式没有关联的一组数字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应的媒体形式展示出来。
康涅狄格州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文・克罗斯比的定义为: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收者融合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
事实上,上述定义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都有各自的强调重点。但无疑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定义所必须依据的新媒体的特点。因此,在给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的特点
形式逻辑告诉我们,所谓定义,就是通过归纳出概念对象的特有属性,通过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方式,从而使该概念对象和其他类似对象区别开来的一种揭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逻辑方法。其中,内涵定义就是要揭示这个概念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外延定义则是要划定该概念所指的范围。从以上提示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定义一个对象概念,关键在于抓住它的特性,或者说是要理清它的特点,抓住它的本质特征。我们通过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新媒体作为新型的传播形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交互性。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单向式传播。媒体高高在上,居高临下,报纸写什么,读者就只能读什么;广播说什么,听众就只能听什么;电视播什么,观众就只能看什么,受众很少能主动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根本无法和媒体互动。而新媒体则不同,由于采用了新的技术。尤其是因特网具有连接网上任何用户、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功能,用户之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广泛的沟通,从而可以实现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交互式的双向交流。
个性化。由于计算机网络把单向的传播变为双向乃至多方位的交流,通过联机网络,只要拥有一台信息处理机和一台调制解调器的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提供者或报道者。这样新闻报道便成了个人行为,即所谓“人人即媒体”,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与收阅的个人化。
复合性。以往的传统媒体传递的信息符号较为单一,而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包含文字、声音、图像。还包含视频、音频、动画等,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图文声一体化。
集成性。集成性充分体现了新媒体传播形态的多样性特点。它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于一体。如:计算机网络媒介=电子报纸+电子杂志+交互式电视+交互式广播+电子图书馆+……其形式的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
新媒体定义的重构
对于“新媒体”一词的认识,既可以从语义学的角度来探索,也可以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新”一般用来描述与传统的、旧的、落后的、不同的事物或者更先进的和最近出现的事物。而“媒体”一词,按照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的界定,它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信息传递所借助的具体媒介,如报纸、电视等:第二层含义是指信息的机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即是能够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或者说是这些方式得以实现的技术形式(如电视机、报纸、影片等)。可见,“媒体”一词越来越被专有化、特指化。从而“新媒体”的含义也被用来仅仅指新的信息载体,而不再涉及媒体机构。
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看,其内涵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内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够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不同的新型媒体。就其外延而言,新媒体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即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等。
可见,无论新媒体具体指的是什么、如何对它加以定义,本质上它无非是一个中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因而可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出现于传统媒体之后的各类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统称,主要指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时地、交互地承载和传递各种个性化、多媒化复合信息的中介。其中。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指电脑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即HITP
协议的发明,它们是新媒体兴起的首发阵容。但是随着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兴起,数字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卫星通信技术’、宽带技术及手机无线服务平台,成了新媒体出现的最基本的科技基础。发展新媒体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更快、更好地相互交流、获取信息。它的出现使得以往种种阻隔人们沟通的障碍得到了革命性的清除,人类从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和互动关系。
新媒体――一把“双刃剑”
新媒体以它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抢占了广阔的受众市场,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受时空等的限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接收信息的新平台,而且为实现信息的交互提供了可能。然而,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社会的双重影响和对传统媒体的双重作用同时表现了出来,新媒体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怎样控制信息有序流动问题。由于以新媒体为工作的信息传播自由度非常高,信息控制就成了一个难题。例如,有时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新闻时会发现,虽然有众多的链接和海量的信息,但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无论什么信息都有可能畅通无阻地在网上,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辨真伪。很多时候,当我们看遍了这些信息后并未感到有多少收获,因为除了网上信息参差不齐外,网络的相互抄袭现象也非常严重。正由于网络把关人的缺失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怎样保护个人隐私问题。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个人的私生活同时也被置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个人隐私,传统上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新闻理论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列为传统媒体不得涉足的三大,严加保护。但是自从新媒体横空出世以后,个人隐私的保护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些与公共事务无关、只涉及私密生活的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而且不断加以放大,最后常常使当事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很受伤”,如台湾的“璩美凤事件”、香港的“艳照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得不让人惊叹新媒体的可怕与可恨,也使得当代社会中如何保护人们的隐私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舆论导向的偏颇问题。在新媒体,特别是网络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中,舆论导向的偏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有些网民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常常会一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情节、胡编乱造的信息,因为其具有刺激人的眼球的特征,就免不了会引来一些不明真相、不明就里的网友跟风评论,甚至不乏恶意发展其故事的情形发生,所以网上以讹传讹、以假当真甚至弄假成真的事件(即网络事件)时有发生,误导网民,损害社会诚信。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他们的好奇心重,对各种信息都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对新事物新观点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他们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之前。舆论导向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青少年过早地接触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的话,往往会受到一些负面信息的冲击,甚至受到一些敌对网站错误信息的不良影响,这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 上一篇: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
- 下一篇:包装企业管理制度范文
相关热门标签
相关文章阅读
精选范文推荐
- 1传播与文化概论
- 2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
- 3传播信息的方式
- 4传播媒体策略
- 5传播学专业毕业论文
- 6传播学发展论文
- 7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
- 8传播学基本概念
- 9传播学概念
- 10传播学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