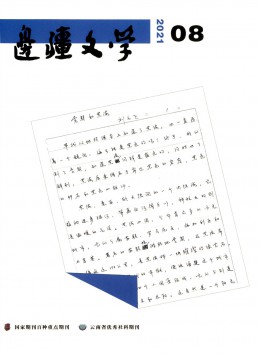文学人类学的尝奇析疑

本文作者:萧兵 单位:淮阴师范学院
阐微索隐,尝奇析疑,被黎锦熙先生在为旧版《辞源》写前言时指出是传统学术在现代的新任务———其实它尤其是文学人类学或民俗神话学的固有本领。它把旧考据学改造为“新考释学”,凭借其比较与推绎功能,发掘古代文化的深层,对某些疑难与问题进行现代性阐释,尽可能地接近或“还原”其本相。这是一种带有“原创性”的阐微索隐。我们十余种《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由于我们面对的“隐微”,大部是旧式学者所不熟悉的民俗神话事象,所以多呈现为所谓“奇闻怪事”,他们一般予以存疑、搁置或回避,使学术史露出大段空白。而我们文学人类学工作者却有可能为之“修复”或“填补”。这并不是我们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我们生于现代,各门新学科争奇斗艳,推陈出新;躬逢其盛,才能予以阐索与赏析。麦克斯•格拉克曼说“: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话不大好听,却是事实。
(1)甲骨文发现,金文材料剧增,有助于我们破解文献的“叙述”层面,厘清文义。
(2)大量实物出土,使我们对古代文物典章制度多了实在与直观的认识。
(3)语言学(包括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引进与发达,使我们的训诂、音韵知识更趋精密,并且多了一重异民族语文的参照系。(4)民族学、民俗学或人类学,使我们有更先进的比较、演绎或综合的能力。
(5)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次进入并且推进我们的研究。
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不是跨学科、跨文化或跨语种的,而且依靠多重证据,包括图像的支持。笔者在为几位青年博士论文(以“神话历史”丛书出版)写的述评里说:她们在导师指导下聪明地将力量集中于“三礼”之学,这样至少会有别于乾嘉诸子的天才考据,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越”那几乎不可企及的学术颠峰,就是因为时代提供了上述的条件,而戴段二王不懂文学人类学。
然而,笔者认为近年来,我们的一些研究多属泛泛之论,“背离”了文学人类学“阐微索隐,赏奇析疑”的特有功能,扬短避长,驾空凌虚,很难从汗牛充栋的学术论著中脱颖而出。也许是个人的抱残守阙,因循守旧吧。笔者比较喜欢史论兼顾,宏微两重,点线并举,夹叙夹议的论文,至少知道它想解决和能解决什么问题,具有长时效和“过期使用率”———笔者检验论著质量的一个办法,是若干年之后还有没有人引用、批评、参证,能“传世”当然更好,还要看在本学科之外有没有“影响”。文章是做不完的。问题层出不穷。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新约》里说,耶稣把他的手杖变成一条蛇———这是真的吗?真的。冬眠的蛇在高寒地带冻成棍子,北极圈的原住民用它做手杖;一旦化冻,手杖复为蛇,蜿蜒而去(笔者不知道巴勒斯坦半沙漠地带为什么也有此事)。民俗学家说,救主耶稣实在是个巫医,这暗示他能够用医药符号的“蛇杖”治病救人,起死回生。古希腊的小医神就以“双蛇杖”为象征,据说他是阿波罗之子,曾以蛇形远赴罗马驱除疾疫与瘟疫。———直至今天,欧洲医生仍然用“蛇杖”为吉祥物,保护神与形象代码。这就是“阐微索隐”,却似乎更多一些“赏奇析疑”。
中外记载,某些蛇能够以药草自疗。民间传说,被“七步蛇”咬了,不要乱动(走七步就死),等它衔来药草为你救治;如果衔来的是木块,那就打棺材吧(可参看《太平广记》卷408引《异苑》所述“蛇衔草”故事)。古代往往蛇蜥不分,有一种草蜥便叫“蛇医”。蛇,蛇毒、蛇蜕、蛇胆本身就是药物。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里,一条蛇闻到香气,把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不死草”给叼走了,连英雄都为之痛苦得“悲恸号啕”(275-290,中译本86-87)。杀死蛇神比东的阿波罗兼为瘟疫与医药之神。《佛本生集经》等说,如来(托为帝释天)曾化身“苏摩蛇”,让感染瘟疫者尝食,“莫不康豫”。《大唐西域记》里Sarpa-osadhi一词由“蛇药”拼缀而成。中国的白蛇也能够“盗仙草”(灵芝),救活被她吓死的丈夫。白族、侗族、黎族、壮族、佤族等有各种形态的蛇龙与药草、仙草相粘连的故事。
人类本来跟孩子一样快乐、好奇,求知欲、探求心旺盛,却被金钱、物欲和电子仪器弄傻了,变得比人工机器还要枯燥乏味。笔者在文学人类学学会成立会议上说:文学人类学应该“走向人类,回归文学”。意思之一就是要复归它的文学形象性、生动性或趣味性。想一想《金枝》成为世界文学的范本,则思过半矣。另一层,是传统在更高层面上的回归,特别是在哲学上的升华,这跟当前取得较大成绩的理论建设可以相辅相成。当然这些都要依靠集体的努力。蛇还是土地、丰产、繁殖的器官与力量的象征。它能够用蜕皮更新自己的生命,以冬眠与复苏显示再生的灵性。
同它作为医药象征一致,增进并且保卫生命者,便是能够战胜恶害与死亡的力量———由此逐渐生长为权力的意象。《旧约•出埃及记》,摩西的哥哥把“上帝的手杖”往地上一扔,同样变成蛇(此为《新约》所本),并且吞食法老术士的“杖蛇”,这已微露其成为权力符号的本意。在《民数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用金属造一条蛇,挂在杆子上,被蛇咬了的人看见这条蛇,就会〔痊愈〕保全性命。”复归“蛇杖”的疗疾功能。而“蛇杆”或“蛇柱”,又意味着摩西获得圣俗二重“神圣性”以及“合法性”的权力。《山海经》里的“操蛇”之神,多表示其掌控着自然力或生命力———其世俗化就是政治权力。这启发我们,无论云南晋宁石寨山铜器“蛇柱”,还是伏波将军(马援)镇水的铁柱或石柱,都代表着占有、统治或厌胜的神圣“权威”。而古希腊“帝使”或交通之神Hermes(就是人们熟悉的“爱马仕”),手中同样持有医神的双蛇杖,表明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蕃育力,加上他足上的鸟翅,便能上天入地,沟通人神,为人类带来财富、知识与爱情,就像伊甸园生命树、智慧树上蟠屈着启蒙的大蛇一样。
“蟠蛇”或“咬尾蛇”,不但是寿数、长生或不死的象征,还是“永恒回归”(eternalreturn)的意象———它再次告诉我们,以虫、蛇、蜥、鳄为主要母型的龙为什么会成为生命、智慧与权力的符号(参看我们的《龙凤龟麟:中国四大灵物》)。生命的力量是至强的力量,生存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蛇的形象当然是多元的,它在一般语境下还意味着卑湿、黑暗、灾患、恶毒乃至死亡。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的先进观念深入人心之后,人们早就不以蛇为敌,对蛇的保护与蛇药的合理开发利用都已蓬勃开展,这里我们不过刻划了它的“正面相”,让我们在阐微索隐的同时,领略一下文学人类学尝奇析疑功能,让我们枯燥机械的生活多少有些诗意、色彩或情趣。
- 上一篇:民间美术课程建设的意义范文
- 下一篇:审美视域下的传统旅游文学范文
相关文章阅读
精选范文推荐
- 1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 2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
- 3文学与影视的关系
- 4文学与教育的关系
- 5文学与文化
- 6文学与文化论文
- 7文学与艺术关系
- 8文学与艺术的碰撞
- 9文学与艺术研究
- 10文学与语言教学